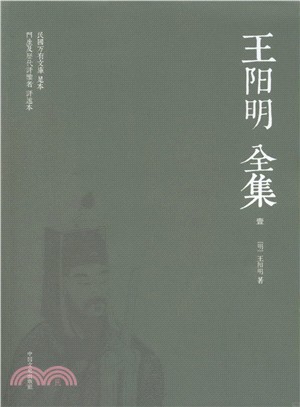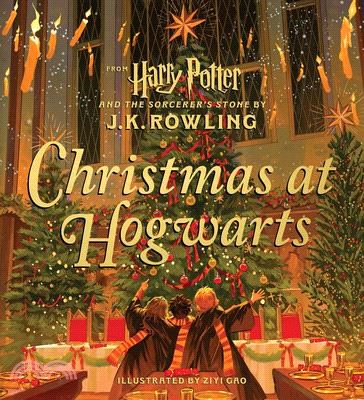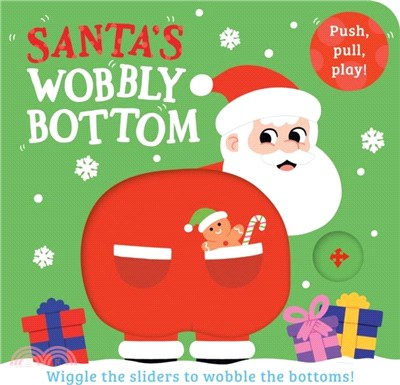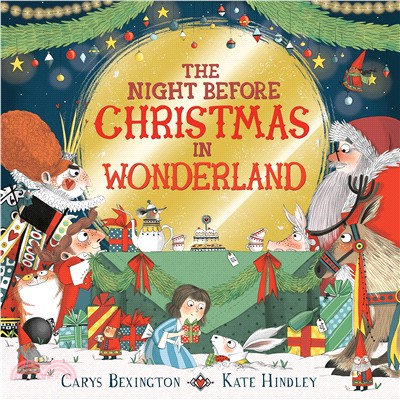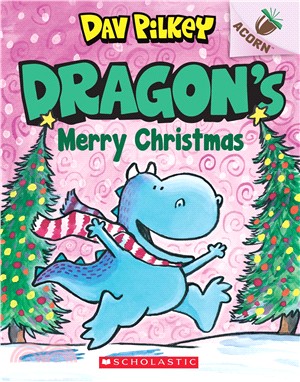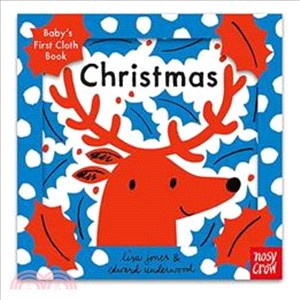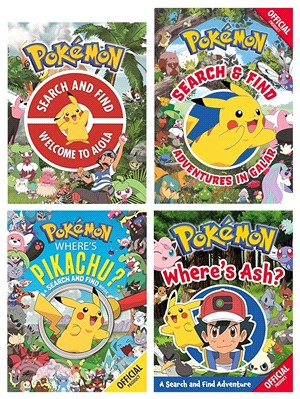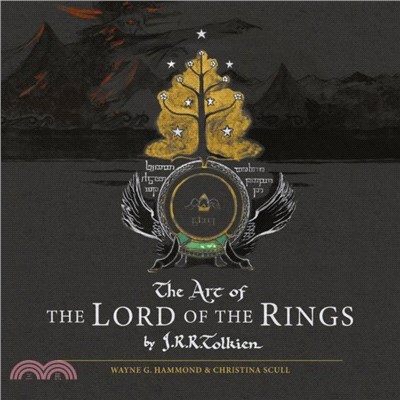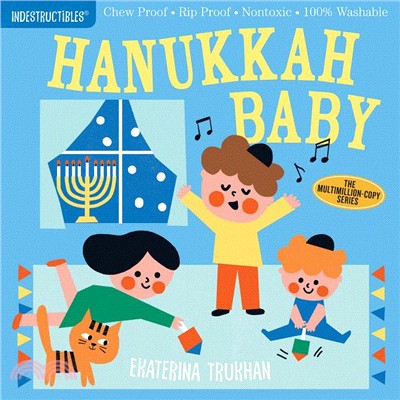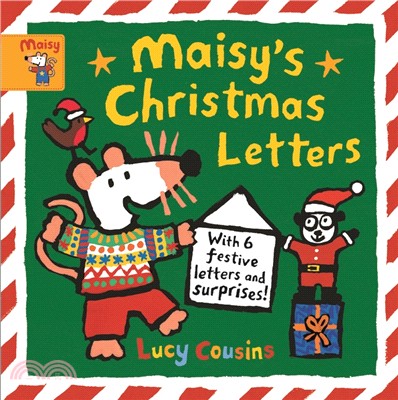商品簡介
王陽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稱於世,對傳承、發展儒學的貢獻尤為卓著。其學說影響,不僅遍於中國,而且遠播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成為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預言,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出版說明 1
前 言 1
王文成公全書序徐 階 1
卷一 傳習錄
傳習錄上 4
徐愛錄 4
徐愛跋 15
陸澄錄 15
薛侃錄 32
傳習錄中 48
錢德洪序 48
答顧東橋書 49
答周道通書 65
答陸原靜書(一) 69
目錄
出版說明 1
前 言 1
王文成公全書序徐 階 1
卷一 傳習錄
傳習錄上 4
徐愛錄 4
徐愛跋 15
陸澄錄 15
薛侃錄 32
傳習錄中 48
錢德洪序 48
答顧東橋書 49
答周道通書 65
答陸原靜書(一) 69
答陸原靜書(二) 70
答歐陽崇一 78
答羅整庵少宰書 82
答聶文蔚(一) 86
答聶文蔚(二) 89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94
教約 95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97
陳九川錄 97
黃直錄 104
黃修易錄 108
黃省曾錄 111
錢德洪錄 113
錢德洪附記 128
黃以方錄 129
錢德洪跋 137
附:朱子晚年定論
朱子晚年定論 140
答黃直卿書 141
答呂子約 141
答何叔京 142
答潘叔昌 142
答潘叔度 143
與呂子約 143
與周叔謹 143
答陸象山 143
答符復仲 144
答呂子約 144
與吳茂實 144
答張敬夫 144
答呂伯恭 145
答周純仁 145
答竇文卿 146
答呂子約 146
答林擇之 146
又 146
答梁文叔 147
答潘叔恭 147
答林充之 147
答何叔景 148
又 148
又 148
答林擇之 149
答楊子直 149
與田侍郎子真 149
答陳才卿 149
與劉子澄 150
與林擇之 150
答呂子約 150
答吳德夫 151
答或人 151
答劉子澄 152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153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154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156
氣候圖序 戊辰 157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158
恩壽雙慶詩后序 戊辰 159
重刊文章軌范序 戊辰 161
五經臆說序 戊辰 162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162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163
壽湯云谷序 甲戌 164
文山別集序 甲戌 165
金壇縣志序 乙亥 166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167
送聞人邦允序 168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169
卷二 文集
大學問 172
教條示龍場諸生 178
五經臆說十三條 180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186
別三子序 丁卯 187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188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189
贈王堯卿序 辛未 190
別張常甫序 辛未 190
別湛甘泉序 壬申 191
別方叔賢序 辛未 192
別王純甫序 辛未 192
別黃宗賢歸天臺序 壬申 193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194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195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196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196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197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198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198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199
別梁日孚序 戊寅 200
大學古本序 戊寅 202
禮記纂言序 庚辰 203
象山文集序 庚辰 204
觀德亭記 戊寅 205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206
從吾道人記 乙酉 207
親民堂記 乙酉 209
萬松書院記 乙酉 211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213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215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217
示弟立志說 乙亥 218
約齋說 甲戌 220
見齋說 乙亥 220
矯亭說 乙亥 221
謹齋說 乙亥 222
夜氣說 乙亥 223
修道說 戊寅 223
自得齋說 甲申 224
博約說 乙酉 224
惜陰說 丙戌 225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226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228
平山書院記 癸亥 229
何陋軒記 戊辰 230
君子亭記 戊辰 231
遠俗亭記 戊辰 232
象祠記 戊辰 233
臥馬冢記 戊辰 234
賓陽堂記 戊辰 235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235
玩易窩記 戊辰 236
東林書院記 癸酉 237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238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240
時雨堂記 丁丑 241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242
浚河記 乙酉 243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244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245
南岡說 丙戌 245
悔齋說 癸酉 247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247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248
龍場生問答 戊辰 249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250
書東齋風雨卷后 癸酉 253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253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254
諭俗四條 丁丑 254
題遙祝圖 戊寅 255
書諸陽伯卷 戊寅 255
書陳世杰卷 庚辰 256
諭泰和楊茂 256
書樂惠卷 庚辰 257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257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258
書徐汝佩卷 癸未 259
題夢槎奇游詩卷 乙酉 260
為善最樂文 丁亥 261
客坐私祝 丁亥 262
鴻泥集序 263
澹然子序 有詩 264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265
對菊聯句序 266
東曹倡和詩序 266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267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268
性天卷詩序 269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270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271
高平縣志序 273
送李柳州序 274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275
慶呂素庵先生封知州序 276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278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279
提牢廳壁題名記 279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281
目錄
卷三 書信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2
與辰中諸生 己巳 2
答徐成之 辛未 3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3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4
寄諸用明 辛未 5
答王虎谷 辛未 6
與黃宗賢 辛未 6
二 壬申 7
三 癸酉 8
四 癸酉 8
五 癸酉 8
六 丙子 10
七 戊寅 10
與王純甫 壬申 10
二 癸酉 12
三 甲戌 13
四 甲戌 13
寄希淵 壬申 14
二 壬申 14
三 癸酉 15
四 己卯 15
與戴子良 癸酉 16
與胡伯忠 癸酉 16
與黃誠甫 癸酉 17
二 丁丑 18
答王天宇 甲戌 18
二 甲戌 19
寄李道夫 乙亥 20
與陸原靜 丙子 21
二 戊寅 22
與希顏臺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23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23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23
二 戊寅 24
三 庚辰 24
寄薛尚謙 戊寅 25
二 戊寅 25
三 戊寅 26
寄諸弟 戊寅 26
與安之 己卯 27
答甘泉 己卯 28
二 庚辰 29
答方叔賢 己卯 29
與陳國英 庚辰 30
復唐虞佐 庚辰 30
書二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32
與鄒謙之 辛巳 32
二 乙酉 32
與夏敦夫 辛巳 33
與朱守忠 辛巳 33
與席元山 辛巳 34
答甘泉 辛巳 34
答倫彥式 辛巳 35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36
答方叔賢 辛巳 37
二 癸未 37
與楊仕鳴 辛巳 38
二 癸未 39
三 癸未 39
與陸原靜 辛巳 40
二 壬午 40
答舒國用 癸未 42
與劉元道 癸未 43
答路賓陽 癸未 44
與黃勉之 甲申 44
二 甲申 45
答劉內重 乙酉 48
與王公弼 乙酉 49
答董沄蘿石 乙酉 50
與黃宗賢 癸未 51
寄薛尚謙 癸未 51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52
寄鄒謙之 丙戌 52
二 丙戌 53
三 丙戌 55
四 丙戌 56
五 丙戌 57
答友人 丙戌 58
答友人問 丙戌 58
答南元善 丙戌 60
二 丙戌 62
答季明德 丙戌 63
與王公弼 丙戌 64
二 丁亥 65
與歐陽崇一 丙戌 65
寄陸原靜 丙戌 65
答甘泉 丙戌 66
答魏師說 丁亥 67
與馬子莘 丁亥 67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68
與黃宗賢 丁亥 69
答以乘憲副 丁亥 70
與戚秀夫 丁亥 70
與陳惟浚 丁亥 71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72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丁亥 72
二 戊子 73
三 戊子 73
答何廷仁 戊子 74
書四 75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75
答毛憲副 戊辰 76
與安宣慰 戊辰 77
二 戊辰 77
三 戊辰 78
答人問神仙 戊辰 80
答徐成之 壬午 80
二 壬午 82
答儲柴墟 壬申 85
二 壬申 88
答何子元 壬申 89
上晉溪司馬 戊寅 90
二 己卯 91
上彭幸庵 壬午 92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93
二 癸未 93
三 丁亥 95
四 丁亥 95
寄席元山 癸未 96
答王亹庵中丞 甲申 96
與陸清伯 甲申 97
與黃誠甫 甲申 97
二 甲申 98
三 乙酉 98
與黃勉之 乙酉 98
復童克剛 乙酉 99
與鄭啟范侍御 丁亥 100
答方叔賢 丁亥 101
二 丁亥 101
與黃宗賢 丁亥 102
二 丁亥 102
三 丁亥 103
四 戊子 104
五 戊子 105
答見山冢宰 丁亥 105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106
答潘直卿 丁亥 107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107
寄何燕泉 戊子 107
書五 109
家書墨跡四首 109
贛州書示四侄正思等 113
又與克彰太叔 113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115
又 117
與郭善甫 119
寄楊仕德 119
與顧惟賢 119
與當道書 124
與汪節夫書 125
寄張世文 125
與王晉溪司馬 126
與陸清伯書 134
與許臺仲書 134
又 135
與林見素 135
與楊邃庵 136
與蕭子雍 137
與德洪 137
卷四詩賦
賦騷七首 140
太白樓賦 丙辰 140
九華山賦 壬戌 141
吊屈平賦 丙寅 143
思歸軒賦 庚辰 144
咎言 丙寅 145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145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146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游作 146
游牛峰寺四首 146
又四絕句 147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147
山中立秋日偶書 147
夜雨山翁家偶書 148
尋春 148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148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148
夜宿無相寺 148
題四老圍棋圖 149
無相寺三首 149
化城寺六首 149
李白祠二首 150
雙峰 150
蓮花峰 150
列仙峰 150
云門峰 150
芙蓉閣二首 150
書梅竹小畫 151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151
登泰山五首 151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152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153
憶龍泉山 153
憶諸弟 153
寄舅 153
送人東歸 153
寄西湖友 153
贈陽伯 154
故山 154
憶鑒湖友 154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154
不寐 154
有室七章 154
讀易 155
歲暮 155
見月 155
天涯 155
屋罅月 156
別友獄中 156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156
答汪抑之三首 156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鐘和之以
五詩于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157
南游三首 157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158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
是以賦也 158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159
因雨和杜韻 159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159
南屏 160
臥病靜慈寫懷 160
移居勝果寺二首 160
憶別 160
泛海 161
武夷次壁間韻 161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161
玉山東岳廟遇舊識嚴星士 161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161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
喬白巖太常諸友 162
過分宜望鈐岡廟 162
雜詩三首 162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163
夜宿宣風館 163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163
宿萍鄉武云觀 163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164
長沙答周生 164
陟湘于邁岳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
寄言二首 164
游岳麓書事 165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166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166
居夷詩 167
去婦嘆五首 167
羅舊驛 168
沅水驛 168
鐘鼓洞 168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168
清平衛即事 168
興隆衛書壁 169
七盤 169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169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 169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170
觀稼 170
采蕨 170
猗猗 170
南溟 171
溪水 171
龍岡新構 171
諸生來 171
西園 172
水濱洞 172
山石 172
無寐二首 172
諸生夜坐 173
艾草次胡少參韻 173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173
鸚鵡和胡韻 173
諸生 174
游來仙洞早發道中 174
別友 174
贈黃太守澍 174
寄友用韻 175
秋夜 175
采薪二首 175
龍岡漫興五首 176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176
書摘/試閱
王文成公全書序
徐 階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死后錢子洪甫輯;最后七卷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
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匯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
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于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于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于于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圣人具是道于心而以時出之,或為文章,或為勛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制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為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圣遠之后,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于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于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為“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于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為文,則是所謂制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匯而梓之,豈唯公之書于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睹道之全也。謝君之為此,其嘉惠后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于后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為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為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后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眾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于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愿相與戒之。
謝君名廷杰,字宗圣。其為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為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后學華亭徐階序。
卷一 傳習錄
傳習錄上
徐愛錄
先生于《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于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咳,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如《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于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后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后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后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有是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于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繆。所以雖在圣人,猶如‘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愛于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卻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乎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于《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
先生曰:“子夏篤信圣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處,亦何嘗茍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
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
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沒有盡心。‘知天’的知猶如知州、知縣的‘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后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圣賢之別。至于‘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夭壽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
開示。”
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于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于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
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
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
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書;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要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
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
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
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
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徐愛跋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后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陸澄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功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