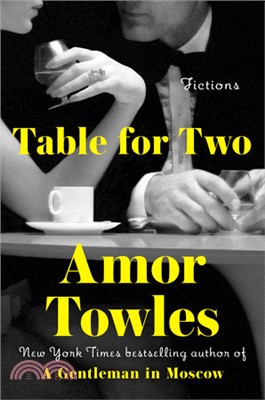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喜歡懸念故事的人,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希區柯克。這個對電影執著一生的胖老頭,已經成為“懸念”和“驚悚”的代名詞。
《如影相隨的人》里所包含的絕大多數作品以人的緊張、焦慮、窺探、恐懼等為敘事主題,設置懸念,故事情節驚險曲折,引人入勝,令人拍案叫絕。如果你未讀完作品,任憑你如何猜測,你也猜不出真相!
《如影相隨的人》里所包含的絕大多數作品以人的緊張、焦慮、窺探、恐懼等為敘事主題,設置懸念,故事情節驚險曲折,引人入勝,令人拍案叫絕。如果你未讀完作品,任憑你如何猜測,你也猜不出真相!
作者簡介
阿爾弗萊德希區柯克(1899-1980),是舉世公認的"懸念大師"。為了表彰他對電影藝術作出的突出貢獻,1979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授予他終身成就獎。1985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封他為爵士。
名人/編輯推薦
世界驚悚懸疑大師、恐怖大師的扛鼎之作。
最經典、最權威、最全面、
最值得收藏的希區柯克故事集。
人類精神世界懸疑驚悚的代名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電影導演的精品作品薈萃。
恐怖片及懸念片的啟蒙教科書,深刻洞察人生的荒謬和人性的脆弱。
本套叢書一共八本,真金印制精裝典藏,
當你一口氣讀到最后,只讓人想放聲尖叫。
最經典、最權威、最全面、
最值得收藏的希區柯克故事集。
人類精神世界懸疑驚悚的代名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電影導演的精品作品薈萃。
恐怖片及懸念片的啟蒙教科書,深刻洞察人生的荒謬和人性的脆弱。
本套叢書一共八本,真金印制精裝典藏,
當你一口氣讀到最后,只讓人想放聲尖叫。
目次
私人偵探
鎖匠的一天
宴會與謀殺
不速之客
門牙
聰明的胡里奧
裸體藝術
劍與錘
四十俱樂部
鴛夢難圓
首次月球旅行
死刑判決
迪靈頓街的回憶
丈夫的詭計
格蘭普插了一手 私人偵探
鎖匠的一天
宴會與謀殺
不速之客
門牙
聰明的胡里奧
裸體藝術
劍與錘
四十俱樂部
鴛夢難圓
首次月球旅行
死刑判決
迪靈頓街的回憶
丈夫的詭計
格蘭普插了一手
英奇的不在場證據
佳期如夢
亂世無聲
謀殺植物
精神殺手
相同的遭遇
見死不救
生死去留
癡情湯米
賭徒的遺書
時差
第三者
枉費心機
致命的錯誤
用心良苦
失蹤的女人
印第安人的咒語
白癡的證詞
尋找真實的故事
最后一位親屬
如影相隨的男人
誰是兇手
越獄
先下手為強
翡翠項鏈
愛情與投資
傷害的代價
栽贓
驚恐的腳步聲
拙劣的騙術
扒手
槍擊事件
移花接木
最后三個月
奇怪的電話
無衣遮體的兇手
失蹤的作家
三十萬元綁票案
鎖匠的一天
宴會與謀殺
不速之客
門牙
聰明的胡里奧
裸體藝術
劍與錘
四十俱樂部
鴛夢難圓
首次月球旅行
死刑判決
迪靈頓街的回憶
丈夫的詭計
格蘭普插了一手 私人偵探
鎖匠的一天
宴會與謀殺
不速之客
門牙
聰明的胡里奧
裸體藝術
劍與錘
四十俱樂部
鴛夢難圓
首次月球旅行
死刑判決
迪靈頓街的回憶
丈夫的詭計
格蘭普插了一手
英奇的不在場證據
佳期如夢
亂世無聲
謀殺植物
精神殺手
相同的遭遇
見死不救
生死去留
癡情湯米
賭徒的遺書
時差
第三者
枉費心機
致命的錯誤
用心良苦
失蹤的女人
印第安人的咒語
白癡的證詞
尋找真實的故事
最后一位親屬
如影相隨的男人
誰是兇手
越獄
先下手為強
翡翠項鏈
愛情與投資
傷害的代價
栽贓
驚恐的腳步聲
拙劣的騙術
扒手
槍擊事件
移花接木
最后三個月
奇怪的電話
無衣遮體的兇手
失蹤的作家
三十萬元綁票案
書摘/試閱
鎖匠的一天
這一天,在特里懷特的生命中,可算是比較快樂的一天,但也不能說是最快樂的。懷特天生就不是快樂的人。他生性小心謹慎,做事昧良心,而且貪得無厭,一有利益一定抓住不放。他最近弄到個情婦,這情婦年輕得可以做他的女兒,至于容貌嘛,說得上美麗可愛,起碼夠吸引一串兒男士。
懷特長得并不英俊,應該說離英俊還很遠。他削肩縮腮,厚厚的鏡片后面,那雙眼睛總是濕漉漉的,一張沒有血色的嘴很少微笑,如果有的話,也是狡猾的笑。對于這張臉,有位顧客曾經說過:“沒人會相信他多久,而那張臉本身也不相信任何人。”
因此,懷特之所以能夠占有雷切爾,不是因為他的外貌,而是因為他的鈔票。
這天早晨,想到萬能的錢時,懷特狡猾地笑了。想到多年來秘密積攢下來的錢,他的笑又變得古怪了。
表面上,懷特是個鎖匠。當然,他還做些別的事——一些合法的事——諸如出租房屋、買賣股票、放高利貸等。他的這份家當都是當鎖匠掙來的。他從年輕時起,一直到現在53歲,一直守著這份老本行。
他在高街上有個小小的門面,右邊是家破落的小店,經營油漆和壁紙,左邊是家生意不怎么興隆的熟肉店。這兒是城中一個沒落地區,像掛在鎖匠店骯臟門簾上的招牌一樣飽經風霜。那招牌是三十一年前創業時做的,一直沿用至今。整個城市,只有五家鎖店登上電話簿,懷特是其中之一。所以,雖然店鋪的地理位置不好,卻有固定的老主顧。
這天上午7點,他像往常一樣,腋下夾著報紙,來到他的店鋪。他推開前門走進店里,隨手又鎖上門,來到后面陰暗的小辦公室里,打開落地燈,燈光從圓球形白色燈泡里射出來,照出一張有爪形腳的圓桌和兩把配套的、搖搖欲墜的椅子。椅子上鋪著深色漆皮墊子,從一個破洞里露出塞在里面的草。這些東西下面,是塊沾滿咖啡和食物的破地毯。特里懷特把帽子和報紙放在桌上,走到一個小水槽前,取出一只搪瓷盤子和一個塑料杯,在水龍頭下洗干凈,然后接了一鍋水放在電爐上。他打開電爐后,回到桌邊,在一把搖搖晃晃的椅子上小心地坐下。幾分鐘內,他就可以沖咖啡喝了。正當他要打開報紙時,前面傳來敲門聲。
特里嘆了口氣,走到前面。外面站著一位年輕人,只有頭部露在掛了半截的門簾上。
特里沒開門。他開門的時間是8點整。他對著外面的人聳聳肩,指指墻上的鐘。年輕人似乎很著急,拼命地推門。
特里又聳聳肩,轉身就走。年輕人開始使勁敲打玻璃。
這時候,任何店主也許都會打電話叫警察,但是,特里從來不叫警察。他站了幾秒鐘,聽著窗戶上的聲音,轉身朝門口走去。
“什么事不能等到8點啊?”開門后,他冷冷地問。
“我有急事,老人家。”年輕人回答說。
“知道。”年輕人什么事都是急匆匆的,特里心中暗想,他們總是魯莽沖動,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雷切爾就這樣,不過,幸虧遇上了他。“好吧,年輕人,告訴我什么急事,說完我好喝咖啡。”
年輕人從夾克口袋里掏出一條手帕,小心地放在玻璃柜臺上。里面是塊旅館用的小肥皂。
“這個,”他問,“夠清楚嗎?”
特里眨眨眼睛,“我今天早晨已經洗過澡了。”
“嘿,老人家,你看都不看,仔細瞧瞧。”
特里彎下腰,鼻尖距肥皂不到兩英寸。
“你看到那印子沒有?”年輕人問。
特里點點頭。肥皂上是一把鑰匙的模子。他從凹線和刻痕上看出,那是典型的耶魯牌筒形鑰匙。第一和第三齒比其他的長一點,這種鑰匙通常是住宅和公寓房子大門用的。
年輕人拍拍特里的肩頭問道:“夠清楚嗎?”
特里直起身子說:“干什么?”
“照樣子再打一把啊。”
“那要看情況。”
“什么情況?”
“你找的人的技術。”
“不是錢?”
“不是錢。因為鑰匙本身的打造費用并不高。”
“多少?”
“十美元。”
“十美元?老人家,你簡直是在敲竹杠。一把這樣的鑰匙,頂多兩塊錢,而且到處都可以打到。”
“那么你到別處去打兩塊錢的好了。”特里不耐煩地說。
“五塊怎么樣?”
“十塊。”
“你真逼得我沒辦法。”
“年輕人,是你自己逼自己,不是我。”
“好吧,十塊就十塊吧。多長時間可以打好?”
“中午。”
“不能早點嗎?”
“不能,別走,”特里說著,走到柜臺后面拿出一張卡片,“寫下姓名和住址。我給你開一張預付十塊的收據。”
“你不太相信人?”
“我相信上帝。”
特里回到他陰暗的辦公室,沖好咖啡后,坐下來看報紙。最吸引他的新聞是一則盜竊案。一位實業家和妻子參加音樂會回來時,發現家中價值十萬元的珠寶被盜。他們出門的這段時間,家里只有一位女仆。她睡在二樓,屋里沒任何強行進入的跡象,所有能進入屋子的門窗全都好好地鎖著。這對夫妻回家時,是用自己的鑰匙打開車庫,通過地下室進屋的。報道說,警方正在調查。
8點整,他開門營業。他所做的不過是把門閂拉開而已。二十分鐘后,第一位顧客上門了。那是位上了年紀的女人,她手中拿著一把汽車鑰匙,說是打不開車門。特里賣給她一管石墨,告訴她用法,然后打發她走了。不到9點鐘,電話鈴響了。特里伸手到柜臺下接電話。
“懷特鎖店。”
“是特里懷特嗎?”
“是我。”
“我是戈登特里,一切順利。”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
“我應該分些利潤給你。”
“贓物我不碰,把鑰匙寄還給我就行了。”
“已經寄出了。現在,再來一把鑰匙怎么樣?”
“幾個月后也許可以。你應該休息一下,那樣會長壽些,別太急。”
“那就幾個月后吧。”
“打電話就行了,人別來。”
10點鐘,特里來到隔壁飲食店,買了杯檸檬茶和一塊櫻桃餅。他在后面房間吃完點心后,又一位顧客走了進來。
忙過一陣后,他瞄了眼掛鐘:11點17分。接下來干些什么呢?哦,對了,早晨那個年輕人的鑰匙。他找出那人留下的肥皂和資料卡。那人叫喬治杜邦,住在首都大道1444號,沒有電話。特里從玻璃板下面拿出一張最新的地圖,在上面查找這個地址。1444號是一家紀念碑公司。
中午,這位杜邦出現了。和早晨一樣,他仍然顯得很緊張。他睜大眼睛問道:“準備好了嗎?”
特里默默地將按肥皂模子打出來的鑰匙遞了過去。他打了兩把,自己留了一把。
“肥皂呢,老人家?”
“我用來洗手了。”
“你真是個聰明的老頭。”
“像首都大道上的紀念碑一樣,我認為沉默是金。”
杜邦搖搖頭,離開了店鋪。
特里從桌子旁邊一臺小型壓力機那兒取回肥皂,連同那把多打的鑰匙一起,放進他的資料柜。他總覺得按杜邦那塊肥皂做出的鑰匙,有點兒……
這時,電話鈴響了。
特里拿起電話。
“我是丘比。”一個大嗓門說道。
“是的,丘比先生。”
“一個叫鮑勃巴林的人,在瓦爾登湖那兒有幢別墅,你知道我在說誰嗎?”
“當然。”
“我早料到你知道。聽說你曾為他做過事?”
“是的,丘比先生,幫他做過事又怎樣?”
“你有沒有他船庫的鑰匙?”
“可能有。”
“好極了,我想租二十四小時。”
“一級還是二級租金?”
“特里,你在開玩笑吧?”
“不,一點兒不開玩笑,丘比先生。過去,你向我租東西,一直是二級租金,也就是一天一百美元,對不對?”
“我洗耳恭聽。”
“你租一把鑰匙不過是去開一扇門。鎖一打開,你便可以為所欲為,要什么拿什么。那些我不管。但去開一個船庫,我很懷疑。丘比先生,你要一條船做什么?去釣魚嗎?”
大嗓門發出一陣大笑,但絲毫沒有笑意:“如果我只是想修理一個朋友的船,好讓他用的時候……”
“我對細節不感興趣。丘比先生,一級租金,你覺得怎樣?”
“一級租金多少?”
“五百美金。”
“很公平。一小時內我就把錢寄出。”
“我會把鑰匙寄到你平時那個地址。”
掛上電話后,他心想,這一天的收獲已經不錯了,何況才過了半天。他要買一瓶酒到雷切爾的公寓吃晚飯。一瓶酒,也許還帶一些花。這是第二次去看她,應該帶點東西,使她覺得他比上次好。
他不得不承認,他第一次去她那兒,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他的行為就像一個放高利貸的。可是,這年頭,誰能相信誰呢?也許可以在短時間內相信一個男人,可是,永遠不能相信一個女人,尤其是像雷切爾那樣美麗的女人。在她生下一個不明來歷的孩子后,連她的親生父母都不再理睬她。這樣的女人,你能相信嗎?
特里雇用的那個收租人可能占過她的便宜,否則,為什么她三個月沒交房租,他還不采取任何行動呢?這個消息傳到特里耳朵時,他親自出馬了。他來到那個貧民窟,看到了她真實的處境,聽了她的遭遇,然后,他向她提出了一個建議。有什么別的辦法呢?他沒結婚,年紀這么大了,難免有些寂寞,他攢了些錢,在康力特大道上有幢高級公寓,雷切爾愿不愿單獨住在那兒,偶爾接待一個孤獨男人的拜訪?
好,既然這樣,那么有些條件絕不向任何人提起特里的名字;明天就搬家,不準留下新住處的地址;除了身上衣服外,什么都不要帶,因為他會給她買最好的;不準再見過去的任何朋友,特別是年輕的,當然,更不能見那個讓她懷孕的流氓;要對他忠心耿,百依百順——能做到嗎?
嬰兒?你要那個嬰兒?好,可以,但有個條件:先照剛才說的那樣表現表現,一個月后我們再談嬰兒。來,親一下,不行?雷切爾,你真固執,二十年來,我還沒吻過任何人。想到這里,他發現自己來到電話機旁。有一陣兒,他有種強烈的沖動,想給她打個電話,但很快就冷靜下來。為什么要說那么多呢?今晚就見面了——而且可以帶著酒,可以把酒言歡。
他站起身,毫無目的地在店里踱來踱去。忽然,他的視線落在那塊粉紅色的肥皂上。潛意識里某種想法讓他吃了一驚。他拿起肥皂,又放下,然后摘下眼鏡,慢慢地揩拭,擦干凈后再小心地放到鼻梁上。他左手拿起肥皂,右手伸進褲口袋,慢吞吞地、幾乎是不情愿地掏出一串鑰匙。他一把一把地看著,直到第八把。他仔細地打量著這把鑰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肥皂上:鑰匙與印模完全相符。他將多打的那把鑰匙拿出來,仔細地比著,臉越來越陰沉。
最后,他來到電話旁,給雷切爾五天前搬進去的公寓打了個電話。沒有人接。他擔心撥錯了號碼,放下電話重撥。還是沒人接。
無奈中,他撥通了公寓管理員的電話。
“拉里,”特里說,“告訴我今天下午的電視節目怎么樣?”
“什么?哦,懷特先生,我剛剛進來拿一把鉗子。”
“鉗子?你那雙眼睛是干什么的?我不是告訴你要留心雷切爾小姐的一舉一動嗎?”
“我是留心著呢。”
“那么為什么還有年輕人去找她?她搬進去不到五天,怎么就會發生這種事?”
“懷特先生,這我都知道。”
“你怎么會知道的?”
“我本來打算晚些時候向您報告的。昨天下午4點過后,有個年輕人來按她的門鈴,當然,就像您安排的那樣,我的門鈴也響了。所以,我便上樓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是個黑發男人,大約六英尺高……”
“我知道他的長相。”
“嗯,總之,小姐不讓他進去,但他硬要進去。后來,她大約讓他進去待了十分鐘,就是這樣。”
“那就夠了。”
“他出來的時候,我聽見小姐說,她永遠不會再見他。我把這些都記下來了,懷特先生。”
“好。現在,你馬上到樓上去,敲雷切爾小姐的房門,如果沒有回答,你用你的鑰匙把門打開。我二十分鐘內趕到。”
特里又打電話給出租汽車公司,叫了輛出租車。
出租車開到雷切爾住的公寓大廈附近時,司機說:“先生,那邊好像出事了,又是警車,又是救護車。”
“就停在這兒吧。”特里命令說。
付完車費,特里好奇地向出事地點走去。有十多個人圍在公寓大樓門口。他小心地走過去,站在兩個胖女人和一個老頭兒后面。
“擔架出來了。”一個女人說。
“連頭帶腳都蓋住了。”老頭兒說,“那只意味著一件事。”
“太可怕了。”胖女人說。
“瞧那兒,”另一個胖女人說,“哦,不!”
特里從兩個女人的肩頭望過去,看到兩個警察抬著一副擔架從大門出來。
“和剛才那個一樣,”老頭兒幸災樂禍地說,“連頭帶腳都蓋住了。”
“他們怎么啦?”一個女人問道,“我是說他們怎么會……”
一個手抱書本、滿臉雀斑的女孩抬頭望望兩個女人,說:“有人說那男的先殺了那個女的,然后自殺了。用切肉的刀。”她靜靜地補充說。
“他們干嗎要這樣呢?”特里自言自語道,“這么年輕,太可惜了!”說著,他轉身走開了。他一邊慢慢地走,一邊想:現在的年輕人總是這么魯莽,事到臨頭,只有一死了之!
這一天,在特里懷特的生命中,可算是比較快樂的一天,但也不能說是最快樂的。懷特天生就不是快樂的人。他生性小心謹慎,做事昧良心,而且貪得無厭,一有利益一定抓住不放。他最近弄到個情婦,這情婦年輕得可以做他的女兒,至于容貌嘛,說得上美麗可愛,起碼夠吸引一串兒男士。
懷特長得并不英俊,應該說離英俊還很遠。他削肩縮腮,厚厚的鏡片后面,那雙眼睛總是濕漉漉的,一張沒有血色的嘴很少微笑,如果有的話,也是狡猾的笑。對于這張臉,有位顧客曾經說過:“沒人會相信他多久,而那張臉本身也不相信任何人。”
因此,懷特之所以能夠占有雷切爾,不是因為他的外貌,而是因為他的鈔票。
這天早晨,想到萬能的錢時,懷特狡猾地笑了。想到多年來秘密積攢下來的錢,他的笑又變得古怪了。
表面上,懷特是個鎖匠。當然,他還做些別的事——一些合法的事——諸如出租房屋、買賣股票、放高利貸等。他的這份家當都是當鎖匠掙來的。他從年輕時起,一直到現在53歲,一直守著這份老本行。
他在高街上有個小小的門面,右邊是家破落的小店,經營油漆和壁紙,左邊是家生意不怎么興隆的熟肉店。這兒是城中一個沒落地區,像掛在鎖匠店骯臟門簾上的招牌一樣飽經風霜。那招牌是三十一年前創業時做的,一直沿用至今。整個城市,只有五家鎖店登上電話簿,懷特是其中之一。所以,雖然店鋪的地理位置不好,卻有固定的老主顧。
這天上午7點,他像往常一樣,腋下夾著報紙,來到他的店鋪。他推開前門走進店里,隨手又鎖上門,來到后面陰暗的小辦公室里,打開落地燈,燈光從圓球形白色燈泡里射出來,照出一張有爪形腳的圓桌和兩把配套的、搖搖欲墜的椅子。椅子上鋪著深色漆皮墊子,從一個破洞里露出塞在里面的草。這些東西下面,是塊沾滿咖啡和食物的破地毯。特里懷特把帽子和報紙放在桌上,走到一個小水槽前,取出一只搪瓷盤子和一個塑料杯,在水龍頭下洗干凈,然后接了一鍋水放在電爐上。他打開電爐后,回到桌邊,在一把搖搖晃晃的椅子上小心地坐下。幾分鐘內,他就可以沖咖啡喝了。正當他要打開報紙時,前面傳來敲門聲。
特里嘆了口氣,走到前面。外面站著一位年輕人,只有頭部露在掛了半截的門簾上。
特里沒開門。他開門的時間是8點整。他對著外面的人聳聳肩,指指墻上的鐘。年輕人似乎很著急,拼命地推門。
特里又聳聳肩,轉身就走。年輕人開始使勁敲打玻璃。
這時候,任何店主也許都會打電話叫警察,但是,特里從來不叫警察。他站了幾秒鐘,聽著窗戶上的聲音,轉身朝門口走去。
“什么事不能等到8點啊?”開門后,他冷冷地問。
“我有急事,老人家。”年輕人回答說。
“知道。”年輕人什么事都是急匆匆的,特里心中暗想,他們總是魯莽沖動,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雷切爾就這樣,不過,幸虧遇上了他。“好吧,年輕人,告訴我什么急事,說完我好喝咖啡。”
年輕人從夾克口袋里掏出一條手帕,小心地放在玻璃柜臺上。里面是塊旅館用的小肥皂。
“這個,”他問,“夠清楚嗎?”
特里眨眨眼睛,“我今天早晨已經洗過澡了。”
“嘿,老人家,你看都不看,仔細瞧瞧。”
特里彎下腰,鼻尖距肥皂不到兩英寸。
“你看到那印子沒有?”年輕人問。
特里點點頭。肥皂上是一把鑰匙的模子。他從凹線和刻痕上看出,那是典型的耶魯牌筒形鑰匙。第一和第三齒比其他的長一點,這種鑰匙通常是住宅和公寓房子大門用的。
年輕人拍拍特里的肩頭問道:“夠清楚嗎?”
特里直起身子說:“干什么?”
“照樣子再打一把啊。”
“那要看情況。”
“什么情況?”
“你找的人的技術。”
“不是錢?”
“不是錢。因為鑰匙本身的打造費用并不高。”
“多少?”
“十美元。”
“十美元?老人家,你簡直是在敲竹杠。一把這樣的鑰匙,頂多兩塊錢,而且到處都可以打到。”
“那么你到別處去打兩塊錢的好了。”特里不耐煩地說。
“五塊怎么樣?”
“十塊。”
“你真逼得我沒辦法。”
“年輕人,是你自己逼自己,不是我。”
“好吧,十塊就十塊吧。多長時間可以打好?”
“中午。”
“不能早點嗎?”
“不能,別走,”特里說著,走到柜臺后面拿出一張卡片,“寫下姓名和住址。我給你開一張預付十塊的收據。”
“你不太相信人?”
“我相信上帝。”
特里回到他陰暗的辦公室,沖好咖啡后,坐下來看報紙。最吸引他的新聞是一則盜竊案。一位實業家和妻子參加音樂會回來時,發現家中價值十萬元的珠寶被盜。他們出門的這段時間,家里只有一位女仆。她睡在二樓,屋里沒任何強行進入的跡象,所有能進入屋子的門窗全都好好地鎖著。這對夫妻回家時,是用自己的鑰匙打開車庫,通過地下室進屋的。報道說,警方正在調查。
8點整,他開門營業。他所做的不過是把門閂拉開而已。二十分鐘后,第一位顧客上門了。那是位上了年紀的女人,她手中拿著一把汽車鑰匙,說是打不開車門。特里賣給她一管石墨,告訴她用法,然后打發她走了。不到9點鐘,電話鈴響了。特里伸手到柜臺下接電話。
“懷特鎖店。”
“是特里懷特嗎?”
“是我。”
“我是戈登特里,一切順利。”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
“我應該分些利潤給你。”
“贓物我不碰,把鑰匙寄還給我就行了。”
“已經寄出了。現在,再來一把鑰匙怎么樣?”
“幾個月后也許可以。你應該休息一下,那樣會長壽些,別太急。”
“那就幾個月后吧。”
“打電話就行了,人別來。”
10點鐘,特里來到隔壁飲食店,買了杯檸檬茶和一塊櫻桃餅。他在后面房間吃完點心后,又一位顧客走了進來。
忙過一陣后,他瞄了眼掛鐘:11點17分。接下來干些什么呢?哦,對了,早晨那個年輕人的鑰匙。他找出那人留下的肥皂和資料卡。那人叫喬治杜邦,住在首都大道1444號,沒有電話。特里從玻璃板下面拿出一張最新的地圖,在上面查找這個地址。1444號是一家紀念碑公司。
中午,這位杜邦出現了。和早晨一樣,他仍然顯得很緊張。他睜大眼睛問道:“準備好了嗎?”
特里默默地將按肥皂模子打出來的鑰匙遞了過去。他打了兩把,自己留了一把。
“肥皂呢,老人家?”
“我用來洗手了。”
“你真是個聰明的老頭。”
“像首都大道上的紀念碑一樣,我認為沉默是金。”
杜邦搖搖頭,離開了店鋪。
特里從桌子旁邊一臺小型壓力機那兒取回肥皂,連同那把多打的鑰匙一起,放進他的資料柜。他總覺得按杜邦那塊肥皂做出的鑰匙,有點兒……
這時,電話鈴響了。
特里拿起電話。
“我是丘比。”一個大嗓門說道。
“是的,丘比先生。”
“一個叫鮑勃巴林的人,在瓦爾登湖那兒有幢別墅,你知道我在說誰嗎?”
“當然。”
“我早料到你知道。聽說你曾為他做過事?”
“是的,丘比先生,幫他做過事又怎樣?”
“你有沒有他船庫的鑰匙?”
“可能有。”
“好極了,我想租二十四小時。”
“一級還是二級租金?”
“特里,你在開玩笑吧?”
“不,一點兒不開玩笑,丘比先生。過去,你向我租東西,一直是二級租金,也就是一天一百美元,對不對?”
“我洗耳恭聽。”
“你租一把鑰匙不過是去開一扇門。鎖一打開,你便可以為所欲為,要什么拿什么。那些我不管。但去開一個船庫,我很懷疑。丘比先生,你要一條船做什么?去釣魚嗎?”
大嗓門發出一陣大笑,但絲毫沒有笑意:“如果我只是想修理一個朋友的船,好讓他用的時候……”
“我對細節不感興趣。丘比先生,一級租金,你覺得怎樣?”
“一級租金多少?”
“五百美金。”
“很公平。一小時內我就把錢寄出。”
“我會把鑰匙寄到你平時那個地址。”
掛上電話后,他心想,這一天的收獲已經不錯了,何況才過了半天。他要買一瓶酒到雷切爾的公寓吃晚飯。一瓶酒,也許還帶一些花。這是第二次去看她,應該帶點東西,使她覺得他比上次好。
他不得不承認,他第一次去她那兒,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他的行為就像一個放高利貸的。可是,這年頭,誰能相信誰呢?也許可以在短時間內相信一個男人,可是,永遠不能相信一個女人,尤其是像雷切爾那樣美麗的女人。在她生下一個不明來歷的孩子后,連她的親生父母都不再理睬她。這樣的女人,你能相信嗎?
特里雇用的那個收租人可能占過她的便宜,否則,為什么她三個月沒交房租,他還不采取任何行動呢?這個消息傳到特里耳朵時,他親自出馬了。他來到那個貧民窟,看到了她真實的處境,聽了她的遭遇,然后,他向她提出了一個建議。有什么別的辦法呢?他沒結婚,年紀這么大了,難免有些寂寞,他攢了些錢,在康力特大道上有幢高級公寓,雷切爾愿不愿單獨住在那兒,偶爾接待一個孤獨男人的拜訪?
好,既然這樣,那么有些條件絕不向任何人提起特里的名字;明天就搬家,不準留下新住處的地址;除了身上衣服外,什么都不要帶,因為他會給她買最好的;不準再見過去的任何朋友,特別是年輕的,當然,更不能見那個讓她懷孕的流氓;要對他忠心耿,百依百順——能做到嗎?
嬰兒?你要那個嬰兒?好,可以,但有個條件:先照剛才說的那樣表現表現,一個月后我們再談嬰兒。來,親一下,不行?雷切爾,你真固執,二十年來,我還沒吻過任何人。想到這里,他發現自己來到電話機旁。有一陣兒,他有種強烈的沖動,想給她打個電話,但很快就冷靜下來。為什么要說那么多呢?今晚就見面了——而且可以帶著酒,可以把酒言歡。
他站起身,毫無目的地在店里踱來踱去。忽然,他的視線落在那塊粉紅色的肥皂上。潛意識里某種想法讓他吃了一驚。他拿起肥皂,又放下,然后摘下眼鏡,慢慢地揩拭,擦干凈后再小心地放到鼻梁上。他左手拿起肥皂,右手伸進褲口袋,慢吞吞地、幾乎是不情愿地掏出一串鑰匙。他一把一把地看著,直到第八把。他仔細地打量著這把鑰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肥皂上:鑰匙與印模完全相符。他將多打的那把鑰匙拿出來,仔細地比著,臉越來越陰沉。
最后,他來到電話旁,給雷切爾五天前搬進去的公寓打了個電話。沒有人接。他擔心撥錯了號碼,放下電話重撥。還是沒人接。
無奈中,他撥通了公寓管理員的電話。
“拉里,”特里說,“告訴我今天下午的電視節目怎么樣?”
“什么?哦,懷特先生,我剛剛進來拿一把鉗子。”
“鉗子?你那雙眼睛是干什么的?我不是告訴你要留心雷切爾小姐的一舉一動嗎?”
“我是留心著呢。”
“那么為什么還有年輕人去找她?她搬進去不到五天,怎么就會發生這種事?”
“懷特先生,這我都知道。”
“你怎么會知道的?”
“我本來打算晚些時候向您報告的。昨天下午4點過后,有個年輕人來按她的門鈴,當然,就像您安排的那樣,我的門鈴也響了。所以,我便上樓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是個黑發男人,大約六英尺高……”
“我知道他的長相。”
“嗯,總之,小姐不讓他進去,但他硬要進去。后來,她大約讓他進去待了十分鐘,就是這樣。”
“那就夠了。”
“他出來的時候,我聽見小姐說,她永遠不會再見他。我把這些都記下來了,懷特先生。”
“好。現在,你馬上到樓上去,敲雷切爾小姐的房門,如果沒有回答,你用你的鑰匙把門打開。我二十分鐘內趕到。”
特里又打電話給出租汽車公司,叫了輛出租車。
出租車開到雷切爾住的公寓大廈附近時,司機說:“先生,那邊好像出事了,又是警車,又是救護車。”
“就停在這兒吧。”特里命令說。
付完車費,特里好奇地向出事地點走去。有十多個人圍在公寓大樓門口。他小心地走過去,站在兩個胖女人和一個老頭兒后面。
“擔架出來了。”一個女人說。
“連頭帶腳都蓋住了。”老頭兒說,“那只意味著一件事。”
“太可怕了。”胖女人說。
“瞧那兒,”另一個胖女人說,“哦,不!”
特里從兩個女人的肩頭望過去,看到兩個警察抬著一副擔架從大門出來。
“和剛才那個一樣,”老頭兒幸災樂禍地說,“連頭帶腳都蓋住了。”
“他們怎么啦?”一個女人問道,“我是說他們怎么會……”
一個手抱書本、滿臉雀斑的女孩抬頭望望兩個女人,說:“有人說那男的先殺了那個女的,然后自殺了。用切肉的刀。”她靜靜地補充說。
“他們干嗎要這樣呢?”特里自言自語道,“這么年輕,太可惜了!”說著,他轉身走開了。他一邊慢慢地走,一邊想:現在的年輕人總是這么魯莽,事到臨頭,只有一死了之!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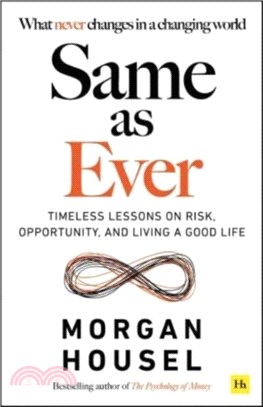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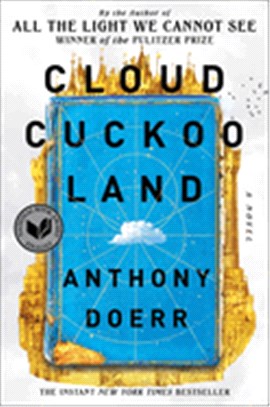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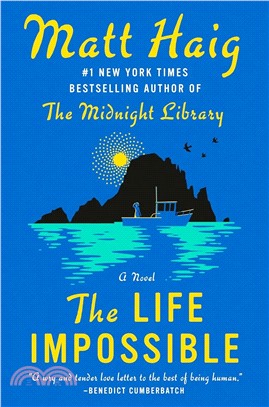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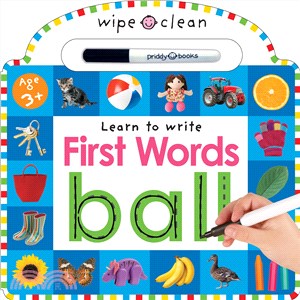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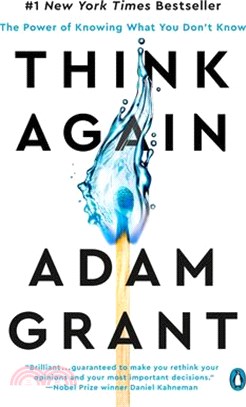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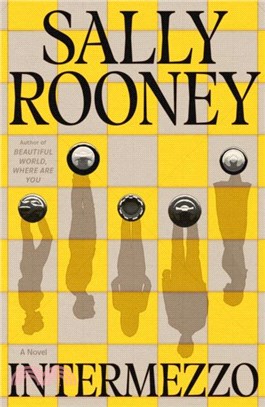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