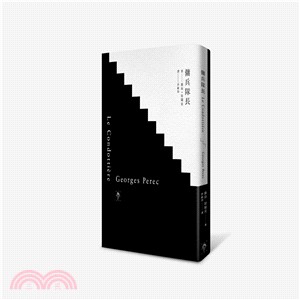傭兵隊長
商品資訊
ISBN13:9789869087780
替代書名:Le Condottière
出版社:行人
作者:喬治‧培瑞克
譯者:許綺玲
出版日:2014/12/24
裝訂/頁數:平裝/219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法國傳奇「文學潛能工坊」(Oulipo)最傑出成員喬治.培瑞克首部完成的驚人小說創作。
★遺失的神祕打字稿,辭世三十年後由法國重要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
★台灣培瑞克研究權威學者許綺玲翻譯及導讀。
一階又一階。一步又一步。我寧可當斷頭台的劊子手也不要被斷頭。一步又一步。一階踩馬。一階踩德。一階踩拉。一階踩你一階踩要一階踩去一階踩殺一階踩死一階踩馬一階踩德一階踩拉。你 要 去 殺 死 馬 德 拉。你要去殺死馬德拉。馬 德 拉。
從一樁血流成河的割喉謀殺案開始,受害者馬德拉已死,沉重的屍體被兇手延著階梯拖行至地下室。此時管家突然進門,兇手丟下屍體,逃往地下室一間擺滿畫具的工作室。馬德拉為什麼被殺?兇手是誰?馬德拉又是誰?
主角賈斯帕是位製造贋畫的高手,因為這個身份,讓他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紀錄,彷彿不存在的幽靈。他受到長期雇主馬德拉之託,必須完成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的名作,於是他選擇了「傭兵隊長」。他希望藉著這幅贋畫,確立自己「不只是會複製」的藝術家身份,甚至因此能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並列。但最後,賈斯帕只完成一幅失敗的畫作,讓他醒悟這一再複製的生活,如牢籠般禁錮著他,無法忍受,必須殺死馬德拉。
作者喬治.培瑞克可說是法國有史以來最瘋狂的小說家,他在文學創作的成就恐怕無人能及,並曾獲多項極高榮譽的文學獎項;法國巴黎有條街以他命名,地球之外還有顆名為「Perec」的小行星。《傭兵隊長》是培瑞克青年時期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真正完成的小說,他在這本小說中已展露出獨特的文學才華,但其過於脫離常軌的書寫讓他屢被退稿,只好將書稿束之高閣,並在一次搬家時遺失。這使他在四十六歲因病離世時,猶帶著懊悔。在他辭世三十年後,這份書稿重新被發現,由法國重要文學出版社於2012年隆重推出。
培瑞克在這本小說中玩弄文字、搬移視角、分裂及擠壓節奏;敘事線在他手中,有如毛線被扭曲、被繃緊、被纏繞。從許多方面來看,《傭兵隊長》整部作品的確很像一球混亂的線團,有許多短詞堆積、不完整句等,甚至有幾處令人懷疑是出自原打字稿的問題或者誤植。而敘事線路的相纏、打結、迷失,更讓讀者慌亂驚跌。但這些從四處冒出來的線頭,卻可以讓我們抽出來,引著我們前往作品的後端。這本尖銳而驚人的《傭兵隊長》,也讓培瑞克實驗了後來他最具代表性的引用他人文本重新組合創造的技法,並如核心一般匯聚了他許多後來的偉大文本,成為閱讀及研究培瑞克的最佳路徑。
兇手賈斯帕選擇要複製《傭兵隊長》這幅名畫,因為他跟畫中的「傭兵隊長」一樣,在唇上有道疤痕;而本書作者培瑞克的唇上,也同樣有道疤痕。藉由這個疤痕,讓三個年代的三種身分重疊在一起,一個單純的殺人案,需要多重後設地解謎,因而賦予這部「首部小說」極其強烈的傳奇色彩。
★遺失的神祕打字稿,辭世三十年後由法國重要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
★台灣培瑞克研究權威學者許綺玲翻譯及導讀。
一階又一階。一步又一步。我寧可當斷頭台的劊子手也不要被斷頭。一步又一步。一階踩馬。一階踩德。一階踩拉。一階踩你一階踩要一階踩去一階踩殺一階踩死一階踩馬一階踩德一階踩拉。你 要 去 殺 死 馬 德 拉。你要去殺死馬德拉。馬 德 拉。
從一樁血流成河的割喉謀殺案開始,受害者馬德拉已死,沉重的屍體被兇手延著階梯拖行至地下室。此時管家突然進門,兇手丟下屍體,逃往地下室一間擺滿畫具的工作室。馬德拉為什麼被殺?兇手是誰?馬德拉又是誰?
主角賈斯帕是位製造贋畫的高手,因為這個身份,讓他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紀錄,彷彿不存在的幽靈。他受到長期雇主馬德拉之託,必須完成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的名作,於是他選擇了「傭兵隊長」。他希望藉著這幅贋畫,確立自己「不只是會複製」的藝術家身份,甚至因此能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並列。但最後,賈斯帕只完成一幅失敗的畫作,讓他醒悟這一再複製的生活,如牢籠般禁錮著他,無法忍受,必須殺死馬德拉。
作者喬治.培瑞克可說是法國有史以來最瘋狂的小說家,他在文學創作的成就恐怕無人能及,並曾獲多項極高榮譽的文學獎項;法國巴黎有條街以他命名,地球之外還有顆名為「Perec」的小行星。《傭兵隊長》是培瑞克青年時期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真正完成的小說,他在這本小說中已展露出獨特的文學才華,但其過於脫離常軌的書寫讓他屢被退稿,只好將書稿束之高閣,並在一次搬家時遺失。這使他在四十六歲因病離世時,猶帶著懊悔。在他辭世三十年後,這份書稿重新被發現,由法國重要文學出版社於2012年隆重推出。
培瑞克在這本小說中玩弄文字、搬移視角、分裂及擠壓節奏;敘事線在他手中,有如毛線被扭曲、被繃緊、被纏繞。從許多方面來看,《傭兵隊長》整部作品的確很像一球混亂的線團,有許多短詞堆積、不完整句等,甚至有幾處令人懷疑是出自原打字稿的問題或者誤植。而敘事線路的相纏、打結、迷失,更讓讀者慌亂驚跌。但這些從四處冒出來的線頭,卻可以讓我們抽出來,引著我們前往作品的後端。這本尖銳而驚人的《傭兵隊長》,也讓培瑞克實驗了後來他最具代表性的引用他人文本重新組合創造的技法,並如核心一般匯聚了他許多後來的偉大文本,成為閱讀及研究培瑞克的最佳路徑。
兇手賈斯帕選擇要複製《傭兵隊長》這幅名畫,因為他跟畫中的「傭兵隊長」一樣,在唇上有道疤痕;而本書作者培瑞克的唇上,也同樣有道疤痕。藉由這個疤痕,讓三個年代的三種身分重疊在一起,一個單純的殺人案,需要多重後設地解謎,因而賦予這部「首部小說」極其強烈的傳奇色彩。
作者簡介
喬治.培瑞克
喬治.培瑞克是法國籍波蘭猶太裔的知名文學家、電影導演,其文學創作包括小說、詩、戲劇、散文和評論隨筆,另外也參與劇本寫作、旁白、製片與導演等工作。培瑞克喜愛文字遊戲,他於1967年加入法國傳奇的「文學潛能工坊」(Oulipo),並在此將他的文字遊戲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中一本著名的懸疑小說《消逝》(La Disparition),完全不使用字母「E」。他的文學作品曾獲賀諾多文壇新人獎(Prix Renaudot)、梅迪奇文學獎(Prix Medicis);電影導演作品曾獲Prix Jean Vigo獎;法國巴黎有條街以他命名,甚至還有顆名為「Perec」的小行星。培瑞克因病過世時,年僅46歲。他的主要作品包含《東西》(Les Choses)、《生活使用指南》(La vie mode d’emploi)、《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以及他過世後才出版的《思考/分類》(Penser/Classer)。
喬治.培瑞克是法國籍波蘭猶太裔的知名文學家、電影導演,其文學創作包括小說、詩、戲劇、散文和評論隨筆,另外也參與劇本寫作、旁白、製片與導演等工作。培瑞克喜愛文字遊戲,他於1967年加入法國傳奇的「文學潛能工坊」(Oulipo),並在此將他的文字遊戲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中一本著名的懸疑小說《消逝》(La Disparition),完全不使用字母「E」。他的文學作品曾獲賀諾多文壇新人獎(Prix Renaudot)、梅迪奇文學獎(Prix Medicis);電影導演作品曾獲Prix Jean Vigo獎;法國巴黎有條街以他命名,甚至還有顆名為「Perec」的小行星。培瑞克因病過世時,年僅46歲。他的主要作品包含《東西》(Les Choses)、《生活使用指南》(La vie mode d’emploi)、《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以及他過世後才出版的《思考/分類》(Penser/Classer)。
目次
譯序──許綺玲
法文版序──克洛德.柏吉蘭
人物介紹
傭兵隊長
法文版序──克洛德.柏吉蘭
人物介紹
傭兵隊長
書摘/試閱
【譯序】還記得賈斯帕.溫克萊? / 許綺玲
一九五○年代末,剛出道的培瑞克嘗試投稿他的第一部小說《傭兵隊長》,卻處處碰壁,沉寂多年後,終於在他去世三十年後出版。這部小說終能問世,表示培瑞克沒被世人遺忘,不只如此,近年來他的地位在歐美日益受到重視,研究他作品的學者,從過去他的朋友輩,已傳承到了第二、三代,而研究的切入角度也隨著新的思潮、理論與方法學與時並進。事實上,在此之前,他發表於四處的文章一一結集出書,如非常另類的《思考/分類》;他因去世未能完成的小說《五十三天》也得以出版;有些一直廣受注目的文本,如《空間物種》,近年也重新再版;絕版的研究專著或論文集亦然。長期關注培瑞克的粉絲都知道有這麼一部未出版的小說《傭兵隊長》,已期待很久。書中主人翁的姓名賈斯帕.溫克萊,被培瑞克一再使用,貫穿於不同文本世界,有著神祕的同一性與差異性,而後來兩次同名者分別出現在其自傳與《生活使用指南》,讀者皆已熟知,就等這第一部小說現身。
故事就是關於這位名叫賈斯帕.溫克萊的贋畫師,因無法達成一次格外艱難且自我期許甚高,高到超乎一般贋畫師能力所及的任務──接近波赫斯筆下那位妄想重新寫出《唐吉訶德》的作家──因而動手殺了訂購者,偽畫畫商馬德拉。小說的敘事始於這件謀殺案發生的時刻,贋畫師殺人後便自行反鎖於地窖,並企圖挖地洞逃逸。於此同時,他回溯過去數月、數年間發生的事,反思事件的來龍去脈。
就故事來講,《傭兵隊長》已帶有培瑞克一生執著的幾個主題方向,尤其是真假、偽造、替代者、復仇、逃脫的主題。巧合的是,培瑞克完成出版的最後一本小說《玩家藏畫室》也是關於偽作騙局的復仇故事,原著序言作者柏吉蘭不忘提及,並與這本處女作對照比較。除此之外,培瑞克曾獲文學獎的《生活使用指南》也有偽造藝術品的詐騙故事。這一主題文學在他反覆精煉之下,幾乎已帶有史詩般的氣勢。
藝術品的仿造和藝術史一般悠久,牽動著人文與科學知識,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時代迷思,亦有賴人性弱點和時勢機運的操弄。真實贋畫案件的分析專著通常強調的是對金錢之貪婪,並以揭露「詐騙」罪行和手法為主要的評敘內容,不免以刑責和道德觀點論之。確實,不少贋畫師自行操控買賣,也是主要、甚至唯一的獲利者。然而,也有一種贋畫師只扮演整體共犯結構中的一環(但卻非主要得利者),且如其必然的隱匿身份一般,在公開場合沒有任何發言權。培瑞克在文學的範疇內發揮想像,讓這類隱形的贋畫師發聲,成為中心陳述者,開啟了一個充滿迷霧的隱蔽世界。
正如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比培瑞克小十來歲的蒙迪亞諾在《拉貢.路西安》所探討的問題類似,賈斯帕.溫克萊因偶然機緣而成為贋畫師,陶醉滿足於個己的成就表現,不問自身行為是非,也欠缺自我意識與對社會的責任感。這不只是許多人戰爭期間陷入的本能求生情境,在非戰時亦然,也時時充滿著近乎「平庸邪惡」的考驗。賈斯帕.溫克萊不斷重覆的「我不知道」讓人聯想到卡繆《異鄉人》那句有名的口頭蟬「我不在乎」。只是從「我不知道」出發,在無數的遲疑與來回思慮中,也在無數的「……」之間,贋畫師慢慢挖掘了自己行動背後的動機,「意識有什麼用?」似乎有了答案。若從有無決斷力與行動力的主題來看,以「哈姆雷特王子與真假父親」的關係模式來解讀小說中贋畫師與畫商老闆之間的關係,的確頗具說服力。
贋畫師的失敗是小說情節開展的起點,然後一路交錯回溯其前日常生活與工作情況、面臨失敗的意識、殺人前後之反應、殺人場景的重覆再現。綜言之,不斷移轉鏡頭般的剪輯,可由兩類型的書寫粗分,約可依五至六章逃出地窖的關鍵時刻為分界:前半部為萬花筒般搖轉的獨白,後半部大體上是口語的告白對話,也是完成拼圖的推敲歷程。從第一章起,敘事焦點便不斷在變換,陳述系統之人稱(他、你、我)和時序也不斷交錯。事實上,敘事手法的實驗性和語調風格不一的傾向,盛行於當時法國前衛性的文學創作。2008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與培瑞克同輩的勒克雷奇歐早年成名的小說(如《訊問筆錄》)便充滿了令人昏眩的風格拼貼流轉。順著賈斯帕的意識流獨白,我們看到他時而反問自責,時而陷入或近或遠的回憶,時而投射想像於未來。語調忽而亢奮,忽而理性,忽而輕佻、戲謔,忽而又充滿抽象哲思;由之,作者會以一生耽溺於自我書寫的米榭.雷希斯為扉頁引言,並非偶然。更奇特的是,有時作者彷彿介入其中,喜好成癖的文字遊戲和典故成語的喬裝耍弄,為故事注入了一種精算過的狂亂失控氛圍,然而遊戲的文字似已帶著讀者跳脫故事外,越向了純粹的文本層次,但這種時刻並不多見。
語言片斷化、口語化,句子不完整又不斷跳接的獨白或準獨白,僅為其中一種表述形式。培瑞克一如年輕時代的普魯斯特,也熱衷於演練風格模仿(不正是贋畫師的工作!),有些段落不禁令人連想到同時代的新小說,或如行為主義式的表象細述,經常聚焦在身體局部:
他剛點了一支菸,一手撐著桌子,稍微側身扭腰站著。他看著傭兵隊長。然後,很快地,他捻息了香菸。左手拂過桌面,擱在上頭,捉住一塊布,揉皺,一塊舊手帕,畫筆用的抹布。
一開頭放慢、顯微的解析描寫,已經有普魯斯特的風味,但偶而也有段落因拖長的隱喻修辭,更像普魯斯特,也有點像福樓拜。兩位都是他在文學書寫上永遠的啟蒙者:
而這深沉的混沌,就像是指揮家來到之前,交響樂團進行的和聲練習,每個樂器都在試奏自己樂譜的前幾小節,忙著調絃、調弓、調活塞、吹琶音、試合弦,就像是為了要突顯那混亂的沒裡沒肉,因為待會兒樂團指揮便會來到現場作明確的引導,並一步步遵循作曲家的提示,重新達到整體的一致性,待會兒,在終將回復的寧靜之中,燈光皆熄滅,將會湧現的是行進中的樂曲,小喇叭與法國號也樂於吹奏響亮,四重奏音量飽滿,定音鼓從時間奪取節奏、強加節奏於時間。
第十二章開頭直接引錄意大利文的畫家列傳,再以中規中矩的傳記文體交代畫家安東尼洛的生平。此外,有些段落與培瑞克後來寫的作品似曾相識,比如讀到冬季滑雪場上的小旗飄揚,怎能不想到《W或童年回憶》?另一段仿照歷險小說在回述往事前常見的橋段,好似陳封已久的祕密或謎團將被揭露,一時充滿著疑神疑鬼的不安氣氛,引喚的是維爾納!
無論在何處,一天,一陣電話鈴響,傳來一個人聲,遠遠地,聞見腳步聲,有隻手在敲你的門,輕輕敲三下,有隻手靠在你肩頭,無論何處,無論何時,在地鐵、在海灘、在街上、在車站。一天、一個月、一年將會過去,幾百幾千萬公里會越過,有人忽然喚你,過來見你,一道眼光和你交會,一秒之間,旋即消失。
挖地道的逃難過程既屬歷險小說的家常菜,也影射卡夫卡式的荒謬世界。正如柏吉蘭指出的,培瑞克後來豈不就在許多作品中大量進行風格模仿與抄襲挪用,並轉化為核心的書寫策略?沒過幾年,一九六七年《一個睡覺的人》已是經典。更多年後,《玩家藏畫室》更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一股作氣,更即物、更細密、更系統化,也更懸疑。相較之下,叼絮不止,彷彿下筆不能自已,有敝帚自珍之嫌……該說是《傭兵隊長》的「敗筆」嗎?若形式有其責任,此處他選擇了多次反復又不失變化的敘述與獨白或許有其必然性。因為主人翁只有在不斷地回望與主動盡力的重整之中,方逐漸體悟,正如普魯斯特從文學的苦心經營中取得實存的經驗與生命確證。撰寫《傭兵隊長》的那些年,培瑞克為電影《廣島之戀》作評,已有了同樣的理解──要從地獄歸來真不容易,況且還須不斷回頭!
【內文試閱】第一章
馬德拉很重。我捉著他的腋下,倒退走下通往工作室的樓梯。他的腳順著階梯一蹬一蹬地彈下,那間續的跳動,隨著我節奏不均地步下樓梯,冷冷地迴響在狹窄的拱頂下。牆上舞動著我們兩人的影子。他血流個不止,濕濕黏黏的鮮血,從吸得飽滿的海綿毛巾滲出來,順著絲質翻領快速流下,迷失在上衣的皺摺當中,一道道粘密且微微發亮的血流,碰到布料略顯粗糙,便滯留於凹折處,有時,則滴滴如珠,垂落下來,掉在地板上,濺開來,血跡斑斑。我把他擺在樓梯下方,緊靠著工作室的門旁邊,想再上樓去拿剃刀,並在奧圖回來之前把血跡擦掉。可是奧圖差不多跟我同時回來,他從另一道門進入。他看著我,一臉困惑。我一邊揮打一邊撤出,從樓梯跑下來,把自己關進了工作室。我把門栓上,還用衣櫃堵住。他幾分鐘之後也下來了,企圖撞門,但門已抵住;他又拖著馬德拉上去。我再把工作檯推過來加強門檔。一會兒之後他又回來了,他喚我。他對門開了兩槍。
你看,你也許自以為這很簡單。沒人在家,附近也無人。假使奧圖沒那麼快就折回來,你會在哪裡?你不知道,你在這兒。在工作室裡,如往常一般,什麼也沒變,或者說,只變了一點點。馬德拉死了。而縱然如此?你依然在這個地下工作室裡,只是比較亂,比較髒。同樣的日光從通風氣窗透進來。傭兵隊長,釘在他的畫架上……。
他看看四周。同樣的辦公室——同樣的玻璃墊,同樣的電話,同樣擺在鍍鋁鋼腳架上的歷年同日大事記。始終如一的嚴峻、低調風格、井然有序,冰冷和諧的色彩——暗綠色的地毯、獸皮紋扶手椅、淺赭色的幔簾——,無個性而拘謹的大型金屬分類夾……,可是,忽然間,馬德拉巨大鬆垮的身體造成了怪誕感,有如走調的樂音,哪裡有些不協調,時序錯亂……。 他從椅子上滑落下來,攤在背上,半瞇著眼,半開著嘴,露出一顆早已沉濁無光的金牙,更突顯其已然僵化,愚蠢而魯鈍的表情。從割開的喉頭,間歇洴出稠濃的血來,地上血流成河,一條條小小的血流,逐漸漫延地毯上,而這流散的、紅得發黑的血,在馬德拉的臉上四處擴散開來;再從那張異常蒼白的臉四周,溫熱的血洶湧而出,如猛獸般活躍,逐漸占據了整個房間,彷彿連牆壁也飽吸了血,也彷彿秩序、嚴謹,瞬時間都已遭翻轉破壞,一掃無遺,掠劫一空;也好似除了這奔騰的血流,除了這污濁荒謬的大片血灘,除了這無盡、倍增、擴張的屍體之外,一切都不存在……。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句子?「我想這不會造成任何困難。」他試著憶起馬德拉的嗓音,到底像什麼?第一回聽到他出聲時,那音色曾令他頗感驚訝,那是種齒唇音,略顯混濁曖昧,低聲呢喃,有些遲疑,咬字不清,但不易察覺,有如跛行——或說像是險些絆了腳——,好像他時時擔心會說錯話。我想……。哪個國籍?西班牙?南美?一種口音?改不了的口音?發音困難?不是。要單純得多:喉音發得沉濁的一種嗓音。還是有點沙啞。他再度見到他,走向他,伸出手來:「賈斯帕——這樣稱呼您沒錯吧,是嗎?——,能夠認識您,真是幸會幸會。」然後呢?這一切在他看來都不對勁?他在這兒幹嘛?他要他做什麼?魯夫事先都沒跟他講一聲……
人常出錯。以為事情自有安排,會順其自然發展。卻都難以預料。要自創願景容易得很。您呢,您要什麼?您要一幅畫?您想要一幅文藝復興時代的好畫?這好解決。那麼何不來一幅傭兵隊長呢……。
他的臉鬆垮垮的,似乎自以為帥氣。他的領帶。「魯夫和我提起很多你的事。」所以呢?一件好交易!你應該要小心,你應該早已料到……。這位你徹頭徹尾不認識的先生……。可是你一股腦地投進這個提議的機會中。太容易了。而現在。現在變成這樣……。
要達到那地步。他很快地算了一下:安置工作室所須的花費,材料,複製品——攝影、放大機、放射照相、紫外線燈、伍德燈、貼地燈——,投影器、歐洲美術館巡覽,保養……——, 這一大筆鉅款就為了這搞笑的結局……。愚蠢的禁閉,這是否有點滑稽?他準備吃飯,好像一點也沒事……那是前一晚……。然而,上頭,馬德拉的身體,正浸在他的一灘血裡……。而奧圖忠心耿耿地巡邏,腳步很重。種種一切導致這樣的境地!假如………的話,他此刻會在哪兒?他想到巴利阿里群島的陽光——也許他當初只要主動表示一下,一年半以前——,珍妮妃芙就會在他身旁……海灘、夕陽……一張美麗的明信片……。而現在一切是否將就此告終?
這時,他想起自己每個微小的動作:他剛點了一支菸,一手撐著桌子,稍微側身扭腰站著。他看著傭兵隊長。然後,很快地,他捻息了香菸。左手拂過桌面,擱在上頭,捉住一塊布,揉皺,一塊舊手帕,畫筆用的抹布。都好了。他重重靠著桌子,越來越重,兩眼不離傭兵隊長。一天又一天,徒勞無功?彷彿在他鬆弛的背後有股怒氣升了上來,漸漸領會豈有不憤怒的道理!他緊捉在手中的抹布已弄得很皺,他的指甲劃過桌面,嘎吱作響。他起身,走向工作檯,在散亂的工具之間四處尋找……。
硬黑皮套子。烏木手柄。發亮的刀片。他把刀片高舉向亮光處,確定它的刀口。他在想什麼?他感覺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只剩這股怒氣與喪氣……。他任自己倒坐在扶手椅,兩手抱頭,剃刀就在他眼前沒幾公分處,清晰、鋒銳,突顯於傭兵隊長上衣那危險光滑的表面上。只稍一下就完結了……,一下就夠了……。手臂高舉,刀光一閃……,只一個動作……,他慢步前進,地毯掩住了他的腳步聲,他溜到馬德拉的背後……。
一刻鐘已過去,差不多吧。為何一切動作竟顯得如此遙遠?幾乎要忘了?他在哪裡?他上樓。他又下樓。馬德拉死了。奧圖在巡邏。現在呢?奧圖會打電話給魯夫,魯夫會趕來。然後呢?如果奧圖找不到魯夫?魯夫在哪裡?全在那兒了。在這愚蠢的賭注。如果魯夫來了,他死定了,如果奧圖找不到魯夫,他就活得下去。還能活多久?奧圖有帶槍。氣窗太高太小。奧圖會不會睡著了?巡邏的人須要睡眠嗎……?
他快死了。這個想法倒有如允諾,反而令他放心。他還活著,他要死了。然後之後呢?達文西死了,安東尼洛死了,而我自己也覺得不太舒服。死得好蠢。事件的受害者。厄運、笨拙、犯錯的受害者。被告缺席被判刑。全體一致通過減一票——哪一票?——被判如耗子般死在地窖裡,在十來個無情眼光的注目之下——貼地光和X光,從羅浮宮的實驗室以驚人的天價買來的——,因殺人被判死刑,依此美好古老的律法:殺人者死,這個美好的、古老傳奇的道德——阿奇里斯的以牙還牙,對等報復——,死亡是精神生命的開端——在各種情境的配合之下,在一些微小事件甚不調和的彙聚之下,被判了死刑……。喂,巴黎,這裡是德赫爾,請稍候,我幫您轉到丹皮耶爾。喂,丹皮耶爾。巴黎在電話線另一端。請講!誰能想見這些戴著耳機,平和冷靜的接線生會是毫無閃失的劊子手……喂,柯寧先生,是我,奧圖在跟您講話,馬德拉剛剛死了……。
在黑夜裡,保時捷將躍起飛奔,車燈恰似噴火龍。不會有任何意外發生。大半夜裡,奧圖將會開門。大半夜裡,他們將要來找他……。
然後呢?這干你何事?他們將要來找你。那之後呢?去躺在扶手椅,瞪大眼睛仔細看,直到死亡到來,笨拙的耍刀者、自作聰明的搞笑者,不可言喻的傭兵隊長。負不負責任?有罪或無罪?當人家把你拖到斷頭台底下時,你會大聲呼喊,我無罪。這就是人家要證實的,劊子手會這麼答道。而斷頭台的刀咖啦一聲。完了。司法的第一證據。這還不明白嗎?這不是合乎常規嗎?為什麼還會有其他出路?
一九五○年代末,剛出道的培瑞克嘗試投稿他的第一部小說《傭兵隊長》,卻處處碰壁,沉寂多年後,終於在他去世三十年後出版。這部小說終能問世,表示培瑞克沒被世人遺忘,不只如此,近年來他的地位在歐美日益受到重視,研究他作品的學者,從過去他的朋友輩,已傳承到了第二、三代,而研究的切入角度也隨著新的思潮、理論與方法學與時並進。事實上,在此之前,他發表於四處的文章一一結集出書,如非常另類的《思考/分類》;他因去世未能完成的小說《五十三天》也得以出版;有些一直廣受注目的文本,如《空間物種》,近年也重新再版;絕版的研究專著或論文集亦然。長期關注培瑞克的粉絲都知道有這麼一部未出版的小說《傭兵隊長》,已期待很久。書中主人翁的姓名賈斯帕.溫克萊,被培瑞克一再使用,貫穿於不同文本世界,有著神祕的同一性與差異性,而後來兩次同名者分別出現在其自傳與《生活使用指南》,讀者皆已熟知,就等這第一部小說現身。
故事就是關於這位名叫賈斯帕.溫克萊的贋畫師,因無法達成一次格外艱難且自我期許甚高,高到超乎一般贋畫師能力所及的任務──接近波赫斯筆下那位妄想重新寫出《唐吉訶德》的作家──因而動手殺了訂購者,偽畫畫商馬德拉。小說的敘事始於這件謀殺案發生的時刻,贋畫師殺人後便自行反鎖於地窖,並企圖挖地洞逃逸。於此同時,他回溯過去數月、數年間發生的事,反思事件的來龍去脈。
就故事來講,《傭兵隊長》已帶有培瑞克一生執著的幾個主題方向,尤其是真假、偽造、替代者、復仇、逃脫的主題。巧合的是,培瑞克完成出版的最後一本小說《玩家藏畫室》也是關於偽作騙局的復仇故事,原著序言作者柏吉蘭不忘提及,並與這本處女作對照比較。除此之外,培瑞克曾獲文學獎的《生活使用指南》也有偽造藝術品的詐騙故事。這一主題文學在他反覆精煉之下,幾乎已帶有史詩般的氣勢。
藝術品的仿造和藝術史一般悠久,牽動著人文與科學知識,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時代迷思,亦有賴人性弱點和時勢機運的操弄。真實贋畫案件的分析專著通常強調的是對金錢之貪婪,並以揭露「詐騙」罪行和手法為主要的評敘內容,不免以刑責和道德觀點論之。確實,不少贋畫師自行操控買賣,也是主要、甚至唯一的獲利者。然而,也有一種贋畫師只扮演整體共犯結構中的一環(但卻非主要得利者),且如其必然的隱匿身份一般,在公開場合沒有任何發言權。培瑞克在文學的範疇內發揮想像,讓這類隱形的贋畫師發聲,成為中心陳述者,開啟了一個充滿迷霧的隱蔽世界。
正如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比培瑞克小十來歲的蒙迪亞諾在《拉貢.路西安》所探討的問題類似,賈斯帕.溫克萊因偶然機緣而成為贋畫師,陶醉滿足於個己的成就表現,不問自身行為是非,也欠缺自我意識與對社會的責任感。這不只是許多人戰爭期間陷入的本能求生情境,在非戰時亦然,也時時充滿著近乎「平庸邪惡」的考驗。賈斯帕.溫克萊不斷重覆的「我不知道」讓人聯想到卡繆《異鄉人》那句有名的口頭蟬「我不在乎」。只是從「我不知道」出發,在無數的遲疑與來回思慮中,也在無數的「……」之間,贋畫師慢慢挖掘了自己行動背後的動機,「意識有什麼用?」似乎有了答案。若從有無決斷力與行動力的主題來看,以「哈姆雷特王子與真假父親」的關係模式來解讀小說中贋畫師與畫商老闆之間的關係,的確頗具說服力。
贋畫師的失敗是小說情節開展的起點,然後一路交錯回溯其前日常生活與工作情況、面臨失敗的意識、殺人前後之反應、殺人場景的重覆再現。綜言之,不斷移轉鏡頭般的剪輯,可由兩類型的書寫粗分,約可依五至六章逃出地窖的關鍵時刻為分界:前半部為萬花筒般搖轉的獨白,後半部大體上是口語的告白對話,也是完成拼圖的推敲歷程。從第一章起,敘事焦點便不斷在變換,陳述系統之人稱(他、你、我)和時序也不斷交錯。事實上,敘事手法的實驗性和語調風格不一的傾向,盛行於當時法國前衛性的文學創作。2008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與培瑞克同輩的勒克雷奇歐早年成名的小說(如《訊問筆錄》)便充滿了令人昏眩的風格拼貼流轉。順著賈斯帕的意識流獨白,我們看到他時而反問自責,時而陷入或近或遠的回憶,時而投射想像於未來。語調忽而亢奮,忽而理性,忽而輕佻、戲謔,忽而又充滿抽象哲思;由之,作者會以一生耽溺於自我書寫的米榭.雷希斯為扉頁引言,並非偶然。更奇特的是,有時作者彷彿介入其中,喜好成癖的文字遊戲和典故成語的喬裝耍弄,為故事注入了一種精算過的狂亂失控氛圍,然而遊戲的文字似已帶著讀者跳脫故事外,越向了純粹的文本層次,但這種時刻並不多見。
語言片斷化、口語化,句子不完整又不斷跳接的獨白或準獨白,僅為其中一種表述形式。培瑞克一如年輕時代的普魯斯特,也熱衷於演練風格模仿(不正是贋畫師的工作!),有些段落不禁令人連想到同時代的新小說,或如行為主義式的表象細述,經常聚焦在身體局部:
他剛點了一支菸,一手撐著桌子,稍微側身扭腰站著。他看著傭兵隊長。然後,很快地,他捻息了香菸。左手拂過桌面,擱在上頭,捉住一塊布,揉皺,一塊舊手帕,畫筆用的抹布。
一開頭放慢、顯微的解析描寫,已經有普魯斯特的風味,但偶而也有段落因拖長的隱喻修辭,更像普魯斯特,也有點像福樓拜。兩位都是他在文學書寫上永遠的啟蒙者:
而這深沉的混沌,就像是指揮家來到之前,交響樂團進行的和聲練習,每個樂器都在試奏自己樂譜的前幾小節,忙著調絃、調弓、調活塞、吹琶音、試合弦,就像是為了要突顯那混亂的沒裡沒肉,因為待會兒樂團指揮便會來到現場作明確的引導,並一步步遵循作曲家的提示,重新達到整體的一致性,待會兒,在終將回復的寧靜之中,燈光皆熄滅,將會湧現的是行進中的樂曲,小喇叭與法國號也樂於吹奏響亮,四重奏音量飽滿,定音鼓從時間奪取節奏、強加節奏於時間。
第十二章開頭直接引錄意大利文的畫家列傳,再以中規中矩的傳記文體交代畫家安東尼洛的生平。此外,有些段落與培瑞克後來寫的作品似曾相識,比如讀到冬季滑雪場上的小旗飄揚,怎能不想到《W或童年回憶》?另一段仿照歷險小說在回述往事前常見的橋段,好似陳封已久的祕密或謎團將被揭露,一時充滿著疑神疑鬼的不安氣氛,引喚的是維爾納!
無論在何處,一天,一陣電話鈴響,傳來一個人聲,遠遠地,聞見腳步聲,有隻手在敲你的門,輕輕敲三下,有隻手靠在你肩頭,無論何處,無論何時,在地鐵、在海灘、在街上、在車站。一天、一個月、一年將會過去,幾百幾千萬公里會越過,有人忽然喚你,過來見你,一道眼光和你交會,一秒之間,旋即消失。
挖地道的逃難過程既屬歷險小說的家常菜,也影射卡夫卡式的荒謬世界。正如柏吉蘭指出的,培瑞克後來豈不就在許多作品中大量進行風格模仿與抄襲挪用,並轉化為核心的書寫策略?沒過幾年,一九六七年《一個睡覺的人》已是經典。更多年後,《玩家藏畫室》更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一股作氣,更即物、更細密、更系統化,也更懸疑。相較之下,叼絮不止,彷彿下筆不能自已,有敝帚自珍之嫌……該說是《傭兵隊長》的「敗筆」嗎?若形式有其責任,此處他選擇了多次反復又不失變化的敘述與獨白或許有其必然性。因為主人翁只有在不斷地回望與主動盡力的重整之中,方逐漸體悟,正如普魯斯特從文學的苦心經營中取得實存的經驗與生命確證。撰寫《傭兵隊長》的那些年,培瑞克為電影《廣島之戀》作評,已有了同樣的理解──要從地獄歸來真不容易,況且還須不斷回頭!
【內文試閱】第一章
馬德拉很重。我捉著他的腋下,倒退走下通往工作室的樓梯。他的腳順著階梯一蹬一蹬地彈下,那間續的跳動,隨著我節奏不均地步下樓梯,冷冷地迴響在狹窄的拱頂下。牆上舞動著我們兩人的影子。他血流個不止,濕濕黏黏的鮮血,從吸得飽滿的海綿毛巾滲出來,順著絲質翻領快速流下,迷失在上衣的皺摺當中,一道道粘密且微微發亮的血流,碰到布料略顯粗糙,便滯留於凹折處,有時,則滴滴如珠,垂落下來,掉在地板上,濺開來,血跡斑斑。我把他擺在樓梯下方,緊靠著工作室的門旁邊,想再上樓去拿剃刀,並在奧圖回來之前把血跡擦掉。可是奧圖差不多跟我同時回來,他從另一道門進入。他看著我,一臉困惑。我一邊揮打一邊撤出,從樓梯跑下來,把自己關進了工作室。我把門栓上,還用衣櫃堵住。他幾分鐘之後也下來了,企圖撞門,但門已抵住;他又拖著馬德拉上去。我再把工作檯推過來加強門檔。一會兒之後他又回來了,他喚我。他對門開了兩槍。
你看,你也許自以為這很簡單。沒人在家,附近也無人。假使奧圖沒那麼快就折回來,你會在哪裡?你不知道,你在這兒。在工作室裡,如往常一般,什麼也沒變,或者說,只變了一點點。馬德拉死了。而縱然如此?你依然在這個地下工作室裡,只是比較亂,比較髒。同樣的日光從通風氣窗透進來。傭兵隊長,釘在他的畫架上……。
他看看四周。同樣的辦公室——同樣的玻璃墊,同樣的電話,同樣擺在鍍鋁鋼腳架上的歷年同日大事記。始終如一的嚴峻、低調風格、井然有序,冰冷和諧的色彩——暗綠色的地毯、獸皮紋扶手椅、淺赭色的幔簾——,無個性而拘謹的大型金屬分類夾……,可是,忽然間,馬德拉巨大鬆垮的身體造成了怪誕感,有如走調的樂音,哪裡有些不協調,時序錯亂……。 他從椅子上滑落下來,攤在背上,半瞇著眼,半開著嘴,露出一顆早已沉濁無光的金牙,更突顯其已然僵化,愚蠢而魯鈍的表情。從割開的喉頭,間歇洴出稠濃的血來,地上血流成河,一條條小小的血流,逐漸漫延地毯上,而這流散的、紅得發黑的血,在馬德拉的臉上四處擴散開來;再從那張異常蒼白的臉四周,溫熱的血洶湧而出,如猛獸般活躍,逐漸占據了整個房間,彷彿連牆壁也飽吸了血,也彷彿秩序、嚴謹,瞬時間都已遭翻轉破壞,一掃無遺,掠劫一空;也好似除了這奔騰的血流,除了這污濁荒謬的大片血灘,除了這無盡、倍增、擴張的屍體之外,一切都不存在……。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句子?「我想這不會造成任何困難。」他試著憶起馬德拉的嗓音,到底像什麼?第一回聽到他出聲時,那音色曾令他頗感驚訝,那是種齒唇音,略顯混濁曖昧,低聲呢喃,有些遲疑,咬字不清,但不易察覺,有如跛行——或說像是險些絆了腳——,好像他時時擔心會說錯話。我想……。哪個國籍?西班牙?南美?一種口音?改不了的口音?發音困難?不是。要單純得多:喉音發得沉濁的一種嗓音。還是有點沙啞。他再度見到他,走向他,伸出手來:「賈斯帕——這樣稱呼您沒錯吧,是嗎?——,能夠認識您,真是幸會幸會。」然後呢?這一切在他看來都不對勁?他在這兒幹嘛?他要他做什麼?魯夫事先都沒跟他講一聲……
人常出錯。以為事情自有安排,會順其自然發展。卻都難以預料。要自創願景容易得很。您呢,您要什麼?您要一幅畫?您想要一幅文藝復興時代的好畫?這好解決。那麼何不來一幅傭兵隊長呢……。
他的臉鬆垮垮的,似乎自以為帥氣。他的領帶。「魯夫和我提起很多你的事。」所以呢?一件好交易!你應該要小心,你應該早已料到……。這位你徹頭徹尾不認識的先生……。可是你一股腦地投進這個提議的機會中。太容易了。而現在。現在變成這樣……。
要達到那地步。他很快地算了一下:安置工作室所須的花費,材料,複製品——攝影、放大機、放射照相、紫外線燈、伍德燈、貼地燈——,投影器、歐洲美術館巡覽,保養……——, 這一大筆鉅款就為了這搞笑的結局……。愚蠢的禁閉,這是否有點滑稽?他準備吃飯,好像一點也沒事……那是前一晚……。然而,上頭,馬德拉的身體,正浸在他的一灘血裡……。而奧圖忠心耿耿地巡邏,腳步很重。種種一切導致這樣的境地!假如………的話,他此刻會在哪兒?他想到巴利阿里群島的陽光——也許他當初只要主動表示一下,一年半以前——,珍妮妃芙就會在他身旁……海灘、夕陽……一張美麗的明信片……。而現在一切是否將就此告終?
這時,他想起自己每個微小的動作:他剛點了一支菸,一手撐著桌子,稍微側身扭腰站著。他看著傭兵隊長。然後,很快地,他捻息了香菸。左手拂過桌面,擱在上頭,捉住一塊布,揉皺,一塊舊手帕,畫筆用的抹布。都好了。他重重靠著桌子,越來越重,兩眼不離傭兵隊長。一天又一天,徒勞無功?彷彿在他鬆弛的背後有股怒氣升了上來,漸漸領會豈有不憤怒的道理!他緊捉在手中的抹布已弄得很皺,他的指甲劃過桌面,嘎吱作響。他起身,走向工作檯,在散亂的工具之間四處尋找……。
硬黑皮套子。烏木手柄。發亮的刀片。他把刀片高舉向亮光處,確定它的刀口。他在想什麼?他感覺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只剩這股怒氣與喪氣……。他任自己倒坐在扶手椅,兩手抱頭,剃刀就在他眼前沒幾公分處,清晰、鋒銳,突顯於傭兵隊長上衣那危險光滑的表面上。只稍一下就完結了……,一下就夠了……。手臂高舉,刀光一閃……,只一個動作……,他慢步前進,地毯掩住了他的腳步聲,他溜到馬德拉的背後……。
一刻鐘已過去,差不多吧。為何一切動作竟顯得如此遙遠?幾乎要忘了?他在哪裡?他上樓。他又下樓。馬德拉死了。奧圖在巡邏。現在呢?奧圖會打電話給魯夫,魯夫會趕來。然後呢?如果奧圖找不到魯夫?魯夫在哪裡?全在那兒了。在這愚蠢的賭注。如果魯夫來了,他死定了,如果奧圖找不到魯夫,他就活得下去。還能活多久?奧圖有帶槍。氣窗太高太小。奧圖會不會睡著了?巡邏的人須要睡眠嗎……?
他快死了。這個想法倒有如允諾,反而令他放心。他還活著,他要死了。然後之後呢?達文西死了,安東尼洛死了,而我自己也覺得不太舒服。死得好蠢。事件的受害者。厄運、笨拙、犯錯的受害者。被告缺席被判刑。全體一致通過減一票——哪一票?——被判如耗子般死在地窖裡,在十來個無情眼光的注目之下——貼地光和X光,從羅浮宮的實驗室以驚人的天價買來的——,因殺人被判死刑,依此美好古老的律法:殺人者死,這個美好的、古老傳奇的道德——阿奇里斯的以牙還牙,對等報復——,死亡是精神生命的開端——在各種情境的配合之下,在一些微小事件甚不調和的彙聚之下,被判了死刑……。喂,巴黎,這裡是德赫爾,請稍候,我幫您轉到丹皮耶爾。喂,丹皮耶爾。巴黎在電話線另一端。請講!誰能想見這些戴著耳機,平和冷靜的接線生會是毫無閃失的劊子手……喂,柯寧先生,是我,奧圖在跟您講話,馬德拉剛剛死了……。
在黑夜裡,保時捷將躍起飛奔,車燈恰似噴火龍。不會有任何意外發生。大半夜裡,奧圖將會開門。大半夜裡,他們將要來找他……。
然後呢?這干你何事?他們將要來找你。那之後呢?去躺在扶手椅,瞪大眼睛仔細看,直到死亡到來,笨拙的耍刀者、自作聰明的搞笑者,不可言喻的傭兵隊長。負不負責任?有罪或無罪?當人家把你拖到斷頭台底下時,你會大聲呼喊,我無罪。這就是人家要證實的,劊子手會這麼答道。而斷頭台的刀咖啦一聲。完了。司法的第一證據。這還不明白嗎?這不是合乎常規嗎?為什麼還會有其他出路?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