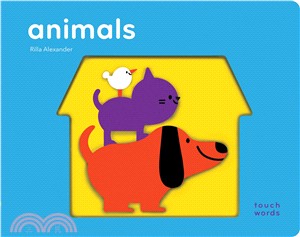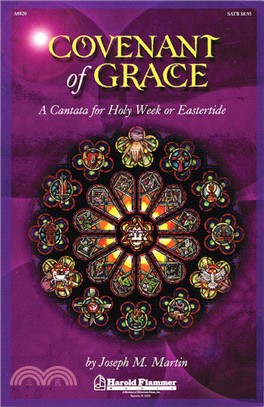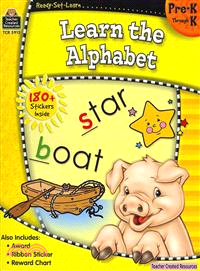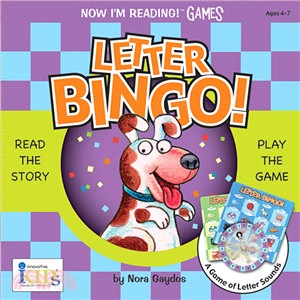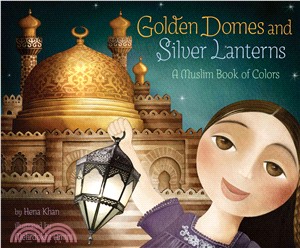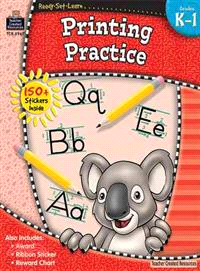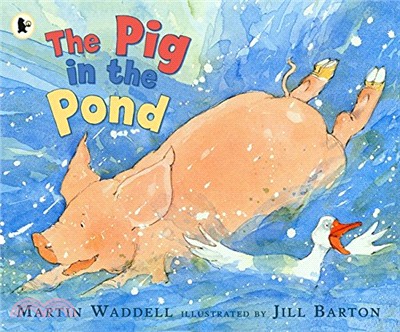商品簡介
哥德派的詭譎美感 × 浮士德的魔鬼交易
挑戰保守社會的極限,改變王爾德一生的轉捩點
「寫出這種故事的作家,應該處以死刑!」
2003年英國《觀察者報》評選百大傑出小說
2006年及2008年皆入選死前必讀的小說
2010年愛爾蘭國家文學季的都柏林代表選書
2014年英國《衛報》評選百大必讀小說
「這是一個關於時間、關於美、關於脆弱、關於愛與傷痛的故事。王爾德用戲謔又諷刺的文字將它包起,咀嚼再三只有更入味,因為在虛幻的劇情裡人性無比真實。」──韋禮安/創作歌手
林佑軒/作家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凌性傑/作家
陳俊志/作家/導演
陳 雪/小說家
鍾文音/作家
──好評推薦(依筆劃順序排列)
如果是我永遠年輕,畫像變老就好了!
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我願意用自己的靈魂交換!
才華洋溢的畫家巴索爾因緣結識了年輕俊美的道林‧格雷,立刻請格雷做自己的模特兒畫肖像畫,巴索爾知道,這幅畫將會是他畢生傑作。隨著畫像即將完成,巴索爾對格雷越加依戀,此時畫家的老友亨利勳爵意外來訪。亨利勳爵雖有貴族身分,但行事放縱不羈,沉浸享樂,他對年輕而單純的格雷十分有興趣,想試試自己對格雷能有多大影響,因此開始灌輸格雷自己那一套享樂主義。肖像畫完成後,格雷也驚艷於自己的美貌,心中的虛榮感隨之甦醒,他害怕自己將會失去青春年華、失去美麗外表,忍不住說出願以靈魂交換畫像中不朽的容顏。
格雷跟著亨利勳爵流連於奢華放蕩的社交宴會,沉溺於旁人對他的愛慕,此時格雷認識了美麗出眾的女演員希珀,折服於她的動人演技,而希珀也深受格雷吸引,兩人陷入熱戀。想不到,希珀嘗試過真正的愛情,對於要在舞台上演出虛假的感情就不屑一顧,演技突然變得生硬做作,讓格雷大失所望,一怒之下斷然與希珀分手,絕望的希珀當晚便自殺身亡。
格雷知道消息後雖然感到震驚,卻不認為自己有錯,他的內心已然失去同情與愛憐;此時格雷無意間看到自己那張畫像,發現畫像中的他,嘴角竟扯出一抹殘忍的神色……
◎特別收錄:王爾德最想讓世人看見的道林‧格雷◎
1889年8月,《利平考特》雜誌的編輯史答達特在倫敦宴請兩位作家,一位是剛寫出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的亞瑟‧柯南‧道爾,另一位就是當時的文壇巨星奧斯卡‧王爾德。宴中,史答達特向兩人邀稿;隔年2月,柯南道爾便交出福爾摩斯與華生破的第二件案子:《四簽名》。反觀王爾德,他一直到1890年4月才交出《格雷的畫像》,初稿只有5萬字,儘管王爾德對許多同性情慾的描寫已經盡量淡化,但史答達特依然又做了一次修改才敢刊出。雜誌出刊後,王爾德便著手將這篇故事延伸成更完整的小說作品。因此,這部小說總共有三個版本:王爾德投稿的原版、經過史答達特修改的連載版,最後由王爾德親自編輯加長後出版的1891年版。遠流重新翻譯出版繁體中文版,特別收錄三個版本的差異比較,從遭到修改、刪除的片段文字,可以推知雜誌編輯以及王爾德的考量,也能感受當時社會氛圍帶給作家的壓力。
◎視覺設計:藍調漩渦的美麗迷惑◎
封面設計的色調以深藍為主,大膽而獨具魅力,讓人聯想到格雷所享受的上流奢華,堆砌雕琢的藝術品味,看一眼就難忘。翻飛的羽毛在深藍間盤旋,彷彿在迷惑觀者的心神,羽毛的輕柔撫觸也對應著戀人間的互動,隱晦點出字裡行間未說明白的情慾。
「我不明白怎麼會有人認為這麼好的作品竟是不道德的。」──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這個故事中帶著超自然的情節,擁有第一流的藝術價值。」──華特‧佩特(Walter Pater),《讀書人》(The Bookman)書評
作者簡介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出身於愛爾蘭世家,是家中次子,父親為外科醫生,母親則是詩人與作家,王爾德從小便接受豐富的知識陶冶,為他日後的成就奠基。1881年出版首部作品《詩集》後,在文壇嶄露頭角,雖然他沒有獲獎加持,但是憑著幽默機智的談吐、特立獨行的穿著與行為,讓他在倫敦社交圈名聲響亮,甚至有人視他為現代「名流」的先驅。
真正讓王爾德聲名大噪的是他的劇本,經典劇作包括《莎樂美》、《不可兒戲》以及《理想的丈夫》等等,時至今日都仍經常搬演、改編;另外,他的童話故事集《快樂王子》、《石榴屋》也為人稱頌,故事中帶著對時事與社會的諷刺批判,更添文學價值。
而王爾德最受爭議的作品則是他的小說《格雷的畫像》,書中的同性戀及墮落罪惡的情節讓這本書備受批評,但王爾德依然堅持出版小說,他曾坦白承認:「巴索爾是我內在對自己的認知,亨利是外人看我的樣貌,而格雷則是我希望成為的形象,只是不在我這個年紀。」
1895年,王爾德因同性戀而遭指控有害風化,法庭審判認定他有罪,他因此入獄服刑兩年。他在獄中仍有寫作,但或許苦役生活艱困,這時的作品已難看出唯美主義的影子。1897年獲釋後,王爾德避走法國巴黎,於1900年因腦膜炎病逝,享年46歲。
譯者簡介:
譯者-吳孟儒(Avery)
台師大口譯碩士,留學美國、荷蘭,現旅居日本。專職中英日口筆譯,譯作累計二十餘本。生性最怕無聊,喜歡挑戰從未譯過的各類題材,覺得口筆譯是世上最棒的工作。
序
作者序
藝術家創造美麗的事物;
藝術的目的就是展現藝術,藏起藝術家的面貌。
評論家則轉化自身對美麗事物的印象,變成另一種形式,甚至是新的東西。
自傳是最高也是最低層次的評論。
如果一個人在美麗的事物中發現醜惡的意義,這個人便是腐敗墮落,毫無魅力可言。此乃大錯特錯。
能在美麗的事物中發現美麗的意義,才算得上受過良好教養。因為這些人的存在,世界還有希望。
這些人是幸運的;對他們來說,美的事物只有一個意義,那就是「美」。
對他們來說,世上沒有所謂道德或不道德的書,只有寫得好或寫得不好的書,如此而已。
十九世紀對現實主義的厭惡之情,不過是卡利班看見鏡中自身容顏而感到憤怒。
十九世紀對浪漫主義的反感,是卡利班看不見鏡中自身容顏而感到的憤怒。
人的道德是藝術家的創作主題之一,但藝術的道德來自不完美媒介的完美運用。
藝術家從沒真的打算證明什麼;如果連真相都需要證明,證明是為了什麼?
藝術家也沒什麼道德同情。藝術家心中若摻了同情,等於荒藝術風格之大謬,不可原諒。
藝術家沒特別喜歡憂鬱,他們可以表現一切事物。
對藝術家來說,想法與語言都是藝術的工具。
善與惡都是藝術的材料。
從形式來看,所有藝術都應以音樂家的藝術為準;從感覺來說,所有藝術都應以演員的演技為標竿。
因此藝術都是既表面又象徵的;
倘若藝術的呈現超過了表面,只是給自己找麻煩;
解讀象徵的人也是,都是自找麻煩。
藝術模仿的其實是觀者,不是人生。
一件藝術作品如果得到各種評論迴響,代表這件作品很創新、很複雜,充滿活力。
評論家的意見不一時,藝術家只會同意自己。
倘若一個人做出有用之物,只要他不崇拜這件作品,我們就能原諒他。若要創作完全無用的東西,唯一的理由就是對這樣東西的極度崇拜。
所有的藝術都沒什麼用。
譯者序
當初試譯這本經典文學,實在不知天高地厚。反正不會過,就當作翻譯練習吧,我心想。沒想到,竟然如此好運,得到難得機會。只是簽了約,才發現這是甜美的惡夢。甜的是作品讀來如沐春風,話語淺白卻妙語如珠。惡的是自覺力有未逮,不是翻得索然無味,便是太過咬文嚼字、文白夾雜。一方面,也因為自己對十九世紀的英國不瞭解,一百多年前的社會風俗加上當時用語的差異(如「pray」在當時口語通常是「please」之意,而不是「祈禱」),不得不開始查找資料。
這裡特別感謝石岱崙老師(Darryl Sterk)幫我提供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還有陳碧珠老師與翻譯所的大家陪我一起研究小說中難譯之處。
文學領域不像資訊取向的書,沒有太多資料可供比對。有些遇到無法確定之處,當下覺得這樣翻雖不中亦不遠;事隔一個月之前再偶然看到,才發現發現自己大錯特錯。
為了能超越之前的舊譯本,我找了過去幾個譯本,包括徐進夫(1972)、姚怡平(2001)與顏湘如(2004)等人的翻譯。比對之下,發現顏湘如的譯本實在翻得太好,時時讓我自嘆不如;到後來,只能求翻出自己的風格,無法強求真正超越前人譯本。或許可以說,顏的風格比較秀麗文雅,我的譯文則力求淺白易懂,縮短讀者與作品時代的距離。
雖然力求盡善盡美,但書中的一首法文詩真是將我打敗了。這首詩找不到現成的中譯本,只能尋求英譯本,再加上我學過的的點法文查閱英法漢字典,但仍遠遠不如顏的譯本(她是法文系畢業)。其他地方或能與顏譯本互別苗頭,但這首法文詩的中譯,小弟只能甘拜下風。
書中關於人生哲學的機巧對白,時而讓我想到朱少麟的作品。在《格雷的畫像》中有一句:「In the slanting beams that streamed through the open doorway the dust danced and was golden.」我譯為「門口透進的斜光中金色的粉翳靜靜翻飛」,眼尖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朱少麟的《燕子》也有一句:「斜光中見得到無數的金色粉翳靜靜翻飛。」還記得高中時讀到這句話,只覺得好美、好美,第一次看到有人能用美得像詩的句子描寫光線裡的粉塵。翻譯這本小說時,看到「the dust danced and was golden」,這句話立刻浮現腦中,揮之不去,乾脆從善如流。
當然,王爾德與朱少麟的風格不盡相同,只是這也反映了每位譯者詮釋文學作品時,必然會帶入自己時代的個人與文化體驗,我想這也是遠流希望重譯一系列經典文學的原因。
謝謝立妍的耐心與寬容,一直相信我、鼓勵我一定可以翻得下去。也謝謝所有幫上忙的夥伴們,有你們真好!
目次
總序-聽見譯者的聲音
譯者序
作者序
格雷的畫像
附錄-王爾德最想讓世人認識的道林‧格雷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畫室裡滿是玫瑰濃郁的香氣。夏日的微風吹過花園林間,便送來紫丁花濃厚的沁人芬芳,抑或粉紅山楂花的微妙香氣,流過敞開的門一洩而入。
亨利.華頓勛爵躺在長沙發椅上,沙發上鋪著波斯鞍袋,他一如往常抽著數不清的菸。從他坐的角落,可以看到蜂黃蜜香的金鏈花盛放,顫抖的枝葉像承載不住火一般燒起來地美。偶爾,奇異的飛鳥點影落在巨大窗前的柞絲長簾,那一瞬間的和風剪影,讓他想到面白如玉的日本東京畫家,如何以絕對靜止的媒介表現靈巧的動感。蜜蜂鑽過久未修剪的蔓生草地,盤旋於錯落無序、滿佈塵土的忍冬花上,在嗡嗡聲的襯托之下,周遭的靜默顯得更加咄咄逼人。倫敦街道隱約傳來的喧囂,像是遠處風琴的低音迴盪。
畫室正中央有座直立畫架,架上放著一幅肖像,真人大小的畫中青年俊美無儔,畫像前坐的正是畫家巴索爾.霍華;幾年前,他突然失蹤,引起眾人議論紛紛,各種奇怪的揣測都有人說。
看著自己重現畫裡的美麗線條,畫家臉上浮現滿意的笑容,那樣的笑彷彿會在他臉上流連許久;但他突然臉色一變,閉上眼,覆以手指掩蓋,像要鎖住腦中的奇異夢境,深怕人醒夢散。
「巴索爾,這是你畫過最好的畫,是你最好的作品。」亨利勛爵懶洋洋地說,「你明年一定要把這幅寄到格羅夫納藝廊。皇家藝術學院太大、太俗氣,我每次去,要不是人多到畫看不清楚,嚇死人;不然就是畫多到人看不清楚,那就更嚇人了。只能寄去格羅夫納。」
「我哪也不寄。」畫家回話時習慣性把頭往後甩;他以前在牛津的朋友老取笑他這個動作。「對,我哪也不寄。」
亨利勛爵挑起雙眉,雙眼透露出訝異,手上的鴉片重菸燃著裊裊青煙,在屋內盤旋繚繞,他看著巴索爾。「哪也不寄?老巴,為什麼不寄?你瘋了嗎?你們畫家真怪!先是不擇手段讓自己出名,出了名後又趕緊低調。真是太傻了,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讓人講話更糟,那就是沒有人講。這幅畫足以讓你遠遠超越英國所有年輕人,讓所有老人都嫉妒你,當然,如果老人還能保有什麼情緒。」
「我知道你會笑我,」他回答,「可是我真的不能公開這幅畫,我放了太多自己在裡面。」
亨利勛爵在長沙發上伸著懶腰,縱聲大笑。
「對,我知道你會笑。可是我說真的,不騙你。」
「放了太多自己在裡面!巴索爾,我不得不說,我不知道你這麼愛往自己臉上貼金,我看不出你跟畫裡的人哪裡像了。你的臉有稜有角、五官凸出,頭髮像黑炭;可是,畫裡的美少年像是希臘神話的阿朵尼斯,說是用象牙和玫瑰葉捏出來的也不為過。真要說,他就像美到愛上自己的納西斯,而你呢,當然,你很有才氣,很會動腦;可是所謂的美,那種真正的美,一但動了腦袋就要完蛋。人一動起腦來,表情難免誇張,誇張就毀了臉的和諧。一旦人坐下來開始動腦,整張臉就擠成一隻鼻子、一塊額頭,甚至是更可怕的樣子。看看需要學識墨水的行業,那些成功人士早就面目全非!當然,教會另當別論,教會的人不思考的。八十歲的主教依然說著十八歲時學的話,也難怪看起來總是這麼開心。你這位年輕朋友這麼神祕,你連名字都不說,他的畫像卻讓我好著迷。我看得出來,他不思考的,我很確定。他是無腦的美麗生物,無花可賞的冬日需要他的點綴,炎炎夏日需要他來冷卻我們的腦袋。巴索爾,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你跟他一點都不像。」
「亨利,你沒聽懂我的意思。」畫家巴索爾回話,「我們看起來當然不像,我自己也很清楚;應該說,要是看起來像就糟了。你聳什麼肩?我說真的。特別好看跟特別聰明的人註定要不幸,就像歷史上很多逐漸失勢的君王,衰亡的腳步早就命中有數。人最好不要出類拔萃。醜人、笨人是最幸運的;他們可以悠悠哉哉坐著看戲,就算不懂『贏』的滋味,至少也不會知道『輸』怎麼寫。他們過的才是人人該過的人生:不叨不擾、不聞不問、不憂不慮。他們既不害人,別人也不會加害他們。亨利,你有階級跟財富;我有腦袋,就是我的藝術,先不論我的藝術有多少價值;而道林.格雷他有美貌,可以說,我們都要因為眾神的這些恩賜而受苦。」
「道林.格雷?他叫道林.格雷嗎?」畫室彼端的亨利勛爵走到巴索爾身邊。
「對,他叫道林.格雷。我本來沒打算告訴你。」
「為什麼不告訴我?」
「噢,我也說不上來。我如果很喜歡誰,就不會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任何人;透露名字,就像放棄了他們的一部分。我愈來愈喜歡祕密,好像只有祕密才能讓現代生活變得神祕或美妙。只要藏起來,再平凡的事物也顯得有意思。我出遠門從不告訴家裡我去哪,說了就沒意思了。這個習慣聽起來傻氣,但實在讓生活增添不少浪漫。我猜,你大概覺得我這種想法很蠢吧?」
「怎麼會,」亨利勛爵回道,「老巴,一點都不蠢。你好像忘了,我已經結婚了;婚姻有種魔力,讓謊言變成雙方的必需品。我從來不知道我太太在哪裡,她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當然,我們偶爾還是會碰面,有時一起吃飯,有時去公爵家,我們相見時就一臉正經地胡說八道。她這方面的功力之高,應該說,她的功力比我高多了。她從來不會搞錯日期,可是我老搞錯;只是就算被她抓到,她也不多吭一聲。我有時候真希望她可以生氣,但她卻只是笑我。」
「亨利,我不喜歡你這樣講自己的婚姻。」巴索爾漫步走向花園那扇門,「我相信你是個好丈夫,可是你卻以自己的美德為恥。你實在不是一般人。你說的話沒一句有良心,卻也從沒犯過錯。你的話那麼憤世嫉俗,其實只是故作姿態。」
「順應自己的本性不過就是種姿態,而且是最惱人的姿態。」亨利勛爵笑鬧回應。兩個年輕人一同走進花園,愜意地坐在高大月桂叢影下的長竹椅上。陽光滑落在晶亮的葉子間,草地上的白色雛菊迎風微微顫抖。
過了一會兒,亨利勛爵拿出錶說:「不好意思,巴索爾,我恐怕得走了。」接著輕聲說道,「我走之前,你得回答我剛剛的問題。」
「什麼問題?」巴索爾看著地上。
「你很清楚是什麼問題。」
「我不清楚。」
「好,那我就告訴你。我要你解釋為什麼不展出道林.格雷的畫像。我要聽真正的理由。」
「我已經告訴你真正的理由了。」
「才怪,你沒有。你說,是因為放了太多的自己在裡面,這種幼稚藉口怎麼騙得了我。」
「亨利,」巴索爾看著勛爵的眼睛回答,「每一幅用感覺畫出來的肖像,畫的都是畫家自己,不是模特兒。模特兒不過是個意外,是種情境。在滿是顏料的畫布上,畫家呈現的不是模特兒,而是他自己。我不想展出,是因為我不想洩露自己靈魂的祕密。」
亨利勛爵笑了。「什麼祕密?」他問。
「我會告訴你的。」巴索爾這樣說,卻面有難色。
「我洗耳恭聽。」亨利勛爵看著他。
「亨利,真的沒什麼好說的。」畫家說,「更何況,說了恐怕你也不懂,或根本不信。」
亨利勛爵笑著往後躺。他拔起草地上一株淡粉花瓣的雛菊仔細端詳,又說:「我肯定會懂。」他凝視手中白羽金輪般的花蕊說,「至於信不信,只要是難以置信的事,我都信。」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