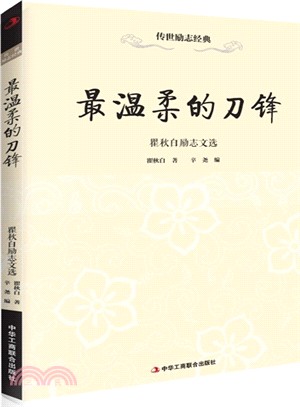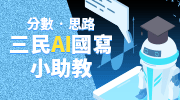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瞿秋白,在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深得人們敬仰。
瞿秋白的一生,才華橫溢,知識淵博,他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魯迅也曾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同懷視之”贈與他。
名人/編輯推薦
勵志并非粘貼在生命上的標簽,而是融匯于人生中一點一滴的氣蘊,最后成長為人的格調和氣質,成就人生的夢想。無論從是哪一行,有志不論年少,無志枉活百歲。
這套《傳世勵志經典》共收輯了100部圖書,包括傳記、文集、選輯。我們想為勵志者提供心靈的營養,有如心靈雞湯那樣鮮美;有如粗茶淡飯卻為生命所需。無論直接或間接,我們定會從先賢們的追求和感悟中收獲一份驚喜。
本書收錄了瞿秋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游記、雜文以及散文。
大知識分子悲憫的情懷和人文反思在瞿秋白的文字中得以體現,同時也讓人了解到學會真實地面對自我需要智慧、勇氣和胸懷。瞿秋白曾幻想:“我愿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著發展什么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但世界是現實的,人是活著的,時間不會給你在夢里繼續做夢的機會,瞿秋白在現實與理想的生活之間痛苦掙扎,卻毫無結果。
與此同時,他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明快清新的文筆,最早報道了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情況,也是第一個將《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為成長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留下了許多珍品,豐富了我國現代文學的寶庫。
這個善良果敢的才子,在浩淼的煙波深處,將自己適時掩埋,像一刃溫柔的刀鋒,在劃向黑暗的同時,翻越了黑暗,最后化作了一朵孤云,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
目次
唉!還不如……002
心的聲音003
“矛盾”的繼續017
青年的九月027
美國的真正悲劇035
王道詩話042
苦悶的答復045
曲的解放048
迎頭經051
出賣靈魂的秘訣054
最藝術的國家056
關于女人059
真假董吉訶德061
內外064 自殺001
唉!還不如……002
心的聲音003
“矛盾”的繼續017
青年的九月027
美國的真正悲劇035
王道詩話042
苦悶的答復045
曲的解放048
迎頭經051
出賣靈魂的秘訣054
最藝術的國家056
關于女人059
真假董吉訶德061
內外064
透底066
人才易得068
“兒時”071
中國文與中國人073
關于高爾基的書——讀鄒韜奮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075
079“非政治化的”高爾基——讀《革命文豪高爾基》二
083擇吉
085“美”
089寫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092致胡適
094致郭沫若
096大眾文藝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
100“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110《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137致楊之華
139勞動底福音(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141江北人拆姘頭
146英雄巧計獻上海
150致魯迅、馮雪峰
152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155鸚哥兒
158多余的話
158何必說?(代序)
159“歷史的誤會”
164脆弱的二元人物
167我和馬克思主義
172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176“文人”
182告別
187一種云
世紀末的悲哀189
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192
那個城273
畫狗罷275
書摘/試閱
自殺
青年呵!你要自殺么?你如其沒有覺著“自殺”的必要,你決不會自殺;要是你已經覺著“自殺”的必要,你為什么還不自殺?自殺!自殺!趕快自殺!你真正有自殺的決心,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殺自己的地步,不要叫社會殺你,不要叫你殺了社會,不要叫社會自殺。你不能不自殺,你應該自殺,你應該天天自殺,時時刻刻自殺。你要在舊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里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里放出萬丈光焰,你這一念“自殺”,只是一線曙光,還待你漸漸的,好好的去發揚他。你既愿意犧牲一切,殺身絕命;你應該更愿意時時刻刻去犧牲,時時刻刻去自殺。你隨時隨地的困難給你苦痛受,你因此覺得不得不自殺;從今以后,你就要隨時隨地感受著自殺的樂趣——仍舊是隨時隨地困難的苦痛。這要有何等的決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快樂!自殺神是自殺神!
唉!還不如……
凄凄的月色,冷冷的秋風,一間水閣憑著細細的河聲——滍滍的好象要浮到汨羅江里去——紙窗上微微的白色,襯著黯沉沉的燈光,慘淡淡的人影;岸邊的衰柳蕭蕭瑟瑟的,花臺下的落葉槭槭楂楂的,又象是低低的私語,又象是遠遠的哭聲,半明不滅的月光,倒象是東方剛剛發白,樹頭小鳥啁啁啾瞅——母鳥飛出去了,這時候似乎剛驚醒了我的噩夢。唉!還是夜色沉沉的,何嘗天亮呢?一年,兩年,三年,足足三年了,經過了多少艱難,痛苦,謬誤,墮落,如今呢,又是何等的沉寂,恐怖,凄涼,悲慘;還不如……還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雙目一瞑,也落得“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天亮了。推開了水閣門,正遇著一個熟識的鄉下人——撐船的——劃著船過去。——“喂!我們多時不見了,我今雇你的船往鎮江去,好么?”——“對不起。我今天要趕下鄉收瓜呢,今年年成倒還好。”劃了一槳又一槳,遠遠的過去了,剩著一蕩一蕩的水浪。站了半天,紅霞掩映著水色天光中的殘月。唉!還不如……這是我幾年前想……時的感想。
心的聲音
緒言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香象渡河,佛教用語,比喻心靈的深澈。,毫無跡象可尋;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鳥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風,更何處來的聲音?靜悄悄地聽一聽:隱隱約約,微微細細,一絲一息的聲音都是外界的,何嘗有什么“心的聲音”,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間久久暫暫的聲音都是外界的,又何嘗有什么“心的聲音”;千里萬里,一寸尺間遠遠近近的聲音,也都是外界的,更何嘗有什么“心的聲音”。鉤辀格磔,殷殷洪洪啾啾唧唧,呼號刁翟,這都聽得狠清清楚楚么,卻是怎樣聽見的呢?一絲一息的響動,澎湃訇磕的震動,鳥獸和人底聲音,風雨江海底聲音幾千萬年來永永不斷,爆竹和發槍底聲音一剎那間已經過去,這都聽得清清楚楚么,都是怎樣聽見的?短衫袋時表的聲音,枕上耳鼓里脈搏的聲音,大西洋海嘯的聲音,太陽系外隕石的聲音,這都聽得清清楚楚么,卻是怎樣聽見的呢?聽見的聲音果真有沒有差誤,我不知道,單要讓他去響者自響讓我來聽者自聽,我已經是不能做到,我靜悄悄地聽著,我安安靜靜地等著;響!心里響呢,心外響呢?心里響的——不是!心里沒有響。心外響的——不是!要是心外響的,又怎樣能聽見他呢?我心上想著,我的心響著。
我聽見的聲音不少了!我聽不了許多鳳簫細細,吳語喁喁底聲音。我聽不了許多管、弦、絲、竹、披霞那披霞那,英語piano的音譯,鋼琴。、繁華令繁華令,英語violin的音譯,小提琴。底聲音。我聽不了許多呼盧喝雉,清脆的骰聲,嘈雜的牌聲。我聽不了許多炮聲,炸彈聲,地雷聲,水雷聲,軍鼓,軍號,指揮刀,鐵鎖鏈底聲。我更聽不了許多高呼愛國底殺敵聲。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亞洲初聽見歐洲一個妖怪的聲音。他這聲音我聽見已遲了。——真聽見了么?可是還正在發揚呢。再聽聽呢,以后的聲音可多著哪!歐洲,美洲,亞洲,北京,上海,紐約,巴黎,倫敦,東京……不用說了。可是,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究竟還是心上底回音呢?還是心的聲音呢?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庚申正月十五夜),靜悄悄地帳子垂下了;月影上窗了,十二點過了,壁上底鐘滴嗒滴嗒,床頭底表悉殺悉殺,夢里聽得枕上隱隱約約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脈搏聲,靜沉沉,靜沉沉,世界寂滅了么?猛聽得硼的一聲爆竹,接二連三響了一陣。鄰家呼酒了:
“春蘭!你又睡著了么?”
“是,著,我沒有。”
“胡說!我聽著呢。剛才還在里間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還要抵賴!快到廚房里去把酒再溫一溫好。”
我心上想道:“打鼾聲么?我剛才夢里也許有的。他許要來罵我了。”一會兒又聽著東邊遠遠地提高著嗓子嚷:“洋……面……餑餑”,接著又有一陣鞭爆聲;聽著自遠而近的三弦聲凄涼的音調,冷澀悲亢的聲韻漸漸的近了……嗚嗚的汽車聲飆然地過去了……還聽得“洋……面……餑餑”叫著,已經漸遠了,不大聽得清楚了,三弦聲更近了,墻壁外的腳步聲,竹杖聲清清楚楚,一步一敲,三弦忽然停住了。——呼呼一陣風聲,月影兒動了兩動,窗簾和帳子搖蕩了一會兒……好冷呵!靜悄悄地再聽一聽,寂然一絲聲息都沒有了,世界寂滅了么?
月影兒冷笑:“哼,世界寂滅了!大地上正奏著好音樂,你自己不去聽!那洪大的聲音,全宇宙都彌漫了,金星人、火星人、地球人都快被他驚醒那千百萬年的迷夢了!地球東半個,亞洲的共和國里難道聽不見?現在他的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已經公布了八十幾種的音樂譜,樂歌,使他國里的人民仔細去聽一聽,你也可以隨喜隨喜,去聽聽罷。”我不懂他所說的聲音。我只知道我所說的聲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響。心響,心上想:“這一切聲音,這一切……都也許是心外心里的聲音,心上的回音,心底的聲音,卻的確都是‘心的聲音’。你靜悄悄地去聽,你以后細細地去聽。心在那?心呢?……在這里。”
一九二〇,三,六。
一錯誤
暗沉沉的屋子,靜悄悄的鐘聲,揭開帳子,窗紙上已經透著魚肚色的曙光。看著窗前的桌子,半面黑魆魆,半面黯沉沉的。窗上更亮了。睡在床上,斜著看那桌面又平又滑,映著亮光,顯得是一絲一毫的凹凸都沒有。果真是平的。果真是平的么?一絲一毫的凹凸都沒有么?也許桌面上,有一邊高出幾毫幾忽,有一邊低下幾忽幾秒,微生蟲看著,真是帕米爾高原和太平洋低岸。也許桌面上,有一絲絲凹紋,有一絲絲凸痕,顯微鏡照著,好象是高山大川,峰巒溪澗。我起身走近桌子摸一摸,沒有什么,好好的平滑桌面。這是張方桌子。方的么?我看著明明是斜方塊的。站在洗臉架子旁邊,又看看桌子,呀,怎么桌子只有兩條腿呢?天色已經大亮,黯沉沉的桌子現在已經是黃澄澄的了。太陽光斜著射進窗子里來,桌面上又忽然有一角亮的,其余呢——黯的,原來如此!他會變的。……唉,都錯了!……
洗完臉,收拾收拾屋子,桌子,椅子,筆墨書都擺得整整齊齊。遠遠的看著樹杪上紅映著可愛的太陽兒,小鳥啁啾唱著新鮮曲調,滿屋子的光明,半院子的清氣。這是現在。猛抬頭瞧著一張照片,照片上:一角花籬,幾盆菊花,花后站著,坐著三個人。我認識他們,有一個就是我!回頭看一看,鏡子里的我,笑著看著我。這是我么?照片上三個影子引著我的心靈回復到五六年前去。——菊花的清香,映著滿地瑣瑣碎碎的影子,橫斜著半明不滅的星河,照耀著干干凈凈的月亮。花籬下坐著三個人,地上縱橫著不大不小的影子,時時微動,喁喁的低語,微微的嘆息,和著秋蟲啾啾唧唧,草尖上也沾著露珠兒,亮晶晶的,一些些拂著他們的衣裳。黯沉沉的樹蔭里颼颼的響,地上參差的樹影密密私語。一陣陣涼風吹著,忽聽得遠遠的笛聲奏著《梅花三弄》,一個人從籬邊站起來,雙手插插腰,和那兩個人說道:“今天月亮真好。”……這就是我。這是在六年以前,這是過去。那又平又滑的桌面上放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請秋白明天同到三貝子花園三貝子花園,即今北京動物園。去。呵!明天到三貝子花園去的,不也是我么?這個我還在未來;如何又有六年,如何又有一夜現在,過去未來又怎樣計算的呢?這果真是現在,那果真是過去和未來么?那時,這時,果真都是我么?……唉!都錯了!……
我記得,四年前,住在一間水閣里,天天開窗,就看著那清澄澄的小河,聽著那咿咿啞啞船上小孩子談談說說的聲音。遠遠的,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江陰的山,有時青隱隱的,有時黑沉沉的,有時模模糊糊的,有時朦朦朧朧的,有時有,有時沒有。那天晚上,憑著水閣的窗沿,看看天上水里的月亮。對岸一星兩星的燈光,月亮兒照著,似乎有幾個小孩子牽著手走來走去,口里唱著山歌呢。忽然聽著一個小孩子說道:
“二哥哥,你們看水里一個太陽,太……”又一個道:
“不是,是月亮,在天上呢,不在水里。”轉身又向著那一個小孩子說道:
“大哥哥,怎么今天月亮兒不圓呢?昨天不是圓的么?”聽著回答道:
“怎么能天天都是圓的呢?過兩天還要沒有月亮呢?”
“大哥騙我,月亮不是天生圓的么?不是天天有的么?”
“我們去問姊姊。姊姊,姊姊。我剛才和阿二說,月亮會沒有的,他不信,他說我說錯了。”
姊姊說道:“媽媽的衣服還沒有縫好呢,你們又來和我吵,管他錯不錯呢……”
一九二〇,三,二十。
二戰爭與和平
小花廳里碧紗窗靜悄悄的,微微度出低低的歌聲。院子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的桃花,綠蔭沉沉兩株楊柳,微風蕩漾著。一個玲瓏剔透六七歲的小孩子坐在花廳窗口,口里低低的唱著:
姊姊妹妹攜手去踏青。
垂垂楊柳,嚦嚦鶯聲,
春風拂衣襟,春已深。
郊前芳草地,正好放風箏……
桌子上放著一個泥人,是一個漁婆,手里提著一只魚籃,背上擱著很長很長一竿釣魚竿,絲線做的釣絲,笑嘻嘻的臉。小孩子一面唱一面用手撫著那釣絲,把許多桃花片,一片一片往釣絲上穿,又抓些榆錢放在那魚籃里。又一個小孩子走來了。說道:“哥哥,我找你半天了,爸爸給我一個皮球。”那哥哥道:“我不愛皮球。弟弟,你來瞧,漁婆請客了,你瞧他體面不體面?籃子里還裝著許多菜呢。”弟弟瞧一瞧說道:“真好玩,我們兩個人來玩罷。”說著,轉身回去拿來許許多多紙盒、畫片、小玻璃缸,兩只小手都握不了。一忽兒又拿些洋囝囝、小泥人來了。兩個小孩子擺擺弄弄都已擺齊了,喜歡得了不得,握握手對著面笑起來。弟弟一舉手碰歪了一只小泥牛,哥哥連忙擺好了說道。“都已齊了,我們請姊姊來看,好不好呢?”弟弟說:“我去請。”說著興頭頭的三腳兩步跑進去了。一忽兒又跑出來氣喘喘的說道:“姊姊不來,他在那兒給漁婆做衣服呢。”
哥哥道:“他不來么?”說著,又把一張畫片放在漁婆面前說道:“弟弟,你瞧,漁婆又笑了。”弟兄兩個人拍著手大笑。一忽兒,哥哥弟弟都從椅子上下來,一面踏步走,一面同聲唱著,嚷著很高的喉嚨,滿花廳的走來走去,只聽得唱道:
……戰袍滴滴胡兒血。
自問生平……頭顱一擲輕。
一面唱一面走出花廳,繞著院子里兩株楊柳,跑了兩三匝。哥哥忽然說道:“漁婆要哭了,進去罷。”弟兄兩個又走進花廳,兩個人都跑得喘吁吁的。哥哥在桌子上一翻,看見一張畫片,詫異道:“誰給你的?我昨天怎么沒有看見他?”弟弟道:“爸爸昨天晚上給我的。”哥哥道:“送給我罷。”弟弟道:“不,為什么呢?爸爸給我的。”弟弟說著,把那張畫片搶著就跑。哥哥生氣道:“這些我都不要了,……”說著,兩只小手往桌子上亂撲亂打了一陣。漁婆、小泥人、玻璃缸打得個稀爛。弟弟聽著打的聲音又跑回來,看一看,哭道:“你把我洋囝囝底頭打歪了,我告訴爸爸去!”說著往里就跑,哥哥追上去,弟兄倆扭做一堆連扭帶推,跑道院子,往里面上房里去了。
只聽花廳背后,弟弟嚷著的聲音:“姊姊!姊姊!哥哥打我……”
院子里綠蔭底下,落花鋪著的地上,卻掉著一張畫片——原來是法國福煦元帥福煦元帥,法國軍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法軍參謀總長及協約國軍總司令。底彩色畫像,帶著軍帽穿著軍衣的……
一九二〇,三,二十八。
三愛
“愛”不是上帝,是上帝心識底一部現象。
——托爾斯泰
“唔唔……媽呢?……”
“好孩子。媽在城外趕著張大人家喪事,討些剩飯剩菜我們吃呢。閉著眼靜靜兒罷。陸毛腿去弄藥草怎么到現在還不來呢?孩子,你餓嗎?難受得厲害嗎?吃什么不要?”
0
0
“我……唔唔……我……我我……不……我不……”
模模糊糊的呻吟聲,發著,斷斷續續的……輕微聲浪隱隱的震著,沉靜的空氣里蕩漾著……唉!
嫩芽婀娜的幾株垂楊底下,一家車門旁邊,臺階上躺著十二三歲的孩子,仰面躺著,那如血的斜陽黯沉沉的映著他姜黃色的臉,只見他鼻孔一扇一扇,透不出氣似的,時時呻吟著。旁邊跪著一個老頭兒,滿臉沙塵,亂茅茅的胡須,蓬蓬松松的頭發,蒼白色的臉,遠看著也分不出口鼻眼睛,只見烏黑陣陣的一團。他跪在地上,一手拿著許多柳枝替小孩子墊頭,一手撫著小孩子底胸,不住的嘆氣,有時翻著自己襤褸不堪的短衫搔搔癢。他不住的嘆氣,不住的嘆氣!心坎里一陣酸一陣苦。他時時望著西頭自言自語:“來了嗎?沒有!不是;好孩子!”……“你媽……”
我在街上走著,走著,柳梢的新月上來了……呼呼一陣狂風。呼……呼……滿目的沙塵。唉!風太大了!……
一個“冥影”飚然一扇,印在我心坎里,身上發顫,心靈震動……震動了。他們……他們那可怕的影子,我不敢看。
“老爺,爺爺!多福多壽的爺爺,賞我們……賞……”
那老頭兒在地上碰著頭直響,臉上底泥沙更多了。小孩子翻一翻眼,唉!可怕!他眼光青沉沉的,……死……死人似的!可怕!
“老爺,我這小孩子病了。怎好?賞幾個錢……”
老頭兒又碰著頭,我走過他們,過去了,又回頭看看,呀!……給他們兩個銅元……兩個銅元?
老頭兒揀著,磕頭道謝;又回身撫著小孩子,塞一個銅元在他手里,又道:“媽來了,來了。”小孩睜一睜眼……我又回頭一看,趕快往前就走。我心里,心里跳。怪,鬼,魔鬼!心里微微的顫著,唉!
……
我事情完了,要回家去。叫洋車。坐上車,一個小孩子跟著車夫。車夫給他一個銅元道:“家去跟著媽罷!”
“爸爸回來吃晚飯?我們等著爸爸……等著您!”
東長安街兩邊的楊柳、榆樹,月亮兒瑩潔沉靜,沉靜的天空。呀!不早了!十點半。車夫拖著車如飛的往前走去。似乎聽得:“媽!……好吃……嘻嘻嘻……”
月亮兒瑩潔沉靜,沉靜的天空!
“愛!”……宇宙建筑在你上。
四勞動?
青隱隱的遠山,一片碧綠的秧田草地,點綴著菜花野花,一灣小溪潺潺流著;蔭沉沉的樹林背后,露出一兩枝梨花,花下有幾間茅屋。風吹著白云,慢慢的一朵朵云影展開,縐得似魚鱗般的浪紋里映著五色錦似的,云呵,水呵,微微的笑著;遠山巔隱隱的烏影閃著,點點頭似乎會意了。啁啁啾啾的小鳥,呢呢喃喃的燕子織梭似的飛來飛去。青澄澄的天,綠茫茫的地,蔭沉沉的樹蔭,靜悄悄的流水,好壯美的宇宙呵,好似一只琉璃盒子。
那琉璃盒,琉璃盒里有些什么?卻點綴著三三兩兩的農夫弓著背曲著腰在田里做活。小溪旁邊,田隴西頭,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穿著一條紅布褲子,一件花布衫,左手臂上補著一大塊白布,蓬著頭,兩條小辮子斜拖著,一只手里拿著一件破衣服,汗漬斑駁的,一只手里提著籃,籃里放著碗筷,慢慢的向著一條板橋走去,口里喃喃的說道:“爸爸今日又把一些菜都吃了,媽又要抱怨呢。”他走到橋上,剛剛兩只燕子掠水飛過,燕子嘴邊掉下幾小塊泥,水面上頓時蕩著三四匝圓圈兒。他看著有趣,站住了,回頭看一看,他父親又叫他快回家。他走過橋去,一忽兒又轉身回來,走向橋塢下,自言自語道:“媽就得到這兒來洗這件衣服,放在這兒罷。”一面說,一面把那件衣服放在橋下石磴上,起身提著籃回去了。
夕陽漸漸的下去了,那小孩子底父親肩著鋤頭回家了,走過橋邊洗洗腳,草鞋脫下來提在手里,走回家去。遠山外還是一片晚霞燦爛,映著他的臉,愈顯得紫澄澄的。他走到家里。“剛換下來的衣服洗了沒有?”一個女人答道:“洗好了。四月里天氣,不信有這么熱!一件襯里布衫通通濕透了。”——接著又道:“張家大哥回來了,還在城里帶著兩包紗來給我,說是一角洋錢紡兩支。”那父親道:“那不好嗎,又多幾文進項。”
那父親又道:“我吃過飯到張家去看看他。”小孩子忙著說道:“我跟著爸爸同去,張家姊姊叫我去幫他推磨呢。”父親道:“好罷,我們就吃飯罷。”大家吃過飯,那女人點著燈去紡紗了,爺兒兩個同著過了橋,到對村張家來。
聽著狗汪汪的叫了兩聲,一間茅屋里走出一個人來說道:“好呀!李大哥來了,我上午還在你家里看你們娘子呢,我剛從城里回來就去看你,誰知道已經上了忙了,飯都沒有工夫回家吃,我去沒有碰著你,你倒來了。”接著三個走進屋子,屋子里點著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擺著幾張竹椅子,土壁上掛一張破鍾馗,底下就擺一張三腳桌子;桌子旁邊坐著一位老婆婆,手里拈著念佛珠,看見李大哥進來忙著叫他孫女翠兒倒茶。一忽兒翠兒同著李家的小孩子到別間屋子里去了,李大就在靠門一張矮竹椅上坐下,說道:“謝謝你,張大哥,給我帶幾支紗回來。”那老婆婆說道:“原來你們娘子也紡‘廠紗’嗎?那才好呢。多少錢紡一支?”張大道:“半角洋錢。”老婆婆說道:“怪不得他們都要紡紗紡線的。在家里紡著不打緊,隔壁的龐家媳婦不是到上海什么工廠紗廠里去了么?山迢水遠的,阿彌陀佛,放著自己兒女在家里不管,赤手赤腳的東摸摸西摸摸,有什么好處!穿吃還不夠,鍍金戒指卻打著一個,后來不知怎么又當了,當票還在我這兒替他收著呢。阿彌陀佛!”
李大問張大道:“龐大現在怎么樣了?”老婆婆搶著說道:“他么?闊得很呢!哼!從城里一回來,就搖搖擺擺的,新洋布短褂,新竹布長衫,好做老爺了。一忽兒鋤頭碰痛了他的手,一忽兒牛鼻子擦臟了他的褲子,什么都不是了;見著叫都不叫一聲,眼眶子里還有人嗎?我看著他吃奶長大了的,這忽兒乾媽也不用叫一聲了,當了什么工頭,還是什么婆頭呢?阿彌陀佛!算了罷!”
張大道:“媽那兒知道呢?他只好在我們鄉下人面前擺擺闊,見他的鬼呢!我親眼看見他在工廠門口吃外國火腿吃外國火腿,指被外國人踢。呢,屁股上挨著兩腳,那外國人還嘰嘰咕咕罵個不住,他只板著一張黑黝黝的臉,瞪著眼,只得罷了,還說什么‘也是’‘也是’。他們那些工廠里的人是人嗎?進了工廠出來,一個個烏嘴白眼的,滿身是煤灰,到鄉下來卻又吵什么干凈不干凈了,我看真象是‘鬼裝人相’,洋車夫還不如。”
老婆婆道:“又來了,拉洋車就好嗎?你還不心死?拉洋車和做小工的,阿彌陀佛,有什么好處!有一頓沒一頓的。你還想改行拉車么?我說你還是不用到城里罷,水也不用挑了。快到頭忙了,自己沒有田,幫著人家做做忙工,在家里守著安安穩穩的不好嗎?”李大道:“嬸嬸說得對。現在人工短得很,所以忙工的錢也貴了,比在城里挑水也差不了多少,還吃了人家的現成飯,比我自己種那一二畝田還劃算得來呢。”
張大道:“差卻不差,我明后天上城和陳家老爺說,我的挑水夫底執照請他替我去銷了罷,橫豎陳家老爺太太多慈悲,下次再去求他沒有不肯的。人家二文錢一擔水,他家給三文,現在漲了,人家給四文錢,他家總算七八文,不然我早已不夠吃了。”老婆婆嘆口氣道:“阿彌陀佛,那位老爺太太多子多孫多福多壽。”李大也說聲“阿彌陀佛”,說著站起來叫他小孩子道:“我們回去罷,小福,出來罷,請翠姐姐空著就到我們家里去玩。”小福答應著,同著翠兒出來。爺兒二個一同告別要走,翠兒還在后面叫著小福道:“不要忘了,福弟弟,我們明天同去看燕子呀。”說著,祖孫三個都進屋子里去。
月亮兒上來了,樹影橫斜,零零落落散得滿地的梨花,狗汪汪的叫著……
五遠!
遠!
遠!遠遠的……
……
青隱隱的西山,初醒;
紅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長街外,
漠漠無垠,晚霧初凝。
更看,依稀如畫,
平鋪春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滾開去!哼!”
警察底指揮刀鏈條聲,
和著呻吟……——“老爺”
“賞……我冷……”……呻吟……
——“站開,督辦底汽車來了,哼!”
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臉上,也是一幅春錦。
掠地長風,一陣,
汽車來了。——“站開……。”
白煙滾滾,臭氣熏人。
看著!長街盡頭,長街盡……
隱隱沉沉一團黑影。……
晚霞擁著,微笑的月影。
……
遠!遠遠的……
“矛盾”的繼續
他夢也似地走下陰暗的扶梯,他哭了!
同事們看到紅著眼睛的他走進辦公室,都笑笑。
他聽著墻頭上的鐘敲了八點,他想那豬也似的人,又要來了。
果然,那人來了,搖搖擺擺的踱進來,他似乎首先向燕樵看了一眼。“首先”看我!那眼光是多么難堪,好象是……——還是不要比方罷!管他呢!橫豎我再拿你一個月的三十六元大洋,是中國大洋,還不是美金哩。最后的一次,最后的一次!
燕樵心上這樣一想,覺得平安了許多;那買辦昨天講的話,又記起來了。哼!他想禁止我們的集會結社的自由……我還是寫一封辭職信,去……到什么地方去呢,那里去找事做,找飯吃呢?——大概總有法子罷。
燕樵發了這樣大的“雄心”之后,身上都覺松快,陡然間從奴隸變成人,從洋奴變成了高等華人,偷偷地伸了一個懶腰,隨手拿起幾件簿記和公事,開始他每天照例的工作。他身上覺得有些熱,抬頭看看窗子外邊:狂風暴雨,象昨天那樣的,雖然是沒有了,可是,天色卻是陰沉得更加可怕,想來街上一定還是冷得很呢,也許還在下雪珠——那對過的屋頂上,似乎是點點滴滴的雪珠在那里跳罷。可是,身上的確是覺得燥熱。他只是想:為什么天天總是這樣?于是他想起家里那個陰暗的扶梯,那間冷凄凄的屋子——朝西的統廂房,窗子縫里板壁縫里呼呼的風,尤其是那后板壁上面半段是空的,只用狹狹的木板搭成了斜方塊的柵欄,那多么“寒酸”,多么陰慘慘的,難怪同樣穿著這些衣服在家就只是覺著冷,燒著爐子亦是不中用的,熱氣還不是從那后板壁的上面半段空的地方跑到外面去,一直跑到弄堂里墻壁上畫著的烏龜身上去,何況今年煤炭這樣貴。天天一清早,——要八點鐘以前到行里去哩,——在熱被窩里真是懶洋洋的,不愿意起床,那房里的空氣是多么冷呵。只有到了行里,在燒著熱水汀的辦公室里,才漸漸覺得四肢舒泰起來。不過因為身上穿著中國衣服,反而會覺得燠熱。如果是穿西裝,那么,進來就脫掉大衣,多么舒服。看那豬也似的買辦,他倒會想法子,狐皮袍子里面,穿著綢夾衫,卸掉了皮袍,好不輕快。只有咱們窮小子倒霉:穿少了在家里中國屋子里面是太冷,穿多了跑到辦公室洋房里來又太熱。他這樣一面想著,一面辦著事,心上悶得厲害。看看已經是可以領薪水的時候了……
“賬房告訴我,下個月薪水加兩塊洋錢了。”他的一個同事笑嘻嘻對他說。
燕樵心上想:奇怪,為什么對我沒有說起呢,他不期而然地抬起眼來看了那買辦一眼,——買辦正在手不停揮的批著公事,那兩只細眼睛緊湊著象沒有縫似的,忽然也抬起頭來四周圍看了一看,仿佛他是已經聽見了有人在低低的說話,他咳了一聲嗽。燕樵馬上把頭低下,幸而眼光沒有和買辦大人的相接觸!
照理,我也應當加薪了,為什么賬房不通知我。要是家里的老婆知道了這個消息,不知道她要怎樣的失望;已經在好幾個月之前,她就劃算著這兩塊錢的用度哩。難道是因為我開了一次會。難道中國地方中國人,反而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反而是外國老板來決定我們的命運了!豈有此理!
當天晚上,從升降機里面走出來,他的同事約他去吃小館子,并且說,他是請一個在市黨部辦事的王先生吃飯。他心上正在氣惱不過,就謝絕了,不去做“光榮的”陪客。可是,他想他的同事是比他“活動”多了,居然請王先生吃飯。乘電車回到家里,在弄口又看見那墻壁上畫著的烏龜——“中國人就只會畫烏龜!”他還只在樓梯上,就聽見他老婆“歡迎”他的聲音:“你回來了,《前鋒月刊》你替我買了沒有?今天不是領著薪水回來了嗎?”
“什么也沒有買!你還是拿兩角錢去買一點炭來生爐子罷。”
“又沒有買!生爐子!天天生爐子,這點錢怎么夠用?成天的服侍,替你當婆媽了。一本新小說都沒得看的,不要說電影了。做了人……高尚的娛樂總得有一些。你怎么呢?……”
“我?我沒有什么,只有一點頭暈……”燕樵說著,順手把那三十六塊薪水塞在他老婆手里。他的心里還在盤算著那封信——要寫給行里的辭職信。
夜飯是馬馬糊糊吃過了,筆,紙,墨水瓶是放在他的面前。信呢,還沒有開始寫。“民族主義的自尊心”要他反抗,反抗,再反抗。但是,那天晚上信是始終沒有寫。
他老婆又在說著那件旗袍是太穿不出去了……
“明天再寫,也不算晚。”
明天是很多的。“矛盾”沒有解決以前,只有請這一位“明天”先生來暫時安慰一下。
孫總理的演講集,是他常常讀的。現在,是更加要讀《民族主義》了。孫總理似乎是在教訓他“處世之方”,真正中國國貨的“處世之方”,中國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民族性。是的,孫總理講的故事也特別動人。香港有一個中國的苦力,靠著一根竹杠挑擔過活的,他積聚了幾個錢買了一張發財票,就放在竹杠的里面。這位苦力是發財心切,把那發財票上的號碼讀得滾熟。那天發財票開彩了,他去一看:頭彩十萬元的號碼,正是他那一張發財票。這還了得!十萬元!從此不要當苦力了。他拿起那根竹杠,就往海里一扔。啊呀!怎么得了——那發財票還放在竹杠子里面呢。吃飯家伙的竹杠,怎么可以扔掉呢!不錯,吃飯家伙要緊。他自從看到了這個故事——這個“民族固有道德”的教訓之后,那外國老板和買辦的顏色,似乎也變得和善些,天氣似乎也好些,不這么悶人了。
時候過得很快,有一個月了。辭職信還是沒有寫。薪水卻的確沒有加。“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主義的自尊心”在他肚皮里面又打仗起來了。
還是他的老婆提醒了他:叫他去借兩本《前鋒月刊》《前鋒周報》來看,他想起了市黨部里面的葉先生和陳先生,——至于王先生那樣大人物,還沒有結識得上呢。常常和葉陳兩先生來往之后,他自己覺得大有進步了,首先是“活動”了些。有一天葉先生露了一句口風,使他心上細細的計畫了一番。從此之后,這個計畫時常想起……總在他的心上盤旋著。
“總理真是偉大!”他突然間象“悟了道”也似的想起來了,“那張發財票得先拿出來,去領到了十萬塊大洋的頭彩,仔仔細細的數清了鈔票,然后再扔掉那竹杠也不遲呵。”
……
醉醺醺的從一家廣東萊館“某某酒家”出來,客氣的朋友是早走了,只有葉先生同他兩個人了。葉先生在他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他連忙答應著:
“那自然,那自然!還得請諸位先生多多領導,多多指教呢。”
他一路回家,還把葉先生送到弄堂口,自己再坐黃包車回去。“這烏龜弄堂真是住不得……老婆那件旗袍的確是再也穿不出去了……那買辦還兇得到我頭上來嗎?三十六塊,四十塊,四十塊之外還有……還有不在四十塊之內的……”他的確有些醉了。
“快些,快些,多買些炭來生爐子,多買些,多買些!”
“今天已經不大冷了,又生什么爐子?”
“你,女人家懂得什么……么?你懂得民族主義嗎?你懂得總理的遺教嗎?”
“什么?你說什么?”
……
幾個人圍著一張圓桌,有兩個坐在沙發上,燕樵坐的是一張椅子;他們面前放著幾只酒杯。
“這次日本人算是好說話的。”
“出手也就不見得大,究竟日本小鬼吝嗇,會打小算盤,那次英美煙……”
“燕樵還是頭兩次辦事,這指導工會的事是很麻煩的,你得給他詳細說說以前的經過情形,不要東扯西拉的什么英美,什么南洋。”
“好,是了是了!”
明天過來,燕樵把一條鮮艷的領帶換了下來,穿著樸素的中山裝,到了一個日本紗廠門口。工人聚著的有好幾百。他走上去,挑選了兩位熟識的工頭,把他們拉到旁邊說了幾句話。然后,他站到一個大木樁上面,對工人演說了:
“工會方面已經替你們辦好了,你們明天就先上工,隨后,資方已經答應談判你們提出的條件。只是開除的那兩個工人,據黨部方面的調查,的確是紅匪,不能復工,你們不要上當。……”
工人之中有人吼著,他沒有聽清吼些什么。可是,一個巡捕已經捉了兩個工人帶著走,那邊又來著一隊印度馬巡,還有好幾個穿著黑布長衫,扎著腿的人踱來踱去,對著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他向他們點點頭。那時,工人已經散了一大半。他也不演講了,只對那熟識的兩個工頭說。
“大家都是中國人,你們得勸勸。做人要知足……”
他走了,他只覺得背后有幾只眼睛釘住了他的背。那些眼睛不知道比買辦的一雙豬眼怎么樣。神氣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些帶血的眼睛。
但是,工人是“安靜”下去了,罷工是終止了。燕樵的這種功績一天天的積聚起來,“工人運動大家”的尊號已經傳遍了他的新舊朋友的口碑。他身體都比以前強健得多,每天早晨總要喝一杯牛奶,吃過午飯總要在新的沙發躺椅上睡睡中覺。時常讀“民族主義的讀物”,研究中國的近百年史,談談提倡國貨,他尤其喜歡讀《清朝全史》,幾十年來中國喪失的領土和主權,據他說,都要從提倡國貨運動里面去取回來。那些“打倒帝國主義”的空口號是沒有什么用的,徒然帶著些紅匪的色彩。
前好幾天,他還給老婆做了兩件——兩件!——國貨的時裝旗袍,去參加國貨時裝的展覽會。
“只是老婆的身材總不大好,不如那幾位‘女同志’的曲線美來得那么肉感,這又仿佛太中國氣了,在這上頭似乎‘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缺欠些,多帶些西洋風味,也不妨事,”他想。他現在早已不是洋奴了,而是高等華人了,低級的趣味也漸漸的消失了,“高尚娛樂”更是每天不能少的了。反正“工作”是不大忙,比以前在洋行里差得多了。他也不必每天放了工急急的跑回去,每天總得“活動活動”,看看朋友——民族主義的朋友。那里,有時候可以碰見“女同志”。
的確,工會的“工作”說多是并不多——會費不用去收,廠方的寫字間會扣下送來;會員呢——那還不容易,工廠的花名冊拿來點點名,那還不都是會員嗎。說少可也不少,天天總得接洽接洽,活動活動。那些工人真是沒有教育,甚至于沒有人性——中國民族固有的道德,時常總要鬧些“小事”,他們太缺乏民族主義了,連提倡國貨的淺近道理都不懂得,還是幾位工頭,“包”字號的弟兄們有見識,能干!
“絲廠罷工了,一萬多人呢。昨天你沒有來,她們一班小姑娘真了不得!警察捉了兩個煽動罷工的人,她們就哄哄的聚了好幾千人來搶,還動手打呢。結果,那兩個女工被她們搶回去了,幸而巡捕房和中國警察幫忙,才又捉住了。今天還有幾十家絲廠沒有上工……她們要求恢復原有工資。”
“這還了得!”燕樵跺跺腳說,“快派一批人出去勸她們上工,這里面一定有紅匪搗亂,你到‘那邊’去招呼一聲,請‘他們,多多幫忙,我自己也就去。”
亂哄哄的只見人頭,許多女工在那里談論,看見“工會方面”的人走來,她們就不做聲了。跟著,巡警來了好幾隊。燕樵看見“工會方面”勸工人復工的好幾個人,有被打的。他很生氣。可是,等到他走近工人的時候,情形已經不同了——她們安靜了許多。草場上的綠色已經告訴大家春天來了,楊柳枝邊亮晶晶的刺刀照耀著溫柔和暖的太陽光,也告訴大家“工會方面”的大人物來了。大家安靜了許多。
“工友們,條件是好商量的,大家先上工。要知道絲業是中國的重要產業,絲業不振興,中國不能和外國……外國……就是帝國主義競爭。要國家有自由,個人就要犧牲自由。工友們要能夠犧牲自由,提倡國貨。中國絲廠很可憐的,生意不好,要勞資合作才好。減低工資是愛國的國民政府批準了的。大家都是國民……國民……”他咳了幾聲嗽,“國民,女的也是國民,國民都要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現在公布了工廠法,每人只要做十點鐘的工作,女工生育的時候,還有休息……”
工人是沉默了好久,她們的頭是仰著的,眼光是直直的——那眼光是表現著愚蠢,怨毒,一點兒民族主義也不慌!說這樣動聽的話,她們也沒有一點感動,真是禽獸!她們那種笨眼睛,不是表現她們是禽獸嗎?!她們表面上仿佛是靜靜的聽講,不知道她們肚皮里面轉著什么鬼念頭。燕樵一面講著,一面這樣想。他似乎聽見人堆里有人嘰哩咕嚕的說:
“十點鐘工作!我們現在做的還不止十二點鐘呢!”
“希罕你們的‘十點鐘’,中國現在有地方只做八點鐘了。”
“那地方就沒你們這種‘工會’,那里是我們的工會。”
“生小孩子有休息!工資呢??”
這話都說得很低,不大聽得見,燕樵還是講他自己的:
“你們先上工,不要聽紅匪的煽動。”
“沒有飯吃呢?!”人堆里忽然大聲的說了這句話,那聲音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大。他本能的——民族主義的本能的,回過眼光去看了一看幾個穿著灰布長袍的“人物”和那亮晶晶的刺刀。
“不要聽紅匪的煽動,”他特別著重的重復了這—句句話,是怕自己的思路被人堆里的聲音打斷了,“沒有什么蘇維矮,蘇維高,沒有什么工農兵會議,沒有什么共產主義,他們只是些殺人放火的土匪。你們不要受利用,快快上工。國民政府現在就要肅清這些紅匪了,國民會議快要開會了。你們快快上工。國民會議上,全體工人的要求都要討論的。”
“有人說國民會議是地主資本家的會議?……”人堆里又來這么一個“問題”。
“那是他們造謠,殺人放火的紅匪造謠!”他很輕巧的回答了這么一句,眼光又向“那邊”轉了一轉。
“造謠!你呢?”突然間人堆里居然敢于發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居然!
“混蛋!!你問的什么?!什么!什么!……”
……
他一路回家來,春天的夕陽更加使他陶醉了。他看著黃包車夫向他哀求添些車錢的神氣,真是又好笑又好氣。這班人真是沒有腦筋的:黃包車夫因為外國人多給幾個銅板,就寧可去拍外國人的馬屁,工人為著多要幾個工錢,就寧可破壞中國的民族工業。中國有這幾百萬幾萬萬甘心做洋奴的人,那得不亡國!要人人都要象我這樣有志氣才好……那班不要臉的女工居然說我造謠,豈有此理,洋奴,洋奴!想想真要生氣,我亦寧可……他搖搖擺擺的摸進了家門。
“怎么?這樣晚又是喝醉了回來?”
他不做聲。過了不久,他的鼾聲已經呼呼的透出那靜悄悄的屋子。屋子里是綠沉沉的——桌子上一盞雅致的綠枱燈,旁邊還煮著蓮子,澌澌的沸水聲和他的鼾聲相應。桌子上那綠色枱燈的圓圈之下,一本《清朝全史》展開著,露出一行字;“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他老婆忽然聽著他哼,他磨著牙齒,他說:
“你你你你你你你呢?!”(NIII11NE?!)
一九三一,四,四。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