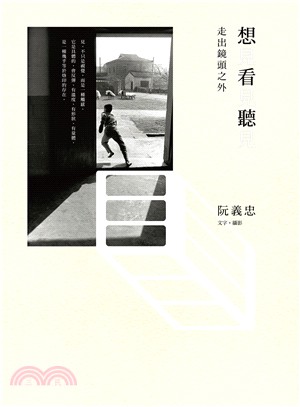商品簡介
見,不只是視覺,而是一種觸感。
它是具體的,會反彈、有溫度、有形狀、有量體,
是一種幾乎等於烙印的存在。
★當代華人攝影大師阮義忠,十一萬字隨筆,三十年生涯回顧
★隨書收錄阮義忠、方大曾、呂楠等著名攝影家代表作品
他所看到的世界,充滿線條、比例、秩序、構圖,
他總有辦法抓住稍縱即逝的一線靈光……
這一次,他以筆代替觀景窗,寫下人生種種見,與不見。
影響兩岸三地華人攝影深遠、當代攝影大師阮義忠生涯首部攝影散文集,橫跨三十年的書寫,以真摯雋永之筆,回顧攝影藝術生命中所有的「想見,看見,聽見」。
輯一「想見」,懷念故鄉風土、童年往事、異族民情,歷數自己從一個宜蘭鄉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攝影之路的偶然與必然,濃縮臺灣社會變遷與不同人群的生活景象;輯二「看見」,介紹方大曾、莊靈、呂楠等攝影家及其作品,以他始終行於時代之先的藝術眼光和文化敏感,捕捉這些曾並不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天才之靈光;輯三「聽見」,是非典型的書評與樂評,藉由書籍與音樂,追溯自己與創作者的緣分,從詩人搖滾歌手李歐納•柯恩,到瑞士攝影大師羅伯‧法蘭克,書寫獨一無二的私人藝術史。
本書同時收錄幅阮義忠攝影作品及方大曾、呂楠等著名攝影家之代表作,從中一窺攝影大師鏡頭之外的故事,以及他的完整生命之旅。
「中國大陸關注『世界攝影』,或我稱之為『嚴肅攝影』的人士,若其年齡正在四十歲上下,那麼,阮義忠的名字想必在他們心中無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攝影之於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我甚至聽說,好幾位大陸攝影家把『攝影教父』這樣的尊稱給予阮義忠。」
——陳丹青(藝術家)
「在阮義忠先生的鏡頭裡,臺灣的鄉親們似乎並不在乎或者顧慮他的鏡頭存在。他們只是在生活,在生活中,而阮義忠先生可能於他們來說,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對攝影中的阮先生並不起外心,有生分、見外之感。阮義忠先生雖然拍攝下了他們的日常,但那也是阮先生的日常。這樣的日常教我們振作,教我們知道感動是什麼,也讓我們驚醒麻木的醜陋。」
——顧錚(攝影家)
「做為一個攝影家,阮義忠在他三十年的攝影歷程中,逐漸在臺灣地域文化和歷史情境中找到了其攝影觀看的立足點,『凝視臺灣即將逝去的人文價值』,見證臺灣的政治變化、農業生活轉變到工業生活的迷茫、都市化給人們帶來的錯亂、根文化和本土文化受到的衝擊等等。在他的攝影中,我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臺灣『鄉土情結』或『鄉土意識』。」
——王璜生(藝術家)
「阮義忠的可貴處,在於他那動人的誠實。」
——陳映真(作家)
作者簡介
一九五○年出生於台灣宜蘭。早期曾任《幼獅文藝》編輯,退伍後任職《漢聲》雜誌英文版,開始攝影生涯。一九七五年轉任《家庭月刊》攝影,同時撰寫本土攝影報導文章。一九八一年,由攝影跨行到電視節目製作,以紀錄片《映象之旅》等廣為人知。一九八八年起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長達二十五年。
三十多年來,阮義忠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
著作豐富,出版《正方形的鄉愁》《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等十餘本攝影集。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被視為海峽兩岸的攝影教育啟蒙書;所創辦的《攝影家》雜誌(1992-2004)被譽為攝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阮義忠攝影作品為海內外重要機構展出及收藏。多年來深刻且廣泛影響全球華人地區的攝影視野。
序
見或不見
從小我的作文成績就不好,長大了對寫文章也沒信心。倒是畫畫一直被誇獎,後來拍照也得了些掌聲。我對圖像掌握的能力遠勝過文字,這跟我的成長背景與環境有關。祖父是鎮上有名的細雕木作師傅,在我還不會走路,於木料刨花堆裡爬的時候,日日所見的就是神案上的龍鳳木雕、考究家具上的花卉禽鳥。長大些,堂兄弟們在玩捉迷藏、官兵捉強盜時,我最愛的卻是用磚頭、木炭在曬穀埕畫東畫西,讓大人十分頭痛。
上了學,有了筆,課本、作業簿的空白處都是我的塗鴉。爸爸媽媽一看就搖頭,認為我不好好唸書,只會鬼畫符。如果說,我的畫畫愛好曾受過什麼鼓勵的話,那就是每當家人生病久久不好,必須舉行去邪、路祭時,就會由我負責用冥紙為紮好的稻草人畫張臉。大人小孩都說:「阿釘仔畫得好像啊!」
我所看到的世界充滿線條、比例、秩序、構圖,卻找不到形容它們的詞句;沒想到這個毛病竟成為我日後的寫作風格。對我來說,大多數的表達方法似乎不太適用,總覺得那不是我所見到的,也不是我想傳達的重點。對於不同事物之間的關係我一向特別敏感,對同一件東西在不同時間的存在狀態我總是特別感興趣,但在意的焦點往往說得不夠清楚,讓別人覺得我敘述事情太跳躍;這是我的缺點。可是,我有辦法抓住稍縱即逝的一線靈光;當我把這個長處與攝影結合為圖文書時,竟引起我沒有料到的熱烈迴響。
這本書以文為重,圖反而為副,在某個方面來說,可說是我眾多出版物的的第一本散文集。會把書取名為《想見,看見,聽見》,是因為我特別注重「見」。我認為那不只是視覺,而是一種觸感。它是具體的,會反彈、有溫度、有形狀、有量體,是一種幾乎等於烙印的存在。若是「想」「看」「聽」而沒有「見」,就等於生命不曾與外在有過接觸。真正的「見」來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閱讀他人的經驗。我的文章若是有一點點特別,大概就是因為文字與生活共頻率;因此我將這本書的二十二篇文章分成這樣三卷。
書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寫於一八九五年,最近的一篇剛完稿。讓我感激的對象很多:《聯合報》副刊及《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幾乎每次收到稿子都會以我不敢妄想的慷慨篇幅刊登;九歌出版社好幾次把我的文章選入年度最佳散文選。大陸的《生活月刊》更是不但跟我邀稿,還將我拉入編輯顧問團,一有合適題材就催促我寫稿;近年來寫的一些稿子都是在這本令人尊敬的刊物首發。其他文章多半是當年開攝影展時趕出來的;事隔三十年重看,有點臉紅,幸好內人袁瑤瑤幫我精簡潤飾。
感恩大家!
目次
序:見或不見
卷一 想見
一 愛哭的童年
二 回家的方向
三 北埔十三巡
四 八尺門、攝影、我
五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六 臺北謠言——為城市造像的感慨
七 四季的故事
八 失落的鐵軌,失色的夢
九 抽屜裡的浪花
十 老伴
卷二 看見
十一 尋找方大曾
十二 會見吳印咸
十三 丈量永恆的尺度——呂楠
十四 謎語和真相——陳傳興
十五 期待上帝——馮君藍的〈微塵聖像〉
十六 君子莊靈‧靈視人間
十七 向自然習法——談張志輝的攝影專題〈胸無成竹〉
卷三 聽見
十八 重聽李歐納•柯恩
十九 徹底的異鄉人——羅伯•法蘭克
二十 黑暗報告,良知之光——唐•麥庫林
二十一 永遠的布列松
二十二 想念亞美尼亞
書摘/試閱
【內文節選一】(選自卷一「想見」)
一 愛哭的童年
很少回憶兒時的情景,因為我的童年彷彿沒有歡樂可言。一想到我就會趕緊打住,讓思緒轉個方向,免得碰觸到無所不在的隱痛。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日子久了,我竟變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記憶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樁都只是殘缺片段,連不成一則稍微完整的情節。印象最強的反倒是結局;留在記憶中的那些經驗無論是怎麼開始和發展的,最後都是不愉快的收場。因此,我大半只記得傷痛,而忘卻其他枝節了。
在我童年的那個年頭,臺灣經濟還是很差的,鄉下人只有靠極為認命的勤奮和節儉,才能勉強養家。繼承祖業木匠的父親有九個小孩要養,把所有體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鑿子、鐵鎚和一批批木材堆裡;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擔子。
他那一日日彎駝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顏、一日日稀少的頭髮,始終不曾給過孩子們慈祥親切的感覺。他很少開口說話,也很少對我們展開笑容。孩子和他的溝通都透過母親傳達,甚至連他在生氣,也都是媽媽咬著我們的耳根:「你爸要處罰你了!」我們才知道。
父親的木訥和嚴厲,使家裡籠罩著一層高壓的氣氛,每個孩子在家裡都無法把自己的感情傾吐出來,彼此很少溝通,大家都是悶著地一日日長大起來。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溫馴聽命的態度來盡子女的本分。我會表示不滿、抗議,甚至以逃學、離家出走來抗拒自己的不幸命運。
不過,在我有膽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兒到學前階段,我只有以每個人都有的本能——哭,來表示抗議。
我的愛哭是極為出名的,連附近鄰居都怕了我。我動不動就哭,而且只要嗓門一開,就沒有人勸得了,只有在我哭夠了,覺得已經把家裡搞得雞犬不寧時,我才會甘願地打住。而那時,我通常是筋疲力盡,喉嚨都哭啞失聲,就地一癱就累極睡倒了。
在那些無理取鬧的哭陣中,我那已經被掃把竹條鞭笞過的手腿,會再加上很多條傷痕。但不論父母怎麼嚇我,或再加打幾頓,我都不會妥協,繼續哭,哭到大人們束手無策,反而會擔心我哭傷了。那時,媽媽或者祖母會塞些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蠟筆,希望我收住哭聲。儘管這些東西都得存上一兩個禮拜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但我都會把它們扔得遠遠的。我記得,自己那時的脾氣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愛哭,被親戚們認為是極沒出息的表現;叔伯在教訓堂兄弟姊妹們時,都會引我的例子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個年紀,我卻一點也不以自己的臭名為辱,還很得意地認為:唯獨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頭痛。
那種哭,是需要極大技巧和毅力的,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小時,除了身體消受不了,有時還會惹來沒人理的慘況。大人鬥不過、哄不住,也就不再嚇唬或施小惠了。於是,我往往會落得既可憐又可笑,獨自在角落裡,從轟轟烈烈的嚎啕變成有氣無力的嗚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來一場聲勢更壯大的,好證明自己沒被打敗。
我把每一場哭都當成突擊戰,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緣故,正是史無前列的一場壯烈長哭。
為什麼而哭倒是忘了,只記得自己沒闔眼地哭到天亮。從傍晚開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飯、拉開嗓門。媽媽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飯桌之後,把我的碗筷留著,將剩菜撥到另一只小碗裡,無可奈何地向靠在門檻旁的我說:「哭餓了,就自己來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裡大小一個個洗過澡,準備上床睡覺了。每個人從我身邊走過,都得把腳抬高一點,以免被我絆倒。
爸爸盯著我,搖搖頭,嘆了一口極為失望的氣,丟下一句:「現世(丟臉)!」姊姊用腳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罷;妹妹掂著腳跟,怕惹火了我遭殃;兩位哥哥則見怪不怪,從我身上一跨而過;弟弟們有的不明究理,有的對我做鬼臉。
我依舊哭我的,不顧一切。不多久,寢室的鼾聲開始響起;月亮漸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長逐漸縮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飯菜終於隱沒在黑暗中。
外面的貓叫、犬吠斷斷續續地傳來,終至寂靜,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我幾近虛脫、如遊絲般的喘息。我隱約地體會到,沒什麼人、什麼事會被我的哭聲打敗;這場仗徹頭徹尾是我在和自己拚鬥。
半夜,媽媽起床來勸我上床,幾乎已敗陣的我卻仍然堅持著不投降。媽媽莫可奈何,憐愛地在我手中塞了一個硬幣。我已無力和以往一樣把它扔遠,只是不願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幣滾在泥地上,沒有半點聲音。
媽媽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氣地盯著眼前的硬幣。在漆黑的角落,銅板稍稍反光。兩毛錢就想讓我妥協? 我哭不出來,彷彿最後一點的自尊都被擊潰了。
天際漸漸露白,硬幣上的花紋愈來愈清楚,我終於知道,那是一枚剛發行的一元新錢,大小與兩毛硬幣相仿。以我當時一週一毛的零用錢,得十個星期才存得起來!
這樣的下場,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破碎的尊嚴已恢復,我的哭終於使家人付出了大代價。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塊錢! 雖然那一塊錢依舊躺在地上,但我已經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還有尊嚴可言,但拒絕之後再拿,豈不連立場都沒? 對不能享用那一大筆財富,我幾乎後悔了整個童年。
這一場難忘的哭的經歷,讓我告別了童年的某個階段。之後,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順遂中逐漸長大。
【內文節選二】(選自卷一「看見」)
尋找方大曾
一想到那一天,那種緊張恐怖、死裡逃生的感覺就鮮明地回來。第一次覺得如此接近死亡。我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不用看臉色也知道,兩人都已經嚇得半死了! 我們和東方航空公司飛機上的一百多位乘客一樣,在一片驚嚇的慘叫聲中意識到,自己可能就這樣沒有了。飛機是從上海開來的,在香港啟德機場的跑道上,輪子已經快要觸地了,可是感覺上好像坐在搖籃裡、或是斷了線的大風箏上。機外正颳著強烈颱風,我們那位十分可能是戰鬥機駕駛員轉行的老共機長,在飛機被強風迎面刮上來之後,還不死心地想再做第二次的降落。飛機一往下衝就被風掀上來,一往下衝就被風掀上來。這個時候,慘叫聲已經變成了無助的哀號,所有的人都把命交出去了,只能任著機場和死神拔河……緊接著,即將摔到海裡的飛機幾乎是垂直地拔起,機身劇烈晃動,艙內的座椅和行李櫃被震得嘎嘎作響,飛機好像隨時會被扯裂、散掉……上升——上升——每個人都知道此刻我們正在掙脫死神的魔掌……飛機不晃了,平穩了,沒事了,命撿回來了! 飛機掉頭返航並最終平安降落廣州,胸腔裡的那顆心也才落實在心窩裡。
久久之後才有辦法平息下來的我跟太太,彼此相詢,快要完蛋的那一刻在想什麼。太太說,她的腦子裡翻來覆去地就是一件事——才十二歲的兒子要怎麼辦? 我老實告訴她,我一心只記掛著左胸口袋裡的五十張底片,覺得我對不起它們的作者小方。這位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攝影家,將隨著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為世人所知。他已經夠倒楣地失蹤、且被遺忘了五十多年,這下子,豈不如同他又死一次!
四年前,我的北京朋友、也是《中國攝影史》的作者之一——陳申跟我提到,他發現了一位在中日戰爭時期失蹤卻很可能已經喪命的、不為人知的戰地記者「小方」,正在整理他的作品,一有結果就會讓我知道。一年多前我去大陸為《攝影家》雜誌第十期的《中國專輯》做採訪工作時,我又跟陳申碰頭了。那天晚上陳申和太太小侯邀我們去他們家吃晚飯。飯桌上,我請陳申為我們注意些大陸老攝影家,這才使我又想起了小方。
原來陳申也差不多把這件事給忘了。他說:「小方啊,他的作品在我這裡擱了快兩年了,沒有出版社想要出版,最近我自己事情又多,也沒有時間再去動它。你要有興趣,吃過飯我拿出來給你瞧瞧!」
小方的八百多格底片,一張張地被裝在小紅紙套裡,分成四排,塞滿了一個約摸三十公分、寬二十公分、高十公分的木盒子。陳申把這批底片做過快速打樣,這些品質不佳的樣片凌亂地被塞在一個大紙袋裡。東西實在太多,我只有請他讓我把樣片帶回旅館,找時間慢慢看。
當天晚上,這些樣片鋪滿在我旅館房間的床上;在昏黃的床頭燈下,我一張張地檢視這位無名攝影家的遺產。儘管這些樣片的濃度、反差都處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就知道,我面對的是位天才。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陳申把底片借給我回到旅館仔細看,以便判斷這些影像的潛在力量有多大。第三天,我費盡口舌,要陳申允許我把底片帶回臺灣,好親自為這位了不起的攝影家放大照片。陳申說他做不了主,建議:「我們何不去拜訪這些底片的主人——小方的妹妹方澄敏? 她就住在北京!」
第四天,陳申約我們在國際飯店見面,因為方澄敏的家就在飯店後面的協和胡同裡。
就這麼幾步之差,我們從資本主義的銷金窟踏進了社會主義的平民窩裡。協和胡同十號的大門門楣上的浮雕,還殘存著往昔的氣派,一進門卻是破落的大雜院,好幾戶人家分居在原是四合院的幾個角落裡。對外人來說,簡直像個迷宮,拐來拐去才找到方澄敏住的那一戶。方澄敏正在她家門外搭的一座爐上燒開水,爐煙彌漫四處,很令人有探險的感覺。
八十歲的方澄敏看來身體不錯,精神也好,對我們的造訪顯得十分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小方的作品又有一個重新曝光的可能性了。除了存在陳申那裡的八百張底片外,方澄敏手頭還有一些比較屬於小方私人性質的照片,加起來一共是一千出頭。方澄敏在每一張底片的封套上都編了號碼,但是對照片的拍攝時間、地點和事件內容,她就不清楚了。不過,她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小方失蹤前兩年所拍的。在這個期間,小方像著了魔似的出門拚命拍照,暗房工作就落到這個敬愛哥哥萬分的妹妹頭上,這也是為什麼方澄敏保有這些底片的原因。五十多年來,歷經八年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大陸解放、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垮臺的種種動亂和遷徙,方澄敏始終仔細地保存這些珍貴的底片,並且不斷地尋求能把哥哥的作品出版的機會。直到現在,她還抱著一絲希望,也許哪一天,小方會像當初突然不見了那樣,又突然出現在她面前。
小方原名方德曾,又名方大曾,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北京。「小方」是他當記者發表作品時使用的筆名。方澄敏回憶,小方在初中時就接觸過照相機,後來也一直把拍照當成重要的休閒活動。但是他不喜歡拍人像,最常拍的是風景、廟宇、古跡。他們的父親當時在外交部做總務工作,家境算是不錯的。除此之外,家裡的氣氛自由,思想開放,父母對小方這項在當時還算是十分奢侈的嗜好並不加以干涉。
「九一八事變」日本進侵東三省,小方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被激起了強烈的愛國心。
一九三七年曾經和小方一道去採訪的陸詒先生,在大陸的報業同仁刊物《報海春秋》上,寫過一篇紀念方大曾的短文——〈悼念抗戰初期犧牲的小方〉。其中敘述了小方投身抗日工作,進而成為攝影記者的經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小方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讀書。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侵略促使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接受實際鬥爭的訓練。一九三二年,他曾任少先隊的機關刊物《少年先鋒》週刊編輯。這個祕密刊物當時僅有他和方殷同志負責,從寫稿、編輯、校對,一直到印刷、發行,都由他們兩人承擔。後來任人民通訊社記者方殷同志和我談起,當時北平在白色恐怖之下,他與小方每次到印刷廠時,總要看看前後左右有沒有特務盯梢;到了出版發行時,又要分頭奔走到幾個書攤上去努力推銷。由於經費困難,這個刊物出不來幾期就停刊了。
一九三五年他從大學畢業以後,先應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當幹事,以後又轉到天津青年會工作,一面仍致力於當地抗日救亡工作。當天津中共地下黨員組建「中外新聞社」時,即聘任小方為該社攝影記者。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那是他採訪報導與攝影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是位活躍的青年記者。他所寫的通訊報導與拍攝的照片,都在國內各著名報刊上發表。……這些通訊報導都寫得文筆流暢,觀察深刻,又配以形象生動的新聞照片,深受讀者歡迎。
儘管小方曾活躍一時,畢竟,兩年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而刊登小方作品的報刊也都壽命不長。隨著時日,小方被人們淡忘,以至於後人編撰的《中國攝影史》一書,也只有短短這麼一段(第七章第二節,第二八○頁)提到他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出版的第四十一期《美術生活》刊出攝影記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攝的《抗戰圖存》和《衛國捐軀》兩組照片。前者是記者在盧溝橋拍中國第一批戰況照片共七幅,占了兩版,特加英文說明。後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問抗戰受傷將士的情況。
目前保留在方澄敏手邊的約一千張底片,絕大部分都從來沒有被放大成照片過,當然也沒有發表過。方澄敏很樂意讓《攝影家》雜誌發表小方的作品,但卻不放心底片漂洋過海到臺灣去。但我深知,只有我把底片帶回臺灣,親自放大,才能把他的作品做最好的呈現。經我熱切的請求和保證,方澄敏終於勉強答應,讓我挑選一部分底片帶回去,並在最短時間內專程請人把底片送回北京。
小方的底片都是120的,片幅大部分都是6×9cm及6×4.5cm,並有少量6×6cm正方形規格。從他掛著相機的肖像看來,他所使用的相機極可能是Rolleiflex以及類似Zeiss Ikon的折疊式相機。所有底片都被剪裁成單張,而且每個畫面只有一格,可能不夠好的作品都已經被小方淘汰了。因為我只被允許帶回五十張,所以我在挑選作品上絕對不能有任何閃失。我反覆地一再審視這些樣片及底片,斟酌了三天之後,終於選定了五十張影像,另外再從陳申那裡已經放出來的5×7小照片中挑了八張。這五十八張作品,加上方澄敏提供的小方不同年齡的生活留影,一張不漏的成為當期《攝影家》雜誌的全部內容。
回到臺灣,我在家裡的暗房內待了一個禮拜。每放一張照片,我就對小方的才氣又服氣一回。他的構圖完美極了,對瞬間的掌握也無可挑剔! 他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節的影響。最令人詫異的是,他的表現手法就是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來,依舊顯得十分現代。方大曾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世界攝影家相比,毫不遜色。
在暗房的安全燈下,小方的作品一張張地顯現出來,讓我覺得好像在與小方的精神做某種程度的溝通。很遺憾我無緣認識他,除了他的妹妹,我也沒有機會碰見任何與他相識或相熟的朋友。即使他有過一些朋友,又有誰今天還活著呢? 他只活了短暫的二十五年,他的親人和朋友沒有足夠機會跟他好好接近,這個世界也沒有足夠時間認識他的才華。
有關小方的文章,現在所能看到的少之又少。寫小方的陸詒事實上也幾乎只與他有過一面之緣。他們分手的兩個多月之後,小方就失去蹤跡,下落不明。他在這篇文章裡描寫的小方,並不知道自己在度著生命裡的最後幾個日子:
我和小方相識,時在抗戰初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們從保定去長辛店前線採訪。范長江特赴車站送別,並為我們做鄭重介紹。當時小方已任上海《大公報》特約記者,年少、英俊,頭上戴一頂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襯衫和黃短褲,足登跑鞋,掛一架相機,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我們搭平漢路上的兵車到長辛店後,即奔三十七師戴旅旅部訪問,戴旅長已到前線陣地指揮去了。走回長辛店的路上,小方為一個年僅十六歲的士兵照相,他身上背著自己的步槍和大刀,手執日本軍官的指揮刀、望遠鏡之類的戰利品,笑嘻嘻地凱旋。這時,一顆炮彈正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顧地對我說:「今天收穫不小。」當晚,宛平縣政府祕書長洪大中接待我們住在長辛店縣政府辦事處,前線槍炮聲徹夜不息。二十九日上午,我們隨軍撤退。三十日早上回到保定,長江為我們慶倖生還。當天下午,保定又遭敵機狂炸,孫連仲部隊連續開赴前線,接替二十九軍防線。長江和我當即搭車回南方,留小方在保定,繼續採訪平漢鐵路北段戰訊……
自此以後,家人和朋友都沒有再見過小方。
今天,他的作品首度正式地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呈現在大家面前,就某種意義來說,小方又回來了!
【內文節選二】(選自卷三「聽見」)
重聽李歐納‧柯恩(節選)
我對音樂的涉獵範圍既廣又雜,除了無法消受重金屬搖滾,所有類型的音樂我都有興趣收藏,在這方面投入的時間與精力,一點也不亞於我的本行——攝影專業。音樂讓我能和完全陌生的人,立即從事最深刻的心靈溝通。現在,我的家當以又重又多的黑膠唱片為主,總數已超過了一萬張。
我對音樂的熱愛源自老家兩位善吹銅管樂器的叔叔,五叔的薩克斯風已達職業水準,六叔的小喇叭也很出色,風流倜儻的四叔更是交際舞高手。他們找同好組成了一個六人的爵士樂隊,經常在家裡舉行祕密舞會。儘管我的童年常在封閉小鎮的菜園裡渡過,但每當週末夜晚,我就能藉著一場場舞會熟悉西洋通俗音樂。叔叔們有一套手搖的留聲機,每當樂隊休息的空檔,我就幫忙上發條、放唱片,有時一個晚上還要換幾次鋼製唱針。
叔叔們搬離祖宅後,市面上的留聲機七十八轉唱片被四十五轉與三十三轉的黑膠唱片取代。他們不要的一些老唱片成為我的第一批收藏,留下來的那套雙聲道音響,更是讓我從美軍電臺熟悉了排行榜上的一首首西洋熱門歌曲。初二那年,我從頭城轉學到冬山中學,認識了一位廖姓同學,才從他那醫師父親的大量收藏中,接觸到古典音樂,認識了巴哈以降的偉大音樂家們。
我省下所有的零用錢去買自己心儀的盜版唱片,雖然封套印刷粗糙,唱片翻製品質不佳,我也把它們當成至寶。高中畢業時,我的古典音樂唱片也有好幾箱了。到臺北工作後搬過幾次家,無論到哪,這些唱片都跟著我,直到去服兵役時把它們寄放在朋友家,後來也沒要回來。
製作電視節目時,由於配樂所需,我又開始大量蒐集唱片。那時,臺北有幾家進口原版唱片的商店,在中山北路的上揚以進口古典音樂與世界音樂為主;南京東路的歌林公司專門進口爵士樂,尤其是歐洲的一些新爵士;位於忠孝東路頂好商圈的方圓唱片則是熱門的搖滾音樂最多,身邊有關柯恩的唱片,都是在這裡買的。
第一次看到那十二英吋正方的專輯封面,李歐納‧ 柯恩便立即從一個抽象人物變得具體起來。他的第一張專輯封面素雅,年輕的帥哥雙目炯炯有神、含情脈脈地對著鏡頭,封底卻是色彩鮮豔的普普畫,一位雙手被鐵鍊銬住的長髮裸女在熊熊烈火當中,表情卻十分安寧,沒有半點受苦的樣子。這幅圖像似乎是在表達色慾與祭典、墮落與贖罪的雙重意象;這也正是柯恩內心的投影。
專輯共有十首歌,包括膾炙人口的:〈Suzanne〉、〈The Sisters of Mercy〉、〈So Long, Marianne〉、〈Hey, That's No Way to Say Goodbye〉等等。這張處女作預告了柯恩未來的事業之途,但在美國受歡迎的程度遠不及歐洲,在英國排行榜上停留了一年半,且曾列名十三,在美國則是直到二十二年後才獲得金唱片(銷售五十萬張)。
〈Suzanne〉是柯恩所做的第一首,也是最常被其他歌手錄製的歌。歌詞出自於他一九六六年的詩集《天堂寄生蟲》(Parasites of Heaven),譜曲後,於同一年由美國歌手茱迪‧科林斯率先灌唱。由於大受歡迎,據說,在那個年代出生的許多女孩都被取名為Suzanne。
蘇珊帶你下到她河畔的居處
你會聽見船隻徐徐駛過
你可與她共渡此夜 你知道她半顛半狂
這就是你為何想在那兒
她餵你柳丁和茶 那是來自遙遠的中國
當你正想告訴她 沒有愛可給她
她從她的波長理解了你 讓河水幫她回答
你一直是她的情人 想和她一起旅行 盲目地旅行
你知道她會信任你
因為你用心靈觸撫過她完美的身軀
耶穌曾是水手 當他行走於水面時
他花了好多時間 從他那孤寂的木塔守望
最後確信 只有溺水的人看得見他
他說 讓所有人都是水手吧 直到海洋釋放了他們
但早在天堂開啟之前
他自己也已殘破 被拋棄 幾乎是個人類
有如石頭 沉沒在你的智慧下
你想和他一起旅行 盲目地旅行
你想 或許可以信任他
因為他用心靈撫觸過你完美的身軀
……
Suzanne Verdal是他的朋友雕刻家Armand Vaillancourt的妻子。一九九四年,柯恩接受BBC專訪時澄清,他只是幻想與Suzanne纏綿,實際上是既沒機會也沒被對方鼓勵,因此,什麼事也沒發生。
從我所收藏的眾多茱迪‧科林斯的唱片中,可以感覺出,她在唱柯恩的歌時格外虔誠;配樂十分節約,幾乎是清唱,彷彿唯有如此才能完整而透徹地詮釋歌曲給她的啟示。在她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自傳《信任你的心》(Trust Your Heart)中,曾如此提到柯恩:「他的歌像捏在手中的符咒或石頭,帶我渡過黑暗歲月,直到太陽升起或火炬點燃。面對成千上萬的人們時,那些歌讓我站在中央,閉著眼,用手繞著吉他的頸部,吟詠著那空靈的歌詞。觀眾呼應著他寫的歌,彷彿乾渴將亡的人獲得了甘霖。當我們的靈魂繃到要斷裂,這就是為靈魂而唱的歌。」
柯恩的第二張專輯是一九六九年出的《來自一個房間的歌》(Songs From A Room),封面是高反差黑白肖像,印刷品質頗為粗糙,封底就是他那著名的、在希臘的房間,正中央是扇緊閉著的大木窗,從窗縫依舊可以感覺得出戶外陽光有多豔。
房間陳設極為簡單,窗旁的面壁角落有張放著手提打字機的木桌,一位圍著浴巾的金髮女郎假裝打字,俏麗的臉蛋卻轉過來對著鏡頭甜笑。女郎身後有一張鋪著白床單的大床,前景是張方方的木製餐桌,上面有盒雙陸棋。
女郎就是〈So Long Marianne〉那首歌的主角。一九六○年,二十六歲的柯恩得到祖母的一筆遺贈,用美金一千五元在希臘的海卓島(Hydra)買了一間三層樓的老舊白房,沒電沒自來水,但從門口走到愛琴海只要十分鐘,而且「有巨大的陽臺,看得見戲劇性的山景和許多耀眼的白房子……。」
他與挪威作家Alex Jenson留在島上的妻子Marianne墜入愛河,與她和她的兒子一起生活。柯恩曾說,Marianne是他見過最美麗的女人,兩人的關係維繫了大約十年,柯恩有多首詩、歌,靈感皆來自Marianne。
《來自一個房間的歌》這張專輯穩固了柯恩的地位。堪稱他代表作的那首〈電線上的鳥〉(Bird on the Wire),靈感便是來自於小島上的生活。他每天上午寫作,其他時間游泳、航海、與朋友喝酒、唱歌、聊到半夜。有一天,他赫然發現,幾世紀以來不曾變過的海卓島,竟然架設起電話線來! 沮喪的他某天望向窗外,卻看到半空中的電線上有隻小鳥。
「這首歌是在希臘開始寫的,一九六九年結束於好萊塢的一家旅店裡,所有其他的事也是。」這是他在日後的加註。
像電線上的鳥 像午夜唱詩班裡的醉漢
我試過用自己的方式 追求自由
像魚鈎上的蟲餌 像古書裡的騎士
我為你保存了我所有的絲帶
如果,如果我曾經不善
希望你忘了它
如果,如果我曾經不真
希望你明白 那從來不是對你
像一個死產的嬰兒 像一頭長角的野獸
我撕裂了每一個將手伸向我的人
但我以此歌起誓
我將為所有犯過的錯補償你
……
一九七一年出的《愛與恨之歌》(Songs of Love and Hate),封面設計也很拙氣,和當時流行的華麗風格背道而馳。一九七三年發行的《舊儀式的新外殼》(New Skin for the Old Ceremony),封面木刻版畫乃取自一本一五五○年古書中的插圖,兩位長翅膀、戴皇冠的男女以媾和姿勢擁抱,使得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在唱片被禁後,將此圖代以柯恩本人的肖像,重新發行。幸好我買的是原版。
一九七五年的《李歐納‧柯恩最著名的歌》(Leonard Cohen Greatest Hits)讓大家對他的才情有更進一步認識,其中還有他的塗鴉及為每首歌寫的劄記。對封面肖像,他顯然相當滿意:「這是皮諾在米蘭的一個旅館,對著房間鏡子拍的。我很少這麼好看過,或是這麼難看過——看你有沒政治手腕。」
封面的他看起來純潔優雅,內套的肖像卻表現了他頹廢的一面,坐在床上吐著菸圈,比前者老了好幾歲。塗鴉就更有意思了,寥寥幾筆把他對女性的渴望與愛慕表露無遺。一名男子膜拜一位舉鏡顧影的長髮裸女,下方有他自創的三行符號,沒人看得懂,可能藉此形容他對此女的臣服已無世俗文體可表達。
一九七七年,由柯恩作詞、菲爾‧史貝特(Phil Spector)作曲的《萬人迷之死》(Death of a Ladies' Man) 在推出後惡評如潮,柯恩自己也稱其為「一場災難」。這張唱片的失敗,讓接下來的《最近的歌》(Recent Songs)、《形形色色的姿態》(Various Position)未能贏得該有的掌聲。
其實,《最近的歌》是我最常聽的專輯, 其中的〈窗〉(The Window)、〈叛徒〉(The Traitor)、〈吉普賽人之妻〉(The Gypsy's Wife)等三首特別觸動我,因為有John Bilezikjian彈奏歐得琴,Raffi Hakopian演奏小提琴,從名字就能知道他們是亞美尼亞人。這張專輯的曲子實在是太美了,編曲與樂手功不可沒,似乎是想把不同地域的音樂元素重新組合,有東方的冥想、西方的抒情;有搖滾的反叛、民歌的素樸;也有吉普賽「深歌」的哀泣、墨西哥街頭樂隊的歡暢,縱使將柯恩的聲音完全拿掉,依舊動聽。
說實在的,柯恩的許多歌,在尚未明白歌詞之前,會覺得重複,像吟詩、像囈語,聽個幾首就會昏昏欲睡。這也難怪,因為他不像在唱歌,倒像與自己對話。他也經常表示,自己連音都抓不準,幸好合音都很棒:「有女人跟我一起唱歌,我的聲音聽起來會好得多,有些沉悶的音質會被抵消。」一九九二年,他獲頒加拿大Juno Award 的年度最佳男歌手獎,於致詞時表示:「像我這種嗓音,只有在加拿大才能得獎!」
在他那些優秀的合音天使當中,七○年代的老班底珍妮佛‧華恩絲(Jennifer Warnes)是最有名的。她既能寫歌,又能編曲、製作,曾得過奧斯卡獎與葛萊美獎。一九八七年,Cypress唱片公司發行了她向柯恩致敬的《著名的藍色雨衣》(Famous Blue Raincoat),將柯恩所作的九首歌詮釋得靈動十足;其中的〈貝爾納黛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且是她與柯恩、比爾‧艾略特(Bill Elliot)的聯合創作。
〈著名的藍色雨衣〉這首以書信形態,敘述三角戀愛的歌,彷彿是柯恩不斷重蹈覆轍的處境。錄製這首歌的歌手最少有四十位,瓊‧ 拜雅在西班牙畢爾包鬥牛場的「鑽石與塵土」(Diamonds and Rust)現場音樂會,就唱得令人心折。雖然拜雅當年翻唱「蘇珊」,因將部分歌詞更動,而讓柯恩宣稱受到「粗魯的侵犯」……。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