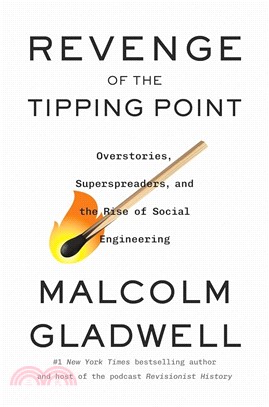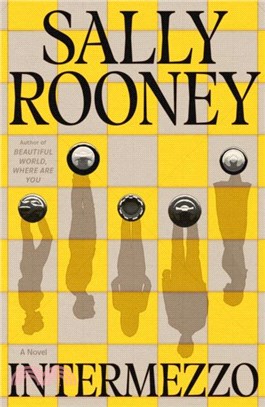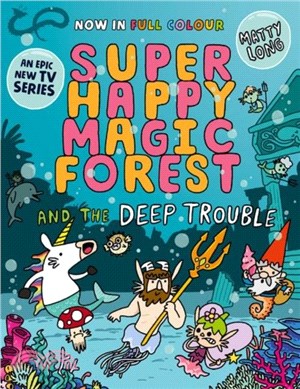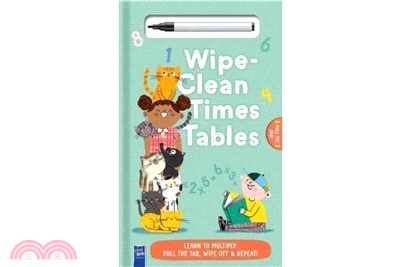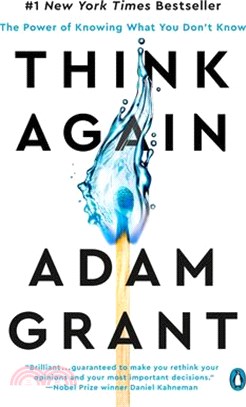定價
:NT$ 320 元優惠價
:75 折 239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1、「引領娛樂小說界的全能寫手」日本最暢銷的警察小說作家
2、《雪蟲》之「刑警鳴澤了」系列為其代表作,多次改拍成日劇(坂口憲二飾演主角)
3、日本書店員力推,讀了就停不下來的「刑警鳴澤了」系列
4、在日系列累銷突破200萬冊
新參者,鳴澤了報到!
前進東京,重拾刑警熱血魂!
在故鄉新潟立下大功,卻質疑自己刑警失格的鳴澤了,最後決定辭職,離開故鄉與家人來到東京流浪。
然而抵不過內心刑警魂的呼喚,又報考了警視廳特別錄用考試,最終又走回了刑警的老路……
考上刑警後,鳴澤了被分派到了多摩署,被刻意冷凍,每天只能待在資料室讀著過去的檔案。有一天,因人手不足,一起襲擊街友的傷害案件轉到了鳴澤了手上。他與同樣遭到白眼孤立的美女刑警小野寺冴同組搭檔,隨即趕往現場。到達案發現場時,受傷的街友卻已消失蹤影……兩人持續循線調查想找出失蹤街友的去向。
無獨有偶,此時發生了另一起殺人未遂的案件。警方意外發現兩起案件的被害人過去同屬於一個學運派系,但高層卻認為兩起案子沒有必然的關聯性,於是鳴澤了與小野寺又奉命持續追蹤街友傷害案。只是愈查真相愈離奇,甚至發現被害人的周邊竟然潛伏著另一組警方人馬──公安蠢蠢欲動著……
過去的黑幕即將浮出水面,真相再度令鳴澤了抱頭狂喊Oh,NO!
子彈不僅奪去了人的性命,擊碎了人心,讓它死了一部分。
精采絕倫,令人廢寢忘食的警察小說
日本刑事控書店員黑著眼圈熬夜也要推薦!
《破彈》相關人物介紹
鳴澤了
祖父、父親都是刑警,從小耳濡目染,深深自覺生來就是要當刑警。他以刑警的工作為榮,享受以正當理由與權力逮捕犯人時的快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曾丟下刑警的身分。做事一板一眼,認為世界非黑即白,即使再細微的犯罪也不容逃脫。不管是親人或是警察同僚,犯了罪都一視同仁。二十九歲離開新潟縣警本部,三十歲重新考進東京警視廳派駐多摩警署。
鳴澤家的男人到中學畢業,一律到東京讀高中、大學,體驗單身生活。大學時代曾留學美國一年,因此精通英語。
考慮到刑警要經常跑現場,因此刻意菸酒不沾,不喝碳酸飲料以維持絕佳體力。
小野寺冴
三十歲,鳴澤了在多摩警署時期的搭檔。
身材姣好,容貌端正的美女刑警。從小母親希望培養她成為模特兒,小學五年級時被火燒傷,留下疤痕後,斷念。當上刑警的原因是,當年火災被住在隔壁的刑警救出,從此崇拜不已。
在多摩署與鳴澤了是同期新人,加上女性身分經常被歧視對待。
2、《雪蟲》之「刑警鳴澤了」系列為其代表作,多次改拍成日劇(坂口憲二飾演主角)
3、日本書店員力推,讀了就停不下來的「刑警鳴澤了」系列
4、在日系列累銷突破200萬冊
新參者,鳴澤了報到!
前進東京,重拾刑警熱血魂!
在故鄉新潟立下大功,卻質疑自己刑警失格的鳴澤了,最後決定辭職,離開故鄉與家人來到東京流浪。
然而抵不過內心刑警魂的呼喚,又報考了警視廳特別錄用考試,最終又走回了刑警的老路……
考上刑警後,鳴澤了被分派到了多摩署,被刻意冷凍,每天只能待在資料室讀著過去的檔案。有一天,因人手不足,一起襲擊街友的傷害案件轉到了鳴澤了手上。他與同樣遭到白眼孤立的美女刑警小野寺冴同組搭檔,隨即趕往現場。到達案發現場時,受傷的街友卻已消失蹤影……兩人持續循線調查想找出失蹤街友的去向。
無獨有偶,此時發生了另一起殺人未遂的案件。警方意外發現兩起案件的被害人過去同屬於一個學運派系,但高層卻認為兩起案子沒有必然的關聯性,於是鳴澤了與小野寺又奉命持續追蹤街友傷害案。只是愈查真相愈離奇,甚至發現被害人的周邊竟然潛伏著另一組警方人馬──公安蠢蠢欲動著……
過去的黑幕即將浮出水面,真相再度令鳴澤了抱頭狂喊Oh,NO!
子彈不僅奪去了人的性命,擊碎了人心,讓它死了一部分。
精采絕倫,令人廢寢忘食的警察小說
日本刑事控書店員黑著眼圈熬夜也要推薦!
《破彈》相關人物介紹
鳴澤了
祖父、父親都是刑警,從小耳濡目染,深深自覺生來就是要當刑警。他以刑警的工作為榮,享受以正當理由與權力逮捕犯人時的快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曾丟下刑警的身分。做事一板一眼,認為世界非黑即白,即使再細微的犯罪也不容逃脫。不管是親人或是警察同僚,犯了罪都一視同仁。二十九歲離開新潟縣警本部,三十歲重新考進東京警視廳派駐多摩警署。
鳴澤家的男人到中學畢業,一律到東京讀高中、大學,體驗單身生活。大學時代曾留學美國一年,因此精通英語。
考慮到刑警要經常跑現場,因此刻意菸酒不沾,不喝碳酸飲料以維持絕佳體力。
小野寺冴
三十歲,鳴澤了在多摩警署時期的搭檔。
身材姣好,容貌端正的美女刑警。從小母親希望培養她成為模特兒,小學五年級時被火燒傷,留下疤痕後,斷念。當上刑警的原因是,當年火災被住在隔壁的刑警救出,從此崇拜不已。
在多摩署與鳴澤了是同期新人,加上女性身分經常被歧視對待。
作者簡介
引領娛樂小說界的全能寫手──堂場瞬一 SHUNICHI DOBA
一九六三年出生於日本茨城縣。畢業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二○○○年出道作以運動小說《8年》獲得集英社創辦的「小說昂新人獎」。隨後風格一變,第二部交出了警察小說「刑警鳴澤了」首部曲《雪蟲》引起文壇注目,從此成為最受日本讀者期待的警察小說作家。除了「刑警鳴澤了」系列,另著有「警視廳失蹤課高城賢吾」系列、「警察廳追蹤搜查係」系列等膾炙人口作品,也屢屢影像化,搬上螢光幕。
堂場瞬一筆耕不輟,本本熱銷,題材新穎,二○一五年寫作生涯邁向第十五個年頭,角川書店前社長角川春樹讚譽他為「引領娛樂小說界的全能寫手」。由於創作冊數即將破百,目前各大出版社為他共同企畫「堂場瞬一Countdown 100」,預計今年(二○一五)十月完成第一百冊作品。
http://www.doba.jp/
一九六三年出生於日本茨城縣。畢業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二○○○年出道作以運動小說《8年》獲得集英社創辦的「小說昂新人獎」。隨後風格一變,第二部交出了警察小說「刑警鳴澤了」首部曲《雪蟲》引起文壇注目,從此成為最受日本讀者期待的警察小說作家。除了「刑警鳴澤了」系列,另著有「警視廳失蹤課高城賢吾」系列、「警察廳追蹤搜查係」系列等膾炙人口作品,也屢屢影像化,搬上螢光幕。
堂場瞬一筆耕不輟,本本熱銷,題材新穎,二○一五年寫作生涯邁向第十五個年頭,角川書店前社長角川春樹讚譽他為「引領娛樂小說界的全能寫手」。由於創作冊數即將破百,目前各大出版社為他共同企畫「堂場瞬一Countdown 100」,預計今年(二○一五)十月完成第一百冊作品。
http://www.doba.jp/
目次
第一部 緩坡
第二部 陰暗的連鎖
第三部 冰凍的雨
第二部 陰暗的連鎖
第三部 冰凍的雨
書摘/試閱
第一部 緩坡
1
刑警的工作有八成是寫報告。
一般人認為報告給誰寫都沒兩樣,但確實有人寫得好,有人寫得差,而無論報告寫得多差,都一定會冒出濃濃的案件味。
我在資料室的摺疊椅上坐了五分滿,桌上攤開一片老舊的辦案資料,是關於三年前發生的便利超商搶案。案件本身並不怎麼稀奇,但有一點與其他搶案不同,那就是案件中的傷者並非店員,而是搶匪。那天晚上值大夜班的工讀生是空手道三段,看到搶匪把手伸向收銀機,就靈活地抓住手腕扭了半圈,接著狠狠對著脖子一記手刀,臉上又一記肘擊,打得搶匪臉部頰骨骨折,身受重傷。
這份報告所描述的經過,簡直就像格鬥技雜誌的專題報導。
我不禁冷笑。兇手是中國人,他後來怎麼了?是不是逃回老家,忍著臉上的凹陷與疼痛,回想闖蕩日本的恐怖經驗?
掛在腰間的手機震動起來,打斷我對受傷中國人的天馬行空。
「鳴澤?」
「是。」
「人在哪?」
「資料室。」
「原來在那裡啊。」
刑警課係長水島一朗的口氣聽來有些錯愕,因為資料室就在刑警課隔壁,我拿好手機反問:「什麼事?」
「發生傷害事件,被害人是街友,地點在多摩南公園,其他人都沒空,就你去一趟吧。」他前半段的口氣平鋪直敘,後半段頓了一下,透露出真心話:「反正你這個時候還在泡資料室,應該也很閒吧。」
是很閒,不用別人提醒自己也清楚得很,現在快晚上九點鐘,我卻沒有回家,而是獨自泡在資料室裡弄得滿身灰。我晚上不是看老案子的資料,就是在街頭隻身閒逛──這算是我的個人巡邏吧。自從到多摩警署上任以來,我的工作就只有處理雜務,就算回家也只能慢跑或擦鞋,這兩件事成了我傍晚之後僅剩的殺時間活動。
我已經打了太久的空檔,這樣下去引擎遲早會報銷,最近我愈來愈想做些刑警該做的工作,什麼都行,今天總算讓我碰上一件,就算只是單純的傷害,被害人又只是個街友,一樣是件刑案。我很高興能幫那些懶得跑現場的人代班。
我沒去刑警課就直接離開警署,綿綿細雨打溼了皮鞋,但今晚我毫不在乎。
來到案發現場多摩南公園,這裡離京王小田急線多摩中心站的鬧區有些距離,處於國宅的角落,公園有些破舊,廁所和飲水機髒兮兮的,沾了秋雨的草木也顯得有氣無力。
公園角落拉起了封鎖線,裡面有許多藍色塑膠布搭成的帳篷,我上任已經好幾個月,還以為早就把管區逛得滴水不漏,卻還不知道這裡住了一批街友。鑑識人員正在採集證據,雨勢逐漸轉強,相機閃光燈把雨絲閃得清晰可見,我把風雨大衣的釦子全扣滿,拉起衣領,寒風毫不留情地吹來,連厚重大衣都擋不住,冰冷刺骨。
當我穿過黃色封鎖線進入現場,突然與某女子四目相接,小野寺冴,一個月前剛來多摩警署上任的刑警,之前和她打過招呼,每天還在警署碰面,卻不記得和她說上半句話。或許她也不認得我,只是皺起眉頭盯著我,應該是在腦海中比對長相和姓名──不對,她看我的眼神還帶些責難,似乎是嫌我太慢。
我暫時放慢腳步,快快打量這人。她頗高,如果再穿高一點的高跟鞋,眼睛的高度應該和我差不多,明明已經這麼晚了,氣色卻像剛睡飽八小時一樣清爽,身穿深藍長褲套裝配薄大衣,服裝相當整齊,只是大衣底下若隱若現的那雙腿稍微長得不像話。
「什麼情況?」
我點頭致意,上前搭話,冴不滿地皺起眉頭。
「真搞不懂。」
「什麼搞不懂?沒線索搞不懂?還是不曉得什麼不懂?」
冴的臉色漲紅起來。
「你是……鳴澤對吧?」
「對,鳴澤了。」
「你是遲到過頭打算找我吵架?」
「原來妳只有這種口氣。」
「你最好改改你那脾氣。」
「三十歲了,脾氣應該改不動。」
「三十?難不成跟我同期?」
「應該是。」
「是喔。」
當冴一發現這件事,口氣立刻從客氣改為隨便,但不代表是拉近距離,態度完全沒有絲毫軟化。
「所以問題在哪?」
「沒有被害人。」
「沒有?」
「消失了。」
我皺起眉頭想確認冴是不是在開玩笑,應該不是,她看起來也不像會說笑的人。「是誰報的案?」
「住這裡的街友,已經問過話了。」
「我再問一次好了。」
「你信不過我?」
「不是不信妳,是不信別人傳的話。」
冴聳聳肩,作勢望向其中一頂帳篷,我上前掀開帳棚入口的毯子,裡面有名男子坐在摺疊椅上,嚇得抬起頭來。看男子縮成一團,我先微笑致意,但男子臭著一張臉,一看就知道他被搞得很不耐煩。
帳篷裡意外地舒適,塑膠布掛在樹枝上,下邊用大釘子釘在地面上,整體呈現三角形,看來有點像雪國的透天厝,屋頂角度相當陡,住在裡面一定很窘迫,但至少不必風吹雨打,而且也不怕下雨天帳篷積水。帳篷角落有台髒兮兮的煤油暖爐,有它應該能撐過不久之後的寒冬。原本以為街友的帳篷裡會有濃濃的腐臭味,但實際上竟然是濃濃的醬油和砂糖味。仔細一看,原來角落還有一座卡式瓦斯爐,爐上放了口黑漆漆的鍋子,瓦斯爐旁有個開過的秋刀魚罐頭,帳篷最裡面還胡亂擺了幾台電腦,應該是從垃圾場撿來的,聽說撿破爛可以賣點錢。另外還有一張歪斜的矮桌,上面的液晶小電視閃著藍白色的雜訊,男子伸手把電視音量轉小。
冴在我身後咕噥一聲。
「他是脇田先生。」
「名字是?」
我回頭問她,她不開心地回答:「一幸,脇田一幸。一二三的一,幸福的幸。」
「脇田先生?」
脇田聽我一喊又抬起頭來,表情困惑又僵硬,皮笑肉不笑。
「你看到什麼了?」
「不是看到,是聽到,隔壁帳篷有人尖叫。」
「怎樣的尖叫?」
「就是叫住手,然後我又聽到揍人的聲音。」脇田嚇得緊緊抱住自己,差點崩潰:「好像有誰離開那個帳篷,可是我沒看見。」
「後來怎麼了?」
「當然是過一陣子就去看看情況啊。」脇田應該是解釋了很多次,口氣相當不耐煩:「然後就發現阿澤倒在地上。」
「被害人姓澤?」
「對。」
「名字呢?」
「不知道。」
「真的?」
脇田努力克制心中怒火,狠狠瞪了我一眼。
「刑警大哥,我說謊有用嗎?這種地方誰還管姓名?大家早就把名字扔在老家裡了!」
阿澤,是單一個澤,還是澤田、澤口之類的?不清楚,說不定其實是名而不是姓。
「傷勢怎樣?」
「腳受傷了。」脇田拍了自己的右膝一下:「穿著褲子看不清楚,不過他很像很痛,說不定膝蓋骨折了。」
「他有說什麼沒有?」
「當時好像沒辦法說話,只會說好痛好痛,然後我就連忙去叫救護車。」
「公共電話對吧?」
「那當然,這裡哪來室內電話?」脇田酸我一句。
最近的公共電話在哪?至少我在公園附近沒見到。
「從你離開去打電話到回來為止,花了多久時間?」
脇田想了想,回答十分鐘左右。
在斷腿的狀況下,十分鐘可以走多遠?我不禁想到是有人帶走了阿澤。
「所以等你回來,那個人就不見了?」
「對。」
「怎麼不見的?」
「我怎麼知道……」脇田咬咬嘴唇,然後突然靈機一動說:「搞不好是腳踏車喔。」
「腳踏車?」
「對,阿澤有輛腳踏車,只是破破爛爛,想騎直線都有困難,搞不好他騎著腳踏車就自己去看醫生了。」
脇田起身從我們身邊經過,離開帳篷,他身上有些汗臭味,但還不致於難以忍受。
我問問身邊的冴:「被害人的帳篷呢?」
「鑑識人員正在裡面。」
脇田停在街友阿澤的帳篷前面,應該是擔心打擾到裡面拍照蒐證的鑑識人員,不敢進去,我就在雨中繼續問他。
「阿澤都把腳踏車放在帳篷裡?」
「對,他做事很謹慎。」脇田說著冷笑一聲,似乎是覺得這種地方沒必要謹慎。
我向鑑識人員打聲招呼,往帳篷裡探頭望去,裡面就像脇田的帳篷一樣堆滿破銅爛鐵,但是沒見到腳踏車,退出帳篷對脇田說了我的發現,脇田點點頭,臉上寫著「我早說了吧?」
我又繼續問他:「你平常跟被害人很熟?」
「說熟也不算熟。」脇田有些為難:「這種地方的規矩,就是大家互相視而不見,或許偶爾聊聊天氣,發點橫財就請大家喝一杯吃一頓,也就這樣了。我不想被人打探經歷,所以也不去打探別人,這裡的人應該都一樣吧。」
「所以你也只知道他叫『阿澤』。」
「就是這樣。」
我走出帳篷,下過雨的地面四處是積水,走著走著鞋就溼了,令我不悅咂了一聲。離開公園四處張望,多摩中心是由山坡地開墾而來,京王線與小田急線的轉乘站位在地勢最低的地方,公園前是個平緩的下坡,只要腳踏車動起來,就算不踩踏板應該也能勉強抵達車站。
但接下來該怎麼辦?膝蓋骨折可不是普通的痛,絕對不可能走路,明明可以躺在公園等救護車來載,為什麼要特地忍著痛楚逃走?
回公園一看,冴無所事事地站在被害人的帳篷前,態度依然充滿戒心,難道是怕有人在她的地盤鬧事?
「其他人呢?」
「沒人來。」冴往四周望了一圈。「可見大家多瞧不起這件案子。」
這我才不管,案子就是案子,我清清喉嚨轉移話題。
「幾點發生的?」
冴伸出手來看看表。
「兩個鐘頭之前吧。」
那我真的是來晚了。或者說不是我來晚,而是水島太晚想起我的名字。
「妳在這裡多久了?」
「其實我也是半小時之前才到,跟派出所的員警交班。」
「感覺不太對勁。」
「是啊。」冴的口氣冷靜了一些,拉拉大衣的衣領。
「其他人都問過話了?」
「差不多。」
「那就回署裡去吧,鑑識也做得差不多了。」
「是啊,今天晚上已經沒什麼好問了。」
「回去之前要不要再看一次現場?」
「我已經看過了。」
「那我自己去就好。」
我離開冴,獨自走入街友阿澤的帳篷裡,向鑑識人員借了手電筒來照明,破銅爛鐵透出一股柴米油鹽味,帳篷正中央有張歪斜的三腳桌,還有椅背少了塑膠墊的摺疊椅,有張床墊擠在塑膠布邊,上面扔了一床毯子,這頂帳篷裡似乎沒有暖爐,空氣感覺比外面更悶更冷。
床墊另一頭有三個塑膠整理箱疊在一起,我戴起手套在裡面翻找,發現裡面整齊地疊著衣服,雖皺但出乎意料地乾淨,不知道去哪裡洗過,想從襯衫裡面找出洗衣店的標籤,但沒有找到。帳篷裡的收音機仍然開著,不斷發出細小的聲音,這時候正好在播報新聞,豎耳聽了聽,跟這件案子似乎沒有關係。
帳篷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身分,只好放棄,離開帳篷吸了口溼冷的空氣,才察覺帳篷裡果然充滿異味。
冴依然站在帳篷外。
「發現什麼沒有?」口氣有些挑釁。
「沒有。」
「我想也是。」這次口氣顯得有些傲。「我也查過一次,毫無線索。」
「意思是妳找不到的東西,我也找不到?」
「沒錯。」冴一針見血,轉身離開公園坐上汽車,那是輛Impreza的箱型車,應該是自用車;這輛車的車主族群是年輕男子而不是女人,風格不太適合一名三十歲的女刑警,但她坐進駕駛座的動作就像穿衣服一樣自然。
有些事會變,有些不會。
不變的,就是我依然在當刑警;變的……我想剩下的應該都變了。大約一年前我在故鄉新潟扯上了一件案子,是仇殺,起因於五十年前的另一件案子,在偵辦過程中,發現曾任新潟縣警本部搜查一課課長的爺爺和那件老案子有關,當爺爺發現我查出真相便自行結束了生命,而我並沒有阻止他。
這件事情讓我辭了新潟縣警的工作,我爸是縣警的幹部之一,明知道爺爺與案子有關卻自己瞞著不說,令人無法接受,而我也不清楚自己對爺爺見死不救,到底還有沒有資格繼續當刑警。
可是我沒有其他選擇,離開故鄉之後,來到念過高中、大學的東京,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走下去,最後還是選了刑警這一行,只是還不清楚這究竟對不對。
回到署裡一看,刑警課的大辦公室還亮著燈,我跟在冴身後走進辦公室,裡面只剩水島一個人在處理文件,發現我們進來先是抬個頭,隨即又低頭辦文,然後開口說了。「聽說被害人逃離現場?」
「是。」冴回答。
「這案子不清不楚,就你們兩個辦吧。」
我和冴面面相覷,她一臉嫌煩的表情,而她眼中的我應該也差不多。冴不滿地扁嘴抗議。「就我們兩個?」
「廢話。」水島又抬起頭,一口駁回冴低調的抗議,眼鏡底下閃著冷冷的光芒。「這點小案子還能給多少人手?」
「……了解。」冴的口氣心不甘情不願,但還是點頭。「今天晚上先告辭了。」
「嗯,辛苦了。」
我默默鞠躬,正要離開辦公室又被水島叫住。
「鳴澤。」
水島勾勾食指叫我過去,這動作讓我不太開心,但還是回到他的座位旁,水島湊向我低聲呢喃。
「小心點,別被咬死了。」
「什麼?」
「那傢伙可是匹野馬。」
水島笑說,眼神不懷好意,其實我只與她相處片刻就知道她是匹野馬,那水島又為什麼要我和她搭檔?我希望水島解釋清楚,只見他又低下頭去處理文件,意思應該是多說無益。
我在停車場趕上了冴,她正要打開Impreza的車門,回頭看到是我,眼裡燃著一抹憤怒的火焰。
「說人是非很有趣?」
「什麼意思?」
「你剛不是跟係長一起說我壞話?」
「哪有。」
「不用騙我。」
「我沒有說妳壞話。」
冴嗤之以鼻,我則是清清喉嚨,想趕走她蠻不講理的怒氣。「明天現場見吧。」
「也好。」
「八點?」
冴低頭看表,點點頭。「八點,可以。」
我正想說送她回家,但又把話吞了回去,因為我們兩個都有車,而且如果隨口就說要送她回家,應該真的會被她咬死。
「哎,這算不算嫌我們麻煩?」冴明顯語帶怒氣。
「算。」
「開什麼玩笑?沒想到公務員這麼陰險。」
我只能聳聳肩,因為自己也是公務員之一。
我偶爾會問自己,當個公務員──刑警──究竟有什麼意義?之前我相信刑警是自己的天職,但現在卻沒有信心這麼說。腦袋裡不斷浮現一個問題,這樣好嗎?辭去新潟縣警的工作卻又跑來警視廳,我算不算是個偽善的大騙子?
而想到我可能得這樣問自己一輩子,就煩悶不已。
冴坐上車發動引擎,停車場響起一陣粗獷的排氣聲浪,Impreza隨即濺起水花疾駛而去;這輛車有兩百八十匹馬力,剛好符合日本法規上限,四輪傳動抓地力十足,車尾又有顯眼的擾流板,似乎吶喊著要跑賽道或越野拉力,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她會選這樣的車。
我住在小山頭上的一棟透天厝。在京王線與小田急線的鐵路北面,南面則是多摩警署,這裡原本是我畢業大學的一位副教授的家,他們夫妻倆正在美國留學,我就借住下來順便看家。副教授家裡是地主,每一代都賣掉一點土地改建國宅,目前攢下來的財產可以讓三代家人過好日子,所以說什麼懶得算稅金,也就沒跟我收錢。
目前我只付水電費就住在這嶄新又時髦的兩層樓透天厝裡,不怕住得困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免錢就開心。但我無所謂,只是運氣好一點罷了。
把車開進車庫,放下鐵門,坐在玄關裡擦拭溼濡的皮鞋,先用乾布擦掉水珠,鞋尖部分已經溼透,所以要往裡面塞報紙,接著用鞋刷刷去泥土,本來想上鞋油打亮,但得等到鞋子乾了才行。
在玄關擦擦大衣,我全身溼透,就像吞了冰塊一樣冷得受不了,兩個星期前穿著輕薄西裝都還會流汗,但一轉眼秋已深。多摩的深秋讓我想起可惡的冬天,多摩乾冷的天氣連我這個新潟小孩都怕,毫不留情的冷風不帶任何水氣,冷上加冷,感覺比新潟還要冷得多。
這城市等於我第二個故鄉。鳴澤家的家規是中學畢業後立刻就要去東京,我也不例外,高中加大學七年都在多摩市生活,但應該直到大學最後兩年才總算習慣這個冷度,這還是因為大二那年去美國留過學,地點又是超冷的中西部城市。之後我回到新潟當了七年的縣警,又恢復了新潟人的體質,現在回到東京要迎接第一個冬天,心情不禁沉重難耐。
我慢條斯理地沖了澡來暖和身體,吹乾頭髮,走到擺滿松木家具的客廳裡坐上沙發,這時候已經凌晨一點。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四個月還是不太習慣,房東夫婦特別喜歡鄉村風格,家裡擺飾就像美國拓荒時代的民宅、沒上漆的松木家具、鋪棉坐墊,一切都讓我感覺不對勁,所以我只使用家裡的客廳、廚房、浴室與廁所,睡覺就睡在客廳旁邊一坪半的書房。書房裡有張小沙發,每天晚上我就拎條毯子窩在沙發上,享受又短又淺的睡眠。
這房子只有一個地方讓我中意,那就是從客廳外推出去的陽台,陽台上能完整俯瞰多摩街景,當然此時的街景已經悄然入睡,只能見到幾家熬夜的燈火在黑暗中做出無謂的抵抗。今晚下雨,連抵抗的人家都見不到,但無論早中晚,這景色我永遠看不膩。
或許這是我現在唯一可得的奢華。
隔天早上雨停了,但天氣更冷,當我不到八點鐘抵達現場,冴已經開始工作,對著一群惶恐的帳篷居民問話。公園周圍依然掛著封鎖線,街坊鄰居與新聞記者們圍在外面探頭探腦。
今天早報只有社會版的角落提到昨天晚上這件案子,標題是「公園街友遭到攻擊?」內容就像那個問號一樣不清不楚,這也難怪,畢竟沒有被害人,連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沒有發生過案子。
冴一看到我就大步走來,但那步伐雖然看起來很大,對她這個長腿姊姊來說很正常。在我問候早安之前,她已板起臉先開口。
「真慢。」
我故意把手表舉到她眼前。「時間還沒到啊。」
「不就是比我慢?」
「妳打算跟我比誰先到現場?」
「如果真要比,我絕對不會輸。」
「我才不比。」
冴聽了有些失望,看來她這個人不鬥個嘴是不能開工的。
冴翻了翻手冊說道:「這裡已經問不出什麼東西了。」
「公園裡這麼多帳篷,竟然沒有人看到任何經過,不覺得奇怪嗎?如果有陌生人出沒,應該有人發現才對。」
「很多人都有收音機或電視,昨天晚上又下雨,應該很難注意到外面的狀況,再說大家互不干涉也是這個地方的規矩。」
或許她說的沒錯,為什麼要拋下家庭到公園裡用塑膠布搭帳篷過日?唯一理由就是想拋棄什麼,而這個「什麼」八成是人際關係。
「到附近打聽看看吧。」
「也對。」冴看看公園四周。「不過可能有點難。」
「好像是。」我也跟著冴望了一圈,公園周圍確實都是老舊的國宅,但不巧都是後門階梯對著公園,就算公園裡發生了什麼事也聽不清楚,昨天晚上又下雨,再說這一帶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全部問過話應該得花不少時間。
目前這件案子就只有我們兩個負責,往後應該也是。
我解開大衣鈕釦,吸入冰冷空氣,眼前一大片藍色帳篷就像成排平房,或者色彩鮮豔的難民營,我再次前往街友阿澤的帳篷觀察。
陽光可以穿透塑膠布,裡面看起來比昨天晚上要清楚,但還是找不到任何與被害人身分有關的線索,帳篷入口附近發現了血跡──昨天晚上沒發現──但血跡很少,無法聯想到被害人的傷勢,比較像是割破手沾上的血跡。
我離開帳篷走向那群帳篷居民,這群人又氣又怕地同時望向我,其中只有脇田向我點頭致意,但看起來也不是很配合。
突然傳來啜飲的聲音,往那裡望過去,有名男子縮在釣魚用的小摺凳上,雙手小心地捧著咖啡杯,我走上前去,男子又更蜷縮了一點。昨天晚上沒見過這張臉,服裝又跟其他男人有點不同,身穿及腰風衣配牛仔褲,腳套短筒靴,雖然料子有點舊但還算乾淨,更重要的是沒有汗臭味。
這人一看到我,就露出燦爛的笑容。
「你是刑警大哥?」
「對,你是?」
「名字?岩隈哲郎,要握個手嗎?」
聽起來像是取笑我,我有點不開心地拒絕。姓岩隈的男子得意地點點頭,又舉杯喝了一口。我聞到濃濃的咖啡味,看他腳底有一台小瓦斯爐正煮著咖啡壺,感覺不像帳篷居民,比較像在公園角落享受戶外時光。
「你也住在這裡?」
「我四海為家,偶爾會來這裡。」
「昨天晚上也來了嗎?」
「昨天來得晚,你們走了之後才來。」
「所以你對案子不清楚?」
岩隈起身從褲袋裡掏出皺巴巴的報紙,沙沙作響地甩開來。
「只知道這上面寫的。」
「你認識阿澤這個人?」
「他應該在這裡住最久了。」岩隈說著,依然笑容滿面。「就我所知,應該在這裡有一年以上了吧。」
「你跟他很熟?」
「聊過天,不過這裡的人不會積極交談啦。」
這話跟昨天晚上脇田說的一樣,看來這種地方有它的江湖規矩。
「都有人被打了,竟然沒幾個人發現,這樣對嗎?通常應該會鬧大吧。」
「大家應該都怕事吧。我跟你說,會在這裡的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可能是被地下錢莊追債,可能有人幹了壞事,當然不會主動去報警。畢竟我們光是待在這裡,就算非法占據公園啦。」
「所以阿澤也幹過什麼壞事?」
「誰知道?」岩隈歪著脖子賣關子:「我跟他真的不算熟。」
「大概幾歲?」
「五十左右吧?可是過這種日子老得快,實際上或許更年輕點。」
「這裡面誰跟阿澤最熟?」
「不知道,我又不是社區管理員,沒那麼清楚,要是清楚我一定配合。」
「我要怎麼聯絡你?」
「我會主動找你。我不覺得警察都是壞蛋,有人打阿澤,當然會幫忙抓出來。」
我拿出名片,岩隈用拇指與食指夾了過去。
「可能有什麼苦衷喔。」岩隈摸摸有點鬍碴的下巴。
「苦衷?」
「應該吧。」岩隈站起身,個子非常小,大概只到我的肩膀,他拍拍腿笑著說:「真要說的話,這裡每個人也都有苦衷,或許我們在你們眼裡都是跟社會脫節,不過也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才落到這個地步來。」
「這我不太清楚。」
「說不定你們也認識阿澤喔。」
「為什麼?」
「如果是以前的案子,應該都有留紀錄吧?不過我說的不是你們刑警,而是公安那邊,他們煩死人了。」
「公安?所以他是極左派?」
「嗯,阿澤感覺不像右翼分子。」
「這些話是真的?」
「冷靜點吧。」岩隈舉起雙手想安撫我:「別太激動,這只是我的感覺,阿澤也沒拿他被逮捕的事情出來炫耀過。」
「你知不知道他來這裡之前過著怎樣的日子?」
「不知道,他也不喜歡提自己的過去,要不要去查查新左翼派系(sect)的案子?說不定能查出他的身分喔。你們加油,可別因為是街友被打就懶得查囉。」
我想反駁,想大聲喊說自己不會歧視立場與生活不同的人,絕對不可能。
但我沒能開口,岩隈似乎是看透我猶豫不決的態度,輕輕揮手之後緩步離去。
(待續)
1
刑警的工作有八成是寫報告。
一般人認為報告給誰寫都沒兩樣,但確實有人寫得好,有人寫得差,而無論報告寫得多差,都一定會冒出濃濃的案件味。
我在資料室的摺疊椅上坐了五分滿,桌上攤開一片老舊的辦案資料,是關於三年前發生的便利超商搶案。案件本身並不怎麼稀奇,但有一點與其他搶案不同,那就是案件中的傷者並非店員,而是搶匪。那天晚上值大夜班的工讀生是空手道三段,看到搶匪把手伸向收銀機,就靈活地抓住手腕扭了半圈,接著狠狠對著脖子一記手刀,臉上又一記肘擊,打得搶匪臉部頰骨骨折,身受重傷。
這份報告所描述的經過,簡直就像格鬥技雜誌的專題報導。
我不禁冷笑。兇手是中國人,他後來怎麼了?是不是逃回老家,忍著臉上的凹陷與疼痛,回想闖蕩日本的恐怖經驗?
掛在腰間的手機震動起來,打斷我對受傷中國人的天馬行空。
「鳴澤?」
「是。」
「人在哪?」
「資料室。」
「原來在那裡啊。」
刑警課係長水島一朗的口氣聽來有些錯愕,因為資料室就在刑警課隔壁,我拿好手機反問:「什麼事?」
「發生傷害事件,被害人是街友,地點在多摩南公園,其他人都沒空,就你去一趟吧。」他前半段的口氣平鋪直敘,後半段頓了一下,透露出真心話:「反正你這個時候還在泡資料室,應該也很閒吧。」
是很閒,不用別人提醒自己也清楚得很,現在快晚上九點鐘,我卻沒有回家,而是獨自泡在資料室裡弄得滿身灰。我晚上不是看老案子的資料,就是在街頭隻身閒逛──這算是我的個人巡邏吧。自從到多摩警署上任以來,我的工作就只有處理雜務,就算回家也只能慢跑或擦鞋,這兩件事成了我傍晚之後僅剩的殺時間活動。
我已經打了太久的空檔,這樣下去引擎遲早會報銷,最近我愈來愈想做些刑警該做的工作,什麼都行,今天總算讓我碰上一件,就算只是單純的傷害,被害人又只是個街友,一樣是件刑案。我很高興能幫那些懶得跑現場的人代班。
我沒去刑警課就直接離開警署,綿綿細雨打溼了皮鞋,但今晚我毫不在乎。
來到案發現場多摩南公園,這裡離京王小田急線多摩中心站的鬧區有些距離,處於國宅的角落,公園有些破舊,廁所和飲水機髒兮兮的,沾了秋雨的草木也顯得有氣無力。
公園角落拉起了封鎖線,裡面有許多藍色塑膠布搭成的帳篷,我上任已經好幾個月,還以為早就把管區逛得滴水不漏,卻還不知道這裡住了一批街友。鑑識人員正在採集證據,雨勢逐漸轉強,相機閃光燈把雨絲閃得清晰可見,我把風雨大衣的釦子全扣滿,拉起衣領,寒風毫不留情地吹來,連厚重大衣都擋不住,冰冷刺骨。
當我穿過黃色封鎖線進入現場,突然與某女子四目相接,小野寺冴,一個月前剛來多摩警署上任的刑警,之前和她打過招呼,每天還在警署碰面,卻不記得和她說上半句話。或許她也不認得我,只是皺起眉頭盯著我,應該是在腦海中比對長相和姓名──不對,她看我的眼神還帶些責難,似乎是嫌我太慢。
我暫時放慢腳步,快快打量這人。她頗高,如果再穿高一點的高跟鞋,眼睛的高度應該和我差不多,明明已經這麼晚了,氣色卻像剛睡飽八小時一樣清爽,身穿深藍長褲套裝配薄大衣,服裝相當整齊,只是大衣底下若隱若現的那雙腿稍微長得不像話。
「什麼情況?」
我點頭致意,上前搭話,冴不滿地皺起眉頭。
「真搞不懂。」
「什麼搞不懂?沒線索搞不懂?還是不曉得什麼不懂?」
冴的臉色漲紅起來。
「你是……鳴澤對吧?」
「對,鳴澤了。」
「你是遲到過頭打算找我吵架?」
「原來妳只有這種口氣。」
「你最好改改你那脾氣。」
「三十歲了,脾氣應該改不動。」
「三十?難不成跟我同期?」
「應該是。」
「是喔。」
當冴一發現這件事,口氣立刻從客氣改為隨便,但不代表是拉近距離,態度完全沒有絲毫軟化。
「所以問題在哪?」
「沒有被害人。」
「沒有?」
「消失了。」
我皺起眉頭想確認冴是不是在開玩笑,應該不是,她看起來也不像會說笑的人。「是誰報的案?」
「住這裡的街友,已經問過話了。」
「我再問一次好了。」
「你信不過我?」
「不是不信妳,是不信別人傳的話。」
冴聳聳肩,作勢望向其中一頂帳篷,我上前掀開帳棚入口的毯子,裡面有名男子坐在摺疊椅上,嚇得抬起頭來。看男子縮成一團,我先微笑致意,但男子臭著一張臉,一看就知道他被搞得很不耐煩。
帳篷裡意外地舒適,塑膠布掛在樹枝上,下邊用大釘子釘在地面上,整體呈現三角形,看來有點像雪國的透天厝,屋頂角度相當陡,住在裡面一定很窘迫,但至少不必風吹雨打,而且也不怕下雨天帳篷積水。帳篷角落有台髒兮兮的煤油暖爐,有它應該能撐過不久之後的寒冬。原本以為街友的帳篷裡會有濃濃的腐臭味,但實際上竟然是濃濃的醬油和砂糖味。仔細一看,原來角落還有一座卡式瓦斯爐,爐上放了口黑漆漆的鍋子,瓦斯爐旁有個開過的秋刀魚罐頭,帳篷最裡面還胡亂擺了幾台電腦,應該是從垃圾場撿來的,聽說撿破爛可以賣點錢。另外還有一張歪斜的矮桌,上面的液晶小電視閃著藍白色的雜訊,男子伸手把電視音量轉小。
冴在我身後咕噥一聲。
「他是脇田先生。」
「名字是?」
我回頭問她,她不開心地回答:「一幸,脇田一幸。一二三的一,幸福的幸。」
「脇田先生?」
脇田聽我一喊又抬起頭來,表情困惑又僵硬,皮笑肉不笑。
「你看到什麼了?」
「不是看到,是聽到,隔壁帳篷有人尖叫。」
「怎樣的尖叫?」
「就是叫住手,然後我又聽到揍人的聲音。」脇田嚇得緊緊抱住自己,差點崩潰:「好像有誰離開那個帳篷,可是我沒看見。」
「後來怎麼了?」
「當然是過一陣子就去看看情況啊。」脇田應該是解釋了很多次,口氣相當不耐煩:「然後就發現阿澤倒在地上。」
「被害人姓澤?」
「對。」
「名字呢?」
「不知道。」
「真的?」
脇田努力克制心中怒火,狠狠瞪了我一眼。
「刑警大哥,我說謊有用嗎?這種地方誰還管姓名?大家早就把名字扔在老家裡了!」
阿澤,是單一個澤,還是澤田、澤口之類的?不清楚,說不定其實是名而不是姓。
「傷勢怎樣?」
「腳受傷了。」脇田拍了自己的右膝一下:「穿著褲子看不清楚,不過他很像很痛,說不定膝蓋骨折了。」
「他有說什麼沒有?」
「當時好像沒辦法說話,只會說好痛好痛,然後我就連忙去叫救護車。」
「公共電話對吧?」
「那當然,這裡哪來室內電話?」脇田酸我一句。
最近的公共電話在哪?至少我在公園附近沒見到。
「從你離開去打電話到回來為止,花了多久時間?」
脇田想了想,回答十分鐘左右。
在斷腿的狀況下,十分鐘可以走多遠?我不禁想到是有人帶走了阿澤。
「所以等你回來,那個人就不見了?」
「對。」
「怎麼不見的?」
「我怎麼知道……」脇田咬咬嘴唇,然後突然靈機一動說:「搞不好是腳踏車喔。」
「腳踏車?」
「對,阿澤有輛腳踏車,只是破破爛爛,想騎直線都有困難,搞不好他騎著腳踏車就自己去看醫生了。」
脇田起身從我們身邊經過,離開帳篷,他身上有些汗臭味,但還不致於難以忍受。
我問問身邊的冴:「被害人的帳篷呢?」
「鑑識人員正在裡面。」
脇田停在街友阿澤的帳篷前面,應該是擔心打擾到裡面拍照蒐證的鑑識人員,不敢進去,我就在雨中繼續問他。
「阿澤都把腳踏車放在帳篷裡?」
「對,他做事很謹慎。」脇田說著冷笑一聲,似乎是覺得這種地方沒必要謹慎。
我向鑑識人員打聲招呼,往帳篷裡探頭望去,裡面就像脇田的帳篷一樣堆滿破銅爛鐵,但是沒見到腳踏車,退出帳篷對脇田說了我的發現,脇田點點頭,臉上寫著「我早說了吧?」
我又繼續問他:「你平常跟被害人很熟?」
「說熟也不算熟。」脇田有些為難:「這種地方的規矩,就是大家互相視而不見,或許偶爾聊聊天氣,發點橫財就請大家喝一杯吃一頓,也就這樣了。我不想被人打探經歷,所以也不去打探別人,這裡的人應該都一樣吧。」
「所以你也只知道他叫『阿澤』。」
「就是這樣。」
我走出帳篷,下過雨的地面四處是積水,走著走著鞋就溼了,令我不悅咂了一聲。離開公園四處張望,多摩中心是由山坡地開墾而來,京王線與小田急線的轉乘站位在地勢最低的地方,公園前是個平緩的下坡,只要腳踏車動起來,就算不踩踏板應該也能勉強抵達車站。
但接下來該怎麼辦?膝蓋骨折可不是普通的痛,絕對不可能走路,明明可以躺在公園等救護車來載,為什麼要特地忍著痛楚逃走?
回公園一看,冴無所事事地站在被害人的帳篷前,態度依然充滿戒心,難道是怕有人在她的地盤鬧事?
「其他人呢?」
「沒人來。」冴往四周望了一圈。「可見大家多瞧不起這件案子。」
這我才不管,案子就是案子,我清清喉嚨轉移話題。
「幾點發生的?」
冴伸出手來看看表。
「兩個鐘頭之前吧。」
那我真的是來晚了。或者說不是我來晚,而是水島太晚想起我的名字。
「妳在這裡多久了?」
「其實我也是半小時之前才到,跟派出所的員警交班。」
「感覺不太對勁。」
「是啊。」冴的口氣冷靜了一些,拉拉大衣的衣領。
「其他人都問過話了?」
「差不多。」
「那就回署裡去吧,鑑識也做得差不多了。」
「是啊,今天晚上已經沒什麼好問了。」
「回去之前要不要再看一次現場?」
「我已經看過了。」
「那我自己去就好。」
我離開冴,獨自走入街友阿澤的帳篷裡,向鑑識人員借了手電筒來照明,破銅爛鐵透出一股柴米油鹽味,帳篷正中央有張歪斜的三腳桌,還有椅背少了塑膠墊的摺疊椅,有張床墊擠在塑膠布邊,上面扔了一床毯子,這頂帳篷裡似乎沒有暖爐,空氣感覺比外面更悶更冷。
床墊另一頭有三個塑膠整理箱疊在一起,我戴起手套在裡面翻找,發現裡面整齊地疊著衣服,雖皺但出乎意料地乾淨,不知道去哪裡洗過,想從襯衫裡面找出洗衣店的標籤,但沒有找到。帳篷裡的收音機仍然開著,不斷發出細小的聲音,這時候正好在播報新聞,豎耳聽了聽,跟這件案子似乎沒有關係。
帳篷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身分,只好放棄,離開帳篷吸了口溼冷的空氣,才察覺帳篷裡果然充滿異味。
冴依然站在帳篷外。
「發現什麼沒有?」口氣有些挑釁。
「沒有。」
「我想也是。」這次口氣顯得有些傲。「我也查過一次,毫無線索。」
「意思是妳找不到的東西,我也找不到?」
「沒錯。」冴一針見血,轉身離開公園坐上汽車,那是輛Impreza的箱型車,應該是自用車;這輛車的車主族群是年輕男子而不是女人,風格不太適合一名三十歲的女刑警,但她坐進駕駛座的動作就像穿衣服一樣自然。
有些事會變,有些不會。
不變的,就是我依然在當刑警;變的……我想剩下的應該都變了。大約一年前我在故鄉新潟扯上了一件案子,是仇殺,起因於五十年前的另一件案子,在偵辦過程中,發現曾任新潟縣警本部搜查一課課長的爺爺和那件老案子有關,當爺爺發現我查出真相便自行結束了生命,而我並沒有阻止他。
這件事情讓我辭了新潟縣警的工作,我爸是縣警的幹部之一,明知道爺爺與案子有關卻自己瞞著不說,令人無法接受,而我也不清楚自己對爺爺見死不救,到底還有沒有資格繼續當刑警。
可是我沒有其他選擇,離開故鄉之後,來到念過高中、大學的東京,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走下去,最後還是選了刑警這一行,只是還不清楚這究竟對不對。
回到署裡一看,刑警課的大辦公室還亮著燈,我跟在冴身後走進辦公室,裡面只剩水島一個人在處理文件,發現我們進來先是抬個頭,隨即又低頭辦文,然後開口說了。「聽說被害人逃離現場?」
「是。」冴回答。
「這案子不清不楚,就你們兩個辦吧。」
我和冴面面相覷,她一臉嫌煩的表情,而她眼中的我應該也差不多。冴不滿地扁嘴抗議。「就我們兩個?」
「廢話。」水島又抬起頭,一口駁回冴低調的抗議,眼鏡底下閃著冷冷的光芒。「這點小案子還能給多少人手?」
「……了解。」冴的口氣心不甘情不願,但還是點頭。「今天晚上先告辭了。」
「嗯,辛苦了。」
我默默鞠躬,正要離開辦公室又被水島叫住。
「鳴澤。」
水島勾勾食指叫我過去,這動作讓我不太開心,但還是回到他的座位旁,水島湊向我低聲呢喃。
「小心點,別被咬死了。」
「什麼?」
「那傢伙可是匹野馬。」
水島笑說,眼神不懷好意,其實我只與她相處片刻就知道她是匹野馬,那水島又為什麼要我和她搭檔?我希望水島解釋清楚,只見他又低下頭去處理文件,意思應該是多說無益。
我在停車場趕上了冴,她正要打開Impreza的車門,回頭看到是我,眼裡燃著一抹憤怒的火焰。
「說人是非很有趣?」
「什麼意思?」
「你剛不是跟係長一起說我壞話?」
「哪有。」
「不用騙我。」
「我沒有說妳壞話。」
冴嗤之以鼻,我則是清清喉嚨,想趕走她蠻不講理的怒氣。「明天現場見吧。」
「也好。」
「八點?」
冴低頭看表,點點頭。「八點,可以。」
我正想說送她回家,但又把話吞了回去,因為我們兩個都有車,而且如果隨口就說要送她回家,應該真的會被她咬死。
「哎,這算不算嫌我們麻煩?」冴明顯語帶怒氣。
「算。」
「開什麼玩笑?沒想到公務員這麼陰險。」
我只能聳聳肩,因為自己也是公務員之一。
我偶爾會問自己,當個公務員──刑警──究竟有什麼意義?之前我相信刑警是自己的天職,但現在卻沒有信心這麼說。腦袋裡不斷浮現一個問題,這樣好嗎?辭去新潟縣警的工作卻又跑來警視廳,我算不算是個偽善的大騙子?
而想到我可能得這樣問自己一輩子,就煩悶不已。
冴坐上車發動引擎,停車場響起一陣粗獷的排氣聲浪,Impreza隨即濺起水花疾駛而去;這輛車有兩百八十匹馬力,剛好符合日本法規上限,四輪傳動抓地力十足,車尾又有顯眼的擾流板,似乎吶喊著要跑賽道或越野拉力,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她會選這樣的車。
我住在小山頭上的一棟透天厝。在京王線與小田急線的鐵路北面,南面則是多摩警署,這裡原本是我畢業大學的一位副教授的家,他們夫妻倆正在美國留學,我就借住下來順便看家。副教授家裡是地主,每一代都賣掉一點土地改建國宅,目前攢下來的財產可以讓三代家人過好日子,所以說什麼懶得算稅金,也就沒跟我收錢。
目前我只付水電費就住在這嶄新又時髦的兩層樓透天厝裡,不怕住得困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免錢就開心。但我無所謂,只是運氣好一點罷了。
把車開進車庫,放下鐵門,坐在玄關裡擦拭溼濡的皮鞋,先用乾布擦掉水珠,鞋尖部分已經溼透,所以要往裡面塞報紙,接著用鞋刷刷去泥土,本來想上鞋油打亮,但得等到鞋子乾了才行。
在玄關擦擦大衣,我全身溼透,就像吞了冰塊一樣冷得受不了,兩個星期前穿著輕薄西裝都還會流汗,但一轉眼秋已深。多摩的深秋讓我想起可惡的冬天,多摩乾冷的天氣連我這個新潟小孩都怕,毫不留情的冷風不帶任何水氣,冷上加冷,感覺比新潟還要冷得多。
這城市等於我第二個故鄉。鳴澤家的家規是中學畢業後立刻就要去東京,我也不例外,高中加大學七年都在多摩市生活,但應該直到大學最後兩年才總算習慣這個冷度,這還是因為大二那年去美國留過學,地點又是超冷的中西部城市。之後我回到新潟當了七年的縣警,又恢復了新潟人的體質,現在回到東京要迎接第一個冬天,心情不禁沉重難耐。
我慢條斯理地沖了澡來暖和身體,吹乾頭髮,走到擺滿松木家具的客廳裡坐上沙發,這時候已經凌晨一點。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四個月還是不太習慣,房東夫婦特別喜歡鄉村風格,家裡擺飾就像美國拓荒時代的民宅、沒上漆的松木家具、鋪棉坐墊,一切都讓我感覺不對勁,所以我只使用家裡的客廳、廚房、浴室與廁所,睡覺就睡在客廳旁邊一坪半的書房。書房裡有張小沙發,每天晚上我就拎條毯子窩在沙發上,享受又短又淺的睡眠。
這房子只有一個地方讓我中意,那就是從客廳外推出去的陽台,陽台上能完整俯瞰多摩街景,當然此時的街景已經悄然入睡,只能見到幾家熬夜的燈火在黑暗中做出無謂的抵抗。今晚下雨,連抵抗的人家都見不到,但無論早中晚,這景色我永遠看不膩。
或許這是我現在唯一可得的奢華。
隔天早上雨停了,但天氣更冷,當我不到八點鐘抵達現場,冴已經開始工作,對著一群惶恐的帳篷居民問話。公園周圍依然掛著封鎖線,街坊鄰居與新聞記者們圍在外面探頭探腦。
今天早報只有社會版的角落提到昨天晚上這件案子,標題是「公園街友遭到攻擊?」內容就像那個問號一樣不清不楚,這也難怪,畢竟沒有被害人,連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沒有發生過案子。
冴一看到我就大步走來,但那步伐雖然看起來很大,對她這個長腿姊姊來說很正常。在我問候早安之前,她已板起臉先開口。
「真慢。」
我故意把手表舉到她眼前。「時間還沒到啊。」
「不就是比我慢?」
「妳打算跟我比誰先到現場?」
「如果真要比,我絕對不會輸。」
「我才不比。」
冴聽了有些失望,看來她這個人不鬥個嘴是不能開工的。
冴翻了翻手冊說道:「這裡已經問不出什麼東西了。」
「公園裡這麼多帳篷,竟然沒有人看到任何經過,不覺得奇怪嗎?如果有陌生人出沒,應該有人發現才對。」
「很多人都有收音機或電視,昨天晚上又下雨,應該很難注意到外面的狀況,再說大家互不干涉也是這個地方的規矩。」
或許她說的沒錯,為什麼要拋下家庭到公園裡用塑膠布搭帳篷過日?唯一理由就是想拋棄什麼,而這個「什麼」八成是人際關係。
「到附近打聽看看吧。」
「也對。」冴看看公園四周。「不過可能有點難。」
「好像是。」我也跟著冴望了一圈,公園周圍確實都是老舊的國宅,但不巧都是後門階梯對著公園,就算公園裡發生了什麼事也聽不清楚,昨天晚上又下雨,再說這一帶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全部問過話應該得花不少時間。
目前這件案子就只有我們兩個負責,往後應該也是。
我解開大衣鈕釦,吸入冰冷空氣,眼前一大片藍色帳篷就像成排平房,或者色彩鮮豔的難民營,我再次前往街友阿澤的帳篷觀察。
陽光可以穿透塑膠布,裡面看起來比昨天晚上要清楚,但還是找不到任何與被害人身分有關的線索,帳篷入口附近發現了血跡──昨天晚上沒發現──但血跡很少,無法聯想到被害人的傷勢,比較像是割破手沾上的血跡。
我離開帳篷走向那群帳篷居民,這群人又氣又怕地同時望向我,其中只有脇田向我點頭致意,但看起來也不是很配合。
突然傳來啜飲的聲音,往那裡望過去,有名男子縮在釣魚用的小摺凳上,雙手小心地捧著咖啡杯,我走上前去,男子又更蜷縮了一點。昨天晚上沒見過這張臉,服裝又跟其他男人有點不同,身穿及腰風衣配牛仔褲,腳套短筒靴,雖然料子有點舊但還算乾淨,更重要的是沒有汗臭味。
這人一看到我,就露出燦爛的笑容。
「你是刑警大哥?」
「對,你是?」
「名字?岩隈哲郎,要握個手嗎?」
聽起來像是取笑我,我有點不開心地拒絕。姓岩隈的男子得意地點點頭,又舉杯喝了一口。我聞到濃濃的咖啡味,看他腳底有一台小瓦斯爐正煮著咖啡壺,感覺不像帳篷居民,比較像在公園角落享受戶外時光。
「你也住在這裡?」
「我四海為家,偶爾會來這裡。」
「昨天晚上也來了嗎?」
「昨天來得晚,你們走了之後才來。」
「所以你對案子不清楚?」
岩隈起身從褲袋裡掏出皺巴巴的報紙,沙沙作響地甩開來。
「只知道這上面寫的。」
「你認識阿澤這個人?」
「他應該在這裡住最久了。」岩隈說著,依然笑容滿面。「就我所知,應該在這裡有一年以上了吧。」
「你跟他很熟?」
「聊過天,不過這裡的人不會積極交談啦。」
這話跟昨天晚上脇田說的一樣,看來這種地方有它的江湖規矩。
「都有人被打了,竟然沒幾個人發現,這樣對嗎?通常應該會鬧大吧。」
「大家應該都怕事吧。我跟你說,會在這裡的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可能是被地下錢莊追債,可能有人幹了壞事,當然不會主動去報警。畢竟我們光是待在這裡,就算非法占據公園啦。」
「所以阿澤也幹過什麼壞事?」
「誰知道?」岩隈歪著脖子賣關子:「我跟他真的不算熟。」
「大概幾歲?」
「五十左右吧?可是過這種日子老得快,實際上或許更年輕點。」
「這裡面誰跟阿澤最熟?」
「不知道,我又不是社區管理員,沒那麼清楚,要是清楚我一定配合。」
「我要怎麼聯絡你?」
「我會主動找你。我不覺得警察都是壞蛋,有人打阿澤,當然會幫忙抓出來。」
我拿出名片,岩隈用拇指與食指夾了過去。
「可能有什麼苦衷喔。」岩隈摸摸有點鬍碴的下巴。
「苦衷?」
「應該吧。」岩隈站起身,個子非常小,大概只到我的肩膀,他拍拍腿笑著說:「真要說的話,這裡每個人也都有苦衷,或許我們在你們眼裡都是跟社會脫節,不過也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才落到這個地步來。」
「這我不太清楚。」
「說不定你們也認識阿澤喔。」
「為什麼?」
「如果是以前的案子,應該都有留紀錄吧?不過我說的不是你們刑警,而是公安那邊,他們煩死人了。」
「公安?所以他是極左派?」
「嗯,阿澤感覺不像右翼分子。」
「這些話是真的?」
「冷靜點吧。」岩隈舉起雙手想安撫我:「別太激動,這只是我的感覺,阿澤也沒拿他被逮捕的事情出來炫耀過。」
「你知不知道他來這裡之前過著怎樣的日子?」
「不知道,他也不喜歡提自己的過去,要不要去查查新左翼派系(sect)的案子?說不定能查出他的身分喔。你們加油,可別因為是街友被打就懶得查囉。」
我想反駁,想大聲喊說自己不會歧視立場與生活不同的人,絕對不可能。
但我沒能開口,岩隈似乎是看透我猶豫不決的態度,輕輕揮手之後緩步離去。
(待續)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