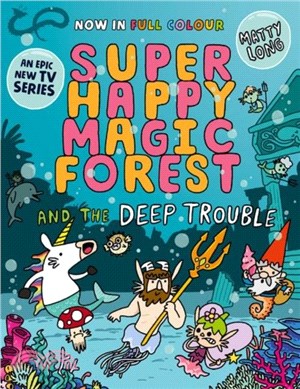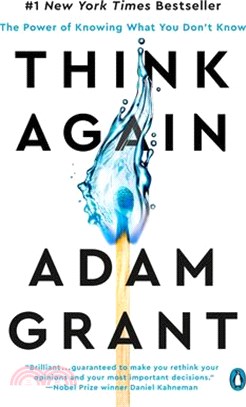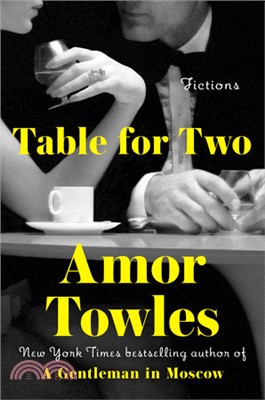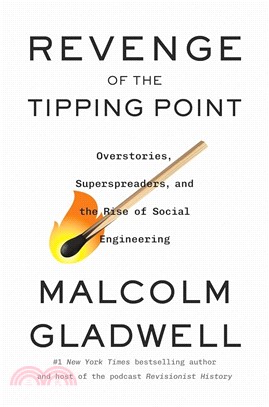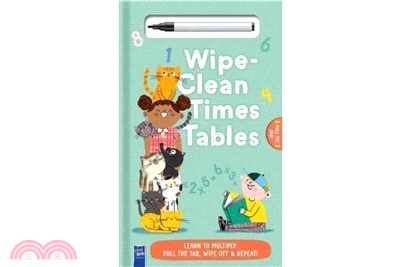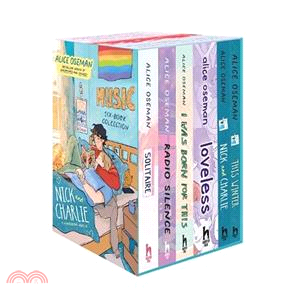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一)1950–1953年,共產黨佔領大陸後,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運動,鬥地主﹑分田地,本人的家庭成份是地主,當時我還是個十歲左右的兒童,我以小孩的感受描述了那幾年間人間發生的殘酷事實。(二)1953–1961年,我重回學校讀書直至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我以當年少年﹑青年和學生的心態描述了我因為家庭出身而受到的不合理歧視,各項政治運動如反右派鬥爭﹑大躍進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等,對教師﹑學生和社會帶來的影響。(三)1961–1964年,六一年我以優異成績完成高中學業(高中二年級時,曾舉行一次全肇慶專區知識質量檢查,各課來次統一考試,本人成績全級第一)。在小學時,老師告訴我,由於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如果我的考試成績和其他學生一般,則我没有機會被(高一級的學校)取錄。一九六一年,是年中共中央召開了蘆山會議,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我連這最後的升學機會也没有了。記得我曾請求學校的共產黨幹部分配工作給我,得到的是粗聲的回答:‘你以為建設社會主義這麼容易,返回郷下耕田去!’連半句安慰的話也不說。我只可返回原籍郷村耕田,但却因為我的家庭出身而遭到完全無理迫害。(四)1964–1971年,那時我開始認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理,意識到只有逃出共產黨的統治範圍,才有將來。六四年四月我逃離了家鄉,流浪於廣州﹑東莞﹑龍門﹑中山﹑三水﹑四會﹑台山等地,其間一合時機便偷渡往香港或澳門,經多次失敗被捕,關進收容所。我將流浪多年所見所聞,在文中描述出來,供有興趣者閱讀。一九七一末,我終於到了香港。
作者簡介
作者的家鄉是廣東省開平縣,記憶中1950年初共產黨的統治已完全進入我的家鄕,我當年還是個兒童。由於我的家庭被定爲「地主成份」,從此我在殘酷的階級鬥爭隂霾下生活和掙扎了近二十一年,直至1971年末,逃出了當年堅持階級鬥爭的共產黨的控制範圍,到達香港,才得到和一般人同等的生存權利。詳情請閱讀「青春之哀歌」,全書其實是我的自傳。
1978年,我當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直至2004年退休。我的太太在香港出生,我們的三名兒女在完成學士或碩士學位後,也進入香港公務員隊伍工作。
1978年,我當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直至2004年退休。我的太太在香港出生,我們的三名兒女在完成學士或碩士學位後,也進入香港公務員隊伍工作。
序
序
我在上世紀七一年到達香港後,於七五年曾想向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移民部要求協助申請移民美國。到香港堅道二號明愛大廈呈交表格時,接見我的女職員要求我補寫第二十七項:到港日期;第二十八項:原因詳述;第二十九項:不願返大陸原因。並將表格交回給我,叫我寫妥後再一併呈交給她。由於最後沒有申請,所以表格連稿件保留至今。我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寫完(在我的原稿,有寫完稿日期),是另紙寫的。將我及我的家庭由一九五零年起的遭
遇,我本人由一九五零年至七一年末在大陸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以寫實的形式寫了下來。後來我因未能找到合適的居住美國的擔保人,打消了申請的念頭。寫好了的稿子也就留了下來。那時我曾想過是否能出版?但由於在大陸生活時,閱讀過一些特工小說使我留下陰影,有點怕大陸的特工會找我(當然,現在看來顧慮是多餘的,因為我亦寫不出什麼重大秘密),所以心大心細。後來我也曾寄信給「讀者文摘」,但沒有回音。我當時亦不懂其他出版的門路。直至去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我和太太往美國探親旅遊,見到我的其中一名外甥的岳丈潘天良先生,他是華文作家,他曾在台北秀威出版了「回聲-潘天良詩文集」,於是他介紹該公司給我,讓我聯絡該公司職員尋求出版途徑。外甥並鼓勵我,如果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甚至有可能已將內容拍了電影,此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我的稿子寫好後只給一名不知名字的女士看過。那是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我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在九龍馬頭圍道與大環道交界處義達工業大廈外旁邊人行路邊擺小販木頭車賣炸魚蛋、辣椒和豆腐,在午餐時間,該大廈某公司的數名年輕女職員幾乎每天來光顧,其中一位年約三十歲略矮小的女士(約五英呎或以下)和我比較談得來,我曾將稿子借了給她閱讀,三丶四日後她仍說未能看完,大約一星期後才交還給我。我現在記得當年應未有影印機。她可能真的是慢慢閱讀,但也可能是抄錄下來。如果是這樣,我寫的內容便可能三十多年前被盜用了,如果是這樣,最不幸的是,我反而被讀者以為是抄襲者。但希望不是這樣。但就算是這樣,其實我寫的是自己的真實自傳,其中出現的人物除了在廣州的有幾個朋友由於某種原因用了假名外,其餘都是真名,我就讀的所有學校,所有老師、同學的名字都是真實的,所有我接觸的人包括共產黨幹部的姓名都是真實。還有,我的原稿還在,今天的科技可驗證是七十年代寫的,甚至在原稿的紙張上,仍可發現上述不知名字的女士的指紋,就算在法庭上,也可證明我是真的。
七十年代我借稿子給上述的女士時,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現在要出版,我才想起並且有些擔心,所以預先向讀者交代一下。為免麻煩,不出版就是了,因為要自己負責出版費用,不會有什麼得益,但我有一種衝動,希望世人知道我當年經歷過的事,特別是我希望我的子孫每人有一本,我的親戚的年長和年幼的一輩也有我寫的書本,知道當年我曾目睹過的事。
張伯強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我在上世紀七一年到達香港後,於七五年曾想向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移民部要求協助申請移民美國。到香港堅道二號明愛大廈呈交表格時,接見我的女職員要求我補寫第二十七項:到港日期;第二十八項:原因詳述;第二十九項:不願返大陸原因。並將表格交回給我,叫我寫妥後再一併呈交給她。由於最後沒有申請,所以表格連稿件保留至今。我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寫完(在我的原稿,有寫完稿日期),是另紙寫的。將我及我的家庭由一九五零年起的遭
遇,我本人由一九五零年至七一年末在大陸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以寫實的形式寫了下來。後來我因未能找到合適的居住美國的擔保人,打消了申請的念頭。寫好了的稿子也就留了下來。那時我曾想過是否能出版?但由於在大陸生活時,閱讀過一些特工小說使我留下陰影,有點怕大陸的特工會找我(當然,現在看來顧慮是多餘的,因為我亦寫不出什麼重大秘密),所以心大心細。後來我也曾寄信給「讀者文摘」,但沒有回音。我當時亦不懂其他出版的門路。直至去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我和太太往美國探親旅遊,見到我的其中一名外甥的岳丈潘天良先生,他是華文作家,他曾在台北秀威出版了「回聲-潘天良詩文集」,於是他介紹該公司給我,讓我聯絡該公司職員尋求出版途徑。外甥並鼓勵我,如果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甚至有可能已將內容拍了電影,此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我的稿子寫好後只給一名不知名字的女士看過。那是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我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在九龍馬頭圍道與大環道交界處義達工業大廈外旁邊人行路邊擺小販木頭車賣炸魚蛋、辣椒和豆腐,在午餐時間,該大廈某公司的數名年輕女職員幾乎每天來光顧,其中一位年約三十歲略矮小的女士(約五英呎或以下)和我比較談得來,我曾將稿子借了給她閱讀,三丶四日後她仍說未能看完,大約一星期後才交還給我。我現在記得當年應未有影印機。她可能真的是慢慢閱讀,但也可能是抄錄下來。如果是這樣,我寫的內容便可能三十多年前被盜用了,如果是這樣,最不幸的是,我反而被讀者以為是抄襲者。但希望不是這樣。但就算是這樣,其實我寫的是自己的真實自傳,其中出現的人物除了在廣州的有幾個朋友由於某種原因用了假名外,其餘都是真名,我就讀的所有學校,所有老師、同學的名字都是真實的,所有我接觸的人包括共產黨幹部的姓名都是真實。還有,我的原稿還在,今天的科技可驗證是七十年代寫的,甚至在原稿的紙張上,仍可發現上述不知名字的女士的指紋,就算在法庭上,也可證明我是真的。
七十年代我借稿子給上述的女士時,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現在要出版,我才想起並且有些擔心,所以預先向讀者交代一下。為免麻煩,不出版就是了,因為要自己負責出版費用,不會有什麼得益,但我有一種衝動,希望世人知道我當年經歷過的事,特別是我希望我的子孫每人有一本,我的親戚的年長和年幼的一輩也有我寫的書本,知道當年我曾目睹過的事。
張伯強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書摘/試閱
(一九五○-一九七一「階級鬥爭」陰霾下的生活紀實)
要解釋我要偷渡來港的原因,必須從我在大陸的經歷說起,才能說個明白。
我的祖居是在廣東省開平縣沙岡鄉高分田村。我家的房子很大,座落在高分田村北閘,是一座西式又兼有唐氣的兩層高的闊大的建築物,有個大花園,園裏有涼亭、水泥建的池塘、人造的石山和許多花木。
父親張培英(又名張秀民),經營內河航業,有「鈞興號」單行輪船,來往梧州、廣州、三埠、澳門各地,另有「利貞」和「利仁」渡等(「渡」是本身沒有動力,靠有動力的小輪拖行的載人貨的大船)。在鄉有田產,除了住屋之外,另有數座屋子。
一九五○年,父親遲遲才從家鄉逃往澳門,從此沒再回鄉(一九六九年初病死於澳門)。跟着兄長們一個個離家他去,不見回來。從大人們的臉上表情看來,我覺得似乎我們的房子被一層層的愁雲慘霧籠罩。家中的人越來越少,往日的熱鬧已不復見。
一九五一年初夏,一天上午我們在廳裏吃早飯,突然電光一閃,隨即聽到巨大的雷聲,其氣浪似乎使整座房子震撼。大亞媽叫我八家姊即上二樓給天神去插香,……。後來才看到,在花園裏的一棵最高的檳榔樹,被那巨雷劈斷了頂部開葉生花的部份,但筆直的樹幹仍然挺立,和房子一樣高。看起來可像一個人被斬了頭,頭垂在胸前,而身軀卻仍站立着。旁邊一棵稍矮一些的檳榔樹卻無恙。
跟隨着這一個兇惡的先兆,人間的災難便接踵而來。農曆五月是鄉人賽龍舟的時節。一天放學回家,見家中多了一些人,那些是所謂族中的叔侄之類,大人們在哭哭啼啼。後來才知道,早些時候共黨派人來通知要「封房子」,大亞媽隨即逃走了,不知所踪(她無親生兒女),二庶母、我母親(四庶母)及二嫂等,怕無人擔頭,和族人商量去找亞媽。那時正值天降暴雨,下個不停。村子北面有座頗大的山,叫梁金山,其山脈縱橫十幾公里,經數小時的暴雨,山洪暴發。她(他)們估計大亞媽會自殺,於是眾人持着燈籠,披着簑衣,往山澗水流較湍急的地方去找人,結果是無功而回。我同胞的二哥、四哥、八家姊都不在家了,我母親和我商量,帶同兩弟去投河自殺。我不想死,表示反對。
數天後,有人來通知暫不「封屋」了。隨後,大亞媽也回來了,原來她逃往娘家。我也無心上學了,我的堂兄弟姊妹也一樣。初冬降臨,花園裏的一切都顯得蕭條。一天黃昏,我看見學校的一群學生仔在花園外高呼口號︰“打倒地主分田地"、“逃亡地主是豺狼"、“窩藏地主是壞人"、“……"然後列隊往村子其他地方去高呼口號。許多事情在發生︰農會派人來我家查點所有的衣物、糧食等,將盛穀米的大容器用封條封口,每十天由農會派人來稱穀給我們吃,每人限四兩米(十六兩為一斤)一餐,將房屋出外的向東向北的三個門口用封條封起,並聲稱如封條破了,格殺勿論,只留向南的一個門口出入,並訂下規矩,每天下午六時要關門,早上民兵來叫門才准開門。每晚六時後,民兵來叫門,叫門時照例用他門手持的木棍、竹枝將鐵皮的窗門亂打一通。門開後,命令所有大人小孩走出門外檢查人數。幾乎每天他們都藉故用木棍、竹枝將大人毆打。他們的藉口很多,如「為甚麼遲遲才開門,一定有陰謀」、「為甚麼見了我們不叫農民老爺?」,有一次,九弟病了,躺在牀上,沒出來。“為甚麼少了一個?病了!?誰說過病了可以不出來?!"於是又將我母親毆打。有時,我往開門,門打開,民兵便用粗竹枝(末端有一個結的)在我頭頂上敲一下,然後哈哈大笑。
冬天。一天夜裏,農會有人來叫大亞媽去東頭村祠堂開會(鬥爭大會)。第二天早晨,民兵吩咐早飯時送飯往神寮(神寮是一座屋子,正月時,村民往附近廟宇將神像接回村,安放在「神寮」,正月「開燈」,也是將燈掛「神寮」內)。送飯自然是我的事了,因八弟、九弟都比我小,大人都害怕。將飯送到「神寮」時,民兵先要檢查籃子裏的東西,並要我先吃一口(大概他們怕我家人將亞媽毒死,便無法追查錢物藏在何處。民兵們初時抱着很大的幻想,以為地主有很大的一座「金山」,他們得到「金山」便可搖身一變而為地主)。大亞媽被關在一房子裏,她告訴我,昨日在祠堂被「鬥爭」。「鬥爭」後被送來此房,綁在房子窗柱上,亞昌嫂(寡婦,後來改嫁農會主席張木榮,又叫木榮嫂,她比木榮大十歲左右,名叫許琼娣)將一桶涼水從窗外倒進來,所有衣服濕透了,叫我回家取衣服來換。
要解釋我要偷渡來港的原因,必須從我在大陸的經歷說起,才能說個明白。
我的祖居是在廣東省開平縣沙岡鄉高分田村。我家的房子很大,座落在高分田村北閘,是一座西式又兼有唐氣的兩層高的闊大的建築物,有個大花園,園裏有涼亭、水泥建的池塘、人造的石山和許多花木。
父親張培英(又名張秀民),經營內河航業,有「鈞興號」單行輪船,來往梧州、廣州、三埠、澳門各地,另有「利貞」和「利仁」渡等(「渡」是本身沒有動力,靠有動力的小輪拖行的載人貨的大船)。在鄉有田產,除了住屋之外,另有數座屋子。
一九五○年,父親遲遲才從家鄉逃往澳門,從此沒再回鄉(一九六九年初病死於澳門)。跟着兄長們一個個離家他去,不見回來。從大人們的臉上表情看來,我覺得似乎我們的房子被一層層的愁雲慘霧籠罩。家中的人越來越少,往日的熱鬧已不復見。
一九五一年初夏,一天上午我們在廳裏吃早飯,突然電光一閃,隨即聽到巨大的雷聲,其氣浪似乎使整座房子震撼。大亞媽叫我八家姊即上二樓給天神去插香,……。後來才看到,在花園裏的一棵最高的檳榔樹,被那巨雷劈斷了頂部開葉生花的部份,但筆直的樹幹仍然挺立,和房子一樣高。看起來可像一個人被斬了頭,頭垂在胸前,而身軀卻仍站立着。旁邊一棵稍矮一些的檳榔樹卻無恙。
跟隨着這一個兇惡的先兆,人間的災難便接踵而來。農曆五月是鄉人賽龍舟的時節。一天放學回家,見家中多了一些人,那些是所謂族中的叔侄之類,大人們在哭哭啼啼。後來才知道,早些時候共黨派人來通知要「封房子」,大亞媽隨即逃走了,不知所踪(她無親生兒女),二庶母、我母親(四庶母)及二嫂等,怕無人擔頭,和族人商量去找亞媽。那時正值天降暴雨,下個不停。村子北面有座頗大的山,叫梁金山,其山脈縱橫十幾公里,經數小時的暴雨,山洪暴發。她(他)們估計大亞媽會自殺,於是眾人持着燈籠,披着簑衣,往山澗水流較湍急的地方去找人,結果是無功而回。我同胞的二哥、四哥、八家姊都不在家了,我母親和我商量,帶同兩弟去投河自殺。我不想死,表示反對。
數天後,有人來通知暫不「封屋」了。隨後,大亞媽也回來了,原來她逃往娘家。我也無心上學了,我的堂兄弟姊妹也一樣。初冬降臨,花園裏的一切都顯得蕭條。一天黃昏,我看見學校的一群學生仔在花園外高呼口號︰“打倒地主分田地"、“逃亡地主是豺狼"、“窩藏地主是壞人"、“……"然後列隊往村子其他地方去高呼口號。許多事情在發生︰農會派人來我家查點所有的衣物、糧食等,將盛穀米的大容器用封條封口,每十天由農會派人來稱穀給我們吃,每人限四兩米(十六兩為一斤)一餐,將房屋出外的向東向北的三個門口用封條封起,並聲稱如封條破了,格殺勿論,只留向南的一個門口出入,並訂下規矩,每天下午六時要關門,早上民兵來叫門才准開門。每晚六時後,民兵來叫門,叫門時照例用他門手持的木棍、竹枝將鐵皮的窗門亂打一通。門開後,命令所有大人小孩走出門外檢查人數。幾乎每天他們都藉故用木棍、竹枝將大人毆打。他們的藉口很多,如「為甚麼遲遲才開門,一定有陰謀」、「為甚麼見了我們不叫農民老爺?」,有一次,九弟病了,躺在牀上,沒出來。“為甚麼少了一個?病了!?誰說過病了可以不出來?!"於是又將我母親毆打。有時,我往開門,門打開,民兵便用粗竹枝(末端有一個結的)在我頭頂上敲一下,然後哈哈大笑。
冬天。一天夜裏,農會有人來叫大亞媽去東頭村祠堂開會(鬥爭大會)。第二天早晨,民兵吩咐早飯時送飯往神寮(神寮是一座屋子,正月時,村民往附近廟宇將神像接回村,安放在「神寮」,正月「開燈」,也是將燈掛「神寮」內)。送飯自然是我的事了,因八弟、九弟都比我小,大人都害怕。將飯送到「神寮」時,民兵先要檢查籃子裏的東西,並要我先吃一口(大概他們怕我家人將亞媽毒死,便無法追查錢物藏在何處。民兵們初時抱着很大的幻想,以為地主有很大的一座「金山」,他們得到「金山」便可搖身一變而為地主)。大亞媽被關在一房子裏,她告訴我,昨日在祠堂被「鬥爭」。「鬥爭」後被送來此房,綁在房子窗柱上,亞昌嫂(寡婦,後來改嫁農會主席張木榮,又叫木榮嫂,她比木榮大十歲左右,名叫許琼娣)將一桶涼水從窗外倒進來,所有衣服濕透了,叫我回家取衣服來換。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