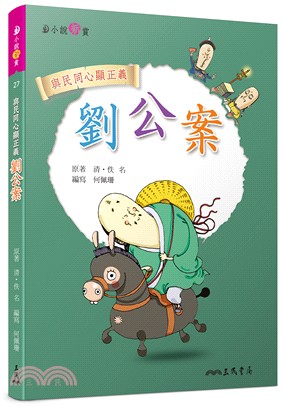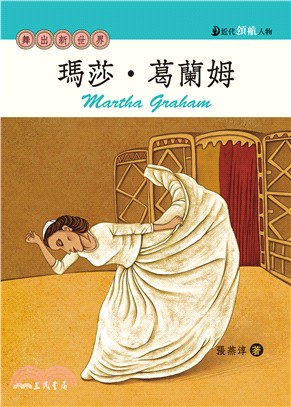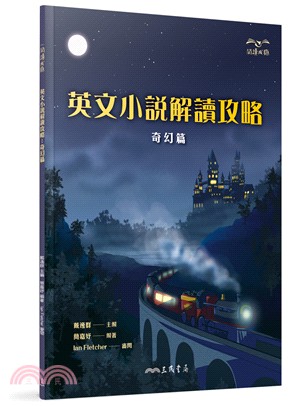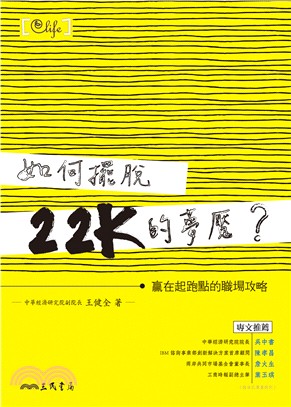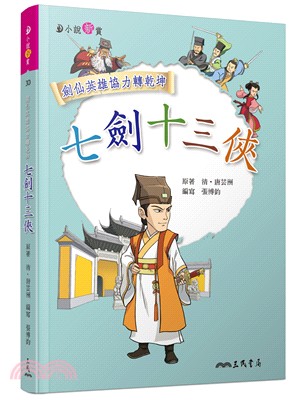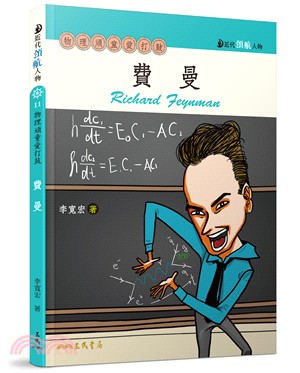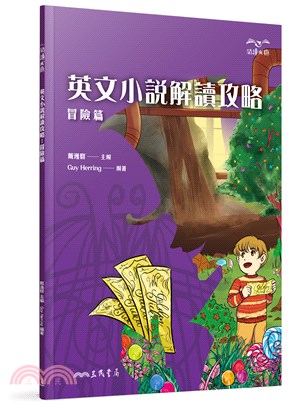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螢火蟲的故事
在作家群體裏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版的趣味數學書。「文革」後全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幹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採用同一種數學試卷)──閒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鬆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衞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麼就讓別人搶在先?
黑板報、油印報、快板詞、小演唱、地方戲⋯⋯捲入這些底層語文活動,純粹是因為自己在「文革」中被拋入鄉村,眼睜睜看着全國大學統統關閉,數理化知識一無所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命運對我的撫慰,也是留給我意外的謀生手段──至少能在縣文化館培訓班裏混個三進兩出,吃幾頓油水稍多的飯。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撓頭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學那裏明白「論點」與「論據」是怎麼回事,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裏明白詞組的「偏正」關係如何不同於「聯合」關係。如果沒有民間流傳的那些「黑書」,我也不可能如夢初醒,知道世界上還有契訶夫和海明威,還有托爾斯泰和雨果,還有那些有趣的文學呵文學,可陪伴我度過油燈下的鄉村長夜。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裏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解凍和復蘇的「新時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時隔多年後的重續,也是歐洲啓蒙主義運動在東土的延時補課,慢了
不過,大時代並非歷史常態,並非一個永無終期的節日。一旦社會改造動力減弱,一旦世界前景藍圖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術革新、思想發明、經濟發展、社會演變、民意要求等因緣條件缺三少四,還缺乏新的足夠積累,沉悶而漫長的「小時代」也許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國產電影正是這樣自我指認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
文學還能做什麼?文學還應該做什麼?一位朋友告訴我,「詩人」眼下已成為罵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詩人!」「你家祖宗八輩子都是詩人!」……這說法不無誇張,玩笑中卻也透出了幾分冷冷的現實。在太多文字產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
坦白地說,一個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時代。同樣坦白地說,「大時代」也許從來都是從「小時代」裏滋生而來,兩者其實很難分割,或者說後者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後者的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不過是懶漢們最標準和最空洞的套話。文學並不是專為節日和盛典準備的,文學在很多時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無人,需要繁瑣甚至乏味的一針一線。哪怕下一輪偉大節日還在遠方,哪怕物質化和利益化的「小時代」正成為現實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們正淪為落伍的手藝人或孤獨的守靈人……那又怎麼樣?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鄉村看到的一幕:當太陽還隱伏在地平線以下,螢火蟲也能發光,劃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線,其微光正因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導人們溫暖的回憶和嚮往。
當不了太陽的人,當一隻螢火蟲也許恰逢其時。
換句話說,本身發不出太多光和熱的傢伙,趁新一輪太陽還未東升的這個大好時機,做一些點點滴滴豈不是躬逢其幸?
這樣也很好。
韓少功
2014年11月
目次
vii 「視野叢書」總序 北島
ix 自序:螢火蟲的故事 韓少功
1 第一部分 少年
45 第二部分 鄉親
99 第三部分 天下
139 第四部分 書卷
195 第五部分 心魂
247 附錄:落花時節讀舊箋
書摘/試閱
第一部分 少年
4
那一天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我去學校查看升學名單的公告,然後在雙槓上閒坐了一會兒,準備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規定不滿16周歲的可繼續升學,父母身邊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兩條都合得上,不必下鄉當知青,被不少同學羨慕。
我似乎還能繼續坐雙槓,投射紙飛機,在上學的路上盤帶小石塊,去學校後門外的小店裏吃米粉,把酸辣湯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時回不去,便在大樓裏閒逛。這時候的學校都成了旅客散盡的站台,一本本沒有字迹的白頁書。全國大亂結束了,中學生幾乎都被趕下鄉去。到處空空蕩蕩,在走廊裏咳嗽一聲竟然回聲四起,讓人禁不住心裏發毛。白牆上到處是紅衞兵的標語殘痕。窗戶玻璃在武鬥的石塊和槍彈下所剩無幾。樓梯上的一個大窟窿標記出這裏曾為戰場──不久前的那一次,一個冒失鬼出於派爭之恨,覺得自己沒罵贏,打架也沒佔上風,居然把一個手榴彈扔上教學樓。幸虧當時周圍沒人,只是把幾塊樓板炸塌了,嚇出了樓板下一窩逃命的老鼠。
我推開202房,我們不久前的紅衞兵司令部,但這裏已沒有大旗橫挑在窗外,沒有我熟悉的鋼板、蠟紙、油印機、糨糊桶,只剩下幾張蒙塵的桌椅,完全是匪軍潰逃後的一片狼藉。「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不知是誰臨走前在牆上塗抹下這樣的筆墨悲壯。忍不住,我又習慣性地走進208、209、311……門吱吱呀呀地開了,但這些地方更冷清,一張床是空的,另一張床是空的,另一張床還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結束一切。破窗紙在風中叭叭響。
我踢到了一個空紙盒,呼吸到夥伴們的氣息,包括女孩子們身上似香若甜的氣息──那些喜歡做鬼臉和發尖聲的姐們。
親愛的,我被你們拋棄了。
我有一種充滿了風聲和雨聲的痛感,於是回家寫詩,寫下了一些誇張的句子,決定放棄自己的升學。
是那山谷的風,
吹動了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們的帳篷……
這是當時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對遠方的想像,幾乎就是由這一類作品逐漸打造成形。遠方是什麼?遠方是手風琴聲中飄忽的草原,是油畫框中的墾荒者夕陽下歸來,是篝火與帳篷的鏡頭特寫,是雕塑般的人體側影,是慢鏡頭搖出的地平線,是高位旋轉拍攝下的兩隻白鷗滑飛,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機時的憂傷遠望……哦憂傷,憂傷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憂傷簡直就是青銅色的輝煌。
相比之下,繼續上學還有什麼意思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語課只會教這一類政治口號,笑死人了。代數課呢,不是算糧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糞一元方程,明天是豬糞二元方程,已經算得教室裏糞味彌漫。學生們都驚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揣上介紹信和戶口材料,跟隨軍哥一同乘火車,再轉汽車,再轉馬車,在路上昏昏沉沉顛了兩天多,在嘩嘩急退的風景裏心潮起伏。我們一路上同縣招待所裏的廚師吵過架,同另一夥知青下過館子和看過電影,直到那個傍晚才抵達白馬湖──山坡上的兩排土平房。我把一口木箱和一個被包砸在這裏,未見歡迎儀式(幾天前已經開過了),未見朋友們前來激情地跳躍和擁抱(他們早來十幾天,已累得無精打采),更沒見到旅遊營地的手風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鉢冷飯堵得胸口冰涼。也許是淘米時太馬虎,飯裏夾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沒有菜,只有蓋在飯上的幾顆鹹黃豆,讓我目瞪口呆,東張西望,無法下咽。更嚴重的情況還在後面。睡覺的土房裏油燈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牆還潮乎乎的透水。木欄窗只蒙了一塊塑料布,被風鼓成了風帆狀,叭啦叭啦的隨風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縫裏就零星飄入小雪,以至帳頂上擋雪的一塊油布不堪其重,半夜裏被積雪壓垮了,嚇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來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來緊急救災。
還不到第二天挑湖泥,我就已經後悔不迭了,明白農村戶口是怎麼回事了。
──摘自長篇小說《日夜書》(2013)
5
手掌皮膚撕裂的那一刻,過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轟的一下閃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墾荒,把耙頭齒和鋤頭口磨鈍了,磨短了,於是不但鐵匠們叮叮噹噹忙個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時半刻,在石階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鐵之聲在整個工區此起彼伏響徹夜天。
那是連鋼鐵都在迅速銷熔的一段歲月,但皮肉比鋼鐵更經久耐用。耙頭挖傷的,鋤頭扎傷的,茅草割傷的,石片劃傷的,毒蟲咬傷的⋯⋯每個人的腿上都有各種血痂,老傷叠上新傷。但衣着襤褸的青年早已習慣。朝傷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處理。我們甚至不會在意傷口,因為流血已經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膚早就在神經反應之外。我們的心身還可一分為二:夜色中挑擔回家的時候,一邊是大腦已經呼呼入睡,一邊是身子還在自動前行,靠着腳趾碰觸路邊的青草,雙腳能自動找回青草之間的路面,如同一具無魂的遊屍。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溝裏去的時候,一聲大叫,意識才會在水溝裏猛醒,發覺眼前的草叢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發現自己兩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個晚上自己是怎麼入睡的,不知道蚊帳忘了放下的情況之下,蚊群怎麼就沒有把自己咬醒。還有一天,我吃着吃着,突然發現面前的飯鉢已經空了四個,這就是說,半斤一鉢的米飯,我已經往肚子一共塞下了兩斤,可褲帶以下的那個位置還是空空,兩斤米不知填塞了哪個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記了這樣的日子,一種身體各個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摘自長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6
人們在工地上經常談到吃。吃的對象、方法、場景、過程、體會一次次進入眾人七嘴八舌的記憶總複習。不,應該說在剛吃過飯的一段,比如上午10點以前,腸胃還有所着落和依附,人們還是可以談一些高雅話題,照顧一下上層建築,比如知青們背記全世界的國名,背記圓周率或平方表,背記一些電影裏的經典台詞⋯⋯來自《列寧在十月》《南征北戰》《賣花姑娘》《廣闊的地平線》什麼的。但到了腹中漸空之時,「看在黨國的分上」一類不好笑了,「讓列寧同志先走」一類也不好玩了,腸胃開始主宰思維。從北京湯包到陝西泡饃,從廣州河粉到北京烤鴨⋯⋯知青們談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覺經驗,包括紅衞兵大串聯時見識過的各地美食。關於「什麼時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識,肯定不是什麼大雪天躲在被窩裏,不是什麼內急時搶到了廁位,而是餓得眼珠子發綠時一口咬個豬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槍斃也值呵。
這一天,爭奪飯票的豪賭又一次展開,姚大甲賭我不敢吃死人骨頭──他是指身邊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剛才開荒時刨出來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覺得陰氣襲人,污濁發霉,有一種鹹魚味,但我嘴上還得硬。「十張飯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腦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賭二十張!」
「我今天沒興趣……」
「二十五!」
其他人覺得有戲可看了,圍上前來,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評點或挑唆,使大甲更為得意地把賭注一再加碼。30,35,40,45,最後漲停在50──如此驚心動魄的豪賭已讓我呼吸粗重。50是什麼意思?50就是50鉢白花花米飯,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時的暈眩,你大快朵頤時的陶醉,還有撫摸肚皮時的腦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裏,你活得出人頭地,光彩照人,活脫脫就是當今皇上,不必再對食堂裏的曹麻子諂笑,讓他的鐵勺給你多抖落幾顆黃豆;也不必捶打鄰居的房門,對屋內的豬油味賊心不死抓肝撓肺;更不必為了爭搶一個生蘿蔔,與這個或那個鬥出一身汗。
生死抉擇,成王敗寇,翻身農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嗎?我抹了一把臉,大聲說:「有什麼了不起?飯票拿來!」
他們被鎮住了,好一陣沉默。
我清點飯票,確認賭資無誤,然後旋旋腰,壓壓腿,捏一捏喉籠,咧一咧牙口,把自己當做出場前的運動員。我閉上眼,想一想捨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捨身堵槍眼的英雄,過一遍電影裏諸多動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準備。最後,我用衣角細細拭去一片骨頭上的霉污泥迹,兩眼緊閉,大喊了一聲:
「毛主席萬歲──」
一次深呼吸之後,我哢哧哢哧地大嚼猛咬,沒覺出就義是什麼味,也不敢去想就義是什麼味,直到胃裏突然一陣惡湧,眼看就要湧上口腔,像高壓水槍一樣把嘴裏的骨渣噴射出去,這才拔腿狂奔,竄到附近的小溪旁一頭撲下去,在那裏拼命嘔吐和洗漱──逃竄前當然沒忘記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飯票。
晚上,隊長買豬娃回來了,聽說此事,覺得問題嚴重而且形勢危急,立即把全隊人召集在地坪,沒顧得點上一盞油燈,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裏開罵:「連先人都不放過呵?什麼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裏生疔?就不怕爛腸子爛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後生個娃仔沒屁眼?」
黑暗中的責罵聲在繼續:「你看你,長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歲了,還像隻三腳貓,不上正版!」
這也太誇張了吧?一口氣滑出七八個數,鉚足了勁給我拔苗助長,怎麼不一口氣把我拔成一個老前輩?其他農民興高采烈,會後一再點頭哈腰笑臉逢迎,爭相找我借飯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聽:那骨頭到底是什麼味?是不是有點酸?是不是有點鹹或者澀?年紀稍長的幾個,問過以後還心重,還嘟囔,看我的目光不無異樣。我喝過水的杯子,他們決不再沾。我用過的臉盆,他們決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個老頭從噩夢中驚醒,大喊大叫,滿頭大汗,找到梁隊長強烈要求換房,說他情願睡牛欄,也不同啃屍鬼同住一窩。
──摘自長篇小說《日夜書》(2013)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無庫存之港版書籍,將需向海外調貨,平均作業時間約3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縮短等待時間,建議您將港書與一般繁體書籍分開下單,以獲得最快的取貨速度。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