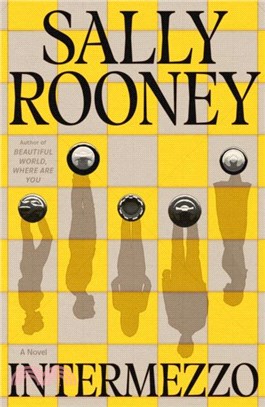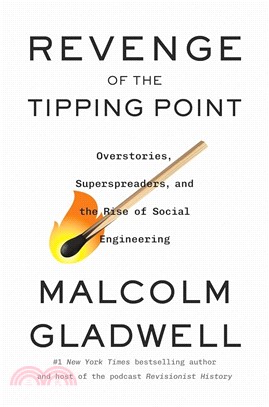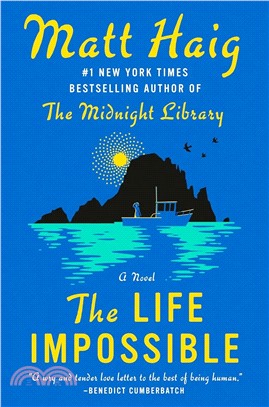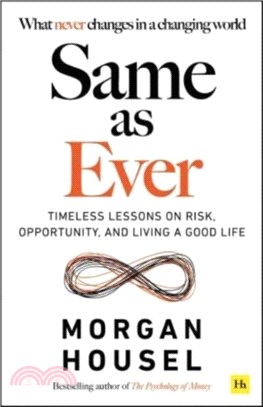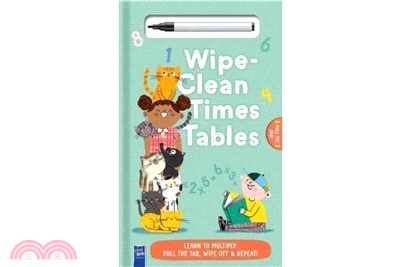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ISBN13:9789863501350
替代書名:The Aesthe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actical Writings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柯慶明
出版日:2016/03/01
裝訂/頁數:平裝/424頁
規格:23cm*17cm*2.7cm (高/寬/厚)
版次:初版
適性閱讀分級:832【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本書以前所未見的宏大視野,直指中國古典實用文類蘊含的美感特質;
照見了中國文學傳統中,不容忽略的半壁江山!
本書集中討論「古典中國實用文類」,正面迎向「文學」這個現代觀念的挑戰,可謂前所未見之創舉。本書作者柯慶明教授為臺灣中文學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中學根底深厚之外,更熟稔於現當代文學美學以及西方文學理論。本書是柯教授個人學術研究又一高峰,也顯現臺灣中文學界推陳出新的動力。
本書質疑近世僅以具有想像、虛構性質的詩歌、小說、戲劇為「文學」的妥適性,因而自古典的實用文類:「論」、「說」、「序」、「跋」、「書」、「箋」、「表」、「奏」、「弔」、「祭」、「碑」、「銘」、「傳」、「狀」、遊覽「記」、山水「記」、修造「記」與器物「記」,探討其文類規約,在實用目的外,仍然涵具特殊的美感潛能與性情表現,深具生命觀照、反映命運情境等特質。既參酌傳統與現代文類理論的認知,亦舉實際的名作為例,論證其所以引發讀者的文學興味,在發情止禮中,深察人性,諦觀人類的特殊而共同之命運:一方面主張推擴「文學」之界義;一方面藉此亦選樣的析論了古典實用文類之代表名作,指出它們不容忽視的美感、情感及智慧等意涵和價值,以補一般「文學史」之不足。以精闢細緻的方式解剖詮釋,讓理論演縯有具體例證支援。作者既深於古典傳統,又別具文學心眼,議論通暢而不板滯,極能啟迪思考。
作者簡介
柯慶明
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中文系名譽教授,曾任臺大出版中心主任、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副院長。《現代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雜誌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同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文學美綜論》、《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中國文學的美感》、《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柯慶明論文學》等文學論著,以及詩集《清唱》、散文集《出發》、《靜思手札》、《省思札記》、《昔往的輝光》。日記《2009/柯慶明:生活與書寫》等。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推薦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王聰威(小說家、聯合文學總編輯)
白先勇(文學家、臺大講座教授)
李隆獻(臺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初安民(印刻文學總編輯)
林文月(臺大中文系榮譽教授)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
胡曉真(中研院研究員兼文哲所所長)
唐 捐(詩人、臺大中文系副教授)
梅家玲(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
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座教授)
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兼所長)
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教授)
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
楊泮池(臺灣大學校長)
楊富閔(作家)
葉國良(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
聯合推薦
序
導言
晚清以降,整個東亞、華夏文明,以吸收效仿西歐、北美為務,積漸成習,我們漸漸忽略了「文學」與「Literature」不但分屬兩種語言系統,而且是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產物。當西方人逐漸以Poetry、Fiction、Drama為Literature的指涉物時,我們亦理所當然地以為:文學指的就是詩歌、小說、與戲劇,它們不但是特殊的語言形式所構成的文體,而且必須是想像、虛構、純粹為了美感需要而創作的產物。從康德以降,我們或者以為美感只是形式,或者以為美感與實用的作為不相容。
因而中國文學的領域,就不知不覺遭到大幅的刪汰。於是中國文學就僅限於《詩經》、《楚辭》以降的詩、賦與志怪、傳奇等以下的小說,然後是宋元才開始的戲曲,但是《莊子》、《史記》等相關著作,則自然排除在外,推給哲學與歷史等領域。這是利用別人的系統,作自家的系譜時,必然會有的張冠李戴、削足適履的現象。於是《昭明文選》裡的泰半作品,除了詩賦之外,都成了行迹可疑的存在;更別提漢唐以降,眾多的古文寫作了。
研究「文學史」,最大的困難,在不僅是中外的異類文化下,大家並沒有共通的文類區分與使用規範;即使以古今而論,歷代的文體、文類亦迭有變遷。漢魏六朝以降的古詩,迥異《詩經》、《楚辭》之作,而唐宋以後方有詞、元明以後乃有曲,其體製、美學型態各不相同,勉強求同,了無益處;不妨先以同情的瞭解,各順其異,來加以接受、加以欣賞。同樣的,《昭明文選》以降的古典實用文類亦有許多篇章,傳統社會皆以「文」視之。正如西方並無所謂「以軟筆寫硬字」的書法,我們就得否定書法是一種藝術一樣?我們不妨重新面對這類作品,探索其作為各別「文類」是否有其美感特質,使得古人以其為美「文」,而我們亦不妨考慮,重新將它們納為「文學」之一部分。
由此一念,由「論」「說」開始,我連續九年的國科會研究計畫都以相關的兩個次文類為題材,探討它們作為「文學類型」的美感特質:真正的意圖是,綜集成冊,或許可以提出一種「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但在教學與行政雙忙的情形下,進展甚為緩慢,而倏忽已屆退休之齡。原以為退休後可以整理改寫成書,但又接了一個臺大「新百家學堂」計畫,加以教學仍未終止,因而四年已過,仍然全無進展。後來想功成未必得在我,僅止此類嘗試,或許亦可號召有志的學者,在踵事增華中,發展為完整的體系,作更為博大精深的呈現。因而本書雖名「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其實比較合宜的說法,應該還得加上「論集」二字;但書名早已過長,就姑存原先構想的書名,既為了簡便,也為了存留自己的原初用心。書中各篇的分析,選文重在知名之外,亦在凸顯類型,以此喻示其種種的可能性。綜集而觀,則略可顯現我對此一文學傳統之各種名文、美文的擇取。
少時立志遍讀中國文學名著,結果志大才疏,涉獵仍然有限。但是文中討論所及的各種篇章亦可略示,多年來浸潤其中的喜悅!
野人獻曝,曝在野人之外,亦非野人所有。野人所獻,終究只是自家體驗的喜悅罷了。惟願有心的讀者自可於冬陽之曝中,各有更深、更廣的體會也!
目次
導言
第一章 「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中古文論的見解
三、《文選》諸「論」類文章的美感分析
四、考察中古文學的暫行結論
五、近古文論的再思
六、近古文學的表現
七、綜合的結論
第二章 「序」「跋」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序」「跋」的傳統理解
三、「小序」、「大序」的寫作方向
四、史傳中的「序」與「序」中的歷史
五、「自序」與「宴集序」的自我介入
六、「餞別序」、「贈序」與「別集序」的人際互動
七、結語:〈金石錄後序〉的特殊型態
第三章 「書」「箋」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書」「箋」的傳統理解
三、「書」「箋」文類的基本寫作特質
四、「書」「箋」的「戲劇性」、「敘事性」美感類型
五、「書」「箋」的「抒情性」、「描寫性」美感類型
六、結語
第四章 「表」「奏」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表」「奏」的傳統理解
三、命運的鑑戒與貞定
四、存亡承繼危機的勸諫
五、用世之心與讓謝之辭
六、對「他者」的祟揚彈抑
七、對帝王本身的規諫
八、另類的「表」作
九、結語
第五章 「弔」「祭」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弔」「祭」的傳統理解
三、幼弱與英年:「哀」的興感動力
四、困境與抉擇:「弔」的倫理反思
五、無名與有名:「祭」的類型I
六、師友與親屬:「祭」的類型II
七、神物與自身:「祭」的類型III
八、結語
第六章 「碑」「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傳人昭德的「碑」「銘」
三、敘事紀功的「碑」「銘」
四、序地弘道的「碑」「銘」
五、刻石以外的「銘」文
六、結語
第七章 「傳」「狀」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傳」「狀」的傳統理解
三、史傳表現的諸種面向
四、私傳寫作的諸種類型
五、結語
第八章 遊覽「記」與山水「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從遊覽「記」到山水「記」
三、山水「記」與遊覽「記」的界限與表現
四、山水「記」與世情的辯證
五、遊覽「記」中的遊覽美學
六、結語
第九章 修造「記」與器物「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
一、前言
二、對「記」的傳統理解
三、修造「記」的基本寫作特質
四、器物「記」的基本性質
五、結語
總結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摘錄)
一、前言
論說文是不是一種「文學」的類型?假如說:「是」,那麼還有什麼「文體」或「文類」,可以不算是「文學」?因為所有科學的研究報告、政治的辯論勸說,正都可以歸類於此。我們明明看到它顯然與詩歌、戲劇、小說等這類,一方面是外在具有各別特殊的寫作形式,一方面是內容與皆具抒情、想像性質的文體,截然不同!論說文,憑什麼可以和它們放在一起歸為「文學」的同類?
近乎同樣的思維,亦可由Cleanth Brooks、John Thibaut Purser、Robert Penn Warren所編撰之著名的文學入門教本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其一九六四年的第四版上,除了Fiction、Poetry、Drama之外,還選入了包括:The Personal Essay、The Essay of Idea and Opinion、The Critical Essay、Biography 等類的Discursive Prose一項;但在後來修訂的版本卻給刪去了。其他同類的著作甚多,但也都不約而同的,只選介小說、詩、戲劇,而散文不與焉,遑論論說文!
不管這樣的發展是否妥當,畢竟散文是「非文學」的書寫亦在使用的文體形式;而論說文的日常應用又總是與現實上的目的關係緊密,我們確實得探察:以說理為主的「論」「說」文,為什麼可以因其所俱的美感性質,而可以當作「文章」或「文學作品」來欣賞?那都是屬於何種美感特質?出於何種修辭或表現策略?也許透過歷代文論與重要選本的細密考察,我們可以獲得若干線索。由於篇幅的限制,目前先只就中古與近古文學的現象,加以考察。
二、中古文論的見解
(一)曹丕《典論.論文》
曹丕也許是最早注意到文體的美感規範顯然有別的評論家,因而他強調:「文本同而末異」,並且作了以下的說明: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雖然他論述的重點,原在強調才性有偏:「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但卻已經提供給我們最早的文體區劃以及相關之美感要求的一個藍圖,後來更加細密的劃分與規定,大體都是由此繁衍,踵事增華而成。
其中和我們論旨相關的是:首先他強調,一切的「書寫」,也就是他所謂的「文」,都因為它們特定的目的與功能,而有一定的美感規範上的要求,也就是各有其「宜」、「尚」或「欲」;而其中僅「詩賦」是純粹以美感為目的,「欲麗」的文體,也就是相當於後世狹義或純粹的「文學」或「美文」的文體。
至於其他的三科,雖然未必以美感欣賞為寫作的主要目的(因為另有其他的目的,如「奏議」、「書論」,原是屬於他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以「經國」為主要目標的寫作;而「銘誄」則正是他所謂的:「不朽之盛事」的一種近於「良史之辭」的文章),但是它們仍是有其特殊的美感特質,即:「宜雅」、「宜理」、「尚實」等文體風格上的要求。以「尚實」而論,正如今日我們仍然要求「新聞報導」不可等於「小說寫作」:這裡所牽涉到的不僅是可否「虛構」或「虛美」的問題;更是行文可否「藝增」、「夸飾」的問題,因而在「詩賦」則可的修辭表現(雖然「銘誄」原來亦同樣具有整齊排比的外在形式),在「銘誄」則未必適當。其次,是「書論」歸為一類,由「唯幹著論,成一家言」,以及其〈與吳質書〉中所謂:「而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裴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對照看來,所謂「著書」,其實正是「著論」,只是其篇數眾多,能「成一家之言」而已。所以,曹丕不但「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而且「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這都顯示了曹丕與其同代人,對於「論」的重視與對於所謂「著書」的瞭解。
由所謂:「集諸儒……,講論大義」,我們亦可窺見其所謂「書論宜理」的涵義,一方面誠如他自謂「文人相輕」,「斯不自見之患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雖曰「論文」,其實更在「說理」,其所講論的,甚至還可以視為就是為人論事之「義理」。一方面,由他評論「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的說法看來,「持論」的重點,正在「理能勝辭」;或至少「辭理相稱」;而且其文辭風格必須是嚴肅的(不可「雜以嘲戲」);甚至必須如徐幹「著論」的「辭義典雅」。曹丕的敘述雖然簡略,但已對於「論」的文辭風格有了初步的規範。
(二)陸機〈文賦〉
在《典論.論文》之後,陸機的〈文賦〉雖然重點在「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但還是對各種文體的美感性質作了比較細密的描述與規定: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
陸機並在這段話之下,作了「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的概括。陸機的文體分類,顯然更為細密,事實上不但對曹丕所未加區分的「詩賦」、「銘誄」兩科,作了區別,並且在曹丕的「銘誄」一科,分出了「碑」、「箴」,在「詩賦」一科分出了「頌」;另一方面則是將「書論」與「奏議」分別為「論」、「奏」、「說」,到了劉勰《文心雕龍》就將「論說」歸為一類,遂為後世「論說文」概念之濫觴。
在上述的區分與規範之前,陸機一方面指出:「體有萬殊,物無一量」;一方面亦強調了:「辭呈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因而他對各種文體的美感規範,其實是從「辭」與「意」兩面同時加以形容的。例如:「詩」就「意」而言是「緣情」;就「辭」而言,是「綺靡」。「賦」就「意」而言是「體物」;就「辭」而言,是「瀏亮」。因而,在陸機看來:「論」的特質,就「意」而言是「精微」,就「辭」而言是「朗暢」;而「說」的特質,就「意」而言是「譎誑」,就「辭」而言,則是「煒曄」。
關於「論」、「說」這兩則,李善《文選注》的解釋是:「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說以感動為先,故煒曄譎誑」。而劉熙載《藝概.文概》則對「論」獨有發揮: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弊且不可勝言也。
不論是李善的「以當為宗」,或者是劉熙載的「惟其是」,其實發揮的反而都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主張,強調的反而都是一種客觀持平的認知的達成。因而都有意強調其文辭的表現必須有所節制,只要「明白通暢」(「朗暢」)就好。事實上摯虞《文章流別論》亦有「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的說法。陸機亦非不重視「理」,由他在概括各體所必須遵守之準繩的「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看來,我們毋寧說他將「辭達理舉」,當成了一切文體的必要準繩,因而他對「文」之寫作的基本描述是:「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如同劉熙載所發揮的:
〈文賦〉:「意司契而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之無窮也。
陸機所持的是一種「尚意」的文論;事實上他在《文賦》的中心思維,誠如他在序中所謂的「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其實一直是一個「意稱物」,「文逮意」的兩面而一體的問題。而「理扶質而立幹」的「理」,正是「意稱物」,近於《莊子.知北遊》所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就是一種對於「天地之(大)美」、「萬物之(成)理」的「原」與「達」,而能在「情瞳矓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之際,了然於胸,以成其與「理」相稱之「意」(故謂之「質」),然後才進入「文逮意」,也就是,「辭呈才以效伎」、「文垂條以結繁」的一面。
因此《文賦》的立場,不僅是「尚意」而已;正如「要辭達而理舉」一語所示,其要正在「文逮意」的「辭達」與「意稱物」的「理舉」。所以說陸機「尚意」固然不錯,但說他尚「辭(達)」、尚「理(舉)」,可能更近事實。因而《文賦》中不斷出現,像:「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或寄辭於瘁音」、「或遺理以存異」、「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等等以「辭」「理」並舉的論述。這種「理」貫一切文體「區分」而為其表現之「內容」的基礎想法,其實已經預示了劉勰「原道」所取的玄學立場;因而在陸機的思想裡,「理」反而不只為「書論」一體所專屬。
因而,陸機對「論」之文體的美感規約,其實不僅「當」、「是」於「理」而已。我們反而應該從「精微」與「朗暢」所具的近乎矛盾的統一或綜合來加以考量,也就是我們平素所謂「言淺意深」或「言近旨遠」之類的說法來加以理解。也就是其「意」當達致「萬物有成理」,「物」的「精微」之「理」;也就是《莊子.秋水》所謂「夫精,小之微也」與「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的瞭解上,以「意之所能察致」而達到「言之所能論」,斯是為「論」。深入淺出,以明白曉暢的話語,表達深奧微妙的意理,才是陸機心目中,關於「論」的文體要求。至於蕭統《文選.序》所謂的:「論則析理精微」,初看似乎是綜合了曹丕與陸機兩人的說法,對於陸機而言,反而只是偏向了「意」的一面的規範,完全忽略了「辭」的一面。
「論」「說」雖在後世漸有合流之勢,但在陸機的觀念裡,卻是涇渭分明的。「論」以見理「精微」為主;「說」,則誠如李善所注,以「感動為先」,其實重在罕譬而喻,往往出以寓言與滑稽,因而陸機以為其文體特質,即具「譎誑」的意想。陸機在這裡顯然是沿用了《毛詩.序》所謂「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的「譎諫」的觀念。
但是,劉勰一方面是未曾注意到「譎誑」原是一種作為美學意義上的文體風格的描述;一方面亦疏忽了陸機在各體規範之上的一致準繩,除了「要辭達而理舉」之外,更先提到了「亦禁邪而制放」的要求。因而雖然完全瞭解在專制時代,任何遊「說」,終得「煩情入機,動言中務」,才能「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卻終不免要從道德或倫理的角度,來理解「譎誑」,而要強調: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雖然劉勰的心目中,仍是以「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的《戰國策》作為「說」體的歷史主流,但他終究只如劉向所謂:「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以儒家道德政治的立場來加以批判;反而無法像劉向能夠同時從「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的角度,來加以欣
賞。
但是,假如我們從「煒曄譎誑」的遊「說」風格切入,則「說」之一體,在歷史上未必僅限於《戰國策》的著錄,其實孟子的泰山北海之說、齊人妻妾之事,固亦合拍,而莊子的鯤鵬化徙之言、夢蝶捕蟬之喻,更是此中翹楚。《莊子.天下》形容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以至:「其書雖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豈非「譎誑」、「煒曄」的最佳寫照?其實陸機「說煒曄而譎誑」,正有對於寓言、滑稽之類,具「意在言外」,且必須「得意忘言」,方為得之的文辭風格與文體性質的深切認識。
這種文體風格,後來我們亦可以在韓、柳的〈雜說〉、〈天說〉之類的作品中見到承續與傳揚。
(三)劉勰《文心雕龍.論說》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論說〉一篇的篇幅來處理這兩類的文體,自然是有關它們最重要的理論著作與歷史評述。他雖然一本其「宗經」的立場,開篇即稱:「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但他「詳觀論體,條流多品」,主要包括:「陳政」、「釋經」、「辨史」、「銓文」等四種方向;而可以該括:「議」、「說」、「傳」、「注」、「贊」、「評」、「序」、「引」,「八名區分,一揆宗論」。事實上他以其「理形於言,敘理成論」的思維來貫串各類文體,而得出「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的基本定義,並且加以引申,以為: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曲論哉!
劉勰身當南朝,已熟知魏晉以降的校練名理,以至清談玄風,是以他在「論」體的「選文以定篇」上,首列《莊子》:「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終於「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因而雖有「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的理想,所敘各篇,若從論述內容來看,反而,如他所述:「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只在發揮儒道兩家思想,或者玄談的義理了。因而,至少在「論」這一體的論述上,顯然還是站在一般「書寫」的立場,未必就是從「文」(「文章」或「文學」)的角度著眼。
因而他所作的風格規約,就只有「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反而是強調了近乎「意稱物」、「文逮意」的普遍原理:「必使心與理合」,「辭共心密」。而他對「論」的深入於表象之內裡的分析性質,則是首見強調「窮于有數,追于無形」,「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但他還是從儒家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的立場,反對「越理而橫斷」、「反義而取通」的「曲論」,其重點似乎又回到了曹丕的「書論宜理」。因而,「圓通」為貴;「巧文」知妄。
他以為「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的說法,自是李善注所謂:「論以評議臧否」之說法的源頭。但是以「辨正然否」為「論」的根本,則「論」就趨向了批判性,而非建構性的思維;探討的恐怕就不是普遍而先驗之「理」,而終歸只是就經驗中特殊的「萬事」加以「權衡」,對既有之「百慮」施以「筌蹄」,而設法在後設的層次上,求「通天下之志」,「齊」顯然參差的「物論」罷了。所以「義貴圓通」(這與「得當為宗」顯然不同)就成了他的理想;一但細加辨析,他的立場與理解,似乎又較曹丕、陸機為窄了。
劉勰在「若夫注釋為詞」上,雖然明白指出其「解散論體,雜文雖異」,在文體結構上,顯然有別;但卻仍從「理形於言,敘理成論」的基本性質上,強調「總會是同」,而提出了「要約明暢,可為式矣」的文體風格上的要求。所謂「明暢」其實就是陸機所謂的「朗暢」;至於「要約」,當然來自注釋的要求,但亦不妨視為是「辭忌枝碎」的正面說法。因此,劉勰雖然對「論」體作了詳密的考察,但在基本的見解上,並未超出前人多少。
(四)蕭統《文選.序》
跟我們的論旨相關,而作出重大突破的反而是蕭統的《文選.序》。在這篇序文中,就各文體加以敘述或規約的部分,如前所述,「論則析理精微」,還是在曹丕與陸機的籠罩之下,有意味的是他明白指出了「析理」,強調了「論」的分析性質與過程。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在編選《文選》之際,所採取的將「詞人才子」「飛文染翰」的「篇什」之「文」(「文章」或「文學」)「雜而集之」的立場。〈序〉中首先解釋了不加選錄經部之類著作的緣由: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翦截。
「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其實正是《文心雕龍.宗經》所謂:「經也者,恆久之至道」,「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洞性靈之奧區」的意思。至於「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則是《文心雕龍.宗經》所謂:「制人紀」,「不刊之鴻教也」的意思。
但蕭統等人,並未如劉勰採「宗經」而以為一切文體皆源出五經,並為其所籠罩的立場: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詺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他們毋寧是採文學演變進化的立場:
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因此與劉勰相信「經也者」,「極文章之骨髓者也」大相逕庭的,蕭統只視為乃姬孔傳述之書籍,而且僅只承認它們在人倫實踐上的指導價值,而未從「文章」上加以肯定。
同樣從「文章」的角度,加以略去的還有諸子與遊說之作。前者,他強調:
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這裡他將這些應該以其思想的性質來加以對待的著作,稱之為「以立意為宗」的作品(這裡正與《文心雕龍》之觀點顯然不同,《文心雕龍》不但「宗經」,而且列入「諸子」,同時就「論」而言,亦更注重其思想性,顯然不同),明顯與「以能文為本」的「文章」加以區別。
於是,就從陸機「意稱物」的「理舉」與「文逮意」的「辭達」等兩個層次之外,另外加上了「辭呈才以效伎」、「期窮形而盡相」的「詞人才子」,「飛文染翰」之「能文」的藝術性表現的又一層次。因而,從藝術性表現上的「能文」和僅只「立意」的「辭達」之間,就有了明顯的區劃。這也是他在強調一己泛覽七代「文章」之際:「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特用「文囿」、「辭林」來表述的緣故。
正因蕭統等人的心目中,「文」必須是具藝術表現性的「篇章」,所以,種種的「言談」、「說」辭:「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雖然具「冰釋泉涌,金相玉振」的美感素質,而且「事美一時,語流千載」,且「雖傳之簡牘」,已見文字之著錄(也就轉化為「文字」了),但卻仍堅持它們「事異篇章」,故而「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另外,對於歷史著作,亦強調它們與具藝術表現性的「文章」有別:「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因而不加選錄。若從蕭統不選經、子、史三部著作的敘述看來,他所強調的重點,似乎總在它們應該以其現實上的功能而得到應用與重視,而不是其藝術性的表現。因此,雖然他們所選錄的文體,未必全無實用性,但是終究還是以藝術的表現性而受到肯定。所以,他在〈序〉中總論選錄的各體之餘,要以此作結:
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強調的正是它們的美感功能。
而在《文選.序》的結尾之際,蕭統更提出了一個既是「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又是與本文的論旨具有絕對相關的「文體」,就是史書的「讚論」。他顯然作出了最具突破性的表述:
若其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因而《文選》一方面在辭賦的系統,也就是「答客指事之制」,選錄了「設論」一體,並將陸機〈文賦〉直接分類為「論文」;一方面也在單純的「論」體之前,收錄了「序」、「贊」、「史論」、「史述贊」等類,因而正強調了各類之「論」,亦可充分具顯「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以至「沉思」、「翰藻」的美感價值。尤其「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將之視為即是「文學作品的定義」,亦大有人在。因而,《文選》選錄的這幾類作品,正是我們探討「論」「說」作為文類所具美感性質,最好的實例與切入點。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