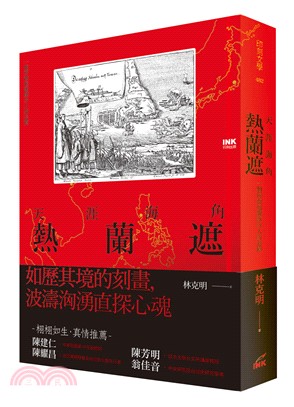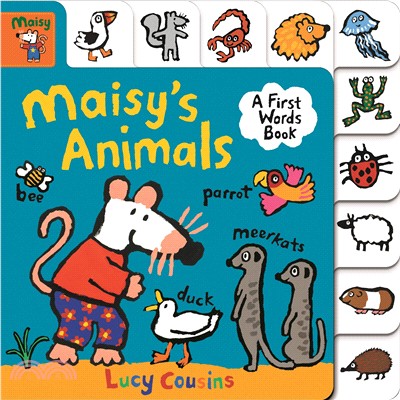定價
:NT$ 420 元優惠價
:90 折 378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1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如歷其境的刻畫,波濤洶湧直探心魂
從米德爾堡到熱蘭遮城,從二十一世紀初回望十七世紀中葉
描摩橫亙東亞海域的大時代
細寫戰爭、貿易、醫藥與傳教士的跨國碰撞
金陵、安海、金門、熱蘭遮、蔴荳、昇龍、長崎……
呈現三百五十年前的城鎮景致,勾畫多彩瑰奇的歷史大網
以他者之眼,重新開啟塵封於荷蘭圖書館匣櫃中的台灣往事
栩栩如生,真情推薦:
陳建仁(中華民國副總統)
陳耀昌(台灣骨髓移植及台灣史小說先行者)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學者)
深受後世景仰的英雄鄭成功,其實是一位躁鬱症及酒癮患者?
一位從小與鄭成功一起長大的荷蘭/福爾摩沙混血青年,晚年追憶他追隨鄭成功驚濤駭浪的半生:金陵一年的旖旎風光、為「明主」而戰的慷慨激昂、與滿清的戰戰和和、海上事業的發展、功敗垂成的金陵圍城、慘烈的熱蘭遮九月圍城。敘事者因其特殊背景,而有機會與不同陣營的人相識相熟,這些人不但包括鄭氏武力海商成員,明朝官吏、大儒、豔妓、名士,也及於當時活躍於明、清各政權及民間的耶穌會、道明會神父、福爾摩沙島的荷蘭傳教士、官員,乃至於福爾摩沙島不同族裔的島民……
波瀾壯闊的人生傳奇,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透過他者的視角,剖析人性的複雜與多面:他們的軟弱與堅強、理想與功利、慈悲與殘忍。
這本小說,是我近幾年來閱讀的同類小說中,非常細膩、難得的傑出作品,連我都被林醫師帶到如幻如真的歷史情境了。——翁佳音
從米德爾堡到熱蘭遮城,從二十一世紀初回望十七世紀中葉
描摩橫亙東亞海域的大時代
細寫戰爭、貿易、醫藥與傳教士的跨國碰撞
金陵、安海、金門、熱蘭遮、蔴荳、昇龍、長崎……
呈現三百五十年前的城鎮景致,勾畫多彩瑰奇的歷史大網
以他者之眼,重新開啟塵封於荷蘭圖書館匣櫃中的台灣往事
栩栩如生,真情推薦:
陳建仁(中華民國副總統)
陳耀昌(台灣骨髓移植及台灣史小說先行者)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學者)
深受後世景仰的英雄鄭成功,其實是一位躁鬱症及酒癮患者?
一位從小與鄭成功一起長大的荷蘭/福爾摩沙混血青年,晚年追憶他追隨鄭成功驚濤駭浪的半生:金陵一年的旖旎風光、為「明主」而戰的慷慨激昂、與滿清的戰戰和和、海上事業的發展、功敗垂成的金陵圍城、慘烈的熱蘭遮九月圍城。敘事者因其特殊背景,而有機會與不同陣營的人相識相熟,這些人不但包括鄭氏武力海商成員,明朝官吏、大儒、豔妓、名士,也及於當時活躍於明、清各政權及民間的耶穌會、道明會神父、福爾摩沙島的荷蘭傳教士、官員,乃至於福爾摩沙島不同族裔的島民……
波瀾壯闊的人生傳奇,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透過他者的視角,剖析人性的複雜與多面:他們的軟弱與堅強、理想與功利、慈悲與殘忍。
這本小說,是我近幾年來閱讀的同類小說中,非常細膩、難得的傑出作品,連我都被林醫師帶到如幻如真的歷史情境了。——翁佳音
作者簡介
林克明
1971年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任職台大神經精神科兩年後赴美,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五年,之後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並從事臨床及研究工作,2004年以榮譽教授銜退休,回台創設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醫學及藥物濫用研究組。2009年在史丹福大學一年,後定居舊金山,半職從事臨床工作之餘,開始專注於寫作,著有《受傷的醫者:心理治療開拓者的生命故事》;譯著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性學三論》、《婚姻的幻象》、《精神分析術》等書。
1971年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任職台大神經精神科兩年後赴美,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五年,之後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並從事臨床及研究工作,2004年以榮譽教授銜退休,回台創設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醫學及藥物濫用研究組。2009年在史丹福大學一年,後定居舊金山,半職從事臨床工作之餘,開始專注於寫作,著有《受傷的醫者:心理治療開拓者的生命故事》;譯著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性學三論》、《婚姻的幻象》、《精神分析術》等書。
序
楔子 愛上鬱金香
1
一個人的一生裡,到底能有幾次那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個新的自己,周遭的世界也同時就變得更有色彩、更有生機?每當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就馬上會想到我初到萊頓的那一年,尤其是那永生難忘的一個早晨。那一年起初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整個冬季,暴風雪一波一波來襲,連續好幾個月不見天日。除了上課,我幾乎把自己完全困在臨時租來的地下斗室裡,沒有想到費盡心思才得來的獎學金,竟把自己帶到這天寒地凍、昏天暗地的地方。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一個清晨,當我終於整裝就緒,爬出那地窖也似的住處,預備去迎接又一個沒有色彩的一天,迎面而來的卻是明亮耀眼的陽光和萬里無雲的藍天時,我真的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僅如此,路旁、運河兩旁高大的椴樹,也忽然都冒出了新芽。再走過幾條街,原來空曠荒蕪,被厚厚的積雪層層覆蓋的空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然幻化成一片花海,紅白紫黃,五顏六色,一行一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彷彿要一直延伸到天邊。鬱金香!全部都是鬱金香!後來我才聽說。
然後就是瑪琳娜,那健步如飛、笑容燦然、滿頭火紅長髮的瑪琳娜。那一天早晨,她彷彿就從那花叢裡蹦出來,直直地走入我的心坎裡、走入我生命的底層。看到她的那一刻,陽光灑在她那一頭飄逸的長髮上,宛如一把烈火,燒得我心慌。更讓我心慌意亂的,是她那燦然的笑容。我呆呆地看著她擦身而過,忘了呼吸。我轉身癡癡地望著,直到她消逝在街角。
那一整天,她的身影不停地在我腦海裡翻騰,胸腔裡空蕩蕩的,好像掉了什麼東西。那頭長髮、那個笑靨、那鮮豔的花圃、那溫煦的陽光,完完全全交融在一起,占據了我分分秒秒的思緒。多年來我常懷疑小說裡提到的一見鍾情是否真有可能,那一天我霍然發現,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覺得有多荒謬,愛戀之情說來就來,擋也別想擋住。
所幸那些鬱金香不是海市蜃樓,瑪琳娜也不是我心裡的幻影。她是個轉學生,剛到萊頓不久。我們很快就認識,成了朋友、好朋友,後來就不只是朋友了。
2
那一年我為什麼會在萊頓?說來也許難以置信,但是我去萊頓,的的確確是為了要尋找我自己。我來自台南新化,在那個小鎮長大,媽媽在附近的高中教英文。印象中她總是那麼溫柔、漂亮,但是她少言寡語,也總是讓人摸不定她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她是小鎮裡知名醫生的獨生女,而我又是她唯一的小孩。我沒有父親,從來不知道他是誰;到了我十歲的時候,媽媽得了白血病,竟然沒多久也就過世了。幸好阿公阿嬤從小照顧我,無微不至,家裡經濟又寬裕、衣食無憂,所以我對我的童年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抱怨的。
我的問題在學校──我的長相、性格,從來就跟其他的同學很不一樣。我又高又瘦、內向畏縮、笨手笨腳、運動神經不好,難以跟人打成一片。我的一頭鬈髮、深陷的眼眶、黝黑的皮膚,又不免讓人側目。小學、中學,年復一年,同學們取笑我,叫我「番仔」。我有時不免想像,也許他們說得沒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媽媽還在的時候,從來不曾提到他,而我大概也從小就知道這是個禁忌,是個不能碰的問題。
這個天大的疑問,一直到了我高中畢業,才開始有了一點眉目。那天阿公難得休診,和阿嬤一起,帶我到台南市區一家新開的日本餐廳,去慶祝我的長大成人。飯後天色還亮,我們慢慢地走到附近的赤崁樓。到達的時候,夏日向晚火紅的太陽正緩緩地沉入大海,映照出滿天絢麗的彩霞。平常滴酒不沾的阿公,那天破例連喝了兩杯,眼睛開始有些迷茫,話也多了起來。閒談著市區市容的變化,他忽然說,「你能想像嗎?從前這裡的海岸線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恰恰就在這裡,就在這赤崁樓的邊緣。」阿嬤笑著說,「別聽他胡扯了,不都是老掉牙的事了嗎?快四百年了吧!」但是微醺的外公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
「從這裡一直到安平,直徑差不多五公里,整個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時就叫做台江(大港)內海、大員內海。現在全都填平了,到處都是樓房,滄海的確會變成桑田。我們管它叫番仔城的安平古堡本來叫做熱蘭遮堡,我們市中心的赤崁樓,本地人稱之為番仔樓,那時則是荷蘭人的普羅民遮城堡,『普羅文西亞』,就是省的意思;兩個城堡的名字和在一起,就是熱蘭遮省。熱蘭遮的意思是海中之地,這『熱蘭遮省』位於荷蘭的最南邊,正是由許多海島組成的。如果不知道這兩個城堡間隔著這麼大的一片內海,就很難瞭解它們為什麼會建在那裡。」
「你能想像當荷蘭人初到這裡時,他們看到的是什麼嗎?」阿公繼續說,「從這裡往東,一直到中央山脈山腳下,綿延七、八十公里,就是一整片的樹林,中間稀稀疏疏住的是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當初就被荷蘭人叫做福爾摩沙人。其中最早與荷蘭人接觸的,就是住在這大員內海四周的『四大社』—新港社、蔴荳社、蕭壟社和目加溜灣社。這其中新港社受到的衝擊最深。他們原本住在現在我們面前的赤崁城附近,後來被迫往東遷移到新市,二、三百年來又逐漸被擠了出去,繼續往東,搬到山腳下。他們的後代,有些還住在那裡,你的父親就是從那裡來的。你可以說他就正是個道道地地的福爾摩沙人。可惜他沒有那個福分看著你長大,他可真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啊!家裡那麼窮,整個村子那麼窮,大部分的小孩從小念的就是放牛班,他居然一路成績優秀,進了我們全島最頂尖的醫學院,還彈著一手好吉他!你的媽媽在大學裡認識他,他們可真是愛得轟轟烈烈!我滿心期望他畢業後到新化來,接我這個診所,可是他卻選擇到他家鄉附近的衛生所。你一歲的那個夏天,颱風之後山溪暴漲,土石流切斷了他的村子和外界唯一的道路,斷水斷糧。你爸爸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條小船,載滿了藥物米糧,衝進去救援,從此就消逝得無影無蹤。」等了那麼多年,我心裡最大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這也許就是阿公特地要給我的畢業禮物吧!原來我的確是個雜種,我父系的祖先在荷蘭人和漢人還沒來到這個島嶼之前,早就已在這一片肥沃的平原闖蕩。難怪我長得有點像菲律賓人、薩摩亞人、大溪地人、夏威夷人。
我後來特地到父親的村子去探望了好幾次,但是每一趟行程都只有更增加我心裡的悵惘。那真是個貧窮得無以想像的地方。每家都只有那麼小小的一塊農地;庭院內外豬、鵝、雞、火雞,四處亂竄;幾乎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嘴裡都一直不停地嚼著檳榔,還不時隨地噴吐猩紅的檳榔汁。酗酒又是另一個不小的問題,常常一大早就會看到好幾個喝到掛的人,躺在馬路旁,不省人事。也許我的出現勾引起太多傷心往事的記憶吧,父親的爸爸媽媽,雖然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是總還是有點防備、有點疏遠。我試著要去接近他們、瞭解他們,可是我們之間,始終有那麼一條無形的,跨不過去的鴻溝。
就這樣,我變得越來越著迷於我父系先人的歷史,以及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我大概覺得,既然無法接近父親的族人,我只好從書本及古老的文件下手。雖然讓阿公傷心失望,大學醫預科讀了一年之後,我還是硬著心腸轉到歷史系就讀。又過了六年,我意外得到萊頓大學的獎學金,去研究荷蘭殖民時代的福爾摩沙。就這個題目而言,萊頓無疑是研究者的天堂。在荷蘭人統治台灣的那三十九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改革派教會留下來的資料汗牛充棟:日誌、報告、書信等等,事事物物,記載得鉅細靡遺,而且大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供學者挖掘、研究。可笑的是,為了尋根,我竟來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未完)
1
一個人的一生裡,到底能有幾次那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個新的自己,周遭的世界也同時就變得更有色彩、更有生機?每當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就馬上會想到我初到萊頓的那一年,尤其是那永生難忘的一個早晨。那一年起初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整個冬季,暴風雪一波一波來襲,連續好幾個月不見天日。除了上課,我幾乎把自己完全困在臨時租來的地下斗室裡,沒有想到費盡心思才得來的獎學金,竟把自己帶到這天寒地凍、昏天暗地的地方。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一個清晨,當我終於整裝就緒,爬出那地窖也似的住處,預備去迎接又一個沒有色彩的一天,迎面而來的卻是明亮耀眼的陽光和萬里無雲的藍天時,我真的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僅如此,路旁、運河兩旁高大的椴樹,也忽然都冒出了新芽。再走過幾條街,原來空曠荒蕪,被厚厚的積雪層層覆蓋的空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然幻化成一片花海,紅白紫黃,五顏六色,一行一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彷彿要一直延伸到天邊。鬱金香!全部都是鬱金香!後來我才聽說。
然後就是瑪琳娜,那健步如飛、笑容燦然、滿頭火紅長髮的瑪琳娜。那一天早晨,她彷彿就從那花叢裡蹦出來,直直地走入我的心坎裡、走入我生命的底層。看到她的那一刻,陽光灑在她那一頭飄逸的長髮上,宛如一把烈火,燒得我心慌。更讓我心慌意亂的,是她那燦然的笑容。我呆呆地看著她擦身而過,忘了呼吸。我轉身癡癡地望著,直到她消逝在街角。
那一整天,她的身影不停地在我腦海裡翻騰,胸腔裡空蕩蕩的,好像掉了什麼東西。那頭長髮、那個笑靨、那鮮豔的花圃、那溫煦的陽光,完完全全交融在一起,占據了我分分秒秒的思緒。多年來我常懷疑小說裡提到的一見鍾情是否真有可能,那一天我霍然發現,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覺得有多荒謬,愛戀之情說來就來,擋也別想擋住。
所幸那些鬱金香不是海市蜃樓,瑪琳娜也不是我心裡的幻影。她是個轉學生,剛到萊頓不久。我們很快就認識,成了朋友、好朋友,後來就不只是朋友了。
2
那一年我為什麼會在萊頓?說來也許難以置信,但是我去萊頓,的的確確是為了要尋找我自己。我來自台南新化,在那個小鎮長大,媽媽在附近的高中教英文。印象中她總是那麼溫柔、漂亮,但是她少言寡語,也總是讓人摸不定她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她是小鎮裡知名醫生的獨生女,而我又是她唯一的小孩。我沒有父親,從來不知道他是誰;到了我十歲的時候,媽媽得了白血病,竟然沒多久也就過世了。幸好阿公阿嬤從小照顧我,無微不至,家裡經濟又寬裕、衣食無憂,所以我對我的童年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抱怨的。
我的問題在學校──我的長相、性格,從來就跟其他的同學很不一樣。我又高又瘦、內向畏縮、笨手笨腳、運動神經不好,難以跟人打成一片。我的一頭鬈髮、深陷的眼眶、黝黑的皮膚,又不免讓人側目。小學、中學,年復一年,同學們取笑我,叫我「番仔」。我有時不免想像,也許他們說得沒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媽媽還在的時候,從來不曾提到他,而我大概也從小就知道這是個禁忌,是個不能碰的問題。
這個天大的疑問,一直到了我高中畢業,才開始有了一點眉目。那天阿公難得休診,和阿嬤一起,帶我到台南市區一家新開的日本餐廳,去慶祝我的長大成人。飯後天色還亮,我們慢慢地走到附近的赤崁樓。到達的時候,夏日向晚火紅的太陽正緩緩地沉入大海,映照出滿天絢麗的彩霞。平常滴酒不沾的阿公,那天破例連喝了兩杯,眼睛開始有些迷茫,話也多了起來。閒談著市區市容的變化,他忽然說,「你能想像嗎?從前這裡的海岸線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恰恰就在這裡,就在這赤崁樓的邊緣。」阿嬤笑著說,「別聽他胡扯了,不都是老掉牙的事了嗎?快四百年了吧!」但是微醺的外公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
「從這裡一直到安平,直徑差不多五公里,整個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時就叫做台江(大港)內海、大員內海。現在全都填平了,到處都是樓房,滄海的確會變成桑田。我們管它叫番仔城的安平古堡本來叫做熱蘭遮堡,我們市中心的赤崁樓,本地人稱之為番仔樓,那時則是荷蘭人的普羅民遮城堡,『普羅文西亞』,就是省的意思;兩個城堡的名字和在一起,就是熱蘭遮省。熱蘭遮的意思是海中之地,這『熱蘭遮省』位於荷蘭的最南邊,正是由許多海島組成的。如果不知道這兩個城堡間隔著這麼大的一片內海,就很難瞭解它們為什麼會建在那裡。」
「你能想像當荷蘭人初到這裡時,他們看到的是什麼嗎?」阿公繼續說,「從這裡往東,一直到中央山脈山腳下,綿延七、八十公里,就是一整片的樹林,中間稀稀疏疏住的是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當初就被荷蘭人叫做福爾摩沙人。其中最早與荷蘭人接觸的,就是住在這大員內海四周的『四大社』—新港社、蔴荳社、蕭壟社和目加溜灣社。這其中新港社受到的衝擊最深。他們原本住在現在我們面前的赤崁城附近,後來被迫往東遷移到新市,二、三百年來又逐漸被擠了出去,繼續往東,搬到山腳下。他們的後代,有些還住在那裡,你的父親就是從那裡來的。你可以說他就正是個道道地地的福爾摩沙人。可惜他沒有那個福分看著你長大,他可真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啊!家裡那麼窮,整個村子那麼窮,大部分的小孩從小念的就是放牛班,他居然一路成績優秀,進了我們全島最頂尖的醫學院,還彈著一手好吉他!你的媽媽在大學裡認識他,他們可真是愛得轟轟烈烈!我滿心期望他畢業後到新化來,接我這個診所,可是他卻選擇到他家鄉附近的衛生所。你一歲的那個夏天,颱風之後山溪暴漲,土石流切斷了他的村子和外界唯一的道路,斷水斷糧。你爸爸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條小船,載滿了藥物米糧,衝進去救援,從此就消逝得無影無蹤。」等了那麼多年,我心裡最大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這也許就是阿公特地要給我的畢業禮物吧!原來我的確是個雜種,我父系的祖先在荷蘭人和漢人還沒來到這個島嶼之前,早就已在這一片肥沃的平原闖蕩。難怪我長得有點像菲律賓人、薩摩亞人、大溪地人、夏威夷人。
我後來特地到父親的村子去探望了好幾次,但是每一趟行程都只有更增加我心裡的悵惘。那真是個貧窮得無以想像的地方。每家都只有那麼小小的一塊農地;庭院內外豬、鵝、雞、火雞,四處亂竄;幾乎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嘴裡都一直不停地嚼著檳榔,還不時隨地噴吐猩紅的檳榔汁。酗酒又是另一個不小的問題,常常一大早就會看到好幾個喝到掛的人,躺在馬路旁,不省人事。也許我的出現勾引起太多傷心往事的記憶吧,父親的爸爸媽媽,雖然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是總還是有點防備、有點疏遠。我試著要去接近他們、瞭解他們,可是我們之間,始終有那麼一條無形的,跨不過去的鴻溝。
就這樣,我變得越來越著迷於我父系先人的歷史,以及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我大概覺得,既然無法接近父親的族人,我只好從書本及古老的文件下手。雖然讓阿公傷心失望,大學醫預科讀了一年之後,我還是硬著心腸轉到歷史系就讀。又過了六年,我意外得到萊頓大學的獎學金,去研究荷蘭殖民時代的福爾摩沙。就這個題目而言,萊頓無疑是研究者的天堂。在荷蘭人統治台灣的那三十九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改革派教會留下來的資料汗牛充棟:日誌、報告、書信等等,事事物物,記載得鉅細靡遺,而且大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供學者挖掘、研究。可笑的是,為了尋根,我竟來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未完)
目次
楔子 愛上鬱金香
第一部 紅毛小鬼
第一章 秦淮河畔年少輕狂
第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第三章 風流教主薄命紅顏
第四章 別矣天堂
第二部 國姓爺
第一章 吾父明皇
第二章 怙恃無存
第三章 碧海青天任遨遊
第四章 尋覓明主
第五章 四海為家
第六章 東海長鯨
第七章 別矣秦淮別矣金陵
第三部 前進島國
第一章 尋覓世外桃源
第二章 黑水溝與美麗島
第三章 在劫難逃
第四章 永別伊甸園
第五章 伊甸園外
尾聲 永遠的鬱金香
後記
附錄
主要人物介紹
南明、滿清、鄭家簡略世系表
大航海時代明清海疆大事年表(一五九五─一六六四)
延伸閱讀
第一部 紅毛小鬼
第一章 秦淮河畔年少輕狂
第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第三章 風流教主薄命紅顏
第四章 別矣天堂
第二部 國姓爺
第一章 吾父明皇
第二章 怙恃無存
第三章 碧海青天任遨遊
第四章 尋覓明主
第五章 四海為家
第六章 東海長鯨
第七章 別矣秦淮別矣金陵
第三部 前進島國
第一章 尋覓世外桃源
第二章 黑水溝與美麗島
第三章 在劫難逃
第四章 永別伊甸園
第五章 伊甸園外
尾聲 永遠的鬱金香
後記
附錄
主要人物介紹
南明、滿清、鄭家簡略世系表
大航海時代明清海疆大事年表(一五九五─一六六四)
延伸閱讀
書摘/試閱
第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1
初識福仔的時候,我們都還是虛歲七歲的小孩。那時我隨著父親,剛從福爾摩沙搬到安海,住入那宛如城堡的鄭家莊園。安海當時是一個非常繁榮的海港,商船、艦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港岸到處都是醉眼惺忪的水手、兵丁,他們操著各地方言、不同的口音,往往雞同鴨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那一群日本浪人,更是危險,經常不知何故,就在碼頭上真槍實刀決鬥了起來;安息、天方、泰西之人,大街小巷隨處亂撞,嘰哩呱啦,大聲喧鬧,講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
鄭家莊園隔著鬧區的酒家、妓院、客棧有蠻長的一段距離,倒是相當安靜。莊園四周,每天十二時辰,不分晝夜,總是有成隊的衛士巡迴守衛。這些衛士個個身材魁梧、身手矯捷,黝黑的皮膚閃閃發亮。他們有些滿臉黑鬍鬚,深陷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大得嚇人,看起來就像佛寺牆壁上常見的達摩祖師像;有些則臉部線條比較柔和,鬍鬚也較少,但是皮膚更黑,頭髮難以想像地鬈曲,一小叢一小叢地,有如佛陀頭上那些為他遮陽的小蝸牛。他們火器精良、武藝高超,日夜巡邏,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鄭家莊園因此可謂固若金湯。莊園牆裡牆外,安靜與喧鬧,仿如兩個世界。
父親的醫院則是唯一的例外。醫院位於莊園邊上,面對通往海港的小河,二十四小時沒日沒夜,隨時有水手、軍士,載著斷腿斷手、血流如注、生命垂危的傷患,溯游而上、直抵醫院。父親有如魔術師,拿出冒著一縷奇香的煙管,給他們抽上幾口,那些哀嚎慘叫的傷患竟然登時就安靜了下來,助手們隨即將之牢牢按在手術桌上。此時父親從炙熱的火爐裡抽出一支火紅的鐵棍,迅速燙上傷口。隨著傷患的聲聲慘叫,烤肉般的焦味瀰漫滿屋,噴灑的血流登時打住。有時面對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的肢體,他從牆上拿下一把大鋸子,用烈酒澆灑抹拭後,毫不遲疑地,三兩下就把該鋸的地方齊根截掉,對病人的哀號充耳不聞。福仔父親的商船、艦隊,在海上經常與海賊、「倭寇」、「佛朗機人」、「紅毛番」戰鬥,傷亡慘重,父親的生意自然也就「門庭若市」。不止如此,他還常常需要隨艦出海,在海戰的現場就近醫治。他的確就這樣子每天從早忙到晚,分身乏術,幾乎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
我們的村莊四周用密不透風的刺竹林圍著;在這裡面,雞鵝豬狗,和我們這群小孩們,無憂無慮、無拘無束、四處奔跑。村裡的小孩親如兄弟姊妹,大人們不是姑姨伯叔,就是阿嬤阿公,他們呵護所有的小孩,有如己出。那是個人間樂園,至少在我的記憶裡就是如此。
2
那個人間樂園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消失了。那一年甘治士牧師進駐我們的村莊;他是個勇猛精進、不苟言笑的人,一心一意要改造我們,拯救我們的靈魂。他自己從來不笑,大概也努力要把我們變成不知歡笑的人。來到福爾摩沙島的最初幾年他四處碰壁,但是那一年他忽然走運,大家爭相入教,一村接著一村,集體受洗。在寫給阿姆斯特丹中會的報告裡,他不無得意地說,這正是真神的旨意、恩典,他自己不過是至高無上的神一個卑微的工具。但是更實在的原因應該是,那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終於讓福爾摩沙人見識到槍炮的威力,許多部落紛紛前來輸誠議和,「心甘情願」地付稅,也「乖乖」地攜家帶眷前來聽道。
甘治士牧師痛恨阿姆,叫她巫婆,誣控她為年輕女孩墮胎,好讓她們繼續縱慾。他懷疑她施放法術,讓四十歲以下的婦女不能懷孕。月光下的夜祭不再能舉行了,阿姆不再與人閒聊,她臉上也不再有笑容。沒多久她的臉就整個垮了下來,雙眼無神、茶飯不思、日漸消瘦,後來竟就起不了床了。她相信甘治士施法詛咒,早晚會要了她的命。失去了笑容的阿姆,竟變得越來越像甘治士了。
父親眼看著阿姆奄奄一息,十分焦急,跑去熱蘭遮堡找長官朴特曼;他們兩人都來自米德爾堡,交情不薄。朴特曼也不喜歡甘治士,但是他愛莫能助;東印度公司急著要將福爾摩沙人全數教化成基督徒,與阿姆斯特丹中會關係深厚的甘治士牧師,自然就成了巴達維亞總督眼中的紅人。朴特曼又說,即使想出辦法把甘治士調到別的村莊,他也不能保證,新來的牧師不會更激進、更不擇手段、更不近人情。
幾個月後阿姆在夜晚酣睡中過世,父親悲哀莫名,幾乎失去理智。他衝到甘治士的屋子裡,把他連拖帶拉,帶到公廨前,拳打腳踢,眼看就要出命案。幸好在最後一刻他克制住自己,垂頭喪氣地離開。他後來提起這件事時說,何必讓甘治士博得殉教的美名?他這一死,也許只會引來十個更狂熱的傳教士。
阿姆葬禮過後沒幾天,父親在半夜把我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帶著簡單的行李,悄悄地走到海邊,搭上一艘小漁船,渡海先到金門,再轉安海。後來我常聽人說,橫渡那當時被叫做黑水溝的海峽有多危險。但是我們的整個航程風平浪靜;深藍色的海水四面八方無盡延伸,平靜得像一面鏡子。天上時時飄浮著幾朵潔白的雲朵,輕盈盈地,一副灑脫的模樣。阿姆常說,人死後會變成小小的雲朵,自由自在,愛去哪裡就去哪裡。渡海的那三天,我不時仰望天空,尋找阿姆的身影。到了晚上,看著滿天閃爍,數也數不清的星斗,我想像阿姆和村裡穿白袍的老少婦孺,就在那裡歌舞,盡情狂歡。
3
許多年後,我才終於對父親的生平、來歷比較有一點瞭解。記憶裡那是個炎熱的夏夜,大概是我十一、二歲的時候。葛雷果理,一位曾在福爾摩沙島北部住過多年的日本道明會修士,來找父親喝酒聊天。他帶來一大瓶他在長崎的哥哥剛寄來的日本清酒。極品的純米阿蘇之酒,他說。這酒的原料是九州最上等的米,每一粒都磨到只剩下不到原來一半大的純白「米心」,用這米心配上阿蘇山上最清純的泉水釀成的。父親啜了一小口,眼睛登時亮了起來。他平常不喝酒,偶爾與人對飲時也很有節制。但是那一晚他卻豁出去了,兩人一起回想他們在福爾摩沙的日子,一杯接著一杯,話也越講越大聲,福佬話、葡萄牙話、荷蘭話、西班牙話,一一出籠。我在旁半懂不懂地聽著,幾乎就要睡著了。忽然間,葛雷果理不知道說了什麼,竟讓父親完全靜了下來。
那寂靜也許就只持續了那麼一、二分鐘,可是卻已經叫人憋得喘不過氣來。終於,那寂靜被隱隱約約的飲泣聲打斷;隨之而來的,居然就是嚎啕大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父親原來也是有眼淚的。良久以後,當他終於又開口說話時,他的聲音卻更讓我心酸。他說:「葛雷,你問我怎樣從荷蘭跑去福爾摩沙。萬里海程,無緣無故地就從地球的那一頭跑到這一頭來,難以瞭解,不是嗎?不過你一個人從日本輾轉經由雞籠來到這裡,有緣來跟我共享你老家這罐瓊漿玉液,不也是同樣地不可思議嗎?」
「仔細想來,我們的境遇其實還蠻像的。你因為身為天主教徒而被迫害,只好離開家鄉。你能想像我離開荷蘭也是同樣的緣故嗎?我出生的地方大多數居民信的是天主教,可是統治者卻是喀爾文派的改革教會信徒。他們是一群勇往直前、刻苦耐勞、執著頑固,沒有一絲幽默感的人。不錯,他們比不上日本人的凶狠,他們並沒有把我們釘在十字架上放火燒,也沒有逼迫我們踐踏聖母像。但是我們的教堂,那麼多華麗壯觀的聖殿,不是被破壞就是被沒收;神父們都被驅逐出城,我們只能在家裡偷偷摸摸做禮拜。我們沒學校可讀,長大後男的只好去做粗工,女的就只有當女傭的份。」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時還不到十三歲,自己一個人偷偷溜進一艘遠洋商船,被發現時船已啟航好幾天。船長氣壞了,起先威脅要把我丟下海,後來決定把我當奴工使喚:刷甲板、搬運貨物、潛水修補船身縫隙,什麼辛苦危險的事都有我的份,但是我甘之若飴。在船上我不但能填飽肚子,還能夠到世界各處見世面,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那你又怎麼變成外科醫生?」葛雷果理問。
「因為我遇上了彼得‧凡金。」父親繼續說:「他毫無疑問是好望角以東最棒的外科醫生!我們那時一起在一艘名叫度以金號的三桅船上工作。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有個水手從桅桿頂摔下來,跌斷了大腿骨。凡金醫生找不到他的助手,看到我正好在身邊,就叫我幫他清理傷口,我從此就成了凡金醫生的學徒。他竭盡所能,傾囊相授:使用鴉片、縫合傷口、接骨正骨、灼燒止血……。不止如此,他還教我閱讀、書寫荷蘭文與葡萄牙文。他自己沒有兒子,把我當成他的兒子來教導,可以說是我的再造父母,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賜。」
「那你怎麼來到福爾摩沙島?」葛雷果理有點遲疑地問。
父親的整張臉登時暗淡了下來,淚珠從他疲憊的眼眶裡不斷湧出,流過他那雜亂的紅鬍鬚,掉落在他的胸前。他低著頭飲泣良久,再抬起頭的時候,那迷茫的醉眼依然掛滿淚珠,但是他終於又找回了他的聲音:「真難相信,時間一晃就是十五年了。那一年我們跟著大名鼎鼎的班德固船長來到華南海岸,從珠江口到長江口,一路尋找與大明的商人、官吏接觸的機會。他們避不見面,消失得無影無蹤;整個千里長的華南海岸,任憑我們縱橫往來、進進出出,竟沒有任何人來阻擋、來交涉。班德固以為文的不行,只有訴諸武力,於是就放任手下四處燒殺劫掠,想用這樣粗暴的方法把他們逼出來,但是他還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不但官吏不見蹤影,連要作戰的對手都找不到。班德固不甘心兩手空空回巴達維亞,把注意力轉向澳門。荷蘭東印度公司那十幾年從非洲到亞洲,侵奪、鯨吞一個又一個葡萄牙人建立的海港、城堡。相較之下,躊躇滿志的班德固認為,占領區區一個澳門,應該易如反掌。沒想到我們在那裡居然吃了一個大敗仗,傷亡慘重,讓彼得與我日以繼夜,忙得不可開交。」
「我聽說那是因為初到的湯若望和幾位耶穌會神父在山頂上架設了炮臺,一陣轟炸後,又領著一群非洲黑奴衝下山來……」
「不管對手是誰,我們這東印度公司的無敵艦隊竟然三兩下就被打敗了!班德固氣急敗壞,再回到華南海岸,四處抓人,逮到了一千多名倒楣的壯丁當奴工。聽說他們後來不是在建造熱蘭遮城堡時過勞而死,就是被運到爪哇,死於擴建巴達維亞城的工程中。生逢亂世,一般百姓真是說有多可憐就多可憐。」
父親說到這時,已經是涕泗縱橫,大概也醉得快要語無倫次了。差不多就要醉昏之前,他又說:「葛雷,有一件事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正就是那件事,讓我覺得做為一個荷蘭人真是丟臉。」
從他那斷斷續續、口齒不清的呢喃裡,我拼湊出的情節大概是這個樣子:在那些被抓來的華人裡,有一個大概二十歲的年輕人,不知何故,已經病得奄奄一息。有一天凡金醫生忽然說:「他反正就要死了,我們來看看他到底生的是什麼病。」父親萬沒想到,彼得就這麼做起解剖來了。雖然他事先已經給了病人大量的鴉片,讓他昏睡過去,但是那到底還是個活生生的人哪!彼得竟然就那樣冷酷地一刀一刀割下去,肌肉、骨頭、五臟六腑,一樣一樣仔細檢驗,詳加解說,好像他就站在萊頓大學那舉世聞名的圓形講堂中間,在做教學示範!到了最後,當彼得捧出還在跳動的心臟,為父親講解威廉‧哈維新近提出的血液循環理論時,父親昏倒了。
不知道多少天後,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位美麗少女的懷裡。那少女對他微笑,繼續餵他喝小米粥。他是從船上掉下海的嗎?那之前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存心要自殺嗎?父親跟葛雷果里說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天之後,我就再不曾聽他提起這整件事情,也不敢讓他知道自己聽到這一段對話。
4
除了想念阿姆、想念家鄉,我初到安海時日子之所以不好過,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抵達安海不久,我就開始到鄭家的學堂上課。一般孩童都是在五、六歲時就學,所以我那時才開始,已經有點晚了。但是更糟糕的是,我對「念書」這件事其實從來都一無準備。父親教過我的任何東西,用的不是荷蘭文就是葡萄牙文,在那學堂裡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從阿姆那裡學到的,包括唱歌、跳舞、古老的神話傳說、哪裡可以找到治什麼病的草藥等等,在安海也都是一文不值。
學堂的塾師姓張,是一位將近六十歲的好好先生,對我這初來乍到、奇形怪狀的異鄉小孩特別關心,不厭其煩地反覆改正我的發音,傳授寫毛筆字的訣竅。我很快就發現,背誦三字經、千家詩並不困難,因為我一直是阿姆的好學生,祭歌、口傳史詩,朗朗上口。但是我當時對漢文的閱讀、書寫,真的是一點概念也沒有。父親自己本來就是門外漢,對中文一竅不通,當然也幫不上忙。不過幸好勤能補拙,不久我也就能夠駕輕就熟、遊刃有餘了。張先生發現我這「化外之民」,居然孺子可教,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課外的時間,才是我真正的困難所在。這塾堂裡除了我,就是七個鄭家的小孩,年紀從八歲到十三歲不等,個個都是大塊頭。他們對我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排斥我、嘲笑我。「小雜種、小混混、番崽子,紅毛小鬼,你是從哪裡鑽出來的?誰是你的親娘?你為什麼會有那一團紅髮?你父親是隻白鬼,那你是隻黑鬼嗎?」
最凶惡的要數聯舍—鄭聯。舍是閩南人對有錢人家少爺的尊稱。雖然大我沒幾歲,他已經長得快要跟大人一樣高了,粗粗壯壯地,渾身都是用不完的精力。他對讀書一點興趣也沒有,成天滿腦子想的是胡鬧、找樂子,整人的花樣層出不窮:把釘子撒在我的椅子上,把蟾蜍放在我的抽屜裡,把寫滿髒話的紙偷偷貼在我的背後。他身手矯捷,常常趁老師閉著眼睛吟誦唐詩的時候打我一拳。偶爾我忍不住回擊,聯舍馬上就告起狀來,挨罵挨罰的當然還都是我。有一天聯舍忽然對我非常友好,送我一片難得一見的金門貢糖。我滿心感激,不是因為貪吃貢糖,而是因為我天真地以為,時來運轉,我不再被當成局外人了。但是糖果一放入嘴裡,聯舍登時開懷大笑、樂不可支,問我可喜歡他臭腳丫子的味道;其他的孩子也跟著起鬨。
5
三個月後,福仔的出現,改變了我的一生。福仔不但與我同樣年紀,竟然還是同月同日生。他來自九州平戶,當時日本最大的對外通商海港。在他出生之前,他那還籍籍無名的父親,人稱尼古拉斯‧一官的鄭芝龍,就因走私罪嫌匆忙逃逸出海,把即將臨盆的太太田川松丟在平戶。之後短短六年間,鄭芝龍居然就變成了整個東亞海域航運、貿易、走私集團的霸主。他透過關係,要求當局放他的家人出國與他團圓。不過當時日本的鎖國令正在雷厲風行,日本人,尤其是女人,嚴禁出國。迫不得已,福仔的母親只好讓福仔一個人遠渡重洋,來到安海。
這期間,鄭芝龍早已妻妾成群,也又有了好幾個子女。但是做為長子,福仔被他那時已成為明皇朝水師統帥的父親寄以厚望,希望他走正途,努力讀書,考取功名。所以到達安海還沒幾天,福仔就開始到學塾來上學了。福仔的到來,改變了整個學塾的氣氛。那時還不太會講福佬話的福仔,竟然已經認得許多漢字,會讀會寫。我當時佩服得五體投地,直認為他是個天才。福仔無疑是個不世出的天才,不過他當時的讀寫能力並不見得就是他天才的表現。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日本人也用漢字、讀漢文書,福仔兩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和外公早就已經開始教他認字了。
1
初識福仔的時候,我們都還是虛歲七歲的小孩。那時我隨著父親,剛從福爾摩沙搬到安海,住入那宛如城堡的鄭家莊園。安海當時是一個非常繁榮的海港,商船、艦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港岸到處都是醉眼惺忪的水手、兵丁,他們操著各地方言、不同的口音,往往雞同鴨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那一群日本浪人,更是危險,經常不知何故,就在碼頭上真槍實刀決鬥了起來;安息、天方、泰西之人,大街小巷隨處亂撞,嘰哩呱啦,大聲喧鬧,講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
鄭家莊園隔著鬧區的酒家、妓院、客棧有蠻長的一段距離,倒是相當安靜。莊園四周,每天十二時辰,不分晝夜,總是有成隊的衛士巡迴守衛。這些衛士個個身材魁梧、身手矯捷,黝黑的皮膚閃閃發亮。他們有些滿臉黑鬍鬚,深陷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大得嚇人,看起來就像佛寺牆壁上常見的達摩祖師像;有些則臉部線條比較柔和,鬍鬚也較少,但是皮膚更黑,頭髮難以想像地鬈曲,一小叢一小叢地,有如佛陀頭上那些為他遮陽的小蝸牛。他們火器精良、武藝高超,日夜巡邏,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鄭家莊園因此可謂固若金湯。莊園牆裡牆外,安靜與喧鬧,仿如兩個世界。
父親的醫院則是唯一的例外。醫院位於莊園邊上,面對通往海港的小河,二十四小時沒日沒夜,隨時有水手、軍士,載著斷腿斷手、血流如注、生命垂危的傷患,溯游而上、直抵醫院。父親有如魔術師,拿出冒著一縷奇香的煙管,給他們抽上幾口,那些哀嚎慘叫的傷患竟然登時就安靜了下來,助手們隨即將之牢牢按在手術桌上。此時父親從炙熱的火爐裡抽出一支火紅的鐵棍,迅速燙上傷口。隨著傷患的聲聲慘叫,烤肉般的焦味瀰漫滿屋,噴灑的血流登時打住。有時面對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的肢體,他從牆上拿下一把大鋸子,用烈酒澆灑抹拭後,毫不遲疑地,三兩下就把該鋸的地方齊根截掉,對病人的哀號充耳不聞。福仔父親的商船、艦隊,在海上經常與海賊、「倭寇」、「佛朗機人」、「紅毛番」戰鬥,傷亡慘重,父親的生意自然也就「門庭若市」。不止如此,他還常常需要隨艦出海,在海戰的現場就近醫治。他的確就這樣子每天從早忙到晚,分身乏術,幾乎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
我們的村莊四周用密不透風的刺竹林圍著;在這裡面,雞鵝豬狗,和我們這群小孩們,無憂無慮、無拘無束、四處奔跑。村裡的小孩親如兄弟姊妹,大人們不是姑姨伯叔,就是阿嬤阿公,他們呵護所有的小孩,有如己出。那是個人間樂園,至少在我的記憶裡就是如此。
2
那個人間樂園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消失了。那一年甘治士牧師進駐我們的村莊;他是個勇猛精進、不苟言笑的人,一心一意要改造我們,拯救我們的靈魂。他自己從來不笑,大概也努力要把我們變成不知歡笑的人。來到福爾摩沙島的最初幾年他四處碰壁,但是那一年他忽然走運,大家爭相入教,一村接著一村,集體受洗。在寫給阿姆斯特丹中會的報告裡,他不無得意地說,這正是真神的旨意、恩典,他自己不過是至高無上的神一個卑微的工具。但是更實在的原因應該是,那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終於讓福爾摩沙人見識到槍炮的威力,許多部落紛紛前來輸誠議和,「心甘情願」地付稅,也「乖乖」地攜家帶眷前來聽道。
甘治士牧師痛恨阿姆,叫她巫婆,誣控她為年輕女孩墮胎,好讓她們繼續縱慾。他懷疑她施放法術,讓四十歲以下的婦女不能懷孕。月光下的夜祭不再能舉行了,阿姆不再與人閒聊,她臉上也不再有笑容。沒多久她的臉就整個垮了下來,雙眼無神、茶飯不思、日漸消瘦,後來竟就起不了床了。她相信甘治士施法詛咒,早晚會要了她的命。失去了笑容的阿姆,竟變得越來越像甘治士了。
父親眼看著阿姆奄奄一息,十分焦急,跑去熱蘭遮堡找長官朴特曼;他們兩人都來自米德爾堡,交情不薄。朴特曼也不喜歡甘治士,但是他愛莫能助;東印度公司急著要將福爾摩沙人全數教化成基督徒,與阿姆斯特丹中會關係深厚的甘治士牧師,自然就成了巴達維亞總督眼中的紅人。朴特曼又說,即使想出辦法把甘治士調到別的村莊,他也不能保證,新來的牧師不會更激進、更不擇手段、更不近人情。
幾個月後阿姆在夜晚酣睡中過世,父親悲哀莫名,幾乎失去理智。他衝到甘治士的屋子裡,把他連拖帶拉,帶到公廨前,拳打腳踢,眼看就要出命案。幸好在最後一刻他克制住自己,垂頭喪氣地離開。他後來提起這件事時說,何必讓甘治士博得殉教的美名?他這一死,也許只會引來十個更狂熱的傳教士。
阿姆葬禮過後沒幾天,父親在半夜把我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帶著簡單的行李,悄悄地走到海邊,搭上一艘小漁船,渡海先到金門,再轉安海。後來我常聽人說,橫渡那當時被叫做黑水溝的海峽有多危險。但是我們的整個航程風平浪靜;深藍色的海水四面八方無盡延伸,平靜得像一面鏡子。天上時時飄浮著幾朵潔白的雲朵,輕盈盈地,一副灑脫的模樣。阿姆常說,人死後會變成小小的雲朵,自由自在,愛去哪裡就去哪裡。渡海的那三天,我不時仰望天空,尋找阿姆的身影。到了晚上,看著滿天閃爍,數也數不清的星斗,我想像阿姆和村裡穿白袍的老少婦孺,就在那裡歌舞,盡情狂歡。
3
許多年後,我才終於對父親的生平、來歷比較有一點瞭解。記憶裡那是個炎熱的夏夜,大概是我十一、二歲的時候。葛雷果理,一位曾在福爾摩沙島北部住過多年的日本道明會修士,來找父親喝酒聊天。他帶來一大瓶他在長崎的哥哥剛寄來的日本清酒。極品的純米阿蘇之酒,他說。這酒的原料是九州最上等的米,每一粒都磨到只剩下不到原來一半大的純白「米心」,用這米心配上阿蘇山上最清純的泉水釀成的。父親啜了一小口,眼睛登時亮了起來。他平常不喝酒,偶爾與人對飲時也很有節制。但是那一晚他卻豁出去了,兩人一起回想他們在福爾摩沙的日子,一杯接著一杯,話也越講越大聲,福佬話、葡萄牙話、荷蘭話、西班牙話,一一出籠。我在旁半懂不懂地聽著,幾乎就要睡著了。忽然間,葛雷果理不知道說了什麼,竟讓父親完全靜了下來。
那寂靜也許就只持續了那麼一、二分鐘,可是卻已經叫人憋得喘不過氣來。終於,那寂靜被隱隱約約的飲泣聲打斷;隨之而來的,居然就是嚎啕大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父親原來也是有眼淚的。良久以後,當他終於又開口說話時,他的聲音卻更讓我心酸。他說:「葛雷,你問我怎樣從荷蘭跑去福爾摩沙。萬里海程,無緣無故地就從地球的那一頭跑到這一頭來,難以瞭解,不是嗎?不過你一個人從日本輾轉經由雞籠來到這裡,有緣來跟我共享你老家這罐瓊漿玉液,不也是同樣地不可思議嗎?」
「仔細想來,我們的境遇其實還蠻像的。你因為身為天主教徒而被迫害,只好離開家鄉。你能想像我離開荷蘭也是同樣的緣故嗎?我出生的地方大多數居民信的是天主教,可是統治者卻是喀爾文派的改革教會信徒。他們是一群勇往直前、刻苦耐勞、執著頑固,沒有一絲幽默感的人。不錯,他們比不上日本人的凶狠,他們並沒有把我們釘在十字架上放火燒,也沒有逼迫我們踐踏聖母像。但是我們的教堂,那麼多華麗壯觀的聖殿,不是被破壞就是被沒收;神父們都被驅逐出城,我們只能在家裡偷偷摸摸做禮拜。我們沒學校可讀,長大後男的只好去做粗工,女的就只有當女傭的份。」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時還不到十三歲,自己一個人偷偷溜進一艘遠洋商船,被發現時船已啟航好幾天。船長氣壞了,起先威脅要把我丟下海,後來決定把我當奴工使喚:刷甲板、搬運貨物、潛水修補船身縫隙,什麼辛苦危險的事都有我的份,但是我甘之若飴。在船上我不但能填飽肚子,還能夠到世界各處見世面,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那你又怎麼變成外科醫生?」葛雷果理問。
「因為我遇上了彼得‧凡金。」父親繼續說:「他毫無疑問是好望角以東最棒的外科醫生!我們那時一起在一艘名叫度以金號的三桅船上工作。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有個水手從桅桿頂摔下來,跌斷了大腿骨。凡金醫生找不到他的助手,看到我正好在身邊,就叫我幫他清理傷口,我從此就成了凡金醫生的學徒。他竭盡所能,傾囊相授:使用鴉片、縫合傷口、接骨正骨、灼燒止血……。不止如此,他還教我閱讀、書寫荷蘭文與葡萄牙文。他自己沒有兒子,把我當成他的兒子來教導,可以說是我的再造父母,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賜。」
「那你怎麼來到福爾摩沙島?」葛雷果理有點遲疑地問。
父親的整張臉登時暗淡了下來,淚珠從他疲憊的眼眶裡不斷湧出,流過他那雜亂的紅鬍鬚,掉落在他的胸前。他低著頭飲泣良久,再抬起頭的時候,那迷茫的醉眼依然掛滿淚珠,但是他終於又找回了他的聲音:「真難相信,時間一晃就是十五年了。那一年我們跟著大名鼎鼎的班德固船長來到華南海岸,從珠江口到長江口,一路尋找與大明的商人、官吏接觸的機會。他們避不見面,消失得無影無蹤;整個千里長的華南海岸,任憑我們縱橫往來、進進出出,竟沒有任何人來阻擋、來交涉。班德固以為文的不行,只有訴諸武力,於是就放任手下四處燒殺劫掠,想用這樣粗暴的方法把他們逼出來,但是他還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不但官吏不見蹤影,連要作戰的對手都找不到。班德固不甘心兩手空空回巴達維亞,把注意力轉向澳門。荷蘭東印度公司那十幾年從非洲到亞洲,侵奪、鯨吞一個又一個葡萄牙人建立的海港、城堡。相較之下,躊躇滿志的班德固認為,占領區區一個澳門,應該易如反掌。沒想到我們在那裡居然吃了一個大敗仗,傷亡慘重,讓彼得與我日以繼夜,忙得不可開交。」
「我聽說那是因為初到的湯若望和幾位耶穌會神父在山頂上架設了炮臺,一陣轟炸後,又領著一群非洲黑奴衝下山來……」
「不管對手是誰,我們這東印度公司的無敵艦隊竟然三兩下就被打敗了!班德固氣急敗壞,再回到華南海岸,四處抓人,逮到了一千多名倒楣的壯丁當奴工。聽說他們後來不是在建造熱蘭遮城堡時過勞而死,就是被運到爪哇,死於擴建巴達維亞城的工程中。生逢亂世,一般百姓真是說有多可憐就多可憐。」
父親說到這時,已經是涕泗縱橫,大概也醉得快要語無倫次了。差不多就要醉昏之前,他又說:「葛雷,有一件事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正就是那件事,讓我覺得做為一個荷蘭人真是丟臉。」
從他那斷斷續續、口齒不清的呢喃裡,我拼湊出的情節大概是這個樣子:在那些被抓來的華人裡,有一個大概二十歲的年輕人,不知何故,已經病得奄奄一息。有一天凡金醫生忽然說:「他反正就要死了,我們來看看他到底生的是什麼病。」父親萬沒想到,彼得就這麼做起解剖來了。雖然他事先已經給了病人大量的鴉片,讓他昏睡過去,但是那到底還是個活生生的人哪!彼得竟然就那樣冷酷地一刀一刀割下去,肌肉、骨頭、五臟六腑,一樣一樣仔細檢驗,詳加解說,好像他就站在萊頓大學那舉世聞名的圓形講堂中間,在做教學示範!到了最後,當彼得捧出還在跳動的心臟,為父親講解威廉‧哈維新近提出的血液循環理論時,父親昏倒了。
不知道多少天後,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位美麗少女的懷裡。那少女對他微笑,繼續餵他喝小米粥。他是從船上掉下海的嗎?那之前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存心要自殺嗎?父親跟葛雷果里說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天之後,我就再不曾聽他提起這整件事情,也不敢讓他知道自己聽到這一段對話。
4
除了想念阿姆、想念家鄉,我初到安海時日子之所以不好過,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抵達安海不久,我就開始到鄭家的學堂上課。一般孩童都是在五、六歲時就學,所以我那時才開始,已經有點晚了。但是更糟糕的是,我對「念書」這件事其實從來都一無準備。父親教過我的任何東西,用的不是荷蘭文就是葡萄牙文,在那學堂裡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從阿姆那裡學到的,包括唱歌、跳舞、古老的神話傳說、哪裡可以找到治什麼病的草藥等等,在安海也都是一文不值。
學堂的塾師姓張,是一位將近六十歲的好好先生,對我這初來乍到、奇形怪狀的異鄉小孩特別關心,不厭其煩地反覆改正我的發音,傳授寫毛筆字的訣竅。我很快就發現,背誦三字經、千家詩並不困難,因為我一直是阿姆的好學生,祭歌、口傳史詩,朗朗上口。但是我當時對漢文的閱讀、書寫,真的是一點概念也沒有。父親自己本來就是門外漢,對中文一竅不通,當然也幫不上忙。不過幸好勤能補拙,不久我也就能夠駕輕就熟、遊刃有餘了。張先生發現我這「化外之民」,居然孺子可教,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課外的時間,才是我真正的困難所在。這塾堂裡除了我,就是七個鄭家的小孩,年紀從八歲到十三歲不等,個個都是大塊頭。他們對我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排斥我、嘲笑我。「小雜種、小混混、番崽子,紅毛小鬼,你是從哪裡鑽出來的?誰是你的親娘?你為什麼會有那一團紅髮?你父親是隻白鬼,那你是隻黑鬼嗎?」
最凶惡的要數聯舍—鄭聯。舍是閩南人對有錢人家少爺的尊稱。雖然大我沒幾歲,他已經長得快要跟大人一樣高了,粗粗壯壯地,渾身都是用不完的精力。他對讀書一點興趣也沒有,成天滿腦子想的是胡鬧、找樂子,整人的花樣層出不窮:把釘子撒在我的椅子上,把蟾蜍放在我的抽屜裡,把寫滿髒話的紙偷偷貼在我的背後。他身手矯捷,常常趁老師閉著眼睛吟誦唐詩的時候打我一拳。偶爾我忍不住回擊,聯舍馬上就告起狀來,挨罵挨罰的當然還都是我。有一天聯舍忽然對我非常友好,送我一片難得一見的金門貢糖。我滿心感激,不是因為貪吃貢糖,而是因為我天真地以為,時來運轉,我不再被當成局外人了。但是糖果一放入嘴裡,聯舍登時開懷大笑、樂不可支,問我可喜歡他臭腳丫子的味道;其他的孩子也跟著起鬨。
5
三個月後,福仔的出現,改變了我的一生。福仔不但與我同樣年紀,竟然還是同月同日生。他來自九州平戶,當時日本最大的對外通商海港。在他出生之前,他那還籍籍無名的父親,人稱尼古拉斯‧一官的鄭芝龍,就因走私罪嫌匆忙逃逸出海,把即將臨盆的太太田川松丟在平戶。之後短短六年間,鄭芝龍居然就變成了整個東亞海域航運、貿易、走私集團的霸主。他透過關係,要求當局放他的家人出國與他團圓。不過當時日本的鎖國令正在雷厲風行,日本人,尤其是女人,嚴禁出國。迫不得已,福仔的母親只好讓福仔一個人遠渡重洋,來到安海。
這期間,鄭芝龍早已妻妾成群,也又有了好幾個子女。但是做為長子,福仔被他那時已成為明皇朝水師統帥的父親寄以厚望,希望他走正途,努力讀書,考取功名。所以到達安海還沒幾天,福仔就開始到學塾來上學了。福仔的到來,改變了整個學塾的氣氛。那時還不太會講福佬話的福仔,竟然已經認得許多漢字,會讀會寫。我當時佩服得五體投地,直認為他是個天才。福仔無疑是個不世出的天才,不過他當時的讀寫能力並不見得就是他天才的表現。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日本人也用漢字、讀漢文書,福仔兩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和外公早就已經開始教他認字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