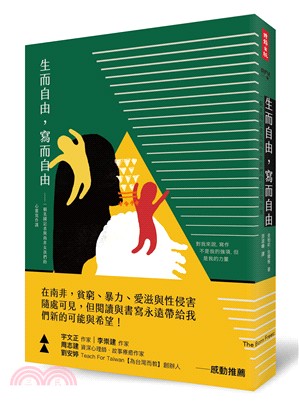生而自由,寫而自由:一個美國記者與南非女孩們的心靈寫作課
商品資訊
系列名:Revolution
ISBN13:9789571367835
替代書名:The Born Frees:Writing with the Girls of Gugulethu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金柏莉.伯爾格
譯者:游淑峰
出版日:2016/10/18
裝訂/頁數:平裝/408頁
規格:21cm*14.8cm*2.4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21【九年級】
商品簡介
在南非──
貧窮、暴力、愛滋與性侵害隨處可見,
但生而自由,寫而自由,
閱讀與書寫永遠帶給我們新的可能與希望!
對我來說,寫作
不是我的強項,但
是我的力量
──呱呱,南非「女孩之聲」寫作社的十六歲女孩
「自由世代」(Born Frees)指的是一九九四年後出生的南非年輕人,遠離種族隔離的歷史傷痕,沒有政治色彩的包袱。但他們的真實生活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南非擁有全世界最多受HIV感染的患者,年輕女性尤其是高危險群;超過三分之一的女孩在十八歲前曾遭受過性暴力;每十個孩子就有一個單親家庭,貧窮與孤兒更是隨處可見……
美國記者金柏莉•伯爾格在南非城鎮古古雷圖成立了「女孩之聲」(Amazw’Entombi)寫作社,她發現了一群傑出的「自由世代」女孩,她們的家庭與社區長期受到貧窮、暴力、性侵害與愛滋病的蹂躪,她們的人生隨時面臨令人生畏的挑戰。然而,伯爾格很快地發現,這些女孩強韌的精神與毅力,在艱困的生活與環境中展露出無比的生命力。
在伯爾格為期一年的帶領下,這個寫作社由個性截然不同、教育程度不等的女孩所組成。透過寫作,她們找到安慰和勇氣,找到了暫時逃避生活苦難的出口。她們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定義她們自身的命運驅力,在這裡,她們找到了書寫所賦予的自由意義。
《生而自由,寫而自由》從真實的記錄出發,描繪出南非的現況,並將個人故事交織在歷史環境、制度論述裡,這些女孩的生命故事以及她們對於社會的體悟,帶領讀者認識了整個南非。本書充滿了同理心與希望,是一本討論女孩自主之必要的見證,同時它也見證了寫作如何促使生命破解自己人生的角色。
在這些精彩的故事裡,可以看到溫暖,也可以看見更多生命的無奈無常,如果你期望讀完這本書會充滿溫暖,也許你只能看到無數的妥協;如果你認為在這本書裡將充滿悲傷,那你將發現人比你想像的更為堅強。生命的精彩在伯爾格細膩溫暖的文字下延展,筆尖劃開了幽暗,未知的黑暗大陸裡處處閃爍著耀眼微光。挫折無所不在,但閱讀與書寫永遠可以帶給我們新的可能與希望。
【好評推薦】
宇文正|作家
李崇建|作家
周志建|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劉安婷|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創辦人
──感動推薦
在這本有說服力、很個人的書中,金柏莉.伯爾格帶著我們進入一群優秀傑出的年輕女子的內心深處,她們的奮鬥與勇氣,是今日南非的典範。
──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紐約時報》暢銷書《不尋常的善》(The Uncommon Good)作者暨《旅居者雜誌》(Sojourners)總裁
在這本令人激動、鼓舞與引人入勝的書中,金柏莉.伯爾格召集了一群二十一世紀年輕的舍赫拉查達(Scheherazades),拯救了她們的人生,並將我們的人生投入在她們的故事與才華當中。這本書充滿智慧、洞察、同理、完全不偽善,伯爾格的筆觸溫暖地、技巧地──而且令人尊敬地──將女孩的敘述交織在仍承受壓迫制度傷口的急遽變化社會中。《生而自由,寫而自由》會是我送給年輕女子與年輕女孩(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男人)的選書,鼓舞他們行動與懷抱希望。
──茱莉亞.阿法瑞茲(Julia Alvarez),《紐約時報》暢銷書《蝴蝶情人》(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與《海地婚禮》(A Wedding in Haiti)的作者
讀者將會永遠記得《生而自由,寫而自由》裡的故事。讓年輕人知道與討論這些故事尤其重要,以建立更寬廣的世界觀,並鼓舞他們對重要事物的熱情探索。
──蘿瑟琳.魏斯曼(Rosalind Wiseman),《紐約時報》暢銷書《女王蜂與跟屁蟲》(Queen Bees and Wannabes)作者
如此溫暖的一本書,裡面都是你永難忘懷的勇敢年輕女子。我的心因為受到她們對自處環境、對她們國家的觀察而深深感動。她們的堅毅與智慧,非常激勵人心,也讓人謙卑。
──阿馬納.豐塔內拉汗(Amana Fontanella-Khan),《粉色莎麗革命》(Pink Sari Revolution)作者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金柏莉•伯爾格 Kimberly Burge
自由記者,之前在南非擔任傅爾布萊特學者。她在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大學拿過藝術創作碩士,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報導計畫」中,全球宗教報導的成員。目前住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譯者簡介
游淑峰
花蓮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曾任地理雜誌採訪與編輯,目前為自由譯者。譯有《如果,不是舒曼──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女鋼琴家克拉拉・舒曼》(合譯)、《雪地淚痕》、《我從人生谷底悟出的快樂致富法》、《失去貞操的橄欖油》(合譯)、《愈跑,心愈強大》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名人推薦語
在這本有說服力、很個人的書中,金柏莉.伯爾格帶著我們進入一群優秀傑出的年輕女子的內心深處,她們的奮鬥與勇氣,是今日南非的典範。
──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紐約時報》暢銷書《不尋常的善》(The Uncommon Good)作者暨《旅居者雜誌》(Sojourners)總裁
在這本令人激動、鼓舞與引人入勝的書中,金柏莉.伯爾格召集了一群二十一世紀年輕的舍赫拉查達(Scheherazades),拯救了她們的人生,並將我們的人生投入在她們的故事與才華當中。這本書充滿智慧、洞察、同理、完全不偽善,伯爾格的筆觸溫暖地、技巧地──而且令人尊敬地──將女孩的敘述交織在仍承受壓迫制度傷口的急遽變化社會中。《生而自由,寫而自由》會是我送給年輕女子與年輕女孩(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男人)的選書,鼓舞他們行動與懷抱希望。
──茱莉亞.阿法瑞茲(Julia Alvarez),《紐約時報》暢銷書《蝴蝶情人》(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與《海地婚禮》(A Wedding in Haiti)的作者
讀者將會永遠記得《生而自由,寫而自由》裡的故事。讓年輕人知道與討論這些故事尤其重要,以建立更寬廣的世界觀,並鼓舞他們對重要事物的熱情探索。
──蘿瑟琳.魏斯曼(Rosalind Wiseman),《紐約時報》暢銷書《女王蜂與跟屁蟲》(Queen Bees and Wannabes)作者
如此溫暖的一本書,裡面都是你永難忘懷的勇敢年輕女子。我的心因為受到她們對自處環境、對她們國家的觀察而深深感動。她們的堅毅與智慧,非常激勵人心,也讓人謙卑。
──阿馬納.豐塔內拉汗(Amana Fontanella-Khan),《粉色莎麗革命》(Pink Sari Revolution)作者
目次
序幕:在我的存在之中
第一部 女孩之聲
第一章 我們的驕傲
第二章 孤兒與弱勢兒童
第三章 疾病告知
第四章 「女孩之聲」
第二部 若你打擊一個女人,就是踢到一塊石頭
第五章 不可忽視的力量
第六章 天堂之路
第七章 你可以穿你的名牌,我可以穿我的地攤貨而不覺得不安
第八章 你可曾問過自己她是誰?
第九章 我心裡和腦中的想法
第十章 完全做你自己
第十一章 你猜怎樣?我還活著
第十二章 選擇活著,而不只是存在著
第三部 豐沛的「烏班圖」:兩年後的古古雷圖
第十三章 和民主一樣,不太老,也不太年輕
第十四章 仍在尋找我的出路
收場白:青年節
致謝
書摘/試閱
序幕:在我的存在之中
心境
心境受到壓迫。
壓得愈久,你愈快崩潰。
選擇讓風狂吹。
歲月的預言還未知。
我仍不知道為何我繼續
感覺狐獨。赤裸的雙腳不知往何處
去。而我也遺忘了回家的路途。
從一數到十,取悅我的
靈魂,雖然當中仍是個大洞。
當我身處最溫暖的時刻,
我依然感到嚴寒掃過,
有著呼叫某人的衝動,
因為我是那個未全然擁有的人。
──安娜史薇那
在某些日子裡,安娜史薇那只想當個小女孩。她無法說出她理想中的女孩時期是怎樣,況且,她也不需要「理想的」女孩時期。如果她可以重新創造她的過去,她會想把自己放在更早以前,在她認識如今吞噬她的苦難之前的日子。
她想重新建構她的家庭生活。她想像母親依然在世,安娜史薇那會跟在她的身邊長大,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他們會全部住在同一個房子裡。她不用一定得和她的父親一起住,但她會知道他是誰。她會有機會見到他,知道他的長相,知道她是否從他那裡遺傳到了較深的膚色。
住開普敦,或者約翰尼斯堡都可以──她不在乎家人是住在哪一個城市。他們不需要富有,房子也不需要寬大。她只關心在意的是,它最好是水泥的、有三個房間,是鎮上政府核發認可的房子,而不只是一間棚屋,只有夾板牆和塑膠防水布,用舊輪胎和笨重的石頭壓住,避免大風捲走瓦楞鐵皮屋頂。夜晚,與其清醒地躺著,聽見老鼠在她的床底下爬行,她會和她的小妹妹一起依偎在一條柔軟的粉紅色毛毯裡。毛毯有一種花香,像是雞蛋花,那是來自母親的香水,她正俯身親吻她的女兒們,向她們道晚安。等妹妹睡著後,安娜史薇那可能會亮著燈到深夜,以便在日記裡寫詩。
隨著年紀漸長,她的哥哥們會保護她,照顧她。不會有其他男性親屬敢朝她投以覬覦的眼光。
她不是非得上私立學校不可,但她會上學,每年都會,不會中輟。她會努力用功,考取好分數,也許除了數學,那是她永遠聽不懂的科目。她也會參加合唱團。不知不覺,她就要升上十二年級了,是她的「麥翠克」(Matric)年。對南非的學生來說,高中的終極目標就是大學入學考試。考試的成績決定了他們是否能獲得高中文憑,以及他們是否有資格上大學。她這一代學生在校的時間,大多還不到考大學入學考便中輟,不然就是無法通過這場考試。但安娜史薇那知道,如果她能撐到入學考,她一定會考過。
為了慶祝她完成這件大事,如果她和斐洛(Phelo)還在一起,她可能會答應讓他陪她參加學校的麥翠克舞會。她會穿上一件長長的紫色緞面禮服。即使她穿上最高的高跟鞋,裙子還是會拖曳在地上。她的頭髮會梳成薄紅褐色的長辮子,她會戴上幾乎垂到肩膀的水晶耳環。這一天,也許會是她和斐洛第一晚同床共眠,雖然老實說,他們可能也不會等這麼久。但那會是她的選擇。而且,如果他們真的發生性關係,他們會小心。
她會是 HIV 陰性,而且會一直維持如此。
但是可惜,安娜史薇那的人生在開始時,她所承襲的任何優勢,便都沒有成真。身為一位年輕的南非人,她是所謂「自由世代」(the Born Frees)的一員。她的國家終於將自由賦予給每個和她相同膚色的人。自由意謂著選擇。但安娜史薇那卻已經看見,她的人生、她的未來、甚至她自己的身體,都是因為其他人的選擇而改變了原來的軌道。自由對她的意義是什麼?當一個小女孩需要一位母親時,身為一位著名歌手母親的女兒,意義是什麼?
如果她可以擁有她夢想的女孩時期,安娜史薇那想像她會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人生。但她只有這樣的人生:十歲成為孤兒,自尋生路。跟著親人或親人的友人東宿西住,從房屋到棚屋,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勉強讀完九年級。HIV 陽性,每天活在病倒的恐懼中。她十八歲。
我遇見安娜史薇那是在二○一○年一月,我剛到南非不久的時候。我擔任傅爾布萊特學者(Fullbright Scholar),要在那裡住一年,並在古古雷圖(Gugulethu)的 J. L. 茲瓦內長老教會與社區中心帶領一個少女創意寫作社。古古雷圖是一個位於開普敦外圍大約十哩(十六公里)的城鎮。安娜史薇那是這個寫作社的首批學員之一。我們為這個寫作社命名為「Amazw’Entombi」,在科薩語(Xhosa)裡意思是「女孩之聲」。
安娜史薇那與其他所有參加「女孩之聲」的女孩,都是所謂「自由世代」的一份子,也就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出生的第一代南非黑人,這是接續在一九九四年大選,尼爾森•曼德拉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宣告南非新民主時代來臨之後。「種族隔離」(apartheid)是一個源自荷蘭文的南非荷蘭語(Afrikaans),字面上的意思是「分開,或者隔離的狀態」。將近五十年的時間,這是在整個南非由政府允許,而且有強制律法的種族隔離政策。種族隔離政策根據膚色和四種種族類別,將每個人區分類別與等級。
「白人」(Whites)是來自歐洲的移民,主要是荷蘭人和英國人。白人占了今天南非人口的八•九%。在種族金字塔的白人下面,是「印度南非人」(Indian South Africans),他們是印度人的後裔,只占南非人口的二•五%,而且主要集中在德爾班(Durban)。接下來是所謂的「有色人」(Coloured),他們是歐洲人、班圖人(Bantu)、亞洲人、科伊科伊人(Khoikhoi)和桑族(San)的混血人種,有些人認為這是帶有侮辱性的字眼。「有色人」是西開普省(Western Cape)與北開普省(Northern Cape),包括開普敦地區的主要族群,雖然這一群人僅占全國人口不到九%。
最後,在金字塔最下層的是「黑人」(Blacks),指的是當時的班圖人、原住民、非洲人。南非最大的族群──幾乎占八○%──是黑人。
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黑人和「有色人」沒有投票權。在種族隔離政策下,你屬於哪一個種族決定了所有的事:你應該住哪裡、去哪裡旅行、就讀哪一所學校,還有,你可以學什麼。你該去哪裡工作、應做哪一類的工作。你可以和誰結婚。你應該去哪裡敬拜上帝。你應該使用哪裡的洗手間、你可以造訪哪一片海灘或公園。你等計程車時,應該坐哪一張椅子,你可以搭哪一輛計程車。甚至你應該在哪一座墓園埋葬你死去的親人。
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這些規定都解除了。但是如今,隨著自由而來的,自由世代承接的是一個被矛盾洗禮過的國家。民主的南非擁有全世界最進步的憲法之一。歧視是不被容許的──不論種族、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懷孕與否、婚姻狀況、族群或社會出身、膚色、性傾向、年齡、身體缺陷、宗教、良知、信仰、文化、語言,或者血統。憲法也為婦女和女孩們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是六個共同推動共和國的民主與人權文化的國家機構之一。
南非同時也是全世界婦女遭受暴力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飽受戰火蹂躪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而且被稱為世界強暴首都。超過三分之一的女孩在十八歲之前曾遭受過性暴力。兒童,包括嬰兒,遭到強暴的比例很可能被低報。這個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受HIV感染的患者,估計為五百六十萬人。年輕女性尤其是高危險群。十五歲到二十四歲遭HIV感染的南非人中,高達四分之三是女性。
這個彩虹國度的貧富差距是全世界第三名,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比種族隔離時期還高。四分之一的南非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美金一•二五元(約合新台幣三十七元);八五%的白人相對較富有,八五%的黑人相對是貧窮的。有人稱此為經濟上的種族隔離。由於教育體系仍極不公平,年輕人失業的情況愈來愈多,無法逃脫經年累世的貧窮循環。有一份報告估計,年齡達十八歲的自由世代,有七成無法讀到高中畢業,或者沒有通過大學入學考試。
這些是我準備前往南非居住時,對南非的認識。當我透過「女孩之聲」認識幾位自由世代的孩子後,我了解了所有這些統計數字背後的含義。這些女孩的生命裡,交織了她們國家複雜且野蠻的歷史、眼前的困境,以及仍保有的希望。當我在南非住久了,這些數字漸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女孩的名字。
這些女孩,像是恩托姆比扎內蕾,這個名字的意思類似「招弟」。她和安娜史薇那一樣,太早失去了母親。她很想重考一次大學入學考,她已經失敗一次,然而,未治療過的憂鬱症卻似乎又要捲土重來。對莎朗而言,她的夢想不只是她自己一個人的。她背負著家人期盼的重擔:要成功,要供給他們物質的需求,能賺取薪資,幫助過度擁擠的家裡多蓋一個房間,或者買一輛車。因為母親患有愛滋病而成為孤兒,而且自己是 HIV 陽性的歐薇圖有時似乎已經向命運投降。更糟的是,她似乎受到引誘,不只逃學,還認識一位年紀較長,而且有虐待傾向的男朋友。雖然歐薇圖一事無成,她的妹妹席薇在一所距離古古雷圖四十哩(約六十四公里)的寄宿學校表現卻相當突出。歐薇圖無法說出她對人生的夢想,更難指出自己的存在的價值。
然後是安娜史薇那,她是我最認識的女孩。她很有勇氣,也有很多藉口,她對人生的期待每天都不一樣。她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偶爾也承認自己的缺點。她最清楚別人虧欠她的地方,而她更知道,她只能依靠自己,有時甚至連自己都不可靠。
這群自由世代與民主的南非一起進入了青春期,成長的痛苦一直是崎嶇而且艱難的。對所有這些女孩而言,成年這件事,在任何一個生日宣告她們的年齡之前,早就進入了她們的生命。就在她們在南非的同儕試圖展現他們這個世代的特質,這些年輕新秀作家發現,她們的手中擁有一股特別的力量──藉由她們的鉛筆、筆記本和一群聽眾,她們擁有定義自己的能力。
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大塊蛋糕。
兩片蛋糕和一杯可樂,是全部
我想拿的,在我寧靜的感知裡,
痛苦在我的意識中雷鳴,釋放出潛
意識的時刻,以及聲明我的主張
令人厭惡。
你只能在有太陽的場景看見我,
在將我藏起來的黑暗角落裡布網,
我期望不被注意到。
但知道我仍然存在著,知道我自己
以人的方式存在。
──安娜史薇那
第一部 女孩之聲
第一章 我們的驕傲
在旅遊文學中,開普敦被盛讚為「母親之城」(Mother City),雖然它最初全然不是為了要建城。一六五二年,當贊•范里貝克(Jan van Riebeeck)與三艘滿載水手的船隻停泊在桌灣(Table Bay)時,他帶著荷蘭母國明確的指示:建造一座堡壘,作為補給站。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來往於歐洲與東亞之間的貿易航線,往往航行數月,途中得繞過距離桌灣約三十哩(四十八公里),位在半島南方的好望角。若水手罹患了壞血病便無法工作,所以他們需要在旅途中的一個據點臨時停留,補給蔬菜、水果、肉類和淡水。
有些水手的勞動契約解除了,被允許留在這塊新的土地開墾、建立農場,供應需要的物資。一個聚落於焉誕生了。這些新住民進口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同時也伴隨著勞動力──從今日我們所知的印尼、馬來西亞、馬達加斯加、安哥拉、莫三比克等地輸入的奴隸。這個聚落起初變成一個小鎮,後來成為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范里貝克成為第一任總督。後來,英國人來了,從荷蘭人手中搶下了這塊殖民地的控制權。但這些荷蘭人繼續留在當地,最後成為所謂的南非白人(Afrikaner)。他們當中有些人繼續留在開普殖民地,有些人開始往東進,成為開拓者(Voortrekkers),意圖占有更多的土地,認為這是上帝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稱之為「在南非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 in southern Africa)。
然而,將開普敦視為「母親之城」,是對這些早期歐洲移民後代的溢美之辭,他們預設當地的開發即是為了歐洲殖民者的利益。這個暱稱忽略了這塊土地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之前,早已哺育當地原住民很長的一段時間。
科伊科伊人,這群原來居住在非洲大陸西南角的牧人,在歐洲水手到來之前,對桌灣有另一個稱呼。他們稱它為「Camissa」,意思是「水甜的地方」。當荷蘭的農民搶走了最肥沃的土地,他們是最早被新來的移民逼迫遷移的人。最初,科伊科伊人與這些移民還維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們用牛、羊交換荷蘭進口的物資。但隨著殖民者獲得了權力,他們對原住民愈來愈殘暴。被懷疑偷竊時,科伊科伊人會被送到桌灣裡,距離陸地七哩(約十一公里)遠的一個小島──羅本島(Robben Island)從那個時候便開始扮演監獄的角色。
對於開普敦長久以來的重要象徵,科伊科伊人也有個名稱。移民所稱的「桌山」(Table Mountain),這個流傳下來令人回味的名字,科伊科伊人叫它「海之山」(Hoerikwaggo)。桌山高三、五五八呎(約一•○八四公尺),有如信號台和哨兵一樣巍然屹立著,是形成迤邐的開普半島脊脈的砂岩山脈的一部分。魔鬼山(Devil’s Peak)接在桌山的東翼,西翼則是獅頭山(Lion’s Head)。當東南風吹起,把風吹上了桌山,在桌山平坦的高原上便形成了一大片雲頂,翻滾的白雲覆蓋在上面,被稱為「桌布」。有時,雲瀑流洩到半山腰。
山的另一側,土地很快變得惡劣而且無情,當冬雨降臨,地勢低窪地區很容易發生洪水。夏季和冬季猛吹著整個開普敦的狂風,不斷地將一層沙子飄撒在原本厚厚的頁岩上,形成不穩定的沙丘和貧瘠的土壤,不適合農耕。這塊區域是開普低地(Cape Flats),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也就是范里貝克抵達開普敦後的三百年,基本上都維持著無人居住的狀態。
一九四八年,由南非白人主導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大選中取得執政權。黑人當時並沒有選舉權。新政府立即開始建立種族隔離政策,企圖由這個國家的少數白人將種族區隔正式化,並強固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其中最先通過的法案之一,是一九五○年的《種族分區法》(Group Areas Act of 1950),規定什麼種族可以住在哪一個城市區域,而且,將城市裡最好的和最發達的地區只留給白人。
種族隔離制度實施以前,開普敦是南非最都會化的城市,有一些混住的社區,如鄰近城市碗(City Bowl)的第六區。在《種族分區法》之下,這樣的社區是被禁止的。許多家庭被強行遷徒到他們被允許與其他同種族生活的指定地區。開普低地的叢林地區明顯成了安置非白人的地點。非洲人被送往已存在的黑人專屬地區之一,如蘭加(Langa)或尼安加(Nyanga),「有色人」家庭也被指定到他們的隔離區域。南非歷史學家蕭恩•菲爾德博士(Dr. Sean Field)將此舉比喻成截肢。「想像一下,你成長的社區和周圍的風景,那些在整個童年歲月與型塑時期圍繞著你的環境。若只是因為你和你的家人不符合外部強加的種族身份分類,而便被要求強迫遷移,命令你不能繼續住在那個空間,和你視為所屬社區的人互動? ⋯⋯截肢之後,你的生活會如何改變?」
當現存的城鎮太擁擠,新的城鎮便開始興建,包括一九六○年,一個稱作古古雷圖的地方。這個名字在科薩語裡,意思是「我們的驕傲」。政府承諾會提供住家給定居在這個城鎮的家庭,但在口述歷史的訪談中,古古雷圖的早期居民告訴菲爾德博士,他們抵達這裡的時候,看見的是那一種房子:「一個混凝土空殼。沒有天花板、沒有室內的門、沒有像樣的地板,沒電、沒熱水、沒有室內浴厠⋯⋯他們理所當然覺得被欺騙了。」開普低地後來被稱為種族隔離的棄置場。
從桌山的山腳,克里楓丹路(Klipfontein Road)展延過開普低地,鎮上最大的馬路 NY1將古古雷圖從中間切開。在這個交叉口之前,有一條帶狀的貨櫃屋店鋪:噴射洗車店、一間理髮店、媽媽夫人餐廳外帶服務、一間「spaza」便利商店,裡面賣不含酒精的飲料和手機通話時數。小販把雞肉和香腸(boerewors)放在自製的鋼桶烤肉架上燒烤(braai),煙和烤肉的香味飄散在空氣裡。一條愛滋病絲帶纏繞著沒點燈的聖誕燈飾,懸在路口上方。
古古雷圖──或暱稱「古古」(Gugs)──的綠地很少,樹也不多。當風揚起,庭院裡都是泥土和沙,在每樣東西上面覆上薄薄一層灰。但意想不到的色彩卻無處不在──雖然有些褪色,而且經過風吹雨打,像是春末最後的花季──這些色彩來自房子和貨櫃屋商店的彩色油漆。鎮上大約有一半的居民是住在正式的房子裡,當年的混凝土房屋,如今安頓得很好,有時還會擴建。還有些古古雷圖的居民增蓋了二樓,在屋頂加裝衛星天線,讓這些房子有些中產階級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些「非正式的住處」。這個用詞使得棚屋聽起來像是暫時的,但其實不然。他們是成千上萬人的住家。木板錯落地釘在一起,成了棚屋的牆。木板上殘留著它之前的用途所留下的褪色剝落的油漆,暗示它是重覆使用的,以及當地人物盡其用的本能。塑膠防水布拉到底,仍難以隔絕與抵擋冬雨。好幾家棚屋冒險從同一個電源分接電線。數百戶的社區外,會有公共廁所和一個水泵。一大片的棚屋,位於稱為KTC的分區裡,沿著克里楓丹路伸展開來,對面則是另一大片古古雷圖墓園。葬禮已經不再這裡舉行了。墓地已經滿了。
在抵達大片棚屋和墓園之前,從克里楓丹路左轉到 NY1 公路,會經過兩座紀念碑,紀念古古雷圖歷史上兩次慘痛的事件。較遠的那處紀念碑,矗立著七座花崗岩柱。每一個柱子上都有一個真人大小的鏤空人形,他們的雙手高舉,雙腳奔跑著,像是在跑步或跳舞,或是走上街頭抗議。這是「古古雷圖七烈士」(Gugulethu Seven)的紀念碑。一九八六年,有七位年紀介於十六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反種族隔離政策的活動份子,遭到南非安全部隊的伏擊,在街頭被開槍射死了。他們被懷疑是「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成員,這是屬於「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 ANC)的軍事組織,也是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遭取締的組織。警察宣稱他們七人正在策畫攻擊一輛警車。
辛西婭•恩格威(Cynthia Ngweu)是古古雷圖七烈士其中一位青年的母親,她於一九九六年在真相與合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ion,簡稱TRC)作證,講述她在電視上看見她兒子的情形:「我對我的小孩說,『我們來看電視上播的事情經過吧,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許電視上會有報導。』當我們還在看七點或六點的新聞時,我看見了我的孩子。我卻看到他們拖著他,腰間綁著繩子,用一輛廂型車拖著。我說,『關掉電視,我已經看到我想看的了。快把它關掉。』」古古雷圖七烈士紀念碑在二○○五年時建立。
不遠處,一個加油站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個小型的花崗岩十字架,上面有鮮明的傅爾布萊特計畫標誌。一九九三年,一位二十六歲的美國傅爾布萊特計畫工作人員艾咪•畢赫(Amy Biehl)在這裡被殺身亡。她是一位反種族隔離政策人士,也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她當時的工作是為隔年的南非首次民主選舉登錄選民名冊。即將返回美國的前三天,她開車載三位友人回到古古雷圖的家。一群剛從政治集會回來的暴民,見到司機白皙的皮膚,以為她是南非人,便群起攻擊她,一邊高喊口號:「一個移民,一顆子彈!」他們把艾咪拖下車,朝她丟擲石塊,將她刺死,完全不顧她的友人苦苦哀求,哭喊說她是南非黑人的朋友。一九九○年代末,艾咪的父母也參加了真相與合解委員會的聽證會,他們公開原諒了四位服監的男子。他們被給予特赦,從監獄釋放出來。其中一人隨後到「艾咪•畢赫基金會」工作,這是她的父母在開普敦成立的基金會。
回到古古雷圖另一邊的克里楓丹路,離開 NY1,距離古古雷圖七烈士紀念碑大約一哩(一•六公里)遠處,J. L. 茲瓦內長老教會(J. L. Zwane Presbyterian Church)與社區中心座落在稍微突起的高地,在NY7 與NY11的轉角。古古雷圖所有的路都是這樣命名的,NY 後面接一個數字。NY 代表的是土人的區域(Native Yards),也就是種族隔離政策的建築師規畫中的城鎮:容納「土人」的地方。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