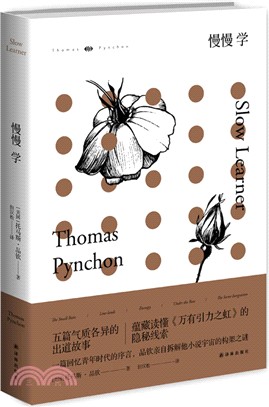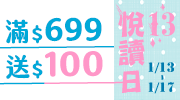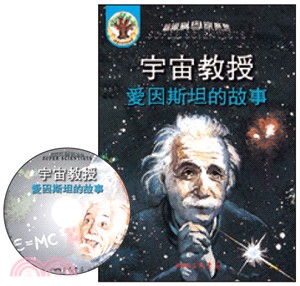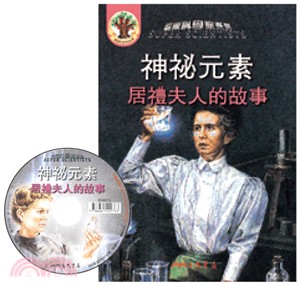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生於1937年5月8日。美國小說家,著有《V.》《拍賣第四十九批》《萬有引力之虹》《葡萄園》《梅森和迪克遜》《反抗時間》《性本惡》《尖鋒時代》,以及短篇集《慢慢學》。1974年因《萬有引力之虹》被授予美國全國圖書獎。
譯者:但漢松
英美文學博士,副教授,現任教于南京大學英文系。主要學術興趣為現當代美國文學及批評理論。業餘從事文學翻譯和書評隨筆寫作,著有個人隨筆集《以讀攻讀》,譯有托馬斯•品欽的《性本惡》,桑頓•懷爾德的《我們的小鎮》和《聖路易斯雷大橋》,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樓拜的鸚鵡》等。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小雨
低地
熵
玫瑰之下
秘密融合
譯注
書摘/試閱
玫瑰之下
隨著午后時光的推移,黃色的云朵開始在穆罕默德· 阿里廣場的上空聚集,留著一星半點的云卷朝著利比亞沙漠的方向飄去。從西南方吹來的風靜靜地掠過易卜拉欣路,穿過廣場,把沙漠里的涼意帶到城里。
那就下點雨吧,潑潘提恩想:快下雨吧。他坐在一家咖啡館門前的鐵質小桌邊,抽著土耳其香煙,喝著第三杯咖啡,長外套則搭在旁邊椅子的靠背上。今天,他穿了淺色花呢衣,戴著一頂氈帽,上面系著一塊平紋細布,以保護脖子不受暴曬;他對陽光總是有些戒心的。云聚攏過來,天漸漸陰了。潑潘提恩在座位上挪了挪屁股,從西裝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塊表,看了看時間,又放了回去。他轉過身,看著廣場上熙熙攘攘的歐洲人:有的人正急著進奧斯曼帝國銀行,有的人在商店櫥窗外溜達,或坐在咖啡館里。他精心設計了自己的表情:沉著淡然,卻又帶著浪子的期待;他就像是要在這里和女士約會。
所有這一切都是做給那些關注者們看的。天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其實,他們就是指老牌間諜莫德威爾普的那幫手下。不知為何,人們總喜歡在提到他時加一句“老牌間諜”。這也許是一種復古的用法,在過去,這種昵稱是對英雄主義或男子氣概的一種褒獎。或者,這可能是因為一個世紀正迅速走向尾聲,隨之終結的是一種間諜傳統——那時,人們默認一切應依紳士風范來行事;那時,伊頓公學的操場塑造了(可以這么說吧)入伍前的行為操守,所以,“老牌間諜”這一標簽可以確保那人在這個特別的上流社會占據一席之地,直到死亡——個體或集體意義上的死亡——以刺芒使之永歸寧靜。而潑潘提恩本人則被那些關注者們稱為“單純的英國人”。
上個星期在布林迪西,他們如往常一樣不斷地展現同情心,這給予了他們某種道德優勢,他們懂得自己的做法令潑潘提恩無法回敬。因此,他們謹小慎微地設計追蹤路線,冷不丁地與他在旅途上相逢。同樣,他們也效仿了他的私人策略:住在客人最多的酒店,坐在游客愛去的咖啡館,總是選最光明正大的路線旅行。這當然令他尤其氣惱;就好像這種巧扮的單純是潑潘提恩的發明,只要是別人——尤其是莫德威爾普的間諜們——用了這一招,那就屬于侵犯專利。如果可能的話,他們還會盜用他那兒童般的眼神,那胖天使般的微笑。對于他們的這種意氣相投,他近十五年來一直是唯恐避之不及;那時是1883年的一個冬夜,在那不勒斯的布里斯托酒店大堂里,你所認識的間諜共濟會全部成員似乎都在那里等待。他們所等待的,是喀土穆的淪陷,是阿富汗危機的不斷惡化,直到人們可以稱之為世界的末日。他去那里見到了已顯老態的莫德威爾普,這位贏家或大師;他知道在這場游戲當中,遲早會有這么一天。他感到這位老人的手關切地摩挲著他的手臂,聽見對方真誠的私語:“事情快到頭了;我們也許都會參與,所有人。要小心。”如何回應?還能怎么回應?只能是小心觀察,幾近急切地尋找虛情假意的蛛絲馬跡。當然,他什么都沒找到;于是,他很快怒火中燒,無法掩蓋自己的無助之感。在此后的歷次遭遇中,潑潘提恩都是如此這般,搬起石頭卻砸了自己的腳,所以等到了1898年的炎夏,他已儼然練就了一副冷石心腸。他們還繼續用這種屢試不爽的方法:從不追蹤他的生活,從不破壞行規,雖然做有些事已成了他們的樂子,但仍克制行事。
他如今坐在這里,懷疑在布林迪西見到的兩人是否有誰跟蹤他到了亞歷山大。他可以肯定在威尼斯的船上并未看見他們,但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有一艘奧地利勞埃德的郵輪從的里雅斯特出發,中途經停了布林迪西,這是他們唯一可選的另一艘船。今天是星期一。潑潘提恩是周五離開的。的里雅斯特的船周四起航,周日晚些時候到達。所以:(1)第二糟糕的情形是,他還有六天時間;(2)最壞的可能,他們已經知道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已在潑潘提恩之前離開,并且已經到了這里。
他看著太陽漸漸暗下去,看著風將穆罕默德· 阿里廣場的刺槐樹葉子吹得啪啪直響。遠處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轉過身,看見了頭發金黃的古德費羅,他興高采烈地沿著謝里夫帕夏街向他大步走來,身上穿著一件大禮服,頭上戴著一頂大了兩個碼子的太陽帽。“喂,”古德費羅喊道,“潑潘提恩,我見到了一位特別迷人的年輕女士。”潑潘提恩又點了一根香煙,閉上眼睛。古德費羅身邊的所有年輕女士都很漂亮。在當了兩年半的搭檔之后,他已經習慣了古德費羅的右臂會不斷引來女性的依偎:就仿佛歐洲的每個首都都是馬蓋特,而海濱的散步路有如大陸那么漫長。假如古德費羅知道他一半的薪水都按月寄給了在利物浦的妻子,那么他至少不露聲色,照樣在那兒樂顛顛地嬉笑瘋鬧。潑潘提恩看過他搭檔的卷宗,但已經決定不摻和他妻子這檔事。他一邊聽古德費羅說,一邊看他拉出一把椅子,用糟糕的阿拉伯語來招呼服務員:“Hat fingan kahwa bisukkar, ya weled.”
“古德費羅,”潑潘提恩說,“你犯不著這樣——”
“Ya weled, ya weled.”古德費羅大聲說。服務生是法國人,并不懂阿拉伯語。“啊,”古德費羅說,“那就咖啡。Café,你懂吧。”
“旅館怎么樣?”潑潘提恩問。
“非常好。”古德費羅住在距離這里七個街區的科迪瓦酒店。因為財政上臨時出了點狀況,所以只能允許一個人維持平常的食宿標準。潑潘提恩則在土耳其廣場和一個朋友同住。“關于這個女孩,”古德費羅說,“今晚在奧地利領事館有個派對。陪她的人,是古德費羅:語言學家,冒險家,外交家……”
“名字?”潑潘提恩說。
“維多利亞· 列恩。和家人來旅行的,他們分別是阿拉斯泰爾· 列恩爵士,英國皇家風琴師學會會員,還有妹妹米爾德里德。母親過世了。明天就要出發去開羅。庫克的尼羅河之旅。”潑潘提恩等他接著說。“還有個神經不正常的考古學家,”古德費羅似乎有些不情不愿,“叫什么班戈–夏弗茲伯里。年紀輕輕,腦子糨糊。不具危害性。”
“噢。”
“切。太亢奮了。應該少喝點咖啡。”
“也許吧。”潑潘提恩說。古德費羅的咖啡來了。潑潘提恩繼續說:“你知道我們最后都是要看運氣的。我們總是這樣。”古德費羅心不在焉地笑了,攪了攪自己的咖啡。
“我已經采取行動了。為了爭得這個年輕女士的芳心,我要和班戈–夏弗茲伯里好好拼一下。這人是個十足的蠢貨。他著了魔地想去看盧克索的底比斯廢墟。”
“當然。”潑潘提恩說。他站起身,把長外套搭到肩上。開始下雨了。古德費羅遞給他一個白色小信封,反面有奧地利的飾章。
“八點,我猜。”潑潘提恩說。
“說得對。你一定要見見這個女孩。”
此時,潑潘提恩突然渾身一緊。這份職業很孤獨,總是需要嚴陣以待,雖然并非總是生死考驗。所以,每隔一段時間,他就需要扮扮小丑。“瘋鬧一下”,他是這樣形容的。他相信,這樣做會讓他更有人情味。“我會戴著假胡子去,”他告訴古德費羅,“假扮成一個意大利的伯爵。”他樂呵呵地筆挺站立,假裝握住一只手: “親愛的小姐。”他彎下腰,親吻了空氣。
“你瘋了吧。”古德費羅開心地說。
“瘋狂的兒子!”潑潘提恩開始用意大利語唱起了起伏的男高音。“看吧,我如何又哭又求……”他的意大利語并不算好,不時夾雜著倫敦東區英語的腔調。一群英國游客急匆匆從外面進來躲雨,好奇地回頭瞅他。
“夠了,”古德費羅皺起眉頭,“是在都靈,我記得。托里諾,對嗎?九三年。我護送一個后背上有痣的侯爵千金,克里莫尼尼唱了《德古耶》。你,潑潘提恩,褻瀆了這份回憶。”
但潑潘提恩如小丑般騰空躍起,用腳跟磕出聲響;他拿腔作勢地站著,拳頭放在胸口,另一只胳膊伸向前方。“當我乞求寬恕!”服務生哭笑不得地看著他們。雨下大了。古德費羅坐在雨中,喝著咖啡。雨點敲打著他的太陽帽。“妹妹還不錯,”他看著潑潘提恩在廣場上肆情玩鬧,“米爾德里德,你知道的。雖然只有十一歲。”最后,他發現自己的燕尾服快要濕透了。他站起身,留了一皮阿斯特加一米利姆的錢在桌上,沖著潑潘提恩點點頭,此時的潑潘提恩正站著看他。廣場上已空無一人,除了穆罕默德· 阿里的騎馬塑像。曾經有多少次,他們就這樣看著彼此,在暮色將至的廣場上,他們的影子無論橫豎,與周遭風景相比都顯得非常渺小。假如我們可以在那一刻暫時確認某種設計論,那么這兩人就一定像是小小的棋子,可以被隨意擺在歐洲棋盤的任何位置。他倆是同色的棋子(雖然其中一個會站在上級的對角線后方以示尊敬),都在掃視著每個大使館的鑲花地板,以尋找敵人的蛛絲馬跡,或觀察每個雕像的臉以再度確信自己還有自我主導(也許,這即不幸意味著自我的人性)。此時的他們會努力忘卻一點,即無論你如何切分每個城市的正方棋格,它都不是什么有生命的東西。很快,兩人裝作正兒八經地轉過身,朝著相反的方向走開了:古德費羅回酒店,潑潘提恩從拉斯埃丁大街去土耳其廣場。在八點之前他會一直思考當前的局勢。
此時各處都是一團糟。英格蘭新近的殖民地英雄是基奇納總司令,他剛在喀土穆打了勝仗,現在正位于白尼羅州大約四百英里的地方,在叢林中摸索前進。據說在附近還有一個叫馬爾尚的將軍。英國不希望法國染指尼羅河谷地區。如果這兩撥部隊遭遇并惹出什么麻煩,新組建的法國內閣的外交部長德爾卡塞寧愿為此開戰。現在所有人都意識到,這場碰面不可避免了。基奇納接到命令不要主動進攻,避免一切挑釁行為。如果打仗,俄國會支持法國,而英國和德國正處于短暫的蜜月期,這當然意味著意大利和奧地利也是盟友。
潑潘提恩認為,莫德威爾普人生的一大樂趣是總不讓別人安生。他所求的,就是終有一戰。不是一次逐鹿瓜分非洲的小打小鬧,而是一次歐洲諸國的末日決戰,大家都玩兒完,弄個魚死網破,一拍兩散。潑潘提恩或許曾經搞不懂為什么他的對頭竟然會這么熱盼戰爭。但在玩犬兔追逐游戲的這十五年里,他已確信自己責無旁貸,應該去阻止這場末日決戰的到來。他覺得,這樣的一種結盟方式,只可能出現在一個間諜行業變得愈發集體化的西方世界,1848年的事件和整個歐洲大陸無政府主義者與極端分子的活動似乎已宣告:歷史不再是由單個君主的文治武功來締造,而是由烏合之眾,由淡藍色網格上那些趨勢圖和冰冷曲線來書寫的。所以這場戰斗注定會是老牌間諜和天真英國人之間的單打獨斗。他們孤零零地站在——天知道位于何處——荒蕪的競技場上。古德費羅知曉這場私人的戰斗,而毫無疑問莫德威爾普的下屬同樣也知道。他們是賣力的副手,關注的完全是國家利益,而他們的頭兒則在某個他們無法企及的高度,過招比拼。名義上潑潘提恩為英格蘭工作,而莫德威爾普為德國服務,但這也只是偶然罷了:假如他們的職位互換,他們很可能還是會選擇原來的立場。潑潘提恩知道,這是因為他和莫德威爾普同屬一個類型:即馬基雅維里黨人,這種人依然玩著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政治游戲,而他們所處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了。于是,這種自我設定的角色僅僅變成了一種尊嚴的表達,尤其是在一個對巴麥尊爵士巧取豪奪之功仍念念不忘的行業中。對潑潘提恩而言,多虧外交部還留著足夠多這種傳統精神,所以才能讓他自行其是。不過就算他們確實起過疑心,他也無從得知。每當他的個人任務與外交政策剛好相符時,潑潘提恩就會給倫敦送一份報告回去,而且似乎沒誰有過埋怨。
對潑潘提恩來說,現在的關鍵人物似乎是英國駐開羅的總領事克勞麥爾勛爵,此人是一個極其能干的外交官,而且行事謹慎,不會意氣用事:譬如發動戰爭。莫德威爾普有可能會采取暗殺行動嗎?似乎要計劃一下去趟開羅。盡可能地顯得毫無歹意;這當然不在話下。
奧地利領事館位于科迪瓦酒店的街對面,那里的盛況一如從前。古德費羅坐在寬大的大理石樓梯的底層臺階上,旁邊是一個姑娘,看樣子還不到十八歲,她和身上穿的長禮服一樣,顯得有點臃腫土氣。古德費羅的正裝因為淋了雨而有些皺;他的外套在腋下和腹部顯得有些緊;沙漠的風吹亂了他的金發,臉也是紅彤彤的,顯得有些不自在。潑潘提恩望著他的模樣,漸漸也意識到自己的模樣:他的晚禮服古怪奇特,是在戈登將軍被馬赫迪打敗的那一年買的。在這種聚會上,他是個無可救藥的土包子,常常就如同是死而復生的無頭戈登。至少在這些群星璀璨、盛裝打扮的外國貴族當中,他的確有那么古怪。那個過時的事:總司令重新奪回來了喀土穆,并一雪前恥,但人們早已忘記了這一切。他曾見過這個當年在中國戰場立過戰功的傳奇英雄,那時此人正站在格雷夫森德的防御土墻上。當時的潑潘提恩只有十多歲,可能被這場面沖昏了頭;他也的確如此。但是,從那一刻到布里斯托酒店聚首的歲月里,世事早已不同。那天夜里,他想到了莫德威爾普,想到了某種末日來臨的可能性;也許還想到了自己的落寞之感。但他并沒有去想那個中國的戈登,那個站在童年時代泰晤士河口的孤獨神秘的身影;據說當他在被圍的喀土穆坐以待斃時,短短一天頭發就全白了。
……
【序言/后記】
自 序
在我記憶中,這些故事寫于1958到1964年之間。其中四篇是我在大學里寫的—第五篇《秘密融合》(1964)才算像出自一個出師的學徒之手,而不是練筆之作。你可能已經知道,重讀自己二十年前寫的任何東西,都會對自尊心造成巨大打擊,甚至包括那些付訖的支票。重讀這些故事時,我第一反應是“噢,天哪”,同時還感受到了身體不適。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徹底重寫。這兩種沖動還是被中年人的沉靜壓制了下來,我現在假裝已經達到了一種清醒的境界,明白自己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年輕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完全把這家伙從我生命里抹掉。另一方面,假如通過某種尚未發明的技術,我能和他在今日邂逅,我會樂意借錢給他嗎?或者為了這次相逢,甚至愿意去街上喝杯啤酒,聊聊過去的事情?
我應該警告那些哪怕最善意的讀者,這里有一些非常令人膩煩的段落,也充滿了年少無知犯的錯。同時,我最希望的是,盡管它們不時有點裝腔作勢,傻里傻氣,設計不周,但讓故事留著這些破綻是有用的,它們能說明那些剛入門的小說家會犯哪些典型的錯誤,提醒年輕作家最好避免某些做法。
《小雨》是我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一個朋友在陸軍服役兩年,其間我正好在海軍服役,是他提供了故事細節。颶風確實發生過,我朋友所在的陸軍通信小分隊承擔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任務。我對自己寫作最不滿意的東西,大部分都以萌芽和更為高級的形式體現在這里了。我當時沒能認識到,首先,主人公的問題真實而有趣,本身就足以發展成一個故事。顯然,那時我覺得必須額外加一層雨的意象,必須要用《荒原》和《永別了,武器》的典故。我那時寫作的座右銘是“要有文學范兒”,這點子很糟糕,完全是我自己搗騰出來的,而且就照這么做了。
還有我糟糕的耳朵,同樣令人尷尬,它們破壞了很多對話,尤其是結尾部分。我那時對不同地區口音的認識還很淺薄。我曾注意到軍隊的人說話都被同化成了一種美國鄉村基調。沒多久,從紐約來的意大利裔街頭小混混說話聽上去就像南方農村人了,佐治亞州的水兵休假回來后,抱怨沒人聽得懂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的口音就像是北方佬。我來自北方,聽到的所謂“南方口音”其實就是這種在軍隊里通用的口音,而不是別的。我以為自己聽到了弗吉尼亞東部老百姓把/ow/音發成了/oo/,其實我不知道在真正的南方民間,不同地方(甚至是弗吉尼亞的不同地方)人們說話的口音都大為不同。在當時的電影中,這個錯誤也很明顯。具體來說,我在酒吧那一段的問題,不僅是我讓一個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孩剛開始就用我沒聽真切的南方東部二合元音說話,更糟的是,我堅持使之成了情節的一個要素—它對于萊文而言很重要,所以對故事發展也如此。我的錯誤是,在自己還沒一副好耳朵之前就去炫耀聽覺。
在故事的核心,最關鍵、最令我不安的,是我的敘事者(他幾乎等同于我,但不是我)處理死亡主題的方式非常糟糕。當我們說起小說的“嚴肅性”時,最終談的其實是對死亡的態度— 譬如人物面對它時會如何行事,或當它并非近在咫尺時,他們如何應對。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但這個話題很少向年輕作家提及,可能是因為他們尚處于打磨技巧的年紀,這種建議提了也是白搭。(我懷疑奇幻小說和科幻小說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年輕讀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書改造了空間和時間,人物可以輕易在時空連續體中任意旅行,因而得以擺脫身體面臨的危險和時間流逝的定數,所以死亡也往往不是什么問題。)
在《小雨》中,這些人物在用未成年人的方式對待死亡。他們逃避:他們睡懶覺,用委婉語談論死亡。當他們真的提到死亡時,就試著插科打諢。更糟的是,他們將之與性攪在一起。你們會發現在故事結尾,似乎發生了某種形式的性事,雖然從文本中難以確定。語言突然變得花哨難懂。也許這不僅僅是出于我年少時對于性的緊張。回想起來,我覺得這可能是出于整個大學時代亞文化中的一種普遍緊張。這是一種自我審查的傾向。這也是《嚎叫》《洛麗塔》和《北回歸線》的時代,這些作品在當時激起了執法部門的過度反應。甚至在那時能讀到的一些美國隱晦色情讀物中,都會用極其夸張的象征手法去避免描寫性行為。今天,這似乎都不再是問題,但在當時它確實是人們寫作時能真切感受到的一種限制。
我現在覺得這個故事有趣的地方,并不是態度的老派和幼稚,而是其階級視角。無論和平時期軍隊能有多少別的好處,它起碼能對社會結構提供一種絕佳的觀照。甚至對年輕人而言,有一點也很明顯,即普通人生活中常常未獲承認的等級差異在軍隊對于“軍官”和“士兵”的區分中體現得格外明顯和直接。人們驚訝地發現,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穿著卡其軍裝、戴著軍銜徽章、肩負重要職責的成年人其實可能是白癡。而那些工人階級出身的普通海軍士兵,雖然按理說屬于可能犯傻的那一撥,卻更可能展現出才能、勇氣、人性、智慧,以及其他受教育階層自以為擁有的美德。雖然用的是文學術語,但“肥腚”萊文在這個故事中的沖突,其實是對誰忠誠的問題。作為一個1950年代不問政治的學生,我當時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但以現在的視角來看,我覺得當時的寫作是出于一種兩難的困境,在某種意義上,當時大部分作家都得應付這個問題。
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它與語言有關。我們受到了各個方向的鼓舞—凱魯亞克和“垮掉派”作家,索爾· 貝婁在《奧吉· 馬奇歷險記》中的用詞,還有那些初露頭角的作家,像赫伯特· 戈爾德和菲利普· 羅斯等—從他們身上,我們發現在小說中至少允許同時存在兩種非常不同的英語。居然允許!那樣去寫其實沒問題!可當時誰知道呢?這種影響令人振奮,它使人獲得解放,給人強烈的鼓舞。它并不是兩選一,而是擴展了可能性。我認為我們并未有意識地去探索如何將之綜合起來,雖然也許我們本應如此。大學生和藍領工人在政治上并未成為同路人,這一點使得1960年代后期“新左派”的成功受到了限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兩個群體在交流方式上,存在著真實而隱形的階級力場。
當年,這種沖突就像大部分其他事物一樣,悄無聲息地進行著。它在文學中形成的對立,就是傳統小說與“垮掉派”小說的對立。雖然相距遙遠,但我們時常聽聞的一個事件就發生在芝加哥大學。譬如,那里有一個文學理論的“芝加哥學派”,廣受矚目和尊敬。與此同時,《芝加哥評論》發生過一次大震蕩,催生了支持“垮掉派”的《大桌》雜志。“芝加哥發生的事”成了某種無法想象的顛覆性威脅的簡稱。當時還有很多其他類似的爭論。為了抵抗傳統的強勢力量,我們當時喜歡向著圓心之外去運動,那些吸引我們的東西,有諾曼· 梅勒的散文《白種黑人》,有隨處可見的爵士樂唱片,還有一本書,我仍然相信它是偉大的美國小說——杰克· 凱魯亞克的《在路上》。
還有一種次要影響(至少對我而言),就是海倫· 沃德爾的《流浪的學者》,它在1950年代初重印,講述了中世紀大批年輕詩人們離開修道院,走到歐洲街頭,以歌唱的方式歡慶他們在學術院墻之外發現的廣闊生活天地。考慮到當時大學的環境,這其中的影射并不難想見。其實并不是說大學生活枯燥乏味,而是因為那些底層另類生活的信息不斷隱秘地滲透進大學的常青藤,我們開始感覺到校園外另一個嗡嗡作響的世界。我們中有些人無法抵抗誘惑,就離開了大學,去外面見識世界。其中相當一些人又回到大學,帶著第一手見聞去鼓動另外一些人也如此嘗試——1960年代的大學生退學潮就是由此發端。
……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