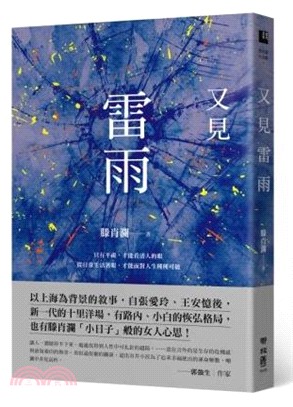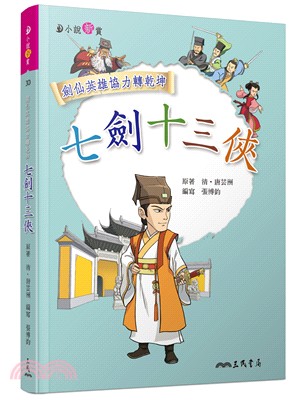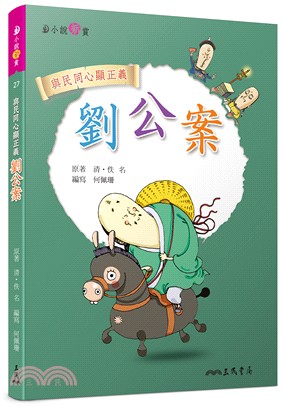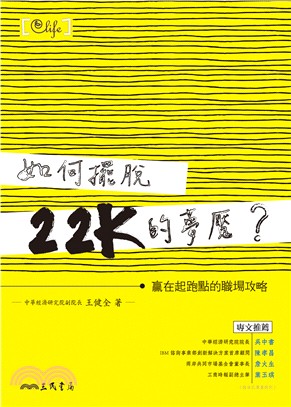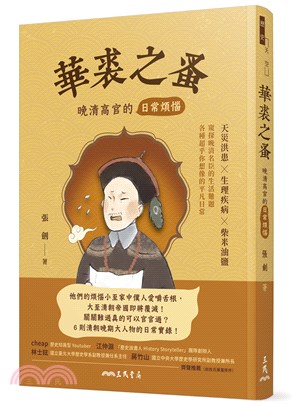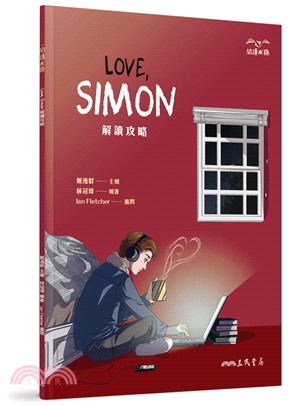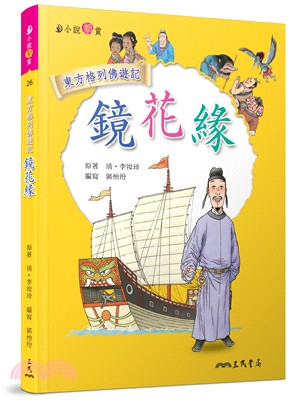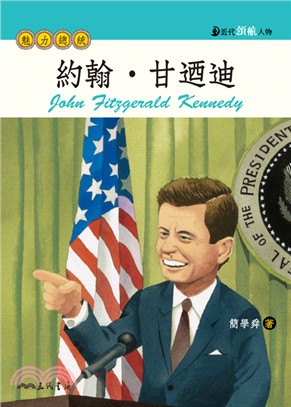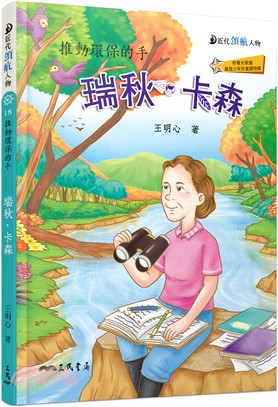又見雷雨
商品資訊
系列名:當代名家‧滕肖瀾作品集
ISBN13:9789570851151
出版社:聯經
作者:滕肖瀾
出版日:2018/05/23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1cm*14.8cm*1.8cm (高/寬/厚)
版次:1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6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滕肖瀾:我偏愛寫那些俗套的情節,最具挑戰性。愈是俗到極點、毫無新意,仿佛人人都能猜到後頭會是如何,便愈是有意思。跟人較勁,也跟自己較勁。又是向死而生,於夾縫中生出些不俗的意趣來。
自張愛玲、王安憶後,以當代上海城市為背景的書寫
屬於這時代的十里洋場、也是平民百姓的「小日子」!
滕肖瀾以通俗情節背景、精練文字描寫,從一般人的日常瑣碎間,挖掘平凡生活之不凡
收錄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作品〈美麗的日子〉,以及中篇小說〈又見雷雨〉、〈快樂王子〉
郭強生(作家):〈美麗的日子〉讓人一讀便停不下來。語言靈活,處處找得到人性中可扎針的縫隙。描寫生活裡的細瑣,婆媳之間的過招,意在言外的是生存的危機感與滄海桑田的無奈。看似通俗劇的搬演,道出市井小民為了追求幸福使出的渾身解數,嘲諷中亦見哀矜。
三則故事,寫的都是上海人家的日常,沒有轟轟烈烈的滿城風雨,著墨在隨處可見的大城小愛,也是大多數人生活的真實樣貌.語言文字生動精練,即便看似可預見結尾的安排,卻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細膩的文字描寫和豐富的角色情感給打動。
〈又見雷雨〉是向大師致敬之作,以話劇〈雷雨〉為本,講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快樂王子〉借王爾德的同名故事為引,是一則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成人童話,寫看似不切實際的純真初衷,卻也是對於人性那美好的想望;而末篇代表作〈美麗的日子〉,寫上海婆婆衛老太與兒子衛興國、外鄉媳婦姚虹之間的情感糾葛.把女人那心有定見,卻不為外人所道的內心世界描寫得異常細膩,婆媳間的相處宛如身懷內力絕學的高手,於日常間不動聲色地頻頻過招.既有真心情意,卻難免針鋒相對。
七○後的中生代作家,滕肖瀾曾提到,絕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如托爾斯泰那句經典的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難寫的故事應該就是寫幸福。因為相似,所以更難拿捏,因為有普遍性,所以反而無從下筆。如果有人能寫幸福的一家,讓人看得迴腸盪氣,又完全信服,這還真不是一般的功力。應該說,苦難比幸福好寫,少數人比多數人好寫。
自張愛玲、王安憶後,以當代上海城市為背景的書寫
屬於這時代的十里洋場、也是平民百姓的「小日子」!
滕肖瀾以通俗情節背景、精練文字描寫,從一般人的日常瑣碎間,挖掘平凡生活之不凡
收錄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作品〈美麗的日子〉,以及中篇小說〈又見雷雨〉、〈快樂王子〉
郭強生(作家):〈美麗的日子〉讓人一讀便停不下來。語言靈活,處處找得到人性中可扎針的縫隙。描寫生活裡的細瑣,婆媳之間的過招,意在言外的是生存的危機感與滄海桑田的無奈。看似通俗劇的搬演,道出市井小民為了追求幸福使出的渾身解數,嘲諷中亦見哀矜。
三則故事,寫的都是上海人家的日常,沒有轟轟烈烈的滿城風雨,著墨在隨處可見的大城小愛,也是大多數人生活的真實樣貌.語言文字生動精練,即便看似可預見結尾的安排,卻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細膩的文字描寫和豐富的角色情感給打動。
〈又見雷雨〉是向大師致敬之作,以話劇〈雷雨〉為本,講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快樂王子〉借王爾德的同名故事為引,是一則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成人童話,寫看似不切實際的純真初衷,卻也是對於人性那美好的想望;而末篇代表作〈美麗的日子〉,寫上海婆婆衛老太與兒子衛興國、外鄉媳婦姚虹之間的情感糾葛.把女人那心有定見,卻不為外人所道的內心世界描寫得異常細膩,婆媳間的相處宛如身懷內力絕學的高手,於日常間不動聲色地頻頻過招.既有真心情意,卻難免針鋒相對。
七○後的中生代作家,滕肖瀾曾提到,絕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如托爾斯泰那句經典的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難寫的故事應該就是寫幸福。因為相似,所以更難拿捏,因為有普遍性,所以反而無從下筆。如果有人能寫幸福的一家,讓人看得迴腸盪氣,又完全信服,這還真不是一般的功力。應該說,苦難比幸福好寫,少數人比多數人好寫。
作者簡介
滕肖瀾
女,1976年10月生於上海,於浦東國際機場工作。2001年開始寫作,至今發表中短篇小說約六十萬字。2006年4月出版小說集《十朵玫瑰》。上海作家協會新世紀首屆青年創作班學員,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因創作的中篇小說〈美麗的日子〉榮獲2014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2001年起開始寫作,在《人民文學》、《鍾山》、《小說界》、《青年文學》等雜誌發表中短篇小說六十餘萬字,小說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小說精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轉載。作品《四人行》被選入《2005年最受關注的中篇小說》及《2005年爭鳴小說精選》。
女,1976年10月生於上海,於浦東國際機場工作。2001年開始寫作,至今發表中短篇小說約六十萬字。2006年4月出版小說集《十朵玫瑰》。上海作家協會新世紀首屆青年創作班學員,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因創作的中篇小說〈美麗的日子〉榮獲2014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2001年起開始寫作,在《人民文學》、《鍾山》、《小說界》、《青年文學》等雜誌發表中短篇小說六十餘萬字,小說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小說精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轉載。作品《四人行》被選入《2005年最受關注的中篇小說》及《2005年爭鳴小說精選》。
目次
◆ 又見雷雨
◆ 快樂王子
◆ 美麗的日子
◆ 後記
書摘/試閱
又見雷雨
清晨六點,陽光從窗簾縫裡漏進一縷,延伸開來,先是窗臺,再是地板,隨即又爬上張一偉的臉,從額角到下巴,細細長長,像粉筆畫的一道。認識他八年了,鄭苹還是第一次離他這麼近,看得這麼仔細。男人長了張圓臉,皮膚又白淨,多少缺些英武氣。所以他留了落腮鬍子。過了一夜,鬍子愈發濃密了。鄭苹起身拿來剃鬚刀,塗上泡沫,替他刮鬍子。小心翼翼地,連下巴與頭頸接縫那樣難處理的地方,也刮得乾乾淨淨。他動也不動,任憑她擺佈。刮完了,她又拿自己的潤膚露,替他薄薄打上一層,免得皮膚發澀。
她朝他看。這麼一番折騰,他依然是不醒。
「是睡著了,還是昏過去了?」她湊近他,往他耳裡呵著熱氣,手指在他脖子輕輕撓著。他沒忍住,撲哧一笑,隨即一把抓住她的手。她另一隻手去搔他腰眼,他呵呵笑著,將那隻手也抓住。隨即在她嘴上親了一下。她朝他看,忽的,很嚴肅地道:
「過來,讓我吃一記耳光。」
他一怔:「什麼?」
「這些年,你讓我受的委屈,一記耳光便宜你了。」她正色道。
他把臉湊過去,「打吧。」
她舉起手,高高揚起,輕輕落下,嘻的一聲,按在他臉上,捋了捋。「算打過了,」她自說自話地點頭,「──以後不可以了,曉得吧?」
他看了她一會兒,那一瞬忽有些心酸,抓過她那只手,放在自己掌心裡,「其實我不值得你這樣,」他道,「你是個好女孩。」
「這年頭,好女孩都喜歡壞男人,」她歎道,「沒法子的事。」
吃早飯時,鄭苹接到維修鋪小弟的電話,說手機修好了,讓她有空去拿。鄭苹答應了,說今天就去。掛掉電話,興沖沖地告訴張一偉,「我爸那只手機修好了。」張一偉道:「那麼老的手機,還能修?」鄭苹道:「修是不難的,就是利太薄沒人肯修,虧得老耿有個親戚在手機店。蠻快,前天剛送過去,今天就修好了。」張一偉替她慶幸:「好險,這個手機要是修不好,難保你不去跳黃浦江。」鄭苹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嗔道:「沒那麼誇張。」
手機是父親的遺物。八年來鄭苹一直用這個手機。她曾把手機裡的視頻給張一偉看──父女倆在草地上搭帳蓬,因是剛買的帳蓬,不怎麼會弄,兩人嘻嘻哈哈折騰了半天,鄭母在鏡頭這邊數落他們「笨手笨腳,有這功夫,人家房子都造好了」。那天風很大,圖像有些抖,呼呼的風聲,比說話聲還大。這是鄭苹與父親最後一次合影。之後不到兩周,父親就去世了。手機摔過幾次,有點故障,上不了網,視頻和照片都導不出來,鄭苹只能把手機帶在身上,想念父親的時候便拿出來看。手機上了年頭,隔三岔五便出狀況。但通常是小毛病,湊合著能用。這次大修是因為前天跟周遊吵了一架,激動時隨手拿起手機便朝他掄去,砸在牆壁再掉下來,摔個稀爛。
「沒跟他拼命?」張一偉問。
「他賤命一條,宰了他我還要抵命,不值得。」
「為了什麼?」他朝她看,「還動手?」
「社裡的事,你也曉得,搞藝術和滿身銅臭的人,總歸說不到一塊去,」她岔開話題,「昨晚的事,──後悔嗎?」
他笑起來,「這話應該男人問女人才對。」
「我不後悔,這你八年前就該曉得了。」
「女人都不後悔,男人說後悔就忒不上路了。」
「主要是昨晚大家都喝醉了。否則我也不問了。」
「酒醉三分醒。」
「那又怎麼樣?什麼意思,我不懂。」
「再說下去就少兒不宜了。」他一把摟住她的肩膀。
鄭苹不喜歡他說話的語氣。人還在床上呢,就算撇清,也該有些過渡才是。沒一句話超過三兩,都是輕飄飄的。──其實也是意料之中。她和他之間,始終是隔了些什麼。八年前,同一天,同一個殯儀館,她的父親,還有他的父親。那是鄭苹第二次見到張一偉。她也不知道怎麼會踱到那裡。一間間過去,哭聲是會重疊的,這邊已入尾聲,漸漸隱去,這邊又掀起一陣,原先那些還未退盡,低低和著,又過一陣,又不知哪裡的哭聲摻雜進來,襯托得這邊更加層次分明。哭聲不同笑聲,笑的人一多,便覺得煩,自顧自的節奏;哭聲卻是往裡收的,一兩個人哭不成氣候,哭的人多了,悄無聲息地蔓延開,是另一種沉著的氣勢。鄭苹到的時候,張一偉父親已經推去火化了,張一偉母親被幾個親戚擁著坐在一邊。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站在角落裡低聲啜泣。鄭苹之前與他見過一面,是周遊父親安排的,請兩位遺孀出來相談。那天鄭苹與張一偉對面坐著,大人在桌子那邊談事,他們靜靜坐著。有人給他們倒上飲料,鄭苹喝了一口,張一偉碰都沒碰。車禍是由於張父過馬路闖紅燈,周父開車送周遊去學校,經過時避讓不及,車衝上非機動車道,又把騎車的鄭父撞倒。鄭父當場死亡,張父送到醫院急救無效,當晚去世。走路的、騎車的,都死了,按法律規定,即便事故原因與周父無關,機動車司機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周父花了些工夫打點,很快便全身而退。至於兩家的賠償金,他開出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數目。鄭母不作聲。張母還未開口,張一偉已站起來:「我不要錢,把爸爸還給我。」說完走到周父面前,霍的亮出一把水果刀,直直朝他胸口刺去。周父沒提防,竟被他刺個正著。送到醫院急救,醫生說再往左邊偏半寸,命就沒了。追悼會上,周父給兩家都送了花圈,人沒到場。那天張一偉倒是表現得很平和,鄭苹在門口靜靜看了他一會兒,想,這人和自己一樣,都沒了爸爸。鄭苹看到他的眼淚,始終在眶裡打轉,卻不落下來。本已平息下來的悲慟,那瞬間重又被勾起來。替自己,也替這個少年。
窗臺上放著一罐紙鶴。是鄭苹八年前疊的。花了整整一周的時間,在張一偉十九歲生日那天送給他,裡面還附了張卡片:「做朋友好嗎?」──結果被張一偉連東西帶卡片退了回來。那天恰恰是鄭苹動身去英國讀高中,行李都搬上車了,當著鄭母和周家父子的面,張一偉放下東西就走。鄭苹也不說話,面無表情地把紙鶴塞進包裡。這事後來被鄭母一直掛在嘴上,說鄭苹你這樣的人還會疊紙鶴啊,不像你的風格,做手榴彈土炸藥倒還差不多。
他看見紙鶴,先是一怔,應該是想起了當年的事。隨即瞥見鄭苹的目光,停頓一下:「現在送給我,行嗎?」鄭苹搖頭:「送給你不要,現在又來討。」他笑笑:「男人都是賤骨頭。」鄭苹嘿的一聲:「喜歡就拿去吧。」停了停,又問他:
「現在,你當我是朋友了嗎?」
「不是朋友是什麼?」他反問。
「不曉得,」她老老實實地道,「我總覺得你一直都挺恨我。」
「就算恨,也是恨周遊他爸。恨你幹嗎?」
「因為我媽嫁給周遊他爸了,所以你恨我也不是一點沒道理。」
「那,就算是愛恨交織吧。」他想了想,「其實,應該說是『同病相憐』更恰當。──同一天成了沒爸的孩子。」
「所以啊,我們更要對彼此好一點,」鄭苹一本正經地,「我們都是受過傷的小孩。別人不疼我們沒關係,我們要自己疼自己。──天底下沒有比我們更合適在一起的人了。」
有八年前的教訓,她故意扮傻大姐,把真話說得像傻話。這樣即便被他彈回去,也好少些尷尬。她以為他聽了會笑。誰知他只是低下頭吃盤裡的煎蛋,像是走神了。她等了他一會兒。女孩子這麼說,男人一點表示沒有。多少有些難為情。鄭苹打開收音機,尖銳的女聲陡的跳出來,「我愛你,轟轟烈烈最瘋狂,我愛你,轟轟烈烈卻不能忘──」
吃完早飯,張一偉先走了。鄭苹奔到陽臺,本想喊他回來帶把傘,今天說是有雷陣雨。但這男人走得匆忙,連背影也是義無反顧。鄭苹便有些氣不過。老夫老妻也就罷了,怎麼說也是第一次留下過夜,一步三回頭也在情理之中。可他的腳步毫無留戀。直到他走出社區,鄭苹才回屋。收拾一下,上網看微博。
照例在搜索欄裡打入關鍵字「鄭寅生,雷雨」。一條條看下去。大多都是老話,「民營話劇社進駐上海大劇院小劇場」、「場景漂亮,演員演技好」,也有人說「一張票送一大盒費列羅巧克力,差不多就值回一半票價了。人家虧本賺吆喝,我們樂得捧場。」往下翻,有人說「那個演魯貴的演員,長得像唐國強,好像以前也有點名氣的,怎麼會讓他演魯貴?」下面跟著一長串評論,有人說「沒錯,這人一看就是正義凜然的那種,演魯貴看著真彆扭,他每次低聲下氣地跟在周樸園邊上說話,我都想笑,感覺他像個潛伏在資本家身邊的地下黨。反倒是那個演周樸園的,看上去獐頭鼠目,一點也不像大資本家。也不曉得是怎麼選的角!」也有人反駁「誰說長得像唐國強就不能演壞人?好人壞人從臉上能看得出來嗎?再說周樸園也不是好人啊。照我說,讓他演魯貴才好呢,老是本色出演有什麼意思,反差越大越是能考驗演技。」又往下看了幾頁,與前陣子一樣,許多微博說的都是「魯貴」,一邊倒地認為這演員與以往的「魯貴」似乎有很大不同。
上月《雷雨》剛上演時,有記者採訪鄭苹,說作為一家民營話劇社,能入駐大劇院演出實屬不易。而且在行銷上別出心裁,比如母親節那場送康乃馨,憑票根參加抽獎,有咖啡券、電影票、聯華OK卡、雙飛自由行……特等獎甚至是一輛小轎車。「網上有您親自頒獎的視頻。您覺得,這次話劇演出之所以大獲成功,是否與這些行銷手段有關?還有,成本預算方面,您是怎麼控制的,說的更明確些,您不怕虧本嗎?」記者口氣裡難掩好奇。鄭苹回答得很簡單,「說句實話,我辦這個話劇社,不是為了賺錢,至於虧本,大家也不必替我擔心。我有贊助。那些行銷策略,都是別人替我想出來的,我只管排話劇,其它事情統統不管。」記者又問起駱以達,「有趣的是,十年前在上海人藝演出的那場《雷雨》,駱老師扮演的是周樸園。時至今日,他竟然演起了魯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逆轉。請問,您是如何請到他加盟的?又為什麼想到讓他來扮演魯貴?是一種噱頭嗎?」鄭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你說是噱頭,──那就算是吧。」記者最後問:「你們話劇社叫『鄭寅生話劇社』,請問,『鄭寅生』是誰,以他命名有特別意義嗎?」鄭苹如實相告:「鄭寅生是我父親,他生前也是個話劇演員。」
關於抽獎的事,鄭苹很早就對周遊表示了不滿,「玩得太過了,連公車上都是《雷雨》的廣告,你看過哪個話劇搞這麼大?送電影票咖啡券也就算了,你還給我弄輛小轎車出來,怎麼不送別墅送遊艇?」周遊說:「我就是怕搞得太大,所以才沒這麼幹。別墅有現成的,你要是答應,下次我就直接去三亞買遊艇了。」鄭苹無語,對付這樣的紈袴子弟,話一定要往狠裡說,「我非常不喜歡這樣,」鄭苹明確告訴他,「別學你爸捧戲子,他那是老一代的做派,八百年前就過時了。」周遊說:「我不捧戲子,我只捧你。你是戲子嗎?你是藝術總監。」鄭苹道:「我不是我媽,別說遊艇,你就是買飛機也沒戲。」周遊照例是笑笑,不妥協,也不跟她真吵。八年來,兩人像親戚,又像朋友。周遊跟她同歲,月分稍大些,初見面那陣客客氣氣,有些半路兄妹的味道,後來熟了,就比親兄妹還隨便,說話行事遊離於自己人和外頭人之間,好起來無所顧忌,狠起來又是剝皮拆骨。當然這主要是鄭苹單方面對周遊,尤其是鄭母剛嫁給周父那陣,面上看著無異,心裡只當他是半個仇人,眼神都是夾槍帶棒。說起來還是周遊難得,待鄭苹就不用說了,對鄭母也是不錯,按理說十幾歲的少年,對後母耍些刁也在情理之中,偏偏他這層看得極開。他曾對鄭苹半開玩笑地說,我爸是多情種子,這點我隨他。鄭苹只當聽不懂:「你爸討三個老婆,你也隨他?」他道,「就算討三個老婆,你也是最後白頭到老的那個。」鄭苹嘴上照例又是一頓揶揄,心裡曉得這話不假。她在英國讀書那幾年,他每隔兩個月便飛去看她。她回國辦話劇社,是他給她張羅,人脈上資金上,料理得妥妥當當。連話劇社門廳正中那幅山水畫,也是他周少爺的真跡。「換了別人,一百萬求我一幅,我都不肯。──你自己要拎得清。」周遊從小習畫,這幾年因為跟著父親學生意,便擱下了。在別人面前,他是少東家太子爺,唯獨對著鄭苹,就成了嘍囉跟班。抽獎那事,連他父親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吃飯時半真半假地訓他,說「總經理我另外找人當,下次調你去行銷部,看你是把好手。」以鄭苹的性格,貼心貼肺的朋友不多。周遊算是僅有的一個。愈是這樣,說話便愈是不講究,心裡想的便是嘴裡說的,一點不加工。也虧得他才忍受得住。他也慣了,好的壞的,中聽的不中聽的,都當補藥吃。從不與她較真。唯獨前天那次,他不知怎的,竟動了真性子。話越說越僵。
「張一偉要是真的喜歡你,我把頭割下來當球踢。」
「他不喜歡我,幹嘛跟我在一起?」
「說了你要生氣。」
「我不生氣,你說。」
「其實我不說你也曉得,這些年他明裡暗裡搞的小動作,加起來都有一籮筐了。在檢察院當了個小辦事員,就人五人六起來。他也不想想,我爸要真跟他頂真,單憑八年前那一刀,他早就進大牢了──」
「這跟我有關係嗎?」鄭苹打斷他,「說重點。」
「怎麼沒關係,你媽嫁給我爸,你就是半個姓周的,在那傢伙眼裡,你跟我們是一夥的。」
「那又怎麼樣?」鄭苹好笑,「所以他想要始亂終棄,或者,先姦後殺?」
周遊歎了口氣,「鄭苹你就裝傻吧。智商135的人,裝35,不累嗎?非要我把話說得那麼明白是不是?那好,我一條條列給你聽。先說那個姓王的女人,是他介紹進來當會計的吧?你也真是到位,二話不說就把老劉給辭了,給人家騰地方。他是變著法子來查帳,你不知道嗎?虧得現在是沒事,要是真有些什麼,我爸、我,還有你,統統都要吃牢飯。」
「你都說了沒事,那怕什麼?」鄭苹沖他一句。
「還有他媽,淋巴瘤晚期,是你自己說的,三個禮拜化療一次,每次打兩支‘美羅華’,一支兩萬多。丙種球蛋白,營養針,五百多一支,兩三天就要打一支。八年了,他早不找你,晚不找你,偏偏挑這個時候找你。為什麼?難不成找人要結婚沖喜?本來這也沒什麼,男人玩女人要花錢,女人玩男人當然也要花錢,我找個小明星睡一晚幾十萬,你給他媽住貴賓病房,大家都是花錢找樂子,什麼玩不是玩,是吧?可你要是來真的,就沒意思了。」
「還有呢?」鄭苹朝他看,「──說下去。」
「是你讓我說的,」周遊猶豫了一下,沒忍住:「也好,索性我給你兜頭澆盆冷水,讓你徹底清醒──男人嘛,就那麼回事,追了他那麼多年,順風蓬也扯得差不多了,見好就收。你長得不難看,身材也過得去,又是自己送上門,這麼便宜的事,不要白不要──」
手機就是那個時候砸壞的。周遊的額頭也撞出個桂圓大小的包。事後鄭苹多少有些後悔,吵就吵了,還動手,又不是小孩子。況且愈是這樣,便愈顯得自己心虛。該一笑了之才是。一股邪氣因那人而起,竟全出在周遊身上。鄭苹又想起前一日晚上,她和張一偉都醉了,他先送她回家,到了她家門口,她邀他進去坐坐。他沒有拒絕。兩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他伸手去解她的襯衫扣子,她問他,「你喜歡我嗎?」兩人都醉得很厲害,腦筋跟不上手,耳朵跟不上嘴。她完全不記得他是怎麼回答的,怎麼想也想不起來。只記得牆上的掛鐘「噠噠」地走著。是時間流動的聲音。此刻不知怎的,那句話忽然一下子從某個角落蹦了出來。──那時,他大著舌頭,貼著她的耳朵,輕聲道:
「我說喜歡你,你信嗎?」
清晨六點,陽光從窗簾縫裡漏進一縷,延伸開來,先是窗臺,再是地板,隨即又爬上張一偉的臉,從額角到下巴,細細長長,像粉筆畫的一道。認識他八年了,鄭苹還是第一次離他這麼近,看得這麼仔細。男人長了張圓臉,皮膚又白淨,多少缺些英武氣。所以他留了落腮鬍子。過了一夜,鬍子愈發濃密了。鄭苹起身拿來剃鬚刀,塗上泡沫,替他刮鬍子。小心翼翼地,連下巴與頭頸接縫那樣難處理的地方,也刮得乾乾淨淨。他動也不動,任憑她擺佈。刮完了,她又拿自己的潤膚露,替他薄薄打上一層,免得皮膚發澀。
她朝他看。這麼一番折騰,他依然是不醒。
「是睡著了,還是昏過去了?」她湊近他,往他耳裡呵著熱氣,手指在他脖子輕輕撓著。他沒忍住,撲哧一笑,隨即一把抓住她的手。她另一隻手去搔他腰眼,他呵呵笑著,將那隻手也抓住。隨即在她嘴上親了一下。她朝他看,忽的,很嚴肅地道:
「過來,讓我吃一記耳光。」
他一怔:「什麼?」
「這些年,你讓我受的委屈,一記耳光便宜你了。」她正色道。
他把臉湊過去,「打吧。」
她舉起手,高高揚起,輕輕落下,嘻的一聲,按在他臉上,捋了捋。「算打過了,」她自說自話地點頭,「──以後不可以了,曉得吧?」
他看了她一會兒,那一瞬忽有些心酸,抓過她那只手,放在自己掌心裡,「其實我不值得你這樣,」他道,「你是個好女孩。」
「這年頭,好女孩都喜歡壞男人,」她歎道,「沒法子的事。」
吃早飯時,鄭苹接到維修鋪小弟的電話,說手機修好了,讓她有空去拿。鄭苹答應了,說今天就去。掛掉電話,興沖沖地告訴張一偉,「我爸那只手機修好了。」張一偉道:「那麼老的手機,還能修?」鄭苹道:「修是不難的,就是利太薄沒人肯修,虧得老耿有個親戚在手機店。蠻快,前天剛送過去,今天就修好了。」張一偉替她慶幸:「好險,這個手機要是修不好,難保你不去跳黃浦江。」鄭苹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嗔道:「沒那麼誇張。」
手機是父親的遺物。八年來鄭苹一直用這個手機。她曾把手機裡的視頻給張一偉看──父女倆在草地上搭帳蓬,因是剛買的帳蓬,不怎麼會弄,兩人嘻嘻哈哈折騰了半天,鄭母在鏡頭這邊數落他們「笨手笨腳,有這功夫,人家房子都造好了」。那天風很大,圖像有些抖,呼呼的風聲,比說話聲還大。這是鄭苹與父親最後一次合影。之後不到兩周,父親就去世了。手機摔過幾次,有點故障,上不了網,視頻和照片都導不出來,鄭苹只能把手機帶在身上,想念父親的時候便拿出來看。手機上了年頭,隔三岔五便出狀況。但通常是小毛病,湊合著能用。這次大修是因為前天跟周遊吵了一架,激動時隨手拿起手機便朝他掄去,砸在牆壁再掉下來,摔個稀爛。
「沒跟他拼命?」張一偉問。
「他賤命一條,宰了他我還要抵命,不值得。」
「為了什麼?」他朝她看,「還動手?」
「社裡的事,你也曉得,搞藝術和滿身銅臭的人,總歸說不到一塊去,」她岔開話題,「昨晚的事,──後悔嗎?」
他笑起來,「這話應該男人問女人才對。」
「我不後悔,這你八年前就該曉得了。」
「女人都不後悔,男人說後悔就忒不上路了。」
「主要是昨晚大家都喝醉了。否則我也不問了。」
「酒醉三分醒。」
「那又怎麼樣?什麼意思,我不懂。」
「再說下去就少兒不宜了。」他一把摟住她的肩膀。
鄭苹不喜歡他說話的語氣。人還在床上呢,就算撇清,也該有些過渡才是。沒一句話超過三兩,都是輕飄飄的。──其實也是意料之中。她和他之間,始終是隔了些什麼。八年前,同一天,同一個殯儀館,她的父親,還有他的父親。那是鄭苹第二次見到張一偉。她也不知道怎麼會踱到那裡。一間間過去,哭聲是會重疊的,這邊已入尾聲,漸漸隱去,這邊又掀起一陣,原先那些還未退盡,低低和著,又過一陣,又不知哪裡的哭聲摻雜進來,襯托得這邊更加層次分明。哭聲不同笑聲,笑的人一多,便覺得煩,自顧自的節奏;哭聲卻是往裡收的,一兩個人哭不成氣候,哭的人多了,悄無聲息地蔓延開,是另一種沉著的氣勢。鄭苹到的時候,張一偉父親已經推去火化了,張一偉母親被幾個親戚擁著坐在一邊。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站在角落裡低聲啜泣。鄭苹之前與他見過一面,是周遊父親安排的,請兩位遺孀出來相談。那天鄭苹與張一偉對面坐著,大人在桌子那邊談事,他們靜靜坐著。有人給他們倒上飲料,鄭苹喝了一口,張一偉碰都沒碰。車禍是由於張父過馬路闖紅燈,周父開車送周遊去學校,經過時避讓不及,車衝上非機動車道,又把騎車的鄭父撞倒。鄭父當場死亡,張父送到醫院急救無效,當晚去世。走路的、騎車的,都死了,按法律規定,即便事故原因與周父無關,機動車司機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周父花了些工夫打點,很快便全身而退。至於兩家的賠償金,他開出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數目。鄭母不作聲。張母還未開口,張一偉已站起來:「我不要錢,把爸爸還給我。」說完走到周父面前,霍的亮出一把水果刀,直直朝他胸口刺去。周父沒提防,竟被他刺個正著。送到醫院急救,醫生說再往左邊偏半寸,命就沒了。追悼會上,周父給兩家都送了花圈,人沒到場。那天張一偉倒是表現得很平和,鄭苹在門口靜靜看了他一會兒,想,這人和自己一樣,都沒了爸爸。鄭苹看到他的眼淚,始終在眶裡打轉,卻不落下來。本已平息下來的悲慟,那瞬間重又被勾起來。替自己,也替這個少年。
窗臺上放著一罐紙鶴。是鄭苹八年前疊的。花了整整一周的時間,在張一偉十九歲生日那天送給他,裡面還附了張卡片:「做朋友好嗎?」──結果被張一偉連東西帶卡片退了回來。那天恰恰是鄭苹動身去英國讀高中,行李都搬上車了,當著鄭母和周家父子的面,張一偉放下東西就走。鄭苹也不說話,面無表情地把紙鶴塞進包裡。這事後來被鄭母一直掛在嘴上,說鄭苹你這樣的人還會疊紙鶴啊,不像你的風格,做手榴彈土炸藥倒還差不多。
他看見紙鶴,先是一怔,應該是想起了當年的事。隨即瞥見鄭苹的目光,停頓一下:「現在送給我,行嗎?」鄭苹搖頭:「送給你不要,現在又來討。」他笑笑:「男人都是賤骨頭。」鄭苹嘿的一聲:「喜歡就拿去吧。」停了停,又問他:
「現在,你當我是朋友了嗎?」
「不是朋友是什麼?」他反問。
「不曉得,」她老老實實地道,「我總覺得你一直都挺恨我。」
「就算恨,也是恨周遊他爸。恨你幹嗎?」
「因為我媽嫁給周遊他爸了,所以你恨我也不是一點沒道理。」
「那,就算是愛恨交織吧。」他想了想,「其實,應該說是『同病相憐』更恰當。──同一天成了沒爸的孩子。」
「所以啊,我們更要對彼此好一點,」鄭苹一本正經地,「我們都是受過傷的小孩。別人不疼我們沒關係,我們要自己疼自己。──天底下沒有比我們更合適在一起的人了。」
有八年前的教訓,她故意扮傻大姐,把真話說得像傻話。這樣即便被他彈回去,也好少些尷尬。她以為他聽了會笑。誰知他只是低下頭吃盤裡的煎蛋,像是走神了。她等了他一會兒。女孩子這麼說,男人一點表示沒有。多少有些難為情。鄭苹打開收音機,尖銳的女聲陡的跳出來,「我愛你,轟轟烈烈最瘋狂,我愛你,轟轟烈烈卻不能忘──」
吃完早飯,張一偉先走了。鄭苹奔到陽臺,本想喊他回來帶把傘,今天說是有雷陣雨。但這男人走得匆忙,連背影也是義無反顧。鄭苹便有些氣不過。老夫老妻也就罷了,怎麼說也是第一次留下過夜,一步三回頭也在情理之中。可他的腳步毫無留戀。直到他走出社區,鄭苹才回屋。收拾一下,上網看微博。
照例在搜索欄裡打入關鍵字「鄭寅生,雷雨」。一條條看下去。大多都是老話,「民營話劇社進駐上海大劇院小劇場」、「場景漂亮,演員演技好」,也有人說「一張票送一大盒費列羅巧克力,差不多就值回一半票價了。人家虧本賺吆喝,我們樂得捧場。」往下翻,有人說「那個演魯貴的演員,長得像唐國強,好像以前也有點名氣的,怎麼會讓他演魯貴?」下面跟著一長串評論,有人說「沒錯,這人一看就是正義凜然的那種,演魯貴看著真彆扭,他每次低聲下氣地跟在周樸園邊上說話,我都想笑,感覺他像個潛伏在資本家身邊的地下黨。反倒是那個演周樸園的,看上去獐頭鼠目,一點也不像大資本家。也不曉得是怎麼選的角!」也有人反駁「誰說長得像唐國強就不能演壞人?好人壞人從臉上能看得出來嗎?再說周樸園也不是好人啊。照我說,讓他演魯貴才好呢,老是本色出演有什麼意思,反差越大越是能考驗演技。」又往下看了幾頁,與前陣子一樣,許多微博說的都是「魯貴」,一邊倒地認為這演員與以往的「魯貴」似乎有很大不同。
上月《雷雨》剛上演時,有記者採訪鄭苹,說作為一家民營話劇社,能入駐大劇院演出實屬不易。而且在行銷上別出心裁,比如母親節那場送康乃馨,憑票根參加抽獎,有咖啡券、電影票、聯華OK卡、雙飛自由行……特等獎甚至是一輛小轎車。「網上有您親自頒獎的視頻。您覺得,這次話劇演出之所以大獲成功,是否與這些行銷手段有關?還有,成本預算方面,您是怎麼控制的,說的更明確些,您不怕虧本嗎?」記者口氣裡難掩好奇。鄭苹回答得很簡單,「說句實話,我辦這個話劇社,不是為了賺錢,至於虧本,大家也不必替我擔心。我有贊助。那些行銷策略,都是別人替我想出來的,我只管排話劇,其它事情統統不管。」記者又問起駱以達,「有趣的是,十年前在上海人藝演出的那場《雷雨》,駱老師扮演的是周樸園。時至今日,他竟然演起了魯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逆轉。請問,您是如何請到他加盟的?又為什麼想到讓他來扮演魯貴?是一種噱頭嗎?」鄭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你說是噱頭,──那就算是吧。」記者最後問:「你們話劇社叫『鄭寅生話劇社』,請問,『鄭寅生』是誰,以他命名有特別意義嗎?」鄭苹如實相告:「鄭寅生是我父親,他生前也是個話劇演員。」
關於抽獎的事,鄭苹很早就對周遊表示了不滿,「玩得太過了,連公車上都是《雷雨》的廣告,你看過哪個話劇搞這麼大?送電影票咖啡券也就算了,你還給我弄輛小轎車出來,怎麼不送別墅送遊艇?」周遊說:「我就是怕搞得太大,所以才沒這麼幹。別墅有現成的,你要是答應,下次我就直接去三亞買遊艇了。」鄭苹無語,對付這樣的紈袴子弟,話一定要往狠裡說,「我非常不喜歡這樣,」鄭苹明確告訴他,「別學你爸捧戲子,他那是老一代的做派,八百年前就過時了。」周遊說:「我不捧戲子,我只捧你。你是戲子嗎?你是藝術總監。」鄭苹道:「我不是我媽,別說遊艇,你就是買飛機也沒戲。」周遊照例是笑笑,不妥協,也不跟她真吵。八年來,兩人像親戚,又像朋友。周遊跟她同歲,月分稍大些,初見面那陣客客氣氣,有些半路兄妹的味道,後來熟了,就比親兄妹還隨便,說話行事遊離於自己人和外頭人之間,好起來無所顧忌,狠起來又是剝皮拆骨。當然這主要是鄭苹單方面對周遊,尤其是鄭母剛嫁給周父那陣,面上看著無異,心裡只當他是半個仇人,眼神都是夾槍帶棒。說起來還是周遊難得,待鄭苹就不用說了,對鄭母也是不錯,按理說十幾歲的少年,對後母耍些刁也在情理之中,偏偏他這層看得極開。他曾對鄭苹半開玩笑地說,我爸是多情種子,這點我隨他。鄭苹只當聽不懂:「你爸討三個老婆,你也隨他?」他道,「就算討三個老婆,你也是最後白頭到老的那個。」鄭苹嘴上照例又是一頓揶揄,心裡曉得這話不假。她在英國讀書那幾年,他每隔兩個月便飛去看她。她回國辦話劇社,是他給她張羅,人脈上資金上,料理得妥妥當當。連話劇社門廳正中那幅山水畫,也是他周少爺的真跡。「換了別人,一百萬求我一幅,我都不肯。──你自己要拎得清。」周遊從小習畫,這幾年因為跟著父親學生意,便擱下了。在別人面前,他是少東家太子爺,唯獨對著鄭苹,就成了嘍囉跟班。抽獎那事,連他父親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吃飯時半真半假地訓他,說「總經理我另外找人當,下次調你去行銷部,看你是把好手。」以鄭苹的性格,貼心貼肺的朋友不多。周遊算是僅有的一個。愈是這樣,說話便愈是不講究,心裡想的便是嘴裡說的,一點不加工。也虧得他才忍受得住。他也慣了,好的壞的,中聽的不中聽的,都當補藥吃。從不與她較真。唯獨前天那次,他不知怎的,竟動了真性子。話越說越僵。
「張一偉要是真的喜歡你,我把頭割下來當球踢。」
「他不喜歡我,幹嘛跟我在一起?」
「說了你要生氣。」
「我不生氣,你說。」
「其實我不說你也曉得,這些年他明裡暗裡搞的小動作,加起來都有一籮筐了。在檢察院當了個小辦事員,就人五人六起來。他也不想想,我爸要真跟他頂真,單憑八年前那一刀,他早就進大牢了──」
「這跟我有關係嗎?」鄭苹打斷他,「說重點。」
「怎麼沒關係,你媽嫁給我爸,你就是半個姓周的,在那傢伙眼裡,你跟我們是一夥的。」
「那又怎麼樣?」鄭苹好笑,「所以他想要始亂終棄,或者,先姦後殺?」
周遊歎了口氣,「鄭苹你就裝傻吧。智商135的人,裝35,不累嗎?非要我把話說得那麼明白是不是?那好,我一條條列給你聽。先說那個姓王的女人,是他介紹進來當會計的吧?你也真是到位,二話不說就把老劉給辭了,給人家騰地方。他是變著法子來查帳,你不知道嗎?虧得現在是沒事,要是真有些什麼,我爸、我,還有你,統統都要吃牢飯。」
「你都說了沒事,那怕什麼?」鄭苹沖他一句。
「還有他媽,淋巴瘤晚期,是你自己說的,三個禮拜化療一次,每次打兩支‘美羅華’,一支兩萬多。丙種球蛋白,營養針,五百多一支,兩三天就要打一支。八年了,他早不找你,晚不找你,偏偏挑這個時候找你。為什麼?難不成找人要結婚沖喜?本來這也沒什麼,男人玩女人要花錢,女人玩男人當然也要花錢,我找個小明星睡一晚幾十萬,你給他媽住貴賓病房,大家都是花錢找樂子,什麼玩不是玩,是吧?可你要是來真的,就沒意思了。」
「還有呢?」鄭苹朝他看,「──說下去。」
「是你讓我說的,」周遊猶豫了一下,沒忍住:「也好,索性我給你兜頭澆盆冷水,讓你徹底清醒──男人嘛,就那麼回事,追了他那麼多年,順風蓬也扯得差不多了,見好就收。你長得不難看,身材也過得去,又是自己送上門,這麼便宜的事,不要白不要──」
手機就是那個時候砸壞的。周遊的額頭也撞出個桂圓大小的包。事後鄭苹多少有些後悔,吵就吵了,還動手,又不是小孩子。況且愈是這樣,便愈顯得自己心虛。該一笑了之才是。一股邪氣因那人而起,竟全出在周遊身上。鄭苹又想起前一日晚上,她和張一偉都醉了,他先送她回家,到了她家門口,她邀他進去坐坐。他沒有拒絕。兩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他伸手去解她的襯衫扣子,她問他,「你喜歡我嗎?」兩人都醉得很厲害,腦筋跟不上手,耳朵跟不上嘴。她完全不記得他是怎麼回答的,怎麼想也想不起來。只記得牆上的掛鐘「噠噠」地走著。是時間流動的聲音。此刻不知怎的,那句話忽然一下子從某個角落蹦了出來。──那時,他大著舌頭,貼著她的耳朵,輕聲道:
「我說喜歡你,你信嗎?」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