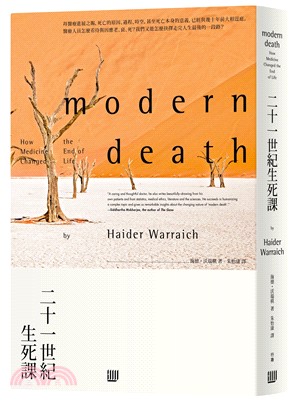二十一世紀生死課
商品資訊
系列名:FOCUS
ISBN13:9789869634847
替代書名:Modern Death: How Medicine Changed the End of Life
出版社:行路
作者:海德・沃瑞棋
譯者:朱怡康
出版日:2018/12/05
裝訂/頁數:平裝/384頁
規格:22.5cm*16cm*2.4cm (高/寬/厚)
重量:544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死亡的原因、地點、時間及過程,都已和幾十年前截然不同。死亡的形貌幡然轉變,我們對它的了解也需從頭來過。海德・沃瑞棋醫師承繼醫界對生命與臨終的思索,本書企圖心直逼努蘭經典之作《死亡的臉》,刻劃細膩不遜葛文德《凝視死亡》,從從細胞之死到死亡的本質定義談起,內容涵蓋死亡的生理機制、死亡社會學、拒絕心肺復甦術(DNR)議題、腦死與心臟死(死亡定義)、死亡與宗教、重症照顧者的重負、代理人問題、安樂死/自殺/醫師協助自殺、死亡與社群媒體等議題。
除了自身臨床服務時的遭遇,作者還以寫論文的精神去經營各章,因此有不少相關數據的蒐集與解讀,比如全球最早安樂死入法的地方,推行的影響與原本的預期有何落差,這結果又意味著什麼?全書內容含括社會、宗教、財務、地理及醫學研究,對於現今我們人生最後一段路的樣貌,如何被各種風潮和事件改變,這本書提供了扎實豐富的回答。
●本書特色
(1)涵蓋死亡的生理機制、死亡社會學、DNR議題、死亡定義、重症照顧者的重負、醫療代理人、安樂死/自殺/醫師協助自殺、死亡與社群媒體等議題,為目前台灣書市此面向書籍中最為全面者。
(2)結合臨床醫療遭遇、判例分析、嚴謹統計數據與學術論述,跨演化生物學、醫學、社會學、認知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觀點。
(3)各章內容提示請參閱下方的「目錄」引文。
作者簡介
出身巴基斯坦,二〇〇九年自當地醫學院畢業後,前往貝絲・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接受住院醫師訓練(該院為哈佛醫學院主要教學醫院之一),現為杜克大學醫療中心心臟科醫師,並定期為《紐約時報》、《大西洋雜誌》、《華爾街日報》、《衛報》、《洛杉磯時報》等報刊撰稿。
譯者
朱怡康
專職譯者,守備範圍以宗教、醫療、政治與科普為主。譯有《漫畫哲學之河》、《漫畫心理學》、《人性較量: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自閉群像: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 走到接納多元》、《偏見地圖1:繪製成見》、《偏見地圖2:航向地平線》、《塔木德精要》、《跟教宗方濟各學領導》、《資訊分享,鎖得住?還在抱怨盜版?可是,網路科技已經回不去了!》、《複製、基因與不朽》(合譯)等書。其他歷史、科普譯作散見於《BBC知識》月刊。
名人/編輯推薦
●台灣推薦者
○楊育正,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董事長,馬偕紀念醫院資深主治醫師
○余尚儒,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理事長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魏書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白明奇,成功大學神經學教授、老年學研究所所長
○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系主任
○郭慧娟,「死亡咖啡館」講座推行人
○許禮安,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理事
○朱為民,老年醫學、安寧緩和專科醫師
●各界好評
「文字優雅之中帶著一抹感傷,掩卷久久不能自已。全書醫者之心溢於言表,流露關懷之餘不失冷靜思索,文筆優美,敘事流暢,病例、數據信手捻來,巧妙地將醫學倫理、文學與科學冶於一爐。死亡議題極其複雜,沃瑞棋卻成功鋪陳出人性脈絡,並對死亡在現代社會裡的變化提出深刻洞察。」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暢銷書《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和《萬病之王》的作者
「海德・沃瑞棋醫師堪稱當代維吉爾,引領我們走過複雜而混亂的現代死亡之旅。他聰慧過人,思考深刻,卻又謙虛誠懇,一步步揭開CPR、DNR、腦死和怠速代號的奧祕。他也點出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大多數醫院裡,死亡都是由最年輕、最缺乏經驗的醫生處理。最重要的是,沃瑞棋醫師諄諄善誘,再次提醒我們顛簸不破的道理:在人生盡頭,與親人同在、與知交同在、與清明同在,才是最重要的事,不論現在或未來都是如此。」
——安娜・萊斯曼(Anna Reisman)醫師,耶魯醫學院醫學人文計畫主持人
「沃瑞棋對人類死亡的歷史作了詳盡而豐富的研究,在此同時,他也完全沒忽略死亡在今天的幾個主要特點——否認、不平等、過度治療和機構化。在人口逐漸老化的此刻,醫療技術的快速進展持續改變健康照顧的樣貌,而醫生就是我們最好的探路者和引路人。沃瑞棋這本書內容豐富、全面而完整,是死亡議題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
——安・紐曼(Ann Neumann),《理想的告別》作者
「面對死亡是所有人最終的學習,讓人學習謙卑和愛,然而每人只有一次機會,不能重來。沃瑞棋醫師此書以當代社會、醫療的眼光描繪死亡,給人提早學習面對的機會。」——楊育正教授,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董事長 馬偕紀念醫院資深主治醫師
「內容相當考據,是一本有深度、認真思考死亡的好書,非常適合成為「醫學教育」,「生死教育」的參考讀物,對於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尤能擴大他們對於死亡的認識與想像。」——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理事長 余尚儒
「本書主要根據地區醫院住院醫師的臨床服務經驗,卻能橫跨演化生物學、醫學、社會學、認知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觀點,交織學術論述、判例分析與臨床故事,還原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進行詮釋,關照臨床場域的移民文化衝擊,以及醫學與宗教/靈性的藕斷絲連,是引人入勝的書寫方式,對昆蘭案的社會影響和臨終照顧議題的評論尤其發人深省。」
——魏書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海德・沃瑞棋以科學家的冷靜之眼、醫生的人道心腸,細心檢視死亡在現代社會的樣貌,歷史、解剖學和公共政策在他精湛的敘事中合而為一。對於如何好好活到人生最後一刻,這本書提供了溫暖而全面的指引。」
——艾倫・古德曼(Ellen Goodman),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我懂你的意思》和《存參》(Paper Trail)作者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是『安寧療護與生死學』的社會教育,總覺得大眾對於臨終關懷與安寧療護的常識極度缺乏,閱讀這本書可以對照台灣民眾的社會觀念。死亡在日常生活中從四面八方包圍著我們,『死』不是『生』的反義詞,而生與死是一條連續線。」
——許禮安,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理事
「一本內容充實、反省深刻的好書,巧妙融合歷史事實、統計數據及人文關懷,並展現極為傑出的敘事技巧。主題豐富精彩,我讀得津津有味,幾乎忘了它的主題是死亡。非常感謝沃瑞棋醫師送給讀者這麼好的禮物,一本深具啟發的好書!它的確是難得之作,我非常喜歡,也推薦大家閱讀。」
——桑吉夫・邱普拉(Sanjiv Chopra),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
「沃瑞棋研究扎實,除適時補充親身經歷的故事之外,對文學、神學、統計數據、法學理論及科學知識亦信手捻來。文詞誠摯動人,佐證資料充足,全書深具說服力⋯⋯真誠而全面地檢視了這個常被忽視的課題。沃瑞棋學養豐富,言詞懇切,本書誠為認識死亡議題不可或缺之作。書中對於死亡的跨學科研究十分出色,作者對於該如何增進(而非迴避)死亡議題亦深具洞見。文字曉暢易讀,資訊新穎即時。」——《書架情報網》
「從最微觀的細胞之死,到生命與死亡的哲學大哉問,海德・沃瑞棋邀請讀者一同思索死亡與臨終的寓意與事實。沃瑞棋帶領我們穿越現代死亡的『醫療化』,重探我們似乎已經遺失的深厚人性。他的文筆、聰慧、勇氣與謙虛,造就出這本不可多得的好書。這本書內容豐富,筆觸優美,我讀得欲罷不能。」
——艾娃・約瑟夫(Eve Joseph),《夾縫之間》(In the Slender Margin)作者
「兼具史家的好奇、醫師的透澈與詩人的靈魂,海德・沃瑞棋為今日死亡繪出一幅驚人的畫像。現代社會企圖解開痛苦之謎,但諷刺的是,這項探索撞上我們內心深處最古老的恐懼。沃瑞棋醫師冷靜爬梳,揭開科學如何改變了我們對死亡的理解,但在此同時,他也謙卑接受我們無法克服死亡的基本事實,同時坦誠接受:在死亡面前,我們只是凡人。」
——拉斐爾・康柏(Rafael Campo)醫師,哈佛醫學院助理教授,著有《另類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
「既冷靜剖析細胞與身體之死的已知與未知,也敏銳掌握臨終議題的文化變遷,例如病患開始在社群媒體上貼文,公開分享自己的最後一段路。沃瑞棋以深具同情的筆調記下他所見證的故事,娓娓道出現代社會裡的人如何面對死亡。」——《科學人》
「身為心臟科醫師,海德・沃瑞棋日日與死亡交手,時時見證喪親之慟,也因此能細膩觀察近年臨終照顧的變化。他的成果相當豐碩,小至細胞之死,大至死亡對社會的衝擊,都在一個個重症案例、醫學軼事和科學事實間串聯起來。」——《自然》
「醫學進展已然挪移生與死的界線,同時為醫師和病患帶來極具爭議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生死課》中,沃瑞棋醫師不但精心探究這些議題,也為醫學史補充了生死邊緣的可貴記錄,這些故事縱然讓人時而不安,時而困惑,卻也發人省思,深具啟發意義。」——《今日心理學》
「沒有議題像死亡這樣人人在意——卻也人人不安。想了解這個諱莫如深的課題,海德・沃瑞棋的這本書是必讀之作,他清晰地點出死亡對當前美國的意義,也勸告我們追求更合理也更溫和的結局。」
——丹妮耶蕾・歐弗里(Danielle Ofri)醫師,藥學博士,著有《病人說的是什麼,醫生又聽見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從這本書獲益。沃瑞棋醫師兼具智慧、熱情與研究精神,為人生在世最陰暗的議題帶來光亮。這本書內容廣博如百科全書,每一頁都充滿啟發。」
——史蒂芬・奇爾南(Stephen P. Kiernan),著有《最後的權利》(Last Rights)和《蜂鳥》(The Hummingbird)
「這本書訴說的故事無比精彩:我們向來以為生死之別清楚簡單,為什麼它現在變得這麼複雜、又這麼重要?儘管這項問題充滿挑戰,海德・沃瑞棋仍勇往直前,以清晰、幽默、知性而熱情的態度娓娓道來。我非常喜歡這本書。」
——丹尼爾・華勒斯(Daniel Wallace),《大智若魚》(Big Fish)作者
「死亡,並不是生的反面,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透過認識死亡,我們更知道如何好好生活。誠摯推薦這本書。」——朱為民,老年醫學、安寧緩和專科醫師
「內容廣博,筆調輕快,娓娓道來死亡與現代醫學的歷史與相互影響,讀來欲罷不能。」
——凱蒂・巴特勒(Katy Butler),暢銷書《偽善的醫療》(Knocking on Heaven's Door)作者
目次
我的病人躺在床上進入彌留,他的家人都圍在身邊。我是房裡年紀最輕的一個,但每個人都望著我等我發話。他們的人生閱歷遠勝於我,但對於死亡,他們所知有限。為了他們,為了無數容我陪伴度過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的人,為了我自己,也為了其他醫護人員,但願這本書能讓我們更有準備,更知道如何幫助他們。但願它好好講出了一個故事――一個我們時代無比重要的故事。
第一章 細胞之死
生醫的進展,使我們對死亡的認知在上個世紀經歷了劇烈演進。目前已知細胞的死亡機制主要有三:凋亡、壞死,以及自噬;三者都有重要的形上意涵。細胞和我們一樣抗拒老化,但損害已難以彌補時,它們更懂得審時度勢,汰舊換新以延續生命;細胞層次的「長生不死」就是癌症。促成死亡的許多機制,對維繫生命也同樣不可或缺,對個體來說是如此,對整個生態系來說也是。我們與老化、疾病與死亡的對抗,帶來的後果就跟細胞企圖不死一樣,它們已深深撼動了經濟與社會結構。
第二章 抗死延生的戰爭
一八五〇年代之後,隨著細菌感染知識的增長、公衛系統的建立,以及麻醉與疫苗技術的發展,死亡的神祕色彩逐漸淡去,醫學終於成了一門科學,它澈底顛覆了人類的經驗,目前看來也不會走上回頭路。世界各地的預期壽命已長足增加,我們與慢性病共存的失能歲月卻也逐漸拉長。現在,美國人大多是被慢性疾病一點一滴磨蝕殆盡――大多數慢性病恐怕不是因為醫學未能阻擋死亡,反而是因為醫學防守得太成功。人瑞是現今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年齡組,這個現象也引起一些相當有趣的演化課題。
第三章 死亡今何在
如今安逝於自家臥榻已是難得的福份。死亡「醫院化」是大多數工業化經濟體的普遍現象,這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列為重要問題。這種趨勢的成因複雜,涵蓋經濟、社會、人口、環境、心理等諸多層面,只有少數和醫學、健康或疾病本身有關。死於何處與疾病性質和失能部位有關,也深受婚姻狀態影響,另外醫療服務取得容易也是把雙刃劍。以往儘管死亡機構化的辯論進行得如火如荼,卻看不到病人和他們的觀點,如今在家去世的呼求和玉成其事的努力,漸漸在促進醫療品質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四章 拒絕急救的一課
一九五〇年代,伊布森為了幫助小兒麻痺症患者呼吸,設計出一套人工呼吸器,他在醫學期刊發表這項成果後,全球醫院爭相仿效,它也成為加護病房照顧呼吸困難病患的標準程序。一九六〇年,庫文霍芬、裘德和尼克鮑克發表論文,一舉整合現代CPR的三項要點(供氧、體外去顫與按壓胸口),此後不僅急診醫療如虎添翼,連大多數人生命結束的方式都發生改變。然而,醫學固然強化了我們的生存能力,卻也開始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凱倫・安・昆蘭的父母為了讓醫師停止治療,提出訴訟,這件時代大案成了「死亡權」運動的先聲。
第五章 重劃生死之界
心臟向來被視為生命之所繫,但新的技術進展(如呼吸器和心肺復甦術)嚴重挑戰死亡的定義。二十世紀上半葉,探索生命跡象的重心從心肺轉向大腦,但一九二〇年代漢斯・伯格記錄下人類第一份腦電波圖後幾十年,腦電波圖透露的生死線索始終無人能識。安慰劑效應研究先驅亨利・畢契爾曾撰文探討「無望恢復意識之病患」的倫理議題,論及死亡時間該怎麼訂,爾後受哈佛醫學院之邀成立委員會,該團隊發表的結論對死亡在社會、法律、醫學、哲學等各層面帶來深刻影響,並且讓「腦死」一詞舉世皆知,不過部分委員會成員與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默里都因「腦死」一詞可能引發爭議,表明反對……
第六章 當心跳停止
隨著麻醉技術和衛生條件有所進展,外科醫生獲得夢寐以求的珍寶――時間,爾後手術領域大幅拓展,連移植人體器官都不再是空中樓閣。這不僅顛覆自古以來的死亡概念,也迫使醫師重新思考該如何客觀地界定死亡,並面對隨之而來的倫理與法律後果。由於器官越是新鮮,移植手術就越可能成功,為了保障病人不受外科醫生覬覦,也為了防止死亡扭曲為器官爭奪戰,美國於一九六八年通過的《統一器官捐贈法》和後續修訂都明確宣告:只能從已經死亡的人身上取得器官(死後捐贈原則)。
第七章 六合之外
雖然乍聽之下相當違反直覺,但死亡在過去難以預測,反倒使人更不懼死。如今在已開發國家,絕大多數人都能活到過去認定的高壽,於是人們也開始依照現代預期壽命規劃人生,這可能使現代人比以往任何時代的人更恐懼死亡。醫學在短短幾十年內迅速疏離化和世俗化,它促成的死亡生態變化,是人類比以前更恐懼死亡的另一原因。雖然年齡、性別、病情、種族和社經條件都會影響病人的決定,但宗教信仰往往一枝獨秀,獨立於其他因素而直接左右思考方向。若想化解對死亡的恐懼,變不能不談宗教與靈性追求的作用。
第八章 照顧之擔
不過幾十年前,慢性病並不普遍,長期失能的人極少,照顧老人和臨終病人並不是什麼負擔。然而隨著平均壽命延長,會有越來越多人得陪伴至親走向苦候已久的死亡。根據美國的調查,五分之一的照顧者最後決定辭去工作,在志願照顧過程中耗盡大半積蓄的人則多達三分之一。在這段步步煎熬的過程中,照顧者逐漸化為「隱形患者」,但他們不在醫療機構業務範圍,其需求也常無人聞問。照顧者還必須面對另一大考驗:很多病人即使大限將至,仍不願好好談談臨終選擇。所幸已有越來越多人領悟:關於臨終選擇的對話,其實是大多數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對話。
第九章 斡旋死亡
「醫生,如果這是你媽媽,你會怎麼辦?」這是病人的至親能向醫師提出的最精明問題之一,卻也是最沒幫助的。設立醫療代理人制度的目的,正是希望能藉助他們對病患的認識,了解病人在個人、靈性、醫療、倫理等各個面向的偏好與價值觀,從而試著判斷病人在當前情境中可能作何選擇。代理人的立場之所以艱難,常常是因為病人自己都不曉得該怎麼處理將來的問題。代理人就像資源、情感與智慧的槓桿,集眾人之力推動醫療進程。只是每個家庭都不一樣,最能看出彼此分歧的時刻,莫過於協調其中一員該如何走完最後一程。
第十章 家屬為何失措
醫師與病患家屬衝突是相對晚近的問題,從某個面向來看,它甚至堪稱病患自主與共同決定革命的最大成就。醫病之間種種扞格裡,很高比例的摩擦與應否採取維生治療有關。對於是否該讓病患接受更具「侵襲性」的治療,代理人傾向接受的比例是醫師的六倍,他們經常偏離自己的角色,不以病患的心願為己任,反而用自己認定的最佳利益和價值觀來下判斷。醫生熟悉倫理原則,理論上也應該更為客觀,但他們為什麼還是時常提油救火激化衝突呢?主要原因常常是溝通技巧不足。
第十一章 死之慾
十九世紀之後,安樂死議題才從哲學家的講壇走向病榻,然而關於死亡權的論辯也摻入另一個邪惡得多的概念:殺人權。率先鼓吹積極安樂死的一直不是醫生,但當時醫界卻進行更敗壞世風的勾當――優生計畫。優生運動在二次戰後歸於沉寂,但這段歷史讓很多人一聽「安樂死」就想起「優生計畫」。於是,關於安樂死的論辯時常變成宣傳戰,一方不斷給安樂死扣上「優生」、「催命」的帽子,另一方則千方百計撕下安樂死的標籤。荷蘭是現代安樂死的聖地,該國幾十年來的研究與調查,讓我們有機會一探普遍接受安樂死的社會是什麼樣子,其經驗彌足珍貴。
第十二章 拔插頭
一九九七年《尊嚴死法案》通過後,奧勒岡州衛生部持續進行調查,嚴謹收集數據,十六年後發現,當初的很多疑慮實屬多心。安樂死合法化後,臨終照顧反而更受重視,醫師也比以前更意識到自己對臨終病人的責任。現在,醫師已逐漸能把臨終過程處理得平和順暢,一大原因是:對安樂死等議題的關注,已逐漸轉向如何幫助病人好走。
一九八九年四月,魯迪・里納瑞帶著手槍衝進兒童加護病房,想讓他受盡折磨的兒子獲得解脫。魯迪後來被以謀殺罪起訴,但在公眾輿論的法庭上卻成了英雄,他對提醒大眾臨終照顧議題重要性的貢獻,可能遠遠超過大多數生命倫理學家。像魯迪這般戲劇性的事件,在八〇年代晚期屢見不鮮,那是革命的年代,美國人起身反抗的,是能讓自己永生不死的機器。有位醫師的話精準點出了時代氛圍:「『維持生命』成了『延長死亡』,病人康復不了也死不成,他們成了科技的囚徒。」
第十三章 #上網談死
我們醫界的人總在嘗試新器具、新處置和新藥,對新溝通方式一直卻步不前,結果是:病人能徵詢醫生的唯一管道就是掛號求診,甚至等到病重了才被送進醫院。現在,大眾已開始用社群媒體和網路等全新工具,分享自己對死亡最私密的看法。雖然醫生私下也會使用社群媒體,但很少有人把新媒介用在工作上。不論怎麼評價數位連結對社交生活的影響,數位科技的確對臨終者具有潛在益處,醫界目前才剛剛開始感受到社群媒體的好處,也逐漸發現這種新媒介有益於協助末期病人。
書摘/試閱
醫療工作者歷時數百年、橫跨各大洲的苦心研究,在現代心肺復甦術(CPR)上集其大成,人類看待死亡的方式也從此改變。從許多層面來看,死亡終極、絕對的地位已被心肺復甦術撼動。在心肺復甦術出現之前,想救回溺水或失去生命跡象的人,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點燃菸草,再設法將煙灌入直腸。由於這種方法太常使用,甚至還獲得皇家人道協會(Royal Humane Society)背書。為妥善滿足營救溺水者之需,泰晤士河畔曾處處放置菸草灌腸器具,就如同今日公共場所都能找到心臟去顫器。在西方國家,這種作法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因此,當尼克鮑克等人在一九六〇年以簡馭繁,綜合供氧、電擊、按壓等三項復甦手段之後,不僅急診醫療如虎添翼,連大多數人生命結束的方式都發生改變。只不過,那篇論文的三位作者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的作品竟然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心肺復甦術的大消息立刻傳遍世界,全球醫界為之轟動。一九六〇年代也是整體醫療環境突飛猛進的黃金時期。緊急應變制度迅速發展,備有專業急救人員的救護車紛紛上路。這項措施快速縮短病患和醫療照護機構的距離,大幅提高他們的就醫機會。也是在這個時期,由於治療和檢驗種類大增,醫生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小診間和小診所,轉往設備更為充足的醫院,而他們原先照顧的病人也跟著轉移陣地。由於對傳染病、心臟病等頭號殺手的控制更加成功,人類平均壽命也隨之提高。不過,醫學雖然越來越能救回心臟病發的病患,但這也代表與心臟病共存的病人大幅增加,他們的問題並沒有根治,很多人也會發展成慢性心臟病(例如心臟衰竭)。另一方面,病人的年紀越大,他們罹患癌症的風險也越高,需要加護醫療照顧的人數自然增多。患病人數急速攀升,加上醫生能夠也願意採取的治療選擇與日俱增,其結果便是現代醫療產業複合體迅速膨脹。
人工呼吸設備的發明,原本是用來治療一種現在幾乎絕跡的疾病——小兒麻痺症。這種病是由病毒傳染,可能導致患者癱瘓。不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深受其害,在它最為猖獗的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甚至每年都有兩萬一千名患者因它癱瘓。小兒麻痺症患者往往從腿部開始失去知覺,嚴重時還會從身體一路向上麻痺,導致呼吸所需的肌肉也一併失能。試想:有幾千名的孩子就這樣窒息而死,但從頭到尾始終意識清醒,這能不令人心痛嗎?當時治療這類孩童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放進一種叫「鐵肺」的人工呼吸設備。鐵肺是一九二九年發明的,狀如圓筒,將病人包在裡頭。設計者是哈佛研究人員菲利浦・錐克(Philip Drinker)和路易斯・雅格西茲・蕭(Louis Agassiz Shaw)。鐵肺的原理是在體外製造負壓,促使胸部和肺部擴張以協助病患呼吸。可惜的是,鐵肺其實對小兒麻痺症患者效果有限,因為他們的胸部肌肉已經無力,根本無法對鐵肺刻意製造的壓力變化有所反應。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小兒麻痺症在北歐大舉肆虐。丹麥各地的病童都轉往哥本哈根的布雷丹醫院(Blegdam Hospital)治療。儘管醫院裡有傳統供氧設備,但因小兒麻痺症而呼吸困難的病童還是凶多吉少,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院裡的麻醉科醫師畢雍・伊布森(Bjorn Ibsen)心急如焚,為救治這群小病人殫精竭慮。最後,他總算想出了幫助他們呼吸的新方法:他刻意模仿人類的生理運作方式,設計出一套全新的人工呼吸器。
人體要讓空氣進入肺部,必須在肺臟內部製造負壓以吸入空氣。於是伊布森做了一條軟管,附上可充氣膨脹的套囊以防空氣外洩,接著劃開頸部前方(即「氣切」〔tracheostomy〕),將軟管從造口伸進咽喉。由於軟管能在肺臟裡製造負壓,因此不但空氣能被吸入,也能順利供氧。這算是現代呼吸器的始祖,而伊布森唯一仍待解決的問題是:這套呼吸器需要隨時有人給幫浦手動打氣,好將空氣送進病人體內,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有足夠的人手在病榻操作。由於醫院裡需要人工供氧的小兒麻痺患者有七十五位,伊布森找了兩百五十名醫學生幫忙,廿四小時輪班為病人手動操作呼吸器。伊布森在《英國醫學期刊》發表這項最新成果,立刻引起轟動,不僅全球醫院爭相仿效,它也成為加護病房照顧呼吸困難病患的標準程序。到一九六〇年代,隨著CPR發展成熟以及引入心臟監測器,現代加護病房如虎添翼,進入黃金時期。
* * *
醫學幾千年來始終是門藝術,直到現代才成了科學。在科技與醫學結盟後,醫師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呈等比級數倍增。在此同時,各式各樣的新發現也傾巢而出,大幅扭轉人類對於生命的既有認知。X光造影和斷層掃描的發展,讓原本不切開身體便無從發現的疾病無所遁形。一九五三年,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立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期刊上發表驚天之作,揭示了生命基本要素DNA的祕密。面對疾病,我們現在不但使用抗生素等新藥物,也研發出制敵機先的疫苗防患未然。目前世上除了三個國家之外,小兒麻痺症疫苗已將這種疾病澈底根除。然而,醫學固然強化了我們的生存能力,卻也開始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
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一名六十八歲的英國醫生被診斷出胃癌。他之前因為心臟病發已經退休,但健康情況還是沒有好轉。他接受手術切除胃部,但效果不佳,因為癌細胞已全身擴散。腫瘤壓迫他的脊椎神經,奇痛無比,即使嗎啡開到最高劑量也舒緩不了。手術結束十天之後,他整個人垮了,肺部也出現大型血栓。一位年輕醫生當機立斷,冒險開刀移除動脈血栓。老醫生恢復意識後,一面感謝醫療團隊盡心照顧,卻也懇請他們滿足他的心願:下次他再心臟病發,請別再為他急救了。他實在痛得受不了,也幾乎沒有讓他輕鬆一點的辦法。他心意已決,也明確表達意願,甚至還親自在病歷上註記,並一一告知醫院員工:他再也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然而,即使他再三提醒,醫護人員也都知道他的意願,他兩個禮拜後再次心臟病發時,還是一晚上就被施以心肺復甦術四次,脖子上還開了造口幫他呼吸。不過這次心臟病發十分嚴重,他命是救下來了,但整體情況已幾乎不像個人。他的大腦無法有意義地發揮功能,他也不斷癲癇發作和劇烈嘔吐。然而,醫護人員還是繼續為他治療,繼續施打抗生素,繼續全力維繫他的生命,直到他心臟停止那天。
從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只要看看一九六九年一名英國醫師的投書,便能了解當時醫界的普遍氛圍:
『只要有擊退死亡的機會,吾等絕無不全力迎擊的道理,不論病人和家屬需要付出的代價多高,都不該怯於艱苦投降認輸。暫不討論酷刑凌虐等不人道行為,人對死亡的恐懼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對死亡本身的恐懼,以及恐懼死亡到來之前必須承受的折磨。現在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們恐懼死亡又多了一個理由——恐懼心肺復甦術?
我輩醫者一向認為:行醫濟世的最大風險是犯下致人於死的錯誤。難不成規矩變了?現在最嚴重的過失怎麼好像是讓病人活下來?』
醫生們既陶醉於醫學發展一日千里,卻也對前所未見的處境茫然若失。醫學的每個領域、每項專業都在突飛猛進,醫界先賢未竟的夢想似乎就要化為現實。打從懸壺濟世成為一門志業以來,代代醫者無不費盡心思想延長他們患者的壽命。可是,延年益壽的長期效應會是如何?他們從沒仔細想過。
科技發展也大幅改變醫病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醫生原本習慣在家中或診所為病人看診。大戰結束後時局穩定,醫學知識與科技進展日新月異,但隨著醫院掌握的治療與檢驗方式越來越多,它們也更有能力醫治病情嚴重的患者,於是,醫療照顧的陣地從診所轉往醫院。問題是,醫生和病患的距離不但未能拉近,醫院的運作方式還進一步破壞醫病關係。越來越多醫師太依賴檢驗報告和掃瞄影像來了解病人,對他們的病情也常依標準程序照表操課。簡言之,科技反而讓醫生和病人更加疏遠。這股風潮恰好與一九六五年聯邦醫療保險生效同時出現,原因很可能是醫療補助讓大批病患得以就醫。醫院不得不增加每位醫生診治病患的人數,而隨著文書作業暴增,醫生能用在病人身上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醫學獲得科學加持之後,醫生的知識基礎也更為扎實,過去不甚了了的生理機制如今能倒背如流。不過,很多醫生也因此變得心高氣傲,像精通玄義奧理的專家一樣不可一世、目中無人。這種情況在一九六〇年代尤其嚴重,醫生和病患的心思幾乎毫無交集。事實上,一項一九六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不贊成告知病患確診癌症的醫生,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當時進行的其他調查也顯示同樣的結果。大多數醫生認為:之所以不該向病患透露病情,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讓他們保持希望。如果病患的情況已不得不接受手術或放射線治療,醫生還是會盡量避談「癌症」,改稱「腫瘤」或「癌前期病變」。
耐人尋味的是,病患的想法截然不同。在研究中受訪的病人裡,絕大多數表示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確切病情。醫界就像當時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行事風格深深充滿父權色彩。有位醫生曾在大名鼎鼎的《刺胳針》上講過:「男醫生和女醫生的職涯展望之所以不同,有些因素是心理上的,有些因素是生理上的,而當然,社會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小覷。」這位醫生接著引用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一九七七年的著作《父權之必要》(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指出女性由於缺乏男性荷爾蒙,所以沒有爭強好勝的動力。
這種父權式的威權態度,對病人造成嚴重而惡劣的影響,對時日無多的病人傷害更大。對於應該採取多激烈的手段來治療病人,大多數醫生常片面決定,不容他人置喙,而他們的處理方向往往天差地遠,有極其激烈的侵入性治療,也有盡量簡化的緩和性處置。即使有些病人明確表達不做積極治療,有些醫師還是充耳不聞,執意進行激烈治療;但另一些時候,醫生又會自行認定病人已無藥可救,繼續治療毫無意義。事實上,早在急救倫理引起全美熱議之前,有些醫院已經開始將治療判斷標準化。例如在紐約皇后區的一間醫院裡,如果醫師判斷某位病人身體太過虛弱,撐不過心肺復甦術,或是不太可能從心肺復甦術得益,他們就會在那位病人的病歷貼上紫色貼紙。這其實賦予醫生很大的權力,讓他們只依主觀判斷就能決定醫療方針,就能決定一名病人值不值得施予心肺復甦術。而且,他們很少把這些決定告知病人或家屬。
另一個日益普遍的作法是所謂「怠速代號」(slow codes)。這種急救程序也叫「做做樣子」、「演一下」、「淺藍代號」或「好萊塢代號」,要是醫生判定病人太虛弱或病情太嚴重,就會用上這種方法,因為萬箭齊發的「藍色代號」對他們已經沒幫助了。雖然這些考量有時是出於人道,不希望急救措施對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但更多時候是醫生和病人或家屬雞同鴨講,完全沒辦法溝通,醫療人員只好「做做樣子」安撫一下家人。由於「怠速代號」既尷尬又曖昧,醫療人員從不公開討論,頂多只在走廊上低聲交換意見。
雖然法律和倫理存在許多空白地帶,但病患和家屬偶爾還是能與醫生達成共識。如果病人疼痛無法減緩、病情已無力回天、預後極不樂觀,或是生活品質已嚴重受到影響,醫生在病人或家屬的提議下,是能予以「審慎怠忽」(judicious neglect)。在私下交談時,醫師往往也會探詢家屬的想法,判斷他們是否有意採取「壯烈手段」(heroic measures,很巧,這也是個經常使用卻充滿爭議的詞彙)——這通常意味使用心肺復甦術和人工呼吸器。
上述作法曾是醫界行之有年的潛規則,直到一位花樣年華的女孩引起軒然大波。凱倫・安・昆蘭(Karen Ann Quinlan)是紐澤西人,出事時二十一歲。參加派對之前,她為了穿上精心挑選的洋裝努力減重,但在派對上玩得興起,不只喝了幾杯酒,還吞了幾顆藥,最後在朋友面前不支倒地。在此之前,昆蘭的人生平凡無奇,但從她癱倒在地那一刻起,她便徘徊遊蕩於生死之間,一再塗改死亡在現代的定義,她的影響之大,歷史上恐怕無人能及。
* * *
凱倫・安・昆蘭生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九日,出生地是賓州斯克蘭頓(Scranton)聖若瑟婦幼醫院(St. Joseph’s Children’s and Maternity Hospital),因為這間醫院專供未婚媽媽待產。凱倫出生一個月後,茱莉亞(Julia)和約瑟夫・昆蘭(Joseph Quinlan)夫婦填好表格,將凱倫領養回家。在出事之前,凱倫的人生大致分為兩段。第一段人生就像一般中產家庭的乖女兒:她游泳、滑雪、約會、和家人一起望彌撒、上中學,還在當地一家陶瓷藝品店打工。可是被那家藝品店辭退之後,她的人生也開始變調。她不斷換工作,也越來越沉迷鎮靜劑和酒精。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那晚,凱倫看不出來有什麼異狀。她跟朋友跑去離拉克瓦納湖(Lake Lackawanna)不遠的法孔內小館(Falconer’s Tavern)玩。為了穿上她為那晚精心挑選的服裝,她已節食節水好幾天。忍飢挨餓算什麼?為了豔冠群芳全都值得。到了酒吧,她喝了幾杯杜松子酒,也吃了幾顆隨身攜帶的鎮靜劑——結果一切走樣,她突然垮了。一個朋友趕忙載她離開,帶她回她和另一個朋友同租的住處。進門沒多久,他們愕然發現凱倫沒了呼吸。
從很多層面來看,凱倫的朋友發現她呼吸停止後的一連串行動,正顯示急救知識在短時間內變得多麼普及。她的朋友開始為她嘴對嘴人工呼吸,好讓她的大腦獲得氧氣,最好還能恢復自主呼吸。只是醫生後來研判:她的大腦至少兩度缺氧十五分鐘。
她的朋友也立刻打電話通報緊急救護中心——又是另一項才出現沒多久的新服務。事實上,全美通用的緊急電話「九一一」,是到一九六七年才由總統執法與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建議設立的。救護車馬上到了,將凱倫送往當地醫院,並接上人工呼吸器。身體檢查時,醫生發現她的瞳孔靜止不動,對光線刺激既不收縮也不放大,這明明是非常基本的反射動作,可是凱倫的瞳孔像定住一樣。在此同時,她對疼痛刺激也毫無反應。
凱倫入院三天後,主治醫師決定請神經科會診,於是當班的神經科醫師羅伯・摩斯(Robert Morse)來為凱倫檢查。在法庭紀錄中,摩斯醫師表示據他判斷凱倫已陷入昏迷,而且證據顯示她有「腦皮質剝除」(decortication),亦即大腦皮質發生大規模損害——從她腿部僵直、雙臂扭曲緊繃的狀態可以判斷。
凱倫的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反而每下愈況。她入院時體重大約一一五磅,醫生為了幫她餵食,給她裝上鼻胃管。這種管子從鼻孔直通胃部,可以把食物或藥物送進體內。但儘管如此,凱倫的體重還是一直往下掉,短短幾個月就剩不到七十磅。凱倫的父母昆蘭夫婦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愛女昏迷不醒,他們還是堅強以對。
凱倫並不是第一個陷入這種困境的病人,但她成了最受矚目的一個。一般說來,家屬和醫生之間通常能達成共識,醫生有時也會片面決定不再繼續急救。凱倫入院五個月後,約瑟夫・昆蘭終於請求醫師停止治療,並撤除呼吸器,但凱倫的醫生羅伯・摩斯和阿爾夏德・賈維德(Arshad Javed)予以拒絕。為了打消醫生對醫療訴訟的顧慮,昆蘭夫婦還特地寫了一份聲明,明確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可是兩位醫生依然婉拒,堅持不願撤除凱倫的呼吸器。
於是,入院時已骨瘦如柴的凱倫,就在醫院裡開啟了第二人生,她沒日沒夜地躺在病床,呼吸也始終得靠呼吸器。她的情況從表面來看不算特別,因為病情和她不相上下的病患所在多有。可是事態發展將她推向風口浪尖,死亡的面貌更因她一再改寫。
每一位參與照顧凱倫的醫生都同意她預後不佳,他們也都認為她從昏迷中甦醒的機率趨近於零。事實上,遇上凱倫這樣的病人,很多醫生都會願意接受昆蘭夫婦的提議,可是凱倫的醫生偏偏不作此想。這確實是個困難的決定,即使我現在重新思索這整件事,還是很難設想如果我是凱倫的醫生會怎麼做。一方面凱倫生活品質很糟,過得簡直不像個人。她得靠機器幫她呼吸,得用人工方式攝取營養,但即使如此,她還是只剩七十磅重。此外,當時根本沒有技術或治療能幫她恢復任何功能。繼續讓她接受這些「治療」有什麼意義呢?她不會因此舒服一點,她的感知也不會因為這些機器而有所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都清楚凱倫懸在倫理和法律的真空狀態。醫師所受的訓練是自主思考,並依照判斷明快處置眼前的病人。醫師每天都得面臨好幾次倫理抉擇,而且從來不能逃避。大多數時候,醫生是照著最符合自己道德良知的方式行事,決定之後便義無反顧,很少瞻前顧後或自我質疑。簡言之,醫師習慣衝鋒陷陣自行其是,因此一旦邁入未知的領域,驟然暴增的選項反而會讓他們四顧茫然。關於生命終點的倫理決定又尤其艱難,畢竟這裡既無前例可循,也無法律規範。
在凱倫的問題上,雖然醫生們一致同意她不可能好轉,但他們也明白自己在法律上立場尷尬:他們沒有權力撤除凱倫賴以為生的醫療處置。在此同時,他們也擔心停止照護措施會惹禍上身。他們就曾向媒體提過:有人警告過他們,如果他們真敢撤除凱倫的呼吸器,檢察官一定會以謀殺罪名起訴他們。這確實不是杞人憂天,因為這個案子並沒有法院判例可循。從某個角度來看,醫生們願意暫時擱置進一步的行動,試著從更廣闊的層面深思這個問題,的確是負責任的作法。
對昆蘭夫婦來說,這個決定其實也不容易。他們花了好幾個月思考這個問題,約瑟夫・昆蘭也和他的神父討論了好幾次。神父也同意撤除醫療照顧,畢竟凱倫幾乎不可能復原。幾番天人交戰之後,他們心意已決:繼續進行這些他們認定為「非常」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s)的照顧,絕不是凱倫樂見的。於是,他們決定提起訴訟,將爭議送交法院裁決。
昆蘭夫婦也許沒有想過:他們提出的這項訴訟,會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司法案件之一。不過判例似乎並不站在他們這邊:幾個禮拜以前,紐澤西法院才判一名卅九歲白血病末期婦女敗訴,否定她有拒絕使用餵食管的權利。當時的社會氛圍也對昆蘭夫婦不利:對於移除末期病患維生儀器一事,社會大眾在情感上依然充滿不安與疑懼。摩斯醫生的律師巧妙運用這點:在開審陳述中,他將昆蘭案比做納粹暴行,其卑劣居心與使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無異。位於紐澤西北部的莫里斯鎮(Morristown)原本沒沒無名,從喬治・華盛頓於一七七〇年代駐紮在此之後,便幾乎從美國大眾的記憶裡消失。但審判消息傳出後,幾百名記者湧進莫里斯鎮大街小巷,在昆蘭家外或坐或站,伸頭張望,法庭旁聽席也立刻被他們佔滿。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紐約客》(New Yorker)特約作家吉兒・勒波(Jill Lepore),在《幸福之家》(The Mansion of Happiness)中寫道:「凱倫・昆蘭案澈底改寫了美國政治史。昆蘭案後幾十年裡,各式各樣的內政議題都被轉化成生死議題——緊急迫切,無可妥協,而且完全沒有讓步空間。」
* * *
凱倫・昆蘭案算是今日「死亡權」運動的先聲。照州檢察官和州檢察長原本的想法,這個案子意在挑戰紐澤西對死亡的既有定義,但審判開始前不久傳出消息:凱倫仍有腦波活動,有時不用呼吸器也能自主呼吸。換言之,訴訟兩造至少都同意一項基本事實:凱倫沒死。雖然死亡定義的確是引人好奇的議題,可是這次案件並不涉及這項爭議。但無論如何,這是法院首次正式審理照料臨終病患的複雜問題,畢竟在此之前,醫療還未進步到讓相關爭議有機會浮現。平心而論,討論臨終照顧問題不但容易流於情緒,而且牽涉層面廣及醫學、神學及法學,不論從哪個層面切入,都須處理錯綜複雜的人類尊嚴、隱私權、自主權等議題,無怪乎法界人士從未曾主動涉入這個領域。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紐澤西高等法院正式開庭,由小羅伯・繆爾(Robert Muir Jr.)法官負責審理,大約兩個星期便作出裁決。從很多層面來看,這次審判猶如預演往後受到高度關注的審判。昆蘭夫婦收到上千份信件和包裹,其中很多是信仰治療者寄的,個個宣稱凱倫問題不大,他們絕對有辦法治好。約瑟夫・昆蘭的主張直接了當:他應該被任命為凱倫的監護人,並獲准移除她的呼吸器,讓她安然離世。
問題是:才開庭審理,法院就拒絕任命約瑟夫・昆蘭為監護人。法院認為他一心只想撤除女兒的維生設備,根本不適任監護人,所以另外任命兼職公設辯護人丹尼爾・柯本(Daniel Coburn)為凱倫的法律監護人,但柯本偏偏不贊成移除呼吸器。繆爾法官認為,應否移除呼吸器「應由負責照顧的醫生定奪⋯⋯我贊成醫生應與家長取得共識,但不認為決定應由家長主導」。簡單來說,繆爾法官只是重申既有概念——醫師知道怎麼做最好。這種成見其實隨處可見,社會向來敬重醫師,甚至對醫師奉若神明,總覺得醫生怎麼做都對。
於是,這場審判就從法庭拒絕昆蘭先生擔任監護人開始。
昆蘭夫婦抵達莫里斯縣司法大樓時,三名天主教神父也陪在他們身邊。其中一位是昆蘭家的堂區神父多默・特拉帕索(Thomas Trapasso),他和昆蘭一家相識多年,也和凱倫很熟。過去幾個月,他和其他神父與昆蘭夫婦談過很多次,幾位神長一致認為:昆蘭夫婦有權不以人為方式延長凱倫目前的狀態。他們之所以這樣判斷,主要是依據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的一次演說。一九五七年,碧岳十二世在一場國際麻醉師會議中言明:在病患無復原可能時,醫師沒有責任違反病患意願延長治療。
在訴訟雙方激辯兩個星期後,繆爾法官作出裁決,而且立場相當堅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繆爾法官宣布:約瑟夫・昆蘭不得擔任病患之監護人,決策責任應由照顧凱倫的醫師承擔。在判決書裡,繆爾法官寫道:
本案事涉人類生命的獨特性、醫療專業的操守、社會大眾對醫師的態度,以及整體社會的道德風氣,吾等應以更高標準對待,並擔負起更高的責任。病患既被託付(或託付自身)給醫師照顧,便已期待醫師將在能力範圍之內全力以赴,窮盡現代醫學一切手段捍衛病患生命。醫師將盡一切人事守護生命、對抗死亡。
繆爾法官在判決中特別強調醫師的角色,他認為醫師不只是醫療事務的專家,更是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的典範。他問道:「吾等有何理由越俎代庖,由法庭代醫療專業人員定奪,逕行認定照顧之定義、內容,及其所應施行之時間長短?」
追根究柢來看,這份判決最想釐清的是:對病患各個照顧階段的醫療處置,法院是否有權置喙?遺憾的是,繆爾法官的思維其實只反映出長久以來的怪象:不論是病患、照顧者或監護人,對健康照顧幾乎沒有發言權。
很多人認為這場訴訟的核心是界定病患權利何在,法庭對此也做了回應。不過,凱倫・昆蘭案畢竟和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不同,羅訴韋德案的爭點是生命權,可是在很多人眼裡,凱倫・昆蘭案爭的是所謂「死亡權」,而停用呼吸器無異於殺人或安樂死。不論移除呼吸器是有意為之或消極不作為所致,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憲法並未賦予死亡權,家長不得為其無行為能力之成年子女主張此一權利」。繆爾法官其實還進一步說:維持生命符合本州最佳利益。
另一項引起激辯的病患權利是隱私權。昆蘭家的律師保羅・阿姆斯壯(Paul Armstrong)指出:昆蘭夫婦決定撤除自家孩子的呼吸器,是行使他們自己的隱私權,州政府以法院裁決橫加干涉,已侵犯昆蘭夫婦的隱私權。昆蘭夫婦也說:隱私權既受保障,他們當然有權自主決定應否撤除本案中似乎無效的「非常措施」。雖然憲法並未明確提及隱私權,但由於自主權範圍一再擴大,隱私權其實已有相當可觀的法院判例支持。事實上,在一八九一年的「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訴博斯福特案」(Unio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v. Botsford)中,何瑞斯・格雷(Horace Gray)法官便呼應先前的判決說:「人對自身的權利,或許就是完全豁免於外在干涉的權利,換句話說:能自行其是而不受干擾。」雖然昆蘭夫婦宣稱隱私權可由父母代子女行使,但法院並不同意,法院也同時指出:生命利益對州政府的重要性高於父母撤除呼吸器的意願。不過,這項爭議就像凱倫・昆蘭案裡的其他課題一樣,引起的問題遠比提出的答案更多。因為在那個時候,根本沒人真正了解病人的權利有哪些。
* * *
繆爾法官的判決對昆蘭夫婦來說是一大打擊,但打擊也強化了他們的決心。他們發現戰術錯誤:這個議題糾結科學、宗教、法律等各個領域,是顆不折不扣的燙手山芋,下級法院接不起。凱倫依舊躺在醫院,毫無復原跡象,昆蘭夫婦並不打算就此罷休,繼續上訴至紐澤西最高法院。
社會大眾和新聞媒體持續關注這個案子,可是風向漸漸變了,大家開始轉而支持昆蘭夫婦。有些報導寫得簡單直白:凱倫・安就是棕髮褐眼版的「白雪公主」,她沉睡的命運走向何方,就看她(養)父母、醫生和法庭三方如何角力。
把注意力放在她外型變化的人也不少。報章媒體登的照片是她高中時拍的,看起來身強體健,讓人不免更加好奇她的遭遇。由於那張照片已經太舊,好事之徒開始胡亂臆測她的現狀。法庭常以「胎兒型」、「怪異」等詞形容她的去皮質姿勢(decorticate posture),而最露骨的描述出自神經學家尤利烏斯・寇瑞恩(Julius Korein),他在作證時說:凱倫像個「無腦症怪物」。
無腦症是相當罕見的先天畸形,罹患此症的胎兒不會長出大腦。無腦症當時也引起一陣熱議,因為耶魯-紐哈芬醫院(Yale–New Haven Hospital)證實:院內的確接生過幾名無腦症胎兒,在告知父母這些孩子預後不佳之後,他們決定停止或不作治療,胎兒因此去世。這些胎兒多半浸在灌滿福馬林的瓶子裡,擺在解剖學實驗室當樣本,有時也出現在胚胎學教科書,像個突然跑出來嚇人的配角。「你要是拿手電筒從他們頭部後方照,光會直接從瞳孔透出來,他們沒有腦嘛!」寇瑞恩說得興起,好像唯恐大家想像的畫面還不夠驚悚。這些獵奇的陳述進一步引發大眾好奇,媒體也深知有幅畫面多能操控輿論走向。於是,關於臨終議題的討論,絕大多數集中在痛苦或磨難。流言蜚語四起,個個把凱倫講得不成人形,彷彿越是渲染她的痛苦,越能證明維繫她的生命多無謂而殘酷。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有報社向昆蘭夫婦開價十萬買一張凱倫近照,有些記者甚至想假扮修女潛入醫院。
昆蘭夫婦也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住吸睛之道。沒過多久,他們便能不疾不徐地一再重述凱倫的故事,他們的談吐相當自然,臉上滿是對女兒的關心與不捨,言詞之間充滿對天主的敬畏。他們就像平平凡凡的一般家長,但為了讓女兒得到平靜,他們不得不挺身與世界相抗。他們有神父、親友和律師保羅・阿姆斯壯作後盾,也贏得報導此案的媒體一致敬重。只要昆蘭夫婦開始說話,原本嘈雜推擠的記者一定自動安靜下來。另一方面,醫師團隊也自始至終凜然自重,明確表示病人是他們的首要考量,更是他們唯一的顧念。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這個案子居然完全沒有「壞人」。
每個人似乎都一心為了凱倫好,問題是彼此的看法天差地遠。從很多方面來看,這跟現代醫學中很多倫理困境一樣:每個人都是一番好意,但看待真理的方式南轅北轍。
不斷追蹤凱倫・昆蘭案的發展,也讓社會大眾開始同理昆蘭夫婦的感受:自己的愛子愛女困在生死之間的渾沌地帶,心裡會怎麼想呢?更重要的是:凱倫現在的情況,到底還算不算是「人」?每天翻開報紙,他們都想像不到又會出現什麼新發展。他們盯著昆蘭夫婦閃躲記者、步入法庭、忍受一切不便,可是,他們的奮鬥卻是為了讓深愛的女兒儘早離去?審判越拖越久,凱倫的情況仍無絲毫變化,體重也一再下滑,昆蘭夫婦心如刀割,幾乎已痛得麻痺。
對媒體來說,凱倫・昆蘭案顯示閱聽大眾對死亡議題有興趣,而且關注角度人人不同,從最嚴肅的到最獵奇的都有。無論是報章雜誌或電視報導,無論是紐澤西州的地方小報或《新聞週刊》的封面故事,凱倫的消息始終是眾人目光焦點。當然,報導品質參差不齊。《紐約時報》精銳盡出,不僅派出紐澤西和紐約最好的記者報導此案,也延請法律和宗教專家為文評論。最嫻熟這個領域的作家或許是瓊・克朗(Joan Kron),她為《紐約》(New York)雜誌寫了篇長篇報導。
克朗的報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她在這個議題上有個人經驗:一九六八年,她也做過艱難的決定,撤除十六歲女兒的醫療照顧。雖然許多報導顯然對昆蘭案下過夫,但也有不少報導扭曲不實,原因或是因為對相關議題缺乏了解,或是為了吸引讀者目光而語出驚人。從消息見諸報端之後,昆蘭案的焦點就被歪曲成「挑戰死亡定義」。可是,雖然昆蘭案確實與此相關,這項議題也的確容易引起好奇,但昆蘭案兩造唯一同意的基本事實或許就是:凱倫並沒有死。從現代對死亡的任何定義來看,她都不算死亡。輿論之所以誤以為本案爭點是死亡定義,也許是因為主流媒體沒有請醫師作家發聲。哈斯丁中心(Hastings Center)的報告指出:「沒有醫師作家報導這則案例。如果有的話,『凱倫是否有腦波?』這種基本問題應該會提出得更早。因為到目前為止,對這個問題及其倫理意義有興趣的都是醫界的人,而不是法律、宗教或科普作家。」
另一方面,對繆爾法官的裁定不以為然的醫生倒是不少。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重症醫療醫師傑克・E・齊瑪曼(Jack E. Zimmerman)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撰文指出:如果凱倫是在他任職的醫院接受治療,醫生們早就決定移除呼吸器了。他也說,醫生早就該主動跟昆蘭夫婦討論這個問題,而不是讓昆蘭先生苦思好幾個月後才自己提出。繆爾法官對醫療決策所持的醫師中心態度也飽受批評,因為這似乎違背美國醫學會一九七三年的聲明——在這項聲明裡,醫師代表指出:在病患不太可能恢復正常功能時,決定是否繼續延長生命的人,應該是「病患及/或其最近親屬」。
繆爾法官認為:醫師應是病患的守護者,而他們有責任保護及延長生命。更進一步說,醫師甚至比病患親屬或照顧者更有資格守護病患權益。但繆爾法官沒有考慮到的是:醫師本身也會有自己的偏見,他們的利益也不見得與病患權益一致。因此,雖然繆爾法官賦予醫師更大的自主權,讓他們能依自己的判斷做出攸關生死的決定,卻沒有任何醫師組織支持昆蘭案中醫師一方的立場。相較之下,以往醫師捲入訴訟多半會有醫師組織加以支持(例如在肯尼斯・艾德林〔Kenneth Edelin〕案中,艾德林醫師因為為成孕六個月的胎兒執行選擇性墮胎,一開始被判殺人罪,當時便有不少醫師組織予以聲援。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法官才一致推翻原判決)。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