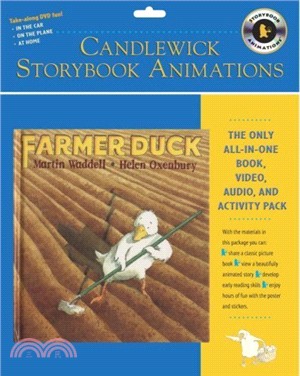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最經典的死樣子.最無賴的頹廢人生
日本文學史上銷售千萬本的經典之作
一次收錄太宰治顛峰之作《人間失格》、《斜陽》、《維榮之妻》
你碰到的苦悶、哀愁、自卑與懦弱,一字一句直指心臟,
你遇見的懦弱、無能、疲憊與無奈,一一寫下不帶憐憫!
敗類什麼的也無所謂,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好了。──《維榮之妻》
幸福感這種東西,不就像是那些沉在悲哀河底,微微發光的金砂嗎?經歷過悲痛極限的不可思議微光。倘若這就是幸福感,那麼我現在確實是幸福的。──《斜陽》
現在的我,既談不上幸福也談不上不幸。只是,讓一切隨風。我在這所謂「人」的世界中一路哭嚎著走來,明白的唯一可以說是真理的東西,就是這個:只是,讓一切隨風。──《人間失格》
世界紛亂,人間無格,雖然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但究竟如何好得起來?我們如何在虛無的一生裡,找到生存的意義?抑或是看透百態生活,任由心地荒蕪?
於是,那些疲憊和無奈,有人願意傾聽,不願承認的懦弱和自卑,也有人理解寫下。本書收錄太宰治最經典的三部小說:《維榮之妻》、《斜陽》與《人間失格》,厭世美學,經典重現。
日本文學史上銷售千萬本的經典之作
一次收錄太宰治顛峰之作《人間失格》、《斜陽》、《維榮之妻》
你碰到的苦悶、哀愁、自卑與懦弱,一字一句直指心臟,
你遇見的懦弱、無能、疲憊與無奈,一一寫下不帶憐憫!
敗類什麼的也無所謂,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好了。──《維榮之妻》
幸福感這種東西,不就像是那些沉在悲哀河底,微微發光的金砂嗎?經歷過悲痛極限的不可思議微光。倘若這就是幸福感,那麼我現在確實是幸福的。──《斜陽》
現在的我,既談不上幸福也談不上不幸。只是,讓一切隨風。我在這所謂「人」的世界中一路哭嚎著走來,明白的唯一可以說是真理的東西,就是這個:只是,讓一切隨風。──《人間失格》
世界紛亂,人間無格,雖然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但究竟如何好得起來?我們如何在虛無的一生裡,找到生存的意義?抑或是看透百態生活,任由心地荒蕪?
於是,那些疲憊和無奈,有人願意傾聽,不願承認的懦弱和自卑,也有人理解寫下。本書收錄太宰治最經典的三部小說:《維榮之妻》、《斜陽》與《人間失格》,厭世美學,經典重現。
作者簡介
太宰治(1909-1948)
本名為津島修治,青森縣人。出生於富有的仕紳家庭,曾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並在當時參與左翼運動。1933年,他以太宰治為筆名開始寫作,屢屢獲獎,風格抑鬱頹廢、自卑厭世,為無賴派代表作家(反俗、反權威、反道德),亦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稱日本戰後文學的巔峰代表人物。太宰治曾自殺多次,最後於1948年投河自盡,結束傳奇一生,《維榮之妻》、《斜陽》和《人間失格》為顛峰之作。
本名為津島修治,青森縣人。出生於富有的仕紳家庭,曾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並在當時參與左翼運動。1933年,他以太宰治為筆名開始寫作,屢屢獲獎,風格抑鬱頹廢、自卑厭世,為無賴派代表作家(反俗、反權威、反道德),亦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稱日本戰後文學的巔峰代表人物。太宰治曾自殺多次,最後於1948年投河自盡,結束傳奇一生,《維榮之妻》、《斜陽》和《人間失格》為顛峰之作。
序
太宰治情死考(代跋)
?口安吾
報紙上說,太宰治每月收入二十萬日元,每天喝二千日元的土酒,然後住在一個五十日元的出租房裡,漏雨他也不修。
沒人能喝下二千日元的土酒,而且太宰治似乎也根本不喝土酒。大概是一年前,他跟我說他沒喝過土酒,我就帶他去了新橋的土酒酒吧,因為當時已經喝醉了,他只喝了一杯,那之後就再沒聽說他喝土酒了。
自從武田麟太郎因工業酒精中毒而死,我也開始對這些劣質白酒變得小心謹慎,但也正是因此,我在威士忌酒吧的賒帳也日益增多,著實讓我苦惱。出門喝酒喝得多了,酒友也就相應增加。一來二去,喝一次酒,兩三千日元根本打不住。奢侈的菜就算一樣不點,單是酒錢就如流水般成千上萬。
前幾天,三根山和新川過來玩,說什麼都希望我去吃一次相撲食膳中的河豚。
「別介別介,在下還不想用河豚自殺。相撲做的河豚啊,你們還是饒了我吧。」聽我這樣回答,三根山像是聽了世上最無厘頭的話一樣擺出一副不解的表情說:「飯館的河豚危險,相撲做的河豚才安心。大家都這麼說,是吧?」
他看了看新川,繼續說:「相撲一共只有兩個人吃河豚死的。福柳和沖海,自開天闢地以來只有他兩個。河豚子的血管都是我們一根一根用鑷子挑出來的,花的時間比飯館要多三倍呢。就算中了毒,吃糞便也能治。我那次全身都發麻了,抓過屎來吃了,把吃進去的都吐出來就治好了。」
相撲巍然不動,他們是一種超越時間空間的存在。前幾天,我去吃相撲食膳,他們還真為我準備了河豚子。一個相撲從冰箱裡把河豚子端出來,跟我說:「先生,有河豚子。」
「不用了,我已經吃不下了,謝謝。」
「先生,您可真是個怪人。」
他說著,歪了歪頂著小辮的光禿禿的大腦殼。
當然,相撲比賽著實有趣,在相撲看來,世界上只有比賽一件大事。他們只知道比賽,也只會以相撲的思考方式去思考。因為糧食短缺,相撲選手都瘦了。三根山只剩下二十八貫的體重,但即使如此,他還是馬上就要升為關脅了。要是他有以前三十三貫的體重,估計大關也不是問題。他聽說為了增加體重必須戒煙,「啊?那我現在就戒。」他說起來輕描淡寫,簡直不像當真的。然而,他當真把煙給戒了。
所謂「藝道」,如果不能變成為此道奉獻生命的傻瓜,是難成大器的。
三根山不通政治,對處世之道也全不瞭解。然而,問起他對於相撲比賽上角逐博弈的各種相關知識,他卻是無所不知。顯然,既然他對於藝道的技術能有如此精深的理解,如果能夠把這份心用在他處,想必也定能出人頭地,然而他卻對別的事情全然不感興趣。
聽說雙葉山和吳清源都皈依了璽宇教。吳八段入教以後棋藝日益精湛,挫敗無數英雄,讓日本棋壇一時間哀號遍野。吳八段最近還經常接讀賣的宣傳棋局,向讀賣索要巨額酬金,據說這都是因為他一人撐起了為璽宇教籌集資金的重任。我也在讀賣新聞的安排下和吳清源對弈了一局。記得那時讀賣新聞告知我說,因為和吳清源對局的酬金異常高昂,已經佔用了文化部的大半資金,所以沒辦法支付安吾先生的酬金、盒飯費、交通費等等。就這樣,我也算間接地為璽宇教貢獻了一筆錢,南無璽宇教尊。
當然,雙葉和吳氏的心並非凡人可以參透。可是,他們卻無一例外地散發出那種角逐的世界中蘊藏的悲痛。
文化愈高,人們反而會變得愈加迷信,這麼說不知各位能否理解。從事相撲格鬥的人或許大都目不識丁,可是這些力士,不,應該說他們中的精英卻反而是高級的文化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們精通相撲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他們縱橫在當今世界。相撲的攻擊速度、出手速度、呼吸、防禦策略,這些都是當今時代文化的一部分。由此,通曉相撲格鬥技巧精髓的他們正是這個時代最高級的技術專家之一,文化人之一。他們是不是目不識丁根本不重要。
叱吒風雲的文化人,處心積慮的謀士,他們都走在距離迷信僅一步之遙的懸崖邊。因為他們在反復的自我檢討之後,知道了限度並感到了絕望。
越傑出的靈魂,越會深陷煩惱,在苦悶之中掙扎。大力士雙葉山,圍棋大師吳八段,這樣的曠世奇才皈依璽宇教,無不源自天才與生俱來的悲劇性的苦痛。單純因為璽宇教的荒誕不羈而忽略了兩個偉大靈魂的苦痛,無疑是大錯特錯。
文學家,說到底也是藝道中人,是技術工人,是獨專一行的專家。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們當然不會是目不識丁,但是他們卻正如目不識丁一般目無常理,因為藝道本來就不能用常理去評判。
在一般人看來,戰爭是非常時期才有的事情。而對於藝道中人,他們的靈魂卻無時無刻都與戰爭同在。
像受到他人或者評論家的批判,那樣的事根本不足掛齒。真正的鬥爭發生在作家本人的內心最深處。他們的靈魂正如暴風驟雨,那是充滿了懷疑、絕望、再生、決意、衰微、奔流的暴風驟雨。
當然,那些不足掛齒的他人的批判一類的事情,也絕非世人所能面對的常態。
力士和棋手在賽場上殊死角逐,而比賽卻成了世人娛樂的工具。勝者收穫歡呼,敗者湮沒於噓聲。
對於一個靈魂而言,在沙場上拼死相搏的事情,卻被世人追求歡愉的粗俗靈魂指指點點,肆意踐踏。
文學家的工作落到那些粗俗的世間評論家手裡變成了水果攤上的香蕉,在叫賣聲中被定價為五十錢,三十錢或被評定為上級,中級。
當然,我們也大可不必為這樣的事情一一憤慨,因為藝道一直以來都苦於來自自身的更加嚴酷的批判和苦痛。
這些無時無刻不在戰鬥中活著的藝道眾生,必須認清自己並非存在於一般意義上的世間法理之中。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中要時刻像特工隊一樣活著,要時時刻刻把靈魂和生命的賭注押在工作上。當然,因為我們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走上的藝道之路,不會像那些受命參加特工隊的人一樣擺出一臉悲痛,我們往往只是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
太宰每晚喝二千日元的土酒,反而對自己漏雨的屋頂不管不顧。大家如果覺得這人是瘋子或變態,那麼對了,因為他如果不是瘋子也定然難有大作為。所謂藝道大成實際就是成為瘋子。
太宰的死是否是殉情呢?兩個人用繩子在腰上綁在一起,死後小幸的手還緊緊摟著太宰的脖子。從上面這些來看,半七也好錢形平次也好都一定會判定太宰是殉情而死的。
然而,世上再沒有比這更難解釋的殉情了。不僅看不出太宰有多喜歡「毛手毛腳小幸」,與其說喜歡,甚至不如說看起來根本瞧不起她。小幸本身就是女人的一個暱稱,是太宰給她取了「毛手毛腳小幸」這個名字。她不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是一個沒腦子的白癡一般的女人,蠢得令編輯們都目瞪口呆。對於只靠腦子工作的文學家來說,蠢女人有時可以成為一種調劑。
太宰身上沒帶遺書,他當時喝得爛醉如泥,而小幸是出了名的千杯不倒,當時應該並沒有醉。「和自己尊敬的先生一起去死是一種光榮,一種幸福。」她寫過這樣的話。如果說太宰在爛醉時因為心血來潮想去自殺,這個時候,這個沒有醉的女人則使這種想法變得更加確定。
太宰確實是死不離口,而且在他的作品中也充滿了自殺或有關自殺的暗示,可是他卻絕對沒有到那種非死不可的無可救藥的地步,也從未有過那種非死不可的無可救藥的想法。即使他在作品中選擇了自殺,在現實中也完全沒有自殺的必要。
酒醉之後,一時興起做下些荒唐之事,第二天一覺醒來,想起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由得自覺羞恥,冷汗一身。人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然而單單是自殺這件荒唐之事,卻再不能在第二天睜開眼睛,所以才會無法收拾。
以前,法國有一個叫奈瓦爾的詩人,深夜爛醉如泥地去敲酒館的門。碰巧這個酒館老闆受不了總是一待待很久不肯離去的奈瓦爾,就裝作已經睡下,不方便起床開門,支支吾吾地敷衍了奈瓦爾幾句,隱約聽到奈瓦爾回去的聲音。可誰知第二天奈瓦爾就在酒館門口的路邊樹上上吊死了。為了一杯酒,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像太宰這樣的男人,如果是真的喜歡上了女人的話,是不會自殺而選擇繼續活下去的。話又說回來,藝道中人也沒有可能會真正喜歡上女人,藝道正是這樣一種魑魅魍魎的棲身之所。所以,如果說太宰和女人一起自殺了,說他不喜歡這個女人一定是沒錯的。
太宰留下的遺書上儘管說自己已經寫不出小說,可是那不過只是一時性的寫不出,並非是絕對性的,我們不能把這種一時性的創作低潮說成是永久性的創作低潮,太宰自身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由此看來,太宰之死純屬一時興起,事出偶然。
退一萬步來看,太宰一方面說自己已經寫不出小說,而另一方面,他還從未就身邊的「毛手毛腳小幸」寫過任何作品。沒法讓作家為其寫出任何作品的女人,一定是十分乏味的、不值一提的女人。如果這個女人值得一提,太宰為了寫這個女人也會活下去,而且也不會說什麼寫不出小說這樣的話了。可世上偏偏有那麼一種人,再怎麼樣都讓人不願下筆去寫。儘管如此卻還是喜歡這樣的女人,或產生喜愛之情,那簡直太荒唐了,特別是對於太宰就更荒唐了。可見他陷入戀愛的方式,以及選擇女人的方式是多麼不成體統。
怎樣都無所謂吧。陷入戀愛的方式不成體統也罷,皈依璽宇教也罷,在玉川上水投河自殺也罷,「毛手毛腳小幸」曾擺上自己和太宰的合照,在死前虔誠禱告也罷,這些事情再荒謬又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職業啊!藝道中人就是如此,在胸中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下,如花般凋零。死法被偽裝,戴上了假面具,但再怎麼奇妙而不成體統,他們生前的作品都無法偽裝。
因為不成體統,我們更應去關注他內心痛苦狂亂的波瀾。
喜歡上了一個女人,然後這個女人就成了他今生唯一的紅顏知己,以至要同赴天國。這樣從一而終為愛而死的故事,在我看來是古怪的。如果真的是喜歡,不如在現世中繼續活下去。
太宰的自殺,與其說是自殺,不如說是藝道中人在苦痛中掙扎的一個縮影,那無疑是與皈依璽宇教一樣的走火入魔。我們應當放下對這些走火入魔的關心,緬懷死者,讓他能夠安息。
藝道裡,無時無刻不是戰場。藝道中人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下是內心深處日夜的悲鳴,他們不得不遁世匿隱,以至於和無足輕重的女人一起殉情,他們用盡全部的生命在拼搏以至於無法選擇自己生與死的方式。太宰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拿來討論。作家的作品才是作家的全部。
?口安吾
報紙上說,太宰治每月收入二十萬日元,每天喝二千日元的土酒,然後住在一個五十日元的出租房裡,漏雨他也不修。
沒人能喝下二千日元的土酒,而且太宰治似乎也根本不喝土酒。大概是一年前,他跟我說他沒喝過土酒,我就帶他去了新橋的土酒酒吧,因為當時已經喝醉了,他只喝了一杯,那之後就再沒聽說他喝土酒了。
自從武田麟太郎因工業酒精中毒而死,我也開始對這些劣質白酒變得小心謹慎,但也正是因此,我在威士忌酒吧的賒帳也日益增多,著實讓我苦惱。出門喝酒喝得多了,酒友也就相應增加。一來二去,喝一次酒,兩三千日元根本打不住。奢侈的菜就算一樣不點,單是酒錢就如流水般成千上萬。
前幾天,三根山和新川過來玩,說什麼都希望我去吃一次相撲食膳中的河豚。
「別介別介,在下還不想用河豚自殺。相撲做的河豚啊,你們還是饒了我吧。」聽我這樣回答,三根山像是聽了世上最無厘頭的話一樣擺出一副不解的表情說:「飯館的河豚危險,相撲做的河豚才安心。大家都這麼說,是吧?」
他看了看新川,繼續說:「相撲一共只有兩個人吃河豚死的。福柳和沖海,自開天闢地以來只有他兩個。河豚子的血管都是我們一根一根用鑷子挑出來的,花的時間比飯館要多三倍呢。就算中了毒,吃糞便也能治。我那次全身都發麻了,抓過屎來吃了,把吃進去的都吐出來就治好了。」
相撲巍然不動,他們是一種超越時間空間的存在。前幾天,我去吃相撲食膳,他們還真為我準備了河豚子。一個相撲從冰箱裡把河豚子端出來,跟我說:「先生,有河豚子。」
「不用了,我已經吃不下了,謝謝。」
「先生,您可真是個怪人。」
他說著,歪了歪頂著小辮的光禿禿的大腦殼。
當然,相撲比賽著實有趣,在相撲看來,世界上只有比賽一件大事。他們只知道比賽,也只會以相撲的思考方式去思考。因為糧食短缺,相撲選手都瘦了。三根山只剩下二十八貫的體重,但即使如此,他還是馬上就要升為關脅了。要是他有以前三十三貫的體重,估計大關也不是問題。他聽說為了增加體重必須戒煙,「啊?那我現在就戒。」他說起來輕描淡寫,簡直不像當真的。然而,他當真把煙給戒了。
所謂「藝道」,如果不能變成為此道奉獻生命的傻瓜,是難成大器的。
三根山不通政治,對處世之道也全不瞭解。然而,問起他對於相撲比賽上角逐博弈的各種相關知識,他卻是無所不知。顯然,既然他對於藝道的技術能有如此精深的理解,如果能夠把這份心用在他處,想必也定能出人頭地,然而他卻對別的事情全然不感興趣。
聽說雙葉山和吳清源都皈依了璽宇教。吳八段入教以後棋藝日益精湛,挫敗無數英雄,讓日本棋壇一時間哀號遍野。吳八段最近還經常接讀賣的宣傳棋局,向讀賣索要巨額酬金,據說這都是因為他一人撐起了為璽宇教籌集資金的重任。我也在讀賣新聞的安排下和吳清源對弈了一局。記得那時讀賣新聞告知我說,因為和吳清源對局的酬金異常高昂,已經佔用了文化部的大半資金,所以沒辦法支付安吾先生的酬金、盒飯費、交通費等等。就這樣,我也算間接地為璽宇教貢獻了一筆錢,南無璽宇教尊。
當然,雙葉和吳氏的心並非凡人可以參透。可是,他們卻無一例外地散發出那種角逐的世界中蘊藏的悲痛。
文化愈高,人們反而會變得愈加迷信,這麼說不知各位能否理解。從事相撲格鬥的人或許大都目不識丁,可是這些力士,不,應該說他們中的精英卻反而是高級的文化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們精通相撲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他們縱橫在當今世界。相撲的攻擊速度、出手速度、呼吸、防禦策略,這些都是當今時代文化的一部分。由此,通曉相撲格鬥技巧精髓的他們正是這個時代最高級的技術專家之一,文化人之一。他們是不是目不識丁根本不重要。
叱吒風雲的文化人,處心積慮的謀士,他們都走在距離迷信僅一步之遙的懸崖邊。因為他們在反復的自我檢討之後,知道了限度並感到了絕望。
越傑出的靈魂,越會深陷煩惱,在苦悶之中掙扎。大力士雙葉山,圍棋大師吳八段,這樣的曠世奇才皈依璽宇教,無不源自天才與生俱來的悲劇性的苦痛。單純因為璽宇教的荒誕不羈而忽略了兩個偉大靈魂的苦痛,無疑是大錯特錯。
文學家,說到底也是藝道中人,是技術工人,是獨專一行的專家。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們當然不會是目不識丁,但是他們卻正如目不識丁一般目無常理,因為藝道本來就不能用常理去評判。
在一般人看來,戰爭是非常時期才有的事情。而對於藝道中人,他們的靈魂卻無時無刻都與戰爭同在。
像受到他人或者評論家的批判,那樣的事根本不足掛齒。真正的鬥爭發生在作家本人的內心最深處。他們的靈魂正如暴風驟雨,那是充滿了懷疑、絕望、再生、決意、衰微、奔流的暴風驟雨。
當然,那些不足掛齒的他人的批判一類的事情,也絕非世人所能面對的常態。
力士和棋手在賽場上殊死角逐,而比賽卻成了世人娛樂的工具。勝者收穫歡呼,敗者湮沒於噓聲。
對於一個靈魂而言,在沙場上拼死相搏的事情,卻被世人追求歡愉的粗俗靈魂指指點點,肆意踐踏。
文學家的工作落到那些粗俗的世間評論家手裡變成了水果攤上的香蕉,在叫賣聲中被定價為五十錢,三十錢或被評定為上級,中級。
當然,我們也大可不必為這樣的事情一一憤慨,因為藝道一直以來都苦於來自自身的更加嚴酷的批判和苦痛。
這些無時無刻不在戰鬥中活著的藝道眾生,必須認清自己並非存在於一般意義上的世間法理之中。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中要時刻像特工隊一樣活著,要時時刻刻把靈魂和生命的賭注押在工作上。當然,因為我們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走上的藝道之路,不會像那些受命參加特工隊的人一樣擺出一臉悲痛,我們往往只是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
太宰每晚喝二千日元的土酒,反而對自己漏雨的屋頂不管不顧。大家如果覺得這人是瘋子或變態,那麼對了,因為他如果不是瘋子也定然難有大作為。所謂藝道大成實際就是成為瘋子。
太宰的死是否是殉情呢?兩個人用繩子在腰上綁在一起,死後小幸的手還緊緊摟著太宰的脖子。從上面這些來看,半七也好錢形平次也好都一定會判定太宰是殉情而死的。
然而,世上再沒有比這更難解釋的殉情了。不僅看不出太宰有多喜歡「毛手毛腳小幸」,與其說喜歡,甚至不如說看起來根本瞧不起她。小幸本身就是女人的一個暱稱,是太宰給她取了「毛手毛腳小幸」這個名字。她不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是一個沒腦子的白癡一般的女人,蠢得令編輯們都目瞪口呆。對於只靠腦子工作的文學家來說,蠢女人有時可以成為一種調劑。
太宰身上沒帶遺書,他當時喝得爛醉如泥,而小幸是出了名的千杯不倒,當時應該並沒有醉。「和自己尊敬的先生一起去死是一種光榮,一種幸福。」她寫過這樣的話。如果說太宰在爛醉時因為心血來潮想去自殺,這個時候,這個沒有醉的女人則使這種想法變得更加確定。
太宰確實是死不離口,而且在他的作品中也充滿了自殺或有關自殺的暗示,可是他卻絕對沒有到那種非死不可的無可救藥的地步,也從未有過那種非死不可的無可救藥的想法。即使他在作品中選擇了自殺,在現實中也完全沒有自殺的必要。
酒醉之後,一時興起做下些荒唐之事,第二天一覺醒來,想起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由得自覺羞恥,冷汗一身。人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然而單單是自殺這件荒唐之事,卻再不能在第二天睜開眼睛,所以才會無法收拾。
以前,法國有一個叫奈瓦爾的詩人,深夜爛醉如泥地去敲酒館的門。碰巧這個酒館老闆受不了總是一待待很久不肯離去的奈瓦爾,就裝作已經睡下,不方便起床開門,支支吾吾地敷衍了奈瓦爾幾句,隱約聽到奈瓦爾回去的聲音。可誰知第二天奈瓦爾就在酒館門口的路邊樹上上吊死了。為了一杯酒,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像太宰這樣的男人,如果是真的喜歡上了女人的話,是不會自殺而選擇繼續活下去的。話又說回來,藝道中人也沒有可能會真正喜歡上女人,藝道正是這樣一種魑魅魍魎的棲身之所。所以,如果說太宰和女人一起自殺了,說他不喜歡這個女人一定是沒錯的。
太宰留下的遺書上儘管說自己已經寫不出小說,可是那不過只是一時性的寫不出,並非是絕對性的,我們不能把這種一時性的創作低潮說成是永久性的創作低潮,太宰自身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由此看來,太宰之死純屬一時興起,事出偶然。
退一萬步來看,太宰一方面說自己已經寫不出小說,而另一方面,他還從未就身邊的「毛手毛腳小幸」寫過任何作品。沒法讓作家為其寫出任何作品的女人,一定是十分乏味的、不值一提的女人。如果這個女人值得一提,太宰為了寫這個女人也會活下去,而且也不會說什麼寫不出小說這樣的話了。可世上偏偏有那麼一種人,再怎麼樣都讓人不願下筆去寫。儘管如此卻還是喜歡這樣的女人,或產生喜愛之情,那簡直太荒唐了,特別是對於太宰就更荒唐了。可見他陷入戀愛的方式,以及選擇女人的方式是多麼不成體統。
怎樣都無所謂吧。陷入戀愛的方式不成體統也罷,皈依璽宇教也罷,在玉川上水投河自殺也罷,「毛手毛腳小幸」曾擺上自己和太宰的合照,在死前虔誠禱告也罷,這些事情再荒謬又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職業啊!藝道中人就是如此,在胸中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下,如花般凋零。死法被偽裝,戴上了假面具,但再怎麼奇妙而不成體統,他們生前的作品都無法偽裝。
因為不成體統,我們更應去關注他內心痛苦狂亂的波瀾。
喜歡上了一個女人,然後這個女人就成了他今生唯一的紅顏知己,以至要同赴天國。這樣從一而終為愛而死的故事,在我看來是古怪的。如果真的是喜歡,不如在現世中繼續活下去。
太宰的自殺,與其說是自殺,不如說是藝道中人在苦痛中掙扎的一個縮影,那無疑是與皈依璽宇教一樣的走火入魔。我們應當放下對這些走火入魔的關心,緬懷死者,讓他能夠安息。
藝道裡,無時無刻不是戰場。藝道中人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下是內心深處日夜的悲鳴,他們不得不遁世匿隱,以至於和無足輕重的女人一起殉情,他們用盡全部的生命在拼搏以至於無法選擇自己生與死的方式。太宰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拿來討論。作家的作品才是作家的全部。
目次
維榮之妻
斜陽
人間失格
序
手記一
手記二
手記三
後記
太宰治情死考(代跋)
太宰治創作年表
斜陽
人間失格
序
手記一
手記二
手記三
後記
太宰治情死考(代跋)
太宰治創作年表
書摘/試閱
維榮之妻.三
也就是三十分鐘,不,甚至可能更短,只一轉念的功夫,老闆就一個人回來了。他走到我身旁說:
「夫人,多謝了,他把錢給還上了。」
「真的?那太好了。全都還了?」老闆詭異地笑著:
「嗯,也就是昨天拿走的那些。」
「那到現在為止一共欠多少呢?大概來說。」
「兩萬塊。」
「就這麼多?」
「沒算零頭。」
「我們一定還。大叔,明天開始,能讓我在你這兒打工嗎?求你了!算是打工還債。」
「夫人,沒看出來,想當小輕(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為夫賣身打工的女人)啊。」
我們兩個齊聲笑了起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我在中野的飯館辭別了眾人,背著孩子回到了自己小金井的家裡。儘管丈夫依舊沒有回來,可是我卻一點也不擔心。明天只要再去飯館裡,說不定就能碰到他。我怎麼這麼長時間都沒意識到有這樣的好事啊,迄今為止吃了那麼多的苦,原來都是因為自己傻,沒有想到這麼好的主意。想想我以前在淺草的父親的攤頭,接待顧客那是一點也不含糊,從今以後在這個中野的飯館裡我也肯定能夠大顯身手。單是今天一晚上,我就拿了將近五百塊的小費呢。
從老闆那裡聽說,丈夫在昨夜的事發生之後就去了不知哪裡的熟人家裡住下了,然後一大早竄到那個漂亮夫人經營的京橋的酒吧裡,大白天的喝起威士忌酒,接著以聖誕禮物為名,隨隨便便拿錢給了在酒吧裡打工的五個女孩,之後在中午左右叫了計程車不知去了哪裡。一會等他回來,帶回了聖誕的三角帽啊、假面啊、裱花蛋糕啊和火雞。他讓人給各處打電話,召集了各種朋友,開了盛大的宴會。酒吧的夫人知道他向來幾乎就是身無分文,心裡覺得奇怪就悄悄質問他錢的來源,誰知他也不避諱,一五一十地就把昨天晚上的事給坦白了。因為那個夫人和他長期以來就不是一般的關係,也不忍看到事情鬧大,
他被人告到員警那裡去,就好言相勸地讓他一定把錢還回去,錢由夫人先行墊付。就這樣,丈夫才帶著那位夫人來了這個中野的飯館。
老闆對我說:「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夫人,你可真是先知先覺,連這一步都能事先看到。你是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嗎?」
老闆大概是覺得因為我早就預測到錢會這樣被還回來,才提前到他店裡去等的。聽他這麼一說,我笑著,簡單地搪塞了一句:
「嗯,看你說的。」
第二天開始,我的生活簡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都變得讓人充滿期待。我迫不及待地去燙髮館做了頭髮,添置了化妝品,縫好了和服,老闆娘還送給了我兩雙新的白襪套。長久以來在我心中積壓的苦悶,全都一掃而光了。
我早上起來和孩子一起吃了飯,然後做了便當,背上孩子就去中野上班了。時逢新年,正是飯館忙碌的時節,我在飯館裡被人叫做椿屋的小幸,每天忙得不可開交。丈夫每兩天裡大概有一次會來這裡喝酒,每次讓我付了錢就一下子又不知去向,然後深夜回來飯館露個臉。
「回家不?」
他悄悄問我,我點點頭就開始準備回去。就這樣,我們也會時常一起開心地回家。
「為什麼一開始沒這麼做呢?我現在覺得特別幸福。」
「對女人而言,沒什麼幸福不幸福的。」
「是嗎?你這麼一說,倒也讓人覺得有點道理。那,男人又怎麼樣呢?」
「對男人而言就只剩不幸了,無時無刻要與恐懼抗爭。」
「聽不懂你說的,可是我真想能夠天天這樣生活,椿屋的老闆和老闆娘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呢。」
「那兩個傻子,他們都是鄉下人,實際上貪婪得很,讓我喝酒說到底還不是為了賺錢。」
「做生意沒辦法的啊。不過話說回來,事情也沒那麼簡單吧?那個老闆娘跟你肯定有一腿。」
「那是以前了。怎麼?老頭察覺出來了?」
「他好像都知道,一邊歎氣一邊說過騙了錢又騙色什麼的。」
「我啊,這麼說聽上去有點裝腔作勢,但我真的很想死,從剛生下來就成天想著死。為了大家,我還是去死的好,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偏偏,我卻怎麼死也死不了。有個奇怪的可怕神靈一樣的東西,總是牽絆著我尋死的腳步。」
「因為有工作要做嘛。」
「工作什麼的,根本就不值一提。壓根就沒有傑作和垃圾的分別,人們說好它就好,說它壞它就壞。就像吸氣呼氣一樣。真是可怕啊,世上的某處有神靈存在。肯定有吧?」
「啊?」
「肯定有吧?」
「我,不知道啊。」
「是嗎?」
在飯館上了十幾二十天班,我漸漸感覺到來椿屋喝酒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是罪犯的,倒是丈夫還算是個善良的人。而且,不僅僅是飯館裡的客人,我漸漸覺得路上走的人們,幾乎都藏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罪惡。一個穿著得體的,五十歲上下的夫人從椿屋的旁門進來推銷酒,清清楚楚地說是三百塊錢一升。因為比市面上的價錢便宜,老闆娘就當即決定買下來,可結果卻是摻水的。看起來那麼高貴的一個夫人都必須幹這樣下三濫的事情才能活下去,這樣的世界,我覺得我根本不可能毫無虧欠地全身而退。這個世間的道德,有沒有可能像玩撲克牌一樣,最終負負得正呢。
神,如果你存在世上,請你出來!
正月末,我被飯館的一個顧客給玷污了。
那天晚上下著雨,丈夫沒有來。丈夫以前認識的出版社的那個偶爾會到家裡給我送生活費的矢島先生和一個看起來也和矢島差不多的四十多歲的同行一起來了。兩個一邊喝酒,一邊大聲半開玩笑地討論大谷的老婆在這樣的地方打工合適不合適什麼的。
我笑著問:「你們說的那個老婆現在在哪啊?」
矢島回答:「不知道現在在哪啊,反正至少比椿屋的小幸漂亮高貴。」
「真讓人嫉妒啊。能和大谷先生那樣的人一起,哪怕只陪他一夜我也願意。我就是喜歡那樣狡猾的人。」
「看見了吧,她就這樣。」
矢島看著同來的那位,撇了撇嘴。
那個時候,和丈夫同來的記者已經知道我是一個叫大谷的詩人的老婆。一傳十十傳百,也有好事之人聞訊專程來找我尋開心。看著飯館一天天生意興隆,老闆高興得喜上眉梢。
那天晚上,矢島兩個就紙張的地下買賣進行了商談,十點多的時候離開了。眼看外面下著雨,丈夫估計也不會來了,儘管還有一個客人沒走,我已經開始準備回家。我抱起裡屋睡著的孩子,把他背在背上,小聲地跟老闆娘說:「又得借你的傘用一下了。」
「我帶傘了,我送你吧。」
最後沒走的那個客人一本正經地站起來跟我說。他二十五六歲,身材瘦小,看上去像是個工人。這位客人我還是今天晚上第一次見到。
「不敢勞您大駕,我一個人習慣了。」
「別客氣,你家遠,我知道。我也是住在小金井附近的,我送你吧。大娘,麻煩結帳。」
他在飯館只喝了三杯酒,看上去倒也沒醉。
我們一起坐上電車,在小金井下了,然後同打一把傘走在下著雨的漆黑的路上。那個年輕人,在那之前一直是不言不語,突然一字一頓地說:「我都知道。我啊,是大谷先生的詩迷。我呢,也寫詩,一直希望著有機會能給大谷先生看看,可是我又特別害怕大谷先生。」
走到家了。
「謝謝你了,那我們店裡再見。」
「嗯,再見。」
年輕人在雨中離去了。
深夜,聽到嘎拉嘎啦有人開大門的聲音,我醒過來,以為又是丈夫酒醉回家,就翻了個身繼續睡覺。
「打擾了,大谷夫人,你在家嗎?」聽著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起來開燈到門口一看,原來是剛才的那個年輕人,看上去他醉得幾乎站都站不住。
「夫人,真是對不起,回家的路上又去攤子上喝了幾杯。其實我家住在立川,走到車站已經沒有車了。夫人,麻煩你了,讓我在你這住一晚吧。被子什麼的都不用,在進門的臺階上都行。我明天一早坐首班車走,麻煩讓我住一晚吧。其實只要不下雨,我在隨便什麼地方的屋簷下都能湊合一晚,可是現在下著雨,真的是沒辦法了。拜託你了。」
「哦,反正我丈夫不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睡進門的臺階吧。」
我說著,給他拿了兩塊破坐墊放在了臺階上。
「對不起。啊,喝醉了。」
他痛苦地小聲念叨著,一頭倒在臺階上睡下。等我回到床上,他已經是鼾聲如雷了。
就這樣,第二天的清晨,我竟然輕易被這個男的給佔有了。那天,我表面上還是一如既往地背著孩子去飯館上班了。中野飯館的院子裡,桌上擺著裝滿酒的玻璃杯,丈夫正一個人看著報紙。在上午的陽光下,玻璃杯顯得十分漂亮。
「一個人都沒有?」
丈夫朝我看看:「嗯,大叔去進貨了還沒回來,大娘剛才好像在廚房裡,現在不在嗎?」
「昨天你怎麼沒來?」
「來了啊。這段時間,看不見椿屋的小幸我都睡不著覺。我十點多過來露了個面,他們說你剛剛回去了。」
「然後呢?」
「然後我就住下了,就在這兒。昨天下那麼大的雨。」
「那我從今往後也乾脆就一直住在這兒算了。」
「行啊,應該沒問題。」「那就這麼說定了。一直租著咱們那個房子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丈夫沒說話,專注地看著報紙。「唉,這些人又在上面寫我的壞話,說我是奉行享樂主義的假貴族。真是信口雌黃,說我是畏懼神靈的享樂主義還差不多。小幸,你看,這裡說我是一個敗類,這不是胡說八道嗎。我實話跟你說,其實去年年末的時候,我是想著讓小幸和孩子過個久違的好年才從這兒拿走那五千塊錢的。正因為我不是敗類所以連這樣的事都幹得出來。」
我聽了倒也沒有怎麼開心。
「敗類什麼的也無所謂吧。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好了。」我說。
也就是三十分鐘,不,甚至可能更短,只一轉念的功夫,老闆就一個人回來了。他走到我身旁說:
「夫人,多謝了,他把錢給還上了。」
「真的?那太好了。全都還了?」老闆詭異地笑著:
「嗯,也就是昨天拿走的那些。」
「那到現在為止一共欠多少呢?大概來說。」
「兩萬塊。」
「就這麼多?」
「沒算零頭。」
「我們一定還。大叔,明天開始,能讓我在你這兒打工嗎?求你了!算是打工還債。」
「夫人,沒看出來,想當小輕(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為夫賣身打工的女人)啊。」
我們兩個齊聲笑了起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我在中野的飯館辭別了眾人,背著孩子回到了自己小金井的家裡。儘管丈夫依舊沒有回來,可是我卻一點也不擔心。明天只要再去飯館裡,說不定就能碰到他。我怎麼這麼長時間都沒意識到有這樣的好事啊,迄今為止吃了那麼多的苦,原來都是因為自己傻,沒有想到這麼好的主意。想想我以前在淺草的父親的攤頭,接待顧客那是一點也不含糊,從今以後在這個中野的飯館裡我也肯定能夠大顯身手。單是今天一晚上,我就拿了將近五百塊的小費呢。
從老闆那裡聽說,丈夫在昨夜的事發生之後就去了不知哪裡的熟人家裡住下了,然後一大早竄到那個漂亮夫人經營的京橋的酒吧裡,大白天的喝起威士忌酒,接著以聖誕禮物為名,隨隨便便拿錢給了在酒吧裡打工的五個女孩,之後在中午左右叫了計程車不知去了哪裡。一會等他回來,帶回了聖誕的三角帽啊、假面啊、裱花蛋糕啊和火雞。他讓人給各處打電話,召集了各種朋友,開了盛大的宴會。酒吧的夫人知道他向來幾乎就是身無分文,心裡覺得奇怪就悄悄質問他錢的來源,誰知他也不避諱,一五一十地就把昨天晚上的事給坦白了。因為那個夫人和他長期以來就不是一般的關係,也不忍看到事情鬧大,
他被人告到員警那裡去,就好言相勸地讓他一定把錢還回去,錢由夫人先行墊付。就這樣,丈夫才帶著那位夫人來了這個中野的飯館。
老闆對我說:「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夫人,你可真是先知先覺,連這一步都能事先看到。你是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嗎?」
老闆大概是覺得因為我早就預測到錢會這樣被還回來,才提前到他店裡去等的。聽他這麼一說,我笑著,簡單地搪塞了一句:
「嗯,看你說的。」
第二天開始,我的生活簡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都變得讓人充滿期待。我迫不及待地去燙髮館做了頭髮,添置了化妝品,縫好了和服,老闆娘還送給了我兩雙新的白襪套。長久以來在我心中積壓的苦悶,全都一掃而光了。
我早上起來和孩子一起吃了飯,然後做了便當,背上孩子就去中野上班了。時逢新年,正是飯館忙碌的時節,我在飯館裡被人叫做椿屋的小幸,每天忙得不可開交。丈夫每兩天裡大概有一次會來這裡喝酒,每次讓我付了錢就一下子又不知去向,然後深夜回來飯館露個臉。
「回家不?」
他悄悄問我,我點點頭就開始準備回去。就這樣,我們也會時常一起開心地回家。
「為什麼一開始沒這麼做呢?我現在覺得特別幸福。」
「對女人而言,沒什麼幸福不幸福的。」
「是嗎?你這麼一說,倒也讓人覺得有點道理。那,男人又怎麼樣呢?」
「對男人而言就只剩不幸了,無時無刻要與恐懼抗爭。」
「聽不懂你說的,可是我真想能夠天天這樣生活,椿屋的老闆和老闆娘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呢。」
「那兩個傻子,他們都是鄉下人,實際上貪婪得很,讓我喝酒說到底還不是為了賺錢。」
「做生意沒辦法的啊。不過話說回來,事情也沒那麼簡單吧?那個老闆娘跟你肯定有一腿。」
「那是以前了。怎麼?老頭察覺出來了?」
「他好像都知道,一邊歎氣一邊說過騙了錢又騙色什麼的。」
「我啊,這麼說聽上去有點裝腔作勢,但我真的很想死,從剛生下來就成天想著死。為了大家,我還是去死的好,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偏偏,我卻怎麼死也死不了。有個奇怪的可怕神靈一樣的東西,總是牽絆著我尋死的腳步。」
「因為有工作要做嘛。」
「工作什麼的,根本就不值一提。壓根就沒有傑作和垃圾的分別,人們說好它就好,說它壞它就壞。就像吸氣呼氣一樣。真是可怕啊,世上的某處有神靈存在。肯定有吧?」
「啊?」
「肯定有吧?」
「我,不知道啊。」
「是嗎?」
在飯館上了十幾二十天班,我漸漸感覺到來椿屋喝酒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是罪犯的,倒是丈夫還算是個善良的人。而且,不僅僅是飯館裡的客人,我漸漸覺得路上走的人們,幾乎都藏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罪惡。一個穿著得體的,五十歲上下的夫人從椿屋的旁門進來推銷酒,清清楚楚地說是三百塊錢一升。因為比市面上的價錢便宜,老闆娘就當即決定買下來,可結果卻是摻水的。看起來那麼高貴的一個夫人都必須幹這樣下三濫的事情才能活下去,這樣的世界,我覺得我根本不可能毫無虧欠地全身而退。這個世間的道德,有沒有可能像玩撲克牌一樣,最終負負得正呢。
神,如果你存在世上,請你出來!
正月末,我被飯館的一個顧客給玷污了。
那天晚上下著雨,丈夫沒有來。丈夫以前認識的出版社的那個偶爾會到家裡給我送生活費的矢島先生和一個看起來也和矢島差不多的四十多歲的同行一起來了。兩個一邊喝酒,一邊大聲半開玩笑地討論大谷的老婆在這樣的地方打工合適不合適什麼的。
我笑著問:「你們說的那個老婆現在在哪啊?」
矢島回答:「不知道現在在哪啊,反正至少比椿屋的小幸漂亮高貴。」
「真讓人嫉妒啊。能和大谷先生那樣的人一起,哪怕只陪他一夜我也願意。我就是喜歡那樣狡猾的人。」
「看見了吧,她就這樣。」
矢島看著同來的那位,撇了撇嘴。
那個時候,和丈夫同來的記者已經知道我是一個叫大谷的詩人的老婆。一傳十十傳百,也有好事之人聞訊專程來找我尋開心。看著飯館一天天生意興隆,老闆高興得喜上眉梢。
那天晚上,矢島兩個就紙張的地下買賣進行了商談,十點多的時候離開了。眼看外面下著雨,丈夫估計也不會來了,儘管還有一個客人沒走,我已經開始準備回家。我抱起裡屋睡著的孩子,把他背在背上,小聲地跟老闆娘說:「又得借你的傘用一下了。」
「我帶傘了,我送你吧。」
最後沒走的那個客人一本正經地站起來跟我說。他二十五六歲,身材瘦小,看上去像是個工人。這位客人我還是今天晚上第一次見到。
「不敢勞您大駕,我一個人習慣了。」
「別客氣,你家遠,我知道。我也是住在小金井附近的,我送你吧。大娘,麻煩結帳。」
他在飯館只喝了三杯酒,看上去倒也沒醉。
我們一起坐上電車,在小金井下了,然後同打一把傘走在下著雨的漆黑的路上。那個年輕人,在那之前一直是不言不語,突然一字一頓地說:「我都知道。我啊,是大谷先生的詩迷。我呢,也寫詩,一直希望著有機會能給大谷先生看看,可是我又特別害怕大谷先生。」
走到家了。
「謝謝你了,那我們店裡再見。」
「嗯,再見。」
年輕人在雨中離去了。
深夜,聽到嘎拉嘎啦有人開大門的聲音,我醒過來,以為又是丈夫酒醉回家,就翻了個身繼續睡覺。
「打擾了,大谷夫人,你在家嗎?」聽著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起來開燈到門口一看,原來是剛才的那個年輕人,看上去他醉得幾乎站都站不住。
「夫人,真是對不起,回家的路上又去攤子上喝了幾杯。其實我家住在立川,走到車站已經沒有車了。夫人,麻煩你了,讓我在你這住一晚吧。被子什麼的都不用,在進門的臺階上都行。我明天一早坐首班車走,麻煩讓我住一晚吧。其實只要不下雨,我在隨便什麼地方的屋簷下都能湊合一晚,可是現在下著雨,真的是沒辦法了。拜託你了。」
「哦,反正我丈夫不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睡進門的臺階吧。」
我說著,給他拿了兩塊破坐墊放在了臺階上。
「對不起。啊,喝醉了。」
他痛苦地小聲念叨著,一頭倒在臺階上睡下。等我回到床上,他已經是鼾聲如雷了。
就這樣,第二天的清晨,我竟然輕易被這個男的給佔有了。那天,我表面上還是一如既往地背著孩子去飯館上班了。中野飯館的院子裡,桌上擺著裝滿酒的玻璃杯,丈夫正一個人看著報紙。在上午的陽光下,玻璃杯顯得十分漂亮。
「一個人都沒有?」
丈夫朝我看看:「嗯,大叔去進貨了還沒回來,大娘剛才好像在廚房裡,現在不在嗎?」
「昨天你怎麼沒來?」
「來了啊。這段時間,看不見椿屋的小幸我都睡不著覺。我十點多過來露了個面,他們說你剛剛回去了。」
「然後呢?」
「然後我就住下了,就在這兒。昨天下那麼大的雨。」
「那我從今往後也乾脆就一直住在這兒算了。」
「行啊,應該沒問題。」「那就這麼說定了。一直租著咱們那個房子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丈夫沒說話,專注地看著報紙。「唉,這些人又在上面寫我的壞話,說我是奉行享樂主義的假貴族。真是信口雌黃,說我是畏懼神靈的享樂主義還差不多。小幸,你看,這裡說我是一個敗類,這不是胡說八道嗎。我實話跟你說,其實去年年末的時候,我是想著讓小幸和孩子過個久違的好年才從這兒拿走那五千塊錢的。正因為我不是敗類所以連這樣的事都幹得出來。」
我聽了倒也沒有怎麼開心。
「敗類什麼的也無所謂吧。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好了。」我說。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