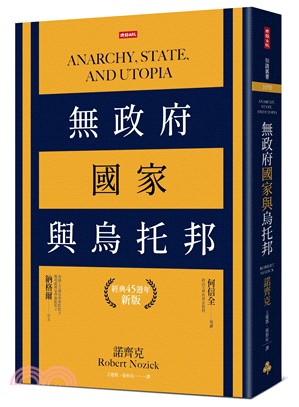商品簡介
自由意志主義奠基之作
美國國家圖書獎最佳哲學與宗教類
全球翻譯超過100種語言
二戰後百大影響人類社會書籍
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暨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納格爾(Thomas Nagel)作序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何信全導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書發表於一九七四年,是繼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之後,英美政治哲學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諾齊克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對現代自由主義的轉向,並要求政府積極介入財富重新分配深表不滿,而主張應該回歸市場機制運作。
諾齊克透過本書,將市場經濟的思潮推向嚴謹的哲學論證。他的論證是以個人權利為核心,而歸結於最低限度的國家,是在道德上真正能被證成烏托邦架構的思惟。諾齊克認為,唯一正當的政府是最小政府,僅限於維持契約執行、保衛公民安全,以及保護財產。他主張:行動與結社自由的個人權利,具備道德優先權,不應受到干涉;政治機構引用的道德原則,必須源於人們的自然權利;並否定減輕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的道德理由。
本書的論證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據洛克式的論證,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自然狀態中個人權利的維護,須由個人來執行,難免造成不便,因此必須有提供保護服務的機構;第二部分顯現他的賦予權利理論,以此批判超越最低限度國家的觀點,這些觀點支持財富重新分配的正義理念,主張規劃與實踐福利國家;第三部分,諾齊克提出烏托邦架構,他以最低限度國家為宗旨,勾勒出可允許人們依據自己認定良善的生活價值,追尋自己的烏托邦國度。
本書是一場辯證的饗宴,展示最高層次智慧的敏銳迅速,其寫作風格有種難以抗拒的聲口,充滿活力與動能,宛如在耳際訴說。諾齊克的中心論點十分明確:只要不違反他人的平等權利,每個人都絕對具備道德權利,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他人干涉。
作者簡介
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
美國哲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教授。他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父親是來自俄羅斯的猶太人企業家。諾齊克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是全球哲學界的重要人物,對政治哲學、決策論和知識論,都做出重大貢獻。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本書以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出發,反駁同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在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
譯者簡介
王建凱(前言至第十章)
台大政治系暨政治學研究所畢業。
張怡沁(序文)
台大政治系學士,紐約大學碩士,曾任新聞記者、金融公關與出版編輯,現專事瑜伽教學與翻譯。
目次
導讀
序文
前言
第一部 自然狀態理論,或如何自然而然地追溯一個國家
第一章 為什麼要探討自然狀態理論?
政治哲學∕解釋性政治理論
第二章 自然狀態
保護性社團∕支配的保護性社團∕「看不見的手」的解釋∕支配的保護性社團是一個國家嗎?
第三章 道德限制與國家
最小限度的國家與超小限度的國家∕道德限制與道德目標∕為什麼是邊際限制?∕自由主義限制∕限制與動物∕體驗機∕道德理論的難於確定∕限制的根據是什麼?∕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
第四章 禁止、賠償與冒險
獨立者與支配性保護機構∕禁止與賠償∕為何要禁止?∕懲罰的報復理論與制止理論∕交換利益的劃分∕恐懼與禁止∕為什麼不一律禁止?∕冒險∕賠償原則∕生產性交換
第五章 國家
禁止個人私自強行正義∕「公平原則」∕程序的權利∕支配性機構可以如何行動?∕事實上的獨佔權∕保護其他人∕國家∕對於國家「看不見的手」的解釋
第六章 對國家論證的進一步探討
停止這一過程?∕先發制人的攻擊∕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正當性∕所有人懲罰的權利∕預防性限制
第二部 超越最小限度的國家?
第七章 分配的正義
第一節:權利理論∕歷史原則與目的:結果原則∕模式化∕自由如何攪亂模式∕
斯恩的論證∕再分配與所有權∕洛克的獲取理論∕洛克的條件
第二節:羅爾斯的理論∕社會合作∕合作的條件與差別原則∕原初狀態與目的:結果原則∕總體與個體∕自然資質與任意性∕肯定的論據∕否定的論據∕集體的資產
第八章 平等、嫉妒、剝削及其他
平等∕機會平等∕自尊與嫉妒∕有意義的工作∕工人自治∕馬克思主義中的剝削∕自願的交換∕慈善∕對影響你的事情的發言權∕非中立的國家∕再分配如何進行?
第九章 民主化
一致性與平行的例證∕功能更多國家的引出∕假設的歷史
第三部 烏托邦
第十章 一種用於烏托邦的架構
模式∕投向我們現實世界的模式∕架構∕設計手段與過濾手段∕作為烏托邦共同基礎的架構∕共同體與國家∕發生改變的共同體∕全面控制的共同體∕烏托邦的手段與目的∕烏托邦產生什麼結果?∕烏托邦與最小限度的國家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機會平等
機會平等在許多作者看來是最低限度的平等主義目標;如果有問題的話,問題僅在於這一要求是否太弱。(許多作者也注意到,家庭的存在如何阻礙這一目標的充分達成。)有兩種試圖提供這種平等的方式,一種是直接削弱那些機會較好者的狀況,另一種是改善那些機會較差者的狀況。後者需要使用資源,所以也涉及剝弱某些人的地位:他們被取走一些持有,以改善別人的地位。但是,這些人擁有權利的持有可能是不可以被奪取的,即使這是為了提供他人的機會平等。在缺少魔杖的情況下,還剩下達到機會平等的唯一手段,就是說服人們自願貢獻一些他們的持有。
為了獎金而賽跑的例子,常被用來討論機會平等。某些人的起點比另一些人更靠近終點的賽跑,是不公平的。同樣地,某些人被迫背負重物或鞋裡放石子的賽跑,也是不公平的。但生活並不是我們都參與競爭以獲取獎金的賽跑,並不存在任何統一、由某人裁判速度的賽跑。相反地,生活是不同的人,分別給別人不同的東西。那些給予者(時常是我們每個人)通常並不關心應得的問題,不關心對方所遇到的障礙;他們關心的只是他們實際上要得到的東西。沒有任何集中的過程來裁判人們對其機會的使用,這也不是社會合作與交換的目的。
有一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某種機會的不平等看來是不公平,而不只是某些人什麼機會也沒有的不幸(有時真是這樣,即使別人並不因此有較大的利益)。有權轉讓的持有人,沒有一定要把它轉讓給某個人的特殊願望,這相對於遺贈財物給孩子或送禮物給某人的情況。這個持有者願意轉讓給滿足某一條件的人(例如,能提供他某種好處或服務以作交換的人,或能做某種工作且能付薪水的人),他也同樣願意轉讓給滿足這一條件的人。是某人得到這一轉讓,而非另一個較少機會滿足轉讓者之條件的人得到這一轉讓,這不是不公平的嗎?既然給予者並不在乎他轉讓給誰,而只要接受者滿足某個一般性的條件;所以作為一個接受者的機會平等,在這種情況下將不會侵犯到給予者的權利。它也不會侵犯有較多機會者的權利。當機會較多者對他持有的東西擁有權利時,他並無權利一定要其所持有的東西多予別人,但如果機會較少者有一平等的機會豈不更好?如果有人能如此增加他的機會,而不侵犯別人的權利,他不是應當這樣做嗎?這不是更公平嗎?如果這將是更公平的,這種公平能不能證明逾越某些人的權利,以獲得資源來援助那些機會較少者進入較平等的競爭地位是正當的呢?
這一過程是競爭性的,就像下面這樣:如果機會較多者並不存在,轉讓者就可能和那些本來機會較少者交易,這些人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可以交易的最好人選。這不同於下述狀況:在其中,沒有聯繫但是相似的存在物生活在不同的行星,面臨不同的困難,並有不同的機會實現他們互異的目標。在那裡,一個存在者的狀況並不影響另一個存在者的狀況,雖然若條件較差的行星得到比它現在要好的條件是較好的事情(如果條件較好的行星得到比它現在更好的條件,那也是較好的事情),但那不是較公正的。它也不同於下述狀況:在其中,一個人雖然能夠,但不願意去改善另一個人的狀況。在我們討論的這種特殊情況中,如果某個機會較多者不存在,機會較少者的狀況就會變得好些。我們不僅可以把機會較少者看作是生活較好的人,或不願助他人的人,還可以把他視為是阻止或妨礙機會較少者處境變好的人。這種阻礙另一個人成為較具吸引力的交易夥伴的情況,固然不能直接削弱(例如經由偷竊)別人的地位相提並論,但是機會較少者也不能合理地抱怨,他被另一個並不應得較好機會,以滿足某些條件的人所阻礙嗎?(暫且不談另一個機會更少者,可能對這個抱怨者做出類似的抱怨。) 雖然我們可以感受到前面兩段所提出的問題的力量,我還是不相信它們能推翻一種徹底的權利概念。如果那個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女子,因為我而拒絕另一個求婚者(若不是因為我,她將會和他結婚);且這種拒絕是由於我的敏銳智力和英俊相貌,而這兩個優點並不是我努力掙來或應得的;那麼,那個智力和相貌稍遜的被拒絕者,可以正當地抱怨說這不公平嗎?我對別的求婚者贏得女性歡心的這種妨礙,是否證明我取走某些資源,為他做美容手術、進行特殊的智力訓練,或者發展他的某些我沒有的優越特徵,以使我們被選中的機會平等是正常的呢?(我在此已假定那種直接削弱機會較好者的地位,以達到機會平等的方式是不允許的。這種方式在這個例子中表現為使機會較好者破相,或藉由注射藥物、製造噪音,而使他不能充分運用智力。)沒有這樣的結論可以被推演出來。(這個被拒絕的求婚者將對誰、對什麼事,有合理的抱怨呢?)如果不平等的機會是來自於人們隨其意願行動,或轉讓其權利的累積結果,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至於那些不可能被合理地指責,對第三方有妨礙結果的消費品,這種論證甚至更為容易。如果一個孩子在有游泳池的家庭長大,他每天使用,即使他並不比另一個家裡沒有游泳池的孩子更應得它,這是不公平的嗎?這樣一種狀況應當被禁止嗎?如果不應禁止,為什麼就應當反對經由遺贈把游泳池轉讓給一個成年人呢?
有人說,每個人對諸如機會平等、生命都有權利,並可強行這種權利;這種說法的主要缺點是:這些「權利」要求某些事物、物質和行為作為基礎,而其他人可能對這些東西已經擁有權利。對於那種需要使用別人擁有權利的事物或活動的東西,任何人都不對它擁有權利。其他人對特殊事物、那枝鉛筆、他們的身體等權利,以及他們選擇使用這些權利的方式,形成任何個人及他能用的資源的外部環境。如果他的目標需要使用別人擁有權利的資源,他必須求得他們的自願合作。甚至,他決定怎樣使用自己擁有的東西的權利時,都可能需要其他人擁有的權利資源(例如使他生存的食物);他必須把其可行的方案與他人合作,聯結起來。
特殊的人對特殊的事物有著特殊權利,各人也有與他人達成協議的特殊權利──只要你和他們都有達成協議的資源。(沒有人必須提供給你一支電話,以便你可以和另一個人達成協議。)在這種與特殊權利基礎的衝突之中,並沒有任何權利存在。既然任何純粹達到一個目標的權利,都不可避免地要和這種基礎發生衝突,因而沒有任何這樣的權利存在。對事物的特殊權利填滿了權利的空間,而沒有給在某種物質條件下存在的一般權利留下餘地。而與此相反的理論,則只想把這種普遍持有、欲達某些目標,或在某種物質條件下存在的一般權利作為其基礎,以便決定所有其他的權利;但就我所知,還沒有人認真地嘗試去敘述這一相反的理論。
自尊與嫉妒
把平等與自尊聯繫起來是合理的。嫉妒的人如果不能夠擁有一件別人擁有的東西,他就寧願別人也不擁有它。比起別人有而自己沒有來說,他寧願大家都沒有。
人們常常指責說,嫉妒構成平等主義的基礎。另一些人則回答:既然平等主義原則是可以另外證明,我們不必把名聲不好的心理歸之平等主義者;他只是希望正確的原則被實現而已。鑒於人們在設想原則使自己的情緒合理化方面本領高超,以及在難於發現平等本身是有價值的論據的情況下,這一回答可以說是未獲證明。(一旦人們接受平等主義原則,他們便可能支持削弱自己的地位實行這一原則的事實,也無法證明這一點。)
在此,我更願注意嫉妒情緒的奇妙性質。為什麼有些人寧願別人在某方面得分不比他們高,而不願為別人的狀況較好或幸運感到高興呢?他們不是可以不屑一顧嗎?有一條看來特別值得探討的線索:在某方面有得分的某人A,希望另一個得較高分數的某人H比自己差──即使這不會提高他的得分;因為在某些人得分比他高的情況下,會威脅或破壞他的自尊,並使他感到自己在某一重要方面劣於別人。別人的行動或其特免,怎麼會影響一個人的自尊呢?我的自尊、自我價值感,不是應當僅依賴於與我有關的事實嗎?如果我以這種方式評價自己,那麼涉及他人的事實怎麼能夠在此起作用呢?答案是:我們經由自己的行為與別人能做的事情比較,而判斷我們做得有多好。假設一個生活在偏僻山村的人,在一百五十次的籃球跳投能命中十五次,而村裡其他人跳投一百五十次只能命中一次,他就會認為自己是長於此道。然而在某一天,來了一位籃球明星,這時情況會怎樣呢?再者,一位非常努力工作的數學家,偶爾想出一個有趣的推測,並巧妙證明一個命題。然後他發現一群數學天才,他努力提出一個推測,但他們很快就證明它或者否定它,並建構出很精緻的論據,且他們自己也想出非常深刻的命題;這時情況會怎樣呢?
在這兩個例子中,當事人最後都將做出結論:他並不很擅長或精於此事。如果不參照別人是怎樣做或能否做這件事,就沒有某件事做得有多好的標準。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在他的《文學與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裡描述,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變成什麼樣子:
人們將變得無可比擬地強壯、聰明和機智,他的身體將變得更和諧,他的活動將更有韻律,他的聲音將更具音樂性,生活方式將變得富於生氣和戲劇性。一般人將提升到亞里斯多德、歌德或馬克思的水準,而在這些山峰之上,又將有新峰頂出現。
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那麼那些只是處在亞里斯多德、歌德或馬克思水準上的一般人,將不認為自己很擅長或精於這些活動。他仍會有自尊的問題。某個處在如前面所述的投籃者或數學家地位的人,可能寧願別人沒有他的那份才能,或至少不再在他面前表現,這樣他的自尊將免受打擊而得到支持。
這將是一個可能的解釋:為什麼某些收入的不平等、工業社會中權力地位的不平等,或企業家相對於其雇員之間的不平等會如此刺傷人;這並不是導因於那種較優越地位是不應得的感覺,而是由於它是應得和掙取來的。它可能傷害某個人的自尊,使他在知道別人成就較大或發展較快時感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較低。工廠裡的工人,剛開始對先前也是工人的成功者感到吃驚,且產生這樣的想法:為何不是我呢?為什麼我沒有這種成就呢?然而若不是每天都碰到他,人們很容易忽略別人在他處取得較大成就。這一點並不依賴於,一個人是否應得他在某方面的優越地位。某個人跳舞跳得很好,這將影響你對自己跳舞跳得有多好的評價。即使你認為,舞蹈大部分都依賴於並非由努力得到的天賦。
作為一個體現這些問題的結構(而不是作為一種心理學理論的探討),考慮下列簡單的模型。有一系列不同面向及人們在其中將隨之不同面向的特質,D1, D2, ……D11, 而人們被認為這些特質是有價值的。人們可能對究竟哪些面向是有價值的,以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面向其價值有多高(非零值)有不同的意見。對每個人來說,將有一種事實描述顯示他在各個面向的客觀地位;例如,在籃球跳投方面,我們可能有這樣的描述:「從二十英尺外跳投一百次的通常得分為──」,而一個人得分可能是二十,或三十四、六十七。
為簡明起見,讓我們假定一個人對有關他的事實描述的看法是相當準確的,並將有一種評價性描述來表現這個人,是怎樣評價他自己在事實描述方面的得分。在這方面還有一些評分標準(例如優良、尚可、滿意、差、極差)來表現他對自己在各面向的評價。這些個人評價──不管他是怎樣從事實描述中得到──將依賴於他對相似的別人之事實描述的實際看法(即:對照組),以及他童年時就確定的目標等等。所有這些評價決定他的抱負水準,而這個水準在一定時間裡將以可覺察的方式變化。每個人都將對自己做某種全面的評價;在最簡單的情況中,這將只依賴於他的評價性描述和他對各個面向的評價。這種依賴的方式將因人而異。有些人可能把他們在所有面向的得分加權起來衡量,另一些人則只要他們在某些重要的面向做得不錯就對自己滿意;還有一些人則可能覺得,只要自己在某個重要的面向失敗就會一蹶不振。
在一個人們同意某些面向是很重要的社會裡,如果人們在這些面向存在著差距,且某些制度公開地根據他們在這些面向的地位來組織他們的社會;那些得分較低的人,可能會覺得自己劣於那些得分較高的人,他們可能覺得自己作為人是低劣的。(因此,卑微的人可能變得把自己看作是卑微的人。)一個人可能試圖經由改造社會來避免這種劣等的感覺,或者使這些把人們區別開的面向變得不那麼重要,或者使人們沒有機會公開實行他們在這些面的能力,或者使大家沒有機會知道別人這些面向上的得分。
很明顯的,如果人們因為他們在某些面向做得很糟而感到低人一等,那麼,如果這些面向的重要性減低,或者大家得分相等,他們將不再感到低人一等。他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的理由被排除了。但別的一些面向,很可能取代被貶低的面向(對另一些人),並產生同樣的效果。在貶低或拉平某一其他的面向(比方說審美力、魅力、智力、體育、探險、體質等等);那麼,這種現象將重新出現。
人們一般都根據他們與別人在某些最重要面向的差別來判斷自己,他們並不會把自己作為人的通常能力,與有這些能力的動物相比較而從中得到自尊。(「我是相當不錯的,我有與其他手指相對的拇指,而且能講某種語言。」)。人們也不會因為他們擁有投票選舉政治領袖的權利而得到或保持自尊,雖然當選舉權並不被廣泛享有時,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同樣,今天的美國人不會因為他們能寫能讀而感到自己有價值,雖然在歷史上許多別的社會裡會有這種情況。當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擁有某種東西或特質時,這種東西或特質並不作為自尊的基礎起作用。自尊是建立在有差別的特質上的,這就是稱其為自尊的原因。正像研究對照組的社會學家喜歡指出的那樣:他人就是改變你的人。知名大學的一年級學生,可能有一種自己進了這個大學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在他們要進又尚未進這個大學前的一段時間裡最明顯。但與他們交往的所有人都處在同一地位時,進這個大學的事實就不再是自尊的基礎,除了放假回家(或在想像中)面對那些並非與他處在同樣地位的人的時候。
那麼,你怎麼為那個也許因為能力有限,而在其他人認為重要的面向都比其他人得分低的人建立自尊呢?你可以告訴那個人,雖然他的絕對分數是低的,但他已經做得很好了(以他有限的能力)。他比大多數人更多地實現自己的才能,比別人更充分地運用自己的潛力;考慮到他的起點,他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這將經由引用另一個重要的面向,而提出比較性的評價,在這個面向上,他與別人比起來確實做得很好。
這些考慮使我們多少產生下述疑問:經由扯平在自尊依賴的某一面向的差距,來平衡自尊和減少嫉妒是否可行。想想有多少種能引起別人嫉妒的特質,就能瞭解為什麼有那麼多自尊不等的機會。現在回想一下托洛斯基的推測: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所有人都將達到亞里斯多德、歌德或馬克思的水準,同時新的高峰又將在那裡出現。這樣,處在歌德等人的水準上的事實,將不再給每個人超過其語言能力和用手抓物能力的自尊和個人價值感。某些簡單和自然的假設,甚至可能導致一個使嫉妒保留的原則,人們可能擔心:如果諸面向的數量不足,且做出巨大的努力來排除差別,那麼隨著有差別的面向的減少,嫉妒將變得更嚴重。因為在有差別的面向不多的情況下,許多人將發現他們在每一個這些面向上都情況不佳。雖然對一系列各個不同的常態分配,其加權總額將是常態,但如果(知道他在各面向得分)每個人對各面向的加權方式不同,那麼所有不同個人的不同加權的總額,就不必然是一種常態分配。即使每個面向的得分都是按標準分配。每個人都可能認為自己處在分配的較高處(即使這是一種常態分配),因為每個人都是經由他選定的特殊加權方式來看待分配。可比較之面向的數量越少,一個人也就越沒有機會成功地使用並不統一的衡量辦法──即更重視他得分高的面向──而為其自導奠定基礎。(這暗示著,嫉妒只能經由對所有差別的排除而消滅。)
即使嫉妒比我們所想的要容易處理,但經由干預來削弱一個人的狀況,以減少知道這個人狀況的其他人的嫉妒和不幸,也是應當反對的。這樣一種辦法可比擬對某種行為的禁止(例如,禁止膚色不同的夫婦手牽手走路),而其禁止僅是因為知道這種行為將使別人不愉快。 這涉及到同一種外部干預。一個社會要避免懸殊的自尊差別,最有希望的方式是在這個社會中沒有對諸面向的統一權衡;相反地,要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及權衡方式。這將擴大每個人發現這些面向的機會:這些面向是別人也認為重要的,而自己在這些面向又做得不錯,因此能對自己做出正常的讚許評價。這種對統一的社會評價的打破,將不可能經由消除某些重要面向的努力來達到。而且,這種努力越是得到集中和廣泛的支持,就越是使某一面向引人注目地成為普遍同意的奠定人們自尊的基礎。
(摘自本書第八章:平等、嫉妒、剝削及其他)
導讀
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發展,自羅爾斯(John Rawls)在1971年發表著名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之後,頗有春雷驚蟄、大地復甦之氣象。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相繼出現。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1974年發表的這本《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便是繼羅爾斯《正義論》之後,所出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一。
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大致上以穆勒(John S. Mill)為界,可以區分為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穆勒的自由主義,正好是二者之間過渡的橋樑。古典與現代自由主義的差異,主要在於對政府功能的看法不同。前者主張政府祇應扮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不宜逾越消極性的功能;後者則認為政府不應侷限於消極的角色,而應積極地謀求社會正義之實現,特別是在財富的分配方面,不宜放任市場機能之自然運作,而應謀所以調節之道。儘管當代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彼此見解不盡一致,不過大致上分佈於上述兩個系譜之下。以諾齊克而言,他是古典自由主義這一系譜在當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代屬於古典自由主義這一系譜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嚴守捍衛個人自由的觀點,對於現代自由主義之轉向平等(特別是財富平等)深致不滿。因此,為了表示與現代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區別,他們根據「liberty」的拉丁字源「libertas」,另創「libertarianism」一字,代表他們的自由主義。在此一自由主義觀點之下,論述的主題集中在推究政府合法的功能究竟是什麼?他們基本上以一種徹底的激進方式,來回答此一問題。
如同上述,當代此一新古典自由主義運動,不滿於政府扮演積極介入財富重分配的角色,主張回歸市場機能的運作。其倡導人之中,頗多主張自由經濟的重鎮,諸如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以及羅斯巴(Murray Rothbard)諸人。他們強烈主張維護個人權利,特別是財產權與契約自由原則。由於認為財富重分配不啻強制某些人為其他人勞動,乃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因而加以拒斥。此一運動在二次大戰之後,於美國此一標榜自由立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獲得重大的伸展。其在現實政治上的展現,則是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與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on),在1980年代的執政期間,達到了頂峰。
諾齊克這一本著作,基本上可以說是將此一以捍衛市場經濟為主調的運動,推向一個嚴格底哲學論證層次。諾齊克的論證系統,以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s)為核心,逐次展開,而歸結於「最低限度的國家」(minimal state),乃是真正能在道德上被證成之理想的烏托邦架構。諾齊克在本書中的論證,分成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根據洛克式的(而非霍布斯式的)論證,指出國家的形成,溯自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個人權利的維護,需由個人自己來執行,難免諸多不便。不過,他沒有遵循洛克契約論的模式,而以一種現代市場的觀點,來解釋國家的形成。他設想由個人自己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既有諸多不便,則必有提供保護權利服務的機構(protective associations)出現。這些保護機構彼此在市場中競爭的結果,最後可能祇賸下少數保護能力較佳的強勢機構(dominant protective associations)。我們可以設想最後賸下兩個強勢機構,則可能的情況有三:一是這兩個保護機構彼此爭戰,則常常贏的一方逐漸將輸方的委託人吸走,使輸方終歸淘汰;二是這兩個保護機構分屬不同地理區域之強勢機構,則委託人將會移居自己委託之保護機構所在的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地理區域之內一個保護機構的情況;三是這兩個保護機構爭戰不已,而又相持不下。於是,他們同意設立一個仲裁者,並由此一仲裁者擁有最後決定權。如此一來,亦形成了一個唯一的強勢機構。要之,不論是上述的任何情況,最後都將形成在某一個地理區域中的人們,在一個裁判彼此爭執以保障個人權利的共同體系之下,國家之雛形於焉形成。
諾齊克此一國家形成之說明,使其將國家角色,定位在個人權利之保障。他雖然對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個人有權管理自己,其權利不容侵犯深有同感,卻不認可無政府主義者所強調任何政府的存在,都是對個人權利之侵犯。他的最低限度國家,基本上沿循古典自由主義「守夜人國家」(nightwatchman state)的基線,將國家功能定位在防止暴力、偷竊、詐欺,以及保障契約之履行等等。他認為此種最低限度的國家,為保障個人權利所必須,卻不會造成無政府主義者所擔心的侵犯個人權利之結果。不過,任何逾越此一最低限度功能之國家(ultraminimal state),則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個人權利侵犯之後果。
諾齊克這本書的第二部份,主要在揭示他的「賦予權利理論」(entitlement theory),據以批判超越最低限度國家的各種觀點。這些觀點,基本上本乎要求財富重分配之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理念,主張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之規劃與實踐。諾齊克批評分配正義是一種模式的正義觀(a patterned conception of justice),而其賦予權利理論則是一種歷史的正義觀(a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模式的正義觀站在社會資源形成的結果處,完全不問這些資源是如何形成的(資源形成的歷史過程),即根據某一特定模式(諸如需要、才能、功績或平等分配等等),做為正義的衡準,據以討論資源應該如何分配始能符合正義原則。他認為探討資源應如何分配始合乎正義的問題,應該考量資源是怎樣形成的歷史過程,始為合理。根據此一歷史的正義觀,他的賦予權利理論包含三項原則:一、佔取原則(principle of acquisition of holdings),即對於無主物的佔取,來自我們的勞動力(屬於人身的一部份)對無主物的改良,使我們對該無主物取得獨占的所有權。例如對於無主荒地之開墾,因而取得獨占的土地所有權,即是一例。諾齊克的財產權觀點,基本上承襲自洛克,他在論佔取原則時亦特別提出「洛克的但書」(Lockean proviso)——即當一個人透過其勞動力而取得對無主物的所有權時,應以「足夠並且使其他的人與以往一樣好」(enough and as good left in common for others)為條件。換句話說,對無主物所有權的取得,因其排他性的獨占而使他人無法再行佔有,其合乎正義與否,繫乎他人是否與其未佔有時一樣好。如其排他性的獨占,卻能對所擁有之生產工具開發利用,使他人不但未蒙受損失,甚至因而獲益,亦即他人之情況與原基點相同甚或更佳,則此一佔取即合乎正義原則。二、轉移原則(principle of transfer of holdings),即資源之所有權的轉移,無論是交換或贈與,皆必須基於彼此自願的同意。三、矯正原則(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violations of the first two principles),如果對於所有物的佔取或轉移未依據上述二原則,即不合乎正義,而必須加以矯正,使其合乎此二原則。諾齊克認為他的賦予權利理論,充份考量資源形成的歷史過程,而非諸如羅爾斯及當代其他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s)僅根據某一時間切面結果之原則(end-result principles or end-state principles),即據以論斷分配之正義。要之,根據賦予權利理論,批判羅爾斯及當代其他平等主義者分配正義之模式的正義觀,構成本書第二部份的主要內容。透過這些批判,諾齊克接續第一部份唯有最低限度國家才是道德上合法(morally legitimate)的論題,指出任何逾越最低限度的國家,皆無法在道德上被證成,並且無可避免地將侵犯了個人的權利。
諾齊克本書的第三部份,則在提出一個烏托邦的架構。諾齊克以他的最低限度國家為基本藍圖,描繪一個可以容許每一個人根據他自己所認定良善的生活觀,去追求他自己的烏托邦之烏托邦架構。就此而言,諾齊克所謂的烏托邦架構,可以說是一種後設的烏托邦(meta-utopia)。他強調要所有的人在某一種烏托邦社會中,快樂地實現生命,實為不太可能之事。原因在於,每個人良善的生活觀可能不同。因此所謂烏托邦應是一種追求各種烏托邦的架構(utopia is a framework for utopias),亦即任由人們自由地自願結合,嘗試尋求在一個理想的社群中,去實現他們自己良善的生活觀。於此,不容任何人將他自己的烏托邦觀點,強加諸他人之上。諾齊克認為在最低限度國家之中,我們是以不容侵犯的個人被看待。任何個人不會被他人以某種方式做為手段或工具,而是被視為擁有權利與尊嚴的個人。最低限度國家,容許我們個別地或與我們自己選擇的人們,在彼此皆為擁有同樣尊嚴的個人自願的協調合作之下,去選擇我們的生活,實現我們的價值目標。要之,他認為最低限度國家,才是一個真正理想的烏托邦架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諾齊克的最低限度國家,乃是一個尊重多元價值的自由國家。誠如庫克薩斯(C. Kukathas)與貝悌(P. Pettit)所指出:「自由主義可以視為對形塑現代世界之多元主義(pluralism)一項重要的哲學回應。在現代社會中,賦予宗教與道德價值多樣性,諸多善的觀點(conceptions of the good)競存,若干人對產生一種為所有人所接受之善的理論已經絕望。對此,自由主義的回應,在於倡導對不同生活方式儘可能地寬容。」自由主義此種尊重多元價值,強調自由國家之價值中立性(liberal neutrality of state)的基本論旨,並非祇是展現在諾齊克理想的烏托邦架構——最低限度國家之中而已。儘管在自由主義的論旨上頗多不同,然而就此一國家價值中立性之基本論旨而言,德渥金(R. Dworkin)、羅爾斯與諾齊克可以說頗為一致。德渥金認為政府應該以平等的關照與尊重(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對待每一個國民,然而如果政府本身有其價值偏好,即無法對價值觀點未必相同的國民,做到平等的關照與尊重。羅爾斯則為了體現在政治界域中對多元價值的尊重,在代表後期思想之《政治的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一書中,以「交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概念為核心,對其正義理論進行重構。
做為當代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諾齊克這本書所要捍衛的自由,誠如若干論者所指出,主要是個人擁有不容侵犯的財產權之自由。蓋諾齊克論證的基礎,既非功利主義者的「幸福」,亦非其他自由主義者的「自由」,而是絕對的財產權——對自己以及世界的事物之所有權。除非是在個人自願同意,或因侵犯他人權利而致個人權利受到剝奪的情況之下,否則此一所有權絕不容他人侵犯。同時,就諾齊克而言,個人的自由權利亦非由任何自由主義原則推導而來,而僅僅是此一對自我的所有權(right to selfownership)之歸結而已。這些論斷,基本上頗為中肯。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諾齊克的這一本著作,乃是對於當代捍衛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運動,提供一個嚴格底哲學論證體系。
諾齊克因此書而與羅爾斯齊名,兩人的觀點不同,而學術上批評討論的文章則歷久不歇。相較於羅爾斯一生論述,皆圍繞其《正義論》一書而言,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在其論述中難免稍顯孤兀。蓋在此書之後,諾齊克的三本後續著作《哲學解釋》(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1981)、《生命之檢驗》(The Examined Life, 1989),以迄最近出版的《理性之性質》(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1993),除了第二本書對《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的論題,做了若干討論之外,主要論題皆不在政治哲學,而是一般性的哲學論題,特別是知識論方面。在當代對知識證成理論的探究中,諾齊克是外在理論(externalism)具代表性的重要哲學家之一。
從一般的社會道德觀點,諾齊克此書中的論點,也許很多人未必贊同。不過,除非我們反對市場經濟,否則我們勢必要面對市場經濟的基底——私有財產制此一基本事實,而這正是諾齊克本書論證的中心。誠如吳爾夫(J. Wolff)所指出:「諾齊克不像羅爾斯,他在學院的政治哲學家中追隨者極少。然而,就實際政治角度而言,在大約最近的十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一種離開羅爾斯所捍衛之左翼的福利主義(left-wing welfarism)之趨勢。就此而言,諾齊克似乎更貼近當前這個時代的政治精神。」放眼當前,市場經濟正在世界各個角落展現空前的、無比的活力。顯然,我們不必盡然同意諾齊克的論點,卻無法忽視諾齊克此書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