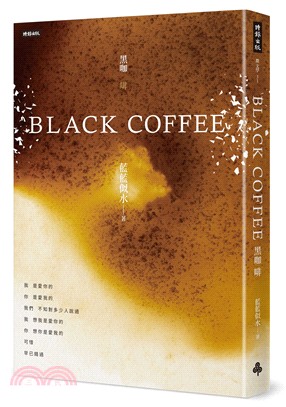Black Coffee黑咖啡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小城,那裡有成長的記憶,有傷痛與歡樂,有大片的慘白、血腥、暴力與深不可測的黑洞,作者敘事風格強烈,採用多線交錯,時而吶喊又時而呢喃,主人翁不斷在過去與現在、夢境與現實間;追尋愛而不可得的故事。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以陸晗冬的視角切入,圍繞在田鼠、甜瓜、瑪奇朵與賤人之間的愛恨糾結,一部集迷幻與黯黑、創傷與療癒、追尋友情與愛情而迷惘的一群熱血青年男女。
我是愛你的
你是愛我的
我們不知對多少人說過
我想我是愛你的
你想你是愛我的
可惜
早已錯過
「愛是什麼?」我問。
「愛是晗冬!」瑪奇朵說。
「是的,愛是寒冬!」我說。
作者簡介
藍藍似水,本名陳雪(Yolanda Chen),出生於中國,現居住在斐濟。
自二○○六年從事寫作至今,現為自由撰稿人和專業攀登者。
二○○六年因緣在《我的大學》徵文比賽中獲獎,而被選進金庸先生
提名的《風采》雜誌,從事編輯及記者工作,創作發表多以散文為主。
二○一四年簽約《春風文藝出版社》,並於二○一五年出版發行
長篇小說《槐楠一夢》。
名人/編輯推薦
瑪奇朵形單影隻 地坐在散臺一角,一頭蓬鬆凌亂的短髮像是被霜雪染過的枯草,銀灰色劉海和深棕色的睫毛互相交垂。他從不飲酒,卻貪戀在做工精細的高腳酒杯中裝滿黑咖啡,且用迷離的眼神專注地看著它,像是在禱告一樣,再無預兆的一飲而下。「陸晗冬,我打賭妳從未見過她無比忠誠的眼神,不僅滿是柔情而且曠古無二……」瑪奇朵陶醉著對我說。
我驚恐萬狀,他看上去卻神采奕然,我猜他定是遇見了心儀的女孩。然而,隨著他在飲盡幾杯後開始「酒」入舌出,我才得知他所指的「她」,只是一條媚態百出的母犬,咖啡因蠱惑他並製造了一連串假象,令我哭笑不得。
瑪奇朵常說:「在飲酒的地方,鮮少有人會跟一個完全不沾酒精的人攀談。這樣的環境裡,即使再閃耀的霓虹燈,也會讓過於清醒的人失去很多曖昧的機會,咖啡和酒精一樣,都會讓人上癮,繼而產生一連串的幻覺。」
我雖半信半疑,卻亦時常如此,偶爾只是看著咖啡豆都會沉醉,而後悒鬱寡歡。伴隨著咖啡機的轟轟聲,我彷彿能聽見咖啡豆被研磨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呐喊,繼而會看見已經多年未見的田鼠。
我曾極其認真的問瑪奇朵:「不做醫生後開咖啡館,是否是因為我?」
瑪奇朵雖沒有正面回答,卻也毫不吝嗇的告訴我:「陸晗冬,太過認真會失去很多做人的樂趣。」
當然,咖啡館也是我生活中樂不思蜀的一部分,卻從不覺得這是瑪奇朵所言的幻覺。幾天後,我在瑪奇朵的咖啡館裡彷彿再次看見田鼠,他獨自坐在一張轉角處的圓桌旁,連續喝下了十杯義式濃縮,在田鼠飲盡後不久,我就見他四肢無力,接著嘔吐不止,然後用手捂住胸口,感覺心跳劇烈又昏昏沉沉,表情看似飄飄欲仙……
我正要走向田鼠,就即刻被瑪奇朵攔住,並聽見他暴跳如雷地對咖啡師呵斥:「你不僅讓陸晗冬靠近咖啡機,而且還讓她喝了十杯黑咖啡……」當時,我已經頭暈目眩,不僅不知道瑪奇朵在說什麼,而且也未見咖啡師作任何辯解。
次日,我居然也離奇地中了咖啡的劇毒,再也喝不得。哪怕只是輕微的抿一口在嘴邊,都會產生像田鼠一樣的生理反應,劇烈的心慌,讓我從此有半年的時間沒有再碰黑咖啡,也沒有再踏進咖啡館一步。「毒癮」發作時,我會用酒精取代它,可是酒精的效果不佳,不僅難以上癮,而且即使爛醉如泥,都再也沒見到過田鼠。
直至我頓覺曾經的習慣讓自己空虛難耐,便開始嘗試著克制自己的身體,每次只喝十毫升的黑咖啡,同時飲盡一千毫升的清水。漸漸地,變成二十毫升黑咖啡加兌八百毫升清水,依此類推。直到有一天我在連續飲盡兩杯黑咖啡後,又再次奇蹟般地看到久違的田鼠,才立刻意識到:與其說自己習慣了黑咖啡,還不如說是自己習慣了田鼠。
在咖啡因的蠱惑下,只見田鼠同上次在瑪奇朵的咖啡館時一樣,也是獨自坐在轉角圓桌的一角,奇怪地是他身旁居然沒有一個女孩。田鼠目不轉睛地望著手中的高腳杯,不知是在孤芳自賞還是自我陶醉,只是看見他,就足以讓我的精神得到滿足。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養成了喝黑咖啡的習慣,只知道光陰在年復一年地流逝中,黑咖啡每天都是我的必需品,它如同田鼠一般陪伴著我度過了很多快樂的和憂傷的時光,也見證了我從「多愁善感」到「鐵石心腸」的心靈蛻變。
瑪奇朵把他的咖啡館轉賣後,為我帶回兩條品種迥異的犬,並給牠們分別取名為:「BLACK」和「COFFEE」。一個星期後,瑪奇朵甚至還幫牠們訂製了兩個價格不菲的鍍銀狗牌,正面是牠們的名字,反面是防走失的電話號碼,並留言:甜蜜的愛。我知道這意味著,如果牠們不慎走失,我將永遠也不能更換電話號碼。
我時常感悟:如果人類對情感的忠誠度能有牠們的一半,那該有多好!可是,瑪奇朵總會殘酷地提醒我:再濃郁的情感,它也可能隨時消失,沒有預兆的消失在生命的盡頭或冰封在記憶的深處。BLACK和COFFEE大概永遠也不會知道人類情感的複雜程度,也不會理解對我而言,只有當牠們在一起時才彰顯得格外重要。待牠們日漸長大,我才意識到瑪奇朵所言並非冷酷無情,而是對之心服首肯。
幾年後,瑪奇朵決定離開黃城離開我。我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他一定會重返醫生的職位,做他真正喜歡並將持之以恆的事。最後只剩下那兩塊沉甸甸鍍銀的狗牌和那串永遠也打不通的電話號碼。
我很不屑地看著瑪奇朵對我說:「陸晗冬,總有一天我們再也不想看見彼此的模樣,彷彿我們的臉頰上都布滿了汙垢,盡是銅臭不堪地骯髒,我希望妳永遠不要醒來,此生盡是美夢!」
「你說得沒錯,田鼠就是我的美夢!」我氣勢洶洶的對瑪奇朵說,那一刻我深信這是我與瑪奇朵此生最後的對白。
曾經,我們各自誓死捍衛著一段情感,以為那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純粹的東西。
我們雖各持己見,卻對「世界上有兩種人」的說詞深信不疑。只是,對於這兩種人的定義,我們始終都存在分歧。
田鼠認為的那兩種人是:男人和女人。
瑪奇朵認為的那兩種人是: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
對我而言,我很忐忑。
唯物的說,是活人和死人。
唯心的說,只有我和你們。
不知何時,我們又在形同陌路中醒悟:無論世界上有多少種人,我們都是其中臭味相投的同一種。而在此之前,我們都曾單純地喜歡過,純樸地愛過,所有的放蕩不羈似乎都在詮釋著田鼠對我說的那句﹁妳的樣子﹂的真正涵義。
你是愛我的,從來沒有變過。
在思念的長河裡,我反覆地對自己說。眼角閃爍的淚花彷彿比南極的冰川水還要清澈。
我是愛你的,從來沒有變過。
在繫念的思緒裡,我重複著對自己說。嘴角流淌的唾液貌似比漠河的初雪還要純潔。
你是愛我的,可惜從未親耳聽過。
我是愛你的,恰好時常在叨念著。
你是愛我的,我是愛你的,殊不知我們彼此曾對多少人說過……
曾經我在沒有黑咖啡的日子裡,時常朗誦田鼠的詩歌,可卻沒能持續多久,我又開始反覆無常地觸碰它,瑪奇朵卻再也沒有念叨我,他對我善變的行為已經習以為常。在黑白顛倒的那些時日,我總會在思潮湧動時喝一口黑咖啡,而後會看見田鼠不由自主地旋轉著我手中的圓珠筆,心亂如麻地翻看著我寫在本子上唯一的一篇日記,一遍接著一遍,並忘情地捂住胸口,自言自語且頗有文采地說:「陸晗冬,我再也不想看見妳,有一種苦不堪言的感覺,猶如心臟即將驟停一樣。」
「這也正是我想對你說的。」我說。而後,我和田鼠都心照不宣地對望著。
那些時日,我不解自己為何總能輕而易舉地看見田鼠,瑪奇朵也早已司空見慣了我這般模樣。可是,無論我飲盡多少杯黑咖啡,我們之間的情景和對話都只能定格在這裡,再無後續或下文。
「今天很好,田鼠只來了一次。」那天,在與田鼠對望之時,耳邊忽然傳來瑪奇朵的聲音。
「是嗎?那他有帶禮物給我嗎?」我的思緒即刻被拉回,目光呆滯地看著瑪奇朵問。
「當然,他帶給妳一本《小花兒的日記》。」瑪奇朵無奈地說。
接著,我接過瑪奇朵遞給我兩粒彩色的藥丸,繼而條件反射般張開僵硬的嘴巴,並用上下牙齒努力地摩擦,伴隨著咖啡機的轟隆聲,我把藥丸磨得粉碎,就像咖啡豆被咖啡機研磨時一樣,然後艱難地嚥下。瑪奇朵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本破舊得只有兩頁紙的記事本,頁腳早已被手指上殘留的菸灰磨成了黑色,他面色枯槁且氣若游絲,大概早已讀膩了……
小花兒的日記
髫年時期,我體會到了人生最奇妙的一種感覺。那是一個懵懂的年紀,又恰逢趕在一個朔風凜冽的時節。
在殘缺不全的記憶裡,那年的寒冬臘月,銀裝素裹,春寒料峭如故。我蜷縮在床頭最溫熱的角落,透過結霜的玻璃隱約看見窗外潔白的雪花肆意飛落,黑色的土地早已被冰雪覆蓋上蒼茫的白色。
一臺黑色落滿灰塵的老式收音機裡,偶爾發出卡帶的「吱吱」聲,我裹著被單,有點五音不全,又有點顫顫巍巍地跟著收音機裡的音樂哼唱著同一句小曲。
單薄的母親隻身在廚房忙碌著,後窗被灶臺上的熱鍋熏上了濃厚的哈氣,我正踮起腳尖,手忙腳亂地擦拭著。
透過模糊的櫥窗,眼前的一幕讓我大驚失色。一株高一公尺多,根莖直立的向陽花,色彩鮮明地映入我的眼簾。
它表皮略呈青綠色,花瓣金光燦燦,中心地帶的黑色如墨般鬼魅而深邃,碩大的「頭顱」圓潤又不失可愛。
在這寒風刺骨的冬日,它昂首挺胸地佇立在草木枯榮的悲傷大地上,且執著又堅韌地看著同一個方向,彷彿早已望眼欲穿。雖看不見陽光,卻仍舊持之以恆地面向太陽,有點荒謬,又有點瘋狂。
那一刻,我一見鍾情地愛上了它,即便筆下生花,也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每日清晨,我都會在天剛濛濛亮時起床,喝上一口熱呼呼的米糊,嘴裡叼著半個饃饃,踩在高度跟我齊腰的椅子上,趴在櫥窗眼巴巴地看著它。
直到它在不知不覺中日漸枯萎,金黃的花瓣也不再閃閃發光,沉默著低下高貴的腦袋,迷茫且沒有了方向。
它不曾伴我逐日長大,我卻逐漸開始懂它。在其清高的外表下,卻有著一塵不染的品行。在其孤芳自賞的同時,又能在沉默中堅強。
……
瑪奇朵離開多年後,我的記憶力大不如往常。但卻總能清楚地記得曾經的它,可我卻怎麼也記不得瑪奇朵為我朗誦《小花兒的日記》時的樣子,也記不得妄想症和憂鬱症曾經困擾了我多久,即便已經看似痊癒,偶爾仍會在藥物延緩的後遺症下,產生一連串的幻影和幻覺。
我不確定田鼠是否真的來過,但卻記得曾經瑪奇朵持之以恆地告訴我,在我所有的意念中,唯有那句「靠近我……﹂是真實存在的。
時隔數十年有餘,在黃金海岸的華納主題公園,戴著剛買的炫酷耳機,裡面循環地播放著同一曲華人音樂。然後,從垂直九十度的雲霄飛車上一躍而下,撕裂了喉嚨,瘋狂地尖叫。彷彿已擺脫了地球引力,在以第一宇宙的速度衝進雲霄,隨時準備離開這血雨腥風的地球。
我雖懼高,卻偏愛這種自由落體似的極限運動,每每回想心臟都會一陣陣地悸動。
總覺得,只有在失重的情況下,恐慌才會一點點地逼近,直至停在離心臟最近的地方。
那是藍與白的天界,猶如身在一望無垠的荒野裡,頭暈目眩的錯覺感像是被如火的純真年代焚燒掉了記憶一樣。
「砰!砰!你聽到了嗎?是斷裂的心隨著記憶在跳。」我對著身旁一個還坐在雲霄飛車上被嚇到魂飛魄散的西班牙人說。
或是在雲霄飛車上被勁風吹的有些耳鳴,他一個勁地問我:「What? Come to me. 」
我觸目驚心地看著他,一遍一遍地跟著他的口形重複著:「Come to me, Come tome... 」沒錯,他的確這麼說。
俯仰之間,想起昔日與友人的一段對話,懵然之際,一切卻已滄海桑田。回憶中整個世界都安靜了……
「站得那麼遠,妳是怕了嗎?」他倚在窗邊,橫眉冷對地看著我。
「夠近了嗎?」我膽怯地挪著小碎步走到他對面。
「再近一點。」他以咄咄逼人的姿態驅使我。
「不能再近了。」我哆哆嗦嗦地回答。言語間,我的鼻尖已挨近他的鼻尖。
「靠近我,讓妳如此心慌不安嗎?」他蹙眉以對地質問我。
「怎麼會?我從不知道心慌是什麼感覺。」我堅毅地看著他,毋庸置疑的回答。
可惜,待我對此能所有體會之時,已是明日黃花。對我而言:靠近恐慌,就意味著靠近心田。我們深知韶華易逝,本應過眼雲煙,卻總是因其在不斷的自我救贖中,間接傳遞給彼此的罪惡感而沒齒難忘。直到被風花雪月磨滅得沒有意念時,才不得不相信,再動人的曲調也總會有曲終人散的一天。
它們的出現,令我在成長的過程中,除了自己的容顏,沒有其他是刻意在意過的,也沒有什麼是感覺上不一樣的。只是,在後知後覺中,對我們而言,我們都失去了一些比自身的得失還珍貴的東西。
譬如,曾經頭頂一片藍天時,有一種季節叫雲淡風輕,有一種無形的呼喚叫小城的雲,有一種美夢叫做隨遇而安。
曾經的我們,總想用畢生的時間去追尋一樣,只是憑空幻想就足以讓我們呆滯許久的東西。我們說不出,也難以形容,就是固執地認為,一旦追到了,人生的意義就不一樣了。在賤人傳統的觀念裡,他說那定是一張「不老的臉」,田鼠卻有著相對時髦的見解,還為之拽了句成語,叫「歲月無痕」。現實卻是,人未老心先衰。
從而,我總會在夢裡看見自己未老先衰的樣子,手捧幾顆像咖啡豆似的向陽花種子或是依偎在向陽花湖畔,回想以前在窮酸潦倒的日子裡,最富貴得志的相見,似乎靠近了向陽花,就靠近了心底的愛戀。可惜,那不單單只是一場看似已終結了遇見。
「Come to me... 」
永遠不見!
「Come to me... 」
無顏再見!
你是愛我的
我是愛你的
或許,是「你們」耗盡一生的時間,都不會用言語表達的。也許,是「我們」用盡一世精力,都無從思索的。待到時過境遷,它把我們塑造成一個曲高和寡之人後才恍然大悟:有一種情感如向陽花,恰似沉默的愛。
然而,愛如黑咖啡。我雖不懂它,卻也知道砂糖只會令它千瘡百孔,鮮奶只會讓它錦上添花。如果想念一個人不知如何表達,不如找一個靜謐無人的角落,喝上一口不加修飾的黑咖啡。
十六歲以前,一直以為我們與生俱來就沒有童年,因為上天給予了我們一張永遠童真的臉。十六歲以後,從不照鏡子,自以為掩耳盜鈴是女人對自己最善意的謊言。
殊不知那副褶皺的容貌猶如句點,依舊讓一張不老的臉在日積月累中沉陷。
世界上最殘忍的事情莫過於我問:「你喜歡我什麼?」
你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妳的樣子。」
僅此……
目次
Black Coffee 黑咖啡
01:最後
02:最好的安排
03:紅房子
04:寺廟和賤人
05:那些女孩
06:墳墓
07:像她一樣
08:如此
09:死亡定義
10:我們的甜瓜
11:上癮
12:這裡和那裡
13:粉絲
14:旅程
15:栽贓者
16:走出塔帕山
17:守夜
18:巴林的愛情
19:焦糖瑪奇朵
20:一個人的冬天
21:黑暗恐懼
22:禮物
23:傷情的背影
24:花秀
25:插秧
26:再見爆米花女孩
27:你的樣子
28:愛是寒冬
書摘/試閱
01 最後
即便苟活一世,也堅信總會有那麼一個地方讓人魂牽夢縈,也總會有那麼幾個人會讓人低徊不已……
「若都沒有,我相信那定是離死不遠了。」田鼠經常這樣對我說。
我和田鼠始終心繫那座小城,即使它已面目全非,如今在似曾相識的輪廓裡,也只能在狹小的記憶空間中,搜索到它那殘留下最純樸的模樣。可是,年復一年地過去,仍舊是甜瓜樸實又固執的思想,以及賤人封閉又質樸的欲望,而一直不變的是田鼠難以捉摸的思緒和我在無望中愈發冷漠的臉龐。
「就是它,沒錯。」一股堅毅地聲音時常穿透我脆弱的耳膜。
然而對它,「他們」都鄙夷不屑,「我」卻心碎的緬懷。儘管它總是讓我們卓絕於它已融入骨髓中的劣根性,但是在欲罷不能中,它的存在,使我們在精神上,依稀地感受到自己仍然是活著。
那天,我和田鼠佇立在牆外,猶如深壁固壘,我們無語凝望,直勾勾地看著那慘白的牆體,乳膠漆已黴變,還有些脫落和龜裂,這是我們離死亡「最近﹂的一次。
「我希望我的亡魂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如果不能,那就盡可能地改變那座小城吧?若還是不行,總可以改變你吧?」這是賤人此生對田鼠說的最後一段話。
而在這之前,賤人也對我說了一句,之後令我精神紊亂,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他被員警帶走。不久後,我和田鼠都出現了相同的幻覺。
「他走的是一條不歸路。是槍聲?他死了!」
田鼠用力地捂住耳朵,不僅神情僵硬,甚至驚嚇到四肢痙攣。
「是血,濺到了臉上,還是熱的!」我一遍又一遍的擦拭著臉頰上的汗液。
在無法接受的事實面前,我們都扭曲到有些人格分裂了。待田鼠清醒過後,他一直在我身旁追問:「陸晗冬,尉遲艦最後對妳說了什麼?」
「最後?」我問。
接著,我麻木地拉著田鼠的手,感覺冷冰冰,而心臟更像是冬日裡結霜的玻璃窗一樣,在準備爆裂時,有著一觸即發的偏激,同樣在被外界的聲音震撼時,又有著頑固不化的倔強。
繼而,我昏厥了。感覺自己正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張熟悉又陌生的泡沫床上,不知身在何處,像是在鐵皮車廂裡,依稀聽見了田鼠的聲音。仔細辨認後,我真切的聽到了,那聲音沒錯,他就是田鼠。
他在抽噎地對我說:「那些年,若我們都還能活在純愛裡,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也許,我們都還是四維世界、三維空間裡,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我很努力地想睜開眼睛,但就是睜不開也醒不來。彷彿眼皮被膠水死死的黏住了一樣,雙眼很沉很痛,眼淚一直順著眼角淌下,它滴在皮膚上,被灼熱後感覺滾燙,有一種被沸騰的開水燙傷的感覺。
聽到聲音卻做不出相應的肢體反應,這種感覺就像是田鼠曾在他的噩夢中驚醒,跟我描述他的夢境時一樣。
接著,我做了一個冗長的夢,夢裡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賤人的「亡靈」,它把我引到從前,那似近又遠的地方,有意讓我再重新回憶一遍,然後就徹底忘記,繼而在餘生中,抓住眾人都在信奉的美好。
不同於他們的是,因為田鼠的存在,我始終都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也因為世界是美好的,所以田鼠存在的本身就是美好。我們都有這種糾結的情愫,以至於內心從未安寧過,但這並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也將是無法抉擇的。
在昏昏欲睡的夢裡,我看到了田鼠曾跟我提及過無數次他最討厭的那座大山,我昂首挺胸地看著它,就像曾經被百鬼眾魅附體一般去仰慕田鼠一樣地看著它,光線射進眼睛裡,不禁頭暈目眩,實在難以琢磨,它究竟是真像還是幻影。
田鼠並不知道我也討厭它,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山丘也會讓我厭煩。但是我知道,只要那座山一直在那裡,它便會一直聳立在田鼠的心裡,他憎惡它就像憎恨昔日四面環山的小城一樣。那種無法自拔的情愫,總會難以自抑地在田鼠的夢中念起,似乎所有的錯都是因為那座閉塞的大山,才會有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去。
久而久之,隨著田鼠跟我念起的次數不斷增多,他的夢也就不知不覺地成了我的夢。初次,我夢中的田鼠只有三歲,他躲在山腳下的石洞裡,用手中的向陽花刻意遮住他巴掌大的臉頰,偷偷地看著他外公為爭奪山頭的一座沙丘而同其他人大打出手。因為田鼠的父親老田曾無數次揚言:「要讓每一個踩過沙丘的人都死無葬身之處。﹂所以,這座沙丘等同打鬥場,田鼠每次都像寄居蟹一般躲在石洞裡,不僅猥瑣而且侷促不安。
田鼠親眼目睹他的外公被亂棒打死在那座群山圍繞的沙丘上,為了祭奠他,老田把他視作英雄,並把他的屍體裸放在沙丘,田鼠每日都要去跪拜,直到他外公的屍體完全腐爛才被掩埋。
幾年後,我告別了上段夢境,隨之而來的是夢見田鼠一直在沙丘前跪拜,他是跪得最久的一個,也是距離腐臭的裸屍最近的一個,且他始終低頭不語,目光呆滯地看著自己手中的那個他外公生前最愛吃的饅頭。偶爾,還會夢見老田逼迫田鼠聞著屍體腐爛的臭味把它吃掉,不能吐出且必須一口氣吃完,在吃的同時還要在心裡默念他外公生前常掛在嘴邊的箴言:「男人必須靠拳頭說話,拳頭愈是硬朗,愈是沒人敢欺負。」
那些觸目驚心的夢境,片段似的歷歷在目,以至於我每次看到饅頭都會嘔吐。然而田鼠卻偏偏喜歡在我面前有滋有味地啃饅頭,並指著我扁平的酥胸,不知廉恥地說:
「我只需要把饅頭想像成是女人的巨乳。」
我不認為田鼠的夢只是夢,也並不覺得我曾丟了魂一樣走進過他的夢,或是他曾使用巫術用託夢的方式扭轉了我的意念。我更不認為三歲的孩子會有足夠的記憶空間,即便有也不會持久。而田鼠卻記住了,深刻到骨髓,清晰又透明。
曾幾何時,我清晰地聽見田鼠對我說:「那座沙丘下,埋葬了我從未謀面的生母。從此,再沒人敢踏進那方淨土,也再沒有人敢靠近沙丘一步。」
那一刻,我不僅毛骨悚然,而且大夢初醒。對我而言,我意識到那方淨土是田鼠孤傲的靈魂,那片沙丘是田鼠傷痕累累的心窩。
奇怪的是,那日與賤人訣別後,直到我從中斷點的睡夢中醒來,部分記憶似乎真的被賤人的「亡魂」帶走了,我的確沒有再念起過,無論是打鬥還是死亡,一些被記憶腐蝕了的爛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我的腦海中變得愈來愈模糊。於是乎,這讓我和田鼠對過去的記憶不斷地產生分歧。那些時光,我們共同歷經了一切,而每一次用妥協來換取心靈深處的安樂,都會讓我們在爭辯中倍感羞辱。
可是,我們都已過天真的年紀,現實對我們來說,卻仍舊很難再快樂。我總會不自覺地想起,那天我從昏迷的狀態甦醒後,田鼠和我說的那段話:「我們悲傷,並不是因為曾經發生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都清楚的知道,在今後的人生中,我們將永遠地少了些什麼。」
那日過後的第二年,田鼠與其結識了兩年零七個月的女孩訂婚了,當時我不在場,正身在黃城一間烏龜養殖場,幫那些長命百歲的烏龜清洗龜殼。田鼠給我打了通電話,然後他的手機按了免提,故意放進了自己胸前的衣兜裡。在鐵軌的轟隆聲中,我還是清楚的聽到了,田鼠對他面前的女孩說:「今年,我已經四十二歲了,我第一次有一種衝動,我想為了妳而努力地做一個好人。」
我流淚了,為之動容的淚,我能想像到,那一刻田鼠的嘴角一定是上揚九十度,而且露出兩顆標誌性的大門牙,樂不思蜀地陶醉在從天而降的幸福裡。而這些僅是我沉浸在自己的夢境中憑空想像的,因為我早已不瞭解他,不瞭解他的程度應該跟他瞭解我的程度差不多。
作為田鼠特意指定的證婚人,我參加了他在黃城頂級飯店舉辦的奢華婚禮,為表莊重在千挑萬選後,用了半年的薪水買了一身藍色的禮服,卻因為提前準備的高跟鞋鞋跟斷裂而臨時配了一雙白色平底帆布鞋。走上臺做證婚詞時,雖然在家中練習了無數遍,還拿了份早就列印好的手稿照念,仍因為被眾人矚目而緊張得讀錯了好幾個關鍵字。
可惜,除了富麗堂皇四個字,我特別不願回想當時的場景,它果真成為我最後一場能預知到結果的夢。但是,我卻真切的記得,當時「夢中」的田鼠大言不慚地挑逗在場所有人時所說的話。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