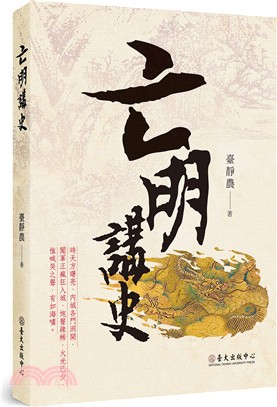亡明講史
商品資訊
ISBN13:9789863503996
替代書名:The Demise of the Ming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臺靜農
出版日:2020/06/01
裝訂/頁數:平裝/236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重量:345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臺靜農先生最後一部小說作品,
成稿八十載後,首次整理出版!
從滿清建立開始,「明末清初」就一直不斷在知識社群記憶中重述、改寫、翻修,不但是史家恆久的關心所在,同樣也提供了眾多文學藝術創作的源泉,更是各方政治勢力主張交鋒動員的話語系統,從民族革命、階級革命、乃至於帝國主義戰爭,不論是文化、宗教、性別種種場域,不論是對外或對內。「明末清初」此一時代話語仍然保持鮮活的能量,臺靜農《亡明講史》一書可以說是他對此一時代圖像的具象化,本書透露出略嫌哀傷無奈的情調,從某個角度來看,也不妨說是一部亂世憂患之書。(封面「亡明講史」四字,取自本書底本,為臺靜農先生親題)
在對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刻,臺靜農寫出一部滿清滅明的小說,自然是甘冒不韙。原因無他,此書太容易被視為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末世寓言。明亡殷鑒不遠,民國的命運又是如何?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這是臺靜農先生的小說作品中,篇幅最長、人物最多的一部作品,對認識臺靜農以及那個時代中具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精神心態,重要性不言可喻,其豐富的意涵尚有待各方持續不斷的深入探索。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簡介
臺靜農(1902-1990)
本名傳嚴,後改名靜農,長期寫作,精於書法。幼年時受傳統私塾教育,後閱讀嚴復的西學著作而萌發改革的思想。中學時與同學合辦《新淮潮》雜誌以響應五四運動。曾和魯迅同組未名社,倡新文學。離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便歷多校教授中國文學。1945年來臺任教於臺灣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達二十餘年,奠定了該系兼容並蓄自由活潑的開放學風。早年的治學重心在小說創作、研究評論、散文和整理編輯民歌集,又是著名的文學家和文學史家;他的一生幾乎橫跨二十世紀,目睹舊中國的變遷,西潮東漸,經歷了革命、五四學運、抗日戰爭,最後落腳於臺灣。然而不論時局如何變遷,臺先生堅守學術崗位,一生治學,文學、書畫、經史,卓然為一代大師。
目次
導論一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王德威
導論二 「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廖肇亨、鄭雅尹
亡明講史
凡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後記 寫在出版之前/廖肇亨
人名索引
書摘/試閱
導論一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摘錄)
王德威
「歷史有如夢魘,我掙扎從中醒來。」──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1937年夏天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臺靜農(1902-1990)和千百萬難民撤退到大後方。他落腳四川江津,先於國立編譯館擔任主編,隨後受聘執教白沙女子師範學院。戰爭帶給他重重考驗,包括痛失愛子。但一如他日後所言,這只是「喪亂」之始。也就在此時,他寫下《亡明講史》。
臺靜農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傳奇人物。因為家國喪亂,他的生命被切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臺靜農生於安徽,青年時期深受五四運動洗禮,關心國家,熱愛文學,並視之為革命啟蒙的利器。1925年他結識魯迅(1881-1936),隨後參與左翼活動,1930年北方左聯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因為左派關係,他飽受國民黨政府懷疑,1928至1934年間曾三次被捕入獄。抗戰時期臺靜農避難四川,巧遇五四先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1879-1942),成為忘年交。
抗戰勝利後,臺靜農並未能立即離開四川。1946年去留兩難之際,他覓得國立臺灣大學一份教職,原以為僅是跨海暫居,未料國共內戰爆發,讓他有家難歸。在臺灣,臺靜農度過了他的後半生,他鄉成為故鄉。
臺靜農在臺大中文系任教二十七年,其間任系主任長達二十年,廣受師生愛戴。除任教治學外,他以書法見知藝壇,尤其擅長倪元璐體,被張大千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臺的才情風範成為五四一輩來臺學者的典型,然而在彼時的政治氛圍下,他對早年的經驗諱莫如深──包括了戰時所寫作的《亡明講史》。
*
《亡明講史》顧名思義,講述明清易代之際,天崩地裂的一段史事。全書始於李自成(1605-1645)攻陷北京,長驅直入紫禁城自立大順王,百官四散,崇禎皇帝(1611-1644)走投無路,自縊景山。繼之福王在亂中建都南京,是為弘光朝。此時清軍已經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兀自內鬥不已。福王昏聵顢頇,耽溺酒色,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左良玉、劉澤清擁兵自重,史可法等少數忠臣良將一籌莫展。這是一齣完美的亡國大戲。果然,清兵不久長驅直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最後南京淪陷,福王竄逃,未幾被俘。南明弘光一朝從開始到結束,為時不過一年。
《亡明講史》完成於抗戰最膠著的時期,廖肇亨推斷為1940年前後;因為陳獨秀在當年秋天已經先睹為快,並致書臺靜農,鼓勵他「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為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實於歷史、小說兩無價值也」。陳獨秀是五四運動和左翼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共黨史早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之後被貼上托派標籤,驅逐出黨,並進了國民黨的監獄。臺靜農認識陳獨秀時,陳甫出獄,窮途潦倒。兩人很快在彼此身上找到默契:他們都曾經是革命理想的信徒,卻各自走上曲折道路。時不我與,他們流落在西南邊陲小城,幽幽相濡以沫。
在對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刻,臺靜農寫出一部滿清滅明的小說,自然是甘冒不韙。原因無他,此書太容易被視為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末世寓言。這段期間他曾先後寫出雜文,針砭時政,感傷民生。《亡明講史》更以「講史」形式,暗示歷史的永劫回歸:大敵當前,國民黨退居西南,紛紛擾擾,何曾全力投入抗戰?明亡殷鑒不遠,民國的命運又是如何?
臺的譏誚可能出於早年政治經驗,但更來自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心聲。不論如何,這是一部危機之作,也是一本危險之作。日後他攜帶此一書稿來到臺灣,在戒嚴的時代裡,當然心存顧忌。《亡明講史》被束之高閣,良有以也。
我們今天該如何評價這部遲到八十年的抗戰小說?抗戰期間流亡知識分子顛沛流離,每有興亡之嘆。南明作為隱喻,清代即有脈絡可尋,此時又成焦點。陳寅恪(1890-1969)北望中原,曾寫下:「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陳的亡明情結延續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別傳》(1958)為高潮。馮友蘭(1895-1990)則以較樂觀的眼光看待,稱之為「第四次南渡」。馮認為中國歷史的前三次南渡分別是第四世紀的晉室南渡、十三世紀的南宋偏安,與十七世紀的南明起義。這四次南渡都是因為異族──胡人、女真、滿人、日本人──侵略中國而發生,每一次侵略都將中華文明逼向一個存亡危機;政治正統、文化與知識命脈都備受考驗。馮友蘭宣稱抗戰引發的第四次南渡將以北歸作結;貞下啟元,剝極必返,中國必能復興。
相對於此,左翼文人如阿英(錢杏邨,1900-1977)在上海寫出南明系列戲劇《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張蒼水》。郭沫若(1892-1978)則於1944年──明亡三百週年(1644-1944)──寫出〈甲申三百年祭〉。郭以李自成農民起義的角度寫出革命的史前史,讚美闖王的反叛精神,遺憾其人剛愎自用,終不能成大業。他並推崇仕宦子弟出身的李岩,「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郭期待延安的共產黨記取甲申教訓,為革命開出新局。郭文引來國民黨強烈抨擊,日後卻成為革命書寫名篇。
臺靜農在甲申之前數年就寫出《亡明講史》,即使無意為風氣先,也的確流露出一種強烈的世變心態。國難當前,當權者卻依然貪腐無能,有識之士怎能不憂心忡忡?但臺靜農與郭沫若極有不同之處。對郭而言,歷史進程必須以革命來實踐,延安勢力不啻是民間起兵的進步表徵。他期望的歷史充滿破舊立新──尤其是建構國家民族──的力量。然而對臺靜農而言,歷史已經失去了這種承載過去、建構未來的目的性。他固然期待巨變,但對於巨變之下的不變──人性的卑劣、世事的無常、命運的「無物之陣」──卻有不能自已的憂懼。
這讓我們再思《亡明講史》敘事風格的特徵。改朝換代、國破家亡原來是再沉重不過的題材,臺靜農卻採用了輕浮滑稽的方式敘述。崇禎王室最後一刻紊亂暴虐、宗室朝臣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爾虞我詐,霎時大難臨頭,一切灰飛煙滅⋯⋯,他的敘事者彷彿立意將明朝滅亡寫成一齣鬧劇。當皇帝與外寇、亂臣與賊子都成了跳梁小丑時,起義也好、戰爭也好、甚至屠殺也好,都不過是充滿血腥的笑話。當歷史自身成為一個非理性的混沌時,史可法等少數典範也只能充當荒謬英雄罷了。
《亡明講史》讀來不像一般我們所熟悉的歷史小說。這也許是為何陳獨秀看過初稿後,有所保留的原因;他希望臺靜農將小說寫成歷史,但臺靜農卻視歷史猶如小說。陳獨秀低估了臺靜農的心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臺靜農何嘗不曾「吶喊」過、「徬徨」過?但到了抗戰前夕,新文學的範式顯然已無法表達他所感的時,或他所憂的國。在革命與啟蒙之外,他感受到更蒼莽的威脅鋪天蓋地而來。無論政治抱負上或個人情性上,他都面臨著此路不通的困境。《亡明講史》那樣陰暗卻又輕佻的口吻,已經清楚標示他的危機感。在這方面,臺靜農對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魯迅。
*
1922年底,臺靜農成為北大學生,不久即參與五四三大現代文學組織之一「明天社」的創立。1925年,臺靜農結識魯迅,迅速成為亦師亦友的知交。他們與幾位友人組織了「未名社」,譯介外國文學,特別是蘇維埃文學。與此同時,他也編輯了文學史上第一本魯迅作品批評論文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1930年秋,臺靜農和一群友人共同提倡創立「北方左聯」(次年年初成立),臺順理成章的擔任常任委員之一。1932年,魯迅因為臺的協助才能回到北京小住,發表了著名的「五場談話」,並參與兩場地下論壇,而未遭到當局刁難。臺靜農與魯迅的深厚情誼也可從兩人的書信往來,以及臺靜農關於魯迅的演講與寫作中一見端倪。1937年北平淪陷前一夜,臺靜農手鈔魯迅舊體詩三十九首,攜帶出奔。
五四之後,臺靜農開始小說創作,1928至1930年間,出版了《地之子》與《建塔者》兩本短篇小說集。《地之子》描繪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深陷苦難與惰性的循環,無法自拔;《建塔者》則彰顯了革命青年如何建立起高塔般的使命,捨身蹈火在所不惜。合而觀之,兩作指出當時小說寫作的兩種趨勢:鄉土寫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穿梭在「地」與「塔」之間,臺靜農為1920年代末中國小說添上最精彩的一筆。他精練的修辭、抑鬱的風格,乃至對寫作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思考,在在令我們想起魯迅。魯迅所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有臺靜農小說四篇,是為收入篇數最多的作家之一,魯迅對臺的欣賞,可見一斑。
樂蘅軍曾指出臺靜農早期小說展現「悲心」與「憤心」的張力。《地之子》直面人世苦難,企圖以無比的悲憫包容眾生。但在革命的時代裡,「悲心」很快就為「憤心」所取代。《建塔者》描寫革命青年如何飽受冷血迫害及自我抑鬱的折磨。這些故事結構零散,聲調若斷若續,彷彿要講述的真相總是難以說清;敘事者就像是個劫後餘生者,從死亡的淵藪帶回那一言難盡的訊息。
1930年代前後,臺靜農遭遇一系列政治打擊。先是1928年初,未名社因為出版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被北京當局強迫關閉。臺靜農和另外兩名譯者韋叢蕪與李霽野,遭到逮捕。臺靜農入獄五十天,案情一度「頗為嚴重」。1932年末,臺再次因持有革命宣傳資料與炸彈的嫌疑被捕。儘管最後無罪釋放,他卻因此失去輔仁大學教職。1934年7月臺靜農第三次入獄,罪名仍為共產黨關係。1935年出獄後,臺靜農在北京已無立足之地,只能在福建、山東等地尋覓教職。這些經驗日後他雖絕口不提,但無疑已成為憂鬱核心,滲入他的寫作甚至書法。
如果臺靜農早期作品證明了他的「悲心」或「憤心」,《亡明講史》則透露出他橫眉冷言、笑罵一切的犬儒姿態。臺靜農的「悲心」與「憤心」來自於他仍然視歷史為有意義的時間過程,有待我們做出情感與政治的取捨。他的犬儒姿態則暗示他看穿一切人性虛浮與愚昧,進而嘲弄任何改變現狀的可能。如此,他筆下的史觀就不賦予任何一個時代,不論過去還是未來,本質上的優越性。當下看來就像是過去的重複,反之亦然。
這一風格立刻讓我們聯想到魯迅的《故事新編》(1936)。晚年魯迅自謂以極盡「油滑」之筆重寫歷史或寓言;他刻意顛倒時代,張冠李戴,故事於是有了新編。在大師筆下,儒墨道德君子淒淒惶惶猶如喪家之犬,自命清高的老莊也難逃裝模作樣的嘲諷。縱是女媧的補天之舉也只落得一場徒勞的鬧劇。「油滑」的極致,不僅人間的秩序失去意義,天地的秩序也紛然瓦解。無物之陣的狂歡一旦啟動,不論什麼革命進步方案都注定被吞噬殆盡,就像〈鑄劍〉中人頭滾動的那口大鼎一樣。
臺靜農以類似角度看待晚明──或抗戰──天崩地解的現象,激烈性可想而知。他隨性出入古今,從晚明看見民國,從文明看見野蠻。他質疑歷史大敘事「詩學正義」的可能。我們閱讀史可法的孤軍奮鬥、或揚州十日的屠城死難,與其說感受到天地不仁的悲愴,不如說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虛浮。錢謙益等士大夫的惺惺作態,崇禎皇帝的殉國死難,或弘光皇帝的昏聵荒淫,不過殊途同歸,都為大明送終而已。臺靜農如此描寫崇禎的最後一刻:
宮中樹木新葉正發,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綠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時間過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陳現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見了,只有漆黑。
他筆下的揚州十日:
且看這偌大的揚州城,被清兵鬧得比地獄還慘,姦搶焚殺,無所不為,正如三百年後現在的日本兵的獸行一樣⋯⋯五天的光景,就屠殺了八十多萬人,婦女上弔的投水的被擄去的,以及餓死的駭死的還不在數,作者不用在這裏重述了,讀者自己去翻翻這篇血史罷,看看同我們的日本敵人現在放下的血債有什麼分別沒有?
在這層意義上,《亡明講史》流露的幽暗意識不再局限於政治、道德批判,而有了本體式的、橫掃一切的戾氣。
*
趙園論明末時代氛圍,總以王夫之所謂「戾氣」二字。她在時人論述裡不斷發現「乖戾」、「躁進」、「氣矜」、「噍殺」、「怨毒」等字眼,顯現一個激切紛亂,上下交征的時代如何動人心魄。始作俑者當然是皇朝無所不在的暴虐統治,尤以對待士大夫為甚。有關明代種種鉗制、杖殺、逮繫、監視、流放的「規訓與懲戒」已有極多研究,趙園則提醒我們,這樣的統治風格如何滲透至各個階層,形成見怪不怪的感覺結構。帝國表面踵事增華,恐怖與頹廢的暗流早已腐蝕民心,以致沆瀣一氣。
時至晚明,朝中閹黨與東林黨鬥爭你死我活,幾無寧日;上行下效,民間也形成尖峭寡恩的風俗。劉宗周因此感嘆:「乃者囂訟起於纍臣,格鬥出於婦女,官評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又何問國家擾攘!」更重要的,戾氣所及,穿透輿論清流,模糊了仁暴分野。鼎革之際,烈夫節婦或殉難、或抵抗者不知凡幾,固然展示誓死如歸的勇氣,換個角度看,卻也不無鋌而走險、甚至「施虐與自虐」的徵候群。
《亡明講史》寫盡了彌漫明清之際的戾氣。這戾氣吞噬袁崇煥、左光斗,也吞噬魏忠賢、李自成;吞噬史可法、高傑,也吞噬馬士英、阮大鋮。掩卷興嘆之餘,我們要問,作者臺靜農自己不也難以倖免?全國抗日的時刻,敵我忠奸的殺伐之氣甚囂塵上,而臺靜農似乎走得更遠,流露出玉石俱焚的憂鬱和詛咒。怨毒著書,史遷不免。但他必已感覺《亡明講史》這類作品可一而不可再。
如何化解這樣的戾氣成為臺靜農最大的考驗。我所關注的是,臺靜農撰寫《亡明講史》同時,已經開始舊體詩創作。他的幼學不乏舊詩訓練,轉向五四後擱置已久。新文學引領他寫出《地之子》、《建塔者》這類標榜現實主義人道精神的作品,然而曾幾何時,他逐漸理解新文學一樣不脫程式化的形式和窠臼,現實主義也每每沾染意識形態色彩,變得毫不現實。生命的困蹇無明讓他體會啟蒙與革命的局限。眼前無路想回頭,臺靜農有意識的透過古典詩歌另闢蹊徑,探尋一個可以疏解鬱憤與憂患的管道。
離開晚明,臺靜農發現了六朝,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大裂變的時代。他從阮籍、嵇康等人的吟詠中找到共鳴。臺靜農此時的舊體詩均收入《白沙草》,其中最動人的作品無不和歷史感喟有關。以〈夜起〉為例:
大圜如夢自沉沉,冥漠難摧夜起心。
起向荒原唱山鬼,驟驚一鳥出寒林。
首聯呈現一個天地玄黃、淒清有如夢魅的情境。次聯寫夜不成眠的詩人起身朗讀〈九歌.山鬼〉,彷彿與兩千年前《楚辭》的迴聲相互應和。詩人的悲聲劃破了夜晚的寧靜,寒林中一隻孤鳥受了驚擾,突然撲簌飛出。而我們記得阮籍《詠懷詩》裡就充滿了孤鳥的意象。
或有人認為臺靜農因此背離了他早期的信念。但我認為舊體詩其實將他從啟蒙萬能、革命至上的決定論中解放出來,也為《亡明講史》那樣的虛無感提出超越之道。舊體詩引領他進入一個更寬廣的記憶閎域中。在那裡,朝代更迭、生死由之,見證著千百年來個人和群體的艱難抉擇。舊體詩的繁複指涉構成一個巨大、多重的時間網絡,不僅瓦解了現代時間單線性軌跡,也促使臺靜農重新思考「講史」的多重面向。面對古今多少的憧憬和虛惘,他豈能無動於衷?換言之,臺靜農是以回歸傳統作為批判、理解現實的方法;他的懷舊姿態與其說是故步自封,不如說形成一種處理中國現代性的迂迴嘗試。
不僅如此,正是寫作《亡明講史》期間,臺靜農開始寄情書法,竟欲罷不能。他在書法方面的創造力要到定居臺灣後才真正迸發,並在晚年達到巔峰。從文學到書法,臺靜農展現了一種獨特的「書寫」政治與美學。他早年追索人生表層下的真相,務求呈現文字的「深度」;饒有意味的是,他晚年則寄情筆墨線條,彷彿更專注於文字的「表面」功夫。
值得注意的是,臺靜農重新開始書藝時,先以王鐸(1593-1652)為模範,後轉向倪元璐(1593-1644)。王鐸風格酣暢奔放,相形之下,倪元璐則字距緊俏,筆鋒欹側凌厲,彷彿急欲脫離常規結構,收筆之際卻又峰迴路轉,彷彿力挽奔放的墨色。倪元璐與王鐸同為東林黨人。東林黨在崇禎時期捲土重來,政治影響力自然有助於倪、王等的書藝地位。但兩人不同之處在於:明亡王鐸降清,倪元璐則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自縊殉國。
臺靜農初遇倪元璐書法時,《亡明講史》完稿不久,倪殉國一事也為小說所描繪。我們不難想像,在滿紙昏君亂臣賊子的荒唐行徑後,臺靜農必然對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書法的創造力有很大的層面來自臨摹參照,促使書寫者進入意圖和中介的辯證層次:就是生命與意象、人格與字體相互指涉的呈現。《亡明講史》對中國文明、政治未來充滿猶疑,而倪元璐的書法則確認了忠烈意識的久而彌堅。
在這樣的脈絡裡,我們見證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對話與轉折。悲心與憤心,戾氣與深情,臺靜農的後半生不斷從書法與寫作中嘗試折衝之道,死而後已。《亡明講史》正位於他生命轉折點上。這本小說未必是臺靜農文學創作的最佳表現,但內蘊的張力關乎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那是怎樣糾結鬱悶的徵兆?大勢既不可為,唯餘小說一遣有涯之生。然而即使是遊戲文章也只能成為「抽屜裡的文學」。
故事新編,亡明「講史」講不出改朝換代的宏大敘事,只透露「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歎息。的確,抗戰流亡只是又一次「喪亂」的開始。幾年之後臺靜農將跨海赴臺,而且在一個他未必認同的政權治下,終老於斯。
《亡明講史》成稿八十年後,我們閱讀此書又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感觸?海峽彼岸大國崛起,文網鋪天蓋地,對知識分子的壓制變本加厲。海峽此岸急欲擺脫南朝宿命,重新「講史」──南明不過是東亞史的一頁,有何相干?當此之際,臺灣小說家駱以軍寫出《明朝》(2019)──「明朝」既是明日黃花的過去,也是明天以後的未來。撥開華麗的表面文章,一個充滿戾氣的時代撲面而來。喧囂與狂躁凌駕一切,虛擬與矯情成為生活常態。
歷史不會重來,一切卻又似曾相識。亡明作為隱喻,有如奇特的接力暗號。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戰鼓聲中,在「芒果乾」的勝利大逃亡中,亡明的幽靈何曾遠去?歷史有如夢魘,我們仍然掙扎著從中醒來。
導論二 「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摘錄)
廖肇亨、鄭雅尹
壹、臺靜農與《亡明講史》
臺靜農(1902-1990),安徽霍邱人,原名傳嚴,後改名靜農,字伯簡。著名的書法家、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學者、教育家。1920年臺靜農先生是最初以魯迅弟子、鄉土小說家的身分在中國文化界登場。曾任教於輔仁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女子師範學院,1946年,應魏建功先生邀約渡海來臺,任教於臺灣大學,1949年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掌系務逾廿年。從臺灣大學退休以後,任教於輔仁大學、東吳大學。1990年逝世於臺北。教學之餘,晚年臺靜農以書藝名世,一代書道大家聲颺四海。
雖然臺靜農先生在廿世紀三十年代,鄉土文學作家聲譽卓著,但在臺灣,直到1990年前後,臺靜農早年的小說,如《地之子》、《建塔者》重新在臺出版,世人對其作為小說家的記憶方才又被喚醒,學者重新解讀箇中的意涵、特徵與技巧。近年以來,學者多方收羅臺靜農散佚的史料文獻,蔚為盛況。《亡明講史》一書由於從未正式出版,故往往不為人知,罕見徵引。但不論從內容或形式來看,對於認識臺靜農文學寫作的特質,《亡明講史》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亡明講史》原件現存臺灣大學特藏組。根據相關史料,《亡明講史》一書大抵1940年已經寫就,陳獨秀致臺靜農的書信中說:「《晚明講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國史》,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為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實於歷史及小說兩無價值也。」陳獨秀此信對於歷史小說頗致不滿,此先姑且不談。除此之外,尚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亡明講史》一書似乎一度亦曾作《晚明講史》。考《亡明講史》之名,目前現存的資料來看,六冊稿本封面作《亡明講史稿》,內文稿紙上作《明亡講史》。封面有可能是後加,如果不是筆誤,《晚明講史》、《亡明講史》、《明末亡國史》的名稱或許都曾在作者考量之列,因此,《亡明講史》此一書名當是作者細加推敲之後的結果。
二、此書正式出版前幾乎是唯一讀者的陳獨秀,其閱讀心得格外值得重視,陳獨秀最直接的感覺是此書描寫明政權滅亡的過程。「亡國史」之類的著作在帝國主義時期十分流行,如越南民族運動領導者潘佩珠《越南亡國史》一書頗受關注,而《亡明講史》原成於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臺靜農等具有良知的自由知識分子,無法如郭沫若左翼文人一般,直接將樂觀的期待投射到共產政權之上。希望與絕望同為虛幻,更多的心情是無奈。陳獨秀對介乎歷史與小說兩者之間的《亡明講史》一書評價似乎不高,或許也影響了作者出版的意願。當然,如此一來,一般讀者也就更難以一窺其內心究竟了。
《亡明講史》一書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已有正式清謄的稿件,可以說距離正式出版只有一步之遙。在臺灣大學圖書館「臺靜農先生手稿書畫展」的展覽時列有三種稿件,稱為《亡明講史稿》「初稿」、「定稿」、「他人代抄稿」,本文依據三種書稿首頁題名,稱《晚明講史》、《亡明講史稿》、《亡明講史》,三種書稿基本相同,但字句偶有出入。茲略說明如下:
(一)《晚明講史》六頁
縱25字,左10行,右10行。本稿字跡潦草,塗抹修改之處幾乎無頁無之。首頁題作「晚明講史」。但初稿基本殘缺不全,字跡不易辨識,只存開頭數頁,題識「晚明講史」四字。
(二)《亡明講史稿》六冊
用縱25字,左10行,右10行稿紙謄寫,共111頁(整理者標示正文103頁,未標示1頁,別紙7頁)。分六冊。前十頁為「星花社」稿紙。第二、三冊為「國立臺灣大學」稿紙,第四、五、六冊為「七七稿箋」。但二至六冊中,不時雜以「國立臺灣編譯館」或全白便條紙,謄寫於其上,以利辨識,此稿可以說是內部情況最為特殊複雜的狀態。每冊封面題做「明亡講史」,總冊封面有臺靜農先生親題「亡明講史稿」五字。此稿狀況特殊,特展時稱為「定稿本」,遂襲用至今。但「定稿」與「他人代抄稿」二者仍然小有出入,難以驟謂之「定稿」。題為「亡明講史稿」。
(三)《亡明講史》上下兩冊
孔雀牌稿紙,縱25字,左12行,右12行。此稿最為清楚可辨,出於一人之手。綜觀其稿,可以說距正式出版只有一步之遙。本次出版以此稿為底本,參酌《晚明講史》與《亡明講史稿》兩者,凡本書未特別註明版本時,即以此稿為準。本書定名「亡明講史」,亦以是稿為準。
以上名稱各異的三種稿本,現皆存於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原作者為臺靜農,只是由於謄寫抄錄者不同,筆跡亦明顯不同。三者之間內容偶有出入,但以《亡明講史》內容最為齊整,辨識度最高,幾乎可以說是小說家臺靜農篇幅最長的作品,對認識臺靜農及其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
貳、《亡明講史》的時代背景
《亡明講史》一書主要以明朝覆滅之際的時空環境為背景,前半寫北京。後半寫南京。全書情節的發展依序大概可以區分為:一、李自成入關之前,至崇禎帝自縊;二、李自成部眾在北京;三、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將李自成部眾逐出北京,以九王爺進入北京城作結;四、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朝政不綱,史可法出鎮揚州;五、南方將領內部矛盾,揚州城破,史可法殉國;六、南京降清,以豫王之宴為全書總結等部分。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折期,時人每以「天崩地解」視之。所謂「天崩地解」,其實就是價值觀的重組、翻轉,且除了政治以外,遍及經濟、宗教、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等不同領域。《亡明講史》一書寫就於抗日戰爭之際,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指涉殆無疑義,全書情節側重在描寫天崩地解之際時救亡圖存的徒勞無功,且聚焦在人事的紛爭與庸劣。
《亡明講史》全書結構十分勻整,幾近於前後對比。前半主要場景在北京,登場的人物群主要是兩次投降的士大夫,且其原本幾乎壟斷政治經濟的一切特權,吳三桂是作者花費較多筆墨描寫的武將,從結構上來說,扮演著「過門」的功能;後半主要場景在南京,武人之間的糾葛是主要的內容,領導階層則唯以排擠忠良、權力鬥爭為務。從小說上來看,文官愛錢,武將怕死(特別是掌握實際軍權的趙之龍),集體人格的墮落或許是知識階層通用的時代表徵。無力回天的史可法像是一個不斷向下的主旋律中一曲突兀振拔的高亢樂段,可以說是全書唯一的悲劇英雄。《亡明講史》一書中對秉國政者的節操氣骨多所嘲諷,顯而易見,作者將明朝國運的衰頹聯繫到當時士人集體人格心態的墮落,然而除了人的因素外,明清鼎革也某種程度反映出當時特殊的時空環境。同時,作者主觀意見不可免的帶入其中,例如武將能詩一事。
在《亡明講史》一書中,「詩人」往往帶有負面評價,特別是提到武將劉澤清,作者嘲諷其作詩一事。不過晚明以來,文人談兵,武將作詩蔚然成風,文武之間的畛域有更頻繁的交流與互動。戚繼光、俞大猷皆屬能詩武將,而洪承疇、袁崇煥則屬文人從軍,劉澤清不過沾其餘風,實非特例。一如文武之間界限的模糊,所謂流寇或者官軍,彼此之間也沒有涇渭分明的差別。明代兵制本來以衛所為主,萬曆以後,田賦、兵役等種種制度皆遭受嚴重破壞,流離失所的民眾往往只能棲身於各類部隊當中,時而歸順政府,時而反叛,不確定的狀態反而成為一種常態。《亡明講史》敘事只到南京投降,但南京投降之後,對抗清軍的部隊主要是過去的流寇,反而成為南明朝廷抗清的主力部隊,高傑所率的部眾即屬此類。
《亡明講史》全書以明思宗崇禎帝向大臣籌餉未果作為開篇,作者或許是在強調大臣的慳吝與貪財,不過這段描寫正好說明了明代後期以來值得注意的財政現象:一、朝廷財政的窘迫;二、金融流通不暢,財富集中於少數權貴之手。萬曆以來,明朝政府長年用兵,尤其是萬曆二十年前後討伐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一事,牽動日後東亞諸國的政局,當然也嚴重拖累朝廷的財政。為了因應日漸窘迫的財政,政府組織進行各種調適方案,但卻沒有良好的配合方案,以致於大幅助長朝廷的反對勢力,後果十分嚴重,實乃始料所未及。至於財富集中現象,廿世紀以來的經濟史家對此已有清楚的認識。當時全世界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海洋貿易多半以走私貿易的方式進行,國家無法積極有效管理海洋貿易的稅收,中國本身的金融流通管道十分有限,且缺乏合理管理的制度,致使財富集中於少數權貴之手,由於朝廷財政無法有效合理的分配,國家政局紊亂也與國家財政重分配有關。
也因此,明清政權交替與個人道德人格境界的墮落固然不無干係,不過從現代的觀點來看,整個大時代的背景與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才是明代政權覆滅更為根本的原因。對於晚明清初整個時代的認識,從清末開始,就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參與知識階層的話語形塑過程。撿取或遺忘,多少都可以看見刻意營構的痕跡。《亡明講史》畢竟還是一部文學作品,可以視作廿世紀前期知識社群當中相當具有普遍性的歷史觀點,帶有強烈的現實指涉,也有它自身的時節因緣。這是在閱讀《亡明講史》一書時應該特別注意的。
參、《亡明講史》及其引用文獻
就性質來說,《亡明講史》一書屬於歷史小說殆無疑義,但小說虛構的成分不多,從眾多史料中稽考、編輯、改寫的基礎之上,作者再適時加入部分屬於作者個人的議論或判斷,可以說是《亡明講史》一書最為明顯的敘事結構與方式。既然名之曰「講史」,作者或許相當程度自覺扮演類似話本說書人的角色,而且基本上對原始史料文獻十分尊重。
臺靜農的書法冠絕一時,初學王鐸,後學倪元璐,曾經對明末清初下過深切功夫原在意料之中。對晚明清初史料熟悉的讀者,對《亡明講史》一書當中的若干情節或有似曾相識之感。《亡明講史》一書引用的史料至少包括《明季稗史初編》之《續幸存錄》、《江南聞見錄》、《青燐屑》、《吳耿尚孔四王合傳》;《明季稗史續編》之《明季遺聞》、《明季實錄》,以及《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紀傳》等諸多文獻。
從各種引證的例子來看,《亡明講史》一書援引資料源出多方,或不當一視同仁。面對諸多史料,因應不同段落與情節的需要,《亡明講史》對於原始史料的處理方式約有以下數端:
一、引錄原文,不加改易。《亡明講史》約有28則獨立引文,有24則謄錄原收錄於《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或《南明野史》的各種原始史料文獻,其中如崇禎〈罪己詔〉、史可法〈請恢復疏〉等名篇,不畏文長大幅引錄,後者更達一千兩百餘字,是全書最長的獨立引文。在此先須說明的是:本書校對臺靜農先生引文,除使用當時常見的刻本,亦參考民初之後重見天日的藏本。如《明季南略》有清刻本與藏抄本二種系統,前者為刪節本,後者為足本,今通行之中華書局點校本以後者為底本。據臺靜農引史可法〈疏〉作「清」國而非「虜」字可知,他徵引自清刻本系統。由於《明季南略》此則文字稍有出入,本書僅此處校對出註列清刻本,並附上中華本位置,其餘出註列中華本。
二、引錄原文,略加改易。臺靜農先生在抄錄一段史料之後,常會化用相關史事,使敘事更為緊密。如闖軍攻破北京的告示云:「仰爾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旦入朝,先具角色手本,青衣小帽,額貼順字,前來報名,我大順皇帝應格外加恩,俾爾等王國順臣,得沐再生之德!」「青衣小帽」前面一段為《明季北略》原文,後面一段及小說之後的敘述,則化用方拱乾事。顧炎武《明季實錄》云:「少詹兼侍讀方拱乾坦菴,桐城人。為賊所執,以美婢四人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青衣小帽,額貼黃紙順字求荐。」「額貼順字」之後的情節,改寫自南明史料對失節明臣的種種記錄。
三、改動原文,加以裁斷。關於「崇禎太子」一案,臺靜農先生取《明季遺聞》云:「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此豈大臣之道」以下來自《南明野史》、《明季南略》等書。計六奇《明季南略》詳述太子案歷程,指出《明季遺聞》與其他諸書大異,強調《遺聞》非信史。臺先生所見南明史料當中,惟《遺聞》判定為假太子,但他取信《遺聞》所述,偏向認定為假太子。
四、在原文的基礎上改寫。如吳三桂降清的歷程,臺先生主要參考《明季北略》〈吳三桂請兵始末〉和《吳耿尚孔四王合傳》,但吳三桂與唐通之間的對話,應為臺先生添加之小說色彩。
傳統史書作者在敘事告一段落時, 往往以「太史公」、「異史氏」之類的身分介入其中,發表議論,這是一種帶有主觀色彩的全知觀點。《亡明講史》一書在敘事或引證史料後往往接上此等議論。例如在援引完史可法上弘光皇帝書之後,作者說道:
這樣的痛切陳詞,有什麼用?宏光皇帝不過令人批下「朕知道了」而已。後人都說可法這篇文章和諸葛亮的〈出師表〉一樣的好,是的,他還想學諸葛亮呢。
文中的「他」,乃指史可法。整體來說,作者在《亡明講史》一書中加入個人議論的成分有漸增的趨勢,全書整體筆調漸次從感傷亡國的悲涼逐漸強化成針對昏庸的激憤,後半引用文獻的次數也明顯增多,亦不難思過半矣。小說作者藉著援引文獻的機會登場,順勢帶入小說家個人的歷史判斷。例如弘光時曾經喧騰一時的崇禎太子,作者在引述左良玉、黃得功的疏文後說道:
要不是馬阮當朝,絕不會引起這樣的掀然大波。本來是□單純的案子,但是大家都集矢在馬阮的身上,真是弄得哭笑不成。這與其說是皇太子的真假問題,不如說是一場政治的鬥爭。
「崇禎太子」一案在弘光朝引起軒然大波,史家於此說法不一,作者於此似乎傾向於冒偽一方,更似乎也沒有十足的把握。但作者立刻將崇禎太子案定位成導致弘光土崩瓦解的政治鬥爭,一方面表示史家個人的歷史見解,另一方面,類似說書人的感慨嘆息也清晰可聞。
不過,《亡明講史》畢竟不是史料檔案, 沒有必要「忠於原著」。眾所周知,「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各種史料瑕瑜互見,彼此記事矛盾衝突之處更是俯拾即是。史料只是這部小說一部分的素材。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看,似乎更應該追問:作者運用史料的技巧是否成熟?在本部作品中,史料有否充分發揮小說藝術的作用?從作者對史料的取捨剪裁,能否看出作者的創作意圖與精神圖像?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