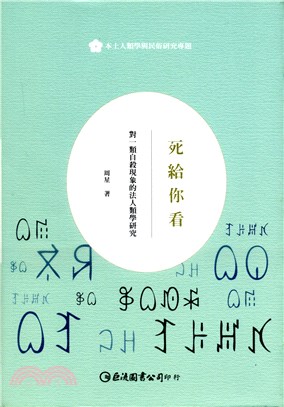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這是威脅,也是賭注。
誰會為了讓另一方付出代價,真的自我了斷?
又有誰會真的付出賠償,給死者一個交代?
遙遠的涼山彝族,有一套「死給」的傳統:將某些情況下的自殺,認定為一種「他殺」,細膩規定所有「死給你看」的人,到底性命值多少──死者可以得到哪些賠償?雙方家族又需要如何回應?無論是言語或肢體衝突、夫妻失和、離婚受阻、家庭失和、偷竊欠債、名譽恢復,通通能適用。例如:彝族女性有強烈的尊嚴,正所謂「人死是一天,羞恥是一世」,若在公共場合不慎放屁出聲,必須以「死給」替家族洗刷聲譽。
此外,因死者的身分,以及選擇赴死的方式不同(如:吊死、服毒、投岩、投水或使用刀具),償付的方式也會不同。
另一方面,一經「死給者」宣告,只要自殺成功,死者家屬就可以到「被死給者」家中打砸搶燒,提出指定賠償。一旦若處理不慎,就會演變為家族間衝突,甚至延續數代,兩家子女互不通婚,成為涼山版羅密歐與茱麗葉;更嚴重的,還會牽扯出「黑巫術」,從器械對戰擴展到「巫術戰爭」,冥陽兩界都不可安寧。
作者透過眾多案例分析,以人類學+民俗研究觀點,為您娓娓道來,這其中奧秘。也期待從尊重和珍惜生命的立場出發,能弱化導致「死給」現象頻繁發生的社會文化機制。
◆本書特色
一、案例豐富、用字淺白
本書作者結合人類學與民俗研究,書中記錄大量涼山本地案例,以及諸多彝族俗諺,透過淺白親近的文字,可讓讀者在理解「死給你看」背後的社會文化結構同時,一窺涼山的傳統風俗樣貌。
二、世代間的價值衝突,在臺灣也是不可迴避的課題
「死給你看」是千百年來彝族所共同遵循的文化傳統,但當接受現代社會受教育的彝族青年遭遇「死給」糾紛,會選擇哪一方呢?執法人員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文化衝突?而在臺灣,許多年輕世代往往不知該如何回應家族期待或主流價值。透過本書不同的民族案例,或許有助於我們辨識、理解與解決傳統文化與價值在現代發展中的矛盾。
作者簡介
日本神奈川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曾任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部教授、大學院博士課程指導教授、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ICCS)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顧問、中國民俗學會海外理事等。
主要著述有《史前史與考古學》(1992)、《民族學新論》(1992)、《民族政治學》(1993)、《境界與象征:橋和民俗》(1998)、《鄉土社會的邏輯──人類學視野中的民俗研究》(2011)、《本土常識的意味──人類學視野中的民俗研究》(2016)、《生熟有度──漢人社會及文化的一項結構主義人類學研究》(2019)、《道在屎溺──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2019)、《百年衣裝──中式服裝的譜系和漢服運動》(2019)等,並主編多種學術圖書。
序
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實踐
1994年6月,費孝通教授為《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通訊》題寫了刊名,該「通訊」由此前不久成立的「北京大學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主辦,我當時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任教,曾經和同事們一起參與了這個中心和這份小刊物的創辦。這份不定期的旨在溝通校內同行學者的學術資訊類刊物,對當時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於是,我們就不再局限於校內,而是把它不定期地郵寄給國內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同行。不經意間,二十多年過去了,世事與人事均有了許多變故,但對我來說,當年導師費孝通的題詞鼓勵一直不曾淡忘,它成為我沿著「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條學術道路持續走來的主要動力。如今人過還曆,確實是到了將多年來學術研究的一己實踐所形成的積累逐一推出,以便向學界同行師友彙報,同時也到了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所歸納的時候了。但值此推出「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系列」之際,我反倒深感不安,覺得還有必要將有關的思路、心路再做一點梳理。
初看起來,我是把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這兩個學術部門「並置」在一起,甚或是攪和在一起,試圖由此做出一點具有新意的探索,但這樣的冒險也可能弄巧成拙。或許在習慣於學科「圈地」中糾結於名正言順的一些同行師友看來,我的這些研究既不像是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可能也遠非人們通常印象中的民俗學。如果容許我自我辯解一下,我想說的是,反過來,它們會不會既有點像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又有點像是一種不同的民俗學呢?至少我是希望,這些研究或者是借重了文化人類學的視野、理念和方法的民俗學研究,由此,它不同於國內以民間文學為偏重的民俗學;但同時,它們或者也可以是一類經由民俗研究而得以實現自立的人類學研究,由此,它雖然沒有那麼高大上,沒有或少了一些洋腔洋調,倒也不失為較接地氣、實實在在、本土化了的人類學,多少是有那麼一點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意思。
文化人類學對於中國來說,原本是「舶來」的學問。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在大規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類學浸染的同時,相對於西方文化人類學而言,其在中國落地生根,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本土人類學。中國本土的文化人類學雖然在以英美法為主導的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中處於邊緣性的地位,但它卻無疑是為中國社會及公眾所迫切需要,這一點反映在它曾經的「家鄉人類學」取向上,而正是這個取向使得它和一直以來致力於本土文化研究的民俗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遭遇。在我看來,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在中國學術界的此種親密關係猶如宿命一般,重要的是,它們的遭遇及互動是相得益彰的,文化人類學因此在中國實現了本土化,民俗學則因此而可以實現朝向現代民俗學的轉型。
在沿著這條多少有些孤單、似乎也「裡外不是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的過程中,我有幸獲得楊堃、費孝通和鐘敬文等學界前輩導師的指教和鼓勵,這幾位大師或多或少都具有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的雙重乃至多重的身分,所以,我從他們的學問中逐漸地體會到了「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前景其實是大有可為的。與此同時,多年來,我也受惠於和我同輩甚或比我年輕的學界同行。比如說,我的朋友小熊誠教授對費孝通和柳田國男這兩位學術大師的方法論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就曾使我深受啟發,因為他的研究不僅使我意識到中國文化人類學作為「自省之學」的意義,還使我覺悟到比較民俗學作為和文化人類學相接近、相連接的路徑而具有的可能性。還有,我拜讀另一位日本文化人類學家桑山敬己教授對於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與日本文化人類學的關係所做的深入研究,很自然地產生了很強的共鳴,他在《本土的人類學與民俗學─知識的世界體系與日本》這部大作中提到,日本長期以來只是被西方表象的對象,這一點頗為類似於文化人類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本地人」(native)。我想,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深切地意識到被「他者」所表象的同時,一直以來習慣於被觀察、被研究、被表象而沉默不語的本地人或本土知識分子,尤其是本土人類學家,不僅能夠閱讀那些關於自己文化的他者的書寫,也能夠開始使用母語講述自己的文化,這該是何等重要的成長!再進一步,便是我以前的同事高丙中教授多年來一直努力的那個方向,亦即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從「家鄉」或「本土」的人類學,朝向「海外民族志」延展的學術之路,不僅講述和表象自己的文化,還要去觀察、研究、講述和表象其他所有我們感興趣的異文化,進而通過以母語積累的學術成果,為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公眾的世界認知做出必要的貢獻。如果說從民俗學走向文化人類學的高丙中教授,他所追求的是更進一步朝向外部世界大踏步邁去的中國人類學,那麼,似乎是從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走向民俗學的我本人,所追求的或許正是本土人類學進一步朝向內部的深入化。無論如何,在使用母語為中國讀者寫作這個意義上,在將通過「人類學與民俗研究」所獲得的點滴知識與成果回饋中國社會與公眾讀者的意義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在嘗試著去踐行費孝通教授所提示的那個「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理念。
有趣的是,上述幾位和我同輩或比我年輕的中日兩國的學者,也大都兼備了文化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的雙重身分,這麼說,並非自詡我也是那樣,而是說我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知到,並且都在實踐著能夠促使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之間相互助益的學術研究。這讓我想起了費孝通教授關於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中能否「進得去」和「出得來」這一難點的歸納,對於異文化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而言,能否進得到對象社區裡去,可能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對於本文化的民俗學研究而言,能否出得來,亦即能否走出母語文化的遮蔽,則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我的理解而言,我們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路徑中,通過對雙方的比照和參鑒,的確是有助於化解上述難點的。實際上,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對應關係,在我的理解中,還有「異域」和「故鄉」(祖國)、「他者」和「同胞」、「田野工作」和「采風」、「外語」和「母語」等許多有趣的方面,也都很值得深思。
不僅在中國,也包括日本以及許多其他非歐美國家的本土人類學家,很多人是在西方受到專業的人類學訓練,所以,他們洞悉歐美人類學的那些主要的「秘密」,包括「寫文化」、表象和話語霸權之間的關係等。誠如桑山敬己教授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家能夠憑藉母語濡化獲得的先賦優勢,揭示更多異文化他者(包括西方及日本以中國為田野的人類學家、或使用漢語去表象少數民族文化的漢族出身的人類學家)往往難以發現及領悟的本土文化的內涵,所以,比起他們的歐美人類學家老師來,他們在認識自己的本土社會、表象本土文化時確實是有更多的優勢或便利,他們容易發現歐美人類學言說的破綻,他們對於自身所屬的本土社會在文化人類學中被表象的部分或對於被外來他者所誤讀的部分,常常傾向於給出不同的答案。雖然他們總是被歐美人類學體系邊緣化,但邊緣也自有邊緣的風景。
現時代的文化人類學已經很難認可某種特定的言說或表象,而是需要在研究者、描寫者和被研究者、被描寫者的雙方之間,基於對相同的研究對象的共同學術興趣,形成對所有人均能夠開放的交流空間。文化人類學的知識越來越被證明其實是來自於它和對象社區的本土知識之間的反復對話,所以,我們應該宣導的是一種在不同的世界之間交流知識和溝通資訊的人類學。在我看來,始終致力於本文化研究的民俗學乃是本土知識的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為主要的源泉,所以,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的相遇、交流和對話,確實是可以促成豐碩的學術產出。所以,中國截至目前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來自文化人類學對於民俗研究的藐視,即便乍看起來似乎是有那麼一些根據,例如,民俗學在田野調查、民俗志積累或是理論建樹方面有較多的欠缺等等,但若仔細斟酌,卻也不難發現在此種姿態背後的傲慢、偏見與短視。
長期以來,中國的本土人類學並不是為了補強那個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系或為它錦上添花而存在的,它主要是基於國內公眾對於新知識的需求,基於中國學術文化體系內在的理據和邏輯而逐漸成長起來的。文化人類學在中國肩負著如何在國內本土的多民族社會中,翻譯、解說和闡釋其他各種異文化的責任,因此,它對於國內各民族的公眾將會形成怎樣的有關異域、他者、異文化或具體的異民族的印象,減少、降低、甚或糾正有關異族他者的誤會、誤解,以至於消除偏見和歧視等,均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它也需要深入地開掘本土文化的知識資源,推動國內公眾的本土文化認知,引導、包容、整合乃至於融化經常表現在民俗研究之中的各種文化民族主義式的認知與思緒,進而引導一般公眾達致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因此,中國文化人類學的「海外民族志」發展取向和對本土文化研究的深入開掘應該是比翼齊飛,而不應有所偏廢。我相信,要達成上述具有公共性的學術目標,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在中國本土社會及文化研究領域裡的互動與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從長遠看,這種互動刺激的路徑能夠在國內的新知識生產中發揮創造性,從而既為中國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術的發展做出貢獻,也在推動民眾提升有關文化多樣性、文化交流、族群和睦、守護傳統遺產、根除歧視等國民教養方面有所作為。
文化人類學在中國的內向深化發展,很需要來自民俗研究的支援;它們兩者的相互結合,既可以促使人類學的本土文化研究不再停留於表皮膚淺的層面而得以邁向深入,也將有助於提升中國民俗研究的品質,擴展中國民俗學的國際學術視野,以及推動它朝向現代民俗學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我多年來較為堅持的學術理念,收入「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系列的若干專題性研究,基本上也大都是在上述理念的支持下,歷經十多年乃至數十年的認真思考與探索才逐步完成的。這些各自獨立的專題性學術研究,大都緣起於個人的學術趣味,雖然它們彼此之間未必有多麼密切的關聯,但大都算得上是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一學術路徑上認真實踐、砥礪前行所留下的一串腳印。現在不揣淺陋使之問世,我由衷地希望它們能夠為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的學術大廈增添幾塊磚瓦,當然,也由衷地希望諸位同行師友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教。
周星
2019年2月29日 記於名古屋
目次
導言
上部 「死給」、「死給案」與涼山社會
第一章 「死給」與「死給案」
第二章 家支內「死給」案例及簡析
第三章 家支間「死給」案例及簡析
第四章 舊涼山的「死給案」及處理規則
第五章 婦女與「死給」
第六章 親家與冤家
第七章 家支與德古
第八章 黑巫術與象徵性的衝突
第九章 追問「社會形態民族學」
第十章 涼山社會的特點及其法文化傳統
討論:關於自殺(包括「死給」)的比較研究
下部 尊嚴了斷:「死給」現象的再追問
第一章 在田野中「發現」問題
第二章 弱者示強與尊嚴的邏輯:「死給」現象再闡釋
第三章 基於案例的分析
第四章 「死穢」與力量:「死給」事件中的遺體
第五章 情緒/情感的衝擊力與「爭勝鬥狠」
第六章 同一案例的兩種表述
第七章 兩種法文化的比較
第八章 民間調解與基層的司法實踐
第九章 漢人鄉土社會的「打人命」與「鬧喪」
討論:如何才能消解或弱化「死給」的邏輯
結語
附錄
家支.德古.習慣法
一、家支:分枝的血緣共同體
二、德古:涼山的世俗權威
三、習慣法:社會生活秩序的規範
習慣法與少數民族社會
一、現代化與國家法制建設
二、多族群與多種法律並存的社會
三、協調及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少數民族法文化研究應與民族法制研究相結合
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的「習慣法」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法人類學
三、民族法制研究的意義
四、應將習慣法研究與民族法制研究相結合
後記.鳴謝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死給」與「死給案」
1995年9月和1996年9月,我有機會前往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進行了兩次實地的社會與民俗調查。在實地的調查中,我特別關心的是,曾經的「奴隸社會」瓦解之後,在當前的涼山社會裡,依然面臨哪些基本和特殊的社會與文化問題。調查時,涼山社會裡一種比較特別的「死給」現象,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書的「上部」就是根據調查所獲的素材,同時參考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在與一些彝族學者的信件討論中獲得啟示,進而試圖從一個比較獨特的亦即「死給案」的角度,採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來由表及裡地重新認識涼山彝族社會。通過「死給案」,我試圖深入地分析該社會中社會關係的結構及矛盾,並在與其社會組織及其他各種重要的社會事實的相互聯繫當中,進一步理解涼山彝族社會的習慣法傳統。
「死給」,是涼山彝族社會裡一種較為普遍而又獨特的社會現象,當地彝語稱之作「死之比」[註1],直譯意為「互相死給」。「死給」即是「死給某人」的簡稱,這是一個本地概念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民俗用語。若是按照都市社會裡人們的說法,「死給」其實就是自殺,是自殺的一種獨特的類型。所謂「死給案」,乃是指涼山社會裡因為「死給」事件而導致的一類較為常見的民間訴訟案件,彝語稱為「死之比確」,直譯意為「互相死給案」。幾乎所有的「死給」事件,在涼山社會都必然會引發出複雜的「死給案」。對於「死給案」,很難用國家法律意義上的刑事案或民事案來界定。「死給案」,通常只被現行的國家法律體系看成是「自殺案」而已,但在涼山社會,多因某種糾紛而引發的「死給」事件卻具有很嚴重的性質,通常總是會引起更嚴重的衝突與糾紛,甚至常被認為具有和殺人案件相似或接近的屬性。
「死給」的基本情形是,某兩人因為任何事情,通常大都是一些小事,發生口角與糾紛,一方(通常是較弱的一方)如果在這個衝突過程中感受到尷尬、侮辱、難堪,尤其是當眾受辱,面子和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感到氣憤難平,他或她就很可能選擇自殺,以死相爭,也就是「死給」對方。「死給」幾乎沒有例外地總是一場重大衝突或暴力事件的導火線。在涼山彝族社會,「死給者」總是能夠立刻得到自己家支的過問,總是可以借助家支和傳統習慣法來將「被死給者」擺平。習俗甚至還允許「死給者」的家支不分青紅皂白地襲擊「被死給者」,實施打砸搶燒,然後再進一步要求賠償。所以,衝突中的弱者,認為自己被欺負後往往就會傾向於選擇「死給」,而「死給案」若調解不好,直接的後果便是家支之間的械鬥。
根據當地彝人的看法,「被死給」的對方,也就是導致某人「死給」的人,一定意義上就是凶手,他或他的家支必須為「死給者」償命或付出為當地習慣法所認可的代價,亦即「賠人命」。換句話說,涼山彝族社會對於「死給」並不完全認為它屬於自殺,而是認為導致「死給者」做出此種舉動的人必須承擔很大的責任,有些乾脆就被視為凶手,多少具有一種認定「死給」為「他殺」的傾向。在涼山彝族的習慣法中,殺人的概念和現行刑法的規定不完全一致,它不僅包括故意殺人和因過失致人死亡,也包括因為相互的爭吵而服毒、自縊、投河、跳崖等自殺行為[註2]。「死給案」一旦發生,死者的家支就會迅速地聯合起來,向對方當事人或對方家支「討人命」,甚至迫使對方當事人自殺。如果對方家支不能滿足「死給者」家支的一些基本要求,就將很難避免衝突升級,以至於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家支之間的戰爭。
涼山社會裡的「死給」事件,看起來並非偶爾發生,因為其發生的比例頗高。目前,雖無全涼山或美姑縣的有關統計資料,但在調查中,「死給」的案例卻出乎意外的多。我們訪問過的若干個村莊的德古,幾乎每位都曾調解過若干此類案例或能順口舉出他們聽說過的「死給」案例。「德古」是涼山彝族社會中專事調解糾紛的頭人,德古所最熟悉的往往也正是與「死給」相關的那些先前的案例和習慣法條文。根據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可以說「死給案」不僅在民主改革之前的「奴隸制時代」很多,以至於形成了許多專門的條文,就是時至今天,其發生依然比較頻繁和普遍;這就使得民主改革以前已形成很多涉及「死給案」的習慣法條文,至今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得到實際上頗為有效的應用。這也意味著「死給」的社會現象,在涼山並沒有因為「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其相關社會制度的變更而消失,它是屬於涼山彝族社會中一類相對穩定的社會現象。
「死給」較多地發生在彼此關係十分親近的人們之間,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丈夫和妻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舅舅與外甥之間、公婆與媳婦之間,包括要好的朋友之間,以及生意合夥人之間等等。如果按照當地彝族人的民間分類,這些「死給案」主要可以分為家支內部和家支之間兩大類型,例如,兄弟姐妹間的相互「死給」屬於同一家支內部,丈夫和妻子間的相互「死給」屬於不同家支之間。依據當事人之間的家支關係,德古們對於具體的「死給案」的評價和處理是很不相同的。例如,舅舅與外甥相互「死給」有命金,因為其家支背景不同;在有些情形下,丈夫「死給」妻子無命金,但若是相反,妻子「死給」丈夫則一定有命金。有一種說法是,正因為是近親至愛之間,發生了糾紛才採取「死給」,否則,關係較遠的話,發生糾紛衝突時便是以暴力相向了。
在「死給」現象和「死給案」中,引起較大社會影響的通常是那些發生在不同家支之間的情形,這是因為家支背景不同所導致的衝突,有可能在該社會裡引發出一系列重大的甚或是戰爭之類的後果。在導致家支之間「死給」命案的諸多糾紛中,起因於婚姻糾紛的「死給」較為普遍;相比之下,婦女「死給」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可能導致「死給」發生的糾紛的種類很多,但大多是一些生活瑣事,除了婚姻方面的糾紛之外,諸如牲畜吃了莊稼、酒醉打架、地界糾紛、兄弟分割家產等等,都有可能引發「死給」。
導致「死給」的某些公開的糾紛或糾紛的公開化,往往是在聚眾喝酒時發生的。在當地社區裡,「被死給」的對象一般都是十分明確的,絕少有某人自殺而人們又不知道其原因或其「死給」對象的情形。就是說,「死給者」選擇「死給」,通常具有直接和強烈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他或她可能會在某種公開吵架的場合有所表示甚或聲明,例如說,「我死給你看」或「我讓你給我出埋葬費」之類威脅的話,並在對方家或其附近實施「死給」。死者選擇「死給」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把衝突推向升級,通過自己選擇死亡而給對方留下一個可以說是天大的麻煩,讓對方的日子不好過,甚至面臨被報復致死的局面。「被死給」的人,將因此立即面臨嚴重的事態、困難的處境和巨大的壓力。在家支之間「死給」的情形下,這些壓力主要來自「死給者」家支集體決意為「死給者」報復的傳統。死者家支對「死給」的反應,通常是由近親向自己的家支申訴,家支則要向「被死給者」及其家支提出種種要求;「被死給」一方的家支,或選擇請人調解,最後集資以均攤的方式為賠償死者的「人命」出錢;或選擇拒絕和迎戰,從而進入戰爭狀態。如果「死給案」發生在家支內部,「被死給者」依然面臨巨大的壓力,並將承受來自本家支的嚴厲制裁。一旦有人「死給」,出了人命,即便「被死給者」在糾紛中有理,糾紛的責任在於死者,也都很難再說誰對誰錯,儘管糾紛與衝突的具體情節在調解談判時會被顧及,但賠償命金或命價卻是不能回避的。如果「死給」未遂,沒有成功,雙方的糾紛和緊張關係就依然如故地存在,且需要第三者迅速前來,以理服人地展開調解。
顯然,在糾紛或衝突當中,表示「死給」某人是一種很嚴重的威脅或策略,是當事人為了使衝突得以繼續、升級或者在衝突中獲得籌碼的重要步驟[註3]。舊涼山曾經發生過一件很能說明「死給」在衝突中的作用的事情:某青年婦女被人懷疑偷了雞,由於偷雞在涼山彝區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恥辱,所以,她便穿戴打扮一番,來到失主家要求拿出證據,否則,就當場「死給」失主,失主沒有證據,只好請來德古調解,最後殺了頭牛招待該婦女的親友,為她恢復了名譽。這可以說是以「死給」為武器的典型例證[註4]。當在衝突或糾紛中的各種關係十分複雜地相互糾葛時,決心「死給」的人對於「死給」的對象是會有所選擇的。例如,父母把女兒許給男方,女兒不願,要求退婚,自己的父母和男方都不同意,於是,女方就有可能在某一天打扮好去男方家,「死給」男方。在這種情形下,死者的選擇是沒有「死給」父母,而是「死給」了男方。
通過實地的調查和案例分析,我們不很確定地傾向於認為,似乎在涼山社會,一旦在個人之間發生糾紛或衝突,假如沒有第三者立即介入調解,衝突往往就會迅速升級,並發展到極端,亦即從瑣事到嚴重事態間的「距離」很短。而「死給」正是使得衝突迅速升級和擴大時較多使用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手段或策略。由於「死給」事件,衝突通常就由個人之間擴展到家支之間的層面,由一般的瑣事糾紛升級為嚴重的人命案件,其馬上和直接的後果便是兩個或多個家支之間的尖銳對抗。
導致「死給」事件發生的具體的情節過程,以及「死給者」選擇的不同的自殺方式,通常會影響德古們對於案件性質之嚴重程度的判斷和處理,例如,賠償的額度就會因此有所不同。這和當地社會對於事件程序的細節、犯罪情節及刑罰級別等均有自己獨特和較為完備的分類體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死給」的形式,主要有服毒、上吊和跳岩等。從有關命金賠償及善後的一些規則看來,選擇「死給」的一方往往被認為是弱者。比如,丈夫「死給」妻子的命金,不如妻子「死給」丈夫的命金多,乃是因為丈夫通常不被視為弱者。但或許正因為是弱者,才更容易極端地表現好勇鬥恨的態度。弱者的「死給」,乃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率先一步走到極端,讓對方為與自己發生的糾紛而後悔。「死給案」的結局,通常不外乎以下幾種:「被死給者」也被迫自殺;死者的近親家人尤其是婦女們前去對方家砸鍋殺豬,抄家鬧事,闖禍者則一面回避,一方面請人規勸,然後再進入調解狀態,亦即「討人命」與「賠人命」;再或者就是對峙、械鬥及戰爭。
在涼山彝族傳統的習慣法裡,經常使用固定的程度副詞,亦即用表示顏色的詞來區分犯罪的情節、案件的屬性、責任以及賠償額度的級別。最常用的是「黑」、「花」、「白」三級,在有的時候,其間再加「黑花」、「花白」,而成為五級;進一步還有將每級再分出三級,計15個級別的說法(一說,「黑」、「花」、「白」三個等級,又分別各有三個次等級),但最為基本的還是「黑」、「花」、「白」三級。無論在文獻中,還是在田野調查時,都能發現這種獨特分類的存在。「阿諾」意為黑色,用來指稱挾嫌報復殺人等重罪「黑案」,一般是要抵命或賠償多達數千兩銀子,「黑案」亦即嚴重的案件[註5],通常需要召開家支會議來解決;「阿則」意為花色,是指可以通過賠償錢財予以解決的罪行;而一般的「死給」屬於花案;「阿曲」意為白色,指誤傷之類,可以視為小罪或有過錯,但至少也要殺牲賠禮[註6]。導致命案的情節,也能夠成為重要的劃分依據,例如,黑彝之間的兇殺案為「黑案」;若是雙方爭吵,一方氣憤吊死即為「花案」;有錯但受到批評後服毒自殺的為「白案」等[註7]。「死給者」生前是否遭到打罵,這是十分重要的,曲諾遭黑彝打罵之後吊頸或服毒自殺,即為「花案」,一般要賠償命價;但發生糾紛後對方未加打罵,本人因一時想不開自殺,則只須賠償輕微的「魂價」,不賠命價[註8]。根據摩瑟磁火先生的介紹,對於案件屬性的分類,其實除了「黑」、「花」、「白」之外,還有第四個特別的層次,亦即彝語所謂「以的」或「以偉」,意為「因某某緣故」,主要是指一些事出有因、但卻查無實據之類的事件,這方面的賠償則要更輕微一些。關於案件屬性之分類的不同說法,在涼山各地,是否會因地域或時代的因素而產生不同,尚有待深究。總之,「死給」無論表現為「家支人命案」,還是表現為「姻親人命案」,通常都屬於性質較為嚴重的「花案」。如果與導致「死給」的原因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是間接有過汙蔑或讒言之類,則賠償的額度也有可能被定為「白案」。
涼山社會的其他制度或習俗,對於「死給案」的定性及處理也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法人類學研究所應遵循的前提[註9],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死給案」,而應該是從「死給案」與其社會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包括社會組織的結構以及與政治、經濟、宗教制度等的相互關聯之中去理解它。例如,除了家支背景和不同家支的實力對比以外,一般不同等級如白彝和黑彝之間的命金額度會有所不同。在舊涼山社會,「死給案」一般並不發生在奴隸佔有者和奴隸之間,在奴隸制度之下,奴隸的自殺多被認為只是一種反抗[註10]。不過,在我看來,奴隸的自殺有時候也可能具有「死給」的屬性,雖然主子是不可能給自殺的奴隸賠償命價的,故奴隸「死給」奴隸主沒有意義,但奴隸的自殺除了反抗,也有可能是為了澄清被誤會的冤屈等,所以,它和通過「死給」表示清白的情形或有一定的相通之處。至於奴隸主,則是絕對不屑於「死給」奴隸的,若真有主子「死給」奴隸的話,是沒有命金的,因為輿論會認為此人太過差勁。
此外,因為長輩教訓晚輩導致其「死給」的,可以不賠命金;作為調解和判案者的「德古」,其命價極高等等,所有這些習慣法的知識,可以說分別反映了舊涼山社會裡等級制度、輩分原理以及「德古」作為頭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等非常重要的社會事實。
[註1]此處和本書其他部分採用之彝語文「民俗語彙」,多係漢語音譯或意譯,由於印刷方面的困難,且將原彝文略去。
[註2]曲畢石美、馬爾子:〈舊涼山彝族家支、姻親人命案及案例〉,《涼山民族研究》,1995年。周星:〈民俗、習慣法與法制:以涼山彝族社會的調查為例〉,喬健、李沛良、馬戎主編:《社會科學的應用與中國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註3]四川省編寫組:《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資料選輯》,第78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2月。
[註4]楊懷英主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法律制度研究》,第69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4月。
[註5]伍精忠:〈涼山彝族社會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具體問題〉,《涼山民族研究》,創刊號,1992年10月。
[註6]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第140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註7]胡慶均:《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第48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5月。
[註8]楊懷英主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法律制度研究》,第64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4月。
[註9]K. F.科克(K. F. KoehlerVerlag)著、楊周雲譯:〈法律與人類學〉,《民族譯叢》,1987年第6期。
[註10]胡慶均:《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第14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5月。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