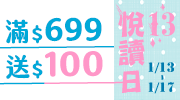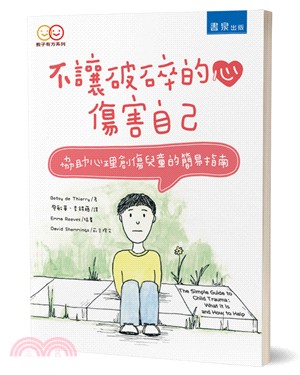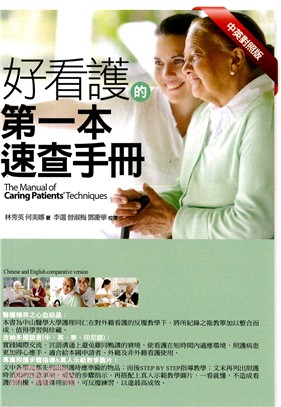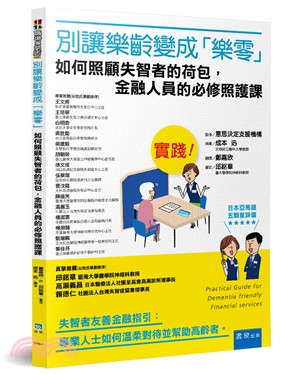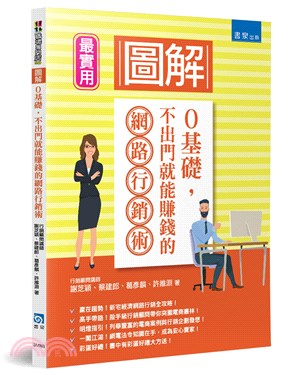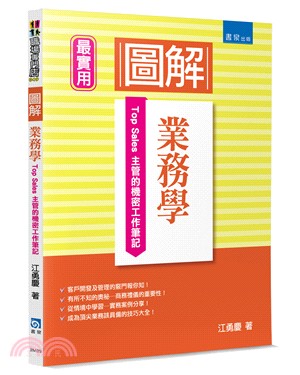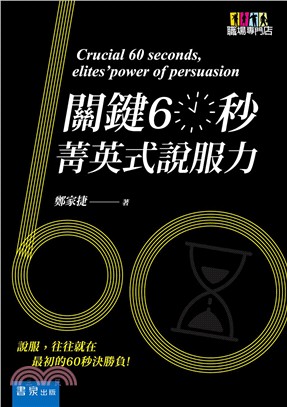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
ISBN13:9787555909606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作者:蘇童
出版日:2020/05/01
裝訂/頁數:平裝/182頁
規格:21cm*14.5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本書是“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叢書中的一種,選錄了蘇童的中篇小說代表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園藝》《離婚指南》。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通過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逃亡,表達了潰敗的農村向新興的都市逃亡的歷史背景,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融入了他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體現了蘇童對現代人荒誕的生存困境和絕望的精神狀態的思考。《園藝》通過對既依賴於婚姻又厭倦於婚姻的孔太太的矛盾內心的描寫,細膩地捕捉到了兩性情感中的微妙皺褶,體現了蘇童的文學敏銳性。在《離婚指南》中,蘇童塑造了一個忙於一場前景黯淡、疲於奔命的離婚官司的三十歲的男人形象,在楊泊與朱蕓看似穩定和諧的生活之中,隱藏著愛與性、理想與現實、自由與禁錮的內在矛盾,真實地表現了婚姻生活中兩性的情感狀態。
作者簡介
蘇童,原名童忠貴,1963年生於蘇州。他的童年伴隨著“文革”運動,他身處於運動之中,又因年幼而置身事外,這種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特殊經歷,對他後來的“文革”敘事有著深遠影響。
1987年發表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被認為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1989年,發表《妻妾成群》,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獎。1990年代後蘇童的創作轉向長篇小說,發表了《米》《菩薩蠻》《我的帝王生涯》等。新世紀以來,蘇童的作品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河岸》獲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茨菰》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香草營》獲《小說月報》第十四屆百花獎,《黃雀記》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萬用表》獲第十七屆百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及第五屆汪曾祺文學獎。
名人/編輯推薦
蘇童著《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為“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叢書之一種。
一、該叢書是首部由當代著名評論家點評的涵括中國百年經典中篇小說、展示中國百年中篇小說創作實績的大型文學叢書。
該叢書對“五四”以來中篇小說創作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讀者可以通過本叢書確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杰出中篇小說的閱讀坐標。當代著名評論家何向陽、孟繁華、陳曉明、白燁、吳義勤對作品的文學價值以及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進行了詳細介紹,對文本進行了精彩點評,這對於讀者欣賞把握這些經典作品起到了引導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叢書以作家分冊,每冊精選該作家最經典、讀者認知度高的作品。除經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學化的作家小傳及作家圖片若幹幅。所附內容既可以為文學研究者、文科學生提供必要的資料,對普通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樣大有裨益。
三、所選作家有較大影響力。
蘇童,原名童忠貴,1963年生,江蘇蘇州人。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駐會專業作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代表作包括《園藝》《紅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說《妻妾成群》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並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第6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獎,蜚聲海內外。《黃雀記》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後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目次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園藝
離婚指南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蘇童中篇小說簡論/吳義勤
書摘/試閱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我的父親也許是個啞巴胎。他的沉默寡言使我家籠罩著一層灰蒙蒙的霧障足有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裡我出世成長蓬勃衰老。父親的楓楊樹人的精血之氣在我身上延續,我也許是個啞巴胎。我也沉默寡言。我屬虎,十九歲那年我離家來到都市,回想昔日少年時光,我多麼像一只虎崽伏在父親的屋檐下,通體幽亮發藍,窺視家中隨日月飄浮越飄越濃的霧障,霧障下生活的是我們家族殘存的八位親人。
去年冬天我站在城市的某盞路燈下研究自己的影子。我意識到這將成為一種習慣在我身上滋生蔓延。城市的燈光往往是雪白寧靜的。我發現我的影子很蠻橫很古怪地在水泥人行道上洇開來,像一片風中蘆葦,我當時被影子追蹤著,雙臂前撲,扶住了那盞高壓氖燈的金屬燈柱。回頭又研究地上的影子,我看見自己在深夜的城市裡畫下了一個逃亡者的像。
一種與生俱來的惶亂使我抱頭逃竄。我像父親。我一路奔跑經過夜色迷離的城市,父親的影子在後面呼嘯著追蹤我,那是一種超於物態的靜力的追蹤。我懂得,我的那次奔跑是一種逃亡。
我特別注重這類奇特的體驗總與回憶有關。我回憶起從前有許多個黃昏,父親站在我的鐵床前,一只手撫摸著我的臉,一只手按在他蒼老的腦門上,回過頭去凝視地上那個變幻的人影,就這樣許多年過去我長到二十六歲。
你們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們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不叫蘇童。我有許多父親遺傳的習慣在城市裡展開,就象一面白色喪旗插在你們前面。我喜歡研究自己的影子。去年冬天我和你們一起喝了白酒後打翻一瓶紅墨水,在墻上畫下了我的八位親人。我還寫了一首詩想夾在少年時代留下的歷史書裡。那是一首胡言亂語口齒不清的自白詩。詩中幻想了我的家族從前的輝煌歲月,幻想了橫亙於這條血脈的黑紅災難線。有許多種開始和結尾交替出現。最後我痛哭失聲,我把紅墨水拼命地往紙上抹,抹得那首詩無法再辨別字跡。我記得最先的幾句寫得異常艱難:
我的楓楊樹老家沉沒多年
我們逃亡到此
便是流浪的黑魚
回歸的路途永遠迷失
你現在去推開我父親的家門,只會看見父親還有我的母親,我的另外六位親人不在家。他們還在外面像黑魚一般涉泥流浪。他們還沒有抵達那幢木樓房子。
我父親喜歡幹草。他的身上一年四季散發著醇厚堅實的幹草清香。他的皮膚褶皺深處生長那種幹草清香。街上人在春秋兩季總看見他擔著兩筐幹草從郊外回來,晃晃悠悠逃入我家大門。那些黃褐色松軟可愛的幹草被碼成堆存放在堂屋和我住過的小房間裡,父親經常躺在草堆上面,高聲咒罵我的瘦小的母親。
我無法解釋一個人對幹草的依戀,正如同無法解釋天理人倫。追溯我的血緣,我們家族的故居也許就有過這種幹草,我的八位親人也許都在故居的幹草堆上投胎問世,帶來這種特殊的記憶。父親面對幹草堆可以把自己變作巫師。他抓起一把幹草在夕陽的餘輝下凝視著便聞見已故的親人的氣息。
祖母蔣氏、祖父陳寶年、老大狗崽、小女人環子從幹草的形象中脫穎而出。
但是我無緣見到那些親人。我說過父親也許是個啞巴胎。
當我想知道我們全是人類生育繁衍大鏈環上的某個環節時,我內心充滿甜蜜的憂傷,我想探究我的血流之源,我曾經糾纏著母親打聽先人的故事。但是我母親不知道,她不是楓楊樹鄉村的人。她說,“你去問他吧,等他喝酒的時候。”我父親醉酒後異常安靜,他往往在醉酒後跟母親同床。在那樣的夜晚父親的微紅的目光悠遠而神秘,他伸出胳膊箍住我的母親,充滿酒氣的嘴唇貼著我的耳朵,慢慢吐出那些親人的名字:祖母蔣氏、祖父陳寶年、老大狗崽、小女人環子。他還反反復復地說,“一九三四年。你知道嗎?”後來他又大聲告訴我,一九三四年是個災年。
一九三四年。
你知道嗎?
一九三四年是個災年。
有一段時間我的歷史書上標滿了一九三四這個年份。一九三四年迸發出強壯的紫色光芒圈住我的思緒。那是不復存在的遙遠的年代,對於我也是一棵古樹的年輪,我可以端坐其上,重溫一九三四年的人間滄桑。我端坐其上,首先會看見我的祖母蔣氏浮出歷史。
蔣氏幹瘦細長的雙腳釘在一片清冷渾濁的水稻田裡一動不動。那是關於初春和農婦的畫面。蔣氏滿面泥垢,雙顴突出,垂下頭去聽腹中嬰兒的聲音。她覺得自己像一座荒山,被男人砍伐後種上一棵又一棵兒女樹。她聽見嬰兒的聲音仿佛是風吹動她,吹動一座荒山。
在我的楓楊樹老家,春日來得很早,原白色的陽光隨丘陵地帶曲折流淌,一點點地溫暖了水田裡的一群長工。祖母蔣氏是財東陳文治家獨特的女長工。女長工終日泡在陳文治家綿延十幾裡的水田中,插下了起碼一萬株稻秧。她時刻感覺到東北坡地黑磚樓的存在,她的後背有一小片被染黑的陽光起伏跌宕。站立在遠處黑磚樓上的人影就是陳文治。他從一架日本望遠鏡裡望見了蔣氏。蔣氏在那年初春就穿著紅布圓肚兜,後面露出男人般瘦精精的背脊。背脊上有一種持久的溫暖的霧靄散起來,遠景模糊,陳文治不停地用衣袖擦拭望遠鏡鏡片。女長工動作奇麗,憑借她的長胳膊長腿把秧子天馬行空般插,插得賞心悅目。陳文治驚嘆於蔣氏的做田功夫,整整一個上午,他都在黑磚樓上窺視蔣氏的一舉一動,蒼白的刀條臉上漾滿了癡迷的神色。正午過後蔣氏綽出水田,她將布褂胡亂披上肩背,手持兩把滴水的秧子,在長工群中甩搭甩搭地走,她的紅布兜有力地鼓起,即使是在望遠鏡裡,財東陳文治也看出來蔣氏懷孕了。
我祖上的女人都極善生養。一九三四年祖母蔣氏又一次懷孕了。我父親正渴望出世,而我伏在歷史的另一側洞口朝他們張望。這就是人類的鎖鏈披掛在我身上的形式。
我對於楓楊樹鄉村早年生活的想象中,總是矗立著那座黑磚樓。黑磚樓是否存在並無意義,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一種沉默的象征,伴隨祖母蔣氏出現,或者說黑磚樓只是祖母蔣氏給我的一塊布景,誘發我的瑰麗的想象力。
所有見過蔣氏的陳姓遺老都告訴我,她是一個丑女人。她沒有那種紅布圓肚兜,她沒有農婦頂起紅布圓肚兜的乳房。
祖父陳寶年十八歲娶了蔣家圩這個長腳女人。他們拜天地結親是在正月初三。楓楊樹人聚集在陳家祠堂喝了三大鍋豬油赤豆菜粥。陳寶年也圍著鐵鍋喝,在他焦灼難耐的等待中,一頂紅竹轎徐徐而來。陳寶年滿臉猩紅,摔掉粥碗歡呼,“陳寶年的雞巴有地方住啰!”所以祖母蔣氏是在楓楊樹人的一陣大笑聲中走出紅竹轎的。蔣氏也聽見了陳寶年的歡呼。陳寶年牽著蔣氏僵硬汗濕的手朝祠堂裡走,他發現那個被紅布帕蒙住臉的蔣家圩女人高過自己一頭,目光下滑最後落在蔣氏的腳上,那雙穿繡鞋的腳碩大結實,呈八字形茫然踩踏陳家宗祠。陳寶年心中長出一棵灰暗的狗尾巴草,他在祖宗像前跪拜天地的時候,不時蜷起尖銳的五指,狠掐女人伸給他的手。陳寶年做這事的時候神色平淡,側耳細聽女人的聲音。
女人只是在喉嚨深處發出含糊的呻吟,同時陳寶年從她身上嗅見了一種牲靈的腥味。
這是六十年前我的家族史中的一幕,至今猶應回味。傳說祖父陳寶年是婚後七日離家去城裡謀生的。陳寶年的肩上圈著兩匝上好的青竹篾,搖搖晃晃走過黎明時分的楓楊樹鄉村。一路上他大肆吞咽口袋裡那堆煮雞蛋,直吃到馬橋鎮上。
鎮上一群開早市的各色手工匠人看見陳寶年急匆匆趕路,青布長褲大門洞開,露出裡面印跡斑斑的花布褲頭,一副不要臉的樣子。有人喊,“陳寶年把你的大門關上。”陳寶年說狗捉老鼠多管閑事大門暢開進出方便。他把雞蛋殼扔到人家頭上,風風火火走過馬橋鎮。自此馬橋鎮人提起陳寶年就會重溫他留下的民間創作。
閂起門過的七天是昏天黑地的。第七天門打開,婚後的蔣家圩女人站在門口朝楓楊樹村子潑了一木盆水。楓楊樹女人們隨後胡蜂般擁進我家祖屋,圍繞蔣氏嗡嗡亂叫。她們看見朝南的窗子被狗日的陳寶年用木板釘死了。我家祖屋陰暗潮濕。蔣氏坐到床沿上,眼睛很亮地睇視眾人。她身上的牲靈味道充溢了整座房子。她懼怕談話,很莽撞地把一件竹器夾在雙膝間醞釀幹活。女人們看清楚那竹器是陳寶年編的竹老婆,大乳房的竹老婆原來是睡在床角的。蔣氏突然對眾人笑了笑,咬住厚嘴唇,從竹老婆頭上抽了一根篾條來,越抽越長,竹老婆的腦袋慢慢地頹落掉在地上。蔣氏的十指瘦筋有力,幹活麻利,從一開始就給楓楊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男人是好竹匠。好竹匠肥褲腰,腰裡銅板到處掉。”楓楊樹的女人都是這樣對蔣氏說的。
蔣氏坐在床上回憶陳寶年這個好竹匠。他的手被竹刀磨成竹刀,觸摸時她忍著那種割裂的疼痛,她心裡想她就是一捆竹篾被陳寶年搬來砍砍弄弄的。楓楊樹的狗女人們,你們知不知道陳寶年還是個小仙人會給女人算命?他說楓楊樹女人十年後要死光殺絕,他從蔣家圩娶來的女人將是顆災星照耀楓楊樹的歷史。
陳寶年沒有讀過《麻衣神相》。他對女人的相貌有著驚人的尖利的敏感,來源於某種神秘的啟示和生活經驗。從前他每路遇圓臉肥臀的女人就眼泛紅潮窮追不舍,興盡方歸。陳寶年娶親後的第一夜月光如水瀉進我家祖屋,他騎在蔣氏身上俯視她的臉,不停地唉聲嘆氣。他的竹刀手砍伐著蔣氏沉睡的面容。她的高聳的雙顴被陳寶年的竹刀手磨出了血絲。
蔣氏總是疼醒,陳寶年的手壓在臉上像個沉重的符咒沁入她身心深處。她拼命想把他翻下去,但陳寶年端坐不動,有如巫師漸入魔境。她看見這男人的瞳仁很深,深處一片亂云翻卷成海。男人低沉地對她說:
“你是災星。”
那七個深夜陳寶年重復著他的預言。
我曾經到過長江下遊的舊日竹器城,沿著頹敗的老城城墻尋訪陳記竹器店的遺址。這個城市如今早已沒有竹篾滿天滿地的清香和絲絲縷縷的鄉村氣息。我背馱紅色帆布包站在城墻的陰影裡,目光猶如垂曳而下的野葛藤纏繞著麻石路面和行人。你們白發蒼蒼的老人,有誰見過我的祖父陳寶年嗎?
祖父陳寶年就是在竹器城裡聽說了蔣氏八次懷孕的消息。去鄉下收竹篾的小伙計告訴陳寶年,你老婆又有了,肚子這麼大了。陳寶年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氣問,到底多大了?小伙計指著隔壁麻油鋪子說,有榨油鍋那麼大。陳寶年說,八個月吧?小伙計說到底幾個月要問你自己,你回去掃蕩一下就彈無虛發,一把百發百中的駁殼槍。陳寶年終於怪笑一聲,感嘆著咕嚕著那狗女人血氣真旺啊。
我設想陳寶年在剎那間為女人和生育惶惑過。他的竹器作坊被蔣氏的女性血光照亮了,掛在墻上吊在梁上堆在地上的竹椅竹席竹籃竹匾一齊聳動,傳導女人和嬰兒渾厚的呼喚撞擊他的神經。陳寶年唯一目睹過的老大狗崽的分娩情景是否會重現眼前?我的祖母蔣氏曾經是位原始的毫無經驗的母親。她仰臥在祖屋金黃的幹草堆上,蒼黃的臉上一片肅穆,雙手緊緊抓握一把幹草。陳寶年倚在門邊,他看著蔣氏手裡的幹草被捏出了黃色水滴,覺得渾身虛顫不止,精氣空空蕩蕩,而蔣氏的眼睛裡跳動著一團火苗,那火苗在整個分娩過程中自始至終地燃燒,直到老大狗崽哇哇墜入幹草堆。這景象仿佛江邊落日一樣莊嚴生動。陳寶年親眼見到陳家幾代人贍養的家鼠從各個屋角跳出來,圍著一堆血腥的幹草歡歌起舞,他的女人面帶微笑,崇敬地向神秘的家鼠致意。
一九三四年我的祖父陳寶年一直在這座城市裡吃喝嫖賭,潛心發跡,沒有回過我的楓楊樹老家。我在一條破陋的百年小巷裡找到陳記竹器店的遺址時夜幕降臨了,舊日的昏黃街燈重新照亮一個楓楊樹人,我茫然四顧,那座木樓肯定已經沉入歷史深處,我是不是還能找到祖父陳寶年在半個世紀前浪蕩竹器城的足跡?
在我的已故親人中,陳家老大狗崽以一個拾糞少年的形象站立在我們家史裡引人注目。狗崽的光輝在一九三四年突放異彩。這年他十五歲,四肢卻像蔣氏般的修長,他的長相類似聰明伶俐的猿猴。
楓楊樹老家人性好養狗。狗群寂寞的時候成群結隊野遊,在七歪八斜的村道上排泄烏黑發亮的狗糞。老大狗崽終日挎著竹箕追逐狗群,忙於回收狗糞。狗糞即使躲在數裡以外的草叢中,也逃脫不了狗崽銳利的眼睛和靈敏的嗅覺。
這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祖母蔣氏對狗崽說,你拾滿一竹箕狗糞去找有田人家,一竹箕狗糞可以換兩個銅板,他們喜歡用狗糞肥田呢。攢夠了銅板娘給你買雙膠鞋穿,到了冬天你的小腳板就可以暖暖和和了。狗崽憐惜地凝視了會兒自己的小光腳,抬頭對推磨碾糠的娘笑著。娘的視線穿在深深的磨孔裡,隨碾下的麩糠痛苦地翻滾著。狗崽聞見那些黃黃黑黑的麩糠散發出一種冷淡的香味。那雙溫暖的膠鞋在他的幻覺中突然放大,他一陣欣喜把身子吊在娘的石磨上,大喊一聲,“讓我爹買一雙膠鞋回家!”蔣氏看著兒子像一只陀螺在磨盤上旋轉,推磨的手卻著魔似的停不下來。在眩惑中蔣氏拍打兒子的屁股,喃喃地說,“你去拾狗糞,拾了狗糞才有膠鞋穿。”“等開冬下了雪還去拾嗎?”狗崽問。“去。下了雪地上白,狗糞一眼就能看見。”
對一雙膠鞋的幻想使狗崽的一九三四年過得忙碌而又充實。他對祖母蔣氏進行了一次反叛。賣狗糞得到的銅板沒有交給蔣氏而放進一只木匣子裡。狗崽將木匣子掩人耳目地藏進墻洞裡,趕走了一群神秘的家鼠。有時候睡到半夜狗崽從草鋪上站起來,踮足越過左右橫陳的家人身子去觀察那只木匣子。在黑暗中狗崽的小臉迷離動人,他忍不住地攪動那堆銅板,銅板沉靜地瑯瑯作響。情深時狗崽會像老人一樣長嘆一聲,浮想連翩。一匣子的銅板以澄黃色的光芒照亮這個鄉村少年。
回顧我家歷史,一九三四年的災難也降臨到老大狗崽的頭上。那只木匣子在某個早晨突然失蹤了。狗崽的指甲在墻洞裡摳爛摳破後變成了一條小瘋狗。他把幾個年幼的弟妹捆成一團麻花,揮起竹鞭拷打他們追逼木匣的下落。我家祖屋裡一片小兒女的哭喊,驚動了整個村子。祖母蔣氏聞訊從地裡趕回來,看到了狗崽拷打弟妹的殘酷壯舉。狗崽暴戾野性的眼神使蔣氏渾身顫抖。那就是陳寶年塞在她懷裡的一個咒符嗎?蔣氏頓時聯想到人的種氣摻滿了惡行。有如日月運轉銜接自然。她斜倚在門上環視她的兒女,又一次懷疑自己是樹,身懷空巢,在八面風雨中飄搖。
木匣子丟失後我家籠罩著一片傷心陰鬱的氣氛。狗崽終日坐在屋角的幹草堆裡監察著他的這個家。他似乎聽到那匣銅板在祖屋某個隱秘之處瑯瑯作響。他懷疑家人藏起了木匣子。有幾次蔣氏感覺到兒子的目光掃過來,執拗地停留在她困倦的臉上,仿佛有一把芒刺刺痛了蔣氏。
“你不去拾狗糞了嗎?”
“不。”
“你是非要那膠鞋對嗎?”蔣氏突然撲過去揪住了狗崽的頭發說你過來你摸摸娘肚裡七個月的弟弟娘不要他了省下錢給你買膠鞋你把拳頭攥緊來朝娘肚子上狠狠地打狠狠地打呀。
狗崽的手觸到了蔣氏懸崖般常年隆起的腹部。他看見娘的臉激動得紅潤發紫朝他俯衝下來,她露出難得的笑容拉住他的手說狗崽打呀打掉弟弟娘給你買膠鞋穿。這種近乎原始的誘惑使狗崽跳起來,他嗚嗚哭著朝娘堅硬豐盈的腹部連打三拳,蔣氏閉起眼睛,從她的女性腹腔深處發出三聲凄愴的共鳴。
被狗崽擊打的胎兒就是我的父親。
我後來聽說了狗崽的木匣子的下落,禁不住為這輝煌的奇聞黯然傷神。我聽說一九三五年南方的洪水泛濫成災。我的楓楊樹故鄉被淹為一片荒墟。祖母蔣氏劃著竹筏逃亡時,看見家屋地基裡突然浮出那只木匣子,七八只半死不活的老鼠護送那只匣子遊向水天深處。蔣氏認得那只匣子那些老鼠。她奇怪陳家的古老家鼠竟然力大無比,曾把狗崽的銅板運送到地基深處。她想那些銅板在水下一定是綠銹斑斑了,即使潛入水底撈起來也聞不到狗崽和狗糞的味道了。那些水中的家鼠要把殘存的木匣子送到哪裡去呢。
我對父親說過,我敬仰我家祖屋的神奇的家鼠。我也喜歡十五歲的拾狗糞的伯父狗崽。
父親這輩子對他在娘腹中遭受的三拳念念不忘。他也許一直仇恨已故的兄長狗崽。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十月,我父親和土地下的竹筍一樣負重成長,躍躍欲試跳出母腹。時值四季的輪回和飛躍,楓楊樹四百畝早稻田由綠轉黃。到秋天楓楊樹鄉村的背景一片金黃,旋卷著一九三四年的植物熏風,氣味復雜,耐人咀嚼。
楓楊樹老家這個秋季充滿倒錯的倫理至今是個謎。那是鄉村的收獲季節。雞在凌晨啼叫,豬在深夜拱圈。從前的楓楊樹人十月裡全村無房事但這個秋季卻是個謎。可能就是那種風吹動了楓楊樹網狀的情欲。割稻的男女為什麼頻頻棄鐮而去都飄進稻浪裡無影無蹤啊你說到底是從哪裡吹來的這種風?
祖母蔣氏拖著沉重的身子在這陣風中發呆。她聽見稻浪深處傳來的男女之聲充滿了快樂的生命力在她和胎兒周圍大肆喧囂。她的一只手輕柔地撫摸著腹中胎兒,另一只手攥成拳頭頂住了嘴唇,幹澀的哭聲倏地從她指縫間躥出去像芝麻開花節節高,令聽者毛骨悚然。他們說我祖母蔣氏哭起來勝過墳地上的女鬼,飽含著神秘悲傷的寓意。
背景還是楓楊樹東北部黃褐色的土坡和土坡上的黑磚樓。祖母蔣氏和父親就這樣站在五十多年前的歷史畫面上。
收割季節裡陳文治精神亢奮,每天吞食大量白面,勝似一只仙鶴神遊他的六百畝水稻田。陳文治在他的黑磚樓上遠眺秋景,那只日本望遠鏡始終追逐著祖母蔣氏,在十月的熏風麗日下,他窺見了蔣氏分娩父親的整個過程。映在玻璃鏡片裡的蔣氏像一頭老母鹿行蹤詭秘。她被大片大片的稻浪前推後涌,渾身金黃耀眼,朝田埂上的陳年幹草垛尋去。後來她就悄無聲息地仰臥在那垛幹草上,將披掛下來的蓬亂頭發噙在嘴裡,眸子痛楚得燒成兩盞小太陽。那是熏風麗日的十月。陳文治第一次目睹了女人的分娩。蔣氏幹瘦發黑的胴體在誕生生命的前後變得豐碩美麗,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菊花盡情燃燒。
父親墜入幹草的剎那間血光衝天,彌漫了楓楊樹鄉村的秋天。他的強勁奔波的啼哭聲震落了陳文治手中的望遠鏡,黑磚樓上隨之出現一陣騷動。望遠鏡的玻璃鏡片碎裂後,陳文治漸漸軟癱在樓頂,他的神情衰弱而絕望,下人趕來扶擁他時發現那白錦緞褲子亮晶晶地濕了一片。
我意識到陳文治這人物是一個古怪的人精不斷地攀在我的家族史的莖莖葉葉上。楓楊樹半村姓陳,陳家族譜記載了我家和陳文治的微薄的血緣關係。陳文治和陳寶年的父親是五代上的叔伯兄弟還是六代上的叔侄關係並非重要,重要的是陳文治家十九世紀便以富庶聞名方圓多裡,而我家世代居於茅屋下面饑寒交迫。祖父陳寶年曾經把他妹妹鳳子跟陳文治換了十畝水田。我想楓楊樹本土的人倫就是這樣經世代滄桑浸蝕幾經沉浮的。那個鳳子仿佛一片美麗絕倫的葉子掉下我們家枝繁葉茂的老樹,化成淤泥。據說那是我祖上最漂亮的女人,她給陳文治家當了兩年小妾,生下三名男嬰,先後被陳文治家埋在竹園裡。有人見過那三名被活埋的男嬰,他們長相又可愛又畸形,頭顱異常柔軟,毛發金黃濃密卻都不會哭。消息走漏後整個楓楊樹鄉村震驚了多日。他們聽見鳳子在陳家竹園裡時斷時續地哀哭,後來她便開始發瘋地搖撼每一棵竹子,借深夜的月光破壞蒼茫一片的陳家竹園。那時候陳寶年十七歲還沒娶親,他站在竹園外的石磨上凍得瑟瑟發抖,他一直拼命跺著腳朝他妹妹叫喊鳳子你別毀竹子你千萬別毀陳家的竹子。他不敢跑到鳳子跟前去攔,只是站在石磨上忍著春寒喊鳳子親妹妹別毀竹子啦哥哥是豬是狗良心掉到尿泡裡了你不要再毀竹子呀。他們兄妹倆的奇怪對峙以鳳子暴死結束。鳳子搖著竹子慢慢地就倒在竹園裡了,死得蹊蹺。記得她遺容是醬紫色的,像一瓣落葉夾在我家史冊中令人惦念。五十多年前楓楊樹鄉親曾經想跟著陳寶年把鳳子棺木抬入陳文治家,陳寶年只是把臉埋在白幔裡無休止地嗚咽,他說,“用不著了,我知道她活不過今年,怎麼死也是死。我給她卜卦了。不怨陳文治,也不怪我,鳳子就是死裡無生的命。”五十多年後我把姑祖母鳳子作為家史中一點紫色光斑來捕捉,鳳子就是一只美麗的螢火蟲匆匆飛過我面前,我又怎能捕捉到她的紫色光亮呢?鳳子的特殊生育區別於祖母蔣氏,我想起那三個葬身在竹園下面的畸形男嬰,想起我學過的遺傳和生育理論,有一種設想和猜疑使我目光呆滯,無法深入探究我的家史。
我需要陳文治的再次浮出。
楓楊樹老家的陳氏大家族中唯有陳文治家是財主,也只有陳文治家祖孫數代性格怪異,各有奇癖,他們的壽數幾乎雷同,只活得到四十坎上。楓楊樹人認為陳文治和他的先輩早夭是耽於酒色的報應。他們幾乎壟斷了近兩百年楓楊樹鄉村的美女。那些女人進入陳家黑幽幽的五層深院仿佛美麗的野虻子悲傷而絕情地叮在陳文治們的身上。她們吸吮了其陰鬱而霉爛的精血後也失卻了往日的芳顏,後來她們擠在後院的柴房裡劈拌子或者燒飯,臉上永久地貼上陳文治家小妾的標志:一顆黑紅色的梅花痣。
間或有一個刺梅花痣的女人被趕出陳家,在馬橋鎮一帶流浪,她會發出那種蒼涼的笑容勾引鎮上的手工藝人。而鎮上人見到刺梅花痣的女人便會朝她圍過來,問及陳家人近來的生死,問及一只神秘的白玉瓷罐。
我需要給你們描述陳文治家的白玉瓷罐。
我沒有也不可能見到那只白玉瓷罐。但我現在看見一九三四年的陳文治家了看見客廳長案上放著那只白玉瓷罐。瓷罐裡裝著楓楊樹人所關心的絕藥。老家的地方野史《滄海志史》對絕藥作了如下記載: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