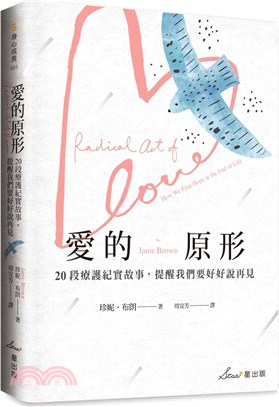愛的原形:20段療護紀實故事,提醒我們要好好說再見
商品資訊
系列名:身心成長
ISBN13:9789869884273
替代書名:Radical Acts of Love: How We Find Hope at the End of Life
出版社:星出版
作者:珍妮・布朗Janie Brown
譯者:周宜芳
出版日:2020/12/09
裝訂/頁數:平裝/304頁
規格:20cm*14cm*1.8cm (高/寬/厚)
重量:383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在生命的最後,無論再愛再恨
為了不留遺憾,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
30年腫瘤科護理與諮商經驗,20段真實人生故事
生之終點,看見愛的原形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現在?還剩多久?」
「我還沒有真正活過就要死了。死亡嚇不倒我,但是一場虛度的人生讓我害怕。」
「我剩下的時間很珍貴,我不想被困在醫院裡,看著所剩無幾的日子流逝。」
「爸爸,你對我的身體虐待和性虐待,讓我賠上了人生。得到癌症的人是我,我快要死了,這似乎不公平。得癌症的人應該是你。」
「媽媽,妳怎麼可以放任他對我做這種事?妳和他一樣該罵。妳應該覺得丟臉,妳有更多理由保護妳的孩子。」
如何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時候,向他們告別?
每個做父母的人,對孩子的死亡都有獨特的敘事。對於任何痛到極致的失喪者,絕對不能自以為知道他們理解的真相是什麼。
「我準備好了。我沒有了結的事已經完成,至少在此生已經足夠。我的靈魂已經準備好展開下一段旅程。」
本書作者珍妮・布朗是執業三十年的腫瘤科護理師、癌末病人的諮商師,在本書記述二十場她與面臨死神之人的對話,其中有些與她有著深厚的個人情誼。死神找的並非白首,每場對話都揭示關於死亡的一種觀點和經歷,同時探索死亡的普世性。
布朗不但對生命臨終時刻提出極為敏銳而有智慧的洞見,也提出實用的方法,把面對死亡的無助轉化成希望,從恐懼到接受,從感覺隔絕和孤單,到成為生命有限這部人類集體巨作的一個篇章。
生之終點,每個人都要去。如何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面對臨終,如何不留遺憾地告別先行者,有意義地活過此生,有勇氣、優雅地面對光的盡頭,本書能夠提供一些省思與答案。
為了不留遺憾,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
30年腫瘤科護理與諮商經驗,20段真實人生故事
生之終點,看見愛的原形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現在?還剩多久?」
「我還沒有真正活過就要死了。死亡嚇不倒我,但是一場虛度的人生讓我害怕。」
「我剩下的時間很珍貴,我不想被困在醫院裡,看著所剩無幾的日子流逝。」
「爸爸,你對我的身體虐待和性虐待,讓我賠上了人生。得到癌症的人是我,我快要死了,這似乎不公平。得癌症的人應該是你。」
「媽媽,妳怎麼可以放任他對我做這種事?妳和他一樣該罵。妳應該覺得丟臉,妳有更多理由保護妳的孩子。」
如何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時候,向他們告別?
每個做父母的人,對孩子的死亡都有獨特的敘事。對於任何痛到極致的失喪者,絕對不能自以為知道他們理解的真相是什麼。
「我準備好了。我沒有了結的事已經完成,至少在此生已經足夠。我的靈魂已經準備好展開下一段旅程。」
本書作者珍妮・布朗是執業三十年的腫瘤科護理師、癌末病人的諮商師,在本書記述二十場她與面臨死神之人的對話,其中有些與她有著深厚的個人情誼。死神找的並非白首,每場對話都揭示關於死亡的一種觀點和經歷,同時探索死亡的普世性。
布朗不但對生命臨終時刻提出極為敏銳而有智慧的洞見,也提出實用的方法,把面對死亡的無助轉化成希望,從恐懼到接受,從感覺隔絕和孤單,到成為生命有限這部人類集體巨作的一個篇章。
生之終點,每個人都要去。如何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面對臨終,如何不留遺憾地告別先行者,有意義地活過此生,有勇氣、優雅地面對光的盡頭,本書能夠提供一些省思與答案。
作者簡介
珍妮・布朗 Janie Brown
英格蘭埃普索姆(Epsom)出生,自4歲起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成長,1984年移民,在溫哥華的卑詩癌症中心(BC Cancer Agency)擔任護理師。擁有英國聖安德魯大學心理學碩士學位,以及卑詩大學護理學碩士。
布朗擁有三十年腫瘤科護理師與諮商師執業經驗,1995年成立總部在溫哥華的卡拉尼什協會(Callanish Society),這是一個為了癌症患者創立的非營利草根組織。
譯者簡介 周宜芳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金融人員、出版社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目前累積譯作三十餘種,包括《正向轉變》。
英格蘭埃普索姆(Epsom)出生,自4歲起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成長,1984年移民,在溫哥華的卑詩癌症中心(BC Cancer Agency)擔任護理師。擁有英國聖安德魯大學心理學碩士學位,以及卑詩大學護理學碩士。
布朗擁有三十年腫瘤科護理師與諮商師執業經驗,1995年成立總部在溫哥華的卡拉尼什協會(Callanish Society),這是一個為了癌症患者創立的非營利草根組織。
譯者簡介 周宜芳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金融人員、出版社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目前累積譯作三十餘種,包括《正向轉變》。
序
序言 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面對生之終點
我第一次親眼看著過世的人是我的祖母。當時我19歲,她81歲。在她人生的最後幾年,她與我們家人一起住在格拉斯哥郊區,棲身在與我們家四個孩子成長所在的砂岩老宅相連的一間小屋裡。祖母死於那個年代比較常見的食道癌,這是因為她是個老菸槍,加上喜歡每日小酌幾杯。我還記得,我跟著母親走進祖母明亮的白色臥房,我站在母親身後,目光越過她的肩頭,看著她為我祖母洗身,換掉髒汙的床單。我想幫母親照料祖母,但是卻僵在那裡,茫然不知所措,儘管我那時已經在醫院工作過兩個暑假。祖母是我的親人,不是病患。在當時,這點讓一切都變得很不一樣。
印象中,我並不害怕死亡,只不過房間裡那股不尋常的氣味,還有她經常咳嗽、很少說話這件事,讓我感到好奇。母親把事情都打理妥當,她看起來也毫無懼色,只是很忙。她自己也曾經是個護理師,想必這有助於她知道該做些什麼。在祖母的病榻前,沒有掏心挖肺的深情漫長對話,也沒有一長串有待完成的遺願。那裡有的,只是身為病人的我祖母,還有身為照顧者的我母親的臨終工作。
我在那時就了解到,死亡大部分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並不容易,但也不見得可怕;沒有創傷,也沒有過度醫療;既不浪漫,也不榮耀。死亡多半尋常平凡,也應付得來,可以坦然接受,但帶著深沉的悲傷。在那個年代,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在家過世,就像我的祖母一樣;那個時代,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天或幾週住進醫院或安寧病房還不常見。
今日,大部分60歲以下的人,都不曾見過有人在自己面前死亡,因此對死亡深感恐懼;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是摯愛的人逝世,都讓他們驚惶。他們沒有榜樣可以學習如何照顧臨終者,因此對自己照顧臨終者的能力也沒有信心。我希望,極力推動回復由產婆接生、掀起去醫療化生產風潮的嬰兒潮世代,也能在拿回臨終主導權上擔綱重要角色。本書是我的獻禮,讓我們所有人重新得到力量,能夠主動面對我們的生命與死亡,記起我們知道如何向世界告別,一如我們知道如何來到這個世界。我們也知道如何療癒,如何在死亡來臨之前,竭盡全力安頓生命。我認為,這是我們可以給予摯愛的人最好的禮物: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到了,做好準備,開放心胸,接納這個時刻。
***
1993年,我受到比爾・莫爾斯(Bill Moyers)製作的《療癒與心靈》(Healing and the Mind)系列電視節目的啟發。第六集描繪的是由麥可・勒納(Michael Lerner)、瑞秋・娜歐米・雷門(Rachel Naomi Remen)為加州波里納斯(Bolinas)的癌友所舉行長達一週的避靜會(retreat)。隔天,我就打電話給他們的組織「康衛」(Commonweal),詢問我如何才能得到更多與他們避靜會相關的資訊。他們剛好要在兩個月後舉辦第一場工作坊,教導醫護專業人士如何籌備癌友避靜會課程,於是我報了名。
參加過康衛的工作坊之後,我召集了有興趣舉辦癌友避靜會的醫護專業人員,組成一支團隊;就這樣,卡拉尼什協會(Callanish Society)隔年在溫哥華誕生了。在我寫作本篇序文之時,卡拉尼什已經舉辦過將近百場為期一週的避靜會,它蓬勃發展,成為抗癌家庭的中心,幫助他們堅強面對生命,而對有些家庭來說,則是讓他們有力量面對死亡。這個園地是獻給因癌症而遭受不可逆之轉變的人們,提供他們避靜會和課程,重新接通人生的重要層面。我們致力於幫助人們開口與關係親近的人談論瀕死,化解過去的傷害和創痛,幫助他們做好準備,以平靜的心態接納、步入死亡。
我希望本書能讓讀者更理解臨終的過程,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是所愛的人的死亡。就像我們為了迎接新生命而細心準備,我們也能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為迎接死亡做準備,讓我們面對這個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定數時,都能從中得到一些自在和安慰。我願本書能夠幫助想要竭盡所能去生活、去愛的家庭,在從得知預後不樂觀到死亡那一刻的期間,激發希望。
在本書出現的家庭,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的經驗無法以普世的方式描述。我知道,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自己對死亡與臨終的經驗與本書所呈現的不符,對此我感到遺憾。
這些故事人物可辨識身分的特質都經過更改,或是綜合好幾個人而寫成,藉此保護隱私。書中的故事都交給在世的家人閱讀過,以求準確,並且徵詢意見。這些溝通感人至深,讓我確信愛必然常存。
本書分成四部,每一部都收錄四到七個故事,闡釋各種經驗,包括接納死亡、為死亡做準備、療癒過去、處理未完成的事、接受沒有解答的事、按照自身條件選擇臨終方式,還有學習如何從自然及死亡的普世性得到安慰。
我的克里族(Cree)朋友莫琳・甘迺迪(Maureen Kennedy)曾告訴我,在他們的傳統裡,長者會從多年的人生經驗蒐集「教誨故事」。
她說:「會有那麼一個時候,長者必須告訴世界這些故事。珍妮,當妳的時候到了,妳會知道。妳現在已經有許多教誨故事了,不是嗎?」
「至少有三十年,」我點頭答覆。
我相信,現在就是公開這些故事的時候。
為死亡做準備,是愛的根本功課,為我們自己,也為那些在我們走後活在這個世上、與我們親近的人。我希望,這些故事能為我們人生中最重要、但最少討論的經驗提供一張路線圖,讓身為讀者的你安心。願這些別人餽贈我的教誨故事,能夠療癒、滋養、強化你的心,打開生與死所蘊藏的美──這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利。
我第一次親眼看著過世的人是我的祖母。當時我19歲,她81歲。在她人生的最後幾年,她與我們家人一起住在格拉斯哥郊區,棲身在與我們家四個孩子成長所在的砂岩老宅相連的一間小屋裡。祖母死於那個年代比較常見的食道癌,這是因為她是個老菸槍,加上喜歡每日小酌幾杯。我還記得,我跟著母親走進祖母明亮的白色臥房,我站在母親身後,目光越過她的肩頭,看著她為我祖母洗身,換掉髒汙的床單。我想幫母親照料祖母,但是卻僵在那裡,茫然不知所措,儘管我那時已經在醫院工作過兩個暑假。祖母是我的親人,不是病患。在當時,這點讓一切都變得很不一樣。
印象中,我並不害怕死亡,只不過房間裡那股不尋常的氣味,還有她經常咳嗽、很少說話這件事,讓我感到好奇。母親把事情都打理妥當,她看起來也毫無懼色,只是很忙。她自己也曾經是個護理師,想必這有助於她知道該做些什麼。在祖母的病榻前,沒有掏心挖肺的深情漫長對話,也沒有一長串有待完成的遺願。那裡有的,只是身為病人的我祖母,還有身為照顧者的我母親的臨終工作。
我在那時就了解到,死亡大部分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並不容易,但也不見得可怕;沒有創傷,也沒有過度醫療;既不浪漫,也不榮耀。死亡多半尋常平凡,也應付得來,可以坦然接受,但帶著深沉的悲傷。在那個年代,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在家過世,就像我的祖母一樣;那個時代,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天或幾週住進醫院或安寧病房還不常見。
今日,大部分60歲以下的人,都不曾見過有人在自己面前死亡,因此對死亡深感恐懼;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是摯愛的人逝世,都讓他們驚惶。他們沒有榜樣可以學習如何照顧臨終者,因此對自己照顧臨終者的能力也沒有信心。我希望,極力推動回復由產婆接生、掀起去醫療化生產風潮的嬰兒潮世代,也能在拿回臨終主導權上擔綱重要角色。本書是我的獻禮,讓我們所有人重新得到力量,能夠主動面對我們的生命與死亡,記起我們知道如何向世界告別,一如我們知道如何來到這個世界。我們也知道如何療癒,如何在死亡來臨之前,竭盡全力安頓生命。我認為,這是我們可以給予摯愛的人最好的禮物: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到了,做好準備,開放心胸,接納這個時刻。
***
1993年,我受到比爾・莫爾斯(Bill Moyers)製作的《療癒與心靈》(Healing and the Mind)系列電視節目的啟發。第六集描繪的是由麥可・勒納(Michael Lerner)、瑞秋・娜歐米・雷門(Rachel Naomi Remen)為加州波里納斯(Bolinas)的癌友所舉行長達一週的避靜會(retreat)。隔天,我就打電話給他們的組織「康衛」(Commonweal),詢問我如何才能得到更多與他們避靜會相關的資訊。他們剛好要在兩個月後舉辦第一場工作坊,教導醫護專業人士如何籌備癌友避靜會課程,於是我報了名。
參加過康衛的工作坊之後,我召集了有興趣舉辦癌友避靜會的醫護專業人員,組成一支團隊;就這樣,卡拉尼什協會(Callanish Society)隔年在溫哥華誕生了。在我寫作本篇序文之時,卡拉尼什已經舉辦過將近百場為期一週的避靜會,它蓬勃發展,成為抗癌家庭的中心,幫助他們堅強面對生命,而對有些家庭來說,則是讓他們有力量面對死亡。這個園地是獻給因癌症而遭受不可逆之轉變的人們,提供他們避靜會和課程,重新接通人生的重要層面。我們致力於幫助人們開口與關係親近的人談論瀕死,化解過去的傷害和創痛,幫助他們做好準備,以平靜的心態接納、步入死亡。
我希望本書能讓讀者更理解臨終的過程,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是所愛的人的死亡。就像我們為了迎接新生命而細心準備,我們也能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為迎接死亡做準備,讓我們面對這個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定數時,都能從中得到一些自在和安慰。我願本書能夠幫助想要竭盡所能去生活、去愛的家庭,在從得知預後不樂觀到死亡那一刻的期間,激發希望。
在本書出現的家庭,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的經驗無法以普世的方式描述。我知道,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自己對死亡與臨終的經驗與本書所呈現的不符,對此我感到遺憾。
這些故事人物可辨識身分的特質都經過更改,或是綜合好幾個人而寫成,藉此保護隱私。書中的故事都交給在世的家人閱讀過,以求準確,並且徵詢意見。這些溝通感人至深,讓我確信愛必然常存。
本書分成四部,每一部都收錄四到七個故事,闡釋各種經驗,包括接納死亡、為死亡做準備、療癒過去、處理未完成的事、接受沒有解答的事、按照自身條件選擇臨終方式,還有學習如何從自然及死亡的普世性得到安慰。
我的克里族(Cree)朋友莫琳・甘迺迪(Maureen Kennedy)曾告訴我,在他們的傳統裡,長者會從多年的人生經驗蒐集「教誨故事」。
她說:「會有那麼一個時候,長者必須告訴世界這些故事。珍妮,當妳的時候到了,妳會知道。妳現在已經有許多教誨故事了,不是嗎?」
「至少有三十年,」我點頭答覆。
我相信,現在就是公開這些故事的時候。
為死亡做準備,是愛的根本功課,為我們自己,也為那些在我們走後活在這個世上、與我們親近的人。我希望,這些故事能為我們人生中最重要、但最少討論的經驗提供一張路線圖,讓身為讀者的你安心。願這些別人餽贈我的教誨故事,能夠療癒、滋養、強化你的心,打開生與死所蘊藏的美──這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利。
目次
目錄
序言 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面對生之終點
第一部 對死亡敞開心扉
1 凱倫:金色的愛
2 丹尼爾:記憶寶盒
3 瑞秋:虎鯨群
4 約翰:恐懼消失
5 丹恩:為自己訂做臨終
第二部 接受沒有解答的心事
6 布麗琪:最佳計畫
7 吉姆:絕口不談死亡
8 派翠西雅:決定
9 喬治:違抗死神
第三部 療癒苦悶之心
10 貝拉:救贖靈魂
11 安娜莉絲:放手
12 克絲汀:為生命目標而寫
13 露易絲:原諒的可能
第四部 寄託於寬闊之心
14 菲力浦:萬事萬物各得其所
15 羅納多與馬可:培養無量之心
16 海瑟:跳進太平洋
17 比爾:十三週
18 珍:驚嘆
19 凱特:舞蹈
20 麗茲:椎心的美
謝辭
序言 以開放而清醒的態度,面對生之終點
第一部 對死亡敞開心扉
1 凱倫:金色的愛
2 丹尼爾:記憶寶盒
3 瑞秋:虎鯨群
4 約翰:恐懼消失
5 丹恩:為自己訂做臨終
第二部 接受沒有解答的心事
6 布麗琪:最佳計畫
7 吉姆:絕口不談死亡
8 派翠西雅:決定
9 喬治:違抗死神
第三部 療癒苦悶之心
10 貝拉:救贖靈魂
11 安娜莉絲:放手
12 克絲汀:為生命目標而寫
13 露易絲:原諒的可能
第四部 寄託於寬闊之心
14 菲力浦:萬事萬物各得其所
15 羅納多與馬可:培養無量之心
16 海瑟:跳進太平洋
17 比爾:十三週
18 珍:驚嘆
19 凱特:舞蹈
20 麗茲:椎心的美
謝辭
書摘/試閱
7 吉姆:絕口不談死亡
我的電話有一通來自秀娜・麥肯齊的留言,她的蘇格蘭腔重到我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聽到格拉斯哥方言,總能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我回電給秀娜,她告訴我,她是從她先生的居家護理師那裡得知我的名字的。
「那位護理師認為,妳或許能讓我先生明理一點,」她說。
「怎麼回事?」我問。
「他還想再去高爾夫球場,但他這是拿自己開玩笑!以他現在病重的程度,他根本不可能再打高爾夫球,」秀娜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但是他不願意談。」
「吉姆知道妳打電話聯絡我嗎?」
「我還沒告訴他。他不是會去諮商的人。」
「蘇格蘭有人會去諮商嗎?」我笑了。
「小姐,妳說得對。要解決情緒問題,一大杯啤酒比較有用啦,」秀娜說。
「告訴吉姆,妳請我過去喝杯茶,我來自老鄉,」我說。「這樣他可能會讓我進門。」
***
每當我開車前往北溫哥華,在快到上獅門大橋(Lions Gate Bridge)的堤道之前,我會右轉,這樣就可以繞一段長路,穿過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這條環繞公園的道路一側,有高大的花旗松和美西紅側柏林立,這些樹對我有一股莫名的穩定力量。某次,我問一位原住民朋友關於大樹的事,由於它們的根系相當淺,必然蘊藏了豐沛的能量,或是生命力,才能頂得住狂風和暴雪。
「真可惜,我們不能汲取大樹的能量為我們所用,或是給需要力量的人,」我對我的朋友貝芙說道。
「當然可以,」她輕快回答。
「怎麼做?」我問。
「只要開口請求它們賜下一些能量,然後謝謝它們,這樣就好啦!它們從來都不會說不,」她笑了。
那一天,我又環繞著公園開車,樹在我的左側,春天的陽光照亮了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的白色風帆,反射在構成城市天際線的摩天高樓。我可以看到布勒內灣(Burrard Inlet)對岸亮黃色的硫磺堆,還有北岸山脈(North Shore Mountains)頂上最後一小塊殘雪。
我在一棟棲身於山腳下的白色立面平房外停了下來。房子後方也有花旗松和側柏,而在這幾分鐘之前,我坐在車裡,閉上眼睛,請求它們給我力量,並且確定我有大聲說:「謝謝你們!」
我走在通往房子的小路上,敲了敲那扇歷經風吹雨打的前門。秀娜的樣子,正如我在電話裡憑著她的聲音所想像的那樣:七十出頭,燙過的礫灰色頭髮,長度剛好在她藍色棉襯杉領子的上方。她的脖子掛了一條十字架金墜項鍊,墜子塞進上衣裡。她下身穿著聚酯纖維布料的寛腳褲,腰際繫著一條海軍藍腰帶,腳上是露趾涼鞋,不過她穿了襪子。
「謝謝妳來。」我伸出手,和她握手。她的手冰涼帶點濕黏,我想或許她也覺得緊張。第一次和一家人見面,通常會讓我緊張,而迅速建立融洽的關係,是能夠幫得上忙的重要條件。在這樣敏感的時刻走進一個家庭的住家,感覺是一種特權,一種你經常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得到的特權。
「我直接帶妳去見吉姆,但他今天身體不大舒服,」秀娜悄聲說道。「他大半個晚上都在流汗,醒著沒睡。他過去這幾天沒吃什麼東西,醫生晚點會來看他。」
秀娜領我走進小小的卧室,一張病床緊挨著一張雙人床擺著。每個能放東西的平面,都放滿了小飾物:迷你瓷器小狗和塑膠芭蕾女伶,發條音樂盒和布滿灰塵的耶穌誕生像。牆上掛滿了蘇格蘭歷史名勝的裝框黑白照片。拉上的窗簾,把像是想從帘間空隙偷溜進來的陽光擋在窗外。吉姆靠著幾顆枕頭支撐,他穿著一套藍色條紋睡衣,上衣一直釦到衣領。他的頭髮潮濕,整齊地梳到一邊。在他熬過辛苦的一夜之後,秀娜可能已在會客之前幫他梳洗一下。
「吉姆,這是珍妮,我和你提過要來喝杯茶的那位護理師,」她說。
「午安,」吉姆說。「抱歉在這裡見妳,我昨晚過得很糟。再等一下,我就可以準備好起身。」秀娜偷偷看了我一眼,揚了揚眉。
「很高興見到你,」我說。「我會一直在這裡等你準備好。」
「準備好做什麼?」他問道,粗長的深色眉毛揚起了一個問號。
「秀娜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見你,看我能不能幫忙,」我說。
「幫什麼?如果妳是心理醫生的話,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出門到高爾夫球場上打幾球。」
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那一定是秀娜為我放在那裡的。她坐在床尾的凳子上,膝蓋交疊翹著腿,一隻拖鞋掛在腳尖上下焦急地晃著。秀娜心裡自有盤算。
「吉姆,親愛的,好心點!珍妮是護理師,而且她來自格拉斯哥,」秀娜說,拍拍他在被子下的腳。
「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對妳有意見,」吉姆說。「那不能怪妳。」他眨了眨眼。
「我爸是在艾爾郡(Ayr)出生、成長的。這有加分嗎?」我問。
「那裡靠近拉格斯(Largs),那是我們兩個來的地方。妳父親打高爾夫球嗎?」
我知道高爾夫球能讓我加分。「他打,在巔峰時期,他的差點可以到9桿。至於我媽,她住在格拉斯哥,一直到86歲,都還在打高爾夫球。我爸過世快二十年了。」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問他的死因是什麼嗎?」吉姆說。
「腦瘤。而且一診斷就是四期,晴天霹靂。」
「我的肺癌也是四期,而且我聽說沒有第五期。」他看著我,一邊揮舞著雙拳和空氣打拳擊。「不過,我是個鬥士,所以它還要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讓我出場。」
我注意到吉姆的指甲泛青,胸口隨著每一次呼吸艱難地起伏。我在想,不知道多久之後他會需要氧氣筒。
秀娜不動聲色地把心中盤算帶入對話。
「吉姆,醫生上週可不是這麼說的。她說,她不能再讓你接受化療,她很抱歉。」
「親愛的,給珍妮端杯茶來。她才不想聽妳說這麼負面的話,」吉姆揮揮他已經瘦到只剩骨頭的手腕,打發她走。
秀娜一進廚房,吉姆便開始說話。
「我擔心她。如果我死了,她怎麼辦?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孩子們都忙,沒辦法來探望她。家裡和錢有關的事,都是我在打理的,那方面沒問題,」吉姆說。
我趕緊把握機會表示:「這對她不好受,一定的。不過,你沒辦法讓她不傷心,她可能也比你想的還要堅強。」
「她以為我不知道自己病得多重,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覺得,不要談這件事比較好,這會讓她慌張失措。」他抬起手,爬梳著他的頭髮,一路到後頸停住。「她慌張失措,我就無法保持鎮定。」
「如果你可以談談這件事,或許對她會有幫助,」我說。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他說。他看起來像是一個依靠自己身體和精神力量的男人,但是隨著他的元氣衰退,供養和保護妻子的能力降低,他不確定要如何調適,才能面對自己愈來愈需要依賴他人的情況,還有隨之而來潛藏在內心的感受。
「來了!」秀娜的聲音傳來,她端著托盤,上面擺著茶杯和碟子、糖罐和奶罐,一具經典款布朗貝蒂壺(Brown Betty),裹在編織的茶壺套裡,還有一盤巧克力消化餅。她把托盤放在床上,那是房裡唯一清空的平面。
「珍妮,妳的茶要加什麼?」
「只要牛奶就好,謝謝。」
她先把牛奶倒進杯子,然後注入冒著熱氣的茶,加到滿。
「吉姆,你想要喝一點嗎?」她問道。
「親愛的,不用了,謝謝。我已經熱得發燙。」
「我不在時,你們兩個說了什麼?」秀娜問道。吉姆望著我,挑起眉毛。
「我們在聊天氣。春天是這麼溫和,」他說。
我啜了口茶。「趁我還在這裡時,你們兩人有沒有什麼想要和我談的,或是想要問我的呢?」
他們相互對望,等著看對方要不要回答。
秀娜再次試了一下。「吉姆,我想要和珍妮談談,你的病情加重之後,會是什麼情況?」
「那有什麼好談的?」他問道,擺好防衛架勢。
「你想住到安寧病房,或是待在這裡?」她問。
「我到底要和妳說多少次?在我雙腿一蹬之前,我還打算再打一兩場高爾夫。這件事,我們改天再談,」吉姆說道,雙眉之間的皺紋更深了。「珍妮,妳是從格拉斯哥的哪裡來的?」
我的電話有一通來自秀娜・麥肯齊的留言,她的蘇格蘭腔重到我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聽到格拉斯哥方言,總能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我回電給秀娜,她告訴我,她是從她先生的居家護理師那裡得知我的名字的。
「那位護理師認為,妳或許能讓我先生明理一點,」她說。
「怎麼回事?」我問。
「他還想再去高爾夫球場,但他這是拿自己開玩笑!以他現在病重的程度,他根本不可能再打高爾夫球,」秀娜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但是他不願意談。」
「吉姆知道妳打電話聯絡我嗎?」
「我還沒告訴他。他不是會去諮商的人。」
「蘇格蘭有人會去諮商嗎?」我笑了。
「小姐,妳說得對。要解決情緒問題,一大杯啤酒比較有用啦,」秀娜說。
「告訴吉姆,妳請我過去喝杯茶,我來自老鄉,」我說。「這樣他可能會讓我進門。」
***
每當我開車前往北溫哥華,在快到上獅門大橋(Lions Gate Bridge)的堤道之前,我會右轉,這樣就可以繞一段長路,穿過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這條環繞公園的道路一側,有高大的花旗松和美西紅側柏林立,這些樹對我有一股莫名的穩定力量。某次,我問一位原住民朋友關於大樹的事,由於它們的根系相當淺,必然蘊藏了豐沛的能量,或是生命力,才能頂得住狂風和暴雪。
「真可惜,我們不能汲取大樹的能量為我們所用,或是給需要力量的人,」我對我的朋友貝芙說道。
「當然可以,」她輕快回答。
「怎麼做?」我問。
「只要開口請求它們賜下一些能量,然後謝謝它們,這樣就好啦!它們從來都不會說不,」她笑了。
那一天,我又環繞著公園開車,樹在我的左側,春天的陽光照亮了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的白色風帆,反射在構成城市天際線的摩天高樓。我可以看到布勒內灣(Burrard Inlet)對岸亮黃色的硫磺堆,還有北岸山脈(North Shore Mountains)頂上最後一小塊殘雪。
我在一棟棲身於山腳下的白色立面平房外停了下來。房子後方也有花旗松和側柏,而在這幾分鐘之前,我坐在車裡,閉上眼睛,請求它們給我力量,並且確定我有大聲說:「謝謝你們!」
我走在通往房子的小路上,敲了敲那扇歷經風吹雨打的前門。秀娜的樣子,正如我在電話裡憑著她的聲音所想像的那樣:七十出頭,燙過的礫灰色頭髮,長度剛好在她藍色棉襯杉領子的上方。她的脖子掛了一條十字架金墜項鍊,墜子塞進上衣裡。她下身穿著聚酯纖維布料的寛腳褲,腰際繫著一條海軍藍腰帶,腳上是露趾涼鞋,不過她穿了襪子。
「謝謝妳來。」我伸出手,和她握手。她的手冰涼帶點濕黏,我想或許她也覺得緊張。第一次和一家人見面,通常會讓我緊張,而迅速建立融洽的關係,是能夠幫得上忙的重要條件。在這樣敏感的時刻走進一個家庭的住家,感覺是一種特權,一種你經常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得到的特權。
「我直接帶妳去見吉姆,但他今天身體不大舒服,」秀娜悄聲說道。「他大半個晚上都在流汗,醒著沒睡。他過去這幾天沒吃什麼東西,醫生晚點會來看他。」
秀娜領我走進小小的卧室,一張病床緊挨著一張雙人床擺著。每個能放東西的平面,都放滿了小飾物:迷你瓷器小狗和塑膠芭蕾女伶,發條音樂盒和布滿灰塵的耶穌誕生像。牆上掛滿了蘇格蘭歷史名勝的裝框黑白照片。拉上的窗簾,把像是想從帘間空隙偷溜進來的陽光擋在窗外。吉姆靠著幾顆枕頭支撐,他穿著一套藍色條紋睡衣,上衣一直釦到衣領。他的頭髮潮濕,整齊地梳到一邊。在他熬過辛苦的一夜之後,秀娜可能已在會客之前幫他梳洗一下。
「吉姆,這是珍妮,我和你提過要來喝杯茶的那位護理師,」她說。
「午安,」吉姆說。「抱歉在這裡見妳,我昨晚過得很糟。再等一下,我就可以準備好起身。」秀娜偷偷看了我一眼,揚了揚眉。
「很高興見到你,」我說。「我會一直在這裡等你準備好。」
「準備好做什麼?」他問道,粗長的深色眉毛揚起了一個問號。
「秀娜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見你,看我能不能幫忙,」我說。
「幫什麼?如果妳是心理醫生的話,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出門到高爾夫球場上打幾球。」
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那一定是秀娜為我放在那裡的。她坐在床尾的凳子上,膝蓋交疊翹著腿,一隻拖鞋掛在腳尖上下焦急地晃著。秀娜心裡自有盤算。
「吉姆,親愛的,好心點!珍妮是護理師,而且她來自格拉斯哥,」秀娜說,拍拍他在被子下的腳。
「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對妳有意見,」吉姆說。「那不能怪妳。」他眨了眨眼。
「我爸是在艾爾郡(Ayr)出生、成長的。這有加分嗎?」我問。
「那裡靠近拉格斯(Largs),那是我們兩個來的地方。妳父親打高爾夫球嗎?」
我知道高爾夫球能讓我加分。「他打,在巔峰時期,他的差點可以到9桿。至於我媽,她住在格拉斯哥,一直到86歲,都還在打高爾夫球。我爸過世快二十年了。」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問他的死因是什麼嗎?」吉姆說。
「腦瘤。而且一診斷就是四期,晴天霹靂。」
「我的肺癌也是四期,而且我聽說沒有第五期。」他看著我,一邊揮舞著雙拳和空氣打拳擊。「不過,我是個鬥士,所以它還要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讓我出場。」
我注意到吉姆的指甲泛青,胸口隨著每一次呼吸艱難地起伏。我在想,不知道多久之後他會需要氧氣筒。
秀娜不動聲色地把心中盤算帶入對話。
「吉姆,醫生上週可不是這麼說的。她說,她不能再讓你接受化療,她很抱歉。」
「親愛的,給珍妮端杯茶來。她才不想聽妳說這麼負面的話,」吉姆揮揮他已經瘦到只剩骨頭的手腕,打發她走。
秀娜一進廚房,吉姆便開始說話。
「我擔心她。如果我死了,她怎麼辦?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孩子們都忙,沒辦法來探望她。家裡和錢有關的事,都是我在打理的,那方面沒問題,」吉姆說。
我趕緊把握機會表示:「這對她不好受,一定的。不過,你沒辦法讓她不傷心,她可能也比你想的還要堅強。」
「她以為我不知道自己病得多重,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覺得,不要談這件事比較好,這會讓她慌張失措。」他抬起手,爬梳著他的頭髮,一路到後頸停住。「她慌張失措,我就無法保持鎮定。」
「如果你可以談談這件事,或許對她會有幫助,」我說。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他說。他看起來像是一個依靠自己身體和精神力量的男人,但是隨著他的元氣衰退,供養和保護妻子的能力降低,他不確定要如何調適,才能面對自己愈來愈需要依賴他人的情況,還有隨之而來潛藏在內心的感受。
「來了!」秀娜的聲音傳來,她端著托盤,上面擺著茶杯和碟子、糖罐和奶罐,一具經典款布朗貝蒂壺(Brown Betty),裹在編織的茶壺套裡,還有一盤巧克力消化餅。她把托盤放在床上,那是房裡唯一清空的平面。
「珍妮,妳的茶要加什麼?」
「只要牛奶就好,謝謝。」
她先把牛奶倒進杯子,然後注入冒著熱氣的茶,加到滿。
「吉姆,你想要喝一點嗎?」她問道。
「親愛的,不用了,謝謝。我已經熱得發燙。」
「我不在時,你們兩個說了什麼?」秀娜問道。吉姆望著我,挑起眉毛。
「我們在聊天氣。春天是這麼溫和,」他說。
我啜了口茶。「趁我還在這裡時,你們兩人有沒有什麼想要和我談的,或是想要問我的呢?」
他們相互對望,等著看對方要不要回答。
秀娜再次試了一下。「吉姆,我想要和珍妮談談,你的病情加重之後,會是什麼情況?」
「那有什麼好談的?」他問道,擺好防衛架勢。
「你想住到安寧病房,或是待在這裡?」她問。
「我到底要和妳說多少次?在我雙腿一蹬之前,我還打算再打一兩場高爾夫。這件事,我們改天再談,」吉姆說道,雙眉之間的皺紋更深了。「珍妮,妳是從格拉斯哥的哪裡來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