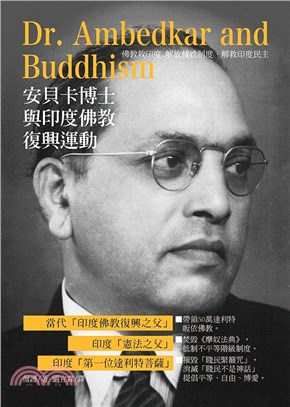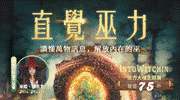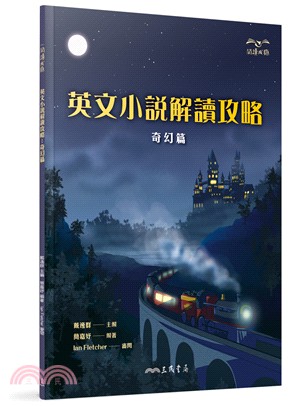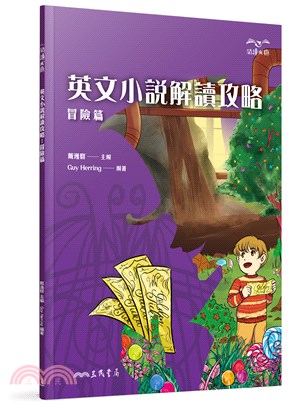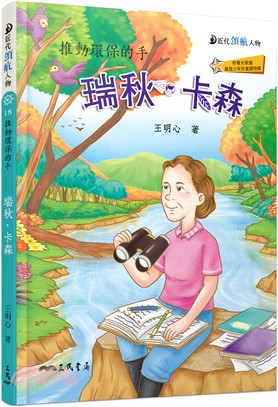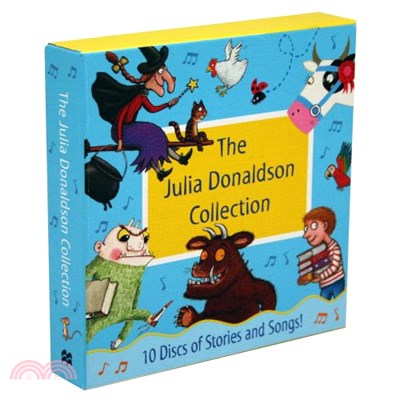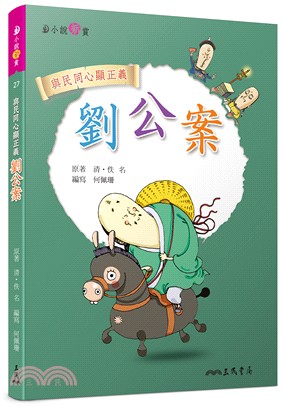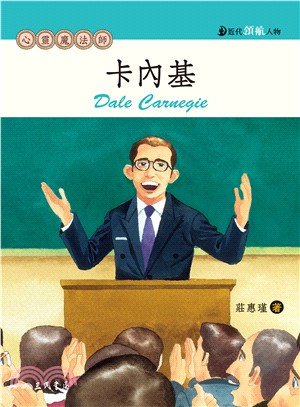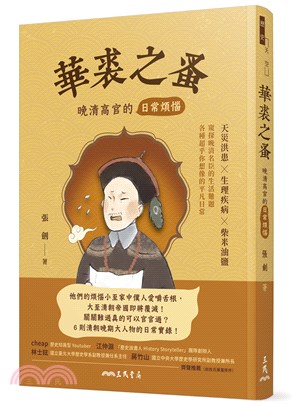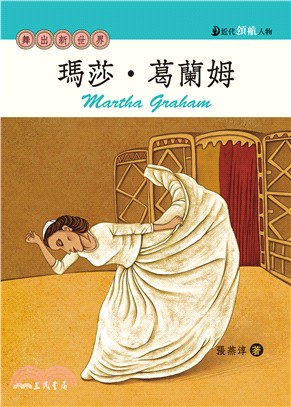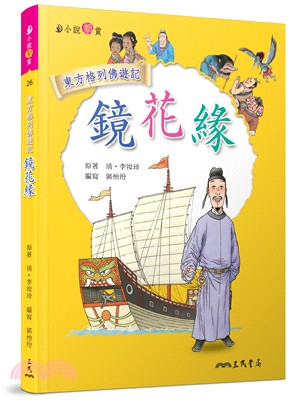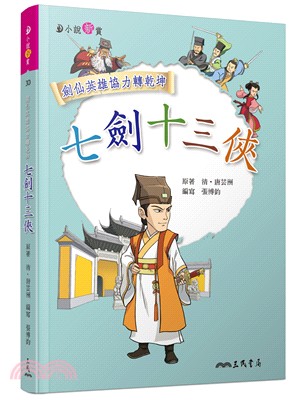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佛教救印度,解放種姓制度、解救印度民主
商品資訊
系列名:以聖為導
ISBN13:9789574473564
替代書名:Ambedkar and Buddhism
出版社:大千
作者:僧護
譯者:劉宜霖
出版日:2021/03/19
裝訂/頁數:平裝/288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重量:420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覺醒,永遠是不曾失去的擁有
讓佛陀再次拯救印度
印度佛教復興運動最輝煌的日子
「自由、平等、博愛」三個普世價值
再度喚起沉寂千百年的人心
佛教在印度沉寂了千百年,直到二十世紀賤民階級的安貝卡博士出現於世,除了帶領賤民同胞寫下革命血淚奮鬥史,最終還寫下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最輝煌一頁。
佛教在印度絕跡,是每個讀過印度史或印度佛教史者共有的結論,然而,那是因為對印度現代史的不熟悉。二十世紀的印度,出現一位安貝卡博士,因為有他擬定印度獨立建國的憲法法條,被尊稱為「憲法之父」,然而,他出身自印度種姓制度的最低賤階級──不可觸賤民。
安貝卡博士與其他賤民同胞無異,備受印度種姓制度荼毒與壓迫,幸運的是,他有受教育的特殊機緣,最終取得歐美名校的博士學位,並憑藉學識專業與魄力,為了帶領賤民同胞爭取基本人權,在印度政治與社會層面掀起賤民革命浪潮。他一邊爭取人權,一邊研究與追溯賤民階級的歷史源頭,赫然發現,原來「不可觸賤民」的起源竟與佛教有關!他們,因為堅持不改對佛教的忠誠,屢受印度教教徒迫害與汙衊,最終背此「賤民」之汙名與忍受非人道待遇,歷經千百年,久遠得忘了自己是誰……。
安貝卡博士發現了這層秘辛,對於擺脫印度教賤民階級的身分有了一線曙光,最終,為了讓這個階級能夠脫離種姓地獄,他以佛教慈悲為懷的精神,在一次次的呼籲與號召下,於1956年10月,他與五十萬賤民追隨者,圓滿受持佛教三皈五戒的心願。讓他們找到佛法「自由、平等、博愛」的三個普世價值,對他們來說,這不是單純的改宗易教,而是靈性的回歸,回到他們被汙衊為「賤民」之前,從此在印度佛教復興史上,寫下嶄新的起始頁…。
本書特色
透過作者僧護居士在他仍是比丘時,以回憶錄的方式介紹當時的印度時代背景,與安貝卡的從出生至死亡的每個重要經歷。當安貝卡以偵探小說的模式追溯不可觸賤民階級的起源,並發表於當時的媒體報導時,僧護也以類似手法,敘述安貝卡如何剝絲抽繭、找尋線索並扣緊線索,逐步挖掘出令人震撼的事實真相。
書中除了主人翁──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卡─的生平經歷外,還側面提及印度「國父」─聖雄甘地。他們二人之間究竟是敵?是友?有沒有上演什麼對手戲呢?
安貝卡在世的數十年,展開不可觸賤民階級在印度政治、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一:佛門不巧事業的締造者:安貝卡博士
1947年8月15日,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然而獨立後的印度,一直深陷於宗教與種姓兩大問題的泥沼中,雖然印度憲法給予所有宗教和種姓平等的權利,但事實上卻非如此,宗教與種姓一直是印度社會長期動亂不安的最重要原因。1950年代,蘇聯和中國分別向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 1891-1956)推銷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都為其拒絕。安貝卡博士在研究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基督教教義後,發現只有佛法可以拯救印度,所以他在1956年10月4日,率領50萬達利特(Dalits,不可觸階級,俗稱賤民)在龍城(Nagapur)集體皈依佛教,成為近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肇始與推動者。
安貝卡博士拒絕共產思想,使印度不被赤化,也使得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無法與印度形成聯合陣線,間接保障了東南亞各國的安全。率領50萬達利特集體皈依佛教,是佛教在1203年因伊斯蘭教入侵而滅亡後,首次露出復興的曙光,現在印度佛教因達利特皈依人口不斷的增加,這一切都要感謝安貝卡博士睿智的抉擇。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叔孫豹對范宣子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巧,是後人為前人一生定位的一種衡量標準。做為印度第一位印度司法部長、法律部長、憲法的首席起草人、首席大法官、達利特佛教運動者,同時也是印度法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社會改革家、作家,安貝卡博士留下四十冊的智慧結晶,是印度達利特最有價值的資產。率領50萬達利特集體皈依佛教,使得達利特擁有發身慧命,印度佛教復興之路因此展開。安貝卡博士一生的功業,確實達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巧的標準。
安貝卡博士在率領50萬達利特集體皈依佛教後六個星期卻與世長辭,值得安慰的是僧護居士(Sangharakshita,1825–2018),以及當代的世友居士(Mr. Lokamitra,1947– )等,都繼承安貝卡博士未完成的志業。僧護居士是一位承先啟後的長者,在1956年,當時身分還是比丘的僧護向安貝卡提出三皈五戒的重要,促成安貝卡正式皈依佛教。在安貝卡博士逝世後,繼續領導達利特皈依佛教,大量從事與這方面相關的書寫與教學,世友居士在印度的志業,也是受到僧護居士的號召與鼓勵。
僧護居士是本書的作者,也是最有資格為安貝卡博士復興佛教運動作見證者,本人福薄,無緣認識僧護居士。記得在2018年11月5日,玄奘大學邀請世友居士、劉宜霖小姐到校,參加「2019年印度學生台灣升學圓夢計畫座談會」,在這場座談會上,決定了印度龍樹學院每年安排一些學生到玄奘大學就讀的議案。在這場座談會舉辦前一星期,我們就接到了僧護居士在英國往生的消息,世友居士為參加恩師的後事,同時又參加玄奘大學的座談會,風塵僕僕的飛往西、東兩半球,可媲美古代高僧為法忘軀的情操。
本書譯者為新加坡籍的劉宜霖小姐,長期擔任印度龍樹學院與台灣交流的橋樑,擔任世友居士的譯者,榮獲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的她,也曾經翻譯了僧護居士的另一本著作:《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尊者傳記》,護法尊者(Anagārika Devamitta Dharmapāla, 1864-1933)是開啟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第一人。相信讀者在閱讀護法尊者、安貝卡博士的佛教志業後,對他們的志行節操將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許讀者對安貝卡博士為何帶領達利特集體皈依佛教,並要求達利特在皈依佛教之後宣誓22大願會感到好奇。個人期盼宜霖小姐可以再接再厲的翻譯安貝卡博士的最後一本著作:《佛陀和他的佛法》(The Buddha and His Dhamma),本書或許可以得到答案。
2021年1月30日
黃運喜教授
推薦序二:安貝卡博士復興印度佛教、解放種姓制度
安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 1891~1956)出身印度社會最底層,所謂「不可觸」的賤民階級,原本沒機會接受教育,然而他透過不懈的努力,並把握難得機緣,最終竟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博士學位。頂著歐美名校雙博士光環,安貝卡回到祖國,在大學與政府單位工作。然而,其「不可觸者」的身份標籤卻始終如影隨形地跟著他。更甚者,眼見無數所謂的「不可觸賤民」同胞,只因種姓出身,即一生備受壓迫凌辱、求脫無門,尤令他痛心不已!1935年,44歲的安貝卡在「被壓迫者研討會」上公開宣佈:「雖生為印度教徒,但絕不以印度教徒身份離世」,正式宣告與印度教傳統決裂。此後,安貝卡認真思考信仰改宗問題,確定「在印度教中,不可觸賤民絕無未來」,然而,不可觸賤民在哪一宗教才可能有光明未來,此一問題則尚待審慎研究評估。
1947年印度獨立,首任總理尼赫魯邀安貝卡入閣任司法部長,並負責草擬憲法。兩年後憲法草案通過,安貝卡廣受各界讚譽,被尊為「憲法之父」;新憲法則被譽為「現代版摩奴(法典)」。故印度獨立建國之根本大法實際出自一「賤民」之手,然而,這樣的事實卻依舊改變不了所謂「賤民」被壓迫的命運,他們依舊是備受歧視、汙穢不潔的「不可觸賤民」。是故,無論如何,只要在印度教中,賤民永遠不得翻身。然而,究竟當改宗何教?安貝卡博士在長期審慎考察評估後,最終認定─唯有佛教才是最理想、最平等的宗教。於是,改宗之日終於來臨,1956年10月14、15兩日,安貝卡博士率五十萬群眾,在龍城迪克沙布米集體皈依佛教,寫下皈依大典的輝煌紀錄,並開啟近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新頁。
本書作者僧護,1925年生於倫敦,十六歲那年讀完金剛經、六祖壇經,驚訝地發現自己曾是且一直都是佛弟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英軍赴印度,大戰結束後,繼續留在印度。1949年披剃出家,之後遍遊印度城邑村鎮,對印度社會、文化有第一手的觀察。與安貝卡博士有過三次會晤。安貝卡驟然離世後,僧護觀察到眾多新皈依弟子的茫然無措,遂義無反顧地投入佛法大義與修行方法的巡迴教學旅行中。新皈依弟子雖云皈依,實則對佛法泰半茫然無知,且絕大多數為文盲,故佛法之學習只能透過聽講進行。至1964年,因緣變化,僧護離印返英,仍惦記安貝卡博士之追隨者——新皈依佛弟子。1977年,僧護之英國弟子世友訪印,僧護囑其拜會老友及眾多弟子,之後進一步希望世友能駐留印度,以協助印度佛弟子。世友不負囑託,自1977年訪印後即駐守印度,迄今歷四十三寒暑,繼承安貝卡博士未竟之志、多有建樹,最主要之代表,厥為建立龍樹學院,使得印度中西部大城那格浦爾(即龍城)成為當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之重鎮。
安貝卡博士以不世出之才,在歐美名校取得博士學位,為個人計,他大可留在美國或英國發展,以追求其事業成就與幸福生活,並徹底擺脫「不可觸賤民」之卑汙印記,然而,他卻選擇回歸祖國,寧受賤民汙名也不改歸國初心,正是為了開展與冥頑習俗奮戰、與不公不義抗爭的一生事業,為解斯民於倒懸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安貝卡博士從出身賤民,到獲歐美名校博士之超高學歷,再到以「賤民」身分制訂建國新憲,最後到領導信仰改宗,使得佛教復興之勢沛然莫禦,其一生事蹟堪比可歌可泣、令人乍喜乍瞋之傳奇故事。然而,此傳奇故事在中文語境中竟付闕如,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所幸劉宜霖博士近日譯成僧護居士1980年代之著作——《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稍稍彌補了缺憾。此書涉及印度歷史、文化之專有名詞,想必翻譯不易,劉博士不畏艱難、不辭辛勞地完成此書翻譯,對中文讀者的幫助很大。劉博士為世友居士往來華人社區之專屬中文翻譯,獲有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學位,為了承擔世友居士之專屬翻譯義工,遂不能擔任任何專職工作,只能以兼職之導遊工作為生,以保持時間之機動性,其精神亦是受安貝卡博士之感召乎!
值本書出版前夕,茲虔誠祝禱:
願安貝卡博士之事蹟廣傳於世,以廉頑立懦,予見聞者無窮啟發;
願台灣及全世界佛弟子發心協助印度之佛教復興;
願安貝卡博士之遺願早日實現,印度「列表種姓」免於壓迫,佛教大興於印度。
是為序。
2020年8月15日
釋悟興
推薦序三:讓佛陀再次拯救印度
就在《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刊行於世之際,安貝卡博士的一生行誼,在印度以外的世界,仍舊知之甚少,更絲毫不知他皈依佛教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佛滅逾七百年之後,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因護法大士及摩訶菩提協會的努力不懈,佛陀教法才又曙光再現。然而,直至安貝卡博士皈依之後,佛教方能以活潑、正能量滿滿的宗教姿態,回到其發祥地—印度。安貝卡博士復興佛教之舉,確是改變了印度的宗教與社會風貌,自阿育王之後,無人能出其右。僧護居士撰寫此一傳記的意圖,是希望引起西方佛教界的關注,這對東方佛教界而言,亦是裨益良多。
這麼一部傳記,由僧護居士來執筆,可謂定位特殊。他生於美國、長於美國,於1944年隨英軍來到印度。在世界第二大戰結束之後,他選擇留在印度,以靈性追尋者之姿走遍印度,並於1949年披剃出家,接著,以佛教學術研究兼實踐者的身份聞名全印度。他雖然身在與社會脫節的英國統治飛地,卻在因緣際會之下,走遍印度各村各鎮,與普通民眾一起生活,實地了解何謂「不可觸性」,以及個中的種種殘酷現實,攢下極特殊的「印度經驗」。作為局外人,他比許多印度種姓體制創造的不可觸性族群,更能看清事實的真相。安貝卡博士和他雖然僅有三面之緣,卻曾(預言式地)提到:在他所有舊雨新知當中,唯有僧護(比丘)堪當荷擔起他一手發起的佛教運動。
安貝卡博士於1956年12月6日辭世,距離他發起的皈依大典僅六週。僧護比丘當時恰好蒞臨龍城,而龍城也正是皈依大典的所在地,兼具新佛教運動的臟腑地位。他生動地描述了追悼會上為十萬群眾開示的情景,並於接下來數日,走遍了所有新皈依佛弟子的社區。繼此之後,他每年都會在印度中部和西部停留數月,協助眾多新皈依佛弟子了解他們的宗教。在當時,印度諸比丘當中,他是唯一能夠洞察當時情勢的重大意義者,因此,對新皈依佛弟子施以援手之際,總是感覺心有戚戚焉。
僧護比丘於1964年返回英國,協助當地發動一輪嶄新的佛教運動。儘管如此,他仍然一心惦記著安貝卡博士的追隨者。
因此,當我1977年訪問印度時,他更不忘叮囑我,要盡最大可能抽時間拜會他的老朋友和眾多弟子。
我當時之行是為了學習瑜伽,因此大部分時間都在浦那。浦那是僧護比丘與新皈依佛弟子度過最長時間的地方。因此,我花費在教導佛法的時間,遠勝於我學習瑜伽的時間。
僧護比丘早在十三年前便離開此地,當地佛弟子因而可謂求法無門,對佛陀教法顯然求之若渴。僧護比丘思量再三,希望我能駐錫印度,與他們同舟共濟。
我能順利完成這項使命的部分原因,也緣於許多新皈依佛弟子對僧護比丘的激賞。一位皈依佛教的政治領導者,曾經雙眼含淚地對我說道:「他(僧護比丘)紆尊降貴來到我們的小村落,還與我們生活在擁擠的小屋,這是印度種姓都辦不到的事情,何況是一個外國人?」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和安貝卡博士二人,對佛法的見解多有雷同。譬如,他們都強調:「佛法關乎的,並非僅止於個人蛻變,更應該是整個世界的蛻變。」另外,他們之間更有著互為因果、難以切割的關係。他二人都強調了「皈依」的核心價值。事實上,僧護比丘表示,正是因為安貝卡博士攜五十萬追隨者皈依了佛教的壯舉,才激起他內心對「皈依」之重視。無論出家與否,其行為才是判定他是否為佛弟子的標準,居士一樣具有同等的能力與責任落實正法。
在過去四十年,僧護比丘為了照顧印度那些最弱勢者,他建立的三寶佛教會(Triratna Buddhist Community),相繼創辦了不少佛法教學的中心和社工項目。迄今最重要的中心,莫過於龍城的龍樹學院(Nagarjuna Training Institute)。因為受到安貝卡博士的啟發,我們創辦了這個住宿培訓中心,培訓來自全印度積極求法的年輕人,讓他們了解佛教如何協助個人蛻變,從而推己及人,乃至遍及整個社會。
僧護比丘在《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一書中,以綜合描述的方式,言簡意賅地介紹安貝卡博士的皈依大典。〈安貝卡的存在意義〉一文中,他回顧這位偉人的一生行誼,描述他如何從印度社會最低的不可觸階層力爭上游,成為印度憲法起草人,並以皈依佛教大典作結。
第一章,他追述自己與安貝卡博士的三次會晤,以安貝卡博士的告別式為句點,描述他在龍城追悼會上的經歷,及他與新皈依佛弟子之間,是什麼因緣建立起極為殊妙的關係。
〈種姓地獄〉一章,為「不可觸性」一詞追根究底,探尋背後的理論與殘酷的真相。這一章亦探討安貝卡博士自身在種姓制度下的切身體驗,說明何以他成了印度當時最高學歷者,卻依然擺脫不了種姓制度的迫害。
僧護比丘借助安貝卡的老師─克魯斯卡─贈予他的《佛陀傳》為引,一路回溯安貝卡博士邁向佛教的經過。整個過程清楚地揭示,安貝卡博士為了解決不可觸性的問題,逐漸往佛教邁進。1936年,更是他投奔佛教的轉捩點。再者,此章亦論及他與聖雄甘地之間的種種差異。
在〈漫漫尋根路〉這一章,僧護比丘透過研讀安貝卡博士的《誰是不可觸者》,告訴讀者:「不可觸者」,本是被迫住於村外的「殘族」。他們之所以是「殘族」,源自於他們是佛弟子的身份,及從牛屍身上取肉而食(他們並未殺害牛隻)的事實。這引發了佛教與印度教對「素食主義」饒富興味的辯論。
第六章〈思考佛教〉,主要討論安貝卡博士1950年於《摩訶菩提雜誌》發表的〈佛陀與其教法之未來〉一文。文章篇幅雖然不長,但是,此一著作卻是他至關重要、最為簡練的佛教相關著作。文章探討佛教與其他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之間的差異,並於結尾列出三個步驟,用以說明:佛教若想在當今世上順利發展,此三步驟不可或缺。
第七和第八章探討此書主題的兩個層面:即皈依大典本身,及堪稱其鉅著的《佛陀與其教法》。該書在他辭世隔年出版。最後一章〈安貝卡殞落後的歲月〉,主要回顧他往生至1964年,特別是僧護比丘駐錫印度那段期間所發生的一切。我認為這一章尚有待更新,因為,後續的許多發展,都具備格外重大意義。
安貝卡雖然1956年底辭世,但是,他發起的社會及政治工作,對那些備受壓迫的人群極具啟發性,參與者人數有增無減,甚至遍及全印度。而他的皈依大典亦是影響深遠,追隨他皈依佛教者成千上萬、前仆後繼,無形中竟成了佛教國家的靈感之源。佛教在東方雖然不至於衰落,但也已經停滯不前。然而,在西方,人們卻越來越關注佛教在社會層面所具的意義。《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是在1980年代中期撰寫的。當時,關注此一課題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如今情況卻已經大不相同。儘管如此,僧護居士對安貝卡博士學佛的過程,簡練卻完整的敘述依然價值無限。
世友合十
印度浦那
2020年3月14日
譯者序:使命
憶起2016年9月29日,末學帶著滿懷的忐忑,在大千出版社梁崇明社長主辦的「獻給佛陀聖地的真愛:印度佛教復興分享會」,分享了《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大士傳記》的翻譯心路歷程。中場休息時,我將譯著恭恭敬敬的呈給世友居士,請託他送給遠在英國的僧護居士,並轉告這位末學無緣見面的年邁原作者,說他的妙筆生花,寫活了護法大士,觸動了不少讀者,讓他們徹夜未眠,灑下了感動的眼淚。世友居士當下接過了書本,認真卻又不失幽默的回答我:「那真是太棒了!我覺得你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翻譯《安貝卡博士與佛教》。這本書,是瞭解現代印度佛教的必讀作品,也是我老師的著作,一樣可以哭倒一堆人。」就這樣,末學又忐忑忐忑的多了一份功課。
分享會之後,末學便風風火火的繼續埋首撰寫論文,同時準備畢業後回國的各項事宜。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始終不敢忘記這份「功課」。2017年中,末學回到新加坡之後依舊相當奔波,並且還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翌年年初,在安頓下來之後,終於稍有閒暇細讀原著,並開始敲起鍵盤。然而,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末學又投入了歷時七個月相當緊湊的學習生涯。截至2018年10月份,進入備考期間,才難得抽出時間繼續翻譯。不料在當月30日,突然接獲僧護居士辭世的消息,頓時內心一陣揪痛,悼念又一位佛教界大善知識的殞落。 猶記得世友敘述僧護收到譯作時的愉悅心情,猶記得世友告訴我,僧護獲知末學已經開始另一部著作的翻譯,心裡很是期待。隨著噩耗傳來,末學內心滿是沉重,因為他老人家,再也看不到自己第二部譯成中文的著作,更懊惱末學自己不夠爭氣,竟未能達成他的期待,讓他親眼目睹譯作刊行於世……。
關於這位長者,據世友居士所言,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作家。末學在著手第二部著作翻譯當兒,便對此深信不疑。僧護居士善於揣摩故事主人翁的脾性,然後將這種寫作手法,融入他的著作中。譬如:護法大士出身顯貴。在捍衛佛教的過程中,雖然也歷經了種種磨難,所幸他常有貴人扶持,一生充滿機遇與傳奇。因此,在《護法大士傳記》一書,整體而言,他採用的是辭藻較為華麗,行文如史詩般莊嚴的文學體裁;傳記幾乎是採用線性的陳述方式,從護法大士的出生、成長、歷練、弘法、朝聖……截至晚年圓了出家夢,然後示寂。
相較於《護法大士傳記》,《安貝卡博士與佛教》的文體與敘事方式,後者差異頗大。安貝卡博士雖然賤民出身,但因其瑪哈爾種姓之故,其曾祖父、祖父及父親都是軍人出身。有鑑於此,安貝卡並非生於貧民窟,而是在軍區誕生。換言之,他在童蒙時期,對種姓制度的殘酷毫不知情。到了略懂世事,父親從軍隊退役之後,才接觸到保護區外充斥著豺狼的世界,領略到「不可觸者」的身份到底有多可悲,以至於在他單純、稚嫩卻早慧的心靈,烙下了極具衝突、深入骨髓的印記。在歷經種姓制度的各種踐踏,印度教高種姓者的諸多霸凌,從政後印度右翼政黨的千般迫害,想為追隨者討回公道卻處處受到掣肘。諸如此類自幼便如影隨形的各種不公不義,導致他逐漸養成嫉惡如仇、焦躁易怒的性情。然而安貝心性聰穎、心如明鏡,思辨能力超群,但凡遇到什麼難題,都力求抽絲剝繭、理出頭緒、釐清過程,直到得出真相。
末學相信,作者撰寫這部傳記之際,便是秉持了上文提到的寫作原則。他深知安貝卡理性、善於歸納的個性,因此整部著作的佈局,並未如同《護法大士傳記》那樣,採用線性時間軸的模式敘事,而是以不同角度、不同議題、不同事件,去詮釋安貝卡其人。能夠將安貝卡思辨能力演繹得酣暢淋漓的篇章,莫過於第三章的〈種姓地獄〉和第五章的〈漫漫尋根路〉。這兩章,作者甚至還效仿安貝卡博士所創「社會現象偵探小說」(sociological whodunit)的體裁, 即:列出命題、梳理文獻、剖析、推理、追根溯源,從一條線索直扣另一條線索,到最終得出答案。他在這兩章,深入探究的問題就包括:
何謂「可觸碰者」(touchable)、「不可觸者」(untouchable)與「不可觸性」(untouchability),
何謂「種姓制度」,
何謂「一生族」與「再生族」,
何謂「哈里真」(神的孩子),
何謂「印度四姓」與「無種姓者」;以及
「薩瓦爾納」(Savarnas,亦即印度種姓)與「瓦爾納」(Avanars,亦即無種姓者)之間的區別。
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議題,莫說是對印度文化甚為陌生的華人,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也都難以說出一個所以然。不過,在安貝卡博士鍥而不捨的尋根決心之下,這些撲朔迷離的問題,最後都給出了確切的說法。
本書第六章〈思考佛教〉與第八章〈佛陀與其教法〉,是深入研究安貝卡思想的篇章。安貝卡自1948年至1956年,皈依佛教之前的這八年期間,是他真正自我沉澱,審思(改宗)佛教的關鍵期。〈思考佛教〉一章,主要介紹他於1950年發表的〈佛陀與其教法之未來〉。在這篇六千餘字的著作中,他對比了佛教與其他三大宗教創始人(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與耆那教)之間的差異,接著探討佛教與其他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之間的區別,並於結尾,列出了傳揚佛教不可或缺的三大步驟。《佛陀與其教法》是他畢生嘔心瀝血的鉅著,在他辭世之後翌年才問世。這部著作,亦是他對廣大追隨者的承諾。僧護居士撰寫的這兩章,行文亦如安貝卡的個性:嚴肅,甚至堪稱高冷!換言之,那絕對不是供人打發時間的暢銷小說。假設我們將《護法大士傳記》類比為文學性強、引人入勝的佛經,那麼這兩章,或許可以類比為佛教三藏當中的《論藏》,雖然不好理解,卻不可或缺!
安貝卡博士雖然個性又冷又酷,但他並非無情之人,只不過是情感極為內斂。他撰寫《佛陀與其教法》之前,為廣大追隨者所作的諸多考量,不得不說就是一種理性的溫柔。另外,書中未曾提及的是,他甚至曾經為了繪製出心中最理想的佛陀,從百忙中擠出時間學習繪畫,事實上亦是一種另類的情感表達。護法居士在撰寫此書時,也並非通篇都是生硬難懂的論述。譬如第四章〈皈依佛教的各種契機〉和第七章〈龍城皈依大典〉,就都是足以觸動人心的章節。對印度佛教史有點概念的讀者都知道,在安貝卡的年代,印度幾乎沒有佛教。安貝卡接觸佛教的契機,和他試圖解決「不可觸性」的問題息息相關。他曾經表示,與其說他逐漸邁向佛教,不如說他逐漸遠離印度教。在他瞭解到「不可觸者」和「破碎的人類」,與佛教有著極深淵源之時,皈依佛陀的理性與感性層面,在這一刻同時具足。因為覓得了依祉的根源,這才促使他立志皈依佛教,為印度現代佛教史,書寫了筆墨濃重、波瀾壯闊的龍城皈依大典。可惜天妒英才,安貝卡博士皈依佛教不到七週時間,便緣盡娑婆。
讀者或許會好奇,安貝卡博士到底是何許人,竟然能夠在通訊維艱、交通極不便利的年代,令五十萬眾齊聚一處,轟轟烈烈的完成皈依壯舉?以教科書的說法,安貝卡是「印度憲法之父」;然而作為一名印度公民,他亦曾是律師、政治人物、社會改革家、佛教捍衛者、作家(撰寫了大量與佛教、政治、社會議題相關的著作)。作為一名印度高種姓者所不齒的卑賤種姓,他是讓諸多婆羅門分外眼紅的「不可觸」精英;從1922年至1953年這三十二年當中,他僅僅花了十年的功夫,就分別從英國、美國和印度,榮獲四個博士學位。可是,對他數量龐大的忠實追隨者而言,安貝卡卻是他們領導人、英雄、再生父母(因此才有「爸爸先生」之稱),甚至是他們的「佛陀」。對這群新皈依佛弟子而言,佛陀太過遙遠,阿育王也只是歷史人物,但安貝卡博士,卻是活生生,引領他們皈依佛教,脫離種姓地獄的偉人。因此,安貝卡的驟然離世,讓整個馬哈拉施特拉邦為之哀慟,讓數量龐大的追隨者陷入愁雲慘霧,讓剛剛轉起的佛教法輪戛然而止,新皈依的佛弟子失去依怙!安貝卡博士究竟是何許人?若要末學加以評論,那麼他絕對是一部活生生的印度現代史兼印度佛教史。
歷史的長河無論遭遇何等重大的衝擊,始終都得向前流淌。因此,在經歷了〈三次會晤〉之後,僧護居士把安貝卡博士的追隨者裝進了心坎裡。在〈安貝卡殞落後的歲月〉,承接了龍城剛剛轉起的法輪,於馬哈拉施特拉邦十餘載,安頓了新皈依佛弟子們倉皇失措的心。到了1970年代初期,僧護居士因為看到了在英國弘揚佛教的契機,故而只能夠以「兼顧」印度佛教復興的方式,數年往返英國與印度之間兩地奔忙。一直到了1977年,他的大弟子決定到印度學習瑜伽,印度的佛教,才又再次迎來一個特殊的因緣。這段奇緣,不禁讓筆者憶起西元560年,天台宗三祖智者大師,初謁二祖慧思禪師於河南大蘇山時,二祖所說的 :
「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 ! 」
還有2010年,美國迪斯尼一部電影《波斯王子:時之刃》(Prince of Persia: The Sands of Time)的開場白:
「曾有斯云,某些具壽之靈,橫跨時空,與遠古之召喚,緊密交匯,迴響蕩漾,千秋萬載、不朽經年。」(《使命》)
“It is said some lives are linked across time. Connected by an ancient calling that echoes through the ages.” (Destiny! )
此一遙遠的召喚,叫當時懵懵懂懂的世友比丘(當時短期出家),一頭撞進了安貝卡博士皈依大典二十一週年慶的會場。而此一盛會帶來的震撼,深深的嵌入了世友的心扉,連帶著把他與安貝卡追隨者的命運緊密交匯,從此與印度的佛教結下不解之緣。自那時起,他披星戴月、篳路藍縷四十餘載。現如今,當年這位年輕力壯、充滿活力的大弟子,已經成了一頭銀髮的睿智長者。印度佛教復興依舊是進行式,世友居士這數十年的耕耘,絕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不過他的作為,絕對足以慰藉安貝卡博士昔日的感傷,告訴他:「印度的佛教,看得到未來!」而未來的這條漫漫長路,尚須十方佛弟子的鼎力護持。
願此譯作,獻給另一時空維度的僧護居士,感念他為印度佛教復興的所有貢獻,同時祈請他護佑自己的大弟子,願世友居士能夠排除萬難,不負安貝卡博士的使命,繼續這條滿是荊棘的印度佛教復興路。
佛弟子 宜霖
於新加坡ami孤邸
2020/08/22
序
前言
印度目前有一億不可觸者(賤民)。他們絕大多數人,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屬弱勢,每年估約有四百至五百人遭受印度種姓(Caste Hindu)殺害。慘遭毆打、強姦、酷刑、劫殺、房屋被燒毀者更是成千上萬。更甚者,還有難以計數的人們,每天都慘遭社會、經濟與宗教歧視,以及默默忍受人身騷擾和屈辱。
過去的兩千年歲月,許多聖者和改革家試圖改善數量龐大不可觸者(Untouchables)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努力終未取得佳績。賓勞‧拉姆齊‧安貝卡博士(Dr. Bhimrao Ramji Ambedkar, 1891-1956)是最後一位、亦是最英勇的嘗試者,而且本身就是世襲的不可觸者。他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印度教無法讓不可觸者取得救贖,因此,他們必須改變信仰。於是,他於1956年10月,號召五十萬追隨者皈依佛教,帶起了印度佛教復興,同時亦開創了意義重大的宗教與社會革命。
德國猶太人遭受納粹主義之苦,及南非黑人遭受白人至上主義所累的事實,皆眾所周知且被廣泛討論。然而,印度不可觸者受印度種姓魔爪凌虐之苦,及安貝卡博士致力解救古老奴隸制度的英勇行為,卻鮮為國外人士所知。他離世三十年後,西方世界遍尋不著這位偉大不可觸者領袖的傳記,他發動的大型佛教皈依大典,亦未見長篇幅的報導或研究。
筆者的這部著作,實在難以彌補上述種種缺憾,權且算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小步。接下來的幾頁,我簡單介紹安貝卡的職業生涯,描述他成為佛弟子的原因與歷程,同時解釋:他心中的佛教到底存在什麼意義。另外,這部著作為普及型而非學術型讀物,因此,梵文與巴利語相關字詞,在大多數情況下,並未標註變音符號,亦不保證本著作與安貝卡的著作之間,所用字詞會有統一的拼音與書寫。
最後,我要感謝世友居士(Lokamitra)、法護居士(Dharmarakshit)、維摩詰居士(Vimalakirti)及浦那的所有成員,為我提供在英國已絕版,或是難以取得的書籍;感謝伊萊恩‧穆雷(Elaine Murra)謄寫我的手稿,阿洛卡居士(Aloka)協助設計封面,善德維拉居士(Shantavira)編輯稿件和安排刊行出版。
僧護合十
目次
愛德華‧賈本德〈邁向民主主義〉
前言
推薦序一:佛門不巧事業的締造者:安貝卡博士
推薦序二:安貝卡博士復興印度佛教、解放種姓制度
推薦序三:讓佛陀再次拯救印度
譯者序
安貝卡本尊的真實義
三次會晤
種姓地獄
皈依佛教的各種契機
漫漫尋根路
思考佛教
皈依大典
佛陀與其教法
安貝卡殞落後的歲月
書摘/試閱
安貝卡的存在意義
在德里國會大樓廣場,有一尊顯胖的長者雕像,一身西裝革履、戴著一副眼鏡。這尊大約十五英尺高的塑像,立於一個高度與塑像幾乎等高的方形基座。塑像右腳微微往前跨步,左手夾著一本大書,右手臂完全伸展開來,食指指向國會大廳的方向。此雕像,就是從1947年至1951年,在印度政府擔任法律部長的賓勞‧拉姆齊‧安貝卡。他夾於右手臂下面那本書,就是印度憲法。其手指向國會大樓,則是因為,他在1948年,向立憲會議提呈了他的憲法草案。一年後,國會接受此草案,並以此為基礎,進而立法通過法案。
安貝卡堪稱印度當時的翹楚,他一生行誼展現:一個才能卓越、品格勇猛出眾者,如何戰勝種種艱鉅的障礙、克服社會種種不公不義,及對個人的迫害。1891年,他背負印度種姓社會最低階人種的命運,以第十四子的身份,誕生在印度中央邦姆霍沃兵站(Mhow Cantt)。按照正統的印度教傳統,他完全沒有資格接受教育或擁有資產,而且僅能從事最卑賤的工作,更不能與更高種姓者肢體接觸。簡言之,安貝卡就是一個無種姓者、一個不可觸者。他被迫必須穿著別人丟棄的衣物、以高種姓主人吃剩的食物為食、謙卑順從地接受自己卑賤的身份,作為前世所造惡業所給予的懲罰。
但是,幸運如他,父親曾於印度陸軍服役,並以英語和瑪拉提語(Marathi)為學習源流,獲得一定程度的正規教育。這賦予他教育孩子的能力,尤其是對安貝卡的栽培,並鼓勵他們傾盡所能求汲取知識。1908年,年輕的安貝卡通過孟買大學的預科考。對於一個不可觸者孩子而言,這的確是非比尋常的例子,因此瑪哈爾公開為他慶祝。四年後,他在同一所大學順利取得政治與經濟兩門學科的畢業學位。緊接著,進入巴羅達士邦(Baroda State)服務,以報答州首長授予他獎學金的恩惠。但是,他的父親不幸於此時往生(母親則在他五歲時便撒手人世)。四個月後,這位痛失親人的孩子便離開了印度,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這次,那位嚮往自由的首長再次頒予他獎學金。當時,安貝卡的學術成就雖然凌駕於任何一名不可觸者,但他並未因此感到自滿。他秉持著「知識就是力量」的理念,深知:若不蓄積足夠的力量,就無望打破枷鎖,解放數以萬計的不可觸者,讓他們脫離虛構的奴隸制度。這個禁錮到底有多霸道?他個人痛徹心扉的經驗,就是最大的明證。
從1913年到1917年,及1920年至1923年之間,安貝卡都置身在西方國家。截至三十二歲那年,才正式回歸孕育自己的祖國,成為當時社會上坐擁最高學歷的佼佼者之一。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三年期間,他研究的學科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哲學、人類學和政治學,以《英屬印度的省級財政演變》(The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Finance in British India)為題撰寫論文並榮獲博士學位,最後還將這篇論文刊行出書。而他的第一篇著作〈印度種姓制度的機制、起源與發展〉(“Castes in India: Their Mechanism, Genesis and Development”),則在他指導教授主辦的人類學研討會發表。安貝卡完成了美國的學業後,便離開紐約前往倫敦,分別為錄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以及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因為獎學金僅維持一年,他回到印度於孟買一所大學任教。1920年,他創立了一個名為《愚蠢的領袖》(Mooknayak)的瑪拉提語周刊。此後,他重回倫敦繼續其學業,並花了三年時間,以《盧比的癥結》(The Problem of Rupee)為題撰寫論文,最後榮獲倫敦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同時獲得律師資格。他離開英國之前,在德國待了三個月,於波昂大學(University of Bonn)深造經濟學。
這位偉人於1923年4月份回到印度,繼續為不可觸者及其他受壓迫階級浴血奮戰。之後,賓勞‧拉姆齊‧安貝卡的傳記,與印度現代史之間愈發難以區隔。就在他離開倫敦的三年間,印度的政治局勢風起雲湧、變化莫測。印度向英國要求獨立的呼聲空前響亮: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 - 1948)開始倡導與政府形成對立的「不合作」(Non-corporation)政策,並於安貝卡歸國前的一年,發起了第一波大規模公民抗爭運動(Mass Civil Disobedience)。儘管安貝卡是個不折不扣的捍衛者,儘管他最初亦認同唯有政治獨立,受壓迫者方能享有社會的平等,然而,他卻同意甘地與其黨員所強調的:任何國家,都不配統治另一個國家。那麼,同理可知,任何一個階級,亦不配統治任何其他階級。當然,印度種姓亦沒有資格奴役其他受壓迫的階級。安貝卡雖然照常嚴厲批判英國的統治,但其主要心力,還是集中在捍衛受壓迫階級,為他們去除社會、經濟、教育和法律方面的障礙。其實,他早在1920年就意識到,獨立的選民,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保障受壓迫階級的利益。然而,亦是基於他對這方面的堅持,最終引爆他與聖雄甘地之間,及他領導的國民大會黨(Congress Party,簡稱國大黨),乃至於整個傳統印度社會的公開衝突。
邁入1932年之後,這個衝突終於達到高潮。那段期間,安貝卡開始在孟買拓展勢力,開拓自己的律師業務、在大學任教、提供證據給各種官方機構、創辦報社、並獲得孟買立法委員會提名,因此在其訴訟中立刻取得主導權。另外,他也出席了由倫敦主辦的三次圓桌會議,讓印度各社區代表及三個英國政黨,研究印度未來憲法的提案。他於1923年回到印度不久,最關鍵的貢獻就是─成立了「受壓迫者福利救濟協會」(Bahishkrit Hitakarini Sabha)。此協會宗旨在於─促進受壓迫階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改善他們的經濟,及為他們伸張正義。
不可觸者遭遇的種種屈辱都極嚴重:被杜絕進入印度教寺廟、禁止從公共水池或水井汲水、入學資格被剝削、無法在公共場所自由活動……等不勝枚舉。有鑑於此,安貝卡從1927年至1932年之間,帶領其追隨者展開了一系列非暴力運動,爭取不可觸者進入印度教寺廟禮拜,及從公共水池和水井汲水的權利。其中有兩項運動可謂重中之重:其一,抗議印度種姓排擠不可觸者進入納西克(Nasik)的卡拉蘭廟(Kalaram Temple),其二,關於馬哈德(Mahad)喬達爾水塘(Chawdar Tank)事件。這兩項運動,涉及成千上萬「被動抗爭」的不可觸者(Untouchable satyagrahis or “passive resisters”),激起了印度種姓的猛烈反擊。單就喬達爾水塘運動一案,歷經多年法律訴訟後,終於為那些遭受壓迫者捎來法律和道義的勝利。此運動亦連帶造成焚毀《摩奴法典》(Manusmriti)的儀式。這部古印度法律典籍,正是不可觸者慘遭印度種姓魔爪的罪魁禍首,甚至,直至今日,不可觸者仍無法脫離種種殘酷對待與人格屈辱。不可觸者之所以將這部至高法典投入火海的目的,是希望那些正統印度種姓,未來能還給他們人類該有的尊嚴。
安貝卡因其發起的運動,讓他跟印度種姓一樣成了「令人嗔」。經過1931和1932兩年之後,其「令人嗔」程度益發嚴重。他自己說,他成了印度最討人厭的人。換言之,他成了印度種姓及他們主導的國大黨之眼中釘。引發事端的根源,是因為安貝卡一再堅持─必須將受壓迫階級歸類為獨立選民,然而,聖雄甘地和國大黨則反對此舉。弔詭的是,他們並不反對穆斯林、錫克教徒、基督教徒和歐洲人作為獨立選民。為此,安貝卡和甘地在第二次圓桌會議上發生衝突。甘地針對此事挑戰安貝卡,質疑他代表不可觸者的權利。然而,安貝卡鏗鏘有力的論點則說服了英國政府。翌年,詹姆士‧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發表「公共獎」當時,受壓迫階級亦獲准成為獨立選民。為此,甘地決定採取絕食來訴求廢除受壓迫階級的獨立選民資格。甘地畢竟是獨立運動公認的領袖,所以,他絕食的行為震驚了整個印度;另一方面,安貝卡則被視為叛徒,及因為威脅甘地性命而深受譴責。安貝卡雖然對外界的輿論與壓力無動於衷,但並非冥頑不靈拒絕談判,因此,他最後同意了以聯合選民交換獨立選民,並大幅增加了保留席位。此一協議具體呈現在一個名為「浦那條約」(Poona Pact)的文件內。安貝卡簽署此條約之際,也奠定了他「受壓迫階級」的領袖身份。
當奄奄一息的甘地結束了絕食抗議後,全國各地民眾都感到寬慰,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可憐的不可觸者。然而,這種悲憫之情並未持續太久,因為,他們心中很快又填滿對安貝卡的憤怒。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獨立選民的問題遇到異議,部分由於不可觸者不斷遭受印度廟的排擠。安貝卡此時開始意識到印度種姓毫不退讓的態度,因此一改原來的方針,儘管那不算是他的策略,但他開始勸誡追隨者把精力投注在提高生活水平,及獲得政治權利。同時,他還認清了不可觸者在印度教內毫無前途,因此必須改變信仰。他出席1935年「受壓迫階級研討會」時,這些念頭演化成極富戲劇性的表述。他發誓自己雖然生為印度教徒,卻絕不頂著印度教徒的身份嚥下最後一口氣。他的這一宣言,在當時印度教教界掀起軒然大波。同年,安貝卡接任孟買政府法律學院(Government Law College)院長一職,為自己和藏書興建了一棟房子,但也失去了摯愛的妻子─拉瑪貝(Ramabai Bhimrao Ambedkar, 1898-1935)。安貝卡與結髮妻子是在1908年締結連理,當年他才十六歲,髮妻僅九歲,妻子為他生了五個孩子,卻只有一個存活。即使公務繁重,令他無暇處理家庭事務,但安貝卡卻極為依賴這位溫婉持家的妻子,因此,妻子之亡故令他悲痛欲絕。
他走出悲痛之後就立即投入例行活動,隨之變得更加忙碌。接下來的幾年,他創立了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參加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之下的省級選舉、當選孟買立法議會議員、要求取消農業農奴制、捍衛工業工人罷工權、主張促進節育,並在孟買管轄區(Bombay Presidency)各處舉行會議。1939年,第二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英國與德國納粹主義陷入生死纏鬥,火焰很快燒到印度政局。對甘地和國大黨而言,英國的危機恰好就是印度的契機,因此,自1940年開始,他們採取了不合作手段來應對英國參戰的努力。安貝卡並不認同這樣的態度,他非但不是一名激進和平主義者,而且視納粹意識形態為威脅印度人民自由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反而慫恿人們支持政府,奮起打擊納粹主義,同時更鼓勵不可觸者加入印度軍隊。1941年,他接任國防諮詢委員(Defence Advisory Committee),翌年加入總督執行委員會(Viceroy’s Executive Council)擔任工黨議員並任足四年。同一時期,他將獨立工黨改造為全印度列表種姓聯盟(All-India Scheduled Caste Federation)、創辦人民教育協會(People’s Education Society),並出版了一系列備受爭議的書籍和小冊子。其中,宣傳最廣的小冊子包括《對巴基斯坦之見解》(Thoughts on Pakistan)、《國會及甘地對不可觸者之操弄》(What Congress and Gandhi have Done to the Untouchables)和《誰是首陀羅?》(Who Were the Shudras?)。
印度終於在1947年取得獨立。安貝卡那時已經是立憲會議成員,而首任印度總統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邀請他進入內閣成為司法部長。數週後,大會授權委託他制定憲法、成立草案委員會,而該會亦推選安貝卡為主席。接下來的兩年,安貝卡將全部心神投注憲法草案的艱苦工作,對每一章節、每一條款皆逐一細審。就在他心無旁騖、聚精會神之際,這個國家陷入動盪,分裂成為取得獨立的代價。而分裂導致穆斯林教徒與印度教徒之間,陷入瘋狂的相互廝殺,聖雄甘地也因此在1948年被暗殺。安貝卡除了特別關切身處巴基斯坦的不可觸者,同時還得面對自己的各種難題。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逐漸惡化,讓他極為擔憂,因此在步入58歲誕辰的前夕,娶了一位在醫院邂逅的婆羅門女醫生,希望能夠為他提供所需的護理。
縱使身體抱恙,安貝卡還是在1948年初完成憲法草案。次年,草案呈達國家層級半年後,成功獲得制憲會議採納。此後,他憑藉自己的才幹通過三讀程序,而新憲法終於在1949年11月份,以極少修正案的情況下,獲得大會拍案通過。新憲法讓敵友雙方皆相當滿意,因此,此時的安貝卡接受到來自四方的熱烈慶賀,受歡迎指數空前飆升。媒體讚譽他為「現代版的摩奴(法典)」,但是,諷刺的是,成就自由印度的竟是一個不可觸者。而這個事實,亦成了街頭巷尾茶餘飯後的話題。安貝卡此刻雖然僅剩七年壽命,但他亦注定了以「憲法工程師」與「現代摩奴」之美譽走人現代印度的官方史冊。他殞落後,其塑像猶如現代摩奴般,高高豎立在議會大樓外,手臂下夾著他所撰憲法,一手指向議會大樓。安貝卡雖然自1948年開始便成績斐然,其憲法之父的美名至今仍廣為人知,但是他真正的豐功偉業,此刻尚有待發掘。
此一有待發掘的成就,是安貝卡歷經政壇的波譎雲詭、花費數年爭取《印度教法典議案》(Hindu Code Bill)立案卻告失敗,生命接近尾聲之際,才實現這個根本的精神成就。《印度教法典議案》是安貝卡在過去十年蒐集而來的個案。這些案例來自於一些傑出印度教律師經手的個案,涉及領域包括結婚、離婚、領養、共同家庭資產、婦女財產與繼承權等相關問題。雖然這僅是一次改良而非革命性舉措,但是,此一法案在大會內外,甚至內閣之間,都遭遇強烈的反對。安貝卡被指控企圖破壞印度教,議會當中,傳統派政敵與他怒目相向、互相指責。最後,在通過了四項條款之後,條例草案被撤銷。1951年,安貝卡帶著疲憊厭倦的心情,辭去了內閣職務。在他的辭呈宣言中(事實是他被阻止於大會上宣誓),他解釋了自己離開內閣的五個原因,其中第二項,他指責內閣對提升「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抱以麻木不仁的態度;第五項指出,尼赫魯未能給予《印度教法典議案》足夠的支持。
安貝卡從內閣之退隱,標示著其政治生涯的實質結束。他從1952年1月的大選中落選,未能贏得人民院(Lok Sabha)的席位,第二年雖然也參加補選卻同樣落敗。到了1952年3月底,他入選為聯邦院(Rajya Sabha)委員會,成為孟買邦十七名代表之一,接著便猛力攻擊政府。儘管他直到生命結束前都置身於聯邦院事務,但從他入選聯邦院委員會開始,便逐步將精力投注在更重要的事件上。打從1935年「被壓迫階級研討會」上,他那句─「雖生為印度教徒,但絕不以印度教徒的身份離開人世」之宣言,震驚了印度社會後,安貝卡便一直在認真思考改變信仰的問題。他愈是深入思考,就愈是相信不可觸者在印度教社會沒有未來,因此必須採納另一個信仰,而佛教正是不二之選。他在職期間,幾乎無暇實現如此重大的改變,但並未錯失教育其追隨者的機會;而他對自己及追隨者應該追尋的方向亦愈發明確。1950年,他不但公開批評克里希那、耶穌基督和穆罕默德來禮讚佛教,同時更應邀拜訪錫蘭位於科倫坡的佛青會(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並於康提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會議上發言,呼籲康提的不可觸者擁護佛教。1951年,佛教被指責導致印度婦女的沉淪,安貝卡因此匯編了一部名為《成佛之道》(Bauddha Upasana Patha)的佛教文集聲援佛教。自他辭去內閣職務,接著參選人民院落敗後,終於有了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實現他最偉大的成就。
他在1954年二度走訪緬甸,而第二次到訪,是為了參加在仰光舉辦的第三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1955年,他創立了印度佛教協會(Bharatiya Bauddha Mahasabha),並於浦那附近德護路(Dehu Road)的一座寺廟裡安奉尊佛像。他當著成千上萬參加盛會的不可觸者許下盡形壽在印度弘揚佛陀教法的誓願,同時承諾─「願以淺顯的文字撰寫一部闡述佛教教法的書籍,以利益一般民眾。」他預估尚需要一年時間來完成此一著作,立下─完稿之日,便是他皈依佛教之時─的誓言。他在1951年便已以《佛陀與其教法》(The Buddha and His Dharma)為題開始著書,終在1956年2月份完稿。書本問世後不久,安貝卡於該年10月皈依佛教,兌現了他許下的承諾。
安貝卡為了舉行此一皈依盛典,在龍城作了妥善的安排。1956年10月14日,這位不可觸者領袖,先以傳統的儀式請一位佛教比丘為他授三皈五戒,接著,他本人特別替響應此號召的三十八萬男女老少主持皈依儀式,龍城和占達(Chanda)緊接著再次舉辦大型皈依,此後,安貝卡回到德里,他深信,印度必將再次轉起佛教的法輪。數週後,他前往尼泊爾加德滿都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並以《佛陀與馬克思》(The Buddha and Karl Marx)為題於大會宣講。他返回德里途中,在瓦拉納西發表了兩場演講,接著拜訪佛陀般涅槃之地─拘尸那羅。回到德里之後,他活躍參與各種佛教活動、出席聯邦院,接著完成《佛陀與馬克思》的最後一章。就在12月5日黃昏,他請人將《佛陀與其教法》的前言和介紹送到他的床邊,以便他夜間繼續忙碌,但是,卻在隔天早晨被發現臥床身亡。12月6日,他享年六十四歲七個月,距離皈依大典僅七週!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