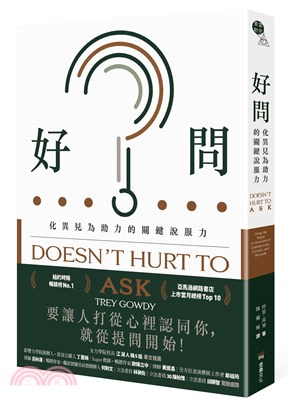好問: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
商品資訊
系列名:亞當斯密
ISBN13:9789860651324
替代書名:Doesn't Hurt to Ask: Using the Power of Questions to Communicate, Connect, and Persuade
出版社:堡壘文化
作者:特雷‧高迪
譯者:陳珮榆
出版日:2021/05/12
裝訂/頁數:平裝/304頁
規格:21cm*14.8cm*2.1cm (高/寬/厚)
重量:414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紐約時報暢銷榜No.1
★亞馬遜網路書店當月暢銷榜Top 10
★福斯新聞台主播達娜‧裴里諾(Dana Perino)、美式足球名人堂教練盧‧霍茲(Lou Holtz)盛讚推薦
爭吵,解決不了對立
有效提問,才能讓人不知不覺被你打動
前美國聯邦檢察官暨眾議院議員──特雷‧高迪,
匯集20年法律工作與政黨協商的案例經驗,教你如何有效溝通,化歧見為助力!
從說服小孩整理房間,到進行提案希望獲取他人支持,在生活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為某些重要事情辯護的時候。然而在說服與溝通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急於陳述自己的意見,並對他人的意見難以採納,導致對話陷入僵局而淪落至爭吵的結局。
從事法律工作20年,並且連任了4屆美國眾議院議員的特雷‧高迪,發現無論你是要說服別人或是與人爭論,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問。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利用問題來改變他人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說服技巧,而提問是最高層次說服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大多數人都可以藉由說明自己觀點和解釋原因來說服別人,但你能在適當的時間和順序裡提出適當的問題來說服他人嗎?更重要的,你能讓與你交談的人說服他們自己嗎?
如果你真的想說服別人,使他們改變思惟方式,你必須先問問自己:
你想實現什麼?
你的目標是什麼?
交流結束後,你如何衡量成功?
誰是你的陪審團?
證明起來有多困難?
無論你是想說服陪審團判定某個被告犯可能犯下死罪,或是說服你的妻子讓你在周末夜出門與朋友小聚一番,在開口準備說服他人之前,都要先問問自己這些問題。藉由知道你的目標,知道你的事實,知道成功的模樣,那麼制定邁向成功的路線就會變得容易許多。說服別人也是如此。
以提問進行說服的關鍵技巧
利用問題來打動別人和說服別人是一門微妙的藝術。大多數人都能陳述自己的信念,但如果你能學會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提出對的問題來說服別人,說服別人這件事情將會輕鬆且容易許多。
在本書中,特雷‧高迪提出了如何以提問進行說服的重要關鍵技巧:
1.所有的問題都只有兩個目的──問題不是用來證實,就是用來反駁。你提出的問題不是支持你的觀點,就是反對對方的觀點。藉由提出問題,幫助你在爭論中證明或駁斥觀點,並更加印證或是更加否定對方的看法。
2.誘導性與非誘導性問題──提問可能帶有挑釁,也有可能是中立的,其目的純粹是為了獲取資訊。當有情況發生時,人們大部分會先問「為什麼?」其次才問「誰做了什麼?」理解別人為何會有不同想法,才有可能用語言和行動說服別人。
3.質疑──你可以質疑事實、質疑對方得出的結論,或是質疑對方本人。當對方明顯存有偏見時,你應該盡量多花時間來突顯這種偏見。
4.順水推舟──人們常常只憑片面獲取的訊息(例如社交網路、報章媒體、人云亦云),就對他們關注的人做出判斷。你可以利用這些看法,將你自己的觀點加入相關討論之中。
5.重複、重複、再重複──重複對於說服來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義,就像大家常說「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一樣,人類本能的反應是:我們重複聽到的次數愈多,記憶程度就越高;我們重複聽到的次數愈多,就會更容易認為這個事實是重要的。
6.重新包裝對方的話──重新包裝可以迫使你聆聽對方究竟在說什麼,迫使你利用洞察力識別邏輯最薄弱的環節,迫使你利用荒誕、極端無理和誇張的黑魔法,去結合對方修辭或邏輯上最薄弱的環節。
很多人認為說服是要對方完全接受自己的想法與意見,然而真正的說服是漸進式的過程,讓對方放棄原本與你相對立的想法而轉投其他想法(不一定是你的想法)也是一種成功說服的結果,因此,在說服之前,你必須要先設定什麼是正確的說服:
‧讓人重新思考立場是成功的說服。
‧讓人不帶偏見地傾聽你的立場是成功的說服。
‧讓人理解你所為何來也是成功的說服。
人是帶有偏見的個體,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與生活歷程來判斷事物,有時亦毫無邏輯可言,也因此硬碰硬的說服溝通是最吃力的方式,學習透過提問的方式溝通,藉由讓對方自我思考、建立連結,學會不要求與不強迫也能獲取自己想要的結果,才是最強而有力的說服方式。
★亞馬遜網路書店當月暢銷榜Top 10
★福斯新聞台主播達娜‧裴里諾(Dana Perino)、美式足球名人堂教練盧‧霍茲(Lou Holtz)盛讚推薦
爭吵,解決不了對立
有效提問,才能讓人不知不覺被你打動
前美國聯邦檢察官暨眾議院議員──特雷‧高迪,
匯集20年法律工作與政黨協商的案例經驗,教你如何有效溝通,化歧見為助力!
從說服小孩整理房間,到進行提案希望獲取他人支持,在生活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為某些重要事情辯護的時候。然而在說服與溝通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急於陳述自己的意見,並對他人的意見難以採納,導致對話陷入僵局而淪落至爭吵的結局。
從事法律工作20年,並且連任了4屆美國眾議院議員的特雷‧高迪,發現無論你是要說服別人或是與人爭論,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問。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利用問題來改變他人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說服技巧,而提問是最高層次說服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大多數人都可以藉由說明自己觀點和解釋原因來說服別人,但你能在適當的時間和順序裡提出適當的問題來說服他人嗎?更重要的,你能讓與你交談的人說服他們自己嗎?
如果你真的想說服別人,使他們改變思惟方式,你必須先問問自己:
你想實現什麼?
你的目標是什麼?
交流結束後,你如何衡量成功?
誰是你的陪審團?
證明起來有多困難?
無論你是想說服陪審團判定某個被告犯可能犯下死罪,或是說服你的妻子讓你在周末夜出門與朋友小聚一番,在開口準備說服他人之前,都要先問問自己這些問題。藉由知道你的目標,知道你的事實,知道成功的模樣,那麼制定邁向成功的路線就會變得容易許多。說服別人也是如此。
以提問進行說服的關鍵技巧
利用問題來打動別人和說服別人是一門微妙的藝術。大多數人都能陳述自己的信念,但如果你能學會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提出對的問題來說服別人,說服別人這件事情將會輕鬆且容易許多。
在本書中,特雷‧高迪提出了如何以提問進行說服的重要關鍵技巧:
1.所有的問題都只有兩個目的──問題不是用來證實,就是用來反駁。你提出的問題不是支持你的觀點,就是反對對方的觀點。藉由提出問題,幫助你在爭論中證明或駁斥觀點,並更加印證或是更加否定對方的看法。
2.誘導性與非誘導性問題──提問可能帶有挑釁,也有可能是中立的,其目的純粹是為了獲取資訊。當有情況發生時,人們大部分會先問「為什麼?」其次才問「誰做了什麼?」理解別人為何會有不同想法,才有可能用語言和行動說服別人。
3.質疑──你可以質疑事實、質疑對方得出的結論,或是質疑對方本人。當對方明顯存有偏見時,你應該盡量多花時間來突顯這種偏見。
4.順水推舟──人們常常只憑片面獲取的訊息(例如社交網路、報章媒體、人云亦云),就對他們關注的人做出判斷。你可以利用這些看法,將你自己的觀點加入相關討論之中。
5.重複、重複、再重複──重複對於說服來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義,就像大家常說「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一樣,人類本能的反應是:我們重複聽到的次數愈多,記憶程度就越高;我們重複聽到的次數愈多,就會更容易認為這個事實是重要的。
6.重新包裝對方的話──重新包裝可以迫使你聆聽對方究竟在說什麼,迫使你利用洞察力識別邏輯最薄弱的環節,迫使你利用荒誕、極端無理和誇張的黑魔法,去結合對方修辭或邏輯上最薄弱的環節。
很多人認為說服是要對方完全接受自己的想法與意見,然而真正的說服是漸進式的過程,讓對方放棄原本與你相對立的想法而轉投其他想法(不一定是你的想法)也是一種成功說服的結果,因此,在說服之前,你必須要先設定什麼是正確的說服:
‧讓人重新思考立場是成功的說服。
‧讓人不帶偏見地傾聽你的立場是成功的說服。
‧讓人理解你所為何來也是成功的說服。
人是帶有偏見的個體,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與生活歷程來判斷事物,有時亦毫無邏輯可言,也因此硬碰硬的說服溝通是最吃力的方式,學習透過提問的方式溝通,藉由讓對方自我思考、建立連結,學會不要求與不強迫也能獲取自己想要的結果,才是最強而有力的說服方式。
作者簡介
特雷‧高迪是前聯邦和州檢察官,在刑事司法體系擁有將近二十年的親身經驗。他於二〇一〇年當選國會議員,並擔任眾議院監督暨改革政府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和班加西問題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Benghazi)主席,亦曾參與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以及司法、紀律、教育和勞動委員會。高迪擔任四屆議員之後,決定不再尋求連任,從而以在法庭上的模範紀錄和在政治選戰中的不敗佳績告別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在擔任檢察官和南卡州訴訟協調委員會(South Commission on Prosecution Coordination)主席期間的勤奮態度,也廣受執法機關和犯罪受害者的認可。他亦是《紐約時報》暢銷書《統一》(Unified)的共同作者。
https://www.treygowdy.com/
Facebook: @RepTreyGowdy
Twitter: @TGowdySC
Instagram: @tgowdysc
https://www.treygowdy.com/
Facebook: @RepTreyGowdy
Twitter: @TGowdySC
Instagram: @tgowdysc
名人/編輯推薦
女力學院校長 江湖人稱S姐 專文推薦
影響力學院創辦人/資深公關人 丁菱娟
Super教師/暢銷作家 歐陽立中
律師 黃國昌
律師 呂秋遠
暢銷作家/職涯實驗室社群創辦人 何則文
全方位表演藝術工作者 郎祖筠
立法委員 林昶佐
立法委員 3Q 陳柏惟
立法委員 邱顯智 驚艷盛讚
影響力學院創辦人/資深公關人 丁菱娟
Super教師/暢銷作家 歐陽立中
律師 黃國昌
律師 呂秋遠
暢銷作家/職涯實驗室社群創辦人 何則文
全方位表演藝術工作者 郎祖筠
立法委員 林昶佐
立法委員 3Q 陳柏惟
立法委員 邱顯智 驚艷盛讚
序
導言
從法庭走到國會
為什麼要說服
十六年來,我面對過無數組沒有成功躲過義務的十二人陪審團。(好吧,這樣說可能不公平,但認了吧!幾乎不會有人興高采烈地收下傳票。)然而,就我的經驗來看,儘管對於出席猶豫不決,但大多數人最後都會享受著參加陪審團服務的樂趣,或者最起碼也領會到美國司法制度的權威性。法庭反映出真實人生,顯示了所有痛苦和快樂、正義和不公、以及源生於試圖掌控和裁決人性的原始情感。雖然你可能不太有機會走進法庭,但「審判」同樣存在生活的各個角落,那些「審判」可能出現在商業場合、社群會議、學校或家中。
我在聯邦法院和州法院經歷過近百場的陪審團審判,案件範圍從槍枝違法到毒品走私、擄人勒贖到劫車、性侵害到搶劫、兒童虐待到謀殺,法庭已經成為我感到最平靜和最舒適的地方。我喜歡這種的邏輯思維,喜歡這裡的遊戲規則,喜歡策畫謀略,喜歡這種需要快速思考的地方,喜歡有機會追求真理,喜歡整個以人和程序為縮影的人類光譜。但最重要的,我之所以喜歡法庭,是因為我熱愛說服的藝術,而且我一直竭盡所能地將這門藝術做到最好。
我所做的一切都要歸功於我的母親。在我和三位妹妹成長的過程中,母親做過許多有益的事情,但她最喜歡的工作是在地方律師事務所擔任受害者辯護人(victim advocate),為犯罪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諮詢,說明他們身為受害者的權益,替他們揭開刑事訴訟過程的神祕面紗。如有需要或要求,受害者辯護人會與受害者及其家屬一起出席審判、抗辯和量刑聽證會。
當我大學和法學院暑假期間在家時,母親下班回來後會流露對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沮喪之情,並公然質疑:「為什麼被告、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雇用任何他或她想要的律師,而受害者卻無法?受害者只能跟指派辦理此案的檢察官綁在一起,為什麼受害者不能聘請最好的律師?」
問得好,媽。我知道教科書的答案是什麼――因為刑事犯罪實際上屬於侵害國家,並非針對個人――但教科書的答案不能給予受害者什麼安慰,受害者必須受到資深刑事辯護律師的詰問,而犯罪者卻未必會受到資深檢察官的詰問。媽,妳說得沒錯。受害者應該有權聘請好的律師,聘請能夠在開審陳述中為其正確預期做好鋪陳的律師;受害者應該有權聘請能夠直接提問,巧妙地以令人信服、邏輯方式誘導證詞的律師;他們應該有權聘請不用低頭看筆記就能有效盤問被告的律師,有權聘請在終結辯論時能結合激情與理性,讓陪審團達成共識的律師,聘請一位甚至能夠克服美國司法認可的最嚴苛舉證責任(即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律師;他們有權聘請一位能夠預測被告辯護律師的下一步,並採取謀略應對的律師;他們有權找一位懂得說服藝術的律師。
即使在法庭之外,人們也希望自己既能得到有效的辯護,又能成為有效的辯護人。如果工作中出現關於升遷或新業務機會的談話機會,你會想參與其中,而要成為談話的一員,可能與你是不是有效的溝通者有相當大的關係。事實上,你會想成為談話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這就是我在法庭上十六年來努力達成的目標:成為受害者願意選擇的辯護人,假如他或她真能像我母親心裡期盼的那樣,能夠挑選國內任何一位律師來擔任他們律師的話……。擔任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的實質辯護人須背負沉重的壓力,但在你日常生活的其它領域,這種壓力並不會減輕多少,你也需要為某些事或某個人成功辯護,你也需要說服他人在某個議題上更接近你的思路,或者至少瞭解你為何相信自己的想法。法庭是我的工作場所,而你也有你自己的工作場所,你我都一樣,都需要有能力進行訊息處理和溝通,以便達到預期結果。無論議題是關於謀殺案件、行銷或是身為人母。
我有時候會稱為「謝客」(receiving line)工作。那些是你希望別人在你離開時還能記住你的工作。如果我比太太先行離世,我會請她做兩件事:一、等我葬禮結束後再開始約會;二、確保我們孩子記得,他們父親最喜歡的工作是擔任檢察官。我會希望別人記住我這份工作,因為這是一份最有意義、最有目標、也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在公平和正當的程序下說服陪審團,利用具備可信度、符合事實、推理、合乎邏輯以及豐富多元的言詞表達,讓陪審團的判決從無罪到有罪。
溝通對話要如何進行,你會有你自己的版本,因為這些與你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但現在就開始思考你想在生活、工作和愛情方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永遠不嫌太早。
還有一件事我希望我太太別忘記:三、確保我們身旁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們能記得我上次起訴的案件,以及我為何這樣做的原因。
若你去過我在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想知道擺在我全家福照片旁邊的照片上那個小女孩是誰的話,她就是我處理過最後一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她是我最後一次站在陪審團面前的原因。
從小罹患先天腦性麻痺的十歲女童梅‧懷德(Meah Weidner),遭母親男友痛下毒手毆打並搖晃致死。母親男友是一名消防員和緊急救護技術員(EMT),沒有任何犯罪紀錄。根據他的說法,女童的傷勢是她癲癇發作從輪椅上摔下來造成的,並聲稱自己可能是替她進行心肺復甦時不小心弄傷了她。但他堅稱,這只是一場意外,並非犯罪行為。
當時我已經一隻腳踏在法庭外,準備前往國會的路上,距離就職宣誓只剩幾個星期。辦公室裡肯定會有別人接下這起案件,我們辦公室裡面有許多非常優秀的檢察官,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替梅討回公道。但我母親的聲音始終在腦海中縈繞:「為什麼被告可以用錢請到最好的律師,受害者卻不能?」
母親的聲音,加上自己身為人父的心情,促使我接下卷宗親自辦案。我想為那位再也不能說話的小女孩發聲,我想保護那位無法保護自己的女孩,為了那位坐在輪椅上的女孩,我願在陪審團面前來回踱步,珍視她生命的程度就如同人們珍視自己孩子一樣。我會代替她進行有效的說服,因為這是符合公平且正義的事。
要讓十二名陪審團相信,眼前這位有好工作、沒有前科的男子殺害一名手無寸鐵的孩童,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但事實就是如此,所以我運用邏輯、真相以及最重要的提問來進行說服工作。
我向陪審團提了幾個問題。當然,有些問題是要讓他們瞭解必要資訊,進而形成完善的觀點;有些是他們和我都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但是,所有問題的最終目的,都是要讓他們自行判斷真相。
最後,陪審團十二人都認定他「有罪」,判定該男子殺害了梅‧懷德,法官判處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從法庭內的氣氛和陪審團達成裁定的速度可以清楚看出,他們被這位年幼女孩的生命所打動,令他們能同理我的感受,令他們能對梅生命的珍視程度就如同對自己的子孫輩一樣,使他們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把梅的照片擺在辦公桌上,可以提醒我許多事情:莫忘生命的脆弱、年輕人的純真、為他人挺身而出的動力,以及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為某些重要事情辯護的時候。不可否認,利用問題來改變他人是一種獨特的說服方式,但我相信,提問是最高層次說服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多數人都可以藉由說明自己觀點和解釋原因來說服別人,但你能在適當的時間和順序裡提出適當的問題來說服他人嗎?更重要的,你能讓與你交談的人說服他們自己嗎?
你不需要在法庭上為別人辯護,也不需要加入國會捍衛某個理想。說服他人的機會比比皆是,從法庭到客廳、從街道對面的鄰居到辦公桌對面與客戶交談、從說服陪審團到說服老闆,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和偶爾有義務要去說服他人。
最有說服力的人傾聽跟講話一樣多;最有說服力的人,問的問題與回答的問題一樣多。提問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想讓別人更瞭解你的立場,或者只是讓他人相互瞭解,那麼在對的時間用正確的方法提問,可能會是你最有效的工具。
達成共識?也許不會
十六年的檢察官生涯教會我如何成為一名律師,教會我瞭解本國公民,教會我如何與他們溝通、說服他們,用確鑿的證據勸誘他們,也教會我如何拆解不可靠的證據。法庭是一種文化與人類學的培養皿,在這裡,人類光譜的所有面向都會受到考驗、分析及審判。這就是為什麼適用於法庭的溝通技巧也能實際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你在自家客廳或會議室運用我們司法體系所採用的流程與程序,可能會有人跟你說:「這裡又不是法庭。」已故的以利亞‧康明茲(Elijah Cummings)在擔任國會議員之前是名傑出的律師,他有次在委員會聽證會溫和地責怪我說:「這裡是法庭嗎?……難道這裡採用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嗎?」美國前國稅局(IRS)局長約翰‧柯斯基寧(John Koskinen)和我在委員會會議室外總保持良好關係,某次他在回答問題時問說:「請問現在是審訊嗎?這裡有人正在受審嗎?」不是的,委員會聽證會並非法庭,這裡也不遵循法庭在證據、程序或流程方面的規則,但也許它們應該遵循。美國司法體系所採用的那些政策、規則、程序和法規並非只是因為在法庭使用,所以本質上合乎「公正性」。它們之所以能在法庭上使用,是因為承受得住時間的考驗,我們集體認同這些規章是闡明真相的最佳工具。換句話說,只因為在法庭上使用就說這些規章合乎公正性是不對的說法,這些規章能夠在法庭上使用,是因為這些是公正的規則。公正性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我熱愛正義、公平、追求真理及說服陪審團,但我還是離開了法庭,因為我無法回答自己關於法庭以外所發生的問題。我無法使我的精神信仰與每天所見事物達成一致。人類彼此越來越殘忍,傷害無辜,殺害自己聲稱所愛之人,弱勢族群成為受害者。社會滋生無端暴力、道德敗壞、充滿仇恨。
在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善良、仁慈、守法,樂於助人。但在司法體系情況並非如此,導致最後對人性產生錯誤認知。法庭不會審判好人、正直或善良的人,這些審判都是針對那些謀殺、強姦或竊盜之人。當你每天都與這些人往來時,你對人類的想法很快就會與社會脫節。當你眼裡看到的只有邪惡,你就會誤以為邪惡就是一切。
我記得,在我越來越懷疑人性時,常常想起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引自聖經某段經文):「萬事皆互相效力得益處。」(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人應該經常聽到這句話。
萬事皆如此嗎?那些被菸頭燙臉的孩子們呢?被性侵的孩子呢?被榔頭打死的無辜夫婦呢?因遭到父親強暴而需縫合傷口的三個月大的孩子呢?那麼梅呢?這些難道就是神祢所謂「萬事皆互相效力得益處」的意思?
我在法庭上的表現相當不錯,幾乎能在任何想要和必要的時候,說服十二人排除所有合理懷疑。十六年來,我可以讓十二個完全陌生的人齊聚一堂並達成共識,對我來說,無論是說服美國公民或法官,都不是什麼難事。
難的是每天晚上下班後,我從法庭開車返家,那些答案開始被一個個反詰問句擊垮。到最後,白晝逐漸被黑夜取代,我努力想抹去腦海中對犯罪現場照片的記憶。家人熟睡的時候,我在床上輾轉難眠,努力分辨外頭傳來的是風聲還是趁勢闖入的邪惡和墮落聲響。我難以將工作與生活其餘部分切割開來,對我最親愛的家人亦是如此。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家女兒會拖著她的枕頭和毯子到我跟我太太的臥室,然後放在我們床邊地板上。她一定是放在我睡的這個方向,因為她知道媽媽會要她回自己房間,而我不會。我甚至試著尋求上帝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位陪伴我渡過成長期不安或焦慮的上帝,不是沒聽就是不理睬。
打敗我的並不是法庭上的辯護律師或陪審團,而是在我自己腦海裡的律師和陪審團。
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慈愛的上帝忍心讓一個孩子被自己父親燒死、打死或強暴;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仁愛的上帝竟會讓一個腦麻孩童慘遭自己母親的男友殺害;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所有事情最終都會朝往好的方向發展,因為對許多無辜之人而言,結局就是死亡,死亡沒有任何談判、妥協或說服的餘地。對於那些倖存下來的人來說,一生將充滿痛苦、恐懼和不信任;他們的問題總是勝過我的回答。我可以告訴他們誰是兇手,只是永遠無法跟他們說清楚原因。
所以我離開法庭的時候,只剩下一點殘餘的信念。我像個憤世嫉俗的人,離開時眼神只剩一絲孱弱的微光。在這些質詢轉化成憤怒、憤怒變成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之前,我就離開了。
現在該怎麼辦?當法庭不再是一個選擇,那些喜歡說服的人能去哪裡?或許是參加更大的陪審團?或許是從政?或許是加入國會?
或許都不是。
說來也怪,我離開國會時對人類的評價,確實比離開法庭時來得高,但我還是選擇離開。我離開法庭是因為那些問題勝過回答,而我離開國會是因為那些問題對政治無關緊要,華盛頓特區幾乎每個人都已經自有一套想法。
即使不在華盛頓特區,幾乎每個人對議題都已有自己的看法。政治是馬不停蹄的,每天都是一場小型選舉日。生活中似乎越來越多的事物帶有政治色彩。職業美式足球聯盟(NFL)被政治化,音樂和電影頒獎典禮涉及政治,颶風與病毒帶有政治色彩,就連在自家廚房的餐桌上,政治也伺機而動,試著插入我們的對話之中。
在國會任職的八年期間,我沒有印象哪個人在委員會或議會辯論期間改變想法。說服需要對方抱持開放的心態,你不能改變一個不願意改變的人,你不能說服一個不願意被說服的人。陪審團成員能夠接受被說服,但國會議員(至少是在現代政治環境下的議員)不願被說服,就算被說服也不肯承認。
在國會工作八年之後,我開始確信所有問題都無關緊要,因為除了我以外,幾乎沒有機會說服任何人。提問的效率極低,但挾帶的訊息量卻相當驚人。奇怪的是,當我在國會的時候,變得更願意被說服。說服我的不是演講或委員會聽證會,而是聰明、可靠的人提出以事實為主的論點,努力讓更多人知道和理解,並且在過程中願意傾聽和瞭解我的立場。
在華盛頓特區的那段歲月讓我瞭解,來到議桌前的人各自擁有不同的經驗,每個人的觀點都是透過那些經驗的濾鏡呈現出來。我同不同意並不重要。每個人理應擁有發言權,如果每個人都能以相同的工具和知識成功地說服對方,那麼爭議就會變成對話,對話變成重要的問題,該問題就能產生真實且有意義的影響。
站在國會大廈的大理石地板上,我領悟到,說服不是爭贏辯論,而是想要迅速且有效地提倡自己相信的事物。說服是一種更加微妙的方法,當你對某個人提出一系列對的問題時,這種方法可以讓對方自然而然走向你希望達到之處。說服就是理解他人的觀點以及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觀點,然後運用說服來揭露或證實他們的立場。說服是不易察覺、漸進且深思熟慮的,很有可能因此改變人生。
想開始學習怎麼說服了嗎?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與兒時好友基斯‧考克(Keith Cox)、還有他的家人在海灘渡假。那年夏天我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我的主修是欠缺方向和動機的歷史。當時的我之所以沒有為往後人生做好規劃,只是因為我沒有規劃未來的渴望。某天上午,我與好友的家人坐在外面的走廊上,眺望著大西洋,基斯母親請我陪她喝完手中的咖啡。其他人都去海灘了。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麼呢,親愛的?」她問道。
「我還不曉得,考克太太,或許會去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Las Cruces),和一個大學同學從事建築工作。」我們坐著聊天,她和藹地向我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問題極多,但這些都是出自於一位母親對兒子最好朋友和從小看著長大孩子的疼愛。她沒有試圖說服我做任何事情。她既不是精神科醫師,也不是律師,她是一位全職媽媽,想盡辦法循序漸進地提出對的問題。
她在那個三十分鐘內達成的事,改變了我的人生。她讓我從原本要去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從事建築,改去就讀法學院。透過傾聽、關心、追問對的問題,她在那天上午請我留步之前就已經看到她的目標,並成功地攻克我的自我懷疑,同時也喚醒我的自豪感。她說:「去讓那些質疑的人大吃一驚,特雷,在生活中做些了不起的事情。你要知道,這些事情之所以不會讓我驚艷,是因為我在你小的時候就見識過了。這是我們的秘密,去讓其他人驚嘆不已吧!」
讓某人去做原本不打算做的事,說服某人相信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尋求的事物,這就是說服力。朋友的媽媽花了三十分鐘,讓我打消念頭跑到半個國家遠的地方蓋房子,決定待在南卡羅萊納州研究侵權行為和憲法。她懷抱同理心、腦中有個預設結果、並提出對的問題,她說服我去做的不只是繼續念三年多的書,也不在乎我是否就讀法學院,她在乎的是讓我對自己懷抱更高的期望,而不是像那天早晨醒來時的那樣。
你可能永遠都不會站在陪審團面前,為刑事訴訟中的某個裁決進行辯護,或在政治競選期間自我爭取當選的機會。你只是想要被傾聽,想要有人理解。你渴望有效地傳達自己的理念、為何有這個理念、以及為何其他人也應該採納你的立場。也許你永遠都不會在激烈的辯論中爭取美國參議院的席次,也許你的人生有比這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說服孩子志向高遠、對自己有更多的期待、更努力地爭取。也許你只是渴望能夠更有效地向同事、家人或伴侶表達自己的立場。也許你渴望大膽說出內心話,但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在工作場所、禮拜會堂或同學聚會上跟人談笑風生。
我想幫助你成為更好的辯護者,透過提問的藝術,讓你在正確的時間點、依循正確的順序、用對的形式提出對的問題,不管你是否知道自己提問的答案,都能完善表達你的想法。說服在某程度上是種積極舉證的責任,但某程度上也是透過質疑的藝術來證明你的觀點。
想開始學習說服他人了嗎?
一開始你必須先回答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這是我最喜歡問的題目,反問自己的內心。我曾以檢察官的身分向警察和一般證人(lay witnesses)提過這個問題,每次出席國會聽證會之前,都會問問自己。現在進行任何演講之前,我也會自我反問,不管演講的對象是面對滿屋子的律師,還是我太太的一年級學生。
你想實現什麼?
這個問題的後面緊接著另一個類似的問題:
你的目標是什麼?
交流結束後,你怎麼衡量成功?
誰是你的陪審團?
證明起來有多困難?
無論你是想說服陪審團判定某個被告犯可能犯下死罪,或是說服你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打掃他/她的房間,在你開始交談之前(在你準備開口之前),先問問自己這些問題。雖然說服青少年去打掃自己的房間確實比較困難,但這也是你日常生活中比較可能碰到的情況。
有的時候,你想達成的目標並不是那麼明確。有時候你渴望打動你的聽眾,讓他們在意識型態光譜上站在你這邊。也許問題不在於讓你的孩子打掃自己房間,而是說服他在大學主修課程方面做些選擇。你必須溫和地引導他們在心中有個特定目標,而不是意圖提出觀點(「請投票支持我的看法,因為我的看法最理想!」)或是證明自己論點(「兒子你要知道,主修英文的學生更有可能成為職場適應力強的應試者。」)。也許重點不在於為你的候選人贏得選票,而是讓別人轉念不投給他們的候選人。有幾次在國會的時候,我的目標不是讓他人跟我一起投票(因為這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而是讓他們投票給自己想要但影響較小的項目,或是讓他們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然後完全錯過委員會的投票(開玩笑的……反正諸如此類)。若是換成我兒子華生,我的目標不是想要他修英文,而是不要去修他的第一選擇政治學。因為沒有哪個青春期的孩子(或是任何人)喜歡被直接告知該做什麼,所以提問就是最隱約且有效的說服方式。他想修政治學,我想要他修英文,最後他選擇哲學。我想我成功了。
無論是與誰交談、誰是你的陪審團,在開口說話之前,你都必須充分掌握自己的目標。
你是想建立關係、修復關係、提升關係,還是結束關係?
你是想安撫糾紛還是激怒他人?
你的目標是達成共識還是造成衝突?
如果你的目標是讓關係破裂、激怒聽眾、認可一些人堅持但卻錯誤的想法,那麼這本書不會給予太多的幫助。在與其他人或團體的大多數交談方面,我的目標是溫和地讓傾聽者轉變到新的立場,或是讓對方對舊的想法重新燃起熱情。
那麼要如何說服別人?哪些作法管用?哪些作法不行?
我們將在本書探討如何說服、為何說服是最值得採用的技巧、以及你可以使用什麼工具,讓你在面對生活上的重要問題和重要人物時變得更有說服力。
在第一部分,我們的焦點將擺在自我導向的問題方面,並在本質上奠定基礎:為何提問?什麼是真正的說服力?我會幫助你找到自己的目標、認識你的陪審團、確立你的證明責任,並且引導你在成為好的溝通者時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無效。
一旦瞭解這些要素,你就可以開始進行說服。在第二部分,自我導向的問題將轉向並針對被說服者。我們這裡的焦點將擺在你可以使用的特定問題類型,還有幫助你擬定問題的工具。有時候是認真的提問,真的想要獲取資訊的問題;有時候是策略性的提問以得到想要的答案;有時候答案並不重要,而是為了引起反應,為了拆穿和質疑你的「陪審團」。
第三部分會告訴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將說服的藝術付諸行動。雖然我可能是個憤世派,但說服大多與理想主義有關。說服指的是,思想開放的人能夠就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指的是,那些立場對立的人都願意傾聽且願意被說服。
不可否認,當我們對於某些自己信仰的事物慷慨激昂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受到感召,要代替它們讓人改變信仰,並且不惜代價去這樣做。但說服是以建設性的方式來達成。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提出對的問題,這門說服藝術是你溝通的關鍵。事實上,如果你想要打動你交談對象的內心和思想,提出對的問題、傾聽對方的回應,並且有條理地採取進一步行動將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因此,我們說服他人的目標應該有以下:努力和那些與我們交談的人溝通並且打動他們。讓他人從同意變成不同意;讓他人的立場變得不確定;讓他人理解我們的立場;讓他人從新的觀點和視野看待事情;讓他們感受到你的感受、理解你所理解的、思考你所思考的。打動他們去做值得做的事情、好的事情和對的事情;說服他們聘用你、給你機會、給你更多的責任。打動他人嘗試採用你的想法,讓他人對於你投入的事物也有一樣程度的投入。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從法庭走到國會
為什麼要說服
十六年來,我面對過無數組沒有成功躲過義務的十二人陪審團。(好吧,這樣說可能不公平,但認了吧!幾乎不會有人興高采烈地收下傳票。)然而,就我的經驗來看,儘管對於出席猶豫不決,但大多數人最後都會享受著參加陪審團服務的樂趣,或者最起碼也領會到美國司法制度的權威性。法庭反映出真實人生,顯示了所有痛苦和快樂、正義和不公、以及源生於試圖掌控和裁決人性的原始情感。雖然你可能不太有機會走進法庭,但「審判」同樣存在生活的各個角落,那些「審判」可能出現在商業場合、社群會議、學校或家中。
我在聯邦法院和州法院經歷過近百場的陪審團審判,案件範圍從槍枝違法到毒品走私、擄人勒贖到劫車、性侵害到搶劫、兒童虐待到謀殺,法庭已經成為我感到最平靜和最舒適的地方。我喜歡這種的邏輯思維,喜歡這裡的遊戲規則,喜歡策畫謀略,喜歡這種需要快速思考的地方,喜歡有機會追求真理,喜歡整個以人和程序為縮影的人類光譜。但最重要的,我之所以喜歡法庭,是因為我熱愛說服的藝術,而且我一直竭盡所能地將這門藝術做到最好。
我所做的一切都要歸功於我的母親。在我和三位妹妹成長的過程中,母親做過許多有益的事情,但她最喜歡的工作是在地方律師事務所擔任受害者辯護人(victim advocate),為犯罪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諮詢,說明他們身為受害者的權益,替他們揭開刑事訴訟過程的神祕面紗。如有需要或要求,受害者辯護人會與受害者及其家屬一起出席審判、抗辯和量刑聽證會。
當我大學和法學院暑假期間在家時,母親下班回來後會流露對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沮喪之情,並公然質疑:「為什麼被告、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雇用任何他或她想要的律師,而受害者卻無法?受害者只能跟指派辦理此案的檢察官綁在一起,為什麼受害者不能聘請最好的律師?」
問得好,媽。我知道教科書的答案是什麼――因為刑事犯罪實際上屬於侵害國家,並非針對個人――但教科書的答案不能給予受害者什麼安慰,受害者必須受到資深刑事辯護律師的詰問,而犯罪者卻未必會受到資深檢察官的詰問。媽,妳說得沒錯。受害者應該有權聘請好的律師,聘請能夠在開審陳述中為其正確預期做好鋪陳的律師;受害者應該有權聘請能夠直接提問,巧妙地以令人信服、邏輯方式誘導證詞的律師;他們應該有權聘請不用低頭看筆記就能有效盤問被告的律師,有權聘請在終結辯論時能結合激情與理性,讓陪審團達成共識的律師,聘請一位甚至能夠克服美國司法認可的最嚴苛舉證責任(即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律師;他們有權聘請一位能夠預測被告辯護律師的下一步,並採取謀略應對的律師;他們有權找一位懂得說服藝術的律師。
即使在法庭之外,人們也希望自己既能得到有效的辯護,又能成為有效的辯護人。如果工作中出現關於升遷或新業務機會的談話機會,你會想參與其中,而要成為談話的一員,可能與你是不是有效的溝通者有相當大的關係。事實上,你會想成為談話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這就是我在法庭上十六年來努力達成的目標:成為受害者願意選擇的辯護人,假如他或她真能像我母親心裡期盼的那樣,能夠挑選國內任何一位律師來擔任他們律師的話……。擔任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的實質辯護人須背負沉重的壓力,但在你日常生活的其它領域,這種壓力並不會減輕多少,你也需要為某些事或某個人成功辯護,你也需要說服他人在某個議題上更接近你的思路,或者至少瞭解你為何相信自己的想法。法庭是我的工作場所,而你也有你自己的工作場所,你我都一樣,都需要有能力進行訊息處理和溝通,以便達到預期結果。無論議題是關於謀殺案件、行銷或是身為人母。
我有時候會稱為「謝客」(receiving line)工作。那些是你希望別人在你離開時還能記住你的工作。如果我比太太先行離世,我會請她做兩件事:一、等我葬禮結束後再開始約會;二、確保我們孩子記得,他們父親最喜歡的工作是擔任檢察官。我會希望別人記住我這份工作,因為這是一份最有意義、最有目標、也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在公平和正當的程序下說服陪審團,利用具備可信度、符合事實、推理、合乎邏輯以及豐富多元的言詞表達,讓陪審團的判決從無罪到有罪。
溝通對話要如何進行,你會有你自己的版本,因為這些與你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但現在就開始思考你想在生活、工作和愛情方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永遠不嫌太早。
還有一件事我希望我太太別忘記:三、確保我們身旁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們能記得我上次起訴的案件,以及我為何這樣做的原因。
若你去過我在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想知道擺在我全家福照片旁邊的照片上那個小女孩是誰的話,她就是我處理過最後一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她是我最後一次站在陪審團面前的原因。
從小罹患先天腦性麻痺的十歲女童梅‧懷德(Meah Weidner),遭母親男友痛下毒手毆打並搖晃致死。母親男友是一名消防員和緊急救護技術員(EMT),沒有任何犯罪紀錄。根據他的說法,女童的傷勢是她癲癇發作從輪椅上摔下來造成的,並聲稱自己可能是替她進行心肺復甦時不小心弄傷了她。但他堅稱,這只是一場意外,並非犯罪行為。
當時我已經一隻腳踏在法庭外,準備前往國會的路上,距離就職宣誓只剩幾個星期。辦公室裡肯定會有別人接下這起案件,我們辦公室裡面有許多非常優秀的檢察官,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替梅討回公道。但我母親的聲音始終在腦海中縈繞:「為什麼被告可以用錢請到最好的律師,受害者卻不能?」
母親的聲音,加上自己身為人父的心情,促使我接下卷宗親自辦案。我想為那位再也不能說話的小女孩發聲,我想保護那位無法保護自己的女孩,為了那位坐在輪椅上的女孩,我願在陪審團面前來回踱步,珍視她生命的程度就如同人們珍視自己孩子一樣。我會代替她進行有效的說服,因為這是符合公平且正義的事。
要讓十二名陪審團相信,眼前這位有好工作、沒有前科的男子殺害一名手無寸鐵的孩童,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但事實就是如此,所以我運用邏輯、真相以及最重要的提問來進行說服工作。
我向陪審團提了幾個問題。當然,有些問題是要讓他們瞭解必要資訊,進而形成完善的觀點;有些是他們和我都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但是,所有問題的最終目的,都是要讓他們自行判斷真相。
最後,陪審團十二人都認定他「有罪」,判定該男子殺害了梅‧懷德,法官判處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從法庭內的氣氛和陪審團達成裁定的速度可以清楚看出,他們被這位年幼女孩的生命所打動,令他們能同理我的感受,令他們能對梅生命的珍視程度就如同對自己的子孫輩一樣,使他們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把梅的照片擺在辦公桌上,可以提醒我許多事情:莫忘生命的脆弱、年輕人的純真、為他人挺身而出的動力,以及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為某些重要事情辯護的時候。不可否認,利用問題來改變他人是一種獨特的說服方式,但我相信,提問是最高層次說服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多數人都可以藉由說明自己觀點和解釋原因來說服別人,但你能在適當的時間和順序裡提出適當的問題來說服他人嗎?更重要的,你能讓與你交談的人說服他們自己嗎?
你不需要在法庭上為別人辯護,也不需要加入國會捍衛某個理想。說服他人的機會比比皆是,從法庭到客廳、從街道對面的鄰居到辦公桌對面與客戶交談、從說服陪審團到說服老闆,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和偶爾有義務要去說服他人。
最有說服力的人傾聽跟講話一樣多;最有說服力的人,問的問題與回答的問題一樣多。提問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想讓別人更瞭解你的立場,或者只是讓他人相互瞭解,那麼在對的時間用正確的方法提問,可能會是你最有效的工具。
達成共識?也許不會
十六年的檢察官生涯教會我如何成為一名律師,教會我瞭解本國公民,教會我如何與他們溝通、說服他們,用確鑿的證據勸誘他們,也教會我如何拆解不可靠的證據。法庭是一種文化與人類學的培養皿,在這裡,人類光譜的所有面向都會受到考驗、分析及審判。這就是為什麼適用於法庭的溝通技巧也能實際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你在自家客廳或會議室運用我們司法體系所採用的流程與程序,可能會有人跟你說:「這裡又不是法庭。」已故的以利亞‧康明茲(Elijah Cummings)在擔任國會議員之前是名傑出的律師,他有次在委員會聽證會溫和地責怪我說:「這裡是法庭嗎?……難道這裡採用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嗎?」美國前國稅局(IRS)局長約翰‧柯斯基寧(John Koskinen)和我在委員會會議室外總保持良好關係,某次他在回答問題時問說:「請問現在是審訊嗎?這裡有人正在受審嗎?」不是的,委員會聽證會並非法庭,這裡也不遵循法庭在證據、程序或流程方面的規則,但也許它們應該遵循。美國司法體系所採用的那些政策、規則、程序和法規並非只是因為在法庭使用,所以本質上合乎「公正性」。它們之所以能在法庭上使用,是因為承受得住時間的考驗,我們集體認同這些規章是闡明真相的最佳工具。換句話說,只因為在法庭上使用就說這些規章合乎公正性是不對的說法,這些規章能夠在法庭上使用,是因為這些是公正的規則。公正性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我熱愛正義、公平、追求真理及說服陪審團,但我還是離開了法庭,因為我無法回答自己關於法庭以外所發生的問題。我無法使我的精神信仰與每天所見事物達成一致。人類彼此越來越殘忍,傷害無辜,殺害自己聲稱所愛之人,弱勢族群成為受害者。社會滋生無端暴力、道德敗壞、充滿仇恨。
在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善良、仁慈、守法,樂於助人。但在司法體系情況並非如此,導致最後對人性產生錯誤認知。法庭不會審判好人、正直或善良的人,這些審判都是針對那些謀殺、強姦或竊盜之人。當你每天都與這些人往來時,你對人類的想法很快就會與社會脫節。當你眼裡看到的只有邪惡,你就會誤以為邪惡就是一切。
我記得,在我越來越懷疑人性時,常常想起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引自聖經某段經文):「萬事皆互相效力得益處。」(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人應該經常聽到這句話。
萬事皆如此嗎?那些被菸頭燙臉的孩子們呢?被性侵的孩子呢?被榔頭打死的無辜夫婦呢?因遭到父親強暴而需縫合傷口的三個月大的孩子呢?那麼梅呢?這些難道就是神祢所謂「萬事皆互相效力得益處」的意思?
我在法庭上的表現相當不錯,幾乎能在任何想要和必要的時候,說服十二人排除所有合理懷疑。十六年來,我可以讓十二個完全陌生的人齊聚一堂並達成共識,對我來說,無論是說服美國公民或法官,都不是什麼難事。
難的是每天晚上下班後,我從法庭開車返家,那些答案開始被一個個反詰問句擊垮。到最後,白晝逐漸被黑夜取代,我努力想抹去腦海中對犯罪現場照片的記憶。家人熟睡的時候,我在床上輾轉難眠,努力分辨外頭傳來的是風聲還是趁勢闖入的邪惡和墮落聲響。我難以將工作與生活其餘部分切割開來,對我最親愛的家人亦是如此。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家女兒會拖著她的枕頭和毯子到我跟我太太的臥室,然後放在我們床邊地板上。她一定是放在我睡的這個方向,因為她知道媽媽會要她回自己房間,而我不會。我甚至試著尋求上帝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位陪伴我渡過成長期不安或焦慮的上帝,不是沒聽就是不理睬。
打敗我的並不是法庭上的辯護律師或陪審團,而是在我自己腦海裡的律師和陪審團。
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慈愛的上帝忍心讓一個孩子被自己父親燒死、打死或強暴;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仁愛的上帝竟會讓一個腦麻孩童慘遭自己母親的男友殺害;我永遠無法說服自己,所有事情最終都會朝往好的方向發展,因為對許多無辜之人而言,結局就是死亡,死亡沒有任何談判、妥協或說服的餘地。對於那些倖存下來的人來說,一生將充滿痛苦、恐懼和不信任;他們的問題總是勝過我的回答。我可以告訴他們誰是兇手,只是永遠無法跟他們說清楚原因。
所以我離開法庭的時候,只剩下一點殘餘的信念。我像個憤世嫉俗的人,離開時眼神只剩一絲孱弱的微光。在這些質詢轉化成憤怒、憤怒變成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之前,我就離開了。
現在該怎麼辦?當法庭不再是一個選擇,那些喜歡說服的人能去哪裡?或許是參加更大的陪審團?或許是從政?或許是加入國會?
或許都不是。
說來也怪,我離開國會時對人類的評價,確實比離開法庭時來得高,但我還是選擇離開。我離開法庭是因為那些問題勝過回答,而我離開國會是因為那些問題對政治無關緊要,華盛頓特區幾乎每個人都已經自有一套想法。
即使不在華盛頓特區,幾乎每個人對議題都已有自己的看法。政治是馬不停蹄的,每天都是一場小型選舉日。生活中似乎越來越多的事物帶有政治色彩。職業美式足球聯盟(NFL)被政治化,音樂和電影頒獎典禮涉及政治,颶風與病毒帶有政治色彩,就連在自家廚房的餐桌上,政治也伺機而動,試著插入我們的對話之中。
在國會任職的八年期間,我沒有印象哪個人在委員會或議會辯論期間改變想法。說服需要對方抱持開放的心態,你不能改變一個不願意改變的人,你不能說服一個不願意被說服的人。陪審團成員能夠接受被說服,但國會議員(至少是在現代政治環境下的議員)不願被說服,就算被說服也不肯承認。
在國會工作八年之後,我開始確信所有問題都無關緊要,因為除了我以外,幾乎沒有機會說服任何人。提問的效率極低,但挾帶的訊息量卻相當驚人。奇怪的是,當我在國會的時候,變得更願意被說服。說服我的不是演講或委員會聽證會,而是聰明、可靠的人提出以事實為主的論點,努力讓更多人知道和理解,並且在過程中願意傾聽和瞭解我的立場。
在華盛頓特區的那段歲月讓我瞭解,來到議桌前的人各自擁有不同的經驗,每個人的觀點都是透過那些經驗的濾鏡呈現出來。我同不同意並不重要。每個人理應擁有發言權,如果每個人都能以相同的工具和知識成功地說服對方,那麼爭議就會變成對話,對話變成重要的問題,該問題就能產生真實且有意義的影響。
站在國會大廈的大理石地板上,我領悟到,說服不是爭贏辯論,而是想要迅速且有效地提倡自己相信的事物。說服是一種更加微妙的方法,當你對某個人提出一系列對的問題時,這種方法可以讓對方自然而然走向你希望達到之處。說服就是理解他人的觀點以及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觀點,然後運用說服來揭露或證實他們的立場。說服是不易察覺、漸進且深思熟慮的,很有可能因此改變人生。
想開始學習怎麼說服了嗎?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與兒時好友基斯‧考克(Keith Cox)、還有他的家人在海灘渡假。那年夏天我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我的主修是欠缺方向和動機的歷史。當時的我之所以沒有為往後人生做好規劃,只是因為我沒有規劃未來的渴望。某天上午,我與好友的家人坐在外面的走廊上,眺望著大西洋,基斯母親請我陪她喝完手中的咖啡。其他人都去海灘了。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麼呢,親愛的?」她問道。
「我還不曉得,考克太太,或許會去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Las Cruces),和一個大學同學從事建築工作。」我們坐著聊天,她和藹地向我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問題極多,但這些都是出自於一位母親對兒子最好朋友和從小看著長大孩子的疼愛。她沒有試圖說服我做任何事情。她既不是精神科醫師,也不是律師,她是一位全職媽媽,想盡辦法循序漸進地提出對的問題。
她在那個三十分鐘內達成的事,改變了我的人生。她讓我從原本要去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從事建築,改去就讀法學院。透過傾聽、關心、追問對的問題,她在那天上午請我留步之前就已經看到她的目標,並成功地攻克我的自我懷疑,同時也喚醒我的自豪感。她說:「去讓那些質疑的人大吃一驚,特雷,在生活中做些了不起的事情。你要知道,這些事情之所以不會讓我驚艷,是因為我在你小的時候就見識過了。這是我們的秘密,去讓其他人驚嘆不已吧!」
讓某人去做原本不打算做的事,說服某人相信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尋求的事物,這就是說服力。朋友的媽媽花了三十分鐘,讓我打消念頭跑到半個國家遠的地方蓋房子,決定待在南卡羅萊納州研究侵權行為和憲法。她懷抱同理心、腦中有個預設結果、並提出對的問題,她說服我去做的不只是繼續念三年多的書,也不在乎我是否就讀法學院,她在乎的是讓我對自己懷抱更高的期望,而不是像那天早晨醒來時的那樣。
你可能永遠都不會站在陪審團面前,為刑事訴訟中的某個裁決進行辯護,或在政治競選期間自我爭取當選的機會。你只是想要被傾聽,想要有人理解。你渴望有效地傳達自己的理念、為何有這個理念、以及為何其他人也應該採納你的立場。也許你永遠都不會在激烈的辯論中爭取美國參議院的席次,也許你的人生有比這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說服孩子志向高遠、對自己有更多的期待、更努力地爭取。也許你只是渴望能夠更有效地向同事、家人或伴侶表達自己的立場。也許你渴望大膽說出內心話,但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在工作場所、禮拜會堂或同學聚會上跟人談笑風生。
我想幫助你成為更好的辯護者,透過提問的藝術,讓你在正確的時間點、依循正確的順序、用對的形式提出對的問題,不管你是否知道自己提問的答案,都能完善表達你的想法。說服在某程度上是種積極舉證的責任,但某程度上也是透過質疑的藝術來證明你的觀點。
想開始學習說服他人了嗎?
一開始你必須先回答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這是我最喜歡問的題目,反問自己的內心。我曾以檢察官的身分向警察和一般證人(lay witnesses)提過這個問題,每次出席國會聽證會之前,都會問問自己。現在進行任何演講之前,我也會自我反問,不管演講的對象是面對滿屋子的律師,還是我太太的一年級學生。
你想實現什麼?
這個問題的後面緊接著另一個類似的問題:
你的目標是什麼?
交流結束後,你怎麼衡量成功?
誰是你的陪審團?
證明起來有多困難?
無論你是想說服陪審團判定某個被告犯可能犯下死罪,或是說服你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打掃他/她的房間,在你開始交談之前(在你準備開口之前),先問問自己這些問題。雖然說服青少年去打掃自己的房間確實比較困難,但這也是你日常生活中比較可能碰到的情況。
有的時候,你想達成的目標並不是那麼明確。有時候你渴望打動你的聽眾,讓他們在意識型態光譜上站在你這邊。也許問題不在於讓你的孩子打掃自己房間,而是說服他在大學主修課程方面做些選擇。你必須溫和地引導他們在心中有個特定目標,而不是意圖提出觀點(「請投票支持我的看法,因為我的看法最理想!」)或是證明自己論點(「兒子你要知道,主修英文的學生更有可能成為職場適應力強的應試者。」)。也許重點不在於為你的候選人贏得選票,而是讓別人轉念不投給他們的候選人。有幾次在國會的時候,我的目標不是讓他人跟我一起投票(因為這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而是讓他們投票給自己想要但影響較小的項目,或是讓他們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然後完全錯過委員會的投票(開玩笑的……反正諸如此類)。若是換成我兒子華生,我的目標不是想要他修英文,而是不要去修他的第一選擇政治學。因為沒有哪個青春期的孩子(或是任何人)喜歡被直接告知該做什麼,所以提問就是最隱約且有效的說服方式。他想修政治學,我想要他修英文,最後他選擇哲學。我想我成功了。
無論是與誰交談、誰是你的陪審團,在開口說話之前,你都必須充分掌握自己的目標。
你是想建立關係、修復關係、提升關係,還是結束關係?
你是想安撫糾紛還是激怒他人?
你的目標是達成共識還是造成衝突?
如果你的目標是讓關係破裂、激怒聽眾、認可一些人堅持但卻錯誤的想法,那麼這本書不會給予太多的幫助。在與其他人或團體的大多數交談方面,我的目標是溫和地讓傾聽者轉變到新的立場,或是讓對方對舊的想法重新燃起熱情。
那麼要如何說服別人?哪些作法管用?哪些作法不行?
我們將在本書探討如何說服、為何說服是最值得採用的技巧、以及你可以使用什麼工具,讓你在面對生活上的重要問題和重要人物時變得更有說服力。
在第一部分,我們的焦點將擺在自我導向的問題方面,並在本質上奠定基礎:為何提問?什麼是真正的說服力?我會幫助你找到自己的目標、認識你的陪審團、確立你的證明責任,並且引導你在成為好的溝通者時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無效。
一旦瞭解這些要素,你就可以開始進行說服。在第二部分,自我導向的問題將轉向並針對被說服者。我們這裡的焦點將擺在你可以使用的特定問題類型,還有幫助你擬定問題的工具。有時候是認真的提問,真的想要獲取資訊的問題;有時候是策略性的提問以得到想要的答案;有時候答案並不重要,而是為了引起反應,為了拆穿和質疑你的「陪審團」。
第三部分會告訴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將說服的藝術付諸行動。雖然我可能是個憤世派,但說服大多與理想主義有關。說服指的是,思想開放的人能夠就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指的是,那些立場對立的人都願意傾聽且願意被說服。
不可否認,當我們對於某些自己信仰的事物慷慨激昂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受到感召,要代替它們讓人改變信仰,並且不惜代價去這樣做。但說服是以建設性的方式來達成。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提出對的問題,這門說服藝術是你溝通的關鍵。事實上,如果你想要打動你交談對象的內心和思想,提出對的問題、傾聽對方的回應,並且有條理地採取進一步行動將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因此,我們說服他人的目標應該有以下:努力和那些與我們交談的人溝通並且打動他們。讓他人從同意變成不同意;讓他人的立場變得不確定;讓他人理解我們的立場;讓他人從新的觀點和視野看待事情;讓他們感受到你的感受、理解你所理解的、思考你所思考的。打動他們去做值得做的事情、好的事情和對的事情;說服他們聘用你、給你機會、給你更多的責任。打動他人嘗試採用你的想法,讓他人對於你投入的事物也有一樣程度的投入。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目次
導言 從法庭走到國會
第一部分 在你開口前需要知道哪些事?
第一章 世上沒有蠢問題?才怪!
第二章 說服是一門微妙的藝術
第三章 確認目標、認清事實、瞭解你自己!
第四章 知道你的陪審團是誰
第五章 評估你的目標與舉證責任是否相符
第六章 一旦學會偽裝真誠,那其它沒什麼是你做不來的
第二部分 提問與說服的行為和藝術
第七章 證實 VS. 反駁
第八章 誘導性問題與非誘導性問題
第九章 有技巧的質疑
第十章 教你怎麼「搭便車」──順水推舟
第十一章 重複、重複、再重複
第十二章 注意你的措辭
第十三章 小改變大收穫――重新包裝就有不錯的效果
第十四章 當辯論居於下風怎麼辦?
第三部分 勇往直前,贏得人心
第十五章 期望值不要設太高
第十六章 如何知道你已經抓到說服的訣竅?
第十七章 我的終結辯論
致謝
第一部分 在你開口前需要知道哪些事?
第一章 世上沒有蠢問題?才怪!
第二章 說服是一門微妙的藝術
第三章 確認目標、認清事實、瞭解你自己!
第四章 知道你的陪審團是誰
第五章 評估你的目標與舉證責任是否相符
第六章 一旦學會偽裝真誠,那其它沒什麼是你做不來的
第二部分 提問與說服的行為和藝術
第七章 證實 VS. 反駁
第八章 誘導性問題與非誘導性問題
第九章 有技巧的質疑
第十章 教你怎麼「搭便車」──順水推舟
第十一章 重複、重複、再重複
第十二章 注意你的措辭
第十三章 小改變大收穫――重新包裝就有不錯的效果
第十四章 當辯論居於下風怎麼辦?
第三部分 勇往直前,贏得人心
第十五章 期望值不要設太高
第十六章 如何知道你已經抓到說服的訣竅?
第十七章 我的終結辯論
致謝
書摘/試閱
第一章
世上沒有蠢問題?才怪!
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凶殺案是一件嚴肅悲傷的事,一條生命已經消逝,另一人正在接受審判,面臨終身監禁的現實,沒有假釋的機會,或者更嚴重的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所以你能想像得到,在任何刑事審判中都沒有幽默的空間。然而,我在第一次進行死刑審判時卻讓全場都笑出眼淚了。那些說「世上沒有蠢問題」的人,都不是二〇〇一年秋天坐在斯帕坦堡郡法庭(Spartanburg County Courthouse)裡面的人。
在這起案件中,一名超商店員因為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遭到搶劫並殺害。該名店員工作勤奮,為人善良且正直,在生活上克服過很多困難,如果嫌犯開口要錢,他會把錢給嫌犯的那種人。
大多數像這樣的案件,只有兩名當事人,而且一名(受害人)已經死亡,所以除了法醫鑑識或任何可能持有的物證之外,你得仰賴被告的肯定性陳述、供詞或不實的辯解陳述。但在這起案件裡,還有另一名目擊證人,當搶劫和槍擊事件發生時,他正坐在一旁玩電動撲克遊戲。
當你有了額外的目擊證人,就會想提前跟他們見面,瞭解要講的內容以及該如何準備。在這起案件中,我與該名目擊證人見過很多次。他非常重要(事實上是極其重要),雖然他在死刑審判中作證時可能會很緊張,但其態度誠懇且可靠。
現在是他出庭表態的時候了。敘述背景給陪審團聽是很重要的事,包括商店規模、證人與收銀機和店員的相對位置、他可以觀察的機會、沒有毒品或酒精影響他的感知能力、以及其它預設陪審團可能會提的問題。
「你和超商前門之間有任何物品嗎?」
「沒有。」
「有任何東西擋住你的視線嗎?」
「沒有。」
「燈是否開著?」
「是的。」
「室內是否煙霧瀰漫或昏暗?」
「沒有。」
「你當時有喝醉嗎?」
「沒有。」
「抱歉問個涉及私人的問題,請問你有沒有服用過處方藥或其它藥物?」
「沒有。」
「嫌疑人走過前門的時候,你注意到他了嗎?」
「有。」
「嫌疑人進門的時候,超商內還有其他人嗎?」
「只有我跟店員。」
「嫌疑人走進來時,你的視線有離開過他嗎?」
「沒有。」
「你有看清楚嫌疑人的長相嗎?」
「有。」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了?」
「那個人走到櫃台前面,然後掏出一把槍。」
「你看得到那把槍嗎?」
「可以。」
「你能向陪審團描述那把槍的樣子嗎?」
「好。槍是黑色的,看起來像手槍,但不是左輪手槍。」
到目前為止該證人都表現得很好,應訊對答一切正常,清楚且精確。但顯然我並沒有就此滿意,我必須繼續問下去。
「先生,我注意到你沒有戴眼鏡,那天晚上你有戴眼鏡嗎?」
「沒有。」
「你的視力很好嗎?」
「對,我的右眼視力很好。」
他剛剛說了什麼?證人先生,你不是獨眼巨人!你有兩隻眼睛啊!
我內心這麼想著。
我給自己惹了什麼麻煩?我該怎麼解套?接下來我該問什麼、說什麼?我應該到此為止,然後希望陪審團沒有聽到他說的話嗎?還是希望陪審團不記得所有人類都有兩隻眼睛?你必須做點什麼,笨蛋特雷,你不能就這樣懸在空中!
「是啊是啊,你的右眼視力當然很好,」我只能這樣說。
「那麼你的左眼……呢?」(換來一陣痛苦的沉默)
「左眼是假的。」
「嗯,是啊,先生,左眼是義眼。」
「對……,左眼是假的,」他回答。
我有一位目擊證人,但我與其他人一樣現在才發現,他只有一隻眼睛看得到。
我很不安,此時我真希望自己出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去伊夫堡(Château d’If)怎麼樣?帶我走!任何地方都好過待在這個法庭。我們在出庭之前,完全沒有問過證人的眼睛狀況。沒有比這更糟的情況了,對吧?但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
「接下來發生什麼了?」我問道。
「嗯,嫌疑人手裡拿著一個藍色袋子。」
「好,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整個法庭哄堂大笑,而那隻眼睛一直看著我,彷彿我瘋了一樣。
也許他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於是我又重複一遍問題,「先生,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更多笑聲傳來。
怎麼回事?為什麼大家會在死刑審判中大笑?
還沒等我重複第三次這個英語系國家史上最愚蠢的問題,法官便大發慈悲地說:「地區檢察官,我想陪審團現在知道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了!你可以繼續問下一題了。」
提問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提問可能是真心想要得到更多的資訊。提問可能是為了再三確認。有些問題你已經知道答案,但你的「陪審團」可能有些人並不知道,所以你用提問的方式來傳遞訊息給他人而不是自己。提問可能是質疑或削弱對方論點。提問可能具有防禦性,讓你重新整編、轉移、重新引導別人的注意力,以待下回反擊論點的機會。
還有一些就是很愚蠢的問題。
問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時候同樣一個問題的好壞是根據提問的情況而定。若是審訊前幾週,在我的辦公室裡詢問我的目擊證人關於他的視力,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在法務官辦公室(Solicitor’s Office) 的工作人員給了我一張這次審判庭上的照片,是當地一家報紙的攝影師在證人說「我的右眼視力很好」時所拍攝的。我的工作人員之所以拿那次審判的照片給我,是因為當證人提到他的一隻眼睛時,我的臉部完全沒有明顯的反應。我的內心其實在垂死掙扎,但陪審團從我的外表看不出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問了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才讓這個錯誤變得更嚴重。我撐過了第一個糟糕的問題,卻因問了第二個糟糕的問題而錯失時機。
防禦機制
沒有人天生就知道如何提出對的問題。即使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不一定擅長提問。這樣做的藝術可能源自於多個推動力,對我而言,提問是幾個思路的匯集,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承認人性的本質是喜歡說話多於傾聽;(3)在無止盡的內心對話中花費了許多時間;(4)意識到問對的問題是扭轉局面的黑魔法(devilish way)。
使用疑問句而非陳述性語句的首要動機是,我把提問當成一種防禦機制,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我從不認為自己聰明到可以加入聰明人士的對話,但我對他們的領域很感興趣。
我爸爸很聰明,他是名醫生,所以我會問他一些關於醫學的問題。例如血壓的最高數字代表什麼意思?為什麼95算是高靜止心率(resting heart rate)?孩童怎麼會罹患白血病?
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基斯‧考克最後考上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並成為口腔外科醫生,他真的很聰明。我應該讓他知道我並不聰明,還是問些問題來掩飾?
蘭迪‧貝爾(Randy Bell)法官是我一生中遇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是南卡州上訴法院的法官,最後獲選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不幸在就職前逝世。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上訴法院任職,那是我剛從法學院畢業的第一年。他是洗腎病患,固定從南卡州哥倫比亞前往喬治亞州奧古斯塔進行洗腎,所以需要有人接送,於是我接下這項任務。他是法律學者、羅馬文化方面的專家,而且對英美法系(English common law,或稱判例法)相當熟悉,能夠引導關於自然法和實證主義的討論。想在蘭迪‧貝爾這樣的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是人之常情,我想談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然後展開對話。記得我們剛認識不久的某天下午,我開車送他到奧古斯塔,他在講述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但當時我對此一無所知。然後他把話題轉移至共同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又稱混和過失、可歸責於己的過失)與比較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我對該話題也不清楚。他不斷變換話題,從羅馬神話講到道義論(deontology),試圖找到一些話題、任何可以讓我參與對話的主題。
但他默驢技窮了。
最後他問我:「孩子,你都知道些什麼?你想談些什麼?」
我其實想聊的是自己怎麼會和一位羅馬法專家待在車上,但我卻回他:「NASCAR(全美運動汽車競賽,又譯美國房車改裝賽),我最近喜歡上NASCAR。」
「很好,」他回應道:「跟我聊聊NASCAR的起源吧。」
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我只知道理查‧佩蒂(Richard Petty),就這樣,法官大人。」
那是我人生中另一個最糟時刻。我擁有歷史學士學位和法律學位,卻沒有真正的知識,我和即將成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坐在同一輛車,他拼命試著找尋世界上任何一個我熟悉的領域,可以在往返南卡州哥倫比亞與喬治亞州奧古斯塔的旅途空檔中聊天的話題,結果卻一無斬獲。我也經常出現自卑的失落感:我覺得自己真的不聰明,我該如何偽裝?我該如何掩飾缺點?要怎麼在不暴露巨大知識落差的情況下參與對話或專業互動?
你可以選擇迅速變聰明,或者找到一種方法來完全掩飾自己認為的知識匱乏。你可以選擇填補知識缺口或選擇填補時間,又或者,你可以找到一種同時滿足兩者的方法,那就是提問。
當時面對貝爾法官或許可以這樣說:
我不瞭解羅馬神話,但我對希臘神話有點印象。希臘眾神與羅馬眾神一樣嗎?還是他們只是名字不同?你最喜歡的神話人物是誰?如果可以選擇,貝爾法官你想要哪種神話人物的力量?比起雅典,你似乎更喜歡羅馬?為什麼呢?你能跟我聊聊斯巴達文化嗎?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
英美判例法嗎?我對這方面不太瞭解。但以我懂得的範圍內可以去問,為什麼有些判例法是由立法機關編纂或通過,但有些卻不是?如果判例法與成文法(statutory law)之間出現衝突,以哪個法條為主?請問貝爾法官,有聯邦判例法(federal common law)嗎?
你可以利用人類最主要的需求之一來學習和消磨時間,那就是被傾聽的渴望。大多數人都有想要說話的天性,所以我利用了這點。比起傾聽,人類更愛說話,若能善加利用人性,我就能掩飾自己的不足。因此,我用不想被人認為無知的渴望來壓抑或取代自己想被傾聽的渴望――如此一來,對你我不都是雙贏嗎?你可以盡情說話,我可以傾聽和學習,還能避免未能達到對方期望的那股失落感。相信我,提問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
愚蠢的問題總比愚蠢的答案好
每當談到說服的藝術,我們通常會想到以下形式:開場白、提出主張、闡述論點。接著是一連串的說明、陳述、證實、描述、聲明、發言,慢慢地建構一個論點,然後盡可能減少漏洞並補充更多有力的主張。這是傳統模式,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呢?
我們一般不會想到可以藉由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來達到說服目的,人們通常認為提問是被動而非主動的行為,對吧?提問有時會被當成是不知道某件事答案的證據,提問會讓人顯得軟弱、狀況外、無知、不確定。那也許是別人想讓我們以為的樣子,但那與我自己的經驗截然相反。提問可以爭取時間、蒐集訊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以那種無法靠簡單表明自己理念的方式進行說服。
前面大家已經見證到,「世上沒有蠢問題」這句古諺在我的例子裡輕而易舉就被推翻,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認可的道理。固然有一些思慮不周、措辭不當和不明智的問題,但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比愚蠢的陳述聲明好上一千倍。
從自己口中說出的每一句陳述性評論都要自己負責,但若以提問方式,你的說法就會有個台階下。正因如此,提問也許是說服藝術中最重要且最保險的方式。
無論是問什麼內容,如果原本想法大錯特錯,你可以回說:「我不知道,所以才會問。」如果原本想法無誤,你可以回說:「我也這麼認為。」除了尋求更多的資訊,你不會有任何愧疚感,這就是聽起來愚蠢和真愚蠢之間的差別。
聽起來愚蠢的問法會是:《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作者是誰?
真愚蠢的說法會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是《罪與罰》的作者。
當然,前者顯示了缺乏資訊的情況,但後者暴露出你自以為知道但實際並不知道的情況,從那一刻起,所有從你口中說出來的話都變得不可靠。前者只是無心的記憶失誤(單純忘記),但後者卻是不老實的情報錯誤(不懂裝懂)。
往後你會相信誰?是老實並提出中肯問題的人,還是明顯說假話的人?是好奇愛問的人,還是堅定說謊的人?我們都見過下述類型的人:在商業會議上,為支持某個觀點或談成某樁生意,這類人會提出不實陳述,結果謊言卻被當場揭穿或將來被拆穿。一旦作出虛假陳述,你就會在與你談話的人或正在聽你講話的人的心中失去信任度。
雖然我們肯定會更深入探討,但這裡也有些不那麼愚蠢的問題,可以達成所有追求提問藝術的最佳理由。比方說,如果你發現自己正與人談論關於《罪與罰》(我最喜歡的書),你對於這個主題既不瞭解也沒有興趣,但又想與我在漫長且痛苦的汽車之旅中保有自我,那麼能夠提出的更好問題是:
你認為《罪與罰》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你認為作者為什麼寫這本書……?
《罪與罰》?真有意思,那麼這本書與你在司法體系的個人經驗有什麼關聯性嗎?
你喜歡《罪與罰》中的哪些部分?
糟糕的問題幾乎總是比錯誤的陳述來得好。有次我在聽復活節佈道會的錄音,傳教士在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中提到路加(Luke)。路加?有說錯嗎?當時他並不在場,即使他在,也肯定不是十二門徒(Twelve Disciples)之一。若傳教士以提問的方式來說,情況會好很多。「當時路加在場嗎?」「你們能幫忙說出門徒的名字嗎?」「站在最後晚餐舉行的那個房間裡,你會有什麼感覺?」利用帶有疑問句的託辭,只是想知道更多的資訊。當你做出肯定、陳述性的說明,若是這些說明錯誤或未經證實,那麼你就會失去陪審團的信任。雖然可以使用「在我看來」作為這些說明的前言,但路加出現在最後晚餐並不是什麼開放認定的觀點,對吧?
身為傳教士,你的工作就是實實在在地說服他人皈依基督。這是一項艱鉅的任,需要運用大量證據來支持論點。不管你犯下的錯誤是多麼無害,或者後面的觀點是多麼令人信服,像前述那樣的陳述句都可能讓聽眾對你的所有說服意圖產生質疑,立即停止傾聽接下來的任何內容。
如果傳教士犯下無心之過,把聖經四部福音書(譯註:分別為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其中一個作者列入很多人可能也以為他在的場所,真的有關係嗎?可能無妨。或許,我對於最後的晚餐出現路加這件事會有如此反應,是因為我將自己的屬靈爭戰精神投射到一個理應比我更瞭解的人身上。儘管生活上有些過失不必付出代價,有些則要賠上生命,也有很多是介於兩者之間,但總有些錯誤會迫使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心魔,帶領你進入更深層次的內省。這種無關痛癢卻又顯而易見的錯誤對於信仰邊緣的聽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傳播所謂聖經真理時,還可能出現哪些與事實不符的部分?這時候問題便轉向內部層面。
自我導向和自我說服
記得我前面提過那個聰明的醫生父親嗎?他對南卡羅萊納大學鬥雞美式足球隊(South Carolina Gamecock football)的熱愛,勝過生活上的任何事情。我非常肯定他愛南卡羅萊納鬥雞比愛我和三個妹妹更多(儘管他否認了這點),他會在開球前六小時把我們丟進一輛木質車身的旅行車,這樣我們就能悠哉地尾隨其後,到看臺上觀看……樂團暖場。沒錯,你沒眼花。不是觀看球員熱身,而是看球員上場前的樂團暖場。那是週六的全天活動,而我們從未遲到過。只有一次例外。
那天汽車駛離了位於斯帕坦堡東邊、我們家中的車道之後便右轉,而不是左轉開往洲際公路,前去哥倫比亞大學看比賽。接著又向右彎,最後停在拉娜與蘭迪‧麥哈菲夫婦(Lana and Randy Mahaffey)和他們兩個兒子克萊(Clay)和大衛(David)居住的那條路上。克萊與大衛年紀只比我小一點,我和他們很熟。拉娜與蘭迪是我父母的摯友,他們倆人都是學校老師。麥哈菲一家跟我們上同一所教堂。蘭迪過去是、現在仍是傑出的高爾夫球手,即使已經八十多歲。我們都叫他「教授」(professor)。他教高中物理,而且能讓物理變得有趣並不容易。拉娜則教高中英文,我對閱讀的愛好有部分來自我在她課上讀的短篇小說。我們的後院相連,大到可以舉行全場的足球比賽。雖然克萊與大衛比我小一點,但我們還是會一起玩,我在十幾歲的時候甚至當過他們的保母。
爸爸到底為什麼會在比賽日當天到他們家?媽媽為什麼面無表情地坐在前座?當我們問爸爸還要在裡面待多久時,媽媽為什麼悶不吭聲?媽媽怎麼落淚了?
爸爸在屋內告訴他和媽媽的摯友,他們的小兒子大衛得了白血病。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這些佔了生活一大部分的問題,在最棘手的「為什麼」問題面前,卻變得如此渺小和無關緊要。
與病魔抗爭的大衛‧麥哈菲最終還是離世,我們每個人生命中至少享受過的一段童年純真也隨他死去。對我而言,那種純真將被人生意義的疑問所取代。
我們搬到另一棟同樣位於斯帕坦堡大約一英里遠的房子。這棟新房有三層樓,裡面設置了衣物滑道,我們可以把衣物從頂樓的通道口扔下去,衣物就會神奇地出現在地下室,這裡對我來說還有個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沒人會想到在那裡找到我的小衣櫥。而這裡就是我內心對話的開始:
我們從何而來?有沒有神所揀選的靈魂寶庫?我怎麼會被選進這個家庭?靈魂是循環的嗎?大衛可能以他人兒子的身分回來嗎?他現在在哪裡?為什麼我沒有兄弟?拉娜與蘭迪只有兩個孩子,為什麼上帝要帶走大衛?為什麼不帶走我或是我其中一個妹妹?如果祂這麼做了,我父母還會有三個小孩嗎?
我不一定喜歡割幾個小時的草,但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一個人坐在旅行車的第三排座位,但我可以和自己講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凌晨四點起床,騎著電動腳踏車送報紙,但沒人起床的時候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
像這樣的對話一直持續到今天,我不斷地詢問自己問題,並演練自己想向別人提出的問題。在法庭上作出的結案陳述,都是我幾週前推著割草機想出來的;在國會上發表的演說,都是我獨自駕車往返機場時思考而來。在現實生活發生以前,我會先在腦海進行演練一遍。我該怎麼問這題?如果她這樣說呢?如果是這個答案,問題要轉到哪個方向?如何用同樣的速度和敏銳度處理「是」或「不是」?
所以,沒錯,提問是幾個因素自然和可能性的集合:(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首先是意識到人性本質是什麼,然後承認人性本質(每個人都渴望被傾聽,於是我決定閉嘴傾聽就有了優勢);(3)我花了好幾個小時進行無止盡的內心對話,試圖理解自己所信仰的事物、為什麼我相信它、以及這些理念是否經得起公眾檢視的考驗;最後(4)久而久之,在談話中扭轉情勢或緩和緊張局面、避免即將發生的衝突中,提問成為一種極其有效的作法。提問似乎是溝通和說服的最佳方式,同時也降低自曝其短的風險。但最重要的是,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提問一直是我說服別人的方式,因為有記憶以來,提問就是我說服自己的方式。
3 X 0 = 3
我說過拉娜與蘭迪有兩個兒子:克萊與大衛。克萊仍然是我的朋友,只是沒有像過去那麼常打高爾夫球。他很早就結婚,娶了一位名叫史黛西(Stacey)的好女人。他就讀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沒有人是完美的)並成為一名工程師。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生活開始出現某種對稱性(symmetry)。克萊的父親讓我終身熱愛高爾夫球。克來第一次一桿進洞的時候,我也在場,這就是為什麼我叫他「Ace」(一桿進洞)而不是克萊,沒有人這樣叫他。
克萊與史黛西也有自己的孩子。他們給第一個兒子命名為大衛,大衛‧麥哈菲(David Mahaffey)二世。這位大衛‧麥哈菲是體格強壯且頭腦聰明的大學生,同時也是高爾夫球手,在我們兩家族半世紀以來一起打過無數場球的球場工作。
大衛‧麥哈菲在SAT(學術水準測驗考試)數學項目的得分,比我所有項目的分數總和還要高,別笑!他的分數可能也比你們高。所以,我當然要和他談談數學方面,對吧?我喜歡挑戰,喜歡挑戰巨人歌利亞(Goliath,譯註:聖經人物)。
問自己數學問題很簡單:我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否正確。這種對話能有多困難?但是問一個數學好的人問題,那就是挑戰。說服比我更博學多聞的人,這就是說服的藝術。
「3 X 0是多少?」我問年輕的大衛‧麥哈菲
他看我的樣子彷彿我在發神經,「答案是零,高迪先生,大家都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大衛。我認為答案不是這樣。0 X 3等於零,我同意,但3 X 0不是零。」
「抱歉,高迪先生,但答案就是這樣。」
「誰說的?」
「人人都這麼說。」
「但我不是人嗎?你是不是因為我對虛無的看法與你不同,就不重視我的想法?難道我不算個人嗎?我不重要嗎,大衛?」
「呃,高迪先生,任何數字乘以零都等於零,」大衛回答。
「不,大衛,我不相信。3 X 0等於3,你不能讓我有的東西消失。我有三件東西,我只是把它乘以零,但我的三件東西並沒有消失,我不認同在等式裡承認它的存在,卻裝作好像什麼都不存在一樣。我不能認同這點,不能支持這種說法,這是錯的,大衛。你想要我這樣嗎?你想要我假裝存在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嗎?」
此時,高爾夫球職業球場總教練、兩位助理教練和六、七個工作人員都站在我們周圍。我就是為這些時刻而生的!
「大衛,我愛你,我認識你家人很久了。你爺爺教我物理,你奶奶教我英文,你父親第一次打出一桿進洞的時候我就在現場。順道一提,你是指你父親並沒有真的一桿進洞,只因為你並不在場嗎?你說的不存在就是這個意思嗎?0 X 3等於零,我認同,我什麼都沒有,所以乘以零還是零。但3 X 0 不等於什麼都沒有,我有三樣東西,你要說我什麼都沒有嗎?你否認我有三樣東西嗎?你擱置現實(suspending reality)是因為想在同事面前贏得數學辯論嗎?大衛,我的三在哪裡?它去哪了?你怎麼能當它不存在?你無法設計出任何數學公式來說服我知道存在的東西,你不能把它拿走,我對於你的嘗試感到驚訝和失望。我的三在哪,大衛?!」
可憐的大衛‧麥哈菲,你要怎麼和一個神經病辯論?要是有人認為3 X 0和0 X 3的結構順序真的會影響答案,那你怎麼跟他辯論數學?在我擦完最後一支高爾夫球桿時,大衛看著我說:「高迪先生,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但我知道我是對的,我回家後會請教父母該怎麼答覆,但我很清楚,任何數乘以零都是零,只是我現在無法解釋。」
當我走出高爾夫球場的停車場時,生活的對稱性在很多層面上都讓我不知所措。
首先,別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那位在高中最後一堂數學課只拿了「D」大學期間所有數學科目都被當的傢伙,卻能與一個數學天才辯論。至少可以慶祝一下吧!
但真正的對稱性是麥哈菲與高迪家族之間五十多年的聯繫。如果你能記住一件事,別忘記說服的藝術並不是要贏得他人支持,而是要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提問的力量(如果運用得宜的話)在於,說話和傾聽之間本身存在對等的施與受。當然,我本來可以詢問大衛棒球和高爾夫球的發展如何;我本來可以問他主修什麼科目,但我卻不斷地問他到底我原來的三跑到哪裡了。因為我希望這個數學很好的年輕人也能擅長溝通,你知道答案是零,然後要說服我答案是零。在觀眾面前、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進行說服、溝通、辯護、建立關係。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大衛回到家,會問他父母如何將簡單的數學概念傳達給一個應該本來就知道的人。但這不就是生活嗎?這不就是我們想做的嗎?有效溝通,保持熱情。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麥哈菲一家人一定笑得很開心,想知道這個不太瞭解基本數學原理的人怎麼會當選國會議員。而且我確定克萊曾說過:「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充分說明了我們的國會議員不懂數學。」
我能完全理解的事情太少: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球上?為什麼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所謂「萬事(無論多麼暗黑或邪惡)皆互相效力得益處」的道理。我還沒完全說服自己認同這點,我懷疑我永遠都無法說服自己。但我已經說服自己,讓這個問題消失,享受提問的藝術和說服的藝術,以此作為一種溝通和交流的方式。我曾經在位於斯帕坦堡東側房屋的一個漆黑壁櫥裡,問過自己一些關於大衛‧麥哈菲一世的問題,如今這些問題似乎比當時更有意義。我學會不要迴避困難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會引導你找到真理。
剛開始你可能會問一些非常愚蠢的問題,例如:「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或者「3 X 0等於多少?」但不要停止問問題。先問你自己,再問別人,詢問關於你的存在、關於他人和每件事情。你最後要說服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有時候你自己就是那個最難說服的陪審團。
世上沒有蠢問題?才怪!
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凶殺案是一件嚴肅悲傷的事,一條生命已經消逝,另一人正在接受審判,面臨終身監禁的現實,沒有假釋的機會,或者更嚴重的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所以你能想像得到,在任何刑事審判中都沒有幽默的空間。然而,我在第一次進行死刑審判時卻讓全場都笑出眼淚了。那些說「世上沒有蠢問題」的人,都不是二〇〇一年秋天坐在斯帕坦堡郡法庭(Spartanburg County Courthouse)裡面的人。
在這起案件中,一名超商店員因為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遭到搶劫並殺害。該名店員工作勤奮,為人善良且正直,在生活上克服過很多困難,如果嫌犯開口要錢,他會把錢給嫌犯的那種人。
大多數像這樣的案件,只有兩名當事人,而且一名(受害人)已經死亡,所以除了法醫鑑識或任何可能持有的物證之外,你得仰賴被告的肯定性陳述、供詞或不實的辯解陳述。但在這起案件裡,還有另一名目擊證人,當搶劫和槍擊事件發生時,他正坐在一旁玩電動撲克遊戲。
當你有了額外的目擊證人,就會想提前跟他們見面,瞭解要講的內容以及該如何準備。在這起案件中,我與該名目擊證人見過很多次。他非常重要(事實上是極其重要),雖然他在死刑審判中作證時可能會很緊張,但其態度誠懇且可靠。
現在是他出庭表態的時候了。敘述背景給陪審團聽是很重要的事,包括商店規模、證人與收銀機和店員的相對位置、他可以觀察的機會、沒有毒品或酒精影響他的感知能力、以及其它預設陪審團可能會提的問題。
「你和超商前門之間有任何物品嗎?」
「沒有。」
「有任何東西擋住你的視線嗎?」
「沒有。」
「燈是否開著?」
「是的。」
「室內是否煙霧瀰漫或昏暗?」
「沒有。」
「你當時有喝醉嗎?」
「沒有。」
「抱歉問個涉及私人的問題,請問你有沒有服用過處方藥或其它藥物?」
「沒有。」
「嫌疑人走過前門的時候,你注意到他了嗎?」
「有。」
「嫌疑人進門的時候,超商內還有其他人嗎?」
「只有我跟店員。」
「嫌疑人走進來時,你的視線有離開過他嗎?」
「沒有。」
「你有看清楚嫌疑人的長相嗎?」
「有。」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了?」
「那個人走到櫃台前面,然後掏出一把槍。」
「你看得到那把槍嗎?」
「可以。」
「你能向陪審團描述那把槍的樣子嗎?」
「好。槍是黑色的,看起來像手槍,但不是左輪手槍。」
到目前為止該證人都表現得很好,應訊對答一切正常,清楚且精確。但顯然我並沒有就此滿意,我必須繼續問下去。
「先生,我注意到你沒有戴眼鏡,那天晚上你有戴眼鏡嗎?」
「沒有。」
「你的視力很好嗎?」
「對,我的右眼視力很好。」
他剛剛說了什麼?證人先生,你不是獨眼巨人!你有兩隻眼睛啊!
我內心這麼想著。
我給自己惹了什麼麻煩?我該怎麼解套?接下來我該問什麼、說什麼?我應該到此為止,然後希望陪審團沒有聽到他說的話嗎?還是希望陪審團不記得所有人類都有兩隻眼睛?你必須做點什麼,笨蛋特雷,你不能就這樣懸在空中!
「是啊是啊,你的右眼視力當然很好,」我只能這樣說。
「那麼你的左眼……呢?」(換來一陣痛苦的沉默)
「左眼是假的。」
「嗯,是啊,先生,左眼是義眼。」
「對……,左眼是假的,」他回答。
我有一位目擊證人,但我與其他人一樣現在才發現,他只有一隻眼睛看得到。
我很不安,此時我真希望自己出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去伊夫堡(Château d’If)怎麼樣?帶我走!任何地方都好過待在這個法庭。我們在出庭之前,完全沒有問過證人的眼睛狀況。沒有比這更糟的情況了,對吧?但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
「接下來發生什麼了?」我問道。
「嗯,嫌疑人手裡拿著一個藍色袋子。」
「好,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整個法庭哄堂大笑,而那隻眼睛一直看著我,彷彿我瘋了一樣。
也許他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於是我又重複一遍問題,「先生,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更多笑聲傳來。
怎麼回事?為什麼大家會在死刑審判中大笑?
還沒等我重複第三次這個英語系國家史上最愚蠢的問題,法官便大發慈悲地說:「地區檢察官,我想陪審團現在知道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了!你可以繼續問下一題了。」
提問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提問可能是真心想要得到更多的資訊。提問可能是為了再三確認。有些問題你已經知道答案,但你的「陪審團」可能有些人並不知道,所以你用提問的方式來傳遞訊息給他人而不是自己。提問可能是質疑或削弱對方論點。提問可能具有防禦性,讓你重新整編、轉移、重新引導別人的注意力,以待下回反擊論點的機會。
還有一些就是很愚蠢的問題。
問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時候同樣一個問題的好壞是根據提問的情況而定。若是審訊前幾週,在我的辦公室裡詢問我的目擊證人關於他的視力,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在法務官辦公室(Solicitor’s Office) 的工作人員給了我一張這次審判庭上的照片,是當地一家報紙的攝影師在證人說「我的右眼視力很好」時所拍攝的。我的工作人員之所以拿那次審判的照片給我,是因為當證人提到他的一隻眼睛時,我的臉部完全沒有明顯的反應。我的內心其實在垂死掙扎,但陪審團從我的外表看不出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問了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才讓這個錯誤變得更嚴重。我撐過了第一個糟糕的問題,卻因問了第二個糟糕的問題而錯失時機。
防禦機制
沒有人天生就知道如何提出對的問題。即使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不一定擅長提問。這樣做的藝術可能源自於多個推動力,對我而言,提問是幾個思路的匯集,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承認人性的本質是喜歡說話多於傾聽;(3)在無止盡的內心對話中花費了許多時間;(4)意識到問對的問題是扭轉局面的黑魔法(devilish way)。
使用疑問句而非陳述性語句的首要動機是,我把提問當成一種防禦機制,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我從不認為自己聰明到可以加入聰明人士的對話,但我對他們的領域很感興趣。
我爸爸很聰明,他是名醫生,所以我會問他一些關於醫學的問題。例如血壓的最高數字代表什麼意思?為什麼95算是高靜止心率(resting heart rate)?孩童怎麼會罹患白血病?
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基斯‧考克最後考上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並成為口腔外科醫生,他真的很聰明。我應該讓他知道我並不聰明,還是問些問題來掩飾?
蘭迪‧貝爾(Randy Bell)法官是我一生中遇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是南卡州上訴法院的法官,最後獲選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不幸在就職前逝世。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上訴法院任職,那是我剛從法學院畢業的第一年。他是洗腎病患,固定從南卡州哥倫比亞前往喬治亞州奧古斯塔進行洗腎,所以需要有人接送,於是我接下這項任務。他是法律學者、羅馬文化方面的專家,而且對英美法系(English common law,或稱判例法)相當熟悉,能夠引導關於自然法和實證主義的討論。想在蘭迪‧貝爾這樣的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是人之常情,我想談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然後展開對話。記得我們剛認識不久的某天下午,我開車送他到奧古斯塔,他在講述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但當時我對此一無所知。然後他把話題轉移至共同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又稱混和過失、可歸責於己的過失)與比較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我對該話題也不清楚。他不斷變換話題,從羅馬神話講到道義論(deontology),試圖找到一些話題、任何可以讓我參與對話的主題。
但他默驢技窮了。
最後他問我:「孩子,你都知道些什麼?你想談些什麼?」
我其實想聊的是自己怎麼會和一位羅馬法專家待在車上,但我卻回他:「NASCAR(全美運動汽車競賽,又譯美國房車改裝賽),我最近喜歡上NASCAR。」
「很好,」他回應道:「跟我聊聊NASCAR的起源吧。」
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我只知道理查‧佩蒂(Richard Petty),就這樣,法官大人。」
那是我人生中另一個最糟時刻。我擁有歷史學士學位和法律學位,卻沒有真正的知識,我和即將成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坐在同一輛車,他拼命試著找尋世界上任何一個我熟悉的領域,可以在往返南卡州哥倫比亞與喬治亞州奧古斯塔的旅途空檔中聊天的話題,結果卻一無斬獲。我也經常出現自卑的失落感:我覺得自己真的不聰明,我該如何偽裝?我該如何掩飾缺點?要怎麼在不暴露巨大知識落差的情況下參與對話或專業互動?
你可以選擇迅速變聰明,或者找到一種方法來完全掩飾自己認為的知識匱乏。你可以選擇填補知識缺口或選擇填補時間,又或者,你可以找到一種同時滿足兩者的方法,那就是提問。
當時面對貝爾法官或許可以這樣說:
我不瞭解羅馬神話,但我對希臘神話有點印象。希臘眾神與羅馬眾神一樣嗎?還是他們只是名字不同?你最喜歡的神話人物是誰?如果可以選擇,貝爾法官你想要哪種神話人物的力量?比起雅典,你似乎更喜歡羅馬?為什麼呢?你能跟我聊聊斯巴達文化嗎?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
英美判例法嗎?我對這方面不太瞭解。但以我懂得的範圍內可以去問,為什麼有些判例法是由立法機關編纂或通過,但有些卻不是?如果判例法與成文法(statutory law)之間出現衝突,以哪個法條為主?請問貝爾法官,有聯邦判例法(federal common law)嗎?
你可以利用人類最主要的需求之一來學習和消磨時間,那就是被傾聽的渴望。大多數人都有想要說話的天性,所以我利用了這點。比起傾聽,人類更愛說話,若能善加利用人性,我就能掩飾自己的不足。因此,我用不想被人認為無知的渴望來壓抑或取代自己想被傾聽的渴望――如此一來,對你我不都是雙贏嗎?你可以盡情說話,我可以傾聽和學習,還能避免未能達到對方期望的那股失落感。相信我,提問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
愚蠢的問題總比愚蠢的答案好
每當談到說服的藝術,我們通常會想到以下形式:開場白、提出主張、闡述論點。接著是一連串的說明、陳述、證實、描述、聲明、發言,慢慢地建構一個論點,然後盡可能減少漏洞並補充更多有力的主張。這是傳統模式,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呢?
我們一般不會想到可以藉由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來達到說服目的,人們通常認為提問是被動而非主動的行為,對吧?提問有時會被當成是不知道某件事答案的證據,提問會讓人顯得軟弱、狀況外、無知、不確定。那也許是別人想讓我們以為的樣子,但那與我自己的經驗截然相反。提問可以爭取時間、蒐集訊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以那種無法靠簡單表明自己理念的方式進行說服。
前面大家已經見證到,「世上沒有蠢問題」這句古諺在我的例子裡輕而易舉就被推翻,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認可的道理。固然有一些思慮不周、措辭不當和不明智的問題,但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比愚蠢的陳述聲明好上一千倍。
從自己口中說出的每一句陳述性評論都要自己負責,但若以提問方式,你的說法就會有個台階下。正因如此,提問也許是說服藝術中最重要且最保險的方式。
無論是問什麼內容,如果原本想法大錯特錯,你可以回說:「我不知道,所以才會問。」如果原本想法無誤,你可以回說:「我也這麼認為。」除了尋求更多的資訊,你不會有任何愧疚感,這就是聽起來愚蠢和真愚蠢之間的差別。
聽起來愚蠢的問法會是:《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作者是誰?
真愚蠢的說法會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是《罪與罰》的作者。
當然,前者顯示了缺乏資訊的情況,但後者暴露出你自以為知道但實際並不知道的情況,從那一刻起,所有從你口中說出來的話都變得不可靠。前者只是無心的記憶失誤(單純忘記),但後者卻是不老實的情報錯誤(不懂裝懂)。
往後你會相信誰?是老實並提出中肯問題的人,還是明顯說假話的人?是好奇愛問的人,還是堅定說謊的人?我們都見過下述類型的人:在商業會議上,為支持某個觀點或談成某樁生意,這類人會提出不實陳述,結果謊言卻被當場揭穿或將來被拆穿。一旦作出虛假陳述,你就會在與你談話的人或正在聽你講話的人的心中失去信任度。
雖然我們肯定會更深入探討,但這裡也有些不那麼愚蠢的問題,可以達成所有追求提問藝術的最佳理由。比方說,如果你發現自己正與人談論關於《罪與罰》(我最喜歡的書),你對於這個主題既不瞭解也沒有興趣,但又想與我在漫長且痛苦的汽車之旅中保有自我,那麼能夠提出的更好問題是:
你認為《罪與罰》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你認為作者為什麼寫這本書……?
《罪與罰》?真有意思,那麼這本書與你在司法體系的個人經驗有什麼關聯性嗎?
你喜歡《罪與罰》中的哪些部分?
糟糕的問題幾乎總是比錯誤的陳述來得好。有次我在聽復活節佈道會的錄音,傳教士在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中提到路加(Luke)。路加?有說錯嗎?當時他並不在場,即使他在,也肯定不是十二門徒(Twelve Disciples)之一。若傳教士以提問的方式來說,情況會好很多。「當時路加在場嗎?」「你們能幫忙說出門徒的名字嗎?」「站在最後晚餐舉行的那個房間裡,你會有什麼感覺?」利用帶有疑問句的託辭,只是想知道更多的資訊。當你做出肯定、陳述性的說明,若是這些說明錯誤或未經證實,那麼你就會失去陪審團的信任。雖然可以使用「在我看來」作為這些說明的前言,但路加出現在最後晚餐並不是什麼開放認定的觀點,對吧?
身為傳教士,你的工作就是實實在在地說服他人皈依基督。這是一項艱鉅的任,需要運用大量證據來支持論點。不管你犯下的錯誤是多麼無害,或者後面的觀點是多麼令人信服,像前述那樣的陳述句都可能讓聽眾對你的所有說服意圖產生質疑,立即停止傾聽接下來的任何內容。
如果傳教士犯下無心之過,把聖經四部福音書(譯註:分別為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其中一個作者列入很多人可能也以為他在的場所,真的有關係嗎?可能無妨。或許,我對於最後的晚餐出現路加這件事會有如此反應,是因為我將自己的屬靈爭戰精神投射到一個理應比我更瞭解的人身上。儘管生活上有些過失不必付出代價,有些則要賠上生命,也有很多是介於兩者之間,但總有些錯誤會迫使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心魔,帶領你進入更深層次的內省。這種無關痛癢卻又顯而易見的錯誤對於信仰邊緣的聽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傳播所謂聖經真理時,還可能出現哪些與事實不符的部分?這時候問題便轉向內部層面。
自我導向和自我說服
記得我前面提過那個聰明的醫生父親嗎?他對南卡羅萊納大學鬥雞美式足球隊(South Carolina Gamecock football)的熱愛,勝過生活上的任何事情。我非常肯定他愛南卡羅萊納鬥雞比愛我和三個妹妹更多(儘管他否認了這點),他會在開球前六小時把我們丟進一輛木質車身的旅行車,這樣我們就能悠哉地尾隨其後,到看臺上觀看……樂團暖場。沒錯,你沒眼花。不是觀看球員熱身,而是看球員上場前的樂團暖場。那是週六的全天活動,而我們從未遲到過。只有一次例外。
那天汽車駛離了位於斯帕坦堡東邊、我們家中的車道之後便右轉,而不是左轉開往洲際公路,前去哥倫比亞大學看比賽。接著又向右彎,最後停在拉娜與蘭迪‧麥哈菲夫婦(Lana and Randy Mahaffey)和他們兩個兒子克萊(Clay)和大衛(David)居住的那條路上。克萊與大衛年紀只比我小一點,我和他們很熟。拉娜與蘭迪是我父母的摯友,他們倆人都是學校老師。麥哈菲一家跟我們上同一所教堂。蘭迪過去是、現在仍是傑出的高爾夫球手,即使已經八十多歲。我們都叫他「教授」(professor)。他教高中物理,而且能讓物理變得有趣並不容易。拉娜則教高中英文,我對閱讀的愛好有部分來自我在她課上讀的短篇小說。我們的後院相連,大到可以舉行全場的足球比賽。雖然克萊與大衛比我小一點,但我們還是會一起玩,我在十幾歲的時候甚至當過他們的保母。
爸爸到底為什麼會在比賽日當天到他們家?媽媽為什麼面無表情地坐在前座?當我們問爸爸還要在裡面待多久時,媽媽為什麼悶不吭聲?媽媽怎麼落淚了?
爸爸在屋內告訴他和媽媽的摯友,他們的小兒子大衛得了白血病。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這些佔了生活一大部分的問題,在最棘手的「為什麼」問題面前,卻變得如此渺小和無關緊要。
與病魔抗爭的大衛‧麥哈菲最終還是離世,我們每個人生命中至少享受過的一段童年純真也隨他死去。對我而言,那種純真將被人生意義的疑問所取代。
我們搬到另一棟同樣位於斯帕坦堡大約一英里遠的房子。這棟新房有三層樓,裡面設置了衣物滑道,我們可以把衣物從頂樓的通道口扔下去,衣物就會神奇地出現在地下室,這裡對我來說還有個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沒人會想到在那裡找到我的小衣櫥。而這裡就是我內心對話的開始:
我們從何而來?有沒有神所揀選的靈魂寶庫?我怎麼會被選進這個家庭?靈魂是循環的嗎?大衛可能以他人兒子的身分回來嗎?他現在在哪裡?為什麼我沒有兄弟?拉娜與蘭迪只有兩個孩子,為什麼上帝要帶走大衛?為什麼不帶走我或是我其中一個妹妹?如果祂這麼做了,我父母還會有三個小孩嗎?
我不一定喜歡割幾個小時的草,但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一個人坐在旅行車的第三排座位,但我可以和自己講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凌晨四點起床,騎著電動腳踏車送報紙,但沒人起床的時候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
像這樣的對話一直持續到今天,我不斷地詢問自己問題,並演練自己想向別人提出的問題。在法庭上作出的結案陳述,都是我幾週前推著割草機想出來的;在國會上發表的演說,都是我獨自駕車往返機場時思考而來。在現實生活發生以前,我會先在腦海進行演練一遍。我該怎麼問這題?如果她這樣說呢?如果是這個答案,問題要轉到哪個方向?如何用同樣的速度和敏銳度處理「是」或「不是」?
所以,沒錯,提問是幾個因素自然和可能性的集合:(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首先是意識到人性本質是什麼,然後承認人性本質(每個人都渴望被傾聽,於是我決定閉嘴傾聽就有了優勢);(3)我花了好幾個小時進行無止盡的內心對話,試圖理解自己所信仰的事物、為什麼我相信它、以及這些理念是否經得起公眾檢視的考驗;最後(4)久而久之,在談話中扭轉情勢或緩和緊張局面、避免即將發生的衝突中,提問成為一種極其有效的作法。提問似乎是溝通和說服的最佳方式,同時也降低自曝其短的風險。但最重要的是,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提問一直是我說服別人的方式,因為有記憶以來,提問就是我說服自己的方式。
3 X 0 = 3
我說過拉娜與蘭迪有兩個兒子:克萊與大衛。克萊仍然是我的朋友,只是沒有像過去那麼常打高爾夫球。他很早就結婚,娶了一位名叫史黛西(Stacey)的好女人。他就讀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沒有人是完美的)並成為一名工程師。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生活開始出現某種對稱性(symmetry)。克萊的父親讓我終身熱愛高爾夫球。克來第一次一桿進洞的時候,我也在場,這就是為什麼我叫他「Ace」(一桿進洞)而不是克萊,沒有人這樣叫他。
克萊與史黛西也有自己的孩子。他們給第一個兒子命名為大衛,大衛‧麥哈菲(David Mahaffey)二世。這位大衛‧麥哈菲是體格強壯且頭腦聰明的大學生,同時也是高爾夫球手,在我們兩家族半世紀以來一起打過無數場球的球場工作。
大衛‧麥哈菲在SAT(學術水準測驗考試)數學項目的得分,比我所有項目的分數總和還要高,別笑!他的分數可能也比你們高。所以,我當然要和他談談數學方面,對吧?我喜歡挑戰,喜歡挑戰巨人歌利亞(Goliath,譯註:聖經人物)。
問自己數學問題很簡單:我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否正確。這種對話能有多困難?但是問一個數學好的人問題,那就是挑戰。說服比我更博學多聞的人,這就是說服的藝術。
「3 X 0是多少?」我問年輕的大衛‧麥哈菲
他看我的樣子彷彿我在發神經,「答案是零,高迪先生,大家都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大衛。我認為答案不是這樣。0 X 3等於零,我同意,但3 X 0不是零。」
「抱歉,高迪先生,但答案就是這樣。」
「誰說的?」
「人人都這麼說。」
「但我不是人嗎?你是不是因為我對虛無的看法與你不同,就不重視我的想法?難道我不算個人嗎?我不重要嗎,大衛?」
「呃,高迪先生,任何數字乘以零都等於零,」大衛回答。
「不,大衛,我不相信。3 X 0等於3,你不能讓我有的東西消失。我有三件東西,我只是把它乘以零,但我的三件東西並沒有消失,我不認同在等式裡承認它的存在,卻裝作好像什麼都不存在一樣。我不能認同這點,不能支持這種說法,這是錯的,大衛。你想要我這樣嗎?你想要我假裝存在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嗎?」
此時,高爾夫球職業球場總教練、兩位助理教練和六、七個工作人員都站在我們周圍。我就是為這些時刻而生的!
「大衛,我愛你,我認識你家人很久了。你爺爺教我物理,你奶奶教我英文,你父親第一次打出一桿進洞的時候我就在現場。順道一提,你是指你父親並沒有真的一桿進洞,只因為你並不在場嗎?你說的不存在就是這個意思嗎?0 X 3等於零,我認同,我什麼都沒有,所以乘以零還是零。但3 X 0 不等於什麼都沒有,我有三樣東西,你要說我什麼都沒有嗎?你否認我有三樣東西嗎?你擱置現實(suspending reality)是因為想在同事面前贏得數學辯論嗎?大衛,我的三在哪裡?它去哪了?你怎麼能當它不存在?你無法設計出任何數學公式來說服我知道存在的東西,你不能把它拿走,我對於你的嘗試感到驚訝和失望。我的三在哪,大衛?!」
可憐的大衛‧麥哈菲,你要怎麼和一個神經病辯論?要是有人認為3 X 0和0 X 3的結構順序真的會影響答案,那你怎麼跟他辯論數學?在我擦完最後一支高爾夫球桿時,大衛看著我說:「高迪先生,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但我知道我是對的,我回家後會請教父母該怎麼答覆,但我很清楚,任何數乘以零都是零,只是我現在無法解釋。」
當我走出高爾夫球場的停車場時,生活的對稱性在很多層面上都讓我不知所措。
首先,別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那位在高中最後一堂數學課只拿了「D」大學期間所有數學科目都被當的傢伙,卻能與一個數學天才辯論。至少可以慶祝一下吧!
但真正的對稱性是麥哈菲與高迪家族之間五十多年的聯繫。如果你能記住一件事,別忘記說服的藝術並不是要贏得他人支持,而是要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提問的力量(如果運用得宜的話)在於,說話和傾聽之間本身存在對等的施與受。當然,我本來可以詢問大衛棒球和高爾夫球的發展如何;我本來可以問他主修什麼科目,但我卻不斷地問他到底我原來的三跑到哪裡了。因為我希望這個數學很好的年輕人也能擅長溝通,你知道答案是零,然後要說服我答案是零。在觀眾面前、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進行說服、溝通、辯護、建立關係。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大衛回到家,會問他父母如何將簡單的數學概念傳達給一個應該本來就知道的人。但這不就是生活嗎?這不就是我們想做的嗎?有效溝通,保持熱情。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麥哈菲一家人一定笑得很開心,想知道這個不太瞭解基本數學原理的人怎麼會當選國會議員。而且我確定克萊曾說過:「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充分說明了我們的國會議員不懂數學。」
我能完全理解的事情太少: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球上?為什麼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所謂「萬事(無論多麼暗黑或邪惡)皆互相效力得益處」的道理。我還沒完全說服自己認同這點,我懷疑我永遠都無法說服自己。但我已經說服自己,讓這個問題消失,享受提問的藝術和說服的藝術,以此作為一種溝通和交流的方式。我曾經在位於斯帕坦堡東側房屋的一個漆黑壁櫥裡,問過自己一些關於大衛‧麥哈菲一世的問題,如今這些問題似乎比當時更有意義。我學會不要迴避困難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會引導你找到真理。
剛開始你可能會問一些非常愚蠢的問題,例如:「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或者「3 X 0等於多少?」但不要停止問問題。先問你自己,再問別人,詢問關於你的存在、關於他人和每件事情。你最後要說服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有時候你自己就是那個最難說服的陪審團。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