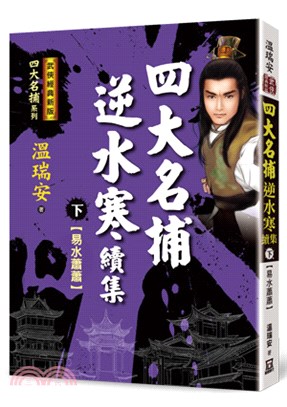商品簡介
戚少商這樣設計,當然是出自一片苦心。
可是他萬未料到,如果雷捲未及回援,無情、唐晚詞都真的要命喪貓耳鄉了。
「逆水寒」看似只是一部描寫逃亡的書,但其中有沖激起千堆雪似的愛情,捲起萬丈濤似的義氣,驚雷似的驟變,夢幻式的遭逢,壯烈的悲歌,解不開的死結,高尚和可鄙的情操……到終卷太息時,讀者或許會頓悟,原來作者寫的「逃亡」,不是逃亡,而是面對整個人生的考驗與歷程。
金庸羽化古龍逝 四大名捕俠氣揚
金古溫黃梁五大師 而今只剩溫瑞安
溫瑞安──與金庸、古龍、梁羽生並列為新武俠四大宗師
他的詩作聞名於星馬港台,他的事蹟如同武俠小說一樣傳奇
《四大名捕》系列為其知名代表作之一,改編為無數電視劇
為了戚少商,息紅淚一手建立的「毀諾城」毀於一旦,眾女弟子死的死,散的散,但息紅淚無悔。愛慕息紅淚的赫連春水,雖明知息紅淚有求於他全是為了相助戚少商,仍一口答應,一路困苦與共。就在無情上京替戚少商反正,戚少商與息紅淚相聚,局勢似轉大好之際,息紅淚竟表明願陪伴赫連春水共度一生……
顧惜朝微微笑著,神態溫和,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講理的人。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實在太講理了。在這世界上,太講理便很難活下去,縱能活著,也未必活得痛快。
像他對付戚少商,便吃虧在「太講理」上:在「思恩鎮」的「安順棧」裡,他因得尤知味之助,已成功的控制了大局,早應該一得手就該先殺掉戚少商,以絕後患!他甚至還覺得自己太「婦人之仁」了。
他還決心「痛悟前非」,以後對人應該要心狠手辣一些。
這一次的「壽宴」已勝券在握,任何人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目。所以他發現巴三奇發現了埋在壽帳內的炸藥。
這列炸藥離那張主客的桌子極近,無疑是為這張桌子上的人而設的。──炸藥一旦引燃,立即把座上的人炸得血肉橫飛,本領再大也無用武之機。這種安排無疑很「絕」。
可是巴三奇立時想到更「絕」的一點。要鐵手這等「賀客」上座,必定會有「陪客」,否則,這些「壽酒」和「炸藥」,都變得派不上用場。──鐵手等人不是在座上被迷倒,就是被炸死!
作者簡介
1954生於馬來西亞,1973來到台灣,最終紮根於香港。他本身就是個詩人。他寫詩遠早於他的武俠小說,他在星、馬、港、台都先以詩知名於世,選入各種極具代表性的年選中。溫瑞安本身就是個俠者。他的事蹟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傳奇。他青年時在台創辦神州詩社,聲勢浩大,結果引起當局忌諱,用政治冤獄打散了他的組織。但他寄居香江一樣照辦「自成一派」文化集團。他又對純粹精專的學問,從醫理、相學、術數、電影及至心理學,水晶念力,氣功等,都肯下功夫去研究。幾乎一切醫卜星相,音樂電影,他都精通;成為一個詩與劍、文學與通俗,濟世抱負和出世情懷交光互映的奇人。他的武俠小說結合了傳統與現代,又揉合了文學與通俗,對喜好武俠的中國人,是一條虎虎生風的出路,也是一條機緣無限的活路。他的作品族繁不及備載,諸如武俠作品、詩集、小說集、評論集及散文、雜文等。
目次
第九十七章 殺手?
第九十八章 希望與失望
第九十九章 單雲雙燭三廳四山
第一百章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第一○一章 祝壽
第一○二章 好戲
第一○三章 乘風歸去
第一○四章 江畔何人初見月?
第一○五章 江月何年初照人?
第一○六章 生死有情
第一○七章 我們又在一起了!
第一○八章 危機
第一○九章 「她不殺,我殺!」
第一一零章 總帳
第一一一章 尾聲
後記 逆水不寒
書摘/試閱
無情愈追近市肆,愈感不安。此時文張已是被逼急了,為了活命,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而自己又無制他之力,旁雜人愈多,愈易殃及無辜。
文張見貓耳鄉近,愈發抖擻精神,待馳近市場,又猶疑起來,因為自己渾身染血,又挾持了個幼童,別人必定生疑。如果過來攔阻,自己倒是不怕,怕的是無情逼近,自己就難逃毒手了!
他心中一急,果見途人對他指指點點,詫目以視;文張因受傷奇重,上身東晃西擺,竭力在馬上維持平衡,這一來,更加怵目。
這只是市場外緣,已引起注意,而市肆間人群擾攘,見此情景,豈不驚愕更甚!文張惶急之下,默運玄功,右手仍挾著銅劍置於身後,以作護身符。
這時,文張的坐騎正掠馳過一家彩綢布店,因店子西斜,生怕陽光太熱,便在外棚撐出了半幕帆布,來遮擋烈陽直射。
棚子外只擺了幾疋不怎麼值錢的粗布,比較好的布料都擺在店裡,這時候也無人在棚外看管。
文張在急掠過之際,左手忍痛遞出,五指一閤,已抓住布篷,「嗤」地撕下一大片,這一來,布棚已支撐不住,轟然而倒,但文張已把一丈來寬的灰布扯在手裡,在臉上一抹,再甩手一張,披裹在他和銅劍身上。
這樣,雖披著奇形怪狀的斗篷大白天裡趕路,極不相襯,但畢竟只是使人詫異,還不似原先披血挾童而馳的令人駭目。
不過,文張那匆匆一抹,並沒有完全抹去臉上的鮮血,反而使他受傷的左目更感到陣陣刺痛,鮮血更不斷的滲淌出來。
市集上人來人往,相當密集,文張一個控制不住,馬前撞倒了幾人,便傳來陣陣怒罵聲,甚至有人要圍繞過來喝打。
文張見無情更加逼近,情急中忽想起一事:
──此地人多,策馬奔馳反而受阻。
──他有馬,無情也有馬,縱再馳二、三十里,也不見得就能擺脫無情!
──不如棄馬而行,趁此地人擠物雜,只要自己以劍僮為盾,穿樑越脊,未必不能逃脫。
──何況,無情雙腿俱廢,縱伏竄行,無情再快、也趕不上他。
文張一想到這點,立即棄馬飛掠,儘往人叢裡鑽:
──在人群裡,無情斷不敢亂發暗器!
文張卻不知道:如果無情不是功力未復,他這下棄馬飛掠是大錯特錯的選擇!
因為無情除了暗器之外,輕功亦是一絕!
無情天生殘疾,不能練武,只能練暗器與輕功,他把這兩項特長發揮無遺,文張輕功也算不錯,但若跟無情相比,就直如山貓與豹!
文張幾個巧閃快竄,已自人潮擁擠的街道轉入另一條巷子,也就因為他不敢縱高飛躍,生怕成了無情暗器的靶子,所以才不致瞬間就把無情完全拋離。
文張挾在人群裡,無情自不能策馬衝入人叢裡,他知道只要文張一擺脫他的追蹤,定會把人質殺死,他不能任由文張對銅劍下毒手,所以只能追下去。
他只有下馬。
他幾乎是摔下馬來的!
這一摔,痛得他骨節欲裂,但他強忍痛楚,用手代足,勉力綴行。
缺少了代步的轎子或車子,而又無法運勁,無情每行一步,都艱苦無比。
可是為了緊追文張,無情只好硬挺。
他在人叢中雙手按地,勉力疾行,只見人潮裡的腿腳往旁閃開,語言裡充滿了驚異或同情:
「這個人在幹什麼?」
「真可憐,年紀輕輕,就已殘廢!」
「他這般急作啥?你過去看看嘛!」
「你看你看,這個人……」
無情以手撐地疾行,由於腿不能立,只及平常人的膝部,只不過「走」了一陣,就大汗淋漓,濕透重衫。
文張跟他相隔一條街,在對面迅行。
無情眼看再追下去,一定追不著他,但也不敢呼求途人出手相助。
──有誰能助?
──不過讓文張多造殺戮而已!
無情又氣又急,既累既喘,忽然,三名衙差、一名地保,攔在他身前,不讓他越過去。
其中一名疏鬚掩唇的捕役,顯然是個班頭,向他叱道:「你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來幹什麼?」
無情一口氣喘不過來,只見遠處文張又要轉入另一條街衖,再稍遲延就要失去影蹤,只急道:「讓路!」
一名削臉官差怪笑道:「哎呀,這殘廢公子兒更可比咱們凶哩!」
另外一名年歲較長的公差卻調解道:「小哥兒趕得忒急,敢情必有事兒,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無情眼看文張就要走脫,恚然道:「那兒走的是殺人凶徒,他正要加害一個無辜幼童!」
那留鬚衙役一怔問:「在哪裡?」他見無情殘廢,心中倒不疑他作惡,聽他這一說,倒信了幾分。
無情用手隔街一指道:「就是他!他還挾著小孩子!」
三人引頸一看,人來人往,人頭洶湧,竟找不到目標,眼看文張就要轉入街道,忽然,有一個人,向他攔了一攔。
文張凝步一看,連鬚落腮密鬍接頷的,穿著身便服,青子官靴,白淨面皮,年約五旬上下,只聽那人喝問道:「你是誰?怎麼身上有血,挾著個小孩子幹啥?這小童是你什麼人﹗﹖ 」
文張一聽,便知道來人打的是官腔,決非尋常百姓,他更不想生事,只想避了開去。
他才一扭身,又給另外三名僕徒打扮的人攔手截住,其中一名幾乎要一巴掌摑過來,道:「我們賓老爺問你的話,你聾了不成﹗﹖」
文張這才發現自己身上披的斗蓬,也滲出血來,而臂彎內挾著的銅劍,也在疾行時露了出來,這一來,自知大概是瞞不過去了,登時惡向膽邊生,叱道:「滾開!」
他這一喝,那三名作威作福慣了的僕役也頓時走火,揮拳踢腳,要把文張打倒制住。
文張那邊一動手,那圍住無情的三名公差,全瞧見了,其中那名年紀最大的喊道:「那豈不是鄰鎮的鄉紳、驛丞賓老爺?你們看,那個人的確挾著一個小孩,正跟何小七、鄧老二、趙鐵勤他們打起來了呢!」
那留鬍子的衙差抽出鐵尺,向無情叱道:「你留在這兒,那人犯了什麼事,待會兒還要你到公堂指證,」轉首向兩名同伴道:「咱們過去拿人!」
兩人吆喝了一聲「是」,一齊橫過街心,趕了過去。
原來那名看出文張大有可疑的人,正是那位燕南鎮主事賓東成,賓東成曾接待過劉獨峰和戚少商,而郗舜才被拒於門外,關於這一點,賓東成咸以為是平生快意,不意又聽聞郗舜才竟迎待了「四大名捕」中的無情,無形中好像扯低了他的榮耀,心中很有點不快,這天帶著三、四名管事、僕從,往貓耳鎮的市集逛逛,合當遇事,竟遇著了挾持幼童、鬧市逃竄的文張!
至於那三名衙差,恰好在市肆巡行,聽到前面騷動,橫出來看個究竟,恰遇上無情,本要審問,卻發現賓東成那兒已跟人動起手來,賓東成是這一帶的地方官,這幾個官差連忙過去護駕,暫不細察無情。
那三名捕役橫搶過街心,奔撲向衖角,文張已陡地丟下銅劍,右手一拳,擊倒了一名僕役,咬牙反手拔出了左肩上的匕首!
文張刀一在手,雖受傷頗為不輕,但那兩名僕役又焉可攔得住他?三五招間,兩名僕役身上都掛了彩。
以文張的武功,要殺死眼前四人,易如反掌,但他既知來人很可能是官面上的人物,若在此鬧市公然殺人,日後不易洗脫罪名,只怕要斷送前程,所以總算不敢猛下殺手,只想嚇退這幾人。
文張拔刀動手,路上行人皆嘩然走避,一時局面十分混亂。
賓東成見此人形同瘋虎,武功非常,見勢不妙,便要喝令手下撤走再說,犯不著把性命賠在這裡,卻正好在此時,那三名捕差又攏了上來,一時人手驟增,膽氣便豪,賓東成於是叱道:「來啊,先拿下這個凶徒!」
三名官差,揮鐵尺圍襲,文張因懼無情掩至,知道不能再拖,性命要緊,把心一橫,搶身猱進,長袖一揮,捲飛二人,一刀把削臉公差剔下半邊臉來,登時血流如注,掩臉摜倒,慘呼不絕。
這一下,可把幾名衙差、僕役及賓東成全皆震住。
文張獰笑道:「誰敢上來,我就一刀宰了他。」他此時滿臉血污,兇狠暴戾,平日溫文威儀已全消失不見。
忽聽一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文張猙獰的神情倏然變了。
他驟然俯身,要伏竄向倒在地上的銅劍。
他身形甫動,那人就說話了。
話並不特別,只說了一句:「別動。」
文張本來要掠起的身子陡然頓住。
賓東成等望了過去,只見一個白衣青年,以單手拄地,全身汗濕重衣,髮散袂掀,但雙目有如銳電,冷若刀芒。
他盯住文張的咽喉。
文張就覺得自己的喉嚨正被兩把刀子抵著。刀鋒冷,比冰還冷。他感到頭部一陣僵硬。
「你最好不要動。」
文張不敢動。
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動,眼前這個看來弱不禁風的無情,立即就會發出暗器。
他既不能撲向銅劍,也不能掠身而去。
他開始後悔為何要放棄手中的人質,去跟這幾個什麼小丑糾纏。
無情全身都在輕微的抖動著。
而且呼息十分不調勻。
他知道自己快要崩潰了。
因為他功力未復,而且又實在太累了。
可是他不能倒。
他已嚇住文張,但卻制他不住,因為他已失去發暗器的能力。
所以他只有強撐下去。
──能撐到幾時?
只聽一聲失聲低呼:「莫非你就是……」說話的人是賓東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捕無情﹗﹖ 」
無情要保留一口元氣,只點頭,儘量不多說話。
那班頭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無情大爺在,你這凶徒還能飛到天上去?還不束手就擒?」說著就要過去擒拿文張。
文張臉上閃過一絲喜悅之色。
無情叱道:「你也不許動!」他知道那名班頭只要一走過去,文張就會借他為盾,或扣到他來作人質。
班頭一怔,馬上停步。
無情用一種寒怖的語音說:「我的暗器是不會認人的。」
文張剩下的一隻眼睛,一直盯著無情的手,似在估計情勢,又似在觀察搖搖欲墜、臉色蒼白的無情,是否能一擊格殺自己?
兩人隔了半箭之地,對峙著。
兩人的中間,便是賓東成和兩個僕役、兩名捕役,另外還有一捕一僕,倒在地上。
街上的行人,早已走避一空。
文張正在估量著無情。
無情正在設法禁制文張。
一個是不敢冒然發動。
一個是不能發動。
不能發動的似乎暫時占了上風,但能發動的一旦發動,在場無人能擋。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