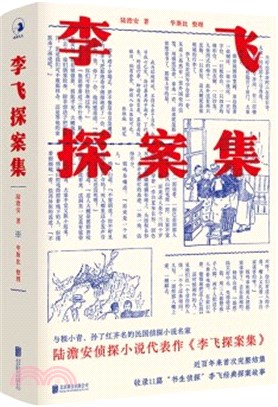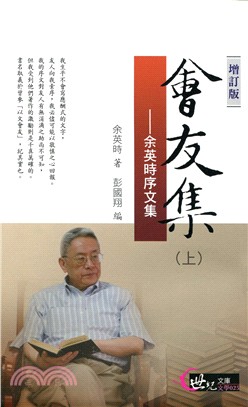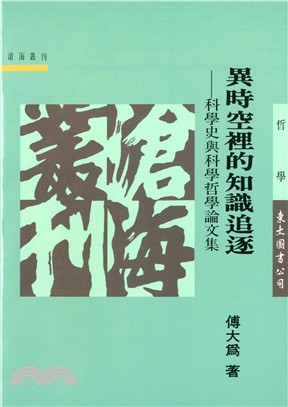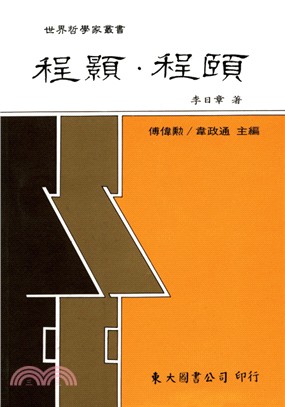李飛探案集(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59649652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
作者:陸澹安
出版日:2021/03/01
裝訂/頁數:精裝/369頁
規格:21cm*14.5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陸澹安是民國偵探小說史上與程小青、孫了紅齊名的偵探小說家,他的代表作《李飛探案集》塑造了一位別具一格的“書生偵探”形象—李飛。
本書收錄目前可見的“李飛探案”系列小說11篇:《棉裡針》《密碼字典》《狐祟》《隔窗人面》《夜半鐘聲》《怪函》《古塔孤囚》《煙波》《合浦還珠》《三A黨》《秘密電聲》,是該系列誕生近百年來首次完整結集。
目次
楔子
棉裡針
密碼字典
狐祟
隔窗人面
夜半鐘聲
怪函
古塔孤囚
煙波
合浦還珠
三A黨
秘密電聲
《李飛探案集》各篇初刊一覽
編後記
書摘/試閱
棉裡針
(上)
這時候李飛才十七歲,在一個中學堂裡讀書,那學堂是私立的,校名叫做亞東公學,地址在靜安寺路的中段。校中分為兩部,一部是中學,一部是中學的預科。校長姓秦,便是創辦時的一個發起人。那秦校長辦事狠認真,辛苦經營,勞瘁不辭,倒的碻(確)是個教育界的熱心人物。校中規則狠嚴肅,課程也狠認真。名譽一好,這學校就發達起來。剛開辦的時候,學生只有五六十人,三四年之後,居然增加到五百多人,其中寄宿的也有二三百人。這學堂的氣象,大有蒸蒸日上的樣子。可是學生的人數多了,內中便難免良莠不齊,寄宿舍之 中,時常有人失去銀錢衣服等物。舍監姓朱,便是李飛的表叔。李飛進這個學堂,也是被這位表叔帶進去的。朱舍監辦事,也狠認真,每逢接到了失物的報告,便立刻將寄宿生的箱籠物件,逐一搜檢,也有時居然搜出了證據。真賊實犯,無可抵賴,就稟明校長,將那竊物的學生,立時開除。但是開除盡管開除,失物卻依舊難免,有時候那失去的東西,竟然無影無蹤,不知去向。舍監查不出來,失主也只能自認晦氣了。
有一天早晨七點鐘,學堂中打過起身鐘後,那位舍監朱先生,正在自己房間裡寫信。忽然有一個學生,推門進來,慌慌張張的說道:“朱先生,我們房間裡又失掉東西了!”舍監抬頭一看,那學生是正科三年級的許幼蘭,就把手中的筆一擱,蹙著眉頭問道:“又丟了什麼東西了?幾時丟的?”許幼蘭道:“我昨晚臨睡的時候,在箱子內取出一套絨衫袴,放在床角裡,預備今天早上換的。不料今天起來,那絨衫袴忽然不見了,真是怪事!”舍監道:“你那套絨衫袴是新的,還是舊的?上面有什麼記號沒有?”幼蘭道:“絨衫袴是舊的,也沒有什麼記號,就是丟掉了,也不值幾個錢。不過現在身上的骯了,沒有更換,倒覺得狠不便當罷了。”舍監點了點頭,把寄宿舍的花名冊一翻,又問他道:“你住在十三號,不是同鄭季蓀、王仁榮、徐義生三個人同房間嗎?”幼蘭道:“正是。他們三人,我都問過了,都說沒有看見。”舍監道:“今天你們四人之中,那一個最先起來?”幼蘭道:“徐義生起來得最早。我們起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房間裡了。我當時不見了絨衫袴,也疑心徐義生同我鬧玩笑,有意把絨衫袴藏過了。後來在操場上找到了他,他說實在沒有看見。這樣說來,一定是有人偷了去了。”舍監道:“你去把他們三個人找來,我還有話問他們呢。”幼蘭答應了一聲,就出去了。
不多一會,許幼蘭帶了同房間的三個人,一同來到舍監室裡。舍監把許幼蘭失去絨衫袴的事,向三人問了一遍。三人的言語,也和幼蘭一樣,都說這件事情奇怪得狠,究競是那一個偷的,我們可實在不知道。舍監察他們的神情,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後來舍監又問他們道:“你們各人的物件,都檢點過了嗎?除了這一套絨衫袴之外,可曾失掉別的東西沒有?”舍監這句話,倒把他們四個人都提醒了,異口同聲的說道:“我們還沒有查過,不知可曾失掉什麼呢!”舍監道:“現在倒也不必著忙,你們同我到宿舍裡去,大家細細的檢查一下,再作道理。”當時舍監便立起身來,帶了四個學生,一窩風的趕到十三號裡。四人把自己的箱籠物件,逐一打開,攤在房裡。一來給舍監過過目,以免嫌疑;二來自己也好檢點檢點,恐怕內中失掉了什麼。舍監先走到許幼蘭的床前,仔細察看了一會,也看不出什麼可疑的痕跡。正在這個當兒,那王仁榮忽然嚷起來道:“不好了!我一只金表不見了。表上還有一條金練條呢!”接連著鄭季蓀也氣吼吼的嚷道:“我箱子裡的鈔票八十元,也一齊不見了!這是那裡說起?照這樣看來,寄宿舍裡,簡直是個賊窩了!我們還能夠住嗎?”舍監聽了,走過來看了一看,點點頭道:“我早已料到你們所丟的,決不止一套絨衫袴的。現在嚷也沒用,須得趕緊偵查才是。”徐義生站在一傍,慢吞吞的道:“我倒好像沒有失掉什麼。可是我的東西太多,一時也記不清楚了。”王仁榮道:“我的金表,本來是帶在身邊的。前天忽然壞了機件,不能用了,所以就放在床面前小桌子的抽屜裡,預備後天禮拜日,帶出去修理的。昨天早上,我開抽屜取一管筆,見那表還好好的擱在抽屜角裡。今天忽然丟了,真是怪事!”鄭季蓀道:“我箱子裡的鈔票八十元,並不是我自己的。前天我的舅舅來看我,聽說我快要放假回去了,所以將這錢交給我,托我帶給舅母的。我恐怕放在身邊,不大穩當,所以鎖在箱子裡。現在忽然失掉了,教我怎樣去見舅母呢?而且還有一樁奇事,這箱子依舊好好鎖著,裡邊的鈔票怎樣會不翼而飛?我倒實在不懂了!”舍監把他箱子上的鎖一看,搖搖頭道:“這種中國式的銅鎖,普通得狠,同樣的鑰匙甚多,就是用一根鐵絲,也能夠把他撥開,這倒不足為奇。據我看來,這偷鈔票和金表的人,當然就是偷絨衫袴的人了。而且失竊的時候,一定在昨晚十點鐘之後,今晨七點鐘之前。但是那時候你們四人,都睡在房裡,這個賊竟敢進來偷東西,他的膽子,未免也太大了。難道他開箱取物的時候,你們四人在床上,竟然一個也不聽見麼?”四人聽了,面面相覷,都說昨天晚上,實在不聽得什麼聲音,就是今天早上,也沒有人到房裡來過。舍監沉吟了一會,便道:“你們收拾課本,預備上課去罷!等我將各房間檢查之後,再定辦法。我想金表和鈔票,都是狠小的東西,一時未必能搜得出來。現在只要把絨衫袴能夠查出,其餘的東西,自然也有著落了。”四人聽了,就跟著舍監,一同出來,命茶房把房門鎖好,便各自往課堂中去了。
舍監把寄宿舍各房間,逐一檢查,白忙了半天,到底也查不出什麼證據來。回到舍監室裡,便把那門房桂生,叫了進來,問他道:“今天一早,可有寄宿的學生出校去嗎?”桂生道:“每天校門一開,就有學生出入。今天早上,進出的學生狠多,一時實在記不清楚了。”舍監道:“可有人帶著包裹出去嗎?”桂生想了一想道:“有的。早晨七點鐘時候,中學二年級的張允文,帶了一個包裹出去,包裹裡面,好像是幾件衣服。”舍監聽了,心中一動,命桂生退了出去,就打發一個茶房,去把二年級的學生張允文,叫來問話。茶房去了一會,把張允文帶到舍監室。舍監劈頭就問他道:“你今天早上七點鐘,到那裡去的?”允文聽了,登時一呆,面上狠露著驚慌的樣子,勉強答道:“我是出外散步去的……”舍監道:“散步為什麼要帶一個包裹呢?那包裹裡是什麼東西?”允文見舍監提起包裹,更覺慌了,支吾著回答道:“包裹裡是一套短衫袴。因為穿得臟了,帶出去洗的。”舍監道:“這話就不對了!洗衣公司的人,天天到這裡來的,你何必自己送去?”允文聽了,無言可對,低頭不語。舍監要把他袋裡的東西,檢查一下。允文起先不肯,後來被舍監逼得沒法,只得把衣袋裡的東西,一齊掏出來,放在桌上。舍監看是皮夾一只、鉛筆一枝、洋刀一把、銅元十幾枚。舍監把皮夾打開一看,裡邊有名片六七張、五元鈔票一張、一元鈔票三張,另外卻還有一張“源來典當”的當票,當價二十元。票上的日子,果然就是這一天。可惜當的什麼東西,卻因為當票上的字,難識得狠,所以看不出來。舍監拿著當票問道:“這票子是那裡來的?你當掉的,究競是什麼東西?”允文哭喪著臉道:“我因為沒有錢用,所以當掉了一件灰鼠皮馬褂!”舍監冷笑道:“恐怕不是皮馬褂罷?”允文道:“實在是一件皮馬褂!先生若不相信,可以贖出來看的。”舍監聽了,也就不與他分辯,立刻在自己身邊,掏出二十一塊錢,打發一個茶房,去把那當的東西,贖了出來;一面對張允文說道:“你不必去上課了,就在這裡坐一會再說。”允文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坐在一旁。舍監卻提起筆來,另外辦他的公事了。
停了半點鐘,贖當的茶房回來。他贖出來的,果然是一件灰鼠皮馬褂。舍監見了,覺得出乎意料之外,當時把那件馬褂,反反覆覆看了一會,忽然問張允文道:“我看這件馬褂,又長又大,與你的身材不合,決不是你自己的。你不妨從實對我說,這馬褂究競是那一個的?”允文此時無可掩飾,只得實說道:“這馬褂是徐義生的。”舍監聽了,又是一楞,心中暗想:徐義生這人,可算得糊塗極了!自己失掉了一件皮馬褂,為何絕不提起呢?這時候舍監的心裡,以為這件馬褂,一定是張允文偷來的,所以他又問道:“這樣說來,那十三號裡失去的金表、鈔票,一定也是你拿的了?”允文聽了一呆,急忙分辯道:“什麼金表、鈔票?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就是這件馬褂,也是徐義生自己給我,教我去當的!”舍監詫異道:“此話奇了!他為什麼要把這馬褂給你當呢?”允文道:“徐義生是我的表兄,他在這一學期內,絡續借了我三十塊錢。現在我問他討,他沒有錢還我,所以把這件馬褂給我,教我替他當了。當下來的錢,就算是還我的。”舍監道:“他幾時給你的呢?”張允文道:“今天早上起來,他叫我到操場上,把這馬褂給我,教我趕緊去當,不要被別人知道。先生不信,盡可把徐義生叫來,我們當面對質。”舍監聽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命茶房去把徐義生叫來。停了一會,徐義生跟了茶房,來到舍監室,一眼看見張允文站在那裡,不覺一呆。舍監就把馬褂給他看道:“這件馬褂是你的嗎?”徐義生硬著頭皮道:“不差,是我的。”舍監道:“你的馬褂,為何卻給張允文當掉了?”徐義生言語支吾,一時回答不出。張允文在旁邊著急道:“這馬褂是你自己教我當的,現在可不能連累我呀!”徐義生知道無可掩飾,便道:“這馬褂的確是我給他的。因為借了他三十塊錢,一時還不出來,他逼得我沒法,所以教他把馬褂當掉,還了他再說。”舍監道:“當來的錢呢?”張允文道:“我還去了十二塊錢的食物帳,所以皮夾裡邊,還剩八塊錢。”舍監嘆口氣道:“你們平常的用途,本來靡費慣了,一到沒錢的時候,便做出這等勾當來!自己想想,豈不慚愧?如今也不用說了,十三號裡失去的東西,定然是你們兩個人拿的,究竟鈔票、金表等物,藏在那裡,快快的說出來罷!”徐、張二人聽了,都駭了一跳,沒口的分辯道:“金表和鈔票,我們實在沒有拿!這可不能怪我們的!”舍監對徐義生道:“十三號裡的東西,據我看來,一定是房間裡人拿的!現在你們四個人,只有你沒失掉東西,這就是一個大大的破綻。況且今天早上,又是你第一個起身,這件案子,你總脫不了千系。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說出來罷。”徐義生見舍監一口咬定是他,急得他面紅耳赤,賭神罰咒,抵死也不肯承認。舍監又向張允文盤問,張允文更叫起撞天屈來。他說連十三號失物的事情,也一點沒有知道。舍監見問不出什麼,只得罷了,當時便把兩人軟禁在一間自修室裡,預備等校長到來,再作道理。可是這樣一來,學堂裡邊,議論紛紛,都說徐義生和張允文偷了東西,給舍監先生查出了。一霎時間,全校學生,沸沸揚揚,都把這事當做新聞講,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了。
(下)
這一天的午後,李飛偶然為著一件事,去看舍監。他們本來是親戚,所以倒也不拘師生的跡形。兩個人坐在舍監室裡,隨意談了一會。舍監偶然提起十三號裡失物的事情,觸動了李飛好奇之心,他便自告奮勇,意欲著手偵查,要求舍監把那案子的內容,敘述一番。舍監也無可無不可,當時就將那案中經過的情節,詳詳細細,講給他聽。他聽過之後,想了一會,便問舍監道:“照表叔看來,這件案子,與徐、張兩人有關係嗎?”舍監狠堅決的說道:“張允文是否同謀,我倒不敢說。至於徐義生卻一定有關係的。”李飛道:“表叔說他有關係,有什麼證據呢?”舍監道:“充分的證據,現在還沒有尋出。不過他對於這件案子,的確有許多可疑的地方。”李飛道:“可疑的地方在那裡呢?”舍監道:“十三號房間裡,一總住著四個人,三個人都失掉東西,只有他一個人沒失什麼,這是第一樁可疑。各物被竊的時間,是在昨晚十點鐘之後、今晨七點鐘之前,這時候四個人都睡在房裡,外人決不敢進去偷東西的,可見這個竊物的人,一定就在房間裡住的了。但是其餘三個人,都是失主,斷沒有可疑的地方。除了徐義生,還有那一個呢?這是第二樁可疑。平常每天早晨,他起身的時候,也和人家差不多。今天卻第一個起來,比人家格外早些,這是第三樁可疑。他平常用錢狠闊綽,這幾天卻在窘鄉。凡人處境窘迫,便是造成罪惡的原因,或者因為窘得沒法,就做出這胠篋的勾當,也是有的。這是第四樁可疑。有此四種原因,所以我敢決定他和失物的案子,狠有嫌疑。”李飛聽舍監說完,便道:“表叔怎生知道失物的時間,是在昨晚十點鐘之後呢?”舍監道:“因為偷金表、鈔票的人,一定就是偷絨衫袴的人。據許幼蘭說,他的線衫袴,是在昨晚十點鐘拿出來的。由此推測,可知這竊物的人,一定在十點鐘之後下手的了。”李飛聽畢,搖搖頭,一聲不響,後來又問道:“假使金表和鈔票,果然是徐義生偷的,那末我倒有些不懂了。他既然有了鈔票,為何還要把自己的皮馬褂當掉呢?”舍監聽了,倒也一呆,想了一會道:“這個問題,果然大可研究。或者他欠人家的債,為數太多,偷來的錢,還不夠抵償,所以又把自己的馬褂當了。”李飛道:“這卻未必!因為學生時代的靡費,究竟有限。八十塊錢的鈔票,再加上一只金表,也有一百多塊錢了,難道還不夠還債嗎?”舍監道:“也許他有意把馬褂當掉,預備事發之後,洗刷自己的嫌疑的。”李飛搖著頭道:“也不見得!他當掉馬褂的時候,並未當眾宣布,要不是表叔給他查出來,有那個知道呢?這樣的預備洗刷,心思未免太曲折了。”舍監道:“據你看來,這件事便怎樣呢?”李飛道:“這件案子,倒狠有研究的價值。據我看來,張、徐二人,對於此案,恐怕沒有什麼關係。其中卻另有一個人,狠是可疑。不過現在還不能說,等我調查一下,自然就明白了。”舍監詫異道:“徐義生沒有關係,倒是那一個有關係呢?”李飛笑道:“寄宿舍裡邊,總有一個有關係的人。不過現在沒有贓證,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宣布,還是不說的好。”這時候李飛便立起身來,走到舍監的寫字臺前,把桌上的告假簿,翻了一翻,忽然微微—笑,好像得到了什麼證據似的。舍監不懂他的意思,又不好問他。停了一會,李飛又問道:“現在徐義生和張允文,還在自修室裡嗎?”舍監道:“還在裡邊。”李飛道:“我要問他們幾句話,問明白了,再來研究罷!”當時便別了舍監,匆匆的去了。
隔了五分鐘,李飛回到舍監室。舍監問他調查得怎樣了,李飛道:“此案的內幕,已經有五六分明白了。不過贓物藏在那裡,一時倒不容易偵查。只要贓物查得,那偷東西的人,自然不敢抵賴了。我想這半日之內,贓物未必就能運出。現在事不宜遲,倒要趕緊想法檢查才好。”舍監道:“寄宿舍裡,我剛才已經完全查過了。查不出來,也是枉然。”李飛道:“據我看來,這贓物還在十三號裡,其餘房間,毫無關係,可以不必查了。現在我們再到十三號裡,細細的檢查一下,你看如何?”舍監道:“狠好。”當時兩人便趕到十三號裡。
李飛到了裡邊,上上下下,仔細查看。後來又在四人的床上,逐一翻視。最後查到許幼蘭的床上,剛把被頭一翻,忽然喊了一聲“啊呀”,把那只右手,縮了出來。舍監跑去一看,原來那被頭的棉絮裡,藏著一枚針。李飛沒有曉得,把手去翻,恰巧碰在針上,被那針刺了一下,手心中間,刺了些血出來。李飛把針拔出,見那針眼上邊,還有一尺多長的一條藍線。舍監道:“這針怎樣會遺失在棉絮裡?豈不要刺痛蓋被的人嗎?”李飛把針和線,拿在手裡,看了一會,好似想起了什麼似的,又把床裡的被頭,細細的看了一會,上上下下,捏了幾下,忽然對舍監道:“不必查了,我已經明白了。現在回到外邊,商量破案的辦法罷!”舍監見他這個樣子,簡直莫名其妙,只得跟了他一同出來。
李飛回到舍監室,想了一會,忽然教舍監把十三號裡的四個人,一齊叫來。舍監點點頭,就打發一個茶房去了。李飛又暗地關照舍監道:“停會他們來了,我說怎樣,你便依我怎樣,切不可和我反對。這件案子,包你就明白了。”舍監點頭答應。不多一會,四個人絡續來到舍監室。李飛等他們到齊了,便發言道:“去年我在蘇州的時候,遇到一個催眠術專家,他教了我一套外國圓光的法子,狠是靈驗。這外國的圓光,與中國不同。譬如失掉了東西,只消拿一碗清水,噴在失物的地方,不到五分鐘,這竊賊的小照,就能在水裡現出來了,五官四肢,清清楚楚。好在隨便男婦老小,都能夠看得出來。這種法子,我已經試過幾遍,百發百中,靈驗得狠。今天十三號寄宿舍裡,忽然失掉了許多東西,舍監因為查不出來,教我把那外國圓光的法子,試演一下,以免冤屈好人。我是義不容辭,只得把諸君請來,我們一同到十三號裡,當眾試驗。要是圓出了那一個的小照,自然不能抵賴了。”眾人聽了李飛這番話,都覺得十分奇怪。外國的圓光術,非但眼睛裡沒有見過,就是耳朵裡也沒有聽見過。大家似信不信,可也沒有人同他辯駁。舍監坐在旁,心中也覺納罕,暗想李飛那裡會圓什麼光,分明在那裡搗鬼,不知弄的是什麼玄虛。幸而李飛早已同他說明,無論怎樣,不能和他反對,也只得由他去說罷。李飛說完之後,便命茶房去到廚房間裡,舀了一大碗的清水來。他就拿著這清水,招呼舍監,帶了許幼蘭等四個人,一同來到十三號裡。舍監和四個人,四散的立著,好似看戲法一般。房間裡邊,寂靜無聲,專等李飛試演他的圓光妙術。李飛定了定神,先問王仁榮道:“你的金表放在那裡的?”王仁榮道:“就在這個桌子的抽屜角裡。”李飛搖搖頭道:“不好,不好。抽屜角太小了,顯出來的小照,恐怕看不清楚。”又問鄭季蓀道:“你的鈔票放在那裡的?”鄭季蓀道:“就在這個箱子裡。”李飛又搖搖頭道:“不好,不好。箱子裡邊,更不清楚了。”第三個便問許幼蘭道:“你的絨衫袴放在那裡的?”許幼蘭道:“放在床角裡被頭上的。”李飛點點頭道:“好了,好了。這個賊的影子,就教他現在被頭上罷!”說著就走到許幼蘭的床前,呼了一口水,要想噴上床去。許幼蘭見了,急忙上前阻擋道:“我的床上,怎好噴水?噴濕了被褥,教我今夜怎樣睡呢?”李飛把水吐在痰盂裡,對著幼蘭笑道:“被褥濕了,可以烘幹的,有何妨礙?你若阻擋我,就是心虛,我也不必試驗了。”舍監和其餘三人,急於要看圓光,也都說道:“被褥濕了,可以烘的,何必著急?”幼蘭見眾人都如此說,只得退了下來。李飛見幼蘭走開了,便索性把一大碗水,望床上一倒,登時那被頭上面,濕了一大塊。眾人立在床前,眼睜睜望著被頭上,預備看那竊賊的小照。連這位舍監朱先生,也目不轉睛,呆呆的望著。不料等了好一會,被頭上面,影蹤全無,不要說小照看不出來,連個影子都沒有看見。舍監把李飛拉到一邊,暗暗的埋怨他道:“你平日歡喜研究偵探學,我以為你一定有些學識,所以借這案子,想讓你練習練習。你怎樣玩起這種荒唐的把戲來了?現在被頭上面,一點也現不出什麼,不但你丟臉,連我也沒有面子!學堂裡的事情,怎好當作兒戲?萬一被校長曉得了,成何體統?我真上了你的當了。”李飛笑道:“我早與表叔約好的,無論怎樣,不可和我反對,現在為何又同我反對起來了?”舍監被他一說,倒也無言可對。這時候許幼蘭等四個人,因為看不出竊賊的小照,議論紛紛,都來質問李飛。許幼蘭因為弄濕了他的被褥,更是忿恨,橫眉怒目,把李飛任意揶揄。李飛卻嘻皮涎臉的笑道:“我的法子,向來是極靈驗的。今天忽然不靈,連我自己也不懂了。現在弄濕了你的被褥,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叫一個茶房來,把被褥拆開,拿去烘幹了再說。這總算是我的不是,請你別生氣罷。”李飛說完,便立刻去叫了一個茶房進來,命他拿一把剪刀,把許幼蘭的被褥拆開。茶房去拿了剪刀來,正要動手,許幼蘭駭了一跳,急忙上前攔阻道:“這被褥雖然濕了,停一會自然會幹的,不必拿去烘了。”李飛忙道:“不行,這水潑得太多了,不烘是決不會幹的,還是拆開的好。”幼蘭發怒道:“我的被褥,怎樣要你做起主來了?真是笑話!”舍監見幼蘭不願拆,意欲上前攔阻,李飛急忙對他施了一個眼色。舍監這時候,也有幾分明白了,便也指揮茶房,趕緊把被褥拆開。幼蘭見舍監上前吩咐,自然不敢再來攔阻,登時急得面如土色。眼見得那茶房一剪一剪,把被頭上的線腳剪開,只急得他臉上的顏色,青一陣,白一陣,好不難看。不多一會,線也拆開了,被面也拉開了。眾人定睛一瞧,忽然異口同聲的嚷道:“咦……絨衫……咦……絨袴……”原來那被面與棉絮的中間,卻夾著一套絨衫袴。舍監看了,也詫異道:“這一套絨衫袴,怎樣會跑到被頭中間去的?真是怪事!”李飛搶步上前,把絨衫拉在手裡,用手一摸,忽然在絨衫的袋裡,掏出兩樣東西來。眾人一看,又異口同聲的嚷道:“咦……金表……咦……鈔票……”這時候的許幼蘭,恨不得有一個地洞,鉆了下去。
案破了,徐義生和張允文的冤枉也明白了。真真的竊賊,原來卻是許幼蘭。舍監把這件事情,回明校長。許幼蘭當然開除,徐、張兩人,也都記了一個小過。王仁榮和鄭季蓀,因為他們的金表、鈔票,珠還合浦,都來向李飛道謝。而徐義生、張允文兩人,心中尤為感激。
事過之後,舍監便問李飛道:“這件事情,隨便那一個看來,都以為是徐義生偷的,你卻怎樣會疑心到許幼蘭的身上?我倒不懂,這個理由,你能講給我聽嗎?”李飛道:“天下的事情,不論怎樣曲折,總逃不出‘情理’二字。這件案子,一定是十三號裡的人所為。這個見解,我與表叔是相同的。十三號裡,一共四個人,倒有三個失掉東西,論理自然是那個沒丟什麼的徐義生,最為可疑了。但是那義生倘然偷了這些東西,為何還要當掉一件皮馬褂呢?這是最大的一個疑問。我剛才已經說過了,除了徐義生之外,據我看來,最可疑的,便是許幼蘭了。他雖然第一個來報告,說是失了一套絨衫袴,你想一套舊的絨衫袴,所值幾何?這個賊既然偷到了金表、鈔票,還要冒著險到他床上去偷一套舊的絨衫袴,是何道理?天下難道有這樣的笨賊嗎?還有一樁,照表叔所說,失竊的時間,一定在昨夜十點鐘之後。這句話我卻不敢贊同。因為這個時候四個人都睡在房裡,那一個膽大包天的,竟敢開箱子、拉抽屜,去偷這許多東西呢?據我看來,金表和鈔票,早在十點鐘之前,被人偷去,與這套絨衫袴,毫無關係,不過當時還沒有覺察罷了!後來我偶然查看告假簿,方知昨天下午,許幼蘭因頭痛請假,沒有上課。大凡寄宿生請了病假,當然睡在寄宿舍裡,這就是偷東西的好機會了。論理表叔檢查的時候,也應該想到這一層,不過當時你的心裡,總以為金表、鈔票,與絨衫袴一同失去的,所以昨晚十點鐘以前的事情,就不注意了。我既然解決了這兩層,便覺得許幼蘭這人,最是可疑。後來我為審慎起見,又親自去見徐義生、張允文、許幼蘭三個人,與他們談了一回。徐、張二人,語語是實,並無可疑的地方;倒是那個許幼蘭,有些神情恍惚,言語支吾。當時我便斷定許幼蘭是個嫌疑犯,他偷了東西以後,恐怕人家起疑,便有意把自己一套舊絨衫袴,設法藏過,一等天明,先來報告。這樣一來,他也算是失主的—份子,自然沒有人再疑心他了。你想他的用心,何等狡詐!我當時雖已證明,可惜贓證毫無,依舊不能宣布,所以我第二步的計劃,便是搜查贓證。後來我們到十三號裡檢查之時,不是在許幼蘭的被絮裡,發現一枚針嗎?這一枚針,倒是揭破黑幕的大關鍵。因為我發現了針之後,見那針上,還有一尺多長的一段藍線,我便仔細將那條被頭,反覆察看,見那被單和被面接連之處,一半是白線縫的,一半卻是藍線縫的。那藍線的針腳,參差不齊,好像倉猝縫攏的一般。再用手一摸,覺得那被絮裡邊,好像有一點不平的樣子。我此時便恍然大悟,知道失去的贓物,都藏在這被絮中間。我還怕猜的不確,所以假做圓光,有意搗鬼,將他的被褥弄濕,便可拆開一看。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偵探的理想和手續,說破了也不值一笑。”舍監點點頭道:“你的偵探學識,果然研究得不差!將來我狠希望你成一個中國的福爾摩斯呢!”李飛笑道:“這樣的案子,也配請教福爾摩斯嗎?”“……當當……當當……當當……” “啊呀!又在那裡敲上課鐘了!我要去上課了。再談罷!再談罷!”
原刊於《紅雜志》(1922年)第二十四期至第二十五期
(未完待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