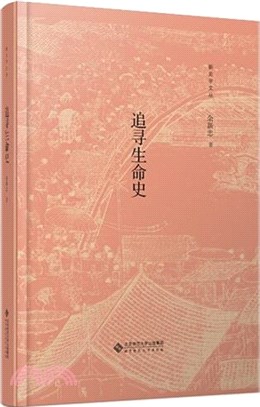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通過多年來自己在社會文化史領域中的研習和對這些個案的探索,更為感觸良深的是,若能跳脫以往過於關注直接關乎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大主題、熱衷宏大敘述的思維,將對歷史的認識與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來,真正將生命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並透過生命來探究歷史的狀貌和演變脈絡,那一定可以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相,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細致地觀察到生命歷程與體驗,並書寫出更接地氣、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讀者內心的記憶、體驗與經驗的歷史。
作者簡介
余新忠,浙江臨安人,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後。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兼院長,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職。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等著作5部,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百余篇。入選教育部領軍人才計劃青年學者和特聘教授等人才項目。榮獲全國優博論文獎,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一、二等獎等獎勵。
序
自 序
我的家鄉在浙西一個有些偏遠的山區小鎮——昌化,東距杭州100公裡,曾經是一個縣,杭州府屬下的一個末邑小縣。當地余姓的族人雖不少,但都無籍籍名,不過倒有一位生活於清後期的出家的先人,在家鄉留下了不少很有些來頭的傳說。他叫法云,曾於19世紀後半葉擔任京師城南的夕照寺住持20余年,因為擅長書法,而與賀壽慈、翁同龢和袁昶等達官貴人交好,在當時京城頗有些聲名,可謂風光一時。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沒有多少文化修養且無著述留世的小人物,時過境遷,雖有一鱗半爪的記載留存於浩瀚的史籍中,但其聲名早已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他的故事,若無我這個從事歷史研究的族中後人的鉤沉,大概已全然無人知曉。無意中看到的有關法云的史料,和記憶中有關法云傳說的關聯,激起了我探究的願望,經過一段時間廣泛的資料搜集,我最終幸運地較為完整地梳理出了這位族人的生命軌跡。透過這位族人的生命軌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個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狀貌,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未曾料想的時代場景和風氣。
站在當下,以歷史的眼光視之,法云無疑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過至少在普通人眼裡,其生前的日子顯然是有些風光的。而盛清揚州的醫生李炳,雖然也可謂是小人物,但在醫學史上則頗有些聲名(著名“溫病學家”),從文獻中看,稱其為盛清揚州第一名醫亦不為過。不過其生前卻窮困潦倒,乃至“身後無余財”。何以如此?以往的解釋都是因為他醫德高尚,有仁義之心,喜歡為貧賤之人治病而不願伺候富人。這樣的解釋顯然過於標簽化,有違日常的情理。當我透過文本,進入李炳的生命世界,便很容易發現,這一解釋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也不真實。之所以如此,主要緣於當時職業醫生地位低下,而他又是個性情耿直率真,行事比較偏執甚至孟浪之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之類的話語,不過是受其恩惠的友人在特定的文本中為其窮困潦倒所做辯解修飾之詞而已。
這些都不過歷史長河中細微的個案,從個案入手探究歷史,早已成為歷史研究十分常見的做法,毫不新鮮。作為專業的研究者,大概沒有人願意就事論事,就個案而個案,而都希望通過個案來呈現更宏大的歷史。那如何將個案和大歷史勾連起來?現有做法往往是努力引入整體史的視野,將自己探究的地方和案例置於較大的區域、全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文化背景中來討論。然而這種結構式的處置,真的可以讓自己以及他人(即便具有整體視野)努力呈現的歷史片段,最終成功地拼成一幅整體的歷史圖景嗎?這顯然值得懷疑,事實上,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已有不少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者對此作出了他們的思考,主張通過“全面史”取代“整體史”來解決這一問題。[1]對此,我甚感認同,不過與此同時,通過多年來自己在社會文化史領域中的研習和對這些個案的探索,更為感觸良深的是,若能跳脫以往過於關注直接關乎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大主題、熱衷宏大敘述的思維,將對歷史的認識與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來,真正將生命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並透過生命來探究歷史的狀貌和演變脈絡,那一定可以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相,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細致地觀察到生命歷程與體驗,並書寫出更接地氣、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讀者內心的記憶、體驗與經驗的歷史。
幾年前,受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史學》編委會委托,我主編了一卷醫療史研究的專輯(第九卷),名之為《醫療史的新探索》。完成組稿開始撰寫序言時,“在對生命的關注中彰顯歷史的意義”這句話突然就冒了出來,感覺這實乃我探究醫療史的主旨,遂將其作為序的題名。事後細想起來,感覺關注生命,其實並非醫療史的專利,如前所述我對族人法云和尚的探究,無疑也是對生命的關注。但將這類關注生命的史學,稱為“生命史學”,似乎是恰當的。自從我開始探究疾病醫療史起,就一直覺得是在關注生命,但應該說早期的關注基本是概念性的,既沒有理論的自覺,也缺乏真切的體認。近十幾年來,我在從事醫療史的實證性研究之余,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以往的研究,思考醫療史研究的趨向和可能,思路和理念開始越來越向以具象的人為中心的新史學靠攏。應該與此有關,三年多前,當《人民日報》“理論版”約我寫一篇有關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小文時,我首先就想到了“生命史學”的概念,並將其作為醫療史研究的趨向。文章刊出後,我突然覺得,這對於當今中國史學的發展來說,應該是一個有一定指向性意義的概念,於是便特別去查詢了這個概念在國內外史學的應用情況,發現,雖然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史學界關於歷史研究中“人”的缺失的反思和批評很多,但“生命史學”的提法並不多,更少見有人明確提出“生命史學”的概念來對此加以救濟。李建民先生曾出版過一本名為《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的著作,他在該書的自序中稱:“《生命史學》旨在建構一個完整的古典醫學研究體系,同時也發掘真知識。”[2]在書中,他並沒有特別解釋這一概念,但通讀全書,感覺他應該是將其當做醫學史的另一種稱謂,而之所以以此名之,大概是因為醫學直接關係生命,希望通過其研究,從中國歷史和中國醫學出發,來體會“生命是什麼”。我所謂的“生命史學”,在理念上似與該著不無一致,但顯然有著非常不同的旨趣。
在我看來,“生命史學”並不只是醫學史或醫療史的代名詞,而且也絕不僅限於醫史,不過也毫無疑問,醫史是“生命史學”最為重要的實踐領域之一。“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讓其回到人間,聚焦健康。也就是說,我們探究的是歷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制度和環境等外在性的事務,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群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我們固然要用學術的理性來梳理歷史的脈絡,但也不能忘記生命的活動和歷史並不是完全用理性所能理解和解釋的,更不能忘記一直以來生命對於健康本能不懈的追求及其種種的體驗與糾結。更進一步說,我想或許可以用三句話來加以闡發。(1)歷史是由生命書寫的。這就意味著我們探究歷史時關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識是理所當然的。(2)生命是豐富多彩而能動的。這就是說,歷史固然有結構、有趨向,但歷史的演變既不是所謂的結構可以全然決定的,似乎也不存在可以預見的規律。鮮活而能動的生命不僅讓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和多樣性,也讓書寫豐富、複雜而生動的歷史成為可能並且變得必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更多地關注文化的意義與影響,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興史學思潮的理念和方法。(3)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
這裡結集的是我近十多年來圍繞著“關注生命”而展開探索的心得,雖然綜合起來,名之為“追尋生命史”似無不可,但因為完成於不同的時期,而且寫作的目標不盡一致,這方面的意蘊的濃淡,差異頗大,不過這也正好展現了自己學術道路上學習和探索的歷程。感謝譚徐鋒先生長期以來對筆者研究的關注和抬愛,讓自己有機會整理舊作,回顧、反省自己的學術歷程,並思索未來可能的進路。同時也謝謝我的博士生宋娟女士,她為本書的編排和核校付出了大量的辛勞。
不知不覺中,我已到了古人所謂的“知天命”之年,雖然遠不敢說自己對人生有什麼通達的認識,但多年的生活和研究經歷,確實讓自己日益真切地體會到,相比於那些歷史舞臺上轟轟烈烈的政經大事和大人物,不起眼的民眾的生命狀態和日常生活,才是更能展現時代風貌的“存在”,也才是影響歷史演進更為基本而綿綿瓜瓞的力量。如是,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在以關注並呈現普通而具象生命為核心的“生命史學”的探究道路上繼續前行呢?!
余新忠
2018年8月4日草於津門寓所
目次
自序
疫病社會史研究:現實與史學發展的共同要求
從社會到生命:中國疾病、醫療社會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
衛生史與環境史:以中國近世歷史為中心的思考
回到人間 聚焦健康:新世紀中國醫療史研究芻議
醫療史研究中的生態視角芻議
微觀史與中國醫療史
當今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問題與前景
生命史學:醫療史研究的趨向
在對具象生命的關注中彰顯歷史的意義
淺議生態史研究中的文化維度:基於疾病與健康議題的思考
環境史研究中的環境維度和歷史維度
文化史視野下的中國災荒史研究芻議
新文化史視野下的史料探論
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
個人·地方·總體史:以晚清法云和尚為個案的思考
“良醫良相”說源流考論:兼論宋至清醫生的社會地位
揚州“名醫”李炳的醫療生涯及其歷史記憶:兼論清代醫生醫名的獲取與流傳
醫聖的層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與現代中醫知識建構系列研究之一
書摘/試閱
疫病社會史研究:
現實與史學發展的共同要求
說起中國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當歷史修養的知識人,也會感到茫然。在傳統的史學視野中,瘟疫這樣似乎無關歷史發展規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規律的內容,不過為歷史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些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至多也只是歷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長期以來,閱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並不能讓人明白“瘟疫”為何物。
如今,生活在科技飛速發展時代、享受著現代醫學種種嘉惠的人們,與那種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記憶自然更是漸行漸遠。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2年年底以來,一種全新的疫病SARS突然降臨於神州大地,並幾乎迅速傳遍全國並遠流海外。面對這一不期而至的現代瘟疫,社會一時流言四起、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令人不得不感喟,原來,那種能夠危及全民的瘟疫並非只存在於塵封的歷史中,而是隨時都有可能進入我們的現實生活。
現在,這場令人心悸的災難至少暫時已經過去,隨著人們日常生活漸漸恢復正常,那些曾經由SARS帶來的生活限制、緊張、焦慮以及混亂也自然會慢慢地淡出蕓蕓眾生的記憶。但無論如何,在思想文化界,知識人顯然不可能輕易地讓這場銘心的災難如此迅速地消散於無形的空氣中,從而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失去一次“亡羊補牢”的機會。毫無疑問,非典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醫療衛生問題,由這場現代瘟疫所引發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無論哪一方面都值得我們整個社會很好地省思。“亡羊補牢,未為晚矣”乃是中華民族早已爛熟於心的道理,事實上,所謂“後SARS時代”的種種反思目前已在學界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些反思是多層面的,既有對現實社會機制的批判和建構,也有對當今社會發展總體理念以及中國文化建設的重新思考,還有有關當下學術發展理路的反省,等等。這些從不同視角出發的反思無疑都自有其價值,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省思不可能僅僅立足於SARS本身而展開,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認識人類以往的相關經驗,否則,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厚度。由此可見,對人類瘟疫歷史的回顧與認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現實意義,實際上,面對非典,我們的政府、社會和民眾所表現出的驚慌無措、應對失宜,也與今人對瘟疫史的失憶不無關係。
顯而易見,瘟疫絕不僅僅是自然生理現象,而是關涉醫療乃至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社會文化問題,故而,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實際上,確切地講,其欲探討的也就不應稱之為瘟疫史,而應是疫病社會史或疫病醫療社會史。即該研究並不只是關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從疫病以及醫療問題入手,呈現歷史上人類的生存境況與社會變遷的軌跡。當然,開展這一研究,並非只是出於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或許更為重要的還是源於其獨特的學術價值。人之一生,與自身最密切相關的莫過於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這些似乎無關社會發展規律之類宏旨的細微小事,其實正是人類歷史最真實、最具體的內容。現代國際學術發展趨向,已經逐漸擺脫對結構、規律和因果關係等的過度追求,而表現出對人本身的關注以及對呈現人類經驗的重視。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史學工作者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社會發展規律等問題的探討之中,而對歷史上人的生存狀況、生活態度和精神信仰等與人本身直接相關的問題則往往視而不見,瘟疫這一雖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但顯然並不直接關乎歷史發展規律且本身又不具規律性的內容,自然就更不在歷史學家的視野之中了。在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雖然隨著社會史研究的興起,衣食住行已越來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關乎生老病死的疾病醫療,基本還是歷史學的“漏網之魚”。然而實際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難發現,疫病與醫療無論對歷史還是當今社會都有著極其重要而深刻的影響,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曾在《瘟疫與人》中指出:“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流行病傳染模式的變遷,過去和現在一直都是人類生態上的基本地標,值得更多地關注。”[1]由於疫病始終與人類相伴隨,給人類帶來了難以盡述的痛苦和恐懼,因此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應對疾病的醫療觀念和實踐也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和形塑著人類的行為和思想,進而廣泛而具體地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呈現和透視歷史上的疾病醫療,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人類的生存狀況以及社會歷史的變遷。由此可見,疫病社會史研究乃是一個十分重要並具有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從筆者自身的研究體會來說,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對了解歷史上人們的生存狀況、精神面貌、環境與社會的變動、民眾的心態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將可以使我們看到一幅“真實存在”卻長期以來未被發掘的重要歷史面相。
歷史學對包括瘟疫在內的疾病醫療的忽視,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乃是一個世界性普遍問題。不過,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一傾向在西方史學界就已出現改觀,至今,探討歷史上的疾病醫療以及借此透視社會和文化的醫療社會史和身體史研究乃是當前史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並業已成為主流史學的一部分。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海外乃至國內的中國史研究,1975年美國的鄧海倫(Helen Dunstan)發表了國際中國史學界最早的具有自覺意識的疫病社會史論文——《明末時疫初探》[2]。隨後,大約分別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和大陸史學界也逐漸興起了疫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當然,海峽兩岸這一研究的興起,並非僅是世界史學潮流影響而致,可能更為重要的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內部對以往研究的不滿與積極反省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和臺灣史學界不約而同地開始對史學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條公式主義的困境”或“社會科學方法的貧乏”展開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對以往研究過於側重政治、經濟、階級斗爭及外交和軍事等做法表示出了強烈不滿,提出了“還歷史以血肉”或“由‘骨骼’進而增益‘血肉’”這樣帶有普遍性的訴求。[3]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社會群體、社會生活、社會人口、社會救濟、社會環境等一些過去不被注意的課題開始紛紛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大大拓展了歷史研究的界域。在臺灣,在梁其姿、杜正勝等人的努力實踐和積極倡導下,其研究目前已漸成風氣,成為臺灣史學的熱點之一。而大陸雖然起步較晚,而且當下的研究與臺灣相比,仍處於散兵遊勇狀態,既乏人倡導,也未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自然就更談不上有什麼指引和規劃,但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甚至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同時,還不斷有年輕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開始介入其中,顯現出這一研究未來良好的發展勢頭。[4]由此,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剛剛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
人類瘟疫歷史長期被歷史學界所忽視,應該不是偶然的,個中的緣由,除了史料中有關瘟疫的記載相對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規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特別對中國史學界來說,恐怕更主要還與我們的學術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關。那就是,在我們學術理念中,缺乏一種對生命的真正的關懷。為了生存和發展以及鑒往知來,往往熱衷於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或者歷史規律的探尋,而唯獨忽視了歷史的主體——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雖然生命的可貴對每個人來說可能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我們整體的社會理念中,個體的生命在很多情況下其實不過是實現某種整體社會目標的一個環節和工具,而較少能真正體認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倫理。其實,對生命的缺乏關懷又豈止存在於學術理念之中,在我們的社會意識、統治思想中又何嘗不是如此?穩定和發展對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這一切不能建立在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珍視的基礎上,不僅穩定和發展恐怕很難長久地保持,而且更為根本的,若穩定和發展不是為了個體生命的福祉,那意義又在哪裡呢?認識到了這一點,其實就不難發現,我們學術上以及現實中的很多積習其實都與我們缺乏對生命的真正關懷和珍視有關。比如,學術上,過於追求宏大敘述而輕忽歷史細節,熱衷於規律的探尋而忽視人的生存境況等;現實中,片面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不加思考地將“革命”“改革”視為社會最高目標,施政辦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災不報等。如果從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過對歷史上與人類生存環境和境況息息相關的瘟疫的鉤沉,將有利於我們真正了解歷史上的生命,從而培養我們關注生命、珍視生命的意識。而一旦這樣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也就增加了破除以往學術上、社會上乃至政治上的種種積習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在我們當前的境遇下,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將有可能同時具備學術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由此可見,從社會史的視角探討歷史上的瘟疫與醫療的疫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在當前的情形下,無論從現實還是學理來說,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義的。
本文原刊於《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