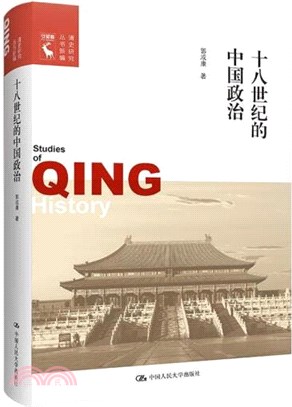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從康熙帝晚年,經雍正朝,直到乾隆帝去世,祖孫三代皇帝的統治跨越了整個18 世紀。這 100 年間,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經過持續變革的重構,以皇帝為核心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高度強化並漸臻完備。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內在矛盾演變、滿洲傳統文化政治取向及國內外形勢日趨嚴峻等多重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
與皇權擴張、國家治理效能強大相同步,18 世紀中葉清朝的國勢達到了為外域矚目、乾隆帝自詡的“全盛”。
18 世紀清朝國家政治體制組織架構嚴整、協調、靈活、高效;國政常規議事流程靈活、實用、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統治者無須眾議或摒棄眾議的所謂“聖衷宸斷”,康雍乾時代並不經見,而通行的則是皇帝諭示議題,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議覆,最後由皇帝欽斷的常規議事程序,這有現存清代軍機處、內閣等浩如煙海的檔案為證。
應充分肯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臨前夜,18 世紀中國政治體制最大限度發揮國家權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強大優勢,對實現大一統偉業、強化多民族國家意識認同的歷史性貢獻。
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皇帝很難始終如一地保持政治開明的作風,君主專制政體禁錮思想、鉗制輿論、銷磨人才、敗壞吏治等黑暗面日益彌漫。乾隆帝晚年喜諛惡諫、喜柔惡剛、喜從惡違的由人性弱點決定的專制偏好,更營造出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的政治迷信。盛清也未能擺脫糾纏古代中國政治的歷史宿命。
與皇權擴張、國家治理效能強大相同步,18 世紀中葉清朝的國勢達到了為外域矚目、乾隆帝自詡的“全盛”。
18 世紀清朝國家政治體制組織架構嚴整、協調、靈活、高效;國政常規議事流程靈活、實用、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統治者無須眾議或摒棄眾議的所謂“聖衷宸斷”,康雍乾時代並不經見,而通行的則是皇帝諭示議題,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議覆,最後由皇帝欽斷的常規議事程序,這有現存清代軍機處、內閣等浩如煙海的檔案為證。
應充分肯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臨前夜,18 世紀中國政治體制最大限度發揮國家權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強大優勢,對實現大一統偉業、強化多民族國家意識認同的歷史性貢獻。
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皇帝很難始終如一地保持政治開明的作風,君主專制政體禁錮思想、鉗制輿論、銷磨人才、敗壞吏治等黑暗面日益彌漫。乾隆帝晚年喜諛惡諫、喜柔惡剛、喜從惡違的由人性弱點決定的專制偏好,更營造出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的政治迷信。盛清也未能擺脫糾纏古代中國政治的歷史宿命。
作者簡介
郭成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已退休。1941 年出生,北京市人。現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文史館館員。主要研究清史。出版《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政治卷》《乾隆正傳》等專著,發表《康乾之際禁南洋案探析——兼論地方利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也談滿族漢化》《清朝皇帝的中國觀》《劉興祚論》等論文。與劉景憲先生合譯《盛京刑部原檔》(滿文)。
名人/編輯推薦
郭成康著的這本《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通過18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和完備、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18世紀後期政治的腐敗、千秋功罪——從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政治的觀感談起四章內容,研究了中國十八世紀的政治制度。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18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和完備
第一節順康時期乾綱獨斷政治目標的初步實現
第二節奏折的創行和推廣
第三節密諭的嬗變與軍機處的肇建
第四節18世紀中國的國家中樞——軍機處
第二章|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
第一節部院與督撫的權力配置
第二節中央決策與地方的關係
第三章| 18世紀後期政治的腐敗
第一節政治腐敗的種種特征
第二節18世紀後期政治嚴重腐敗的原因
第四章| 千秋功罪——從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政治的
觀感談起
參考書目
第一章| 18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和完備
第一節順康時期乾綱獨斷政治目標的初步實現
第二節奏折的創行和推廣
第三節密諭的嬗變與軍機處的肇建
第四節18世紀中國的國家中樞——軍機處
第二章|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
第一節部院與督撫的權力配置
第二節中央決策與地方的關係
第三章| 18世紀後期政治的腐敗
第一節政治腐敗的種種特征
第二節18世紀後期政治嚴重腐敗的原因
第四章| 千秋功罪——從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政治的
觀感談起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再版前言
這本書初版刊行於二十年前,書名是《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政治卷》(遼海出版社,1999),2001年臺灣昭明出版社以《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為名又出過一版,這次有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我想借此機會,談談這些年來對18世紀中國政治的再思考。
01
從康熙晚年,經雍正朝,直到乾隆去世,祖孫三代皇帝的統治跨越了整個18世紀。這100年間,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經過持續變革的重構,以皇帝為核心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漸臻完備,國家權力的集中、高效、強大,超越了以往歷代王朝。
下面從三個維度來考察這一中國古代政治新局面的成因。
其一,輿論環境有利於強化皇權。
明初是中國君主專制政治體制變革的一大關鍵。明太祖朱元璋打出復古旗號,高標“事皆朝廷總之”,一舉廢棄通行千年的人主分寄大權於宰相的漢唐舊制。但經過有明二百餘年的政治實踐,皇帝獨攬朝政不僅徹底落了空,還鬧出了晚明天子怠政,閹宦竊權,閣臣狼狽,言路囂張,朋黨亂政,以至社稷傾覆的慘禍。明清之際,厭倦了政局混亂的國人望治心切,有識之士激切指斥“先朝君子”同同相扶,異異交擊,有好惡而無是非,遂致事體蠱壞,國勢凌夷,“害深河北之賊,罪浮東海之波!”包括漢族精英主流在內要求強化皇權的思潮興起,而黃宗羲復宰相制的主張應者寥寥。清初統治者因利乘便,從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初期,在沿襲包括內閣在內的明代官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其高度警惕宰相制的復活,並以有別於明帝的躬理萬機的勤政姿態,將用人行政大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另一方面,則悉心探索如何對掣皇權之肘的內閣及科道等前明官制加以全面改造。
其二,滿洲崇尚集中、統一和“實行”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
滿族與漢族是各有不同歷史譜系、文化傳統的民族,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漢文化雖始終居於主體地位,但滿文化卻挾有政治威權發揮著主導作用,其政治體制變革始終堅持清帝所標榜“乾綱獨斷”的集中、統一取向,凡與此相悖而足以紊亂朝政者,諸如朋黨、權臣以及言官幹政之類,皆在撻伐掃蕩之列。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雍正對發祥時期滿洲文化精華的提煉與運用,貫徹重構政治體制的始終。18世紀初期,正當清朝統一中原後邁向國勢全盛時代的新起點,雍正回顧歷史,對滿洲百年崛起的最大優勢和根本經驗做了精辟概括:“我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略耳。”在他看來,東北一隅的滿洲之所以無敵於天下,靠的就是“實行”和“武略”兩大法寶,而今人哲學範疇的方法論――“實行”,竟被置於“武略”之上,著實耐人尋味。“實”者,重在認知,崇實務實;“行”者,強調知易行難,行勝於言。雍正不取漢儒習用的“實事求是”,而別出心裁地選擇“實行”一詞,更可以看出他對“行”的格外看重。康雍乾三帝,堪稱“實行”路線一脈相承的踐行者,對於至關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造與新創,其胸中絕對沒有現成的藍圖,也不像漢族士大夫要遵循什麼神聖古訓、金科玉律,他們只確定了最終目標――被推崇為“治隆唐宋”的明太祖首倡的“事皆朝廷總之”,設定了校正前進方向的反面參照物――明祖子孫怠荒懶政及由制度性缺陷而釀成的朝政囂雜紛亂,然後就一路“實行”起來,摸索前進了。從康熙不經意間創行密折,以周知天下隱情,到雍正時政務運行的主要載體奏事折子的普遍行用;從皇帝隨手在奏折上親書密批,到親重大臣代書密諭,再到密發諭旨規範為威重天地的“廷寄”;從選調名為“內中堂”的閣臣到內廷當值承旨書諭,到雍正間西北兩路用兵,辦理機務的親重大臣為天子所須臾不可離,國家新型軍政中樞軍機處遂浮出水面;從廢止巡按御史,到臺省合一,強化言路管控;從不立太子、皇帝晏駕前指定嗣君,到仿漢制立太子,行不通,廢太子,再立再廢,直到以“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立儲”的所謂秘密立儲垂為定制――在漫長的政治體制變革路上,舉凡國家權力機構、政治制度有所興革,無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率先實行起來,然後不斷在實踐中驗證、反思、改進、完善,最終決定取舍的標準只看是否行之有效。就這樣,持續百年,歷盡坎坷,終於在改造傳統宰相制和前明內閣制的基礎上,創建出最便於人主乾綱獨斷的新型政治體制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
其三,國內外形勢日趨嚴峻的壓力。
最早把遙遠的歐洲國家視為中國最危險的潛在對手的是康熙,他君臨天下55年時曾鄭重告誡身邊重臣:“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西洋,清初以來一般指大西洋歐洲國家。這位極富政治閱歷的老人正是基於其對西洋人侵略本性的認識和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安,才做出這一帶有預言性質的警告的。乾隆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全盤接受了其祖父對西洋人的疑懼和防範。18世紀中葉,清廷鎮壓了一起未遂的反清陰謀,為首者馬朝柱曾向其信徒宣稱“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統兵三萬七千”,乾隆得悉深為驚悚,為此持續多年窮追“西洋”之所在。而他在位時的厲行禁教,固然考慮到了西洋天主教“煽惑愚民”,有害於“世道人心”這一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著眼於政治,唯恐居心叵測的西洋人潛入內地,勾結奸民顛覆清廷統治。不能說他的政治判斷沒有現實的根據:一方面是來自歐洲列強越來越逼近國門的威脅;另一方面,在盛世繁花似錦的表象下,確實隱伏著難以化解的滿漢民族矛盾和由於人口倍增、物價持續上漲、吏治腐敗所引發的社會騷動。在18世紀快要落下帷幕之際,西洋最強大的國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訪華,其使臣馬戛爾尼的傲慢倔強,英王禮物反映出來的科技水平、軍事實力,給予乾隆強烈震撼。他一再密令軍機大臣傳諭沿海各督撫:“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該國夷人雖能諳悉海道,善於駕馭,然便於水而不便於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內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面對稱霸海上的英國艦隊,乾隆深知中國的制海權已淪於英人之手。在日益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壓力下,缺乏自信的乾隆越來越趨向選擇對外封閉、對內嚴控作為基本國策。
02
在上述主客觀多重因素疊加作用的推動下,與皇權擴張到空前強大相同步,18世紀中葉清朝的國勢達到了外域矚目、乾隆皇帝自詡的“全盛”。這不盡是妄自尊大的浮夸,隨同馬戛爾尼使華、周歷半個中國的斯當東稱中國“國勢的隆盛是超越千古的”,當代美國史學家魏斐德也贊譽當時清朝是“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如果說在相權對皇權構成某種制衡的“聖君賢相”開明專制下,相繼出現“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治世合乎儒家政治理念、順乎天下人心,而無須特別論證的話,那麼,康雍乾三帝另辟蹊徑,擺脫對皇權的種種羈絆和制約,在堪稱極端君主專制體制下,竟也締造出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那又該如何解釋呢?
請看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特征。
首先,保留滿洲開國時期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皇帝以新創的軍機處為中樞,處理國家緊急、重大、機密的軍政要務,輔之以固有的內閣處理日常的有例可循的庶政,在皇帝的控制、督責與協調下,軍機處與內閣、六部分工明確,朝政最後由皇帝裁斷。
其次,改造傳統題本的僵化程式,創行奏折制度,皇帝及時掌握事關國家安危治亂的重要信息,信息的搜集、處理和反饋以及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夸張一點說,已呈現出某種近代性。加以驛站、軍臺、塘鋪網絡覆蓋全國,驛傳制度周備,政令傳達迅速通暢,不存在君主鞭長莫及的死角。
再次,通過機密的廷寄諭旨,對各省督撫和邊遠地區將軍等嚴加操控,朝廷之於地方,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轉自如,令行禁止。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都絕對聽命於皇帝。
最後,新創秘密立儲制的審慎運作,既能防範傳統皇位繼承制度預立太子難免激化諸皇子之間,甚至太子與其父皇之間的矛盾,又可以不拘嫡長子的限制,在所有皇子中遴選最優秀的皇儲,並通過長期培養、教育和暗中考察,由皇帝做出最終是否令其承繼皇位的決定。清帝先天素質較高,且凜然恪守“勤政”家法,有助於實現乾綱獨斷。
康雍乾三帝在明洪武廢相後,經過長期摸索和縝密思考,終於構建起以君主個人之力獨攬朝政的國家中樞――軍機處和內閣,加以廷寄、奏折及驛傳聯絡朝廷與地方,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嚴整、協調、靈活、高效,較之漢唐盛世有過之而無不及。
政治體制架構的完備,只是超越前代、國勢興盛的組織前提,只有深入探討其權力的運行機制,才能揭示出其內在奧秘。
權力運行機制集中體現在諸凡政務的處理,特別是軍國大計的決策上。其整個過程的常規程序一般是須經皇帝諭示議題,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議覆,最後由皇帝欽斷。皇帝也完全可以不循常規程序,不經眾議而獨斷,即所謂“聖衷宸斷”。
以關係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民生及國家金融的18世紀前期禁南洋貿易案為例,從嚴禁到弛禁、從封閉到開放,其間朝廷決策幾經反復:康熙晚年事前既沒有征詢東南沿海督撫的意見,也未經交付大學士、九卿、科道合議,即倉促獨斷,頒布禁南洋貿易令;雍正中期,皇帝將福建總督高其倬《復開洋禁折》批交怡親王允祥與大學士、九卿等共同會議,廷臣議覆請開南洋商販,雍正允準實行;乾隆初年,署閩浙總督策楞密折奏請再禁南洋,皇帝批交“議政王大臣速議具奏”,隨即又將閩籍御史李清芳反對全面禁南洋一折交“議政王大臣一並議奏”,議政王大臣以此案事關東南沿海各省,奏準交閩廣江浙督撫妥議具奏,迨各該督撫陸續奏到,乾隆再交付議政王大臣等議奏,經裕親王廣祿等會議,奏請維持雍正既定方針,仍準南洋“照舊通商”,乾隆降旨準行,開放政策未發生逆轉,自康熙晚年以來一波三折的禁南洋貿易案至此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清帝常掛在嘴上的“乾綱獨斷”,既指朝政一般經過眾議,最後由皇帝裁斷的常規程序,也有如康熙的撤三藩、驅準安藏、禁南洋貿易和乾隆平準那樣無須眾議或摒棄眾議的“聖衷宸斷”。後者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並不經見,而前者則是通行的、連皇帝也不肯輕易違反的常規,這有現存清代軍機處、宮中及內閣浩如煙海的檔案為證。
中國18世紀通行的朝政議事和軍國大計決策常規,與唐太宗凡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的主張與實踐,在通過眾議以力求規避國家政務失誤與皇權高度集中相統一的實質上,並無區別,至於交由哪個國家機構、眾議采取何種程序,也都沒有嚴格的法律規範,而完全由皇帝作風、經驗和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所決定。如果說二者有所不同的話,在形式上清代常規議事流程更靈活,更實用,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因為它要應對比漢唐時代更大、更復雜的內外變局,倒不是因為康雍乾三帝比唐太宗更加高明。
總之,深入研究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內在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客觀評價其最大限度發揮國家權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強大優勢,對國家和民族做出的歷史性積極貢獻,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極端君主專制體制下出現了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
03
縱觀18世紀極端專制體制,在皇帝比較開明的前提下,朝政議事和軍國大計決策才往往失誤較少,而問題在於,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皇帝很難始終如一地保持開明的為政作風,一旦轉而好自專斷,拒諫飾非,以至群臣緘口或阿諛順旨,就可能因重大決策錯誤而埋下危及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巨大隱患。
還是就18世紀中國開放還是封閉這件大事來檢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獨斷禁南洋貿易,絕非一時的孤立事件。身歷康雍乾三朝,對其間政治氣候冷暖有切身體會的方苞論及康熙晚年為政風格時曾說:“時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京外熟諳東南環海形勢與地方民情的閩籍廣東副都統陳昂對禁南洋雖持異議卻不敢直言,直到臨死上遺疏謂其子曰:“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為民請命,我今疾作,終此而不言,則終莫上達矣。”廷臣“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地方大員“又莫敢為民請命”,人之將死才敢跟皇上講真話,蓋懾伏於康熙皇帝自恃的所謂“英明果斷”,這就是當時極端專制黑暗面的生動寫照。
雍正繼位,一改其父晚年專制獨斷作風,親筆朱諭向兩廣總督孔毓?求教:“朕實不達海洋情形,所以總無主見”,並委托其“博訪廣詢,謹慎斟酌其至當奏聞”。乾隆初政,如臨如履,唯恐失誤,一日之中朱筆細書,折成方寸,或咨詢張廷玉、鄂爾泰,或咨詢孫嘉淦、朱軾,“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可見雍正,繼之以乾隆,糾正康熙晚年獨斷禁南洋的失誤,絕非一時孤立的事件,同樣是皇權不受制衡的極端專制,可以因皇帝的開明而呈現政治和煦氣象。
順帶說一下雍正晚年在決策軍政大計前對眾議的重視和自覺堅持。18世紀30年代,繼續出兵準噶爾蒙古,抑或遣使議和,是關係重大的頭等軍務,雍正反復斟酌,自言“二者均難遽定”,故特召西北兩路統兵將軍來京與軍機大臣等悉心計議,結果意見仍然分歧。雍正以茲事體大,“理應博采眾議,詳慎籌劃”,遂命滿漢文武大臣共同會議,“各陳己見,據實具奏”。此時距他執政最後一年以57歲辭世,大約一年光景。
與雍正有所不同,乾隆初政的開明逐漸向專斷轉化了。18世紀中葉限制西方國家來華貿易的廣州單口通商的決策,就是在未經廷議,也沒有很好協調廣東與江浙等沿海省份利益關係的情況下,由皇帝采取非常規決策程序“聖衷宸斷”的。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首次來華談判中英貿易,其時中國還具有足以同這個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相抗衡的實力,通過外交手段為中國爭取到最大利益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一方,但乾隆壓根兒就不打算跟這幫不懂“禮儀”的野蠻人打交道,更談不上考慮應采取何種策略以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決策時不僅沒有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撫議奏,也沒有交軍機大臣等統治集團最核心層會議,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諭英王”的口吻將英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與合理的――一股腦兒地全部回絕,隨即有禮貌地將英國使臣推出國門拉倒。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中英貿易談判,就這樣以簡單草率的方式關上了大門。如同康熙一樣,乾隆這時也“臨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斷”的專制威權更遠遠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在往返京師與云南原籍後向皇帝講了點真話,奏稱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庫帑虧空,“商民半皆蹙額興嘆”,乾隆大為光火,厲聲呵斥其“將所奏直隸等省虧空者何處?商民興嘆究系何人?逐一指實覆奏!”嚇得失魂落魄的尹壯圖無法也不敢指實,乾隆仍令其隨同欽差大臣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實地盤庫,自然是欽差未到,各省早已挪掩完畢,尹壯圖往返數千裡,最後承認“各省庫項豐盈,倉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法司以尹壯圖妄生異議論斬,乾隆雖饒他一命,但在處理這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大案中,皇帝鉗制人口、愚弄天下的淫威,以及暮年君主恃氣虛驕的心態已暴露無遺。乾隆晚年喜諛惡諫、喜柔惡剛、喜從惡違的由人性弱點決定的專制偏好,營造了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的政治迷信,反過來又助長了乾隆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自我膨脹,他譏諷唐太宗的納諫為沽名釣譽,把襄贊政務的大學士視為贅疣。在這樣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中,出現對西方貿易決策的兩次重大失誤絕對不是偶然的;在這樣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中,即使遵循常規議事程序,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也要大打折扣,臣下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議政又怎麼能充分深入?
18世紀的中國,對皇權的制度性約束已蕩然無存,政治開明與否,只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即孫嘉淦所期望的“皇上之聖心自懔之”。誠然,乾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為了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也確實“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專制體制內在的邏輯力量,最終還是把他推上極端專制的頂峰。
平心而論,即使在史家稱頌“君明臣直”的貞觀年間,在位不過23年的唐太宗也邁不過這道坎兒,未能永葆開明作風。貞觀十七年(643年),以面折廷爭、犯顏苦諫而為帝所敬畏的魏徵病卒,皇上親制碑文,命陪葬昭陵,可謂備極身後哀榮。然尸骨未寒,太宗就以魏徵“阿黨”、沽名這樣莫須有的罪名,撲毀所撰墓碑,一代諫臣瞬間從天上墜入地下。司馬光以獨到的史識、細膩的筆觸描述了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到貞觀中“雖勉從之,猶有難色”的演變心跡。其間太宗曾以“魏徵每廷辱我”,揚言早晚殺了這個“田舍翁”!可見他的“踣所撰碑”,乃對魏徵多年積怨的總爆發,也是封殺悠悠眾口的示威。據《資治通鑒》記載,魏徵去世兩年,太宗親征高麗,無功而返,深悔之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遂“復立所制碑”。這不過是司馬光為唐太宗納諫故事平添的一個光明尾巴,但他以史為鏡警戒為帝為王者的良苦用心,揆諸古代政治史,即使在皇權受到某種制度性制衡的君相制時代,效果也實在有限。
總而言之,唐太宗沒有解開古代政治這一死結,乾隆皇帝也沒有解開這一死結。
郭成康
2019年11月
這本書初版刊行於二十年前,書名是《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政治卷》(遼海出版社,1999),2001年臺灣昭明出版社以《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為名又出過一版,這次有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我想借此機會,談談這些年來對18世紀中國政治的再思考。
01
從康熙晚年,經雍正朝,直到乾隆去世,祖孫三代皇帝的統治跨越了整個18世紀。這100年間,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經過持續變革的重構,以皇帝為核心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漸臻完備,國家權力的集中、高效、強大,超越了以往歷代王朝。
下面從三個維度來考察這一中國古代政治新局面的成因。
其一,輿論環境有利於強化皇權。
明初是中國君主專制政治體制變革的一大關鍵。明太祖朱元璋打出復古旗號,高標“事皆朝廷總之”,一舉廢棄通行千年的人主分寄大權於宰相的漢唐舊制。但經過有明二百餘年的政治實踐,皇帝獨攬朝政不僅徹底落了空,還鬧出了晚明天子怠政,閹宦竊權,閣臣狼狽,言路囂張,朋黨亂政,以至社稷傾覆的慘禍。明清之際,厭倦了政局混亂的國人望治心切,有識之士激切指斥“先朝君子”同同相扶,異異交擊,有好惡而無是非,遂致事體蠱壞,國勢凌夷,“害深河北之賊,罪浮東海之波!”包括漢族精英主流在內要求強化皇權的思潮興起,而黃宗羲復宰相制的主張應者寥寥。清初統治者因利乘便,從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初期,在沿襲包括內閣在內的明代官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其高度警惕宰相制的復活,並以有別於明帝的躬理萬機的勤政姿態,將用人行政大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另一方面,則悉心探索如何對掣皇權之肘的內閣及科道等前明官制加以全面改造。
其二,滿洲崇尚集中、統一和“實行”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
滿族與漢族是各有不同歷史譜系、文化傳統的民族,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漢文化雖始終居於主體地位,但滿文化卻挾有政治威權發揮著主導作用,其政治體制變革始終堅持清帝所標榜“乾綱獨斷”的集中、統一取向,凡與此相悖而足以紊亂朝政者,諸如朋黨、權臣以及言官幹政之類,皆在撻伐掃蕩之列。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雍正對發祥時期滿洲文化精華的提煉與運用,貫徹重構政治體制的始終。18世紀初期,正當清朝統一中原後邁向國勢全盛時代的新起點,雍正回顧歷史,對滿洲百年崛起的最大優勢和根本經驗做了精辟概括:“我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略耳。”在他看來,東北一隅的滿洲之所以無敵於天下,靠的就是“實行”和“武略”兩大法寶,而今人哲學範疇的方法論――“實行”,竟被置於“武略”之上,著實耐人尋味。“實”者,重在認知,崇實務實;“行”者,強調知易行難,行勝於言。雍正不取漢儒習用的“實事求是”,而別出心裁地選擇“實行”一詞,更可以看出他對“行”的格外看重。康雍乾三帝,堪稱“實行”路線一脈相承的踐行者,對於至關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造與新創,其胸中絕對沒有現成的藍圖,也不像漢族士大夫要遵循什麼神聖古訓、金科玉律,他們只確定了最終目標――被推崇為“治隆唐宋”的明太祖首倡的“事皆朝廷總之”,設定了校正前進方向的反面參照物――明祖子孫怠荒懶政及由制度性缺陷而釀成的朝政囂雜紛亂,然後就一路“實行”起來,摸索前進了。從康熙不經意間創行密折,以周知天下隱情,到雍正時政務運行的主要載體奏事折子的普遍行用;從皇帝隨手在奏折上親書密批,到親重大臣代書密諭,再到密發諭旨規範為威重天地的“廷寄”;從選調名為“內中堂”的閣臣到內廷當值承旨書諭,到雍正間西北兩路用兵,辦理機務的親重大臣為天子所須臾不可離,國家新型軍政中樞軍機處遂浮出水面;從廢止巡按御史,到臺省合一,強化言路管控;從不立太子、皇帝晏駕前指定嗣君,到仿漢制立太子,行不通,廢太子,再立再廢,直到以“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立儲”的所謂秘密立儲垂為定制――在漫長的政治體制變革路上,舉凡國家權力機構、政治制度有所興革,無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率先實行起來,然後不斷在實踐中驗證、反思、改進、完善,最終決定取舍的標準只看是否行之有效。就這樣,持續百年,歷盡坎坷,終於在改造傳統宰相制和前明內閣制的基礎上,創建出最便於人主乾綱獨斷的新型政治體制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
其三,國內外形勢日趨嚴峻的壓力。
最早把遙遠的歐洲國家視為中國最危險的潛在對手的是康熙,他君臨天下55年時曾鄭重告誡身邊重臣:“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西洋,清初以來一般指大西洋歐洲國家。這位極富政治閱歷的老人正是基於其對西洋人侵略本性的認識和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安,才做出這一帶有預言性質的警告的。乾隆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全盤接受了其祖父對西洋人的疑懼和防範。18世紀中葉,清廷鎮壓了一起未遂的反清陰謀,為首者馬朝柱曾向其信徒宣稱“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統兵三萬七千”,乾隆得悉深為驚悚,為此持續多年窮追“西洋”之所在。而他在位時的厲行禁教,固然考慮到了西洋天主教“煽惑愚民”,有害於“世道人心”這一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著眼於政治,唯恐居心叵測的西洋人潛入內地,勾結奸民顛覆清廷統治。不能說他的政治判斷沒有現實的根據:一方面是來自歐洲列強越來越逼近國門的威脅;另一方面,在盛世繁花似錦的表象下,確實隱伏著難以化解的滿漢民族矛盾和由於人口倍增、物價持續上漲、吏治腐敗所引發的社會騷動。在18世紀快要落下帷幕之際,西洋最強大的國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訪華,其使臣馬戛爾尼的傲慢倔強,英王禮物反映出來的科技水平、軍事實力,給予乾隆強烈震撼。他一再密令軍機大臣傳諭沿海各督撫:“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該國夷人雖能諳悉海道,善於駕馭,然便於水而不便於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內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面對稱霸海上的英國艦隊,乾隆深知中國的制海權已淪於英人之手。在日益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壓力下,缺乏自信的乾隆越來越趨向選擇對外封閉、對內嚴控作為基本國策。
02
在上述主客觀多重因素疊加作用的推動下,與皇權擴張到空前強大相同步,18世紀中葉清朝的國勢達到了外域矚目、乾隆皇帝自詡的“全盛”。這不盡是妄自尊大的浮夸,隨同馬戛爾尼使華、周歷半個中國的斯當東稱中國“國勢的隆盛是超越千古的”,當代美國史學家魏斐德也贊譽當時清朝是“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如果說在相權對皇權構成某種制衡的“聖君賢相”開明專制下,相繼出現“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治世合乎儒家政治理念、順乎天下人心,而無須特別論證的話,那麼,康雍乾三帝另辟蹊徑,擺脫對皇權的種種羈絆和制約,在堪稱極端君主專制體制下,竟也締造出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那又該如何解釋呢?
請看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特征。
首先,保留滿洲開國時期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皇帝以新創的軍機處為中樞,處理國家緊急、重大、機密的軍政要務,輔之以固有的內閣處理日常的有例可循的庶政,在皇帝的控制、督責與協調下,軍機處與內閣、六部分工明確,朝政最後由皇帝裁斷。
其次,改造傳統題本的僵化程式,創行奏折制度,皇帝及時掌握事關國家安危治亂的重要信息,信息的搜集、處理和反饋以及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夸張一點說,已呈現出某種近代性。加以驛站、軍臺、塘鋪網絡覆蓋全國,驛傳制度周備,政令傳達迅速通暢,不存在君主鞭長莫及的死角。
再次,通過機密的廷寄諭旨,對各省督撫和邊遠地區將軍等嚴加操控,朝廷之於地方,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轉自如,令行禁止。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都絕對聽命於皇帝。
最後,新創秘密立儲制的審慎運作,既能防範傳統皇位繼承制度預立太子難免激化諸皇子之間,甚至太子與其父皇之間的矛盾,又可以不拘嫡長子的限制,在所有皇子中遴選最優秀的皇儲,並通過長期培養、教育和暗中考察,由皇帝做出最終是否令其承繼皇位的決定。清帝先天素質較高,且凜然恪守“勤政”家法,有助於實現乾綱獨斷。
康雍乾三帝在明洪武廢相後,經過長期摸索和縝密思考,終於構建起以君主個人之力獨攬朝政的國家中樞――軍機處和內閣,加以廷寄、奏折及驛傳聯絡朝廷與地方,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嚴整、協調、靈活、高效,較之漢唐盛世有過之而無不及。
政治體制架構的完備,只是超越前代、國勢興盛的組織前提,只有深入探討其權力的運行機制,才能揭示出其內在奧秘。
權力運行機制集中體現在諸凡政務的處理,特別是軍國大計的決策上。其整個過程的常規程序一般是須經皇帝諭示議題,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議覆,最後由皇帝欽斷。皇帝也完全可以不循常規程序,不經眾議而獨斷,即所謂“聖衷宸斷”。
以關係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民生及國家金融的18世紀前期禁南洋貿易案為例,從嚴禁到弛禁、從封閉到開放,其間朝廷決策幾經反復:康熙晚年事前既沒有征詢東南沿海督撫的意見,也未經交付大學士、九卿、科道合議,即倉促獨斷,頒布禁南洋貿易令;雍正中期,皇帝將福建總督高其倬《復開洋禁折》批交怡親王允祥與大學士、九卿等共同會議,廷臣議覆請開南洋商販,雍正允準實行;乾隆初年,署閩浙總督策楞密折奏請再禁南洋,皇帝批交“議政王大臣速議具奏”,隨即又將閩籍御史李清芳反對全面禁南洋一折交“議政王大臣一並議奏”,議政王大臣以此案事關東南沿海各省,奏準交閩廣江浙督撫妥議具奏,迨各該督撫陸續奏到,乾隆再交付議政王大臣等議奏,經裕親王廣祿等會議,奏請維持雍正既定方針,仍準南洋“照舊通商”,乾隆降旨準行,開放政策未發生逆轉,自康熙晚年以來一波三折的禁南洋貿易案至此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清帝常掛在嘴上的“乾綱獨斷”,既指朝政一般經過眾議,最後由皇帝裁斷的常規程序,也有如康熙的撤三藩、驅準安藏、禁南洋貿易和乾隆平準那樣無須眾議或摒棄眾議的“聖衷宸斷”。後者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並不經見,而前者則是通行的、連皇帝也不肯輕易違反的常規,這有現存清代軍機處、宮中及內閣浩如煙海的檔案為證。
中國18世紀通行的朝政議事和軍國大計決策常規,與唐太宗凡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的主張與實踐,在通過眾議以力求規避國家政務失誤與皇權高度集中相統一的實質上,並無區別,至於交由哪個國家機構、眾議采取何種程序,也都沒有嚴格的法律規範,而完全由皇帝作風、經驗和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所決定。如果說二者有所不同的話,在形式上清代常規議事流程更靈活,更實用,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因為它要應對比漢唐時代更大、更復雜的內外變局,倒不是因為康雍乾三帝比唐太宗更加高明。
總之,深入研究18世紀清朝政治體制內在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客觀評價其最大限度發揮國家權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強大優勢,對國家和民族做出的歷史性積極貢獻,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極端君主專制體制下出現了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
03
縱觀18世紀極端專制體制,在皇帝比較開明的前提下,朝政議事和軍國大計決策才往往失誤較少,而問題在於,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皇帝很難始終如一地保持開明的為政作風,一旦轉而好自專斷,拒諫飾非,以至群臣緘口或阿諛順旨,就可能因重大決策錯誤而埋下危及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巨大隱患。
還是就18世紀中國開放還是封閉這件大事來檢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獨斷禁南洋貿易,絕非一時的孤立事件。身歷康雍乾三朝,對其間政治氣候冷暖有切身體會的方苞論及康熙晚年為政風格時曾說:“時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京外熟諳東南環海形勢與地方民情的閩籍廣東副都統陳昂對禁南洋雖持異議卻不敢直言,直到臨死上遺疏謂其子曰:“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為民請命,我今疾作,終此而不言,則終莫上達矣。”廷臣“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地方大員“又莫敢為民請命”,人之將死才敢跟皇上講真話,蓋懾伏於康熙皇帝自恃的所謂“英明果斷”,這就是當時極端專制黑暗面的生動寫照。
雍正繼位,一改其父晚年專制獨斷作風,親筆朱諭向兩廣總督孔毓?求教:“朕實不達海洋情形,所以總無主見”,並委托其“博訪廣詢,謹慎斟酌其至當奏聞”。乾隆初政,如臨如履,唯恐失誤,一日之中朱筆細書,折成方寸,或咨詢張廷玉、鄂爾泰,或咨詢孫嘉淦、朱軾,“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可見雍正,繼之以乾隆,糾正康熙晚年獨斷禁南洋的失誤,絕非一時孤立的事件,同樣是皇權不受制衡的極端專制,可以因皇帝的開明而呈現政治和煦氣象。
順帶說一下雍正晚年在決策軍政大計前對眾議的重視和自覺堅持。18世紀30年代,繼續出兵準噶爾蒙古,抑或遣使議和,是關係重大的頭等軍務,雍正反復斟酌,自言“二者均難遽定”,故特召西北兩路統兵將軍來京與軍機大臣等悉心計議,結果意見仍然分歧。雍正以茲事體大,“理應博采眾議,詳慎籌劃”,遂命滿漢文武大臣共同會議,“各陳己見,據實具奏”。此時距他執政最後一年以57歲辭世,大約一年光景。
與雍正有所不同,乾隆初政的開明逐漸向專斷轉化了。18世紀中葉限制西方國家來華貿易的廣州單口通商的決策,就是在未經廷議,也沒有很好協調廣東與江浙等沿海省份利益關係的情況下,由皇帝采取非常規決策程序“聖衷宸斷”的。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首次來華談判中英貿易,其時中國還具有足以同這個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相抗衡的實力,通過外交手段為中國爭取到最大利益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一方,但乾隆壓根兒就不打算跟這幫不懂“禮儀”的野蠻人打交道,更談不上考慮應采取何種策略以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決策時不僅沒有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撫議奏,也沒有交軍機大臣等統治集團最核心層會議,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諭英王”的口吻將英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與合理的――一股腦兒地全部回絕,隨即有禮貌地將英國使臣推出國門拉倒。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中英貿易談判,就這樣以簡單草率的方式關上了大門。如同康熙一樣,乾隆這時也“臨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斷”的專制威權更遠遠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在往返京師與云南原籍後向皇帝講了點真話,奏稱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庫帑虧空,“商民半皆蹙額興嘆”,乾隆大為光火,厲聲呵斥其“將所奏直隸等省虧空者何處?商民興嘆究系何人?逐一指實覆奏!”嚇得失魂落魄的尹壯圖無法也不敢指實,乾隆仍令其隨同欽差大臣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實地盤庫,自然是欽差未到,各省早已挪掩完畢,尹壯圖往返數千裡,最後承認“各省庫項豐盈,倉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法司以尹壯圖妄生異議論斬,乾隆雖饒他一命,但在處理這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大案中,皇帝鉗制人口、愚弄天下的淫威,以及暮年君主恃氣虛驕的心態已暴露無遺。乾隆晚年喜諛惡諫、喜柔惡剛、喜從惡違的由人性弱點決定的專制偏好,營造了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的政治迷信,反過來又助長了乾隆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自我膨脹,他譏諷唐太宗的納諫為沽名釣譽,把襄贊政務的大學士視為贅疣。在這樣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中,出現對西方貿易決策的兩次重大失誤絕對不是偶然的;在這樣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中,即使遵循常規議事程序,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也要大打折扣,臣下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議政又怎麼能充分深入?
18世紀的中國,對皇權的制度性約束已蕩然無存,政治開明與否,只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即孫嘉淦所期望的“皇上之聖心自懔之”。誠然,乾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為了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也確實“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專制體制內在的邏輯力量,最終還是把他推上極端專制的頂峰。
平心而論,即使在史家稱頌“君明臣直”的貞觀年間,在位不過23年的唐太宗也邁不過這道坎兒,未能永葆開明作風。貞觀十七年(643年),以面折廷爭、犯顏苦諫而為帝所敬畏的魏徵病卒,皇上親制碑文,命陪葬昭陵,可謂備極身後哀榮。然尸骨未寒,太宗就以魏徵“阿黨”、沽名這樣莫須有的罪名,撲毀所撰墓碑,一代諫臣瞬間從天上墜入地下。司馬光以獨到的史識、細膩的筆觸描述了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到貞觀中“雖勉從之,猶有難色”的演變心跡。其間太宗曾以“魏徵每廷辱我”,揚言早晚殺了這個“田舍翁”!可見他的“踣所撰碑”,乃對魏徵多年積怨的總爆發,也是封殺悠悠眾口的示威。據《資治通鑒》記載,魏徵去世兩年,太宗親征高麗,無功而返,深悔之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遂“復立所制碑”。這不過是司馬光為唐太宗納諫故事平添的一個光明尾巴,但他以史為鏡警戒為帝為王者的良苦用心,揆諸古代政治史,即使在皇權受到某種制度性制衡的君相制時代,效果也實在有限。
總而言之,唐太宗沒有解開古代政治這一死結,乾隆皇帝也沒有解開這一死結。
郭成康
2019年11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