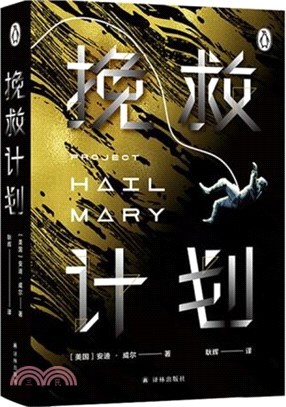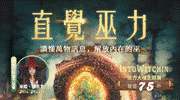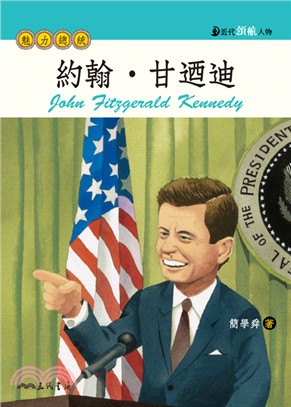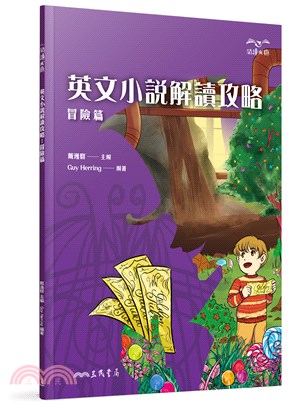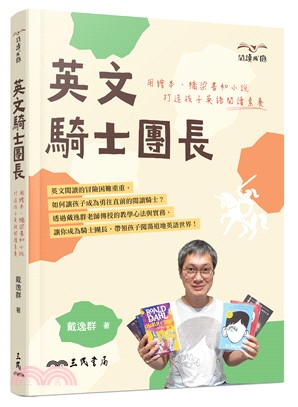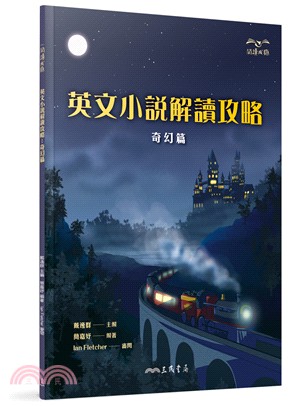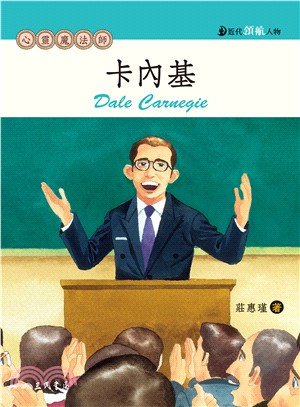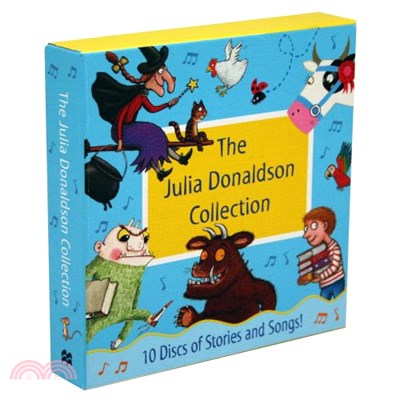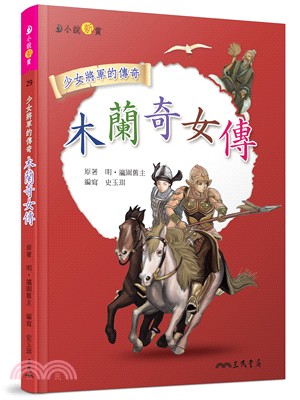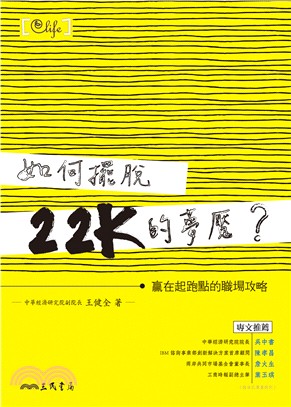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一趟孤注一擲的太空遠征,一座沒有盡頭的科學迷宮。
一次爭分奪秒的冒險營救,一段跨越星際的真摯友誼。
浩瀚宇宙中,瑞恩·格雷斯是整個人類文明僅存的希望。但在醒來的那一刻,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他在未知的恐懼中尋找身份,從記憶的碎片中獲取線索。這個肩負拯救地球重任的關鍵人物,現已命懸一線!人類文明究竟能否存續?在這場“挽救計劃”裡,一切都充滿了挑戰……
一次爭分奪秒的冒險營救,一段跨越星際的真摯友誼。
浩瀚宇宙中,瑞恩·格雷斯是整個人類文明僅存的希望。但在醒來的那一刻,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他在未知的恐懼中尋找身份,從記憶的碎片中獲取線索。這個肩負拯救地球重任的關鍵人物,現已命懸一線!人類文明究竟能否存續?在這場“挽救計劃”裡,一切都充滿了挑戰……
作者簡介
安迪·威爾,從15歲起就被美國國家實驗室聘為軟件工程師。執著的太空宅男,沉迷於相對論物理學、軌道力學和載人飛船。憑借處女作《火星救援》一炮而紅,由此改編的同名電影獲七項奧斯卡提名。現專職寫作。已出版作品:《火星救援》《月球城市》。《挽救計劃》是他的第三部長篇科幻小說。
名人/編輯推薦
1.科技宅男+跨星系好友聯袂上演太空大救援;硬核工程風+幽默碎碎念打造年度科幻。
2.出版後連續16周雄踞亞馬遜科幻暢銷榜。
3.萬人五星好評,讀者直呼比《火星救援》更燃、更爆;譯者坦言閱讀體驗像是在大腦裡進行了“一場煙花表演”。
4. 入選奧巴馬2021夏日書單;《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R.R.馬丁力薦:“這本書擁有老科幻迷所喜愛的一切。”
5.小說正式出版前,電影版權已高價售出;同名電影正在拍攝中,瑞恩·高斯林擔綱男主。
2.出版後連續16周雄踞亞馬遜科幻暢銷榜。
3.萬人五星好評,讀者直呼比《火星救援》更燃、更爆;譯者坦言閱讀體驗像是在大腦裡進行了“一場煙花表演”。
4. 入選奧巴馬2021夏日書單;《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R.R.馬丁力薦:“這本書擁有老科幻迷所喜愛的一切。”
5.小說正式出版前,電影版權已高價售出;同名電影正在拍攝中,瑞恩·高斯林擔綱男主。
書摘/試閱
第一章
“二加二等於幾?”
這個問題讓我有點煩躁。我累了,又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過了幾分鐘,問題又在我耳邊響起。
“二加二等於幾?”
輕柔的女性聲音,毫無感情,跟她上次提問的發音一模一樣。是計算機,是一臺計算機在折騰我。這讓我更煩躁了。
“不扶吾。”我說。我想要說的是“別煩我”——就我個人看來,眼下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可我說不清楚。
“錯誤,”計算機說,“二加二等於幾?”
是時候做個實驗了。我要試著打招呼。
“你嚎?”我說。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怎麼回事?我想要弄清楚,可又無從下手。我看不見,除了計算機也沒聽見別的聲音,甚至沒有觸覺。不,不對,有點觸覺。我正躺著,身下軟綿綿的,是一張床。
我覺得自己閉著眼睛,還不算太糟,只要睜開眼就行。我努力嘗試,可是沒有用。
為什麼睜不開?
睜。
睜……開!
睜。媽的!
噢!這回我感到一絲顫動,眼瞼動了,我能感受到。
睜開!
我的眼皮慢慢抬起,炫目的光線刺激著我的視網膜。
“晃!”我說。純粹依靠意志力我才強睜著眼睛,視野內白茫茫一片,讓我感到些許刺痛。
“檢測到眼動。”折磨我的家伙說,“二加二等於幾?”
白色減退,眼睛慢慢地適應,我開始看見形狀,但是還無法理解。我試試……手能不能動?不行。
腳呢?也不行。
可是我能動嘴,對吧?我一直在說話,雖然都是些廢話,但也算是在說。
“嘶。”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我開始明白眼前物體的形狀,我躺在一張……近似橢圓形的床上。
LED 燈照射著我,屋頂的攝像頭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盡管那很嚇人,可我更擔心機械臂。
屋頂上懸掛著兩條金屬手臂,表面處理成拉絲效果,每條手臂的末端本來應該是一只手,實際卻安裝著一種頗具穿透力的工具,令人深感不安,真是沒法讓我喜歡。
“嘶……嘶……”我說。能聽懂嗎?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該死的東西。我集中精神,匯聚全身的力量。另外,我開始有點恐慌了,不過沒關係,恐慌也能化為動力。
“嘶……四。”我總算說了出來。
“正確。”
謝天謝地,勉勉強強能說清了。
我放心地長出一口氣。等等——這不就是在控制呼吸?我有意識地又呼吸了一次,嘴巴幹澀,喉嚨生疼,可這都是我自己的感覺。我能掌控。
我戴著呼吸面罩,它緊緊扣在臉上,連接的軟管伸向我腦後。
我能起來嗎?
不能,但是可以稍微動一動頭。我低頭看自己的身體,發現我不僅一絲不掛,還連著數不清的管子。四肢上各有一根,“男性器官”上有一根,還有兩根伸到大腿下方,我猜其中一根插進了太陽曬不著的地方。
這可不妙。
而且,我渾身上下覆蓋著電極片。就跟檢查心電圖用的那種導聯貼一樣,只不過我這兒貼得到處都是。不過呢,還好只是覆蓋在皮膚上,沒有塞進身體裡。
“喔——”只有氣息沒有聲音,我又試了一次,“我…… 在哪兒?”
“八的立方根等於幾?”計算機問。
“我在哪兒?”我又問一遍,這次挺輕鬆。
“錯誤。八的立方根等於幾?”
我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說道:“2e(2pi)。”
“錯誤。八的立方根是多少?”
不過我沒錯,我只是想看看計算機有多聰明。結果:不怎麼聰明。
“二。”我說。
“正確。”
我等著聽接下來的問題,可計算機似乎已經滿意。
我累了,又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我醒過來。昏迷了多久?肯定有一會兒了,因為我感到精力充沛,不費吹灰之力就睜開眼睛。有進步。
我嘗試動動手指,並如願讓它們晃起來。沒問題,這回我真的好轉了。
“檢測到手部運動,”計算機說,“保持靜止。”
“什麼?為什麼——”
機械臂向我伸過來,它們移動快速,還沒等我弄明白,就除去了我身上大多數的管子。我沒有任何感覺,只是皮膚有點兒麻木。
最後我身上只剩下三根管子:手臂上的靜脈注射、伸進屁股的管子和導尿管。後兩者是我更想拔掉的玩意,不過,好吧。
我抬起右臂,然後任它墜落在床上,同樣的動作,我用左臂也做了一遍。我的雙臂像是灌了鉛一樣。我把這一過程重復了幾遍。我的手臂強壯,沒理由出現這種情況。我猜自己有嚴重的健康問題,而且已經在這張床上躺了一段時間。否則他們為什麼把我連接到那麼多設備上呢?不應該有肌肉萎縮嗎?
不應該有醫生嗎?或者醫院裡的聲音呢?這張床是怎麼回事?它不是長方形,而是橢圓形,我覺得它安裝在墻上,而不是在地板上。
“拔……”我沒了聲音,還是有點累,“拔掉管子……”
計算機沒有響應。
我又抬了幾次手臂,動了動腳趾,絕對是在好轉。
我前後活動腳踝,它們還能動,我抬起膝蓋,雙腿也強健有力,雖然不像健身愛好者那樣壯實,但是對於一個瀕死之人而言,也算十分健壯了。不過,我不確定我的雙腿原本是什麼樣的。
我把手掌按在床上,用力撐起上身。我居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雖然用盡了力氣,但我繼續堅持。這張床隨著我的移動輕輕搖晃,可以肯定,這不是一張普通的床。我把頭伸得更高,看見橢圓床的床頭和床尾固定在墻上,看上去很結實。它有點像固定的吊床,真奇怪。
很快,我就坐在了那根伸進屁股裡的管子上。這肯定不是最舒服的感覺,不過,什麼時候屁股裡插根管子會舒服呢?
此刻我看得更清楚了,這不是普通的病房。墻壁看似由塑料構成,整個房間是圓形,屋頂的LED 燈發出慘淡的白光。
墻上還有另外兩個類似吊床的床位,上面各躺著一個病人。我們排成一個三角形。騷擾我們的機械臂固定在房頂的正中間,我猜它們照顧我們所有人。我看不清兩位病友——他們跟我之前一樣陷進了床鋪裡。
房間沒有門,只有墻上的一段梯子通向……一扇艙門?艙門呈圓形,中間有一個轉輪把手。嗯,它肯定是某種艙門,像潛水艇上的一樣。也許我們三個得了傳染病?也許這是一間密閉的隔離病房?墻上各處布置著小型通風孔,我能感受到一股微弱的氣流。這裡的環境可能是受控的。
我把一條腿挪出床沿,結果床抖動起來,機械臂向我衝過來。我嚇得渾身一哆嗦,可是機械臂突然停住並懸在旁邊。我覺得它們時刻準備著在我摔倒時扶住我。
“檢測到全身運動,”計算機說,“你的名字?”
“噗,認真的嗎?”我問。
“錯誤,第二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張嘴想要回答。
“呃……”
“錯誤,第三次嘗試:你的名字?”
這時我才覺察出,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什麼都記不起來。
“呃。”我說。
“錯誤。”
一陣疲憊感襲來,不過感覺還挺舒服。一定是計算機通過靜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等……下……”我含混地說。
機械臂輕輕地把我放倒在床上。
我再次醒來,一條機械臂就在我面前。它在幹什麼?!
我嚇得往後一躲,只剩下震驚。機械臂撤回到屋頂的原位。我在臉上摸索,檢查是否受傷。一側有胡茬,一側光溜溜。
“你在給我刮胡子?”
“檢測到意識,”計算機說,“你的名字?”
“我還不知道呢。”
“錯誤,第二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是白人男性,說英語。讓我們賭一把,“約……約翰?”
“錯誤,第三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從胳膊上扯下輸液管。“與你無關。”
“錯誤。”機械臂朝我伸過來。我滾下床,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另外兩根管子還連在我身上。
屁股上的管子掉下來,一點都不疼。可充滿尿液的導尿管直接從我的下體被扯出去,這可疼壞了,感覺就像尿出了一顆高爾夫球。我疼得一邊尖叫一邊在地上打滾。
“身體疼痛。”計算機說。機械臂追過來,我在地上連滾帶爬,逃到另一張床底下。機械臂立即停住,但它們沒有放棄,而是在等待。
它們受一臺計算機操控,根本不會像人類一樣失去耐心。
我頭向後躺在地上,大口地喘息。過了一會兒,疼痛消退,我抹去了眼角的淚水。
我一點兒都不清楚這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嘿!”我喊道,“你們誰醒一醒!”
“你的名字?”計算機問。
“請你們哪個人類醒一醒。”
“錯誤。”計算機說。
這簡直太荒謬了,盡管下體疼得厲害,可我還是笑起來。此外腎上腺素也開始起作用,所以我感到頭暈目眩。我回頭看了下床邊的導尿管,心存敬畏地搖搖頭,那東西穿過了我的尿道,真不可思議。
而且拔出時它還造成了傷害,地面留下一絲血跡,一條細細的紅線——
我抿了一口咖啡,把最後一塊吐司扔進嘴裡,然後招呼服務員結帳。我本可以省點兒錢在家裡吃早餐,不必每天早晨來餐廳。考慮到我微薄的薪水,那大概是個好主意,可我討厭做飯,又喜歡吃雞蛋和培根。
服務員點點頭,走向收銀臺。可是就在這個空當,又有一位顧客坐進來,需要她招呼。
我看了眼手表,時間剛過七點,不著急。我習慣七點二十上班,這樣可以有時間準備下當天的工作。不過實際上八點上班就行。於是我掏出手機查看郵件。
收件人:天文奇觀(astrocurious@scilists.org)
發件人:伊琳娜•佩特洛娃博士(ipetrova@gaoran.ru)
主題:細細的紅線
我對著屏幕皺起眉頭,我以為已經退訂了這個郵件。我離開那個圈子也很久了。天文奇觀往來的郵件不多,如果我沒記錯,收到的內容其實挺有趣,就是一群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專家一起聊聊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兒。
我瞄了一眼服務員,顧客還在對著菜單問東問西,大概是在了解薩莉的餐廳是否供應無麩質素食碎菜葉之類的餐食,有時洛杉磯來的精英們確實挺難搞的。
鑒於沒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我讀起了郵件。
專家們,你們好。我是伊琳娜•佩特洛娃博士,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普爾科沃天文臺工作。
我寫信給你們是為了尋求幫助。
過去兩年,我一直在研究星云紅外發射的相關理論,因此對特定紅外波段的光譜進行了細致的觀察。結果我發現了一件怪事——不是在哪座星云,而是在我們的太陽系。
太陽系裡有一條非常微弱但可以檢測到的線條,向外發射波長為25.984 微米的紅外光,這個數值似乎固定不變。
附件是我的數據表格,我還提供了根據數據建立的三維模型。
在模型上你們可以看到,那是一條傾斜的弧線,從太陽的北極向上沿直線延伸370萬千米,然後從那裡向下急劇轉向,偏離太陽向金星延伸。在弧形的頂點,線條展開成漏斗狀云團,在金星處,弧形的截面幾乎跟那顆行星一樣寬。
它的紅外輻射非常微弱,我能檢測到完全是因為使用了極為敏感的星云紅外發射探測裝置。
為了進一步確定,我求助了智利阿塔卡馬天文臺(我心目中最好的天文臺)。他們證實了我的發現。
在行星際空間可以觀測到紅外光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宇宙塵埃或其他粒子反射太陽光,或者是某些分子化合物可以吸收能量並在紅外波段釋放,這甚至可以解釋波長不變的原因。
弧線的形狀特別有趣。我最初猜測那是沿磁力線移動的一束粒子,可是金星沒有磁場可言,既沒有磁層,又沒有電離層,是什麼力量迫使弧線指向金星?它又為什麼會有紅外輻射?
歡迎提出任何建議和理論。
這是什麼鬼?
我突然一下回憶起這些,那段經歷毫無征兆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關於自己的事情我沒想起多少。我住在舊金山——這我記得。我喜歡吃早餐,以前還對天文學感興趣,可是現在沒有興趣了?
顯然,我的大腦認為,關鍵的是回憶起那封郵件,而不是我姓字名誰這種瑣事。
我的潛意識想告訴我一件事,一定是看見血跡讓我想起那封標題為“細細的紅線”的電子郵件。
可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二加二等於幾?”
這個問題讓我有點煩躁。我累了,又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過了幾分鐘,問題又在我耳邊響起。
“二加二等於幾?”
輕柔的女性聲音,毫無感情,跟她上次提問的發音一模一樣。是計算機,是一臺計算機在折騰我。這讓我更煩躁了。
“不扶吾。”我說。我想要說的是“別煩我”——就我個人看來,眼下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可我說不清楚。
“錯誤,”計算機說,“二加二等於幾?”
是時候做個實驗了。我要試著打招呼。
“你嚎?”我說。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怎麼回事?我想要弄清楚,可又無從下手。我看不見,除了計算機也沒聽見別的聲音,甚至沒有觸覺。不,不對,有點觸覺。我正躺著,身下軟綿綿的,是一張床。
我覺得自己閉著眼睛,還不算太糟,只要睜開眼就行。我努力嘗試,可是沒有用。
為什麼睜不開?
睜。
睜……開!
睜。媽的!
噢!這回我感到一絲顫動,眼瞼動了,我能感受到。
睜開!
我的眼皮慢慢抬起,炫目的光線刺激著我的視網膜。
“晃!”我說。純粹依靠意志力我才強睜著眼睛,視野內白茫茫一片,讓我感到些許刺痛。
“檢測到眼動。”折磨我的家伙說,“二加二等於幾?”
白色減退,眼睛慢慢地適應,我開始看見形狀,但是還無法理解。我試試……手能不能動?不行。
腳呢?也不行。
可是我能動嘴,對吧?我一直在說話,雖然都是些廢話,但也算是在說。
“嘶。”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我開始明白眼前物體的形狀,我躺在一張……近似橢圓形的床上。
LED 燈照射著我,屋頂的攝像頭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盡管那很嚇人,可我更擔心機械臂。
屋頂上懸掛著兩條金屬手臂,表面處理成拉絲效果,每條手臂的末端本來應該是一只手,實際卻安裝著一種頗具穿透力的工具,令人深感不安,真是沒法讓我喜歡。
“嘶……嘶……”我說。能聽懂嗎?
“錯誤,二加二等於幾?”
該死的東西。我集中精神,匯聚全身的力量。另外,我開始有點恐慌了,不過沒關係,恐慌也能化為動力。
“嘶……四。”我總算說了出來。
“正確。”
謝天謝地,勉勉強強能說清了。
我放心地長出一口氣。等等——這不就是在控制呼吸?我有意識地又呼吸了一次,嘴巴幹澀,喉嚨生疼,可這都是我自己的感覺。我能掌控。
我戴著呼吸面罩,它緊緊扣在臉上,連接的軟管伸向我腦後。
我能起來嗎?
不能,但是可以稍微動一動頭。我低頭看自己的身體,發現我不僅一絲不掛,還連著數不清的管子。四肢上各有一根,“男性器官”上有一根,還有兩根伸到大腿下方,我猜其中一根插進了太陽曬不著的地方。
這可不妙。
而且,我渾身上下覆蓋著電極片。就跟檢查心電圖用的那種導聯貼一樣,只不過我這兒貼得到處都是。不過呢,還好只是覆蓋在皮膚上,沒有塞進身體裡。
“喔——”只有氣息沒有聲音,我又試了一次,“我…… 在哪兒?”
“八的立方根等於幾?”計算機問。
“我在哪兒?”我又問一遍,這次挺輕鬆。
“錯誤。八的立方根等於幾?”
我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說道:“2e(2pi)。”
“錯誤。八的立方根是多少?”
不過我沒錯,我只是想看看計算機有多聰明。結果:不怎麼聰明。
“二。”我說。
“正確。”
我等著聽接下來的問題,可計算機似乎已經滿意。
我累了,又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我醒過來。昏迷了多久?肯定有一會兒了,因為我感到精力充沛,不費吹灰之力就睜開眼睛。有進步。
我嘗試動動手指,並如願讓它們晃起來。沒問題,這回我真的好轉了。
“檢測到手部運動,”計算機說,“保持靜止。”
“什麼?為什麼——”
機械臂向我伸過來,它們移動快速,還沒等我弄明白,就除去了我身上大多數的管子。我沒有任何感覺,只是皮膚有點兒麻木。
最後我身上只剩下三根管子:手臂上的靜脈注射、伸進屁股的管子和導尿管。後兩者是我更想拔掉的玩意,不過,好吧。
我抬起右臂,然後任它墜落在床上,同樣的動作,我用左臂也做了一遍。我的雙臂像是灌了鉛一樣。我把這一過程重復了幾遍。我的手臂強壯,沒理由出現這種情況。我猜自己有嚴重的健康問題,而且已經在這張床上躺了一段時間。否則他們為什麼把我連接到那麼多設備上呢?不應該有肌肉萎縮嗎?
不應該有醫生嗎?或者醫院裡的聲音呢?這張床是怎麼回事?它不是長方形,而是橢圓形,我覺得它安裝在墻上,而不是在地板上。
“拔……”我沒了聲音,還是有點累,“拔掉管子……”
計算機沒有響應。
我又抬了幾次手臂,動了動腳趾,絕對是在好轉。
我前後活動腳踝,它們還能動,我抬起膝蓋,雙腿也強健有力,雖然不像健身愛好者那樣壯實,但是對於一個瀕死之人而言,也算十分健壯了。不過,我不確定我的雙腿原本是什麼樣的。
我把手掌按在床上,用力撐起上身。我居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雖然用盡了力氣,但我繼續堅持。這張床隨著我的移動輕輕搖晃,可以肯定,這不是一張普通的床。我把頭伸得更高,看見橢圓床的床頭和床尾固定在墻上,看上去很結實。它有點像固定的吊床,真奇怪。
很快,我就坐在了那根伸進屁股裡的管子上。這肯定不是最舒服的感覺,不過,什麼時候屁股裡插根管子會舒服呢?
此刻我看得更清楚了,這不是普通的病房。墻壁看似由塑料構成,整個房間是圓形,屋頂的LED 燈發出慘淡的白光。
墻上還有另外兩個類似吊床的床位,上面各躺著一個病人。我們排成一個三角形。騷擾我們的機械臂固定在房頂的正中間,我猜它們照顧我們所有人。我看不清兩位病友——他們跟我之前一樣陷進了床鋪裡。
房間沒有門,只有墻上的一段梯子通向……一扇艙門?艙門呈圓形,中間有一個轉輪把手。嗯,它肯定是某種艙門,像潛水艇上的一樣。也許我們三個得了傳染病?也許這是一間密閉的隔離病房?墻上各處布置著小型通風孔,我能感受到一股微弱的氣流。這裡的環境可能是受控的。
我把一條腿挪出床沿,結果床抖動起來,機械臂向我衝過來。我嚇得渾身一哆嗦,可是機械臂突然停住並懸在旁邊。我覺得它們時刻準備著在我摔倒時扶住我。
“檢測到全身運動,”計算機說,“你的名字?”
“噗,認真的嗎?”我問。
“錯誤,第二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張嘴想要回答。
“呃……”
“錯誤,第三次嘗試:你的名字?”
這時我才覺察出,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什麼都記不起來。
“呃。”我說。
“錯誤。”
一陣疲憊感襲來,不過感覺還挺舒服。一定是計算機通過靜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等……下……”我含混地說。
機械臂輕輕地把我放倒在床上。
我再次醒來,一條機械臂就在我面前。它在幹什麼?!
我嚇得往後一躲,只剩下震驚。機械臂撤回到屋頂的原位。我在臉上摸索,檢查是否受傷。一側有胡茬,一側光溜溜。
“你在給我刮胡子?”
“檢測到意識,”計算機說,“你的名字?”
“我還不知道呢。”
“錯誤,第二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是白人男性,說英語。讓我們賭一把,“約……約翰?”
“錯誤,第三次嘗試:你的名字?”
我從胳膊上扯下輸液管。“與你無關。”
“錯誤。”機械臂朝我伸過來。我滾下床,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另外兩根管子還連在我身上。
屁股上的管子掉下來,一點都不疼。可充滿尿液的導尿管直接從我的下體被扯出去,這可疼壞了,感覺就像尿出了一顆高爾夫球。我疼得一邊尖叫一邊在地上打滾。
“身體疼痛。”計算機說。機械臂追過來,我在地上連滾帶爬,逃到另一張床底下。機械臂立即停住,但它們沒有放棄,而是在等待。
它們受一臺計算機操控,根本不會像人類一樣失去耐心。
我頭向後躺在地上,大口地喘息。過了一會兒,疼痛消退,我抹去了眼角的淚水。
我一點兒都不清楚這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嘿!”我喊道,“你們誰醒一醒!”
“你的名字?”計算機問。
“請你們哪個人類醒一醒。”
“錯誤。”計算機說。
這簡直太荒謬了,盡管下體疼得厲害,可我還是笑起來。此外腎上腺素也開始起作用,所以我感到頭暈目眩。我回頭看了下床邊的導尿管,心存敬畏地搖搖頭,那東西穿過了我的尿道,真不可思議。
而且拔出時它還造成了傷害,地面留下一絲血跡,一條細細的紅線——
我抿了一口咖啡,把最後一塊吐司扔進嘴裡,然後招呼服務員結帳。我本可以省點兒錢在家裡吃早餐,不必每天早晨來餐廳。考慮到我微薄的薪水,那大概是個好主意,可我討厭做飯,又喜歡吃雞蛋和培根。
服務員點點頭,走向收銀臺。可是就在這個空當,又有一位顧客坐進來,需要她招呼。
我看了眼手表,時間剛過七點,不著急。我習慣七點二十上班,這樣可以有時間準備下當天的工作。不過實際上八點上班就行。於是我掏出手機查看郵件。
收件人:天文奇觀(astrocurious@scilists.org)
發件人:伊琳娜•佩特洛娃博士(ipetrova@gaoran.ru)
主題:細細的紅線
我對著屏幕皺起眉頭,我以為已經退訂了這個郵件。我離開那個圈子也很久了。天文奇觀往來的郵件不多,如果我沒記錯,收到的內容其實挺有趣,就是一群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專家一起聊聊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兒。
我瞄了一眼服務員,顧客還在對著菜單問東問西,大概是在了解薩莉的餐廳是否供應無麩質素食碎菜葉之類的餐食,有時洛杉磯來的精英們確實挺難搞的。
鑒於沒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我讀起了郵件。
專家們,你們好。我是伊琳娜•佩特洛娃博士,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普爾科沃天文臺工作。
我寫信給你們是為了尋求幫助。
過去兩年,我一直在研究星云紅外發射的相關理論,因此對特定紅外波段的光譜進行了細致的觀察。結果我發現了一件怪事——不是在哪座星云,而是在我們的太陽系。
太陽系裡有一條非常微弱但可以檢測到的線條,向外發射波長為25.984 微米的紅外光,這個數值似乎固定不變。
附件是我的數據表格,我還提供了根據數據建立的三維模型。
在模型上你們可以看到,那是一條傾斜的弧線,從太陽的北極向上沿直線延伸370萬千米,然後從那裡向下急劇轉向,偏離太陽向金星延伸。在弧形的頂點,線條展開成漏斗狀云團,在金星處,弧形的截面幾乎跟那顆行星一樣寬。
它的紅外輻射非常微弱,我能檢測到完全是因為使用了極為敏感的星云紅外發射探測裝置。
為了進一步確定,我求助了智利阿塔卡馬天文臺(我心目中最好的天文臺)。他們證實了我的發現。
在行星際空間可以觀測到紅外光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宇宙塵埃或其他粒子反射太陽光,或者是某些分子化合物可以吸收能量並在紅外波段釋放,這甚至可以解釋波長不變的原因。
弧線的形狀特別有趣。我最初猜測那是沿磁力線移動的一束粒子,可是金星沒有磁場可言,既沒有磁層,又沒有電離層,是什麼力量迫使弧線指向金星?它又為什麼會有紅外輻射?
歡迎提出任何建議和理論。
這是什麼鬼?
我突然一下回憶起這些,那段經歷毫無征兆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關於自己的事情我沒想起多少。我住在舊金山——這我記得。我喜歡吃早餐,以前還對天文學感興趣,可是現在沒有興趣了?
顯然,我的大腦認為,關鍵的是回憶起那封郵件,而不是我姓字名誰這種瑣事。
我的潛意識想告訴我一件事,一定是看見血跡讓我想起那封標題為“細細的紅線”的電子郵件。
可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