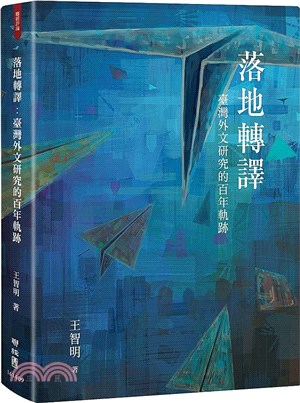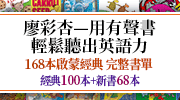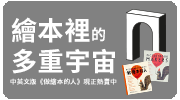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商品資訊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3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檢視與分析百年來西方文學知識的引進、翻譯和探討,
如何從清末的「西學東漸」,
經殖民、冷戰與解嚴,
形塑了當前外文研究的建制與發展。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擷選重要的變化與論辯,以突出形塑外文研究的體制性力量;同時對幾個重要案例──奠基學人、重要機構、關鍵論辯與新興領域──進行分析,以掌握外文研究的知識生產與時代、社會與西方學術的互動,思考其流轉與變異,並藉此回顧,重新測定外文研究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究竟,西洋文學與思想如何在落地轉譯的跨國行旅中成為我們的「外文研究」?外文學者以文學思想的譯介來適應與超克殖民現代性的努力,又如何定義與突破外文「之外」的想像,挑戰自由人文主義的基本設定?
如何從清末的「西學東漸」,
經殖民、冷戰與解嚴,
形塑了當前外文研究的建制與發展。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擷選重要的變化與論辯,以突出形塑外文研究的體制性力量;同時對幾個重要案例──奠基學人、重要機構、關鍵論辯與新興領域──進行分析,以掌握外文研究的知識生產與時代、社會與西方學術的互動,思考其流轉與變異,並藉此回顧,重新測定外文研究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究竟,西洋文學與思想如何在落地轉譯的跨國行旅中成為我們的「外文研究」?外文學者以文學思想的譯介來適應與超克殖民現代性的努力,又如何定義與突破外文「之外」的想像,挑戰自由人文主義的基本設定?
作者簡介
王智明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陽明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副教授,以及《文化研究》主編。 研究領域為亞裔美國文學、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理論。 曾獲得國科會吳大猷紀念獎(2009)以及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2014)。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陽明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副教授,以及《文化研究》主編。 研究領域為亞裔美國文學、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理論。 曾獲得國科會吳大猷紀念獎(2009)以及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2014)。
序
緒論(節錄)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研究與殖民現代性
想要學好一國的文學,非誦讀該國文學傳統裡的經典之作不可;甚至我們認為,想要學好一國的語言,也必須誦讀該國文學傳統?的經典之作。文學和語言是累積的傳統,一點一滴匯集成川;文學和語言只有演進,沒有突變――此文學和語言不同於自然科學之所在。職是之故,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所有學生,無論志在文學研究,語言實用,或語文教學,都必須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惟有扎根於古典,始能開花於現代;惟有浸淫於經典文學的文字技巧,始能在使用和翻譯當代語言的時候左右逢源,瀟洒自如。
――楊牧(1977: 159)
1976年4月16日,《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論革新英文系與文藝教育―增益精神建設投資的先聲〉。該文批評外文系課程的編排「每每與時代的需要與氣氛絕緣」,應該加重現代英文的比重,以培養口譯與導遊人才以及中學師資為要,而不必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已故詩人,也是外文學者的楊牧為此寫了一篇短文回應,於5月2日的《聯合報》上發表,題目就叫〈外文系是幹甚麼的?〉,後來收錄在《柏克萊精神》這本書裡。楊牧指出,今天外文系在實際教學和研究上以英文為主,其來有自,並未與時代脫節,而且強制學生修習中國文學史,加強現代青年的國文知識,更是「從未曾有的積極措施」。外文系不是「就業英語的補習班」,也不是「訓練高級導遊,供你『用者稱便』的地方」,因為外文系的目的在於培養「一流的翻譯人才」,能夠溝通中外思想的優異學者和譯者,承擔在「學術文化上評介和傳承的任務」以及「興滅繼絕的使命」(1977: 160)。
面對實用主義的批評,楊牧人文主義式的辯護凸顯了幾個外文系的重要命題以及至今不斷的辯論:為什麼外文系在教學與研究上會以英文為主,歷史緣由何在?外國文學研究(以下簡稱「外文研究」)所要評介的對象與目的是什麼?語言、文學,孰輕孰重?翻譯、研究或創作,哪個才是其興滅繼絕的使命?溝通中外的歷史條件與可能性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範疇怎麼界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的思想內涵與歷史形貌?究竟「外文研究」這門學科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生產了什麼樣的知識,又承擔著什麼樣的使命?
一同收錄在《柏克萊精神》裡的,是楊牧原先發表於《中國論壇》上的另一篇文章:〈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在這篇文章中,楊牧強調現代大學雖然分科細密繁複,但是人文教育實為根本,因為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礎即是對人文主義的貫徹與發揚;這個西方傳統中最為輝煌的人文精神就「相當於儒家之所謂文學,包括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文學(literature),卻又超越了文學,強調其外發的力量,所以也不是孤立的學業而已」(1976: 163);是故「我們在倡議『文化復興』的時候,應該對於傳統文史哲的教育加以激勵,不可以任其荒蕪,更不可橫加打擊」(1976: 167)。楊牧將西方的「人文」等同於傳統的文史哲教育,強調一種貫通中外的思維以及「士以弘毅」的態度,以抵抗社會發展過度傾向技術與功利的現象,尤其當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抗大陸「文革」之際,他更主張多以鼓勵,少予打擊。楊牧的辯護顯現人文學科的發展一直面對著來自於實用主義的挑戰,也突出文學研究與教育的目的,絕不止於內心的修養與知識的精進,而在於「弘毅」的展望,既要「負有興滅繼絕的道德使命」,又要具備「從古典中毅然走出,面對現實,不惜為降魔驅邪而戰鬥」的知識勇氣(1976: 164)。
楊牧的主張不為外文學者獨有,也因此討論外文研究的發展,其意義也不僅止於外文系的師生而已,而是關於語言政策與人文研究的總體衡平與反省。但是,貫穿楊牧思考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正是民國以來外文研究發展的思想底色,亦是在政治動盪與思想解放的百年歷程中,外文學者與外文研究賴以維繫的核心價值。《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嘗試的,正是要回到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去檢視與分析隨著西方文學知識的引進、翻譯、探討與建制化,外文研究究竟如何生長、發展、流轉與變異,並在回顧當中,重新測定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本書的核心關懷是:西洋文學與思想究竟如何在落地轉譯的跨國行旅中成為我們的外文研究?這個歷史過程有何特殊的軌跡,它與當前臺灣人文的發展又有怎麼樣的關聯?
「外文學門」是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自1970年代起,在學科架構調整的過程中逐步確立的一個學門分類,百年前並不存在。但是作為知識生產的形式,它卻有一段不短的歷史可尋,上可溯及清末西式學堂與現代大學的建立、五四新文學運動和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西洋文學講座,並銜接上1949年後渡臺大陸籍學者的學術奠基工程,直至1970年代以降臺灣比較文學的發展以及解嚴前後西方理論在地操演所帶來的變貌。然而,書寫外文學門的百年發展並不容易,這不僅是因為既成的歷史研究十分有限,更是因為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使「臺灣」「外文研究」的實踐總在不同的知識譜系間擺盪,不易收攏。理想上,外文研究的範疇應當涵納所有非本國的文學與文化,但真實狀況卻是「西方」文學與文化統攝了我們的外文想像;即令舊俄文學(如普希金、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等)曾是好幾代外文學人與知識青年的重要養分,但自二戰結束以來,英美文學才是臺灣外文學門的主流,輔以法、德、西等國的語言訓練與有限的文學引介;北歐、東歐、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文學甚少出現,非西方語文(除了日文、韓文之外)更絕少出現在外文學門的視野裡。同時,文學與文化研究需要語言訓練為基礎,這使得語言學和外語教學自然而然地成為外文學門的重要元素,並且逐漸發展出各自的專業想像與學術領域。這樣一來,「外文系」一詞所統轄的往往不只是本國文學(不論是中文、臺文或是原住民文學)之外的廣大世界,更是一個不同專業(外語教學、語言學、翻譯訓練、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區域研究等)並置與競逐的學術機構與學科想像。當然,全球貿易與實用思維將英文視為「工具」,而不在乎其內涵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影響,並逐漸推動外文系往「應用外文」發展。這樣的多樣性一方面成就了外文系在思想訓練與教學內涵上的豐富性,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學科要求與教學理性也在學門內部與系所建制上形成張力,在拉扯中形塑著外文學門的百年風貌。
然而,外文系究竟從何而來?不同的學科範疇與專業要求又如何進入並形成了外文系的建制與想像?百年前的外文系就是今天的樣貌嗎?百年來有什麼改變與創新呢?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下的西洋文學講座呈現了什麼狀態、留下了哪些影響?它與之後的外文系又有什麼差別?外文研究究竟所為何事,任務何在?它是文學研究、語文研究,還是區域研究?它的目的是認識與翻譯西方,還是批判與改造自身?百年來不同的思想與時勢又如何影響外文學門的發展?百年後回首前塵,我們又當如何理解外文研究在華文與華人思想史上的知識狀態與文化位置,並且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中展望將來?
本書將外文學門的知識實踐座落在百年來學術建制與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回顧,試圖指出:當代意義的外文研究,其源起與19世紀中葉以降殖民主義脈絡下的西學東漸密不可分;它不只標示著近代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文學至此有新舊之分、中西之別)以及殖民現代性的到來,更承載了「溝通中外、再建文明」的使命。外文研究的發展代表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企圖以文學思想的譯介來適應與超克殖民現代性的努力。陳長房在題為〈外國文學學門未來整合與發展〉的調查報告中曾指出,外文學門的任務在於「融鑄西方文學理論,並針對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與文化,進行比較和詮釋性的研究工作,俾使本土文學文化能展現新的生機和意涵」(1999: 428)。何春蕤(1998)亦看到外文研究處在臺灣國際化與本土化的中介位置,不僅對內面對引介、翻譯國外學術成果的要求,對外亦承擔與國際交流、對話的責任。面對夾纏在中外之界的外文研究,劉紀蕙(2000a)如此質問:「我們所承接的文化知識體系與我們對話的對象在何處?我們所回應的問題是什麼?面對學術規範與西方觀點,我們要如何以創造性的思考發展本地的學術對話」?單德興亦追問:「在臺灣發展英美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歷史、文化脈絡如何?有什麼理論及方法學上的意義?從相對於國際學術主流的邊緣位置出發,我們如何能以有限的資源來有效介入?到底有哪些稱得上是『我們的』立場、觀點、甚至特色與創見」(2002: 204)?這些當代學者對外文研究自身定位的叩問與反思,顯示外文研究,不論過去或現在,始終建立在國家內部思想發展的邊界上,甚或,其歷史即源於文化與語言邊境上的思想碰撞。這些問題也是本書的關切,但其解答方法必須來自於歷史,來自於對「我們」自身歷史形成的深入理解與深刻反省。因此,與其就字義而將外文研究定位為一門研究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學問,不如將之理解為一個文化、語言與思想的邊境,一種不斷跨界迻譯、比較批判,尋求文明改造的知識實踐。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研究與殖民現代性
想要學好一國的文學,非誦讀該國文學傳統裡的經典之作不可;甚至我們認為,想要學好一國的語言,也必須誦讀該國文學傳統?的經典之作。文學和語言是累積的傳統,一點一滴匯集成川;文學和語言只有演進,沒有突變――此文學和語言不同於自然科學之所在。職是之故,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所有學生,無論志在文學研究,語言實用,或語文教學,都必須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惟有扎根於古典,始能開花於現代;惟有浸淫於經典文學的文字技巧,始能在使用和翻譯當代語言的時候左右逢源,瀟洒自如。
――楊牧(1977: 159)
1976年4月16日,《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論革新英文系與文藝教育―增益精神建設投資的先聲〉。該文批評外文系課程的編排「每每與時代的需要與氣氛絕緣」,應該加重現代英文的比重,以培養口譯與導遊人才以及中學師資為要,而不必學習「深奧的古典英文」。已故詩人,也是外文學者的楊牧為此寫了一篇短文回應,於5月2日的《聯合報》上發表,題目就叫〈外文系是幹甚麼的?〉,後來收錄在《柏克萊精神》這本書裡。楊牧指出,今天外文系在實際教學和研究上以英文為主,其來有自,並未與時代脫節,而且強制學生修習中國文學史,加強現代青年的國文知識,更是「從未曾有的積極措施」。外文系不是「就業英語的補習班」,也不是「訓練高級導遊,供你『用者稱便』的地方」,因為外文系的目的在於培養「一流的翻譯人才」,能夠溝通中外思想的優異學者和譯者,承擔在「學術文化上評介和傳承的任務」以及「興滅繼絕的使命」(1977: 160)。
面對實用主義的批評,楊牧人文主義式的辯護凸顯了幾個外文系的重要命題以及至今不斷的辯論:為什麼外文系在教學與研究上會以英文為主,歷史緣由何在?外國文學研究(以下簡稱「外文研究」)所要評介的對象與目的是什麼?語言、文學,孰輕孰重?翻譯、研究或創作,哪個才是其興滅繼絕的使命?溝通中外的歷史條件與可能性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範疇怎麼界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的思想內涵與歷史形貌?究竟「外文研究」這門學科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生產了什麼樣的知識,又承擔著什麼樣的使命?
一同收錄在《柏克萊精神》裡的,是楊牧原先發表於《中國論壇》上的另一篇文章:〈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在這篇文章中,楊牧強調現代大學雖然分科細密繁複,但是人文教育實為根本,因為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礎即是對人文主義的貫徹與發揚;這個西方傳統中最為輝煌的人文精神就「相當於儒家之所謂文學,包括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文學(literature),卻又超越了文學,強調其外發的力量,所以也不是孤立的學業而已」(1976: 163);是故「我們在倡議『文化復興』的時候,應該對於傳統文史哲的教育加以激勵,不可以任其荒蕪,更不可橫加打擊」(1976: 167)。楊牧將西方的「人文」等同於傳統的文史哲教育,強調一種貫通中外的思維以及「士以弘毅」的態度,以抵抗社會發展過度傾向技術與功利的現象,尤其當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抗大陸「文革」之際,他更主張多以鼓勵,少予打擊。楊牧的辯護顯現人文學科的發展一直面對著來自於實用主義的挑戰,也突出文學研究與教育的目的,絕不止於內心的修養與知識的精進,而在於「弘毅」的展望,既要「負有興滅繼絕的道德使命」,又要具備「從古典中毅然走出,面對現實,不惜為降魔驅邪而戰鬥」的知識勇氣(1976: 164)。
楊牧的主張不為外文學者獨有,也因此討論外文研究的發展,其意義也不僅止於外文系的師生而已,而是關於語言政策與人文研究的總體衡平與反省。但是,貫穿楊牧思考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正是民國以來外文研究發展的思想底色,亦是在政治動盪與思想解放的百年歷程中,外文學者與外文研究賴以維繫的核心價值。《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嘗試的,正是要回到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去檢視與分析隨著西方文學知識的引進、翻譯、探討與建制化,外文研究究竟如何生長、發展、流轉與變異,並在回顧當中,重新測定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本書的核心關懷是:西洋文學與思想究竟如何在落地轉譯的跨國行旅中成為我們的外文研究?這個歷史過程有何特殊的軌跡,它與當前臺灣人文的發展又有怎麼樣的關聯?
「外文學門」是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自1970年代起,在學科架構調整的過程中逐步確立的一個學門分類,百年前並不存在。但是作為知識生產的形式,它卻有一段不短的歷史可尋,上可溯及清末西式學堂與現代大學的建立、五四新文學運動和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西洋文學講座,並銜接上1949年後渡臺大陸籍學者的學術奠基工程,直至1970年代以降臺灣比較文學的發展以及解嚴前後西方理論在地操演所帶來的變貌。然而,書寫外文學門的百年發展並不容易,這不僅是因為既成的歷史研究十分有限,更是因為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使「臺灣」「外文研究」的實踐總在不同的知識譜系間擺盪,不易收攏。理想上,外文研究的範疇應當涵納所有非本國的文學與文化,但真實狀況卻是「西方」文學與文化統攝了我們的外文想像;即令舊俄文學(如普希金、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等)曾是好幾代外文學人與知識青年的重要養分,但自二戰結束以來,英美文學才是臺灣外文學門的主流,輔以法、德、西等國的語言訓練與有限的文學引介;北歐、東歐、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文學甚少出現,非西方語文(除了日文、韓文之外)更絕少出現在外文學門的視野裡。同時,文學與文化研究需要語言訓練為基礎,這使得語言學和外語教學自然而然地成為外文學門的重要元素,並且逐漸發展出各自的專業想像與學術領域。這樣一來,「外文系」一詞所統轄的往往不只是本國文學(不論是中文、臺文或是原住民文學)之外的廣大世界,更是一個不同專業(外語教學、語言學、翻譯訓練、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區域研究等)並置與競逐的學術機構與學科想像。當然,全球貿易與實用思維將英文視為「工具」,而不在乎其內涵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影響,並逐漸推動外文系往「應用外文」發展。這樣的多樣性一方面成就了外文系在思想訓練與教學內涵上的豐富性,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學科要求與教學理性也在學門內部與系所建制上形成張力,在拉扯中形塑著外文學門的百年風貌。
然而,外文系究竟從何而來?不同的學科範疇與專業要求又如何進入並形成了外文系的建制與想像?百年前的外文系就是今天的樣貌嗎?百年來有什麼改變與創新呢?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下的西洋文學講座呈現了什麼狀態、留下了哪些影響?它與之後的外文系又有什麼差別?外文研究究竟所為何事,任務何在?它是文學研究、語文研究,還是區域研究?它的目的是認識與翻譯西方,還是批判與改造自身?百年來不同的思想與時勢又如何影響外文學門的發展?百年後回首前塵,我們又當如何理解外文研究在華文與華人思想史上的知識狀態與文化位置,並且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中展望將來?
本書將外文學門的知識實踐座落在百年來學術建制與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回顧,試圖指出:當代意義的外文研究,其源起與19世紀中葉以降殖民主義脈絡下的西學東漸密不可分;它不只標示著近代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文學至此有新舊之分、中西之別)以及殖民現代性的到來,更承載了「溝通中外、再建文明」的使命。外文研究的發展代表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企圖以文學思想的譯介來適應與超克殖民現代性的努力。陳長房在題為〈外國文學學門未來整合與發展〉的調查報告中曾指出,外文學門的任務在於「融鑄西方文學理論,並針對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與文化,進行比較和詮釋性的研究工作,俾使本土文學文化能展現新的生機和意涵」(1999: 428)。何春蕤(1998)亦看到外文研究處在臺灣國際化與本土化的中介位置,不僅對內面對引介、翻譯國外學術成果的要求,對外亦承擔與國際交流、對話的責任。面對夾纏在中外之界的外文研究,劉紀蕙(2000a)如此質問:「我們所承接的文化知識體系與我們對話的對象在何處?我們所回應的問題是什麼?面對學術規範與西方觀點,我們要如何以創造性的思考發展本地的學術對話」?單德興亦追問:「在臺灣發展英美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歷史、文化脈絡如何?有什麼理論及方法學上的意義?從相對於國際學術主流的邊緣位置出發,我們如何能以有限的資源來有效介入?到底有哪些稱得上是『我們的』立場、觀點、甚至特色與創見」(2002: 204)?這些當代學者對外文研究自身定位的叩問與反思,顯示外文研究,不論過去或現在,始終建立在國家內部思想發展的邊界上,甚或,其歷史即源於文化與語言邊境上的思想碰撞。這些問題也是本書的關切,但其解答方法必須來自於歷史,來自於對「我們」自身歷史形成的深入理解與深刻反省。因此,與其就字義而將外文研究定位為一門研究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學問,不如將之理解為一個文化、語言與思想的邊境,一種不斷跨界迻譯、比較批判,尋求文明改造的知識實踐。
目次
緒 論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研究與殖民現代性
從建制史到思想史:方法與材料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理論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歷史
三源匯流: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第一部分 「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
前言
第一章 西學東漸:外文研究的源起與建制
機構的建立:從教會學校、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
民初大學外文系的發展與變化
語文各分、中外合併?:課程設置的爭議
溝通中外:思想翻譯與新造文學
自由普世:吳宓藏書中的人文國際主義
第二章 比較的幽靈:帝國大學時代的西洋文學講座
「樹立帝國學術上的權威於新領土上」
西洋文學的移入:倫敦、東京而臺北
殖民之內外:外國文學研究與外地文學論
歌謠、俚語、蒼蠅和山水:蘇維熊的「自然文學」
比較的幽靈:顛倒的望遠鏡
第二部分 冷戰分斷:(新)人文主義的流轉
前言
第三章 反浪漫主義:夏濟安的文學與政治
戰後知識狀況:美援文藝體制與臺大外文系
只是「朱顏改」:現代化、在地化、比較化
文學與政治:夏濟安的「反浪漫主義」
從匪情研究到現代中國研究:「中共詞彙研究」與《黑暗的閘門》
餘論:文學的使命
第四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化冷戰:侯健與新人文主義的兩岸軌跡
冷戰與比較文學:方法的思考
文學與人生:侯健的位置
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
「五四」紀念的政治:文學革命與思想戰
分斷的現在
第五章 冷戰人文主義:顏元叔及其批評實踐
「不規範」的時代:臺大外文系課程改革
爭議中的顏元叔:四場論戰與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化
再探新批評:冷戰與人文主義的跨國譜系
冷戰的制約與抵抗:社會寫實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歐美研究的原點
懷念與致敬
第三部分 理論年代:外文研究與後冷戰形構
前言
第六章 創造「主體性」:理論的轉譯與落地
理論的引介:以臺大外文系為座標
理論的轉譯:「空白主體」與「身分危機」
理論的落地:千禧年後
臺灣理論的可能:欲望、不滿與焦慮
理論之後:朝向基進的想像
第七章 重新接合與表述:文化研究的冒現與情感
接合╱表述(articulation):文化研究的源起
多重的建制史I:以《當代》和《島嶼邊緣》為線索
多重的建制史II:學會與學刊的成立和變化
理論的接合:「番易」與「迻譯」現代性的思想重構
情感的表述:罔兩作為方法
美學製造的差異:不自由的人文主義
第八章 外文「之外」:族裔研究與相關性的追索
多重關係性
「利基」!:書目、故事和體制
他者的樣貌:膚色、離散與地理
「遠處的文學」:傳會的誘惑與限制
傳會的誤區:「黑命關天」與亞美研究
後╱冷戰的挑戰:知識生產的地緣政治與種族邏輯
結 語 讀外文系的人誌謝
附錄 外文系所「族裔研究」碩博士論文清單(2000-2020)
徵引書目
索引詞條
從建制史到思想史:方法與材料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理論
「文學」與殖民現代性:歷史
三源匯流: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第一部分 「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
前言
第一章 西學東漸:外文研究的源起與建制
機構的建立:從教會學校、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
民初大學外文系的發展與變化
語文各分、中外合併?:課程設置的爭議
溝通中外:思想翻譯與新造文學
自由普世:吳宓藏書中的人文國際主義
第二章 比較的幽靈:帝國大學時代的西洋文學講座
「樹立帝國學術上的權威於新領土上」
西洋文學的移入:倫敦、東京而臺北
殖民之內外:外國文學研究與外地文學論
歌謠、俚語、蒼蠅和山水:蘇維熊的「自然文學」
比較的幽靈:顛倒的望遠鏡
第二部分 冷戰分斷:(新)人文主義的流轉
前言
第三章 反浪漫主義:夏濟安的文學與政治
戰後知識狀況:美援文藝體制與臺大外文系
只是「朱顏改」:現代化、在地化、比較化
文學與政治:夏濟安的「反浪漫主義」
從匪情研究到現代中國研究:「中共詞彙研究」與《黑暗的閘門》
餘論:文學的使命
第四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化冷戰:侯健與新人文主義的兩岸軌跡
冷戰與比較文學:方法的思考
文學與人生:侯健的位置
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
「五四」紀念的政治:文學革命與思想戰
分斷的現在
第五章 冷戰人文主義:顏元叔及其批評實踐
「不規範」的時代:臺大外文系課程改革
爭議中的顏元叔:四場論戰與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化
再探新批評:冷戰與人文主義的跨國譜系
冷戰的制約與抵抗:社會寫實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歐美研究的原點
懷念與致敬
第三部分 理論年代:外文研究與後冷戰形構
前言
第六章 創造「主體性」:理論的轉譯與落地
理論的引介:以臺大外文系為座標
理論的轉譯:「空白主體」與「身分危機」
理論的落地:千禧年後
臺灣理論的可能:欲望、不滿與焦慮
理論之後:朝向基進的想像
第七章 重新接合與表述:文化研究的冒現與情感
接合╱表述(articulation):文化研究的源起
多重的建制史I:以《當代》和《島嶼邊緣》為線索
多重的建制史II:學會與學刊的成立和變化
理論的接合:「番易」與「迻譯」現代性的思想重構
情感的表述:罔兩作為方法
美學製造的差異:不自由的人文主義
第八章 外文「之外」:族裔研究與相關性的追索
多重關係性
「利基」!:書目、故事和體制
他者的樣貌:膚色、離散與地理
「遠處的文學」:傳會的誘惑與限制
傳會的誤區:「黑命關天」與亞美研究
後╱冷戰的挑戰:知識生產的地緣政治與種族邏輯
結 語 讀外文系的人誌謝
附錄 外文系所「族裔研究」碩博士論文清單(2000-2020)
徵引書目
索引詞條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西學東漸:外文研究的源起與建制
西洋文學的介紹入中國,遠在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前,在清末民初時代已有顯著的、雖是零星的成績;至於它的正式的系統的研究,卻還是近數十年來的事情。
――柳無忌(1978: 1)
胡適在《四十自述》這本「給史家作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的自傳裡,將自己的童年生活、求學歷程乃至於文學革命的開端,做了一番生動的說明,其中的許多篇章,如談及母親對他的照顧以及他自己如何變成無神論者的段落,對中年以上的臺灣讀者來說,可能還是耳熟能詳。然而,書中提及的幾個細節,卻是在其哲學、史學與文學革命成就之外,一般甚少注意的。比方說,開始讀書後,除了《水滸》、《聊齋》、《紅樓夢》這些舊式小說外,胡適也能讀到《經國美談》這類由日本人翻譯,講希臘愛國志士的外國小說。胡適1904年(15歲)初到上海就讀梅溪學堂時,就開始修習英文,用的課本是《華英初階》,而且當時他的英文成績還好過國文;隔年,轉到澄衷學堂後,他閱讀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深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念的震撼而選擇了「適之」為字。更有趣的,是他1906年轉念中國公學後,雖然仍在學英文,但他最佩服的卻是當時能作中國詩詞的英文教員,其中一位名為姚康侯的先生還是辜鴻銘的弟子,拿辜鴻銘譯的《論語》為範本,教他們中英翻譯。爾後被聘為中國新公學的英文教員時,胡適回憶道:
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卻在文法方面得著很好的練習。(2015: 94)
雖說對於曾為庚款留學生、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胡適來說,英文不錯,不過是基本能力,不足為奇,但這些細節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民國初年英文研究與教學的概況:雖然文法與翻譯是根本,但尚未邁出國門的青年胡適已經開始涉獵經日本翻譯的西洋文學。如江勇振所述,這個時候在上海的青年胡適,還懷抱著留學西洋、研究文學的夢想,想攻考庚款留學,成為「外國狀元」(2011: 22);同時,他也在自己編輯的《競業旬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白話章回小說〈真如島〉,宣揚自己的無神論(2011: 95),而他們的英文教員大多是教會學校或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這些細節側面描繪了當時的上海,雖然以英文為時尚,但各方思潮與民族情緒已然湧動的時代氛圍。
尤其重要的是,在附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這篇文章裡,胡適把文學革命的起因歸諸於鍾文鰲這個不通漢文,卻在清華學生監督處做書記,時不時寄發「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傳單的「怪人」(2015: 111),因為正是鍾文鰲的刺激使他開始思考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胡適寫道,他當時在日記裡記下自己關於中國採行拼音文字的四點看法,「都是從我早年的經驗裡得來的」,其中講求字源、文法與標點符號的想法,尤其是「學外國文得來的教訓」(2015: 116)。換句話說,文學革命首先是文字、語言革命,是在追求言文一致,以西方經驗為摹本的前提下,所衍生和展開的探索。如胡適所說:
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化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2015: 121)
胡適所謂的「文學工具」即是語言。雖然他最終沒有往漢字拉丁化的方向前進,但「白話」文學的想像確實推動了一場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革命,而這一切的起點並不只是西方表面上的船堅炮利,而是西方語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理解以及想像現代與文學的雙語原點。
林毓凱整理了胡適在澄衷學堂的課表,強調胡適的雙語閱讀與寫作有紮實的基礎,而他在康乃爾大學廣泛涉獵的西洋文學經典更是關鍵,為其白話文學論奠定了一個現實主義的核心;因此白話與文言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為了表情達意、反映現實的一種語言「性質」或「元素」(2018: 291)。加拿大學者傅雲博(Daniel Fried)指出,胡適的新詩創作(如《嘗試集》)只是在語言的表達上展現新意,在骨子裡,他的詩學靈感還是來自於傳統的英詩,即他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留學時所讀的伊莉沙白詩人、浪漫主義詩人和維多利亞詩人(2006: 372)。傅雲博寫道,胡適的創作靈感與當時的歐洲與美國文學(如意象派)關係不大,而與華茲華斯更有關係;他是「透過翻譯英詩,特別是19世紀的英詩,才首度獲得在古典的詩詞傳統之外,創作中文詩的經驗」(2006: 373, 375)。因此,江勇振也特別強調:「白話文學革命的歷史跟胡適個人的文學教育過程是不可分割的。沒有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所受的英國文學教育,也就不會有白話文學革命。5胡適所提倡的詩國革命絕對不是逼上梁山,而是經由他自己實地實驗――包括英詩的寫作――以後所取得的經驗、心得與信念的發揮」(2011: 615)。
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文學革命得以展開的前提要件,正是西方文字與文學對於新青年們的召喚與啟迪,那麼外國語言與文學就不是現代中國語言和文學的對立面,而是其內在構造的一部分,是現代中國文學風景的內面。胡適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挖掘,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文學革命的旗手與現代中國學術的一代宗師,更是因為旗手與宗師的名號,在某個意義上,遮蔽了他自身知識構成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尤其是外國語言與文學曾在其中扮演的巨大作用。這樣的遮蔽使得我們無法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與外文研究的建制過程有機地聯繫起來,看到兩方分途與共濟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對於胡適,我們或許不該忘記,他1917年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恰恰是北大文科英文門的教授兼教授會主任;他既在哲學門開設「歐美最近哲學之趨勢」和「中國名學鉤沉」,也在英文門和國文門教授「高級修辭學」與「小說」(見江勇振,2013: 54)。這麼說,並不是要否認胡適學術的獨特性與貢獻,將其思想洞見與文學實踐歸諸於對西方傳統的模仿與搬弄,而是希望透過他這麼一個鮮明的例子指向單一學科視角的陰翳之處,從而對外文研究的建制歷史展開細緻而深入的討論,說明一個學科的成長與變化如何與時代發生關係,西方又如何借道語言與文學――而不只是船堅炮利――深入東方,成為亞洲現代性的核心組成。
因此,本章將從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建立講起,爬梳從清末學堂章程到民初大學規程的具體變化,輔以中、外文系是否合併、語言、文學應否分家的相關討論,以描述外國文學如何在殖民╱現代的脈絡中浮現,並且在民初大學的建制發展中,逐漸成為一個學科領域。同時,本章也將討論當時的文學翻譯與創作活動,尤其是外文學人的種種成績――包括開設的課程、翻譯、藏書、撰寫的教材和創作的實驗等――來勾勒外國文學進入中國的過程。最後,本章以吳宓先生的藏書為例,說明外文研究如何在中國語境中落地且轉譯為一種「感性知識」與「人文素養」,體現出一種自由普世的精神以及人文國際的想像。
西洋文學的介紹入中國,遠在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前,在清末民初時代已有顯著的、雖是零星的成績;至於它的正式的系統的研究,卻還是近數十年來的事情。
――柳無忌(1978: 1)
胡適在《四十自述》這本「給史家作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的自傳裡,將自己的童年生活、求學歷程乃至於文學革命的開端,做了一番生動的說明,其中的許多篇章,如談及母親對他的照顧以及他自己如何變成無神論者的段落,對中年以上的臺灣讀者來說,可能還是耳熟能詳。然而,書中提及的幾個細節,卻是在其哲學、史學與文學革命成就之外,一般甚少注意的。比方說,開始讀書後,除了《水滸》、《聊齋》、《紅樓夢》這些舊式小說外,胡適也能讀到《經國美談》這類由日本人翻譯,講希臘愛國志士的外國小說。胡適1904年(15歲)初到上海就讀梅溪學堂時,就開始修習英文,用的課本是《華英初階》,而且當時他的英文成績還好過國文;隔年,轉到澄衷學堂後,他閱讀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深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念的震撼而選擇了「適之」為字。更有趣的,是他1906年轉念中國公學後,雖然仍在學英文,但他最佩服的卻是當時能作中國詩詞的英文教員,其中一位名為姚康侯的先生還是辜鴻銘的弟子,拿辜鴻銘譯的《論語》為範本,教他們中英翻譯。爾後被聘為中國新公學的英文教員時,胡適回憶道:
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卻在文法方面得著很好的練習。(2015: 94)
雖說對於曾為庚款留學生、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胡適來說,英文不錯,不過是基本能力,不足為奇,但這些細節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民國初年英文研究與教學的概況:雖然文法與翻譯是根本,但尚未邁出國門的青年胡適已經開始涉獵經日本翻譯的西洋文學。如江勇振所述,這個時候在上海的青年胡適,還懷抱著留學西洋、研究文學的夢想,想攻考庚款留學,成為「外國狀元」(2011: 22);同時,他也在自己編輯的《競業旬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白話章回小說〈真如島〉,宣揚自己的無神論(2011: 95),而他們的英文教員大多是教會學校或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這些細節側面描繪了當時的上海,雖然以英文為時尚,但各方思潮與民族情緒已然湧動的時代氛圍。
尤其重要的是,在附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這篇文章裡,胡適把文學革命的起因歸諸於鍾文鰲這個不通漢文,卻在清華學生監督處做書記,時不時寄發「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傳單的「怪人」(2015: 111),因為正是鍾文鰲的刺激使他開始思考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胡適寫道,他當時在日記裡記下自己關於中國採行拼音文字的四點看法,「都是從我早年的經驗裡得來的」,其中講求字源、文法與標點符號的想法,尤其是「學外國文得來的教訓」(2015: 116)。換句話說,文學革命首先是文字、語言革命,是在追求言文一致,以西方經驗為摹本的前提下,所衍生和展開的探索。如胡適所說:
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化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2015: 121)
胡適所謂的「文學工具」即是語言。雖然他最終沒有往漢字拉丁化的方向前進,但「白話」文學的想像確實推動了一場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革命,而這一切的起點並不只是西方表面上的船堅炮利,而是西方語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理解以及想像現代與文學的雙語原點。
林毓凱整理了胡適在澄衷學堂的課表,強調胡適的雙語閱讀與寫作有紮實的基礎,而他在康乃爾大學廣泛涉獵的西洋文學經典更是關鍵,為其白話文學論奠定了一個現實主義的核心;因此白話與文言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為了表情達意、反映現實的一種語言「性質」或「元素」(2018: 291)。加拿大學者傅雲博(Daniel Fried)指出,胡適的新詩創作(如《嘗試集》)只是在語言的表達上展現新意,在骨子裡,他的詩學靈感還是來自於傳統的英詩,即他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留學時所讀的伊莉沙白詩人、浪漫主義詩人和維多利亞詩人(2006: 372)。傅雲博寫道,胡適的創作靈感與當時的歐洲與美國文學(如意象派)關係不大,而與華茲華斯更有關係;他是「透過翻譯英詩,特別是19世紀的英詩,才首度獲得在古典的詩詞傳統之外,創作中文詩的經驗」(2006: 373, 375)。因此,江勇振也特別強調:「白話文學革命的歷史跟胡適個人的文學教育過程是不可分割的。沒有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所受的英國文學教育,也就不會有白話文學革命。5胡適所提倡的詩國革命絕對不是逼上梁山,而是經由他自己實地實驗――包括英詩的寫作――以後所取得的經驗、心得與信念的發揮」(2011: 615)。
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文學革命得以展開的前提要件,正是西方文字與文學對於新青年們的召喚與啟迪,那麼外國語言與文學就不是現代中國語言和文學的對立面,而是其內在構造的一部分,是現代中國文學風景的內面。胡適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挖掘,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文學革命的旗手與現代中國學術的一代宗師,更是因為旗手與宗師的名號,在某個意義上,遮蔽了他自身知識構成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尤其是外國語言與文學曾在其中扮演的巨大作用。這樣的遮蔽使得我們無法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與外文研究的建制過程有機地聯繫起來,看到兩方分途與共濟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對於胡適,我們或許不該忘記,他1917年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恰恰是北大文科英文門的教授兼教授會主任;他既在哲學門開設「歐美最近哲學之趨勢」和「中國名學鉤沉」,也在英文門和國文門教授「高級修辭學」與「小說」(見江勇振,2013: 54)。這麼說,並不是要否認胡適學術的獨特性與貢獻,將其思想洞見與文學實踐歸諸於對西方傳統的模仿與搬弄,而是希望透過他這麼一個鮮明的例子指向單一學科視角的陰翳之處,從而對外文研究的建制歷史展開細緻而深入的討論,說明一個學科的成長與變化如何與時代發生關係,西方又如何借道語言與文學――而不只是船堅炮利――深入東方,成為亞洲現代性的核心組成。
因此,本章將從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建立講起,爬梳從清末學堂章程到民初大學規程的具體變化,輔以中、外文系是否合併、語言、文學應否分家的相關討論,以描述外國文學如何在殖民╱現代的脈絡中浮現,並且在民初大學的建制發展中,逐漸成為一個學科領域。同時,本章也將討論當時的文學翻譯與創作活動,尤其是外文學人的種種成績――包括開設的課程、翻譯、藏書、撰寫的教材和創作的實驗等――來勾勒外國文學進入中國的過程。最後,本章以吳宓先生的藏書為例,說明外文研究如何在中國語境中落地且轉譯為一種「感性知識」與「人文素養」,體現出一種自由普世的精神以及人文國際的想像。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