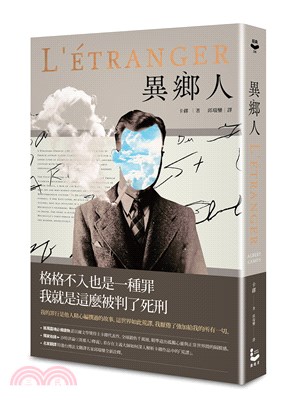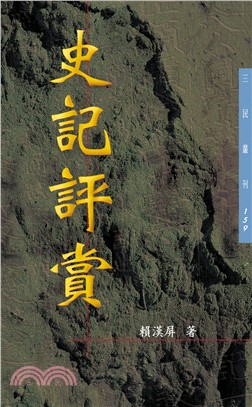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格格不入也是一種罪 我就是這麼被判了死刑
我的罪行是他人精心編撰過的故事,
唯有我不能在我的審判裡辯駁;
他們讓我道歉、認錯、偽裝、皈依上帝,
這世界如此荒謬,我厭倦了強加給我的所有一切。
★【孤獨靈魂必備讀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代表作,全球銷售千萬冊,精準道出孤獨心靈與正常世界間的隔膜感。
★【獨家收錄】沙特評論〈《異鄉人》釋義〉,看存在主義大師如何深入解析卡繆作品中的「荒謬」。
★【名家翻譯】特邀台灣法文翻譯名家邱瑞鑾全新詮釋。
★《異鄉人》完成於一九四O年,卡繆那時才二十六歲。這是卡繆《荒謬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在這個被認為荒謬的世界,且因果意義已經被精心撤除,最細微的意外都有其重量;
沒有一個意外不導致主人翁犯下罪行,最後被送上斷頭台。
《異鄉人》是一部古典作品,一部秩序的作品,關於荒謬,也與荒謬對立。
――沙特
一個至死都拒絕為了順從社會而說謊的人
面對世界溫柔的冷漠,他始終是一個異鄉人
主角默爾索是住在阿爾及爾的一個沉默寡言的上班族。故事從一封後來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簡短的電報開始,結束於一場死亡的審判。而這場審判與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堪稱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兩個審判場景。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一開始,電報帶來了主角在養老院的母親簡潔的死亡訊息,接著是默爾索不帶感情、直白的敘述自己奔喪的過程,以及奔喪後短短幾日的經歷。
緊接著的一場海灘謀殺案,則把默爾索的人生切成了兩半,也完成了兩段故事。
第二部則是默爾索深陷法庭,在法律、宗教、與道德之間被交相指控的過程。
在這期間,默爾索的種種經歷,後來都一一被證明不過是人生的種種荒謬。
同時,第二部分出現了與第一部分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一種戲劇性的表現與轉折。最後,默爾索不再用冰冷的敘述方式,而是用吶喊、用反抗的姿態,直接擁抱了這個冰冷的世界。
我的罪行是他人精心編撰過的故事,
唯有我不能在我的審判裡辯駁;
他們讓我道歉、認錯、偽裝、皈依上帝,
這世界如此荒謬,我厭倦了強加給我的所有一切。
★【孤獨靈魂必備讀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代表作,全球銷售千萬冊,精準道出孤獨心靈與正常世界間的隔膜感。
★【獨家收錄】沙特評論〈《異鄉人》釋義〉,看存在主義大師如何深入解析卡繆作品中的「荒謬」。
★【名家翻譯】特邀台灣法文翻譯名家邱瑞鑾全新詮釋。
★《異鄉人》完成於一九四O年,卡繆那時才二十六歲。這是卡繆《荒謬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在這個被認為荒謬的世界,且因果意義已經被精心撤除,最細微的意外都有其重量;
沒有一個意外不導致主人翁犯下罪行,最後被送上斷頭台。
《異鄉人》是一部古典作品,一部秩序的作品,關於荒謬,也與荒謬對立。
――沙特
一個至死都拒絕為了順從社會而說謊的人
面對世界溫柔的冷漠,他始終是一個異鄉人
主角默爾索是住在阿爾及爾的一個沉默寡言的上班族。故事從一封後來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簡短的電報開始,結束於一場死亡的審判。而這場審判與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堪稱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兩個審判場景。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一開始,電報帶來了主角在養老院的母親簡潔的死亡訊息,接著是默爾索不帶感情、直白的敘述自己奔喪的過程,以及奔喪後短短幾日的經歷。
緊接著的一場海灘謀殺案,則把默爾索的人生切成了兩半,也完成了兩段故事。
第二部則是默爾索深陷法庭,在法律、宗教、與道德之間被交相指控的過程。
在這期間,默爾索的種種經歷,後來都一一被證明不過是人生的種種荒謬。
同時,第二部分出現了與第一部分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一種戲劇性的表現與轉折。最後,默爾索不再用冰冷的敘述方式,而是用吶喊、用反抗的姿態,直接擁抱了這個冰冷的世界。
作者簡介
作者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是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與評論家。
二十六歲時,他創作了不朽的《異鄉人》,並因此成名。幾年後,小說《鼠疫》的出版更獲好評並大為暢銷。四十三歲,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這個獎項史上第二年輕的得主。
一九六O年,卡繆在法國死於車禍,年僅四十六歲。
********************
卡繆未滿周歲,父親就在一戰時陣亡,文盲與聽障的母親帶著他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的外祖母家,生活極為艱困。與聽障的母親和同為聽障的一位舅舅同住,卡繆從小就在靜默中成長。他與母親之間,只有母親默默追隨的眼神。這些對他後來的寫作,有極深的影響,特別是《異鄉人》。
卡繆靠獎助學金讀完中學,接著在阿爾及爾大學半工半讀,攻讀哲學。學生時代卡繆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畢業後,因為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從此決定了卡繆在正統學院外的生涯。
二戰期間,卡繆參加了地下反抗運動,德軍入侵法國時,他負責地下反抗刊物的出版工作。這個時期,也醞釀著《鼠疫》的創作。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兩個系列就是「荒謬三部曲」與「反抗三部曲」。
「荒謬三部曲」包含了小說《異鄉人》、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與劇作《卡里古拉》(也有人認為應該包含他的劇作《誤會》)。
「反抗三部曲」則包含了小說《鼠疫》、劇作《正直的人》、隨筆《反抗者》。
當人們在爭論卡繆是不是存在主義者,或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到底在說甚麼時,法國哲學家沙特則在卡繆的葬禮上,以「固執的人文主義」一詞向卡繆的一生致敬。
卡繆不只是一位小說家,他更是一個社會行動者,一個反叛者,一個思想的實踐者。
邱瑞鑾
法文譯者,東海大學哲學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法國現代文學DEA(高等深入研究文憑)畢業。長年專事法文文學作品翻譯,譯筆信實流暢,致力呈現原著文風,譯著包括《可笑的愛》,《貓咪躲高高》、《綠色牝馬》,《潛水鐘與蝴蝶》、《位置》、《身分》、《小姐變成豬》、《金魚》、《戴眼鏡的女孩》、《一直下雨的星期天》、《O孃》、《種樹的男人》、《第二性》、《論老年》。曾將十多年來每日進駐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讀書日記寫成《布朗修哪裡去了?一個普通讀者的法式閱讀》。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是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與評論家。
二十六歲時,他創作了不朽的《異鄉人》,並因此成名。幾年後,小說《鼠疫》的出版更獲好評並大為暢銷。四十三歲,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這個獎項史上第二年輕的得主。
一九六O年,卡繆在法國死於車禍,年僅四十六歲。
********************
卡繆未滿周歲,父親就在一戰時陣亡,文盲與聽障的母親帶著他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的外祖母家,生活極為艱困。與聽障的母親和同為聽障的一位舅舅同住,卡繆從小就在靜默中成長。他與母親之間,只有母親默默追隨的眼神。這些對他後來的寫作,有極深的影響,特別是《異鄉人》。
卡繆靠獎助學金讀完中學,接著在阿爾及爾大學半工半讀,攻讀哲學。學生時代卡繆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畢業後,因為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從此決定了卡繆在正統學院外的生涯。
二戰期間,卡繆參加了地下反抗運動,德軍入侵法國時,他負責地下反抗刊物的出版工作。這個時期,也醞釀著《鼠疫》的創作。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兩個系列就是「荒謬三部曲」與「反抗三部曲」。
「荒謬三部曲」包含了小說《異鄉人》、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與劇作《卡里古拉》(也有人認為應該包含他的劇作《誤會》)。
「反抗三部曲」則包含了小說《鼠疫》、劇作《正直的人》、隨筆《反抗者》。
當人們在爭論卡繆是不是存在主義者,或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到底在說甚麼時,法國哲學家沙特則在卡繆的葬禮上,以「固執的人文主義」一詞向卡繆的一生致敬。
卡繆不只是一位小說家,他更是一個社會行動者,一個反叛者,一個思想的實踐者。
邱瑞鑾
法文譯者,東海大學哲學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法國現代文學DEA(高等深入研究文憑)畢業。長年專事法文文學作品翻譯,譯筆信實流暢,致力呈現原著文風,譯著包括《可笑的愛》,《貓咪躲高高》、《綠色牝馬》,《潛水鐘與蝴蝶》、《位置》、《身分》、《小姐變成豬》、《金魚》、《戴眼鏡的女孩》、《一直下雨的星期天》、《O孃》、《種樹的男人》、《第二性》、《論老年》。曾將十多年來每日進駐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讀書日記寫成《布朗修哪裡去了?一個普通讀者的法式閱讀》。
序
《異鄉人》釋義――沙特(摘錄)
卡繆先生的《異鄉人》才一出版,便廣受歡迎,佳評如潮。評論都異口同聲說,「這是戰後最優秀的小說」。就當下的文學創作來說,這本小說本身就是個「異鄉人」。它來自分界線的另一邊,來自海的彼端;值此春寒料峭,煤炭短缺之際,小說跟我們講到太陽,但並非把太陽描述成異國情調的裝飾,而是帶著一種過度享受陽光,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的人所有的倦意來談論。這本書並非又要再次親手埋葬舊體制,也不是要直搗我們對自身感到的恥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突然想起以前有一些作品宣稱自身的存在就已足夠,沒有要證明甚麼。但是和這種「無為」之作相較之下,這本小說依然有其模稜兩可的地方:要如何理解這個人物,他在母親過世的隔天,「去游泳,與人有不尋常的關係,去看一部搞笑片,開懷大笑」,他殺了一位阿拉伯人,「由於太陽的緣故」,後來在行刑的前夕,他說他「曾經很幸福,現在依然如此」,並且希望斷頭台周圍會有很多的群眾,「用怨恨的呼喊聲迎接他」。有些人說:「不過就是個傻瓜,可憐的人」;另一些人更有想法:「這是個無辜的人」。至少必須了解此處無辜的意思為何。
卡繆先生在幾個月後出版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中,為我們提供關於這部作品正確的評論:他的主人翁既非好人也非壞人,既不是甚麼有道德也不是沒有道德的人。這些分類框架不適用在他身上:他屬於一種特殊的族群,作者用了「荒謬」這個說法。然而,荒謬在卡繆先生的筆下具有兩種非常不同的意義:荒謬既是一個事實的狀態,也是某些人對這個狀態的明澈意識。荒謬的人會從根本的荒謬性中不偏不倚提出必定的結論。以前swing有「時髦」的意思,若用這個字來形容跳swing的年輕世代,意思已經跑掉了,就像荒謬一詞也一樣。荒謬作為一種狀態,作為一種原初的呈現,所指究竟為何?其實不外乎就是人與世界的關係。荒謬首先展現在一種分離:人追求合一,而精神和自然無法克服二元論,這是分離;人追求永恆,而自身的存在確有其侷限,這是分離;人的本質就是「關注」,然而他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這也是分離。死亡、真理與人類無可化約的多重性、真實的不可理解特性、偶然,這些都是荒謬的幾個端點。
***
不過,卡繆先生或許還是會認同我們這些話。在他眼中,他獨特之處,在於把自己的想法貫徹到底:的確,他並不甘於只是收錄一些悲觀主義的格言錄。當然,荒謬不在於人,也不在於世界,如果我們將這兩件事情分開來看;然而,人基本的特徵就是他的「在世存有」,荒謬的人與人類處境這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因此,荒謬並非單純的概念問題:是某種晦暗陰鬱的亮光向我們揭示了荒謬。「起床、電車、四個小時辦公室或工廠、吃飯、電車、四小時工作、吃飯、睡覺,接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循著一成不變的節奏中……」,接著猝不及防,「背景垮掉了」,我們掉入一道毫無希望的明澈意識中。於是,如果我們懂得摒拒宗教或存在哲學那種騙人的拯救,我們可以掌握基本的真實:世界是一個混沌,一個「從混亂衍生而出」、足以亂真的東西;―沒有明天,反正人人都會死。「……在一個突然沒有假象,沒有光明的世界裡,人自覺是異鄉人。這場放逐是無可拯救,因為人被剝奪了對某個失落國度的記憶,也失去了重返失落樂園的希望。」因為人並非世界:「如果我是森林中的一棵樹,這個生命也許還有一個意義,或者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意義,因為我屬於這個世界。我變成我現在對立的世界,透過我的意識……這個荒誕可笑的理由,讓我與我的創作對立。」這樣就部分解釋了這本書的標題:異鄉人,就是面對世界的人;卡繆先生或許也可以選一個類似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小說標題:《在放逐中誕生》(Né en exil)。異鄉人,這也是人群中的人。「有那麼一些日子,我們尋獲愛過的那個女子,像是個異鄉人。」這是我相對於我來說,也就是自然的人相對於精神來說:「異鄉人,在某些時刻,會出現在鏡中,與我們相會。」
卡繆先生的《異鄉人》才一出版,便廣受歡迎,佳評如潮。評論都異口同聲說,「這是戰後最優秀的小說」。就當下的文學創作來說,這本小說本身就是個「異鄉人」。它來自分界線的另一邊,來自海的彼端;值此春寒料峭,煤炭短缺之際,小說跟我們講到太陽,但並非把太陽描述成異國情調的裝飾,而是帶著一種過度享受陽光,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的人所有的倦意來談論。這本書並非又要再次親手埋葬舊體制,也不是要直搗我們對自身感到的恥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突然想起以前有一些作品宣稱自身的存在就已足夠,沒有要證明甚麼。但是和這種「無為」之作相較之下,這本小說依然有其模稜兩可的地方:要如何理解這個人物,他在母親過世的隔天,「去游泳,與人有不尋常的關係,去看一部搞笑片,開懷大笑」,他殺了一位阿拉伯人,「由於太陽的緣故」,後來在行刑的前夕,他說他「曾經很幸福,現在依然如此」,並且希望斷頭台周圍會有很多的群眾,「用怨恨的呼喊聲迎接他」。有些人說:「不過就是個傻瓜,可憐的人」;另一些人更有想法:「這是個無辜的人」。至少必須了解此處無辜的意思為何。
卡繆先生在幾個月後出版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中,為我們提供關於這部作品正確的評論:他的主人翁既非好人也非壞人,既不是甚麼有道德也不是沒有道德的人。這些分類框架不適用在他身上:他屬於一種特殊的族群,作者用了「荒謬」這個說法。然而,荒謬在卡繆先生的筆下具有兩種非常不同的意義:荒謬既是一個事實的狀態,也是某些人對這個狀態的明澈意識。荒謬的人會從根本的荒謬性中不偏不倚提出必定的結論。以前swing有「時髦」的意思,若用這個字來形容跳swing的年輕世代,意思已經跑掉了,就像荒謬一詞也一樣。荒謬作為一種狀態,作為一種原初的呈現,所指究竟為何?其實不外乎就是人與世界的關係。荒謬首先展現在一種分離:人追求合一,而精神和自然無法克服二元論,這是分離;人追求永恆,而自身的存在確有其侷限,這是分離;人的本質就是「關注」,然而他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這也是分離。死亡、真理與人類無可化約的多重性、真實的不可理解特性、偶然,這些都是荒謬的幾個端點。
***
不過,卡繆先生或許還是會認同我們這些話。在他眼中,他獨特之處,在於把自己的想法貫徹到底:的確,他並不甘於只是收錄一些悲觀主義的格言錄。當然,荒謬不在於人,也不在於世界,如果我們將這兩件事情分開來看;然而,人基本的特徵就是他的「在世存有」,荒謬的人與人類處境這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因此,荒謬並非單純的概念問題:是某種晦暗陰鬱的亮光向我們揭示了荒謬。「起床、電車、四個小時辦公室或工廠、吃飯、電車、四小時工作、吃飯、睡覺,接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循著一成不變的節奏中……」,接著猝不及防,「背景垮掉了」,我們掉入一道毫無希望的明澈意識中。於是,如果我們懂得摒拒宗教或存在哲學那種騙人的拯救,我們可以掌握基本的真實:世界是一個混沌,一個「從混亂衍生而出」、足以亂真的東西;―沒有明天,反正人人都會死。「……在一個突然沒有假象,沒有光明的世界裡,人自覺是異鄉人。這場放逐是無可拯救,因為人被剝奪了對某個失落國度的記憶,也失去了重返失落樂園的希望。」因為人並非世界:「如果我是森林中的一棵樹,這個生命也許還有一個意義,或者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意義,因為我屬於這個世界。我變成我現在對立的世界,透過我的意識……這個荒誕可笑的理由,讓我與我的創作對立。」這樣就部分解釋了這本書的標題:異鄉人,就是面對世界的人;卡繆先生或許也可以選一個類似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小說標題:《在放逐中誕生》(Né en exil)。異鄉人,這也是人群中的人。「有那麼一些日子,我們尋獲愛過的那個女子,像是個異鄉人。」這是我相對於我來說,也就是自然的人相對於精神來說:「異鄉人,在某些時刻,會出現在鏡中,與我們相會。」
目次
異鄉人
《異鄉人》釋義――沙特
卡繆年表
《異鄉人》釋義――沙特
卡繆年表
書摘/試閱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電報:「母歿。明日葬。致哀。」這並不表示什麼。說不定是昨天。
養老院在馬倫哥,離阿爾及爾八十公里。我會搭兩點的巴士,下午就會到了。這樣,我就能守靈,明天晚上回家。我跟老闆請了兩天假,這樣的理由,他不能不准假。但他看起來不太高興。我跟他說:「這不是我的錯。」他沒答腔。我心想,不該這麼跟他說的。總之,我沒什麼好抱歉的。反倒是他應該慰問我。不過後天他一看到我服喪,可能就會這麼做了。在這個時候,有點像是媽媽還沒死。下葬以後,這件事就算了結了,這一切會顯得比較正式。
我搭的是兩點的巴士。天氣熱得很。我中午照例去塞勒斯特的餐館吃飯,他們每個人都為我難過,塞勒斯特對我說:「母親只有一個。」我離開時,他們全都送我到門口。我有點昏,因為還得上樓到艾曼紐爾那裡,跟他借黑領帶和臂紗。他叔叔在幾個月前死了。
我跑著去趕車,免得誤了班次。大概是因為又是匆忙、又是奔跑,再加上車子顛簸、汽油味、路面的熱氣,還有天光的反射,弄得我昏沉沉的。我幾乎一整路都在睡。醒來時,身子緊靠著一位軍人,他對我笑了笑,問我是不是從遠地來。我只簡短的應了聲「是」,避免交談下去。
養老院離鎮上兩公里。我一路走過去。到了之後,我想立刻去看媽媽。但是門房跟我說,必須先和院長見個面。院長正忙著,我等了一會兒。等待的時候,門房也一直跟我說著話,後來,我見到了院長。他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院長是個小老頭,佩戴著榮譽軍團勳章。他用清澈的眼睛看著我。然後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讓我不知道怎麼把手抽回來。他看了一份資料,對我說:「默爾索太太是三年前來到這裡的。您是她唯一的支柱。」我以為他在責怪我什麼,不禁辯白起來。但他打斷了我:「親愛的孩子,您沒有必要說明。我看了您母親的資料。您無力供養她的。您母親必須有人看護。但您薪水也不高。不過,畢竟,她在這裡比較快樂。」我說:「是的,院長。」他又加了一句:「您知道,她有朋友,和她年齡相近。他們對過去的事有共同的興趣,可以彼此分享。您年紀輕,她和您在一起會很無聊的。」
的確。媽媽住在家裡時,整天只是用眼神尾隨著我,默不作聲。她到養老院的頭幾天還常常哭。但這是習慣問題。幾個月過後,如果要把她帶離養老院,她也會哭的。這一樣是習慣問題。有點是因為這個原因,最後這一年我幾乎沒來看她。也因為這樣會占用我的星期日──更別提還得花力氣到巴士站、買票、坐兩個小時的車。
院長還繼續對我說了些話。但我沒怎麼聽進去。然後,他又對我說:「我想您會想要看看您母親。」我站了起來,什麼也沒說。院長領著我走出了辦公室。在樓梯上,他向我解釋:「我們把她安置在小太平間裡,免得其他人情緒受影響。每逢有院友過世,其他人就會兩、三天心緒不寧,這會造成工作人員的困擾。」我們走過一個院子,有許多老人在那兒,三三兩兩聚著聊天。我們經過時,他們就全噤了口。我們一走過,身後就又響起了交談聲。那聲音真像是鸚鵡唧唧呱呱個不停。來到一棟小型建築物門前,院長向我告辭:「默爾索先生,我先走一步。有事請到辦公室找我。原則上,葬禮是敲定早上十點。我們想這樣您就可以為亡者守靈了。還有,您母親似乎常向同伴表示希望依照宗教儀式舉行葬禮。我已經安排好一切,不過還是知會您一聲。」我向院長道了謝。其實,媽媽雖然不是無神論者,但她生前從沒想過信仰的事。
我走了進去。這是一間明亮的大廳,白石灰牆,玻璃屋頂。裡面擺著幾張椅子,和幾個X形的托架。在大廳中央,兩個托架上承放著一具棺木,棺木的封蓋是闔上的。只見發亮的螺絲釘稍稍旋了進去,襯著深褐色的棺木看得特別清楚。一旁,有個阿拉伯護士,穿著白色罩衫,包著顏色鮮豔的頭巾。
這個時候,門房跟在我身後進來了。想必他是跑來的。他上氣不接下氣的的說:「棺蓋蓋上了。我拿開螺絲釘,好讓您看看她。」門房走近棺木時,我攔住了他。他對我說:「您不看看嗎?」我回答他:「不了。」門房頓時僵住了,這讓我很尷尬,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該這麼說。過了一會兒,門房看了看我,問我:「為什麼?」不過語氣不帶一絲譴責,好像只是想弄明白。我說:「我不知道。」然後,門房捻了捻自己的白鬍子,也沒有看我,只說:「我瞭解。」門房有著漂亮的淡藍色雙眼,氣色還算紅潤。他遞了一張椅子給我,自己坐在我後面一點的地方。護士站起來,往出口走去。這時候,門房對我說:「她長了個爛瘡。」我不太明白他要說什麼,就瞧著護士。護士的臉上,從眼睛以下,前前後後都纏滿了布條。連鼻子上的布條看起來都是平的。她臉上只看得見雪白的布條。
護士出去之後,門房說:「那我就先走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手勢,結果讓他留了下來,仍然站在我的背後。背後有個人其實讓我很不自在。傍晚絢麗的陽光充盈著整個大廳。兩隻大胡蜂就著玻璃屋頂嗡嗡鳴叫著。這時我有了睡意。我沒轉身,便背對著門房問他:「您在這兒多久了?」他很快就回我:「五年。」好像早就在等著我問他。
接著他喋喋不休地說了許多:如果當年有人跟他說,他最終會在馬倫哥的養老院裡當門房,他一定不會相信。他那時候六十四歲,還是巴黎人。一聽到這裡,我打斷了他:「喔!您不是這兒的人?」這時我才想到在他帶我去院長辦公室之前,他跟我提起媽媽。他說要快點下葬,因為平原天氣燠熱,尤其是這個地方。他之前也跟我說到他曾經住過巴黎,他忘不了巴黎。在那裡,靈柩可以停放三天,有時候四天。但在這裡,可沒那個時間,還沒接受死亡的事實,就得跟著靈車去下葬了。這時門房的太太說話了:「別說了,這種事怎麼好拿來跟先生說。」老頭子臉紅了,道著歉。我連聲說:「不要緊。不要緊。」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又有意思。
在這個小太平間裡,門房跟我說,他是以窮人的身分住進養老院的。因為他身體硬朗,就向院方提議由他來擔任門房。當我指出他也算是院友時。他說他可不是。我之前就注意到,門房在提到院友時,總是說「他們」、「其他人」,偶爾會說「老人」,其中有些人年紀還沒他大。不過,他和他們當然不同。他是門房,某種程度來說,他有權利管他們。
護士在這時候進來了。天色忽然暗下來。玻璃屋頂上很快就是一片漆黑的夜。門房扭開電燈開關,乍亮的光線扎得我眼睛睜不開。他請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餓。他說可以幫我端來一杯咖啡牛奶。我很喜歡咖啡牛奶,就接受了,不一會兒他就端著餐盤回來了。喝了咖啡,這時我好想抽根菸。但是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媽面前這麼做。我想了想,覺得這一點都不重要。我給了門房一根煙,然後我們抽了起來。
過一會兒,門房對我說:「您知道,您母親有幾個朋友也會來守靈。這是慣例。我得去搬幾張椅子,還要準備黑咖啡。」我問他能不能關掉一盞燈。照在白牆上的光線讓我疲倦。他跟我說沒辦法。這燈就是這麼設計的:要嘛全亮,要嘛全不亮。我不再怎麼留意門房了。他出去,又回來,擺好椅子。他在一張椅子上圍著咖啡壺放了一疊杯子。然後他在媽媽的另一頭,和我面對面坐下。護士也坐在大廳後面,背對著我。我看不出來她在做什麼,不過從她手部的動作看,我猜是在打毛線。大廳裡很暖和,咖啡暖了我的身子,夜色和花朵的氣味從打開的門裡透進來。我想我有點打瞌睡了。
一陣窸窣聲把我吵醒。再睜開眼,大廳看來更是白得發亮。眼前,連一點陰影也沒有,每樣物品、每個角落、每個曲線都顯得純粹而刺眼。就在這時候,媽媽的朋友進了大廳。他們總共十來個,都靜悄悄地走入這令人目眩的燈光裡。他們坐下來,沒有一張椅子發出嘎吱聲。我仔細端詳他們,把他們臉上、衣服上的細節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聽不見他們發出任何聲響。我差一點以為這都是幻覺。女人幾乎都穿著圍裙,繫在腰上的帶子讓她們的肚子鼓了起來。我從沒注意到老太太的肚子會這麼大。男人則幾乎都很瘦,一律拄著拐杖。讓我吃驚的是,我看不見他們臉上的眼睛,只見到擠在皺紋中的一道黯淡微光。他們坐下來以後大多都看著我,並侷促地點了點頭,他們的嘴唇全縮進了沒有牙齒的嘴巴裡,我不知道這動作是在向我致意,或者只是肌肉不隨意的抽動。我想比較像是向我致意吧。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他們全都圍在門房左右,坐在我對面,微微晃著腦袋。我忽然有一種可笑的感覺,認為他們之所以在這兒是為了審判我。
養老院在馬倫哥,離阿爾及爾八十公里。我會搭兩點的巴士,下午就會到了。這樣,我就能守靈,明天晚上回家。我跟老闆請了兩天假,這樣的理由,他不能不准假。但他看起來不太高興。我跟他說:「這不是我的錯。」他沒答腔。我心想,不該這麼跟他說的。總之,我沒什麼好抱歉的。反倒是他應該慰問我。不過後天他一看到我服喪,可能就會這麼做了。在這個時候,有點像是媽媽還沒死。下葬以後,這件事就算了結了,這一切會顯得比較正式。
我搭的是兩點的巴士。天氣熱得很。我中午照例去塞勒斯特的餐館吃飯,他們每個人都為我難過,塞勒斯特對我說:「母親只有一個。」我離開時,他們全都送我到門口。我有點昏,因為還得上樓到艾曼紐爾那裡,跟他借黑領帶和臂紗。他叔叔在幾個月前死了。
我跑著去趕車,免得誤了班次。大概是因為又是匆忙、又是奔跑,再加上車子顛簸、汽油味、路面的熱氣,還有天光的反射,弄得我昏沉沉的。我幾乎一整路都在睡。醒來時,身子緊靠著一位軍人,他對我笑了笑,問我是不是從遠地來。我只簡短的應了聲「是」,避免交談下去。
養老院離鎮上兩公里。我一路走過去。到了之後,我想立刻去看媽媽。但是門房跟我說,必須先和院長見個面。院長正忙著,我等了一會兒。等待的時候,門房也一直跟我說著話,後來,我見到了院長。他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院長是個小老頭,佩戴著榮譽軍團勳章。他用清澈的眼睛看著我。然後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讓我不知道怎麼把手抽回來。他看了一份資料,對我說:「默爾索太太是三年前來到這裡的。您是她唯一的支柱。」我以為他在責怪我什麼,不禁辯白起來。但他打斷了我:「親愛的孩子,您沒有必要說明。我看了您母親的資料。您無力供養她的。您母親必須有人看護。但您薪水也不高。不過,畢竟,她在這裡比較快樂。」我說:「是的,院長。」他又加了一句:「您知道,她有朋友,和她年齡相近。他們對過去的事有共同的興趣,可以彼此分享。您年紀輕,她和您在一起會很無聊的。」
的確。媽媽住在家裡時,整天只是用眼神尾隨著我,默不作聲。她到養老院的頭幾天還常常哭。但這是習慣問題。幾個月過後,如果要把她帶離養老院,她也會哭的。這一樣是習慣問題。有點是因為這個原因,最後這一年我幾乎沒來看她。也因為這樣會占用我的星期日──更別提還得花力氣到巴士站、買票、坐兩個小時的車。
院長還繼續對我說了些話。但我沒怎麼聽進去。然後,他又對我說:「我想您會想要看看您母親。」我站了起來,什麼也沒說。院長領著我走出了辦公室。在樓梯上,他向我解釋:「我們把她安置在小太平間裡,免得其他人情緒受影響。每逢有院友過世,其他人就會兩、三天心緒不寧,這會造成工作人員的困擾。」我們走過一個院子,有許多老人在那兒,三三兩兩聚著聊天。我們經過時,他們就全噤了口。我們一走過,身後就又響起了交談聲。那聲音真像是鸚鵡唧唧呱呱個不停。來到一棟小型建築物門前,院長向我告辭:「默爾索先生,我先走一步。有事請到辦公室找我。原則上,葬禮是敲定早上十點。我們想這樣您就可以為亡者守靈了。還有,您母親似乎常向同伴表示希望依照宗教儀式舉行葬禮。我已經安排好一切,不過還是知會您一聲。」我向院長道了謝。其實,媽媽雖然不是無神論者,但她生前從沒想過信仰的事。
我走了進去。這是一間明亮的大廳,白石灰牆,玻璃屋頂。裡面擺著幾張椅子,和幾個X形的托架。在大廳中央,兩個托架上承放著一具棺木,棺木的封蓋是闔上的。只見發亮的螺絲釘稍稍旋了進去,襯著深褐色的棺木看得特別清楚。一旁,有個阿拉伯護士,穿著白色罩衫,包著顏色鮮豔的頭巾。
這個時候,門房跟在我身後進來了。想必他是跑來的。他上氣不接下氣的的說:「棺蓋蓋上了。我拿開螺絲釘,好讓您看看她。」門房走近棺木時,我攔住了他。他對我說:「您不看看嗎?」我回答他:「不了。」門房頓時僵住了,這讓我很尷尬,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該這麼說。過了一會兒,門房看了看我,問我:「為什麼?」不過語氣不帶一絲譴責,好像只是想弄明白。我說:「我不知道。」然後,門房捻了捻自己的白鬍子,也沒有看我,只說:「我瞭解。」門房有著漂亮的淡藍色雙眼,氣色還算紅潤。他遞了一張椅子給我,自己坐在我後面一點的地方。護士站起來,往出口走去。這時候,門房對我說:「她長了個爛瘡。」我不太明白他要說什麼,就瞧著護士。護士的臉上,從眼睛以下,前前後後都纏滿了布條。連鼻子上的布條看起來都是平的。她臉上只看得見雪白的布條。
護士出去之後,門房說:「那我就先走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手勢,結果讓他留了下來,仍然站在我的背後。背後有個人其實讓我很不自在。傍晚絢麗的陽光充盈著整個大廳。兩隻大胡蜂就著玻璃屋頂嗡嗡鳴叫著。這時我有了睡意。我沒轉身,便背對著門房問他:「您在這兒多久了?」他很快就回我:「五年。」好像早就在等著我問他。
接著他喋喋不休地說了許多:如果當年有人跟他說,他最終會在馬倫哥的養老院裡當門房,他一定不會相信。他那時候六十四歲,還是巴黎人。一聽到這裡,我打斷了他:「喔!您不是這兒的人?」這時我才想到在他帶我去院長辦公室之前,他跟我提起媽媽。他說要快點下葬,因為平原天氣燠熱,尤其是這個地方。他之前也跟我說到他曾經住過巴黎,他忘不了巴黎。在那裡,靈柩可以停放三天,有時候四天。但在這裡,可沒那個時間,還沒接受死亡的事實,就得跟著靈車去下葬了。這時門房的太太說話了:「別說了,這種事怎麼好拿來跟先生說。」老頭子臉紅了,道著歉。我連聲說:「不要緊。不要緊。」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又有意思。
在這個小太平間裡,門房跟我說,他是以窮人的身分住進養老院的。因為他身體硬朗,就向院方提議由他來擔任門房。當我指出他也算是院友時。他說他可不是。我之前就注意到,門房在提到院友時,總是說「他們」、「其他人」,偶爾會說「老人」,其中有些人年紀還沒他大。不過,他和他們當然不同。他是門房,某種程度來說,他有權利管他們。
護士在這時候進來了。天色忽然暗下來。玻璃屋頂上很快就是一片漆黑的夜。門房扭開電燈開關,乍亮的光線扎得我眼睛睜不開。他請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餓。他說可以幫我端來一杯咖啡牛奶。我很喜歡咖啡牛奶,就接受了,不一會兒他就端著餐盤回來了。喝了咖啡,這時我好想抽根菸。但是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媽面前這麼做。我想了想,覺得這一點都不重要。我給了門房一根煙,然後我們抽了起來。
過一會兒,門房對我說:「您知道,您母親有幾個朋友也會來守靈。這是慣例。我得去搬幾張椅子,還要準備黑咖啡。」我問他能不能關掉一盞燈。照在白牆上的光線讓我疲倦。他跟我說沒辦法。這燈就是這麼設計的:要嘛全亮,要嘛全不亮。我不再怎麼留意門房了。他出去,又回來,擺好椅子。他在一張椅子上圍著咖啡壺放了一疊杯子。然後他在媽媽的另一頭,和我面對面坐下。護士也坐在大廳後面,背對著我。我看不出來她在做什麼,不過從她手部的動作看,我猜是在打毛線。大廳裡很暖和,咖啡暖了我的身子,夜色和花朵的氣味從打開的門裡透進來。我想我有點打瞌睡了。
一陣窸窣聲把我吵醒。再睜開眼,大廳看來更是白得發亮。眼前,連一點陰影也沒有,每樣物品、每個角落、每個曲線都顯得純粹而刺眼。就在這時候,媽媽的朋友進了大廳。他們總共十來個,都靜悄悄地走入這令人目眩的燈光裡。他們坐下來,沒有一張椅子發出嘎吱聲。我仔細端詳他們,把他們臉上、衣服上的細節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聽不見他們發出任何聲響。我差一點以為這都是幻覺。女人幾乎都穿著圍裙,繫在腰上的帶子讓她們的肚子鼓了起來。我從沒注意到老太太的肚子會這麼大。男人則幾乎都很瘦,一律拄著拐杖。讓我吃驚的是,我看不見他們臉上的眼睛,只見到擠在皺紋中的一道黯淡微光。他們坐下來以後大多都看著我,並侷促地點了點頭,他們的嘴唇全縮進了沒有牙齒的嘴巴裡,我不知道這動作是在向我致意,或者只是肌肉不隨意的抽動。我想比較像是向我致意吧。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他們全都圍在門房左右,坐在我對面,微微晃著腦袋。我忽然有一種可笑的感覺,認為他們之所以在這兒是為了審判我。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