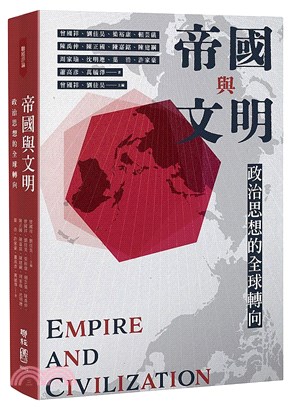定價
:NT$ 580 元優惠價
:90 折 522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5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從格勞秀斯到馬克思
以13位思想大家之眼,看近代歐洲帝國與政治思想的歷史全景。
▍探討帝國與文明的悖論
帝國與文明這兩大主題,自15世紀歐洲列強著眼世界的劇變時代起始,始終是與現代政治發展並行的核心悖論。在邁向帝國化、全球化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如何彼此激辯,又如何與現實碰撞呢?
《帝國與文明》試圖透過哲學、歷史的雙重視野,循全球政治思想的多重時空軸線,深入探索「帝國與文明」這兩個理念,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激發的理論爭議、現實難題,由跨文化的角度,論述西方文明為軸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普遍價值,兼具哲學與歷史縱深。
▍7大主題,定義時代的13位思想家
為了準確追索在時代脈動中的文明與政治、世界秩序與普遍價值的流變,《帝國與文明》以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盧梭、亞當‧斯密、康德、柏克、孔多塞、邊沁、黑格爾、托克維爾、彌爾、馬克思等13位橫跨英、法、德三大政治哲學傳統的思想家為核心,並透過7大主題的聚焦:自然法的詮釋、商業社會、對人文主義的批判、理性法則的求索、自由帝國主義、帝國論述的轉向、全球資本帝國,來看個人價值與人性想像、民族與國家、歐洲精神與世界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
▍立足東亞,看「全球轉向」
《帝國與文明》以東亞學者視角為立足點,呼應英美思想界的「全球轉向」,除了意欲重新檢視近代歐洲政治與思想的文化、歷史影響,探尋型塑現代政治與價值的關鍵,更期待能拋磚引玉,開拓華語政治思想研究的新視界。
作者簡介
主編
曾國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
曾國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梁裕康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賴芸儀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禹仲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陳正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嘉銘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建綱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周家瑜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沈明璁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葉 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許家豪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助理教授
蕭高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依文章先後次序排序)
曾國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
曾國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梁裕康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賴芸儀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禹仲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陳正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嘉銘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建綱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周家瑜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沈明璁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葉 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許家豪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助理教授
蕭高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依文章先後次序排序)
序
導論(節錄)
在帝國主義之前
曾國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帝國與文明
本書屬於全球政治思想史之研究範疇,嘗試在「帝國與文明」的問題架構下,涉足從歐洲到美洲、亞洲的跨文化視域,針對以西方文明為軸心的世界秩序和普遍價值論述,進行兼具哲學深度與歷史縱深的批判性反思。為此,我們邀集國內史學、社會學與政治思想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協力合作的方式,全面探索引領時代風騷的近代政治理論大師,如何在親臨歐洲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政治場景中,著手闡述個人價值、民族國家、歐洲精神與世界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終而自信地從歐洲的特定文化傳統來界定人類文明的普遍意涵。
更具體地說,本書各篇文章共同追索的核心問題,聚焦於帝國與文明的悖論,並在結合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下,呈現兩大特色。在縱向上,本書的討論範圍涵蓋了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乃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等,賦予人類政治以「現代」新意之偉大作家的經典文本。就此而言,本書所涉獵的知識版圖,不僅包含英、法、德三大政治哲學傳統,並翔實地勾勒出歐洲近代帝國與文明思想發展的數百年軌跡。
在橫向上,自15、16世紀起,當歐洲強權將其擴張野心轉向美洲、亞洲,乃至世界時,歐洲政治思想的視域,即向全球著眼。在此視域轉換的過程裡,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線索,乃無可避免地與「帝國與帝國主義」、「文明與野蠻」、「歐洲中心主義」等課題密切交織。換言之,正因為現代政治的主要概念,諸如:國家、憲法、自由、權利、平等、公民、商業社會、民主,乃至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等,無一不是源起於近代歐洲,而近代歐洲的政治史實質上又涉足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史。因此,從全球政治史的觀點來看,形塑現代政治概念的歷史語境,同時承載著一套有關世界秩序與普遍價值之論述的議題叢結,諸如:自然法、萬民法、政治法、征服、義戰、奴隸、占有、殖民、自由貿易、商業社會、同意、契約、國家建構、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國際法、普遍人性、普世人權、民族意識、資本主義、文明進步史觀等等。就此而言,本書最重要的一項貢獻,便是呼應英美思想界的「全球轉向」,立足於東亞學者的視角,來重新檢視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跨文化意涵及其歷史影響,進而開拓華語政治思想研究的新視界。
本書收錄的十三篇文章,針對從格勞秀斯到馬克思這十三位思想大家的帝國政治思想,進行了細緻的討論和綿密的梳理。而在章節順序的安排上,則是以議題線索為導向,並未完全依照思想家的出生年分先後。通過本文所規劃的七大討論主題,讀者將可在影響歐洲、改變世界的偉大哲學心靈的引導下,對近代歐洲政治思想的歷史全景形成更完整的認識。在我們進入七大主題之前,或不妨先就「全球」、「帝國」、「文明」、「歐洲中心主義」等貫穿全書的主要概念略作說明,以利讀者掌握各篇文章共同關注的核心課題之梗概。
帝國與帝國主義
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相當盛行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角度來看,我們如果要對近代歐洲政治語言之起源及發展提出具體的考察,就必須聚焦於「ideas in context」,緊扣現代國家、政教衝突、政治動盪(尤其是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商業社會、科技昌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等重大歷史事件,來釐清政治詞彙的意義脈絡。雖然在過去已有不少論著討論過,15世紀到17世紀的歐洲地理大發現對於近代政治思想史發展的影響,而其中最顯著的例證,大概就是探索海外貿易與殖民活動所引發的文化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自然法與萬民法的適用範圍之論爭。不過,真正以「帝國」所表徵的歐洲強權之「跨洲擴張」作為重探近代政治思想史之新視點的做法,即便是在英美學界,也不過是晚近這二十年間才興起的風潮。
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全球」(global)與「國際」(international)儼然是同義詞。然而,在本書中,此二概念將依照不同的語境審慎使用。這主要是基於以下的考量:首先,「國際」一詞實為邊沁所創用,因此貿然使用「國際」概念來詮釋邊沁以前的作家關於「帝國」的省思,恐有時代錯置之嫌。其次,顧名思義,「國際」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舉例來說,實質上代表英國治理印度的機構是成立於1600年的東印度公司,所謂的國際關係顯然不適合指稱18世紀「帝國」脈絡下的英印關係。再者,正也因為現代「國家」的概念源自歐洲,所以到了19世紀後半葉,國際法的學習與適用問題再度成為全球政治的爭論焦點,因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為國際法之權利義務主體的依據,恰恰是根源於西方世界的「文明」標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帝國」(empire)或「帝國的」(imperial)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雖然有著相同的字源,卻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意涵(Muthu, 2012: 4-6)。英文的empire源自拉丁文的imperio,原意是指最高治權或軍事統治。引用梅爾(Charles Maier, 2006: 24-25)的話來說:「帝國,就其古典意涵而言,通常被認為是,第一、藉著征服與脅迫擴大其控制;第二、控制其所征服之領地的忠誠。其或直接統治這些臣屬之地,或任命順從的讓在地領導者代其治理,但他們之間絕非是平等夥伴的結盟體系。」在「征服」的問題上,如一般所知,霍布斯的觀點具有開創性,影響深遠。不過,有待補充說明的是:到了18世紀,「帝國」的內涵開始出現轉變,由征服、占領,轉為因殖民、移居而對一群廣大土地進行控制,有時也意味著對貿易駐點的商業壟斷(亦即「商業帝國」)或對海外居民的間接統治(亦即「海洋帝國」)。舉例而言,雖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使用了「殖民」與「大英帝國」等字眼,但其內涵即與征服型帝國不同,甚至與我們今天所認定的「帝國主義」相去甚遠。正如其他主要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一詞也是在19世紀以後才流行開來的。就此而言,區辨「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內涵差異,可以幫助我們思索歐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歷史性轉向,進而挖掘許多18世紀的經典文本所蘊藏的反對帝國暴政的思想素材。
就「帝國主義」一詞的內涵來說,其在近代歐洲的普遍使用,多是指拿破崙在1804年稱帝之後,向歐洲各地與海外非歐洲地區推展的擴張主義。不過,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知識界來說,拿破崙以其軍事優勢為歐洲帶來的,不僅是帝國的擴張思維,更是一種足以顛覆長久以來歐洲社會崇敬的共和政體想像,進而致使各國走向民族國家體制的現代國際政治發展。在勃森(J. A. Hobson)的名著《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結尾處,便曾提到:「帝國主義是個墮落的民族生活選擇,是由貪求物豐和過去百年來追求動物性生存處境而展開的武力支配,這雙重自利的訴求造成。」(1902: 390)換言之,帝國主義的特色除了武力擴張、物質榨取之外,更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有關。然而,如果帝國主義的內涵,與民族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此語詞自然和「國際」一語相同,很難如實指稱19世紀以前的歐洲國家海外貿易與殖民行徑。
當然,從列寧的角度來說,雖然「帝國主義」一語是在19世紀才於英國廣泛使用,但他認為在16、17世紀英國伊莉莎白世代,「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一語便已廣泛為時人所用,而且此時的大英帝國已然具有武力擴張、物質榨取等特徵。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接受列寧所言,「帝國主義」作為一個常見語詞固然是在19世紀才成型,但其現實特徵卻可能早在16、17世紀便已見端倪。列寧的分析誠有其道理,但正如羅伯.楊(Robert Young, 2001: 110)所指出的,「對列寧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帝國主義描述的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個階段,而非跨歷史向度的政治與軍事支配作為。」因此,從本書涵蓋的時間與空間軸線來說,我們著眼的是「帝國主義」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的歐洲政治思想發展;這也就是說,探討「帝國」從武力征服到自由貿易的變化,仍為本書多數作者所共同關注者。不過,正因為帝國主義與帝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透過考察帝國,我們其實也為更進一步認識、分析帝國主義的發展,作了鋪墊。
延續這點來說,按一般分類,近代歐洲強權的海外霸業屬於「海洋帝國」的型態,而與傳統中國透過天下體系與朝貢制度所建立的「大陸帝國」有所差別。在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著名的定義上,大英帝國即標示著「自由、基督教、海洋、貿易」的特徵。在本書中,我們因此將結合下列四項要素來定義「帝國」:
(1)擁有相對「廣大」(large)的領土。
(2)一種「普遍」(universal)的信念。
(3)包含不同國家於其中,並由某一族群或部落來「統治」(rule over)其他族群或部落。
(4)此一統治事實通常是經由「征服」(conquest)而取得的(Pagden, 2015: 1)。
這一用法的好處是:只要略加修飾就可以適用於東亞傳統。換言之,帝國的「廣大」、「普遍」、對不同族群之「統治」等特徵,基本上相應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唯一顯著的差別可能是基於儒家傳統,天下體系認為以德服人在道德判斷上是高於窮兵黷武的,雖然在許多場合中戰爭仍是在所難免。持平而論,正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行並列,近代歐洲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歷史發展大抵上也是在普遍的正義原則與特殊的國家利益之間游蕩。在這點上,中西傳統似無決定性的差異。
在帝國主義之前
曾國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帝國與文明
本書屬於全球政治思想史之研究範疇,嘗試在「帝國與文明」的問題架構下,涉足從歐洲到美洲、亞洲的跨文化視域,針對以西方文明為軸心的世界秩序和普遍價值論述,進行兼具哲學深度與歷史縱深的批判性反思。為此,我們邀集國內史學、社會學與政治思想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協力合作的方式,全面探索引領時代風騷的近代政治理論大師,如何在親臨歐洲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政治場景中,著手闡述個人價值、民族國家、歐洲精神與世界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終而自信地從歐洲的特定文化傳統來界定人類文明的普遍意涵。
更具體地說,本書各篇文章共同追索的核心問題,聚焦於帝國與文明的悖論,並在結合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下,呈現兩大特色。在縱向上,本書的討論範圍涵蓋了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乃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等,賦予人類政治以「現代」新意之偉大作家的經典文本。就此而言,本書所涉獵的知識版圖,不僅包含英、法、德三大政治哲學傳統,並翔實地勾勒出歐洲近代帝國與文明思想發展的數百年軌跡。
在橫向上,自15、16世紀起,當歐洲強權將其擴張野心轉向美洲、亞洲,乃至世界時,歐洲政治思想的視域,即向全球著眼。在此視域轉換的過程裡,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線索,乃無可避免地與「帝國與帝國主義」、「文明與野蠻」、「歐洲中心主義」等課題密切交織。換言之,正因為現代政治的主要概念,諸如:國家、憲法、自由、權利、平等、公民、商業社會、民主,乃至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等,無一不是源起於近代歐洲,而近代歐洲的政治史實質上又涉足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史。因此,從全球政治史的觀點來看,形塑現代政治概念的歷史語境,同時承載著一套有關世界秩序與普遍價值之論述的議題叢結,諸如:自然法、萬民法、政治法、征服、義戰、奴隸、占有、殖民、自由貿易、商業社會、同意、契約、國家建構、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國際法、普遍人性、普世人權、民族意識、資本主義、文明進步史觀等等。就此而言,本書最重要的一項貢獻,便是呼應英美思想界的「全球轉向」,立足於東亞學者的視角,來重新檢視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跨文化意涵及其歷史影響,進而開拓華語政治思想研究的新視界。
本書收錄的十三篇文章,針對從格勞秀斯到馬克思這十三位思想大家的帝國政治思想,進行了細緻的討論和綿密的梳理。而在章節順序的安排上,則是以議題線索為導向,並未完全依照思想家的出生年分先後。通過本文所規劃的七大討論主題,讀者將可在影響歐洲、改變世界的偉大哲學心靈的引導下,對近代歐洲政治思想的歷史全景形成更完整的認識。在我們進入七大主題之前,或不妨先就「全球」、「帝國」、「文明」、「歐洲中心主義」等貫穿全書的主要概念略作說明,以利讀者掌握各篇文章共同關注的核心課題之梗概。
帝國與帝國主義
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相當盛行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角度來看,我們如果要對近代歐洲政治語言之起源及發展提出具體的考察,就必須聚焦於「ideas in context」,緊扣現代國家、政教衝突、政治動盪(尤其是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商業社會、科技昌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等重大歷史事件,來釐清政治詞彙的意義脈絡。雖然在過去已有不少論著討論過,15世紀到17世紀的歐洲地理大發現對於近代政治思想史發展的影響,而其中最顯著的例證,大概就是探索海外貿易與殖民活動所引發的文化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自然法與萬民法的適用範圍之論爭。不過,真正以「帝國」所表徵的歐洲強權之「跨洲擴張」作為重探近代政治思想史之新視點的做法,即便是在英美學界,也不過是晚近這二十年間才興起的風潮。
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全球」(global)與「國際」(international)儼然是同義詞。然而,在本書中,此二概念將依照不同的語境審慎使用。這主要是基於以下的考量:首先,「國際」一詞實為邊沁所創用,因此貿然使用「國際」概念來詮釋邊沁以前的作家關於「帝國」的省思,恐有時代錯置之嫌。其次,顧名思義,「國際」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舉例來說,實質上代表英國治理印度的機構是成立於1600年的東印度公司,所謂的國際關係顯然不適合指稱18世紀「帝國」脈絡下的英印關係。再者,正也因為現代「國家」的概念源自歐洲,所以到了19世紀後半葉,國際法的學習與適用問題再度成為全球政治的爭論焦點,因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為國際法之權利義務主體的依據,恰恰是根源於西方世界的「文明」標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帝國」(empire)或「帝國的」(imperial)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雖然有著相同的字源,卻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意涵(Muthu, 2012: 4-6)。英文的empire源自拉丁文的imperio,原意是指最高治權或軍事統治。引用梅爾(Charles Maier, 2006: 24-25)的話來說:「帝國,就其古典意涵而言,通常被認為是,第一、藉著征服與脅迫擴大其控制;第二、控制其所征服之領地的忠誠。其或直接統治這些臣屬之地,或任命順從的讓在地領導者代其治理,但他們之間絕非是平等夥伴的結盟體系。」在「征服」的問題上,如一般所知,霍布斯的觀點具有開創性,影響深遠。不過,有待補充說明的是:到了18世紀,「帝國」的內涵開始出現轉變,由征服、占領,轉為因殖民、移居而對一群廣大土地進行控制,有時也意味著對貿易駐點的商業壟斷(亦即「商業帝國」)或對海外居民的間接統治(亦即「海洋帝國」)。舉例而言,雖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使用了「殖民」與「大英帝國」等字眼,但其內涵即與征服型帝國不同,甚至與我們今天所認定的「帝國主義」相去甚遠。正如其他主要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一詞也是在19世紀以後才流行開來的。就此而言,區辨「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內涵差異,可以幫助我們思索歐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歷史性轉向,進而挖掘許多18世紀的經典文本所蘊藏的反對帝國暴政的思想素材。
就「帝國主義」一詞的內涵來說,其在近代歐洲的普遍使用,多是指拿破崙在1804年稱帝之後,向歐洲各地與海外非歐洲地區推展的擴張主義。不過,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知識界來說,拿破崙以其軍事優勢為歐洲帶來的,不僅是帝國的擴張思維,更是一種足以顛覆長久以來歐洲社會崇敬的共和政體想像,進而致使各國走向民族國家體制的現代國際政治發展。在勃森(J. A. Hobson)的名著《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結尾處,便曾提到:「帝國主義是個墮落的民族生活選擇,是由貪求物豐和過去百年來追求動物性生存處境而展開的武力支配,這雙重自利的訴求造成。」(1902: 390)換言之,帝國主義的特色除了武力擴張、物質榨取之外,更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有關。然而,如果帝國主義的內涵,與民族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此語詞自然和「國際」一語相同,很難如實指稱19世紀以前的歐洲國家海外貿易與殖民行徑。
當然,從列寧的角度來說,雖然「帝國主義」一語是在19世紀才於英國廣泛使用,但他認為在16、17世紀英國伊莉莎白世代,「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一語便已廣泛為時人所用,而且此時的大英帝國已然具有武力擴張、物質榨取等特徵。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接受列寧所言,「帝國主義」作為一個常見語詞固然是在19世紀才成型,但其現實特徵卻可能早在16、17世紀便已見端倪。列寧的分析誠有其道理,但正如羅伯.楊(Robert Young, 2001: 110)所指出的,「對列寧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帝國主義描述的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個階段,而非跨歷史向度的政治與軍事支配作為。」因此,從本書涵蓋的時間與空間軸線來說,我們著眼的是「帝國主義」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的歐洲政治思想發展;這也就是說,探討「帝國」從武力征服到自由貿易的變化,仍為本書多數作者所共同關注者。不過,正因為帝國主義與帝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透過考察帝國,我們其實也為更進一步認識、分析帝國主義的發展,作了鋪墊。
延續這點來說,按一般分類,近代歐洲強權的海外霸業屬於「海洋帝國」的型態,而與傳統中國透過天下體系與朝貢制度所建立的「大陸帝國」有所差別。在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著名的定義上,大英帝國即標示著「自由、基督教、海洋、貿易」的特徵。在本書中,我們因此將結合下列四項要素來定義「帝國」:
(1)擁有相對「廣大」(large)的領土。
(2)一種「普遍」(universal)的信念。
(3)包含不同國家於其中,並由某一族群或部落來「統治」(rule over)其他族群或部落。
(4)此一統治事實通常是經由「征服」(conquest)而取得的(Pagden, 2015: 1)。
這一用法的好處是:只要略加修飾就可以適用於東亞傳統。換言之,帝國的「廣大」、「普遍」、對不同族群之「統治」等特徵,基本上相應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唯一顯著的差別可能是基於儒家傳統,天下體系認為以德服人在道德判斷上是高於窮兵黷武的,雖然在許多場合中戰爭仍是在所難免。持平而論,正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行並列,近代歐洲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歷史發展大抵上也是在普遍的正義原則與特殊的國家利益之間游蕩。在這點上,中西傳統似無決定性的差異。
目次
導論 在帝國主義之前 曾國祥、劉佳昊
01 帝國殖民與霍布斯 梁裕康
舊教-湯瑪斯式的殖民觀
新教-奧古斯丁式與伊莉莎白時期及詹姆士時期的殖民觀
霍布斯、開溫第士家族與維吉尼亞公司
霍布斯論征服
結語
02 格勞秀斯《論捕獲法》之政治論述發展 賴芸儀
前言
尼德蘭獨立運動與格勞秀斯政治論述的發展
《論捕獲法》內的政治論述建構
聖地牙哥號、聖卡特琳娜號兩案的影響
國家意志:為貿易發起正義戰爭
貿易自由:為建國與諸國達成同盟
結語
03 洛克:反奴隸的政治社會 陳禹仲
洛克的自由主義?
洛克與殖民批判
洛克與政治性
政治社會與規範情境
結語
04 亞當.斯密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 陳正國
導言
斯密論現代歐洲帝國的發生
巴本的帝國論:貿易、人民與國家
巴本、戴夫儂與政治經濟學帝國論
斯密的帝國論述
帝國正義與大英帝國的十字路口
結語
05 文明帝國vs.野蠻帝國:從社會情感觀點重建柏克的全球政治思想 曾國祥
導言
社會情感:基本觀點
社會情感:政治論述
文明帝國:追索全球正義
野蠻帝國:對帝國暴政的批判
結語
06 「自然非群性」的盧梭變奏:從共和帝國主義到共和邦聯 陳嘉銘
人文主義的戰爭思想與人的「自然非群性」
初探「自然非群性」:四種自然狀態
再探「自然非群性」:盧梭的思考與利用
共和國間的「自然非群性」:第五種自然狀態
結語
07 蹣跚徒行於荒野與田園之間:論邊沁的文明觀 陳建綱
研究緣起:約翰.彌爾是否誤解了邊沁
進步與改革是不同文明的共同課題
務實的法律完善論
結語:公眾啟蒙的未竟之路
08 「帝國主義的後設敘事?」:康德論文化、文明與世界公民法權 周家瑜
導論
康德論世界公民法權: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如何違反普遍的友善?
結語
09 天真的孔多塞?反思孔多塞的帝國思想 沈明璁
前言:天真的孔多塞?
一元論的孔多塞:柏林的觀點
自然主義、進步與文明
優越感的帝國主義的孔多塞:珍妮佛.皮茲的觀點
具多元論色彩的孔多塞?
追求不正義的孔多塞:帝國主義?
結語:另個角度看《進步》與孔多塞
10 自由主義式帝國主義作為提升人類文明的政治工程:彌爾的國際政治思想及其當代意涵 葉浩
前言
文明概念與大英帝國的天命
性格學與社會進步的定理
干預的條件,以及雙方的意願與意志
代議政府作為「最好的」體制,及其批評
結語
11 托克維爾論東方文明中的專制主義 許家豪
緒論
社會條件的平等:專制與民主
文明發展的進程與「必要性」
關於東方文明與專制帝國的思想史簡史
托克維爾眼中的東方文明、專制主義與停滯的帝國
結語:拒絕對人類絕望
12 黑格爾論市民社會、國家、民族與帝國 蕭高彥
前言:黑格爾與國家祕思
《法哲學原理》中的市民社會與國家
黑格爾的中介政治論:以等級概念為例
文明、帝國與歷史辯證
結語:從國家理性到理性國家
13 帝國的邊界:再論馬克思 萬毓澤
通過MEGA2,回到馬克思
帝國內與外(一):對《倫敦筆記》的「中間考察」
帝國內與外(二):「棉花帝國」下的美國資本主義與奴隸制
帝國內與外(三):南北戰爭與國際主義
結語
參考文獻
01 帝國殖民與霍布斯 梁裕康
舊教-湯瑪斯式的殖民觀
新教-奧古斯丁式與伊莉莎白時期及詹姆士時期的殖民觀
霍布斯、開溫第士家族與維吉尼亞公司
霍布斯論征服
結語
02 格勞秀斯《論捕獲法》之政治論述發展 賴芸儀
前言
尼德蘭獨立運動與格勞秀斯政治論述的發展
《論捕獲法》內的政治論述建構
聖地牙哥號、聖卡特琳娜號兩案的影響
國家意志:為貿易發起正義戰爭
貿易自由:為建國與諸國達成同盟
結語
03 洛克:反奴隸的政治社會 陳禹仲
洛克的自由主義?
洛克與殖民批判
洛克與政治性
政治社會與規範情境
結語
04 亞當.斯密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 陳正國
導言
斯密論現代歐洲帝國的發生
巴本的帝國論:貿易、人民與國家
巴本、戴夫儂與政治經濟學帝國論
斯密的帝國論述
帝國正義與大英帝國的十字路口
結語
05 文明帝國vs.野蠻帝國:從社會情感觀點重建柏克的全球政治思想 曾國祥
導言
社會情感:基本觀點
社會情感:政治論述
文明帝國:追索全球正義
野蠻帝國:對帝國暴政的批判
結語
06 「自然非群性」的盧梭變奏:從共和帝國主義到共和邦聯 陳嘉銘
人文主義的戰爭思想與人的「自然非群性」
初探「自然非群性」:四種自然狀態
再探「自然非群性」:盧梭的思考與利用
共和國間的「自然非群性」:第五種自然狀態
結語
07 蹣跚徒行於荒野與田園之間:論邊沁的文明觀 陳建綱
研究緣起:約翰.彌爾是否誤解了邊沁
進步與改革是不同文明的共同課題
務實的法律完善論
結語:公眾啟蒙的未竟之路
08 「帝國主義的後設敘事?」:康德論文化、文明與世界公民法權 周家瑜
導論
康德論世界公民法權: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如何違反普遍的友善?
結語
09 天真的孔多塞?反思孔多塞的帝國思想 沈明璁
前言:天真的孔多塞?
一元論的孔多塞:柏林的觀點
自然主義、進步與文明
優越感的帝國主義的孔多塞:珍妮佛.皮茲的觀點
具多元論色彩的孔多塞?
追求不正義的孔多塞:帝國主義?
結語:另個角度看《進步》與孔多塞
10 自由主義式帝國主義作為提升人類文明的政治工程:彌爾的國際政治思想及其當代意涵 葉浩
前言
文明概念與大英帝國的天命
性格學與社會進步的定理
干預的條件,以及雙方的意願與意志
代議政府作為「最好的」體制,及其批評
結語
11 托克維爾論東方文明中的專制主義 許家豪
緒論
社會條件的平等:專制與民主
文明發展的進程與「必要性」
關於東方文明與專制帝國的思想史簡史
托克維爾眼中的東方文明、專制主義與停滯的帝國
結語:拒絕對人類絕望
12 黑格爾論市民社會、國家、民族與帝國 蕭高彥
前言:黑格爾與國家祕思
《法哲學原理》中的市民社會與國家
黑格爾的中介政治論:以等級概念為例
文明、帝國與歷史辯證
結語:從國家理性到理性國家
13 帝國的邊界:再論馬克思 萬毓澤
通過MEGA2,回到馬克思
帝國內與外(一):對《倫敦筆記》的「中間考察」
帝國內與外(二):「棉花帝國」下的美國資本主義與奴隸制
帝國內與外(三):南北戰爭與國際主義
結語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帝國殖民與霍布斯
梁裕康(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在他於1629年翻譯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400 BC)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431 BC)之前,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仍是一位籍籍無名的文人,所以在此之前有關霍布斯的歷史紀錄十分有限。然而就在這段期間當中,霍布斯實際上涉入了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本文所嘗試要探討的,正是這段殖民經歷背後的思想爭論為何,以及其可能如何影響了霍布斯對帝國(empire)─特別是征服(conquest)這個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霍布斯的征服概念,又如何影響了日後大英帝國對外擴張的見解。
舊教-湯瑪斯式的殖民觀
根據安東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的分類,在16世紀晚期之後的近代(modern)歐洲,至少在劃定疆界(borders)的議題上,基督教可以分成舊教-湯瑪斯式(Catholic Thomist)與新教-奧古斯丁式(Protestant and Augustinian)二大陣營(Pagden, 2003: 122),另外理查.塔克(Richard Tuck)也有類似的分類。從15世紀末期歐洲人開始展開海外探險,並且促成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列強如何證成其對新世界(New World)的統治正當性成為一個新的而且急迫的議題(Pagden, 2015: 121-2)。最早從事海外探索的歐洲國家是葡萄牙王國(The Kingdom of Portugal),從1419年起「航海家」恩里克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 o Navegador,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開始,歷經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s-1524)成功穿越地中海與阿拉伯半島抵達印度,一躍成為歐洲最早的海上強權。在1452年時,同屬基督教徒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國王康世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1405-1453,又譯君士坦丁)請求教皇尼古拉五世出兵解救異教徒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包圍,尼古拉五世便在1452年下了一道名為「當不同之時」(Dum Diversas, while different)的教皇飭令(papal bull),授權葡萄牙國王「攻擊、征服,以及馴服薩拉森人(Saracens)、異教徒,以及其他他們所遭遇的任何基督敵人(Rodriguez, 1997: II, 469)」。
然而在此間其鄰國卡斯提爾王國(Corona de Castilla, The Crown of Castile)也開始海外拓展事業,因此逐漸與葡萄牙發生齟齬。與葡萄牙不同之處,在於卡斯提爾王國不僅止於獲取貿易商業利益與占領歐洲人已知的範圍,上述卡斯提爾王國所征服並且殖民的地區都位於新大陸,這是一個從未出現在歐洲人理解的世界範圍中的新領域。因此到了1520年代時,卡斯提爾王國開始意識到統治合法性的問題:雖然他們實際上(de facto)統治了這些新領土,但是他們並沒有辦法提出任何一種明確獨占統治此區域的主張。如此一來,卡斯提爾將很難行使排他性的統治與獨占此區域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卡斯提爾王國迫切地需要一種可以被證成的殖民論述。
針對這個問題,又被稱之為「經院哲學復興」(‘Second Scholasticism’)的西班牙薩拉曼加學派(School of Salamanca)創始人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 1483-1546)的若干觀點,為當時的西班牙所持的基本態度。他有時與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 1552-1608)跟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被並稱為「國際法之父」(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law),並曾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與西班牙國王的諮詢者。有意思的是,維多利亞在1504年成為天主教道明會修士(Dominican),而在他之後的道明會基本上認為西班牙征服美洲並不具有正當性。維多利亞本人大體上也持相同立場,因此在《線上版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中有關維多利亞的條目,一開始便稱他「以他抵抗西班牙殖民者而維護新世界中的印地安人的權利,以及他對有關義戰限制的看法而聞名(Hamilton, 2018)」。這種說法固然不能說錯,但卻過於簡略,畢竟如果維多利亞的論點是完全反對西班牙殖民美洲,就不可能被西班牙挪用為證成殖民美洲的論點。在他於1537到1539年間的三次演講中,維多利亞指出雖然美洲印地安人是異教徒,但是他們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以及其首領對部落的統治權都是無庸置疑的,不論是教皇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對此都不具正當權力,因此對其任何的侵害都是不正義的,從而否定教皇具有普及世界的權力(Dominium Mundi, dominion of world)。上述的說法與道明會觀點並無二致,可是除此之外,他卻指出有一種例外情況,是當這些美洲印地安人侵害了西班牙的合法權利時,西班牙就能征服其土地與財產(Vitoria, 1991: chaps 5, 6, 7)。正是這條但書,讓西班牙找到殖民美洲的理由。如同塔克所說,維多利亞出身反對西班牙殖民的道明會修士身分,反而讓他的論點深受官方信任(Tuck, 1999: 75),畢竟來自反方的證成顯得本身的立場更具說服力。派格登特別指出,雖然維多利亞等人都被泛稱為「神學家與法學家」,但實際上他們還是以神學家的身分為重。在近代初期,作為「科學之母」(mother of sciences)的神學,因為被認為是直接處理第一因(first causes)的學問,因此地位高於其他學科(其中當然包括法學)(Pagden, 2015: 46)。有關新世界的問題,被他們看作是有關「良知的事件」(a case of conscience),因此屬於「神學的爭議」(theological disputations)(Pagden, 2015: 48)。
作為最早海外殖民的二個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之間很快就面臨了利益衝突,特別是在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發現新大陸之後,二國間的衝突更形尖銳:如何分配新世界的利益。在1493年在西葡二個聲索國請求之下,教皇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 1431-1503),發布了統稱《贈與飭令》(Bulls of Donation)的三道教皇飭令,作為二國未來於新世界的劃界準則。然而根據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分類,維多利亞指出能證成西班牙統治新大陸的依據來自於《贈與飭令》,而《贈與飭令》若要生效,前提必須是教皇具有統治世界的權力,然而這種普世權力只能由對全人類都有效的法律中取得,其中可能的選項包括神聖法(divine law)、人類法(human law)中的市民法(civil law)或萬民法(ius gentium, law of nations),以及自然法(ius naturae, natural law)。可是,首先,當中的市民法不能適用,因為市民法並非普世法則,只適用於被統治轄區內的市民,對於從未被統治過的人民(也就是新大陸的印地安人)並無效力;其次、神聖法也無效,因為神聖法中從來沒有提到過美洲這個歐洲人未知的土地,遑論住在之上的人民(Vitoria, 1991: 264, 238)。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西班牙人還存有任何占有與統治新大陸的理由,就只能來自於自然法或萬民法。與教會法學家相比,根據他的新湯瑪斯主義式(neo-Thomasit)觀點,維多利亞不認為教會存在統治世界的合法權力,因此美洲不為教皇所轄,而是由美洲土著自行統治著。但是根據萬民法,美洲的原住民的確缺乏合法的領土治理權。
維多利亞真正的貢獻,在於他將萬民法與自然法並列於相當的位階。他認為在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3-1357)對萬民法的分類中,主要萬民法(ius gentium primaevum, primary law of nations)就是自然法,因為即使是異教徒,只要是人類─既然其具有理性─就能理解,因此「其自身就是公正的(equitable to itself)」。然而次要萬民法(ius gentium secundarium, secondary law of nations)與前者不同,其並非「自身就是公正的,而是透過具有理性的人所創造的(Vitoria, 1932: 89-90; 轉引自Pagden, 2015: 54)。」如派格登所說,維多利亞式的萬民法雖然是人類法,但是其具有相當於自然法的超然地位,因為其蘊含了如果每個人都能運用理性的話,那麼萬民法的內容必然會為所有人同意。在這個意義之下,萬民法產生了二個特點:一是與市民法不同,萬民法不需要一個實體的立法機關來立法,因為其效力是建築在所有人的理性之上;二是萬民法雖然保留自然法效力的普遍性,然而其內容卻不是僵固不變的;畢竟自然法針對的是一般性原則,而萬民法的標的物則是特定人類事物(Pagden, 2015: 54-5)。
在確定了萬民法的效力之後,維多利亞認為根據萬民法的內容,西班牙能以「捍衛無辜者」(the defence of the innocent)的原則,合理(而且合法)介入美洲事物。他認為在美洲存在殘暴的野蠻統治者或者法律時,西班牙可以正當地以「捍衛無辜者」的理由介入美洲。當時美洲印地安人最常被認為違反上述原則的罪行是活人獻祭(human sacrifice)與食人習俗(cannibalism)。維多利亞承認在其他地方(甚至歐洲)也會有類似的野蠻行為,但是二者的差別在於,在其他地方這些暴行視為法律所禁止─換句話說、符合萬民法,而在美洲這些暴行卻是其法律所認可而由國家所行使。
綜觀上述論點,維多利亞的新湯瑪斯式觀點,雖然教皇不是世界的統治者,因此西班牙也不能合法地從教皇那裡獲得統治新大陸與其上的原住民的統治權,但是西班牙卻能根據新湯瑪斯主義式的萬民法,對新大陸及其居民進行管轄。維多利亞所證成的萬民法,是奠基於人類的普遍理性,因此萬民法在假言的(hypothetical)層面上就能成立,而不像市民法需要真實的國家進行實際的立法工作。這裡隱含了存在一個超越在個別國家之上、以普遍理性為基礎的人類普遍道德實體。在美洲殖民的議題中,可以看到這個普遍道德實體化身為西班牙來行使其普遍權力。
梁裕康(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在他於1629年翻譯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400 BC)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431 BC)之前,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仍是一位籍籍無名的文人,所以在此之前有關霍布斯的歷史紀錄十分有限。然而就在這段期間當中,霍布斯實際上涉入了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本文所嘗試要探討的,正是這段殖民經歷背後的思想爭論為何,以及其可能如何影響了霍布斯對帝國(empire)─特別是征服(conquest)這個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霍布斯的征服概念,又如何影響了日後大英帝國對外擴張的見解。
舊教-湯瑪斯式的殖民觀
根據安東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的分類,在16世紀晚期之後的近代(modern)歐洲,至少在劃定疆界(borders)的議題上,基督教可以分成舊教-湯瑪斯式(Catholic Thomist)與新教-奧古斯丁式(Protestant and Augustinian)二大陣營(Pagden, 2003: 122),另外理查.塔克(Richard Tuck)也有類似的分類。從15世紀末期歐洲人開始展開海外探險,並且促成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列強如何證成其對新世界(New World)的統治正當性成為一個新的而且急迫的議題(Pagden, 2015: 121-2)。最早從事海外探索的歐洲國家是葡萄牙王國(The Kingdom of Portugal),從1419年起「航海家」恩里克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 o Navegador,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開始,歷經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s-1524)成功穿越地中海與阿拉伯半島抵達印度,一躍成為歐洲最早的海上強權。在1452年時,同屬基督教徒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國王康世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1405-1453,又譯君士坦丁)請求教皇尼古拉五世出兵解救異教徒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包圍,尼古拉五世便在1452年下了一道名為「當不同之時」(Dum Diversas, while different)的教皇飭令(papal bull),授權葡萄牙國王「攻擊、征服,以及馴服薩拉森人(Saracens)、異教徒,以及其他他們所遭遇的任何基督敵人(Rodriguez, 1997: II, 469)」。
然而在此間其鄰國卡斯提爾王國(Corona de Castilla, The Crown of Castile)也開始海外拓展事業,因此逐漸與葡萄牙發生齟齬。與葡萄牙不同之處,在於卡斯提爾王國不僅止於獲取貿易商業利益與占領歐洲人已知的範圍,上述卡斯提爾王國所征服並且殖民的地區都位於新大陸,這是一個從未出現在歐洲人理解的世界範圍中的新領域。因此到了1520年代時,卡斯提爾王國開始意識到統治合法性的問題:雖然他們實際上(de facto)統治了這些新領土,但是他們並沒有辦法提出任何一種明確獨占統治此區域的主張。如此一來,卡斯提爾將很難行使排他性的統治與獨占此區域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卡斯提爾王國迫切地需要一種可以被證成的殖民論述。
針對這個問題,又被稱之為「經院哲學復興」(‘Second Scholasticism’)的西班牙薩拉曼加學派(School of Salamanca)創始人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 1483-1546)的若干觀點,為當時的西班牙所持的基本態度。他有時與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 1552-1608)跟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被並稱為「國際法之父」(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law),並曾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與西班牙國王的諮詢者。有意思的是,維多利亞在1504年成為天主教道明會修士(Dominican),而在他之後的道明會基本上認為西班牙征服美洲並不具有正當性。維多利亞本人大體上也持相同立場,因此在《線上版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中有關維多利亞的條目,一開始便稱他「以他抵抗西班牙殖民者而維護新世界中的印地安人的權利,以及他對有關義戰限制的看法而聞名(Hamilton, 2018)」。這種說法固然不能說錯,但卻過於簡略,畢竟如果維多利亞的論點是完全反對西班牙殖民美洲,就不可能被西班牙挪用為證成殖民美洲的論點。在他於1537到1539年間的三次演講中,維多利亞指出雖然美洲印地安人是異教徒,但是他們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以及其首領對部落的統治權都是無庸置疑的,不論是教皇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對此都不具正當權力,因此對其任何的侵害都是不正義的,從而否定教皇具有普及世界的權力(Dominium Mundi, dominion of world)。上述的說法與道明會觀點並無二致,可是除此之外,他卻指出有一種例外情況,是當這些美洲印地安人侵害了西班牙的合法權利時,西班牙就能征服其土地與財產(Vitoria, 1991: chaps 5, 6, 7)。正是這條但書,讓西班牙找到殖民美洲的理由。如同塔克所說,維多利亞出身反對西班牙殖民的道明會修士身分,反而讓他的論點深受官方信任(Tuck, 1999: 75),畢竟來自反方的證成顯得本身的立場更具說服力。派格登特別指出,雖然維多利亞等人都被泛稱為「神學家與法學家」,但實際上他們還是以神學家的身分為重。在近代初期,作為「科學之母」(mother of sciences)的神學,因為被認為是直接處理第一因(first causes)的學問,因此地位高於其他學科(其中當然包括法學)(Pagden, 2015: 46)。有關新世界的問題,被他們看作是有關「良知的事件」(a case of conscience),因此屬於「神學的爭議」(theological disputations)(Pagden, 2015: 48)。
作為最早海外殖民的二個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之間很快就面臨了利益衝突,特別是在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發現新大陸之後,二國間的衝突更形尖銳:如何分配新世界的利益。在1493年在西葡二個聲索國請求之下,教皇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 1431-1503),發布了統稱《贈與飭令》(Bulls of Donation)的三道教皇飭令,作為二國未來於新世界的劃界準則。然而根據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分類,維多利亞指出能證成西班牙統治新大陸的依據來自於《贈與飭令》,而《贈與飭令》若要生效,前提必須是教皇具有統治世界的權力,然而這種普世權力只能由對全人類都有效的法律中取得,其中可能的選項包括神聖法(divine law)、人類法(human law)中的市民法(civil law)或萬民法(ius gentium, law of nations),以及自然法(ius naturae, natural law)。可是,首先,當中的市民法不能適用,因為市民法並非普世法則,只適用於被統治轄區內的市民,對於從未被統治過的人民(也就是新大陸的印地安人)並無效力;其次、神聖法也無效,因為神聖法中從來沒有提到過美洲這個歐洲人未知的土地,遑論住在之上的人民(Vitoria, 1991: 264, 238)。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西班牙人還存有任何占有與統治新大陸的理由,就只能來自於自然法或萬民法。與教會法學家相比,根據他的新湯瑪斯主義式(neo-Thomasit)觀點,維多利亞不認為教會存在統治世界的合法權力,因此美洲不為教皇所轄,而是由美洲土著自行統治著。但是根據萬民法,美洲的原住民的確缺乏合法的領土治理權。
維多利亞真正的貢獻,在於他將萬民法與自然法並列於相當的位階。他認為在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3-1357)對萬民法的分類中,主要萬民法(ius gentium primaevum, primary law of nations)就是自然法,因為即使是異教徒,只要是人類─既然其具有理性─就能理解,因此「其自身就是公正的(equitable to itself)」。然而次要萬民法(ius gentium secundarium, secondary law of nations)與前者不同,其並非「自身就是公正的,而是透過具有理性的人所創造的(Vitoria, 1932: 89-90; 轉引自Pagden, 2015: 54)。」如派格登所說,維多利亞式的萬民法雖然是人類法,但是其具有相當於自然法的超然地位,因為其蘊含了如果每個人都能運用理性的話,那麼萬民法的內容必然會為所有人同意。在這個意義之下,萬民法產生了二個特點:一是與市民法不同,萬民法不需要一個實體的立法機關來立法,因為其效力是建築在所有人的理性之上;二是萬民法雖然保留自然法效力的普遍性,然而其內容卻不是僵固不變的;畢竟自然法針對的是一般性原則,而萬民法的標的物則是特定人類事物(Pagden, 2015: 54-5)。
在確定了萬民法的效力之後,維多利亞認為根據萬民法的內容,西班牙能以「捍衛無辜者」(the defence of the innocent)的原則,合理(而且合法)介入美洲事物。他認為在美洲存在殘暴的野蠻統治者或者法律時,西班牙可以正當地以「捍衛無辜者」的理由介入美洲。當時美洲印地安人最常被認為違反上述原則的罪行是活人獻祭(human sacrifice)與食人習俗(cannibalism)。維多利亞承認在其他地方(甚至歐洲)也會有類似的野蠻行為,但是二者的差別在於,在其他地方這些暴行視為法律所禁止─換句話說、符合萬民法,而在美洲這些暴行卻是其法律所認可而由國家所行使。
綜觀上述論點,維多利亞的新湯瑪斯式觀點,雖然教皇不是世界的統治者,因此西班牙也不能合法地從教皇那裡獲得統治新大陸與其上的原住民的統治權,但是西班牙卻能根據新湯瑪斯主義式的萬民法,對新大陸及其居民進行管轄。維多利亞所證成的萬民法,是奠基於人類的普遍理性,因此萬民法在假言的(hypothetical)層面上就能成立,而不像市民法需要真實的國家進行實際的立法工作。這裡隱含了存在一個超越在個別國家之上、以普遍理性為基礎的人類普遍道德實體。在美洲殖民的議題中,可以看到這個普遍道德實體化身為西班牙來行使其普遍權力。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