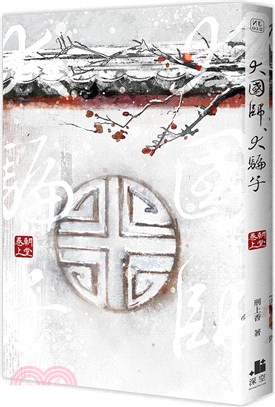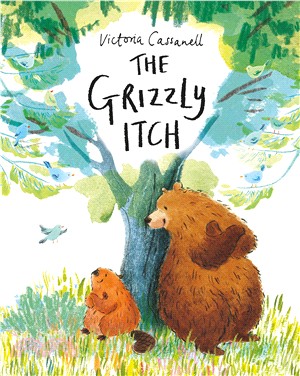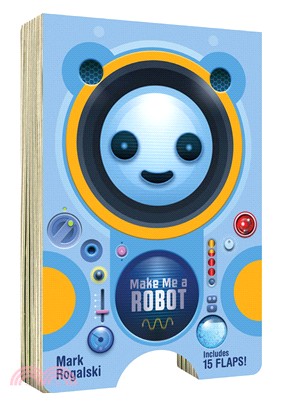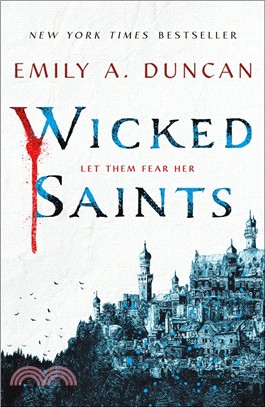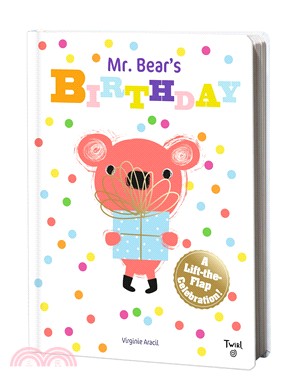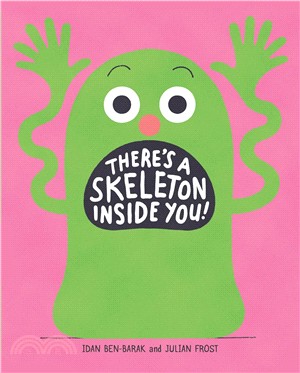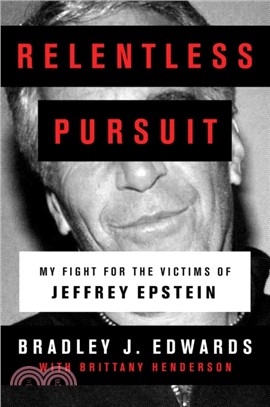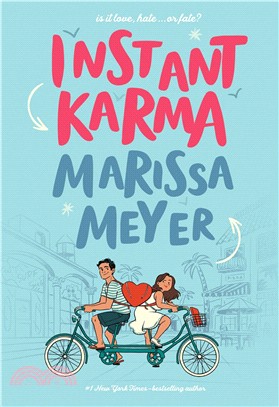定價
:NT$ 350 元優惠價
:85 折 297 元
促銷優惠
:特殊書展庫存:1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8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 古風耽美作者 刑上香 經典之作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 特邀古風水彩繪師 慕容緋潔 繪製絕美封面
◆ 古風耽美作者 刑上香 經典之作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 特邀古風水彩繪師 慕容緋潔 繪製絕美封面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執著難捨,
孰料愛恨竟是一場大夢……
姬雲羲站在原地,神色依然迷濛,一雙眼卻帶著隱約的寒光。
「你不是宋玄。」
那人上前兩步,低低地笑了起來,眼眸色彩逐漸變化,竟然成了琉璃珠兒樣的色彩。
他的輪廓身影,在姬雲羲的面前逐漸模糊,
只剩下那一雙譎異莫測的眼眸,彷彿來自深淵的怪物,正遙遙地向他召喚。
一別數年,宋玄終是回到盛京,
坐上了那他曾百般抗拒的國師之位。
只因在這廟堂之上,
有著他忘不了的人,有著他一路顛沛都未能放下的牽掛。
六年前他狼狽遠走,
六年後,竟是再也逃不出姬雲羲以愛織就的牢籠。
可那逐漸明朗的心跡,
卻在朝中眾臣與南圖祭司的設計下被殘忍湮滅。
失去記憶,讓姬雲羲做回了陰鷙殘酷的帝王,
但在他內心深處,
那模糊溫暖的身影又時時刻刻灼燒著他,
教他愛不得,卻又割捨不下……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 特邀古風水彩繪師 慕容緋潔 繪製絕美封面
◆ 古風耽美作者 刑上香 經典之作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 特邀古風水彩繪師 慕容緋潔 繪製絕美封面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執著難捨,
孰料愛恨竟是一場大夢……
姬雲羲站在原地,神色依然迷濛,一雙眼卻帶著隱約的寒光。
「你不是宋玄。」
那人上前兩步,低低地笑了起來,眼眸色彩逐漸變化,竟然成了琉璃珠兒樣的色彩。
他的輪廓身影,在姬雲羲的面前逐漸模糊,
只剩下那一雙譎異莫測的眼眸,彷彿來自深淵的怪物,正遙遙地向他召喚。
一別數年,宋玄終是回到盛京,
坐上了那他曾百般抗拒的國師之位。
只因在這廟堂之上,
有著他忘不了的人,有著他一路顛沛都未能放下的牽掛。
六年前他狼狽遠走,
六年後,竟是再也逃不出姬雲羲以愛織就的牢籠。
可那逐漸明朗的心跡,
卻在朝中眾臣與南圖祭司的設計下被殘忍湮滅。
失去記憶,讓姬雲羲做回了陰鷙殘酷的帝王,
但在他內心深處,
那模糊溫暖的身影又時時刻刻灼燒著他,
教他愛不得,卻又割捨不下……
作者簡介
刑上香
產地遼寧,一臺半舊不新的故事製造機。
國家一級火鍋愛好者,日常沉迷遊戲漫畫,是個熱衷於製造故事的超級懶鬼。
夢想是可以製造出不需要動手動嘴的溝通機器,把腦洞揉揉捏捏直連給讀者大腦共享快樂。
慕容緋潔(繪者)
自由接案插畫家,專精水彩與半厚塗電繪,近期偏好古風類型的設計,一名遊戲深坑人。
產地遼寧,一臺半舊不新的故事製造機。
國家一級火鍋愛好者,日常沉迷遊戲漫畫,是個熱衷於製造故事的超級懶鬼。
夢想是可以製造出不需要動手動嘴的溝通機器,把腦洞揉揉捏捏直連給讀者大腦共享快樂。
慕容緋潔(繪者)
自由接案插畫家,專精水彩與半厚塗電繪,近期偏好古風類型的設計,一名遊戲深坑人。
目次
第二十一章 驚醒
第二十二章 春水
第二十三章 祕密
第二十四章 無窮
第二十五章 孽障
第二十六章 心悅
第二十七章 渴求
第二十八章 朝顏
第二十九章 金鞭
第三十章 參天
第二十二章 春水
第二十三章 祕密
第二十四章 無窮
第二十五章 孽障
第二十六章 心悅
第二十七章 渴求
第二十八章 朝顏
第二十九章 金鞭
第三十章 參天
書摘/試閱
第二十一章 驚醒
姬回在一個冬日死去了。
人們將帝王死去稱為「山陵崩」,以形容其逝去之影響甚鉅。可姬回的死,對於一名帝王來說卻著實有些平淡。
眾臣對他的離去早有準備,廢太子姬雲弈自縊那年,姬回就已是一具被丹藥掏空的空殼,卻仍固執地不肯停用丹藥。
終於在某日早上,姬回再也沒有醒來。
大臣們按部就班地處理好了一切,萬民號哭,天下縞素,寺觀鐘聲長鳴,群臣長跪不起,心裡卻清楚,這為時七年的暗流洶湧,終於在這一刻塵埃落定。
最終能夠坐上那張椅子的人,只有一個。
是七年前,所有人都沒想到的那個人。
姬雲羲。
姬回駕崩三日後,四方城在鵝毛大雪中迎來一位舊友。
那是一位穿著石青色道袍、披著牙白斗篷的男子。他的臉隱匿在兜帽之下,左手抱著拂塵,右手提著一罈冷酒,頭上身上都落滿了雪花,踩著厚厚的積雪,一步一步走到了花下樓後頭。
皇帝駕崩,舉國服喪,昔日歌舞不休的花下樓如今也是門庭冷落,一派淒涼。
男子敲了敲花下樓的後門。過了許久,才傳來一聲女人的怒吼:「敲什麼敲!這個月不做生意!回去找自己婆娘吧!」
男子笑了起來,「不是來夜宿的。」
「喝酒也不成!」
裡頭傳來了重重的腳步聲,緊接著是乒乒乓乓東西落地的聲音,女人打開門,張嘴便罵:「大清早的來……」
她的話還沒說完,就瞪大了雙眼,嘴巴也合不攏,動了動唇,才發出兩個音節來:「……宋玄?」
對面的男子將兜帽脫下,露出那溫潤如玉的面孔,正是消失了多年的宋玄。
「想容,好久不見。」
門內的女人已經愣住了。
宋玄抖了抖身上的積雪,露出笑容,「不請我進去?」
「宋玄,你……」想容呆呆地瞧著他,遲疑了片刻,第一反應竟是抄起閂門用的棍子,劈頭蓋臉便要打,「你還知道回來?!我打死你這無情無義的東西──」
宋玄連忙跳進門裡頭,三步併作兩步地往裡逃,想容在後頭一路狂追,將人硬是逼到了死角。
宋玄見實在逃不掉,才伸手去奪想容手中的棍子,腆著臉笑道:「好姑娘,我在雪裡頭凍了大半日,連皮肉都凍脆生了,妳這一棍子下來,還不把我砸碎了?」
想容氣得跳腳,「我就該砸你個筋斷骨折才是,你還有臉回來?一走就是六年,連個信兒都沒有,我還以為你死在哪了──」
這話原是怨婦的腔調,可從想容嘴裡說出來,反倒像賭場逼債的惡棍。
宋玄乾笑一聲,「一言難盡,這些年讓人四處追債,實在不敢貿然回來,生怕將妳也連累了。」
想容冷哼一聲,不肯相信他的鬼話,神色卻終究是略微緩和了,讓開半個身子,讓他到屋裡,「先進來再說吧,我幫你找點吃的去。」
宋玄叫住了她,將手上一直提著的冷酒遞過去,「順道幫我熱熱吧。」
想容接過酒,嗅了嗅,「哪裡弄來的好酒?說好了啊,見一面,分一半。」
宋玄搖了搖頭,笑著說:「下次再尋好的給妳,這酒可不行。」
想容貪圖酒香又嗅了兩下,「小氣,我給你銀子就是了。」
「這酒是拿來祭奠一位朋友的。」宋玄說。
想容愣了愣,終究什麼話都沒說,出去熱酒去了。
宋玄獨自坐在房間裡,將斗篷脫了,抖乾淨殘餘的雪,又將手中的拂塵放到一邊,正對上一面銅鏡。
裡頭模模糊糊的還是他那張臉,六年的時光似乎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跡。
他還是那個來去如風、孑然一身的宋玄。
但似乎又有什麼變了,讓二十七歲的宋玄,越發地溫柔隨和起來。
過了一會,想容抱著熱酒進來,見宋玄正站在鏡子前,忍不住嘲笑:「一把年紀的老男人,還照什麼鏡子。」
宋玄笑道:「老男人才要照鏡子,否則邋裡邋遢,更是討不到婆娘了。」
想容忍不住問:「你還沒成家?」
宋玄搖了搖頭。
二十七歲,還沒成家,這放在整個大堯似乎都極為罕見。
他這六年來走南闖北,連同行都忍不住同情他,要給他介紹一兩個溫柔穩重的姑娘,好讓他安頓下來。
可宋玄似乎一直在本能地抗拒著什麼。
宋玄搖了搖頭,嘆息一聲。
他斟了一杯酒給自己,又斟了一杯放到對面。酒水順著胃腸流下去,連帶著身體也暖了起來。
想容有些好奇,忍不住問:「這是個什麼朋友?」
宋玄想了想,才回答:「是一個有很多祕密、說話很靈驗的朋友。」
想容有些好奇,「比你還靈驗嗎?」
「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他想到了。妳說靈不靈驗?」宋玄笑著說。
想容點了點頭,「那確實是厲害。」
「這樣厲害的人吶……」宋玄盯著那滿滿的酒盞,忍不住有些茫然。
在知道姬回死去的那一刻,宋玄才清晰地意識到。
真的已經過去六年了。
他四處漂泊,仍是那個招搖撞騙的宋半仙,只不過每天遇見的都是陌生的風景、陌生的人。
當變化已經成了慣常,也就意識不到歲月的流逝了。
只有偶爾聽到朝堂那邊的傳聞,才能意會到時移境遷。
太子每況愈下,姬雲羲如日中天,方秋棠趁勢崛起,朝堂上的交鋒隱約可見,明明是熟悉的名字,可落在傳聞中,卻成了陌生的故事。
若說自在,似乎也是自在的,他是天生的市井逍遙客,鎮日遊歷四方、看盡世間百態,又怎麼會不快活?
只是在這自在快活之中,似乎又有什麼不一樣了。
他逃了六年,仍是沒有讓自己那顆心安定下來,反而越發焦躁不安。
彷彿有什麼東西,一直埋在他的心底,總是牽掛著,卻遲遲沒有得到答案。
如今姬回走了,他竟有一種夢中驚醒的錯覺。
有什麼,正悄悄地發生改變。
及至三月,草長鶯飛,按大堯律,國喪過了百日,平民百姓間便一切如常,婚喪嫁娶,諸多不忌,連帶著四方城的說書先生都活絡了起來。
「說起某朝某代,有這樣一位殿下──」
四方城裡的說書先生總是有最新奇的故事。
諸如兩年前講的是某朝太子無德自縊而亡,四年前講的是某國帝王長子為愛私奔,七年前講的是某位皇子死而復生。
而近來最新鮮的故事,也就是先帝故去許久,眾臣三請三辭,繼承人仍不肯登基的故事。
而依著四方城的規矩,這某朝某代某國某人,也不過就是今時今日此地此事。
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聽著聽著也就明白了。
只不過這些胡編亂造的故事,只怕是兩分真、八分假,虛虛實實,就是聽個熱鬧罷了。
諸如宋玄,早見識過這些說書先生天馬行空的本事,是以並不將這些故事放在心上。
反倒是一邊的想容聽得入神,一邊喝著茶一邊問:「他們說的是真的?這大堯當真有什麼龍鼎?要挖出來皇帝才能登基?」
「他們敢說,妳就敢信?」宋玄忍不住笑了,「聽他們的,妳連年都能過錯。」
想容踹他一腳,「就你是明白人,你有本事,你倒是給我說說看?」
宋玄自顧自地喝茶,「皇帝老兒的事情,我們哪能知道。」
想容嘀咕了一句:「就是好奇而已,那椅子不都爭著搶著坐嗎?現在倒好,椅子洗乾淨了,就差一個屁股,反倒不去坐了。」
宋玄聽了好笑,也不去詳細解釋。
自姬回殯天已過了三月有餘,宋玄便在這四方城滯留了三個多月,深居簡出,只偶爾與想容一道吃茶談天,儼然成了一名養老的鄉紳。
說來也怪,前些年宋玄還是個停不住腳步的傢伙,這陣子竟是莫名安生下來了。
大抵是走得多了,走得累了,總要找個地方歇歇腳。
四方城最大的好處就是消息靈通,姬雲羲遲遲不肯登基稱帝,也是讓宋玄頗為費解。
按例,過了百日,群臣三請三辭,姬雲羲早就該走馬上任,坐上那天下至尊的位置,可直到如今,官府都沒有下發告示,民間對於姬雲羲的稱呼,也遲遲停在「三殿下」。
倒是引來了無數離奇荒謬的故事。
這邊正說著,忽地聽見一聲喧鬧,外頭竟湧進了一群官兵。
宋玄和想容俱是回頭去看,便瞧見一個衣著華貴、面容姣好的男子,正大步流星地踏進來,用下巴尖朝著那說書人,「我聽聞這裡有人妄議朝廷,果然如此。」
宋玄微微一愣,仔細去瞧那男子的眉眼,是個不曾見過的陌生面孔。
妄議朝廷,這天大的一頂帽子說書人哪裡敢接,也沒弄清來人是誰,只曉得這些都是官府的官兵,連連告饒,連茶樓的老闆也出來說情。
「把人帶走,店給我砸了。」那男子卻趾高氣揚地喝罵,一副有恃無恐、盛氣凌人的樣子。「若是再讓本公子聽見你們胡說八道,有你們的好看。」
那男子旁邊跟著的官兵頭子倒也是宋玄的熟人──趙捕快,聽聞男子要砸店,忍不住勸了什麼。
「怎麼?本公子說話不好用?我說讓你砸,你就給我砸。」男子冷笑一聲。「區區一個捕快,難道要反了不成?」
這男子身分不明,帽子卻扣得一頂比一頂大,嚇得那趙捕快閉了嘴,一眾官兵將吃茶的客人驅趕出去,抄起桌上的碗碟杯筷一氣兒亂砸。一時之間,只能聽見那茶館老闆焦急的勸阻聲,和瓷器破碎、桌椅翻倒的響聲。
眾多客人不知其中緣由,生怕惹禍上身,紛紛避退,只有宋玄忍不住瞧了一眼,低聲問想容:「這又是哪路的神仙,我離了四方城這些時候,竟連天都變了不成?」
「小聲點。」想容用手肘大力戳了戳他。
宋玄被這一下頂得沒防備,連連咳嗽,險些連方才吃進肚的茶點都吐了出來。
想容大大咧咧地拍了拍他的後背,「這是兩個月前來的神仙,人都稱他南榮君,你還不知道?」
「南榮君?」宋玄微微在腦子裡過了一遍,九流三教,確實都沒這樣一個名號,這才搖了搖頭。「是外城來的?」
「盛京來的。」想容壓低了聲音,「我聽客人說,這小子是三殿下的親信。」
宋玄微微一愣,「什麼?」
現在人們口中的三殿下,只能是姬雲羲一個人。
想容並不大清楚宋玄當年的舊事,也不太明白他跟姬雲羲的糾葛,只當他是好奇。
「就是現在那個三殿下,南榮君是他身邊的人。聽說是來替那勞什子三殿下辦事的,整日裡正事沒見他做一件,斂財滋事倒沒少幹,上頭那幫官員都瘋了似地向他送禮走門路──」
宋玄不知怎麼,彷彿有些走神,「走什麼門路?」
「走三殿下的門路啊!你不是傻了吧?」想容奇道,「先皇三個兒子,一個失蹤,一個自縊。現在連三歲小兒都知道,那位置鐵板釘釘,就是那三殿下的了。官員不趁著現在走門路,還什麼時候走?」
宋玄敷衍地點點頭。
他在聽到事關姬雲羲的時候,神思就已經飄忽到不知哪兒去了,連帶著後頭想容的話,一個字兒都沒聽進腦子裡。
他沉默了一會,忽地想起了什麼:「他是替姬雲羲來辦什麼事的?」
「這誰知道,我是沒看出來他有什麼事。」想容皺著眉道:「我只知道,這南榮君果真不是個省油的燈,早些弄完早些滾蛋才是,別再來禍害這四方城了。」
宋玄想到方才那人的情態,忍不住微微皺了眉頭。
阿羲的親信,竟是這樣的人嗎?
連宋玄也沒想到,這個南榮君會在四方城掀起這樣大的波瀾。
四方城的地上地下兩套班子,官家與八門之間相互勾結,魚龍混雜、深淺難測,算得上一個凶險的地界。
就算上頭偶爾有欽差來訪,也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只要面子給足、禮數送到,便也就那麼回事了。
不想這南榮君卻是個貪心不足、膽大包天的人物,這幾日裡仗著三殿下的名號,在四方城攪風攪雨,專挑做生意的平頭百姓坑害。
他找盡理由,從妄議朝政到窩藏賊贓,有的沒的都拿出來,一氣兒封了十餘家店鋪。只等著人送銀兩去才肯鬆口,一副擺明了要斂財的嘴臉。便宜些的便是破財消災,運氣差些的被扣了親眷,為贖回家人搞得散盡家財。
這樣一來,竟逼得不少店鋪關門歇業,只等著這一波過去。
「官府也不管?」想容生來便有幾分俠義心腸,如今聽了這事更是生氣。「什麼狗屁南榮君,聽都沒聽過的東西,也敢在四方城撒野。」
「早有人去問過上頭了,這人是三殿下的人,官府那邊也沒什麼法子,都是哄著捧著的。」常雨將茶水一放,也是愁眉苦臉。
他是來替人送貨的。這些日子他們兄弟倆的賭場為避風頭,也是關了門。兄弟兩個為了賺口飯吃,也是什麼零工都做起來了。
區區一個南榮君,竟攪得四方城百業蕭條,這是眾人都沒有想到的。
宋玄聽聞此言,忍不住轉了目光,「當真是三殿下的人?你可曾打聽過嗎?」
常雨笑道:「聽官府那頭說,這南榮君手上有三殿下的信物,且是幫三殿下來尋龍鼎的。」
宋玄皺著眉,「龍鼎?真有這麼個東西?」那不是那些說書人編出來的?
「管它是不是真的。就現在這個架勢,三殿下要尋,那就是沒有也得有。」常雨壓低了聲音,靠近宋玄低聲說,「而且,您有所不知,我聽人家說,這個南榮君和三殿下,是那個關係。」
他掐了掐小指,比劃了一個齷齪的動作。
想容見了便一腳踹翻他的凳子,讓常雨直接一屁股坐地上去了,「哎呦哎呦」叫個沒完。
「在我這兒胡扯什麼玩意?」想容見這男人齷齪的表情,滿臉嫌棄。
常雨哭喪著臉,「這也不是我說的,是南榮君自己透露的。」
宋玄盯著常雨,眉頭越皺越緊,眼神凝重,「此話當真?」
「八九不離十,」常雨見宋玄有興趣,愈加高興,也不嫌屁股疼了,拖著凳子就湊到宋玄邊上嚼舌頭,「你想啊,打這兒之前,南榮君可是連聽都沒聽過的一個人。盛京裡大小官員幕僚,就是天師也是成群結隊的,憑什麼讓他來尋龍鼎?可不就是枕邊關係,最讓人親近信任嗎?再者,這三殿下如今也二十有二了,連側妃都沒有一個。若不是不行,那只怕志不在此啊。」
砰──
常雨這回又摔地上了,抬頭一看,竟是宋玄將他的凳子踹翻的。
「宋先生這是做什麼?」常雨哭喪著一張臉,嚷嚷起來。
想容在邊上幸災樂禍,「你宋先生可是二十有七,也沒見娶個媳婦兒,這是被戳到痛處了。」
常雨這才意識到自己言多必失,嘿嘿地笑著圓話:「先生不一樣,先生是半仙兒,清心寡欲超凡脫俗,哪能看得上庸脂俗粉呢。」
想容嗤之以鼻,「油嘴滑舌。」
宋玄神色淡淡,心裡卻是憑生波瀾,分明知道此事與自己無關,卻又忍不住在意。
「總之且瞧著吧,這南榮君一日不走,咱們四方城就一日太平不下來。」常雨下了定論,又蹭了想容半壺茶水,才顛顛兒地從後門走了。
想容見宋玄半晌無話,大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想什麼呢?」
宋玄被拍得一哆嗦,忙從自己的思緒中回過神來,隨口道:「沒什麼,只是在想這個南榮君,讓他這樣興風作浪,也不是個事兒。」
想容登時瞪大眼睛,「你也這樣覺得?」
宋玄看她這表情,就知道她又想管閒事了。
這人就是一顆天生的俠義心腸,見到不平之事總想摻合兩下。上回打從茶樓回來,她就天天惦記著,只是沒說出來罷了。
果然,想容做賊似地把門關上,一雙圓眼滴溜溜地轉,拉著他道:「前兩日還有客人跟我問起你,想託你去打探南榮君的底細,我曉得你那三不沾的規矩,才幫你回了。你若也瞧那南榮君不順眼,這倒是個好機會──」
宋玄聽了便問:「什麼客人?」
想容低低地比劃了一下,「無非是三爺他們那幫子人。」
宋玄一聽便明白,四方城地下掌舵的那幾位他也都見過,現在領頭的那位姓傅,外號三爺,是個一等一的狠角色。
當初季硝頭腦機敏,又背靠大山,這才壓了他們一頭。自打幾年前季硝追著方秋棠去了京城,轉移了生意重心,這四方城就成了三爺的半個天下。
如今見這南榮君囂張,官府不敢管,三爺卻不可能坐視不理。他顯然是想出手干預,卻又摸不清底細,算來算去,才找到了宋玄的頭上。
宋玄回來的消息,知道的人不多,但對於這些掌舵人來說,只怕並不是個祕密。
宋玄猶豫了片刻,沒有應聲。
想容以為他不願意,便道:「你若不想去,當我沒說過就是了,也不是什麼大事。」
宋玄不沾黨政權謀,想容也明白他的用意,行走江湖想要保命,這樣的渾水蹚得越少越好。
「妳去聯繫他吧,」宋玄忽地說,「就說這事我應承了,記得欠我一回情。」
想容一愣,「當真?」
宋玄點了點頭。
他倒是真的想會會這南榮君。
姬回在一個冬日死去了。
人們將帝王死去稱為「山陵崩」,以形容其逝去之影響甚鉅。可姬回的死,對於一名帝王來說卻著實有些平淡。
眾臣對他的離去早有準備,廢太子姬雲弈自縊那年,姬回就已是一具被丹藥掏空的空殼,卻仍固執地不肯停用丹藥。
終於在某日早上,姬回再也沒有醒來。
大臣們按部就班地處理好了一切,萬民號哭,天下縞素,寺觀鐘聲長鳴,群臣長跪不起,心裡卻清楚,這為時七年的暗流洶湧,終於在這一刻塵埃落定。
最終能夠坐上那張椅子的人,只有一個。
是七年前,所有人都沒想到的那個人。
姬雲羲。
姬回駕崩三日後,四方城在鵝毛大雪中迎來一位舊友。
那是一位穿著石青色道袍、披著牙白斗篷的男子。他的臉隱匿在兜帽之下,左手抱著拂塵,右手提著一罈冷酒,頭上身上都落滿了雪花,踩著厚厚的積雪,一步一步走到了花下樓後頭。
皇帝駕崩,舉國服喪,昔日歌舞不休的花下樓如今也是門庭冷落,一派淒涼。
男子敲了敲花下樓的後門。過了許久,才傳來一聲女人的怒吼:「敲什麼敲!這個月不做生意!回去找自己婆娘吧!」
男子笑了起來,「不是來夜宿的。」
「喝酒也不成!」
裡頭傳來了重重的腳步聲,緊接著是乒乒乓乓東西落地的聲音,女人打開門,張嘴便罵:「大清早的來……」
她的話還沒說完,就瞪大了雙眼,嘴巴也合不攏,動了動唇,才發出兩個音節來:「……宋玄?」
對面的男子將兜帽脫下,露出那溫潤如玉的面孔,正是消失了多年的宋玄。
「想容,好久不見。」
門內的女人已經愣住了。
宋玄抖了抖身上的積雪,露出笑容,「不請我進去?」
「宋玄,你……」想容呆呆地瞧著他,遲疑了片刻,第一反應竟是抄起閂門用的棍子,劈頭蓋臉便要打,「你還知道回來?!我打死你這無情無義的東西──」
宋玄連忙跳進門裡頭,三步併作兩步地往裡逃,想容在後頭一路狂追,將人硬是逼到了死角。
宋玄見實在逃不掉,才伸手去奪想容手中的棍子,腆著臉笑道:「好姑娘,我在雪裡頭凍了大半日,連皮肉都凍脆生了,妳這一棍子下來,還不把我砸碎了?」
想容氣得跳腳,「我就該砸你個筋斷骨折才是,你還有臉回來?一走就是六年,連個信兒都沒有,我還以為你死在哪了──」
這話原是怨婦的腔調,可從想容嘴裡說出來,反倒像賭場逼債的惡棍。
宋玄乾笑一聲,「一言難盡,這些年讓人四處追債,實在不敢貿然回來,生怕將妳也連累了。」
想容冷哼一聲,不肯相信他的鬼話,神色卻終究是略微緩和了,讓開半個身子,讓他到屋裡,「先進來再說吧,我幫你找點吃的去。」
宋玄叫住了她,將手上一直提著的冷酒遞過去,「順道幫我熱熱吧。」
想容接過酒,嗅了嗅,「哪裡弄來的好酒?說好了啊,見一面,分一半。」
宋玄搖了搖頭,笑著說:「下次再尋好的給妳,這酒可不行。」
想容貪圖酒香又嗅了兩下,「小氣,我給你銀子就是了。」
「這酒是拿來祭奠一位朋友的。」宋玄說。
想容愣了愣,終究什麼話都沒說,出去熱酒去了。
宋玄獨自坐在房間裡,將斗篷脫了,抖乾淨殘餘的雪,又將手中的拂塵放到一邊,正對上一面銅鏡。
裡頭模模糊糊的還是他那張臉,六年的時光似乎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跡。
他還是那個來去如風、孑然一身的宋玄。
但似乎又有什麼變了,讓二十七歲的宋玄,越發地溫柔隨和起來。
過了一會,想容抱著熱酒進來,見宋玄正站在鏡子前,忍不住嘲笑:「一把年紀的老男人,還照什麼鏡子。」
宋玄笑道:「老男人才要照鏡子,否則邋裡邋遢,更是討不到婆娘了。」
想容忍不住問:「你還沒成家?」
宋玄搖了搖頭。
二十七歲,還沒成家,這放在整個大堯似乎都極為罕見。
他這六年來走南闖北,連同行都忍不住同情他,要給他介紹一兩個溫柔穩重的姑娘,好讓他安頓下來。
可宋玄似乎一直在本能地抗拒著什麼。
宋玄搖了搖頭,嘆息一聲。
他斟了一杯酒給自己,又斟了一杯放到對面。酒水順著胃腸流下去,連帶著身體也暖了起來。
想容有些好奇,忍不住問:「這是個什麼朋友?」
宋玄想了想,才回答:「是一個有很多祕密、說話很靈驗的朋友。」
想容有些好奇,「比你還靈驗嗎?」
「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他想到了。妳說靈不靈驗?」宋玄笑著說。
想容點了點頭,「那確實是厲害。」
「這樣厲害的人吶……」宋玄盯著那滿滿的酒盞,忍不住有些茫然。
在知道姬回死去的那一刻,宋玄才清晰地意識到。
真的已經過去六年了。
他四處漂泊,仍是那個招搖撞騙的宋半仙,只不過每天遇見的都是陌生的風景、陌生的人。
當變化已經成了慣常,也就意識不到歲月的流逝了。
只有偶爾聽到朝堂那邊的傳聞,才能意會到時移境遷。
太子每況愈下,姬雲羲如日中天,方秋棠趁勢崛起,朝堂上的交鋒隱約可見,明明是熟悉的名字,可落在傳聞中,卻成了陌生的故事。
若說自在,似乎也是自在的,他是天生的市井逍遙客,鎮日遊歷四方、看盡世間百態,又怎麼會不快活?
只是在這自在快活之中,似乎又有什麼不一樣了。
他逃了六年,仍是沒有讓自己那顆心安定下來,反而越發焦躁不安。
彷彿有什麼東西,一直埋在他的心底,總是牽掛著,卻遲遲沒有得到答案。
如今姬回走了,他竟有一種夢中驚醒的錯覺。
有什麼,正悄悄地發生改變。
及至三月,草長鶯飛,按大堯律,國喪過了百日,平民百姓間便一切如常,婚喪嫁娶,諸多不忌,連帶著四方城的說書先生都活絡了起來。
「說起某朝某代,有這樣一位殿下──」
四方城裡的說書先生總是有最新奇的故事。
諸如兩年前講的是某朝太子無德自縊而亡,四年前講的是某國帝王長子為愛私奔,七年前講的是某位皇子死而復生。
而近來最新鮮的故事,也就是先帝故去許久,眾臣三請三辭,繼承人仍不肯登基的故事。
而依著四方城的規矩,這某朝某代某國某人,也不過就是今時今日此地此事。
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聽著聽著也就明白了。
只不過這些胡編亂造的故事,只怕是兩分真、八分假,虛虛實實,就是聽個熱鬧罷了。
諸如宋玄,早見識過這些說書先生天馬行空的本事,是以並不將這些故事放在心上。
反倒是一邊的想容聽得入神,一邊喝著茶一邊問:「他們說的是真的?這大堯當真有什麼龍鼎?要挖出來皇帝才能登基?」
「他們敢說,妳就敢信?」宋玄忍不住笑了,「聽他們的,妳連年都能過錯。」
想容踹他一腳,「就你是明白人,你有本事,你倒是給我說說看?」
宋玄自顧自地喝茶,「皇帝老兒的事情,我們哪能知道。」
想容嘀咕了一句:「就是好奇而已,那椅子不都爭著搶著坐嗎?現在倒好,椅子洗乾淨了,就差一個屁股,反倒不去坐了。」
宋玄聽了好笑,也不去詳細解釋。
自姬回殯天已過了三月有餘,宋玄便在這四方城滯留了三個多月,深居簡出,只偶爾與想容一道吃茶談天,儼然成了一名養老的鄉紳。
說來也怪,前些年宋玄還是個停不住腳步的傢伙,這陣子竟是莫名安生下來了。
大抵是走得多了,走得累了,總要找個地方歇歇腳。
四方城最大的好處就是消息靈通,姬雲羲遲遲不肯登基稱帝,也是讓宋玄頗為費解。
按例,過了百日,群臣三請三辭,姬雲羲早就該走馬上任,坐上那天下至尊的位置,可直到如今,官府都沒有下發告示,民間對於姬雲羲的稱呼,也遲遲停在「三殿下」。
倒是引來了無數離奇荒謬的故事。
這邊正說著,忽地聽見一聲喧鬧,外頭竟湧進了一群官兵。
宋玄和想容俱是回頭去看,便瞧見一個衣著華貴、面容姣好的男子,正大步流星地踏進來,用下巴尖朝著那說書人,「我聽聞這裡有人妄議朝廷,果然如此。」
宋玄微微一愣,仔細去瞧那男子的眉眼,是個不曾見過的陌生面孔。
妄議朝廷,這天大的一頂帽子說書人哪裡敢接,也沒弄清來人是誰,只曉得這些都是官府的官兵,連連告饒,連茶樓的老闆也出來說情。
「把人帶走,店給我砸了。」那男子卻趾高氣揚地喝罵,一副有恃無恐、盛氣凌人的樣子。「若是再讓本公子聽見你們胡說八道,有你們的好看。」
那男子旁邊跟著的官兵頭子倒也是宋玄的熟人──趙捕快,聽聞男子要砸店,忍不住勸了什麼。
「怎麼?本公子說話不好用?我說讓你砸,你就給我砸。」男子冷笑一聲。「區區一個捕快,難道要反了不成?」
這男子身分不明,帽子卻扣得一頂比一頂大,嚇得那趙捕快閉了嘴,一眾官兵將吃茶的客人驅趕出去,抄起桌上的碗碟杯筷一氣兒亂砸。一時之間,只能聽見那茶館老闆焦急的勸阻聲,和瓷器破碎、桌椅翻倒的響聲。
眾多客人不知其中緣由,生怕惹禍上身,紛紛避退,只有宋玄忍不住瞧了一眼,低聲問想容:「這又是哪路的神仙,我離了四方城這些時候,竟連天都變了不成?」
「小聲點。」想容用手肘大力戳了戳他。
宋玄被這一下頂得沒防備,連連咳嗽,險些連方才吃進肚的茶點都吐了出來。
想容大大咧咧地拍了拍他的後背,「這是兩個月前來的神仙,人都稱他南榮君,你還不知道?」
「南榮君?」宋玄微微在腦子裡過了一遍,九流三教,確實都沒這樣一個名號,這才搖了搖頭。「是外城來的?」
「盛京來的。」想容壓低了聲音,「我聽客人說,這小子是三殿下的親信。」
宋玄微微一愣,「什麼?」
現在人們口中的三殿下,只能是姬雲羲一個人。
想容並不大清楚宋玄當年的舊事,也不太明白他跟姬雲羲的糾葛,只當他是好奇。
「就是現在那個三殿下,南榮君是他身邊的人。聽說是來替那勞什子三殿下辦事的,整日裡正事沒見他做一件,斂財滋事倒沒少幹,上頭那幫官員都瘋了似地向他送禮走門路──」
宋玄不知怎麼,彷彿有些走神,「走什麼門路?」
「走三殿下的門路啊!你不是傻了吧?」想容奇道,「先皇三個兒子,一個失蹤,一個自縊。現在連三歲小兒都知道,那位置鐵板釘釘,就是那三殿下的了。官員不趁著現在走門路,還什麼時候走?」
宋玄敷衍地點點頭。
他在聽到事關姬雲羲的時候,神思就已經飄忽到不知哪兒去了,連帶著後頭想容的話,一個字兒都沒聽進腦子裡。
他沉默了一會,忽地想起了什麼:「他是替姬雲羲來辦什麼事的?」
「這誰知道,我是沒看出來他有什麼事。」想容皺著眉道:「我只知道,這南榮君果真不是個省油的燈,早些弄完早些滾蛋才是,別再來禍害這四方城了。」
宋玄想到方才那人的情態,忍不住微微皺了眉頭。
阿羲的親信,竟是這樣的人嗎?
連宋玄也沒想到,這個南榮君會在四方城掀起這樣大的波瀾。
四方城的地上地下兩套班子,官家與八門之間相互勾結,魚龍混雜、深淺難測,算得上一個凶險的地界。
就算上頭偶爾有欽差來訪,也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只要面子給足、禮數送到,便也就那麼回事了。
不想這南榮君卻是個貪心不足、膽大包天的人物,這幾日裡仗著三殿下的名號,在四方城攪風攪雨,專挑做生意的平頭百姓坑害。
他找盡理由,從妄議朝政到窩藏賊贓,有的沒的都拿出來,一氣兒封了十餘家店鋪。只等著人送銀兩去才肯鬆口,一副擺明了要斂財的嘴臉。便宜些的便是破財消災,運氣差些的被扣了親眷,為贖回家人搞得散盡家財。
這樣一來,竟逼得不少店鋪關門歇業,只等著這一波過去。
「官府也不管?」想容生來便有幾分俠義心腸,如今聽了這事更是生氣。「什麼狗屁南榮君,聽都沒聽過的東西,也敢在四方城撒野。」
「早有人去問過上頭了,這人是三殿下的人,官府那邊也沒什麼法子,都是哄著捧著的。」常雨將茶水一放,也是愁眉苦臉。
他是來替人送貨的。這些日子他們兄弟倆的賭場為避風頭,也是關了門。兄弟兩個為了賺口飯吃,也是什麼零工都做起來了。
區區一個南榮君,竟攪得四方城百業蕭條,這是眾人都沒有想到的。
宋玄聽聞此言,忍不住轉了目光,「當真是三殿下的人?你可曾打聽過嗎?」
常雨笑道:「聽官府那頭說,這南榮君手上有三殿下的信物,且是幫三殿下來尋龍鼎的。」
宋玄皺著眉,「龍鼎?真有這麼個東西?」那不是那些說書人編出來的?
「管它是不是真的。就現在這個架勢,三殿下要尋,那就是沒有也得有。」常雨壓低了聲音,靠近宋玄低聲說,「而且,您有所不知,我聽人家說,這個南榮君和三殿下,是那個關係。」
他掐了掐小指,比劃了一個齷齪的動作。
想容見了便一腳踹翻他的凳子,讓常雨直接一屁股坐地上去了,「哎呦哎呦」叫個沒完。
「在我這兒胡扯什麼玩意?」想容見這男人齷齪的表情,滿臉嫌棄。
常雨哭喪著臉,「這也不是我說的,是南榮君自己透露的。」
宋玄盯著常雨,眉頭越皺越緊,眼神凝重,「此話當真?」
「八九不離十,」常雨見宋玄有興趣,愈加高興,也不嫌屁股疼了,拖著凳子就湊到宋玄邊上嚼舌頭,「你想啊,打這兒之前,南榮君可是連聽都沒聽過的一個人。盛京裡大小官員幕僚,就是天師也是成群結隊的,憑什麼讓他來尋龍鼎?可不就是枕邊關係,最讓人親近信任嗎?再者,這三殿下如今也二十有二了,連側妃都沒有一個。若不是不行,那只怕志不在此啊。」
砰──
常雨這回又摔地上了,抬頭一看,竟是宋玄將他的凳子踹翻的。
「宋先生這是做什麼?」常雨哭喪著一張臉,嚷嚷起來。
想容在邊上幸災樂禍,「你宋先生可是二十有七,也沒見娶個媳婦兒,這是被戳到痛處了。」
常雨這才意識到自己言多必失,嘿嘿地笑著圓話:「先生不一樣,先生是半仙兒,清心寡欲超凡脫俗,哪能看得上庸脂俗粉呢。」
想容嗤之以鼻,「油嘴滑舌。」
宋玄神色淡淡,心裡卻是憑生波瀾,分明知道此事與自己無關,卻又忍不住在意。
「總之且瞧著吧,這南榮君一日不走,咱們四方城就一日太平不下來。」常雨下了定論,又蹭了想容半壺茶水,才顛顛兒地從後門走了。
想容見宋玄半晌無話,大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想什麼呢?」
宋玄被拍得一哆嗦,忙從自己的思緒中回過神來,隨口道:「沒什麼,只是在想這個南榮君,讓他這樣興風作浪,也不是個事兒。」
想容登時瞪大眼睛,「你也這樣覺得?」
宋玄看她這表情,就知道她又想管閒事了。
這人就是一顆天生的俠義心腸,見到不平之事總想摻合兩下。上回打從茶樓回來,她就天天惦記著,只是沒說出來罷了。
果然,想容做賊似地把門關上,一雙圓眼滴溜溜地轉,拉著他道:「前兩日還有客人跟我問起你,想託你去打探南榮君的底細,我曉得你那三不沾的規矩,才幫你回了。你若也瞧那南榮君不順眼,這倒是個好機會──」
宋玄聽了便問:「什麼客人?」
想容低低地比劃了一下,「無非是三爺他們那幫子人。」
宋玄一聽便明白,四方城地下掌舵的那幾位他也都見過,現在領頭的那位姓傅,外號三爺,是個一等一的狠角色。
當初季硝頭腦機敏,又背靠大山,這才壓了他們一頭。自打幾年前季硝追著方秋棠去了京城,轉移了生意重心,這四方城就成了三爺的半個天下。
如今見這南榮君囂張,官府不敢管,三爺卻不可能坐視不理。他顯然是想出手干預,卻又摸不清底細,算來算去,才找到了宋玄的頭上。
宋玄回來的消息,知道的人不多,但對於這些掌舵人來說,只怕並不是個祕密。
宋玄猶豫了片刻,沒有應聲。
想容以為他不願意,便道:「你若不想去,當我沒說過就是了,也不是什麼大事。」
宋玄不沾黨政權謀,想容也明白他的用意,行走江湖想要保命,這樣的渾水蹚得越少越好。
「妳去聯繫他吧,」宋玄忽地說,「就說這事我應承了,記得欠我一回情。」
想容一愣,「當真?」
宋玄點了點頭。
他倒是真的想會會這南榮君。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