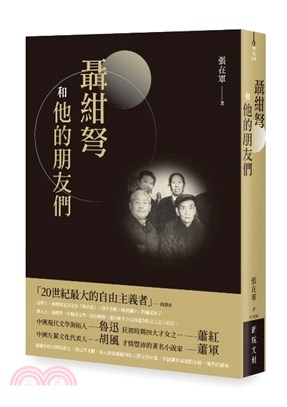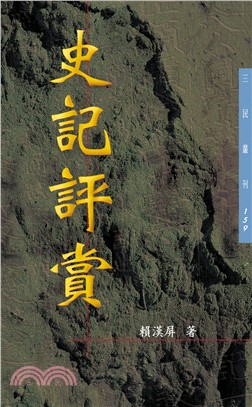定價
:NT$ 600 元優惠價
:90 折 540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6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章詒和回憶聶紺弩:「敢想、敢怒、敢罵、敢笑、敢哭。」
聶紺弩1922年加入國民黨,是黃埔二期學生,作為蔣介石衛隊第一次東征;後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學,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同學。
聶紺弩的仕途卻未因此而發達,為追求革命他在1935年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筆為戈。這一信念使他坐過日本人的監房,躲過國民黨的抓捕,及至文革期間被劃為「右派」分子,遭受十年牢獄之災。聶紺弩一生經歷刀山火海,也因此結識了各種各樣的知心好友。
本書記述聶紺弩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不同人生階段與不同身分之人交往,既有中國文化大家,如魯迅、馮雪峰、邵荃麟、胡風、鍾敬文、蕭紅、蕭軍、羅孚、舒蕪、黃永玉、劉再復等,也有平凡小輩如周健強、黨沛家、李世強等;亦收錄了珍貴的史料照片、詩信手稿,從聶紺弩與友人的互動,既可見其為人思想,同時也折射出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
聶紺弩1922年加入國民黨,是黃埔二期學生,作為蔣介石衛隊第一次東征;後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學,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同學。
聶紺弩的仕途卻未因此而發達,為追求革命他在1935年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筆為戈。這一信念使他坐過日本人的監房,躲過國民黨的抓捕,及至文革期間被劃為「右派」分子,遭受十年牢獄之災。聶紺弩一生經歷刀山火海,也因此結識了各種各樣的知心好友。
本書記述聶紺弩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不同人生階段與不同身分之人交往,既有中國文化大家,如魯迅、馮雪峰、邵荃麟、胡風、鍾敬文、蕭紅、蕭軍、羅孚、舒蕪、黃永玉、劉再復等,也有平凡小輩如周健強、黨沛家、李世強等;亦收錄了珍貴的史料照片、詩信手稿,從聶紺弩與友人的互動,既可見其為人思想,同時也折射出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
作者簡介
張在軍
生於荊楚,客居嶺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理事。早年熱衷雜文隨筆寫作,近年致力歷史文化研究。已經出各類版著作十幾種,多次入選圖書排行榜。主要作品有《苦難與輝煌:抗戰時期的武漢大學》、《戰亂與革命中的東北大學》、《歷史的插曲:一座後方小城的抗戰記憶》、《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蘇雪林和她的鄰居們》、《西北聯大》、《發現樂山》、《發現永安》等。
生於荊楚,客居嶺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理事。早年熱衷雜文隨筆寫作,近年致力歷史文化研究。已經出各類版著作十幾種,多次入選圖書排行榜。主要作品有《苦難與輝煌:抗戰時期的武漢大學》、《戰亂與革命中的東北大學》、《歷史的插曲:一座後方小城的抗戰記憶》、《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蘇雪林和她的鄰居們》、《西北聯大》、《發現樂山》、《發現永安》等。
序
紺弩和他的朋友(代序) 文/彭燕郊
紺弩是個很重友情的人,有不少朋友。
鍾敬文、胡風是他的終生好友。鍾敬文,他的文學生活的第一個夥伴,胡風,他的生死與共的文學戰友。
認識紺弩以來,所見到的他的交友之道,憑印象歸結起來有這幾點,他是前輩,是我的老師,有些事情我可能不知道,不懂,理解不準確。
他擇友,最重要的一條是興趣相近。他一生癡迷於文學,癡迷到成癖,夠得上「癡絕」,是個「有癖」的人,「無癖則無情」,無癖之人不可交。不是「可」與「不可」的事,而是不是同好,就談不上相知,更談不上相交。
有志於文學事業的人不少,喜歡弄弄文學的人不少,他結交的範圍卻很小,並非因為自視甚高,因為孤高什麼的而落落寡合,他是愛交友,對朋友非常熱情的,但是有個前提,就是要讓他傾慕,讓他佩服。他的標準是「我寫不出」的就無保留的佩服,傾情結交。胡風的論文,蕭軍、蕭紅的小說,曹白的散文在他屬於「我寫不出」,於是自然成為好友,朋友寫的好文章他津津樂道,比自己寫出來的還要叫他高興。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時,文協桂林分會經費困難,大家想了個辦法,每人自選一篇作品,請他編一本《二十九人自選集》,稿費捐給文協分會,正巧胡繩寫了一篇批判馮友蘭的《新事論》的評論,紺弩讀了讚口不絕。馮友蘭當時有蔣介石的「文房四寶」之一之稱,煊赫一時,胡繩的評論一時找不到地方發表。雖然他不是文協會員,紺弩還是把這篇文章編進《自選集》,並非只因為是老朋友,而是因為讀到老朋友的文章而高興得情不自禁,一定要讓更多人讀到它。
思想上,他是堅定的革命者。但他不喜歡「唯我獨左」,把馬列掛在嘴上的衛道君子。各種各樣的人他見得多了,這種人往往「色厲內荏」,馬列是用來裝門面的。在軍隊裡時,有人寫情書,開頭第一句就是「列寧說」,傳為笑話,他卻並不覺得好笑,只覺得氣憤。有個青年詩人寫評論,強調作者沒有那種生活經驗就不可能寫那種題材,意思是提倡深入生活,但強調過頭了。他寫文章批評,恰巧這位青年詩人用的筆名是「高崗」,抗戰初期,誰能知道有一個後來當上國家副主席的高崗,但軍隊的領導人是知道的,以為他是在攻擊大人物,和他爭論了大半天。他就是這樣與愛用「正確」的一套訓人的人遠遠隔開距離。
有些人就喜歡用「正確」來為自己謀好處,同樣有些人善於用自己的那一分「本領」、才能學問之類的為自己謀好處,「汲汲於富貴,戚戚於成名」,在權力者面前,就難免奴顏婢膝。在軍隊裡時,有個知名度相當高的作家,和他也算是老相識了,他也相當欣賞他的才能,但就是看不慣他對首長的那副畢恭畢敬的樣子,終於沒能成為朋友,雖然也還是以一個戰士敬重他。
他最討厭那種自私而且自私到損人利己程度的人。有個名氣很大,確實也寫過不少好詩的詩人,也算是老熟人了,給他的總的印象是:「我喜歡他的詩,不喜歡他的人。」他並沒有數落這位詩人所以讓他不喜歡的事。後來我有機會認識這位詩人,交往中發現他真很自私,斤斤計較,常背後講別人壞話,「愛惜羽毛」,自我保護意識很強,這些,在他的詩裡倒是看不到的,也許那不一定是他的主要一面吧。
有一位也很有名氣,寫過一些引起廣泛注意的作品的小說家,也是老熟人,紺弩很不喜歡他。在桂林,我和他一度同住在一棟小樓上,一天晚上,紺弩到我這裡來聊天,忽然下起大雨,回不去了,我在中間小廳上給他搞了個地鋪,「就在這裡過一夜算了」。住對面房的那位小說家這時也被雨阻還沒回來,紺弩想了一下,說:「還是回去,我不能跟他同睡在一個屋頂下。」原來,這位小說家和也是老朋友的另一位小說家的伴侶,也是小說家的一位女作家曾經有過一段讓人議論紛紛的共同生活,整個過程紺弩十分清楚。人們都認為這位小說家在這件事情上私德有虧,不過我知道紺弩不全是從「挖老朋友牆腳」這個角度看的。男女間事,在他看來,關鍵在於有沒有愛情,問題是如果出於愛情以外的什麼目的,那就是失德,而這位小說家和這位女作家的結合,到她病終前已經很難維護下去,人們同情她而責難他,也是情理中事。紺弩絕不道學,也是在桂林和他一起辦那個很有影響的雜文刊物的一位青年作家,有婦之夫,忽然和一位曾是某評論家的伴侶,出版過一本小說集的女作家熱戀起來,如火如荼,鬧得沸沸揚揚,紺弩就認為別人多事,「他們果真愛了,關你什麼事!」
說這些,並不就是說紺弩在人際關係上很潔癖。人嘛,總是要和人打交道的。朋友也就有各種不同類型,講學問的寫文章是宋雲彬;舊體詩是陳邇冬,小說是蕭軍、蕭紅。搞事業的,辦報的是張稚琴、歐陽敏訥、羅孚、曾敏之,辦刊物的是秦似,出版界的是朱希、戲劇界的是冼群、戴浩,美術界的是余所亞、丁聰、黃苗子、黃永玉等等,他的朋友很多。不用說,政治上的朋友對他更重要,吳奚如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曾一度失去組織聯繫,是邵荃麟幫助他恢復關係的,千方百計營救他出獄的朱靜芳,要講朋友義氣,該數她第一,紺弩尊重她,不會忘記她,我們誰都不應該忘記她。
我注意到他在交友上有個特點,有時和他有很深友誼的人,對他不怎麼友好,他不計較,對這位朋友還是一往情深,我說的是胡風。胡風對他的小說、新詩要求特別苛刻,小說〈姐姐〉,胡風就不喜歡,好久不給發表,後來還是黎烈文、王西彥給發表了。長詩〈收穫的季節〉,胡風也不喜歡,說「不知為什麼寫得那麼多」。我喜歡這首詩,覺得比個別胡風喜歡的年輕人寫的近於空洞叫喊的好,但是紺弩從不計較這些。《七月》停刊,胡風怪他壞事,有個時期甚至不和他講話,形同陌路。他編《藝文志》,胡風不支持,終於辦不下去,他不計較,老朋友自然知道各自的老脾氣。胡風是有這個缺點,奚如說他「沒有容人之德」,招致後來栽在一個倒很相信的人手裡。但是缺點歸缺點,胡風畢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至死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深知胡風的紺弩,絕不會因為朋友間有一點不愉快的事就要「洩憤」,他是絕不會有這種極端不近人情的「憤」的。晚年,胡風在難中時,更顯出紺弩和他之間友情之美、之崇高。胡風被發配去四川,他甚至想去四川探望,那時候,一般人對胡風,都唯恐避之不及呢。他們的酬唱詩,說是千古絕唱,也不算過分。
但是他在這方面,也有個不算小的缺點。不知我這比喻恰當不:像個容易受男人甜言蜜語騙上手的女人。有些人就有這種本領,從自己需要出發,認定獵物,然後精心設計一套獵取方案,針對目標的弱點,一步一步地靠近,一鋤頭一鋤頭不動聲色挖陷阱,在陷阱上一層一層地加偽裝,最後讓獵物舒舒服服地掉下去。也許我這比喻有點刻薄,我的本意卻實在不想刻薄,我只是為紺弩的不設防而最後落到被人誤解為「馬大哈」,「是非不分」,甚至讓人懷疑他和胡風是不是真朋友感到他受委屈,感到他蒙冤,感到難過。
文藝圈裡,報館、出版社熟人、同事很多,他不孤芳自賞,也不八面玲瓏,朝夕相處,對人和氣,但不熱絡,不套近乎。他的有些朋友幾乎近於「神交」,好朋友卻不露形跡,有時他會突然問:「那個某某人現在在哪裡?」某某在他是個好朋友,多年不見,彼此都懶得寫信,他很少寫信,不得不寫也往往寫得很短。晚年他的朋友多起來了,北大荒難友,報社出版社同事之外,添加了不少詩友。他寫舊體詩,神差鬼使,搞出了一場舊體詩革命,有那麼多知音同好,那麼多愛談他的詩仰慕他的人加入到都不是為別的而只為愛他敬他的同道隊伍裡,說不上親密卻比親密更可貴。
當然他不是沒有親密朋友,鍾敬文、胡風、蕭軍、蕭紅、吳奚如、徐平羽都是。我知道較多的也是他喜歡提到的,還有伍禾、陳邇冬,從他們兩人可以看到紺弩的擇友之道。這兩個人,依我看都是湖海之士,淡泊名利,簡直有點飄然物外,然而執著人生理想、社會理想,鍾愛文學藝術,不知生計,甘於清貧,然而自有一種旁人不及的瀟灑、風趣,一種癡迷,一種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癖」。抗日戰爭時期在桂林,伍禾寫詩,生活的清苦更顯得他的日子過得那麼自得其樂。對他,紺弩那篇〈我和伍禾〉開頭兩句話:「伍禾是詩人,不,伍禾是首人詩」,已經寫盡。紺弩最愛提到他的兩件事,一是他曾經把一本什麼書上的目錄排列成一首新詩寄給某雜誌,主編先生居然大為激賞,鄭重其事地刊登出來。一是他認為刪節本的《金瓶梅》比沒有刪節的更「淫」。紺弩說他和伍禾是「酒肉朋友」,「一塊兒坐茶館」,「一塊兒上館子,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天天上館子」,「這之外就是上澡堂」。在桂林,廣東茶館很大眾化,不花什麼錢,上館子也可以不花什麼錢,有如現在的吃盒飯,絕非大吃大喝。至於澡堂,我一輩子沒上過,桂林有沒有澡堂,有,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被迫離開報社後,他們常在一起聊天,有時可以整天整夜聊,對於紺弩,這是非常重要的,他有那麼多積鬱心頭的話需要傾訴,需要有善於聽他的傾訴,而且迅速作出共鳴的知心朋友。那時不作興寫舊體詩,但紺弩愛寫字,他寫給伍禾的我記得的就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之類的。作於一九九六年春的〈聞伍禾入院求醫〉:「漢江日夜東流水,你我乾坤無盡情。端午前當能出院,欲披明月武昌行。」現在我們能讀到的還有〈贈伍禾〉二首,〈追念伍禾〉三首,和〈秋夜北海懷冰(董冰如)奚(吳奚如)禾(伍禾)曙(郭曙南)〉,皆情見乎辭,足見二人友誼之篤。邇冬,我常戲呼他為「桂林名士」,其實我很想稱他為「隱士」,他太愛他為自己構築的那個精神樂園了。他一直在個什麼機關裡當個小公務員,不求仕進,以他的資歷名望,加上他的朋友裡有陳銘樞這樣的大人物,謀個一官半職或到大學裡搞個教職是很容易的。他寫新詩,也寫舊詩,卻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有真情,有靈氣。湘桂大撤退,逃難時他先到獨山,夫人馬兜鈴後到,他有一首七絕:「君來無復首飛蓬,膏沐成妝為我容。藕孔避兵西子老,五湖無棹載陶公。」逃難到重慶時,我把這首詩寫給紺弩看,他看了說:「這樣的詩我寫不出。」後來他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對邇冬人品詩才有更深瞭解,誠心向他求教。一九八一年他在〈散宜生自序〉中寫道:「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老師,陳邇冬和鍾靜聞(敬文)。邇冬樂於獎掖後進。詩格寬,隱惡揚善,盡說好不說壞。假如八句詩,沒有一句他會說不好的,只好從他未稱讚或未太稱讚的地方去領悟它如何不好。」對邇冬他是很尊敬很尊敬的。對邇冬的詩,他的讚賞可以說無以復加:「尊作三句讀之嚇倒,疑為七絕而非七律,將毫無關係之三事聯為一詩,一絕也,一用雙簧喝破古今,二絕也,前半為政治事,後半為精神事,若即若離,天衣無縫,三絕也。如此數去,雙手所不能盡,何止七絕……但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人口幾十億,今日鄰里乃由此人此詩,一口道盡,此真藝文絕境……人生幾何,能作幾詩,若此詩者,能得幾首,想作者心中得意也?謹函馳賀,餘不多言。」平生不輕易許人而作此高評,真是人生難得是知音,一談到邇冬,他就興奮,就要背「千山縮腳讓延河」,就佩服,「逢茲百煉千錘句,愧我南腔北調人」。常聽人說「詩友」,他們才真正是詩友,更難得是,邇冬一家都成了他的詩友,「詩夫詩妻詩兒詩女詩翁詩婿,一團活火,燃之以詩」。紺弩全集中贈答詩,贈胡風之外,最耐讀的是贈邇冬的。
(本文經彭燕郊先生之女張丹丹老師同意作為代序,特此致謝!──作者)
紺弩是個很重友情的人,有不少朋友。
鍾敬文、胡風是他的終生好友。鍾敬文,他的文學生活的第一個夥伴,胡風,他的生死與共的文學戰友。
認識紺弩以來,所見到的他的交友之道,憑印象歸結起來有這幾點,他是前輩,是我的老師,有些事情我可能不知道,不懂,理解不準確。
他擇友,最重要的一條是興趣相近。他一生癡迷於文學,癡迷到成癖,夠得上「癡絕」,是個「有癖」的人,「無癖則無情」,無癖之人不可交。不是「可」與「不可」的事,而是不是同好,就談不上相知,更談不上相交。
有志於文學事業的人不少,喜歡弄弄文學的人不少,他結交的範圍卻很小,並非因為自視甚高,因為孤高什麼的而落落寡合,他是愛交友,對朋友非常熱情的,但是有個前提,就是要讓他傾慕,讓他佩服。他的標準是「我寫不出」的就無保留的佩服,傾情結交。胡風的論文,蕭軍、蕭紅的小說,曹白的散文在他屬於「我寫不出」,於是自然成為好友,朋友寫的好文章他津津樂道,比自己寫出來的還要叫他高興。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時,文協桂林分會經費困難,大家想了個辦法,每人自選一篇作品,請他編一本《二十九人自選集》,稿費捐給文協分會,正巧胡繩寫了一篇批判馮友蘭的《新事論》的評論,紺弩讀了讚口不絕。馮友蘭當時有蔣介石的「文房四寶」之一之稱,煊赫一時,胡繩的評論一時找不到地方發表。雖然他不是文協會員,紺弩還是把這篇文章編進《自選集》,並非只因為是老朋友,而是因為讀到老朋友的文章而高興得情不自禁,一定要讓更多人讀到它。
思想上,他是堅定的革命者。但他不喜歡「唯我獨左」,把馬列掛在嘴上的衛道君子。各種各樣的人他見得多了,這種人往往「色厲內荏」,馬列是用來裝門面的。在軍隊裡時,有人寫情書,開頭第一句就是「列寧說」,傳為笑話,他卻並不覺得好笑,只覺得氣憤。有個青年詩人寫評論,強調作者沒有那種生活經驗就不可能寫那種題材,意思是提倡深入生活,但強調過頭了。他寫文章批評,恰巧這位青年詩人用的筆名是「高崗」,抗戰初期,誰能知道有一個後來當上國家副主席的高崗,但軍隊的領導人是知道的,以為他是在攻擊大人物,和他爭論了大半天。他就是這樣與愛用「正確」的一套訓人的人遠遠隔開距離。
有些人就喜歡用「正確」來為自己謀好處,同樣有些人善於用自己的那一分「本領」、才能學問之類的為自己謀好處,「汲汲於富貴,戚戚於成名」,在權力者面前,就難免奴顏婢膝。在軍隊裡時,有個知名度相當高的作家,和他也算是老相識了,他也相當欣賞他的才能,但就是看不慣他對首長的那副畢恭畢敬的樣子,終於沒能成為朋友,雖然也還是以一個戰士敬重他。
他最討厭那種自私而且自私到損人利己程度的人。有個名氣很大,確實也寫過不少好詩的詩人,也算是老熟人了,給他的總的印象是:「我喜歡他的詩,不喜歡他的人。」他並沒有數落這位詩人所以讓他不喜歡的事。後來我有機會認識這位詩人,交往中發現他真很自私,斤斤計較,常背後講別人壞話,「愛惜羽毛」,自我保護意識很強,這些,在他的詩裡倒是看不到的,也許那不一定是他的主要一面吧。
有一位也很有名氣,寫過一些引起廣泛注意的作品的小說家,也是老熟人,紺弩很不喜歡他。在桂林,我和他一度同住在一棟小樓上,一天晚上,紺弩到我這裡來聊天,忽然下起大雨,回不去了,我在中間小廳上給他搞了個地鋪,「就在這裡過一夜算了」。住對面房的那位小說家這時也被雨阻還沒回來,紺弩想了一下,說:「還是回去,我不能跟他同睡在一個屋頂下。」原來,這位小說家和也是老朋友的另一位小說家的伴侶,也是小說家的一位女作家曾經有過一段讓人議論紛紛的共同生活,整個過程紺弩十分清楚。人們都認為這位小說家在這件事情上私德有虧,不過我知道紺弩不全是從「挖老朋友牆腳」這個角度看的。男女間事,在他看來,關鍵在於有沒有愛情,問題是如果出於愛情以外的什麼目的,那就是失德,而這位小說家和這位女作家的結合,到她病終前已經很難維護下去,人們同情她而責難他,也是情理中事。紺弩絕不道學,也是在桂林和他一起辦那個很有影響的雜文刊物的一位青年作家,有婦之夫,忽然和一位曾是某評論家的伴侶,出版過一本小說集的女作家熱戀起來,如火如荼,鬧得沸沸揚揚,紺弩就認為別人多事,「他們果真愛了,關你什麼事!」
說這些,並不就是說紺弩在人際關係上很潔癖。人嘛,總是要和人打交道的。朋友也就有各種不同類型,講學問的寫文章是宋雲彬;舊體詩是陳邇冬,小說是蕭軍、蕭紅。搞事業的,辦報的是張稚琴、歐陽敏訥、羅孚、曾敏之,辦刊物的是秦似,出版界的是朱希、戲劇界的是冼群、戴浩,美術界的是余所亞、丁聰、黃苗子、黃永玉等等,他的朋友很多。不用說,政治上的朋友對他更重要,吳奚如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曾一度失去組織聯繫,是邵荃麟幫助他恢復關係的,千方百計營救他出獄的朱靜芳,要講朋友義氣,該數她第一,紺弩尊重她,不會忘記她,我們誰都不應該忘記她。
我注意到他在交友上有個特點,有時和他有很深友誼的人,對他不怎麼友好,他不計較,對這位朋友還是一往情深,我說的是胡風。胡風對他的小說、新詩要求特別苛刻,小說〈姐姐〉,胡風就不喜歡,好久不給發表,後來還是黎烈文、王西彥給發表了。長詩〈收穫的季節〉,胡風也不喜歡,說「不知為什麼寫得那麼多」。我喜歡這首詩,覺得比個別胡風喜歡的年輕人寫的近於空洞叫喊的好,但是紺弩從不計較這些。《七月》停刊,胡風怪他壞事,有個時期甚至不和他講話,形同陌路。他編《藝文志》,胡風不支持,終於辦不下去,他不計較,老朋友自然知道各自的老脾氣。胡風是有這個缺點,奚如說他「沒有容人之德」,招致後來栽在一個倒很相信的人手裡。但是缺點歸缺點,胡風畢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至死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深知胡風的紺弩,絕不會因為朋友間有一點不愉快的事就要「洩憤」,他是絕不會有這種極端不近人情的「憤」的。晚年,胡風在難中時,更顯出紺弩和他之間友情之美、之崇高。胡風被發配去四川,他甚至想去四川探望,那時候,一般人對胡風,都唯恐避之不及呢。他們的酬唱詩,說是千古絕唱,也不算過分。
但是他在這方面,也有個不算小的缺點。不知我這比喻恰當不:像個容易受男人甜言蜜語騙上手的女人。有些人就有這種本領,從自己需要出發,認定獵物,然後精心設計一套獵取方案,針對目標的弱點,一步一步地靠近,一鋤頭一鋤頭不動聲色挖陷阱,在陷阱上一層一層地加偽裝,最後讓獵物舒舒服服地掉下去。也許我這比喻有點刻薄,我的本意卻實在不想刻薄,我只是為紺弩的不設防而最後落到被人誤解為「馬大哈」,「是非不分」,甚至讓人懷疑他和胡風是不是真朋友感到他受委屈,感到他蒙冤,感到難過。
文藝圈裡,報館、出版社熟人、同事很多,他不孤芳自賞,也不八面玲瓏,朝夕相處,對人和氣,但不熱絡,不套近乎。他的有些朋友幾乎近於「神交」,好朋友卻不露形跡,有時他會突然問:「那個某某人現在在哪裡?」某某在他是個好朋友,多年不見,彼此都懶得寫信,他很少寫信,不得不寫也往往寫得很短。晚年他的朋友多起來了,北大荒難友,報社出版社同事之外,添加了不少詩友。他寫舊體詩,神差鬼使,搞出了一場舊體詩革命,有那麼多知音同好,那麼多愛談他的詩仰慕他的人加入到都不是為別的而只為愛他敬他的同道隊伍裡,說不上親密卻比親密更可貴。
當然他不是沒有親密朋友,鍾敬文、胡風、蕭軍、蕭紅、吳奚如、徐平羽都是。我知道較多的也是他喜歡提到的,還有伍禾、陳邇冬,從他們兩人可以看到紺弩的擇友之道。這兩個人,依我看都是湖海之士,淡泊名利,簡直有點飄然物外,然而執著人生理想、社會理想,鍾愛文學藝術,不知生計,甘於清貧,然而自有一種旁人不及的瀟灑、風趣,一種癡迷,一種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癖」。抗日戰爭時期在桂林,伍禾寫詩,生活的清苦更顯得他的日子過得那麼自得其樂。對他,紺弩那篇〈我和伍禾〉開頭兩句話:「伍禾是詩人,不,伍禾是首人詩」,已經寫盡。紺弩最愛提到他的兩件事,一是他曾經把一本什麼書上的目錄排列成一首新詩寄給某雜誌,主編先生居然大為激賞,鄭重其事地刊登出來。一是他認為刪節本的《金瓶梅》比沒有刪節的更「淫」。紺弩說他和伍禾是「酒肉朋友」,「一塊兒坐茶館」,「一塊兒上館子,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天天上館子」,「這之外就是上澡堂」。在桂林,廣東茶館很大眾化,不花什麼錢,上館子也可以不花什麼錢,有如現在的吃盒飯,絕非大吃大喝。至於澡堂,我一輩子沒上過,桂林有沒有澡堂,有,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被迫離開報社後,他們常在一起聊天,有時可以整天整夜聊,對於紺弩,這是非常重要的,他有那麼多積鬱心頭的話需要傾訴,需要有善於聽他的傾訴,而且迅速作出共鳴的知心朋友。那時不作興寫舊體詩,但紺弩愛寫字,他寫給伍禾的我記得的就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之類的。作於一九九六年春的〈聞伍禾入院求醫〉:「漢江日夜東流水,你我乾坤無盡情。端午前當能出院,欲披明月武昌行。」現在我們能讀到的還有〈贈伍禾〉二首,〈追念伍禾〉三首,和〈秋夜北海懷冰(董冰如)奚(吳奚如)禾(伍禾)曙(郭曙南)〉,皆情見乎辭,足見二人友誼之篤。邇冬,我常戲呼他為「桂林名士」,其實我很想稱他為「隱士」,他太愛他為自己構築的那個精神樂園了。他一直在個什麼機關裡當個小公務員,不求仕進,以他的資歷名望,加上他的朋友裡有陳銘樞這樣的大人物,謀個一官半職或到大學裡搞個教職是很容易的。他寫新詩,也寫舊詩,卻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有真情,有靈氣。湘桂大撤退,逃難時他先到獨山,夫人馬兜鈴後到,他有一首七絕:「君來無復首飛蓬,膏沐成妝為我容。藕孔避兵西子老,五湖無棹載陶公。」逃難到重慶時,我把這首詩寫給紺弩看,他看了說:「這樣的詩我寫不出。」後來他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對邇冬人品詩才有更深瞭解,誠心向他求教。一九八一年他在〈散宜生自序〉中寫道:「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老師,陳邇冬和鍾靜聞(敬文)。邇冬樂於獎掖後進。詩格寬,隱惡揚善,盡說好不說壞。假如八句詩,沒有一句他會說不好的,只好從他未稱讚或未太稱讚的地方去領悟它如何不好。」對邇冬他是很尊敬很尊敬的。對邇冬的詩,他的讚賞可以說無以復加:「尊作三句讀之嚇倒,疑為七絕而非七律,將毫無關係之三事聯為一詩,一絕也,一用雙簧喝破古今,二絕也,前半為政治事,後半為精神事,若即若離,天衣無縫,三絕也。如此數去,雙手所不能盡,何止七絕……但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人口幾十億,今日鄰里乃由此人此詩,一口道盡,此真藝文絕境……人生幾何,能作幾詩,若此詩者,能得幾首,想作者心中得意也?謹函馳賀,餘不多言。」平生不輕易許人而作此高評,真是人生難得是知音,一談到邇冬,他就興奮,就要背「千山縮腳讓延河」,就佩服,「逢茲百煉千錘句,愧我南腔北調人」。常聽人說「詩友」,他們才真正是詩友,更難得是,邇冬一家都成了他的詩友,「詩夫詩妻詩兒詩女詩翁詩婿,一團活火,燃之以詩」。紺弩全集中贈答詩,贈胡風之外,最耐讀的是贈邇冬的。
(本文經彭燕郊先生之女張丹丹老師同意作為代序,特此致謝!──作者)
目次
紺弩和他的朋友(代序)/彭燕郊
斯民卅載沐恩來──聶紺弩與周恩來
一個甲子的友情──聶紺弩與鍾敬文
「跟你永遠作朋友」──聶紺弩與康澤
輸贏何止百盤棋──聶紺弩與金滿成陳鳳兮夫婦
新聞記者古典編──聶紺弩與張友鸞
三十萬言三十年──聶紺弩與胡風
始於東京的友誼──聶紺弩與樓適夷
同鄉同學亦同志──聶紺弩與吳奚如
文朋戰友同騎馬──聶紺弩與丘東平
多少心思念荃麟──聶紺弩與邵荃麟
一個高大的背影──聶紺弩與魯迅
何人繪得蕭紅影──聶紺弩與蕭紅
開門猛訝爾蕭軍──聶紺弩與蕭軍
絕筆留詩祭雪峰──聶紺弩與馮雪峰
港中高旅最高文──聶紺弩與高旅
不與 D.M. 睡一屋──聶紺弩與端木蕻良
比鄰而居的情誼──聶紺弩與辛勞
戰友師徒如兄弟──聶紺弩與彭燕郊
流亡路上忘年交──聶紺弩與駱賓基
奇肥怪瘦話連床──聶紺弩與秦似
兀者畫家「申徒嘉」──聶紺弩與余所亞
夢裡相見幾多回──聶紺弩與杲向真
尹畫聶詩題贈多──聶紺弩與尹瘦石
錯從耶弟方猶大──聶紺弩與舒蕪
活著就為了等你──聶紺弩與何滿子
我行我素我羅孚──聶紺弩與羅孚
黃家不樂誰家樂──聶紺弩與黃永玉
開膛毛肚會苗公──聶紺弩與黃苗子
一雙老小北大荒──聶紺弩與黨沛家
人生七十號間逢──聶紺弩與李世強
寫傳記的四姑娘──聶紺弩與周健強
一部太陽土地人──聶紺弩與劉再復
後記
斯民卅載沐恩來──聶紺弩與周恩來
一個甲子的友情──聶紺弩與鍾敬文
「跟你永遠作朋友」──聶紺弩與康澤
輸贏何止百盤棋──聶紺弩與金滿成陳鳳兮夫婦
新聞記者古典編──聶紺弩與張友鸞
三十萬言三十年──聶紺弩與胡風
始於東京的友誼──聶紺弩與樓適夷
同鄉同學亦同志──聶紺弩與吳奚如
文朋戰友同騎馬──聶紺弩與丘東平
多少心思念荃麟──聶紺弩與邵荃麟
一個高大的背影──聶紺弩與魯迅
何人繪得蕭紅影──聶紺弩與蕭紅
開門猛訝爾蕭軍──聶紺弩與蕭軍
絕筆留詩祭雪峰──聶紺弩與馮雪峰
港中高旅最高文──聶紺弩與高旅
不與 D.M. 睡一屋──聶紺弩與端木蕻良
比鄰而居的情誼──聶紺弩與辛勞
戰友師徒如兄弟──聶紺弩與彭燕郊
流亡路上忘年交──聶紺弩與駱賓基
奇肥怪瘦話連床──聶紺弩與秦似
兀者畫家「申徒嘉」──聶紺弩與余所亞
夢裡相見幾多回──聶紺弩與杲向真
尹畫聶詩題贈多──聶紺弩與尹瘦石
錯從耶弟方猶大──聶紺弩與舒蕪
活著就為了等你──聶紺弩與何滿子
我行我素我羅孚──聶紺弩與羅孚
黃家不樂誰家樂──聶紺弩與黃永玉
開膛毛肚會苗公──聶紺弩與黃苗子
一雙老小北大荒──聶紺弩與黨沛家
人生七十號間逢──聶紺弩與李世強
寫傳記的四姑娘──聶紺弩與周健強
一部太陽土地人──聶紺弩與劉再復
後記
書摘/試閱
〈「跟你永遠作朋友」──聶紺弩與康澤〉
聶紺弩和康澤既是黃埔軍校同學,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聶紺弩是共產黨左翼作家,康澤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他倆各自的身分,彼此心裡都十分明白。在政治分野上,他們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但在私人感情上,卻又頗為投契。康澤真的履行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朋友」的諾言,從沒向聶紺弩要求過什麼,除了要聶為他死後立傳;聶紺弩沒有負約,也先後為康澤寫過兩篇文章(〈時間的啟示〉和〈記康澤〉)。就因為這層關係,聶紺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種種誤解和詰難,乃至痛苦和屈辱。
大海上的談話
聶紺弩比康澤大一歲,也比康澤早一年考入黃埔軍校,聶是二期,康是三期。一九二五年秋,康澤因深得蔣介石賞識,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學,於十一月底先出發;聶紺弩則是自己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稍遲於十二月中旬啟程。這樣,他們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然而,聶紺弩在蘇聯待了一年半,「竟沒有和康澤談過一回話」,或許緣分沒到吧。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之後,蘇聯方面通知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代表、校理事會成員邵力子回國。邵力子離開莫斯科,國民黨在中山大學再無代表,預示這所學校國共合作的局面即將結束。六月十六日,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將國民黨右派學生遣送回國,以避免他們對其他國民黨學生施加不良影響。遣送回國的通告公布後,共有一百七十餘名國民黨學員提出回國申請。要求回國的國民黨學員人數之多超出了蘇方的預計,因此蘇方決定將國民黨學生分批遣送回國。聶紺弩當時作為國民黨學員,亦於六月底被遣送回國。回國的路線主要是從莫斯科坐火車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然後轉輪船到上海。
在茫茫大海上,聶紺弩和康澤終於開始了談話,「一次考驗性的談話」。據紺弩回憶:
晚飯之後,我們斜倚著鐵欄,大海在旁邊咆哮,海風吹散我們的頭髮,落日的霞光把世界照得通紅。康澤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著我,似乎要望進我心裡去,似乎已經望進我心裡去了。我明知這次談話的嚴重性,但並不心慌!我的綽號叫托爾斯泰,即專心文藝,不問政治的糊塗蛋之意,不怕他們會殺我;別的則真不在乎,我本沒打算跟他們混在一道。我不知道康澤是會談話的呢,還是不會。總之,他在我開口之先,自己談了許多,可惜那些高明的理論,現在不容易記起了,大概說,蘇聯的成功,是民生主義的成功而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合國情的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戴季陶先生的三民主義。我老實告訴他:我不喜歡戴季陶。戴季陶的《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要孫中山承繼中國的道統,要捧孫中山的神主牌進聖廟,是復古,是開倒車,不是革命。也不喜歡孫中山。孫中山的天才,在他把中國問題分成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但他談的卻很壞,比如民族主義,分析日本幾天可以亡中國,英國幾天可以亡中國……結論卻是恢復中國固有道德,這太不可理解了!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姑不論對不對,總是專就都市立論,對廣大的農民與土地問題沒有提起。雖在民生主義之外,講過一次「耕者有其田」,但也只是一個題目,內容對耕者有其田這事幾乎什麼也未說。更不喜歡蔣介石。他,沒有什麼可談的,完完全全的投機軍閥。當我還在黃埔的時候,就曾宣稱,不等兩年,我就要作反蔣運動。
「那麼,那麼,」他像吃一口辣椒似地問:「你對共產黨的看法呢?」
我說:我沒有看法。我的思想沒有出路,也正在此。讀過幾本書,覺得離認識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還很遠,也沒有力量批評,除了在莫斯科,覺得學校裡的投機分子太多以外,我不想談什麼。這裡也許須注解一下:在當時,有許多同學加入共產黨,並非為了革命信仰,而是為了回國後可以作官,那些人後來又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轉變了,比如蔣經國就是一個。所以我在當時確有此感。
「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誠實的人。」說完之後,他和我握手說,他的手捏我的捏得很緊,似乎表示他的話也是誠懇的。「而且倔強」。(〈記康澤〉)
後來康澤告訴聶紺弩,他當時的印象,認為聶太不世故,太任性,近於《三國演義》上的禰衡。如不留心,難免殺身之禍的。但是──康澤又說,正因為如此,反而看得起聶紺弩。
=============================================================
〈始於東京的友誼──聶紺弩與樓適夷〉
聶紺弩說,樓適夷「儘管有時簡單」,「但表裡如一」。樓適夷是聶紺弩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認識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領導。
東京初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左聯宣傳部副部長樓適夷受上級委派出席遠東泛太平洋反戰會議籌備會,和胡風同船去東京。「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陽翰笙指示樓適夷,順帶處理一下在留日革命進步學生文化團體「新興文化研究會」與「社會科學研究會」之間的糾紛問題。據樓適夷回憶:
事情是這樣的,在留日左翼中國學生中,當時有兩個文化團體。一個是「新興文化研究會」(「文化研」),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它的成員是張光人(胡風)、方翰(何定華)、聶衣葛(聶紺弩)、王承志(王達夫)、周穎、樓憲。他們受國內「左聯」的領導。其中成員如胡風,也參加日本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會(「普洛科」),直接受日共的領導。曾先後辦過《文化鬥爭》、《文化之光》等刊物。另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日本分會」(「社研分」)。它的成員有日本法政大學留學生漆憲章、郭兆昌,東京醫專學生汪成模,工大學生習明倫,明治大學學生黃鐘銘等。他們先後辦過《科學半月刊》、《科學新聞》等刊物。這個團體名稱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日本分會,實際在國內,「社研」只是在「左翼社會科學聯盟」指導下的各種群眾社會科學研究小團體的一個總稱,並不存在這名義的總會。他們和國內「社聯」盟員有個別聯繫,實沒有正式的組織關係。兩個團體的問題,是從理論性的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論爭開始的。首先在「文化研」的《文化鬥爭》第二期上,批評了「社研分」方面提出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言論;並在《文化鬥爭》第三、四期中,明白闡述了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從理論鬥爭,發展到宗派的指責。例如在一期《科學半月刊》上發表了編委的聲明,申述「社研分」在留日學生運動中歷年的鬥爭歷史,認為「文化研」的成員對這種歷史是不了解的。於是《文化鬥爭》上又以來稿名義,發表了翳鍋(按,即聶紺弩筆名)的《休矣,科學半月刊》和細鴛的《答〈科學〉對〈文鬥〉的批判》,駁斥「社研分」的自我炫耀,名之為「面子主義」與「風頭主義」。這個糾紛一直鬧到指摘有不良分子向日本員警告密的嚴重程度。(〈關於遠東反戰大會〉)
為了解決這個糾紛,樓適夷以「文總」代表身分找兩個團體負責人談話,瞭解事情的實況。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訪談,得出以下結論:產生糾紛的原因主要在「社研」一方。「社研」對其他組織進行不負責任的批判,不相信革命的日本文化組織,不與這些組織取得聯繫。另一方面,「文化研」的組織方針是正確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文化研」的缺點是對「社研」的批判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根據以上結論,特訂出以下三點方針:立即停止攻擊;兩組織同時解散,接受日本文化組織的領導,要改變活動方式;在重新組織的過程中,「社研」的全體成員應該就以前對其他組織的逃避態度進行自我批判,接受日本文化組織的領導,同時,還應同「文化研」相互協作,共同前進。
樓適夷調解完就回國了。接著發生小林多喜二被害事件,不久聶紺弩、周穎、胡風等人,也在東京被捕,關押數月後遭受驅逐,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回到上海。
同年九月,樓適夷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直至一九三七年出獄。
建國前夕
兩人再次短暫相見,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聶紺弩和樓適夷等人共同參加了在漢口胡風家裡組織的「抗戰以後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
十年之後兩人才真正相聚。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聶紺弩輾轉抵達香港。正式恢復了中共黨組織關係後,與以群(黨小組長)、樓適夷、蔣天佐等人在同一黨小組參加各種活動。
聶紺弩單身一人住在香港中國勞動協會的集體宿舍裡,樓適夷一早從九龍渡海去找他,他大半還懶洋洋地剛從床上起身,好像還沒睡足的樣子。若樓適夷編刊物,要稿子,他總是有求必應,答應得很痛快,要什麼有什麼,幾乎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不會讓人久盼。
樓適夷說:「可那個脾氣也怪,有一次上香港,在德輔道還不知是皇后道碰上了,他一把拉我,上了平時我不大敢上門的一家什麼外國招牌的高級咖啡館的大廳,喝喝咖啡,吃點西點,兩個人親熱熱,談得津津有味。忽然他站起來說:『好,我走了,你付錢。』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了。我原以為是他請我開洋葷,樂得享受一下子,現在可只好把剛從報社領來、準備買米回家的幾塊錢,硬著頭皮傾囊而出,暗暗嘆了口氣,想想『紺弩嘛,你什麼辦法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聶紺弩和樓適夷、蘇怡作為香港的代表,坐船北上,赴北平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大沽口賓館住了一晚,大家上火車赴北京。紺弩倒好,當大家都上車了,偏偏找不到人影,火車是不等待旅客的,沒奈何,樓適夷和夫人黃煒只好帶上他的寶貝女兒海燕,同大夥一起先去北京。到了北京住在前門外的一家旅館裡,大家都忙著開會,紺弩又讓不開會的黃煒照顧他的女兒,可他剛開完幾天會,又獨自跑得沒影子,甚至兩三天都沒回來。於是樓適夷夫婦又暫時成了海燕的保護人。
聶紺弩和康澤既是黃埔軍校同學,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聶紺弩是共產黨左翼作家,康澤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他倆各自的身分,彼此心裡都十分明白。在政治分野上,他們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但在私人感情上,卻又頗為投契。康澤真的履行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朋友」的諾言,從沒向聶紺弩要求過什麼,除了要聶為他死後立傳;聶紺弩沒有負約,也先後為康澤寫過兩篇文章(〈時間的啟示〉和〈記康澤〉)。就因為這層關係,聶紺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種種誤解和詰難,乃至痛苦和屈辱。
大海上的談話
聶紺弩比康澤大一歲,也比康澤早一年考入黃埔軍校,聶是二期,康是三期。一九二五年秋,康澤因深得蔣介石賞識,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學,於十一月底先出發;聶紺弩則是自己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稍遲於十二月中旬啟程。這樣,他們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然而,聶紺弩在蘇聯待了一年半,「竟沒有和康澤談過一回話」,或許緣分沒到吧。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之後,蘇聯方面通知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代表、校理事會成員邵力子回國。邵力子離開莫斯科,國民黨在中山大學再無代表,預示這所學校國共合作的局面即將結束。六月十六日,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將國民黨右派學生遣送回國,以避免他們對其他國民黨學生施加不良影響。遣送回國的通告公布後,共有一百七十餘名國民黨學員提出回國申請。要求回國的國民黨學員人數之多超出了蘇方的預計,因此蘇方決定將國民黨學生分批遣送回國。聶紺弩當時作為國民黨學員,亦於六月底被遣送回國。回國的路線主要是從莫斯科坐火車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然後轉輪船到上海。
在茫茫大海上,聶紺弩和康澤終於開始了談話,「一次考驗性的談話」。據紺弩回憶:
晚飯之後,我們斜倚著鐵欄,大海在旁邊咆哮,海風吹散我們的頭髮,落日的霞光把世界照得通紅。康澤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著我,似乎要望進我心裡去,似乎已經望進我心裡去了。我明知這次談話的嚴重性,但並不心慌!我的綽號叫托爾斯泰,即專心文藝,不問政治的糊塗蛋之意,不怕他們會殺我;別的則真不在乎,我本沒打算跟他們混在一道。我不知道康澤是會談話的呢,還是不會。總之,他在我開口之先,自己談了許多,可惜那些高明的理論,現在不容易記起了,大概說,蘇聯的成功,是民生主義的成功而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合國情的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戴季陶先生的三民主義。我老實告訴他:我不喜歡戴季陶。戴季陶的《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要孫中山承繼中國的道統,要捧孫中山的神主牌進聖廟,是復古,是開倒車,不是革命。也不喜歡孫中山。孫中山的天才,在他把中國問題分成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但他談的卻很壞,比如民族主義,分析日本幾天可以亡中國,英國幾天可以亡中國……結論卻是恢復中國固有道德,這太不可理解了!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姑不論對不對,總是專就都市立論,對廣大的農民與土地問題沒有提起。雖在民生主義之外,講過一次「耕者有其田」,但也只是一個題目,內容對耕者有其田這事幾乎什麼也未說。更不喜歡蔣介石。他,沒有什麼可談的,完完全全的投機軍閥。當我還在黃埔的時候,就曾宣稱,不等兩年,我就要作反蔣運動。
「那麼,那麼,」他像吃一口辣椒似地問:「你對共產黨的看法呢?」
我說:我沒有看法。我的思想沒有出路,也正在此。讀過幾本書,覺得離認識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還很遠,也沒有力量批評,除了在莫斯科,覺得學校裡的投機分子太多以外,我不想談什麼。這裡也許須注解一下:在當時,有許多同學加入共產黨,並非為了革命信仰,而是為了回國後可以作官,那些人後來又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轉變了,比如蔣經國就是一個。所以我在當時確有此感。
「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誠實的人。」說完之後,他和我握手說,他的手捏我的捏得很緊,似乎表示他的話也是誠懇的。「而且倔強」。(〈記康澤〉)
後來康澤告訴聶紺弩,他當時的印象,認為聶太不世故,太任性,近於《三國演義》上的禰衡。如不留心,難免殺身之禍的。但是──康澤又說,正因為如此,反而看得起聶紺弩。
=============================================================
〈始於東京的友誼──聶紺弩與樓適夷〉
聶紺弩說,樓適夷「儘管有時簡單」,「但表裡如一」。樓適夷是聶紺弩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認識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領導。
東京初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左聯宣傳部副部長樓適夷受上級委派出席遠東泛太平洋反戰會議籌備會,和胡風同船去東京。「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陽翰笙指示樓適夷,順帶處理一下在留日革命進步學生文化團體「新興文化研究會」與「社會科學研究會」之間的糾紛問題。據樓適夷回憶:
事情是這樣的,在留日左翼中國學生中,當時有兩個文化團體。一個是「新興文化研究會」(「文化研」),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它的成員是張光人(胡風)、方翰(何定華)、聶衣葛(聶紺弩)、王承志(王達夫)、周穎、樓憲。他們受國內「左聯」的領導。其中成員如胡風,也參加日本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會(「普洛科」),直接受日共的領導。曾先後辦過《文化鬥爭》、《文化之光》等刊物。另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日本分會」(「社研分」)。它的成員有日本法政大學留學生漆憲章、郭兆昌,東京醫專學生汪成模,工大學生習明倫,明治大學學生黃鐘銘等。他們先後辦過《科學半月刊》、《科學新聞》等刊物。這個團體名稱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日本分會,實際在國內,「社研」只是在「左翼社會科學聯盟」指導下的各種群眾社會科學研究小團體的一個總稱,並不存在這名義的總會。他們和國內「社聯」盟員有個別聯繫,實沒有正式的組織關係。兩個團體的問題,是從理論性的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論爭開始的。首先在「文化研」的《文化鬥爭》第二期上,批評了「社研分」方面提出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言論;並在《文化鬥爭》第三、四期中,明白闡述了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從理論鬥爭,發展到宗派的指責。例如在一期《科學半月刊》上發表了編委的聲明,申述「社研分」在留日學生運動中歷年的鬥爭歷史,認為「文化研」的成員對這種歷史是不了解的。於是《文化鬥爭》上又以來稿名義,發表了翳鍋(按,即聶紺弩筆名)的《休矣,科學半月刊》和細鴛的《答〈科學〉對〈文鬥〉的批判》,駁斥「社研分」的自我炫耀,名之為「面子主義」與「風頭主義」。這個糾紛一直鬧到指摘有不良分子向日本員警告密的嚴重程度。(〈關於遠東反戰大會〉)
為了解決這個糾紛,樓適夷以「文總」代表身分找兩個團體負責人談話,瞭解事情的實況。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訪談,得出以下結論:產生糾紛的原因主要在「社研」一方。「社研」對其他組織進行不負責任的批判,不相信革命的日本文化組織,不與這些組織取得聯繫。另一方面,「文化研」的組織方針是正確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文化研」的缺點是對「社研」的批判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根據以上結論,特訂出以下三點方針:立即停止攻擊;兩組織同時解散,接受日本文化組織的領導,要改變活動方式;在重新組織的過程中,「社研」的全體成員應該就以前對其他組織的逃避態度進行自我批判,接受日本文化組織的領導,同時,還應同「文化研」相互協作,共同前進。
樓適夷調解完就回國了。接著發生小林多喜二被害事件,不久聶紺弩、周穎、胡風等人,也在東京被捕,關押數月後遭受驅逐,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回到上海。
同年九月,樓適夷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直至一九三七年出獄。
建國前夕
兩人再次短暫相見,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聶紺弩和樓適夷等人共同參加了在漢口胡風家裡組織的「抗戰以後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
十年之後兩人才真正相聚。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聶紺弩輾轉抵達香港。正式恢復了中共黨組織關係後,與以群(黨小組長)、樓適夷、蔣天佐等人在同一黨小組參加各種活動。
聶紺弩單身一人住在香港中國勞動協會的集體宿舍裡,樓適夷一早從九龍渡海去找他,他大半還懶洋洋地剛從床上起身,好像還沒睡足的樣子。若樓適夷編刊物,要稿子,他總是有求必應,答應得很痛快,要什麼有什麼,幾乎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不會讓人久盼。
樓適夷說:「可那個脾氣也怪,有一次上香港,在德輔道還不知是皇后道碰上了,他一把拉我,上了平時我不大敢上門的一家什麼外國招牌的高級咖啡館的大廳,喝喝咖啡,吃點西點,兩個人親熱熱,談得津津有味。忽然他站起來說:『好,我走了,你付錢。』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了。我原以為是他請我開洋葷,樂得享受一下子,現在可只好把剛從報社領來、準備買米回家的幾塊錢,硬著頭皮傾囊而出,暗暗嘆了口氣,想想『紺弩嘛,你什麼辦法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聶紺弩和樓適夷、蘇怡作為香港的代表,坐船北上,赴北平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大沽口賓館住了一晚,大家上火車赴北京。紺弩倒好,當大家都上車了,偏偏找不到人影,火車是不等待旅客的,沒奈何,樓適夷和夫人黃煒只好帶上他的寶貝女兒海燕,同大夥一起先去北京。到了北京住在前門外的一家旅館裡,大家都忙著開會,紺弩又讓不開會的黃煒照顧他的女兒,可他剛開完幾天會,又獨自跑得沒影子,甚至兩三天都沒回來。於是樓適夷夫婦又暫時成了海燕的保護人。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