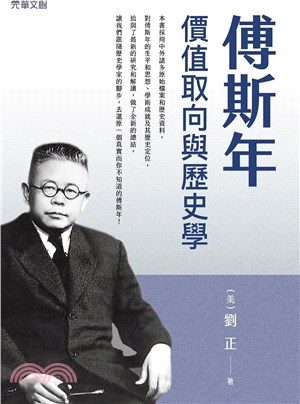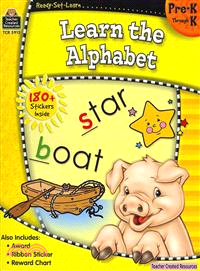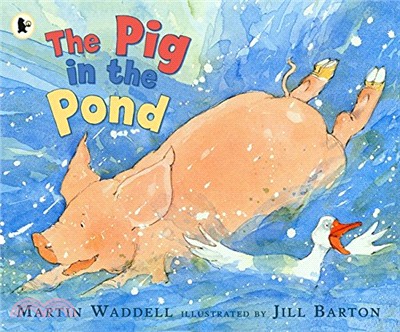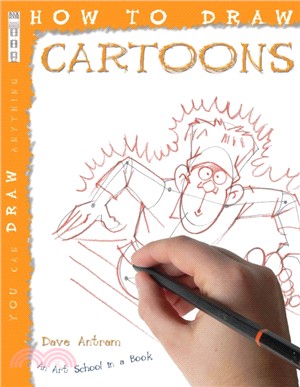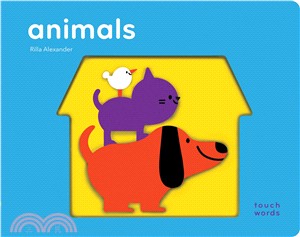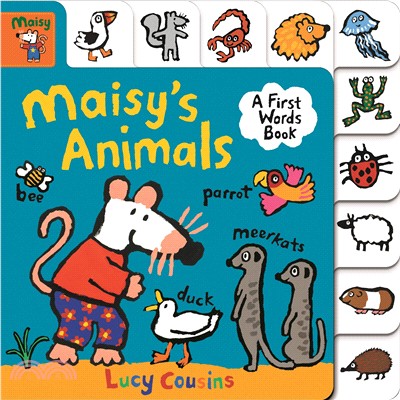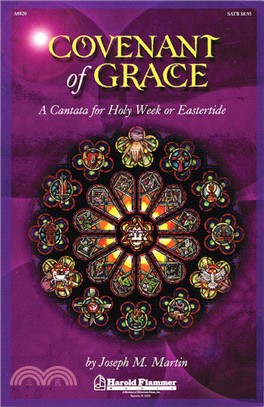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這部將近30萬字的專著,使用原始檔案對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及其歷史學給與了最新的研究和解讀。尤其是傅斯年的國民黨員身份的認證、長期參加國民黨部組織活動、和軍情機構保持長期秘密聯繫等等重大歷史事實,都是第一次被劉正教授披露出來!更為重要的是:劉正教授對傅斯年炮打宋子文的行為給與了深刻的批判,他肯定了宋子文的清廉和無貪腐行為。並且對傅斯年炮打孔祥熙的行為給出了最新的調查和結論。該書還特別批判了學術界不負責任的誇大傅斯年的各類作品。
本書還原一個真實而你不知道的傅斯年!
本書採用中外諸多原始檔案和歷史資料,
對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學術成就及其歷史定位,
給與了最新的研究和解讀,做了全新的總結,
讓我們跟隨歷史學家的腳步,去還原一個真實而你不知道的傅斯年!
本書還原一個真實而你不知道的傅斯年!
本書採用中外諸多原始檔案和歷史資料,
對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學術成就及其歷史定位,
給與了最新的研究和解讀,做了全新的總結,
讓我們跟隨歷史學家的腳步,去還原一個真實而你不知道的傅斯年!
作者簡介
(美)劉正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清代學術世家直系後裔,高祖系著名歷史學家和經學家、同治三年進士劉鍾麟。先後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碩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後。曾任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校教授、客座研究員。迄今為止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60餘篇。另有商周歷史和古文字、金文學術、國際漢學、傳統經學、近代歷史和人物等方面學術研究專著40餘部、總篇幅達到1200餘萬字在海內外出版。現為美國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終身教授及該學會學術季刊發行人。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清代學術世家直系後裔,高祖系著名歷史學家和經學家、同治三年進士劉鍾麟。先後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碩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後。曾任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校教授、客座研究員。迄今為止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60餘篇。另有商周歷史和古文字、金文學術、國際漢學、傳統經學、近代歷史和人物等方面學術研究專著40餘部、總篇幅達到1200餘萬字在海內外出版。現為美國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終身教授及該學會學術季刊發行人。
序
引 子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傅斯年出生在山東聊城。
傅斯年,初字夢簪,後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和臺灣大學(一九四九―一九五○)校長。但是他更為學界所熟知的是他創立並長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這個嫉惡如仇而快人快語、身材高胖的傅斯年,有著山東大漢固有的剛烈性情,敢於直言邪惡而不懼得罪權貴,為他贏得了「傅大炮」的美稱。
在他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內,培養了大批歷史學、思想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諸多學術領域的專門人才。尤其是他組織出版了學術著作七十餘種;組織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殷墟甲骨發掘,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和對殷商歷史的研究。傅斯年在傳統歷史學研究方面,他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實物證據和文獻解釋的結合,擺脫傳統故紙堆理論和結論的束縛。特別是他將東西方語言學理論及其成果在現代用到歷史學研究方法中的結合和使用,使得傳統歷史學豁然開朗而煥發出新的光芒,由此而取得了遠超前人的重要的學術建樹和學術成就,因此他有著近現代新史學開山祖師的崇高地位。大陸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曾評價傅斯年說:「凡是真正瞭解傅斯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學問淵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所做的貢獻是很大的。」
傅斯年還組織收購了明清大庫檔案資料,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不僅如此,他還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發展做出了無人能及的重要貢獻。因此之故,胡適對他的評價是:「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二○一五年的西泠秋拍:中外名人手跡暨虛空草堂藏名人書法專場第二○五六號至二○六一號拍品為「傅樂成舊藏傅斯年重要文獻」。其內容涵蓋最近新發現的一大批以傅斯年為中心的珍貴文獻:傅氏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學講學筆記、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抗戰日記、一九四七年與中研院同仁等致傅仁軌題詞冊、一九五○年去世後由傅樂成整理的照片和傳記材料等,煌煌數十種,涵蓋傅斯年身前的學術創作和日常生活,以及身後的文獻整理,傅斯年侄子、歷史學家傅樂成舊藏,為異常豐富的傅斯年相關文獻,亦是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學者們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之一。
如今保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一共有五箱共五千三百多種文獻資料。這是研究他的第一手個人檔案。另外,保存在臺灣國史館和臺灣大學、大陸北京大學和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相關檔案和文獻,也是研究傅斯年必須給與特別關注的核心要點。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突發腦溢血而愕然仙逝;留給中外學術界的是他厚重而深邃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
研究傅斯年的生平及其思想,胡適提出了四個階段劃分說。即:「我們可以把他從做學生時代到死,分為四個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他青年做學生時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壯年個人做學術時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壯年時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國家最危急最動盪的時候的思想。」由此可知,胡適特別看重的是傅斯年晚年的思想,認為這是國家和社會處於最危急和最動盪時期的一個知識人的價值理性及其政治選擇所在。胡適這一劃分是有創建的。大陸和港臺已經出版的傅斯年研究論著卻更多的關注的只是第二和第三部分而已。因此之故,本書尤其關注的則是第三、第四部分時期的傅斯年的生平及其思想。這是本書有別於同類題材著作的最大區別之一。我也很不理解歐陽哲生為何在《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一書中聲稱胡適是按照三個階段來劃分傅斯年生平及其思想的?明明胡適的劃分是四個階段。
傅斯年作為親身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之一,歷經幾十年的風雨滄桑而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和他一同走向街頭的那些同學們,有的成為漢奸,有的成為愚頑,只有他一生高舉著五四精神的大旗,九死不悔地為科學和民主奮鬥了一生。
當然,毋庸諱言,目前為止的傅斯年研究和所出版的傅斯年傳記,大多集中在傅斯年開創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功績和戰後清理偽北京大學的行政措施這兩個核心點上,再點綴一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和訪問延安見聞之傅斯年,僅此而已。雖然每部論著用筆多少不一,但是每部作品中都熱衷於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去宣傳所謂學術清流的傅斯年,為國為民去炮打孔祥熙和宋子文、揭露國民政府高官們的貪腐行為,維持著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政治定論。甚至很多論著及其作者們居然不知道傅斯年很早就是國民黨員,也根本不知道傅斯年多次定期參加國民黨組織的每月一次的「精神月會」(如同大陸共產黨基層各級組織定期舉行的黨員學習和思想彙報)活動。
――當然,這些已經出版和刊行於世的有關傅斯年的文學作品和史學論著,也從未想到傅斯年和國民政府高層、軍事高官及情報機構負責人有著長期的互動關係和個人友誼,正是因為傅斯年屬於蔣介石身邊文武兩大幕僚陣營中的重要成員―如同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出身派系的地方背景的不同而劃分成多個相互傾軋的勢力角逐一樣,蔣介石身邊文官幕僚也截然分成了以孔祥熙和宋子文為首的買辦資本家的集團,和以傅斯年和朱家驊為首的留洋學者集團這兩大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幫派勢力――正是出於對自身政治幫派勢力的維護,這才出現了傅斯年領頭炮打孔祥熙和宋子文等諸多政治事件。這是本書得出的與眾不同的結論之一。
因此,本書非常側重於傅斯年在歷次重大歷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的價值取向及其政治思想、以及在諸多政治事件中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社會作用等角度,基於原始檔案真實的還原傅斯年的人生經歷、政治思想及其學術理性。故此將本書書名定為《傅斯年:價值取向與歷史學》。本書作者在詳細分析和閱覽了中外諸多原始檔案文獻和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傅斯年的生平、思想和學術成就及其歷史定位給與了全新的總結。
好了,請您坐下來,翻開此書,跟著我走進對傅斯年展開一個與眾不同的全新解讀。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傅斯年出生在山東聊城。
傅斯年,初字夢簪,後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和臺灣大學(一九四九―一九五○)校長。但是他更為學界所熟知的是他創立並長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這個嫉惡如仇而快人快語、身材高胖的傅斯年,有著山東大漢固有的剛烈性情,敢於直言邪惡而不懼得罪權貴,為他贏得了「傅大炮」的美稱。
在他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內,培養了大批歷史學、思想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諸多學術領域的專門人才。尤其是他組織出版了學術著作七十餘種;組織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殷墟甲骨發掘,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和對殷商歷史的研究。傅斯年在傳統歷史學研究方面,他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實物證據和文獻解釋的結合,擺脫傳統故紙堆理論和結論的束縛。特別是他將東西方語言學理論及其成果在現代用到歷史學研究方法中的結合和使用,使得傳統歷史學豁然開朗而煥發出新的光芒,由此而取得了遠超前人的重要的學術建樹和學術成就,因此他有著近現代新史學開山祖師的崇高地位。大陸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曾評價傅斯年說:「凡是真正瞭解傅斯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學問淵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所做的貢獻是很大的。」
傅斯年還組織收購了明清大庫檔案資料,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不僅如此,他還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發展做出了無人能及的重要貢獻。因此之故,胡適對他的評價是:「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二○一五年的西泠秋拍:中外名人手跡暨虛空草堂藏名人書法專場第二○五六號至二○六一號拍品為「傅樂成舊藏傅斯年重要文獻」。其內容涵蓋最近新發現的一大批以傅斯年為中心的珍貴文獻:傅氏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學講學筆記、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抗戰日記、一九四七年與中研院同仁等致傅仁軌題詞冊、一九五○年去世後由傅樂成整理的照片和傳記材料等,煌煌數十種,涵蓋傅斯年身前的學術創作和日常生活,以及身後的文獻整理,傅斯年侄子、歷史學家傅樂成舊藏,為異常豐富的傅斯年相關文獻,亦是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學者們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之一。
如今保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一共有五箱共五千三百多種文獻資料。這是研究他的第一手個人檔案。另外,保存在臺灣國史館和臺灣大學、大陸北京大學和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相關檔案和文獻,也是研究傅斯年必須給與特別關注的核心要點。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突發腦溢血而愕然仙逝;留給中外學術界的是他厚重而深邃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
研究傅斯年的生平及其思想,胡適提出了四個階段劃分說。即:「我們可以把他從做學生時代到死,分為四個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他青年做學生時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壯年個人做學術時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壯年時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國家最危急最動盪的時候的思想。」由此可知,胡適特別看重的是傅斯年晚年的思想,認為這是國家和社會處於最危急和最動盪時期的一個知識人的價值理性及其政治選擇所在。胡適這一劃分是有創建的。大陸和港臺已經出版的傅斯年研究論著卻更多的關注的只是第二和第三部分而已。因此之故,本書尤其關注的則是第三、第四部分時期的傅斯年的生平及其思想。這是本書有別於同類題材著作的最大區別之一。我也很不理解歐陽哲生為何在《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一書中聲稱胡適是按照三個階段來劃分傅斯年生平及其思想的?明明胡適的劃分是四個階段。
傅斯年作為親身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之一,歷經幾十年的風雨滄桑而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和他一同走向街頭的那些同學們,有的成為漢奸,有的成為愚頑,只有他一生高舉著五四精神的大旗,九死不悔地為科學和民主奮鬥了一生。
當然,毋庸諱言,目前為止的傅斯年研究和所出版的傅斯年傳記,大多集中在傅斯年開創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功績和戰後清理偽北京大學的行政措施這兩個核心點上,再點綴一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和訪問延安見聞之傅斯年,僅此而已。雖然每部論著用筆多少不一,但是每部作品中都熱衷於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去宣傳所謂學術清流的傅斯年,為國為民去炮打孔祥熙和宋子文、揭露國民政府高官們的貪腐行為,維持著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政治定論。甚至很多論著及其作者們居然不知道傅斯年很早就是國民黨員,也根本不知道傅斯年多次定期參加國民黨組織的每月一次的「精神月會」(如同大陸共產黨基層各級組織定期舉行的黨員學習和思想彙報)活動。
――當然,這些已經出版和刊行於世的有關傅斯年的文學作品和史學論著,也從未想到傅斯年和國民政府高層、軍事高官及情報機構負責人有著長期的互動關係和個人友誼,正是因為傅斯年屬於蔣介石身邊文武兩大幕僚陣營中的重要成員―如同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出身派系的地方背景的不同而劃分成多個相互傾軋的勢力角逐一樣,蔣介石身邊文官幕僚也截然分成了以孔祥熙和宋子文為首的買辦資本家的集團,和以傅斯年和朱家驊為首的留洋學者集團這兩大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幫派勢力――正是出於對自身政治幫派勢力的維護,這才出現了傅斯年領頭炮打孔祥熙和宋子文等諸多政治事件。這是本書得出的與眾不同的結論之一。
因此,本書非常側重於傅斯年在歷次重大歷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的價值取向及其政治思想、以及在諸多政治事件中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社會作用等角度,基於原始檔案真實的還原傅斯年的人生經歷、政治思想及其學術理性。故此將本書書名定為《傅斯年:價值取向與歷史學》。本書作者在詳細分析和閱覽了中外諸多原始檔案文獻和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傅斯年的生平、思想和學術成就及其歷史定位給與了全新的總結。
好了,請您坐下來,翻開此書,跟著我走進對傅斯年展開一個與眾不同的全新解讀。
目次
目 次
引 子
第一章 聊城望族:學生時代的傅斯年
第二章 初試身手:中山大學時期的傅斯年
第三章 橫空出世:史語所早期的考古和整理史料活動
第四章 增加史料:傅斯年和新史學的誕生
第五章 國破身病:奔波在西南聯大中的傅斯年
第六章 價值取向:傅斯年的政治觀
第七章 忠臣本色:傅斯年和蔣介石關係經緯
第八章 懲貪治腐:傅斯年炮打孔祥熙
第九章 相互傾軋:傅大炮轟走宋子文
第十章 歷史誤會:傅斯年出訪延安
第十一章 嫉惡如仇:傅斯年代管下的北京大學
第十二章 霸氣古今:戰後中研院和傅斯年
第十三章 同床異夢:越走越遠的傅斯年和陳寅恪關係
第十四章 歸骨田衡:傅斯年校長和臺灣大學
跋
引 子
第一章 聊城望族:學生時代的傅斯年
第二章 初試身手:中山大學時期的傅斯年
第三章 橫空出世:史語所早期的考古和整理史料活動
第四章 增加史料:傅斯年和新史學的誕生
第五章 國破身病:奔波在西南聯大中的傅斯年
第六章 價值取向:傅斯年的政治觀
第七章 忠臣本色:傅斯年和蔣介石關係經緯
第八章 懲貪治腐:傅斯年炮打孔祥熙
第九章 相互傾軋:傅大炮轟走宋子文
第十章 歷史誤會:傅斯年出訪延安
第十一章 嫉惡如仇:傅斯年代管下的北京大學
第十二章 霸氣古今:戰後中研院和傅斯年
第十三章 同床異夢:越走越遠的傅斯年和陳寅恪關係
第十四章 歸骨田衡:傅斯年校長和臺灣大學
跋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聊城望族:學生時代的傅斯年
傅斯年的七世祖先是清朝開國以後的第一位狀元傅以漸。這個傅以漸,生於一六○九年,卒於一六六五年。字於磐,號星岩,山東聊城人。他的祖籍?是江西永豐。根據《清史稿·列傳二十五·傅以漸》記載,清順治三年,即西曆一六四六年,他獲得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成為殿前欽點的狀元。先被授弘文院編修,而後歷任國史院侍講、左庶子、秘書院侍講、少詹事、國史院學士;乃至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晚年還被加封太子太保。絕對稱得上是朝廷的重臣。
傅氏先塋暨傅狀元塋位於傅墳村東南約二百米處,南臨徒駭河,北眺光岳樓。塋地南北長三百六十米,東西寬一百二十米,佔地約八十畝,塋牆外另有護塋地四十畝,總占地約一百二十畝。塋內碑石林立,柏木森森,蔚爲壯觀。塋門有二,東西並列。其門為單簷歇山頂,高約一丈五尺。門洞一。北向砌石,南面敷磚。西門鐫石門額爲「傅氏先塋」,東門鐫石門額爲「傅狀元塋」。
有塋牆作屏,正面爲砌磚花牆,高約二米,東西南三面塋牆高一米左右。傅氏先塋門前有石獅一對,通座高二米有餘。塋門內有一甬道,迎面不遠處聳立一牌坊,爲重樓三 洞式石坊,北向正中簷下,上鐫橫額「皇恩寵錫」四字,下鐫橫額「一品三世」四字。主間楹聯上聯為:「浩浩蔭功千年篤佑狀元後」;下聯為:「煌煌誥命三代同稱宰相家」。南向鐫額,是上下兩層。上層爲「祖德長光」四字,下爲「修慎叚銘」四字。
路旁對置兩統袞龍冠龜馱石碑,西面一碑鐫「忠樸清慎」四字,東面一碑鐫「文行端良四字」,相傳系康熙皇帝御筆欽賜聖旨碑。
根據《東郡傅氏祖譜》記載,墓地內除傅以漸墓以外,還葬有傅氏家族歷代所出進士四人、舉人七人、監生三十六人、貢生六十六人,布政使二人、知府六人、知縣十二人等人墓。
傅繼勳,傅斯年之曾祖。生於一八○七年,卒於一八六六年。字述之,號玉溪。東郡傅氏十一世祖,十歲能文、善書,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中秀才,十八歲拔貢,分發安徽省,歷任廬江、東流、歙縣、合肥、貴池、全椒、霍山等縣知縣。所至有績,擢升徽州知府,後改任鳳陽知府,特授太平知府、安慶知府。咸豐初年安徽巡撫福濟專摺密奏保以道員署理蕃司(布政使)。其兄長傅繩勳是清嘉慶十九年( 一八一四年) 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軍機處章京及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咸豐元年( 一八五一年) 辭官返鄉。
據說,傅氏祠堂東鄰有一戶人家進士及第後在原址上翻建新齋,加大了房檐。遮擋住了傅家宅院牆。兩家人因此而其糾紛,相持不下,告到縣衙。傅家人則同時寫信給在京爲官傅以漸。他接到信後揮筆寫下四句詩:千里來書爲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傅家人見信後立即拆牆,將牆基後退三尺,並主動撤訴。鄰居見狀,十分感動,也退讓三尺。結果形成了至今依然可見的傅氏祠堂東鄰的一條六尺胡同。後來康熙皇帝駐蹕聊城,聞聽此事,遂書「仁義胡同」四個大字以倡義舉。
光緒二十二年陰曆二月十三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傅斯年就生於山東省聊城縣北門內傅家祖宅內。
傅家在聊城當地屬於名門望族, 諜譜學所謂的「 閣老傅」就是其家族祖先。因古城北門裡路東為傅以漸「相府」故址,故此稱之為「閣老傅」。
根據《東郡傅氏族譜》記載,傅家遠祖傅回,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該族譜中記載說:「傅氏其先江西吉安之永豐人,明成化中始祖仕為冠縣令,任滿歸,四子從南,三子留北,有諱祥者,奉母李僑居東昌,李歿城南,祥不忍去,遂占籍焉。」
傅繼勳第三個兒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出生時,其家道進一步衰落。再加之生父早逝。因此,在家學方面影響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風的,應該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生於同治五年。光緒二十年鄉試中舉後,出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但是光緒三十年,傅旭安病逝,年僅三十九歲。
傅斯年的生母李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賀家海人。根據柳堂《複東平範實齋等書》記載:「前奉手示,知曉麓山長(指傅旭安)已歸道山,涕泣之餘,為鬱鬱不樂者累日,似此家貧、親老、子幼,何以為生?欲代謀一善後之策而力有未逮,頃聞諸執事與夏公子溥齋同籌鉅款,發當生息,有此一舉,使山長老親幼子不至凍餒,山長死已瞑目矣。山長誠有造於貴州士子,而士子之所以報之者亦厚矣哉。山長九泉能毋冥感耶。弟與山長交非泛泛,謹遵囑,寄去賻儀百金,即祈附入生息款內,雖為數無多,集腋成裘,未始無補。」
《聯合週報》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裕桓《聶湘溪談傅斯年》一文報導傅斯年同鄉聶湘溪回憶說:「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到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闢地,系統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在他的幼小心靈裡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歷史學家,委以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
而傅斯年成年後對其弟傅斯岩曾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
傅斯年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實際上,在傅斯年的童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就是他的祖父和母親。
光緒二十七年春,傅斯年不滿六歲,傅淦便把他送入了私塾,先後向孫達宸、馬殿仁就讀。當時清朝的科舉制已經廢除了,但聊城的人們仍然對科舉制重開抱有希望。傅斯年小時候,正處於「經降史升」的時期,因此傅斯年自小就酷愛文史,十一歲便讀完了《十三經》,是當地遠近聞名的神童。
光緒三十一年,東昌府和聊城縣行政當局實行教育改革,書院一律改為學堂。傅斯年結束了長達四年的塾學生活,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
一九○九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
關於這時期的生活,傅斯年家族的世交好友英千里曾有文章回憶說:「傅先生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學。當時學校尚無宿舍,他就住在我家裡。那時他年齡十四歲,我才九歲。幾個月以後,學校有了宿舍,他就搬進去了。可是每逢假期,他必到我家裡看望。――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決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和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一種『敬而畏之』的心理。這種心理,雖然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當時,他父親的學生侯延塽從生活上和學業上給與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和甚至學術上的引導。以至於著名學者毛子水特別指出:「傅先生幼時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養的益處很多。就是他生平樂於幫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樣亦不會沒有幾分影響的。」
一九一一年臘月,他與聊城縣紳丁理臣之長女丁馥萃女士結婚。
一九一三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同學中就有日後大名頂頂的袁同禮、毛子水、顧頡剛等人。當時的北京大學預科分為兩部:一部是理工科的預科,二部是文史法科的預科。這一劃分顯然是接受了當時日本大學預科的劃分方法。三年預科學習中,考試三次,他每次都是全班第一。
他在預科三年的學習中,因為對清代張惠言經學的推崇而震驚了當時的任課教師們,以至於北京大學的遺老遺少的國學家們如劉申叔等人以為找到了可以傳承學術衣缽的經學弟子。但是,時代的呼喚,特別是受胡適思想的影響,使得他反而逐漸走上了新文化運動,並且成為新時代思想的積極參與者和開創者。
據說,傅斯年在預科時期就與沈沅等同學成立了「文學會」,創辦了《勸學》雜誌。後來又更名為「雄辯會」。其宗旨乃是意圖提高各位同學的文學素養和邏輯能力,鍛煉演講才能。可見當時的傅斯年已經開始鍛煉自己的領導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這為他日後在北京大學的活動奠定了基礎。
一九一六年夏,他卒業於北京大學預科。秋,他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
根據毛子水的回憶文章記載:「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托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 又,他在北京大學預科的同學伍淑也曾回憶說:「我認識孟真,是在民國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課的第一天。大約在一個上午,上什麼歷史,一位長鬍子的教員來了,分到三張講義,彷彿都是四個字一句的。上課半小時,黑板上寫滿了講義校勘記,感覺到乏味,於是開始注意班上的同學;發現第二排當中一位大胖子有點特別,因為教員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退了課,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馬一樣的同學在課堂的角落談起天來了,圍起一班同學來聽,議論風生,夾雜些笑聲。我就很欣賞他的風度,到他臺子上一看,放了幾本《檢論》,上面有了紅色的批點,卻沒有仔細去看他,下了課,回到宿舍,才打聽到他就是山東傅斯年。」
這一點也可以通過當時羅家倫的回憶得到見證:「就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是要舉發這些錯誤,學生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這是由學生們自己發覺的,並且似乎要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詰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那時候同學們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擔負這個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起來了,分擔的人回答的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學生們也一聲不響,一鞠躬魚貫退出。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當然,因為傅斯年的國學基礎實在超群,以至於當時甚至出現了「當時真正的國學大師如劉申叔、黃季剛、陳伯弢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 這樣的局面。
在此期間,傅斯年曾撰寫《文學革新申義》一文,顯然這是積極地回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而來的,目的也是提倡白話文。而此文的出現還有著同學顧頡剛的功勞。
根據顧頡剛的回憶:「傅斯年本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黃侃教授的高足,而黃侃則是北大裡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為此,胡適評述說:「他認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的改革運動。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話來寫」,進而胡適還引用傅斯年的原話「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
――胡適甚至主張傅斯年到了晚年依然秉持著這樣的見解。
根據胡適的親身回憶,我們知道當時的傅斯年曾經暗中聽課考察剛回國任教的胡適的學問和思想的深淺:
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諸位看過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集,上邊一個七萬字的長序嗎?裡邊曾說到我當時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情形。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剿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因此,這是胡適和傅斯年師生情誼的起點,他們二人從一開始就有著相同和相近的學術理性和價值選擇。
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傅斯年主動致函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出了他主張哲學門應該歸屬理科的看法:「校長先生鈞鑒:月來學生對於吾校哲學門隸屬文科之制度,頗存懷疑之念,謹貢愚見於次。以哲學、文學、史學統為一科,而號曰文科,在於西洋,恐無此學制。旦主大學制度,本屬集合殊國性質至不齊一之學制,而強合之,其不倫不類,一望而知。即以文科一端而論,卒業於哲學門者,乃號『文學士』,文科之內,有哲學門,稍思其義,便生『瓠不呱』之感也。中國人之硏治哲學者,?以歷史為材料,西洋人則?以自然科學為材料。考之哲學歷史,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時,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以歷史為哲學之根據,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學為哲學之根據,其用至溥。美國硏治科學,得博士位者,號『哲學博士』,英國牛津諸大學,硏治哲學,得博士位者,號『科學博士』,於是可知哲學與科學之關係長,而與文學之關係薄也。今文科統括三門,曰哲學,曰文學,曰史學,文史兩途,性質固不齊一。史為科學,而文為藝術,今世有以科學方法,硏治文學原理者,或字此曰 (Science of Literature) (《赫胥黎雜論集》),或字此曰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赫文引他說),然是不過文學硏究之一面,其主體固是藝術,不爲科學也。雖然,文史二事,相用至殷,自通常觀之,史書之文,為文學之一部,而中國『文史』一稱,相習沿用久矣。循名責實,文史二門,宜不必分也。返觀哲學,於文學,絕少聯絡,不可以文史合科之例衡之。」
有鑒於此,傅斯年得出的結論是:「今學生所以主張哲學門應歸入理科者,不僅按名求實,以為哲學不應被以文科之名也,實緣哲學入之文科,眾多誤會,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則大眾對之,觀念頓異,然後謀哲學與理科諸門課程上之聯絡,一轉移間,精神上之變革,為不少矣。」
這封信的觀點和論據都十分幼稚,顯然傅斯年目的是想引起校長對他的特別關注,而非真的想將哲學門納入理科。那個時候,年輕的傅斯年希望表現的心理可以理解。而當時的北京大學也正鼓勵青年學生思想解放、暢所欲言。
雖然這封來信中的觀點顯得過於偏激而且幼稚,但是很榮幸,作為教育家的校長蔡元培親自給他回信答覆說:「傅君以哲學門隸屬文科爲不當,誠然。然組入理科,則所謂文科者,不異將使人視爲空虛之府乎。治哲學者不能不根據科學,即文學史學,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學史學近皆用科學的硏究法也。文學必根據於心理學及美學等,今之實驗心理學,及實驗美學,皆可屬於理科者也。史學必根擄於地質學、地文學、人類學等,是數者,皆屬於理科者也。如哲學可併入理科,則文史亦然。如以理科之名,僅足為自然科學之代表,不足以包文學,則哲學之玄學,亦決非理科所能包也。至於分設文哲理三科,則彼此錯綜之處更多。以上兩法似皆不如破除文理兩科之界限,而合組爲大學本科之爲適當也。蔡元培附識。」
傅斯年和蔡元培一生的師生結緣正是源於此事、此信,其意義對傅斯年來說實在重大。
傅斯年的七世祖先是清朝開國以後的第一位狀元傅以漸。這個傅以漸,生於一六○九年,卒於一六六五年。字於磐,號星岩,山東聊城人。他的祖籍?是江西永豐。根據《清史稿·列傳二十五·傅以漸》記載,清順治三年,即西曆一六四六年,他獲得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成為殿前欽點的狀元。先被授弘文院編修,而後歷任國史院侍講、左庶子、秘書院侍講、少詹事、國史院學士;乃至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晚年還被加封太子太保。絕對稱得上是朝廷的重臣。
傅氏先塋暨傅狀元塋位於傅墳村東南約二百米處,南臨徒駭河,北眺光岳樓。塋地南北長三百六十米,東西寬一百二十米,佔地約八十畝,塋牆外另有護塋地四十畝,總占地約一百二十畝。塋內碑石林立,柏木森森,蔚爲壯觀。塋門有二,東西並列。其門為單簷歇山頂,高約一丈五尺。門洞一。北向砌石,南面敷磚。西門鐫石門額爲「傅氏先塋」,東門鐫石門額爲「傅狀元塋」。
有塋牆作屏,正面爲砌磚花牆,高約二米,東西南三面塋牆高一米左右。傅氏先塋門前有石獅一對,通座高二米有餘。塋門內有一甬道,迎面不遠處聳立一牌坊,爲重樓三 洞式石坊,北向正中簷下,上鐫橫額「皇恩寵錫」四字,下鐫橫額「一品三世」四字。主間楹聯上聯為:「浩浩蔭功千年篤佑狀元後」;下聯為:「煌煌誥命三代同稱宰相家」。南向鐫額,是上下兩層。上層爲「祖德長光」四字,下爲「修慎叚銘」四字。
路旁對置兩統袞龍冠龜馱石碑,西面一碑鐫「忠樸清慎」四字,東面一碑鐫「文行端良四字」,相傳系康熙皇帝御筆欽賜聖旨碑。
根據《東郡傅氏祖譜》記載,墓地內除傅以漸墓以外,還葬有傅氏家族歷代所出進士四人、舉人七人、監生三十六人、貢生六十六人,布政使二人、知府六人、知縣十二人等人墓。
傅繼勳,傅斯年之曾祖。生於一八○七年,卒於一八六六年。字述之,號玉溪。東郡傅氏十一世祖,十歲能文、善書,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中秀才,十八歲拔貢,分發安徽省,歷任廬江、東流、歙縣、合肥、貴池、全椒、霍山等縣知縣。所至有績,擢升徽州知府,後改任鳳陽知府,特授太平知府、安慶知府。咸豐初年安徽巡撫福濟專摺密奏保以道員署理蕃司(布政使)。其兄長傅繩勳是清嘉慶十九年( 一八一四年) 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軍機處章京及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咸豐元年( 一八五一年) 辭官返鄉。
據說,傅氏祠堂東鄰有一戶人家進士及第後在原址上翻建新齋,加大了房檐。遮擋住了傅家宅院牆。兩家人因此而其糾紛,相持不下,告到縣衙。傅家人則同時寫信給在京爲官傅以漸。他接到信後揮筆寫下四句詩:千里來書爲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傅家人見信後立即拆牆,將牆基後退三尺,並主動撤訴。鄰居見狀,十分感動,也退讓三尺。結果形成了至今依然可見的傅氏祠堂東鄰的一條六尺胡同。後來康熙皇帝駐蹕聊城,聞聽此事,遂書「仁義胡同」四個大字以倡義舉。
光緒二十二年陰曆二月十三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傅斯年就生於山東省聊城縣北門內傅家祖宅內。
傅家在聊城當地屬於名門望族, 諜譜學所謂的「 閣老傅」就是其家族祖先。因古城北門裡路東為傅以漸「相府」故址,故此稱之為「閣老傅」。
根據《東郡傅氏族譜》記載,傅家遠祖傅回,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該族譜中記載說:「傅氏其先江西吉安之永豐人,明成化中始祖仕為冠縣令,任滿歸,四子從南,三子留北,有諱祥者,奉母李僑居東昌,李歿城南,祥不忍去,遂占籍焉。」
傅繼勳第三個兒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出生時,其家道進一步衰落。再加之生父早逝。因此,在家學方面影響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風的,應該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生於同治五年。光緒二十年鄉試中舉後,出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但是光緒三十年,傅旭安病逝,年僅三十九歲。
傅斯年的生母李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賀家海人。根據柳堂《複東平範實齋等書》記載:「前奉手示,知曉麓山長(指傅旭安)已歸道山,涕泣之餘,為鬱鬱不樂者累日,似此家貧、親老、子幼,何以為生?欲代謀一善後之策而力有未逮,頃聞諸執事與夏公子溥齋同籌鉅款,發當生息,有此一舉,使山長老親幼子不至凍餒,山長死已瞑目矣。山長誠有造於貴州士子,而士子之所以報之者亦厚矣哉。山長九泉能毋冥感耶。弟與山長交非泛泛,謹遵囑,寄去賻儀百金,即祈附入生息款內,雖為數無多,集腋成裘,未始無補。」
《聯合週報》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裕桓《聶湘溪談傅斯年》一文報導傅斯年同鄉聶湘溪回憶說:「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到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闢地,系統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在他的幼小心靈裡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歷史學家,委以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
而傅斯年成年後對其弟傅斯岩曾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
傅斯年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實際上,在傅斯年的童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就是他的祖父和母親。
光緒二十七年春,傅斯年不滿六歲,傅淦便把他送入了私塾,先後向孫達宸、馬殿仁就讀。當時清朝的科舉制已經廢除了,但聊城的人們仍然對科舉制重開抱有希望。傅斯年小時候,正處於「經降史升」的時期,因此傅斯年自小就酷愛文史,十一歲便讀完了《十三經》,是當地遠近聞名的神童。
光緒三十一年,東昌府和聊城縣行政當局實行教育改革,書院一律改為學堂。傅斯年結束了長達四年的塾學生活,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
一九○九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
關於這時期的生活,傅斯年家族的世交好友英千里曾有文章回憶說:「傅先生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學。當時學校尚無宿舍,他就住在我家裡。那時他年齡十四歲,我才九歲。幾個月以後,學校有了宿舍,他就搬進去了。可是每逢假期,他必到我家裡看望。――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決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和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一種『敬而畏之』的心理。這種心理,雖然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當時,他父親的學生侯延塽從生活上和學業上給與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和甚至學術上的引導。以至於著名學者毛子水特別指出:「傅先生幼時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養的益處很多。就是他生平樂於幫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樣亦不會沒有幾分影響的。」
一九一一年臘月,他與聊城縣紳丁理臣之長女丁馥萃女士結婚。
一九一三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同學中就有日後大名頂頂的袁同禮、毛子水、顧頡剛等人。當時的北京大學預科分為兩部:一部是理工科的預科,二部是文史法科的預科。這一劃分顯然是接受了當時日本大學預科的劃分方法。三年預科學習中,考試三次,他每次都是全班第一。
他在預科三年的學習中,因為對清代張惠言經學的推崇而震驚了當時的任課教師們,以至於北京大學的遺老遺少的國學家們如劉申叔等人以為找到了可以傳承學術衣缽的經學弟子。但是,時代的呼喚,特別是受胡適思想的影響,使得他反而逐漸走上了新文化運動,並且成為新時代思想的積極參與者和開創者。
據說,傅斯年在預科時期就與沈沅等同學成立了「文學會」,創辦了《勸學》雜誌。後來又更名為「雄辯會」。其宗旨乃是意圖提高各位同學的文學素養和邏輯能力,鍛煉演講才能。可見當時的傅斯年已經開始鍛煉自己的領導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這為他日後在北京大學的活動奠定了基礎。
一九一六年夏,他卒業於北京大學預科。秋,他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
根據毛子水的回憶文章記載:「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托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 又,他在北京大學預科的同學伍淑也曾回憶說:「我認識孟真,是在民國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課的第一天。大約在一個上午,上什麼歷史,一位長鬍子的教員來了,分到三張講義,彷彿都是四個字一句的。上課半小時,黑板上寫滿了講義校勘記,感覺到乏味,於是開始注意班上的同學;發現第二排當中一位大胖子有點特別,因為教員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退了課,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馬一樣的同學在課堂的角落談起天來了,圍起一班同學來聽,議論風生,夾雜些笑聲。我就很欣賞他的風度,到他臺子上一看,放了幾本《檢論》,上面有了紅色的批點,卻沒有仔細去看他,下了課,回到宿舍,才打聽到他就是山東傅斯年。」
這一點也可以通過當時羅家倫的回憶得到見證:「就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是要舉發這些錯誤,學生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這是由學生們自己發覺的,並且似乎要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詰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那時候同學們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擔負這個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起來了,分擔的人回答的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學生們也一聲不響,一鞠躬魚貫退出。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當然,因為傅斯年的國學基礎實在超群,以至於當時甚至出現了「當時真正的國學大師如劉申叔、黃季剛、陳伯弢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 這樣的局面。
在此期間,傅斯年曾撰寫《文學革新申義》一文,顯然這是積極地回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而來的,目的也是提倡白話文。而此文的出現還有著同學顧頡剛的功勞。
根據顧頡剛的回憶:「傅斯年本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黃侃教授的高足,而黃侃則是北大裡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為此,胡適評述說:「他認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的改革運動。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話來寫」,進而胡適還引用傅斯年的原話「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
――胡適甚至主張傅斯年到了晚年依然秉持著這樣的見解。
根據胡適的親身回憶,我們知道當時的傅斯年曾經暗中聽課考察剛回國任教的胡適的學問和思想的深淺:
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諸位看過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集,上邊一個七萬字的長序嗎?裡邊曾說到我當時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情形。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剿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因此,這是胡適和傅斯年師生情誼的起點,他們二人從一開始就有著相同和相近的學術理性和價值選擇。
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傅斯年主動致函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出了他主張哲學門應該歸屬理科的看法:「校長先生鈞鑒:月來學生對於吾校哲學門隸屬文科之制度,頗存懷疑之念,謹貢愚見於次。以哲學、文學、史學統為一科,而號曰文科,在於西洋,恐無此學制。旦主大學制度,本屬集合殊國性質至不齊一之學制,而強合之,其不倫不類,一望而知。即以文科一端而論,卒業於哲學門者,乃號『文學士』,文科之內,有哲學門,稍思其義,便生『瓠不呱』之感也。中國人之硏治哲學者,?以歷史為材料,西洋人則?以自然科學為材料。考之哲學歷史,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時,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以歷史為哲學之根據,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學為哲學之根據,其用至溥。美國硏治科學,得博士位者,號『哲學博士』,英國牛津諸大學,硏治哲學,得博士位者,號『科學博士』,於是可知哲學與科學之關係長,而與文學之關係薄也。今文科統括三門,曰哲學,曰文學,曰史學,文史兩途,性質固不齊一。史為科學,而文為藝術,今世有以科學方法,硏治文學原理者,或字此曰 (Science of Literature) (《赫胥黎雜論集》),或字此曰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赫文引他說),然是不過文學硏究之一面,其主體固是藝術,不爲科學也。雖然,文史二事,相用至殷,自通常觀之,史書之文,為文學之一部,而中國『文史』一稱,相習沿用久矣。循名責實,文史二門,宜不必分也。返觀哲學,於文學,絕少聯絡,不可以文史合科之例衡之。」
有鑒於此,傅斯年得出的結論是:「今學生所以主張哲學門應歸入理科者,不僅按名求實,以為哲學不應被以文科之名也,實緣哲學入之文科,眾多誤會,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則大眾對之,觀念頓異,然後謀哲學與理科諸門課程上之聯絡,一轉移間,精神上之變革,為不少矣。」
這封信的觀點和論據都十分幼稚,顯然傅斯年目的是想引起校長對他的特別關注,而非真的想將哲學門納入理科。那個時候,年輕的傅斯年希望表現的心理可以理解。而當時的北京大學也正鼓勵青年學生思想解放、暢所欲言。
雖然這封來信中的觀點顯得過於偏激而且幼稚,但是很榮幸,作為教育家的校長蔡元培親自給他回信答覆說:「傅君以哲學門隸屬文科爲不當,誠然。然組入理科,則所謂文科者,不異將使人視爲空虛之府乎。治哲學者不能不根據科學,即文學史學,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學史學近皆用科學的硏究法也。文學必根據於心理學及美學等,今之實驗心理學,及實驗美學,皆可屬於理科者也。史學必根擄於地質學、地文學、人類學等,是數者,皆屬於理科者也。如哲學可併入理科,則文史亦然。如以理科之名,僅足為自然科學之代表,不足以包文學,則哲學之玄學,亦決非理科所能包也。至於分設文哲理三科,則彼此錯綜之處更多。以上兩法似皆不如破除文理兩科之界限,而合組爲大學本科之爲適當也。蔡元培附識。」
傅斯年和蔡元培一生的師生結緣正是源於此事、此信,其意義對傅斯年來說實在重大。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