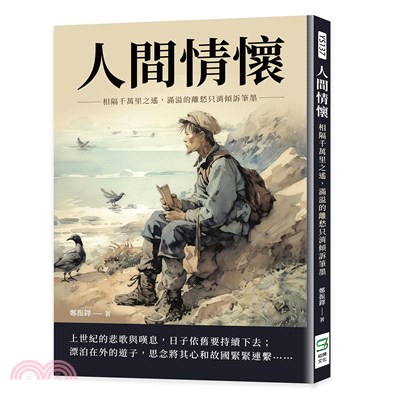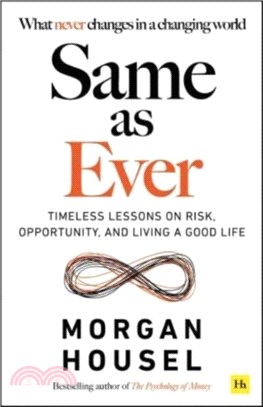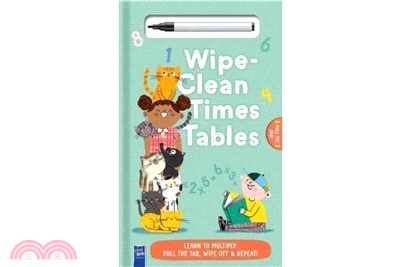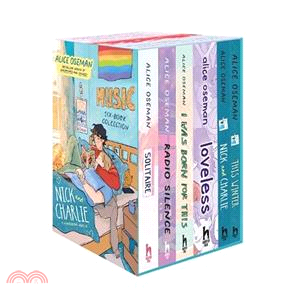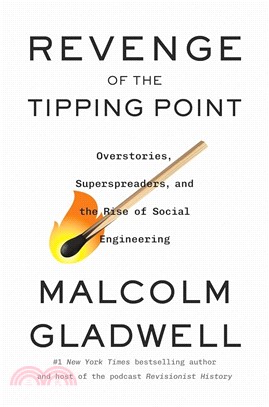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上世紀的悲歌與嘆息,日子依舊要持續下去;
漂泊在外的遊子,思念將其心和故國緊緊連繫……
【蝴蝶的文學】
――鼓動翅膀自在飛翔,掀起生活陣陣波瀾
當我們在和暖宜人的陽光底下,走到一望無際的開放著金黃色的花的菜田間,或雜生著不可數的無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時,大的小的蝴蝶們總在那裡飛翔著。一刻飛向這朵花,一刻飛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雙翼也還在不息不住的搧動著。一群兒童們嘻笑著追逐在牠們之後,見牠們停下了,悄悄的便躡足走近,等到他們走近時,蝴蝶卻又態度閒暇的舒翼飛開。
在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感得全個宇宙都耀著微笑,都泛溢著快樂,每個生命都在生長,在向前或向上發展。
【苦鴉子】
――文學作品時見身影,卻對其叫聲產生無限哀戚
太陽的淡金色光線,弱了,柔和了,暮靄漸漸的朦朧的如輕紗似的幔罩於崗巒之腰、田野之上,西方是血紅的一個大圓盤懸在地平上,四邊是金彩斑斕的雲霞,點染在半天;工作之後,躺在藤榻上,有意無意的領略著這晚霞天氣的圖畫。經過了這樣靜謐的生活的,準保他一輩子不會忘了,至少是要在城市的狹室中不時想起的。不幸這恬靜可愛的山中的黃昏,卻往往為「苦呀,苦呀」的鴉聲所亂。
【海燕】
――遠走他鄉的青年,偶遇海燕引發綿綿鄉愁
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賓主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卻不來光顧,那便很使主人憂戚,他們邀召不到那麼雋逸的嘉賓,每以為自己運命的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的孩子們歡呼著,注意著,沉醉著,曾使幾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憂戚著,或舒懷的指點著,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託身於浮宅之上,奔馳於萬頃海濤之間,不料卻見到我們的小燕子。
【鵜鶘與魚】
――中日戰爭時期,那些為虎作倀的「漢奸」們
鵜鶘們為漁人所餵養,發揮著牠們捕捉魚兒的天性,為漁人幹著這種可怖的殺魚的事業。牠們自己所得的卻是那麼微小的酬報!
當牠們興高采烈的鑽沒人水面以下時,牠們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牠們曾經想到過:鑽出水面,上了船頭時,牠們所捕捉、所吞食的魚兒們依然要給漁人所逐一捏壓出來,自己絲毫不能享用的麼?
漁人卻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閒的抽著板煙,等待著鵜鶘們為他捕捉魚兒。一切的擺布,結果,都是他事前所預計著的。
〔本書特色〕
本書為民初作家鄭振鐸散文合集,一共收錄15篇,包括〈蝴蝶的文學〉、〈蟬與紡織娘〉、〈苦鴉子〉、〈宴之趣〉、〈秋夜吟〉等等,作者借物喻理,透過細膩的文筆、獨到的眼光,還原對周遭事物的觀察,有平靜時期的安逸自然,也有動盪年代的人間百態,時而輕快時而沉重,帶領讀者一齊追憶舊時代的味道。
漂泊在外的遊子,思念將其心和故國緊緊連繫……
【蝴蝶的文學】
――鼓動翅膀自在飛翔,掀起生活陣陣波瀾
當我們在和暖宜人的陽光底下,走到一望無際的開放著金黃色的花的菜田間,或雜生著不可數的無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時,大的小的蝴蝶們總在那裡飛翔著。一刻飛向這朵花,一刻飛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雙翼也還在不息不住的搧動著。一群兒童們嘻笑著追逐在牠們之後,見牠們停下了,悄悄的便躡足走近,等到他們走近時,蝴蝶卻又態度閒暇的舒翼飛開。
在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感得全個宇宙都耀著微笑,都泛溢著快樂,每個生命都在生長,在向前或向上發展。
【苦鴉子】
――文學作品時見身影,卻對其叫聲產生無限哀戚
太陽的淡金色光線,弱了,柔和了,暮靄漸漸的朦朧的如輕紗似的幔罩於崗巒之腰、田野之上,西方是血紅的一個大圓盤懸在地平上,四邊是金彩斑斕的雲霞,點染在半天;工作之後,躺在藤榻上,有意無意的領略著這晚霞天氣的圖畫。經過了這樣靜謐的生活的,準保他一輩子不會忘了,至少是要在城市的狹室中不時想起的。不幸這恬靜可愛的山中的黃昏,卻往往為「苦呀,苦呀」的鴉聲所亂。
【海燕】
――遠走他鄉的青年,偶遇海燕引發綿綿鄉愁
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賓主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卻不來光顧,那便很使主人憂戚,他們邀召不到那麼雋逸的嘉賓,每以為自己運命的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的孩子們歡呼著,注意著,沉醉著,曾使幾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憂戚著,或舒懷的指點著,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託身於浮宅之上,奔馳於萬頃海濤之間,不料卻見到我們的小燕子。
【鵜鶘與魚】
――中日戰爭時期,那些為虎作倀的「漢奸」們
鵜鶘們為漁人所餵養,發揮著牠們捕捉魚兒的天性,為漁人幹著這種可怖的殺魚的事業。牠們自己所得的卻是那麼微小的酬報!
當牠們興高采烈的鑽沒人水面以下時,牠們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牠們曾經想到過:鑽出水面,上了船頭時,牠們所捕捉、所吞食的魚兒們依然要給漁人所逐一捏壓出來,自己絲毫不能享用的麼?
漁人卻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閒的抽著板煙,等待著鵜鶘們為他捕捉魚兒。一切的擺布,結果,都是他事前所預計著的。
〔本書特色〕
本書為民初作家鄭振鐸散文合集,一共收錄15篇,包括〈蝴蝶的文學〉、〈蟬與紡織娘〉、〈苦鴉子〉、〈宴之趣〉、〈秋夜吟〉等等,作者借物喻理,透過細膩的文筆、獨到的眼光,還原對周遭事物的觀察,有平靜時期的安逸自然,也有動盪年代的人間百態,時而輕快時而沉重,帶領讀者一齊追憶舊時代的味道。
作者簡介
鄭振鐸(西元1898~1958年),筆名郭源新、落雪等,中國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景星學社社員,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代表作有:專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小說《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僂集》、《歐行日記》;翻譯《漂鳥集》、《沙寧》、《灰色馬》、《新月集》、《血痕》等書。
目次
蝴蝶的文學
蟬與紡織娘
苦鴉子
宴之趣
離別
海燕
回過頭去──獻給上海的諸友
同舟者
黃昏的觀前街
訪箋雜記
北平
幻境
暮影籠罩了一切
鵜鶘與魚
秋夜吟
蟬與紡織娘
苦鴉子
宴之趣
離別
海燕
回過頭去──獻給上海的諸友
同舟者
黃昏的觀前街
訪箋雜記
北平
幻境
暮影籠罩了一切
鵜鶘與魚
秋夜吟
書摘/試閱
宴之趣
雖然是冬天,天氣卻並不怎麼冷,雨點淅淅瀝瀝的滴個不已,灰色雲是瀰漫著;火爐的火是熄下了,在這樣的秋天似的天氣中,生了火爐未免是過於燠暖了。家裡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出外「應酬」去了。獨自在這樣的房裡坐著,讀書的興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報翻著,翻著,看看它的廣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吧。於是獨自的上了電車,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戲院中,樂隊悠揚的奏著樂,白幕上的黑影,坐著,立著,追著,哭著,笑著,愁著,怒著,戀著,失望著,決鬥著,那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寫了又寫,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話記住在心上了:「有多少次,我是餓著肚子從晚餐席上跑開了。」
這是一句雋妙無比的名句;借來形容我們宴會無虛日的交際社會,真是很確切的。
每一個商人,每一個官僚,每一個略略交際廣了些的人,差不多他們的每一個黃昏,都是消磨在酒樓菜館之中的。有的時候,一個黃昏要趕著去赴三四處的宴會。這些忙碌的交際者真是妓女一樣,在這裡坐一坐,就走開了,又趕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在那一個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趕到再一個地方去了。他們的肚子定是不會飽的,我想。有幾個這樣的交際者,當酒闌燈池,應酬完畢之後,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燒了稀飯來堆補空腸的。
我們在廣漠繁華的上海,簡直是一個村氣十足的「鄉下人」;我們住的是鄉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們過的是鄉間的生活,一月中難得有幾個黃昏是在「應酬」場中度過的。有許多人也許要說我們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個名詞。但我們實在不是如此,我們不過是不慣徵逐於酒肉之場,始終保持著不大見世面的「鄉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幾次,承一二個朋友的好意,邀請我們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個熟人,那一半生客,還要主人介紹或自己去請教尊姓大名,或交換名片,把應有的初見面的應酬的話訥訥的說完了之後,便默默的相對無言了。說的話都不是有著落,都不是從心裡發出的;泛泛的,是幾個音聲,由喉嚨頭溜到口外的而已。過後自己想起那樣的敷衍的對話,未免要為之失笑。如此的,說是一個黃昏在繁燈絮語之宴席上度過了,然而那是如何沒有生趣的一個黃昏呀!
有幾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沒有一個是認識的;請教了姓名之後,也隨即忘記了。除了和主人說幾句話之外,簡直的無從和他們談起。不曉得他們是什麼行業,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性質的人,有話在口頭也不敢隨意的高談起來。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針氈;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來,也不知是什麼味兒。終於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個謊,說身體不大好過,或說是還有應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謠言很多的這幾天當然是更好託辭了,說我怕戒嚴提早,要被留在華界之外──雖然這是無禮貌的,不大應該的,雖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著,然而我卻不顧一切的不得不走了。這個黃昏實在是太難挨得過去了!回到家裡以後,買了一碗稀飯,即使只有一小盞蘿蔔乾下稀飯,反而覺得舒暢,有意味。
如果有什麼友人做喜事,或壽事,在某某花園,某某旅社的大廳裡,大張旗鼓的宴客,不幸我們是被邀請了,更不幸我們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壽,立刻就託辭溜走的,於是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黃昏。常常地張大了兩眼,在尋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緊緊地和他們擠在一起,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時,便至少有兩三人在一塊兒可以談談了,不至於一個人獨自的侷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當中,惶恐而且空虛。當我們兩三個人在津津的談著自己的事時,偶然抬起眼來看著對面的一個座客,他是淒然無侶的坐著;大家酒杯舉了,他也舉著;菜來了,一個人說「請,請」,同時把牙箸伸到盤邊,他也說「請,請」,也同樣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沒有目的,菜完了,他便侷促的獨坐著。我們見了他,總要代他難過,然而他終於能夠終了席方才起身離座。
宴會之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麼,我們將咒詛那第一個發明請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麼,我們也將打倒杜康與狄奧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會卻幸而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也還有別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環境。
獨酌。據說,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時,常見祖父一個人執了一把錫的酒壺,把黃色的酒倒在白瓷小杯裡,舉了杯獨酌著;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來夾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飯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離座了,而他卻還在舉著酒杯,不匆不忙地喝著。他的吃飯,尚在再一個半點鐘之後呢。而他喝著酒,顏微酡著,常常叫道:「孩子,來!」而我們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夾了一塊只有他獨享著的菜蔬放在我們口中,問道:「好吃麼?」我們往往以點點頭答之,在孫男與孫女中,他特別的喜歡我,叫我前去的時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髯的嘴吻著我的面頰。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氣從他的口鼻中直噴出來。這是使我很難受的。
這樣的,他消磨過了一個中午和一個黃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樂趣。然而回想起來,似乎他那時是非常的高興,他是陶醉著,為快樂的霧所圍著,似乎他的沉重的憂鬱都從心上移開了,這裡便是他的全個世界,而全個世界也便是他的。
別一個宴之趣,是我們近幾年所常常領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幾個無所不談的朋友,全座沒有一個生面孔,在隨意的喝著酒,吃著菜,上天下地的談著。有時說著很輕妙的話,說著很可發笑的話,有時是如火如劍的激動的話,有時是深切的論學談藝的話,有時是隨意的取笑著,有時是面紅耳熱的爭辯著,有時是高妙的理想在我們的談鋒上觸著,有時是戀愛的遇合與家庭的與個人的身世使我們談個不休。每個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地袒開了,每個人都把他的向來不肯給人看的面孔顯露出來了;每個人都談著,談著,談著,只有更興奮的談著,毫不覺得「疲倦」是怎麼一個樣子。酒是喝得乾了,菜是已經沒有了,而他們卻還是談著,談著,談著。那個地方,即使是很喧鬧的,很激狹的,向來所不願意多坐的,而這時大家卻都忘記了這些事,只是談著,談著,談著,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起告別的話。要不是為了戒嚴或家庭的命令,竟不會有人想走開的。雖然這些閒談都是瑣屑之至的,都是無意味的,而我們卻已在其間得到宴之趣了──其實在這些閒談中,我們是時時可發現許多珠寶的;大家都互相的受著影響,大家都更進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從那裡得到些教益與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實在的。」
不會喝酒的人每每這樣的被強迫著而喝了過量的酒。面部紅紅的,映在燈光之下,是向來所未有的壯美的風采。
「聖陶,乾一杯,乾一杯!」我往往地舉起杯來對著他說,我是很喜歡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這樣快,喝酒的趣味,在於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於『乾杯』!」聖陶反抗似的說,然而終於他是一口乾了。一杯又是一杯。
連不會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時,竟也被我們強迫地乾了一杯。於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發出於心之絕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節,合家團團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幾雙的紅漆筷子,連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著一雙筷子,都排著一個座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鬧著吵著,母親和祖母溫和的笑著,妻子忙碌著,指揮著廚房中廳堂中僕人們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種融融泄泄的樂趣,為孤獨者所妒羨不止的,雖然並沒有和同伴們同在時那樣的宴之趣。
還有,一對戀人獨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還有,從戲院中偕了妻子出來,同登酒樓喝一二杯酒;還有,伴著祖母或母親在熊熊的爐火旁邊,放了幾盞小菜,閒吃著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臨其境的人心醉神情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雖然是冬天,天氣卻並不怎麼冷,雨點淅淅瀝瀝的滴個不已,灰色雲是瀰漫著;火爐的火是熄下了,在這樣的秋天似的天氣中,生了火爐未免是過於燠暖了。家裡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出外「應酬」去了。獨自在這樣的房裡坐著,讀書的興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報翻著,翻著,看看它的廣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吧。於是獨自的上了電車,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戲院中,樂隊悠揚的奏著樂,白幕上的黑影,坐著,立著,追著,哭著,笑著,愁著,怒著,戀著,失望著,決鬥著,那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寫了又寫,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話記住在心上了:「有多少次,我是餓著肚子從晚餐席上跑開了。」
這是一句雋妙無比的名句;借來形容我們宴會無虛日的交際社會,真是很確切的。
每一個商人,每一個官僚,每一個略略交際廣了些的人,差不多他們的每一個黃昏,都是消磨在酒樓菜館之中的。有的時候,一個黃昏要趕著去赴三四處的宴會。這些忙碌的交際者真是妓女一樣,在這裡坐一坐,就走開了,又趕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在那一個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趕到再一個地方去了。他們的肚子定是不會飽的,我想。有幾個這樣的交際者,當酒闌燈池,應酬完畢之後,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燒了稀飯來堆補空腸的。
我們在廣漠繁華的上海,簡直是一個村氣十足的「鄉下人」;我們住的是鄉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們過的是鄉間的生活,一月中難得有幾個黃昏是在「應酬」場中度過的。有許多人也許要說我們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個名詞。但我們實在不是如此,我們不過是不慣徵逐於酒肉之場,始終保持著不大見世面的「鄉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幾次,承一二個朋友的好意,邀請我們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個熟人,那一半生客,還要主人介紹或自己去請教尊姓大名,或交換名片,把應有的初見面的應酬的話訥訥的說完了之後,便默默的相對無言了。說的話都不是有著落,都不是從心裡發出的;泛泛的,是幾個音聲,由喉嚨頭溜到口外的而已。過後自己想起那樣的敷衍的對話,未免要為之失笑。如此的,說是一個黃昏在繁燈絮語之宴席上度過了,然而那是如何沒有生趣的一個黃昏呀!
有幾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沒有一個是認識的;請教了姓名之後,也隨即忘記了。除了和主人說幾句話之外,簡直的無從和他們談起。不曉得他們是什麼行業,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性質的人,有話在口頭也不敢隨意的高談起來。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針氈;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來,也不知是什麼味兒。終於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個謊,說身體不大好過,或說是還有應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謠言很多的這幾天當然是更好託辭了,說我怕戒嚴提早,要被留在華界之外──雖然這是無禮貌的,不大應該的,雖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著,然而我卻不顧一切的不得不走了。這個黃昏實在是太難挨得過去了!回到家裡以後,買了一碗稀飯,即使只有一小盞蘿蔔乾下稀飯,反而覺得舒暢,有意味。
如果有什麼友人做喜事,或壽事,在某某花園,某某旅社的大廳裡,大張旗鼓的宴客,不幸我們是被邀請了,更不幸我們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壽,立刻就託辭溜走的,於是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黃昏。常常地張大了兩眼,在尋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緊緊地和他們擠在一起,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時,便至少有兩三人在一塊兒可以談談了,不至於一個人獨自的侷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當中,惶恐而且空虛。當我們兩三個人在津津的談著自己的事時,偶然抬起眼來看著對面的一個座客,他是淒然無侶的坐著;大家酒杯舉了,他也舉著;菜來了,一個人說「請,請」,同時把牙箸伸到盤邊,他也說「請,請」,也同樣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沒有目的,菜完了,他便侷促的獨坐著。我們見了他,總要代他難過,然而他終於能夠終了席方才起身離座。
宴會之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麼,我們將咒詛那第一個發明請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麼,我們也將打倒杜康與狄奧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會卻幸而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也還有別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環境。
獨酌。據說,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時,常見祖父一個人執了一把錫的酒壺,把黃色的酒倒在白瓷小杯裡,舉了杯獨酌著;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來夾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飯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離座了,而他卻還在舉著酒杯,不匆不忙地喝著。他的吃飯,尚在再一個半點鐘之後呢。而他喝著酒,顏微酡著,常常叫道:「孩子,來!」而我們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夾了一塊只有他獨享著的菜蔬放在我們口中,問道:「好吃麼?」我們往往以點點頭答之,在孫男與孫女中,他特別的喜歡我,叫我前去的時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髯的嘴吻著我的面頰。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氣從他的口鼻中直噴出來。這是使我很難受的。
這樣的,他消磨過了一個中午和一個黃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樂趣。然而回想起來,似乎他那時是非常的高興,他是陶醉著,為快樂的霧所圍著,似乎他的沉重的憂鬱都從心上移開了,這裡便是他的全個世界,而全個世界也便是他的。
別一個宴之趣,是我們近幾年所常常領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幾個無所不談的朋友,全座沒有一個生面孔,在隨意的喝著酒,吃著菜,上天下地的談著。有時說著很輕妙的話,說著很可發笑的話,有時是如火如劍的激動的話,有時是深切的論學談藝的話,有時是隨意的取笑著,有時是面紅耳熱的爭辯著,有時是高妙的理想在我們的談鋒上觸著,有時是戀愛的遇合與家庭的與個人的身世使我們談個不休。每個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地袒開了,每個人都把他的向來不肯給人看的面孔顯露出來了;每個人都談著,談著,談著,只有更興奮的談著,毫不覺得「疲倦」是怎麼一個樣子。酒是喝得乾了,菜是已經沒有了,而他們卻還是談著,談著,談著。那個地方,即使是很喧鬧的,很激狹的,向來所不願意多坐的,而這時大家卻都忘記了這些事,只是談著,談著,談著,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起告別的話。要不是為了戒嚴或家庭的命令,竟不會有人想走開的。雖然這些閒談都是瑣屑之至的,都是無意味的,而我們卻已在其間得到宴之趣了──其實在這些閒談中,我們是時時可發現許多珠寶的;大家都互相的受著影響,大家都更進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從那裡得到些教益與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實在的。」
不會喝酒的人每每這樣的被強迫著而喝了過量的酒。面部紅紅的,映在燈光之下,是向來所未有的壯美的風采。
「聖陶,乾一杯,乾一杯!」我往往地舉起杯來對著他說,我是很喜歡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這樣快,喝酒的趣味,在於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於『乾杯』!」聖陶反抗似的說,然而終於他是一口乾了。一杯又是一杯。
連不會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時,竟也被我們強迫地乾了一杯。於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發出於心之絕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節,合家團團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幾雙的紅漆筷子,連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著一雙筷子,都排著一個座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鬧著吵著,母親和祖母溫和的笑著,妻子忙碌著,指揮著廚房中廳堂中僕人們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種融融泄泄的樂趣,為孤獨者所妒羨不止的,雖然並沒有和同伴們同在時那樣的宴之趣。
還有,一對戀人獨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還有,從戲院中偕了妻子出來,同登酒樓喝一二杯酒;還有,伴著祖母或母親在熊熊的爐火旁邊,放了幾盞小菜,閒吃著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臨其境的人心醉神情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