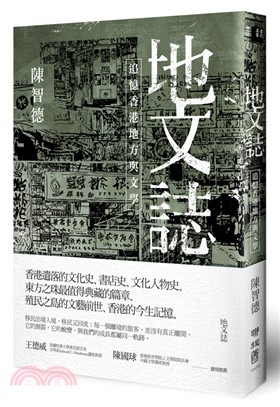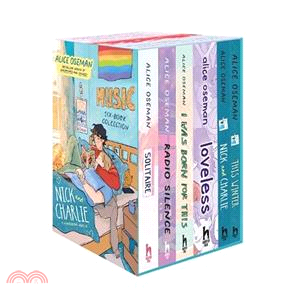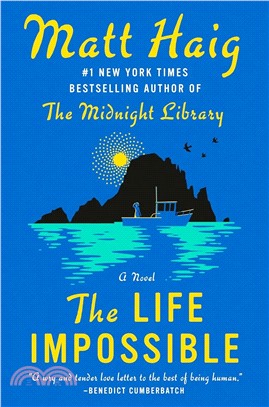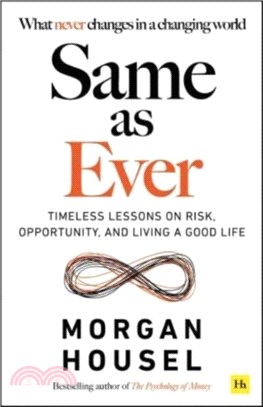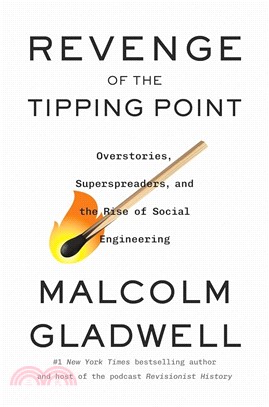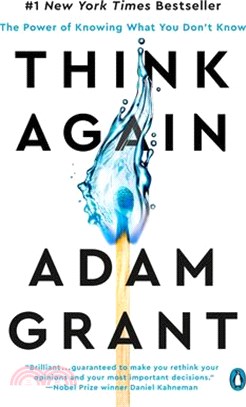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商品資訊
系列名:當代名家‧陳智德作品集
ISBN13:9789570870428
出版社:聯經
作者:陳智德
出版日:2023/08/24
裝訂/頁數:平裝/288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香港遺落的文化史、書店史、文化人物史
東方之珠最值得典藏的篇章
殖民之島的文藝前世、香港的今生記憶
香港詩人、學者作家陳智德
以文學、歷史、音樂、流行文化為範疇,結合史料、詩作、典故、圖像
為讀者一一細數香港的前世今生,填寫香港記憶的補遺
讀《地文誌》,我看到我城我民的前世今生。
──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陳智德為香港的地景與藝文做出觀察的宏願不容小覷。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然而如陳所言,「『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誠哉斯言。破卻陸沉,洞昭盲瞽,陳智德的香港抒情考古,可以如是!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最後一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任務,經過一段搬遷日子後,原來的客運大樓被分割為許多不同部分重新開放,分租給各種不同機構,作許多不同用途。二○○三年四月,「沙士」陰霾籠罩的日子,我重回沒有飛機升降的啟德機場客運大樓,穿梭於人跡杳杳的不同區間,記下種種不由自主的割裂。每感它的割裂,它的蛻變,與我們的成長都屬同一軌跡。
──陳智德
香港做為亞洲重要經濟樞紐,有其獨特的商業地位。長久以來,其文學與文化領域的關鍵發展需要更深度的論述。香港詩人、學者陳智德在《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一書裡,從啟德機場的停用開始,回顧歷史脈絡,描繪今日香港的現狀。「香港反覆被稱甚至自稱為『文化沙漠』,彷彿樂此不疲」,殊不知有《中國學生周報》、《70年代雙週刊》、《盤古》、《大拇指》、《詩風》、《突破》、《素葉文學》等等幾代人創建的文化刊物,像旺角的書店就是不可抹滅的閱讀記憶:「至今日為止,旺角仍是九龍地區的書店集中地,多家樓上書店密集地分布在旺角的心臟地域──西洋菜街及奶路臣街一帶,且有它歷史的痕跡:已消失或已搬遷的包括南山、五車、洪葉、文星、東岸、貽善堂、實用、復興、精神、學峰、紫羅蘭;仍健在的有田園、新亞、樂文、學津,這四家書店至少經營了二、三十年,都是我中學時代就開始流連的所在。」
《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糅合了不同的文類,例如地方紀事、掌故拾遺、成長回憶、文學談片,同時穿插個人及他人的詩作。全書共分兩卷,【上卷】「破卻陸沉」──以文學為樞紐,編列地區為經緯,旁及述說、引用、評論多位香港前輩和同代作者的香港城市故事、經驗描寫,和自己的地方生活體驗互為闡發。【下卷】「藝文叢談」則以書與城為主調:香港的老書店、二樓書店、文藝刊物,讀者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在終年不散的灰塵和霉味中,那些被遺忘的書店、文藝刊物和它們承載的傳統,以及書店老闆、文化人,陳智德以文字為他/它們留下動人的記憶。
陳智德在《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裡,範疇橫跨文學、歷史、音樂,結合史料、詩作與圖片;他大膽提問:當許多人視「本土」──尤其是「香港的本土」為一種「狹窄」的題材時,又對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學有多少認識?這是對地方書寫的提醒,也戳破人們慣常的歷史觀,為香港的身世補充了最重要的文化篇章。
作者簡介
筆名陳滅,1969年香港出生,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及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助理編輯(1994-1997)、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客席授課導師(2004-2006)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站計劃」副研究員(2008-2009)等職,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1992年獲東海文藝創作獎詩組首獎,1993年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社會組散文佳作,另獲1990、1994、1996及2002年度之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獎項。評論集《愔齋書話》於2007年獲第九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詩集《市場,去死吧》於2009年獲第十屆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推薦獎,2012年獲選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著有詩集《市場,去死吧》、《低保真》、《單聲道》;評論集《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愔齋讀書錄》、《愔齋書話》及散文集《抗世詩話》等,另編有《三、四○年代香港詩選》、《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詩選1997-2010》等。
序
序一(節錄)
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誰是陳滅?
很多年前,故人影印《信報》一篇專欄文章給我看,還笑著臉,說:「是你的仇人寫的吧?」文章作者是「陳滅」,內容是評論我和朋友合編的一本書。故人的言說方式,是文人的,迷信文字有其魔力;也是庶民的,一切行為以實用為尚,不作無謂之事。
我回說:「你沒有看到『滅』字的『火』嗎?」
我這個解釋,當然不合字源之學;可是,我看到的,確是陳滅不滅的火,那「抗世」的火。後來看到更多陳滅的詩與詩話。
後來認識了嶺南大學的博士陳智德。看到智德在研討會宣讀論文,解說香港文學歷史,編集香港的詩與詩論;從他說話的節奏、語調,的確是唯智尚德。
在香港,如果對文學還未絕望,大概有賴心中的一團火。在香港,如果要提倡文學,還是需要智慧、需要具備「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意志。
讀《地文誌》,我既看到陳滅,也看到陳智德:「歷史不容竄改?歷史一向被現實竄改,還有生命、故事、文學、香港或什麼都可以……。」「音樂是一種美,搖滾教我們看穿假象。假象不美,假象令人作嘔生厭,但有時竟和美融合,這是悲哀的。……」「由一九九七年起,香港的時鐘開始撥快,各種事物加速消逝,彼此的距離愈行愈遠……。」
讀《地文誌》,我看到我城我民的前世今生。
我的父母長輩,經歷戰火亂離、時代興廢,別去南中國的故土,只帶來「休洗紅」的文化記憶;同鄉聚居,他們營造了香港又一個互相取暖的「半下流社會」,無效地抗衡城市經濟與一切的聲光化電;父親手握一管充滿鄉音濃情的筆,心中有一面虛幻的旗。這許多的精神史,以超簡式的書寫,呈現為《地文誌》。
打開《地文誌》,還見到我的童年往事、我的青葱歲月,灑落在九龍半島的西岸。「芒角」是我的「好望角」;爸爸跟小時候的我說:不要怕迷路,只要你記得彌敦道,你一定可以回到旺角西陲,你的家。像同時代的小孩、少年,我們還有一個可以歷險成長的實景空間;書,還是可以手捧揭頁的。花近高樓,登樓訪書可以望盡天涯;由彌敦道的「港明」,花園街的「寰球」,洗衣街的「新亞」、「南山」,西洋菜街的「田園」,到奶路臣街的「學津」、「學峰」、「文星」……記憶中就是不歇之數;最有象徵意義的,莫如回轉地下,離棺材店不遠的「廣華」,店內灰塵撲面,盈眼是朦朧書影。
如斯種種,感盪心靈;《地文誌》對於一輩香港人如我,弦動共鳴自是縈迴不盡。
然而,《地文誌》不止於傷逝的金鍼指南。智德寫《地文誌》,寄心乎晚明的《帝京景物略》。
方逢年序《帝京略》說:「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燕難為書,燕不可無書也。」
一個城市的故事,真的這麼難說?
序二
破卻陸沉──陳智德的「抒情考古」書寫/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香港不是一塊滋潤文學生長的地方,但香港文學卻有靈根自植的能力。
多少年來,香港的文人墨客,從侶倫到也斯、從劉以鬯到董啟章、從張愛玲到西西,為他們生長或移駐於斯的土地書寫他們的心影屐痕。筆鋒所至,皆成有情文章。而放大角度,香港本身的歷史與地理從無到有,或璀璨、或滄桑,又何嘗不已經就是一種傳奇,一種文學?
陳智德先生是詩人、學者,也是地道的香港人。他憑著個人對香港文學的熱愛、以及對文學香港的深情,寫出了一本獨特的散文集《地文誌》。這本散文集糅合了不同的文類,地方紀事、掌故拾遺、成長回憶、文學談片,無不引人入勝。述之敘之不足處,又穿插個人及他人的詩作。以此更加凸顯本書作為極具魅力的個人書寫風格。
陳智德娓娓回憶香港啟德機場的升沉,如何與九龍半島、甚至遺民歷史相輔相成;北角的一晌繁華,竟成為三代詩人李育中、馬朗、也斯的生涯註腳;維多利亞公園見證香港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以及與作家如辛其氏等的創作起伏。屯門萬丈高樓興起,掩不住原來魑魅虎狼的陰影;調景嶺曾經的風風雨雨,又埋藏多少人的家國心事?
少年陳智德出入港九大街小巷,但讓他駐足最久的地方是書店。這是香港文學最奇特的所在。陋街深處,危樓一角,卻偏偏散發出書香,或更多時候是霉臭,的味道。廣華復興,青文東岸,就在狹仄的空間中、層三疊四的書堆裡,一個文學啟蒙的故事緩緩展開。曾幾何時,少年已經微近中年,那一間間書店已經歇業關門,那灰塵中的風雅只成為少數人的回憶。
在這層意義上,《地文誌》所要從事的是一個人的考古學。陳智德其生也晚,已經錯過香港文學無端興起的那神奇的一刻,而後現代加後社會主義治下的香港,以往人文景觀快速崩毀。他尋尋覓覓,鉤沉訪舊,無非期望在一個時代灰飛煙滅之前,考證、存留一鱗半爪的證據。就像在熙熙攘攘的旺角鬧市地下,誰能想像能發掘出漢代、晉代、唐代文物?在浮光掠影的生活中,想必還有珍貴的文學靜靜等待有緣的讀者:
事物之真象,向為我輩所執著,然詩人筆下之城市,每多流光幻象,唯秉燭探照,終見本真幽隱其內。
陳智德的考古學又是一種抒情考古學,此無他,他考察的對象是文字的因緣,情感的流轉,想像的歸宿。「抒情考古」語出汪曾祺,原用來描述業師沈從文後半生從事工藝美術研究的方法。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無緣繼續創作,卻在工藝史裡發現了另外一種「創作」的可能,並從中有了深刻體悟。沈在《抽象的抒情》(一九六一)寫道,生命的發展「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遠的空間,讓另外一時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陳智德也許無從比擬大師所經歷的生命斫喪。但在面對歷史的另一刻僵局時,是否也心有慼慼焉?用陳所敬重的女作家鍾玲玲的話來說,《地文誌》所要追尋記錄的正是「時光中無法摧毀的糊狀物,終於凝固為形狀不一的物質,成為心靈中,易碎的珍愛物」。
《地文誌》的書名或有諧仿《漢書.藝文志》─中國最早藝文經籍的目錄─的意圖。無論如何,陳智德為香港的地景與藝文做出觀察的宏願不容小覷。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然而如陳所言,「『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誠哉斯言。破卻陸沉,洞昭盲瞽,陳智德的香港抒情考古,可以如是!
前記
陳智德
我的文學啟蒙不在學校或課本,而是初中時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帶的路邊書攤,繼而是樓上的書店,仍記得初次讀到一九四八年上海星群版辛笛《手掌集》、一九七五年臺北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楊牧《瓶中稿》和一九八二年香港素葉版馬博良《焚琴的浪子》三書的情形,盛載真正文藝的書籍那溫婉而堅軔的本質,教我著迷而無從脫離。
辛笛〈夏夜的和平〉一詩這樣寫上海:「最後一列電車回廠了/都市心臟停止它不自然的抽搐」,楊牧〈瓶中稿〉有這樣的名句:「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馬博良〈北角之夜〉這樣寫香港的北角:「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三首詩談的都是作者自己的本土經驗,正給時屆初中年紀的我以莫大的震動和啟發。
由那時開始,我矢志從事文學,不覺流連至今。從古典到現代,從中華到香港,無論走到何處,都離不開腳踏的土地。本土經驗本就是我們的成長以至更大範圍下的共同體社會經驗,我們生活其中,也愈發認清我與非我的真幻;是以書寫本土絕不等同歌頌本土,本土也有許多負面事物,教我們疾首,我們有時也嚮往遙遠的他方、願意承接更古老的傳統、參與更宏大的整體世界,但知每一個出發點,不都由當下腳踏的土地開始。
二○一二年,我有幸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香港作家,八月底出發赴美,參與為期兩個半月的計畫,與國際作家交流之餘,我把握近幾年難得的空閒,起草構思多時的《地文誌》系列寫作,本書大部分文章的初稿,都在愛荷華完成。除了珍貴的閒暇,也認識到國際作家層次不同的本土關懷,讓我再思本土經驗的普世共性。十一月中回港後,以僅有的工餘時間修訂內容、補充資料,再加入若干增補過內容的舊文,耗時多月始得完書。
本書以散文形式撰寫,結合香港文學的地方書寫、歷史掌故和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穿插他人及我個人的相關文學片段,節錄的文字有新詩也有舊詩,有散文也有小說的片段,由此引申出相應的評論性文字,但不同於學術評論,主要用以結合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互為闡發,也嘗試讓散文與自己的詩作融合,有時,散文部分成了詩的載體,有時是詩作為文意未盡的延伸。本書追跡地方性的文學故事,建構基於本土文化認同的情志和關懷,這樣的散文創作,用現有的術語來說,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應該不完全等同,我姑且暫稱為一種「地文誌體」。
我知道許多人視「本土」─尤其是「香港的本土」為一種「狹窄」的題材,我不想在這裡申辯,只想說,香港一地,無論感覺多狹窄,從文學的角度,與地球每寸土地、每個城市都是平等的。我時常自警於本土之可能褊狹和自我封閉,然而「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如果本書最終也淪入「狹窄」之議,責任在我力有不逮,與香港無干。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首有言:「夫都燕,天人所合發也。陰陽異特,睠顧維宅,吾知之以天。流泉膴原,士烝民止,吾知之以人。此《帝京景物略》所為著也。」本書也差不多以同一態度去寫香港,也同樣視香港是由「天人所合發」,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歷史,以至由土地化生的願望、情志,本歸於更超越的共同。願這書屬於香港,也獻予所有關懷土地的人、寫給與大地同一呼息的地方─即使不現實,至少可作此文學幻想。是為記。
目次
序一/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陳國球
序二/破卻陸沉──陳智德的「抒情考古」書寫──王德威
前記
【上卷】破卻陸沉
白光熄滅九龍城
維園可以竄改的虛實
我的北角之夜
破卻陸沉:從芒角到旺角
高山搖滾超簡史
虎地的學院和魑魅
旗幟的倒影:調景嶺一九五○─一九九六
黃幡故事探源
達德學院的詩人們
浪蕩兒童樂園
【下卷】藝文叢談
書和城
廣華書店和它的灰塵
復興書店的肥佬
書蟲的形狀
貽善堂的天使
冷門書刊堆疊史
最後來到東岸書店
詩人筆下的港督
大大公司與《大大月報》
十年生滅:香港的文藝刊物
主要引錄文獻一覽
書摘/試閱
白光熄滅九龍城
燈光與碎片
啟德機場跑道燈光徹夜明亮,像堅固的星座,為夜間升降的飛機提示路徑。我們以為星座總比我們持久,但這晚看來那麼虛弱。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降臨,跑道燈光倏然熄滅,市民不禁叫喚,短暫漆黑後,燈光突然再亮起,市民雀躍起哄,但它只閃爍了幾下,然後真正熄滅,結束比我們年長的光,歷史裡的離合、笑靨淚痕,奔向了冷卻宇宙。
再沒有飛機掠過九龍城的低空,再沒有頻繁的震耳巨響,我們反而不習慣,但知早晚會戀上這新的寧靜。因鄰近機場的建屋高度限制,大半世紀以來,整片九龍城社區維持低矮樓房外觀,在這晚,我們也預見它早晚撤換作新的高樓。
承認新舊輪替是必然,我們不敢否定新事,卻總忐忑於「發展」二字;只有九龍城一面淡然,看慣變幻。但九龍城也在我們不察覺的時候回首前塵,追憶城寨渡頭往返的清廷官吏、城寨門前腳戴枷鎖的罪犯、宋皇臺前痛惜文化失落的前清遺民、被日軍夷為平地的啟德濱。
時流洗淨鉛華,九龍城只暗自追懷,不肯在人前話舊,我們都理解,它藏著半島最幽隱的歷史記號,歷劫時代遺下依稀可辨的痕跡:宋皇臺、九龍城寨、啟德濱、啟德機場,面目全非,但未完全逝去。至若我輩在飛機巨響下的唐樓中的蹦跳嬉鬧、烙印腦際的笑靨淚影,待得雙燕歸來,也未必願意記起。
直至我們翻開紙頁,滿眼不滅跡印,盡是前人的文字。
目前所見,最具古風的九龍城風景,莫如侶倫筆下的記述。一九三○年與友人組織島上社,創辦文學雜誌《島上》的侶倫,二○年代末居於九龍城,位於近海的啟德濱外圍,他為居所命名「向水屋」,並邀得徐悲鴻題字,書橫幅掛於壁上。侶倫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散文集《無名草》,有一篇文章〈故居〉,為戰前九龍城留下世外桃園式的記錄:
我的住居是一列新建樓房的一間四層樓上,沿住屋外有一個寬廣的,鋪了花磚子的迴廊式的陽臺,……可以看見由高聳的獅子山下面伸展過來的一塊巨幅的風景畫:一簇簇蒼翠的樹木和一片灰色的屋頂─是一世紀來不輕易變動的古風的殘留。隱蔽在灰色之中的,是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園地和人家。一個小丘橫在那裡,小丘的中部,像腰帶似地鑲著古舊卻還完整的九龍城的城牆。
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讀到的,戰前從啟德濱外圍望向九龍城寨風景地貌的最完整紀錄。這優美散文同時是記錄九龍城地貌的重要文獻,《無名草》一九五三年曾再版一次,早已絕版,之後未有再版,讀到的人恐怕不多,侶倫後來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文章〈向水屋追懷〉中,引用了部分〈故居〉的內容,但不及原文詳細。
侶倫文中所指的「新建樓房」,是指建於一九二○年代的啟德濱住宅。一九一○年代,由何啟與區德等多人創辦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主持填海建屋計畫,新建成的社區稱為啟德濱。啟德公司的填海計畫,未竟全工就倒閉,政府接收後在填海區興建機場,命名為「啟德」。二戰期間,日軍攻占香港後,為擴建機場拆去九龍城寨城牆,宋皇臺、啟德濱社區亦被夷平。
侶倫在《向水屋筆語》一書,多處談及九龍城,其中〈故人之思〉記錄了葉靈鳳一九二九年偕郭林鳳在香港短暫居住的日子,侶倫安排他們租住在九龍城:
那是座落「宋皇臺」旁邊一間房子的第二層樓。從那「走馬騎樓」向外望,正面是鯉魚門,右面是香港,左面是一條向前伸展的海堤;景色很美。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漁船燈火在澄明的水面溜來溜去,下面傳來潮水拍岸的有節奏的聲音。在海闊天空之中,人彷彿置身超然物外境界。
因為「向水屋」之名以及葉靈鳳短住九龍城,一時傳遍香港文壇,《伴侶》雜誌編輯張稚廬送給侶倫一首舊詩寫道:「半島爭看一俊才,宋皇臺下寫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見翩翩靈鳳來。」前兩句寫侶倫,後兩句寫葉靈鳳。寫侶倫時提及宋皇臺,只就其居處位置而言,侶倫是早期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創辦新文學社團和刊物,宋皇臺與侶倫其人其文無多大關係,它另有迥異於新文藝取向的象徵意義。
宋皇臺本九龍城以南海濱山坡上一塊大石,南宋末年,宋帝昰與宋帝昺被元朝軍隊追逼,在文天祥、陸秀夫等人護送下逃至九龍城一帶,短暫停駐再繼續逃亡。後人紀念其事,於相傳宋帝曾登臨之大石刻「宋王臺」三字,旁邊另有「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為保護古蹟,香港政府於一八九九年通過「保存宋王臺勝蹟條例」,其後修茸鄰近地方,闢為公園。日治時期,大石被炸,裂為數塊,刻字部分竟奇蹟倖存,戰後港府擴建啟德機場,於大石原址興建機場客運大樓,石刻部分切割成長方形,移送機場附近空地,闢作「宋皇臺公園」。
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前清文人避居香港,有感山河變易,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文人將家國與身世之悲寄託於宋皇臺,藉雅集相互唱酬。一九一七年,蘇澤東輯錄前清探花陳伯陶等人所著宋皇臺詩詞,編為《宋臺秋唱》。宋皇臺向為香港最著名古蹟,文人懷古之餘,亦追溯九龍古事,如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
九龍,古官富場地,明初置巡司,嘉慶間,總督百齡築砦,改名九龍。道光間復改官富巡司為九龍巡司,而官富場之名遂隱。
前清文人追懷失去的時光,以歷史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不意間為香港敘述了遺民角度的歷史。宋皇臺也不只是前清文人吟詠對象,抗日戰爭期間,南來香港避亂的文人,也有許多藉宋皇臺抒發時局憂患,如陳居霖〈雨訪宋皇臺偕雪瑛三首錄二〉其一云:「抱得春愁海樣深,江山如晦忍重臨。崖門極目蒼波冷,空憶當年帝璽沉。」正將時代憂患與個人飄零之悲合而為一。二十世紀初,香港仍有許多與宋皇臺相關的古蹟,如二王殿村、侯王廟、國母梳妝石等,同為前清文人避港必訪之地。二王殿位於二王殿村內,即《新安縣志》中的二黃店村,位於今日的馬頭圍區,陳伯陶〈宋行宮遺瓦歌並序〉記云:「官富場宋皇臺之東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宮舊基也,新安縣志稱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廟即此,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麤朴,然頗經久。」序後有詩,抒其獲得古殿遺瓦的感慨:「凄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宋皇臺、二王殿村與古殿遺瓦為前清遺民共同吟詠之對象,吳道鎔亦有詩云:
寒林擁日到虞淵,戎馬艱難瘴海邊。七百年來陵谷變,二王村尚鳥啼煙(二王村)。敷天左袒語非虛,直到窮邊有帝居。破碎河山瓦全少,千秋一片重璠璵(宋行宮瓦)。
吳道鎔與陳伯陶、張學華等合稱「嶺南九老」,皆前清遺民,辛亥革命後避居香港。陳伯陶手執古瓦而垂淚,吳道鎔視瓦片如古玉,不僅視為古物,實為難以重整的文化中國碎片,其懷古、歷史意識與離散海外之悲,已糾結難分。
蛻變的軌跡
戰後侶倫從回港,舊居已隨啟德濱湮滅,侶倫仍居九龍城,住在獅子石道,其後一再搬遷,徐悲鴻題字的橫幅「向水屋」仍掛屋中。原來日軍攻占香港前夕,侶倫把橫幅從鏡架取出,摺疊後夾進書中,藏於塞滿舊書的箱子裡,待戰後回港,箱子仍在,那橫幅也成了劫後倖存的珍寶。
侶倫筆下的啟德濱,遠望可見一片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於我來說,可說是一個「史前」的九龍城,它引發歷史想像,但不涉個人回憶。一九九五年,當讀到郭麗容小說〈城市慢慢的遠去〉,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
在龍崗道的郵局,還有代人寫信的攤子。雜貨店仍然是六、七○年代模式,穿著白背心的老闆坐在櫃面,無線電播出南音。
其實香港還有許多地區,如上環、土瓜灣、西灣河等,保存六、七○年代或更早的模樣,直至我們的青年時代為止。不同年代都有屬於那年代的新事,我們許多年後才了解,除了新事物,舊物的延續也是一種時代產物和集體記認:
當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後,九龍城將會重新發展。那時由香港島望去九龍城區,據說會像紐約曼赫頓。在矗矗的摩天大廈之間,玻璃幕牆與陽光閃爍。「天地良心,我愛你就是因為我愛你。」這些句子將沒處停留。
郭麗容的小說教我追思前事,九龍城的獅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時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號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號巴士前赴九龍城,是小時除了上學以外最熟悉的路途,車窗外的風景多年如一,我默認著如何沿巴士駛過的路徑,步行往返兩地。媽媽經營的兩家店鋪、姑婆經營的時裝店、姨婆開設的裁縫店都位於九龍城,是祖母輩、父輩與親戚們最常聚會的地方,尤當「作牙」時節。
九龍城總給我破舊、熱鬧,具人情味而嘈雜的感覺,麻雀牌聲混和飛機間歇經過的聲音,在幽僻的冷巷,傳來收音機播送的鬼故事。不過最恐怖的,莫如給父親帶到九龍城寨的簡陋牙醫診所脫牙,只為著老牙醫是他的朋友。經驗豐富但沒有專業認可資格的老牙醫,沒使用任何麻醉藥物,以簡陋工具把未完全鬆脫的乳齒用力拔出,我每次都發出比我小時所能承受的痛苦更尖銳的呼聲。
追隨哥哥、眾位表姐和表哥,攀上高聳而狹窄的木樓梯,我像一隻流竄的蟑螂。有時在梯間與拿著空漱口盅到大牌檔買白粥的大人打個照面,我側身讓過,梯間響徹我喜聽的木屐躂躂之聲。屋內大人在搓麻將,小孩在走廊玩,黑白電視傳來真的槍聲,教我們知道遠方有戰爭,我特別記得大人物逝世和有人被審判的新聞畫面,大人們有的切齒憤慨,有的低聲惋嘆。傍晚過後,收音機播送鬼故事,再傳來一首又一首粵曲,鑼鼓喧天,女聲婉轉,夾雜眾人不息的爭鬧,我不知應該掩耳,還是學習。
偌大的屋內,除大廳以外,以木板、衣櫃分割出許多小房間,我走進其中一所昏暗無窗的房間,書桌上一盞小燈,照出一個寫字的青年,也照出香煙裊裊,但照不亮身旁凌亂的書刊和紙頁。某天,那人遞給我一疊廢棄稿紙,在鋼筆增刪塗改的暗藍色墨水字跡間,我記著一些寫著「高爾基」、「契可夫」這樣奇怪組合的字詞。
後來媽媽結束九龍城的店鋪,祖母過世,很少再往九龍城,直至八○年代中,香港移民潮澎湃,啟德機場成了同學間最後話別之所,那幾年間,我們熟悉機場甚於圖書館。那時並不知道,移民的人若干年後又舉家回流,但同學間已很難碰面,友誼早晚褪色,九七問題卻帶來過早的斷裂。一九九○年我赴臺灣升讀大學,又幾度往返機場,到我畢業之時,機場準備遷往大嶼山,大片連接大嶼山之北的人工島嶼工程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到臺灣探望隔別三年的同學,最後一次從啟德機場登上飛機,回程時最後一次越過九龍城的低空降落。機場繁忙如昔,轉換航班資訊的告示板仍發出熟悉的「躂躂躂躂」聲響。啟德機場即將關閉,我已作好離別的準備,那知它的消失並不像一次爆炸。
九龍城的蛻變早於一九九四年拆卸九龍城寨已發其端,啟德機場的關閉,只是這蛻變之另一端。對城外人來說,城寨像個大迷宮,除了建築格局因素,城寨也儲存了前代香港的歷史、英占香港後種種烙印人心的陰暗記憶,董啟章《繁勝錄》中之一節,正寫出城寨如同迷宮的深意:「有人說走進寨城的人沒有一個能走出來,因為寨城會奪走人的記憶,令人不願意再離開。」城寨關乎我城的陰暗記憶,拆掉它是攻克陰暗記憶的最簡單卻又帶點暴虐的方法,在城寨低空掠過的飛機,也許提供另一種超越的可能,《繁勝錄》的敘事者走進城寨最後抵達出口,正遇見這種超越:「降落的飛機又在低空掠過,我掩著耳,抬頭望向那一隙天空,卻甚麼也沒看見,只感到四周好像陰暗了一下。」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最後一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任務,經過一段搬遷日子後,原來的客運大樓被分割為許多不同部分重新開放,分租給各種不同機構,作許多不同用途。二○○三年四月,「沙士」陰霾籠罩的日子,我重回沒有飛機升降的啟德機場客運大樓,穿梭於人跡杳杳的不同區間,記下種種不由自主的割裂。每感它的割裂,它的蛻變,與我們的成長都屬同一軌跡。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