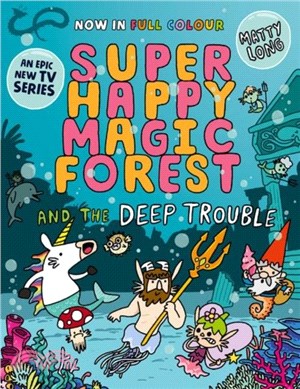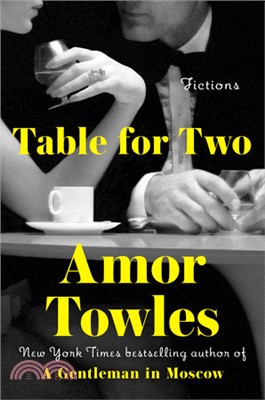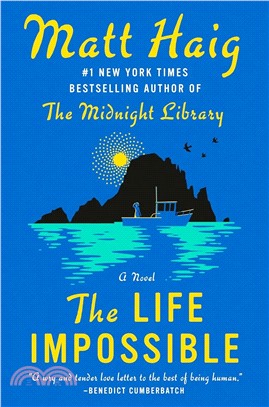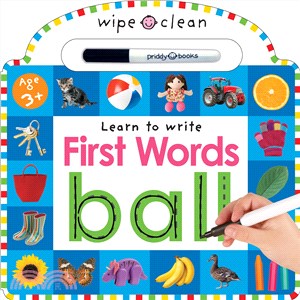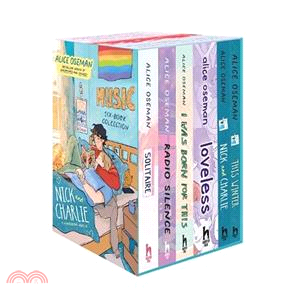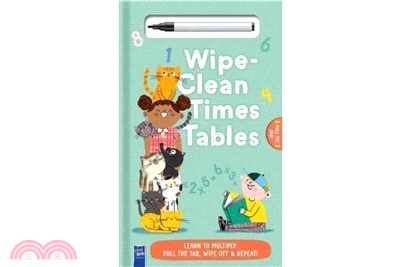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有最後的一線希望麼?
向誰屈服呢?
在倒下去之前,
他們還能掙扎一下麼?
還能鼓動一番風波麼?
忠臣文天祥×叛軍黃公俊×權臣阮大鋮,
廟堂之間的權力遊戲、由下而上的革命火種、國破家亡時的利慾薰心
▎桂公塘
──南宋文天祥與元朝講和後冒死奔逃南歸,
寫盡其中從熱血沸騰的希望到如澆冷水的絕望
雖在流離顛沛之中,他的高華的氣度,淵雅的局量,還不曾改變。他憂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臉,好幾天不曾洗了,但還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際聚集了幾條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還勉強的站立著。……他已經歷過千辛萬苦;他還準備著要經歷千百倍於此的苦楚。
▎黃公俊之最後
──晚清太平軍將領黃公俊毅然參軍,
於太平軍失敗後仍堅守理想,寧赴一死
他的懷疑整個的冰釋,那批紳士們所流布的恐怖和侮蔑是無根的,是卑鄙得可憐的。還不該去做太平軍的一個馬前走卒,伸一伸久鬱的悶氣麼?他們是正合於他理想的一個革命。雖然天父、天兄,講道理、說敎義的那一套,顯得火辣辣的和他的習慣相去太遠。但他相信,那是小節道。他也並不是什麼頑固的孔敎徒,這犧牲是並不大。
▎毀滅
──南明權臣阮大鋮在朝廷崩潰之際費盡心機保全自己,
但最終,他搜刮來的珍貴文物財寶在大火之中付之一炬
心裡只覺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卹!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絕不能讓仇人們占了上風……不,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還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退縮!
本書特色:本書是鄭振鐸的歷史短篇小說集,書中共收錄〈桂公塘〉、〈黃公俊之最後〉、〈毀滅〉三篇小說。鄭振鐸歷史背景深厚、筆力雄勁、用字遣詞典雅,述說人物心境和其間曲折絲絲入扣,又扣連到希望振興國家的歷史情境,讓人沉浸於歷史,亦產生無窮的同情和悲憫。
向誰屈服呢?
在倒下去之前,
他們還能掙扎一下麼?
還能鼓動一番風波麼?
忠臣文天祥×叛軍黃公俊×權臣阮大鋮,
廟堂之間的權力遊戲、由下而上的革命火種、國破家亡時的利慾薰心
▎桂公塘
──南宋文天祥與元朝講和後冒死奔逃南歸,
寫盡其中從熱血沸騰的希望到如澆冷水的絕望
雖在流離顛沛之中,他的高華的氣度,淵雅的局量,還不曾改變。他憂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臉,好幾天不曾洗了,但還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際聚集了幾條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還勉強的站立著。……他已經歷過千辛萬苦;他還準備著要經歷千百倍於此的苦楚。
▎黃公俊之最後
──晚清太平軍將領黃公俊毅然參軍,
於太平軍失敗後仍堅守理想,寧赴一死
他的懷疑整個的冰釋,那批紳士們所流布的恐怖和侮蔑是無根的,是卑鄙得可憐的。還不該去做太平軍的一個馬前走卒,伸一伸久鬱的悶氣麼?他們是正合於他理想的一個革命。雖然天父、天兄,講道理、說敎義的那一套,顯得火辣辣的和他的習慣相去太遠。但他相信,那是小節道。他也並不是什麼頑固的孔敎徒,這犧牲是並不大。
▎毀滅
──南明權臣阮大鋮在朝廷崩潰之際費盡心機保全自己,
但最終,他搜刮來的珍貴文物財寶在大火之中付之一炬
心裡只覺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卹!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絕不能讓仇人們占了上風……不,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還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退縮!
本書特色:本書是鄭振鐸的歷史短篇小說集,書中共收錄〈桂公塘〉、〈黃公俊之最後〉、〈毀滅〉三篇小說。鄭振鐸歷史背景深厚、筆力雄勁、用字遣詞典雅,述說人物心境和其間曲折絲絲入扣,又扣連到希望振興國家的歷史情境,讓人沉浸於歷史,亦產生無窮的同情和悲憫。
作者簡介
鄭振鐸(西元1898~1958年),筆名郭源新、落雪等,中國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景星學社社員,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代表作有:專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小說《取火者的逮捕》、《家庭的故事》、《佝僂集》、《歐行日記》;翻譯《漂鳥集》、《沙寧》、《灰色馬》、《新月集》、《血痕》等書。
目次
桂公塘
一 掙扎
二 沉默
三 羈留
四 沉默
五 深思
六 打聽
七 絕望
八 取笑
九 決意
十 暢談
十一 默禱
十二 櫓聲
十三 投奔
十四 想念
十五 怨恨
十六 夜天
黃公俊之最後
一 疏影
二 紅焰
三 真相
四 荒原
五 討賊
六 歸降
七 口號
八 屈服
九 蜚語
毀滅
一 權力
二 大計
三 整飭
四 希望
五 迎降
六 謠言
七 風聲
八 瓦解
九 犧牲
十 下場
一 掙扎
二 沉默
三 羈留
四 沉默
五 深思
六 打聽
七 絕望
八 取笑
九 決意
十 暢談
十一 默禱
十二 櫓聲
十三 投奔
十四 想念
十五 怨恨
十六 夜天
黃公俊之最後
一 疏影
二 紅焰
三 真相
四 荒原
五 討賊
六 歸降
七 口號
八 屈服
九 蜚語
毀滅
一 權力
二 大計
三 整飭
四 希望
五 迎降
六 謠言
七 風聲
八 瓦解
九 犧牲
十 下場
書摘/試閱
桂公塘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角?
江南父老還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文天祥:〈旅懷〉
一 掙扎
他們是十二個。杜滸,那精悍的中年人,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似的,不擇地的坐了下去。剛坐下,立刻跳了起來,叫道:
「慢著!地上太潮溼。」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淤溼了。
疲倦得快要癱化了的幾個人,聽了這叫聲,勉強的掙扎的站著,背靠在土牆上。
一地的溼泥,還雜著一堆堆的牛糞,狗糞。這土圍至少有十丈見方,本是一個牛欄。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不知那些牛隻是被兵士們牽去了呢,還是已經逃避到深山裡去,這裡只剩下空空的一個大牛欄。溼泥裡吐射出很濃厚的腥騷氣。周遭的糞堆,那臭惡的氣味,更陣陣的撲鼻而來。他們站定了時,在靜寂清鮮的夜間的空氣裡,這氣味兒益發重,益發難聞,隨了一陣陣的晚風直衝撲而來。個個人都要嘔吐似的,長袖的袖口連忙緊掩了鼻孔。
「今夜就歇在這土圍裡?」杜滸無可奈何的問道。
「這周圍的幾十里內,不會有一個比這個土圍更機密隱祕的地方。我們以快些走離這危險的地帶為上策,怎麼敢到民家裡去叩門呢?冷不防那宅裡住的是韃子兵呢。」那作為嚮導的本地人余元慶又仔細的叮囑道。
十丈見方的一個土圍上面,沒有任何的蔽蓋。天色藍得可愛。晶亮的小星點兒,此明彼滅的似在打著燈語。苗條的一彎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圍靜悄悄的,偶然在很遠的東方,有幾聲犬吠,其聲悽慘的像在哭。
露天的憩息是這幾天便過慣了的,倒沒有什麼。天氣是那末好。沒有一點下雨的徵兆。季春的氣候,夜間是不涼不暖。睡在沒有蔽蓋的地方倒不是什麼難堪的事。所難堪的只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氣,就從立足的地面蒸騰上來,更有那一陣陣的難堪的糞臭氣濃烈的夾雜在空中,薰沖得人站立不住。
「在這個齷齪的地方,丞相怎麼能睡呢?」杜滸躊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書生,如今是改扮著一個商人,穿著藍布衣褲,腰繫布條,足登草鞋。雖在流離顛沛之中,他的高華的氣度,淵雅的局量,還不曾改變。他憂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臉,好幾天不曾洗了,但還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際聚集了幾條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還勉強的站立著。他的手扶在一個侍從的肩上,足底板是又痠痛,又溼熱;過多的汗水把襪子都浸得溼了,有點怪難受的苦楚。但他不說什麼,他能夠吃苦。他已經歷過千辛萬苦;他還準備著要經歷千百倍於此的苦楚。
他的頭微微的仰向天空。清麗的夜色彷彿使他沉醉。涼颸吹得他疲勞的神色有些蘇復──雖然腿的小肚和腳底是仍然在痠痛。
「我們怎麼好呢?這個地方沒法睡,總得想個法子。至少,丞相得憩息一下!」杜滸熱心地焦急著說道。
文丞相不說什麼,依然昂首向天。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麼或是在領略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詩句呢!」年輕的金應悄悄的對鄰近他身旁的一個侍從說。
「我們得想個法子!」杜滸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
嚮導的余元慶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能勉強的打掃出一片乾淨土出來再說。」
「那末,大家就動手打掃,」杜滸立刻下命令似的說。
他首先尋到一條樹枝,枝頭綠葉紛披的,當作了掃帚,開始在地上掃括去腥溼的穢土。
個個人都照他的榜樣做。
「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臉上了!」
「小心點,我的衣服被你的樹枝掃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漿呢。」
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在責罵,然而一團的高興,幾乎把剛才的過分的疲倦忘記了。他們孩子們似的在打鬧。
不知掃折了多少樹枝,落下了多少的綠葉,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顯得乾淨些。
「就是這樣了罷,」杜滸嘆了一口氣,放下了他的打掃的工作,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個侍從,打開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鋪在地上。
「丞相也該息息了,」他憐惜的說道。
「諸位都坐下了罷,」文丞相藹然和氣的招呼道。
陸陸續續的都圍住了文丞相而坐下。他們是十二個。
年輕的金應道:「我覺得有點冷,該生個火才好。」
「剛才走得熱了,倒不覺什麼。現在坐定了下來,倒真覺得有些冷抖抖的了。」杜滸道。
「得生個火,我去找乾樹枝去。」好動的金應說著,便跳了起來。
嚮導,那個瘦削的終年像有深憂似的余元慶,立刻也跳起身來,擋住了金應的去路,嚴峻的說道:「你幹什麼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誰知道附近不埋伏著韃子兵呢?生火招他們來麼?」
金應一肚子的高興,橫被打斷了,咕嘟著嘴,自言自語道:「老是韃子兵韃子兵的嚇唬人!老子一個打得他媽的十個!」然而他終於仍然坐了下去。
「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來巡邏的麼?到正午便都歸了隊,夜間是不會來的。」杜滸自己寬慰的說道。
「那也說不定。這裡離瓜州揚子橋不遠,大軍營在那邊,時時有徵調,總得特別小心些好。」余元慶的瘦削見骨的臉上露出深謀遠慮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響,眼睛還是望著夜天。
鐮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掛在偏西的一方了;東邊的天上略顯得陰暗。有些烏雲在聚集。中天也有幾朵大的雲塊,橫亙在那裡,不知在什麼時候出現的。
晚風漸漸的大了起來。土圍外的樹林在簌簌的微語,在淒楚的呻吟。
二 沉默
沉默了好久。有幾個年輕人打熬不住,已經橫躺在地上睡熟了;呼呼的發出鼾聲來。金應是其一,他呼嚕呼嚕的在打鼾,彷彿忘記了睡在什麼地方。
文丞相耿耿的光著雙眼,一點睡意也沒有。他的腿和腳經了好一會的休息,已不怎麼痠楚了。
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滸──那位死生與共,為了國家,為了他,而犧牲了一切的義士。杜滸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著他。杜滸哪一刻曾把眼光離開了他所敬愛的這位忠貞的大臣呢!
「丞相,」杜滸低聲的喚道;「不躺下息息麼?」他愛惜的提議道。
「杜架閣,不,我閉不上眼,還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該好好的睡一會兒。」
「不,丞相,我也睡不著。」
文丞相從都城裡帶出來的門客們已都逃得乾乾淨淨了;只剩下杜架閣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離開他。
他們只是新的相識。然而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患難與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們倆幾成了一體。文丞相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閣的。而杜架閣也嘗對丞相吐露其心腑道:
「大事是不可為的了!吳堅伴食中書,家鉉翁衰老無用,賈餘慶卑鄙無恥;這一批官僚們是絕對的不能擔負得起國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奮發有為的。他們妒忌得要死,我們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設計要把你送到韃子的大營裡去講和。這魔穴得離開,我們該創出一個新的有作為的局面出來,才抵抗得了那韃子的侵略。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們只有一腔的熱血,一雙有力的手腕。擁護你,也便是為國家的復興運動而努力。」
丞相不好說什麼,他明白這一切。他時刻的在羅致才士俊俠們。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訓練得很精銳;可惜糧餉不夠──他是毀家勤王的──正和杜滸相同。人數不能多。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實權,然後徐圖展布,徹底的來一次掃蕩澄清的工作。然而那些把國家當作了私家的產業,把國事當作了家事的老官僚們,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們盲了目。「寧願送給外賊,不願送給家人」,他們是抱著這樣的不可告人的隱衷的。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諭旨剛剛下來,他們便設下了一個毒計。
蒙古帥伯顏遣人來邀請宋邦負責的大臣到他軍營裡開談判。
這難題困住了一班的朝士們,議論紛紛的沒有一毫的定見。誰都沒有勇氣去和伯顏談判。家鉉翁是太老了,吳堅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鎮,又多病,也不能去。這難題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剛拜命的左丞相,年剛氣銳,足以當此大任。大家把這使命,這重責,都想往他身上推。
「誰去最能勝任愉快呢?」吳堅道。
「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個效力於君國的機會,我倒想請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沒有用。」家鉉翁喘息的說道,全身安頓在東邊的一張太師椅上。
「國家興亡,在此一舉,非精明強幹,有大勇大謀的不足以當此重任,」賈餘慶獻諛似的說,兩眼老望著文天祥。他是別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左丞相的肥缺兒便要順推給他享受了,所以他慫恿得最有力。
朝臣們紛紛的你一言我一語的,都互相在推諉,其意卻常在「沛公」。
那紛紛營營的青蠅似的聲響,都不足以打動文天祥的心。在他的心裡正有兩個矛盾的觀念在作戰。
他不曾預備著要去。並不是退縮怕事。他早已是準備著為國家而犧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軍營裡會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卻不欲便這樣沒有作用的給糟蹋掉。
當陳宜中為丞相的時候,伯顏也遣人來要宜中去面講和款,那時天祥在他的幕下,再三的諍諫道:
「相公該為國家自重。蒙古人不可信,虎狼之區萬不宜入。若有些許差池,國家將何所賴乎?」
宜中相信了他的話,不曾去。
如今這重擔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為國家惜此身。他要做的事比這重要得多。他不願便這樣輕忽的犧牲了。他還有千萬件的大事要做。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他一去,國家將何所賴乎?杜滸,他的新相識的一位俠士,也極力的阻止他去;勸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滸集合了四千個子弟兵,還有一腔的熱血,要和他合作,同負起救國的責任。也有別的門客們,紛紛擾擾的在發揮種種不同的意見。但他相信,純出於熱情而為遠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個杜滸。
然而,文天祥在右丞相吳堅府第裡議事時,看見眾官們的互相推諉,看見那種卑鄙齷齪的態度,臨難退縮,見危求脫的那副怯懦的神氣,他不禁覺得有些冒火。他的雙眼如銅鈴似的發著侃侃的懇摯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
「你們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們呀,走開;讓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個更大的救國的使命在著,便勉強的把那股憤氣倒嚥了下去。他板著臉,好久不開口。
但狡猾如狐的賈餘慶,卻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來,慢條斯理的說道:
「要說呢,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強虜的銳鋒──不過文丞相是國家的柱石──」
他很想叫道:「不錯,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話,我便去了!」
然終於也把這句不客氣的話強嚥了下去。
「文丞相論理是不該冒這大險。不過……國家在危急存亡之候,他老人家……是最適宜於擔著這大任的。」吳堅也吞吞吐吐的應和著說道。
一個醜眉怪目的小人,劉岊,他是永遠逢迎著吳堅、賈餘慶之流的老官僚的,他擠著眼,怪惹人討厭的尖聲說道:
「文丞相耿耿忠心,天日可鑒;當此大任,必不致貽國家以憂戚。昔者,富鄭公折辱遼寇……」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方張的寇勢,能以一二語折之使退麼?這非有心雄萬夫的勇敢的大臣,比之富鄭公更……」賈餘慶的眼鋒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故意的要激動他。
對於這一批老奸巨猾們的心理,他是洞若觀火的。他實在有些忍不住,幾乎不顧一切的叫道:
「我便去!」
他究竟有素養,還是沉默著,只是用威嚴有稜的眼光,來回的掃在賈餘慶和劉岊們的身上。
一時敞亮的大廳上,鴉雀無聲的悄靜了下來,雖然在那裡聚集了不下百餘個貴官大僚。
空氣石塊似的僵硬,個個人呼吸都艱難異樣。一分一秒鐘,比一年一紀還難度過。
還是昏庸異常的右丞相吳堅打破了這個難堪的局面:
「文丞相的高見怎樣呢?以丞相的大才,當此重任,自能綽有餘裕,國家實利賴之。」
他不能不表示什麼了。鋒稜的眼光橫掃過一堂,那一堂是行屍走肉的世界;個個人都低下了眼,望著地,彷彿內疚於心,不敢和他的銳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觸。他在心底深喟了一聲,沉痛的說道:
「如果實在沒有人肯去,而諸位老先生們的意見,都以為非天祥去不可的時候,天祥願為國家粉碎此無用之身。唯恐囂張萬狀的強虜,未必片言可折耳。」
如護國的大神似的,他坐在西向一張太師椅上。西斜的太陽光,正照在他的身上,投影於壁,碩大無朋,正足以於影中籠罩此群懦夫萬輩!
個個人都像從危難中逃出了似的,鬆了一口氣。
文天祥轉了一個念,覺得毅然前去,也未嘗不是一條活路。中國雖曾扣留了北使郝經到十幾年之久──那是賈似道的荒唐的挑釁的盲舉,但北廷卻從不曾扣留過宋使。奉使講和的人,從不曾受過無禮的待遇。恃著他自己的耿耿忠心,不懼艱危,也許可以說服伯顏,保全宋室,使它在不至過分難堪的條件之下,偷生苟活了若干時,然後再徐圖恢復、中興。這未必較之提萬千壯丁和北虜作孤注一擲的辦法便有遜。這也是一個辦法。即使冒觸虜帥而被羈,甚至被殺,還不是和戰死在戰場上一樣的麼?人生總有一個死,隨時隨處無非可死之時地,為國家,個個人都該貢獻了他的生命,而如何死法,卻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為政治活動者,正像入伍當一個小小的兵丁,自己是早已喪失了自由的──自己絕對沒有選擇死的時和地的自由。
況且北虜的虛實,久已傳聞異辭,究竟他們的軍隊是怎樣的勇猛,其各軍的組織是怎樣的,他們用什麼方法訓練這長勝之軍,一切都該自己去仔細的考察一下,作為將來的準備。那末,這一行,其意義正是至重且大。
這樣一想,他便心平氣和起來,隨即站起身來,說道:
「諸位老先生,事機危矣,天祥明天一早便行;現在還要和北使面談一切。失陪了。」
頭也不回的,剛毅有若一個鐵鑄的人,踏著堅定的足步離開大廳而去。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角?
江南父老還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文天祥:〈旅懷〉
一 掙扎
他們是十二個。杜滸,那精悍的中年人,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似的,不擇地的坐了下去。剛坐下,立刻跳了起來,叫道:
「慢著!地上太潮溼。」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淤溼了。
疲倦得快要癱化了的幾個人,聽了這叫聲,勉強的掙扎的站著,背靠在土牆上。
一地的溼泥,還雜著一堆堆的牛糞,狗糞。這土圍至少有十丈見方,本是一個牛欄。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不知那些牛隻是被兵士們牽去了呢,還是已經逃避到深山裡去,這裡只剩下空空的一個大牛欄。溼泥裡吐射出很濃厚的腥騷氣。周遭的糞堆,那臭惡的氣味,更陣陣的撲鼻而來。他們站定了時,在靜寂清鮮的夜間的空氣裡,這氣味兒益發重,益發難聞,隨了一陣陣的晚風直衝撲而來。個個人都要嘔吐似的,長袖的袖口連忙緊掩了鼻孔。
「今夜就歇在這土圍裡?」杜滸無可奈何的問道。
「這周圍的幾十里內,不會有一個比這個土圍更機密隱祕的地方。我們以快些走離這危險的地帶為上策,怎麼敢到民家裡去叩門呢?冷不防那宅裡住的是韃子兵呢。」那作為嚮導的本地人余元慶又仔細的叮囑道。
十丈見方的一個土圍上面,沒有任何的蔽蓋。天色藍得可愛。晶亮的小星點兒,此明彼滅的似在打著燈語。苗條的一彎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圍靜悄悄的,偶然在很遠的東方,有幾聲犬吠,其聲悽慘的像在哭。
露天的憩息是這幾天便過慣了的,倒沒有什麼。天氣是那末好。沒有一點下雨的徵兆。季春的氣候,夜間是不涼不暖。睡在沒有蔽蓋的地方倒不是什麼難堪的事。所難堪的只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氣,就從立足的地面蒸騰上來,更有那一陣陣的難堪的糞臭氣濃烈的夾雜在空中,薰沖得人站立不住。
「在這個齷齪的地方,丞相怎麼能睡呢?」杜滸躊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書生,如今是改扮著一個商人,穿著藍布衣褲,腰繫布條,足登草鞋。雖在流離顛沛之中,他的高華的氣度,淵雅的局量,還不曾改變。他憂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臉,好幾天不曾洗了,但還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際聚集了幾條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還勉強的站立著。他的手扶在一個侍從的肩上,足底板是又痠痛,又溼熱;過多的汗水把襪子都浸得溼了,有點怪難受的苦楚。但他不說什麼,他能夠吃苦。他已經歷過千辛萬苦;他還準備著要經歷千百倍於此的苦楚。
他的頭微微的仰向天空。清麗的夜色彷彿使他沉醉。涼颸吹得他疲勞的神色有些蘇復──雖然腿的小肚和腳底是仍然在痠痛。
「我們怎麼好呢?這個地方沒法睡,總得想個法子。至少,丞相得憩息一下!」杜滸熱心地焦急著說道。
文丞相不說什麼,依然昂首向天。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麼或是在領略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詩句呢!」年輕的金應悄悄的對鄰近他身旁的一個侍從說。
「我們得想個法子!」杜滸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
嚮導的余元慶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能勉強的打掃出一片乾淨土出來再說。」
「那末,大家就動手打掃,」杜滸立刻下命令似的說。
他首先尋到一條樹枝,枝頭綠葉紛披的,當作了掃帚,開始在地上掃括去腥溼的穢土。
個個人都照他的榜樣做。
「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臉上了!」
「小心點,我的衣服被你的樹枝掃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漿呢。」
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在責罵,然而一團的高興,幾乎把剛才的過分的疲倦忘記了。他們孩子們似的在打鬧。
不知掃折了多少樹枝,落下了多少的綠葉,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顯得乾淨些。
「就是這樣了罷,」杜滸嘆了一口氣,放下了他的打掃的工作,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個侍從,打開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鋪在地上。
「丞相也該息息了,」他憐惜的說道。
「諸位都坐下了罷,」文丞相藹然和氣的招呼道。
陸陸續續的都圍住了文丞相而坐下。他們是十二個。
年輕的金應道:「我覺得有點冷,該生個火才好。」
「剛才走得熱了,倒不覺什麼。現在坐定了下來,倒真覺得有些冷抖抖的了。」杜滸道。
「得生個火,我去找乾樹枝去。」好動的金應說著,便跳了起來。
嚮導,那個瘦削的終年像有深憂似的余元慶,立刻也跳起身來,擋住了金應的去路,嚴峻的說道:「你幹什麼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誰知道附近不埋伏著韃子兵呢?生火招他們來麼?」
金應一肚子的高興,橫被打斷了,咕嘟著嘴,自言自語道:「老是韃子兵韃子兵的嚇唬人!老子一個打得他媽的十個!」然而他終於仍然坐了下去。
「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來巡邏的麼?到正午便都歸了隊,夜間是不會來的。」杜滸自己寬慰的說道。
「那也說不定。這裡離瓜州揚子橋不遠,大軍營在那邊,時時有徵調,總得特別小心些好。」余元慶的瘦削見骨的臉上露出深謀遠慮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響,眼睛還是望著夜天。
鐮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掛在偏西的一方了;東邊的天上略顯得陰暗。有些烏雲在聚集。中天也有幾朵大的雲塊,橫亙在那裡,不知在什麼時候出現的。
晚風漸漸的大了起來。土圍外的樹林在簌簌的微語,在淒楚的呻吟。
二 沉默
沉默了好久。有幾個年輕人打熬不住,已經橫躺在地上睡熟了;呼呼的發出鼾聲來。金應是其一,他呼嚕呼嚕的在打鼾,彷彿忘記了睡在什麼地方。
文丞相耿耿的光著雙眼,一點睡意也沒有。他的腿和腳經了好一會的休息,已不怎麼痠楚了。
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滸──那位死生與共,為了國家,為了他,而犧牲了一切的義士。杜滸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著他。杜滸哪一刻曾把眼光離開了他所敬愛的這位忠貞的大臣呢!
「丞相,」杜滸低聲的喚道;「不躺下息息麼?」他愛惜的提議道。
「杜架閣,不,我閉不上眼,還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該好好的睡一會兒。」
「不,丞相,我也睡不著。」
文丞相從都城裡帶出來的門客們已都逃得乾乾淨淨了;只剩下杜架閣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離開他。
他們只是新的相識。然而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患難與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們倆幾成了一體。文丞相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閣的。而杜架閣也嘗對丞相吐露其心腑道:
「大事是不可為的了!吳堅伴食中書,家鉉翁衰老無用,賈餘慶卑鄙無恥;這一批官僚們是絕對的不能擔負得起國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奮發有為的。他們妒忌得要死,我們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設計要把你送到韃子的大營裡去講和。這魔穴得離開,我們該創出一個新的有作為的局面出來,才抵抗得了那韃子的侵略。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們只有一腔的熱血,一雙有力的手腕。擁護你,也便是為國家的復興運動而努力。」
丞相不好說什麼,他明白這一切。他時刻的在羅致才士俊俠們。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訓練得很精銳;可惜糧餉不夠──他是毀家勤王的──正和杜滸相同。人數不能多。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實權,然後徐圖展布,徹底的來一次掃蕩澄清的工作。然而那些把國家當作了私家的產業,把國事當作了家事的老官僚們,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們盲了目。「寧願送給外賊,不願送給家人」,他們是抱著這樣的不可告人的隱衷的。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諭旨剛剛下來,他們便設下了一個毒計。
蒙古帥伯顏遣人來邀請宋邦負責的大臣到他軍營裡開談判。
這難題困住了一班的朝士們,議論紛紛的沒有一毫的定見。誰都沒有勇氣去和伯顏談判。家鉉翁是太老了,吳堅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鎮,又多病,也不能去。這難題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剛拜命的左丞相,年剛氣銳,足以當此大任。大家把這使命,這重責,都想往他身上推。
「誰去最能勝任愉快呢?」吳堅道。
「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個效力於君國的機會,我倒想請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沒有用。」家鉉翁喘息的說道,全身安頓在東邊的一張太師椅上。
「國家興亡,在此一舉,非精明強幹,有大勇大謀的不足以當此重任,」賈餘慶獻諛似的說,兩眼老望著文天祥。他是別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左丞相的肥缺兒便要順推給他享受了,所以他慫恿得最有力。
朝臣們紛紛的你一言我一語的,都互相在推諉,其意卻常在「沛公」。
那紛紛營營的青蠅似的聲響,都不足以打動文天祥的心。在他的心裡正有兩個矛盾的觀念在作戰。
他不曾預備著要去。並不是退縮怕事。他早已是準備著為國家而犧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軍營裡會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卻不欲便這樣沒有作用的給糟蹋掉。
當陳宜中為丞相的時候,伯顏也遣人來要宜中去面講和款,那時天祥在他的幕下,再三的諍諫道:
「相公該為國家自重。蒙古人不可信,虎狼之區萬不宜入。若有些許差池,國家將何所賴乎?」
宜中相信了他的話,不曾去。
如今這重擔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為國家惜此身。他要做的事比這重要得多。他不願便這樣輕忽的犧牲了。他還有千萬件的大事要做。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他一去,國家將何所賴乎?杜滸,他的新相識的一位俠士,也極力的阻止他去;勸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滸集合了四千個子弟兵,還有一腔的熱血,要和他合作,同負起救國的責任。也有別的門客們,紛紛擾擾的在發揮種種不同的意見。但他相信,純出於熱情而為遠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個杜滸。
然而,文天祥在右丞相吳堅府第裡議事時,看見眾官們的互相推諉,看見那種卑鄙齷齪的態度,臨難退縮,見危求脫的那副怯懦的神氣,他不禁覺得有些冒火。他的雙眼如銅鈴似的發著侃侃的懇摯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
「你們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們呀,走開;讓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個更大的救國的使命在著,便勉強的把那股憤氣倒嚥了下去。他板著臉,好久不開口。
但狡猾如狐的賈餘慶,卻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來,慢條斯理的說道:
「要說呢,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強虜的銳鋒──不過文丞相是國家的柱石──」
他很想叫道:「不錯,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話,我便去了!」
然終於也把這句不客氣的話強嚥了下去。
「文丞相論理是不該冒這大險。不過……國家在危急存亡之候,他老人家……是最適宜於擔著這大任的。」吳堅也吞吞吐吐的應和著說道。
一個醜眉怪目的小人,劉岊,他是永遠逢迎著吳堅、賈餘慶之流的老官僚的,他擠著眼,怪惹人討厭的尖聲說道:
「文丞相耿耿忠心,天日可鑒;當此大任,必不致貽國家以憂戚。昔者,富鄭公折辱遼寇……」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方張的寇勢,能以一二語折之使退麼?這非有心雄萬夫的勇敢的大臣,比之富鄭公更……」賈餘慶的眼鋒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故意的要激動他。
對於這一批老奸巨猾們的心理,他是洞若觀火的。他實在有些忍不住,幾乎不顧一切的叫道:
「我便去!」
他究竟有素養,還是沉默著,只是用威嚴有稜的眼光,來回的掃在賈餘慶和劉岊們的身上。
一時敞亮的大廳上,鴉雀無聲的悄靜了下來,雖然在那裡聚集了不下百餘個貴官大僚。
空氣石塊似的僵硬,個個人呼吸都艱難異樣。一分一秒鐘,比一年一紀還難度過。
還是昏庸異常的右丞相吳堅打破了這個難堪的局面:
「文丞相的高見怎樣呢?以丞相的大才,當此重任,自能綽有餘裕,國家實利賴之。」
他不能不表示什麼了。鋒稜的眼光橫掃過一堂,那一堂是行屍走肉的世界;個個人都低下了眼,望著地,彷彿內疚於心,不敢和他的銳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觸。他在心底深喟了一聲,沉痛的說道:
「如果實在沒有人肯去,而諸位老先生們的意見,都以為非天祥去不可的時候,天祥願為國家粉碎此無用之身。唯恐囂張萬狀的強虜,未必片言可折耳。」
如護國的大神似的,他坐在西向一張太師椅上。西斜的太陽光,正照在他的身上,投影於壁,碩大無朋,正足以於影中籠罩此群懦夫萬輩!
個個人都像從危難中逃出了似的,鬆了一口氣。
文天祥轉了一個念,覺得毅然前去,也未嘗不是一條活路。中國雖曾扣留了北使郝經到十幾年之久──那是賈似道的荒唐的挑釁的盲舉,但北廷卻從不曾扣留過宋使。奉使講和的人,從不曾受過無禮的待遇。恃著他自己的耿耿忠心,不懼艱危,也許可以說服伯顏,保全宋室,使它在不至過分難堪的條件之下,偷生苟活了若干時,然後再徐圖恢復、中興。這未必較之提萬千壯丁和北虜作孤注一擲的辦法便有遜。這也是一個辦法。即使冒觸虜帥而被羈,甚至被殺,還不是和戰死在戰場上一樣的麼?人生總有一個死,隨時隨處無非可死之時地,為國家,個個人都該貢獻了他的生命,而如何死法,卻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為政治活動者,正像入伍當一個小小的兵丁,自己是早已喪失了自由的──自己絕對沒有選擇死的時和地的自由。
況且北虜的虛實,久已傳聞異辭,究竟他們的軍隊是怎樣的勇猛,其各軍的組織是怎樣的,他們用什麼方法訓練這長勝之軍,一切都該自己去仔細的考察一下,作為將來的準備。那末,這一行,其意義正是至重且大。
這樣一想,他便心平氣和起來,隨即站起身來,說道:
「諸位老先生,事機危矣,天祥明天一早便行;現在還要和北使面談一切。失陪了。」
頭也不回的,剛毅有若一個鐵鑄的人,踏著堅定的足步離開大廳而去。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