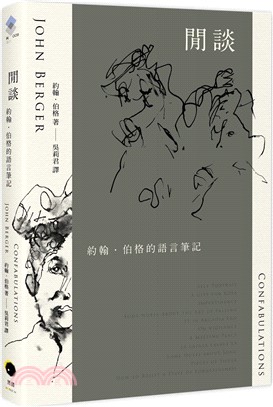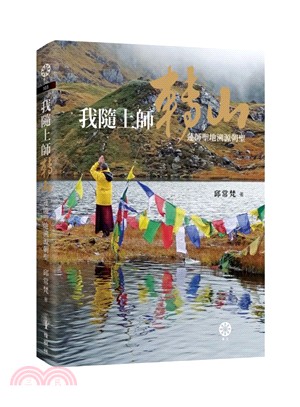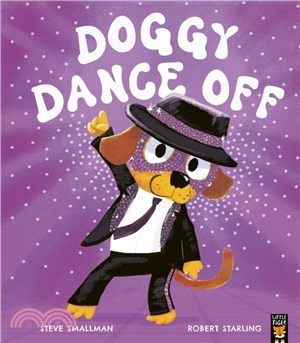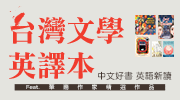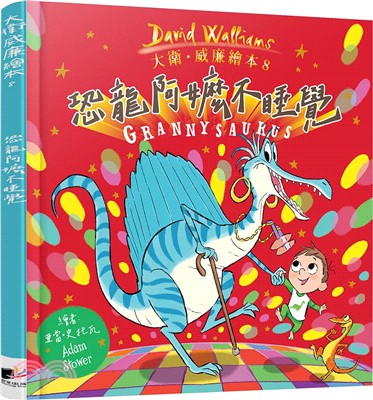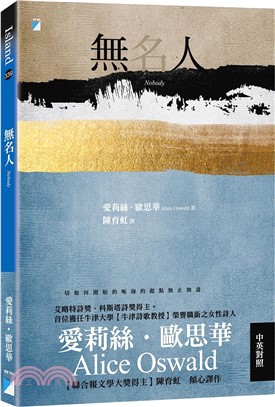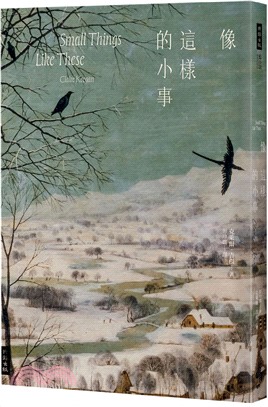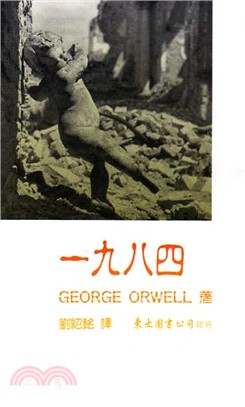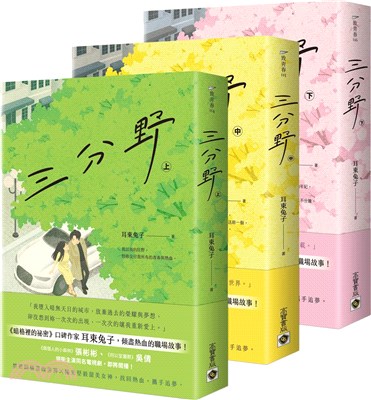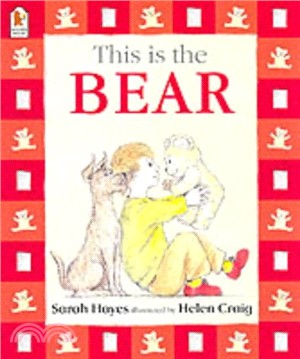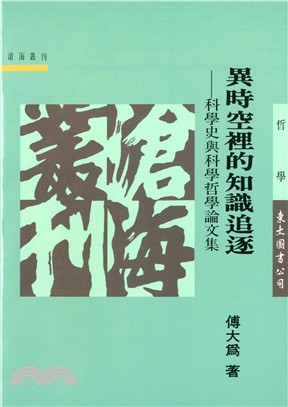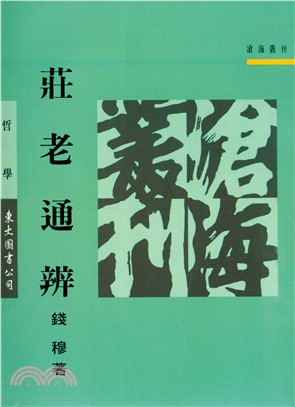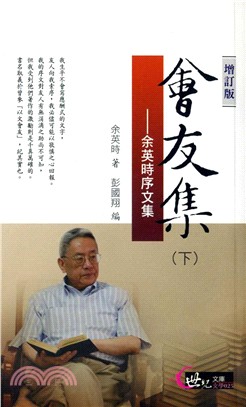閒談:約翰.伯格的語言筆記
商品資訊
系列名:灰盒子
ISBN13:9786267263372
替代書名:Confabulations
出版社:黑體
作者:約翰.伯格
譯者:吳莉君
出版日:2023/11/01
裝訂/頁數:平裝/168頁
規格:19cm*12.8cm*1.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約翰.伯格生前最後作品之一
「口語是身體,是活物,它的外形容貌來自言詞,它的臟腑功能涉及語言學。而這個生物的家不只是那些可以言說的,更是那些不可言說的。」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約翰.伯格是一位熱愛並全身投入寫作的作家,他勤於筆耕,盡可能每天寫作。他的寫作浩繁多元,批判色彩濃厚,對藝術、社會、政治議題的看法也獨具一格,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評家之一。他的作品徹底改變了我們理解視覺語言的方式。
《閒談》這本小書在伯格過世前一年(2016)出版,意義非凡。在本書中,他書寫了語言本身,語言如何與今日的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相關,內容也涉及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書中收錄伯格自身的素描、筆記、回憶和省思,主題從卡謬、羅莎.盧森堡、卓別林到全球資本主義,無所不包。
《閒談》一書帶我們關注「基本、真實且迫切的事物」。
「口語是身體,是活物,它的外形容貌來自言詞,它的臟腑功能涉及語言學。而這個生物的家不只是那些可以言說的,更是那些不可言說的。」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約翰.伯格是一位熱愛並全身投入寫作的作家,他勤於筆耕,盡可能每天寫作。他的寫作浩繁多元,批判色彩濃厚,對藝術、社會、政治議題的看法也獨具一格,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評家之一。他的作品徹底改變了我們理解視覺語言的方式。
《閒談》這本小書在伯格過世前一年(2016)出版,意義非凡。在本書中,他書寫了語言本身,語言如何與今日的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相關,內容也涉及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書中收錄伯格自身的素描、筆記、回憶和省思,主題從卡謬、羅莎.盧森堡、卓別林到全球資本主義,無所不包。
《閒談》一書帶我們關注「基本、真實且迫切的事物」。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2017)
文化藝術評論家、小說家、畫家、劇作家、詩人。192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2017年逝世於法國巴黎。伯格的著作浩繁多元,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評家之一。其備受讚譽的小說和非小說作品包括:開創先河的《觀看的方式》、1972年贏得布克獎的小說《G》、《班托的素描簿》等。
譯者簡介
吳莉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持續進行的瞬間》、《悲傷地形考》等書。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2017)
文化藝術評論家、小說家、畫家、劇作家、詩人。192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2017年逝世於法國巴黎。伯格的著作浩繁多元,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評家之一。其備受讚譽的小說和非小說作品包括:開創先河的《觀看的方式》、1972年贏得布克獎的小說《G》、《班托的素描簿》等。
譯者簡介
吳莉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持續進行的瞬間》、《悲傷地形考》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在約翰.伯格過世前一年(2016)出版,意義非凡。
◎伯格書寫了語言本身,語言如何與今日的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相關,內容也涉及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
◎書中收錄數十張圖片,包括作者的繪圖。
林志明(臺北教育大學特聘教授、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專文導讀
「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
──《觀察者報》(Obsever)
「他揮灑思想一如藝術家揮灑顏料。」
──作家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伯格書寫了語言本身,語言如何與今日的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相關,內容也涉及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
◎書中收錄數十張圖片,包括作者的繪圖。
林志明(臺北教育大學特聘教授、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專文導讀
「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
──《觀察者報》(Obsever)
「他揮灑思想一如藝術家揮灑顏料。」
──作家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序
導讀
林志明
(臺北教育大學特聘教授、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1
「觀看在詞語之前來到。兒童在會說話之前,先觀看及辨認。」
(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 The child looks and recognizes before it can speak.)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最有名的著作《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由以上的句子開場。然而,這句話顯得相當武斷:根據現在的醫學知識,嬰兒剛出生時,視力發展不夠完整,因而所謂的看及辨視應該是出生後更晩的事。的確,在嚴格的概念下,幼兒「說話」大約是一歲之後的事,但若是聽到語言及感受其中的意涵或甚至感情呢?這應該是更早發生的事情。因此,「觀看在詞語之前來到」,如果加入「聽到語詞」作為考量,便有很多探討的空間。
《閒談》(Confabulations)這本小書在伯格過世之前出版,它的意義絕不只是「閒談」:這次的中文翻譯版本加上了副題「約翰.伯格的語言筆記」,強調書中對於語言的重視,但它也不只是涉及語言或只集中在語言的討論之上。伯格在開頭的一篇筆記「自畫像」中說明: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一直以來,伯格是一位熱愛並全身投入寫作的作家;據說,他盡可能每日寫作。
語言在本書中比較像是一個輻湊的中心──除了「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本書書背簡介),還有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甚而,在本書第一篇文章裡,伯格便提出了一個相當深奧但也普遍受到探討的「不僅止於語言」問題,它涉及到「字詞背後」、「言詞之前」和「不可言說」。
雖說這是有關語言一個深奧且普遍受探討的主題,但伯格導出此一主題的方式相當特別:他由翻譯切入,並且說,在文學翻譯中,除了出發的語言及到達的語言之外,還有一個第三個元素:那便是「隱藏在原始文本書寫之前的字詞背後。真正的翻譯要求你回歸到言詞之前。」
伯格正面地回應他所提出的問題,但也提到嬰兒時期最早聽到的語言──由母親嘴裡聽到話語;這彷彿在回應他自己在《觀看的方式》中所提出的斷言。在稍遠之處,他再繼續說道,母語和非說寫語言也有關連,這些語言包括「符號語言,行為語言,空間語言」;但由他之後的行文,我們也知道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圖像。
回到一個根基的語言(母親的話語),以及它與其他形式語言的內在關連,伯格重新處理了他對各種感官及相關語言的先後順序、甚至優先性的問題:它們都和一個「前語言」的層次相關,但也因而有相互的內在關連性:這時若提問何者具有優先位置,便顯得沒有那麼重要,反而是尋求並展示它們之間的關連性,才更為有趣。
2
如此,對於本書的題名,我們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解讀。本書英文原名 “Confabulations” 除了一般意義下的「閒談」或更具醫學意義的「虛構、臆想」之外,還有一個作者更具個人意謂的使用方式,即字詞之間的「交談議論」。伯格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他的書寫經驗:
書寫時,完成幾行之後,我會讓那些字詞溜回去,溜回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在那裡,它們馬上就被其他一堆字詞認出來,並熱烈歡迎,它們和那些字詞有一種意義的或對立的或隱喻的或頭韻的或節奏的親近性。我聽著他們交談議論。它們聚在一起,針對我挑選的字詞,爭辯我的用法。它們質疑我分派給它們的角色。
於是我調整文句,修改一、兩個字,再次提交出去。另一陣交談議論接著展開。
字詞之間有其自身的關係和動力,伯格用了「語言生物」和「議論交談」這兩個隱喻來作說明。那麼,是否能順著前面的各種非說寫語言間的內在關係,更進一步地說,這個「生態圈」中的「交談」,不只侷限於字詞之間,還包括言說與歌曲、繪畫、聆聽等各種身體經驗及更綜合性的回憶之間的關係?
3
雖然伯格被視為擅長書寫「知性散文」,而且也曾因為小說《G》榮獲布克獎,但在他的「時代傳記」作者史博林(Joshua Sperling)眼中,更具開創性的應是一種可稱為「非虛構創意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所謂「無法歸類」的書寫:「拗彎各種文類,把遊記和知性散文、回憶錄和理論折疊在一起──這一切如果沒有他的榜樣在前是無法想像的。」《閒談》這本他生前的最後出版,可說是此一「非虛構創意寫作」爐火純青的表現。
比如書中一篇題名為〈死神也在世外桃源〉的文章,先由對瑞典畫家友人斯溫(Sven)在南法鄉間共同生活的回憶開始,中間突然插入了一幅林布蘭最後的畫作〈聖殿中的西緬〉作為伏筆,後來在其喪禮中才揭露這幅畫的大型複製釘掛於其最後畫室的牆上。而這中間書寫已經歷了對友人水果靜物畫的品評(畫雖小、但其中「所有色彩都能彼此交流」),對於法國克難但吸引許多友人前來的生活回憶(「斯溫將他的世外桃源隨身攜帶」),對於瑞典食物有趣的描寫(「一大堆蛋糕和五顏六色的點心,如玩具一般陳列出來,供賓客挑選。」);在斯溫的喪禮結束後,伯格繼續了一段機車之旅,目標是一座小島;在島上除了一艘大船突然的出現之外,一位小男孩早上見到麋鹿,提供整個旅程輕微的夢幻感。回到法國上薩伏依的居所,伯格想起他和斯溫在倫敦普桑(Poussin)大展中的初遇,而〈死神也在世外桃源〉正是其中重要的展出畫作。這篇編織回憶、遊記和簡短畫評的散文,正是篇記述著深刻友誼的「非虛構創意寫作」。
《閒談》中最長的一篇文章〈關於歌曲的幾點筆記〉,更是交織著回憶、歌詞、舞蹈、照片、繪畫、對於手語的觀察、詩作的長篇引用等,可說是把各種說寫和非說寫「語言」無間縫地交織在一起。在其中,伯格透過歌曲提出了身體和語言的關係,甚至更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語言(歌曲)內在於身體的理論雛形:
我們追隨歌曲,是為了被歌曲包圍。正因如此,歌曲提供給我們的東西,不同於其他的交流訊息或形式。我們置身於訊息內部。那個未被唱出的、與個人無關的世界,依然留在外面,在胎盤的另一邊。
*
伯格一直有個寫作時間之書的計畫,但終其一生並沒有實現。在《閒談》這本書的最後,他仍回到此一主題,而以下應是他的最後證詞:
時間並非線性,而是循環的圈。我們的人生並非一條直線上的某一點──史無前例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正用它的「即時貪婪」(Instant Greed)截斷那條線。我們不是一條直線上的某一點;我們是環圈的中心。
在這個環圈的中心,伯格回到「母語」,編織著各種「語言」、身體經驗和回憶;如同本書的最後一語,他的寫作終止了,但對他的閱讀,「無休無止」。
林志明
(臺北教育大學特聘教授、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1
「觀看在詞語之前來到。兒童在會說話之前,先觀看及辨認。」
(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 The child looks and recognizes before it can speak.)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最有名的著作《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由以上的句子開場。然而,這句話顯得相當武斷:根據現在的醫學知識,嬰兒剛出生時,視力發展不夠完整,因而所謂的看及辨視應該是出生後更晩的事。的確,在嚴格的概念下,幼兒「說話」大約是一歲之後的事,但若是聽到語言及感受其中的意涵或甚至感情呢?這應該是更早發生的事情。因此,「觀看在詞語之前來到」,如果加入「聽到語詞」作為考量,便有很多探討的空間。
《閒談》(Confabulations)這本小書在伯格過世之前出版,它的意義絕不只是「閒談」:這次的中文翻譯版本加上了副題「約翰.伯格的語言筆記」,強調書中對於語言的重視,但它也不只是涉及語言或只集中在語言的討論之上。伯格在開頭的一篇筆記「自畫像」中說明: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一直以來,伯格是一位熱愛並全身投入寫作的作家;據說,他盡可能每日寫作。
語言在本書中比較像是一個輻湊的中心──除了「思想、藝術、歌曲、說故事和政治論述」(本書書背簡介),還有勞作、回憶、苦難、希望、共同生活甚至對鳥鳴的聆聽;甚而,在本書第一篇文章裡,伯格便提出了一個相當深奧但也普遍受到探討的「不僅止於語言」問題,它涉及到「字詞背後」、「言詞之前」和「不可言說」。
雖說這是有關語言一個深奧且普遍受探討的主題,但伯格導出此一主題的方式相當特別:他由翻譯切入,並且說,在文學翻譯中,除了出發的語言及到達的語言之外,還有一個第三個元素:那便是「隱藏在原始文本書寫之前的字詞背後。真正的翻譯要求你回歸到言詞之前。」
伯格正面地回應他所提出的問題,但也提到嬰兒時期最早聽到的語言──由母親嘴裡聽到話語;這彷彿在回應他自己在《觀看的方式》中所提出的斷言。在稍遠之處,他再繼續說道,母語和非說寫語言也有關連,這些語言包括「符號語言,行為語言,空間語言」;但由他之後的行文,我們也知道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圖像。
回到一個根基的語言(母親的話語),以及它與其他形式語言的內在關連,伯格重新處理了他對各種感官及相關語言的先後順序、甚至優先性的問題:它們都和一個「前語言」的層次相關,但也因而有相互的內在關連性:這時若提問何者具有優先位置,便顯得沒有那麼重要,反而是尋求並展示它們之間的關連性,才更為有趣。
2
如此,對於本書的題名,我們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解讀。本書英文原名 “Confabulations” 除了一般意義下的「閒談」或更具醫學意義的「虛構、臆想」之外,還有一個作者更具個人意謂的使用方式,即字詞之間的「交談議論」。伯格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他的書寫經驗:
書寫時,完成幾行之後,我會讓那些字詞溜回去,溜回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在那裡,它們馬上就被其他一堆字詞認出來,並熱烈歡迎,它們和那些字詞有一種意義的或對立的或隱喻的或頭韻的或節奏的親近性。我聽著他們交談議論。它們聚在一起,針對我挑選的字詞,爭辯我的用法。它們質疑我分派給它們的角色。
於是我調整文句,修改一、兩個字,再次提交出去。另一陣交談議論接著展開。
字詞之間有其自身的關係和動力,伯格用了「語言生物」和「議論交談」這兩個隱喻來作說明。那麼,是否能順著前面的各種非說寫語言間的內在關係,更進一步地說,這個「生態圈」中的「交談」,不只侷限於字詞之間,還包括言說與歌曲、繪畫、聆聽等各種身體經驗及更綜合性的回憶之間的關係?
3
雖然伯格被視為擅長書寫「知性散文」,而且也曾因為小說《G》榮獲布克獎,但在他的「時代傳記」作者史博林(Joshua Sperling)眼中,更具開創性的應是一種可稱為「非虛構創意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所謂「無法歸類」的書寫:「拗彎各種文類,把遊記和知性散文、回憶錄和理論折疊在一起──這一切如果沒有他的榜樣在前是無法想像的。」《閒談》這本他生前的最後出版,可說是此一「非虛構創意寫作」爐火純青的表現。
比如書中一篇題名為〈死神也在世外桃源〉的文章,先由對瑞典畫家友人斯溫(Sven)在南法鄉間共同生活的回憶開始,中間突然插入了一幅林布蘭最後的畫作〈聖殿中的西緬〉作為伏筆,後來在其喪禮中才揭露這幅畫的大型複製釘掛於其最後畫室的牆上。而這中間書寫已經歷了對友人水果靜物畫的品評(畫雖小、但其中「所有色彩都能彼此交流」),對於法國克難但吸引許多友人前來的生活回憶(「斯溫將他的世外桃源隨身攜帶」),對於瑞典食物有趣的描寫(「一大堆蛋糕和五顏六色的點心,如玩具一般陳列出來,供賓客挑選。」);在斯溫的喪禮結束後,伯格繼續了一段機車之旅,目標是一座小島;在島上除了一艘大船突然的出現之外,一位小男孩早上見到麋鹿,提供整個旅程輕微的夢幻感。回到法國上薩伏依的居所,伯格想起他和斯溫在倫敦普桑(Poussin)大展中的初遇,而〈死神也在世外桃源〉正是其中重要的展出畫作。這篇編織回憶、遊記和簡短畫評的散文,正是篇記述著深刻友誼的「非虛構創意寫作」。
《閒談》中最長的一篇文章〈關於歌曲的幾點筆記〉,更是交織著回憶、歌詞、舞蹈、照片、繪畫、對於手語的觀察、詩作的長篇引用等,可說是把各種說寫和非說寫「語言」無間縫地交織在一起。在其中,伯格透過歌曲提出了身體和語言的關係,甚至更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語言(歌曲)內在於身體的理論雛形:
我們追隨歌曲,是為了被歌曲包圍。正因如此,歌曲提供給我們的東西,不同於其他的交流訊息或形式。我們置身於訊息內部。那個未被唱出的、與個人無關的世界,依然留在外面,在胎盤的另一邊。
*
伯格一直有個寫作時間之書的計畫,但終其一生並沒有實現。在《閒談》這本書的最後,他仍回到此一主題,而以下應是他的最後證詞:
時間並非線性,而是循環的圈。我們的人生並非一條直線上的某一點──史無前例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正用它的「即時貪婪」(Instant Greed)截斷那條線。我們不是一條直線上的某一點;我們是環圈的中心。
在這個環圈的中心,伯格回到「母語」,編織著各種「語言」、身體經驗和回憶;如同本書的最後一語,他的寫作終止了,但對他的閱讀,「無休無止」。
目次
導讀/林志明
自畫像
Self-Portrait
給羅莎的禮物
A Gift for Rosa
沒教養
Impertinence
跌倒的藝術:幾則筆記
Some Notes About the Art of Falling
死神也在世外桃源
Et in Arcadia Ego
保持警戒
On Vigilance
聚會之所
A Meeting Plac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a Lalala Lalala La
關於歌曲的幾點筆記
Some Notes about Song
銀光片片
Pieces of Silver
如何對抗失憶狀態
How to Resist a State of Forgetfulness
圖片出處
自畫像
Self-Portrait
給羅莎的禮物
A Gift for Rosa
沒教養
Impertinence
跌倒的藝術:幾則筆記
Some Notes About the Art of Falling
死神也在世外桃源
Et in Arcadia Ego
保持警戒
On Vigilance
聚會之所
A Meeting Plac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a Lalala Lalala La
關於歌曲的幾點筆記
Some Notes about Song
銀光片片
Pieces of Silver
如何對抗失憶狀態
How to Resist a State of Forgetfulness
圖片出處
書摘/試閱
自畫像
Self-Portrait
我已經寫了約莫八十年。起先是書信,接著是詩歌與講演,後來是故事、文章與書籍,如今是筆記。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讓我們從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行為開始檢視。今日大多數的翻譯都是技術方面的,而我要談的是文學翻譯。也就是說,翻譯的文本內容與個人經驗有關。
傳統上對翻譯的看法,涉及到研究某一頁面上以某種語言書寫的字詞,然後將它們轉化成另一頁面上的另一種語言。這過程首先要進行所謂的逐字翻譯;接著要做出適當調整,以尊重並融入第二種語言的傳統和規則;最後要再下番苦功,重新創造出可等同於原始文本的「聲音」(voice)。許多翻譯,或說大多數的翻譯是遵循這樣的程序,得到的成果也頗具價值,但終究是二流翻譯。
何以這麼說?因為真正的翻譯並非兩種語言之間的二元關係,而是一種三角關係。這個三角形的第三點,是隱藏在原始文本書寫之前的字詞背後。真正的翻譯要求你回歸到言詞之前。
我們反覆閱讀、一再咀嚼原始文本,希望能穿透字詞,觸及到當初激發出這些字詞的景象或經驗。接著,我們採集在字詞背後發現之物,拿起那個顫顫巍巍、近乎無言的「東西」,把它放置在需要將它翻譯出來的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背後。接下來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主方語言接納並歡迎那個等著被言說出來的「東西」。
這種做法提醒我們,語言無法簡化成字典或詞庫。語言也無法減縮成以該語言書寫的作品庫。
口語是身體,是活物,它的外形容貌來自言詞,它的臟腑功能涉及語言學。而這個生物的家不只是那些可以言說的,更是那些不可言說的。
想想「母語」(Mother Tongue,字義是「母親的舌頭」)一詞。俄文的母語是Rodnoi-yazyk,意思是「最接近或最親近的舌頭」(Nearest or Dearest Tongue)。必要時,你可以稱它為「親愛的舌頭」(Darling Tongue)。
母語是我們的第一語言,是嬰兒時期最早從母親嘴裡聽到的。「母語」一詞就是這樣來的。
之所以提及這點,是因為我正在描述的語言生物毫無疑問是女性。我想像,那個語言生物的核心部位是語音子宮。
一種母語裡包含了所有母語。或者,換個說法:每一種母語都是共通的。
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做出精彩論述,證明所有語言都擁有某些共同的結構和程序,不僅限於說寫語言。也就是說,母語和非說寫式的語言也有關聯(也能押韻?),例如符號語言,行為語言,空間語言。
畫畫時,我就是在試圖解開並謄抄一份由形貌構成的文本,我知道,這份文本在我的母語裡已經有一個無法言喻但肯定無疑的位置。
單字、詞彙和短句,可以脫離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僅當成標籤使用。但如此一來,它們會變得呆板空洞。重複使用首字母縮寫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範例。今日大多數的主流政治論述,都是由這類脫離了語言生物、無趣死氣的字詞所構成。而這類死氣沉沉的「浮言夸語」會抹除記憶,滋長無情的自滿。
多年來,促使我寫作的驅力,是我預感到有些事情需要被講述,如果我不試著講述它,它可能永遠沒機會被講述。所以,我不太會把自己想像成具有影響力的專業作家,更像是臨時上來救場的人。
書寫時,完成幾行之後,我會讓那些字詞溜回去,溜回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在那裡,它們馬上就被其他一堆字詞認出來,並熱烈歡迎,它們和那些字詞有一種意義的或對立的或隱喻的或頭韻的或節奏的親近性。我聽著他們交談議論。它們聚在一起,針對我挑選的字詞,爭辯我的用法。它們質疑我分派給它們的角色。
於是我調整文句,修改一兩個字,再次提交出去。另一陣交談議論接著展開。
如此這般循環往復,直到出現暫時達成共識的喃喃低語。我接著朝下一段推進。
另一陣交談議論再次展開……
其他人可以隨自己高興,把我定位成一名作家。但對我而言,我是惡女之子(the son of a bitch)──你們應該能猜出那個惡女是誰,對吧?
Self-Portrait
我已經寫了約莫八十年。起先是書信,接著是詩歌與講演,後來是故事、文章與書籍,如今是筆記。
一直以來,書寫行為對我至關緊要;它幫助我理解事物,延續人生。不過,書寫其實是分支,衍生自某個更深刻、更普遍的事物──我們和語言本身的關係。而這幾則筆記的主題,正是語言。
讓我們從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行為開始檢視。今日大多數的翻譯都是技術方面的,而我要談的是文學翻譯。也就是說,翻譯的文本內容與個人經驗有關。
傳統上對翻譯的看法,涉及到研究某一頁面上以某種語言書寫的字詞,然後將它們轉化成另一頁面上的另一種語言。這過程首先要進行所謂的逐字翻譯;接著要做出適當調整,以尊重並融入第二種語言的傳統和規則;最後要再下番苦功,重新創造出可等同於原始文本的「聲音」(voice)。許多翻譯,或說大多數的翻譯是遵循這樣的程序,得到的成果也頗具價值,但終究是二流翻譯。
何以這麼說?因為真正的翻譯並非兩種語言之間的二元關係,而是一種三角關係。這個三角形的第三點,是隱藏在原始文本書寫之前的字詞背後。真正的翻譯要求你回歸到言詞之前。
我們反覆閱讀、一再咀嚼原始文本,希望能穿透字詞,觸及到當初激發出這些字詞的景象或經驗。接著,我們採集在字詞背後發現之物,拿起那個顫顫巍巍、近乎無言的「東西」,把它放置在需要將它翻譯出來的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背後。接下來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主方語言接納並歡迎那個等著被言說出來的「東西」。
這種做法提醒我們,語言無法簡化成字典或詞庫。語言也無法減縮成以該語言書寫的作品庫。
口語是身體,是活物,它的外形容貌來自言詞,它的臟腑功能涉及語言學。而這個生物的家不只是那些可以言說的,更是那些不可言說的。
想想「母語」(Mother Tongue,字義是「母親的舌頭」)一詞。俄文的母語是Rodnoi-yazyk,意思是「最接近或最親近的舌頭」(Nearest or Dearest Tongue)。必要時,你可以稱它為「親愛的舌頭」(Darling Tongue)。
母語是我們的第一語言,是嬰兒時期最早從母親嘴裡聽到的。「母語」一詞就是這樣來的。
之所以提及這點,是因為我正在描述的語言生物毫無疑問是女性。我想像,那個語言生物的核心部位是語音子宮。
一種母語裡包含了所有母語。或者,換個說法:每一種母語都是共通的。
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做出精彩論述,證明所有語言都擁有某些共同的結構和程序,不僅限於說寫語言。也就是說,母語和非說寫式的語言也有關聯(也能押韻?),例如符號語言,行為語言,空間語言。
畫畫時,我就是在試圖解開並謄抄一份由形貌構成的文本,我知道,這份文本在我的母語裡已經有一個無法言喻但肯定無疑的位置。
單字、詞彙和短句,可以脫離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僅當成標籤使用。但如此一來,它們會變得呆板空洞。重複使用首字母縮寫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範例。今日大多數的主流政治論述,都是由這類脫離了語言生物、無趣死氣的字詞所構成。而這類死氣沉沉的「浮言夸語」會抹除記憶,滋長無情的自滿。
多年來,促使我寫作的驅力,是我預感到有些事情需要被講述,如果我不試著講述它,它可能永遠沒機會被講述。所以,我不太會把自己想像成具有影響力的專業作家,更像是臨時上來救場的人。
書寫時,完成幾行之後,我會讓那些字詞溜回去,溜回它們所屬的語言生物。在那裡,它們馬上就被其他一堆字詞認出來,並熱烈歡迎,它們和那些字詞有一種意義的或對立的或隱喻的或頭韻的或節奏的親近性。我聽著他們交談議論。它們聚在一起,針對我挑選的字詞,爭辯我的用法。它們質疑我分派給它們的角色。
於是我調整文句,修改一兩個字,再次提交出去。另一陣交談議論接著展開。
如此這般循環往復,直到出現暫時達成共識的喃喃低語。我接著朝下一段推進。
另一陣交談議論再次展開……
其他人可以隨自己高興,把我定位成一名作家。但對我而言,我是惡女之子(the son of a bitch)──你們應該能猜出那個惡女是誰,對吧?
主題書展
更多
相關商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