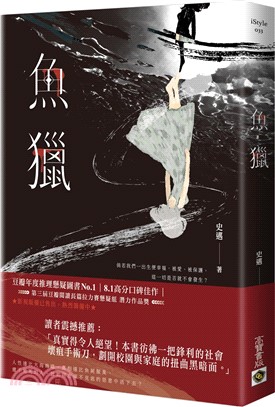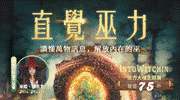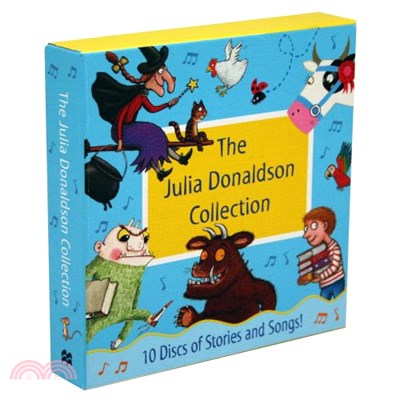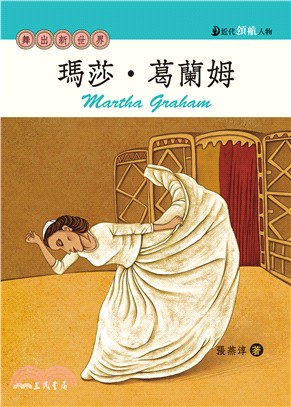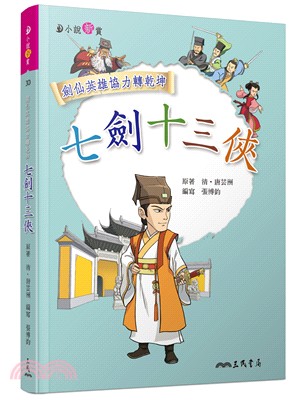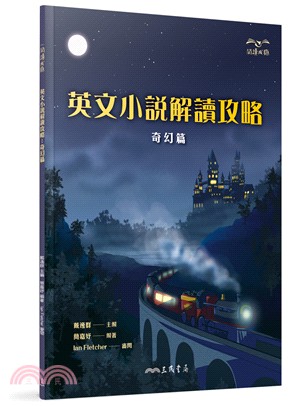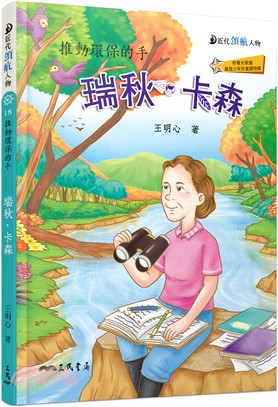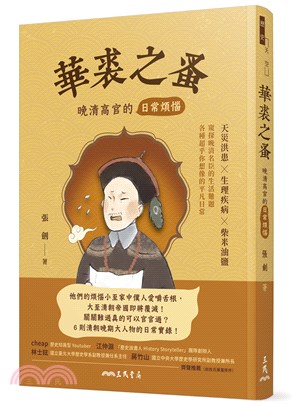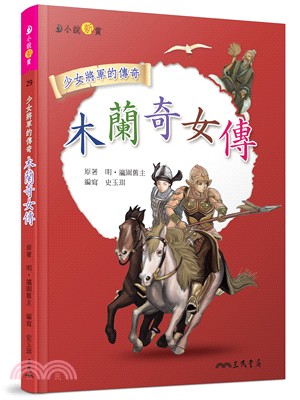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豆瓣年度推理懸疑圖書No. 1、8.1高分口碑佳作
★第三屆豆瓣閱讀長篇拉力賽懸疑組 潛力作品獎
★影視版權已售出,熱烈籌備中
讀者震撼推薦:
「真實得令人絕望!本書彷彿一把鋒利的社會壞疽手術刀,劃開校園與家庭的扭曲陰暗面。」
人性遠比深海黑暗,真相遠比魚屍腥臭。
還不能死的人,該如何在惡意洶湧的世界裡活下去?
──「倘若我們一出生便幸福、被愛、被保護,這一切是否就不會發生?」
*
魚獵,通「漁獵」。
謂捕魚,謂貪色。
謂竊取,謂掠奪。
鹽洋市的兩個漁村裡誕生了兩個女孩,一個名叫俞靜,一個取作何器。
兩人高中畢業那年,何器參加完同學聚會便失蹤了。
她的最後一次呼吸消散在黏膩的海風裡,漁民在海邊岩石上發現了她的屍體,像隻擱淺的魚。
殺死她的不是海浪,是更加洶湧的惡意。
下一個冬季,俞靜意外昏迷數天,在招魂儀式後悠悠醒轉,說自己叫作「何器」,舉手投足和死去的她一模一樣,唯有記憶停留在死前一週。
「何器」開始追查自己死亡的真相,在所有人都不願回想的黑暗記憶中,埋藏著萬劫不復的深淵。
「她」究竟真是何器,還是俞靜?
那個冰冷的夏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張漁網徐徐展開,魚與獵手,都在暗處……
【讀者熱烈好評】
《魚獵》真的太好看了,感謝有人買了影視版權,期待能拍出來。被懸疑故事的標籤吸引,但是不只這個亮點,清晰的敘事邏輯,夾雜著樸素的哲學和抒情文字,還有生動的人物刻畫和心理獨白,真情實感地為女孩子的友情感動了,值得二刷。
――豆瓣閱讀網友 銀醬一生推333
很會寫,好到讓我覺得羡慕和嫉妒。感覺每一句描述都不是多餘的。是一段充滿海風的腥辣故事,可以說是一場復仇,也可以說是不斷接近真相所經歷的成長和自我救贖,有女生之間的友誼,各自的懦弱和勇敢,有校園暴力,重男輕女,畸形家庭教育,勢力勾結,權力交織……有著非常豐富的細節但並不雜亂,一切進展都有跡可循。我太喜歡充滿畫面感的語言了,厲害的是還十分精準。
――豆瓣閱讀網友 瘋了恩珠
心情就如同海水的漲潮退潮,沉浸於作者細膩的文字技巧和故事邏輯;每次在回憶的故事點,總會讓我想起《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同的是,它真實的讓人絕望,而這些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魚獵》揪心後終有釋懷的那一刻,釋懷的是報應終將來臨,這就是所有懸疑小說寬慰人的一點。
――豆瓣閱讀網友 無適無莫
★第三屆豆瓣閱讀長篇拉力賽懸疑組 潛力作品獎
★影視版權已售出,熱烈籌備中
讀者震撼推薦:
「真實得令人絕望!本書彷彿一把鋒利的社會壞疽手術刀,劃開校園與家庭的扭曲陰暗面。」
人性遠比深海黑暗,真相遠比魚屍腥臭。
還不能死的人,該如何在惡意洶湧的世界裡活下去?
──「倘若我們一出生便幸福、被愛、被保護,這一切是否就不會發生?」
*
魚獵,通「漁獵」。
謂捕魚,謂貪色。
謂竊取,謂掠奪。
鹽洋市的兩個漁村裡誕生了兩個女孩,一個名叫俞靜,一個取作何器。
兩人高中畢業那年,何器參加完同學聚會便失蹤了。
她的最後一次呼吸消散在黏膩的海風裡,漁民在海邊岩石上發現了她的屍體,像隻擱淺的魚。
殺死她的不是海浪,是更加洶湧的惡意。
下一個冬季,俞靜意外昏迷數天,在招魂儀式後悠悠醒轉,說自己叫作「何器」,舉手投足和死去的她一模一樣,唯有記憶停留在死前一週。
「何器」開始追查自己死亡的真相,在所有人都不願回想的黑暗記憶中,埋藏著萬劫不復的深淵。
「她」究竟真是何器,還是俞靜?
那個冰冷的夏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張漁網徐徐展開,魚與獵手,都在暗處……
【讀者熱烈好評】
《魚獵》真的太好看了,感謝有人買了影視版權,期待能拍出來。被懸疑故事的標籤吸引,但是不只這個亮點,清晰的敘事邏輯,夾雜著樸素的哲學和抒情文字,還有生動的人物刻畫和心理獨白,真情實感地為女孩子的友情感動了,值得二刷。
――豆瓣閱讀網友 銀醬一生推333
很會寫,好到讓我覺得羡慕和嫉妒。感覺每一句描述都不是多餘的。是一段充滿海風的腥辣故事,可以說是一場復仇,也可以說是不斷接近真相所經歷的成長和自我救贖,有女生之間的友誼,各自的懦弱和勇敢,有校園暴力,重男輕女,畸形家庭教育,勢力勾結,權力交織……有著非常豐富的細節但並不雜亂,一切進展都有跡可循。我太喜歡充滿畫面感的語言了,厲害的是還十分精準。
――豆瓣閱讀網友 瘋了恩珠
心情就如同海水的漲潮退潮,沉浸於作者細膩的文字技巧和故事邏輯;每次在回憶的故事點,總會讓我想起《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同的是,它真實的讓人絕望,而這些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魚獵》揪心後終有釋懷的那一刻,釋懷的是報應終將來臨,這就是所有懸疑小說寬慰人的一點。
――豆瓣閱讀網友 無適無莫
作者簡介
史邁
筆名:邁可貼
編劇,豆瓣閱讀高人氣作者。
畢業於中國電影資料館。
曾獲第十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
筆名:邁可貼
編劇,豆瓣閱讀高人氣作者。
畢業於中國電影資料館。
曾獲第十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
目次
楔子
Chapter 01
01.黑魚
02.紅線
03.青銅白鶴
04.聾羊
05.鬣狗們
06.腥氣
07.魚鉤(上)
08.魚鉤(下)
Chapter 02
09.生銹
10.蝦皮
11.結痂(上)
12.結痂(下)
13.本能
Chapter 03
14.鋸齒
15.蚌殼
16.蠶食
17.蝸牛
18.暗礁
19.燒船
Chapter 04
20.海鳥
21.寄居
22.香灰
23.壁櫥
24.倒刺(上)
25.倒刺(下)
Chapter 05
26寒栗
27.活殺
28.鱗片
29.擰緊
30.海霧
31.盛夏
番外 燈火
Chapter 01
01.黑魚
02.紅線
03.青銅白鶴
04.聾羊
05.鬣狗們
06.腥氣
07.魚鉤(上)
08.魚鉤(下)
Chapter 02
09.生銹
10.蝦皮
11.結痂(上)
12.結痂(下)
13.本能
Chapter 03
14.鋸齒
15.蚌殼
16.蠶食
17.蝸牛
18.暗礁
19.燒船
Chapter 04
20.海鳥
21.寄居
22.香灰
23.壁櫥
24.倒刺(上)
25.倒刺(下)
Chapter 05
26寒栗
27.活殺
28.鱗片
29.擰緊
30.海霧
31.盛夏
番外 燈火
書摘/試閱
楔子
二○○三年,中國癸未(羊)年。
街道上摻雜著紅色鞭炮屑的髒雪還未化完,SARS爆發了。
平時十塊錢 一包的板藍根 漲到了四十,五塊錢一瓶的白醋幾乎一天翻一倍。
白醋漲到八十塊錢一瓶的時候,與鹽洋市相隔不遠的兩座漁村出生了兩個女孩。
大泉港的名叫何器,俞家臺的名叫俞靜,兩人前後相差一週。
羊年出生的女孩命苦。
這個說法最早好像是從清朝開始的。儘管沒有什麼依據,但信者眾多,尤其是在鹽洋這種比較封閉的北方小城。
村裡的老人出於好心,說三月出生的孩子反而有福氣,因為驚蟄過後,萬物復生,所以一輩子總能逢凶化吉,平安順遂。
可惜的是,老人說錯了。
二○二○年七月,何器參加完高中畢業聚會後失蹤。三天後,沿岸橫七豎八的消波塊隨著退潮裸露出來,去岩石上耙海蠣子 肉的漁民在那裡發現了她。
何器靜靜地趴在一塊岩石上,尖銳粗礪的貝殼把她的四肢剮出一道道蒼白的口子,拇指大的螃蟹在她的髮絲中鑽來鑽去。那條昂貴的墨綠色長裙沾滿泥沙,纏繞在一堆亂蓬蓬的海藻裡。
她垂在沙灘上的右手隨著海浪輕輕擺動,遠遠看起來,像是在玩水。
第一章
1. 黑魚
冬天的海邊很少見到烏鴉了。
老俞盯著灰藻色的海面發愁。潮水還在漲,海浪每吞吐一次白沫,沙岸上就多一些保麗龍垃圾,見不到一星點死貝爛蝦。而且臨近年關,碼頭上的人空前地多,鳥就更不敢來了。
要是再找不到烏鴉,俞靜就真醒不過來了。
老俞臉上的褶子被海風吹成一張粗糙的漁網。他把尖頭的捲菸一口吸到底,彈進海裡,起身打了通電話。
一天前老俞獨自出海,想多打點海產賣了過年。這幾年休漁期越來越長,很多漁民養不起大船,都被馳航水產低價買走,等休漁期一過,開了海,又轉頭高價租給漁民。像自家這種幾十馬力的老破漁船沒有水產公司願意收,老俞也捨不得賣。他想,多出幾趟海,養活一家子也沒問題。
往回退二十年,那是大海和老俞的鼎盛期,俞家臺大小漁船加起來有上百條,老俞一百九的個子,身強力壯,熬幾個大夜都沒問題。跟村裡的老少爺們出趟海,每回都是滿艙而歸,隔三差五就能打上一條幾十公斤重的大魚。哪像現在,出一次海,拉回來的全是一些小魚小蝦,堆地上都沒人踩。
這次也一樣。老俞一天一夜沒闔眼,臉上沾滿了細小的魚鱗,渾身腥臭,手指頭凍 得伸不直,就撈了幾十斤的東西,空碎貝殼占了一半,漁網也在打盹的時候被暗礁拉破了。
前兩天,幫工的大飛辭了職,去馳航水產當撿魚工,說那裡提供五險一金 。現在願意出海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賺不到錢是一個原因,還有就是風吹日晒,一年到頭在海上漂著見不到人,一不小心就會打一輩子光棍。大飛一走,老俞一時半刻找不著人頂替,網破了也只能自己補。潮要落了,他心煩意亂,只想趕緊回家蒙頭睡一覺。
老俞開動了馬達,震得海面嘩啦作響。突然,一條大黑頭魚蹦上了他的船,把船艙砸得劈里啪啦響,消停了就鼓著兩扇寬鰓呼蚩猛喘。
老俞在海上漂了半輩子,魚蹦上船的事不是頭一回見。但老話說「開船不吃自來魚」,說這種魚是龍王預付的買命錢,所以漁民見了基本上都是扔回海裡。
老俞掐起黑頭魚的鰓,掂了掂,有八九斤重。
他很久沒見過這麼肥的魚了。
臨近中午,細長的碼頭上早就撐起一排彩色的遮雨棚,擠得密不透風。畢竟到了年關,一年就這麼一回,各家都卯足了勁吆喝賣貨。
每頂遮雨棚下面都擠擠挨挨擺著幾隻大紅盆、幾個塑膠魚箱、沾滿魚鱗的電子秤,還有裹得鼓鼓囊囊、圍著彩色頭巾、臉皮皴紅的漁家婦女。等丈夫們把海產拉上岸,就一邊賣貨,一邊在冰水裡熟練挑揀,最大的梭子蟹扔到「九○」的盆裡,小的就扔到「三○」的盆裡,小黃魚在地上堆成小山。
日頭升起來,買年貨的人踩著髒水在雨棚下面鑽來鑽去。有人專門開車來俞家碼頭買海產,一是圖剛打上來新鮮,二是比海鮮市場便宜,買多了還能再搭一隻肥蟹。
老俞泊了船,拴好,把海產倒進鏤空的魚箱,再拎起一個小紅桶,大黑頭魚蜷在裡面艱難地喘著。他朝自家印著「娃哈哈」的綠色遮雨棚走去。
老俞遠遠看見只有幾個盆在那兒,沒瞧見人。他趕緊跑了幾步,才發現女兒俞靜又躲在貨箱後面,學著抖音上的尖臉小姑娘編辮子。她把又厚又長的頭髮分成十八綹,纏上小彩繩,一下一下扭成麻花,那認真勁像修文物似的,好幾個客人來問價也不搭理,讓人家挑完自己過秤。
老俞再一看,注活水的塑膠管翹得老高,水都噴到外面去了,紅盆裡的梭子蟹沉了底,全都一動不動。
他的火轟一下子就上來了。
俞靜是他的大女兒,也可以說是老二。老婆房玲第一胎是個兒子,出生三個月就染病死了。農村有規矩,小孩不能立墳頭,得去荒山扔掉,說是對下一胎好。老俞不忍心,還是幫他買了幾身小衣服,偷偷託人埋在後山上,每年清明都和房玲去燒點金紙。
一年之後就生了俞靜。
足月,順產,剛生出來就活蹦亂跳得像條泥鰍,哭聲特別大,不到一歲就學會走路了,像隻小狗似的天天跟在老俞後頭。而且學東西很快,動手能力極強,老俞和房玲在碼頭賣貨的時候,小俞靜就在旁邊的沙灘上玩,別的小孩堆沙堡,她拿著小耙子挖蛤蜊,一個下午就能挖一小桶。
房玲是個樸實的海邊婦女,兩隻腳從沒邁出鹽洋的地界,兩隻手除了扒拉海產不會幹別的,更別說編辮子這種精細活了。所以俞靜從小就是短髮,再加上天天吃海鮮,蛋白質充足,到了青春期,個子躥得很快,手長腿長,小學時就是女生堆裡最高的。碼頭上的人都說俞靜遠看像個假小子似的,要是再來一胎肯定是個男孩。
雖然是開玩笑,但回回都戳得老俞心裡一緊。
有時候俞靜趴在飯桌上做作業,老俞就會偷偷打量她。不仔細看還真像個小子,性格也像,可惜就不是。
老俞想再生個兒子。
這個念頭在海上的時候尤其強烈。要是老大沒死,現在就有個大小夥子跟自己一起打魚了,可以傳授他這些年自己一船一船撈上來的經驗,教他怎麼利用潮水走向撒網,怎麼判斷哪裡有最肥的魚。房玲和俞靜什麼都不懂,在家吃完飯就一起看電視,很少聊天。老俞總覺得說不出來的「話」是有形狀的,悶在肚子裡的話越來越多,撐得自己的肚皮也越來越大。要是再有個兒子,這些話就能一點一點順出來,否則只能跟著他百年之後爛到地裡。
他把這個念頭跟房玲一說,房玲也同意了。她一輩子沒自己拿過主意,結婚之前聽父母的,結婚之後就聽老俞的。
於是俞靜考大學那年,房玲就懷孕了。沒跟俞靜打過招呼,俞靜知道後也沒問什麼。老俞心想,這一點倒是像自己,不愛問話,遇到不懂的事就先裝到肚子裡自己琢磨,琢磨過來就琢磨過來,沒琢磨過來就算了。這樣挺好的,人一輩子不能每件事都想得明白。
房玲現在懷孕八個多月,肚子鼓得老大,有經驗的產婆看了都說是小子。老俞生怕有什麼閃失,不讓房玲碰冰水。剛好俞靜放寒假,就想讓她幫忙分擔一下家裡的活。
俞靜升學考成績不好,沒考上大學,去了市裡的職業學校學飯店管理。老俞記得她小時候明明成績不錯,還拿過幾張獎狀,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讀書的。可能是高中,當時實驗高中為了方便管理,強制學生寄宿,兩週放一次假。從那時候起,俞靜的性格就變了,不再瘋瘋癲癲地到處亂跑,頭髮也越來越長,開始學別人穿裙子,畫眉毛,看起來確實有了女孩的樣子,但考試名次就像扔鐵錨似的,一溜煙就沉到海底。
考上職業學校之後就更放飛了。雖然學校離家不遠,坐一八路公車一個小時就能到,但俞靜只願意在寒暑假回來。每次回來頭髮都換個顏色,有一回整整數出四個顏色。房玲特別看不慣染髮,一開始還數落兩句,後來就不管了。俞靜在家裡也不願意和他們多說話,醒了就躺床上滑手機,餓了就下床找吃的,別說幫忙揀魚看攤了,吃完飯的碗都不願意洗。
眼見房玲肚子越來越大,坐著都費勁,老俞沒轍了,說可以發薪水給俞靜,賣一天貨給五十塊錢,她才不情不願地答應。
之前老俞老聽人說,兒女是父母前世的債主。他一點都不信,後來每回被俞靜氣到不行的時候他就在心裡默念這句話:「我上輩子欠她的,這輩子還清,下輩子就不用見了。」還真的滿管用,每次一想完,氣就消一半了。
但今天不行,默念一百遍也不行。
他把魚箱啪一聲扔到地上,俞靜嚇得一抖,趕緊收起手機,把腫得老高的右手戳到老俞面前。
「我長凍瘡了,不能碰冷水。」
老俞氣血翻湧,顧不得碼頭上人來人往,從桶裡抓起大黑頭魚就朝俞靜臉上用力甩去。
黑頭魚掉地上劈里啪啦蹦得老高,俞靜卻倒在一窪髒水裡不動了。
老俞這下也傻了。他以前也不是沒打過俞靜,但一下子抽昏的情況還是第一次。他趕緊去探了探鼻息,還有氣,但兩隻手臂就像兩條軟塌塌的海帶。
老俞駕著運貨的小三輪貨車一路風馳電掣把俞靜送去市立醫院,吊了點滴驗了血,一路查下來,除了臉上擦傷,還有點低血糖之外,也沒發現什麼大毛病,但俞靜就是醒不了,一直低燒。醫生建議再住院觀察兩天,老俞一問,算上藥費一天得花三四百,住幾天的話這一船的魚就白搭了。年前就這幾天能賣出貨,不能總這麼耗著。見老俞和房玲的臉愁成疙瘩,同病房一個老人提醒說這種情況海邊常有,可能碰了不乾淨的東西,不如去找二姑奶想想辦法。
二姑奶就是隔壁村「會看事的」,老家在四川,年輕時嫁到俞家臺,可惜命帶喪門,剋死了老公孩子,六十多歲的時候眼睛還瞎了,靠撿礦泉水瓶活到八十多,有一天突然能看見「東西」了。一開始就是幫人尋貓找狗,後來漸漸有了名氣,現在逢年過節門口能排起長隊來。平日裡都是取名、合八字、算風水的,一到開海的時候,大小船隊都會排隊請她來做法事。海邊的人多少都有點迷信,畢竟靠海吃飯,命都拴在桅杆上,就算不信也能圖個心安。但二姑奶有個規矩,要是碰上極難處理的情況,會先要請她的人找個偏門的「引子」。之前老俞村裡有人難產,二姑奶用菜頭蛇身上七寸的鱗當「引子」,作完法孩子就生出來了;還有七村村長找走丟的媽媽,二姑奶要了生過小孩的狸花貓後掌,沒過幾天,派出所就把他媽媽送回來了。
老俞裝了一箱二姑奶最愛吃的冷凍鮁魚和一袋散菸絲就去了。
院裡果然站了不少人,但二姑奶一天只看九個。老俞想辦法插了個隊,到他剛好第九個。
二姑奶聽他說完,深深抽了口長桿菸斗,軟綿綿的腮幫子縮成一團棉絮,菸頭裡灰黑的菸絲皺成暗紅色。二姑奶噴了一口白煙,往地上彈了彈灰。
「魂掉了。你去找隻烏鴉,剪三個指甲尖。今天晚上十二點,把院子騰出來。要快,過了這個時間,找誰都白搭。」
最後這句話把老俞嚇得不輕。可是這大冬天的海邊上哪裡找烏鴉呢?
老俞蹲在碼頭抽了三根菸,終於想到一個人。
鹽洋市唯一的一座公墓「千秋苑」建在西郊的後山上,墓地管理員叫宋大嘴。宋大嘴愛吃海產,嘴很刁,眼也利,聽說坐過牢,會看面相。他第一眼看到老俞的時候覺得煞氣太重,不實在。但觀察了幾次,發現老俞既不用假秤,也不往螃蟹裡灌水,從此他只認老俞攤子上的貨,一來二去就熟了。
宋大嘴聽老俞說完,拍胸脯說:「等著。」
鹽洋人極其重視死後的體面,再窮的人家上墳也會備上進口的蘋果、香蕉,油滋滋的肥肉、燒雞、蒸魚,一到冬天,烏鴉鳥獸都躲到後山上,靠這些供品過活。
天黑前,宋大嘴就網住了一隻烏鴉。
他把剪下來的烏鴉指甲包嚴實,裝進一個空菸盒,騎著電動車去碼頭給了老俞。
夜幕降臨,老俞家的大門敞著,外頭圍了些看熱鬧的村民。
俞家臺大多都是平房,中間有個院子,院牆之間拉起一張「網布」防蠅蚊,平時就可以在院子裡晒鮁魚乾、墨魚乾。老俞家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晾杆上還掛著好幾串貝殼風鈴。房玲懷孕的時候手閒不住,就開始學做這個,把貝殼海螺洗淨晒乾、鑽孔、染色,用棉線穿成一串一串的,就可以賣到海邊的紀念品店。
門口的人堆裡探出一根黑亮的導盲杖,二姑奶跟著導盲杖鑽出來。她佝僂著腰走進院子,問老俞:「準備好了?」
老俞點點頭,把包在黃紙裡的烏鴉指甲遞給她。
二姑奶讓老俞把俞靜平放在地上。俞靜還是沒有要醒的跡象,臉色蒼白,手指冰涼。老俞眉頭緊鎖。
不知道是誰「噓」了一聲,門口嗡嗡的閒聊聲瞬間沒了。院子裡能聽到的除了呼呼的海風,就是遠處幾聲零星的狗叫,橫杆上的貝殼輕輕碰出脆響。
「滅燈。」
老俞趕緊把院子裡的照明燈關上,院子瞬間一片漆黑。
「哧――」二姑奶劃亮火柴,引燃事先準備好的一遝黃紙放進鐵盆,火光瞬間沖亮十幾平方公尺的院子。
二姑奶蹲下身子,把第一枚指甲尖放在俞靜的眉心,另外兩枚分別放在了她左右手心。
可能是火光的緣故,老俞發現俞靜的眼皮動了一下。
二姑奶用導盲杖頭在水泥地面上畫了兩個「十」字,一腳踏一個。然後開始用導盲杖使勁敲擊著地面,配合著節奏嘴裡念念有詞。
海風呼呼吹著,被網布篩進院子,貝殼風鈴開始嘩啦作響。
二姑奶的導盲杖越敲越快,念詞越來越急,風鈴聲也越來越大。老俞忍不住朝牆角看去,掛著海螺貝殼的風鈴垂線在急促地攪動,碰撞出亂糟糟的聲響。
「起來了起來了!」門口有人沒忍住叫起來。
老俞回頭,發現俞靜的上半身慢慢挺了起來,但眼睛還緊緊閉著。
她伸出手,用沙啞的聲音說:「我要喝水。」
二姑奶的導盲杖停下來,問她:「俞靜回來了?」
俞靜緩緩垂下雙手,沒說話。
二姑奶皺眉,又問了一遍:「俞靜回來了?」
俞靜喉嚨突然卡住,大聲咳嗽起來,震得五臟六腑發出悶響,然後急促地呼吸著,像快要窒息一樣。
二姑奶大喝一聲:「開燈!」
老俞趕忙打開高瓦數的照明燈,院子瞬間亮如白晝。
俞靜的動作停止了。過了一會,她緩緩睜開眼睛,慢慢掃了眼周圍,最後在二姑奶的臉上定了神。
二姑奶湊近,輕輕問:「俞靜回來了?」
俞靜搖搖頭,一字一頓地說:「我不叫俞靜,我叫何器。」
俞靜坐在沙發上捧著茶杯,一小口一小口抿著熱水,然後抬眼打量著客廳。
俞家的客廳本來不小,但是老俞和房玲節儉,捨不得扔東西,所以房間牆角都堆滿了生鏽的漁具家什,能坐的只有這張磨破洞的紅皮沙發和兩個馬扎 。
老俞和房玲坐在馬扎上,老俞死死盯著俞靜,妄圖從她臉上找出一絲絲撒謊的痕跡。
「妳什麼時候生的?」
「二○○三年三月十五號。」
不對,俞靜是三月二十二號生的,比他第一個孩子晚三天。
「住哪裡?」
「我家在海韻花園第六大樓第三區一○○二號房。」
海韻花園,那是鹽洋市數一數二的高級社區,住的人大都非富即貴。
「妳父母呢?」
「我爸叫何世濤,是個廚師,我媽叫朱麗萍,早就跟我爸離婚了,後來去了日本……」不知為何,她的臉上閃過一絲悲傷。老俞沒注意,他在仔細回憶何世濤這個人,耳熟,之前總來碼頭買魚,非常挑剔,所以很多商販都不愛搭理他。
「俞叔叔,你不記得我了嗎?」
老俞被菸頭燙到了手,趕緊甩開,踩滅,才繼續抬頭看女兒。
不,不是女兒了。
雖然還是俞靜的臉――細長的眉毛像房玲,黑嘛嘛的皮膚和高額頭像自己,眼皮內雙,鼻尖一顆小痣,手上的凍瘡還很腫,但她看自己的表情完全變了。說話也是,文謅謅的,而且有一點口齒不清。俞靜從來不會這樣講話,也不會叫自己「俞叔叔」。
二○○三年,中國癸未(羊)年。
街道上摻雜著紅色鞭炮屑的髒雪還未化完,SARS爆發了。
平時十塊錢 一包的板藍根 漲到了四十,五塊錢一瓶的白醋幾乎一天翻一倍。
白醋漲到八十塊錢一瓶的時候,與鹽洋市相隔不遠的兩座漁村出生了兩個女孩。
大泉港的名叫何器,俞家臺的名叫俞靜,兩人前後相差一週。
羊年出生的女孩命苦。
這個說法最早好像是從清朝開始的。儘管沒有什麼依據,但信者眾多,尤其是在鹽洋這種比較封閉的北方小城。
村裡的老人出於好心,說三月出生的孩子反而有福氣,因為驚蟄過後,萬物復生,所以一輩子總能逢凶化吉,平安順遂。
可惜的是,老人說錯了。
二○二○年七月,何器參加完高中畢業聚會後失蹤。三天後,沿岸橫七豎八的消波塊隨著退潮裸露出來,去岩石上耙海蠣子 肉的漁民在那裡發現了她。
何器靜靜地趴在一塊岩石上,尖銳粗礪的貝殼把她的四肢剮出一道道蒼白的口子,拇指大的螃蟹在她的髮絲中鑽來鑽去。那條昂貴的墨綠色長裙沾滿泥沙,纏繞在一堆亂蓬蓬的海藻裡。
她垂在沙灘上的右手隨著海浪輕輕擺動,遠遠看起來,像是在玩水。
第一章
1. 黑魚
冬天的海邊很少見到烏鴉了。
老俞盯著灰藻色的海面發愁。潮水還在漲,海浪每吞吐一次白沫,沙岸上就多一些保麗龍垃圾,見不到一星點死貝爛蝦。而且臨近年關,碼頭上的人空前地多,鳥就更不敢來了。
要是再找不到烏鴉,俞靜就真醒不過來了。
老俞臉上的褶子被海風吹成一張粗糙的漁網。他把尖頭的捲菸一口吸到底,彈進海裡,起身打了通電話。
一天前老俞獨自出海,想多打點海產賣了過年。這幾年休漁期越來越長,很多漁民養不起大船,都被馳航水產低價買走,等休漁期一過,開了海,又轉頭高價租給漁民。像自家這種幾十馬力的老破漁船沒有水產公司願意收,老俞也捨不得賣。他想,多出幾趟海,養活一家子也沒問題。
往回退二十年,那是大海和老俞的鼎盛期,俞家臺大小漁船加起來有上百條,老俞一百九的個子,身強力壯,熬幾個大夜都沒問題。跟村裡的老少爺們出趟海,每回都是滿艙而歸,隔三差五就能打上一條幾十公斤重的大魚。哪像現在,出一次海,拉回來的全是一些小魚小蝦,堆地上都沒人踩。
這次也一樣。老俞一天一夜沒闔眼,臉上沾滿了細小的魚鱗,渾身腥臭,手指頭凍 得伸不直,就撈了幾十斤的東西,空碎貝殼占了一半,漁網也在打盹的時候被暗礁拉破了。
前兩天,幫工的大飛辭了職,去馳航水產當撿魚工,說那裡提供五險一金 。現在願意出海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賺不到錢是一個原因,還有就是風吹日晒,一年到頭在海上漂著見不到人,一不小心就會打一輩子光棍。大飛一走,老俞一時半刻找不著人頂替,網破了也只能自己補。潮要落了,他心煩意亂,只想趕緊回家蒙頭睡一覺。
老俞開動了馬達,震得海面嘩啦作響。突然,一條大黑頭魚蹦上了他的船,把船艙砸得劈里啪啦響,消停了就鼓著兩扇寬鰓呼蚩猛喘。
老俞在海上漂了半輩子,魚蹦上船的事不是頭一回見。但老話說「開船不吃自來魚」,說這種魚是龍王預付的買命錢,所以漁民見了基本上都是扔回海裡。
老俞掐起黑頭魚的鰓,掂了掂,有八九斤重。
他很久沒見過這麼肥的魚了。
臨近中午,細長的碼頭上早就撐起一排彩色的遮雨棚,擠得密不透風。畢竟到了年關,一年就這麼一回,各家都卯足了勁吆喝賣貨。
每頂遮雨棚下面都擠擠挨挨擺著幾隻大紅盆、幾個塑膠魚箱、沾滿魚鱗的電子秤,還有裹得鼓鼓囊囊、圍著彩色頭巾、臉皮皴紅的漁家婦女。等丈夫們把海產拉上岸,就一邊賣貨,一邊在冰水裡熟練挑揀,最大的梭子蟹扔到「九○」的盆裡,小的就扔到「三○」的盆裡,小黃魚在地上堆成小山。
日頭升起來,買年貨的人踩著髒水在雨棚下面鑽來鑽去。有人專門開車來俞家碼頭買海產,一是圖剛打上來新鮮,二是比海鮮市場便宜,買多了還能再搭一隻肥蟹。
老俞泊了船,拴好,把海產倒進鏤空的魚箱,再拎起一個小紅桶,大黑頭魚蜷在裡面艱難地喘著。他朝自家印著「娃哈哈」的綠色遮雨棚走去。
老俞遠遠看見只有幾個盆在那兒,沒瞧見人。他趕緊跑了幾步,才發現女兒俞靜又躲在貨箱後面,學著抖音上的尖臉小姑娘編辮子。她把又厚又長的頭髮分成十八綹,纏上小彩繩,一下一下扭成麻花,那認真勁像修文物似的,好幾個客人來問價也不搭理,讓人家挑完自己過秤。
老俞再一看,注活水的塑膠管翹得老高,水都噴到外面去了,紅盆裡的梭子蟹沉了底,全都一動不動。
他的火轟一下子就上來了。
俞靜是他的大女兒,也可以說是老二。老婆房玲第一胎是個兒子,出生三個月就染病死了。農村有規矩,小孩不能立墳頭,得去荒山扔掉,說是對下一胎好。老俞不忍心,還是幫他買了幾身小衣服,偷偷託人埋在後山上,每年清明都和房玲去燒點金紙。
一年之後就生了俞靜。
足月,順產,剛生出來就活蹦亂跳得像條泥鰍,哭聲特別大,不到一歲就學會走路了,像隻小狗似的天天跟在老俞後頭。而且學東西很快,動手能力極強,老俞和房玲在碼頭賣貨的時候,小俞靜就在旁邊的沙灘上玩,別的小孩堆沙堡,她拿著小耙子挖蛤蜊,一個下午就能挖一小桶。
房玲是個樸實的海邊婦女,兩隻腳從沒邁出鹽洋的地界,兩隻手除了扒拉海產不會幹別的,更別說編辮子這種精細活了。所以俞靜從小就是短髮,再加上天天吃海鮮,蛋白質充足,到了青春期,個子躥得很快,手長腿長,小學時就是女生堆裡最高的。碼頭上的人都說俞靜遠看像個假小子似的,要是再來一胎肯定是個男孩。
雖然是開玩笑,但回回都戳得老俞心裡一緊。
有時候俞靜趴在飯桌上做作業,老俞就會偷偷打量她。不仔細看還真像個小子,性格也像,可惜就不是。
老俞想再生個兒子。
這個念頭在海上的時候尤其強烈。要是老大沒死,現在就有個大小夥子跟自己一起打魚了,可以傳授他這些年自己一船一船撈上來的經驗,教他怎麼利用潮水走向撒網,怎麼判斷哪裡有最肥的魚。房玲和俞靜什麼都不懂,在家吃完飯就一起看電視,很少聊天。老俞總覺得說不出來的「話」是有形狀的,悶在肚子裡的話越來越多,撐得自己的肚皮也越來越大。要是再有個兒子,這些話就能一點一點順出來,否則只能跟著他百年之後爛到地裡。
他把這個念頭跟房玲一說,房玲也同意了。她一輩子沒自己拿過主意,結婚之前聽父母的,結婚之後就聽老俞的。
於是俞靜考大學那年,房玲就懷孕了。沒跟俞靜打過招呼,俞靜知道後也沒問什麼。老俞心想,這一點倒是像自己,不愛問話,遇到不懂的事就先裝到肚子裡自己琢磨,琢磨過來就琢磨過來,沒琢磨過來就算了。這樣挺好的,人一輩子不能每件事都想得明白。
房玲現在懷孕八個多月,肚子鼓得老大,有經驗的產婆看了都說是小子。老俞生怕有什麼閃失,不讓房玲碰冰水。剛好俞靜放寒假,就想讓她幫忙分擔一下家裡的活。
俞靜升學考成績不好,沒考上大學,去了市裡的職業學校學飯店管理。老俞記得她小時候明明成績不錯,還拿過幾張獎狀,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讀書的。可能是高中,當時實驗高中為了方便管理,強制學生寄宿,兩週放一次假。從那時候起,俞靜的性格就變了,不再瘋瘋癲癲地到處亂跑,頭髮也越來越長,開始學別人穿裙子,畫眉毛,看起來確實有了女孩的樣子,但考試名次就像扔鐵錨似的,一溜煙就沉到海底。
考上職業學校之後就更放飛了。雖然學校離家不遠,坐一八路公車一個小時就能到,但俞靜只願意在寒暑假回來。每次回來頭髮都換個顏色,有一回整整數出四個顏色。房玲特別看不慣染髮,一開始還數落兩句,後來就不管了。俞靜在家裡也不願意和他們多說話,醒了就躺床上滑手機,餓了就下床找吃的,別說幫忙揀魚看攤了,吃完飯的碗都不願意洗。
眼見房玲肚子越來越大,坐著都費勁,老俞沒轍了,說可以發薪水給俞靜,賣一天貨給五十塊錢,她才不情不願地答應。
之前老俞老聽人說,兒女是父母前世的債主。他一點都不信,後來每回被俞靜氣到不行的時候他就在心裡默念這句話:「我上輩子欠她的,這輩子還清,下輩子就不用見了。」還真的滿管用,每次一想完,氣就消一半了。
但今天不行,默念一百遍也不行。
他把魚箱啪一聲扔到地上,俞靜嚇得一抖,趕緊收起手機,把腫得老高的右手戳到老俞面前。
「我長凍瘡了,不能碰冷水。」
老俞氣血翻湧,顧不得碼頭上人來人往,從桶裡抓起大黑頭魚就朝俞靜臉上用力甩去。
黑頭魚掉地上劈里啪啦蹦得老高,俞靜卻倒在一窪髒水裡不動了。
老俞這下也傻了。他以前也不是沒打過俞靜,但一下子抽昏的情況還是第一次。他趕緊去探了探鼻息,還有氣,但兩隻手臂就像兩條軟塌塌的海帶。
老俞駕著運貨的小三輪貨車一路風馳電掣把俞靜送去市立醫院,吊了點滴驗了血,一路查下來,除了臉上擦傷,還有點低血糖之外,也沒發現什麼大毛病,但俞靜就是醒不了,一直低燒。醫生建議再住院觀察兩天,老俞一問,算上藥費一天得花三四百,住幾天的話這一船的魚就白搭了。年前就這幾天能賣出貨,不能總這麼耗著。見老俞和房玲的臉愁成疙瘩,同病房一個老人提醒說這種情況海邊常有,可能碰了不乾淨的東西,不如去找二姑奶想想辦法。
二姑奶就是隔壁村「會看事的」,老家在四川,年輕時嫁到俞家臺,可惜命帶喪門,剋死了老公孩子,六十多歲的時候眼睛還瞎了,靠撿礦泉水瓶活到八十多,有一天突然能看見「東西」了。一開始就是幫人尋貓找狗,後來漸漸有了名氣,現在逢年過節門口能排起長隊來。平日裡都是取名、合八字、算風水的,一到開海的時候,大小船隊都會排隊請她來做法事。海邊的人多少都有點迷信,畢竟靠海吃飯,命都拴在桅杆上,就算不信也能圖個心安。但二姑奶有個規矩,要是碰上極難處理的情況,會先要請她的人找個偏門的「引子」。之前老俞村裡有人難產,二姑奶用菜頭蛇身上七寸的鱗當「引子」,作完法孩子就生出來了;還有七村村長找走丟的媽媽,二姑奶要了生過小孩的狸花貓後掌,沒過幾天,派出所就把他媽媽送回來了。
老俞裝了一箱二姑奶最愛吃的冷凍鮁魚和一袋散菸絲就去了。
院裡果然站了不少人,但二姑奶一天只看九個。老俞想辦法插了個隊,到他剛好第九個。
二姑奶聽他說完,深深抽了口長桿菸斗,軟綿綿的腮幫子縮成一團棉絮,菸頭裡灰黑的菸絲皺成暗紅色。二姑奶噴了一口白煙,往地上彈了彈灰。
「魂掉了。你去找隻烏鴉,剪三個指甲尖。今天晚上十二點,把院子騰出來。要快,過了這個時間,找誰都白搭。」
最後這句話把老俞嚇得不輕。可是這大冬天的海邊上哪裡找烏鴉呢?
老俞蹲在碼頭抽了三根菸,終於想到一個人。
鹽洋市唯一的一座公墓「千秋苑」建在西郊的後山上,墓地管理員叫宋大嘴。宋大嘴愛吃海產,嘴很刁,眼也利,聽說坐過牢,會看面相。他第一眼看到老俞的時候覺得煞氣太重,不實在。但觀察了幾次,發現老俞既不用假秤,也不往螃蟹裡灌水,從此他只認老俞攤子上的貨,一來二去就熟了。
宋大嘴聽老俞說完,拍胸脯說:「等著。」
鹽洋人極其重視死後的體面,再窮的人家上墳也會備上進口的蘋果、香蕉,油滋滋的肥肉、燒雞、蒸魚,一到冬天,烏鴉鳥獸都躲到後山上,靠這些供品過活。
天黑前,宋大嘴就網住了一隻烏鴉。
他把剪下來的烏鴉指甲包嚴實,裝進一個空菸盒,騎著電動車去碼頭給了老俞。
夜幕降臨,老俞家的大門敞著,外頭圍了些看熱鬧的村民。
俞家臺大多都是平房,中間有個院子,院牆之間拉起一張「網布」防蠅蚊,平時就可以在院子裡晒鮁魚乾、墨魚乾。老俞家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晾杆上還掛著好幾串貝殼風鈴。房玲懷孕的時候手閒不住,就開始學做這個,把貝殼海螺洗淨晒乾、鑽孔、染色,用棉線穿成一串一串的,就可以賣到海邊的紀念品店。
門口的人堆裡探出一根黑亮的導盲杖,二姑奶跟著導盲杖鑽出來。她佝僂著腰走進院子,問老俞:「準備好了?」
老俞點點頭,把包在黃紙裡的烏鴉指甲遞給她。
二姑奶讓老俞把俞靜平放在地上。俞靜還是沒有要醒的跡象,臉色蒼白,手指冰涼。老俞眉頭緊鎖。
不知道是誰「噓」了一聲,門口嗡嗡的閒聊聲瞬間沒了。院子裡能聽到的除了呼呼的海風,就是遠處幾聲零星的狗叫,橫杆上的貝殼輕輕碰出脆響。
「滅燈。」
老俞趕緊把院子裡的照明燈關上,院子瞬間一片漆黑。
「哧――」二姑奶劃亮火柴,引燃事先準備好的一遝黃紙放進鐵盆,火光瞬間沖亮十幾平方公尺的院子。
二姑奶蹲下身子,把第一枚指甲尖放在俞靜的眉心,另外兩枚分別放在了她左右手心。
可能是火光的緣故,老俞發現俞靜的眼皮動了一下。
二姑奶用導盲杖頭在水泥地面上畫了兩個「十」字,一腳踏一個。然後開始用導盲杖使勁敲擊著地面,配合著節奏嘴裡念念有詞。
海風呼呼吹著,被網布篩進院子,貝殼風鈴開始嘩啦作響。
二姑奶的導盲杖越敲越快,念詞越來越急,風鈴聲也越來越大。老俞忍不住朝牆角看去,掛著海螺貝殼的風鈴垂線在急促地攪動,碰撞出亂糟糟的聲響。
「起來了起來了!」門口有人沒忍住叫起來。
老俞回頭,發現俞靜的上半身慢慢挺了起來,但眼睛還緊緊閉著。
她伸出手,用沙啞的聲音說:「我要喝水。」
二姑奶的導盲杖停下來,問她:「俞靜回來了?」
俞靜緩緩垂下雙手,沒說話。
二姑奶皺眉,又問了一遍:「俞靜回來了?」
俞靜喉嚨突然卡住,大聲咳嗽起來,震得五臟六腑發出悶響,然後急促地呼吸著,像快要窒息一樣。
二姑奶大喝一聲:「開燈!」
老俞趕忙打開高瓦數的照明燈,院子瞬間亮如白晝。
俞靜的動作停止了。過了一會,她緩緩睜開眼睛,慢慢掃了眼周圍,最後在二姑奶的臉上定了神。
二姑奶湊近,輕輕問:「俞靜回來了?」
俞靜搖搖頭,一字一頓地說:「我不叫俞靜,我叫何器。」
俞靜坐在沙發上捧著茶杯,一小口一小口抿著熱水,然後抬眼打量著客廳。
俞家的客廳本來不小,但是老俞和房玲節儉,捨不得扔東西,所以房間牆角都堆滿了生鏽的漁具家什,能坐的只有這張磨破洞的紅皮沙發和兩個馬扎 。
老俞和房玲坐在馬扎上,老俞死死盯著俞靜,妄圖從她臉上找出一絲絲撒謊的痕跡。
「妳什麼時候生的?」
「二○○三年三月十五號。」
不對,俞靜是三月二十二號生的,比他第一個孩子晚三天。
「住哪裡?」
「我家在海韻花園第六大樓第三區一○○二號房。」
海韻花園,那是鹽洋市數一數二的高級社區,住的人大都非富即貴。
「妳父母呢?」
「我爸叫何世濤,是個廚師,我媽叫朱麗萍,早就跟我爸離婚了,後來去了日本……」不知為何,她的臉上閃過一絲悲傷。老俞沒注意,他在仔細回憶何世濤這個人,耳熟,之前總來碼頭買魚,非常挑剔,所以很多商販都不愛搭理他。
「俞叔叔,你不記得我了嗎?」
老俞被菸頭燙到了手,趕緊甩開,踩滅,才繼續抬頭看女兒。
不,不是女兒了。
雖然還是俞靜的臉――細長的眉毛像房玲,黑嘛嘛的皮膚和高額頭像自己,眼皮內雙,鼻尖一顆小痣,手上的凍瘡還很腫,但她看自己的表情完全變了。說話也是,文謅謅的,而且有一點口齒不清。俞靜從來不會這樣講話,也不會叫自己「俞叔叔」。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