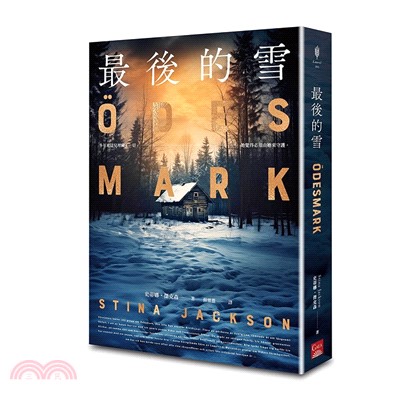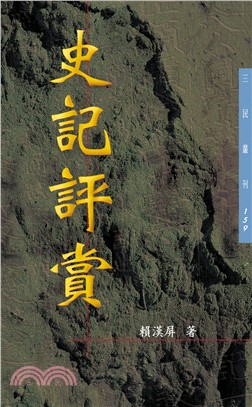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讓光明變得更加明亮的黑暗。
暢銷作家史蒂娜・傑克森最新力作!
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超過一百萬冊!
在這極北之地,每個人都互相認識,所有往事都被記得⋯⋯
在幾乎被遺忘的荒涼農舍牆內,隱藏著什麼秘密?
早春的寒冷籠罩著歐德斯馬克,這是瑞典北方的小村子,許多居民都搬離這片荒地、任憑家屋腐朽,但麗芙·畢爾盧從未離開。她與兒子賽門,以及年邁的父親威達住在破舊的房子裡,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家庭。
麗芙知道為數不多鄰居對自己議論紛紛。為什麼她這些年一直守在霸道的父親身邊?威達真如傳言般坐擁一筆不小的財富嗎?多年來,他的生意為他樹立了許多敵人,在歐德斯馬克,每個人都互相認識,所有的往事都被放在心裡記著。
而現在有人想要拿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誰阻擋在前,他們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得到⋯⋯
史蒂娜・傑克森是眾所矚目的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已累積超過一百萬冊,並獲得許多獎項肯定。本書以人口所剩無幾的瑞典北部村落為背景,描述在這荒涼聚落裡的人際關係,以及存在其中的祕密與猜疑。凶案之後,村裡每個人對受害者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否能導出真正的真相,並修復破裂的人與
心?
暢銷作家史蒂娜・傑克森最新力作!
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超過一百萬冊!
在這極北之地,每個人都互相認識,所有往事都被記得⋯⋯
在幾乎被遺忘的荒涼農舍牆內,隱藏著什麼秘密?
早春的寒冷籠罩著歐德斯馬克,這是瑞典北方的小村子,許多居民都搬離這片荒地、任憑家屋腐朽,但麗芙·畢爾盧從未離開。她與兒子賽門,以及年邁的父親威達住在破舊的房子裡,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家庭。
麗芙知道為數不多鄰居對自己議論紛紛。為什麼她這些年一直守在霸道的父親身邊?威達真如傳言般坐擁一筆不小的財富嗎?多年來,他的生意為他樹立了許多敵人,在歐德斯馬克,每個人都互相認識,所有的往事都被放在心裡記著。
而現在有人想要拿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誰阻擋在前,他們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得到⋯⋯
史蒂娜・傑克森是眾所矚目的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已累積超過一百萬冊,並獲得許多獎項肯定。本書以人口所剩無幾的瑞典北部村落為背景,描述在這荒涼聚落裡的人際關係,以及存在其中的祕密與猜疑。凶案之後,村裡每個人對受害者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否能導出真正的真相,並修復破裂的人與
心?
作者簡介
作者|史蒂娜・傑克森(Stina Jackson)
生於1983年,生長於瑞典北部小鎮。後來她搬到了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創作出第一本長篇小說《銀色公路》。
《銀色公路》被瑞典 Bonnier 出版集團簽下,當作強打的新人小說,出版後迅速登上瑞典的暢銷榜,引起各國出版社的注意,強力爭取本書版權。目前本書已賣出英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波蘭、芬蘭、丹麥等各地語言版權。
《銀色公路》出版後入圍諸多推理犯罪小說或大眾文學獎項,並獲得北歐犯罪文學大獎玻璃鑰匙獎、瑞典犯罪作家學院年度最佳小說大獎與瑞典年度最佳好書獎的肯定。傑克森的第二本小說《最後的雪》,也在瑞典創下銷售佳績、入圍諸多獎項,是眾所矚目的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已累積超過一百萬本
。
傑克森作品
銀色公路
最後的雪
譯者簡介|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柏青哥》、《失落手稿》、《搶救野鳥的夏天》等書。
生於1983年,生長於瑞典北部小鎮。後來她搬到了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創作出第一本長篇小說《銀色公路》。
《銀色公路》被瑞典 Bonnier 出版集團簽下,當作強打的新人小說,出版後迅速登上瑞典的暢銷榜,引起各國出版社的注意,強力爭取本書版權。目前本書已賣出英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波蘭、芬蘭、丹麥等各地語言版權。
《銀色公路》出版後入圍諸多推理犯罪小說或大眾文學獎項,並獲得北歐犯罪文學大獎玻璃鑰匙獎、瑞典犯罪作家學院年度最佳小說大獎與瑞典年度最佳好書獎的肯定。傑克森的第二本小說《最後的雪》,也在瑞典創下銷售佳績、入圍諸多獎項,是眾所矚目的北歐犯罪文學新星,作品全球銷量已累積超過一百萬本
。
傑克森作品
銀色公路
最後的雪
譯者簡介|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柏青哥》、《失落手稿》、《搶救野鳥的夏天》等書。
序
Amazon書店讀者四星推薦|瑞典暢銷榜No.1|《泰晤士報》最佳犯罪小說書單|瑞典《每日新聞報》年度最佳犯罪小說書單|瑞典Storytel Awards決選|瑞典年度最佳好書獎決選|瑞典犯罪作家學院年度最佳犯罪小說決選|
推理評論人 冬陽
文字工作者 臥斧
文字工作者 栞
香港推理小說作家 譚劍
暢銷作家 護玄
好評推薦(依筆畫排序)
犯罪作家盛讚
「我是史蒂娜・傑克森的超級粉絲,所以對《最後的雪》寄以厚望,而它並沒有讓人失望。令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文筆優美,她擁有罕見的能力,能夠創作出精彩、引人入勝的小說,讓你脈搏加速、心痛不已。」
――金匕首獎得主《黑暗中凝視天光》作者 克里斯.惠戴克(Chris Whitaker)
「史蒂娜・傑克森用無與倫比的技巧,帶領我們穿行於一處暗潮洶湧、瀕臨糟糕記憶深淵的社區。《最後的雪》是部傑作,充滿淚水和鮮血、愛與絕望、安慰與憤怒,以及令光明變得更加明亮的黑暗。」
――《狼與守夜人》作者 尼可拉斯.納歐達(Niklas Natt och Dag)
各界好評如潮
「史蒂娜·傑克森精彩的第二本小說有著童話的特質⋯⋯⋯⋯它以如此完美的散文風格、如此平實的方式描述了可怕的事情――成癮、暴力、身心虐待――讓那些本應難以忍受的事情變得令人目不轉睛。無論好人壞人,以充滿洞察力的同理心處理每個角色,這意味著:『沒有任何怪物。只有人。』效果就像看柏格
曼導演的希臘悲劇。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說,充滿了愛與恐懼,當罪魁禍首的身分被揭露時,會讓你震驚不已。」
――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故事在人物與場景間巧妙切換,從一開始就給人電影般的感覺⋯⋯《最後的雪》讓人想起史蒂芬・金,重現了一個小社區的生活,裡面充滿受了傷但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且像金的大多數作品一樣,是令人生出幽閉恐怖的家庭劇或恐怖故事,也是驚悚故事。」
――愛爾蘭《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緊湊且扎實,她以畫家之眼再現森林邊緣的村莊,充滿黑暗、童話般的單純和威脅⋯⋯每一個句子都伴隨著輕柔、迷人的音樂;累積出令人難以忘懷且無法抗拒的效果。」
――愛爾蘭《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可以嚐到、聞到、感覺到的懸疑感⋯⋯在《最後的雪》中,瑞典的新犯罪女王深掘出關於親職和傳承那些痛苦而複雜的課題。」
――芬蘭《首都日報》(Hufvudstadsbladet)
「她的小說比其他懸疑類作品更有分量與層次。傑克森是個能善用驚悚類型優勢的出色文學作家。」
――丹麥《貝林時報》(Berlingske)五星好評
「一部精彩的犯罪小說――而且不只如此⋯⋯感覺真實又悲傷,同時充滿了我們在北歐犯罪中很少看到的東西:一種相信前方會有更光明事物的頑強信念。」
――挪威《斯塔萬格晚報》(Stavanger Aftenblad)五星好評
「《最後的雪》是一部扣人心弦、悲傷、有趣且富有詩意的小說。」
――挪威《Adresseavisen報》五星好評
推理評論人 冬陽
文字工作者 臥斧
文字工作者 栞
香港推理小說作家 譚劍
暢銷作家 護玄
好評推薦(依筆畫排序)
犯罪作家盛讚
「我是史蒂娜・傑克森的超級粉絲,所以對《最後的雪》寄以厚望,而它並沒有讓人失望。令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文筆優美,她擁有罕見的能力,能夠創作出精彩、引人入勝的小說,讓你脈搏加速、心痛不已。」
――金匕首獎得主《黑暗中凝視天光》作者 克里斯.惠戴克(Chris Whitaker)
「史蒂娜・傑克森用無與倫比的技巧,帶領我們穿行於一處暗潮洶湧、瀕臨糟糕記憶深淵的社區。《最後的雪》是部傑作,充滿淚水和鮮血、愛與絕望、安慰與憤怒,以及令光明變得更加明亮的黑暗。」
――《狼與守夜人》作者 尼可拉斯.納歐達(Niklas Natt och Dag)
各界好評如潮
「史蒂娜·傑克森精彩的第二本小說有著童話的特質⋯⋯⋯⋯它以如此完美的散文風格、如此平實的方式描述了可怕的事情――成癮、暴力、身心虐待――讓那些本應難以忍受的事情變得令人目不轉睛。無論好人壞人,以充滿洞察力的同理心處理每個角色,這意味著:『沒有任何怪物。只有人。』效果就像看柏格
曼導演的希臘悲劇。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說,充滿了愛與恐懼,當罪魁禍首的身分被揭露時,會讓你震驚不已。」
――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故事在人物與場景間巧妙切換,從一開始就給人電影般的感覺⋯⋯《最後的雪》讓人想起史蒂芬・金,重現了一個小社區的生活,裡面充滿受了傷但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且像金的大多數作品一樣,是令人生出幽閉恐怖的家庭劇或恐怖故事,也是驚悚故事。」
――愛爾蘭《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緊湊且扎實,她以畫家之眼再現森林邊緣的村莊,充滿黑暗、童話般的單純和威脅⋯⋯每一個句子都伴隨著輕柔、迷人的音樂;累積出令人難以忘懷且無法抗拒的效果。」
――愛爾蘭《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可以嚐到、聞到、感覺到的懸疑感⋯⋯在《最後的雪》中,瑞典的新犯罪女王深掘出關於親職和傳承那些痛苦而複雜的課題。」
――芬蘭《首都日報》(Hufvudstadsbladet)
「她的小說比其他懸疑類作品更有分量與層次。傑克森是個能善用驚悚類型優勢的出色文學作家。」
――丹麥《貝林時報》(Berlingske)五星好評
「一部精彩的犯罪小說――而且不只如此⋯⋯感覺真實又悲傷,同時充滿了我們在北歐犯罪中很少看到的東西:一種相信前方會有更光明事物的頑強信念。」
――挪威《斯塔萬格晚報》(Stavanger Aftenblad)五星好評
「《最後的雪》是一部扣人心弦、悲傷、有趣且富有詩意的小說。」
――挪威《Adresseavisen報》五星好評
書摘/試閱
麗芙與黎明獨處。陽光穿透光禿的樺木,像發光的斑點落在陰暗的樹林上。農舍在她身後,她避著不回頭看。她結凍的吐息是隔離世界的盾牌。她沒看到燈亮起,沒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直到瘦骨如柴的拉普蘭獵犬從灌木叢飛奔過來,繞著她轉圈圈,她才停下斧頭轉過身。
威達站在門廊上,雙眼像黑色細縫。
他用沙啞的聲音叫道,「進來吃飯。」
然後他便消失了。麗芙拍乾淨外套,不情願地走向屋子,腳步在寂靜中宛如鼓聲。
老人和孩子坐在廚房,沉浸在咖啡香之中。威達的雙手在夜間僵住,早上手指就像僵硬的爪子,幾乎無法舉杯就口。賽門極為專注地替他把吐司切片,抹上奶油。
「阿公,你吃藥了沒?」
威達繼續嚼麵包。他根本不想吃藥,要不是賽門每天早上在他面前把藥丸排成整齊的彩虹,他絕不會吃。
「你嘮叨的樣子比老太婆還糟。」
不過威達仍一一吞下藥丸,吃完後輕拍賽門的手,男孩的手比他大了一號。賽門低頭朝桌面笑了。麗芙撇開眼,心想這孩子的美德、內心的光輝從哪兒來的。肯定不是遺傳到她。
她上樓到房間更衣。賽門的房門開著,幽暗房內吸引她的視線。被子從床上滑下來,捲成一團落在地上,旁邊是一堆髒衣服,還有書架塞不下的書。遮光簾拉下來,房內唯一的光源是桌上嗡嗡叫的老電腦。當年雖然威達反對,她仍替他買了,電腦也成為孤單男孩的朋友。他在電腦上有她完全不了解的完整生活。
她把臉湊到門縫,吸進青春期、汗濕襪子和焦慮的氣味。她先確認他們在樓下廚房的聲音,才推門進去。她撿起棉被,膝蓋嘎吱作響,灰塵在房內翻騰。床下有什麼一閃,她彎下腰,看到是沒有標籤的玻璃瓶,酒味重到不用轉開瓶蓋都知道裡頭裝什麼。某種私釀酒,烈到她都流淚了。可能是威達釀的。
「欸,媽,妳在做什麼?妳不能亂翻我的東西。」
賽門站在門口,臉氣得發黑。麗芙站起身,手裡拿著酒瓶,清涼的玻璃緊貼肌膚。
「我本來要替你鋪床,」她說,「結果找到這個。」
「不是我的,我替朋友保管。」
他們都知道他在撒謊,根本沒什麼朋友,但她不能說。麗芙拍乾淨酒瓶,輕放在電腦旁的桌上。思緒隨著她的脈搏流動。他十七歲了,沒必要和他爭執。他做一般少年會做的事,或許還是好事。
她問道,「哪個朋友?」
「不干妳的事。」
他們盯著彼此好一會兒。他皺起眉心,看起來像威達。即便如此,她仍在男孩臉上看到自己。倔強,渴求更多,渴求自由。要不是為了他,她不會站在這兒,留在她出生的家。她會在別處,跑得遠遠的。或許他知道原因是他,或許他們之間的距離因此越來越遠。她猜想他是否真的交到了朋友,搞不好是最惡劣的那群,會喝酒打架的孩子。或者他是否獨自坐在電腦的藍光中,整晚喝酒。兩者都令她心感沉重。
賽門伸手去拿背包,臉頰上憤怒的紅潮已退去。
「我上學要遲到了。」
她點點頭。
「我們晚上再談。」
「我不在的時候,妳別進我房間。」
「我現在就出去。」
他等她離開房間,裝模作樣關門鎖上,才走下樓。麗芙跟著他;她看他長毛的孩子氣後頸,想起她曾多次把臉埋在那兒,吸滿他的氣味。無數的夜晚,她用身子裹著保護他,一手放在他脆弱的肩胛骨之間,只為了確保他有呼吸,不會死去拋下她。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另一個時代了。
麗芙和老人站在廚房窗口,看他走向校車。他們的視線一直追著男孩高瘦的身影,直到森林吞噬他。
威達說,「我覺得他有女人了。」
「當真?」
「是啊,我聞得出來,他聞起來不一樣。」
「我沒注意到。」
威達咬住方糖,用茶碟端起杯子,透過糖塊啜飲咖啡,意味深長看了她一眼。
「妳聽清楚,他就像他媽媽。不用多久,他晚上就不回家了。」
□
在尤哈‧別克的小屋很難呼吸。連恩和加百列坐在不穩的桌旁,細瘦男子在他們前方來回踱步。灰塵和松針繞著他的靴子打轉,煙霧繚繞的空氣刺痛他們的眼睛。他的視線在兩人間擺盪,但他們無法和他對上眼。
「你們得原諒我,」他說,「我不習慣人。」
連恩試圖隱藏竄過全身的不安。他瞥向加百列,哥哥表情饒富興味,唇邊掛著一絲笑意,雙眼掃視小屋,看進奇怪的物品和打獵的紀念品。桌上插著一把刀,乾掉的血在刮傷的桌面留下深色陰影。動物的頭像窗簾掛在唯一的窗口,擁擠的室內又熱又悶。尤哈站在爐火一側,看著他們,雙眼似乎在燃燒。他的聲音沙啞,彷彿聲帶開始在喉嚨裡生鏽。沒有人和他說話就會這樣吧。
「你們這種瘋子會騎雪上摩托車獵狐狸,」他說,「我光看就知道了。」
「聽你在亂說,」連恩說,「我們看起來像該死的獵人嗎?」
「可是你們追著錢跑吧?你們的人生不過如此,只有毒品和好賺的錢。」
加百列雙腳拍打地面,連恩感到他的雙腿震動。兩人都沒說話。
「你們不會出於好心,帶咖啡和菸給老人家吧?你們這麼辛苦,就是想拿錢。」
「照你的說法,對,我們不做公益。」加百列說,「還是要講公平。」
尤哈嘎嘎大笑。連恩用眼角瞄那把刀,只要伸出手,刀就是他的了。他感到冷靜一些。
尤哈把咖啡壺掛在爐火上。
「你們很飢渴。」他說,「我很欣賞,我也飢渴過。但餓了夠久,你就不會再聽到肚子抱怨,會變得靜得要命。」
他的聲道雖然生鏽,聲音卻有種旋律,彷彿他寧可用唱的。
「我年輕的時候認識你們爸爸。」他繼續說,「我們是同學。他真是了不得,脾氣和獾一樣差,也很狡猾。但如果你有麻煩,他都會出手相助。」
加百列說,「我家老頭死了。」
「我知道呀,沒有人躲得過癌症。一旦給癌症的爪子抓住,就只能說謝謝再見了。」
他第一次想買大麻時,也提過和他們父親的情誼,試圖贏得他們的信任。連恩覺得現在也一樣,尤哈想利用他們過世的父親贏取他們的信心。
尤哈搔搔凹陷的胸口,雙眼看著火焰。室內滿溢咖啡香。連恩和加百列看著彼此,繼續等。
「我有一份工作想找你們,」尤哈終於說,「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加百列問,「哪種工作?」
尤哈笑著倒咖啡,小心翼翼把兩個冒煙的馬克杯放在他們面前桌上。巨大斧頭占據火爐上方的主位,刀鋒在火光中閃耀。連恩的肚子開始絞痛,窒息的熱氣和動物頭顱的味道令他反胃。
尤哈站在桌子一端,身體前後搖晃。他發出口哨聲,吹涼咖啡。
「距離這兒不遠有一座未開發的金礦,就在那兒,等著你們這種飢渴的可憐傢伙。」
他的毛衣像寬鬆的皮膚覆蓋身子,因為久穿和汗水而褪色。他的褲子有長長裂痕,下頭露出蒼白的肌膚。他渾身散發松針和腐葉土的味道。他突然一動,從桌面拔起刀子,開始清潔指甲。連恩瞥向大門。只要三步,他就能回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
「給我們錢,」他說,「你拿到大麻了。我哥說得沒錯,我們不做公益。」
「我也有過哥哥。」尤哈說,「我們就像你們倆,形影不離。哥哥和我萬夫莫敵,全世界任我們宰制。但後來那個臭小子給我死了,那時我才意識到人生沒有規則可言,命運只會當面笑你。」
他吃痛般揪起臉,好一陣子沒說話。四周靜了下來,只有火焰在他背後兀自竄升,燒得劈啪響。昏暗光線中很難判讀他的表情,很難預先提防。加百列在桌下把腳湊到連恩腳邊,踢了一下。
「和我們多講講這座金礦。」他說,「在哪裡?」
尤哈笑得像在皺眉。
「你們知道歐德斯馬克的威達‧畢爾盧嗎?」
「大家都知道那隻老鐵公雞。」
「他或許活得像窮困的教堂老鼠,但他可有錢了,還不少呢。多年來他累積了一堆錢,一毛不拔的混帳。而且他不相信銀行,大部分的錢都藏在他房間的保險箱。他年紀老,體力衰弱,搶他的錢和拿走小嬰兒的糖果一樣簡單。」
加百列挑起眉毛。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和他很久以前做過生意,當時我還太蠢,沒發現他騙走老實人的土地,再賣給伐木公司。威達啊,真是貪心的混帳。現在沒人想和他做生意了。他只剩下女兒麗芙,不過叫她女僕還比較貼切。可憐的女孩,沒能過自己的人生。她還和爸爸住在歐德斯馬克,即使她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顧。或者孩子才是原因吧。」
尤哈轉頭朝爐火吐口水。他繼續說,雙頰血色加深,聲音顫抖。
「只有威達知道保險箱的密碼,扯到錢,他連自己的家人都不信。他的女兒和孫子對他唯命是從,只要他活著,他們都不能作決定。我向你們保證,他們不會礙事,所以別動他們,懂嗎?沒道理動他女兒或孫子一根寒毛。你們只要出其不意突襲老傢伙,錢就是你們的了。」
連恩看了加百列一眼。他的鼻孔擴張,混濁雙眼露出新的光澤。
「如果那麼容易,你為什麼不自己去?」
尤哈臉上閃過痛苦的神情,讓他顯得老一些。
「最近我連進村都很難,我受不了看到人,更別說去偷錢了。還是把機會讓給你們兩個能幹的小夥子吧,我知道你們做得到。」
「你手邊沒錢了吧?」
「胡說,可惡,我過得很好。這麼說吧,我打從心底受夠威達‧畢爾盧了。那個蠢材我行我素夠久了,是時候讓他嘗點苦頭。」
老人雙眼盯著連恩,比手刀畫過喉嚨。看來很滑稽,但連恩感到後背一陣顫慄。他看向加百列,看他臉上亮起新的光芒,便知道他下定決心了。要激發他的饑渴並不難,他總是夢想輕鬆賺錢。反觀他自己,可沒那麼容易被說服。他腦中浮現范娜的臉龐,想到出生前他就替她編織的夢想。夢想過正常的生活,住在好多房間的房子,屋內各個角落都不會讓人覺得羞恥。他想起她出生後住了好多天保溫箱,一團還看不見的小東西,全身每個開口都插上管子,藥在她微小的體內流竄。他不能碰她,只能在一旁看她躺在那兒奮戰。那個畫面永遠是驅使他的動力。
連恩說,「你要我們給你什麼?」
「什麼意思?」
「你和我們說這些,因為你想要回報吧?」
「我不要你們一毛錢,我只想看威達‧畢爾盧甘拜下風。我想看他丟掉這一大筆錢,反正本來就不該是他的。」
連恩把椅子往後推,站起身。尤哈站在原地盯著他,掂著手裡的刀。
「你確定他家有保險箱?」
「我很肯定,就像我知道太陽白天升起晚上落下。等一下,我有東西給你們看。」
尤哈遁入陰影,背對他們,開始翻找放在地上的櫃子。灰塵像煙繞著他飛舞,塞滿他們的鼻孔。他終於悶哼一聲,舉起一張泛黃的紙,上頭可見歲月和油膩手指的痕跡。他比出勝利的手勢,把紙放在他們之間的桌上。
「這是什麼?」
「你們有眼睛吧?這是一張圖。」
紙上畫的像是粗略的平面圖――黑色墨水顫巍巍畫出走廊、廚房和一個房間,詳細標示房門和窗戶,黑色箭頭指向房間。房間角落打了一個黑色的粗叉叉。尤哈俯身在桌上,把刀戳進叉叉中心,用力到刀柄都震動起來。
「那兒,」他說,「就是你們夢想的答案。」
□
麗芙站在水槽旁喝咖啡,省得坐在父親旁邊。威達盯著窗外,在寂寥的碎石路上尋找生命跡象。他穿得溫暖,即使近來他的手很難用刀了,但他腰帶上仍插著刀。他從不看電視,不讀書,不玩填字遊戲,也不賭馬。他的日子都花在喝咖啡和守望村子。即使拒絕和鄰居往來,他還是要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無情地監視家人,對待鄰居也是一樣。什麼事都躲不過老人,他迷濛的雙眼仍看清一切。
麗芙沒有提起她在賽門房內找到的酒瓶,反正威達終究會發現。
一輛車沿街開過。威達從椅子起身,關節嘎吱作響。他飢渴地伸長脖子。
「妳看看,卡爾埃里克又跑出去了。他們真該沒收那個笨蛋的駕照。」
「坐下來,別盯著人家看。」
「他從來沒有清醒到可以開車。妳等著瞧,總有一天他會撞死哪個可憐的傢伙。」
麗芙俯瞰泥濘的碎石路,以及融雪反射的陽光。她聽見卡爾埃里克的車轉上大路離開。她知道威達討厭鄰居是因為他很孤單。他不再懂得與人相處,別人靠近會嚇到他,使他變得惡毒。
她說,「鏈鋸有點問題。」
「是嗎?」
「我不想徒手劈完所有的木柴。」
「小鬼可以幫妳。他練出那身肌肉,總得拿來用用。」
威達慢慢咬著麵包。早餐他只抹奶油,就這樣,加料要等中餐。麗芙倒了更多咖啡,端詳外頭可悲的柴堆。一片灰中,斧頭亮紅色的把手宛如刺耳的尖叫。鏈鋸也是多餘的用具,如果她想換新的,得自己去買。連一片起司都不肯吃的人,絕不會同意買新的鏈鋸。
威達長繭的手撫平面前桌上的報紙,她用紅筆圈起的房屋出售廣告在紙面上盯著他。她是為了他好,讓他了解她和兒子要離開了。多年前她開始圈廣告時,他還會生氣,但現在他只會拿這件事開玩笑。
「妳不會想住在鎮上,那裡只有廢氣、垃圾和眼神空洞的人。在這兒晚上至少可以看到星星。」
他起身去倒咖啡,她趁機逃進浴室。她坐在生鏽的馬桶尿尿,然後雙手撐著龜裂的洗臉槽站了好久。鏡子也壞了,其中一角的裂痕像蜘蛛網。她避著不看自己的倒影;看到疲憊的嘴巴和哀傷的眼睛只會讓她更加疲憊哀傷。不僅房子逐漸破敗,她的臉也充滿傷痕。她聽到威達在廚房哼唱。他才是這個家的老人,他才應該想到死亡,然而卻是她在想。每天她都想,不可能太久了,她只要再忍幾年,人生便會開始。
她回到廚房時,威達已坐回椅子上。他們彷彿有默認的協議,像跳舞一般,一個人坐在桌旁,另一人就待在水槽邊,一個人四處走動,另一人就站著不動,好像房子無法同時容忍過多的動作。雖然她出生以來,他們便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兩人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一輛四輪機車沿路開過,威達躲到窗簾後。炫彩夾克在松樹間若隱若現。
「唉呀,真沒想到。」他說,「老莫迪又買了一台新玩具。那個傢伙都沒零錢搭公車了,卻還是一直買東西。」
「你怎麼知道是新的?」
「我頭上有眼睛不是嗎?舊的那台是黑色,這台是紅色。」
麗芙走到窗邊。道格拉斯‧莫迪停在柵欄旁,舉起手。她朝他揮手。
「或許我可以向他借鏈鋸,」她說,「直到我們買新的。」
威達開始咳嗽,氣管黏液在肺部翻騰。
「想都別想。」他恢復後說,「我不會讓那個混蛋踏上我的地,我寧可自己劈柴。」
很快她又回到柴堆旁。春陽燦爛,每次她舉起斧頭,都得閉上眼睛。當她揮下斧頭,她想像劈開父親的頭。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最後的雪》
威達站在門廊上,雙眼像黑色細縫。
他用沙啞的聲音叫道,「進來吃飯。」
然後他便消失了。麗芙拍乾淨外套,不情願地走向屋子,腳步在寂靜中宛如鼓聲。
老人和孩子坐在廚房,沉浸在咖啡香之中。威達的雙手在夜間僵住,早上手指就像僵硬的爪子,幾乎無法舉杯就口。賽門極為專注地替他把吐司切片,抹上奶油。
「阿公,你吃藥了沒?」
威達繼續嚼麵包。他根本不想吃藥,要不是賽門每天早上在他面前把藥丸排成整齊的彩虹,他絕不會吃。
「你嘮叨的樣子比老太婆還糟。」
不過威達仍一一吞下藥丸,吃完後輕拍賽門的手,男孩的手比他大了一號。賽門低頭朝桌面笑了。麗芙撇開眼,心想這孩子的美德、內心的光輝從哪兒來的。肯定不是遺傳到她。
她上樓到房間更衣。賽門的房門開著,幽暗房內吸引她的視線。被子從床上滑下來,捲成一團落在地上,旁邊是一堆髒衣服,還有書架塞不下的書。遮光簾拉下來,房內唯一的光源是桌上嗡嗡叫的老電腦。當年雖然威達反對,她仍替他買了,電腦也成為孤單男孩的朋友。他在電腦上有她完全不了解的完整生活。
她把臉湊到門縫,吸進青春期、汗濕襪子和焦慮的氣味。她先確認他們在樓下廚房的聲音,才推門進去。她撿起棉被,膝蓋嘎吱作響,灰塵在房內翻騰。床下有什麼一閃,她彎下腰,看到是沒有標籤的玻璃瓶,酒味重到不用轉開瓶蓋都知道裡頭裝什麼。某種私釀酒,烈到她都流淚了。可能是威達釀的。
「欸,媽,妳在做什麼?妳不能亂翻我的東西。」
賽門站在門口,臉氣得發黑。麗芙站起身,手裡拿著酒瓶,清涼的玻璃緊貼肌膚。
「我本來要替你鋪床,」她說,「結果找到這個。」
「不是我的,我替朋友保管。」
他們都知道他在撒謊,根本沒什麼朋友,但她不能說。麗芙拍乾淨酒瓶,輕放在電腦旁的桌上。思緒隨著她的脈搏流動。他十七歲了,沒必要和他爭執。他做一般少年會做的事,或許還是好事。
她問道,「哪個朋友?」
「不干妳的事。」
他們盯著彼此好一會兒。他皺起眉心,看起來像威達。即便如此,她仍在男孩臉上看到自己。倔強,渴求更多,渴求自由。要不是為了他,她不會站在這兒,留在她出生的家。她會在別處,跑得遠遠的。或許他知道原因是他,或許他們之間的距離因此越來越遠。她猜想他是否真的交到了朋友,搞不好是最惡劣的那群,會喝酒打架的孩子。或者他是否獨自坐在電腦的藍光中,整晚喝酒。兩者都令她心感沉重。
賽門伸手去拿背包,臉頰上憤怒的紅潮已退去。
「我上學要遲到了。」
她點點頭。
「我們晚上再談。」
「我不在的時候,妳別進我房間。」
「我現在就出去。」
他等她離開房間,裝模作樣關門鎖上,才走下樓。麗芙跟著他;她看他長毛的孩子氣後頸,想起她曾多次把臉埋在那兒,吸滿他的氣味。無數的夜晚,她用身子裹著保護他,一手放在他脆弱的肩胛骨之間,只為了確保他有呼吸,不會死去拋下她。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另一個時代了。
麗芙和老人站在廚房窗口,看他走向校車。他們的視線一直追著男孩高瘦的身影,直到森林吞噬他。
威達說,「我覺得他有女人了。」
「當真?」
「是啊,我聞得出來,他聞起來不一樣。」
「我沒注意到。」
威達咬住方糖,用茶碟端起杯子,透過糖塊啜飲咖啡,意味深長看了她一眼。
「妳聽清楚,他就像他媽媽。不用多久,他晚上就不回家了。」
□
在尤哈‧別克的小屋很難呼吸。連恩和加百列坐在不穩的桌旁,細瘦男子在他們前方來回踱步。灰塵和松針繞著他的靴子打轉,煙霧繚繞的空氣刺痛他們的眼睛。他的視線在兩人間擺盪,但他們無法和他對上眼。
「你們得原諒我,」他說,「我不習慣人。」
連恩試圖隱藏竄過全身的不安。他瞥向加百列,哥哥表情饒富興味,唇邊掛著一絲笑意,雙眼掃視小屋,看進奇怪的物品和打獵的紀念品。桌上插著一把刀,乾掉的血在刮傷的桌面留下深色陰影。動物的頭像窗簾掛在唯一的窗口,擁擠的室內又熱又悶。尤哈站在爐火一側,看著他們,雙眼似乎在燃燒。他的聲音沙啞,彷彿聲帶開始在喉嚨裡生鏽。沒有人和他說話就會這樣吧。
「你們這種瘋子會騎雪上摩托車獵狐狸,」他說,「我光看就知道了。」
「聽你在亂說,」連恩說,「我們看起來像該死的獵人嗎?」
「可是你們追著錢跑吧?你們的人生不過如此,只有毒品和好賺的錢。」
加百列雙腳拍打地面,連恩感到他的雙腿震動。兩人都沒說話。
「你們不會出於好心,帶咖啡和菸給老人家吧?你們這麼辛苦,就是想拿錢。」
「照你的說法,對,我們不做公益。」加百列說,「還是要講公平。」
尤哈嘎嘎大笑。連恩用眼角瞄那把刀,只要伸出手,刀就是他的了。他感到冷靜一些。
尤哈把咖啡壺掛在爐火上。
「你們很飢渴。」他說,「我很欣賞,我也飢渴過。但餓了夠久,你就不會再聽到肚子抱怨,會變得靜得要命。」
他的聲道雖然生鏽,聲音卻有種旋律,彷彿他寧可用唱的。
「我年輕的時候認識你們爸爸。」他繼續說,「我們是同學。他真是了不得,脾氣和獾一樣差,也很狡猾。但如果你有麻煩,他都會出手相助。」
加百列說,「我家老頭死了。」
「我知道呀,沒有人躲得過癌症。一旦給癌症的爪子抓住,就只能說謝謝再見了。」
他第一次想買大麻時,也提過和他們父親的情誼,試圖贏得他們的信任。連恩覺得現在也一樣,尤哈想利用他們過世的父親贏取他們的信心。
尤哈搔搔凹陷的胸口,雙眼看著火焰。室內滿溢咖啡香。連恩和加百列看著彼此,繼續等。
「我有一份工作想找你們,」尤哈終於說,「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加百列問,「哪種工作?」
尤哈笑著倒咖啡,小心翼翼把兩個冒煙的馬克杯放在他們面前桌上。巨大斧頭占據火爐上方的主位,刀鋒在火光中閃耀。連恩的肚子開始絞痛,窒息的熱氣和動物頭顱的味道令他反胃。
尤哈站在桌子一端,身體前後搖晃。他發出口哨聲,吹涼咖啡。
「距離這兒不遠有一座未開發的金礦,就在那兒,等著你們這種飢渴的可憐傢伙。」
他的毛衣像寬鬆的皮膚覆蓋身子,因為久穿和汗水而褪色。他的褲子有長長裂痕,下頭露出蒼白的肌膚。他渾身散發松針和腐葉土的味道。他突然一動,從桌面拔起刀子,開始清潔指甲。連恩瞥向大門。只要三步,他就能回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
「給我們錢,」他說,「你拿到大麻了。我哥說得沒錯,我們不做公益。」
「我也有過哥哥。」尤哈說,「我們就像你們倆,形影不離。哥哥和我萬夫莫敵,全世界任我們宰制。但後來那個臭小子給我死了,那時我才意識到人生沒有規則可言,命運只會當面笑你。」
他吃痛般揪起臉,好一陣子沒說話。四周靜了下來,只有火焰在他背後兀自竄升,燒得劈啪響。昏暗光線中很難判讀他的表情,很難預先提防。加百列在桌下把腳湊到連恩腳邊,踢了一下。
「和我們多講講這座金礦。」他說,「在哪裡?」
尤哈笑得像在皺眉。
「你們知道歐德斯馬克的威達‧畢爾盧嗎?」
「大家都知道那隻老鐵公雞。」
「他或許活得像窮困的教堂老鼠,但他可有錢了,還不少呢。多年來他累積了一堆錢,一毛不拔的混帳。而且他不相信銀行,大部分的錢都藏在他房間的保險箱。他年紀老,體力衰弱,搶他的錢和拿走小嬰兒的糖果一樣簡單。」
加百列挑起眉毛。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和他很久以前做過生意,當時我還太蠢,沒發現他騙走老實人的土地,再賣給伐木公司。威達啊,真是貪心的混帳。現在沒人想和他做生意了。他只剩下女兒麗芙,不過叫她女僕還比較貼切。可憐的女孩,沒能過自己的人生。她還和爸爸住在歐德斯馬克,即使她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顧。或者孩子才是原因吧。」
尤哈轉頭朝爐火吐口水。他繼續說,雙頰血色加深,聲音顫抖。
「只有威達知道保險箱的密碼,扯到錢,他連自己的家人都不信。他的女兒和孫子對他唯命是從,只要他活著,他們都不能作決定。我向你們保證,他們不會礙事,所以別動他們,懂嗎?沒道理動他女兒或孫子一根寒毛。你們只要出其不意突襲老傢伙,錢就是你們的了。」
連恩看了加百列一眼。他的鼻孔擴張,混濁雙眼露出新的光澤。
「如果那麼容易,你為什麼不自己去?」
尤哈臉上閃過痛苦的神情,讓他顯得老一些。
「最近我連進村都很難,我受不了看到人,更別說去偷錢了。還是把機會讓給你們兩個能幹的小夥子吧,我知道你們做得到。」
「你手邊沒錢了吧?」
「胡說,可惡,我過得很好。這麼說吧,我打從心底受夠威達‧畢爾盧了。那個蠢材我行我素夠久了,是時候讓他嘗點苦頭。」
老人雙眼盯著連恩,比手刀畫過喉嚨。看來很滑稽,但連恩感到後背一陣顫慄。他看向加百列,看他臉上亮起新的光芒,便知道他下定決心了。要激發他的饑渴並不難,他總是夢想輕鬆賺錢。反觀他自己,可沒那麼容易被說服。他腦中浮現范娜的臉龐,想到出生前他就替她編織的夢想。夢想過正常的生活,住在好多房間的房子,屋內各個角落都不會讓人覺得羞恥。他想起她出生後住了好多天保溫箱,一團還看不見的小東西,全身每個開口都插上管子,藥在她微小的體內流竄。他不能碰她,只能在一旁看她躺在那兒奮戰。那個畫面永遠是驅使他的動力。
連恩說,「你要我們給你什麼?」
「什麼意思?」
「你和我們說這些,因為你想要回報吧?」
「我不要你們一毛錢,我只想看威達‧畢爾盧甘拜下風。我想看他丟掉這一大筆錢,反正本來就不該是他的。」
連恩把椅子往後推,站起身。尤哈站在原地盯著他,掂著手裡的刀。
「你確定他家有保險箱?」
「我很肯定,就像我知道太陽白天升起晚上落下。等一下,我有東西給你們看。」
尤哈遁入陰影,背對他們,開始翻找放在地上的櫃子。灰塵像煙繞著他飛舞,塞滿他們的鼻孔。他終於悶哼一聲,舉起一張泛黃的紙,上頭可見歲月和油膩手指的痕跡。他比出勝利的手勢,把紙放在他們之間的桌上。
「這是什麼?」
「你們有眼睛吧?這是一張圖。」
紙上畫的像是粗略的平面圖――黑色墨水顫巍巍畫出走廊、廚房和一個房間,詳細標示房門和窗戶,黑色箭頭指向房間。房間角落打了一個黑色的粗叉叉。尤哈俯身在桌上,把刀戳進叉叉中心,用力到刀柄都震動起來。
「那兒,」他說,「就是你們夢想的答案。」
□
麗芙站在水槽旁喝咖啡,省得坐在父親旁邊。威達盯著窗外,在寂寥的碎石路上尋找生命跡象。他穿得溫暖,即使近來他的手很難用刀了,但他腰帶上仍插著刀。他從不看電視,不讀書,不玩填字遊戲,也不賭馬。他的日子都花在喝咖啡和守望村子。即使拒絕和鄰居往來,他還是要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無情地監視家人,對待鄰居也是一樣。什麼事都躲不過老人,他迷濛的雙眼仍看清一切。
麗芙沒有提起她在賽門房內找到的酒瓶,反正威達終究會發現。
一輛車沿街開過。威達從椅子起身,關節嘎吱作響。他飢渴地伸長脖子。
「妳看看,卡爾埃里克又跑出去了。他們真該沒收那個笨蛋的駕照。」
「坐下來,別盯著人家看。」
「他從來沒有清醒到可以開車。妳等著瞧,總有一天他會撞死哪個可憐的傢伙。」
麗芙俯瞰泥濘的碎石路,以及融雪反射的陽光。她聽見卡爾埃里克的車轉上大路離開。她知道威達討厭鄰居是因為他很孤單。他不再懂得與人相處,別人靠近會嚇到他,使他變得惡毒。
她說,「鏈鋸有點問題。」
「是嗎?」
「我不想徒手劈完所有的木柴。」
「小鬼可以幫妳。他練出那身肌肉,總得拿來用用。」
威達慢慢咬著麵包。早餐他只抹奶油,就這樣,加料要等中餐。麗芙倒了更多咖啡,端詳外頭可悲的柴堆。一片灰中,斧頭亮紅色的把手宛如刺耳的尖叫。鏈鋸也是多餘的用具,如果她想換新的,得自己去買。連一片起司都不肯吃的人,絕不會同意買新的鏈鋸。
威達長繭的手撫平面前桌上的報紙,她用紅筆圈起的房屋出售廣告在紙面上盯著他。她是為了他好,讓他了解她和兒子要離開了。多年前她開始圈廣告時,他還會生氣,但現在他只會拿這件事開玩笑。
「妳不會想住在鎮上,那裡只有廢氣、垃圾和眼神空洞的人。在這兒晚上至少可以看到星星。」
他起身去倒咖啡,她趁機逃進浴室。她坐在生鏽的馬桶尿尿,然後雙手撐著龜裂的洗臉槽站了好久。鏡子也壞了,其中一角的裂痕像蜘蛛網。她避著不看自己的倒影;看到疲憊的嘴巴和哀傷的眼睛只會讓她更加疲憊哀傷。不僅房子逐漸破敗,她的臉也充滿傷痕。她聽到威達在廚房哼唱。他才是這個家的老人,他才應該想到死亡,然而卻是她在想。每天她都想,不可能太久了,她只要再忍幾年,人生便會開始。
她回到廚房時,威達已坐回椅子上。他們彷彿有默認的協議,像跳舞一般,一個人坐在桌旁,另一人就待在水槽邊,一個人四處走動,另一人就站著不動,好像房子無法同時容忍過多的動作。雖然她出生以來,他們便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兩人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一輛四輪機車沿路開過,威達躲到窗簾後。炫彩夾克在松樹間若隱若現。
「唉呀,真沒想到。」他說,「老莫迪又買了一台新玩具。那個傢伙都沒零錢搭公車了,卻還是一直買東西。」
「你怎麼知道是新的?」
「我頭上有眼睛不是嗎?舊的那台是黑色,這台是紅色。」
麗芙走到窗邊。道格拉斯‧莫迪停在柵欄旁,舉起手。她朝他揮手。
「或許我可以向他借鏈鋸,」她說,「直到我們買新的。」
威達開始咳嗽,氣管黏液在肺部翻騰。
「想都別想。」他恢復後說,「我不會讓那個混蛋踏上我的地,我寧可自己劈柴。」
很快她又回到柴堆旁。春陽燦爛,每次她舉起斧頭,都得閉上眼睛。當她揮下斧頭,她想像劈開父親的頭。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最後的雪》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