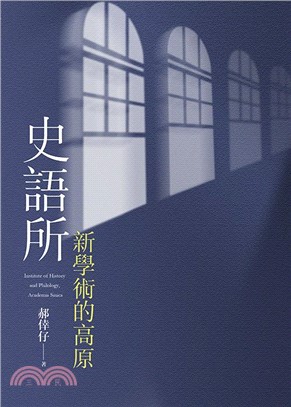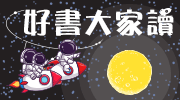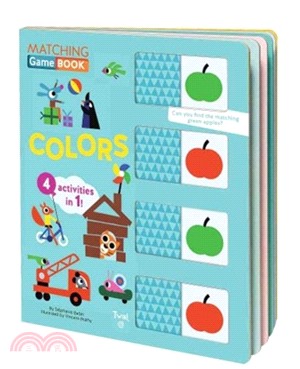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史語所的歷史將近百年,若衡諸民國以來所創制的學術機構,確實罕見。
郝博士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學有專精,古典文學尤為通曉。她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根據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親自訪談,三路齊發,終於成就這部生動有趣、信實可靠的對話錄。她不辭辛勞,曾多次到南港史語所親自採訪,與所內同仁深入交談,並且和海內外的學術知情人士交換意見,遂得完成此一巨作。
——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黃進興
2018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建所90週年。本書借此契機梳理史語所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後的情況。前些年大陸持續民國學術熱,為大眾追捧的民國大師,如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皆為史語所的開山前輩。那麼1950年之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如何?這些前輩離開大陸之後的狀況如何?接續上來的人物後勁又如何?時代變遷,學風是否依舊,精神是否長存?
本書從創意策劃、口述採訪、實地考察、查閱檔案,到分篇發表,再到成書付梓,歷時六載。其間中研院與史語所的全力支持自不待言。除卻黃進興副院長慨然應邀總論所史之外,先是王明珂所長(2016-2019),後是李貞德所長(2020-迄今),費心安排聯絡,遂得以遍訪史語所學人。疫情之前我數次來史語所,集中進行實地採訪,每次歷時兩週,每天上下午兩到三位受訪者。工作量臨界體力的極限。我手中存有所內外70位學人的近300個鐘頭的錄音,都是口述的纍纍碩果。杜正勝、丁邦新二位老所長,又為本書批閱全稿、審定史實。這本書記錄的只是史語所的局部。人生就是局部的,我們只能與人類社會同行這一段。希望本書可以構成一座橋樑,助益對史語所、對民國學脈感興趣的人,從局部引渡到歷史之真的彼岸。—— 本書著者 郝倖仔
郝博士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學有專精,古典文學尤為通曉。她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根據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親自訪談,三路齊發,終於成就這部生動有趣、信實可靠的對話錄。她不辭辛勞,曾多次到南港史語所親自採訪,與所內同仁深入交談,並且和海內外的學術知情人士交換意見,遂得完成此一巨作。
——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黃進興
2018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建所90週年。本書借此契機梳理史語所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後的情況。前些年大陸持續民國學術熱,為大眾追捧的民國大師,如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皆為史語所的開山前輩。那麼1950年之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如何?這些前輩離開大陸之後的狀況如何?接續上來的人物後勁又如何?時代變遷,學風是否依舊,精神是否長存?
本書從創意策劃、口述採訪、實地考察、查閱檔案,到分篇發表,再到成書付梓,歷時六載。其間中研院與史語所的全力支持自不待言。除卻黃進興副院長慨然應邀總論所史之外,先是王明珂所長(2016-2019),後是李貞德所長(2020-迄今),費心安排聯絡,遂得以遍訪史語所學人。疫情之前我數次來史語所,集中進行實地採訪,每次歷時兩週,每天上下午兩到三位受訪者。工作量臨界體力的極限。我手中存有所內外70位學人的近300個鐘頭的錄音,都是口述的纍纍碩果。杜正勝、丁邦新二位老所長,又為本書批閱全稿、審定史實。這本書記錄的只是史語所的局部。人生就是局部的,我們只能與人類社會同行這一段。希望本書可以構成一座橋樑,助益對史語所、對民國學脈感興趣的人,從局部引渡到歷史之真的彼岸。—— 本書著者 郝倖仔
作者簡介
郝倖仔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博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學者
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研究員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博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學者
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研究員
序
序 黃進興
頭回見到郝倖仔博士是2016年5月,她隨學術代表團前來史語所訪問。當時只覺得郝博士爽朗健談,不知是否這次參訪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後她遂發願撰寫「史語所的簡史」。由於近年大陸有股「民國熱」,書寫大陸時期史語所的文學或歷史均相當蓬勃,居中亦不乏佳作。我遂建議她不妨聚焦於「史語所在臺灣」。一來,史語所在臺灣時間上業已遠逾大陸時期;二來在臺灣的史語所,一方面不只繼承了前人成果,並且能推陳出新,帶來一股新學術的風氣,而與大陸時期迥然有別;加上兩岸隔閡既久,或許更能滿足外在學界的好奇心,從而幫助彼此的交流與切磋。果真,郝博士從善如流,接納我的建議,徑取臺灣的史語所作為分析的焦點。
按郝博士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學有專精,古典文學尤為通曉;有意以現代學術史為志業,理應駕輕就熟。她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根據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親自訪談,三路齊發,終於成就這部生動有趣、信實可靠的對話錄。她不辭辛勞,曾多次到南港史語所親自採訪,與所內同仁深入交談,並且和海內外的學術知情人士交換意見,遂得完成此一巨作。
個人曾忝為史語所所長七年之久,得見郝博士有此努力的成果,尤感欣喜與欽佩,盼此一對話錄有助於學界瞭解史語所近況,不吝予以批評與鼓勵,促進未來學術的交流和進步。
史語所第一代的前輩,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曾言「史語所凡九遷。」蓋謂其時國家多難,社會動盪,史語所逼不得已東西南北顛沛流離,但終究香火不絕如縷:一群知識分子兢兢業業,堅守崗位,薪火相傳,此或許可激發後人,追求學問的榜樣。
史語所的歷史將近百年,若衡諸民國以來所創制的學術機構,確實罕見。在史語所擔任所長期間,我常接到大陸學人的溢美之詞,謂「史語所」乃是「學術的麥加」或「求知的淨土」,此不外著眼本所自由、多元、不進則退的學風。但對我個人而言,在我的想像中,「史語所」毋乃更像宮崎駿動畫中的「霍爾的堡壘」,是一棟無時不在變化和移動的「知識堡壘」,雖只是一粒殘存的火種,但仍隨時發光發熱照亮身處之境。
頭回見到郝倖仔博士是2016年5月,她隨學術代表團前來史語所訪問。當時只覺得郝博士爽朗健談,不知是否這次參訪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後她遂發願撰寫「史語所的簡史」。由於近年大陸有股「民國熱」,書寫大陸時期史語所的文學或歷史均相當蓬勃,居中亦不乏佳作。我遂建議她不妨聚焦於「史語所在臺灣」。一來,史語所在臺灣時間上業已遠逾大陸時期;二來在臺灣的史語所,一方面不只繼承了前人成果,並且能推陳出新,帶來一股新學術的風氣,而與大陸時期迥然有別;加上兩岸隔閡既久,或許更能滿足外在學界的好奇心,從而幫助彼此的交流與切磋。果真,郝博士從善如流,接納我的建議,徑取臺灣的史語所作為分析的焦點。
按郝博士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學有專精,古典文學尤為通曉;有意以現代學術史為志業,理應駕輕就熟。她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根據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親自訪談,三路齊發,終於成就這部生動有趣、信實可靠的對話錄。她不辭辛勞,曾多次到南港史語所親自採訪,與所內同仁深入交談,並且和海內外的學術知情人士交換意見,遂得完成此一巨作。
個人曾忝為史語所所長七年之久,得見郝博士有此努力的成果,尤感欣喜與欽佩,盼此一對話錄有助於學界瞭解史語所近況,不吝予以批評與鼓勵,促進未來學術的交流和進步。
史語所第一代的前輩,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曾言「史語所凡九遷。」蓋謂其時國家多難,社會動盪,史語所逼不得已東西南北顛沛流離,但終究香火不絕如縷:一群知識分子兢兢業業,堅守崗位,薪火相傳,此或許可激發後人,追求學問的榜樣。
史語所的歷史將近百年,若衡諸民國以來所創制的學術機構,確實罕見。在史語所擔任所長期間,我常接到大陸學人的溢美之詞,謂「史語所」乃是「學術的麥加」或「求知的淨土」,此不外著眼本所自由、多元、不進則退的學風。但對我個人而言,在我的想像中,「史語所」毋乃更像宮崎駿動畫中的「霍爾的堡壘」,是一棟無時不在變化和移動的「知識堡壘」,雖只是一粒殘存的火種,但仍隨時發光發熱照亮身處之境。
目次
序(黃進興)
導言
第1章—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歷史學門
三、人類學門
四、考古學門
五、文字學門
第2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上)
1950-1970年代:老史語所的延續和新思潮的湧入
一、結束與重啟
二、黨禁與新思潮(1960-70年代)
三、臺大合聘開課
四、智識時代的落幕
第3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下)
1980年代的重新起飛
一、人文研究最好的環境(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二、收穫季與院士制度
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四、院士養成記
五、考核標準與「君子國」
第4章—史語所的歷次分合
一、1997:語言組獨立成所
二、考古組獨立計畫夭折
三、1955:史語所分所? 民族所創所?
四、近代史所:與民族所同時增設
第5章—所長與人才
一、屈萬裡時代:文籍考訂獨步,歷史學式微
二、所長眼中的「所長」
三、所長角色的變與不變
四、求賢虜學人才
第6章—殷墟古物在臺灣的保存
一、歷史沿革與舊館改造
二、檔案中的老史語所殷墟發掘
三、學術研究型博物館
四、兩岸合作與探索
五、社會影響與文創開發
第7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上)
爭取國際學術空間
一、從西洋史到世界史
二、GIS:國際化與「產業化」
三、傅斯年講座的靈驗
四、胡適夢想的實踐
五、史語所的大陸印記
第8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下)
唐獎漢學獎的評審
一、仿效諾貝爾獎,沒有秘密
二、評審委員與評審團
三、打造國際學術獎品牌
四、召集人的故事及期待
第9章—方法論與代表作
一、史籍自動化:史料學派的新路徑
二、集眾工作方法
三、他山之石的評價
四、方法論:閱讀與研究
參考文獻
所史
回憶錄、口述、傳記
專著
文章
人物索引
後記
導言
第1章—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歷史學門
三、人類學門
四、考古學門
五、文字學門
第2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上)
1950-1970年代:老史語所的延續和新思潮的湧入
一、結束與重啟
二、黨禁與新思潮(1960-70年代)
三、臺大合聘開課
四、智識時代的落幕
第3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下)
1980年代的重新起飛
一、人文研究最好的環境(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二、收穫季與院士制度
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四、院士養成記
五、考核標準與「君子國」
第4章—史語所的歷次分合
一、1997:語言組獨立成所
二、考古組獨立計畫夭折
三、1955:史語所分所? 民族所創所?
四、近代史所:與民族所同時增設
第5章—所長與人才
一、屈萬裡時代:文籍考訂獨步,歷史學式微
二、所長眼中的「所長」
三、所長角色的變與不變
四、求賢虜學人才
第6章—殷墟古物在臺灣的保存
一、歷史沿革與舊館改造
二、檔案中的老史語所殷墟發掘
三、學術研究型博物館
四、兩岸合作與探索
五、社會影響與文創開發
第7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上)
爭取國際學術空間
一、從西洋史到世界史
二、GIS:國際化與「產業化」
三、傅斯年講座的靈驗
四、胡適夢想的實踐
五、史語所的大陸印記
第8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下)
唐獎漢學獎的評審
一、仿效諾貝爾獎,沒有秘密
二、評審委員與評審團
三、打造國際學術獎品牌
四、召集人的故事及期待
第9章—方法論與代表作
一、史籍自動化:史料學派的新路徑
二、集眾工作方法
三、他山之石的評價
四、方法論:閱讀與研究
參考文獻
所史
回憶錄、口述、傳記
專著
文章
人物索引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 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郝倖仔:「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個老名字,反映開山前輩的建所初衷,以及他們那個時代對於歷史學的判斷。
黃進興:老史語所人都是在西方接受的學術訓練。史學組的傅斯年、陳寅恪在德國受訓,認為文獻學與歷史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學科,做歷史要從語言文獻的掌握入手。所名故而題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英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語言組(1997年獨立出去成為語言所)兩位重要人物,趙元任和李方桂,都是在美國受的訓練;另外考古組李濟也是哈佛的博士。建所伊始取向即見,就是要借助歐美已經發展出來的方法和制度,應用到中國的研究上。必須說一句,老語言組開山的這幾位前輩,都是祖師爺,今天看來皆不可及,他們成長求學的過程與際遇,皆非吾輩所能複製。
郝倖仔:史語所也因此成為最先受到國際關注的中國學術機構,當時著名的漢學家,法國伯希和都曾實地考察過安陽發掘。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所所長陳星燦就說,老史語所主持的殷墟考古是各民族各國家的集體協作,就是奧林匹克金牌。
黃進興:老史語所的確把西方的訓練看的比中國本土的訓練更重要。你提到殷墟發掘,我來舉個例子說明中西訓練的差別。傅斯年在德國不只接受19世紀末的philology,還有蘭克史學的發展,以及考古學的興起。他把董作賓送到安陽去,結果董寫報告回來說,挖出來的東西沒什麼價值,因為上面都沒有文字,董認為有字的東西才算數。傅斯年不認同:地下出土的文物,文字只是一部份,而器物、墓葬等等,可能會更重要。於是又派李濟過去,方才拉開科學考古的序幕。可見,學術傳統和學術背景不同,對於看到的東西,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給出的解釋也不同。殷墟發掘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傅斯年和李濟他們明白,考古的目標不僅僅在於文字。
郝倖仔:不僅史學,文學也如此。民國初年,陳寅恪從西方帶回文獻整理的理念,用於研究中古的文學,剛開始是佛教和敦煌的文學,後來用於明清文學。這條從語言學入手文獻的路子,是文史研究最正的一條路子。大陸五十年代之後就中斷了。歐美漢學基本上繼承的就是這條路子。哈佛大學即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界重鎮,在這一領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藏書。
黃進興:說到史語所收藏之重要文物資料,包括殷墟古物、商周青銅器、居延漢簡、歷代碑帖、墓誌、中國少數民族文物、明清檔案、俗文學資料等等,皆為1928年建所以來長期積累的財富。抗戰發生後,為了保護研究材料,所有典藏,包括文物、儀器、標本等等,統統裝成1000多箱,輸運後方,跟著史語所輾轉遷徙。1949年撤退到臺灣,直至1955年遷至現址(臺北南港)之前,其間27年,史語所的大部份時間都在戰亂流離中度過。雖然部份圖書文物在戰爭中遭到損毀,但大多數得以保存,史語所的研究工作亦得以持續。
郝倖仔:王汎森院士在史語所所長任上,逢80周年所慶,編寫一部《中國史新論》,還拍攝一部紀錄片,《走過八十年》。但好像未曾在大陸公映過。
黃進興:史語所研究人員為此特意回訪大陸與臺灣的舊址,探索當年遷徙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紀錄片。拍的不錯,但確如你所說,大陸沒放映過。
郝倖仔:我仔細觀摩兩遍。此片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很想表明親近大陸的態度。一則,史語所創於廣州中山大學,有獨立所址始於遷入「柏園」,與中共三大會址「逵園」,位於同一條恤孤院路上,門牌號分別為35號與31號,強調咫尺之遙與冥冥之緣。第二,強調1948年底史語所本想遷往廣東、廣西,或者臺灣—即臺灣並不是方向性明確的唯一選擇—但因為1948年12月15日,傅斯年被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所以史語所才最終遷往臺灣。我查了王懋勤所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記載1948年12月1日,史語所召開所務會議,決議聽候政府及總院作最後之決定,因此遷往臺灣。
黃進興:這部紀錄片偏重於地景和建築,而不是學術。如果是學術的發展,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了,所以偏重在地方的記錄。就像你這本書,偏重於學人的口述,也是這個邏輯。
郝倖仔:史語所一直以來的標籤就是「史料學派」,傅斯年老所長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深入人心。因為強調史料,且史料不限文字,所以才會有多年來對於考古、地質、文書、採集民謠、各種標本的收集。像紀錄片這樣的影像表達,其實也是史料,這又說到史語所另一項世界第一—數位典藏。
黃進興: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工作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典籍數位化的前提和基礎是典藏。史語所自己典藏豐富,所以率先做起來,1984年發端,也是摸索,畢竟華人世界尚無機構做過。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很多新的概念,包括空間人文學的概念、物質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統計、人群的移動、文本裡面的情緒等等,都是要依靠數位工具的幫助來完成。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運動還未結束,中研院的數位典藏工作就開始了,7000件相關文物以及影音材料得以保存,一周年後完成上線,是臺灣史上對於社會運動反應最快、檔案保存最完整的一次。傅斯年老所長一直強調新材料、新方法,所以為了能將史料說盡說透,就應該窮盡各種研究方法。而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即延伸並且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
郝倖仔:做史語所所長,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即所外之人批判史料學派時,身為所長應該怎樣去回應。我向前所長杜正勝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對於我們的老祖宗,不能總是大概的恭維,應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要能夠具體講出他在學術探索上的意義。當然,這個瞭解應該是同情、肯定的瞭解,而不是批判性的瞭解,因為我們到底是史語所的人。
黃進興:史語所創建之初,史學組的研究重點有二:文籍考訂和史料徵集;遷臺之後,第二代的勞榦和嚴耕望在1960年代,第三代的許倬雲和陶晉生在1970年代,都先後離開臺灣。在這個時候,史語所的歷史學基本上完全就是文獻考訂之學了,外界對於「史料學派」的負面評價,包括胡適和何炳棣批評史語所不懂社會科學,大多集中在這個時期。六十年代以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大規模引入臺灣,才開始廣泛影響新一代的歷史學者。
郝倖仔:錢穆在臺北早年的寓所「素書樓」,展示過一封錢穆寫給嚴耕望的信(七月廿七日),談到自己的新書《雙溪獨語》時說:「近來士不悅學,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恐讀吾書難入。然亦自娛而已。並稍立標格,欲使真向學者,知有一規模耳。院士選舉如沈某,豈非一索即得,言之增慨。」信中所言「院士選舉」,應該是指中央研究院第8屆院士評選(1970),嚴耕望與沈剛伯同屆折桂;錢穆是第7屆院士(1968); 後此信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卷,標注的寫信日期為1972年。由以上細節可推測,信中所言「沈某」大概是指沈剛伯。因為沈當選院士的1970年正是臺灣史學界新學風興起之時,即您說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史學的新思潮;而錢穆與嚴耕望皆為舊史學的典型。所以我進一步推測,嚴、沈二人同在第8屆選院士,審查討論環節必有互相比較,且錢前屆當選,應該參與新屆之評定。所以錢穆才會有信中感慨,「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似言沈剛伯代表之新學風。杜正勝先生看到這一部份,表示想為沈剛伯多說幾句。杜公很佩服沈的史識,固非沈為其業師之故;且杜與錢穆曾有近距離接觸的經驗,受益於他的指點,〈徘徊於素書樓門
墻之外〉一文有記。但錢穆1976年9月曾有一篇文章,事後的驗證讓杜公感覺之史識實在不及沈。杜公舉此例想說明多為沈講兩句公平話的理由。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的歷史學,面臨的學風轉向就是這個樣子;語言學這一塊,與初創時期也有很大改變,傅斯年、陳寅恪的時代過去了,他們當年認定的歷史語言學,即英文所名中的philology,與現代的語言學,在學科系統上已經不一樣了。所以,史語所的語言學組於1997年分出去,成立獨立的語言學所。史語所這棵老樹,一直保留最初的歷史、考古、文字學的主幹,並持續發展;遷臺之後,又分出來兩條新枝,一個是民族學研究所,另一個是語言學研究所,構成1950年以來史語所在建制上的變化走向。老所名稱「歷史語言研究所」維持不變。
郝倖仔:有一個細節,我列席第33屆院士會議現場,發現正中央懸掛中山先生像與國民黨黨旗。是否歷次院士會議一直如此佈置?
黃進興:是的。至今如此。
郝倖仔:說到建制,關於「組」這個概念,得請您好好說說。所裡老人都跟我說,搞清楚「組」的意義、「組」的精神,對瞭解史語所的歷史非常重要。2003年,中研院取消「組」建制,代之以「學門」。研究所史時,我原以為只是名稱的變更,後來發現遠非如此簡單。
黃進興:史語所初創於廣州,1929年遷北平後,建制調整為歷史丶語言丶考古三個組。1933年由北平遷上海,繼遷南京,同年5月增設人類學組。撤退臺灣之後,1958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後易名文字學組。1997年語言學組獨立成所。2003年配合院方廢組政策,改「組」為「學門」。這條線捋下來,你就看清楚了,「組」是一個從創所伊始就沿用的老建制。老史語所的規格就好像大學裡面的文學院。文學院下面有若干個系,史語所下面有若干個組。第一組是史學組,第二組是語言組,第三組是考古組,第四組是人類學組,第五組是文字學組。
郝倖仔:第幾組是正式的名稱嗎?
黃進興:是的。正式的名稱就是稱呼第幾組。因為組是有建制的組,每個組主任都有行政加給,是拿津貼的。組的人事權歸組管控,組也有經費。
郝倖仔:那組的權力蠻大的。大陸文教系統大多屬於事業單位,一個單位的權力說到底也就是人事權和財權這兩項,且事業單位不創造經濟效益,所謂財權不外乎財政預算的分配權。所以大陸此類事業單位的一把手—臺灣稱為「長官」—說白了只是有個級別和相應的待遇,權力很有限。因此流行一句話,說文教系統的領導是紙老虎,咬人也不疼。
黃進興:組主任有人事權,就是用人的提名權。提名權在組,不在所。當然用人也不是組主任一個人說了算,最後還要到所務會議上投票,取得各組的認同,才能算數。但是發動機還是在組。所以組主任的任務就是要有眼光去物色人才。
郝倖仔:這樣看來,組主任重視哪一方面,甚至可以決定這個組今後的發展偏重哪一方面。
黃進興:是的。組主任要把握這個組的學術方向。只要發現一個人足夠優秀,能夠說服其他人,組主任就可以提名進用這個人,但如果組主任按兵不動,所長也沒有辦法。
郝倖仔:所長不能提名一個人進所嗎?
黃進興:不能。因為被提名者只能以「組」為單位進來,別人要問你,也是問屬於哪一組啊?沒有回答說是屬於史語所的。這就是發動機的作用,是「組」的關鍵所在。
郝倖仔:2003年以後取消「組」建制,改成「學門」。學門召集人是不是就沒有行政加給,沒有這些權力了?
黃進興:都沒有了。所以從「組」到「學門」,絕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
郝倖仔:1990年代張光直回臺灣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希望將考古組獨立成所卻未能如願一事,已成為國際漢學界一大公案。我跟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談及此事,他感歎,原來還是考古組呢,結果不光沒獨立出來,連組也沒了。可見「組」和「學門」的差異。只有史語所下設這樣的「組」建制嗎?中研院其他所呢?
黃進興:只有史語所如此,其他所沒有。以前老史語所的組主任在中研院都是有投票權的。一直到1980年代,院裡開院務會議,史語所有五票,除了所長那一票,四個組主任還各有一票。人文的兄弟所像近代史所只有一票,民族所也只有一票,就是只有所長有投票權。1980年代還是這種情況,至於什麼時候改了要查檔案。所以傅斯年創所的時候說,史語所每一個組主任—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出去都是要當所長的。
郝倖仔:感覺以前的中研院和史語所都是地方分權制。即在院裡,所是重心;在所裡,組是重心。現在都打散了。
黃進興:的確如此。如今的「學門」,就好像是區分一下學術領域,有個人來負責,遠遠不是「組」的內涵。
郝倖仔:杜正勝先生還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教我理解「組」的一體感。人類學門要請吃飯,請的就是原來人類學組的同仁。不會有哪位同仁說把其他組—或者史學組或者考古組—哪個好朋友叫來一起吃飯。人人都有這個邊際感。
黃進興:我這裡也有個例子。考古學門有一個自己的節日,10月13日「考古節」,紀念殷墟破土開掘的日子。而且這個考古節比史語所的所慶—10月22日—還早九天
郝倖仔:石璋如在回憶錄裡說,考古節是他擔任考古組組主任(1977年9月始)時所訂立。據說這個圈子式的節日儀式一直延續至今,每年這一天考古學門都會有聚會,並到李濟、高去尋、石璋如等前輩墳前祭拜,以志不忘。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自1928年創立,至今已超過90年,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具此歷史背景的研究機構並不多。老所便有不少老規矩,新人進來又有新氣象。新舊激蕩,自然有話可說。所以你要多觀察,用心發現。
一、 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郝倖仔:「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個老名字,反映開山前輩的建所初衷,以及他們那個時代對於歷史學的判斷。
黃進興:老史語所人都是在西方接受的學術訓練。史學組的傅斯年、陳寅恪在德國受訓,認為文獻學與歷史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學科,做歷史要從語言文獻的掌握入手。所名故而題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英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語言組(1997年獨立出去成為語言所)兩位重要人物,趙元任和李方桂,都是在美國受的訓練;另外考古組李濟也是哈佛的博士。建所伊始取向即見,就是要借助歐美已經發展出來的方法和制度,應用到中國的研究上。必須說一句,老語言組開山的這幾位前輩,都是祖師爺,今天看來皆不可及,他們成長求學的過程與際遇,皆非吾輩所能複製。
郝倖仔:史語所也因此成為最先受到國際關注的中國學術機構,當時著名的漢學家,法國伯希和都曾實地考察過安陽發掘。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所所長陳星燦就說,老史語所主持的殷墟考古是各民族各國家的集體協作,就是奧林匹克金牌。
黃進興:老史語所的確把西方的訓練看的比中國本土的訓練更重要。你提到殷墟發掘,我來舉個例子說明中西訓練的差別。傅斯年在德國不只接受19世紀末的philology,還有蘭克史學的發展,以及考古學的興起。他把董作賓送到安陽去,結果董寫報告回來說,挖出來的東西沒什麼價值,因為上面都沒有文字,董認為有字的東西才算數。傅斯年不認同:地下出土的文物,文字只是一部份,而器物、墓葬等等,可能會更重要。於是又派李濟過去,方才拉開科學考古的序幕。可見,學術傳統和學術背景不同,對於看到的東西,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給出的解釋也不同。殷墟發掘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傅斯年和李濟他們明白,考古的目標不僅僅在於文字。
郝倖仔:不僅史學,文學也如此。民國初年,陳寅恪從西方帶回文獻整理的理念,用於研究中古的文學,剛開始是佛教和敦煌的文學,後來用於明清文學。這條從語言學入手文獻的路子,是文史研究最正的一條路子。大陸五十年代之後就中斷了。歐美漢學基本上繼承的就是這條路子。哈佛大學即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界重鎮,在這一領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藏書。
黃進興:說到史語所收藏之重要文物資料,包括殷墟古物、商周青銅器、居延漢簡、歷代碑帖、墓誌、中國少數民族文物、明清檔案、俗文學資料等等,皆為1928年建所以來長期積累的財富。抗戰發生後,為了保護研究材料,所有典藏,包括文物、儀器、標本等等,統統裝成1000多箱,輸運後方,跟著史語所輾轉遷徙。1949年撤退到臺灣,直至1955年遷至現址(臺北南港)之前,其間27年,史語所的大部份時間都在戰亂流離中度過。雖然部份圖書文物在戰爭中遭到損毀,但大多數得以保存,史語所的研究工作亦得以持續。
郝倖仔:王汎森院士在史語所所長任上,逢80周年所慶,編寫一部《中國史新論》,還拍攝一部紀錄片,《走過八十年》。但好像未曾在大陸公映過。
黃進興:史語所研究人員為此特意回訪大陸與臺灣的舊址,探索當年遷徙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紀錄片。拍的不錯,但確如你所說,大陸沒放映過。
郝倖仔:我仔細觀摩兩遍。此片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很想表明親近大陸的態度。一則,史語所創於廣州中山大學,有獨立所址始於遷入「柏園」,與中共三大會址「逵園」,位於同一條恤孤院路上,門牌號分別為35號與31號,強調咫尺之遙與冥冥之緣。第二,強調1948年底史語所本想遷往廣東、廣西,或者臺灣—即臺灣並不是方向性明確的唯一選擇—但因為1948年12月15日,傅斯年被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所以史語所才最終遷往臺灣。我查了王懋勤所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記載1948年12月1日,史語所召開所務會議,決議聽候政府及總院作最後之決定,因此遷往臺灣。
黃進興:這部紀錄片偏重於地景和建築,而不是學術。如果是學術的發展,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了,所以偏重在地方的記錄。就像你這本書,偏重於學人的口述,也是這個邏輯。
郝倖仔:史語所一直以來的標籤就是「史料學派」,傅斯年老所長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深入人心。因為強調史料,且史料不限文字,所以才會有多年來對於考古、地質、文書、採集民謠、各種標本的收集。像紀錄片這樣的影像表達,其實也是史料,這又說到史語所另一項世界第一—數位典藏。
黃進興: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工作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典籍數位化的前提和基礎是典藏。史語所自己典藏豐富,所以率先做起來,1984年發端,也是摸索,畢竟華人世界尚無機構做過。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很多新的概念,包括空間人文學的概念、物質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統計、人群的移動、文本裡面的情緒等等,都是要依靠數位工具的幫助來完成。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運動還未結束,中研院的數位典藏工作就開始了,7000件相關文物以及影音材料得以保存,一周年後完成上線,是臺灣史上對於社會運動反應最快、檔案保存最完整的一次。傅斯年老所長一直強調新材料、新方法,所以為了能將史料說盡說透,就應該窮盡各種研究方法。而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即延伸並且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
郝倖仔:做史語所所長,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即所外之人批判史料學派時,身為所長應該怎樣去回應。我向前所長杜正勝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對於我們的老祖宗,不能總是大概的恭維,應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要能夠具體講出他在學術探索上的意義。當然,這個瞭解應該是同情、肯定的瞭解,而不是批判性的瞭解,因為我們到底是史語所的人。
黃進興:史語所創建之初,史學組的研究重點有二:文籍考訂和史料徵集;遷臺之後,第二代的勞榦和嚴耕望在1960年代,第三代的許倬雲和陶晉生在1970年代,都先後離開臺灣。在這個時候,史語所的歷史學基本上完全就是文獻考訂之學了,外界對於「史料學派」的負面評價,包括胡適和何炳棣批評史語所不懂社會科學,大多集中在這個時期。六十年代以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大規模引入臺灣,才開始廣泛影響新一代的歷史學者。
郝倖仔:錢穆在臺北早年的寓所「素書樓」,展示過一封錢穆寫給嚴耕望的信(七月廿七日),談到自己的新書《雙溪獨語》時說:「近來士不悅學,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恐讀吾書難入。然亦自娛而已。並稍立標格,欲使真向學者,知有一規模耳。院士選舉如沈某,豈非一索即得,言之增慨。」信中所言「院士選舉」,應該是指中央研究院第8屆院士評選(1970),嚴耕望與沈剛伯同屆折桂;錢穆是第7屆院士(1968); 後此信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卷,標注的寫信日期為1972年。由以上細節可推測,信中所言「沈某」大概是指沈剛伯。因為沈當選院士的1970年正是臺灣史學界新學風興起之時,即您說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史學的新思潮;而錢穆與嚴耕望皆為舊史學的典型。所以我進一步推測,嚴、沈二人同在第8屆選院士,審查討論環節必有互相比較,且錢前屆當選,應該參與新屆之評定。所以錢穆才會有信中感慨,「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似言沈剛伯代表之新學風。杜正勝先生看到這一部份,表示想為沈剛伯多說幾句。杜公很佩服沈的史識,固非沈為其業師之故;且杜與錢穆曾有近距離接觸的經驗,受益於他的指點,〈徘徊於素書樓門
墻之外〉一文有記。但錢穆1976年9月曾有一篇文章,事後的驗證讓杜公感覺之史識實在不及沈。杜公舉此例想說明多為沈講兩句公平話的理由。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的歷史學,面臨的學風轉向就是這個樣子;語言學這一塊,與初創時期也有很大改變,傅斯年、陳寅恪的時代過去了,他們當年認定的歷史語言學,即英文所名中的philology,與現代的語言學,在學科系統上已經不一樣了。所以,史語所的語言學組於1997年分出去,成立獨立的語言學所。史語所這棵老樹,一直保留最初的歷史、考古、文字學的主幹,並持續發展;遷臺之後,又分出來兩條新枝,一個是民族學研究所,另一個是語言學研究所,構成1950年以來史語所在建制上的變化走向。老所名稱「歷史語言研究所」維持不變。
郝倖仔:有一個細節,我列席第33屆院士會議現場,發現正中央懸掛中山先生像與國民黨黨旗。是否歷次院士會議一直如此佈置?
黃進興:是的。至今如此。
郝倖仔:說到建制,關於「組」這個概念,得請您好好說說。所裡老人都跟我說,搞清楚「組」的意義、「組」的精神,對瞭解史語所的歷史非常重要。2003年,中研院取消「組」建制,代之以「學門」。研究所史時,我原以為只是名稱的變更,後來發現遠非如此簡單。
黃進興:史語所初創於廣州,1929年遷北平後,建制調整為歷史丶語言丶考古三個組。1933年由北平遷上海,繼遷南京,同年5月增設人類學組。撤退臺灣之後,1958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後易名文字學組。1997年語言學組獨立成所。2003年配合院方廢組政策,改「組」為「學門」。這條線捋下來,你就看清楚了,「組」是一個從創所伊始就沿用的老建制。老史語所的規格就好像大學裡面的文學院。文學院下面有若干個系,史語所下面有若干個組。第一組是史學組,第二組是語言組,第三組是考古組,第四組是人類學組,第五組是文字學組。
郝倖仔:第幾組是正式的名稱嗎?
黃進興:是的。正式的名稱就是稱呼第幾組。因為組是有建制的組,每個組主任都有行政加給,是拿津貼的。組的人事權歸組管控,組也有經費。
郝倖仔:那組的權力蠻大的。大陸文教系統大多屬於事業單位,一個單位的權力說到底也就是人事權和財權這兩項,且事業單位不創造經濟效益,所謂財權不外乎財政預算的分配權。所以大陸此類事業單位的一把手—臺灣稱為「長官」—說白了只是有個級別和相應的待遇,權力很有限。因此流行一句話,說文教系統的領導是紙老虎,咬人也不疼。
黃進興:組主任有人事權,就是用人的提名權。提名權在組,不在所。當然用人也不是組主任一個人說了算,最後還要到所務會議上投票,取得各組的認同,才能算數。但是發動機還是在組。所以組主任的任務就是要有眼光去物色人才。
郝倖仔:這樣看來,組主任重視哪一方面,甚至可以決定這個組今後的發展偏重哪一方面。
黃進興:是的。組主任要把握這個組的學術方向。只要發現一個人足夠優秀,能夠說服其他人,組主任就可以提名進用這個人,但如果組主任按兵不動,所長也沒有辦法。
郝倖仔:所長不能提名一個人進所嗎?
黃進興:不能。因為被提名者只能以「組」為單位進來,別人要問你,也是問屬於哪一組啊?沒有回答說是屬於史語所的。這就是發動機的作用,是「組」的關鍵所在。
郝倖仔:2003年以後取消「組」建制,改成「學門」。學門召集人是不是就沒有行政加給,沒有這些權力了?
黃進興:都沒有了。所以從「組」到「學門」,絕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
郝倖仔:1990年代張光直回臺灣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希望將考古組獨立成所卻未能如願一事,已成為國際漢學界一大公案。我跟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談及此事,他感歎,原來還是考古組呢,結果不光沒獨立出來,連組也沒了。可見「組」和「學門」的差異。只有史語所下設這樣的「組」建制嗎?中研院其他所呢?
黃進興:只有史語所如此,其他所沒有。以前老史語所的組主任在中研院都是有投票權的。一直到1980年代,院裡開院務會議,史語所有五票,除了所長那一票,四個組主任還各有一票。人文的兄弟所像近代史所只有一票,民族所也只有一票,就是只有所長有投票權。1980年代還是這種情況,至於什麼時候改了要查檔案。所以傅斯年創所的時候說,史語所每一個組主任—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出去都是要當所長的。
郝倖仔:感覺以前的中研院和史語所都是地方分權制。即在院裡,所是重心;在所裡,組是重心。現在都打散了。
黃進興:的確如此。如今的「學門」,就好像是區分一下學術領域,有個人來負責,遠遠不是「組」的內涵。
郝倖仔:杜正勝先生還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教我理解「組」的一體感。人類學門要請吃飯,請的就是原來人類學組的同仁。不會有哪位同仁說把其他組—或者史學組或者考古組—哪個好朋友叫來一起吃飯。人人都有這個邊際感。
黃進興:我這裡也有個例子。考古學門有一個自己的節日,10月13日「考古節」,紀念殷墟破土開掘的日子。而且這個考古節比史語所的所慶—10月22日—還早九天
郝倖仔:石璋如在回憶錄裡說,考古節是他擔任考古組組主任(1977年9月始)時所訂立。據說這個圈子式的節日儀式一直延續至今,每年這一天考古學門都會有聚會,並到李濟、高去尋、石璋如等前輩墳前祭拜,以志不忘。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自1928年創立,至今已超過90年,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具此歷史背景的研究機構並不多。老所便有不少老規矩,新人進來又有新氣象。新舊激蕩,自然有話可說。所以你要多觀察,用心發現。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