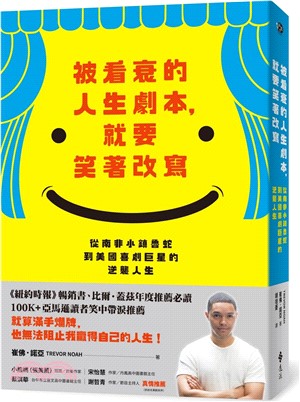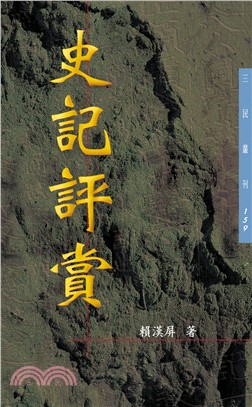被看衰的人生劇本,就要笑著改寫:從南非小鎮魯蛇到美國喜劇巨星的逆襲人生(《以母之名》新版)
商品資訊
系列名:綠蠹魚Read It
ISBN13:9786263618060
替代書名:Born a Crime
出版社:遠流
作者:崔佛‧諾亞
譯者:胡培菱
出版日:2024/08/28
裝訂/頁數:平裝/352頁
規格:21cm*14.8cm*1.9cm (高/寬/厚)
版次:2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紐約時報》暢銷書、比爾‧蓋茲年度推薦必讀
★100K+亞馬遜讀者笑中帶淚推薦
就算滿手爛牌,也無法阻止我贏得自己的人生!
崔佛‧諾亞一出生,就拿到堪稱「地獄級難度」的人生劇本:
● 他是不被政府允許存在的小孩
● 鄰居中就有熱愛告密的「抓耙仔」
● 童年住在動亂暴力的一級戰區
● 混血身分讓他到哪裡都遭到排擠
● 靠吃蟲子或便宜的骨頭、肉末果腹是家常便飯
崔佛在困苦黑人社群長大,絕大多數的親戚鄰居出路只有農場、工廠、礦坑,一輩子最大的期盼是幫簡陋的家多蓋一個房間,再不然就是走上犯罪道路。拿了一手壞牌、看似難以翻身的他,卻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生教練及隊友──他的母親。
崔佛的母親諾邦絲不願讓自己的人生被社會設限,更拒絕讓兒子複製這樣的生活。她不只努力學習祕書課程,抓準機會進入白領階級的最下層,教養崔佛時,也不吝提供所有可以幫助他自由發展的工具:語言、書籍、寄宿學校、看電影、時髦的休閒娛樂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崔佛得以看到更廣大的世界,對於生命發展有不同於傳統的視野。最終,崔佛也成功從南非發跡,躍升為英美等地大受歡迎的喜劇巨星。
母子倆一路走來經歷諸多痛楚艱難,流血流淚的同時總不忘報以笑聲。這樣的堅強與豁達,或許也正是我們許多人所需要的特質──世界可能對你很殘酷,但你永遠能做出屬於自己的選擇。
★100K+亞馬遜讀者笑中帶淚推薦
就算滿手爛牌,也無法阻止我贏得自己的人生!
崔佛‧諾亞一出生,就拿到堪稱「地獄級難度」的人生劇本:
● 他是不被政府允許存在的小孩
● 鄰居中就有熱愛告密的「抓耙仔」
● 童年住在動亂暴力的一級戰區
● 混血身分讓他到哪裡都遭到排擠
● 靠吃蟲子或便宜的骨頭、肉末果腹是家常便飯
崔佛在困苦黑人社群長大,絕大多數的親戚鄰居出路只有農場、工廠、礦坑,一輩子最大的期盼是幫簡陋的家多蓋一個房間,再不然就是走上犯罪道路。拿了一手壞牌、看似難以翻身的他,卻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生教練及隊友──他的母親。
崔佛的母親諾邦絲不願讓自己的人生被社會設限,更拒絕讓兒子複製這樣的生活。她不只努力學習祕書課程,抓準機會進入白領階級的最下層,教養崔佛時,也不吝提供所有可以幫助他自由發展的工具:語言、書籍、寄宿學校、看電影、時髦的休閒娛樂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崔佛得以看到更廣大的世界,對於生命發展有不同於傳統的視野。最終,崔佛也成功從南非發跡,躍升為英美等地大受歡迎的喜劇巨星。
母子倆一路走來經歷諸多痛楚艱難,流血流淚的同時總不忘報以笑聲。這樣的堅強與豁達,或許也正是我們許多人所需要的特質──世界可能對你很殘酷,但你永遠能做出屬於自己的選擇。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崔佛‧諾亞(Trevor Noah)
美國當紅喜劇演員,混血,來自南非。
母親是南非科薩族黑人,父親是瑞士籍德裔白人。
二○一四年~二○二二年擔任美國《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主持人。
曾獲頒MTV Movie & TV 最佳主持人與艾美獎,並被《時代雜誌》評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譯者簡介
胡培菱
美國 Rutgers 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於大學任教、於媒體寫文、並有譯作些許。專論當代美國文學與文化社會,評論文章見於博客來 OKAPI、開卷 Openbook 及各大報章雜誌。現定居美國。
名人/編輯推薦
小熊媽(張美蘭)|親職/教養作家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蔡淇華|台中市立惠文高中圖書館主任
謝哲青|作家/節目主持人
──真情推薦(依姓名筆劃排序)
目次
第一部
1 快跑
2 天生的罪名
3 崔佛,禱告
4 變色龍
5 排行老二的女孩
6 漏洞
7 噗吠
8 羅伯特
第二部
9 桑樹
10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一堂:情人節
11 局外人
12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二堂:迷戀
13 色盲
14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三堂:舞會
第三部
15 跳!希特勒!
16 起司男孩
17 這世界並不愛你
18 我媽的人生
1 快跑
2 天生的罪名
3 崔佛,禱告
4 變色龍
5 排行老二的女孩
6 漏洞
7 噗吠
8 羅伯特
第二部
9 桑樹
10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一堂:情人節
11 局外人
12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二堂:迷戀
13 色盲
14 一個年輕男子漫長、彆扭、有時悲劇、經常丟臉的愛情必修課。 第三堂:舞會
第三部
15 跳!希特勒!
16 起司男孩
17 這世界並不愛你
18 我媽的人生
書摘/試閱
第5章 排行老二的女孩(節錄)
我媽曾跟我說:「我選擇生你是因為,我希望有個我可以愛也會無條件愛我的人。」她兩手皆空的長大,所以渴望一個屬於她的東西。
我外公外婆的婚姻並不美滿,他們在索菲雅鎮相遇並結婚,但是一年後軍隊入駐就把他們驅逐出城。政府奪走了他們的房子,把整個區域剷平,蓋了一個豪華、全新的白人郊區叫翠昂夫,就是勝利的意思。與其他命運相同的幾萬名黑人一起,我外公外婆被強制遷移到索維托,他們不久之後就離婚了。
我媽是個問題兒童,她像男人婆,固執又愛挑釁,我外婆不知道該怎麼帶她。我媽九歲的時候,她告訴我外婆她想要去跟爸爸一起住。外婆說:「如果這是妳想要的,那妳就去吧。」唐柏來接我媽,她快樂的跳進他的車裡,準備要跟她深愛的父親一起過日子。但是唐柏沒有載著她到梅朵蘭與他同住,他什麼都沒跟她解釋,就把她的行李打包,送去跟他住在科薩人黑人家園川斯凱的姊姊同住──他也不想要她。我媽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姊姊是老大,她弟弟是唯一的兒子,可以延續家族香火。他們兩個都留在索維托,由父母照顧帶大。但是我媽沒人要,她是排行老二的女兒,大概只有在中國,她的命運才有可能比在南非更慘。
我媽從此有十二年沒再與她家人見面。她跟十四個表兄弟姐妹住在一間小茅舍裡──這十四個表兄弟姐妹分別來自不同的母親跟父親,那些沒人要、或是沒人養得起的小孩就全被送到這個阿姨的農場裡。阿姨收留我媽不是在做慈善,她到那裡是去工作的。
「我是那裡的一頭母牛。」我媽後來曾這麼回憶。她和她的表兄弟姐妹早上四點半就起床,開始犁田、放牧牲畜直到太陽把土地烤得跟水泥一樣硬,熱到哪裡都去不了。
晚餐可能就只有一隻雞,卻要餵飽十四個小孩,我媽得要跟大孩子們奮戰才能搶到一手掌的肉或是一小口肉汁,或甚至只是一根骨頭把骨髓吸出來。而且這還是有食物的時候,沒有食物的時候,她就會去偷餵豬或狗的東西來吃。有些時候,她真的得吃土。她會去河邊,從岸邊拿一些泥土,加水攪拌成一種灰色的奶狀液體,就喝那個來裹腹。
但是我媽很幸運,有少數幾個教會學校不顧政府的教育政策設法辦學,這村裡的學校就是其一,在那裡她遇到一個白人牧師教她英文。她沒有食物或鞋子,甚至連一條內褲都沒有,但是她有英文,她會讀會寫。當她夠大的時候,她在附近城鎮的工廠裡找到工作,用縫紉機做學校制服,每天的薪資是一盤晚餐。
我媽二十一歲時,她阿姨生病,所以阿姨的家人無法再讓她留在川斯凱。我媽寫信給我外婆,叫她寄買火車票的錢過來讓她回家,大約三十蘭特。回到索維托之後,之後我媽去念了祕書訓練課程,這讓她得以抓住白領階級世界中最下層的一層階梯。她開始工作、工作又工作,但是住在我外婆的屋簷下,她不被允許保留自己的薪資,擔任祕書,我媽比任何人都賺更多錢,我外婆堅持那些錢都要留為家用。家裡需要收音機、烤箱、冰箱,現在是我媽的責任該把錢拿出來。
很多黑人家庭把他們的時間都花在解決過去的問題上,這就是身為黑人且一貧如洗的詛咒,並且這是個代代相傳的詛咒,我媽稱之為「黑人稅」。因為你之前好幾個世代的族人都被掠奪一空,你無法自由利用你的技能與教育往上爬,而是用盡一切資源只是設法把所有遠遠落後的族人拉到最低基準點。
我媽在索維托工作的收入都只是拿來養活她的家人,她並沒有比在川斯凱時自由,所以她決定離家出走。她一路跑到火車站,跳上火車,隱身於大城市中,下定決心,即使得睡在公共廁所,也在所不惜,她要在這個世界走出自己的路。
我媽從沒有坐下來從頭到尾跟我說她在川斯凱所經歷的一切,她只是偶爾沒來由的吐出一點。我媽告訴我這些事的用意,是讓我不會視我們的現狀為理所當然,她說這些事不是為了要自我憐憫,她總是說:「要從過去中學習,並因為你的過去而過得更好。」她會說:「但永遠不要為過去的事流淚,生命充滿了苦痛,讓這些苦痛鍛鍊你,但是不要執著於其上,不要憤世嫉俗。」
就如同她不計較過去,她也堅持決不重蹈覆轍──我的童年跟她的童年完全南轅北轍,從幫我取名字開始。科薩家庭幫他們孩子所取的名字通常都有含義,而那個含義到頭來也通常總是會自我應驗。我表哥叫馬朗紀,是「擺平者」的意思,每次我闖禍,他總是那個幫我善後的人。我舅舅是不小心懷孕生的,他被取名費里,意思是「不知從哪冒出的人」。我媽,派西雅‧諾邦絲‧諾亞,意思是「會回報的人」,她就是這樣的人,總是付出、付出,又付出。
她要幫我取名字的時候,她選了崔佛這個名字,一個在南非沒有任何含義的名字,在我家族裡從沒人取過的名字,它甚至不是個聖經裡的名字,就只是個名字。我媽希望她的孩子不用承受任何命運的安排,她希望我可以自由發展、做任何事、成為任何人。
她也給我可以幫助我自由發展的工具,她教我英文成為我的母語,她經常唸書給我聽,我第一本學會念的書就是聖經。我們大部分的書也都是從教會那邊取得的,我媽會把一箱箱白人捐獻的書帶回家──繪本、章節書,任何她可以弄到手的書。她還有去註冊加入一個郵寄書本的訂閱服務,那是一系列的工具書:《如何成為好朋友》、《如何誠實》那類的。她也買過一整套百科全書,雖然那套是十五年前出版的,資訊早就都過時了,但是我還是坐下來讀得津津有味。
如果說我媽有一個終極目標,那就是釋放我的心智。我媽把我當大人一樣跟我講話,這很少見。在南非,小孩跟小孩玩,大人跟大人講話。大人會監督你,但是他們不會降低他們的層級來跟你講話。我媽會,一天到晚。我就像她最好的朋友,她總是講故事給我聽、給我上課,尤其是講解聖經。她很喜歡詩經,所以我每天都得讀詩經,她也會考我詩經。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它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你如何將它運用到生活上?」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媽教了我學校沒教的事:她教我如何思考。
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是一件緩慢進行的事,它不像柏林圍牆倒塌,某一天就突然瓦解。種族隔離制度的城牆是年復一年逐漸裂開崩頹的,制度的鬆綁東一點西一點的發生,有些法令被廢止,有些則是不再施行。到了某個時間點,在曼德拉被釋放前的幾個月,我們就已經感覺漸漸可以活得光明正大一些。就在這個時候我媽決定我們應該搬家,她感覺我們已經藏身在我們的小公寓裡夠久了。
伊登公園是在東蘭德的一個有色人區,臨近好幾個黑人區。她想,那裡既是有色人區,又很接近黑人區,就像我們一樣,我們應該可以很容易混進去。雖然事實並不如想像,我們在那裡一直都格格不入,但至少當我們搬過去的時候,她是這樣認為的。並且那是一個買房子的機會──我們自己的房子。
我們搬去伊登公園之後終於有了一輛車,我媽用很低的價錢買來一台破爛、橘色的二手福斯汽車。五次裡面有一次它會發不動,它沒有空調,每次我不小心開到送風,那個風扇就會吹得我整身都是樹葉跟灰塵。它發不動的時候,我們就去搭小巴,或者有時候我們會搭別人的順風車。
我們的車會動的時候,我們會把窗戶搖下來,在烈陽炙烤下隨著引擎劈劈啪啪往前走。那輛車的收音機永遠只收聽一個電台,叫做廣播講壇,節目內容就如其名,是個佈道及讚美上帝的節目。我不被允許動那個電台旋鈕。每次收音機收不到訊號的時候,我媽就會放吉米.史華格的佈道卡帶。
但是不管那台車有多破爛,它終究是台車,它就是自由。我們不是被困在黑人區,等大眾交通工具的黑人,我們是在世界裡自由闖蕩的黑人,我們是每天起床後可以討論「我們今天要去哪裡?」的黑人。
如果我們不用上學、上班或上教會,我們就會出門探索。我媽的態度是「我選擇了你,孩子。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我要給你我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一切。」她全心貫注在我身上,她會找我們不用花錢就可以去的地方。我們一定去遍了約翰尼斯堡所有的公園,我媽會坐在樹下讀聖經,讓我跑去一直玩一直玩。星期天下午作完禮拜之後,我們會去鄉間兜風。
我媽會找有風景的地方讓我們坐下來野餐。我們沒有那些可以拿來炫耀的野餐籃或盤子之類的東西,只有用吸油紙包起來的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直到今日,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都還是會瞬間帶我回到從前。你可以給我所有米其林星等美食,但我只要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就會宛如置身天堂。
食物,或說買不買得起食物,通常可以看出我們的日子好不好過。我媽總是說:「我的工作是餵飽你的身體、你的精神、及你的心智。」而她也是這麼做,她存錢來買食物跟書,就是不花一毛錢在任何其他東西上,她節儉是出了名的。
我們總是穿二手衣,去二手商店買的,或是教會裡白人捐獻的。在學校裡其他小孩都有名牌衣物,耐吉和愛迪達那些,我從來沒有名牌。有一次我跟我媽要一雙愛迪達的運動鞋,她拿了一雙假貨回來,愛比達。
「媽,這雙是假冒的。」我說。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妳看這商標。這裡有四條線而不是三條線。」
「那你可真幸運,」她說:「你還比別人多了一條。」
雖然我們在家過得很清寒,但我從不覺得自己窮,因為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冒險。我們總是出門去玩,到處趴趴走。
我媽帶我去黑人從不會去的地方,她拒絕接受那些黑人不可以或不應該做什麼事的可笑說法。她會帶我去溜冰場溜冰,約翰尼斯堡以前有個超棒的露天電影院,超級巨星露天電影院,在城外一個巨大的廢礦堆頂端。她會帶我去那裡看電影,我們會買零食,把喇叭掛在車窗上。超級巨星有三百六十度的視野可以看到城裡、郊區、還有索維托,在那裡我往每個方向看都可以看到好幾英哩遠,我感覺好像自己在世界的頂點。
我媽拉拔我長大時,從不限制我可以去哪裡或做什麼,我現在回頭看才了解,她把我當成白人小孩在教養──不是教我白人文化,而是讓我相信這世界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可以為自己發言,我的想法跟決定是重要的。
我們常告訴人們要追隨他們的夢想,但是你只能嚮往你所能夠想像得到的事物,視你的家庭背景而定,你的想像力其實有可能非常侷限。在索維托長大,我們的夢想就只是幫我們的房子再多蓋一個房間;或許,蓋個車道;或許,有一天,在車道入口再蓋個鐵門,因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但是可能性的最高點,往往遠在你可以看到的世界之外,我媽讓我看到那個無限的可能。我對我媽的一生感到最佩服的是從沒有人為她指引迷津,從來都沒有人要她,她靠自己白手起家,她純粹是靠著自己堅強的意志走出一條路。
或許更讓我佩服的,是我媽開始這樣教養我的時候,她根本不知道種族隔離制度有天會結束,她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個制度會垮台,因為它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代。我快要六歲的時候,曼德拉被釋放,等到我十歲時民主制度才終於成立,但是她早在自由還不存在的時候,就教導我如何過著自由的生活。
我的生命選項中,最有可能的是在黑人區裡勞苦一生,或是被送去有色人孤兒院,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讓這兩個選項發生,我們永遠一直不斷往前走、一直不斷伺機而動、掌握先機。所以等到法律及人民終於覺醒過來的時候,我們早就已經領先了好幾英哩,開著我們亮橘色、破爛的福斯、搖下窗戶聽著吉米.史華格聲嘶力竭的耶穌盛讚,在高速公路上恣意疾行。
很多人認為我媽瘋了,溜冰場、露天電影院和郊區,這些都是izinto zabelungu──白人的玩意兒。有許多黑人早已內化種族隔離的邏輯,而對之深信不疑。為什麼要教一個黑人小孩白人的玩意兒呢?鄰居和親戚以前總是會這樣質疑我媽:「為什麼要教他這些?反正他永遠離不開黑人區,讓他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什麼用呢?」
「因為,」我媽總是這麼說:「即使他永遠離不開黑人區,他也會知道黑人區不是世界的全部。如果我到頭來只能讓他明白這點,我也心滿意足了。」
我媽曾跟我說:「我選擇生你是因為,我希望有個我可以愛也會無條件愛我的人。」她兩手皆空的長大,所以渴望一個屬於她的東西。
我外公外婆的婚姻並不美滿,他們在索菲雅鎮相遇並結婚,但是一年後軍隊入駐就把他們驅逐出城。政府奪走了他們的房子,把整個區域剷平,蓋了一個豪華、全新的白人郊區叫翠昂夫,就是勝利的意思。與其他命運相同的幾萬名黑人一起,我外公外婆被強制遷移到索維托,他們不久之後就離婚了。
我媽是個問題兒童,她像男人婆,固執又愛挑釁,我外婆不知道該怎麼帶她。我媽九歲的時候,她告訴我外婆她想要去跟爸爸一起住。外婆說:「如果這是妳想要的,那妳就去吧。」唐柏來接我媽,她快樂的跳進他的車裡,準備要跟她深愛的父親一起過日子。但是唐柏沒有載著她到梅朵蘭與他同住,他什麼都沒跟她解釋,就把她的行李打包,送去跟他住在科薩人黑人家園川斯凱的姊姊同住──他也不想要她。我媽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姊姊是老大,她弟弟是唯一的兒子,可以延續家族香火。他們兩個都留在索維托,由父母照顧帶大。但是我媽沒人要,她是排行老二的女兒,大概只有在中國,她的命運才有可能比在南非更慘。
我媽從此有十二年沒再與她家人見面。她跟十四個表兄弟姐妹住在一間小茅舍裡──這十四個表兄弟姐妹分別來自不同的母親跟父親,那些沒人要、或是沒人養得起的小孩就全被送到這個阿姨的農場裡。阿姨收留我媽不是在做慈善,她到那裡是去工作的。
「我是那裡的一頭母牛。」我媽後來曾這麼回憶。她和她的表兄弟姐妹早上四點半就起床,開始犁田、放牧牲畜直到太陽把土地烤得跟水泥一樣硬,熱到哪裡都去不了。
晚餐可能就只有一隻雞,卻要餵飽十四個小孩,我媽得要跟大孩子們奮戰才能搶到一手掌的肉或是一小口肉汁,或甚至只是一根骨頭把骨髓吸出來。而且這還是有食物的時候,沒有食物的時候,她就會去偷餵豬或狗的東西來吃。有些時候,她真的得吃土。她會去河邊,從岸邊拿一些泥土,加水攪拌成一種灰色的奶狀液體,就喝那個來裹腹。
但是我媽很幸運,有少數幾個教會學校不顧政府的教育政策設法辦學,這村裡的學校就是其一,在那裡她遇到一個白人牧師教她英文。她沒有食物或鞋子,甚至連一條內褲都沒有,但是她有英文,她會讀會寫。當她夠大的時候,她在附近城鎮的工廠裡找到工作,用縫紉機做學校制服,每天的薪資是一盤晚餐。
我媽二十一歲時,她阿姨生病,所以阿姨的家人無法再讓她留在川斯凱。我媽寫信給我外婆,叫她寄買火車票的錢過來讓她回家,大約三十蘭特。回到索維托之後,之後我媽去念了祕書訓練課程,這讓她得以抓住白領階級世界中最下層的一層階梯。她開始工作、工作又工作,但是住在我外婆的屋簷下,她不被允許保留自己的薪資,擔任祕書,我媽比任何人都賺更多錢,我外婆堅持那些錢都要留為家用。家裡需要收音機、烤箱、冰箱,現在是我媽的責任該把錢拿出來。
很多黑人家庭把他們的時間都花在解決過去的問題上,這就是身為黑人且一貧如洗的詛咒,並且這是個代代相傳的詛咒,我媽稱之為「黑人稅」。因為你之前好幾個世代的族人都被掠奪一空,你無法自由利用你的技能與教育往上爬,而是用盡一切資源只是設法把所有遠遠落後的族人拉到最低基準點。
我媽在索維托工作的收入都只是拿來養活她的家人,她並沒有比在川斯凱時自由,所以她決定離家出走。她一路跑到火車站,跳上火車,隱身於大城市中,下定決心,即使得睡在公共廁所,也在所不惜,她要在這個世界走出自己的路。
我媽從沒有坐下來從頭到尾跟我說她在川斯凱所經歷的一切,她只是偶爾沒來由的吐出一點。我媽告訴我這些事的用意,是讓我不會視我們的現狀為理所當然,她說這些事不是為了要自我憐憫,她總是說:「要從過去中學習,並因為你的過去而過得更好。」她會說:「但永遠不要為過去的事流淚,生命充滿了苦痛,讓這些苦痛鍛鍊你,但是不要執著於其上,不要憤世嫉俗。」
就如同她不計較過去,她也堅持決不重蹈覆轍──我的童年跟她的童年完全南轅北轍,從幫我取名字開始。科薩家庭幫他們孩子所取的名字通常都有含義,而那個含義到頭來也通常總是會自我應驗。我表哥叫馬朗紀,是「擺平者」的意思,每次我闖禍,他總是那個幫我善後的人。我舅舅是不小心懷孕生的,他被取名費里,意思是「不知從哪冒出的人」。我媽,派西雅‧諾邦絲‧諾亞,意思是「會回報的人」,她就是這樣的人,總是付出、付出,又付出。
她要幫我取名字的時候,她選了崔佛這個名字,一個在南非沒有任何含義的名字,在我家族裡從沒人取過的名字,它甚至不是個聖經裡的名字,就只是個名字。我媽希望她的孩子不用承受任何命運的安排,她希望我可以自由發展、做任何事、成為任何人。
她也給我可以幫助我自由發展的工具,她教我英文成為我的母語,她經常唸書給我聽,我第一本學會念的書就是聖經。我們大部分的書也都是從教會那邊取得的,我媽會把一箱箱白人捐獻的書帶回家──繪本、章節書,任何她可以弄到手的書。她還有去註冊加入一個郵寄書本的訂閱服務,那是一系列的工具書:《如何成為好朋友》、《如何誠實》那類的。她也買過一整套百科全書,雖然那套是十五年前出版的,資訊早就都過時了,但是我還是坐下來讀得津津有味。
如果說我媽有一個終極目標,那就是釋放我的心智。我媽把我當大人一樣跟我講話,這很少見。在南非,小孩跟小孩玩,大人跟大人講話。大人會監督你,但是他們不會降低他們的層級來跟你講話。我媽會,一天到晚。我就像她最好的朋友,她總是講故事給我聽、給我上課,尤其是講解聖經。她很喜歡詩經,所以我每天都得讀詩經,她也會考我詩經。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它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你如何將它運用到生活上?」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媽教了我學校沒教的事:她教我如何思考。
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是一件緩慢進行的事,它不像柏林圍牆倒塌,某一天就突然瓦解。種族隔離制度的城牆是年復一年逐漸裂開崩頹的,制度的鬆綁東一點西一點的發生,有些法令被廢止,有些則是不再施行。到了某個時間點,在曼德拉被釋放前的幾個月,我們就已經感覺漸漸可以活得光明正大一些。就在這個時候我媽決定我們應該搬家,她感覺我們已經藏身在我們的小公寓裡夠久了。
伊登公園是在東蘭德的一個有色人區,臨近好幾個黑人區。她想,那裡既是有色人區,又很接近黑人區,就像我們一樣,我們應該可以很容易混進去。雖然事實並不如想像,我們在那裡一直都格格不入,但至少當我們搬過去的時候,她是這樣認為的。並且那是一個買房子的機會──我們自己的房子。
我們搬去伊登公園之後終於有了一輛車,我媽用很低的價錢買來一台破爛、橘色的二手福斯汽車。五次裡面有一次它會發不動,它沒有空調,每次我不小心開到送風,那個風扇就會吹得我整身都是樹葉跟灰塵。它發不動的時候,我們就去搭小巴,或者有時候我們會搭別人的順風車。
我們的車會動的時候,我們會把窗戶搖下來,在烈陽炙烤下隨著引擎劈劈啪啪往前走。那輛車的收音機永遠只收聽一個電台,叫做廣播講壇,節目內容就如其名,是個佈道及讚美上帝的節目。我不被允許動那個電台旋鈕。每次收音機收不到訊號的時候,我媽就會放吉米.史華格的佈道卡帶。
但是不管那台車有多破爛,它終究是台車,它就是自由。我們不是被困在黑人區,等大眾交通工具的黑人,我們是在世界裡自由闖蕩的黑人,我們是每天起床後可以討論「我們今天要去哪裡?」的黑人。
如果我們不用上學、上班或上教會,我們就會出門探索。我媽的態度是「我選擇了你,孩子。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我要給你我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一切。」她全心貫注在我身上,她會找我們不用花錢就可以去的地方。我們一定去遍了約翰尼斯堡所有的公園,我媽會坐在樹下讀聖經,讓我跑去一直玩一直玩。星期天下午作完禮拜之後,我們會去鄉間兜風。
我媽會找有風景的地方讓我們坐下來野餐。我們沒有那些可以拿來炫耀的野餐籃或盤子之類的東西,只有用吸油紙包起來的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直到今日,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都還是會瞬間帶我回到從前。你可以給我所有米其林星等美食,但我只要香腸肉奶油黑麵包三明治,就會宛如置身天堂。
食物,或說買不買得起食物,通常可以看出我們的日子好不好過。我媽總是說:「我的工作是餵飽你的身體、你的精神、及你的心智。」而她也是這麼做,她存錢來買食物跟書,就是不花一毛錢在任何其他東西上,她節儉是出了名的。
我們總是穿二手衣,去二手商店買的,或是教會裡白人捐獻的。在學校裡其他小孩都有名牌衣物,耐吉和愛迪達那些,我從來沒有名牌。有一次我跟我媽要一雙愛迪達的運動鞋,她拿了一雙假貨回來,愛比達。
「媽,這雙是假冒的。」我說。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妳看這商標。這裡有四條線而不是三條線。」
「那你可真幸運,」她說:「你還比別人多了一條。」
雖然我們在家過得很清寒,但我從不覺得自己窮,因為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冒險。我們總是出門去玩,到處趴趴走。
我媽帶我去黑人從不會去的地方,她拒絕接受那些黑人不可以或不應該做什麼事的可笑說法。她會帶我去溜冰場溜冰,約翰尼斯堡以前有個超棒的露天電影院,超級巨星露天電影院,在城外一個巨大的廢礦堆頂端。她會帶我去那裡看電影,我們會買零食,把喇叭掛在車窗上。超級巨星有三百六十度的視野可以看到城裡、郊區、還有索維托,在那裡我往每個方向看都可以看到好幾英哩遠,我感覺好像自己在世界的頂點。
我媽拉拔我長大時,從不限制我可以去哪裡或做什麼,我現在回頭看才了解,她把我當成白人小孩在教養──不是教我白人文化,而是讓我相信這世界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可以為自己發言,我的想法跟決定是重要的。
我們常告訴人們要追隨他們的夢想,但是你只能嚮往你所能夠想像得到的事物,視你的家庭背景而定,你的想像力其實有可能非常侷限。在索維托長大,我們的夢想就只是幫我們的房子再多蓋一個房間;或許,蓋個車道;或許,有一天,在車道入口再蓋個鐵門,因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但是可能性的最高點,往往遠在你可以看到的世界之外,我媽讓我看到那個無限的可能。我對我媽的一生感到最佩服的是從沒有人為她指引迷津,從來都沒有人要她,她靠自己白手起家,她純粹是靠著自己堅強的意志走出一條路。
或許更讓我佩服的,是我媽開始這樣教養我的時候,她根本不知道種族隔離制度有天會結束,她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個制度會垮台,因為它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代。我快要六歲的時候,曼德拉被釋放,等到我十歲時民主制度才終於成立,但是她早在自由還不存在的時候,就教導我如何過著自由的生活。
我的生命選項中,最有可能的是在黑人區裡勞苦一生,或是被送去有色人孤兒院,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讓這兩個選項發生,我們永遠一直不斷往前走、一直不斷伺機而動、掌握先機。所以等到法律及人民終於覺醒過來的時候,我們早就已經領先了好幾英哩,開著我們亮橘色、破爛的福斯、搖下窗戶聽著吉米.史華格聲嘶力竭的耶穌盛讚,在高速公路上恣意疾行。
很多人認為我媽瘋了,溜冰場、露天電影院和郊區,這些都是izinto zabelungu──白人的玩意兒。有許多黑人早已內化種族隔離的邏輯,而對之深信不疑。為什麼要教一個黑人小孩白人的玩意兒呢?鄰居和親戚以前總是會這樣質疑我媽:「為什麼要教他這些?反正他永遠離不開黑人區,讓他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什麼用呢?」
「因為,」我媽總是這麼說:「即使他永遠離不開黑人區,他也會知道黑人區不是世界的全部。如果我到頭來只能讓他明白這點,我也心滿意足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