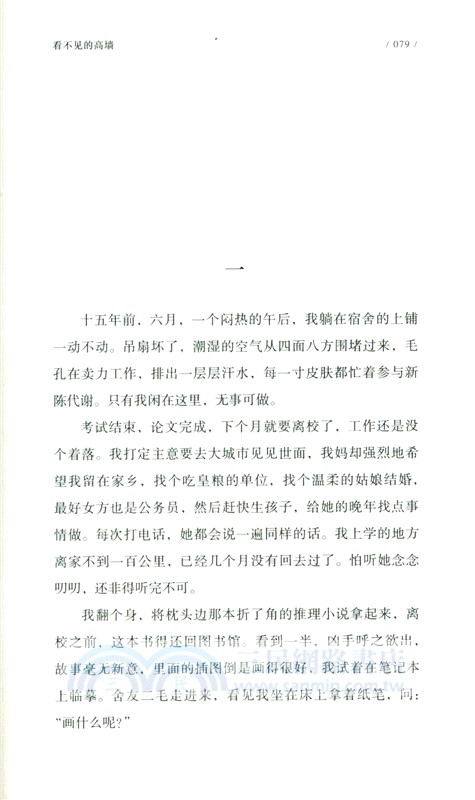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每個女人普通的情緒波動,都勝過一場戰爭!————2019年豆瓣年度圖書,月度熱門圖書新京報、澎湃、界面文化、新浪讀書、深港書評、豆瓣讀書、做書、商報、十點視頻推薦-當代中國女性的困境啟示錄生活的偶然和無序裡,總有些微不足道卻又不容忽視的東西《我要告訴我媽媽》:3架鋼琴,4個家庭,1個媽媽突然崩潰了《模特》:他的情人因車禍喪生的那天,他的妻子向他坦白了外遇 《看不見的高牆》:她太習慣獨自承受,連找他分擔秘密都只講一半《一個人的羅生門》:我是全職媽媽,也是小區女童失蹤案的唯一目擊證人《新婚之夜》:她放棄了抵抗,否認自己的感受,相信只要從心理上說服自己,她就不必被強姦-用5種都市日常,3個不同人生階段,抖出人生這條華麗被單裡的跳蚤關於生命中不得不經歷的種種馴服,以及那些失敗與反抗
作者簡介
遼京,小說作者,出版小說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長篇小說《晚婚》《白露春分》。
名人/編輯推薦
◆ 每個女人普通的情緒波動,都勝過一場戰爭!
21歲—37歲,糾結和迷茫奇多。戀愛難題、人際壓力、代際衝突、女性貧困、育兒煩惱、精神危機……
突然走到轉折點,必須自己做決定。你不是獨自一人,看似自由,實被規則、秘密和欲望束縛著。
◆ 遲來的講故事高手遼京,令中短篇故事也能承載命運感
有卡佛的儉省敘事,麥克尤恩的刁鑽視角,索爾‧貝婁的以小見大。遼京寫城市裡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試圖透過故事裡個人的境遇和選擇來表達整個社會的現實。
◆ 用5種都市日常,3個不同人生階段,抖出人生這條華麗被單裡的跳蚤
◆ 關照平凡生活,涉及的話題卻十分嚴肅:
《我要告訴我媽媽》:單親家庭;代際衝突;躁郁症
《模特》:婚內出軌;情欲炸彈;孤獨的根源
《看不見的高牆》:北漂的迷惘;階級壁壘;童年陰影
《一個人的羅生門》:全職媽媽;兒童安全;中年危機
《新婚之夜》:校園霸淩;婚內強姦;自我意識的覺醒
◆ 當大家都在轟隆隆地向前,遼京關心那些留在原地的人,疑問和自嘲
遼京擅長從生活中揪出故事的線頭,發現我們普通日子裡的重大時刻。在講述女性隱含悲劇的平常生活時,緊湊地展現女孩和女人們暗湧的內心、自我意識的覺醒。覺醒後的生活則充分留白,任讀者想像。
◆ 當代中國女性的困境啟示錄
21歲—37歲,糾結和迷茫奇多。戀愛難題、人際壓力、代際衝突、女性貧困、育兒煩惱、精神危機……
突然走到轉折點,必須自己做決定。你不是獨自一人,看似自由,實被規則、秘密和欲望束縛著。
◆ 遲來的講故事高手遼京,令中短篇故事也能承載命運感
有卡佛的儉省敘事,麥克尤恩的刁鑽視角,索爾‧貝婁的以小見大。遼京寫城市裡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試圖透過故事裡個人的境遇和選擇來表達整個社會的現實。
◆ 用5種都市日常,3個不同人生階段,抖出人生這條華麗被單裡的跳蚤
◆ 關照平凡生活,涉及的話題卻十分嚴肅:
《我要告訴我媽媽》:單親家庭;代際衝突;躁郁症
《模特》:婚內出軌;情欲炸彈;孤獨的根源
《看不見的高牆》:北漂的迷惘;階級壁壘;童年陰影
《一個人的羅生門》:全職媽媽;兒童安全;中年危機
《新婚之夜》:校園霸淩;婚內強姦;自我意識的覺醒
◆ 當大家都在轟隆隆地向前,遼京關心那些留在原地的人,疑問和自嘲
遼京擅長從生活中揪出故事的線頭,發現我們普通日子裡的重大時刻。在講述女性隱含悲劇的平常生活時,緊湊地展現女孩和女人們暗湧的內心、自我意識的覺醒。覺醒後的生活則充分留白,任讀者想像。
◆ 當代中國女性的困境啟示錄
目次
目錄
我要告訴我媽媽
模特
看不見的高牆
一個人的羅生門
新婚之夜
我要告訴我媽媽
模特
看不見的高牆
一個人的羅生門
新婚之夜
書摘/試閱
【《新婚之夜》精彩書摘】
婚慶公司做好了電子版的喜帖,傳過來。檢查無誤,再群發出去,看著郵件發送完畢的窗口陸續彈出,袁穎終於松了一口氣。一切準備就緒。她計劃辦一場小而精緻的婚禮,只請最親近的家人和朋友,羅翰的想法同她一樣。
“其餘的,等蜜月回來,請一頓飯就可以了。”他說。他和袁穎是高中同學,畢業後好幾年都沒有聯絡過,一次偶然的聚會上又遇見了。上學的時候,羅翰是班裡女生戀慕的對象,成績好,籃球打得好,長得也很帥,有人說他像流川楓,不過,他性格並沒有那麼冷淡,跟同學相處得不錯。他和他的幾個好朋友組成一個小圈子,核心人物是羅翰和一個名叫韓柳的女生,袁穎當然不在其中。有傳言說羅翰追過韓柳,被拒絕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戀愛之後,袁穎曾經問過羅翰,羅翰聽了就笑,說:“沒有,我把她當成兄弟。”
韓柳自然是要請的,袁穎心裡其實有點彆扭。在她的印象中,韓柳是那種受歡迎的漂亮女生,人也聰明機靈,無論在哪裡,做什麼,三言兩語就能贏得人心。大家都喜歡她,同時又免不了嫉妒。對於這種強勢而熱烈的風格給周圍人帶來的陰影,袁穎格外敏感,畢竟,她自己也是自命不凡的。當年,袁穎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所有老師都喜歡她,如果不是高考意外失利,可能她已經在北京的大醫院當醫生,而不是留在家鄉的縣城,做個小小的公務員。
無論如何,婚禮是一個女人的高光時刻,她希望以最好的狀態面對昔日的同學。羅翰出面邀請的這些人,沒一個是袁穎的朋友,確切地說,在整個高中階段,她就沒什麼朋友。伴娘雖然也是同班同學,其實是她的表妹,但即便是章玉,上學的時候也不怎麼和表姐一起玩。
“章玉跟你姑姑說,袁穎怎麼像個木頭人似的,都不跟我們一起玩?”有一次,袁穎的媽媽問她,她撇撇嘴,抱起書本回了自己的房間。“木頭人”三個字久久地在她心裡盤旋。她不明白,為什麼寫作文表達不清的表妹,諷刺別人倒是用詞精准。
說破天,也都是過去的事了。她結婚,伴娘是章玉,邀請的賓客中除了親戚,就是一些老同學。章玉跟她同歲,一路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同校,幾乎所有的來賓章玉都認識。當地有鬧伴娘的習俗,章玉機靈潑辣,擅長應對這種場面。除此之外,一切都西化了:教堂婚禮,冒泡的香檳,雞尾酒,長長的拖尾婚紗。羅翰的西裝是去上海找裁縫定制的。他媽媽說這套西裝又實惠又好看,比現成的大牌划算多了,只不過多花了兩程火車票錢。袁穎覺得他媽媽這話是說給她聽的,她選的婚紗是個外國牌子,就只穿一次的價值而言,貴得離譜。羅翰和她都是公務員,薪水不高,但是袁穎一眼就看上了這套婚紗,信用卡分期付款,買了下來。
戀愛很甜美,輕快得如同一場夢。羅翰向袁穎示好的時候,她還有點遲疑。羅翰跟她從來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長得帥,受歡迎,朋友眾多,而她自己不過是趴在角落裡只會死讀書的人。更可笑的是,她這麼用功,結果並沒有考好,第一志願差了三分,落在本地的一個三流大學,畢業後靠著家裡的關係,在老家做公務員,莫名其妙地,人就快三十歲了。
那次聚會,要不是章玉拖著,她也不會去。同學聚會最考驗人品,能忍住了,不在混得差的同學面前炫耀,需要深厚的涵養。袁穎想,我才不去給你們當下酒菜。可是章玉想去,非要拖著她一起。就在那天,羅翰主動送她回家,走了很久打不到車,兩個人一起走著走著,發覺已經到家了。小地方就是有這樣的好處,約會見面都很方便。第二天,袁穎加班,走出單位門口時,發現羅翰正在等她。
這樣的情景,如果發生在高中時期,袁穎想,韓柳和她那幾個狗腿子似的跟班女生會驚訝得合不上嘴,可惜,這些人都散了,如今各幹各的,不再關注羅翰喜歡誰。要辦婚禮了,袁穎決定把她們都請來,讓她們看看,當年的醜小鴨不僅變成了天鵝,還俘獲了王子。儘管羅翰這些年很少運動,發胖得厲害,和過去判若兩人,袁穎卻仍然覺得,嫁給他是自己充滿失敗的青春年華中,唯一可圈可點的勝利。光憑這,她就覺得,這場昂貴的婚禮辦得很值。
地點選在縣城郊外的一家木屋酒店,風格前衛,專做婚慶。雖然縣城地方小,人口也不多,仍有不少追求時髦的年輕人在這裡舉辦婚禮。玻璃教堂只是個空房子,神父是婚慶公司職員扮的,長袍的衣料嘶啦作響,起著靜電,說話拉著長音。
“我宣佈你們—”這種拿腔拿調,像是從古老的譯製片裡學來的,“結為夫妻。”
底下響起一陣掌聲。夫妻倆走下紅毯,幾位女賓站在兩邊,往新人頭上拋撒花瓣。韓柳也在其中,她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緊身連衣裙,露出兩條修長的小腿,化了濃妝,從籃子裡抓起一把鮮紅的玫瑰花瓣,往新人的臉上拋撒。袁穎低下頭,看見落紅如雨,細而尖的高跟鞋踩了過去。
婚宴在酒店的宴會廳舉行,兩邊的親戚朋友都是本地人,熱鬧一番過後,人漸漸散了。有幾個同學要留下來過夜,羅翰早跟他們說好,一定要陪著他跟袁穎住一晚再走。第二天,新婚夫婦就會從酒店出發去火車站,坐火車到上海,再飛往馬來西亞度蜜月。袁穎早早地訂好了機票,價格非常划算。
人都散了,袁穎回到房間。他們訂了一晚別墅,是酒店裡最寬敞的房型,上下兩層,四間臥室,除了他們夫妻二人,還有兩男兩女留下來。章玉一進來就挑了樓上風景最好的房間,窗戶對著一片濃綠的山谷,用她的話說:“你們都要出國旅行了,今晚就讓我享受一下吧。”
袁穎去一樓的房間裡換衣服,那身敬酒服外面綴滿亮片,很不舒服。她換上T 恤和牛仔褲,順便把自己和羅翰帶的兩套睡衣也拿了出來,坐在床邊的梳粧檯前開始卸妝。
門突然開了,韓柳探進頭:“能進來嗎?”
她進來後,把門關好,說:“客廳是冰涼的,雨下起來沒完。你屋裡好暖和。”
“小屋子比較暖和。”她說,“章玉屋裡估計也陰冷,窗戶那麼大。一會兒讓酒店的人過來調調溫度。”
“我剛才試過,空調好像壞了。”韓柳說,她脫掉了高跟鞋,穿著酒店的無紡布拖鞋,肩上披著一條毛茸茸的白色披肩,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雨幕。屋頂上,中央空調的出風口吹出暖風,發出嗡嗡的聲音。
“明天幾點的飛機?”她沒話找話說。
“下午四點。”袁穎用潤濕的化妝棉擦乾淨全臉,只剩下素顏。韓柳的臉也映在鏡子裡,妝容嬌豔,上學的時候,她就會化妝,自己用電發棒卷劉海,不穿校服的日子,就穿超短裙和非常貼身的牛仔褲,章玉對她崇拜得不得了。後來兩個人因為小事鬧掰了,章玉跟袁穎說過她不少壞話。
一對假睫毛扔在梳粧檯上,韓柳拿起來仔細研究。“一點也看不出來是假的,很自然呢。”她說。
“化妝師給的。”袁穎說。她摘掉了長長的眼睫毛,妝也擦掉了,眼睛一下子顯得小而無神,臉色也發黃,頭天晚上因為怕睡過頭,她幾乎整夜清醒。車隊六點就出發來接人,在那之前她得化好妝準備著。
有人敲門,章玉來了,她也喊冷,已經打電話給前臺。羅翰和另外兩個留下來的朋友—趙智和李浩成在外面的
門廊下抽煙聊天,從袁穎的房間裡,可以聽見他們低低的說笑聲。
“這酒店的環境真不錯,是新建的?”韓柳放下兩條睫毛,挨著章玉坐在床上。她在上海工作,只有過年才回來,對家鄉的變化很陌生。
“前年就有了。”袁穎說。幾個男人在門廊下發出一陣哄笑,就在窗戶邊上。“生意特別好,提前半年才訂得上,別墅只有兩間。”
“感覺不到這兒有人。”章玉說,“房間太分散了,顯得很冷清,其實都住滿了。”向窗外望去,細雨中,一座座小木屋散落在山谷的斜坡上,樹木掩映間,露出棕色的尖頂,濕漉漉的。
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章玉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有妖怪路過。”大家都笑了起來。
男生們抽完煙,回到客廳,燒水煮茶,叫她們都出來喝點熱的。趙智從自己的背包裡翻出一包普洱茶,從雲南帶來的。他是一名旅遊雜誌的攝影記者,說起自己的工作,大家聽著就很羡慕。
“到處玩,還能賺錢,太幸福了吧。”章玉捧著一小杯濃茶,坐在寬大的飄窗上。茶具也是酒店提供的,款式很古典,是不值錢的樣子貨。
“根本不是玩,”趙智說,又遞了一杯給韓柳,“每次一休假,就想宅在家裡,哪兒也不去。”
“你家還住原來的老房子?”韓柳問道。袁穎坐在沙發旁的腳凳上,覺得杯子裡的茶冷得特別快,指尖也凍得冰涼。酒店什麼時候派人來修空調?只有一個房間的出風口正常工作。
“沒有,早搬走了。”趙智說,“我爸去世後,我媽想換個地方住,就把老房子賣了,在新區換了一套大的。”他說的新區,是指縣城北邊的那片樓盤,房子設計得好,價格比老城區低,很多人在那裡買房子。
“換作我,我也想搬。”章玉說,“太不吉利了。”
“又有妖怪經過。”這次,是李浩成打破了沉默,他是個大塊頭的男生,在學校時,經常跟羅翰一起打籃球。他說:“我聽見有人敲門。”說著,就起身去大門。果然,面帶微笑的服務員帶著一個穿藍色制服的年輕維修工走了進來,很快,出風口修好了,熱風呼呼地吹了出來。
為了表示歉意,服務員送來一盤水果,章玉順手拿起一隻蘋果啃著。
“你非得提這個。”韓柳說,“能不能別提這麼晦氣的事。”
“這有什麼。”章玉說,“人誰無死呢。”她一邊嚼著蘋果,一邊繼續說,“屍體就在,好像就在這附近被發現的,對吧?當年還上了報紙。”
她指的是這片山谷。建酒店之前,這裡曾是荒山野嶺,密林遮天蔽日,是個自殺的好地方。
“好像是吧。”李浩成接過話頭,“真是,一晃都這麼多年了。她媽媽還沒搬走?”
“沒有。”趙智說,“上次回來過年,聽我媽說,崔淩媽媽一直住在那兒,就一個人住。”
“她的病好了沒有?”李浩成問。
“那種病怎麼可能好。”趙智說,“反正從我記事起,鄰居都說她是精神病。崔淩死後,她又做過幾份工作,沒一份做得長。”
“有這種媽媽,崔淩也真可憐。”韓柳說,屋裡漸漸地暖和起來,她摘掉了披肩,丟在沙發的硬木扶手上。她沉思著,說:“沒錯,就在這片山裡。被人發現的時候,已經好幾天了。”
“所以,我們換個話題吧。”羅翰說。燒水壺又一次沸騰,趙智把開水倒進小巧的泡茶壺,用壺蓋悶住。
“說說你們倆。”韓柳換了一種戲謔的語氣,“你們倆是怎麼搞到一起去的?”
袁穎和羅翰相視一笑。“說來話長。”羅翰說,“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她,從上學的時候開始。”屋裡響起一陣低低的驚呼。
“我怎麼不知道!”韓柳佯怒,“真的嗎?”
“應該是吧。”袁穎說,她的手沒來由地哆嗦了一下,“不過,我倆那時候並不太熟。”
“是真的。”羅翰看著袁穎,看見她的臉漸漸漲紅了,“不過她那時候總和崔淩在一起,不跟我們玩。”不知為什麼,有關崔淩的話題再度逼近,像一隻禿鷹在空中緩慢盤旋,覬覦著食物。
“你們那時候管我倆叫什麼?我可記著呢。”袁穎的語氣很輕鬆,像開玩笑。
“雙塔。哈哈,對吧?你們倆都是又高又壯。”李浩成說,羅翰有些不自然地看了他一眼。
“對不起,對不起,”李浩成誇張地道歉,道歉也是在開玩笑,“都是鬧著玩兒的。”
“就你叫得最歡。”韓柳說,“不過,崔淩好像不喜歡這個外號。”
沒人喜歡,袁穎心裡想,沒有說出口。她拿起一杯溫暾的茶水,一口氣喝光,把茶杯放回黑沉沉的檀木茶盤上。
“是啊,為了這個,她還跟趙智吵過架。”
“我叫她黑鐵塔,她差點撲過來打我。”趙智說,“我從小就認識她,她性格怪異,多半是她媽媽的遺傳。精神病嘛,多少有點影響。”
“就算沒有遺傳,從小跟著瘋子一起生活,性格一定不正常的。”韓柳說,說著還瞥了袁穎一眼,見她垂著眼睛,面色如常,便收住了話頭。
羅翰搖搖頭:“她的成績那麼好,肯定不是瘋,只是我們那時候太小了,誰也不瞭解誰。”
“確實有那麼一種人,”李浩成插嘴進來,“雖然有一點瘋病的基因,但是頭腦卻很聰明。你們記得吧?物理老師最喜歡她,說她腦袋靈活。”
“那時候,章玉在班裡到處跟人說,崔淩暗戀物理老師。”韓柳說,有些不懷好意地看了章玉一眼。
“拜託,明明是你告訴我的。”章玉說,“你說你看見崔淩去物理老師的辦公室,然後哭著出來。”
“表白被拒絕?”趙智說。這傢伙和過去一樣嘴巴碎、愛八卦,當個狗仔或許更適合他,袁穎想著。她說:“才不是呢。你怎麼會這麼想?”
“很自然啊,表白被拒絕,然後哭了一頓。”趙智說,“難道另有隱情?”
羅翰說:“為什麼要談她呢?大喜的日子,多晦氣。”窗外的雨絲變得密集起來,簌簌敲打著寬大的飄窗。山谷一片靜寂。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韓柳問袁穎。
“很簡單,她那次沒考好。”袁穎說,“她壓力很大,必須得考上大學,如果考不上,她爸爸就會斷掉她的撫養費,教育費也不會再給,她連複讀的機會都沒有。”
章玉又拿起一隻蘋果,婚宴上她沒怎麼吃東西。
羅翰提議讓酒店送餐過來,袁穎也餓了,他們點了三份套餐,加上點心和咖啡,不久就送來了。
“這兒的咖啡還不錯呢。”韓柳說,“我在上海租的房子樓下,有一家特別好的咖啡館,只做外賣,每天下班路過,我都要買一杯帶回家。”
“一個人住,多麼自由啊。”章玉感歎道,“我要是不結婚,我媽絕不會讓我一個人出來租房子。”
“我養了一隻貓做伴,不然太冷清了。”
“我看到了,你整天曬貓的照片。”
袁穎正在吃那份白切雞飯,雞骨頭是嫩粉紅色的,似乎沒熟透,被她撥到盤子的一邊。她邊吃邊說:“我記得你從前很討厭貓。”
“人會變的嘛。”韓柳說,“那只貓,是我前男友留下的。人走了,貓還在,挺諷刺的,有時候男人還不如一隻寵物。”
韓柳的前男友,袁穎從羅翰那裡聽說過,是她從前公司的同事。一開始轟轟烈烈,沒多久兩個人就住在一起了。甜蜜了幾個月,後來男生主動承認自己移情別戀,要求分手,甩得韓柳措手不及。分開沒多久,韓柳就跳槽離開了那家公司。這段戀情大概是她有生以來遭遇過的最大失敗。
袁穎把剩下的米飯和鹵蛋都給了羅翰,羅翰很自然地接過去。韓柳笑著說:“不要在單身狗面前秀恩愛,真受不了。”
羅翰吃掉了鹵蛋的蛋清,剝出完整的蛋黃還給袁穎,這下連章玉也在抱怨:“你們是故意的吧,辣眼睛。”
“你們真的是,”趙智終於不再沏茶,身體向後靠在沙發上,“高中時候就互相有意思?”
“他說他是,”袁穎笑著說,“不過我沒感覺到,他不怎麼跟我說話。”章玉低低地笑了起來,看看韓柳,又看看夫妻二人,笑聲中別有含義。韓柳的臉上微微地泛紅。
“那時候大家都互相喜歡,一會兒就換一個喜歡的對象。”章玉說,“很多人悄悄約會,你們還記得學校旁邊那個甜品店嗎?老闆娘長得像容嬤嬤的。”
“記得。”袁穎很快地搭腔,“我跟崔淩經常一起去,她喜歡那裡的燒仙草,每次去,她總是加雙份的煉乳。”
“所以她長得那麼胖,”章玉用雙手拱出一個圈,比畫崔淩的身材,“還吃個不停。”
“她壓力很大。”袁穎輕輕地說,“吃燒仙草的時候,她最開心。”
“你是怎麼跟她相處的?”趙智突兀地問道,“你不覺得,她有點奇怪嗎?”
“是有一點,但是她人很善良。”袁穎站起身來,穿著輕薄的紅緞鞋踩在地板上,有種輕盈涼爽的觸覺。雨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她走到窗前,窗外是陰沉、潮濕、鮮綠的一大片,一整塊,度過漫長的陰雨季節,夏天就要來了。
“她沒什麼朋友,”袁穎繼續說,背對著他們,“我算一個。趙智也算?你跟她從小就認識。”
“小學以後我就不跟她玩了,”趙智說,“我媽不讓。她媽媽犯過兩次病,整棟樓都知道。”
“那你真是錯過了,她很有趣,”袁穎說,“沒想到她會走到那一步。”
“所以說,這就是瘋子的基因。”李浩成說,在場的所有人中,他始終游離在有關崔淩的話題之外。旁觀者的論斷往往是清晰明瞭、毫無疑義的。可惜啊,袁穎想,曲折的事實並不能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
“有一段時間,崔淩總是提起你。”袁穎說。李浩成面露驚訝:“她說我什麼?”
章玉發出咯咯的笑聲,一邊笑一邊說:“原來有這麼多八卦,我都不知道。”
“你經常抄她的物理作業,還請她吃燒仙草,後來文理科分班,你選了文科班,就不理她了。”
“抄她作業的又不止我一個。”李浩成說,“羅翰也抄過,對吧?”
“你們倆上物理課的時候,老是偷看漫畫書。”章玉說,“想起來了,崔淩是物理課代表,負責收作業。”
“結果她還是沒什麼朋友,除了袁穎。”章玉說,“她以為抄作業就能換來交情?”
“你非得這麼刻薄嗎?”袁穎輕輕地說,她不確定自己真的說出口了,也許只是在心裡打了個滾,變成一道輕輕的哈氣,白濛濛地浮在玻璃窗上。
“怎麼又冷起來了?”韓柳抱怨著,重新裹緊她的毛披肩。
中央空調的出風口再次安靜下來,不再呼呼作響。李浩成說:“她沒什麼零花錢,我請她喝個飲料,她就給我抄作業,然後,羅翰再抄我的。”
“有時候,你們連抄都抄錯。”韓柳說,“咱們班的學風真是一團糟。”
“崔淩要是活著,她一定能考上大學吧。”趙智說,“不過,以她那樣的性格,走到哪裡都不會吃得開,說話磕磕巴巴的,還經常莫名其妙地發呆。”
袁穎覺得這句話描述的倒像是自己,走到哪裡都吃不開。的確,崔淩平常話不多,尤其是面對男生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緊張。並不是因為她喜歡誰,而是一種對異性的整體恐懼,或許與她的家庭背景有關。袁穎將雙臂抱在胸前,覺得房間確實在一點點地變冷。
前臺電話沒人接,又打一遍,還是沒人接。他們把所有臥室的暖風都打開了,再打開門,希望能渡來一些溫暖。趙智重新燒起水來,換了新茶葉。午後陰冷而漫長。
“我只想喝點熱水。”韓柳說,“到底能不能換個輕鬆的話題?”崔淩的屍體在附近被發現時,已經好幾天了,現場的照片毫無遮掩地登在報紙上。
“我和她一起去吃燒仙草,她跟我說,你曾經帶她來過。”袁穎對李浩成說,“她以為你們算是朋友,結果你轉到文科班,就再也不搭理她了。”
李浩成勉強地笑笑,袁穎的話讓他覺得不舒服:“她借我作業,我就給她買個飲料或者別的什麼吃的,反正她嘴饞,又沒有零花錢。說是朋友也行,但是她實在太無聊了,跟她聊天,她連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她小時候不是這樣。”趙智說,“不過,自從她媽媽的瘋病發作過兩次之後,全樓的小孩都不跟她玩,她就越來越孤僻。可憐歸可憐,也怪不得別人啊。”
“不過,她有什麼理由自殺呢?”章玉說,“這麼多年過去,我還是想不明白。”
韓柳半天都沒說話,忽然有些不耐煩了,她說:“崔淩精神有問題,當年報紙上都這麼說嘛。考前壓力過大,有精神失常的徵兆,深夜從家中出走,過幾天屍體被發現在西郊的山林裡。瘋子根本就沒有理智。”
“她不是瘋子,”袁穎說,“我確定。我和她做了三年同桌。她確實性格內向,但絕不是瘋子。”
“瘋不瘋有什麼區別?反正她死了。”韓柳說,用叉子紮向盤子裡的黑森林蛋糕。當時,崔淩的自殺在學校裡引起了一陣短暫的議論,不過很快就平息了,大家都要面對高考,沒空為一個不太熟的同學悲傷太久,況且那也不是什麼真正的同情,而是驚訝,是好奇,是課間的八卦話題,熱鬧一陣就過去了。畢竟,崔淩是那麼孤僻的人,沒什麼朋友,只有袁穎,但是袁穎和她差不多,都是班裡的透明人。
所以,韓柳還是覺得奇怪,問羅翰:“上學的時候你就喜歡袁穎?我怎麼沒看出來。”
“暗戀。” 章玉在一旁替羅翰回答,“就像崔淩暗戀他一樣。”
“真是夠了。”韓柳盯著章玉,“你為什麼要跟一個死人過不去?”
“大家都知道啊,還拿這個事情取笑羅翰。”章玉說,抱起了雙臂取暖,“羅翰怎麼說來著?就那次,自習課上,大家都在,崔淩找羅翰借一本漫畫書,羅翰說沒有。”
“她根本不愛看漫畫。”羅翰說。他似乎想為自己辯解什麼,卻也沒什麼好辯的,不過是個傻乎乎的女生而已。
袁穎再次低下頭,水壺咕嘟起來,再一次接近沸騰。
“你還說崔淩身上有貓味兒,”章玉說,這句話是對著韓柳說的,“很大聲,我記得。”
“貓屎味兒。”韓柳面不改色。袁穎抬起頭看看她,又看看羅翰,羅翰胖了不少,不是當初的翩翩少年了。
“我記得,那時候你很討厭貓。”羅翰說。
“問題不在於貓。”袁穎說,她換了個姿勢,把一條腿蹺到另一條腿上面。韓柳放下了手裡的小茶杯。
“討厭一個人,就跟喜歡一個人一樣,”袁穎說,“不需要什麼理由吧。”
趙智說:“她家的貓養了好多年,是我見過的最大的貓,像只小獅子。”
“其實,”羅翰開口了,“崔淩是個很敏感的人,可能那時候我們都太幼稚,沒有人懂她,我也不懂,她表白的方式太奇怪了。”
袁穎微微笑著,聽著他試圖為自己開脫。人就是這樣,終其一生都在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解釋,否則簡直沒辦法活
下去。
李浩成輕輕地吹了聲口哨。
“她跟我借漫畫書那天,我沒借給她,是因為那本正好沒有。你們都以為我在敷衍?是真的沒有,最新的一本,我還沒買呢。第二天放學,我去跑步,跑完天都黑了,她就一直在操場邊上轉來轉去。”羅翰說著,給自己倒了一杯茶。他身子前傾,肚子上出現幾道肉堆的褶紋,他大概有七八年不怎麼運動了。
“她在操場邊上,一會兒坐,一會兒站,只有我一個人在一圈圈地跑,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我恨不得一輩子就這麼跑下去,不要停下來。她怎麼也不肯走。”
“哈哈,有點恐怖啊。”韓柳說,“你居然沒跟我提起過。”
“等我跑完了,準備拿書包回家,她就走過來,把一本漫畫塞到我手裡,就是她想跟我借的那本。我想她是從學校北門邊上那家小書店買來的,每期到了,老闆會給我留一本。我就告訴她我不需要,她非送不可,說到最後,我都懶得解釋了。”
“也許她在書裡夾了些什麼,情書一類的。”韓柳說,“你應該接過來看看。然後呢?”
“後來她走了,把書放在臺階上,這人真怪。”羅翰說,“她好像不知道人與人應該怎麼交往。”
“那個年紀,其實沒人知道。”袁穎說,“大家都很粗魯。”
“一般人不會像她那樣。”章玉小聲地說,“書裡有夾著情書嗎?”
“沒有。”羅翰說,“什麼也沒有。”
“看來你還真的去找了。”韓柳笑道,“幸虧沒有。不知道她會寫出什麼奇怪的東西。你們還記得語文老師念她的作文嗎?反面例子,零分。”
我記得,袁穎想。又一次,她克制住自己,沒有說出口。
“我記得。”趙智說,“她寫的是她媽媽,全程只有一個句式:我媽媽喜歡如何如何,她喜歡吃什麼,喜歡穿什麼,喜歡看什麼電視節目,最後說,我媽媽最喜歡的人就是她自己,念完大家都在笑。”
“語文老師不喜歡她,她上課總是打瞌睡。”李浩成說,“有一次發脾氣,差點把她趕出教室,她都睡得打起呼嚕了。”
剛才那位服務員又來了,帶著另一個維修工,看起來比剛才那位更年長,更有經驗。對話停止了,大家靜靜地等著空調恢復工作。
最終,維修工從出風口的管道裡面掏到一隻肥大的死老鼠,已經開始腐爛了,但仍舊很肥大。章玉噁心地捂住了口鼻,韓柳只看了一眼,就趕緊轉過臉去—它被托在維修工人的塑膠手套上,眼睛睜著,眼球向外鼓。
“山裡的環境就是這樣,小動物很多。”服務員帶著歉意,微微鞠躬。酒店的員工都是從本地招聘來的,受過專業的服務培訓,一舉一動合乎標準,等她走了,大家重新放鬆下來。
“噁心死了。”章玉說,“不知道別的地方有沒有老鼠?”今天晚上,她和韓柳一人占一間臥室,另外兩個男生擠一間。
“半夜爬到你床上。”李浩成用手指模仿老鼠爪子,章玉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
韓柳起身,去了衛生間,出來後,妝容煥然一新,嘴唇重新塗得紅紅的。雨聲敲著屋頂,依舊輕細綿密。
“崔淩喜歡羅翰,”袁穎說,“全班都猜著了,結果羅翰居然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所以說,被暗戀和被出軌一樣,主角都是最後才恍然大悟。”趙智說,“你當時有沒有覺得很驚悚?被那樣一個女生惦記著。”
“那倒沒有。”羅翰看了袁穎一眼,她的樣子跟高中時相比,幾乎一點沒變,只是瘦了些。那時候,她跟崔淩幾乎形影不離。兩個人都沒有別的朋友。
“後來呢?”韓柳問,她對羅翰和崔淩的這段往事來了興趣,“後來她又找過你嗎?”
“沒有。”羅翰簡短地回答,“不過有一次,就在她出事前不久,有一次收物理作業,我沒寫完,她來催我交作業,語氣很生硬,我跟她吵了幾句。”
“你罵她是黑鐵塔,蠢貨。”袁穎說,“她都告訴我了。”
羅翰的臉有點發紅,趙智打圓場說:“那時候大家說話都很隨便。反正崔淩也無所謂,她本來就有點傻。”
“她找我哭了一場。”袁穎說,“就在那間甜品店裡,她連燒仙草都沒吃完。”
“為什麼?”章玉剛才兩眼空空地發呆,若有所思的樣子,此刻終於回過神來。
“因為羅翰罵她啊。”李浩成說,“你還想吃蘋果嗎?”盤子裡的蘋果只剩下一個了,章玉搖搖頭。
“沒人想吃蘋果嗎?”沒人回應,李浩成拿起蘋果啃了一口,只一口,就咬出一條淡黃色的肉蟲。
他把果肉啐了出來,肉蟲爬到他咬出的缺口上,被他連著整個蘋果一道丟進垃圾桶。
“你不喜歡她,也不用這麼罵她吧?”章玉說。
“那有什麼?說她笨的又不是羅翰一個。語文老師也說她腦袋像個木魚。”
袁穎把李浩成用過的水果刀輕輕放回盤子裡,發出清脆的微響。
韓柳說:“語文老師最愛批評的就是崔淩,她的作文寫得太差勁。”
“她很聰明。”袁穎開口了,“崔淩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女生,她想報理論物理專業。”
“她有瘋子的基因,”趙智說,“這種人今天想東,明天想西,前一天還活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跑去自殺。”
“說起來,她出事之前,曾經問過我,要不要養貓。”章玉說,“她是不是已經問過你,被拒絕了?”
袁穎點點頭:“我父母不喜歡貓,我要離家上大學,沒人照顧。”
“怪不得,”趙智說,“她也問過我。我告訴她,我們家不養那玩意兒。沒過兩天,那只貓被吊死在陽臺上,她家在二樓,下面路過的人都能看見。”
“她媽媽幹的。”袁穎很快地說,“她媽媽失眠,夜裡貓總在跑來跑去,崔淩跟我講,那天早上她一醒來,就看見貓在陽臺上蕩悠。”
“然後她自己也選擇了這種死法?”章玉說,打了個寒戰。
“等等,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李浩成忽然插嘴進來。剛才他在專注地削一隻梨,確定沒有果蟲之後,才放進嘴裡,咬下一口。
“春天,天天下雨。”趙智說,“那只貓都快要爛了,才被解下來丟掉。聽說是崔淩的爸爸來處理了屍體,她們母女倆都不管,像是有意賭氣,報復彼此。”
“她嚇壞了。”袁穎說,“我要是幫她養幾天,也許就沒事了。那只貓在她家十幾年,陪著崔淩長大。”
“有人覺得太熱了嗎?”韓柳站起來,去把窗戶拉開一道縫,讓外面陰涼的空氣吹進來,緩解暖風帶來的焦躁感。
“自殺是她自己的事。”趙智突然開口,好像是為了驅趕那只盤旋的禿鷹,憑空放了一槍。
“因為一次模擬考試沒考好就跑去自殺,這種人到了社會上也不會順利的。”韓柳說,“再叫杯咖啡吧,好嗎?我有點瞌睡。”
“所以,韓柳說崔淩身上有貓屎味兒的時候,那只貓已經死了幾個月了?”李浩成說。
“我早說過了,這不是貓的問題。”袁穎看了一眼羅翰。
羅翰有些尷尬地動了動身體,韓柳微笑著,不答言。章玉跟韓柳有過矛盾,此刻趁勢跟上一句:“我就說嘛,韓柳一定喜歡羅翰的。”
“我討厭崔淩,不是因為羅翰。”韓柳說,“你不要這麼膚淺,以為什麼都是因為男人?”
“像她那樣的人,招人喜歡才不正常呢。”她繼續說,“長得醜,胖得像頭豬,跟她說話,她總是發愣,除了物理成績好,其餘都一塌糊塗,笨得要命。你們不覺得,她跟我們一點都不像嗎?”
“關於她,最有發言權的是袁穎。”李浩成說,“她們倆好得跟一個人似的。”
“我一直想不通羅翰為什麼要罵她。你明知道她喜歡你啊。”袁穎說。
羅翰給她倒了茶,袁穎接過來,心想:他一定以為自己喝多了酒,胡言亂語。
“無論是誰,被崔淩那樣的人盯著,都很噁心吧。”韓柳說,“羅翰一定很煩她。”
“罵就罵唄,”李浩成說,“說她兩句也不算什麼。有一次她向我借語文課的筆記,還回來的時候,邊角都給折了,我很生氣,也說了她幾句。”
“你說她是笨豬。”袁穎說,“看書折頁是她的習慣,確實是個壞習慣,但是罵人笨豬有點過分吧。”
“這麼說,我也想起來了,她所有的本子都有折角,人也很邋遢。她好像完全沒有家教的,她媽媽不會教她的嗎?連鞋帶都系不好,老是耷拉著拖地,隨時會絆倒。”
袁穎笑了:“這倒是, 每回上體育課, 我都要幫她系鞋帶。”
“說起來,崔淩真是無處不在啊。”李浩成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盒煙,韓柳跟他要了一根,點了起來。
“討厭的人都很有存在感。”章玉說,“我還記得,有一次她穿了一身舊衣服來上學,像那種鹹菜的顏色,非常難看,像是她奶奶的衣服。”這話是對著袁穎說的。
“那是她媽媽的,她奶奶早去世了。”
韓柳吐出一口煙:“所以啊,自殺一定是她自己的問題。你知道為什麼嗎,袁穎?”
袁穎搖搖頭,羅翰說:“我不明白你怎麼會跟她成為好朋友。”
“那,如果不是因為羅翰,那是為什麼呢?”袁穎問韓柳,“你為什麼要那樣對她?”
“哪樣?”韓柳停止了吸煙的動作。木屋別墅裡禁止煙火。
“就是從那天開始,從崔淩被羅翰罵的那天開始,班裡的人忽然都不理崔淩了。你們似乎形成了一種默契,不管崔淩跟哪個人說話,收物理作業或者是別的什麼事,一律裝作聽不懂,然後哈哈大笑。”
“這是一個玩笑。”趙智說。當然,他也參與了這個玩笑,大概持續了一周。一周之後,所有人都覺得沒意思了。他們不再無緣無故地傻笑,崔淩反倒不適應了,她悄悄地問袁穎:“他們為什麼不笑了?”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笑夠了吧。他們為什麼笑你?”
“他們為什麼笑我?”崔淩反問,袁穎啞口無言。
“那時候大家壓力都很大,”章玉說,“傻樂一下也挺開心。再說她也不在乎嘛。”
羅翰說:“十幾歲的人就是很莽撞,這也沒啥。”
“全班都笑瘋了。”韓柳說,“崔淩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就一臉傻樣地愣在那兒。”
“喜歡一個男生而已,” 袁穎輕輕地歎道,“這有什麼錯呢?”
“沒人說她錯。”李浩成的語氣裡帶著勸慰,“我們只是覺得,她呆愣愣的樣子很好玩。”
“她活著就是個樂子。”章玉說,似乎帶著一絲惋惜之意,“如果我喜歡的男生那樣罵我,估計我也會想死了算了。”
“你才不會去死呢。”趙智說,“你不是那種人。”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章玉笑著反駁他,“據說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上百次想自殺的念頭,雜誌上說的。”
咖啡送來了,六杯,熱騰騰的,上面浮著細密的奶泡。雨已經停了,服務員沒有打傘,彎腰放下託盤,她有些年紀了,盤起來的頭髮裡面雜著幾莖銀白。天色仍舊陰沉。
“來,”趙智提議,“為活著乾杯。”大家都笑了,章玉蜷起腿來,她坐在一隻寬大的籐椅上,人縮成一團。
杯子們彼此相撞,然後陸續放下,咖啡嫋嫋地冒著白汽。
婚慶公司做好了電子版的喜帖,傳過來。檢查無誤,再群發出去,看著郵件發送完畢的窗口陸續彈出,袁穎終於松了一口氣。一切準備就緒。她計劃辦一場小而精緻的婚禮,只請最親近的家人和朋友,羅翰的想法同她一樣。
“其餘的,等蜜月回來,請一頓飯就可以了。”他說。他和袁穎是高中同學,畢業後好幾年都沒有聯絡過,一次偶然的聚會上又遇見了。上學的時候,羅翰是班裡女生戀慕的對象,成績好,籃球打得好,長得也很帥,有人說他像流川楓,不過,他性格並沒有那麼冷淡,跟同學相處得不錯。他和他的幾個好朋友組成一個小圈子,核心人物是羅翰和一個名叫韓柳的女生,袁穎當然不在其中。有傳言說羅翰追過韓柳,被拒絕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戀愛之後,袁穎曾經問過羅翰,羅翰聽了就笑,說:“沒有,我把她當成兄弟。”
韓柳自然是要請的,袁穎心裡其實有點彆扭。在她的印象中,韓柳是那種受歡迎的漂亮女生,人也聰明機靈,無論在哪裡,做什麼,三言兩語就能贏得人心。大家都喜歡她,同時又免不了嫉妒。對於這種強勢而熱烈的風格給周圍人帶來的陰影,袁穎格外敏感,畢竟,她自己也是自命不凡的。當年,袁穎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所有老師都喜歡她,如果不是高考意外失利,可能她已經在北京的大醫院當醫生,而不是留在家鄉的縣城,做個小小的公務員。
無論如何,婚禮是一個女人的高光時刻,她希望以最好的狀態面對昔日的同學。羅翰出面邀請的這些人,沒一個是袁穎的朋友,確切地說,在整個高中階段,她就沒什麼朋友。伴娘雖然也是同班同學,其實是她的表妹,但即便是章玉,上學的時候也不怎麼和表姐一起玩。
“章玉跟你姑姑說,袁穎怎麼像個木頭人似的,都不跟我們一起玩?”有一次,袁穎的媽媽問她,她撇撇嘴,抱起書本回了自己的房間。“木頭人”三個字久久地在她心裡盤旋。她不明白,為什麼寫作文表達不清的表妹,諷刺別人倒是用詞精准。
說破天,也都是過去的事了。她結婚,伴娘是章玉,邀請的賓客中除了親戚,就是一些老同學。章玉跟她同歲,一路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同校,幾乎所有的來賓章玉都認識。當地有鬧伴娘的習俗,章玉機靈潑辣,擅長應對這種場面。除此之外,一切都西化了:教堂婚禮,冒泡的香檳,雞尾酒,長長的拖尾婚紗。羅翰的西裝是去上海找裁縫定制的。他媽媽說這套西裝又實惠又好看,比現成的大牌划算多了,只不過多花了兩程火車票錢。袁穎覺得他媽媽這話是說給她聽的,她選的婚紗是個外國牌子,就只穿一次的價值而言,貴得離譜。羅翰和她都是公務員,薪水不高,但是袁穎一眼就看上了這套婚紗,信用卡分期付款,買了下來。
戀愛很甜美,輕快得如同一場夢。羅翰向袁穎示好的時候,她還有點遲疑。羅翰跟她從來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長得帥,受歡迎,朋友眾多,而她自己不過是趴在角落裡只會死讀書的人。更可笑的是,她這麼用功,結果並沒有考好,第一志願差了三分,落在本地的一個三流大學,畢業後靠著家裡的關係,在老家做公務員,莫名其妙地,人就快三十歲了。
那次聚會,要不是章玉拖著,她也不會去。同學聚會最考驗人品,能忍住了,不在混得差的同學面前炫耀,需要深厚的涵養。袁穎想,我才不去給你們當下酒菜。可是章玉想去,非要拖著她一起。就在那天,羅翰主動送她回家,走了很久打不到車,兩個人一起走著走著,發覺已經到家了。小地方就是有這樣的好處,約會見面都很方便。第二天,袁穎加班,走出單位門口時,發現羅翰正在等她。
這樣的情景,如果發生在高中時期,袁穎想,韓柳和她那幾個狗腿子似的跟班女生會驚訝得合不上嘴,可惜,這些人都散了,如今各幹各的,不再關注羅翰喜歡誰。要辦婚禮了,袁穎決定把她們都請來,讓她們看看,當年的醜小鴨不僅變成了天鵝,還俘獲了王子。儘管羅翰這些年很少運動,發胖得厲害,和過去判若兩人,袁穎卻仍然覺得,嫁給他是自己充滿失敗的青春年華中,唯一可圈可點的勝利。光憑這,她就覺得,這場昂貴的婚禮辦得很值。
地點選在縣城郊外的一家木屋酒店,風格前衛,專做婚慶。雖然縣城地方小,人口也不多,仍有不少追求時髦的年輕人在這裡舉辦婚禮。玻璃教堂只是個空房子,神父是婚慶公司職員扮的,長袍的衣料嘶啦作響,起著靜電,說話拉著長音。
“我宣佈你們—”這種拿腔拿調,像是從古老的譯製片裡學來的,“結為夫妻。”
底下響起一陣掌聲。夫妻倆走下紅毯,幾位女賓站在兩邊,往新人頭上拋撒花瓣。韓柳也在其中,她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緊身連衣裙,露出兩條修長的小腿,化了濃妝,從籃子裡抓起一把鮮紅的玫瑰花瓣,往新人的臉上拋撒。袁穎低下頭,看見落紅如雨,細而尖的高跟鞋踩了過去。
婚宴在酒店的宴會廳舉行,兩邊的親戚朋友都是本地人,熱鬧一番過後,人漸漸散了。有幾個同學要留下來過夜,羅翰早跟他們說好,一定要陪著他跟袁穎住一晚再走。第二天,新婚夫婦就會從酒店出發去火車站,坐火車到上海,再飛往馬來西亞度蜜月。袁穎早早地訂好了機票,價格非常划算。
人都散了,袁穎回到房間。他們訂了一晚別墅,是酒店裡最寬敞的房型,上下兩層,四間臥室,除了他們夫妻二人,還有兩男兩女留下來。章玉一進來就挑了樓上風景最好的房間,窗戶對著一片濃綠的山谷,用她的話說:“你們都要出國旅行了,今晚就讓我享受一下吧。”
袁穎去一樓的房間裡換衣服,那身敬酒服外面綴滿亮片,很不舒服。她換上T 恤和牛仔褲,順便把自己和羅翰帶的兩套睡衣也拿了出來,坐在床邊的梳粧檯前開始卸妝。
門突然開了,韓柳探進頭:“能進來嗎?”
她進來後,把門關好,說:“客廳是冰涼的,雨下起來沒完。你屋裡好暖和。”
“小屋子比較暖和。”她說,“章玉屋裡估計也陰冷,窗戶那麼大。一會兒讓酒店的人過來調調溫度。”
“我剛才試過,空調好像壞了。”韓柳說,她脫掉了高跟鞋,穿著酒店的無紡布拖鞋,肩上披著一條毛茸茸的白色披肩,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雨幕。屋頂上,中央空調的出風口吹出暖風,發出嗡嗡的聲音。
“明天幾點的飛機?”她沒話找話說。
“下午四點。”袁穎用潤濕的化妝棉擦乾淨全臉,只剩下素顏。韓柳的臉也映在鏡子裡,妝容嬌豔,上學的時候,她就會化妝,自己用電發棒卷劉海,不穿校服的日子,就穿超短裙和非常貼身的牛仔褲,章玉對她崇拜得不得了。後來兩個人因為小事鬧掰了,章玉跟袁穎說過她不少壞話。
一對假睫毛扔在梳粧檯上,韓柳拿起來仔細研究。“一點也看不出來是假的,很自然呢。”她說。
“化妝師給的。”袁穎說。她摘掉了長長的眼睫毛,妝也擦掉了,眼睛一下子顯得小而無神,臉色也發黃,頭天晚上因為怕睡過頭,她幾乎整夜清醒。車隊六點就出發來接人,在那之前她得化好妝準備著。
有人敲門,章玉來了,她也喊冷,已經打電話給前臺。羅翰和另外兩個留下來的朋友—趙智和李浩成在外面的
門廊下抽煙聊天,從袁穎的房間裡,可以聽見他們低低的說笑聲。
“這酒店的環境真不錯,是新建的?”韓柳放下兩條睫毛,挨著章玉坐在床上。她在上海工作,只有過年才回來,對家鄉的變化很陌生。
“前年就有了。”袁穎說。幾個男人在門廊下發出一陣哄笑,就在窗戶邊上。“生意特別好,提前半年才訂得上,別墅只有兩間。”
“感覺不到這兒有人。”章玉說,“房間太分散了,顯得很冷清,其實都住滿了。”向窗外望去,細雨中,一座座小木屋散落在山谷的斜坡上,樹木掩映間,露出棕色的尖頂,濕漉漉的。
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章玉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有妖怪路過。”大家都笑了起來。
男生們抽完煙,回到客廳,燒水煮茶,叫她們都出來喝點熱的。趙智從自己的背包裡翻出一包普洱茶,從雲南帶來的。他是一名旅遊雜誌的攝影記者,說起自己的工作,大家聽著就很羡慕。
“到處玩,還能賺錢,太幸福了吧。”章玉捧著一小杯濃茶,坐在寬大的飄窗上。茶具也是酒店提供的,款式很古典,是不值錢的樣子貨。
“根本不是玩,”趙智說,又遞了一杯給韓柳,“每次一休假,就想宅在家裡,哪兒也不去。”
“你家還住原來的老房子?”韓柳問道。袁穎坐在沙發旁的腳凳上,覺得杯子裡的茶冷得特別快,指尖也凍得冰涼。酒店什麼時候派人來修空調?只有一個房間的出風口正常工作。
“沒有,早搬走了。”趙智說,“我爸去世後,我媽想換個地方住,就把老房子賣了,在新區換了一套大的。”他說的新區,是指縣城北邊的那片樓盤,房子設計得好,價格比老城區低,很多人在那裡買房子。
“換作我,我也想搬。”章玉說,“太不吉利了。”
“又有妖怪經過。”這次,是李浩成打破了沉默,他是個大塊頭的男生,在學校時,經常跟羅翰一起打籃球。他說:“我聽見有人敲門。”說著,就起身去大門。果然,面帶微笑的服務員帶著一個穿藍色制服的年輕維修工走了進來,很快,出風口修好了,熱風呼呼地吹了出來。
為了表示歉意,服務員送來一盤水果,章玉順手拿起一隻蘋果啃著。
“你非得提這個。”韓柳說,“能不能別提這麼晦氣的事。”
“這有什麼。”章玉說,“人誰無死呢。”她一邊嚼著蘋果,一邊繼續說,“屍體就在,好像就在這附近被發現的,對吧?當年還上了報紙。”
她指的是這片山谷。建酒店之前,這裡曾是荒山野嶺,密林遮天蔽日,是個自殺的好地方。
“好像是吧。”李浩成接過話頭,“真是,一晃都這麼多年了。她媽媽還沒搬走?”
“沒有。”趙智說,“上次回來過年,聽我媽說,崔淩媽媽一直住在那兒,就一個人住。”
“她的病好了沒有?”李浩成問。
“那種病怎麼可能好。”趙智說,“反正從我記事起,鄰居都說她是精神病。崔淩死後,她又做過幾份工作,沒一份做得長。”
“有這種媽媽,崔淩也真可憐。”韓柳說,屋裡漸漸地暖和起來,她摘掉了披肩,丟在沙發的硬木扶手上。她沉思著,說:“沒錯,就在這片山裡。被人發現的時候,已經好幾天了。”
“所以,我們換個話題吧。”羅翰說。燒水壺又一次沸騰,趙智把開水倒進小巧的泡茶壺,用壺蓋悶住。
“說說你們倆。”韓柳換了一種戲謔的語氣,“你們倆是怎麼搞到一起去的?”
袁穎和羅翰相視一笑。“說來話長。”羅翰說,“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她,從上學的時候開始。”屋裡響起一陣低低的驚呼。
“我怎麼不知道!”韓柳佯怒,“真的嗎?”
“應該是吧。”袁穎說,她的手沒來由地哆嗦了一下,“不過,我倆那時候並不太熟。”
“是真的。”羅翰看著袁穎,看見她的臉漸漸漲紅了,“不過她那時候總和崔淩在一起,不跟我們玩。”不知為什麼,有關崔淩的話題再度逼近,像一隻禿鷹在空中緩慢盤旋,覬覦著食物。
“你們那時候管我倆叫什麼?我可記著呢。”袁穎的語氣很輕鬆,像開玩笑。
“雙塔。哈哈,對吧?你們倆都是又高又壯。”李浩成說,羅翰有些不自然地看了他一眼。
“對不起,對不起,”李浩成誇張地道歉,道歉也是在開玩笑,“都是鬧著玩兒的。”
“就你叫得最歡。”韓柳說,“不過,崔淩好像不喜歡這個外號。”
沒人喜歡,袁穎心裡想,沒有說出口。她拿起一杯溫暾的茶水,一口氣喝光,把茶杯放回黑沉沉的檀木茶盤上。
“是啊,為了這個,她還跟趙智吵過架。”
“我叫她黑鐵塔,她差點撲過來打我。”趙智說,“我從小就認識她,她性格怪異,多半是她媽媽的遺傳。精神病嘛,多少有點影響。”
“就算沒有遺傳,從小跟著瘋子一起生活,性格一定不正常的。”韓柳說,說著還瞥了袁穎一眼,見她垂著眼睛,面色如常,便收住了話頭。
羅翰搖搖頭:“她的成績那麼好,肯定不是瘋,只是我們那時候太小了,誰也不瞭解誰。”
“確實有那麼一種人,”李浩成插嘴進來,“雖然有一點瘋病的基因,但是頭腦卻很聰明。你們記得吧?物理老師最喜歡她,說她腦袋靈活。”
“那時候,章玉在班裡到處跟人說,崔淩暗戀物理老師。”韓柳說,有些不懷好意地看了章玉一眼。
“拜託,明明是你告訴我的。”章玉說,“你說你看見崔淩去物理老師的辦公室,然後哭著出來。”
“表白被拒絕?”趙智說。這傢伙和過去一樣嘴巴碎、愛八卦,當個狗仔或許更適合他,袁穎想著。她說:“才不是呢。你怎麼會這麼想?”
“很自然啊,表白被拒絕,然後哭了一頓。”趙智說,“難道另有隱情?”
羅翰說:“為什麼要談她呢?大喜的日子,多晦氣。”窗外的雨絲變得密集起來,簌簌敲打著寬大的飄窗。山谷一片靜寂。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韓柳問袁穎。
“很簡單,她那次沒考好。”袁穎說,“她壓力很大,必須得考上大學,如果考不上,她爸爸就會斷掉她的撫養費,教育費也不會再給,她連複讀的機會都沒有。”
章玉又拿起一隻蘋果,婚宴上她沒怎麼吃東西。
羅翰提議讓酒店送餐過來,袁穎也餓了,他們點了三份套餐,加上點心和咖啡,不久就送來了。
“這兒的咖啡還不錯呢。”韓柳說,“我在上海租的房子樓下,有一家特別好的咖啡館,只做外賣,每天下班路過,我都要買一杯帶回家。”
“一個人住,多麼自由啊。”章玉感歎道,“我要是不結婚,我媽絕不會讓我一個人出來租房子。”
“我養了一隻貓做伴,不然太冷清了。”
“我看到了,你整天曬貓的照片。”
袁穎正在吃那份白切雞飯,雞骨頭是嫩粉紅色的,似乎沒熟透,被她撥到盤子的一邊。她邊吃邊說:“我記得你從前很討厭貓。”
“人會變的嘛。”韓柳說,“那只貓,是我前男友留下的。人走了,貓還在,挺諷刺的,有時候男人還不如一隻寵物。”
韓柳的前男友,袁穎從羅翰那裡聽說過,是她從前公司的同事。一開始轟轟烈烈,沒多久兩個人就住在一起了。甜蜜了幾個月,後來男生主動承認自己移情別戀,要求分手,甩得韓柳措手不及。分開沒多久,韓柳就跳槽離開了那家公司。這段戀情大概是她有生以來遭遇過的最大失敗。
袁穎把剩下的米飯和鹵蛋都給了羅翰,羅翰很自然地接過去。韓柳笑著說:“不要在單身狗面前秀恩愛,真受不了。”
羅翰吃掉了鹵蛋的蛋清,剝出完整的蛋黃還給袁穎,這下連章玉也在抱怨:“你們是故意的吧,辣眼睛。”
“你們真的是,”趙智終於不再沏茶,身體向後靠在沙發上,“高中時候就互相有意思?”
“他說他是,”袁穎笑著說,“不過我沒感覺到,他不怎麼跟我說話。”章玉低低地笑了起來,看看韓柳,又看看夫妻二人,笑聲中別有含義。韓柳的臉上微微地泛紅。
“那時候大家都互相喜歡,一會兒就換一個喜歡的對象。”章玉說,“很多人悄悄約會,你們還記得學校旁邊那個甜品店嗎?老闆娘長得像容嬤嬤的。”
“記得。”袁穎很快地搭腔,“我跟崔淩經常一起去,她喜歡那裡的燒仙草,每次去,她總是加雙份的煉乳。”
“所以她長得那麼胖,”章玉用雙手拱出一個圈,比畫崔淩的身材,“還吃個不停。”
“她壓力很大。”袁穎輕輕地說,“吃燒仙草的時候,她最開心。”
“你是怎麼跟她相處的?”趙智突兀地問道,“你不覺得,她有點奇怪嗎?”
“是有一點,但是她人很善良。”袁穎站起身來,穿著輕薄的紅緞鞋踩在地板上,有種輕盈涼爽的觸覺。雨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她走到窗前,窗外是陰沉、潮濕、鮮綠的一大片,一整塊,度過漫長的陰雨季節,夏天就要來了。
“她沒什麼朋友,”袁穎繼續說,背對著他們,“我算一個。趙智也算?你跟她從小就認識。”
“小學以後我就不跟她玩了,”趙智說,“我媽不讓。她媽媽犯過兩次病,整棟樓都知道。”
“那你真是錯過了,她很有趣,”袁穎說,“沒想到她會走到那一步。”
“所以說,這就是瘋子的基因。”李浩成說,在場的所有人中,他始終游離在有關崔淩的話題之外。旁觀者的論斷往往是清晰明瞭、毫無疑義的。可惜啊,袁穎想,曲折的事實並不能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
“有一段時間,崔淩總是提起你。”袁穎說。李浩成面露驚訝:“她說我什麼?”
章玉發出咯咯的笑聲,一邊笑一邊說:“原來有這麼多八卦,我都不知道。”
“你經常抄她的物理作業,還請她吃燒仙草,後來文理科分班,你選了文科班,就不理她了。”
“抄她作業的又不止我一個。”李浩成說,“羅翰也抄過,對吧?”
“你們倆上物理課的時候,老是偷看漫畫書。”章玉說,“想起來了,崔淩是物理課代表,負責收作業。”
“結果她還是沒什麼朋友,除了袁穎。”章玉說,“她以為抄作業就能換來交情?”
“你非得這麼刻薄嗎?”袁穎輕輕地說,她不確定自己真的說出口了,也許只是在心裡打了個滾,變成一道輕輕的哈氣,白濛濛地浮在玻璃窗上。
“怎麼又冷起來了?”韓柳抱怨著,重新裹緊她的毛披肩。
中央空調的出風口再次安靜下來,不再呼呼作響。李浩成說:“她沒什麼零花錢,我請她喝個飲料,她就給我抄作業,然後,羅翰再抄我的。”
“有時候,你們連抄都抄錯。”韓柳說,“咱們班的學風真是一團糟。”
“崔淩要是活著,她一定能考上大學吧。”趙智說,“不過,以她那樣的性格,走到哪裡都不會吃得開,說話磕磕巴巴的,還經常莫名其妙地發呆。”
袁穎覺得這句話描述的倒像是自己,走到哪裡都吃不開。的確,崔淩平常話不多,尤其是面對男生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緊張。並不是因為她喜歡誰,而是一種對異性的整體恐懼,或許與她的家庭背景有關。袁穎將雙臂抱在胸前,覺得房間確實在一點點地變冷。
前臺電話沒人接,又打一遍,還是沒人接。他們把所有臥室的暖風都打開了,再打開門,希望能渡來一些溫暖。趙智重新燒起水來,換了新茶葉。午後陰冷而漫長。
“我只想喝點熱水。”韓柳說,“到底能不能換個輕鬆的話題?”崔淩的屍體在附近被發現時,已經好幾天了,現場的照片毫無遮掩地登在報紙上。
“我和她一起去吃燒仙草,她跟我說,你曾經帶她來過。”袁穎對李浩成說,“她以為你們算是朋友,結果你轉到文科班,就再也不搭理她了。”
李浩成勉強地笑笑,袁穎的話讓他覺得不舒服:“她借我作業,我就給她買個飲料或者別的什麼吃的,反正她嘴饞,又沒有零花錢。說是朋友也行,但是她實在太無聊了,跟她聊天,她連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她小時候不是這樣。”趙智說,“不過,自從她媽媽的瘋病發作過兩次之後,全樓的小孩都不跟她玩,她就越來越孤僻。可憐歸可憐,也怪不得別人啊。”
“不過,她有什麼理由自殺呢?”章玉說,“這麼多年過去,我還是想不明白。”
韓柳半天都沒說話,忽然有些不耐煩了,她說:“崔淩精神有問題,當年報紙上都這麼說嘛。考前壓力過大,有精神失常的徵兆,深夜從家中出走,過幾天屍體被發現在西郊的山林裡。瘋子根本就沒有理智。”
“她不是瘋子,”袁穎說,“我確定。我和她做了三年同桌。她確實性格內向,但絕不是瘋子。”
“瘋不瘋有什麼區別?反正她死了。”韓柳說,用叉子紮向盤子裡的黑森林蛋糕。當時,崔淩的自殺在學校裡引起了一陣短暫的議論,不過很快就平息了,大家都要面對高考,沒空為一個不太熟的同學悲傷太久,況且那也不是什麼真正的同情,而是驚訝,是好奇,是課間的八卦話題,熱鬧一陣就過去了。畢竟,崔淩是那麼孤僻的人,沒什麼朋友,只有袁穎,但是袁穎和她差不多,都是班裡的透明人。
所以,韓柳還是覺得奇怪,問羅翰:“上學的時候你就喜歡袁穎?我怎麼沒看出來。”
“暗戀。” 章玉在一旁替羅翰回答,“就像崔淩暗戀他一樣。”
“真是夠了。”韓柳盯著章玉,“你為什麼要跟一個死人過不去?”
“大家都知道啊,還拿這個事情取笑羅翰。”章玉說,抱起了雙臂取暖,“羅翰怎麼說來著?就那次,自習課上,大家都在,崔淩找羅翰借一本漫畫書,羅翰說沒有。”
“她根本不愛看漫畫。”羅翰說。他似乎想為自己辯解什麼,卻也沒什麼好辯的,不過是個傻乎乎的女生而已。
袁穎再次低下頭,水壺咕嘟起來,再一次接近沸騰。
“你還說崔淩身上有貓味兒,”章玉說,這句話是對著韓柳說的,“很大聲,我記得。”
“貓屎味兒。”韓柳面不改色。袁穎抬起頭看看她,又看看羅翰,羅翰胖了不少,不是當初的翩翩少年了。
“我記得,那時候你很討厭貓。”羅翰說。
“問題不在於貓。”袁穎說,她換了個姿勢,把一條腿蹺到另一條腿上面。韓柳放下了手裡的小茶杯。
“討厭一個人,就跟喜歡一個人一樣,”袁穎說,“不需要什麼理由吧。”
趙智說:“她家的貓養了好多年,是我見過的最大的貓,像只小獅子。”
“其實,”羅翰開口了,“崔淩是個很敏感的人,可能那時候我們都太幼稚,沒有人懂她,我也不懂,她表白的方式太奇怪了。”
袁穎微微笑著,聽著他試圖為自己開脫。人就是這樣,終其一生都在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解釋,否則簡直沒辦法活
下去。
李浩成輕輕地吹了聲口哨。
“她跟我借漫畫書那天,我沒借給她,是因為那本正好沒有。你們都以為我在敷衍?是真的沒有,最新的一本,我還沒買呢。第二天放學,我去跑步,跑完天都黑了,她就一直在操場邊上轉來轉去。”羅翰說著,給自己倒了一杯茶。他身子前傾,肚子上出現幾道肉堆的褶紋,他大概有七八年不怎麼運動了。
“她在操場邊上,一會兒坐,一會兒站,只有我一個人在一圈圈地跑,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我恨不得一輩子就這麼跑下去,不要停下來。她怎麼也不肯走。”
“哈哈,有點恐怖啊。”韓柳說,“你居然沒跟我提起過。”
“等我跑完了,準備拿書包回家,她就走過來,把一本漫畫塞到我手裡,就是她想跟我借的那本。我想她是從學校北門邊上那家小書店買來的,每期到了,老闆會給我留一本。我就告訴她我不需要,她非送不可,說到最後,我都懶得解釋了。”
“也許她在書裡夾了些什麼,情書一類的。”韓柳說,“你應該接過來看看。然後呢?”
“後來她走了,把書放在臺階上,這人真怪。”羅翰說,“她好像不知道人與人應該怎麼交往。”
“那個年紀,其實沒人知道。”袁穎說,“大家都很粗魯。”
“一般人不會像她那樣。”章玉小聲地說,“書裡有夾著情書嗎?”
“沒有。”羅翰說,“什麼也沒有。”
“看來你還真的去找了。”韓柳笑道,“幸虧沒有。不知道她會寫出什麼奇怪的東西。你們還記得語文老師念她的作文嗎?反面例子,零分。”
我記得,袁穎想。又一次,她克制住自己,沒有說出口。
“我記得。”趙智說,“她寫的是她媽媽,全程只有一個句式:我媽媽喜歡如何如何,她喜歡吃什麼,喜歡穿什麼,喜歡看什麼電視節目,最後說,我媽媽最喜歡的人就是她自己,念完大家都在笑。”
“語文老師不喜歡她,她上課總是打瞌睡。”李浩成說,“有一次發脾氣,差點把她趕出教室,她都睡得打起呼嚕了。”
剛才那位服務員又來了,帶著另一個維修工,看起來比剛才那位更年長,更有經驗。對話停止了,大家靜靜地等著空調恢復工作。
最終,維修工從出風口的管道裡面掏到一隻肥大的死老鼠,已經開始腐爛了,但仍舊很肥大。章玉噁心地捂住了口鼻,韓柳只看了一眼,就趕緊轉過臉去—它被托在維修工人的塑膠手套上,眼睛睜著,眼球向外鼓。
“山裡的環境就是這樣,小動物很多。”服務員帶著歉意,微微鞠躬。酒店的員工都是從本地招聘來的,受過專業的服務培訓,一舉一動合乎標準,等她走了,大家重新放鬆下來。
“噁心死了。”章玉說,“不知道別的地方有沒有老鼠?”今天晚上,她和韓柳一人占一間臥室,另外兩個男生擠一間。
“半夜爬到你床上。”李浩成用手指模仿老鼠爪子,章玉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
韓柳起身,去了衛生間,出來後,妝容煥然一新,嘴唇重新塗得紅紅的。雨聲敲著屋頂,依舊輕細綿密。
“崔淩喜歡羅翰,”袁穎說,“全班都猜著了,結果羅翰居然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所以說,被暗戀和被出軌一樣,主角都是最後才恍然大悟。”趙智說,“你當時有沒有覺得很驚悚?被那樣一個女生惦記著。”
“那倒沒有。”羅翰看了袁穎一眼,她的樣子跟高中時相比,幾乎一點沒變,只是瘦了些。那時候,她跟崔淩幾乎形影不離。兩個人都沒有別的朋友。
“後來呢?”韓柳問,她對羅翰和崔淩的這段往事來了興趣,“後來她又找過你嗎?”
“沒有。”羅翰簡短地回答,“不過有一次,就在她出事前不久,有一次收物理作業,我沒寫完,她來催我交作業,語氣很生硬,我跟她吵了幾句。”
“你罵她是黑鐵塔,蠢貨。”袁穎說,“她都告訴我了。”
羅翰的臉有點發紅,趙智打圓場說:“那時候大家說話都很隨便。反正崔淩也無所謂,她本來就有點傻。”
“她找我哭了一場。”袁穎說,“就在那間甜品店裡,她連燒仙草都沒吃完。”
“為什麼?”章玉剛才兩眼空空地發呆,若有所思的樣子,此刻終於回過神來。
“因為羅翰罵她啊。”李浩成說,“你還想吃蘋果嗎?”盤子裡的蘋果只剩下一個了,章玉搖搖頭。
“沒人想吃蘋果嗎?”沒人回應,李浩成拿起蘋果啃了一口,只一口,就咬出一條淡黃色的肉蟲。
他把果肉啐了出來,肉蟲爬到他咬出的缺口上,被他連著整個蘋果一道丟進垃圾桶。
“你不喜歡她,也不用這麼罵她吧?”章玉說。
“那有什麼?說她笨的又不是羅翰一個。語文老師也說她腦袋像個木魚。”
袁穎把李浩成用過的水果刀輕輕放回盤子裡,發出清脆的微響。
韓柳說:“語文老師最愛批評的就是崔淩,她的作文寫得太差勁。”
“她很聰明。”袁穎開口了,“崔淩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女生,她想報理論物理專業。”
“她有瘋子的基因,”趙智說,“這種人今天想東,明天想西,前一天還活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跑去自殺。”
“說起來,她出事之前,曾經問過我,要不要養貓。”章玉說,“她是不是已經問過你,被拒絕了?”
袁穎點點頭:“我父母不喜歡貓,我要離家上大學,沒人照顧。”
“怪不得,”趙智說,“她也問過我。我告訴她,我們家不養那玩意兒。沒過兩天,那只貓被吊死在陽臺上,她家在二樓,下面路過的人都能看見。”
“她媽媽幹的。”袁穎很快地說,“她媽媽失眠,夜裡貓總在跑來跑去,崔淩跟我講,那天早上她一醒來,就看見貓在陽臺上蕩悠。”
“然後她自己也選擇了這種死法?”章玉說,打了個寒戰。
“等等,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李浩成忽然插嘴進來。剛才他在專注地削一隻梨,確定沒有果蟲之後,才放進嘴裡,咬下一口。
“春天,天天下雨。”趙智說,“那只貓都快要爛了,才被解下來丟掉。聽說是崔淩的爸爸來處理了屍體,她們母女倆都不管,像是有意賭氣,報復彼此。”
“她嚇壞了。”袁穎說,“我要是幫她養幾天,也許就沒事了。那只貓在她家十幾年,陪著崔淩長大。”
“有人覺得太熱了嗎?”韓柳站起來,去把窗戶拉開一道縫,讓外面陰涼的空氣吹進來,緩解暖風帶來的焦躁感。
“自殺是她自己的事。”趙智突然開口,好像是為了驅趕那只盤旋的禿鷹,憑空放了一槍。
“因為一次模擬考試沒考好就跑去自殺,這種人到了社會上也不會順利的。”韓柳說,“再叫杯咖啡吧,好嗎?我有點瞌睡。”
“所以,韓柳說崔淩身上有貓屎味兒的時候,那只貓已經死了幾個月了?”李浩成說。
“我早說過了,這不是貓的問題。”袁穎看了一眼羅翰。
羅翰有些尷尬地動了動身體,韓柳微笑著,不答言。章玉跟韓柳有過矛盾,此刻趁勢跟上一句:“我就說嘛,韓柳一定喜歡羅翰的。”
“我討厭崔淩,不是因為羅翰。”韓柳說,“你不要這麼膚淺,以為什麼都是因為男人?”
“像她那樣的人,招人喜歡才不正常呢。”她繼續說,“長得醜,胖得像頭豬,跟她說話,她總是發愣,除了物理成績好,其餘都一塌糊塗,笨得要命。你們不覺得,她跟我們一點都不像嗎?”
“關於她,最有發言權的是袁穎。”李浩成說,“她們倆好得跟一個人似的。”
“我一直想不通羅翰為什麼要罵她。你明知道她喜歡你啊。”袁穎說。
羅翰給她倒了茶,袁穎接過來,心想:他一定以為自己喝多了酒,胡言亂語。
“無論是誰,被崔淩那樣的人盯著,都很噁心吧。”韓柳說,“羅翰一定很煩她。”
“罵就罵唄,”李浩成說,“說她兩句也不算什麼。有一次她向我借語文課的筆記,還回來的時候,邊角都給折了,我很生氣,也說了她幾句。”
“你說她是笨豬。”袁穎說,“看書折頁是她的習慣,確實是個壞習慣,但是罵人笨豬有點過分吧。”
“這麼說,我也想起來了,她所有的本子都有折角,人也很邋遢。她好像完全沒有家教的,她媽媽不會教她的嗎?連鞋帶都系不好,老是耷拉著拖地,隨時會絆倒。”
袁穎笑了:“這倒是, 每回上體育課, 我都要幫她系鞋帶。”
“說起來,崔淩真是無處不在啊。”李浩成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盒煙,韓柳跟他要了一根,點了起來。
“討厭的人都很有存在感。”章玉說,“我還記得,有一次她穿了一身舊衣服來上學,像那種鹹菜的顏色,非常難看,像是她奶奶的衣服。”這話是對著袁穎說的。
“那是她媽媽的,她奶奶早去世了。”
韓柳吐出一口煙:“所以啊,自殺一定是她自己的問題。你知道為什麼嗎,袁穎?”
袁穎搖搖頭,羅翰說:“我不明白你怎麼會跟她成為好朋友。”
“那,如果不是因為羅翰,那是為什麼呢?”袁穎問韓柳,“你為什麼要那樣對她?”
“哪樣?”韓柳停止了吸煙的動作。木屋別墅裡禁止煙火。
“就是從那天開始,從崔淩被羅翰罵的那天開始,班裡的人忽然都不理崔淩了。你們似乎形成了一種默契,不管崔淩跟哪個人說話,收物理作業或者是別的什麼事,一律裝作聽不懂,然後哈哈大笑。”
“這是一個玩笑。”趙智說。當然,他也參與了這個玩笑,大概持續了一周。一周之後,所有人都覺得沒意思了。他們不再無緣無故地傻笑,崔淩反倒不適應了,她悄悄地問袁穎:“他們為什麼不笑了?”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笑夠了吧。他們為什麼笑你?”
“他們為什麼笑我?”崔淩反問,袁穎啞口無言。
“那時候大家壓力都很大,”章玉說,“傻樂一下也挺開心。再說她也不在乎嘛。”
羅翰說:“十幾歲的人就是很莽撞,這也沒啥。”
“全班都笑瘋了。”韓柳說,“崔淩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就一臉傻樣地愣在那兒。”
“喜歡一個男生而已,” 袁穎輕輕地歎道,“這有什麼錯呢?”
“沒人說她錯。”李浩成的語氣裡帶著勸慰,“我們只是覺得,她呆愣愣的樣子很好玩。”
“她活著就是個樂子。”章玉說,似乎帶著一絲惋惜之意,“如果我喜歡的男生那樣罵我,估計我也會想死了算了。”
“你才不會去死呢。”趙智說,“你不是那種人。”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章玉笑著反駁他,“據說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上百次想自殺的念頭,雜誌上說的。”
咖啡送來了,六杯,熱騰騰的,上面浮著細密的奶泡。雨已經停了,服務員沒有打傘,彎腰放下託盤,她有些年紀了,盤起來的頭髮裡面雜著幾莖銀白。天色仍舊陰沉。
“來,”趙智提議,“為活著乾杯。”大家都笑了,章玉蜷起腿來,她坐在一隻寬大的籐椅上,人縮成一團。
杯子們彼此相撞,然後陸續放下,咖啡嫋嫋地冒著白汽。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