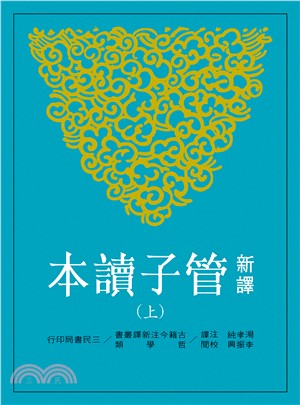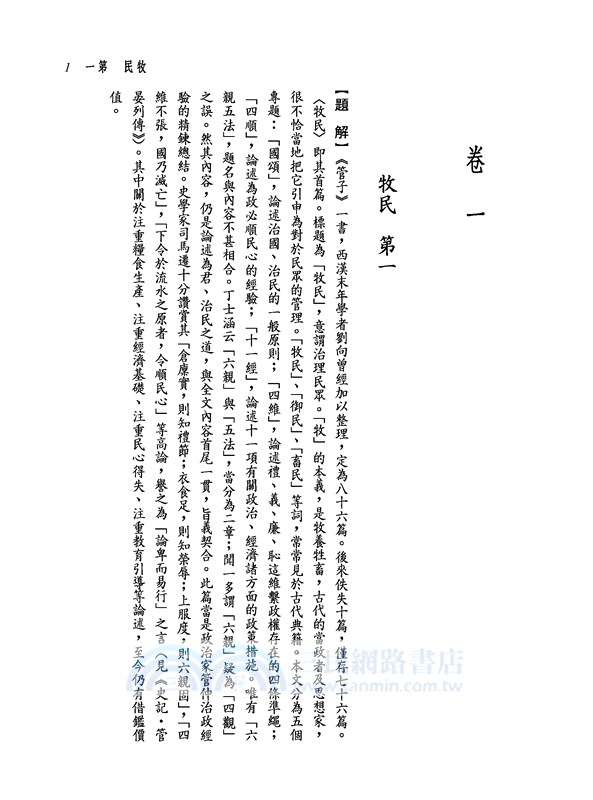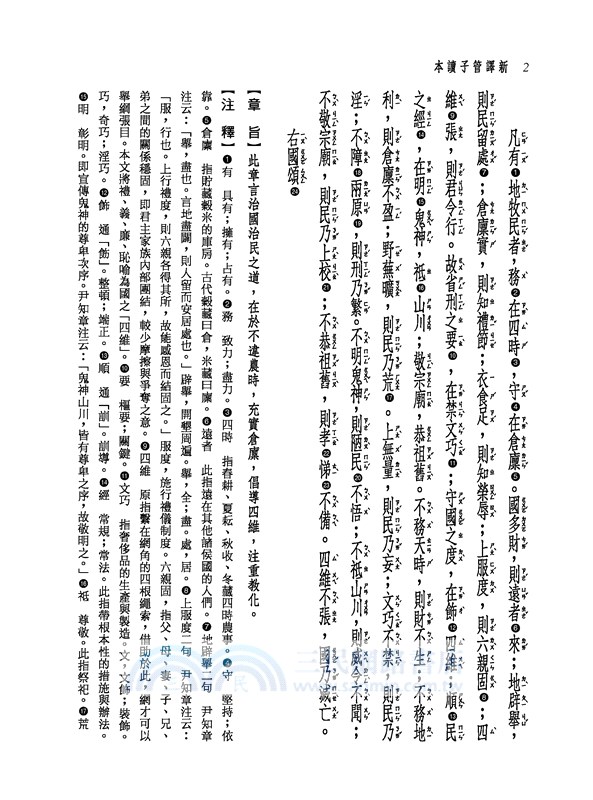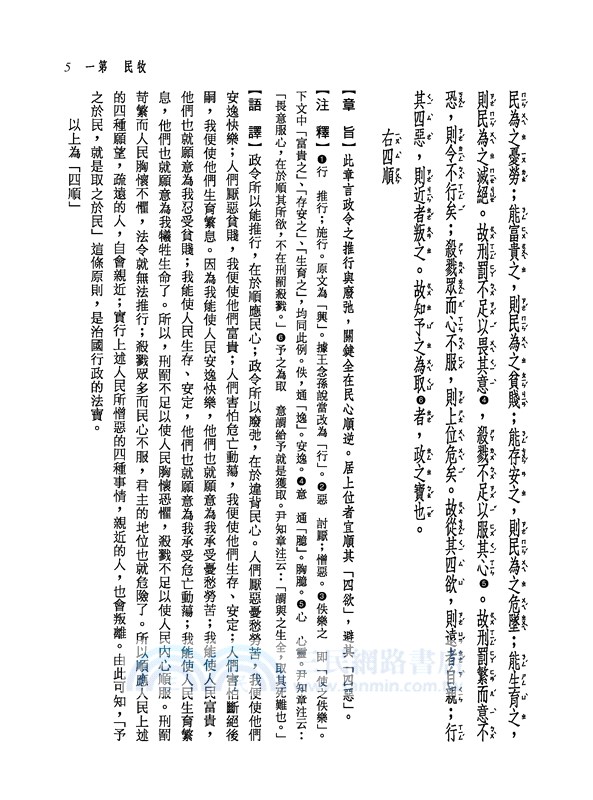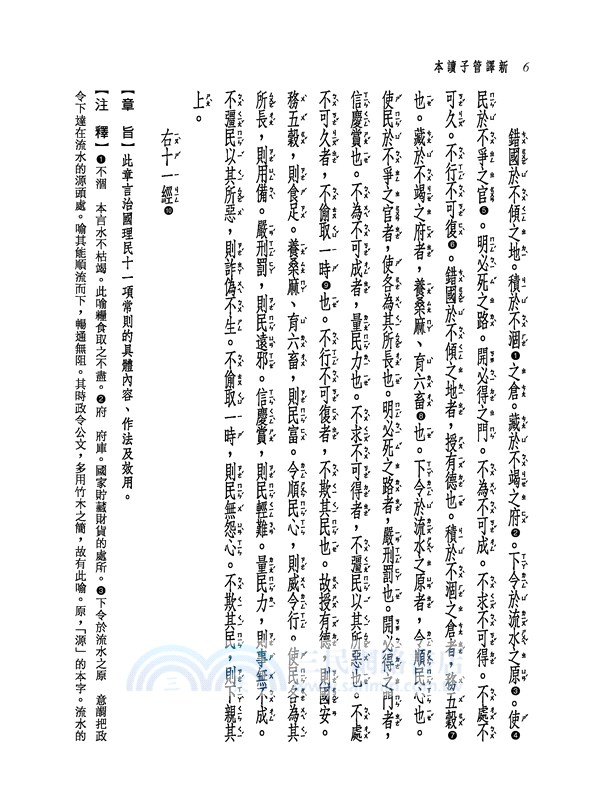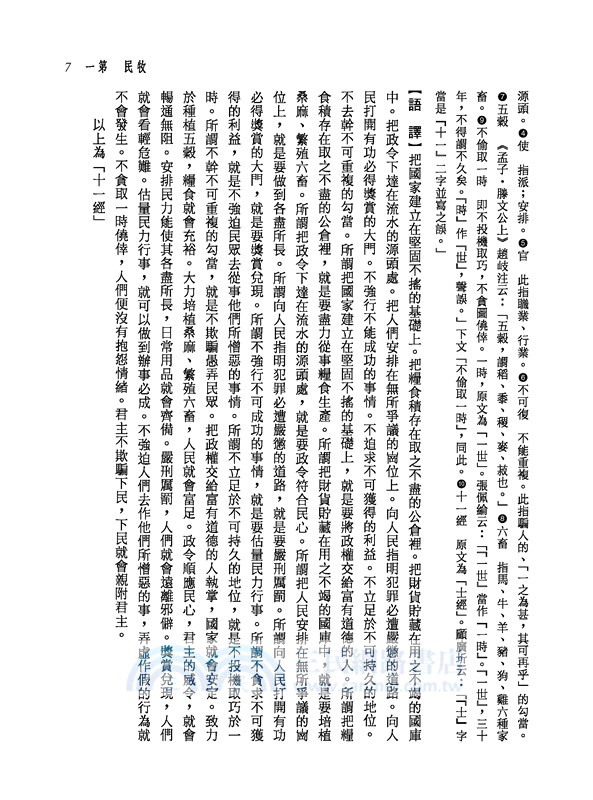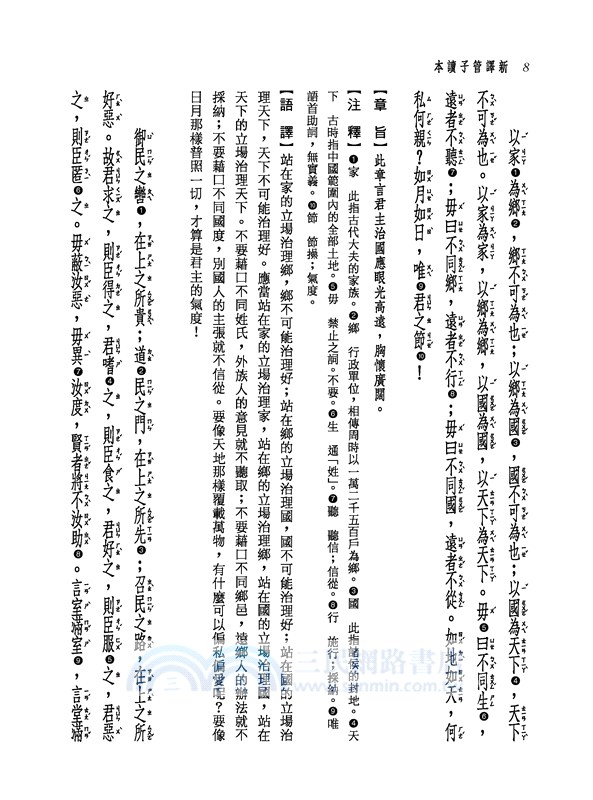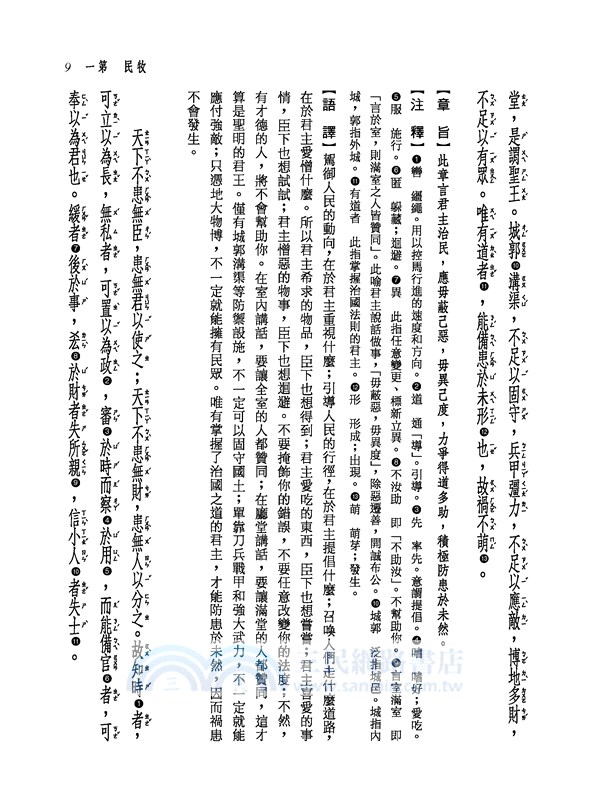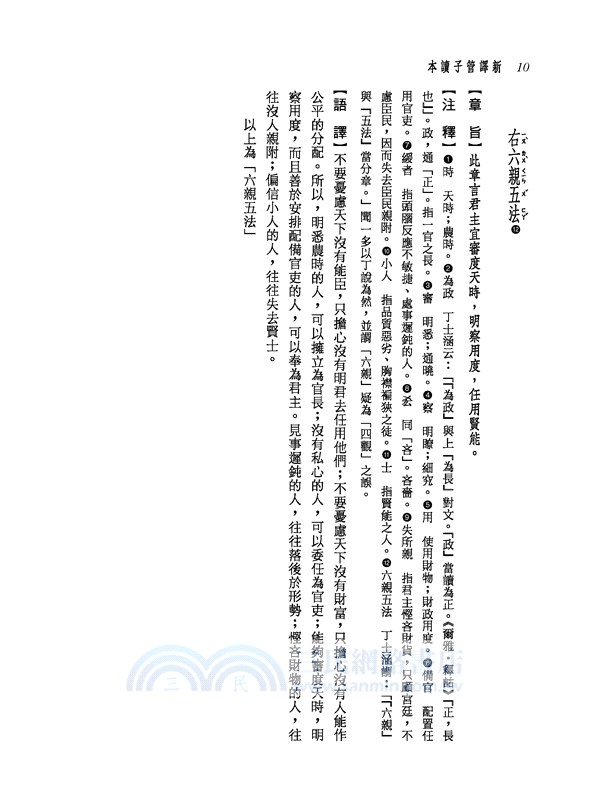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管子》一書乃是依附春秋時期政治家管仲之名而成,既非寫於一人之筆,亦非作於一時之書。就內容而言,《管子》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大凡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教育和自然科學等思想,無不包容。但因此書內容紛繁複雜,加上詞義古奧,簡篇錯亂,因而歷來號稱為難讀之書。本注譯本集歷代學者研究之精華,以及近代學者之成就,注釋淺明,語譯通暢,讓一般讀者也能輕鬆閱讀這本難得的好書。
《管子》一書,究係何人所著?作於何時?歷來爭論甚多。現在,基本上趨於一致的看法是:《管子》並非管仲之作,乃是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書,而且既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
說《管子》並非管仲所作,最有力的證據便是其中不少篇章,言及管仲死後的史實。比如〈立政〉批評「兼愛」學說,便非管仲時事。「兼愛」是墨翟的主張,墨翟的出生,已在管仲逝世一百七十餘年之後。〈小稱〉說:「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毛嬙、西施,是吳、越稱霸時人。其時,管仲早已不在人世。《管子》諸篇,多有「管子」與「桓公」的對話,但「桓公」是公子小白死後的諡號,管仲早死於小白,當然不知「桓公」之稱。又書中多次出現「管子曰」,多存錄「管子《解》」,這些,顯然都是後人用語。此類篇章,為後人所作無疑。因此,《管子》其書與管仲其人,在著述關係方面,只能說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所謂聯繫,是全書確實記述了管仲的思想和言行,闡述了管仲的主張;所謂區別,則是這些記述和闡釋,並非出自管仲之手。《管子》的作者,既欲追述管仲的言論與實踐,發揚光大管仲的主張,又欲借助管仲的名號,闡發傳播自己的見解,託名「管子」,文以人傳,也是頗為自然的。
說《管子》並非一時之書,則主要是從諸篇內容所揭示的時代特徵而言。依據這個特徵來辨《管子》,可以斷言,雖然其中也有春秋時代的作品,如牛力達〈管子書各篇斷代瑣談〉中所指出的〈版法〉、〈大匡〉之類〔《管子研究》(第一輯)第二十五頁,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但其大部分作品當成於戰國時代。比如,曾被人認為是「管仲遺著」的「經言」九篇(指〈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圖〉)和「外言」(指〈五輔〉),就大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因為從現存典籍來看,中國古代的富國主張,出現於戰國中期。而以上所列十篇中,〈立政〉、〈五輔〉,就正面提出了「富國」之說,〈權修〉、〈七法〉,則間接提出了「富國」的問題。又比如,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也是產生於戰國時期,而以上所列十篇中,〈牧民〉、〈權修〉、〈立政〉、〈幼官〉、〈幼官圖〉及〈五輔〉諸篇,就都提出了「務本飾末」的主張。這是從經濟思想角度而言。若從政治角度而言,則《管子》中不少篇章,可以找出田齊政權的特色。比如,田氏代齊的主要手段,是博取民心。他們的大斗出、小斗進,貸糧濟民一類措施,就曾獲得了齊國百姓「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左傳‧昭公三年》)的極佳效果。〈牧民〉中的如下一段話,就很像是對於這類措施的理論性的概括,〈牧民〉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種欲取先予、取予並施的治政經驗,深得司馬遷的讚賞;而這種全面闡述得失取予的精鍊文字,在先秦諸子中,也是很難見到的。田氏代齊的治政實踐,與〈牧民〉的理論概括之間,出現的這種密切聯繫,也很難說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已。又比如,田氏代齊的奪權特點,是以臣代君,這在先秦諸子,特別是儒家經典中,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然而《管子》卻說:「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形勢〉)「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權修〉)「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牧民〉)這些言論的傾向很鮮明,對於田氏代齊之舉,顯然持認可和贊同的態度。如果將這類言論,說成是為田氏奪權提供了理論依據,應當說,也是不為牽強的。不少《管子》研究者都已指出,這類篇章,應是戰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們的著作。
不但如此,《管子》中的若干篇章,還是秦漢時人之所作。郭沫若謂〈明法〉「必係秦文無疑」,而〈明法解〉「乃不通秦語之漢人所為也」〔《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七卷《管子集校》(三)第一○二頁〕。至於「輕重十九篇」,則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郭沫若《管子集校》(四)、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等著,均舉有大量例證,論為西漢時期所作。
就內容而言,《管子》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大凡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學思想等等,無不包容,其中不乏精闢的議論、深邃的見解,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首先談政治思想:
《管子》的作者,十分強調「以民為本」,明確肯定民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作用。〈霸形〉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五輔〉說:「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作者認為,民眾就是成就霸王之業的根本;重視民眾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最高天道原則的。執政者,不但應該十分重視民力,而且必須十分注重民心。〈牧民〉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可以決定政權興廢。執政者,務必明察民心向背,順乎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唯其如此,施政才能得到預期效果,「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若是一味威壓,不但「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反而會弄得「令不行」而「上位危矣」。總之,「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執政者務必深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這最後一句,說得至為明白,只有順應民心,給予人民以必要的物質利益,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而使之盡心效力。另一方面,取用民財民力,也須「有度」、「有止」,因為「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權修〉)。君主絕對不應為了滿足一己的無窮之欲,而採取竭澤而漁的愚蠢辦法。《管子》的這些議論,與孟子的「民貴君輕」、賈誼的「民無不為本」、黃宗羲的「民主君客」、王夫之的「民心之大同」等見解,無疑地,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後先輝映的光芒,同時也構成了中國古代歷史觀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管子》十分強調君主集權,認為立法、決策及人事任免等大權,君主尤須獨攬,不可須臾旁落。〈立政〉篇中,就頗為具體地論述了君主制定、頒布法律政令的制度:「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這種作法,旨在保證法出於一孔,令出於一型,不致中途增損異樣。而後,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立即出朝,將憲令傳達到鄉官、鄉屬、游宗,一直發布到民眾。留令者、違令者、增令者、虧令者,一律「罪死不赦」。
欲使君令暢通,還需有一個完整的行政體系。「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權修〉)。「主」,是指軍中統帥,「長」,是指朝廷輔相,二者在國君統領之下,分理軍政大權。至於地方鄉里,則須按行政區劃設置官吏。「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權修〉),「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立政〉)。從中央朝廷到地方鄉里,建立這樣一個較為嚴密的行政管理系統,此無他,目的就在於加強君主專制。
治政必須注意選拔人才。在這方面,《管子》提出的原則是選賢任能。「備長在乎任賢」(〈版法〉),國君在人事任免方面,必須持審慎的態度,務必使臣下的德義與其爵位相稱,功績與其俸祿相稱,才能與其官職相稱。「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農業),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立政〉)。很顯然,這個原則的提出,是為實現長治久安、富國強兵而王天下的大目標服務的,對於任人唯親、世卿世祿的用人制度,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否定。
什麼是賢?《管子》在這上面的標準,一是「義立」,二是「奉法」。「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宙合〉)。這就是說,大人之行,沒有先例常規,合乎義者即為賢。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五輔〉)。這些內容,主要是屬於道德方面的要求。「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重令〉)。這些內容,主要是屬於行為方面的要求。「經臣」也就是賢臣、法臣。「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就是以奉法為賢。兩項標準,前者側重於賢臣的主觀素質,後者側重於賢臣的客觀行為,二者得以兼顧,任人的標準是很全面的。
賢在何處?如何求賢?《管子》的高明處不但在於認識到了「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這個客觀事實,也制定了一份頗為完整而縝密的人材普查提綱(見〈問〉),更在於提出了一個「下什伍以徵」(〈君臣下〉)而選拔賢才的嶄新觀點。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所謂賢才,不但存在於貴胄之中,也同樣存在於平民之中。這正是《管子》求賢理論中閃耀的民主色彩。〈山權數〉中所提出的「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 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此國筴之大者也」,即以獎勵的重點在農事、畜牧、園藝、醫藥、曆法、養殖等方面有貢獻的科技人才,作為一項重大的國策措施,也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的具體運用。
其次談經濟思想:
《管子》主張經濟治國,認為「民富則易治」(〈治國〉),則國安。「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牧民〉),只有加速發展經濟,才能稱霸天下。如何實施經濟治國的方針呢?《管子》認為必須以地為本,以農為本。作者把土地問題,看得至為重要,認為「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因而首先必須採取「正地」措施,激起農民的務農熱情。「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只有核實了田畝,授田才能「平均和調」。農民知道了耕田多少,繳稅多少,自得多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餓寒之至于身也」,才會「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不憚勞苦」(以上引文,均見〈乘馬〉)而勤勞事農。其次,必須不斷開墾土地,擴大耕地面積,生產才能發展。作者明確指出「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權修〉),「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七法〉),焉能安國而王天下?因此,〈治國〉一文,反覆強調「辟地」、「墾田」是「富國多粟」的前提,一再指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也正是基於欲實現「國富」、「兵彊」、「戰勝」而王天下這個總目標,因而《管子》重農重地而不輕工商,認為工商之業,可為農事提供資金,可為農產物資找到銷路,認為工商之民,同樣是建設國家的基石。〈小匡〉說得十分明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所謂「石民」,即柱石之民,亦即國之基石。將工商業者和農民提到與「士」平列的地位,同稱之為「石民」,正是著眼於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為了實施經濟治國的方針,作者還提出了「務本飾末」的主張。〈幼官〉說:「務本飭,末則富。」「本」,指農事;「末」,指「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立政〉)之類的奢侈品生產。「飭末」,即對奢侈品生產加以整頓和限制,其目的是為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務本」,以期促進農業發展。這道理很簡單,因為「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權修〉)。
《管子》的經濟思想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是「輕重」學說。「輕重」學說的內容,主要反映在「輕重十九篇」之中。「輕重十九篇」中,〈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等,已是有目無文,因而實際上現存的只有十六篇。這是一組專門闡釋財政經濟問題的著述。作者已經認識到客觀的價格規律的自發作用,對於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已經認識到人們的生產勞動與物價之間的密切關係,認為「凡將為國」,不可「不通於輕重」,國君必須認識價格規律,並自覺地運用這一規律來「調通民利」,控制市場,採取「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國蓄〉)的措施來積累資財,平衡物價,穩定民心,鞏固政權。
如何運用價格規律,來獲取高額利潤呢?《管子》認為國君必須注意兩個要點:一是要「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國蓄〉),即掌握黃金刀幣這個流通手段來調動民力,促進五穀食米的生產。生產發展了,理財才好辦。否則,縱有「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正如〈輕重己〉所說:「通輕重」固為治國妙術,但若無四時所生之萬物,則雖有妙術,也將無法施展。二是要堅持「利出於一孔」(〈國蓄〉),即實行高度集中。糧食、鹽、鐵是廣大民眾維持生活、擴大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資,當由國家統一掌握。國家掌握了財利、資源,掌握了貨幣發行,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流通樞要,控制市場物價,才能達到避免動亂和「無籍而贍國」的目的。尤其可貴的是,作者的眼光,不但看到了國內,而且看到了國外。在〈地數〉、〈輕重甲〉諸篇中,作者提出善於治國的君主,不僅要善於掌握天財地利,及時調控物價,經營國內流通,而且要借助對外通商手段,善於汲取國外資金,利用國外勞力,使「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地數〉),並通過加強和各國的貿易往來,以期造成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這種理財見解,是十分可取的。總之,《管子》重視經濟治國的思想,在諸子百家中,確實是獨具特色的。
再其次談軍事思想:
《管子》中談兵的篇幅甚多。〈七法〉、〈幼官〉、〈重令〉、〈法法〉、〈兵法〉、〈地圖〉、〈參患〉、〈制分〉、〈勢〉、〈九變〉、〈小問〉、〈禁藏〉、〈輕重甲〉等,或通篇,或部分,都談了兵事,包涵了豐富的軍事見解。〈參患〉說:「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這裡,作者明確指出,正義戰爭不可廢除,它是「尊主安國」、「誅暴」、「禁邪」的必要手段。這段論述,既規定了軍隊的內外職能,又提出了正義戰爭的客觀標準,揭示了當時國君以軍事手段來謀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願望與要求,否定了孔子提倡「去兵」、墨子提倡「弭兵」的主觀臆想,議論是頗為精闢的。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戰爭手段,必須慎於使用。這是個變化無常的「詭物」,是個耗盡資財的「禍根」,「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參患〉)。因而欲「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七法〉)。「理」,指事物發展的規律;「義」,指順乎民心。不看當時的具體條件,違背「理」、「義」行事,即使一時取勝,終將造成政權危亡。這正是作者總結周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經驗之後,對當時執政者所提出的嚴重警告。
《管子》作者,在探討戰爭制勝的諸因素時,不但指出了戰爭必合於「理」、「義」,必賴於雄厚的經濟實力及隱兵於田、寓兵於政、耕戰合一等一整套相關制度的保證,而且有賴於將士素質及武器裝備。〈參患〉說:「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重令〉說:「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法法〉說:「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參患〉說:「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這些論述,從要求兵精、士勇、將賢、主聖眾多方面,通盤論述了制勝的必要條件。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不忽視武器裝備之類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強調戰爭的正義性,而不忽視與敵方作人力、物力、財力的全面較量,這正是《管子》軍事思想的高明處。
現在談哲學思想:
《管子》的哲學思想,也是兼融各家,其主體則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其中,關於「道」的論述最為詳盡。比如,〈心術上〉說:「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樞言〉說:「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內業〉說:「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形勢解〉說:「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這些論述,頗為清楚地說明了《管子》所謂「道」,既源於老子之「道」,又已有別於老子之「道」。《管子》之「道」,已經包含著兩個層次。其一,「道」是「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且包容著「精氣」的物質實體,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其二,「道」的活動,具有「人不能固」的規律,誰也不能違背。「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形勢〉)。而此中所謂「天道」,就自然觀而言,是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就社會觀而言,則是指治國治民的基本法則。很明顯,這是對老子之「道」的改造、補充和發展。
《管子》對「法」的論述也頗詳盡。〈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然後將「法」的「準則」這一概念加以擴展,衍為「法令」、「法律」、「法制」。〈法法〉說:「法者,民之父母也。」〈權修〉說:「法者,將立朝廷者也。」〈禁藏〉說:「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重令〉說:「治民之本」,「莫要於令」。這些論述,簡明扼要地闡釋了「法」的巨大作用,強調了「法」的極端重要性。國君以之為治民的根本,百姓以之為活命的依憑,都是不可須臾廢離的。〈明法解〉說:「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七臣七主〉說:「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心術上〉說:「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些論述,進而將法、術、勢融為一體,無疑是對法家思想的綜合與補充。
但《管子》的「重法」思想的特點,並不在於此,而在於通過對老子哲學的改造,為「法」提供了哲學論證,實現了「道」與「法」的結合。〈七法〉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不明於則,而欲錯儀畫制,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這些論述,從「常則」的角度,論證了「法」的客觀性。〈版法解〉說:「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形勢解〉說:「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形勢〉說:「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些論述,從「天常」、「地則」即「道」的永恒性,論證了「法」的常存性。正因為《管子》既重「道」,又重「法」,視「道」為宇宙之大法,視「法」為社會之大道,因而「道法並重」、建常立儀的思想,成了全書的主線。
《管子》雖重道、法,但並不排斥禮、義。〈牧民〉說:「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很重要,是為鞏固國家政權所必須堅持的基本準則。那麼,禮、義與道、法的關係怎樣呢?〈心術上〉有一段頗為通盤的解釋:「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末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也。」這就是說,萬物稟「道」而生成之後,便各自具有其一定的形狀和性質。體現在社會生活中,就是「義」。將各種不同事物、人事關係制度化,就是「禮」。將這類關係、制度統一起來,用政權的強力加以保證,就是「法」。而仁義禮法的結合點則是「道」,四者都是以「道」為本體的。尊虛靜,尚變化,重道、法,容禮、義,將齊魯之學的旨義熔鑄一爐,這就是《管子》哲學思想的特徵。
下面談談教育思想:
《管子》的治國理論,是既重視法治,又重視德治。而「德治」的成功,其主要措施,是靠灌輸,靠感化,亦即教育。因此,《管子》對教育問題,也多所論及。〈權修〉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又說:「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顯然,《管子》的作者,已經認識到法律和道德是人類社會的兩大支柱。要鞏固政權,要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單靠法治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發揮教育這一特殊手段的作用。教育民眾,提高民眾的素質,是百年大計,是治政之本,是「一樹百穫」的美事。
「樹」什麼人?要「樹」明禮義、知榮辱的賢人。「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牧民〉)。掌握了教育,造就了明禮義、知榮辱的賢才,養成了明禮義、知榮辱的民風,國家便能長治久安。
如何「樹」人?一是政策誘導。〈五輔〉說得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用政策、政績來教育人們,是最起作用的措施。如果施行「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君臣下〉)論功行賞、不分貴賤的政策,即任人唯賢而不唯親,視德譽為重而不論資排輩,賞功不但及於執法有功之臣、師旅有勞之將、治理有方之官,且施及農工技藝之徒而不計身分尊卑,那麼,這種政策導向,就是最簡明的教科書,必將對整個國家的社會風氣產生良好的影響。二是興辦學校。這是造就人才的主要途徑。〈弟子職〉就是關於學校教育的專論。它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內容最豐富、篇章最完整、記述最明晰、年代最久遠的學校教育史料。雖然主要篇幅只是記述校規學則,但其中關於進德修業、尊師重教、寓教於行、使習與性成之類的教育觀點與教學方法,至今仍可借鑑。三是優化社會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說,環境就是學校,風氣就是教師。《管子》提出「教訓成俗」,即通過引導、教育,形成良好的環境和風氣,亦即「必先順教,萬民鄉風」(〈版法〉),這是很有見地的。「萬民鄉風」的條件之一,是「先順教」,即有人領頭,垂範導向。〈牧民〉說:「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君主與各級官員,如果能夠「立儀以自正」(〈法法〉),以身垂範,顯示出一種優良作風,對全國民眾,就會有很好的引導作用。「萬民鄉風」的條件之二,是遞相傳導,相互模仿。〈小匡〉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 (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餘農工商三民,亦復如此。由於群居相染,相沿成習,導向作用也就更加強烈而深入。當然,「萬民鄉風」局面的形成,也還需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即〈七法〉所謂「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被潛移默化。待到「教訓習俗者眾,則民化變而不自知也」(〈八觀〉。
但無論政策導向也好,興辦學校也好,優化環境也好,要使教育能發揮其自身的作用,必須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這已成為千古名言。對於這個著名的論斷,韓非在〈五蠹〉中論述得很明確:「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王充在《論衡‧治期》中也有一段精闢的解說:「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集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集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之性,在於歲之饑穰。」《管子》的論斷和韓非、王充的解說,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而深刻地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即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教育活動,必然要受經濟生活的制約。
此外,無論政策誘導也罷,學校造就也罷,環境陶冶也罷,以教育作為治國的一項措施來說,顯然具有其自身的、任何別的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特點。對此,〈侈靡〉中有一段極妙的描述:「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窵然若皜月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這段文字十分精彩,極為形象地說明了教育的作用,在引導人們追求賢,追求善,追求美。特點是感化受教育者,使之潛移默化。教育的過程,就好像秋雲高揚遠翥,能夠激起人們沈思;又好像夏雲含雨,溼潤清涼,能夠浸及人們的肌膚;深幽得像皓月的寧靜,能夠觸發人們的怨慕;悠悠如流水,引人遐思,令人神往。教育的首要因素,必須是在上位者,能夠率先垂範,好比秋雲初現,讓賢者和不肖者,都潛移默化。人皆有向善求賢之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加上教育誘導,不肖者雖多,焉能不化?這段富有詩意的論述文字,真個把教育自身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這一特點,形容得淋漓盡致。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自然科學思想:
《管子》中論及自然科學思想的篇幅不少,涉及的問題也比較廣泛。除了天文、曆法、農、林、牧、鹽、礦業之外,還論及了城建、水利、土壤、樂律等方面的內容。
〈乘馬〉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度地〉說:「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又說:「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材,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這些,是《管子》關於建國立都、抉擇地理的總原則。這個原則的出發點,是要求凡立都興城,其規劃與布局,要有利於經濟、文化的發展,但首先必須服務於軍事、經濟、文化的需要,必須受軍事的制約。〈八觀〉說:「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這是對於城建設施的具體要求。這種築城必須堅牢,街道宜少外通,城邑既要是人口聚集的經濟、文化中心,又要近乎是軍事堡壘的理論,反映了古代城市建築的一般規律。這類關於城建的論述,是古代城建科學的總結,也是我們探討、研究古代城建歷史的鑰匙。
〈度地〉則是一篇甚有學術價值的治水專論。全文從都邑建設的地理條件,而言及水、旱、風霧雹霜、厲、蟲「五害」,由「五害」而重點論及治水,提出了一套頗為完整而具體的治水方案。諸如怎樣選拔治水人才,怎樣組織治水勞力,怎樣徵集治水器材,怎樣確定治水季節,怎樣保護壩基堤防等等,皆有所論及。尤可貴者,在於提出了蓄泄並舉、常備不懈的方針。這一方針,一直為後世治水者所沿用。
〈地員〉是一篇關於土壤與物產的專論,全面分析了土壤的優劣、性狀及類別,記述了農產、畜產、果樹、林木與其他物產的品種及產量情況。分土壤為三類六等九十種,記糧食作物為三十六種。記述之完整,分類之細密,實為我國古代農家文獻所罕見。〈地員〉還提出了「五度相生律」、「三分損益法」。這是關於我國古代樂律學的最早記載。「五度相生律」的數理律學,形成了中華律學的傳統理論,至少早於希臘畢達哥拉斯的「五度循環定律法」一個半世紀。「三分損益法」則是世界上最早的樂律計算法。
綜上所述,《管子》涉及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若就其思想派系而言,則兼容著道家、法家、儒家、兵家、陰陽家、農家、醫家等學派的思想和主張。但細繹起來,卻並不同於典型意義上的各家,而是有所交匯、貫通、變化和創造。可以說是博採百家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思想派系,成為一個以「道」、「法」思想為核心的綜合體。若命之曰「雜家」,或者「通家」,也許更符合《管子》思想的實際。
另一方面,又正因為《管子》內容紛繁複雜,且不出一人之手,間有抵牾之處,加之詞義古奧,簡篇錯亂,文字奪誤,因而歷來號稱難讀之書。幸自有唐國子博士尹知章為之作注以來,賢者相繼或校勘,或詮釋,篳路藍縷,代有開掘。僅郭沫若《管子集校》開列「所據《管子》宋明版本」,即有宋楊忱本、陸貽典校劉績《補注》本、明抄劉績《補注》本、十行無注古本、朱東光《中都四子》本、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等十七種;所開列「引用校釋書目提要」,即有豬飼彥博《管子補正》(日本寬政十年刊本)、洪頤煊《管子義證》、王念孫、王引之《讀書雜志》、安井衡《管子纂詁》(日本元治元年刊本)、俞樾《諸子平議》、戴望《管子校正》、王紹蘭《管子說》、何如璋《管子析疑》、孫詒讓《札迻》、張佩綸《管子學》、陶鴻慶《讀管子札記》、姚永概《慎宜軒筆記》、劉師培《管子斠補》、尹桐陽《管子新詮》、李哲明《管本校義》、黃鞏《管子編注》、石一參《管子今詮》、顏昌嶢《管校異義》、于省吾《管子新詮》、馬非百(元材)《管子輕重篇新詮》等四十二種之多。以上所錄著述,為拙作多所引用者。然拙作反覆引用者,尚有許維遹、聞一多、郭沫若諸前輩之論。具瞻前修,霑溉後學,集累代之精華,成今日之巨帙。爰在付梓之前,謹向給予拙作啟迪甚多的戴望(篇目、語譯、注釋均以其《管子校正》作為底本)、石一參、馬非百、郭沫若、趙守正等前賢今哲,表示崇高的敬意。惟恐學識淺陋,執筆倉卒,拾芥遺珠,領會謬誤之處,自所難免。臨深履薄,每懷惴惴,敬祈海內外方家及讀者有以是正。
目次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 讀
卷 一
牧民第一 三
形勢第二 一三
權修第三 二二
立政第四 三五
乘馬第五 五一
卷 二
七法第六 七一
版法第七 八五
卷 三
幼官第八 九三
幼官圖第九 一一八
五輔第十 一二九
卷 四
宙合第十一 一四三
樞言第十二 一六八
卷 五
八觀第十三 一九一
法禁第十四 二○六
重令第十五 二一五
卷 六
法法第十六 二二七
兵法第十七 二五○
卷 七
大匡第十八 二六三
卷 八
中匡第十九 二九三
小匡第二十 二九九
王言第二十一(亡) 三三三
卷 九
霸形第二十二 三三七
霸言第二十三 三四六
問第二十四 三六一
謀失第二十五(亡) 三七○
卷 十
戒第二十六 三七三
地圖第二十七 三八五
參患第二十八 三八八
制分第二十九 三九三
君臣上第三十 三九七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四一七
小稱第三十二 四三六
四稱第三十三 四四五
正言第三十四(亡) 四五一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四五五
下 冊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四九七
心術下第三十七 五○九
白心第三十八 五一七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五三三
四時第四十 五四四
五行第四十一 五五六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五七一
正第四十三 五七八
九變第四十四 五八二
任法第四十五 五八五
明法第四十六 五九八
正世第四十七 六○三
治國第四十八 六○九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六一七
封禪第五十 六三二
小問第五十一 六三六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六五七
禁藏第五十三 六六九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六八五
九守第五十五 六九○
桓公問第五十六 六九七
度地第五十七 七○○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七一五
弟子職第五十九 七三七
言昭第六十(亡) 七四三
修身第六十一(亡) 七四四
問霸第六十二(亡) 七四四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七四四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七四七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七八一
版法解第六十六 七八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八○○
匡乘馬第六十八 八二○
乘馬數第六十九 八二五
問乘馬第七十(亡) 八三○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八三三
海王第七十二 八三七
國蓄第七十三 八四二
山國軌第七十四 八五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八六六
山至數第七十六 八八○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九○一
揆度第七十八 九一一
國准第七十九 九二九
輕重甲第八十 九三四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九六三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九八一
輕重丁第八十三 九八二
輕重戊第八十四 一○○六
輕重己第八十五 一○一八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一○二七
上 冊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 讀
卷 一
牧民第一 三
形勢第二 一三
權修第三 二二
立政第四 三五
乘馬第五 五一
卷 二
七法第六 七一
版法第七 八五
卷 三
幼官第八 九三
幼官圖第九 一一八
五輔第十 一二九
卷 四
宙合第十一 一四三
樞言第十二 一六八
卷 五
八觀第十三 一九一
法禁第十四 二○六
重令第十五 二一五
卷 六
法法第十六 二二七
兵法第十七 二五○
卷 七
大匡第十八 二六三
卷 八
中匡第十九 二九三
小匡第二十 二九九
王言第二十一(亡) 三三三
卷 九
霸形第二十二 三三七
霸言第二十三 三四六
問第二十四 三六一
謀失第二十五(亡) 三七○
卷 十
戒第二十六 三七三
地圖第二十七 三八五
參患第二十八 三八八
制分第二十九 三九三
君臣上第三十 三九七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四一七
小稱第三十二 四三六
四稱第三十三 四四五
正言第三十四(亡) 四五一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四五五
下 冊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四九七
心術下第三十七 五○九
白心第三十八 五一七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五三三
四時第四十 五四四
五行第四十一 五五六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五七一
正第四十三 五七八
九變第四十四 五八二
任法第四十五 五八五
明法第四十六 五九八
正世第四十七 六○三
治國第四十八 六○九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六一七
封禪第五十 六三二
小問第五十一 六三六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六五七
禁藏第五十三 六六九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六八五
九守第五十五 六九○
桓公問第五十六 六九七
度地第五十七 七○○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七一五
弟子職第五十九 七三七
言昭第六十(亡) 七四三
修身第六十一(亡) 七四四
問霸第六十二(亡) 七四四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七四四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七四七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七八一
版法解第六十六 七八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八○○
匡乘馬第六十八 八二○
乘馬數第六十九 八二五
問乘馬第七十(亡) 八三○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八三三
海王第七十二 八三七
國蓄第七十三 八四二
山國軌第七十四 八五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八六六
山至數第七十六 八八○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九○一
揆度第七十八 九一一
國准第七十九 九二九
輕重甲第八十 九三四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九六三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九八一
輕重丁第八十三 九八二
輕重戊第八十四 一○○六
輕重己第八十五 一○一八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一○二七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