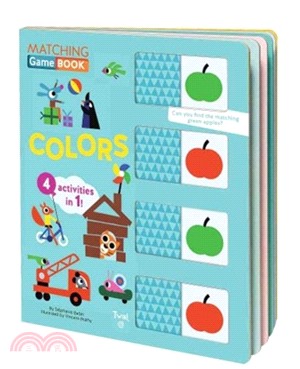定價
:NT$ 420 元優惠價
:90 折 378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1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業在讀大學生以及文藝愛好者,從事影劇創作和影劇欣賞的必讀教材之一種。
曹禺先生(萬家寶老師),生性柔弱,對人謙恭有禮,能編、導、演,一首莫札兒特的〈安魂曲〉,卻未能使他安魂。年輕時,為理想寫作。老了時,卻被迫為極權吶喊《豔陽天》下,卻使他老淚縱橫!良師益友,永遠懷念。
知名劇作家崔小萍老師
張耀杰這本文藝性學術傳記是有個人色彩的。作者對傳主評價的一個主要事實依據就是傳主的婚姻,特別是傳主對女性的態度。張耀杰寫作傳記的一大長處,是他不平面地列舉材料。他能讓人從材料的選擇和評價中看出自己的觀點,還有就是對傳主的負面東西毫不留情。像他這樣以解剖的眼光寫作傳記的,現在還不是很多,所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廈門大學文史學者謝泳教授
張耀杰1989年報考的是南京大學的影劇學研究生,很遺憾我把他給放跑了。在他之前我還把北京人藝的劇作家李龍雲給放跑了。我沒有想到張耀傑在文史研究方面表現得如此精彩,我認為他的這本書,是可以傳世的。
南京大學文藝史家董健教授
作者簡介
張耀杰
1964年生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文史學者,文藝史專家,傳記作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已經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話劇史》、《戲劇大師曹禺——嘔心瀝血的人間悲劇》、《影劇之王田漢——愛國唯美的浪漫人生》、《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百年懸疑:政學兩界人和事》、《懸案百年:宋教仁案與國民黨》等十餘部。
1964年生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文史學者,文藝史專家,傳記作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已經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話劇史》、《戲劇大師曹禺——嘔心瀝血的人間悲劇》、《影劇之王田漢——愛國唯美的浪漫人生》、《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百年懸疑:政學兩界人和事》、《懸案百年:宋教仁案與國民黨》等十餘部。
目次
題記:曹禺影劇的斯芬克斯之謎
第一章、曹禺早年的戲劇與情愛
一、童年時代的神道環境
二、南開中學的戲劇活動
三、處女小說的男權意識
四、中學時代的神聖初戀
五、罵人有理的時評雜感
六、一網打盡的天譴詛咒
七、清華園內的演劇與情愛
八、曹禺《雷雨》的橫空出世
九、《雷雨》的發表和出版
第二章、「絕子絕孫」的《雷雨》
一、原始情緒中的文化密碼
二、《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
三、周樸園的保家護種
四、周蘩漪的亂倫通姦
五、魯大海的天譴詛咒
六、周沖的陽光天堂
七、周萍的人性幽暗
八、魯四鳳的在劫難逃
九、天堂天譴的詩化悲劇
第三章、應運而生的《日出》
一、《雷雨》的演出與論爭
二、李健吾的《雷雨》評論
二、田漢、張庚論《雷雨》
四、與張彭春的再次合作
五、陳白露與民國美女王右家
六、曹禺對王右家的一往情深
七、王右家與羅隆基的情愛傳奇
八、王右家與羅隆基的絕情離異
九、應運而生的《日出》
十、《日出》演出的轟動效應
十一、周揚與黃芝岡「批評的批評」
第四章、《日出》中的陽光天堂
一、陳白露的「有餘」與「不足」
二、「奉有餘」的黃省三
三、「損不足」的李石清
四、從「有餘」到「不足」的潘月亭
五、「閻王」加「財神」的金八
六、空喊高調的方達生
七、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
八、「予及汝偕亡」的天譴詛咒
九、怕官仇富的陽光天堂
第五章、《原野》中的野蠻復仇
一、《原野》的創作與演出
二、保家護種的焦母
三、退化變種的焦大星
四、野蠻復仇的仇虎
五、花金子的黃金天堂
六、白傻子的愚不可及
七、原始情緒的全面推演
第六章、捨家愛國的《蛻變》
一、從南京到重慶
二、關於編劇術的演講
三、《全民總動員》
四、與時俱進的《正在想》
五、《蛻變》中的權與法
六、天譴罰罪的思想改造
七、捨家愛國的丁大夫
八、清官救星梁公仰
九、「屁」一般的孔秋萍
十、天人感應的陽光天堂
第七章、《北京人》的男權美夢
一、《蛻變》後的精神失落
二、方瑞與楊振聲的舊情往事
三、楊振聲與曹禺的師承關係
四、《北京人》的戲外故事
五、陰盛陽衰的男權王國
六、情景交融的秋聲秋韻
七、天人感應的精神強暴
八、天涯比鄰的謬托知己
九、天堂淨土的精神超度
第八章、《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一、美輪美奐的神話故事
二、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戀
三、盛夏之夜的「捨身愛人」
四、一男二女的男權美夢
五、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
六、「捨身愛人」的男權神話
七、與周恩來的親密交往
八、架不起的彼岸之《橋》
九、《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第九章、《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一、新時代的文藝高官
二、《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
三、一男二女的婚姻離散
四、《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五、《胡風在說謊》
六、反右運動的踴躍表現
第十章、垂老之年的人生
一、《膽劍篇》的「怪力亂神」
二、周恩來論「新的迷信」
三、政治風浪中的失魂落魄
四、《王昭君》的超凡入聖
五、撥亂反正的公開表態
六、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後記:曹禺影劇藝術的密碼模式
第一章、曹禺早年的戲劇與情愛
一、童年時代的神道環境
二、南開中學的戲劇活動
三、處女小說的男權意識
四、中學時代的神聖初戀
五、罵人有理的時評雜感
六、一網打盡的天譴詛咒
七、清華園內的演劇與情愛
八、曹禺《雷雨》的橫空出世
九、《雷雨》的發表和出版
第二章、「絕子絕孫」的《雷雨》
一、原始情緒中的文化密碼
二、《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
三、周樸園的保家護種
四、周蘩漪的亂倫通姦
五、魯大海的天譴詛咒
六、周沖的陽光天堂
七、周萍的人性幽暗
八、魯四鳳的在劫難逃
九、天堂天譴的詩化悲劇
第三章、應運而生的《日出》
一、《雷雨》的演出與論爭
二、李健吾的《雷雨》評論
二、田漢、張庚論《雷雨》
四、與張彭春的再次合作
五、陳白露與民國美女王右家
六、曹禺對王右家的一往情深
七、王右家與羅隆基的情愛傳奇
八、王右家與羅隆基的絕情離異
九、應運而生的《日出》
十、《日出》演出的轟動效應
十一、周揚與黃芝岡「批評的批評」
第四章、《日出》中的陽光天堂
一、陳白露的「有餘」與「不足」
二、「奉有餘」的黃省三
三、「損不足」的李石清
四、從「有餘」到「不足」的潘月亭
五、「閻王」加「財神」的金八
六、空喊高調的方達生
七、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
八、「予及汝偕亡」的天譴詛咒
九、怕官仇富的陽光天堂
第五章、《原野》中的野蠻復仇
一、《原野》的創作與演出
二、保家護種的焦母
三、退化變種的焦大星
四、野蠻復仇的仇虎
五、花金子的黃金天堂
六、白傻子的愚不可及
七、原始情緒的全面推演
第六章、捨家愛國的《蛻變》
一、從南京到重慶
二、關於編劇術的演講
三、《全民總動員》
四、與時俱進的《正在想》
五、《蛻變》中的權與法
六、天譴罰罪的思想改造
七、捨家愛國的丁大夫
八、清官救星梁公仰
九、「屁」一般的孔秋萍
十、天人感應的陽光天堂
第七章、《北京人》的男權美夢
一、《蛻變》後的精神失落
二、方瑞與楊振聲的舊情往事
三、楊振聲與曹禺的師承關係
四、《北京人》的戲外故事
五、陰盛陽衰的男權王國
六、情景交融的秋聲秋韻
七、天人感應的精神強暴
八、天涯比鄰的謬托知己
九、天堂淨土的精神超度
第八章、《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一、美輪美奐的神話故事
二、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戀
三、盛夏之夜的「捨身愛人」
四、一男二女的男權美夢
五、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
六、「捨身愛人」的男權神話
七、與周恩來的親密交往
八、架不起的彼岸之《橋》
九、《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第九章、《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一、新時代的文藝高官
二、《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
三、一男二女的婚姻離散
四、《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五、《胡風在說謊》
六、反右運動的踴躍表現
第十章、垂老之年的人生
一、《膽劍篇》的「怪力亂神」
二、周恩來論「新的迷信」
三、政治風浪中的失魂落魄
四、《王昭君》的超凡入聖
五、撥亂反正的公開表態
六、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後記:曹禺影劇藝術的密碼模式
書摘/試閱
曹禺本姓萬,名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田本相在《曹禺傳》中認為,曹禺於一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天津租界,也就是現在的天津河北區民主道二十三號曹禺故居所在地。另據劉清祥、董尚華著《中國戲劇大師——曹禺》考證,曹禺其實是出生於湖北潛江的萬氏塾館。
曹禺的親生母親產後三天就因病去世。生母的早亡以及由此而來的戀母情結,決定了他對於富有犧牲奉獻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聖美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年曹禺在致巴金信中表白說:
「人是很不幸的動物,因為他有敏銳的感覺。但正因如此,才產生宇宙間罕有的事物,美的人和美的詩和藝術。有時,我想自然賜與我的種種夠多了。我應該感謝母親給我以生命,尤其是我,我的母親生下我三天,便因產褥熱死去,她才十九歲。我對她沒有一點印象,只覺得一切做母親的都可憐,都偉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讓人心痛……」(1)
曹禺的父親萬德尊,字宗石,湖北潛江人,祖上幾代都是家境清貧、飽讀經書的私塾先生,致使萬德尊常有「窶人(窮人)之子」的浩歎。萬德尊十五歲考中秀才,後來到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求學,一九○四年被選派到日本留學深造,先後在振武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九年畢業的第六期學員。他的同學中先後成為大小軍閥的,有閻錫山、孫傳芳、趙恆惕、李烈鈞、程潛、李根源、胡謙、劉存厚、羅佩金、楊文愷、孔庚、張開儒、張鳳翽、盧香亭、顧品珍、周蔭人等人。
萬德尊學成歸國後,考中滿清政府的陸軍步兵科舉人,被直隸總督端方任命為直隸衛隊的標統。他先後娶過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姓燕,在萬德尊留學日本期間病死於湖北老家,留下長子萬家修和女兒萬家瑛兩個孩子。一九○九年冬天,萬德尊續娶武昌商人之女薛氏為妻,一年後生下曹禺即萬家寶。薛氏夫人去世後,萬德尊與薛氏的孿生妹妹薛詠南結為夫妻。
繼母薛詠南沒有生育,一直把曹禺當作親生兒子來看待。她是個戲迷,無論京戲、評戲、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韻大鼓、文明戲都愛看。曹禺三歲時就被繼母抱在懷裡到戲院看戲,潛移默化中成長為表演慾極強的一個小戲迷,家裡一本一本的《戲考》,被他翻得滾瓜爛熟、破爛不堪。薛詠南還是個小說迷,她喜歡讀《紅樓夢》,能夠把黛玉的《葬花詞》背誦得聲情並茂、滾瓜爛熟。《雷雨》中關於蘩漪的舞臺提示——「她是一個中國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靜,她的明慧,──她對詩文的愛好……」——中,就有薛詠南的影子。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曹禺接受田本相採訪時回憶說:「周樸園有我父親的影子,在蘩漪身上也可以找到我繼母的東西,主要是那股脾氣。」(2)
繼母還像曹禺戲劇中的周樸園、焦母、曾皓、梅小姐、鳴鳳、馮樂山那樣,是一位佛教信徒。她從小就教曹禺背誦《往生咒》中的經典咒語「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據曹禺在《〈日出〉跋》中介紹,一九一二年他兩歲生日時,「母親」薛詠南給他買來的「護神和玩物」中,就有他「最心愛的馬瓷觀音」。
辛亥革命特別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去世之後,萬德尊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命運,與以繼任大總統黎元洪為首的湖北幫捆綁在一起。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因為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萬德尊也只好賦閑回家,在天津義大利租界的二馬路三十六號過起寓公生活。他除了陪太太抽鴉片、與友人吟詩寫字之外,還在一次中風後很虔誠地念起了《金剛經》。
對於當年或官場得志或失意下野的軍閥政客來說,居住在外國人統治下的租界區裡誦經禮佛、皈依宗教,是十分時髦的一種普遍現象:段祺瑞下野後「復歸於禪」卻又不甘寂寞,還要發起「佛教救國」運動以撈取政治資本。山東膠東半島的小軍閥劉珍年,甚至命令士兵佩帶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挖掘西太后和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創辦號稱廟會道的教派並且自任道首,幾萬官兵都是他的道徒。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一個顧和尚,從此迷戀藏傳佛教,親自領著法師給受戒官兵發放受戒證章。馮玉祥在接受來自蘇聯的革命理論之前,曾經一度號稱是「基督將軍」。孫傳芳倒臺後與萬德尊一樣在天津租界充當頌經禮佛的居士寓公,最後依然沒有躲過血仇報復的血光之災。與萬德尊一起留學日本的閻錫山,乾脆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組織方法照搬到山西農村,在村、閭、鄰的行政網路之外,另外組織「息訟會」、「監察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村閭長都是省裡登記在案的「村幹部」,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用老百姓的話說,閻錫山通過「村幹部」控制農村社會,等於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抗日戰爭時期,閻錫山還組織過幫會式宗教團體「洗心團」,企圖利用宗教神道的神聖天理來鼓舞鬥志。
伴隨著父親萬德尊和繼母薛詠南的誦經禮佛,曹禺很小就開始有意識地接觸中外宗教。晚年曹禺在與田本相談話時回憶說:
「記得小的時候,有一段接觸過教堂。……少年時期,對生活有一種胡思亂想、東撞西撞的味道。接觸一下教堂,到裡邊去看看,似乎是想解決一個人生問題,究竟人到底應該走什麼道路,人應該怎麼活著,人為什麼活著,活著又為什麼?總之,是莫明其妙,覺得宗教很有意思。在清華大學時,有音樂唱片的欣賞,對巴赫的音樂有過接觸。我對佛教不感興趣,太講出世了,跟父親念了一段佛經,念不下去。讀《聖經》覺得文章漂亮。……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的《復活》,我讀過,我非常想看看復活節是怎麼搞的,也想看看大彌撒,參加參加。它為什麼叫人入迷?……一進教堂,就覺得它裡面很高很高,在幽暗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無邊的蒼穹,是異常寧靜肅穆,聖母像美麗得不得了。人一進教堂就安靜下來了,真好像使人的靈魂得到休息。其實我根本不信教,我現在是個共產黨員,我更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很喜歡教堂中那種寧靜肅穆的氛圍。」(3)
一九一七年,不滿七周歲的曹禺,曾經有過替大總統黎元洪「圓光」的經歷。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免去實力派軍閥段祺瑞的內閣總理職務。段祺瑞跑到天津通電全國,拒不承認黎元洪的此項命令,導致保皇派首領張勳率領辮子軍乘虛而入推行復辟。在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黎元洪和幕僚們想出依靠「圓光」來預測政局的辦法。由於萬德尊時任黎元洪的秘書,小小年紀的曹禺便有了直接為大總統效勞的機遇和榮耀。
所謂「圓光」,就是把童男子曹禺即萬家寶與另一名童女子關進黑屋子裡,讓他們把一張白紙貼在牆壁上,然後透過蠟燭的光線說出從白紙上看到了什麼?這種以童男童女的靈性可以交通神鬼的「圓光」法術,只是中國傳統道教巫術自欺欺人的一種老把戲,卻為喜歡表演的萬家寶提供了一次難能可貴的表演機會。在「圓光」過程中,當大人們問他看到什麼時,他煞有介事地把代神立言的靈童角色扮演得活靈活現,說是自己看到了打勝仗的千軍萬馬,而且從帽徽軍服上看出率領千軍萬馬的首領,就是大總統黎元洪……
與曹禺同時參加「圓光」的童女子,回答大人們的卻是什麼也沒有看見的老實話。關於自己在「圓光」中的表現,曹禺晚年在與田本相談話中解釋說:「我當時是順嘴溜出來的,講得那麼神氣。……其實,也不奇怪,家裡有客人來,他們談這談那,有時也說點有關時局的東西,我雖然不能全懂,但也多少知道一點點。當他們問我時,我就順著說了幾句。也許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演戲吧。」(4)
一個所謂的民選大總統和他手下為數眾多的精英智囊,在窮途末路、黔驢技窮之際,竟然要借助七、八歲的童男童女代神立言的老把戲,來預測自己連同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傳統神道文化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難能接軌,由此便可見出一斑。
曹禺的親生母親產後三天就因病去世。生母的早亡以及由此而來的戀母情結,決定了他對於富有犧牲奉獻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聖美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年曹禺在致巴金信中表白說:
「人是很不幸的動物,因為他有敏銳的感覺。但正因如此,才產生宇宙間罕有的事物,美的人和美的詩和藝術。有時,我想自然賜與我的種種夠多了。我應該感謝母親給我以生命,尤其是我,我的母親生下我三天,便因產褥熱死去,她才十九歲。我對她沒有一點印象,只覺得一切做母親的都可憐,都偉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讓人心痛……」(1)
曹禺的父親萬德尊,字宗石,湖北潛江人,祖上幾代都是家境清貧、飽讀經書的私塾先生,致使萬德尊常有「窶人(窮人)之子」的浩歎。萬德尊十五歲考中秀才,後來到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求學,一九○四年被選派到日本留學深造,先後在振武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九年畢業的第六期學員。他的同學中先後成為大小軍閥的,有閻錫山、孫傳芳、趙恆惕、李烈鈞、程潛、李根源、胡謙、劉存厚、羅佩金、楊文愷、孔庚、張開儒、張鳳翽、盧香亭、顧品珍、周蔭人等人。
萬德尊學成歸國後,考中滿清政府的陸軍步兵科舉人,被直隸總督端方任命為直隸衛隊的標統。他先後娶過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姓燕,在萬德尊留學日本期間病死於湖北老家,留下長子萬家修和女兒萬家瑛兩個孩子。一九○九年冬天,萬德尊續娶武昌商人之女薛氏為妻,一年後生下曹禺即萬家寶。薛氏夫人去世後,萬德尊與薛氏的孿生妹妹薛詠南結為夫妻。
繼母薛詠南沒有生育,一直把曹禺當作親生兒子來看待。她是個戲迷,無論京戲、評戲、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韻大鼓、文明戲都愛看。曹禺三歲時就被繼母抱在懷裡到戲院看戲,潛移默化中成長為表演慾極強的一個小戲迷,家裡一本一本的《戲考》,被他翻得滾瓜爛熟、破爛不堪。薛詠南還是個小說迷,她喜歡讀《紅樓夢》,能夠把黛玉的《葬花詞》背誦得聲情並茂、滾瓜爛熟。《雷雨》中關於蘩漪的舞臺提示——「她是一個中國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靜,她的明慧,──她對詩文的愛好……」——中,就有薛詠南的影子。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曹禺接受田本相採訪時回憶說:「周樸園有我父親的影子,在蘩漪身上也可以找到我繼母的東西,主要是那股脾氣。」(2)
繼母還像曹禺戲劇中的周樸園、焦母、曾皓、梅小姐、鳴鳳、馮樂山那樣,是一位佛教信徒。她從小就教曹禺背誦《往生咒》中的經典咒語「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據曹禺在《〈日出〉跋》中介紹,一九一二年他兩歲生日時,「母親」薛詠南給他買來的「護神和玩物」中,就有他「最心愛的馬瓷觀音」。
辛亥革命特別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去世之後,萬德尊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命運,與以繼任大總統黎元洪為首的湖北幫捆綁在一起。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因為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萬德尊也只好賦閑回家,在天津義大利租界的二馬路三十六號過起寓公生活。他除了陪太太抽鴉片、與友人吟詩寫字之外,還在一次中風後很虔誠地念起了《金剛經》。
對於當年或官場得志或失意下野的軍閥政客來說,居住在外國人統治下的租界區裡誦經禮佛、皈依宗教,是十分時髦的一種普遍現象:段祺瑞下野後「復歸於禪」卻又不甘寂寞,還要發起「佛教救國」運動以撈取政治資本。山東膠東半島的小軍閥劉珍年,甚至命令士兵佩帶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挖掘西太后和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創辦號稱廟會道的教派並且自任道首,幾萬官兵都是他的道徒。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一個顧和尚,從此迷戀藏傳佛教,親自領著法師給受戒官兵發放受戒證章。馮玉祥在接受來自蘇聯的革命理論之前,曾經一度號稱是「基督將軍」。孫傳芳倒臺後與萬德尊一樣在天津租界充當頌經禮佛的居士寓公,最後依然沒有躲過血仇報復的血光之災。與萬德尊一起留學日本的閻錫山,乾脆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組織方法照搬到山西農村,在村、閭、鄰的行政網路之外,另外組織「息訟會」、「監察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村閭長都是省裡登記在案的「村幹部」,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用老百姓的話說,閻錫山通過「村幹部」控制農村社會,等於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抗日戰爭時期,閻錫山還組織過幫會式宗教團體「洗心團」,企圖利用宗教神道的神聖天理來鼓舞鬥志。
伴隨著父親萬德尊和繼母薛詠南的誦經禮佛,曹禺很小就開始有意識地接觸中外宗教。晚年曹禺在與田本相談話時回憶說:
「記得小的時候,有一段接觸過教堂。……少年時期,對生活有一種胡思亂想、東撞西撞的味道。接觸一下教堂,到裡邊去看看,似乎是想解決一個人生問題,究竟人到底應該走什麼道路,人應該怎麼活著,人為什麼活著,活著又為什麼?總之,是莫明其妙,覺得宗教很有意思。在清華大學時,有音樂唱片的欣賞,對巴赫的音樂有過接觸。我對佛教不感興趣,太講出世了,跟父親念了一段佛經,念不下去。讀《聖經》覺得文章漂亮。……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的《復活》,我讀過,我非常想看看復活節是怎麼搞的,也想看看大彌撒,參加參加。它為什麼叫人入迷?……一進教堂,就覺得它裡面很高很高,在幽暗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無邊的蒼穹,是異常寧靜肅穆,聖母像美麗得不得了。人一進教堂就安靜下來了,真好像使人的靈魂得到休息。其實我根本不信教,我現在是個共產黨員,我更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很喜歡教堂中那種寧靜肅穆的氛圍。」(3)
一九一七年,不滿七周歲的曹禺,曾經有過替大總統黎元洪「圓光」的經歷。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免去實力派軍閥段祺瑞的內閣總理職務。段祺瑞跑到天津通電全國,拒不承認黎元洪的此項命令,導致保皇派首領張勳率領辮子軍乘虛而入推行復辟。在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黎元洪和幕僚們想出依靠「圓光」來預測政局的辦法。由於萬德尊時任黎元洪的秘書,小小年紀的曹禺便有了直接為大總統效勞的機遇和榮耀。
所謂「圓光」,就是把童男子曹禺即萬家寶與另一名童女子關進黑屋子裡,讓他們把一張白紙貼在牆壁上,然後透過蠟燭的光線說出從白紙上看到了什麼?這種以童男童女的靈性可以交通神鬼的「圓光」法術,只是中國傳統道教巫術自欺欺人的一種老把戲,卻為喜歡表演的萬家寶提供了一次難能可貴的表演機會。在「圓光」過程中,當大人們問他看到什麼時,他煞有介事地把代神立言的靈童角色扮演得活靈活現,說是自己看到了打勝仗的千軍萬馬,而且從帽徽軍服上看出率領千軍萬馬的首領,就是大總統黎元洪……
與曹禺同時參加「圓光」的童女子,回答大人們的卻是什麼也沒有看見的老實話。關於自己在「圓光」中的表現,曹禺晚年在與田本相談話中解釋說:「我當時是順嘴溜出來的,講得那麼神氣。……其實,也不奇怪,家裡有客人來,他們談這談那,有時也說點有關時局的東西,我雖然不能全懂,但也多少知道一點點。當他們問我時,我就順著說了幾句。也許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演戲吧。」(4)
一個所謂的民選大總統和他手下為數眾多的精英智囊,在窮途末路、黔驢技窮之際,竟然要借助七、八歲的童男童女代神立言的老把戲,來預測自己連同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傳統神道文化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難能接軌,由此便可見出一斑。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