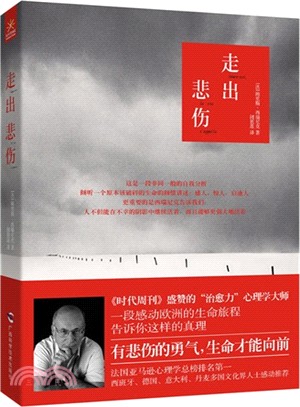商品簡介
《走出悲傷》,一位世界級心理學大師的生命剖析。
《走出悲傷》中,心理學家西瑞尼克不懼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尋那些已被埋藏的記憶,質問那些記憶的陷阱,并試圖說出在重獲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說而無法說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傷的心路歷程。他以自身經歷告訴那些心中有傷的人,走出悲傷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聯系,二是相信生命與生俱來的內在能量。
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生命的悲傷和命運的曲折,是生活在這塵世中無法避免的修行,我們不能阻止和壓抑自己的情緒,但可以選擇與悲傷相處,克服悲傷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陰影中繼續活著,而且能夠更強大地活著。
要有悲傷的勇氣,生命才能向前。
作者簡介
【法】鮑里斯·西瑞尼克(Boris Cyrulnik),心理學家,心理咨詢師,人類和動物行為學家,土倫大學教授,在歐洲領導著多個學術前沿的研究室。以在心理創傷方面的研究享譽世界。
身為一個猶太人,他童年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并在戰爭中失去了父母、朋友,生活自此動蕩,七歲的他作為孤兒還被特意安排越過敵軍的封鎖給法國軍隊送情報。直到二戰結束,他的世界才得以靜下來。
此后他接觸到心理學,開始進行系統地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他逐漸認識了自我,治愈平息了過去的回憶,并最終成為了治愈無數人的心理學家。
名人/編輯推薦
當代最具盛名的“治愈力”專家
《時代周刊》盛贊的心理學大師
一段感動歐洲的心路歷程
一個原本該破碎生命的傾情講述
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
有悲傷的勇氣,生命才能向前
法國亞馬遜心理類總榜排名第一
西班牙、德國、意大利、丹麥多國文化界人士感動推薦
西瑞尼克治愈了眾多人,眾多國家
——《時代周刊》
海報:
目次
在悲傷中更強大的活著
記憶是個鐘愛討好他人的懦夫,這個懦夫習慣于自欺和欺人,尤其是在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大創傷后,過去的陰影會像一雙大手一樣捂住當事人的嘴,讓其對往事緘口不語。
疼時說疼是正常人的反應(義者、勇士除外),所以如果你還有力氣吐槽,那不用擔心,你的心理健康,至少,你患抑郁癥、自閉癥的幾率降低了。如果你滿心傷痕,不僅不哭,還要笑給別人看,那么,你可能已經患病。
這種病叫選擇性沉默,或者說,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創傷心理癥候群(病入膏肓者的境界)。幼年時經歷的身體、心理上的虐待,父母的離世、戰爭、自然災害等,都可能在經歷者腦海里留下深深的記憶,像大大的傷口愈合留下駭人的傷疤,讓他們成為一名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間失格》的主人公葉藏,敏感的他幼年時遭到傭人侵犯。不講述,不哭訴,忍氣吞聲,盡管他在心里一直大罵,沒有比傭人的行為更丑陋、低級的事情了。把憤怒、厭惡掩藏起來,連同那個真實而重傷的自己。他一面用滑稽的言行討好他人,另一面,他看著人們的奇怪舉動,感到詫異、扭曲,沒有認同感,沒有歸屬感。
別人眼中,葉藏是個幽默、優秀的樂天派;可是,只有葉藏知道,自己對這個世界是多么懼怕。
童年被侵犯的記憶揮之不去,猶如黑色的水墨浸透葉藏的眼睛,讓他覺得精彩不屬于自己。那段記憶是個幽暗的地牢,葉藏囚禁在里面,一輩子都沒走出來,葬身在那里。
不控訴,不訴苦,不說實話,因為他們對“向人訴苦”這種事不抱任何希望。深諳世事的人們總能想出花言巧語調侃傷痛。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仿佛膽小的軟體動物,有時甚至會被幸福所傷。
如果說,太宰治用小說的形式剖析了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的真實內心,那么,鮑里斯·西瑞尼克則在這本書中,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心理學的創傷療法,給囚禁在地牢里的人帶去了光,帶他們找到超越痛苦的勇氣。
太宰治安撫傷痛,鮑里斯治愈傷口。
鮑里斯在童年的時候遭遇世界上最殘忍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心智還未成熟時失去父母,在還未來得及領悟幸福時,就見證了生活的冷酷和人性的殘忍。身世不能選擇,但是作者卻要為不在能力掌控范圍內的事遭遇歧視、仇恨、逮捕、逃亡和背叛。
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6歲的孩童在陌生人之間輾轉,最糟糕時差點喪命,最幸福的時候忘記自己隨時會喪命。無論是美好還是糟糕,孩童將其記下,然后在記憶里無限放大扭曲的自我認知:我是個怪物,比洪水猛獸更可怕。
悲慘的記憶比悲慘本身更可怕。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發現那是多么荒謬、多么瘋狂的時期。但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無法從那樣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斷掙扎。我身處其中,我與困境纏斗,但我感覺自己心臟的位置上像是戳著一塊木頭,我的腦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駭人的怪物。這不是個比喻,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沒有家,沒有過去,別人覺得我是個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過披著人皮的軀殼罷了。”
單是讀作者的這段文字都感同身受地后怕。心臟被戳了木樁的那種鈍疼,腦子如稻草一般的迷惑掙扎。認定自己是異類,所以孤單,因為孤單,所以想要從別人身上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恐怖沒有定義,對惡沒有概念,還不了解可怕所以不會害怕。傷口已經留下了,但是痛感還未被感知,明明已經狀態不佳,卻對人說:“我很好。”
“披著人皮的軀殼”真的是一個太貼切的比喻。
像太宰治筆下的葉藏一樣,鮑里斯說每個心理創傷癥候群患者心里都有一個地牢,他稱其為“地下室”,一個可供“取悅他人的小丑”卸下油彩,展露真實表情的避難所。不堪回首的往事鎖住心房,也封閉了傷惘者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對幸福的感知。
痛苦有多深,回憶就會有多沉,走不出去的痛苦回憶,即使手無寸鐵,也會讓你遍體鱗傷。反過來,再深重的痛苦也可能化作嘴角一抹自信的微笑。
人不但可以從創傷中走出來,還可以更強大地活著。
人們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作為一名從創傷中走出來的心理醫生,鮑里斯·西瑞尼克更懂得如何讓你卸下堅強的偽裝,給痛苦的記憶找到出口,讓你和往事溫暖相擁。
世界上60億人口,疼痛每天都會牽動一些人的敏感神經。當疼痛在時間的流逝下成了“疼過,痛過”,人們就應該學著與回憶和平相處,哪怕有天想起來,也不會覺得痛不欲生。沒有哪個人完全快樂,也沒有哪個人沒有過去,你我不是心理癥候群患者,可是我們心里依舊有傷。那個你想起就會落淚心疼的人,那段你想起就會讓世界暗淡的往事,何嘗不是你沒有安放好的記憶?
真正的傷痛無法言說,看不見的傷口最疼,讀讀心理學家的創傷獨白,和那個一直躲在地下室的自己談談。傷痛不是痛到無法恢復,只是忘記也需要練習,你才能放下你不曾向別人說起,卻讓你在午夜夢回時眼角含淚的那些事,那個人。
噓,我是猶太人
那年我六歲,“死”這個詞于我而言顯得過于生澀,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兩年里,我才對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來。
法爾熱太太穿著長睡衣,一邊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邊說道:“如果你們放他一條生路,人們就不會以為他是猶太人了。”我很震驚,這些男人顯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聽完法爾熱太太這番話,我明白了他們用槍指著我的緣由——我是猶太人!
猶太人意味著什么,我一無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
他們把我弄醒,一只手拿著槍,另一只手拿著電筒,頭頂著氈帽,鼻梁上架著黑色眼鏡,上衣的領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難道槍斃一個小男孩,人們就要這打扮嗎?
一個看起來像長官的男人回應道:“立刻讓這個孩子消失,否則他很快就會成為希特勒的敵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錯在哪里。
這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在我身體里催生出一個扎根于我靈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槍,夜色中的黑色眼鏡,走廊里肩挎長槍的德國士兵,那句揭露我未來罪犯身份的話語……
我即刻明白了: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顧惜生命的寶貴。
然而,你們一定難以置信,在經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夜晚后,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當時的我不過是個年僅六歲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爾多的猶太人突然被逮捕,而當時的我還無法對時局做出判斷,不知道事情為什么就發生了。
對于第二次出生的經歷,少了記憶之外的點醒,我很難理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去年,我被邀請到波爾多,去法語地區基督教廣播電臺錄制一期文學節目。那日天氣晴朗,節目錄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氣爽。我正朝出口走,這時,陪在我身旁的記者對我說:“第一條路左轉,在路盡頭你會看見有軌電車車站,乘上電車你就能到梅花廣場,那里是波爾多的中心地帶。”
他這么說著,某些情景闖入了我的腦海:那個夜晚,那條街道,沿著人行道用篷布蓋住的卡車,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車,武裝的德國士兵圍追堵截……我暗自驚訝,是什么觸動了回憶的按鈕,為什么往昔遙遠的回憶來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錄制節目這天,我約了人在莫拉書店碰面。
我來到車站,看到一棟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著:“兒童醫院”。
記憶中,法爾熱太太的女兒,瑪格特的告誡猛然響起:“千萬別去兒童醫院那條街,那里人來人往,你可能會被揭發。”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雙腳,惘然若失,停下腳步時,我早已穿過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過了法爾熱太太家門口,卻全然沒有察覺。
1944年后,我和法爾熱太太再未謀面,不過總有一些跡象,比如石子路間的草坪,再比如階梯的風格,觸發記憶,讓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場景。即便心情平和時,這樣那樣的跡象依舊會喚醒過去的種種。悲慘的經歷往往經不住生活點滴瑣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絲馬跡,也會牽扯出回憶的千頭萬緒。我發現,那些兒時的經歷從未被遺忘,只是自覺忘記,自動屏蔽,僅此而已。
1944年1月,從未料到我的生活會卷入這個故事。誠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邊緣徘徊過的人:“我感受過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為我的一種人生經歷 ……”那時,我年僅六歲,所有發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跡。死亡體驗銘刻在記憶中,我成長的同時它也在慢慢發育。
也許,是我害死了媽媽
回憶讓一些場景顯得意義深長。
第一個場景:德國軍隊魚貫穿過寬闊的林蔭大道。士兵們步伐穩健,腳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氣勢,我看得出神。音樂響起,士兵們開始邁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馬的側邊,節奏鏗鏘頓挫,既叫人嘆好,又讓人心生懼怕。一匹馬在行進中打滑跌倒,士兵們把戰馬扶起來,再次發號施令。這難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嗎?但我身旁的人都淚流滿面,我感到費解。
第二個場景:我隨母親來到郵局,看見德國士兵結成小隊在城里溜達。他們沒有帶槍,也沒戴軍帽,甚至連腰帶都沒系,這樣的衣著讓我覺得他們沒那么強橫兇猛。其中一個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遞給我幾粒糖果。母親眼疾手快,一下奪走我手中的糖果,還給士兵,口中還念念咒罵:“無論如何,都不準和德國人搭話。” 母親的舉止讓我很驚訝。沒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個場景:父親獲準休假,我們一家人去加龍河河畔散步。那天,父親和母親坐在一條長登上,而我在另一條長凳上玩子彈球,長凳一邊坐著兩個士兵。一個士兵撿起我的子彈球遞給我,一開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瞇瞇的,我還是接過了子彈球。沒過多久,父親再次回到部隊。自從那以后,母親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后來,我的父母失蹤了。
回想起我曾不顧母親的禁令和德國士兵交談,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與我有關,那么毫無疑問,正式因為我在談話中無意間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會被抓走了。”
一個孩子怎么可能解釋清楚父母失蹤的緣由,況且他對反猶太法聞所未聞,唯一的可能就是:我違反母親的禁令,和德國人搭話了。一系列相關的記憶碎片,片片組裝有如拼圖,讓過去的事情變得清晰。
我整理凌亂的記憶,得出這樣的結論: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離世并沒有讓我痛徹心扉。他們曾在我生命中出現,然后消失。對于他們的死,我毫無頭緒,我僅是得知他們消失了。我們曾一起生活,他們突然離去,沒有他們的日子,我無依無靠。
我成了孤兒,無家可歸,可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絕望總是大于痛苦,我的處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記得戰前的家庭生活,那時我才兩歲,牙牙學語,但仍舊記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廚房的正中堆著一堆煤炭,父親總是在廚房餐桌上讀報紙,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等著我自個脫下鞋子;我總跑去同一層樓的鄰居家,眼巴巴地盯著他們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歲的雅克,用橡膠箭射中我的額頭,我朝他高聲嚷嚷,說他一定會受到懲罰;男人們從大船上走下來,背著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無數靜默的場景我都還記得,這些正是我度過的戰前生活。
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身穿軍服。我得知父親加入了“外籍志愿者邊境軍團”,一支由猶太人和西班牙共和黨人組成的軍隊。大軍在蘇瓦松作戰,遭到重創。在那個時代,我自然不懂這些意味著什么,而今,我為有個軍人父親引以為豪,只是我不太喜歡那頂軍帽,兩個尖點看起來很滑稽。不過,有時候,我也反問自己:“兩歲的我真有這種感覺嗎?難道不是戰后看到照片引發的感覺?”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個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蒼鷹的翅膀,獅子的腦袋,盡管這樣的動物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烙在記憶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憶中的畫面本來真實,經過重組后形成回憶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實了。
一件事淪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簡單不過的碰面都會勾起回憶。但是,不愿去回憶,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圖爾德,1945年在美國軍隊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營,他身邊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為自己能夠幸存下來感到驚訝。后來,他成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學家,他不認為幸存者有罪,堅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對病人的心理治療中,精神分析學家和患者之間的會面交流,引發患者回憶的爆發:他的一個女病人對他敞開心扉,她向他講述了集中營的經歷:她曾是囚犯隊伍中的一員,那時她還是個孩子,被帶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她突然松開了握著母親的手,走開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頂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親走進了毒氣室,門合上,姐姐因此逃過一死。“這是至今為止她都不愿揭開的回憶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邊發生的回憶。母親離世,有關他們的回憶也隨之淡去。
……
書摘/試閱
在悲傷中更強大的活著
記憶是個鐘愛討好他人的懦夫,這個懦夫習慣于自欺和欺人,尤其是在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大創傷后,過去的陰影會像一雙大手一樣捂住當事人的嘴,讓其對往事緘口不語。
疼時說疼是正常人的反應(義者、勇士除外),所以如果你還有力氣吐槽,那不用擔心,你的心理健康,至少,你患抑郁癥、自閉癥的幾率降低了。如果你滿心傷痕,不僅不哭,還要笑給別人看,那么,你可能已經患病。
這種病叫選擇性沉默,或者說,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創傷心理癥候群(病入膏肓者的境界)。幼年時經歷的身體、心理上的虐待,父母的離世、戰爭、自然災害等,都可能在經歷者腦海里留下深深的記憶,像大大的傷口愈合留下駭人的傷疤,讓他們成為一名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間失格》的主人公葉藏,敏感的他幼年時遭到傭人侵犯。不講述,不哭訴,忍氣吞聲,盡管他在心里一直大罵,沒有比傭人的行為更丑陋、低級的事情了。把憤怒、厭惡掩藏起來,連同那個真實而重傷的自己。他一面用滑稽的言行討好他人,另一面,他看著人們的奇怪舉動,感到詫異、扭曲,沒有認同感,沒有歸屬感。
別人眼中,葉藏是個幽默、優秀的樂天派;可是,只有葉藏知道,自己對這個世界是多么懼怕。
童年被侵犯的記憶揮之不去,猶如黑色的水墨浸透葉藏的眼睛,讓他覺得精彩不屬于自己。那段記憶是個幽暗的地牢,葉藏囚禁在里面,一輩子都沒走出來,葬身在那里。
不控訴,不訴苦,不說實話,因為他們對“向人訴苦”這種事不抱任何希望。深諳世事的人們總能想出花言巧語調侃傷痛。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仿佛膽小的軟體動物,有時甚至會被幸福所傷。
如果說,太宰治用小說的形式剖析了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的真實內心,那么,鮑里斯·西瑞尼克則在這本書中,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心理學的創傷療法,給囚禁在地牢里的人帶去了光,帶他們找到超越痛苦的勇氣。
太宰治安撫傷痛,鮑里斯治愈傷口。
鮑里斯在童年的時候遭遇世界上最殘忍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心智還未成熟時失去父母,在還未來得及領悟幸福時,就見證了生活的冷酷和人性的殘忍。身世不能選擇,但是作者卻要為不在能力掌控范圍內的事遭遇歧視、仇恨、逮捕、逃亡和背叛。
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6歲的孩童在陌生人之間輾轉,最糟糕時差點喪命,最幸福的時候忘記自己隨時會喪命。無論是美好還是糟糕,孩童將其記下,然后在記憶里無限放大扭曲的自我認知:我是個怪物,比洪水猛獸更可怕。
悲慘的記憶比悲慘本身更可怕。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發現那是多么荒謬、多么瘋狂的時期。但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無法從那樣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斷掙扎。我身處其中,我與困境纏斗,但我感覺自己心臟的位置上像是戳著一塊木頭,我的腦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駭人的怪物。這不是個比喻,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沒有家,沒有過去,別人覺得我是個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過披著人皮的軀殼罷了。”
單是讀作者的這段文字都感同身受地后怕。心臟被戳了木樁的那種鈍疼,腦子如稻草一般的迷惑掙扎。認定自己是異類,所以孤單,因為孤單,所以想要從別人身上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恐怖沒有定義,對惡沒有概念,還不了解可怕所以不會害怕。傷口已經留下了,但是痛感還未被感知,明明已經狀態不佳,卻對人說:“我很好。”
“披著人皮的軀殼”真的是一個太貼切的比喻。
像太宰治筆下的葉藏一樣,鮑里斯說每個心理創傷癥候群患者心里都有一個地牢,他稱其為“地下室”,一個可供“取悅他人的小丑”卸下油彩,展露真實表情的避難所。不堪回首的往事鎖住心房,也封閉了傷惘者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對幸福的感知。
痛苦有多深,回憶就會有多沉,走不出去的痛苦回憶,即使手無寸鐵,也會讓你遍體鱗傷。反過來,再深重的痛苦也可能化作嘴角一抹自信的微笑。
人不但可以從創傷中走出來,還可以更強大地活著。
人們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作為一名從創傷中走出來的心理醫生,鮑里斯·西瑞尼克更懂得如何讓你卸下堅強的偽裝,給痛苦的記憶找到出口,讓你和往事溫暖相擁。
世界上60億人口,疼痛每天都會牽動一些人的敏感神經。當疼痛在時間的流逝下成了“疼過,痛過”,人們就應該學著與回憶和平相處,哪怕有天想起來,也不會覺得痛不欲生。沒有哪個人完全快樂,也沒有哪個人沒有過去,你我不是心理癥候群患者,可是我們心里依舊有傷。那個你想起就會落淚心疼的人,那段你想起就會讓世界暗淡的往事,何嘗不是你沒有安放好的記憶?
真正的傷痛無法言說,看不見的傷口最疼,讀讀心理學家的創傷獨白,和那個一直躲在地下室的自己談談。傷痛不是痛到無法恢復,只是忘記也需要練習,你才能放下你不曾向別人說起,卻讓你在午夜夢回時眼角含淚的那些事,那個人。
噓,我是猶太人
那年我六歲,“死”這個詞于我而言顯得過于生澀,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兩年里,我才對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來。
法爾熱太太穿著長睡衣,一邊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邊說道:“如果你們放他一條生路,人們就不會以為他是猶太人了。”我很震驚,這些男人顯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聽完法爾熱太太這番話,我明白了他們用槍指著我的緣由——我是猶太人!
猶太人意味著什么,我一無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
他們把我弄醒,一只手拿著槍,另一只手拿著電筒,頭頂著氈帽,鼻梁上架著黑色眼鏡,上衣的領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難道槍斃一個小男孩,人們就要這打扮嗎?
一個看起來像長官的男人回應道:“立刻讓這個孩子消失,否則他很快就會成為希特勒的敵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錯在哪里。
這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在我身體里催生出一個扎根于我靈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槍,夜色中的黑色眼鏡,走廊里肩挎長槍的德國士兵,那句揭露我未來罪犯身份的話語……
我即刻明白了: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顧惜生命的寶貴。
然而,你們一定難以置信,在經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夜晚后,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當時的我不過是個年僅六歲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爾多的猶太人突然被逮捕,而當時的我還無法對時局做出判斷,不知道事情為什么就發生了。
對于第二次出生的經歷,少了記憶之外的點醒,我很難理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去年,我被邀請到波爾多,去法語地區基督教廣播電臺錄制一期文學節目。那日天氣晴朗,節目錄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氣爽。我正朝出口走,這時,陪在我身旁的記者對我說:“第一條路左轉,在路盡頭你會看見有軌電車車站,乘上電車你就能到梅花廣場,那里是波爾多的中心地帶。”
他這么說著,某些情景闖入了我的腦海:那個夜晚,那條街道,沿著人行道用篷布蓋住的卡車,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車,武裝的德國士兵圍追堵截……我暗自驚訝,是什么觸動了回憶的按鈕,為什么往昔遙遠的回憶來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錄制節目這天,我約了人在莫拉書店碰面。
我來到車站,看到一棟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著:“兒童醫院”。
記憶中,法爾熱太太的女兒,瑪格特的告誡猛然響起:“千萬別去兒童醫院那條街,那里人來人往,你可能會被揭發。”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雙腳,惘然若失,停下腳步時,我早已穿過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過了法爾熱太太家門口,卻全然沒有察覺。
1944年后,我和法爾熱太太再未謀面,不過總有一些跡象,比如石子路間的草坪,再比如階梯的風格,觸發記憶,讓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場景。即便心情平和時,這樣那樣的跡象依舊會喚醒過去的種種。悲慘的經歷往往經不住生活點滴瑣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絲馬跡,也會牽扯出回憶的千頭萬緒。我發現,那些兒時的經歷從未被遺忘,只是自覺忘記,自動屏蔽,僅此而已。
1944年1月,從未料到我的生活會卷入這個故事。誠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邊緣徘徊過的人:“我感受過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為我的一種人生經歷 ……”那時,我年僅六歲,所有發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跡。死亡體驗銘刻在記憶中,我成長的同時它也在慢慢發育。
也許,是我害死了媽媽
回憶讓一些場景顯得意義深長。
第一個場景:德國軍隊魚貫穿過寬闊的林蔭大道。士兵們步伐穩健,腳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氣勢,我看得出神。音樂響起,士兵們開始邁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馬的側邊,節奏鏗鏘頓挫,既叫人嘆好,又讓人心生懼怕。一匹馬在行進中打滑跌倒,士兵們把戰馬扶起來,再次發號施令。這難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嗎?但我身旁的人都淚流滿面,我感到費解。
第二個場景:我隨母親來到郵局,看見德國士兵結成小隊在城里溜達。他們沒有帶槍,也沒戴軍帽,甚至連腰帶都沒系,這樣的衣著讓我覺得他們沒那么強橫兇猛。其中一個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遞給我幾粒糖果。母親眼疾手快,一下奪走我手中的糖果,還給士兵,口中還念念咒罵:“無論如何,都不準和德國人搭話。” 母親的舉止讓我很驚訝。沒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個場景:父親獲準休假,我們一家人去加龍河河畔散步。那天,父親和母親坐在一條長登上,而我在另一條長凳上玩子彈球,長凳一邊坐著兩個士兵。一個士兵撿起我的子彈球遞給我,一開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瞇瞇的,我還是接過了子彈球。沒過多久,父親再次回到部隊。自從那以后,母親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后來,我的父母失蹤了。
回想起我曾不顧母親的禁令和德國士兵交談,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與我有關,那么毫無疑問,正式因為我在談話中無意間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會被抓走了。”
一個孩子怎么可能解釋清楚父母失蹤的緣由,況且他對反猶太法聞所未聞,唯一的可能就是:我違反母親的禁令,和德國人搭話了。一系列相關的記憶碎片,片片組裝有如拼圖,讓過去的事情變得清晰。
我整理凌亂的記憶,得出這樣的結論: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離世并沒有讓我痛徹心扉。他們曾在我生命中出現,然后消失。對于他們的死,我毫無頭緒,我僅是得知他們消失了。我們曾一起生活,他們突然離去,沒有他們的日子,我無依無靠。
我成了孤兒,無家可歸,可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絕望總是大于痛苦,我的處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記得戰前的家庭生活,那時我才兩歲,牙牙學語,但仍舊記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廚房的正中堆著一堆煤炭,父親總是在廚房餐桌上讀報紙,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等著我自個脫下鞋子;我總跑去同一層樓的鄰居家,眼巴巴地盯著他們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歲的雅克,用橡膠箭射中我的額頭,我朝他高聲嚷嚷,說他一定會受到懲罰;男人們從大船上走下來,背著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無數靜默的場景我都還記得,這些正是我度過的戰前生活。
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身穿軍服。我得知父親加入了“外籍志愿者邊境軍團”,一支由猶太人和西班牙共和黨人組成的軍隊。大軍在蘇瓦松作戰,遭到重創。在那個時代,我自然不懂這些意味著什么,而今,我為有個軍人父親引以為豪,只是我不太喜歡那頂軍帽,兩個尖點看起來很滑稽。不過,有時候,我也反問自己:“兩歲的我真有這種感覺嗎?難道不是戰后看到照片引發的感覺?”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個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蒼鷹的翅膀,獅子的腦袋,盡管這樣的動物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烙在記憶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憶中的畫面本來真實,經過重組后形成回憶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實了。
一件事淪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簡單不過的碰面都會勾起回憶。但是,不愿去回憶,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圖爾德,1945年在美國軍隊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營,他身邊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為自己能夠幸存下來感到驚訝。后來,他成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學家,他不認為幸存者有罪,堅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對病人的心理治療中,精神分析學家和患者之間的會面交流,引發患者回憶的爆發:他的一個女病人對他敞開心扉,她向他講述了集中營的經歷:她曾是囚犯隊伍中的一員,那時她還是個孩子,被帶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她突然松開了握著母親的手,走開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頂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親走進了毒氣室,門合上,姐姐因此逃過一死。“這是至今為止她都不愿揭開的回憶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邊發生的回憶。母親離世,有關他們的回憶也隨之淡去。
……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