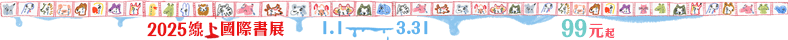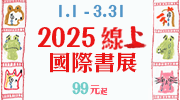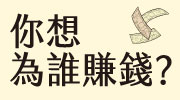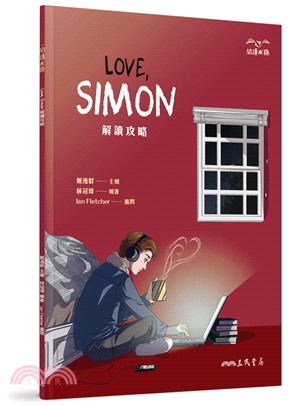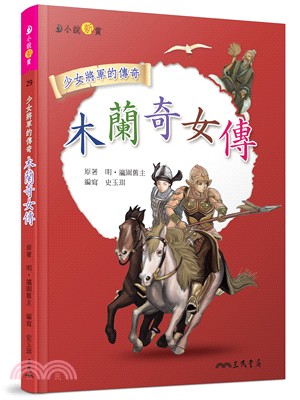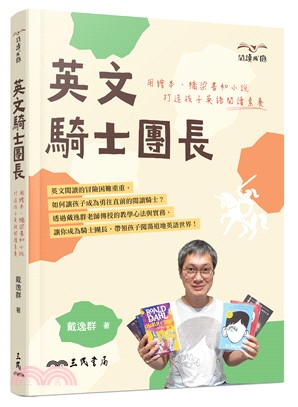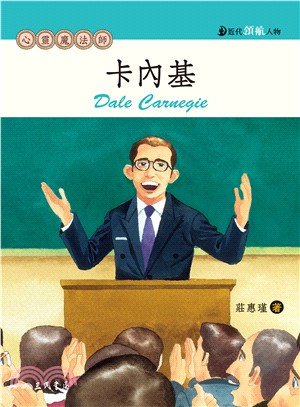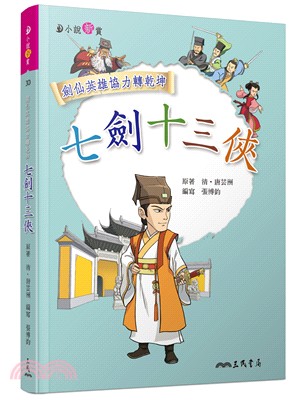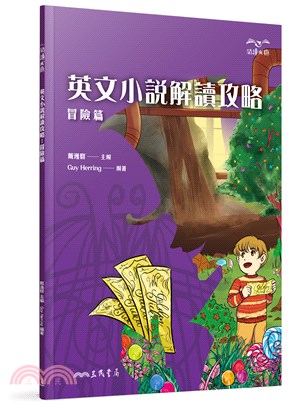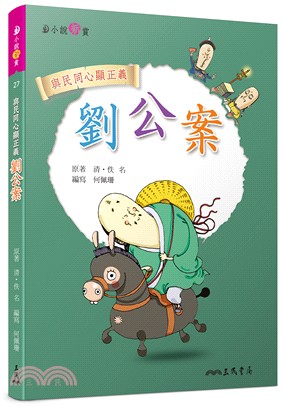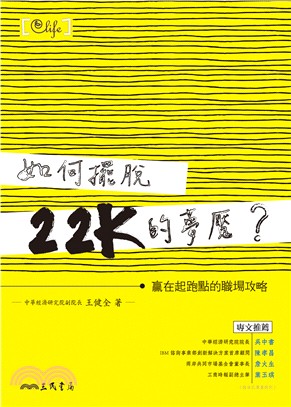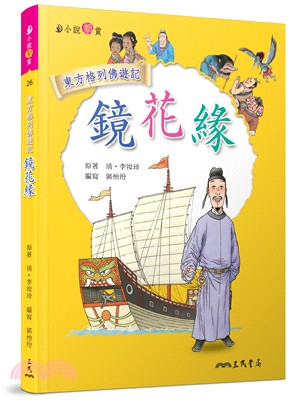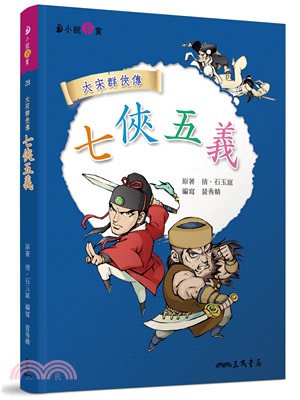庫存 > 10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4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宋詩是文化高度繁榮時代社會精神文化、人格修養、審美趣味和想像力的結晶。宋人順應時代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以新型的文化趣味和審美眼光觀照生活和自然,拓展題材,向深度開掘,並從藝術構思、手法技巧、遣辭造句等方面努力創新,創造了不同於唐詩的美學風格而與唐詩雙峰並峙,許多名篇佳作,更是膾炙人口,歷代傳誦不衰。
本書精選宋詩菁華360首,按體裁分體編排,並加詳細注釋和講解,為讀者領略宋詩之美提供參考。前言介紹宋詩文化特色和歷史地位,並概述宋詩發展歷程,可看作一篇簡明宋詩小史;書後還附有入選詩人小傳,都對讀者深入理解宋詩有所助益。
作者簡介
張鳴,北京大學教授,1954年生,山東成武人。198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執教。曾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與研究,講授「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古代文學通論」、「宋詩研究」、「唐宋詞選講」等課程。曾被評為北京大學第四屆「最受學生愛戴教師」。有〈誠齋體與理學〉、〈宋詩活法論與理學關係初探〉、〈從「白體」到「西崑體」〉、〈即物即理,即境即心〉、〈宋代詞的演唱形式考述〉等論文,以及《宋詩選》、《簡明中國文學史(下)》(合著)等著作。
序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追隨先師趙齊平先生研讀宋詩時,宋詩還時常被作為反面教材,宋詩研究更是門庭冷落。那時,常有師友對我的選擇表示疑惑,因此,常要向他們解釋為什麼。當然,更多的時候,是要找出理由說服自己。說服自己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不過歸根到底,好的理由還在宋詩本身。那時,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是手頭常翻的書,但讀這部詩選的感受,卻有很多困惑。《宋詩選註》是名著,學術水平之高,有口皆碑。錢先生選詩,眼光如炬,書中所選的作品都很優秀,尤其注釋所體現的博學睿智更令人佩服,許多注文都以過人的學養和感悟揭示出所選詩歌的精彩,可是在全書的序言中,錢先生在總體上卻對宋詩多有微詞,似乎並不怎麼欣賞。這種反差頗讓人疑惑,雖然後來對個中原委有一點了解,但當初的這個困惑,卻成了促使我去認真翻閱宋人詩集的重要原因。那時《全宋詩》還沒有編纂,研讀宋詩只能依靠閱讀宋人別集和《宋詩鈔》。好在北大圖書館藏書豐富,尤其原屬於燕京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中的宋人別集,不僅收藏全面、系統,版本豐富,而且書目卡片做得非常專業,學術信息一應俱全。當時一邊在趙齊平先生的指導下做《宋元文學史參考資料》的注釋,一邊根據燕大藏書目錄卡片的指引,將宋代詩人的別集,按時代先後一家一家讀下去。開始時受學養限制,對宋詩的好處並無太多體會。後來讀得多了,慢慢發現,其實宋詩真的不像世人批評的那樣一無是處,許多詩人作品,並不比唐詩遜色,有的甚至可以說是「英光四射」(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評歐陽修〈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詩的評語,參見本書所選該詩解說)。有了這樣的閱讀體會,再向他人介紹宋詩好處時,底氣雖不一定充足,但起碼內心比較踏實了。
總之,體會主要是兩條:
第一條是多讀。要想知道宋詩究竟如何,得沉下心來認真閱讀,不能輕信他人的批評意見。宋詩好不好,個人喜不喜歡,不讀,怎麼知道?明代楊慎曾拿了宋人張耒的〈蓮花〉、寇準的〈江南春〉、杜衍的〈雨中荷花〉和劉美中的〈夜度娘歌〉等四首詩,給倡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的何景明辨認是唐詩還是宋詩,結果何景明認作唐詩。這四首詩都以風神情韻見長,確實近似於唐詩,以至於專學唐詩的何景明也會看錯。後來楊慎告訴何景明「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何沉吟久之,強辯說:「細看亦不佳。」(見《升庵詩話》卷十二)。這件事只是歷代唐宋詩優劣之爭中的一個小插曲,不過卻反映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歷史上許多批評、否定宋詩的人,其實並未認真讀過宋詩。不讀,便不可能獲得對宋詩的真了解。古代禪宗大德主張「食必親嘗」,宋代高僧大慧宗杲也說:「佛性須是眼見始得。」(見《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這些話,移用於治學,也是至理名言。像何景明那樣未認真讀過多少宋人詩,便從先入為主的某些觀念出發否定宋詩,其實正是治學之大忌。因此,多讀才能真正進入宋詩,並獲得自己對宋詩的認知。
第二條是細讀。要真正認識宋詩藝術價值所在,僅多讀還不夠,還得在閱讀時仔細推敲。尤其是對宋詩特有的一些寫法,更需細心體會才能得其妙處。比如蘇東坡名作〈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此詩對西湖風景之美的描寫,立意在於說明美的豐富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於美的發現和欣賞,必須具備善於發現美的眼光和寬廣的審美心態(參本書該詩解說),不過就詩中具體比喻而言,卻有許多耐人咀嚼的意味。比喻的一般原則,多是用具體可感的直觀形象,比喻較為抽象不易感知把握的描寫對象,以增強形象刻畫之功。但在此詩中,詩人描寫的西湖是眼前實景,具體可見,可是作為喻體的「西子」,卻並不存在於現實時空,「西子」的形象,其實誰也沒見過,「西子」之美究竟如何,完全依賴於書本的記載和以往文學作品的描繪渲染。也就是說,「西子」之美,只存在於文字之中,存在於人們的意念想像之中,並不具有確定的形象,不同的人對「西子」之美的想像肯定各不相同,可以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西子」。因此,用這樣不確定的形象比喻眼前具體可見的西湖美景,其實並不符合比喻的一般原則。就具體寫法而言,這是「反常」的,但就效果而言,卻「反常而合道」,詩人正是利用了這種美的形象的不確定性特點,營造出無限想像的空間,讓不同讀者生發不同的聯想,從而帶領讀者真正領略西湖無往不在的美景,領略形象描寫中所蘊含的「理趣」。在宋詩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宋詩的想像力價值和審美創造的價值,所謂「英光四射」的東西,正是體現在這些地方。讀宋詩,若在這些方面草率看過,那就難免「入寶山而空回」了。總之,細讀才能真正領悟宋詩的妙處,保證入寶山而不空回。
當然,無論多讀,還是細讀,都不能只讀宋詩本身,要想真正理解宋詩,還得讀唐詩,只有讀懂了唐詩,才能認識宋詩的傳承和新變。此外,還應該強調,宋詩的時代特色,與宋代文化的繁榮密切相關。在宋代繁榮興盛的文化氛圍中,宋代文學,豐富全面,各種文類共存共榮,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了繁榮的文學景觀。古文、賦、駢文、筆記等由士大夫階層掌握的文體,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革新發展;話本、諸宮調、鼓子詞、雜劇、唱賺等由新生的各種民間通俗文藝派生的通俗文學,也正式進入文學史的領域,成為此後文學主流的源頭;而興起於唐代的音樂文學曲子詞,也在宋代達到了發展的高峰。宋詩就是在這樣全面繁榮的文學景觀之中生存發展,在其他文體的輝映下,成為宋代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因此,要真正了解宋詩,只讀詩歌本身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廣泛閱讀宋人的其他文學作品,並廣泛涉獵宋人思想學術方面的著述,在更廣泛的思想文化和文學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宋詩的時代特色是怎樣形成的。
話說回來,無論多讀還是細讀,總要有起手入門之處。宋人作詩十分高產,現存宋詩數量超過唐詩許多倍,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撰《全宋詩》,共收現存宋詩作品二四七一八三首(不含殘句),詩人九○七九人(參見漆永祥〈簡論《全宋詩》的編纂與學術價值〉,載於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整理工作簡報》,二○○○年第五期),如此龐大的數量,濫竽充數的詩人、品質不高的作品自然也會很多。因此讀宋詩最好從讀選本開始,好的選本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引路作用。本書的選注,不敢自許可以引路,只希望盡自己的努力把宋詩的菁華選出來,加以講解,為讀者領略宋詩之美提供參考。不過,限於學識和鑒賞水平,所選之詩,難免有魚目混珠者,注釋難免有疏漏或錯誤,鑒賞解說也難免有不得要領之處,這都希望能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宋詩的優秀作品,還有很多,遠非這個小小的選讀本所能備載。限於篇幅,許多好詩不得不捨棄,一些曾廣泛傳誦過或被其他選本反覆選錄過的作品,也因篇幅的原因沒有選入。像蘇軾這樣的大詩人,各體詩歌只選了二十八首,其實再增加一倍也不嫌多,不過為了留出篇幅讓其他各具特色的小詩人也能出場亮相,不得不把他的許多好詩捨去。選詩的過程,其實難點和關鍵都不在選,而在如何捨棄,取捨之間,真是很費斟酌。作為編選者,自己知道許多好詩被捨棄了,但希望還能盡量保留宋詩的菁華,以見宋詩特色之一斑。
目次
自 序
前 言
新市驛別郭同年 張 詠 三
雨 夜 張 詠 三
塞 上 柳 開 四
柳枝詞 鄭文寶 六
泛吳松江 王禹偁 七
畬田詞(五首選二) 王禹偁 八
南平驛 寇 準 九
行 色 司馬池 十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選一) 范仲淹 一一
江上漁者 范仲淹 一二
書光化軍寺壁 祕 演 一三
南 朝 石延年 一三
朱雲傳 宋 祁 一四
陶 者 梅堯臣 一五
宿雲夢館 歐陽修 一六
鷺 鷥 歐陽修 一七
夢中作 歐陽修 一八
過沛題歌風臺 張方平 一八
淮中晚泊犢頭 蘇舜欽 二○
獨步遊滄浪亭 蘇舜欽 二一
夏 意 蘇舜欽 二二
出雁蕩回望常雲峰 趙 抃 二三
憶錢塘江 李 覯 二四
讀長恨辭二首(選一) 李 覯 二五
月陂閑步 邵 雍 二六
感雪吟 邵 雍 二七
夢遊洛中十首(選一) 蔡 襄 二七
度南澗 蔡 襄 二八
入天竺山留客 蔡 襄 三○
涵碧亭 文 同 三二
亭 口 文 同 三二
可笑口號七章(選一) 文 同 三三
詠 柳 曾 鞏 三四
西 樓 曾 鞏 三五
微雨登城二首(選一) 劉 敞 三五
別永叔後記事 劉 敞 三六
夏日西齋書事 司馬光 三七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選一) 王安石 三八
南 浦 王安石 三九
梅 花 王安石 四○
山 中 王安石 四○
泊船瓜洲 王安石 四一
夜 直 王安石 四四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選一) 王安石 四五
北 山 王安石 四七
木 末 王安石 四八
金陵即事三首(選一) 王安石 四九
北陂杏花 王安石 五○
宿蔣山棲霞寺 俞紫芝 五一
無 題 俞紫芝 五二
新 晴 劉 攽 五三
雨後池上 劉 攽 五四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五首選二) 蘇 軾 五五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選一) 蘇 軾 五七
東欄梨花 蘇 軾 五八
東 坡 蘇 軾 六○
海 棠 蘇 軾 六一
題西林壁 蘇 軾 六二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選一) 蘇 軾 六三
贈劉景文 蘇 軾 六四
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選一) 蘇 軾 六五
縱筆三首(選二) 蘇 軾 六七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選一) 蘇 軾 六七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選一) 蘇 轍 六八
寄 內 孔平仲 六九
秋 江 道 潛 七○
臨平道中 道 潛 七一
夜發分寧寄杜澗叟 黃庭堅 七二
六月十七日晝寢 黃庭堅 七三
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選一) 黃庭堅 七四
蟻蝶圖 黃庭堅 七五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 黃庭堅 七六
鄂州南樓書事四首(選一) 黃庭堅 七八
秋日三首(選二) 秦 觀 七九
春日五首(選一) 秦 觀 八一
賞酴醾有感 秦 觀 八二
首 夏 秦 觀 八三
垂虹亭 米 芾 八三
野 步 賀 鑄 八四
十七日觀潮 陳師道 八五
絕句四首(選一) 陳師道 八六
題穀熟驛舍二首 晁補之 八七
初見嵩山 張 耒 八八
夜 坐 張 耒 八九
秋夜寄遠 張 耒 八九
偶題二首(選一) 張 耒 九○
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為三絕(選一) 謝 逸 九一
偶 成 饒 節 九二
晚 起 饒 節 九三
春遊湖 徐 俯 九四
十絕為亞卿作(選二) 韓 駒 九四
憶 舊 朱敦儒 九六
聽 雨 呂本中 九六
三衢道中 曾 幾 九七
襄邑道中 陳與義 九八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選一) 陳與義 九九
牡 丹 陳與義 一○○
夏日即事 張九成 一○一
汴京紀事二十首(選二) 劉子翬 一○二
絕句送巨山二首(選一) 劉子翬 一○四
清 晝 朱淑真 一○四
劍門道中遇微雨 陸 游 一○五
花時遍遊諸家園(十首選一) 陸 游 一○七
小園四首(選一) 陸 游 一○七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陸 游 一○八
沈園二首 陸 游 一○九
梅花絕句六首(選一) 陸 游 一一○
示 兒 陸 游 一一一
州 橋 范成大 一一二
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選十一) 范成大 一一三
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
(選一) 楊萬里 一一七
夏夜追涼 楊萬里 一一八
小 池 楊萬里 一一九
寒 雀 楊萬里 一二○
稚子弄冰 楊萬里 一二○
道旁小憩觀物化 楊萬里 一二一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
(選一) 楊萬里 一二二
採蓮曲二首 蕭德藻 一二三
古梅二絕(選一) 蕭德藻 一二四
涉澗水作 朱 熹 一二六
春 日 朱 熹 一二六
入瑞巖道間得四絕句呈彥集充父二兄(選一) 朱 熹 一二七
觀書有感二首 朱 熹 一二八
醉下祝融峰 朱 熹 一三○
舟 次 志 南 一三○
東 渚 張 栻 一三一
立春日禊亭偶成 張 栻 一三二
晚 晴 張 栻 一三三
遊 絲 呂祖謙 一三四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選三) 姜 夔 一三五
過垂虹 姜 夔 一三六
野 望 翁 卷 一三七
鄉村四月 翁 卷 一三八
約 客 趙師秀 一三九
數 日 趙師秀 一四○
寒 夜 杜 耒 一四○
江陰浮遠堂 戴復古 一四一
山 村 戴復古 一四二
無題二首(選一) 高 翥 一四三
秋 日 高 翥 一四四
夜過西湖 陳 起 一四四
戊辰即事 劉克莊 一四五
西 山 劉克莊 一四六
歲晚書事十首(選一) 劉克莊 一四七
遊園不值 葉紹翁 一四七
夜書所見 葉紹翁 一四九
嘲 蝶 文 ? 一四九
過 湖 俞 桂 一五一
春暮遊小園 王 淇 一五二
武夷山中 謝枋得 一五三
醉歌(十首選一) 汪元量 一五四
湖州歌九十八首(選二) 汪元量 一五五
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閱之有感 林景熙 一五六
第四橋 蕭立之 一五六
秋夜詞 謝 翱 一五七
寒食中寄鄭起侍郎 楊徽之 一六一
村 行 王禹偁 一六二
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惠 崇 一六三
懷廣南轉運陳學士 希 晝 一六四
登原州城呈張蕡從事 魏 野 一六六
秋日登樓客次懷張覃進士 潘 閬 一六七
春日登樓懷歸 寇 準 一六八
山園小梅 林 逋 一六九
小隱自題 林 逋 一七一
南 朝 劉 筠 一七二
漢 武 楊 億 一七四
無 題 晏 殊 一七七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 晏 殊 一七八
城隅晚意 宋 祁 一八○
魯山山行 梅堯臣 一八一
小 村 梅堯臣 一八三
秋日家居 梅堯臣 一八四
東 溪 梅堯臣 一八五
戲答元珍 歐陽修 一八七
黃溪夜泊 歐陽修 一八八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歐陽修 一八九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蘇舜欽 一九一
淮中風浪 蘇舜欽 一九二
晚泊龜山 蘇舜欽 一九三
次韻孔憲蓬萊閣 趙 抃 一九四
愁花吟 邵 雍 一九六
閑適吟 邵 雍 一九七
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周敦頤 一九八
和張屯田秋晚靈峰東閣閑望 文 同 一九九
春 庭 文 同 二○○
葛溪驛 王安石 二○一
壬辰寒食 王安石 二○二
示長安君 王安石 二○三
春 盡 鄭 獬 二○四
遊廬山宿棲賢寺 王安國 二○六
郊行即事 程 顥 二○七
和子由澠池懷舊 蘇 軾 二○八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蘇 軾 二○九
新城道中二首(選一) 蘇 軾 二一一
初到黃州 蘇 軾 二一二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蘇 軾 二一四
次韻江晦叔二首(選一) 蘇 軾 二一五
春日耕者 蘇 轍 二一六
霽 夜 孔平仲 二一八
夏日龍井書事(四首選一) 道 潛 二一八
登快閣 黃庭堅 二二○
寄黃幾復 黃庭堅 二二二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庭堅 二二五
題落星寺嵐漪軒 黃庭堅 二二六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黃庭堅 二二八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黃庭堅 二三○
遊鑒湖 秦 觀 二三一
病後登快哉亭 賀 鑄 二三二
次韻春懷 陳師道 二三三
春懷示鄰里 陳師道 二三四
宿合清口 陳師道 二三五
宿齊河 陳師道 二三六
自蒲赴湖早行作 晁補之 二三七
己卯十二月二十日感事二首
(選一) 張 耒 二三八
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沖、表之、公實野步 洪 炎 二三九
春日郊外 唐 庚 二四○
醉 眠 唐 庚 二四○
感梅憶王立之 晁沖之 二四二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侄四首
(選一) 汪 藻 二四三
移居東村作 王庭珪 二四四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選一) 王庭珪 二四五
夜泊寧陵 韓 駒 二四六
春日即事二首(選一) 呂本中 二四七
兵亂後自嬉雜詩
(二十九首選五) 呂本中 二四八
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 曾 幾 二五二
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 曾 幾 二五三
春 陰 朱 弁 二五四
登岳陽樓(二首選一) 陳與義 二五五
傷 春 陳與義 二五六
觀 雨 陳與義 二五七
北 風 劉子翬 二五八
春 望 劉子翬 二五九
元夜三首(選一) 朱淑真 二六○
送七兄赴揚州帥幕 陸 游 二六○
遊山西村 陸 游 二六一
夜泊水村 陸 游 二六三
書 憤 陸 游 二六三
臨安春雨初霽 陸 游 二六五
書室明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二首(選一) 陸 游 二六七
過揚子江(二首選一) 楊萬里 二六八
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
(二首選一) 楊萬里 二七○
雪 尤 袤 二七一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 朱 熹 二七二
鵝湖寺和陸子壽 朱 熹 二七三
晚泊東流 王 質 二七五
送別湖南部曲 辛棄疾 二七五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選一) 徐 照 二七七
黃 碧 徐 璣 二七八
薛氏瓜廬 趙師秀 二七九
庚子薦饑(六首選一) 戴復古 二八一
落 梅 劉克莊 二八一
山中(六首選一) 方 岳 二八三
過零丁洋 文天祥 二八四
金陵驛 文天祥 二八六
除 夜 文天祥 二八六
京口月夕書懷 林景熙 二八七
茶陵道中 蕭立之 二八八
書文山卷後 謝 翱 二八八
對 雪 王禹偁 二九三
江南春 寇 準 二九五
煮海歌 柳 永 二九七
代意寄師魯 石延年 二九九
涼 蟾 宋 祁 三○一
猛虎行 梅堯臣 三○二
田家語 梅堯臣 三○四
汝墳貧女 梅堯臣 三○六
書 哀 梅堯臣 三○八
看山寄宋中道 梅堯臣 三一○
晚泊岳陽 歐陽修 三一一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歐陽修 三一二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修 三一四
盤車圖 歐陽修 三一七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歐陽修 三一九
再和明妃曲 歐陽修 三二一
吾 聞 蘇舜欽 三二三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謨蔡大 蘇舜欽 三二五
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叟兄弟 司馬光 三二七
河北民 王安石 三二八
桃源行 王安石 三二九
明妃曲二首 王安石 三三一
採鳧茨 鄭 獬 三三五
暑旱苦熱 王 令 三三六
戲子由 蘇 軾 三三七
法惠寺橫翠閣 蘇 軾 三四○
無錫道中賦水車 蘇 軾 三四一
百步洪二首(選一) 蘇 軾 三四三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蘇 軾 三四六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蘇 軾 三四七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選一) 蘇 軾 三四九
泛 潁 蘇 軾 三五一
荔支歎 蘇 軾 三五四
買 炭 蘇 轍 三五八
秋 稼 蘇 轍 三六○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孔平仲 三六二
打 麥 張舜民 三六四
贛上食蓮有感 黃庭堅 三六五
上大蒙籠 黃庭堅 三六七
送王郎 黃庭堅 三六九
戲呈孔毅父 黃庭堅 三七二
題竹石牧牛 黃庭堅 三七四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 黃庭堅 三七五
跋子瞻〈和陶詩〉 黃庭堅 三七六
武昌松風閣 黃庭堅 三七八
老 樵 呂南公 三八一
別三子 陳師道 三八三
芳儀怨 晁補之 三八四
勞 歌 張 耒 三九○
對蓮花戲寄晁應之 張 耒 三九一
牛酥行 江端友 三九三
瑜上人自靈石來求鳴玉軒詩,會予斷作語,復決堤作一首 惠 洪 三九五
夷門行贈秦夷仲 晁沖之 三九七
山中聞杜鵑 洪 炎 三九九
春 日 汪 藻 四○○
正月二十日出城 張九成 四○一
夜讀兵書 陸 游 四○二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陸 游 四○三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陸 游 四○四
關山月 陸 游 四○五
農家歎 陸 游 四○六
催租行 范成大 四○七
插秧歌 楊萬里 四○九
夜宿東渚放歌三首(選一) 楊萬里 四一○
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 楊萬里 四一一
倦繡圖 王 質 四一三
昔遊詩(十五首選一) 姜 夔 四一四
頻酌淮河水 戴復古 四一五
耕織歎二首 趙汝鐩 四一五
軍中樂 劉克莊 四一七
正氣歌 文天祥 四一九
送人之常德 蕭立之 四二三
楊徽之 四二七
張 詠 四二七
柳 開 四二八
鄭文寶 四二八
王禹偁 四二九
惠 崇 四二九
希 晝 四三○
魏 野 四三○
潘 閬 四三一
寇 準 四三二
林 逋 四三二
劉 筠 四三三
楊 億 四三四
司馬池 四三五
柳 永 四三五
范仲淹 四三五
晏 殊 四三六
祕 演 四三七
石延年 四三八
宋 祁 四三九
梅堯臣 四四○
歐陽修 四四一
張方平 四四三
蘇舜欽 四四四
趙 抃 四四五
李 覯 四四六
邵 雍 四四六
蔡 襄 四四八
周敦頤 四四九
文 同 四五○
劉 敞 四五一
曾 鞏 四五一
司馬光 四五二
王安石 四五三
俞紫芝 四五五
劉 攽 四五五
王安國 四五六
王 令 四五六
程 顥 四五七
蘇 軾 四五八
蘇 轍 四六○
孔平仲 四六二
張舜民 四六二
道 潛 四六三
黃庭堅 四六四
呂南公 四六七
秦 觀 四六八
米 芾 四六八
賀 鑄 四六九
陳師道 四七○
晁補之 四七一
張 耒 四七一
謝 逸 四七三
饒 節 四七四
江端友 四七四
洪 炎 四七五
唐 庚 四七五
惠 洪 四七六
晁沖之 四七七
徐 俯 四七七
汪 藻 四七八
王庭珪 四七九
韓 駒 四八○
朱敦儒 四八一
呂本中 四八一
曾 幾 四八二
朱 弁 四八三
陳與義 四八四
張九成 四八五
劉子翬 四八六
朱淑真 四八七
陸 游 四八八
范成大 四九○
楊萬里 四九二
尤 袤 四九四
蕭德藻 四九五
朱 熹 四九六
志 南 四九七
張 栻 四九七
王 質 四九八
呂祖謙 四九八
辛棄疾 四九九
姜 夔 四九九
徐 照 五○○
徐 璣 五○一
翁 卷 五○一
趙師秀 五○二
杜 耒 五○三
戴復古 五○三
高 翥 五○四
趙汝鐩 五○四
陳 起 五○四
劉克莊 五○五
葉紹翁 五○六
方 岳 五○六
文 ? 五○七
俞 桂 五○八
王 淇 五○八
謝枋得 五○八
文天祥 五○八
汪元量 五○九
林景熙 五一○
蕭立之 五一○
謝 翱 五一○
前 言
新市驛別郭同年 張 詠 三
雨 夜 張 詠 三
塞 上 柳 開 四
柳枝詞 鄭文寶 六
泛吳松江 王禹偁 七
畬田詞(五首選二) 王禹偁 八
南平驛 寇 準 九
行 色 司馬池 十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選一) 范仲淹 一一
江上漁者 范仲淹 一二
書光化軍寺壁 祕 演 一三
南 朝 石延年 一三
朱雲傳 宋 祁 一四
陶 者 梅堯臣 一五
宿雲夢館 歐陽修 一六
鷺 鷥 歐陽修 一七
夢中作 歐陽修 一八
過沛題歌風臺 張方平 一八
淮中晚泊犢頭 蘇舜欽 二○
獨步遊滄浪亭 蘇舜欽 二一
夏 意 蘇舜欽 二二
出雁蕩回望常雲峰 趙 抃 二三
憶錢塘江 李 覯 二四
讀長恨辭二首(選一) 李 覯 二五
月陂閑步 邵 雍 二六
感雪吟 邵 雍 二七
夢遊洛中十首(選一) 蔡 襄 二七
度南澗 蔡 襄 二八
入天竺山留客 蔡 襄 三○
涵碧亭 文 同 三二
亭 口 文 同 三二
可笑口號七章(選一) 文 同 三三
詠 柳 曾 鞏 三四
西 樓 曾 鞏 三五
微雨登城二首(選一) 劉 敞 三五
別永叔後記事 劉 敞 三六
夏日西齋書事 司馬光 三七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選一) 王安石 三八
南 浦 王安石 三九
梅 花 王安石 四○
山 中 王安石 四○
泊船瓜洲 王安石 四一
夜 直 王安石 四四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選一) 王安石 四五
北 山 王安石 四七
木 末 王安石 四八
金陵即事三首(選一) 王安石 四九
北陂杏花 王安石 五○
宿蔣山棲霞寺 俞紫芝 五一
無 題 俞紫芝 五二
新 晴 劉 攽 五三
雨後池上 劉 攽 五四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五首選二) 蘇 軾 五五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選一) 蘇 軾 五七
東欄梨花 蘇 軾 五八
東 坡 蘇 軾 六○
海 棠 蘇 軾 六一
題西林壁 蘇 軾 六二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選一) 蘇 軾 六三
贈劉景文 蘇 軾 六四
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選一) 蘇 軾 六五
縱筆三首(選二) 蘇 軾 六七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選一) 蘇 軾 六七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選一) 蘇 轍 六八
寄 內 孔平仲 六九
秋 江 道 潛 七○
臨平道中 道 潛 七一
夜發分寧寄杜澗叟 黃庭堅 七二
六月十七日晝寢 黃庭堅 七三
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選一) 黃庭堅 七四
蟻蝶圖 黃庭堅 七五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 黃庭堅 七六
鄂州南樓書事四首(選一) 黃庭堅 七八
秋日三首(選二) 秦 觀 七九
春日五首(選一) 秦 觀 八一
賞酴醾有感 秦 觀 八二
首 夏 秦 觀 八三
垂虹亭 米 芾 八三
野 步 賀 鑄 八四
十七日觀潮 陳師道 八五
絕句四首(選一) 陳師道 八六
題穀熟驛舍二首 晁補之 八七
初見嵩山 張 耒 八八
夜 坐 張 耒 八九
秋夜寄遠 張 耒 八九
偶題二首(選一) 張 耒 九○
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為三絕(選一) 謝 逸 九一
偶 成 饒 節 九二
晚 起 饒 節 九三
春遊湖 徐 俯 九四
十絕為亞卿作(選二) 韓 駒 九四
憶 舊 朱敦儒 九六
聽 雨 呂本中 九六
三衢道中 曾 幾 九七
襄邑道中 陳與義 九八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選一) 陳與義 九九
牡 丹 陳與義 一○○
夏日即事 張九成 一○一
汴京紀事二十首(選二) 劉子翬 一○二
絕句送巨山二首(選一) 劉子翬 一○四
清 晝 朱淑真 一○四
劍門道中遇微雨 陸 游 一○五
花時遍遊諸家園(十首選一) 陸 游 一○七
小園四首(選一) 陸 游 一○七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陸 游 一○八
沈園二首 陸 游 一○九
梅花絕句六首(選一) 陸 游 一一○
示 兒 陸 游 一一一
州 橋 范成大 一一二
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選十一) 范成大 一一三
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
(選一) 楊萬里 一一七
夏夜追涼 楊萬里 一一八
小 池 楊萬里 一一九
寒 雀 楊萬里 一二○
稚子弄冰 楊萬里 一二○
道旁小憩觀物化 楊萬里 一二一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
(選一) 楊萬里 一二二
採蓮曲二首 蕭德藻 一二三
古梅二絕(選一) 蕭德藻 一二四
涉澗水作 朱 熹 一二六
春 日 朱 熹 一二六
入瑞巖道間得四絕句呈彥集充父二兄(選一) 朱 熹 一二七
觀書有感二首 朱 熹 一二八
醉下祝融峰 朱 熹 一三○
舟 次 志 南 一三○
東 渚 張 栻 一三一
立春日禊亭偶成 張 栻 一三二
晚 晴 張 栻 一三三
遊 絲 呂祖謙 一三四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選三) 姜 夔 一三五
過垂虹 姜 夔 一三六
野 望 翁 卷 一三七
鄉村四月 翁 卷 一三八
約 客 趙師秀 一三九
數 日 趙師秀 一四○
寒 夜 杜 耒 一四○
江陰浮遠堂 戴復古 一四一
山 村 戴復古 一四二
無題二首(選一) 高 翥 一四三
秋 日 高 翥 一四四
夜過西湖 陳 起 一四四
戊辰即事 劉克莊 一四五
西 山 劉克莊 一四六
歲晚書事十首(選一) 劉克莊 一四七
遊園不值 葉紹翁 一四七
夜書所見 葉紹翁 一四九
嘲 蝶 文 ? 一四九
過 湖 俞 桂 一五一
春暮遊小園 王 淇 一五二
武夷山中 謝枋得 一五三
醉歌(十首選一) 汪元量 一五四
湖州歌九十八首(選二) 汪元量 一五五
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閱之有感 林景熙 一五六
第四橋 蕭立之 一五六
秋夜詞 謝 翱 一五七
寒食中寄鄭起侍郎 楊徽之 一六一
村 行 王禹偁 一六二
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惠 崇 一六三
懷廣南轉運陳學士 希 晝 一六四
登原州城呈張蕡從事 魏 野 一六六
秋日登樓客次懷張覃進士 潘 閬 一六七
春日登樓懷歸 寇 準 一六八
山園小梅 林 逋 一六九
小隱自題 林 逋 一七一
南 朝 劉 筠 一七二
漢 武 楊 億 一七四
無 題 晏 殊 一七七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 晏 殊 一七八
城隅晚意 宋 祁 一八○
魯山山行 梅堯臣 一八一
小 村 梅堯臣 一八三
秋日家居 梅堯臣 一八四
東 溪 梅堯臣 一八五
戲答元珍 歐陽修 一八七
黃溪夜泊 歐陽修 一八八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歐陽修 一八九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蘇舜欽 一九一
淮中風浪 蘇舜欽 一九二
晚泊龜山 蘇舜欽 一九三
次韻孔憲蓬萊閣 趙 抃 一九四
愁花吟 邵 雍 一九六
閑適吟 邵 雍 一九七
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周敦頤 一九八
和張屯田秋晚靈峰東閣閑望 文 同 一九九
春 庭 文 同 二○○
葛溪驛 王安石 二○一
壬辰寒食 王安石 二○二
示長安君 王安石 二○三
春 盡 鄭 獬 二○四
遊廬山宿棲賢寺 王安國 二○六
郊行即事 程 顥 二○七
和子由澠池懷舊 蘇 軾 二○八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蘇 軾 二○九
新城道中二首(選一) 蘇 軾 二一一
初到黃州 蘇 軾 二一二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蘇 軾 二一四
次韻江晦叔二首(選一) 蘇 軾 二一五
春日耕者 蘇 轍 二一六
霽 夜 孔平仲 二一八
夏日龍井書事(四首選一) 道 潛 二一八
登快閣 黃庭堅 二二○
寄黃幾復 黃庭堅 二二二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庭堅 二二五
題落星寺嵐漪軒 黃庭堅 二二六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黃庭堅 二二八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黃庭堅 二三○
遊鑒湖 秦 觀 二三一
病後登快哉亭 賀 鑄 二三二
次韻春懷 陳師道 二三三
春懷示鄰里 陳師道 二三四
宿合清口 陳師道 二三五
宿齊河 陳師道 二三六
自蒲赴湖早行作 晁補之 二三七
己卯十二月二十日感事二首
(選一) 張 耒 二三八
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沖、表之、公實野步 洪 炎 二三九
春日郊外 唐 庚 二四○
醉 眠 唐 庚 二四○
感梅憶王立之 晁沖之 二四二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侄四首
(選一) 汪 藻 二四三
移居東村作 王庭珪 二四四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選一) 王庭珪 二四五
夜泊寧陵 韓 駒 二四六
春日即事二首(選一) 呂本中 二四七
兵亂後自嬉雜詩
(二十九首選五) 呂本中 二四八
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 曾 幾 二五二
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 曾 幾 二五三
春 陰 朱 弁 二五四
登岳陽樓(二首選一) 陳與義 二五五
傷 春 陳與義 二五六
觀 雨 陳與義 二五七
北 風 劉子翬 二五八
春 望 劉子翬 二五九
元夜三首(選一) 朱淑真 二六○
送七兄赴揚州帥幕 陸 游 二六○
遊山西村 陸 游 二六一
夜泊水村 陸 游 二六三
書 憤 陸 游 二六三
臨安春雨初霽 陸 游 二六五
書室明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二首(選一) 陸 游 二六七
過揚子江(二首選一) 楊萬里 二六八
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
(二首選一) 楊萬里 二七○
雪 尤 袤 二七一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 朱 熹 二七二
鵝湖寺和陸子壽 朱 熹 二七三
晚泊東流 王 質 二七五
送別湖南部曲 辛棄疾 二七五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選一) 徐 照 二七七
黃 碧 徐 璣 二七八
薛氏瓜廬 趙師秀 二七九
庚子薦饑(六首選一) 戴復古 二八一
落 梅 劉克莊 二八一
山中(六首選一) 方 岳 二八三
過零丁洋 文天祥 二八四
金陵驛 文天祥 二八六
除 夜 文天祥 二八六
京口月夕書懷 林景熙 二八七
茶陵道中 蕭立之 二八八
書文山卷後 謝 翱 二八八
對 雪 王禹偁 二九三
江南春 寇 準 二九五
煮海歌 柳 永 二九七
代意寄師魯 石延年 二九九
涼 蟾 宋 祁 三○一
猛虎行 梅堯臣 三○二
田家語 梅堯臣 三○四
汝墳貧女 梅堯臣 三○六
書 哀 梅堯臣 三○八
看山寄宋中道 梅堯臣 三一○
晚泊岳陽 歐陽修 三一一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歐陽修 三一二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修 三一四
盤車圖 歐陽修 三一七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歐陽修 三一九
再和明妃曲 歐陽修 三二一
吾 聞 蘇舜欽 三二三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謨蔡大 蘇舜欽 三二五
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叟兄弟 司馬光 三二七
河北民 王安石 三二八
桃源行 王安石 三二九
明妃曲二首 王安石 三三一
採鳧茨 鄭 獬 三三五
暑旱苦熱 王 令 三三六
戲子由 蘇 軾 三三七
法惠寺橫翠閣 蘇 軾 三四○
無錫道中賦水車 蘇 軾 三四一
百步洪二首(選一) 蘇 軾 三四三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蘇 軾 三四六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蘇 軾 三四七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選一) 蘇 軾 三四九
泛 潁 蘇 軾 三五一
荔支歎 蘇 軾 三五四
買 炭 蘇 轍 三五八
秋 稼 蘇 轍 三六○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孔平仲 三六二
打 麥 張舜民 三六四
贛上食蓮有感 黃庭堅 三六五
上大蒙籠 黃庭堅 三六七
送王郎 黃庭堅 三六九
戲呈孔毅父 黃庭堅 三七二
題竹石牧牛 黃庭堅 三七四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 黃庭堅 三七五
跋子瞻〈和陶詩〉 黃庭堅 三七六
武昌松風閣 黃庭堅 三七八
老 樵 呂南公 三八一
別三子 陳師道 三八三
芳儀怨 晁補之 三八四
勞 歌 張 耒 三九○
對蓮花戲寄晁應之 張 耒 三九一
牛酥行 江端友 三九三
瑜上人自靈石來求鳴玉軒詩,會予斷作語,復決堤作一首 惠 洪 三九五
夷門行贈秦夷仲 晁沖之 三九七
山中聞杜鵑 洪 炎 三九九
春 日 汪 藻 四○○
正月二十日出城 張九成 四○一
夜讀兵書 陸 游 四○二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陸 游 四○三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陸 游 四○四
關山月 陸 游 四○五
農家歎 陸 游 四○六
催租行 范成大 四○七
插秧歌 楊萬里 四○九
夜宿東渚放歌三首(選一) 楊萬里 四一○
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 楊萬里 四一一
倦繡圖 王 質 四一三
昔遊詩(十五首選一) 姜 夔 四一四
頻酌淮河水 戴復古 四一五
耕織歎二首 趙汝鐩 四一五
軍中樂 劉克莊 四一七
正氣歌 文天祥 四一九
送人之常德 蕭立之 四二三
楊徽之 四二七
張 詠 四二七
柳 開 四二八
鄭文寶 四二八
王禹偁 四二九
惠 崇 四二九
希 晝 四三○
魏 野 四三○
潘 閬 四三一
寇 準 四三二
林 逋 四三二
劉 筠 四三三
楊 億 四三四
司馬池 四三五
柳 永 四三五
范仲淹 四三五
晏 殊 四三六
祕 演 四三七
石延年 四三八
宋 祁 四三九
梅堯臣 四四○
歐陽修 四四一
張方平 四四三
蘇舜欽 四四四
趙 抃 四四五
李 覯 四四六
邵 雍 四四六
蔡 襄 四四八
周敦頤 四四九
文 同 四五○
劉 敞 四五一
曾 鞏 四五一
司馬光 四五二
王安石 四五三
俞紫芝 四五五
劉 攽 四五五
王安國 四五六
王 令 四五六
程 顥 四五七
蘇 軾 四五八
蘇 轍 四六○
孔平仲 四六二
張舜民 四六二
道 潛 四六三
黃庭堅 四六四
呂南公 四六七
秦 觀 四六八
米 芾 四六八
賀 鑄 四六九
陳師道 四七○
晁補之 四七一
張 耒 四七一
謝 逸 四七三
饒 節 四七四
江端友 四七四
洪 炎 四七五
唐 庚 四七五
惠 洪 四七六
晁沖之 四七七
徐 俯 四七七
汪 藻 四七八
王庭珪 四七九
韓 駒 四八○
朱敦儒 四八一
呂本中 四八一
曾 幾 四八二
朱 弁 四八三
陳與義 四八四
張九成 四八五
劉子翬 四八六
朱淑真 四八七
陸 游 四八八
范成大 四九○
楊萬里 四九二
尤 袤 四九四
蕭德藻 四九五
朱 熹 四九六
志 南 四九七
張 栻 四九七
王 質 四九八
呂祖謙 四九八
辛棄疾 四九九
姜 夔 四九九
徐 照 五○○
徐 璣 五○一
翁 卷 五○一
趙師秀 五○二
杜 耒 五○三
戴復古 五○三
高 翥 五○四
趙汝鐩 五○四
陳 起 五○四
劉克莊 五○五
葉紹翁 五○六
方 岳 五○六
文 ? 五○七
俞 桂 五○八
王 淇 五○八
謝枋得 五○八
文天祥 五○八
汪元量 五○九
林景熙 五一○
蕭立之 五一○
謝 翱 五一○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