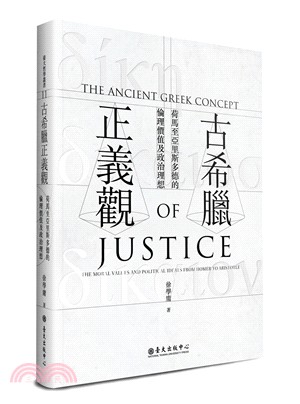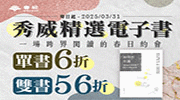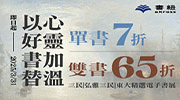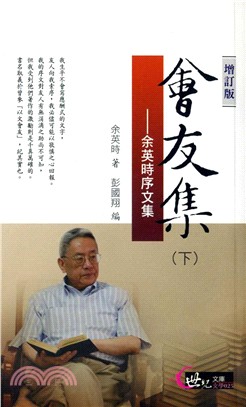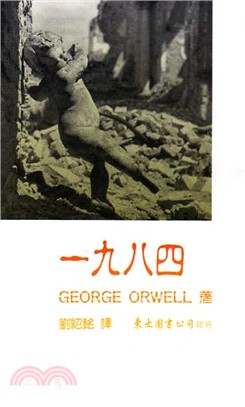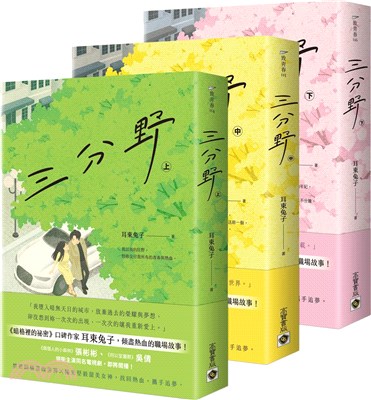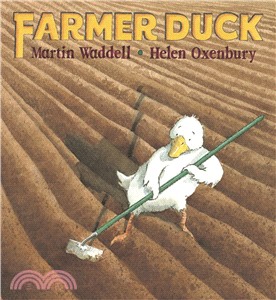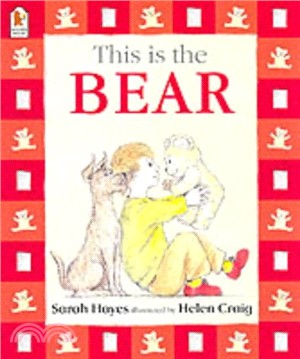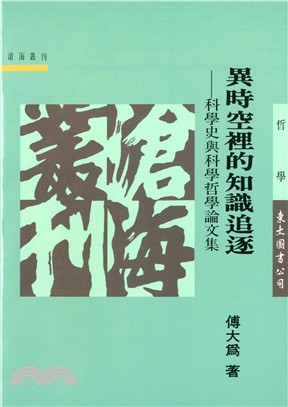古希臘正義觀: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價值及政治理想
商品資訊
系列名:臺大哲學叢書
ISBN13:9789863501695
替代書名:The Ancient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 The 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Ideals from Homer to Aristotle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徐學庸
出版日:2016/07/29
裝訂/頁數:平裝/328頁
規格:21cm*14.8cm*1.8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70【十一年級】
商品簡介
古希臘的正義觀如何與當代發生關聯?
「正義」又是如何從外在規範轉化為內在狀態,影響了兩千多年來的西方政治倫理思想?
西方當代正義思想,包括司法正義、程序正義、分配正義或矯正正義等概念,皆植基於其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文化傳統──古希臘。正義是西元前八世紀至四世紀,也就是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時代,最為核心的概念,要理解跟正義相關的任何議題,最適切的做法便是「回到原點」,從古希臘對正義的看法入手。
本書主張,古希臘正義概念的演變,顯現時人對其時代的反省及回應。儘管各時期的正義觀或有不同,但無論是人倫關係和諧、城邦運作有序、個人靈魂調和或是宇宙自然的運行調順,都展現了正義的核心意涵──秩序的維繫與恢復。從中也勾勒出正義,就其為德性而言,在時代、文化和社會的遞移中,逐步由指涉行為的外在規範,轉化為關乎靈魂的內在概念,隨後再變回行為外在準則的過程。
書中涉及的文本涵納文學、戲劇及哲學,探討荷馬、赫希俄德、立法者與輓歌詩人、早期希臘哲學家、悲劇作家艾斯曲婁斯、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等先賢的正義觀,希望帶領讀者從其優美的文字、動人的故事及崇高的理想中,反省我們的生命現況,妥善回應當前面對的倫理難題。
作者簡介
徐學庸
1998年取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9至2000年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2000至2012年任教於輔仁大學哲學系,2005至2006年為牛津大學訪問學人,現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洋古代倫理學及政治哲學。除本書外,另著有《靈魂的奧迪賽:柏拉圖〈費多篇〉》、《道德與合理:西洋古代倫理議題研究》;譯注有《〈理想國篇〉譯注與詮釋》、《〈米諾篇〉〈費多篇〉譯注》,以及西塞羅的《論友誼》、《論老年》和《論義務》。
序
導論(摘錄)
「正義」,這是個眾人熟悉且朗朗上口的詞彙;近年來各種不同形式的正義不絕於耳,例如司法正義、程序正義、實質正義、土地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分配正義及修正或矯正正義等。我們或許或多或少能對這些不同正義觀的內涵說出一二,然而我們可能不知道,這些正義觀皆是植基於西方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文化傳統裡,可回溯至西方文化思想的源頭—— 古希臘。正義在古希臘的文化中原是一神祇名,Dikē,祂是宙斯與塞迷絲(Themis)之女,且是合宜女神(The Horai)之一。合宜女神除了皆有春天生機盎然的意涵外,亦有著濃厚、顯著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旨趣。祂們的現身表示了社會公平、秩序及平和的狀態。近代以來,正義女神的形象多被認為具有三個主要特徵:右手持劍、左手捧天秤及雙眼遮蔽。劍表示法律或法庭的強制力量,天秤度量正反雙方的意見,遮眼顯示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祂的角色是維繫社會秩序與祥和,並在它們遭到破壞時能以其判斷與仲裁使之恢復。
本書的主旨是藉由爬梳及探討部分古希臘文學、戲劇及哲學的文本,以了解正義這個概念在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眼中具有的意義功能為何。涉及的文本設定在西元前八世紀至四世紀的作品,即從荷馬(Homer)的史詩開始,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倫理學作品結束。這五個世紀的範圍,正是古希臘城邦政治從氏族政治逐漸萌芽、茁壯、成熟及衰敗的過程,且在此歷程中,正義的倫理及政治的意涵極為凸顯。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的城邦為維持城邦秩序,皆需求助於正義。
關於古希臘正義觀的流變,中西方學者皆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及提出相關的詮釋,大致有兩種理解:其一是將流變理解成發展與進步,例如E. R. Dodds教授,認為古希臘的倫理道德及宗教文化的發展,是從羞恥文化進入罪惡文化的歷程。在荷馬史詩清楚可見羞恥文化,英雄們為了維繫個人的優秀(aretē),無法坐視個人的榮譽(timē)被不當剝奪,因為被剝奪榮譽是身為英雄的恥辱。這個文化隨後被罪惡文化取代,後者強調犯錯必須接受懲罰,無論懲罰是在今生(如赫希俄德的主張),或在來世(如柏拉圖〔Plato, 424-347 BC〕的描繪)。Dodds教授的主張得到A. W. H. Adkins教授呼應,並認為羞恥文化是古代的文化,而罪惡文化是現代的文化。
然而,若我們審視古希臘倫理文化的發展,其實無法得出Dodds及Adkins兩位教授所主張的從羞恥文化到罪惡文化的發展歷程。因為就算在赫希俄德及柏拉圖的思想裡有著罪惡及懲罰的概念,也不表示兩位詩人之間的艾斯曲婁斯(Aeschylos, 525-456 BC)與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生於515 BC),以及柏拉圖之後的亞里斯多德,亦特別看重罪惡及懲罰這兩個元素。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尼科馬哥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四卷關於「雄心」(megalopsuchia)(1123a-1125a35)及羞恥(1128b10-35)的論述,皆顯示古希臘倫理文化發展至亞里斯多德並未轉化成罪惡文化。此外,將柏拉圖的倫理學思想單純地理解為罪惡文化亦有不妥,因為他在《高爾奇亞斯篇》(The Gorgias)讓蘇格拉底以羞恥感來說服三位對話者追求正義及避免不正義(494d);此外《理想國篇》(The Republic)卷四言及「激情」(thumos)與羞恥感的關係,並說當它成為理智的幫手有助於維持靈魂的秩序與和諧;卷八進一步強調thumos與榮譽名聲的追求有關。這兩部對話錄雖皆言及來世懲罰的概念,但就此斷言柏拉圖的倫理學思想具有罪惡文化的特色,似乎過於躁進,畢竟他在這兩部對話錄裡多次強調羞恥感對人的倫理生命甚為重要。這顯示了舊文化觀被新文化觀取代的主張,對古希臘文化流變,特別是正義觀的流變,並非是妥適的詮釋。
此外,德國古典學研究者B. Snell教授論述古希臘靈魂觀時,亦抱持著進步觀點來理解古希臘文化的流變,他認為荷馬史詩如《奧迪賽》(Odyssey),看不到道德推論的元素,英雄的決定——如奧迪修斯(Odysseus)的抉擇——皆是出於直覺。此觀點獲得崔延強教授的認可,在《正義與邏各斯》一書中他寫道:「從荷馬到赫希俄德表明了一種使世間道德——法律秩序——逐步合理化的趨勢在不斷地得以發展,但真正成為一種自覺的現實活動是在希臘步入城邦時代之後,……」Snell教授的主張主要建立在康德倫理學及廣義的義務論,如效益主義的基礎上,這類的倫理學思想強調道德判斷的有效及正當,必須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然而為求道德判斷具普遍性,經常遭致的結果是道德判斷是在去文化及社會脈絡下進行,與行為者的倫理生命失去連結。這帶領我們進入對第二個「流變」的理解。另一個關於「流變」的理解,則不認為進步發展是對古希臘倫理及政治文化的適切理解。抱持此詮釋立場的學者咸認為: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在作品裡提出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觀點,是針對他們各自身處之政治社會的回應與反省;換言之,任何一位作者提出的倫理學及政治哲學的觀點,都具有文化及社會關連性;對任何一個文化裡的倫理及政治觀念的探討體察,不能以去脈絡化的方式進行,因為這些觀念不只是等候分析研判的理論,它們是扎實而活生生地被當時的人們,在某一特定的時空背景、倫理文化及社會架構中運用。因此在理解這些觀念時,若忽略它們與其所在之社群文化的緊密關係,極可能會曲解這些觀念。由於倫理及政治觀點與社會文化密不可分,不同文本的主張,便與作者所身處的政治社會及面臨的問題有直接的聯繫。這使得前一個「流變」所謂之線性發展進步,變得不甚適切,因為在古希臘的文化歷史演變中,我們見不到倫理政治觀的線性發展趨勢,反而是在每個階段、不同的社會結構中,這些觀點被作者用來反省及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各領域問題。
不過,「進步」這一概念並非在此歷程中無足輕重,例如aretē(優點、優秀或德性)的內涵演變,便可看到進步的徵象。原本它在荷馬史詩裡只適用於特別族群——貴族及英雄,因為這個字在字源上與aristos(最優秀的、最高貴的)、aristeuō(表現最佳)及aretaō(興旺、成功)等字相近。然而在隨後的文獻,例如赫希俄德《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中,aretē一字更擴大用於辛勤與大地及天候奮鬥的勞動者,戮力工作者即擁有德性與優秀之人。然而這不表示,aretē這個概念——指一事物或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且藉此特質該事物及人能充分表現與扮演其功能與角色——有實質的改變,無論用於貴族與英雄,或用於勤苦的勞動階級,aretē根本上都是指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進步」這個詞在此意義下便不是意味新取代舊——前者具有後者全沒有的內涵,且後者徹底被棄置;反而是,同一個倫理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及社會脈絡裡,有不同的應用。
審視這兩種詮釋,本書採取第二種立場為論述古希臘正義觀的基調,因為我們始終認為,反省自己所處時代中所面臨的各方面議題,並針對問題提出解決之道,是每一個時代的作者所表現的關懷,無論創作形式是文學、戲劇或哲學。欲理解作品中的倫理政治觀,絕不可無視於作者的個別時空背景。亦即,對所有相關概念,如德性、道德推論、秩序、正義等,皆須置於時代前提下才可確切把握。換言之,我們對於書中所選擇之文本的理解,除了文本內部的證據,亦須將外部證據納入考量。唯有如此,我們對古希臘正義觀的析論,才能有時代、文化及社會向度。此外這個論證的立場與方法選擇,也影響到書中對於欲探討之相關文本的篩選。詩人、立法者、劇作家及哲學家的文本,是針對作者實際面臨的政治及倫理問題進行思索與反省。
目次
自 序
導 論
第一章 荷馬
第一節 正義
第二節 風俗習慣與法律
第三節 正義及風俗習慣與法律
第四節 結論
第二章 赫希俄德
第一節 遺產之爭
第二節 神話
第三節 正義
第四節 結論
第三章 立法者與詩人
第一節 呂庫爾勾斯
第二節 提爾泰歐斯
第三節 塞歐格尼斯
第四節 梭倫
第五節 結論
第四章 早期希臘哲學家
第一節 亞納西曼德
第二節 赫拉克利圖斯
第三節 巴曼尼德斯
第四節 德謨克利圖斯
第五節 普羅大哥拉斯及安提豐
第六節 結論
第五章 艾斯曲婁斯
第一節 《阿加曼農》:合理的謀殺?
第二節 《祭酒者》:正義是復仇
第三節 《和善女神》:和解
第四節 《歐瑞斯特斯的故事》:雅典政治現狀
第五節 結論
第六章 柏拉圖:初論正義
第一節 正義是歸還所借(欠)之物
第二節 正義與技藝
第三節 正義是強者的利益
第四節 結論
第七章 柏拉圖:再論正義
第一節 正義與契約
第二節 城邦的正義
第三節 個人的正義
第四節 正義與形上知識
第五節 結論
第八章 亞里斯多德
第一節 完全正義
第二節 個別正義
第三節 正義與中庸之道
第四節 結論
結 論
參考書目
總索引
古代作者索引
書摘/試閱
第六章 柏拉圖:初論正義(摘錄)
第三節 正義是強者的利益
波雷馬爾侯斯在定義正義是什麼一事上的失敗,並未令在場聆聽對話者對蘇格拉底的論述感到滿意,塞拉胥馬侯斯在他們兩人的對話過程中,急於參與談話,但被制止。就在兩人結束對話之際,塞拉胥馬侯斯大聲說道,這是個可笑愚昧的談話,且希望蘇格拉底不要只問問題,也應提出自己對正義的定義;此外,他要求蘇格拉底對正義下的定義應避免「它是應為之事,有益之事,有用之事,有利之事及有好處之事」(336d1-2)的說詞。此限定條件似乎顯示塞拉胥馬侯斯對正義的理解較為深刻,即他不再以固定外在行為規則與產生的結果來解釋正義。然而當塞拉胥馬侯斯提出其正義觀——正義是為了強者的利益(338c2-3)——時,原先對他樂觀的期待瞬時落空,因為他不但使用他拒絕蘇格拉底使用的那些條件之一,也沒跳脫波雷馬爾侯斯論證的窠臼:正義被以行為的結果來說明。
塞拉胥馬侯斯陳述完自己對正義的定義後,原欲起身離席,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對正義無懈可擊的定義。但蘇格拉底勸他留下來繼續對話,並承諾雖然沒錢付學費,但若塞拉胥馬侯斯的說法正確,他會不吝給予讚美。蘇格拉底首先問塞拉胥馬侯斯:所謂強者的利益應不是指牛肉對運動選手的身體有益(338c)?後者回答:強者指的是在政治上擁有權力者,在各種政治體制的城邦裡正義皆相同——「有利於所建立的統治權力之事」(339a1-2)。亦即,有統治權者有特權接觸城邦裡的政治制度及法律系統,並藉此強迫被統治者同意有利於統治者的公共政策。這個對正義的定義顯示,塞拉胥馬侯斯認為欲理解在城邦裡的正義之事,我們應該探究擁有統治權力者,因為城邦裡的政治制度及法律系統是透過統治權設立,且統治權藉由它們表達自己。因此正義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會有不同的意涵,如民主制裡的正義不同於寡頭制中的正義,但這不妨礙塞拉胥馬侯斯的主張,即正義的定義是建立在政治的脈絡上。再者,這個看似對正義相對主義的說明,不可掩蓋塞拉胥馬侯斯對正義有更深沉及具普遍性的見解:正義是統治者的利益。
蘇格拉底針對此正義的定義,進行了一系列的質疑,並希望塞拉胥馬侯斯回應。首先,蘇格拉底認為統治者不必然不會犯錯,若他在立法上出錯,他有可能訂立有損自身利益的法律,所以正義不一定是強者的利益(339c-e)。波雷馬爾侯斯及克雷投豐(Cleitophon)此時介入,後者並代之回答:塞拉胥馬侯斯的意思是,強者或統治者所想之事皆為有利於他的事,且是弱者或被統治者應為之事(340b6-8)。然而塞拉胥馬侯斯未順著兩人的說法接續論述,而是以強者或有政治權力者是具備專業知識的人,來回應蘇格拉底:若專家以具有專業知識的資格或身分(an expert qua expertise)不會犯錯,統治者以具有知識的資格或身分(a ruler qua knowledge)亦不會犯錯,因此統治者絕不可能在擁有知識的情況下犯錯。對話至此,塞拉胥馬侯斯從原先對統治者的一種政治社會學的描述,轉而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立場勾勒統治者的形象:完美的統治者是不會在關乎自身利益之事上犯錯。此外拒絕克雷投豐提供的答案,顯示塞拉胥馬侯斯不是一位主張依從俗例、墨守成規之人。
由於塞拉胥馬侯斯以technē的概念說明真正的強者不會犯錯,蘇格拉底接續指出,每一種技藝存在的理由是為了追求其所對應對象的利益,而非自身的利益。例如醫術追求的不是其自身之利益,而是身體的利益——健康。若技藝與其對應之對象相較,前者為強者,後者為弱者,看來正義不會是強者的利益,而應是弱者的利益(342c-e)。若是如此,塞拉胥馬侯斯所說的統治者便不會是一位具有技藝之人,且真正的技藝應該是無涉個人利益,亦非自利的。
有技藝者關注其對象的利益的觀點,亦可見於《高爾奇亞斯篇》503e1-504a4,蘇格拉底說:
就像所有其他的工匠師〔注視〕他們的工作一樣,他們各自不會以隨興選擇的方式來對待,而是為了讓他所製作的東西擁有某個形式在身上。例如若你願意的話看那些畫家、建築師、造船師及其他所有的工匠師,你想要他們之中任何一位,他們各自將各自的事物安排入某秩序中,他會有所安排,且迫使一物適合另一物及一物與另一物和諧,直到他將一事組成有秩序及有組織的整體;其他的工匠師及我們剛才所提的那些與身體有關的人——體育老師及醫生,他們想必保持及安排身體的秩序。
這段引文充分顯示,擁有技藝者關心的是其技藝的對象,而非其自身。如塞拉胥馬侯斯所承認的,統治者亦具有專業技藝,即政治技藝,且此項技藝關注的對象是靈魂(463b3-4)。它可賦予靈魂秩序及組織,這被稱為合法及法律,藉此被統治者會成為正直與有秩序之人,這是正義及節制的表現(504d1-3)。因此統治者——強者,能以其知識使被統治者成為正義與節制之人,根據上一節的原因與效果相似之論述,統治者也應是位正義與節制者。這使得塞拉胥馬侯斯後續以「擁有技藝者(如牧羊人)不會關注其對象的利益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來回駁蘇格拉底(343a-c)時,變得毫無說服力。畢竟德性就其為知識而言,它不可能出現有害於其對象的效果。
儘管如此,塞拉胥馬侯斯並未放棄他對正義的主張,且認為蘇格拉底依然沒懂得正義的真諦——「正義及正義之事其實是他人的好(allotrion agathon)」(343c3)。這個主張乍看之下似乎與塞拉胥馬侯斯之前的主張對反,但他所謂的「他人」指的是強者,亦即從被統治者的立場觀之,所以被統治者或弱者循規蹈矩,依循正義,是統治者或強者的利益;不正義是「自身」的利益,即統治者或強者的利益。因此對塞拉胥馬侯斯而言,無論正義或不正義,最終獲益者皆為強者。這凸顯了塞拉胥馬侯斯在政治上抱持的專制獨裁思想,在道德上替不道德主義背書。詭辯學派哲學家波婁斯與卡利克雷斯的思想亦包含此種不道德主義,前者認為不正義的行為是有利於行為者,且大多數的雅典人認同此觀點;後者則認為根據自然,強者及優秀之人應擁有較多的資源,但弱者卻以風俗習慣及約定俗成的道德規範或法律,來限縮強者的能力。卡利克雷斯的思想在另一位詭辯學者安提豐的論述裡得到呼應。在第四章第五節已見,安提豐主張正義是不僭越法律的規範,在人前一個人會視守法對自身最有利,但在人後獨處時,他會看重人性,「因為與法律相關之事是人為的,但與人性相關之事是必要的」。此外一個人或可違法不被發現,免於懲罪;但若他違背自己人性的要求,就算世人皆不知,他內心所受的傷害也不會少。安提豐論述的要旨,主要是守法或正義其實是人性的桎梏,但出於人性的行為應是必要而且自由的。總而言之,這幾位詭辯學派哲學家都分享一個概念:人性允許一個人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與優勢,並藉此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即使是以不道德的手段。然而若上一節的論述合理,強者或統治者的人性不會使他有不道德的行為,因為有德性的靈魂只會促使有德性的行為產生。
蘇格拉底的第三個質疑是,若每一項技藝,如醫術及航行術,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要賦予其相對應的對象,那麼沒有人會因為操作及實踐一項技藝而獲利及賺錢,因為獲利與賺錢是出於與賺錢有關的技藝(346a-347e)。雖然我們可以理解蘇格拉底在這個論證裡欲表達的觀點——技藝關心的是其施用對象的利益,但論證本身卻有令人不解處。例如,在正常情況下每一項技藝應該都伴隨著賺錢,所以操作技藝者會因此獲利。這個問題較易解決,蘇格拉底可以接受技藝伴隨著賺錢,但強調賺錢不是技藝實踐的「目的」。因此塞拉胥馬侯斯「技藝具有自利的特質」的主張,是建立在將技藝自身與偶發在技藝上的獲利混為一談。較不易解決的問題是,蘇格拉底「每一種技藝存在的理由是為了追求其所對應對象的利益」的主張,放在賺錢術上會產生奇怪的結果。賺錢術施用的對象是錢或薪資,根據蘇格拉底的主張,此技藝照顧關心的對象因而是錢或薪資。從此觀之,這個論證不僅無法直接回應塞拉胥馬侯斯牧羊人的例子,它又為蘇格拉底多添了問題。然而,若如Morris教授所言,賺錢術稱不上是一項技藝,那賺錢就成了實踐技藝別有用心的動機。這成了柏拉圖在之後卷次的論證裡,強調哲學家的統治是出於必要(anagkē),而不是為了獲取薪資,也不是為了名聲榮譽(499b-d, 519d-521c)的原因。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