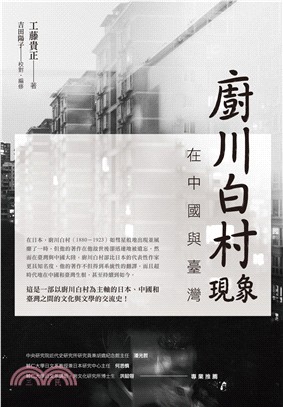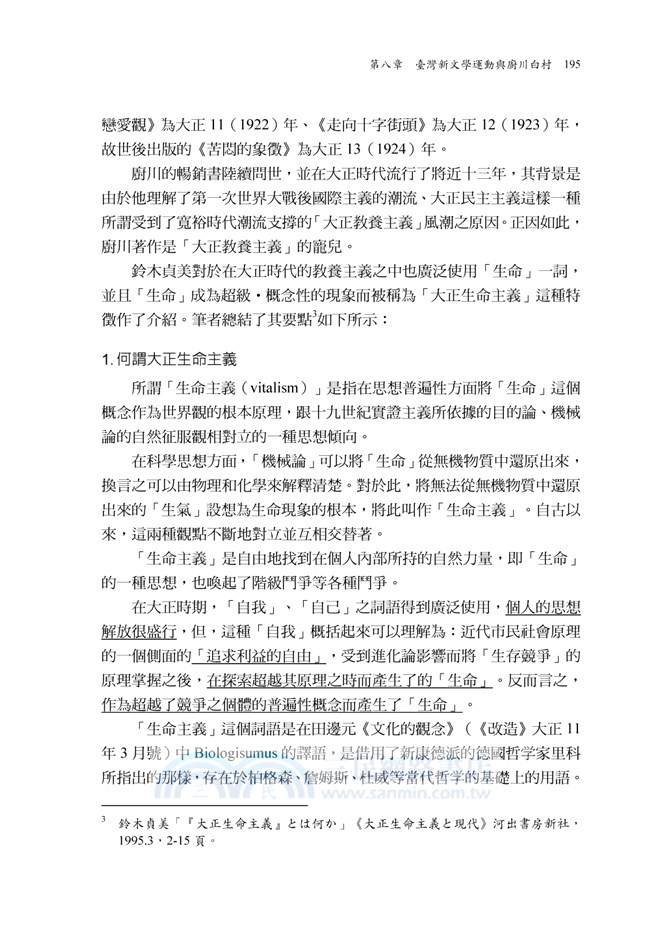商品簡介
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進行文學研究,
有誰的名字比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和川端康成等日本代表性作家更具知名度!?
他的作品被系統地譯成中文,堪稱與當今的村上春樹匹敵!?
這個作家超越時代在各個地域生根並保留下來,
他就是廚川白村!
這就是「廚川白村現象」!
廚川白村著作在日本獲得什麼評價?
為何臺灣和中國大陸兩個民國文壇會接受廚川白村的著作與思維?
翻譯後的廚川文體又具有如何的特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潘光哲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講師、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洪韶翎
專業推薦
在日本,廚川白村(1880-1923)如彗星般地出現並風靡了一時,但他的著作在他故世後卻迅速地被遺忘。然而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廚川白村卻比日本的代表性作家更具知名度,他的著作不但得到系統性的翻譯,而且超時代地在中國和臺灣生根,甚至持續到如今。
這是一部以廚川白村為主軸的日本、中國和臺灣之間的文化與文學的交流史!
本書特色
★特別針對1980年後在中國大陸再次掀起的接受廚川著作熱潮的現狀探析!
★臺灣新文學運動時期、戰後臺灣與代表日本大正主義的廚川白村著作關聯徹底解透!
作者簡介
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院兼國際文化研究院碩士・博士班教授,文學博士(名古屋大學)。專業為中國近現代文化文學與日・中・台比較文化文學。撰著有《魯迅與西洋近代文藝思潮》(汲古書院,2008.9)、《通往現代中國之指南Ⅱ》(白帝社,2009.9)、《中文語境中的廚川白村現象──隆盛・衰退・回歸與連續》(思文閣出版,2010.2)等。
名人/編輯推薦
書籍推薦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潘光哲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講師、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洪韶翎
序
■前言
近代台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互動往來,關係多重,面向繁複,多樣難盡。只是,彼此之間悲劇性的遭遇,往往讓世眾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和認識,難逃國族主義之網羅。如何竭力跳脫既存的認識架構,創生別出新裁的實質歷史知識,進而打造彼此可能和解共生的認識基礎,自是吾輩學界中人的本分職責。至於怎樣以這等意念開展研究,工藤貴正教授的這部力作,正做出了具體的示範,深具路向意義;有意問津於斯的後繼者,實在值得再三揣摩品味。
由於魯迅的關係,厨川白村在漢語思想界裡,從來就不是異鄉他邦的「陌生人」;學界的研究,自是不可勝數。然而,如同本書顯示的,一旦放寬視野,厨川白村的影響所及,絕對不會只是魯迅而已;其間歷程,更是曲折蜿蜒。借用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論述觀點,觀念和理論從這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動際遇,從這一場景(setting)到另一場景的歷史轉移過程(a historical transfer),錯綜複雜。厨川白村在漢語世界的「理論旅行」,同樣不是水到渠成。工藤教授詳縝考察了厨川白村著作的各種漢語譯本,進而闡明,厨川的文本,經過了翻譯之後,如何為中國大陸、民國文壇的知識人接受,並且探討經過翻譯的厨川文體的特點。繼而,他研究台灣脈絡下的厨川白村;特別是,工藤教授認為,1949年之後的台灣,做為「持續的民國文壇」,厨川白村及其著作,被反覆翻譯出版,始終「人氣」不衰,箇中原因,在於厨川的著作猶如啟蒙之作,概論之書,是親近「西洋近代文學」的方便之門。在漢語世界裡的厨川形象與其著作,既與時代的需要相呼應,也引領時代的思想路向。
經過工藤教授的講述,厨川白村在漢語世界的「理論旅行」這段故事,看似清晰曉暢,其實「多年辛苦不尋常」。工藤教授好似「上窮碧落下黃泉」,一一尋覓厨川著作的各種版本,檢覈同異;比對原著與漢譯的內容,查考去取,方始歸納具體的結論。工藤教授的業績,具體顯現日本學界「實證主義」的治學風範,自可突破既有研究的闕失;較諸一筆灑遍天下勝景的泛泛之論,工藤教授以繡花針織就的圖景,自是美不勝收。
舉例而言,本書第六章:〈一個中學教師的《文學概論》〉,工藤教授考察了任教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的「一介無名中學教師王耘莊」,教授「文學概論」課程的教材《文學概論》(1929年),如何徵引襲取了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和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的文藝論。藉由文本的詳縝比對,工藤教授揭示的歷史圖像,豐瞻華美。近代日本對中國的思想變遷,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動力,又怎樣代代傳承相衍,就此個案,工藤教授創造的知識空間,明確實在,無可移易。再如,就台灣來說,工藤教授追溯了厨川白村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論證其淵源所在,卻是來自北京的「大正生命主義」(本書第八章);況且,厨川白村在寶島台灣的思想遺產,實不以1949年為斷限。即如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的《人人文庫》,物美價廉,筆者少年時期搜求不遺餘力,其中署名「本間久雄著,章錫光譯」的《新文學概論》,現在還擱在書架上。據工藤教授的研究,這個版本,根本就是「章錫琛」的譯本(本書第九章)。顯然,在台灣成長的青年,沾潤的「思想資源」,恐怕不乏「五四」世代的心血。聯想所及,「五四」的思想種子,如何在台灣成長茁壯,乃至花開滿園,確實大有琢磨空間。工藤教授奉獻的智慧與力氣,自可開啟多重的知識之窗,在在值得吾人頂禮以敬。
當然,在知識的海洋裡,領航者已然指出了方向,後繼者續航而進,自應「百尺竿頭」。像是工藤教授將王耘莊視為「一介無名中學教師」,即可稍予補充。其實,王耘莊也不完全是無名之輩。值此網際網路發達,資料檢索更為便利的時代,稍一考察,其大致生平,即已見諸網路報導(尹芙生,〈王耘莊教授的一生〉,嵊州新聞網,2012年06月07日〔http:// sznews.zjol.com.cn/sznews/system/2012/06/07/015107017.shtml;讀取時間:2016/8/15〕),藉此略可知曉,他是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學生;筆者進而「順藤摸瓜」,檢索清華國學研究院相關文獻,知悉王耘莊嘗介紹同學朱芳圃擔任位於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國文教員(陳紀洋,〈中國古文字學家朱芳圃〉,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學者追憶叢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228-229)。自可確證,王耘莊實乃系出名門。那麼,他會取引當時堪稱最新思潮的本間久雄與厨川白村的文藝論,藉以傳授生徒,布道開講,當是其來有自;就此一例,自可遙想,清華園內那群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承受的知識與訓練,絕對不僅是「國學」而已。
工藤教授遠居東瀛,本無緣相識。筆者研究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形象,拜讀其大著:〈魯迅の翻訳研究(1)─外國文學の受容と思想形成への影響、そして展開〉(1989),驚其博學多聞;經摯友孫江與黃東蘭教授之中介,得以結緣,論學史林,其樂無窮。工藤教授積多年心力完成的這部力作,即將堂皇與漢語世界的讀者見面,讓更多的學林同好得以分享他的心力所聚,其實就是台灣與日本文化交流互動的一樁盛事。在這部力作的漢譯本問世前夕,承工藤教授厚愛,邀請為序,力辭不果,謹此敬述一二。倘若有助於讀者領略本書的妙諦精義之所在,掌握工藤貴正教授的智慧成果積蘊的啟發意義,必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潘光哲敬筆 2016年8月15日
目次
推薦序:其實,還是因為「愛」!/何思慎、洪韶翎
前言/潘光哲
序 章 何謂中國語境中的「廚川白村現象」
第一章 廚川白村著作的普及與評價──以日本同時代人的評價為中心
第二章 民國文壇知識分子對廚川白村著作的反應
第三章 圍繞三位譯者接受《近代的戀愛觀》的差異
第四章 魯迅譯・豐子愷譯《苦悶的象徵》的誕生及其周邊情況
第五章 翻譯作品中的廚川白村──以魯迅譯・豐子愷譯《苦悶的象徵》為中心
第六章 一個中學教師的《文學概論》──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和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的普及
第七章 《近代的戀愛觀》中描寫的戀愛論對文藝界的波及與展開──以比昂松和施尼茨勒的翻譯狀況為例
第八章 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廚川白村──來自北京的「大正生命主義」
第九章 廚川白村在戰後臺灣──持續性普及的背景、要因以及方法
終 章 廚川白村著作的回歸與其研究意義
附錄 廚川白村生平及寫作年表(1880-1923)
【參考資料1】 民國時期廚川白村著作單行本的出版狀況(以出版年代篇為順)
【參考資料2】 任白濤翻譯《戀愛論》兩種
【參考資料3】 夏丏尊譯《近代的戀愛觀》目錄
廚川白村著『近代の戀愛觀』目錄
【參考資料4】 在報刊雜誌和選集上廚川白村的譯作以及聯以評論(民國時期)
【參考資料5】 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的出版狀況
作者及編譯簡介
書摘/試閱
序章 何謂中國語境中的「廚川白村現象」
何謂中國語境中的「廚川白村現象」呢?
在日本如彗星般出現、風靡一時的廚川白村(1880.11.19-1923.9.2)的著作,在他逝世後卻迅速地被遺忘了。然而,在中國語境(以中國大陸、臺灣為中心,包括香港地區)的知識分子之中,他卻比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和川端康成等日本代表性作家更具知名度。並且就日本人的著作而言,他的作品被系統地譯成中文,可以與當今的村上春樹匹敵。再者,他超越時代在各個地域生根並保留下來。這種現象即是「廚川白村現象」。不過廚川的著作在中國語境中被接受的始作俑者的譯者是著名的知識分子,接受對象是以學生、評論家、作家為主的知識分子,因此,換言之「廚川現象」也指作為知性現象的廚川白村及其著作被重視的狀況。
這種現象是從一九二○、三○年代的民國文壇,留學日本的田漢、鄭伯奇訪問廚川白村、郭沫若以「創作論」對《苦悶的象徵》的接受為開端的。對此進行了推動的是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與《出了象牙之塔》。魯迅‧豐子愷所譯《苦悶的象徵》作為創作論、文學論的著作得到普及,羅迪先所譯《近代文學十講》被當作介紹西洋近代文藝思潮的著作來使用。任白濤所譯《戀愛論》和夏丏尊所譯《近代的戀愛觀》則作為介紹「近代」論的戀愛、結婚觀的著作用以閱讀;魯迅所譯《出了象牙之塔》和劉大杰所譯《走向十字街頭》等代表作則以其批判文明及改造國民性等主張,作為具有反抗精神的社會批評論來閱讀。閱讀了廚川白村的諸多經翻譯後的作品,葉靈鳳等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指出,廚川文體對民國時期的散文(小品文)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对他的文體给予了高度評價。
此後國共內戰,戰敗後的國民黨遷移至臺灣,在臺灣形成了持續的「民國文壇」。一九五○年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的「反共」牽制著文壇,而另一方面從大陸來臺灣的所謂外省人的第一代作家「鄉愁」文學時代應運而生。六○年代隨著成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基地的《現代文學》的創刊,迎來了作為現代想像模式的西洋近代文學的接受時代。在這種情況下, 廚川白村的著作作為便於簡要地理解「西洋近代文學」的啟蒙概說書籍得到反復翻譯出版。僅僅初版書,從1957.12到2002.12至少出版了十二種,其中六種集中出版於七○年代。從七○年代的特徵來看,這些被看作是以解說「西洋近代文學」的概論書而起到了作用。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路線下,經歷了一九八○年代的漫長的空白時期後廚川白村的著作再次得以出版。從八○年代以「走向世界」為關鍵詞,諸如「魯迅與廚川白村」為代表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開始,發展到九○年代的以「現代性」為關鍵詞,以與西洋近代文藝思潮有關的文藝思想相置換的研究方法,再到二○○○年代從各個角度再次接納廚川的著作為止,甚至出現了研究廚川其人及其文藝觀的「廚川白村研究」。
筆者所謂的中國語境中的「廚川白村現象」,即指諸如此類的廚川白村的著作以各個時代及各個地區的特性為條件而被持續下來的現象。
筆者1998年12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廚川白村著‧羅迪先譯的《近代文學十講》,讀到了如下引用的一部分廚川的中文翻譯。當時筆者的感受是這部著作所描述的不正是當今的中國現狀嗎?也就是說,九○年代後期中國人的生活及精神狀態,正如廚川如下所指出的那樣:是由於受「外部生活」以及科學精神的影響「內部生活」所起的變化。
近代的歐羅巴,不像古時,有貴族僧侶。階級制度滅了,變成自由平等的世,全然是個人實力競爭的世了。無論怎樣有銅錢,競爭比人後一步,馬上要遭著流離落魄的悲運。起居坐臥,一日一刻,生活問題不能離開人人的念頭。而且現在所謂暴富(Parvenu)很多,埭臺安Alphonse Daudet 的小說Le Nabob 裡,所描寫的起身卑賤,一躍獲得了鉅萬的財,在交際社會好運的暴富黨,現在是很多了。黃金萬能的勢,假使依此而名譽,地位,權利,都已得到,富的人更想求富,苦心焦慮,自己知足的決沒有,因此貧富的相隔更甚,成了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狀態,所以近代社會生出種種弊病來了。曹拉Zola一流自然派文學,所寫的下層社會的悲慘狀態,-生存競爭的劣敗者,落伍者的浮浪生活,今日文明進步的國家,更加厲害。實際在近代歐洲各貧窮Pauperism 的悲慘狀態,到底為吾人想像所不及的,不到倫敦的貧民窟Slum,不知道那種慘狀,犯罪的,自殺的,年年增多,這是在統計上所表明的事實。
近代雖是重個人自由的時代,但因為有激烈的生存競爭,個人不能任意伸展他的自由,因為有這種矛盾衝突,個人對於社會,自己覺得自己的弱,苦悶的也多了。
─第一講「序論」二「時代的概觀」
實際「都市病」的原因,不單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就是外界激烈的刺戟,波及到神經,也為有力的原因,是不容疑的事實了。要之,都會受了近代文明的恩惠最大。同時受了他的弊害,也很利害的。
所以說近代的歐洲文學,是都會的文學,這個決不是像十八世紀時候,都雅,典麗,高尚的文學的意味,是指刺戟很強烈的都會生活做中心的文學而說的。都會生活的種種病的現象,是最顯明表現出來的文學。在近代田園文學,雖即不是說沒有,但和古時潘士Bruus華士華爾斯Wordsworth的作品,全然是異性質的東西了。譬如疲倦了都會生活的人心,常常回想幼少時的田園風光,和簡朴的的生活。這是一種望鄉心Nostalgia。還有飽厭了種種刺戟的人,遇著靜穩無事的田園的生活,這個卻又成了一種新的刺戟。近代的田園文學,都多從這樣的心想生出來的,所以這個決不是純粹的田園文學,仍舊是都會生活做中心的文學,不免是都會人所見的田園文學。近來,德國有稱為「鄉土藝術」一類的小說,離了都會生活,描寫作家的鄉土話的文學,也不過是這類的文藝罷了。
─第二講「近代生活」三「疲勞以及神經之病的狀態」
以上是在上海圖書館讀到的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中的一段。
曾經放棄了西洋近代文明而去追求具有本國特色的「近代」的中國,在二十年前雖然生活貧困但收入平均的中國、暗中信奉「有權就有錢」的中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如今都市物質豐富,生存競爭激烈,拜金主義橫行,貧富差距頗大,富人有錢卻變得愈加苛刻,窮人嚮往財富卻愈加困窘。正諸如「有錢就有一切」、「有錢就是爺」、「錢不是萬能的,沒錢是萬萬不能的」之類的流行語所象徵的那種價值觀念的核心已經發生了變化,由上海為代表的都市市民的「外部生活」為之一變。並且筆者回日本後閱覽到了《編年體大正文學全集.第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5)所收錄的「《近代文學十講》(抄)第二講〈近代的生活〉三、四」,其中有一部分與筆者以上引用部分重合,這說明當時就有人認識到日本也有著與中國相似的危機而想要敲響警鐘的。
日本全體國民在明治維新後確立了義務教育制度,西洋近代文藝思潮之中從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從浪漫主義到自然主義,從自然主義到新浪漫派(象徵主義、唯美主義和表現主義等)的文藝思潮的變遷階段,都一一登場並在最後被取代。但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在向西洋的近代化邁進的過程中,在中國發生了確立白話文文學的「文學革命」的1910年後期,不管是歐洲還是日本的文學作品的傾向,都已經發展到了新浪漫派了。因此結果在中國,不管是浪漫主義還是自然主義都沒有經過「批判」洗禮的過程,浪漫派的作品、自然派的作品和新浪漫派的作品在同一時期得以翻譯,從而登上了同一文壇。
的確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之中,既有意識到文藝思潮中創作手法和流派的變遷而著手翻譯作品的魯迅,也有意識到近代文藝思潮變遷並預感到無產階級文藝即將到來的李漢俊(1890.4.2-1927.12.17)等等,可是除了這樣的人物以外,不少一般的知識分子的傾向是,「辛亥革命」之前有日本留學經驗的人傾向於自然主義(不是日本的自然主義,而是西洋近代文藝思潮的「自然主義」)的作品,而且其作品也是自然主義的。有「辛亥革命」及「文學革命」以後留學經驗的,則強烈地傾向於時代尖端的新浪漫派的作品,而且其文風也是新浪漫派的。而且1920年中期以後留學日本者,則學到很多無產階級文學以及文藝理論。
一九三○年代的大都會上海,追隨著同時代歐洲和日本的步調,產生了超越國家和國籍的近代都市文學。其創作手法及作品傾向有自然派的、有新浪漫派的、同時也有無產階級文學派的,形成了多樣化的都市文學。然後,六十年後的一九九○年代的上海,又出現了打著「上海某某」招牌的作品,使得失去了中國獨特濃厚的國民文學的特色,又出現了國家和國籍不明的全球化的都市文學。
筆者在1998年讀到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的中文譯本時,真正的體會到了中國曾一度放棄的西洋近代文化又得以回歸。這樣就產生了去探討廚川的著作給民國文壇帶來的意義,以及給一九八○年代後的現代所帶來的意義的構思。
最近在中國的「翻譯文學研究」領域中引用了勞倫斯(Lawrence Venuti的《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TheTranslatorte'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1995)中「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這兩個關鍵詞的論文集上刊登了好幾篇論文。在日本,藤井省三新譯的《故鄉/阿Q正傳》(光文社,古典新譯文庫,2009.4)的「譯者後記」中提到:對於「把魯迅本土化的竹內好譯本」論述為,所謂把魯迅本土化也不是說把魯迅文學翻譯成現代日語,而藤井氏的新譯則試圖把日譯文變為魯迅化(Luxunization)。在日本戰後,通過竹內好翻譯的魯迅文學廣泛地被日本各種年齡的人們所接受。譬如1972年以後竹內好所譯《故鄉》被用於初三的語文課本之中(由學校圖書、教育出版、三省堂、東京書籍和光村社等出版),滲透到了廣大年輕人之中。但,藤井氏一方面評價竹內好的功績,一方面避開他的那種短句型的漢語訓讀式的語言、雖清晰但非冗長乏味的文體,而是重視魯迅文體自身的句讀,進行了對照性的翻譯,以彆扭的長句來呈現如迷宮般的思考表現的魯迅文體的特徵,嘗試了所謂的日語譯文的魯迅化。並且本書從這篇「譯者後記」中得到啟示,以廚川文體和他的中文翻譯文體為線索,去考察廚川白村為何在日本不被重視而為人遺忘,但在中國大陸、臺灣被翻成的中文文體卻博得了好評,並提出了如下的一個概念:
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venuti)從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兩方面來分析外語翻譯活動。Domestication就是外語、外來文化的當地化、本土化,foreignization就是當地文化、本土文化的異國化。中文各自將其翻成「歸化」和「異化」。就魯迅文學的日語化來說,也可以說是魯迅文體和現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當地化,以及日本文化的魯迅化、中國化。至今為止的魯迅翻譯,總的說來帶著濃厚的domestication的傾向,而其中竹內好(1910-1977)的翻譯堪稱當地化之最。
廚川白村的譯本在中國語境中廣為流行並博得好評,其原因是否因進行中文翻譯而實現了廚川文體、廚川白村的當地化即中國化(中文譯為「歸化」)呢?反言之,是否中文翻譯也實現了日本化、廚川白村化(「異化」)呢?還是跟藤井氏所言及的「歸化」及「異化」根本就沒有關係呢?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將於最後一章進行探討。
在此,將廚川白村的著作集(粗體字)和以單行本出版的翻譯集按年代順序作如下的排列:
(1) 《近代文學十講》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2年3月17日初版。)
(2) 《文藝思潮論》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4年4月28日初版。)
(3) 《狂犬》(翻譯小說集7篇) 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5年12月初版。)
(4) 《新門羅主義》(Sherrill著 譯本)東京:警醒社(1916年12月初版。)
(5) 《印象記》東京:積善館(1918年5月15日初版。)
(6) 《小泉八雲及其他》東京:積善館(1919年2月20日初版。)
(7) 《出了象牙之塔》東京:福永書店(1920年6月22日初版。)
(8) 《英文短篇小說集》(編) 東京:積善館(1920年8月初版。)
(9) 《北美印象記》東京:積善館(1920年9月25日初版,縮印版。)
(10)《英詩選釋》1卷(譯詩集)東京:アルス社(1922年3月初版。)
(11)《近代的戀愛觀》東京:改造社(1922月10月29日初版。)
(12)《走向十字街頭》東京:福永書店(1923年12月10日初版。)
(13)《苦悶的象徵》東京:改造社(1924年2月4日初版。)
(14)《現代抒情詩選》(英詩選釋第2卷、翻譯詩集)東京:アルス社(1924年3月初版。)
(15)《最近英詩概論》東京:福永書店(1926年7月8日初版。)
這十五本中除了翻譯集以及把《印象記》中屬於北美旅行記的作品再版的《北美印象記》之外,廚川白村的著作可以整理出《近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小泉八雲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戀愛觀》、《走出十字街頭》、《印象記》、《苦悶的象徵》、《最近英詩概論》這九篇。從《近代文學十講》開始,到去世後出版的《苦悶的象徵》為止,廚川的每一部著作都是暢銷書,特別是《近代的戀愛觀》,從初版付梓僅僅三年就印了一百二十多版。
喜好新事物的日本人敏感地呼應時代的風潮和時尚,對勞動問題、社會問題、戀愛‧結婚問題等作出評論的《近代文學十講》、《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戀愛觀》、《走向十字街頭》這樣的作品走在時代的先端,使得廚川白村在一夜之間成了時代的寵兒。可是這些著作雖然引起了褒貶不一的反響,但因作者喪命於1923年9月1日發生的關東大地震,這些論爭也就失去了當事人。曾給予廣大知識分子、一般大眾以莫大影響的廚川白村也就過早地被人遺忘了。
再把視線轉移到中國來看,在一九二○、三○年代的中國,廚川白村的著作僅除了《最近英詩概論》一部之外,均被譯成了中文,這個事實是值得一提的。在第二章中將詳細探討民國文壇的知識分子與廚川白村的關係。在此先按時間順序列出其譯本十一冊,並列出譯者留學日本的時期。([ ]內是留學日本的時期及留學地點。)
①《近代文學十講》上(1922年8月初版)、下(1922年10月初版。)譯者:羅迪先(?-?)[?-?]
②編譯《戀愛論》(1923年7月初譯版,1926年改譯版。)譯者:任白濤(1890-1952)[1916-1921,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
③《文藝思潮論》(1924年12月初版。)譯者:樊從予,即樊仲雲(1901-1989)[?-?,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
④《苦悶的象徵》(1924年12月初版。)譯者:魯迅(1881-1936)[1902-1909,弘文學院,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德語專修學校。]
⑤《苦悶的象徵》(1925年3月初版。)譯者:豐子愷(1898-1975)[1921年春-1921年冬。]
⑥《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初版。)譯者:同前魯迅
⑦《走向十字街頭》(1928年8月初版。)譯者:綠蕉‧大杰,即劉大杰(1904-1977)[1926-1930,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畢業。]
⑧《近代的戀愛觀》(1928年9月初版。)譯者:夏丏尊(1885-1946)[1905-1907,弘文學院,東京高等工業學校。]
⑨《北美印象記》(1929年4月初版。)譯者: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1920-1927,福岡明治專門學校電氣系畢業,九州帝國大學。]
⑩《小泉八雲及其他》(1930年4月初版。)譯者:綠蕉(一碧校),即同前的劉大杰。
⑪《歐美文學評論》(1931年1月初版)譯者:夏綠蕉,即同前的劉大杰。
其中,魯迅和夏丏尊可以稱得上為第一代日本留學生,辛亥革命前置身於日本,和廚川是修學年代差不多的同輩人。
羅迪先的經歷不明,樊仲雲的留學時期也尚不確定。但作為《近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的譯者,他們的留學時期可以確定在廚川作為文藝批評家、社會批評家的活躍時期。
另外,在廚川的活躍期間留學日本的還有任白濤、豐子愷和夏衍。
廚川白村去世後留學日本的是劉大杰。他是在中國已經出版了魯迅所譯《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之後才到日本留學的,對於廚川已有所了解,在早稻田大學在學期間的1929年9月曾參加了在京都舉行的廚川的七週年忌辰。他把《走向十字街頭》、《小泉八雲及其他》以及《印象記》中除去《北美印象記》的部分進行了翻譯,題為《歐美文學評論》。
以上是廚川白村著作單行本的八位譯者。
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的中華民國時期,日本人的個人的著作這樣被系統翻譯的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從幾乎與日本在同時期,並跨越了十年以上廚川白村的著作在中國大為流行這點來看,廚川可以說是給民國文壇帶來巨大影響的人物。並且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再版到十二版、共發行了兩萬六千冊。同樣魯迅翻譯的《出了象牙之塔》前後五版共計十版,大約發行了一萬九千五百冊。廚川白村也可以稱為是民國文壇上時代的寵兒。
在日本,廚川白村死後迅速地被遺忘了。然而在戰後日本人退去、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也就是在「持續的民國文壇」,廚川的著作繼續被翻譯出來。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強制實行了對國民國家的言論以北京話為國語的語言政策。隨即出現了使用標準語翻譯廚川著作的知識分子。比如,僅以《苦悶的象徵》為例,就可以列出九種民國版本。
①徐雲濤譯《苦悶的象徵》臺南市:經緯書局,民國46年(1957)12月初版。
②琥珀出版部編譯《苦悶的象徵》臺北縣板橋市:民國61年(1972)5月出版。
③摹容菡(程思嘉)編譯《苦悶的象徵》臺北市:常春樹書坊,民國62年(1973)出版。
④德華出版社編輯部編譯《苦悶的象徵》臺南市:民國64年(1975)2月初版。
⑤顧寧譯《苦悶的象徵》臺中市:晨星出版社,民國65年(1976)三月版。
⑥林文瑞譯《苦悶的象徵》臺北市:志文出版社,民國68年(1979)11月初版。
⑦吳忠林譯《苦悶的象徵》臺北市:金楓出版社,民國79年(1990)11月版。
⑧魯迅譯《苦悶的象徵》臺北市:昭明出版社,民國89年(2000)7月版。
⑨魯迅譯《苦悶的象徵》臺北縣新店市:正中書局,民國91年(2002)12月初版。
1987年7月15解除戒嚴令以後,漸漸地魯迅的著作也不再是禁書了。二○○○年代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正式登場,在此之前也已在暗中對臺灣「民國文壇」的翻譯家們產生著影響。上述《苦悶的象徵》的譯者,除魯迅之外,加上徐雲濤、摹容菡、顧寧、林文瑞、吳忠林五位,還有琥珀出版部編譯版和德華出版社編輯部編譯版的二位譯者。關於這一點將於第五章「翻譯作品中的廚川白村」中詳細論述。不過在此想強調的是廚川著作的翻譯集中在七○年代這一點。九種《苦悶的象徵》之中五種出現於七○年代,還有以下列出的除《苦悶的象徵》以外的三種譯書中有兩種也是七○年代出版的。
①金溟若譯《出了象牙之塔》臺北市:志文出版社,民國56年(1967)11月初版。
②陳曉南譯《西洋近代文藝思潮》臺北市:志文出版社,民國64年(1975)12月初版。
③青欣譯《走向十字街頭》臺北市:志文出版社,民國69年(1980)7月初版。
臺灣以七○年代為中心接受廚川白村著作的理由,將在第八章的「廚川白村在臺灣」中詳細闡述。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在中國大陸對於廚川白村的接受開始衰退的時期,以中國內戰敗北以後去臺灣的國民黨方面的外省人為中心,繼承了廚川作品的人望而繼續進行翻譯,至今為止翻譯並發行的書籍共有十二種之多。
那麼廚川白村的著作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為何深受歡迎並如此受到熱誠對待呢?相反來說,日本人對於廚川及其著作卻為何只是引起了一時性的熱潮,隨後即遭到冷淡對待並很快被遺忘了呢?關於這一點正是之所以執筆該書的問題意識之根本所在。
前些日子,筆者拜訪了廚川白村在京都岡崎南御所町四拾番地的故居。他最終居住於此,告別儀式也是在此舉行的。這所廚川曾居住過的在岡崎的家是一幢西式的小洋樓,在一樓有十幾張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間據說是書齋兼會客室。這幢房子被稱作「鬼屋」,因為曾一度被毀而已經失去了當時的風貌。但是筆者拜訪之後,看到在岡崎大街平安神宮的東面緊靠著關西美術院旁邊,掛著「廚川白村舊宅」指南標牌的是一家漂亮的日本式小玩意的銷售店鋪,裡面有著壁龕的日本式房間做成的茶室。在那裡筆者一邊品茶,一邊凝視著院子裡的石燈籠,腦海中不禁浮現出田漢和鄭伯奇的廚川白村訪問記。
1920年3月18日的晚上,中國知識分子代表之一的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和鄭伯奇(1895年6月11日-1979年11月2日)一起對他們從心底裡尊敬並敬佩的廚川白村作了直接訪談。記有當時情況的文章被收錄在田漢的自傳中,其內容將在該「序章」的結尾部分進行介紹。從這篇文章中能夠領會到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廚川的仰慕之情。
以下引用的文章是董健的「訪問廚川白村」(收錄於《田漢傳》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中,有關廚川白村與田漢、鄭伯奇對談場面的介紹。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寫於1920年4月,在此之前,田漢訪問過廚川白村。訪問之前,他已讀過一些廚川氏的著作,特別是《近代文學十講》一書對他影響頗大。此次訪問,進一步加強了他對新浪漫主義的信仰。
1920年3月春假,田漢應約到福岡去看郭沫若,路過京都,逗留四天。18日晚,他和在京都留學的鄭伯奇一道去訪問心儀已久的批評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廚川白村。在岡崎公園旁邊白村先生的家裡,自我介紹一番之後,田鄭二人脫鞋上了「榻榻米」,入了書室。話題很快便集中在文學問題上。
(……)
「現在我們這些二十歲上下的人,在文學與社會人生這兩者之間,如何找到一個『接合點』呢?這真是一個大問題。」
「此話怎講?」廚川白村沒有弄懂田漢的「接合點」是什麼意思。
「這問題是從先生的大作《近代文學十講》來的……」
「噢,是嗎?」
「先生分析近代文藝思潮的變遷,非常透徹。您把浪漫主義時代、自然主義時代、現代主義(田漢的原著中為〈新浪漫主義〉─筆者)時代比做人的一生中的三個時期……」
「是的,」廚川白村接下去說,「二十歲前後,天真熱情,朝氣勃勃,但又涉世不深,好作空想,這不是浪漫主義時代嗎?三十歲前後,懂事多、實在多了,現實感強起來了,體驗人生的矛盾和苦悶也多起來了,年輕時的好夢一破,悲慘世相畢現於眼前,這不是自然主義的時代嗎?」
「到了四十歲前後,人生甘苦已嘗了不少,─」熟悉廚川白村那部著作的田漢替他接著說下去,「對世事也看得更深更透了。雖有更大的煩悶,但也有更圓熟的靈質。這時奮起向未來追求,也更加思周慮密了,這就是現代主義、新浪漫主義的時代。我看先生這樣的比擬,不是真嘗過人間味和藝術味的人是道不出也道不得這麼親切的。可是,我們的問題也就從這裡產生了……」
「噢,什麼問題?」
「人到了您說的第三個時期,老辣是老辣了,圓熟是圓熟了,可接著就是老朽、停滯以致死亡,難道文藝也如此嗎?現代主義藝術是否會變成腐水、死水呢?」
(……)
田漢趕快把所謂「接合點」問題提出來。「是這樣的,白村先生,照現代主義思潮來看,這是一個文藝的煩悶圓熟時代,正相當於您所說的人生四十歲上下之時;相對於那個熱情的舊浪漫主義時代來說,這是一個新浪漫主義的時代。我們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本來是最適合與那個熱情時代的舊浪漫主義接合的,可是我們似乎生錯了年代。當今,以我們熱烈奔放之妙齡,卻要面對一個煩悶圓熟的流派,這似乎有些「錯位」。叫我們處在煩悶圓熟的當代卻要去唱百年之前那熱情時代的歌,或者以百年之前熱情時代的靈質來對待當今這煩悶的時代,似乎都有些脫節,這不就需要尋出一個「接合點」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廚川白村十分佩服田漢敏銳的思考力,他想:「是的,像你們這樣的妙齡青年,入世未深,對人生之大悲苦了無體察,對西方近代哲學又未下功夫研究,是很難理解現代主義藝術的。」想到這裡,他慢慢地作答:
「田君的問題,我看可從兩端入手來解答。第一,當前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西方反封建專制的浪漫主義啦,暴露社會黑暗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啦,在西方似已成隔日黃花,但對中國來說恐怕還是新東西。你們年輕人切不可因為熱衷於現代主義、新浪漫主義而忽視了這些傳統的或說舊的思潮和方法。與它們的『接合點』是好找的,單看你們國內的『易卜生熱』就很可說明這一點。第二,現代主義諸流派,即所謂新。
但由於時代不同,文化土壤不同,亦不必強求。如果對人生悲苦沒有深切的體察,只能識其皮毛而已,就像你們中國大詩人辛棄疾所說的:『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當然,那些藝術表現的新方法拿來試試也無妨。所以,與現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的『接合點』,首先要從人生體驗上去找。我並不希望你們個人很倒霉,但不吃些人生之苦,如何能懂得藝術呢?……」
聽了這話,田漢想起不久前讀過的廚川白村的《北美印象紀》中《左腳切斷》一文,知道這位學者確實是深有所苦才對文學有那麼深的感悟。相比之下,自己簡直是太淺薄了。什麼「世紀病」啊,什麼「世界苦」啊,自己在詩中也煞有介事地叫喊過,但究竟有什麼「苦」的真體驗呢?他帶著敬佩的目光,看著面前這位四十歲的批評家,覺得他額上和眼角上的皺紋裡不僅埋藏著篤學深思的學者之氣,而且也瀰漫著人生的苦味。廚川白村這時也把話停下,看著沉思的的田漢。
「先生,中國提倡新文化已經三四年了,」鄭伯奇乘機插進話來,「可至今連一個純粹研究文學的團體和一種純文學刊物都沒有,這樣下去,真是走投無路了!」
鄭伯奇的話,把話頭轉到了當下中國的新文學問題上。白村說:「中國新文學將來如何,要看有沒有好作品出來。我對中國新文學希望很大。像田君這樣能動腦筋想問題,一定會大有作為的!」
「謝謝白村先生的鼓勵!不過─」田漢聽白村這樣鼓勵他,頗有些激動而又惶惑,因想到國內這兩年的新人物中間浮囂者多,真擎者少,對士風不無擔心,遂說:「不過現在新說迭出,新主義也不少,又太容易推許人,有些叫人眼花繚亂。」
「作家只管盡力去創作,不要去管評論家的說長道短。」白村先生說。「最重要的是,你們要多事創作。心中若是想要寫甚麼,便馬上要寫出來,不要管它好還是壞。因為思想這個東西不同別物,若不用它,它便要發霉發臭起來,記住:一有感觸,就要寫下來!」白村把手向小桌子重重地一放。
「創作自然重要,那麼請問,翻譯呢?」田漢問道。
「當然,翻譯也很要緊。」
「先生」鄭伯奇接著問,「您看世界文學中,首先值得我們翻譯的是哪些作品?」
「要建設自然主義文學,最好多譯易卜生。」
「還有呢?」田漢緊追著問。
「我覺得最最值得你們翻譯的是,恐怕還是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廚川白村沈吟片刻又說:「大家天天都在說社會改造,但畢竟應該從個人的改造做起。在這方面,陀氏的作品能教我們做出多麼深刻的反省啊!」
「不過,白村先生,」鄭伯奇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調太過於陰冷、灰暗了。」
「是啊,而且─」田漢補充說,「他的心理描寫又多是病態的,中國人不一定能接受。」
「這才是剛才田君說的『接合點』的問題了,」廚川白村的談興被兩位青年的問題所激,一下子更濃了,「你們不是很佩服現代主義的新浪漫主義嗎?我看,不懂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難得懂現代主義。田君的『接合點』能不能就從理解陀氏精神上找一找?什麼變態心理的描寫啦,什麼基調陰冷、灰暗啦,應該從人生體驗上多去想想,
找出這背後的東西來,從『冷』裡覺出熱,從『暗』裡察出人性的亮色來。」
(……)
「壽昌!」鄭伯奇看田漢似乎還要興致勃勃地談下去,便叫他打住,「你看看都什麼時候了,明天一早你還要趕去九州的車呢。」
夜九點半多,兩位中國的文學青年戀戀不捨地與廚川白村握別。
「『接合點』……人生大悲苦……新浪漫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萊爾……」這幾個詞,這兩個人名,像簇簇火苗在田漢的意念世界裡不斷地跳躍、閃灼,直到第二天在開往九州的火車上,也沒有消失。
翌月3月19日,田漢去福岡拜訪郭沫若,告知自己從與廚川白村的對談中得益非淺,並告訴他自己所受的感動。以田漢、郭沫若和郁達夫為中心,1921年先是在東京成立了創造社,隨後21年1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在《改造》(3卷1號)上得以發表。不難想像這些創造社同人們在頻繁地交換文藝論的意見之中,對廚川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一說產生了共鳴與共感,同時對作為創作論的《苦悶的象徵》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對此達成了共識。
以上闡述了廚川白村被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所仰慕、尊敬,並且後來在臺灣他的著作也繼續博得人望的概況。
因此在本書中首先將考察廚川白村的著作在日本得到了如何的評價。其次將闡明經過了中文翻譯的廚川著作的文本是如何被中國大陸、民國文壇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並且將探討經過翻譯的廚川文體的特點是什麼。繼而研究在臺灣這個「持續的民國文壇」中,廚川白村及其著作何以維持了他的人望。另外也將查明在同樣是中國語境中的香港的情況。最後對1980年以後廚川白村及其著作在中國大陸再次深受歡迎的現狀加以分析。
範紫江 翻譯/吉田陽子 校對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